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жҪҳз»ҙпјҲеҢ—дә¬еӨ§еӯҰеӣҪйҷ…е…ізі»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гҖҒдёӯеӣҪдёҺдё–з•Ң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дё»д»»пјү дёҖгҖҒдёҠдёӢйҪҗжүӢжҺЁж”№йқ©зҡ„жҝҖжғ…е№ҙд»Ј
дәҢеҚҒе№ҙеүҚпјҢеҸ—зҫҺеӣҪдәәжҢ‘иө·зҡ„вҖңдәҡжҙІ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вҖқеҪұе“ҚпјҢдёӯеӣҪеҮәеҸЈж–ӯеҙ–ејҸдёӢйҷҚпјҢ银иЎҢеҸҠ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вҖңдёүи§’еҖәвҖқеҖәеҸ°й«ҳзӯ‘пјҢеӨ„еңЁз ҙдә§иҫ№зјҳгҖӮиҝҷи§ҰеҸ‘дәҶжңұй••еҹәжҖ»зҗҶй“Ғи…•ж“Қзӣҳзҡ„дёҖеңәжғҠеӨ©ең°жіЈй¬јзҘһзҡ„ж”№йқ©пјҡеҗ„зә§ж”ҝеәңжӢҘжңүзҡ„еӣҪдјҒвҖңжҠ“еӨ§ж”ҫе°ҸвҖқжё…з®—еҮәе”®гҖӮеңЁеӣҪжңүиө„дә§иў«еҸҳеҚ–зҡ„зӣӣе®ҙдёӯж•°еҚғдёҮеӣҪдјҒе·ҘдәәвҖңдёӢеІ—вҖқпјҢиҖҒе№јеҰҮеӯәжҖЁеЈ°иҪҪйҒ“пјҢе…ЁеӣҪзӨҫдҝқдҪ“зі»еҚҙз”ұжӯӨе»әз«ӢпјҢжҲ‘еӣҪ银иЎҢдҪ“зі»д№ҹжӯҘе…ҘеҒҘеә·еҸ‘еұ•зҡ„еҝ«иҪҰйҒ“гҖӮдёҺеҹҺйҮҢдәәдёӢеІ—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Ҫңдёә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Ӣжёёзҡ„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пјҲд№Ўж”ҝеәңе’Ңжқ‘ж”ҝжқғеҠһзҡ„дјҒдёҡпјҢе®ҳз§°вҖңд№Ўй•ҮдјҒдёҡвҖқпјүд№ҹйҷ·е…Ҙеӣ°еўғпјҢиў«е®ҳж–№д»ҘвҖңж”ҝдјҒеҲҶејҖвҖқдёәз”ұжҳҺд»ӨвҖңиҪ¬еҲ¶вҖқгҖӮжӯӨеүҚеңЁеҮ д№Һж•ҙдёӘ90е№ҙд»ЈпјҢдёӯеӣҪ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вҖңејӮеҶӣзӘҒиө·пјҢдёүеҲҶеӨ©дёӢжңүе…¶дёҖвҖқпјҢеңЁдё–з•ҢдёҠеЈ°еҗҚжҳҫиө«гҖӮвҖңејӮеҶӣвҖқеҚіжқӮзүҢеҶӣгҖҒйқһжӯЈи§„еҶӣпјӣвҖңдёүеҲҶвҖқжҢҮеҚ е…ЁеӣҪе·Ҙдёҡдә§еҖјгҖҒеҮәеҸЈдә§еҖје’ҢзЁҺ收еҗ„дёүеҲҶд№ӢдёҖгҖӮйӮЈж—¶жқ‘жқ‘еҶ’зғҹеҠһе·ҘдёҡпјҢеҪ“然д№ҹз•ҷдёӢйҒҚең°жұЎжҹ“гҖӮйӮЈдёӘжҝҖеҠЁдәәеҝғзҡ„жөӘжҪ®д»ҠеӨ©иҝҳз•ҷдәҶдёӘвҖң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з”Ёең°вҖқзҡ„иӮҘзЎ•е°ҫе·ҙгҖӮ笔иҖ…еңЁ9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д»Ҙ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дёәйўҳеңЁзҫҺеӣҪе®ҢжҲҗдәҶеҚҡеЈ«и®әж–ҮпјҢеҚіе•ҶеҠЎеҚ°д№ҰйҰҶеҮәзүҲзҡ„гҖҠеҶңж°‘дёҺеёӮеңәгҖӢгҖӮйЈҺдә‘зӘҒеҸҳпјҢеҲ°21дё–зәӘеҲқпјҢ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вҖңиҪ¬еҲ¶вҖқжё…з®—еҮәе”®пјҢеҺҹжң¬еҚҠе·ҘеҚҠеҶңзҡ„вҖңе·ҘдәәвҖқеҸҳеӣһзәҜзІ№еҠЎеҶң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и§ҰеҸ‘дәҶе…ЁеӣҪиҢғеӣҙзҡ„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й—®йўҳгҖӮ2000е№ҙжҳҘеӨ©пјҢж№–еҢ—зӣ‘еҲ©еҺҝжҹҗд№Ўе…ҡ委д№Ұи®°жқҺжҳҢе№із»ҷжңұй••еҹәжҖ»зҗҶеҶҷдҝЎпјҢз§°ж№–еҢ—зҡ„вҖңеҶңж°‘зңҹиӢҰпјҢеҶңжқ‘зңҹз©·пјҢеҶңдёҡзңҹеҚұйҷ©вҖқгҖӮе°ұжӯӨпјҢ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жҲҗдёәе°ҪдәәзҡҶзҹҘзҡ„иҜҚжұҮгҖӮ
еңЁжқҺжҳҢе№із»ҷжҖ»зҗҶеҶҷдҝЎзҡ„еҚҒеҮ е№ҙеүҚпјҢеҶңжқ‘жҳҜдёӯеӣҪеёӮеңәеҢ–ж”№йқ©зҡ„е…Ҳй”ӢпјҢд№ҹжҳҜж”№йқ©жҲҗжһңз«Ӣз«ҝи§ҒеҪұзҡ„ж©ұзӘ—гҖҒвҖңдёҮе…ғжҲ·вҖқзҡ„ж‘ҮзҜ®гҖӮжӯҘе…Ҙ21дё–зәӘд№Ӣйҷ…пјҢеҺҹжң¬дёҚжҲҗй—®йўҳзҡ„еҶңжқ‘зЁҺиҙ№жҲҗдәҶеӨ§й—®йўҳгҖӮвҖңзЁҺвҖқжҢҮзҡ„жҳҜеҶңжҲ·зјҙзәіз»ҷеӣҪ家дёҠе№ҙзәҜ收е…Ҙд№Ӣ5%зҡ„еҶңдёҡзЁҺгҖӮвҖңиҙ№вҖқжҢҮзҡ„жҳҜвҖңдёүжҸҗдә”з»ҹвҖқпјҲжқ‘ж”ҝжқғеҗ‘еҶңжҲ·ж”¶е…¬з§ҜйҮ‘гҖҒе…¬зӣҠйҮ‘гҖҒз®ЎзҗҶиҙ№зӯүвҖңжҸҗз•ҷвҖқпјӣ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еҗ‘еҶңжқ‘з»ҸжөҺжңәжһ„е’ҢеҶңжҲ·жҸҗеҸ–ж•ҷиӮІгҖҒдјҳжҠҡгҖҒи®Ўз”ҹгҖҒж°‘е…өгҖҒеҹәе»әзӯүвҖңз»ҹзӯ№вҖқпјүпјҢеҸ–д№ӢдәҺеҶңж°‘пјҢз”Ёд№ӢдәҺеҶңжқ‘пјҢжҖ»ж•°д№ҹйҷҗе®ҡеңЁеҶңжҲ·дёҠе№ҙзәҜ收е…Ҙд№Ӣ5%гҖӮвҖңеҶңжҲ·дёҠе№ҙзәҜ收е…ҘвҖқжҳҜеӨҡе°‘пјҹеҲ«иҜҙж”ҝеәңпјҢе°ұжҳҜеҶңж°‘иҮӘе·ұд№ҹз®—дёҚжё…гҖӮеҶңжҲ·жқЎд»¶еҗ„дёҚзӣёеҗҢпјҢж ҮеҮҶдј°еҖје’ҢжңүеҶңжҲ·еҖҹж•…жӢ–延дёҚдәӨйғҪеј•еҸ‘еҚұжңәгҖӮеҶҚжңүпјҢиҮӘ8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еәҹе…¬зӨҫж”№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д»ҘжқҘпјҢ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жңәжһ„дёҚж–ӯе……е®һпјҢйә»йӣҖиҷҪе°Ҹдә”и„Ҹдҝұе…ЁпјҢдёҺеҺҝж”ҝеәңеҗ„жңәжһ„еҜ№жҺҘпјҢеҪўжҲҗвҖңдёғз«ҷе…«жүҖвҖқпјҲеҶңжңәгҖҒеҶңжҠҖгҖҒи®Ўз”ҹгҖҒе№ҝж’ӯгҖҒж–ҮеҢ–гҖҒз»Ҹз®ЎгҖҒе®ўиҝҗзӯүвҖңз«ҷвҖқпјӣдёҠзә§жҙҫеҮәзҡ„еҸёжі•гҖҒиҙўж”ҝгҖҒиӯҰеҠЎгҖҒжһ—дёҡгҖҒжҲҝз®ЎгҖҒеңҹең°гҖҒдҫӣз”өгҖҒйӮ®ж”ҝгҖҒе·Ҙе•ҶзӯүвҖңжүҖвҖқпјүгҖӮеҲ¶еәҰеҢ–дёҚйҖӮеә”еҸҳеҢ–пјҢеҠ йҮҚдәҶеҶңж°‘иҙҹжӢ…гҖӮеҶңж°‘дәәеӨҡең°е°‘пјҢеҶңдёҡдёҚиөҡй’ұпјҢжІЎжңүйӣҶдҪ“з»ҸжөҺд»ЈзјҙзЁҺиҙ№пјҢеҶңж°‘иҙҹжӢ…е°ұжҲҗдәҶеҺӢеһ®йӘҶй©јзҡ„жңҖеҗҺдёҖж №зЁ»иҚүпјҢз»ҙжқғжҠ—дәүпјҢвҖңзғҪзғҹйҒҚең°вҖқгҖӮйӮЈж—¶пјҢ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и®Өе®ҡеҶңжқ‘еҹәеұӮж”ҝжқғиғЎдҪңйқһдёәеҜјиҮҙдәҶеҶңж°‘иҙҹжӢ…пјҢе°ұе…ҲеәҹжҺүдәҶвҖңиҙ№вҖқгҖӮжІЎдәҶвҖңиҙ№вҖқпјҢеҶңжқ‘еҹәеұӮж”ҝжқғжҖҺд№Ҳжҙ»пјҹеңЁдёҖжү№дә¬еҹҺдё»з®Ўзҡ„жғіиұЎйҮҢпјҢзӯ”жЎҲжҳҜвҖңйҖүдёҫвҖқпјҢиҖҢдё”жҳҜвҖңжө·йҖүвҖқпјҢе…Ҳз«һйҖүеҖҷйҖүдәәпјҢеҶҚз«һйҖү第дәҢиҪ®гҖӮйҖүдёҠжқ‘дё»д»»е°ұиў«зӘҒеҮ»е…Ҙе…ҡпјҢжқ‘дё»д»»е’Ңжқ‘д№Ұи®°вҖңдёҖиӮ©жҢ‘вҖқгҖӮеҰӮжӯӨпјҢе…ҡзҡ„йўҶеҜјжј”еҸҳжҲҗдәҶвҖңе°Ғе»әеңҹеӣҙеӯҗвҖқгҖӮеҪ“ж—¶е®ҳеӯҰдёӨз•ҢдёҚе°‘жңүеҪұе“ҚеҠӣзҡ„дәәи®ӨдёәпјҢз«һйҖүе°ұжҳҜж°‘дё»пјҢж°‘дё»е°ұжҳҜз«һйҖүпјҢе°ҶжқҘжӯҘжӯҘеҚҮзә§дёәжө·йҖүд№Ўй•Үй•ҝгҖҒеҺҝеёӮй•ҝгҖҒзңҒй•ҝгҖҒжҖ»зҗҶпјҢе°ұжҳҜдёӯеӣҪж”ҝжІ»ж”№йқ©зҡ„ж–№еҗ‘гҖӮеҫҲеҝ«пјҢдёӯеӨ®еҸ‘зҺ°ж”¶еҶңдёҡзЁҺж—Ҙжёҗиү°йҡҫпјҢ收зЁҺжҲҗжң¬иҝңеӨ§дәҺ收еҲ°зҡ„зЁҺж¬ҫпјҢдҫҝеңЁ2006е№ҙ1жңҲ1ж—ҘеҪ»еә•еәҹйҷӨдәҶдёӯеӣҪдёӨеҚғе…ӯзҷҫе№ҙзҡ„еҶңдёҡзЁҺ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дёҖдёӨе№ҙеүҚпјҢ2004е№ҙпјҢдёӯеӨ®е·ІејҖе§Ӣе®һж–ҪеҶңдёҡвҖңзӣҙиЎҘвҖқпјҢи®©еҹҺйҮҢдәәеҸҚе“әеҶңдёҡ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ҶҚдёӨдёүе№ҙеүҚпјҢ2001е№ҙ12жңҲ11ж—ҘпјҢдёӯеӣҪеҠ е…ҘWTOпјҢејҖе§Ӣеҗ‘дё–з•ҢејҖж”ҫеҶңдёҡеёӮеңәпјҢд»ҺжӯӨжҲ‘еӣҪдё»иҰҒеҶңдә§е“Ғд»·ж је°ұдёҖ蹶дёҚжҢҜдәҶгҖӮеҮәд№Һж„Ҹж–ҷзҡ„жҳҜпјҢжҲ‘еӣҪеҶңдёҡгҖҒеҶңжқ‘гҖҒеҶңж°‘зҡ„з ҙдә§еҜјиҮҙдәҶе»үд»·еҠіеҠӣдҫӣеә”жҡҙеўһпјҢжқҘж–ҷеҠ е·ҘеҮәеҸЈдјҒдёҡзҲҶзӮёејҸеҸ‘еұ•гҖӮдәҡжҙІ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еҚҒе№ҙеҗҺпјҢеҲ°2008е№ҙзҫҺеӣҪеј•еҸ‘дё–з•Ң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ж—¶пјҢдёӯеӣҪе·ІжҲҗвҖңдё–з•Ңе·ҘеҺӮвҖқпјҢд№ҹжҳҜвҖңдё–з•ҢзғҹеӣұвҖқгҖӮиІҢдјјж— и§Јзҡ„гҖҒд»ҘдәәеӨҡең°е°‘дёәж ёеҝғзҡ„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й—®йўҳеҝҪ然ж¶ҲеӨұгҖӮжқ‘йҮҢеӨҡдёәиҖҒејұеҰҮеӯәз—…ж®ӢпјҢиҖ•ең°жҠӣиҚ’жёҗжҲҗвҖңж–°еёёжҖҒвҖқгҖӮдё–дәӢйҡҫж–ҷпјҢеӨ§еӨҡж•°йҡҫйўҳдёҚжҳҜвҖңи§ЈеҶівҖқ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вҖңзҶ¬вҖқиҝҮеҺ»зҡ„гҖӮиҮӘдҪңиҒӘжҳҺпјҢеӮІж…ўең°и®ӨдёәиғҪйў„и§Ғз”ҡиҮіжҠҠжҺ§жңӘжқҘе°ұйҡҫе…ҚзҠҜй”ҷпјҢжҜ”еҰӮдёҖиғҺж”ҝзӯ–гҖӮ
д»ҺдәҡжҙІ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еҲ°дё–з•Ң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зҡ„еҚҒе№ҙжҳҜдёӘеӣ°йҡҫж—¶д»ЈпјҢ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жҳҜдё»ж—ӢеҫӢпјҢиҖҢдё”ж”№йқ©дјҡеҮәз«Ӣз«ҝи§ҒеҪұзҡ„жҲҗе°ұгҖӮж”№йқ©пјҢдёӨжқЎи…ҝиө°и·ҜпјҢдёҚд»…жқҘиҮӘдёӯеӨ®пјҢиҖҢдё”жқҘиҮӘдёӢеұӮзҡ„еҺҝгҖӮйӮЈж—¶еҺҝзә§зҡ„и‘—еҗҚж”№йқ©дәәзү©еұӮеҮәдёҚз©·пјҢе…¶дёӯе°ұеҢ…жӢ¬ж№–еҢ—зҡ„е®Ӣдәҡе№ігҖӮйӮЈеҚҒе№ҙжҳҜжҝҖжғ…вҖңж”№йқ©вҖқж—¶д»ЈпјҢдёҠдёӢйғҪж•ўдәҺжӢ…еҪ“гҖӮдёҺ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вҖңж‘ёзқҖзҹіеӨҙиҝҮжІівҖқдёҚеҗҢпјҢйӮЈжҳҜйҒҮеҲ°д»Җд№ҲеӨ§й—®йўҳе°ұдјҳе…Ҳи§ЈеҶід»Җд№Ҳй—®йўҳзҡ„еҚҒе№ҙпјҢжҳҜвҖңе®һдәӢжұӮжҳҜвҖқзҡ„е№ҙд»ЈгҖӮйӮЈж—¶ж— дәәдәүи®әвҖңеёӮеңәдёҺж”ҝеәңе…ізі»вҖқд№Ӣзұ»зҡ„е®ҸеӨ§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иҜқйўҳпјҢд№ҹжІЎдәәж•ўз§°иҮӘе·ұжңүиғҪеҠӣиҝӣиЎҢвҖңйЎ¶еұӮи®ҫи®ЎвҖқгҖӮеӨ§е®¶йғҪеңЁиҜ•й”ҷгҖӮи§ЈеҶідёҚдәҶй—®йўҳзҡ„ж”№йқ©ж–№жЎҲе°ұеәҹйҷӨпјӣж–°ж–№жЎҲеҲ¶йҖ дәҶж–°й—®йўҳпјҢе°ұй’ҲеҜ№ж–°й—®йўҳеҶҚжҸҗж–°зҡ„ж”№йқ©ж–№жЎҲгҖӮдёҠдёӢйҪҗжүӢпјҢж—ўйҖ е°ұдәҶ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зҡ„зҒ«зәўе№ҙд»ЈпјҢд№ҹйҖ е°ұдәҶж”ҝеҮәеӨҡй—Ёзҡ„ж··д№ұе’Ңи…җиҙҘгҖӮж··д№ұзҡ„еҠЁиғҪжҳҜжғҠдәәзҡ„пјҢ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еҘҮиҝ№е°ұиҜһз”ҹдәҺж··д№ұдёӯгҖӮ
дәҢгҖҒ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зҡ„ж ёеҝғжҳҜ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
жқҺжҳҢе№ізҡ„иҜүиӢҰдҝЎе’Ңе®Ӣдәҡе№ізҡ„ж”№йқ©йғҪеҸ‘з”ҹеңЁж№–еҢ—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жҳҜж№–еҢ—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еҸ‘з”ҹеңЁж№–еҢ—пјҹжҲ‘е°‘е№ҙж—¶жӣҫжҺҘиҝһеңЁиҙөе·һгҖҒжұҹиҘҝгҖҒж№–еҢ—еҗ„з”ҹжҙ»дёҖе№ҙгҖӮж№–еҢ—иҚҶе·һжқЎд»¶жңҖеҘҪпјҢжңүзұіжңүиҺІи—•иҸұи§’иҝҳжңүйұјиҷҫпјҢдёҖдёҫз»Ҳз»“дәҶйҘҘйҘҝи®°еҝҶгҖӮжқҺжҳҢе№ізҡ„зӣ‘еҲ©еҺҝеҺ»жӯҰжұүдёҚдҫҝпјҢеҚҙеұһиҚҶе·һең°еҢәпјҢеңЁжұҹжұүе№іеҺҹеҚ—дҫ§пјҢйӮ»жҙһеәӯж№–гҖҒжҙӘж№–гҖҒй•ҝжұҹпјҢиҝҳзҙ§йӮ»ж№–еҚ—第дәҢеӨ§еҹҺеІійҳігҖӮиҮӘ然жқЎд»¶еҘҪпјҢ3500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ж—¶еёёжј«ж°ҙзҡ„еңҹең°е…»жҙ»дәҶ100дёҮиӢҰж’‘зқҖеҠЎеҶңзҡ„зҷҫ姓пјҢдёҚж„ҝиғҢдә•зҰ»д№ЎеҠЎе·ҘгҖӮдёҚдёңдёҚиҘҝпјҢдёҚжҳҜдёңиҘҝпјҢй—®йўҳд№ҹдёҚиҘҝдёҚдёңгҖӮ
зәөи§ӮжҲ‘еӣҪеӣӣеҚҒе№ҙжқҘзҡ„ж”№йқ©пјҢеӨ§ж–№еҗ‘еҪ“然жҳҜеёӮеңәеҢ–гҖӮдҪҶж”№йқ©з»қйқһдёәж”№йқ©иҖҢж”№йқ©гҖҒдёәеӨ§ж–№еҗ‘иҖҢж”№йқ©пјҢжӣҙйқһж— зҡ„ж”ҫзҹўгҖҒйҡҸж„ҸжҠҳи…ҫдёӢеұһе’Ңзҷҫ姓гҖӮж”№йқ©еҠЁеҠӣжқҘиҮӘйЈҺдә‘зӘҒеҸҳпјҢжӯӨеүҚеҚҒдҪҷе№ҙеҲҡи®ҫз«Ӣзҡ„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зһ¬й—ҙеҸҳжҲҗйңҖиҰҒз«ӢеҚіи§ЈеҶізҡ„еӨ§й—®йўҳгҖӮ10%зҡ„иҙҹжӢ…еҶңж°‘жүҝеҸ—дёҚиө·дәҶпјҢеҸӘеҘҪеәҹжҺүзЁҺиҙ№гҖӮејҖж”ҫдәҶеҶңдә§е“ҒиҝӣеҸЈпјҢеҶңж°‘иҰҒз ҙдә§пјҢеҸӘеҘҪеҸ‘з§ҚжӨҚиЎҘиҙҙгҖӮжӯӨж—¶ж•ҷиӮІйғЁвҖңзҒ«дёҠжөҮжІ№вҖқжҗһвҖңжҷ®д№қвҖқпјҢ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жІЎй’ұпјҢеҸӘеҘҪж”№дёәеҺҝе’ҢзңҒжүҝжӢ…гҖӮдёҠзә§ж”ҝеәңд№ҹжӢ…дёҚиө·пјҢе°ұеҸ·еҸ¬зӨҫдјҡжҚҗиө„е»әвҖңеёҢжңӣе°ҸеӯҰвҖқгҖӮеҪ“е№ҙеҠһ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зјәй’ұпјҢ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йӣҶиө„еҠһвҖңеҶңжқ‘еҗҲдҪңеҹәйҮ‘дјҡвҖқгҖӮдјҒдёҡеһ®дәҶпјҢвҖңеҹәйҮ‘дјҡвҖқж¬ дёӢжө·йҮҸеҖәеҠЎпјҢеҺҝеәңе°ұеҫ—жғіеҠһжі•жҗһз ҙдә§жё…еҖәпјҢвҖңи°Ғзҡ„еӯ©еӯҗи°ҒжҠұиө°вҖқгҖӮ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дҪ“еҲ¶е»әжҲҗдәҶпјҢеҚҙжІЎдәҶдјҒдёҡеҒҡеҗҺзӣҫпјҢеҜјиҮҙеҶңж°‘иҙҹжӢ…еҠ йҮҚпјҢеҸӘеҘҪеҸҲжӢҶжҺүгҖӮе®Ӣдәҡе№ізӯүвҖңдёғе“ҒвҖқ们иҮӘдёӢиҖҢдёҠжҺЁеҠЁ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пјҢе°ұжңүдәҶиҖҢд»Ҡзҡ„д№ЎиҙўеҺҝз®ЎгҖҒд№Ўй•Үж”ҝеәңдәәе‘ҳеҸҠе·ҘдҪңејҖж”Ҝз”ұеҺҝйҮҢжӢЁж¬ҫгҖӮиҝҷдәӣвҖң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вҖқжҳҜдёҚжҳҜвҖңеёӮеңәеҢ–вҖқпјҹдёҚйҮҚиҰҒпјҢ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еҮәд»Җд№Ҳй—®йўҳи§ЈеҶід»Җд№Ҳй—®йўҳпјҢе“ӘйҮҢеҮәй—®йўҳе°ұеңЁе“ӘйҮҢи§ЈеҶігҖӮе®һдәӢжұӮжҳҜпјҢеӣҪ家е°ұеңЁдёҚж–ӯи§ЈеҶій—®йўҳдёӯиҝӣжӯҘгҖӮдёҚиҝҮеҚҒеҮ 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жқ‘еҠһе°ҸеӯҰж¶ҲеӨұдәҶпјҢд№Ўй•ҮдёӯеӯҰд№ҹеҮӢйӣ¶дәҶпјҢеҪ“е№ҙеңЁеұұжқ‘йҮҢе»әзҡ„вҖңеёҢжңӣе°ҸеӯҰвҖқе·ІжҲҗж®ӢеһЈж–ӯеЈҒгҖӮ家зҢӘеҸҳйҮҺзҢӘпјҢз”ҹжҖҒжӯЈжҒўеӨҚпјҢвҖңжІүиҲҹдҫ§з•”еҚғеёҶиҝҮпјҢз—…ж ‘еүҚеӨҙдёҮжңЁжҳҘвҖқгҖӮ
д»Җд№ҲжҳҜ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пјҹж”№йқ©ж”№зҡ„жҳҜжқғеҠӣжңәжһ„е’ҢжқғеҠӣиҝҗиЎҢжңәеҲ¶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иҰҒж”№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пјҹдёҚжҳҜеӣ дёәвҖңеӨ§ж–№еҗ‘вҖқпјҢдёҚжҳҜеӣ дёәиҰҒдёҺе…Ҳиҝӣзҡ„еӨ–еӣҪжҺҘиҪЁпјҢдёҚжҳҜеӣ дёәеӨ–еӣҪеҺӢзқҖжҲ‘们改пјҢдёҚжҳҜеӣ дёәеӨ–еӣҪзҡ„жңҲдә®жҜ”дёӯеӣҪеңҶпјҢиҖҢжҳҜеӣ дёәеүҚиҝӣйҒҮеҲ°дәҶиҝҮдёҚеҺ»зҡ„еқҺпјҢзҺ°еӯҳзҡ„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ҲҗдәҶй—®йўҳжң¬иә«гҖӮ
з»ҸжөҺе’ҢжҲҝең°дә§з№ҒиҚЈеҜјиҮҙзЁҺ收еҝ«йҖҹеўһеҠ пјҢеҹәе»әиө„йҮ‘е……иЈ•пјҢдәәж°‘з”ҹжҙ»еҝ«йҖҹж”№е–„пјҢд№ҹеӮ¬з”ҹдәҶи¶ҠжқҘи¶Ҡз№ҒжқӮзҡ„ж”ҝеәңжңҚеҠЎе’Ңзӣ‘з®ЎгҖӮж”ҝеәңжңәжһ„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йӣҮз”Ёзҡ„дёҙж—¶её®жүӢд№ҹ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гҖӮдҪҶеҪ“з»ҸжөҺйҒҮеҲ°еӣ°йҡҫе°ұеҫ—вҖң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вҖқдәҶгҖӮеӣӣеҚҒе№ҙ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жіўжҠҳдёҚж–ӯпјҢ并йқһдёҖи·ҜеҮҜжӯҢпјҢжүҖд»Ҙ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д№ҹжҗһиҝҮеӨҡж¬ЎгҖӮиҖҢд»ҠдёҚеҗҢпјҢзҙ§ж—Ҙеӯҗй•ҝжңҹеҢ–пјҢ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дёҚеҶҚжҳҜзҹӯжңҹиЎҢдёәдәҶгҖӮ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жҳҜи§ЈеҶіз»ҸжөҺеӣ°еўғзҡ„еҠһжі•пјҢжүҖд»Ҙж— и®әеҸӨд»ҠдёӯеӨ–пјҢ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зҡ„ж ёеҝғжҒ’е®ҡжҳҜ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гҖӮе…Ҳй”Ӣж”№йқ©иҖ…еҰӮе®Ӣдәҡ平们вҖңиғҶеӨ§еҰ„дёәвҖқжҗһж”№йқ©пјҢ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жҳҜдё»иҰҒеҶ…е®№гҖӮеӣҪдәәзҶҹзҹҘ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иҝҷдёӘиҜҚеӨҡжҳҜеӣ 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еҗҢеҝ—зҡ„ж–Үз« гҖҠдёәдәәж°‘жңҚеҠЎгҖӢгҖӮж–Үдёӯжңүж®өйқһеёёи‘—еҗҚзҡ„иҜқпјҡ
гҖҗвҖңвҖҳ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вҖҷиҝҷдёҖжқЎж„Ҹи§ҒпјҢе°ұжҳҜе…ҡеӨ–дәәеЈ«жқҺйјҺй“ӯе…Ҳз”ҹжҸҗеҮәжқҘзҡ„пјӣд»–жҸҗеҫ—еҘҪпјҢеҜ№дәәж°‘жңүеҘҪеӨ„пјҢжҲ‘们е°ұйҮҮз”ЁдәҶгҖӮеҸӘиҰҒжҲ‘们дёәдәәж°‘зҡ„еҲ©зӣҠеқҡжҢҒеҘҪзҡ„пјҢдёәдәәж°‘зҡ„еҲ©зӣҠж”№жӯЈй”ҷзҡ„пјҢжҲ‘们иҝҷдёӘйҳҹдјҚе°ұдёҖе®ҡдјҡе…ҙж—әиө·жқҘгҖӮвҖқгҖ‘
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дёҚжҳҜзӣ®зҡ„иҖҢжҳҜжүӢж®өгҖӮжҳҜжүӢж®өе°ұжңүе‘ЁжңҹжҖ§иҙЁпјҢз»ҸжөҺеҘҪж—¶жү©еј пјҢз»ҸжөҺе·®дәҶ收缩гҖӮдҪҶз®Җж”ҝиҝҷдёӘиҜҚзІ—зіҷпјҢиҝҳеҸҜиғҪзІ—жҡҙпјҢеј„еҮәд№ұеӯҗгҖӮж”ҫејғиҚҜе“ҒйЈҹе“Ғзӣ‘з®ЎеҸҜиғҪеј•еҸ‘е…¬е…ұе®үе…Ёй—®йўҳгҖӮж”ҫејғзӣ‘з®ЎйҮ‘иһҚдёҡиҖҢеҜјиҮҙ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пјҢжҲҗжң¬е°ұдёҚд»…жҳҜзӣ‘з®Ўдәәе‘ҳзҡ„ејҖж”ҜдәҶгҖӮжңүдәӣвҖңж”ҝвҖқйқһдҪҶеҮҸдёҚеҫ—пјҢиҝҳеҫ—еҠ ејә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…өдёҚеңЁеӨҡиҖҢеңЁвҖңзІҫвҖқпјҢжҸҗй«ҳиЎҢж”ҝж•ҲзҺҮжүҚжҳҜ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зҡ„е…ій”®гҖӮйғҪеёӮзҡ„ж ёеҝғжҳҜе…¬жңүе’Ңе…ұжңүиҙўдә§пјҢжүҖд»ҘеӨ§йғҪеёӮ秩еәҸзҡ„еҹәзЎҖжҳҜдҝқжҠӨе…¬жңүе’Ңе…ұжңүиҙўдә§пјҢйҳІжӯўиў«дҫөеҚ жҲҗз§Ғ家еҲ©зӣҠгҖӮдҝқжҠӨе…¬жңүиҙўдә§ж„Ҹе‘ізқҖдёҘзҰҒе…¬е…ұйҒ“и·ҜеҸҳдёәз§Ғ家иҪҰеҒңиҪҰеңәгҖӮдҝқжҠӨе…ұжңүиҙўдә§йңҖиҰҒжү§жі•жңәе…іиҝӣе…¬еҜ“еӨ§жҘјзӨҫеҢәпјҢеҲ¶жӯўе•ҶдҪҸж··еҗҲпјҢеҲ¶жӯўиҝқз« е»әзӯ‘пјҢеҲ¶жӯўжӢ–延зјҙзәізү©дёҡиҙ№гҖӮиҝҷдјјд№ҺйғҪиҰҒжұӮжӣҙеӨҡзҡ„жү§жі•дәәжүӢгҖӮ然иҖҢпјҢд»ҘзҪҡд»Јз®ЎпјҢи®©иҝқжі•жҲҗжң¬иҝңиҝңй«ҳдәҺжү§жі•жҲҗжң¬пјҢжҳҜй«ҳж•Ҳз»ҙжҠӨйғҪеёӮ秩еәҸзҡ„дёҚдәҢжі•й—ЁгҖӮиҝҷд№ҹиҰҒжұӮеҸёжі•е’Ңз«Ӣжі•жңәе…іж”ҜжҢҒж°‘жі•еҘ‘зәҰгҖӮдёҚеҺ»ж”ҜжҢҒеҹҺеёӮ秩еәҸзҡ„жӯЈд№үдёҚжҳҜвҖңи®Іж”ҝжІ»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и®©ж”ҝжІ»и…җзғӮпјҢи®©иҝқжі•е’ҢеҚ 公家дҫҝе®ңжҲҗдёәд№ дҝ—пјҢи®©еӨ§йғҪеёӮ秩еәҸеҸҜжңӣиҖҢдёҚеҸҜеҚігҖӮеңЁеӨ§еӯҰжҗһдёҖеҚғе№ҙвҖңйҖҡиҜҶж•ҷиӮІвҖқд№ҹйЎ¶дёҚдёҠжҠҠеқҡеҶіжҚҚеҚ«е…¬жңүе’Ңе…ұжңүиҙўдә§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ҝзӯ–еқҡжҢҒеҚҒе№ҙгҖӮе…¬зӣҠзІҫзҘһзҡ„ж»‘еқЎдёҚжҳҜж•ҷиӮІеҜјиҮҙзҡ„пјҢжҳҜж”ҝзӯ–з»“жһ„еҜјиҮҙзҡ„гҖӮ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дёәзҡ„жҳҜжҸҗй«ҳжү“д»—зҡ„ж•ҲзҺҮ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жү“иғңд»—гҖӮжү“дёҚиөўпјҢз”ҡиҮіжәғиҙҘпјҢзІҫе…өз®Җж”ҝе°ұеӨұиҙҘдәҶгҖӮеҺҶеҸІеҗ‘жқҘд»Ҙз»“жһңи®әиӢұйӣ„гҖӮ
дёүгҖҒвҖңиһәж—ӢејҸ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и·Ҝеҫ„
жҲ‘еӣҪд»ҘвҖңж”№йқ©вҖқе‘ҪеҗҚдёҖдёӘй•ҝиҫҫеӣӣеҚҒе№ҙзҡ„ж—¶д»ЈгҖӮеҶҚж—©зҡ„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еҗҚдёәвҖңйқ©е‘ҪвҖқпјҢжӣҙж—©зҡ„йӮЈдёӘз§°вҖң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гҖӮе°Ҫз®ЎвҖңе‘ЁиҷҪж—§йӮҰпјҢе…¶е‘Ҫз»ҙж–°вҖқпјҢдҪҶдёӯеӣҪдёӨеҚғеӨҡе№ҙвҖңдёҚеҸҳзҡ„е°Ғе»әвҖқеңЁдәәзұ»ж–ҮжҳҺеҸІдёҠд№ҹжҳҜжңөеҘҮи‘©гҖӮзҷҫе№ҙ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еҸҳйқ©ж¬ІеҰӮжӯӨејәзғҲпјҢдё–з•ҢдёҠеҶҚжүҫдёҚеҮә第дәҢеӣҪ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пјҹзӯ”жЎҲдјјд№ҺжҳҜиҝҪжұӮвҖң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гҖӮдҪҶд»Җд№ҲжҳҜзҺ°д»Јпјҹд»Җд№ҲжҳҜзҺ°д»ЈеҢ–пјҹ
еңЁд»Ҙ欧жҙІз»ҸйӘҢ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иҘҝеӯҰзҹҘиҜҶйҮҢпјҢвҖңзҺ°д»ЈвҖқдёҺвҖңдј з»ҹвҖқжҳҜдёӨеҲҶзҡ„гҖӮз”ұдәҺ第дёҖдә§дёҡзҡ„дё»еҜјдҪң用被第дәҢдә§дёҡеҸ–д»ЈпјҢдҫӣйңҖдёӨж—әгҖҒдҫӣйңҖдёӨзӣёдҫқеӯҳзҡ„еёӮеңәдҪ“зі»еҸ‘еұ•иө·жқҘдәҶпјҢд№ жғҜгҖҒе®—ж•ҷгҖҒиЎҖзјҳгҖҒең°еҹҹдё»еҜјзҡ„вҖңдј з»ҹвҖқзӨҫдјҡи®©дҪҚдәҺвҖңеёӮеңәзҗҶжҖ§вҖқпјҲзҗҶжҖ§еҚізІҫз®—еҫ—еӨұиҙҰпјүдё»еҜјзҡ„вҖңзҺ°д»ЈвҖқзӨҫдјҡгҖӮеёӮеңәзҗҶжҖ§еӮ¬з”ҹдәҶз”ұдёӯз«Ӣжү§жі•дҪ“зі»ж”Ҝж’‘зҡ„вҖңзӨҫдјҡзҗҶжҖ§вҖқгҖӮзӨҫдјҡзҗҶжҖ§еҸҲеӮ¬з”ҹдәҶвҖңж”ҝжІ»зҗҶжҖ§вҖқпјҢеҚіе…¬ејҖжӢҚеҚ–ж”ҝеәңжқғеҠӣпјҢеҮәд»·й«ҳиҖ…еҫ—гҖӮжӯӨеҚівҖңзҺ°д»ЈжҖ§вҖқгҖӮеҫҖзҺ°д»ЈжҖ§ж–№еҗ‘еҸҳеҢ–еҚівҖң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пјҢжҲ–з§°еёӮеңәеҢ–гҖҒжі•жІ»еҢ–гҖҒж°‘дё»еҢ–гҖӮ
дёӯеӣҪж—©еңЁвҖңдј з»ҹзӨҫдјҡвҖқзҡ„еҲқжңҹе°ұе®ҢжҲҗдәҶвҖңдё–дҝ—еҢ–вҖқпјҢд№ҹж—©жңүвҖңеёӮеңәзҗҶжҖ§вҖқпјҢиҖҢдё”еёӮеңәзҗҶжҖ§дёҺиЎҖзјҳгҖҒең°еҹҹгҖҒд№ жғҜзӯүзӯүвҖңдј з»ҹвҖқз»“еҗҲеҫ—еӨ©иЎЈж— зј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ёӯеӣҪж”ҝеӯҰдёӨз•ҢдёҚиҖҗзғҰиҘҝеӯҰйӮЈдәӣејҜејҜз»•гҖӮ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вҖң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зҡ„е®ҡд№үз®ҖеҚ•еҲ°еӣӣдёӘеӯ—пјҡвҖңеӣҪејәж°‘еҜҢвҖқгҖӮдҪ•дёәеӣҪејәпјҹеғҸд»»дҪ•иҘҝж–№ејәеӣҪдёҖж ·ејәгҖӮдҪ•дёәж°‘еҜҢпјҹеғҸд»»дҪ•иҘҝж–№еӣҪ家зҡ„ж°‘дј—дёҖж ·еҜҢгҖӮж—Ҙжң¬жҸҗж—©еңЁвҖңиҝ‘д»ЈвҖқе°ұеҒҡеҲ°дәҶеӣҪејәж°‘еҜҢпјҢж•…з§°вҖңиҝ‘д»ЈеҢ–вҖқгҖӮдёӯеӣҪеӨ§еҫ—еӨҡпјҢжғ…еҶөд№ҹеӨҚжқӮеҫ—еӨҡпјҢзӣҙеҲ°вҖңзҺ°д»ЈвҖқжҲ–вҖңеҪ“д»ЈвҖқиҝҳжІЎеҒҡеҲ°пјҢжүҖд»ҘиҮід»ҠиҝҳиҰҒвҖң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гҖӮ
еҸҜжҖҺд№ҲжүҚиғҪиҫҫеҲ°еӣҪејәж°‘еҜҢпјҹеңЁиҘҝеӯҰз»ҹжІ»еӨ§еӯҰж–Ү科зҡ„ж—¶д»ЈпјҢй—®йўҳдјјд№ҺеҸҲеӣһеҲ°дәҶвҖңеёӮеңәеҢ–гҖҒжі•жІ»еҢ–гҖҒж°‘дё»еҢ–вҖқиҝҷз§ҚеӨ§иҖҢеҢ–д№Ӣзҡ„жҰӮеҝөгҖҒи§ӮеҝөгҖӮ
еӣӣеҚҒе№ҙж”№йқ©зҡ„е·ЁеӨ§жҲҗе°ұжҳҜи°Ғд№ҹеҗҰи®ӨдёҚдәҶзҡ„гҖӮдҪҶиҖҢд»ҠеҫҲеӨҡдәәи®ӨдёәпјҢеҗҰе®ҡдёӨдёӘдёүеҚҒе№ҙдёӯзҡ„еӨҙдёҖдёӘпјҢжҳҜеҗҺдёүеҚҒе№ҙзҡ„ж•ҷи®ӯжүҖеңЁгҖӮиҜҙ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ж—¶д»ЈеҸӘжңүжҲҗе°ұжІЎжңүж•ҷи®ӯжҳҜзқҒзңјиҜҙзһҺиҜқгҖӮеҶӣж”ҝи…җиҙҘпјҢзӨҫдјҡдёҖзӣҳж•ЈжІҷпјҢе…¬еҫ·ж»‘еқЎпјҢзІҫиӢұдёҺе№іж°‘еҲҶиЈӮпјҢжҖқжғіж··д№ұпјҢзҷҫ姓养е°ҸйҖҒиҖҒж—Ҙжёҗиү°йҡҫпјҢиҮӘ然зҺҜеўғеӨ§з ҙеқҸпјҢйғҪжҢҮеҗ‘зӨҫдјҡйўҶеҹҹзҡ„еёӮеңәеҢ–д№ӢиҜҜпјҢд№ҹжҢҮеҗ‘и®©е…ЁзӨҫдјҡжүҝжӢ…дјҒдёҡиөҡй’ұзҡ„вҖңиҙҹеӨ–йғЁжҖ§вҖқжҲҗжң¬д№ӢиҜҜгҖӮеӣә然пјҢеҸ‘еұ•еҝ…йЎ»д»ҳд»Јд»·пјҢжІЎжңүдёҚд»ҳжҲҗжң¬зҡ„иҝӣжӯҘгҖӮз”ҡиҮіпјҢжҲҗе°ұи¶ҠеӨ§пјҢжҲҗжң¬и¶Ҡй«ҳпјҢеӣ дёәеӨ©дёҠдёҚжҺүйҰ…йҘјгҖӮ然иҖҢпјҢз»ҲдәҺжңүдёҖеӨ©пјҢжҲҗжң¬зӯүдәҺз”ҡиҮій«ҳдәҺжҲҗе°ұпјҢиҖҒеҠһжі•жҢҒз»ӯдёҚдёӢеҺ»пјҢеҸ‘еұ•е°ұиҝҹж»һдәҶгҖӮе•ғеҲ°дәҶиҖҒзҷҫ姓зҡ„йӘЁеӨҙпјҢйӘЁеӨҙе°ұи¶ҠжқҘи¶ҠзЎ¬пјҢж—©жҷҡдјҡеҙ©жҺүзүҷйҪҝ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жҲ‘еӣҪе°ұиҝӣе…ҘдәҶвҖңж–°ж—¶д»ЈвҖқгҖӮеңЁеҚҒд№қеӨ§пјҢе…ҡдёӯеӨ®еҮҶзЎ®ең°жҠҠвҖңдёҚе№іиЎЎеҸ‘еұ•вҖқж”ҫеңЁдәҶвҖңдёҚе……еҲҶеҸ‘еұ•вҖқд№ӢеүҚдҪңдёәдёӨеӨ§дё»иҰҒзҹӣзӣҫд№ӢдёҖгҖӮ
д»Җд№ҲжҳҜ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пјҹеңЁжҲ‘зңӢпјҢ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дёҺдј з»ҹзӨҫдјҡжңҖеӨ§зҡ„дёҚеҗҢжҳҜеҝ«йҖҹзҡ„гҖҒдёҚй—ҙж–ӯ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科жҠҖеҲӣж–°жҳҜиҝҷ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дё»ж—ӢеҫӢпјҢдёҚж–ӯеҠ йҖҹзҡ„科жҠҖеҲӣж–°еёҰжқҘдәҶдёҚй—ҙж–ӯзҡ„зӨҫдјҡеҸҳеҢ–гҖӮиҝҷеңЁйқ еӨ©еҗғйҘӯзҡ„第дёҖдә§дёҡж—¶д»Јз»қйҡҫжғіиұЎгҖӮеңЁдёҚй—ҙж–ӯзҡ„е·ЁеҸҳдёӯпјҢдёҚеҸҜйў„жөӢжҳҜе”ҜдёҖиғҪйў„жөӢзҡ„гҖӮиҝҷеёҰжқҘдәҶдёӨеӨ§з»“жһңпјҡе…¶дёҖжҳҜдәә们иҝҪжұӮеҲ¶еәҰеҢ–пјҢдјҒеӣҫд»ҘеҲ¶еәҰеңЁж— еәҸдёӯжүҫеҲ°зЁіе®ҡе’ҢеҪ’еұһпјӣе…¶дәҢжҳҜеҲ¶еәҰзЁідёҚдҪҸпјҢеҲҡе»әзҡ„еҲ¶еәҰеҫҲеҝ«е°ұиҝҮж—¶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еңЁжёҙжңӣвҖң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зҡ„дёӯеӣҪпјҢ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ж”№йқ©вҖңж°ёиҝңеңЁи·ҜдёҠвҖқгҖӮ
еҰӮжһңж”№йқ©ж°ёиҝңеңЁи·ҜдёҠпјҢзә жӯЈеӨұиҜҜе°ұж„Ҹе‘ізқҖвҖңиһәж—ӢејҸвҖқзҡ„еҸ‘еұ•гҖӮеҺҶеҸІдёҚдјҡеҖ’йҖҖпјҢдәәдёҚеҸҜиғҪдёӨж¬ЎиёҸе…ҘеҗҢдёҖжқЎжІігҖӮдҪҶж”№йқ©д№ӢеҗҺеҶҚж”№йқ©ж„Ҹе‘ід»Җд№Ҳпјҹж„Ҹе‘ізқҖи§ЈеҶій—®йўҳзҡ„ж–°ж–№жі•иІҢдјјеӣһеҲ°иҝҮеҺ»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вҖңеҗҰе®ҡд№ӢеҗҰе®ҡвҖқ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вҖңжӯЈеҸҚеҗҲвҖқйўҳ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вҖңеӣһеҲ°жңӘжқҘвҖқгҖӮ
еңЁиҖ•ең°еӨ§йқўз§Ҝж’ӮиҚ’д№Ӣйҷ…пјҢжҲ‘们дёҖеҰӮж—ўеҫҖең°зҫЎж…•е…Ҳиҝӣзҡ„вҖң规模еҶңдёҡвҖқгҖӮеӣӣеҚҒе№ҙеүҚпјҢжҲ‘еӣҪд»ҺвҖңдёүзә§жүҖжңүпјҢйҳҹдёәеҹәзЎҖвҖқзҡ„еҶңжқ‘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еӣһеҪ’дәҶе°ҸеҶң家еәӯиҖ•дҪңгҖӮдҪҶйӮЈдёҚжҳҜз®ҖеҚ•зҡ„вҖңеӣһеҪ’вҖқпјҢжҳҜеңЁж–°дёӯеӣҪеңҹең°ж”№йқ©еҹәзЎҖдёҠзҡ„еӣһеҪ’пјҢжҳҜеңЁиҖ•ең°з»қеҜ№е№іеқҮеҢ–еҹәзЎҖдёҠзҡ„вҖңеӣһеҪ’вҖқгҖӮйӮЈдёӘвҖңеӣһеҪ’вҖқз»ҷдәҶеҶңж°‘иҮӘз”ұ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зҰ»еңҹзҰ»д№ЎеҺ»еҹҺйҮҢеҠЎе·Ҙзҡ„иҮӘз”ұпјҢжӣҙжҝҖеҸ‘дәҶеҶңж°‘з§Қз”°зҡ„з§ҜжһҒжҖ§гҖӮиҖҢд»ҠпјҢеңЁеҗҢж ·зҡ„еңҹең°е®¶еәӯжүҝеҢ…еҲ¶еәҰдёӢпјҢеҶңж°‘з§Қз”°з§ҜжһҒжҖ§йҷҚеҲ°дәҶдёӯеӣҪжңүеҸІд»ҘжқҘзҡ„жңҖдҪҺзӮ№гҖӮе»ә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жҳҜдёәдәҶ规模з»ҸжөҺпјҢдҪҶ规模з»ҸжөҺеҚҙеёҰжқҘеӨ§зҒҫйҡҫпјҢжүҖд»ҘйҖҖеҲ°дәҶвҖңйҳҹдёәеҹәзЎҖвҖқпјҲвҖңз”ҹдә§йҳҹвҖқпјҢеҚід»ҠеӨ©иҮӘ然жқ‘зҡ„вҖңжқ‘з»„вҖқпјҢиө·еҲқе№іеқҮд»…24жҲ·пјүпјҢеӣӣеҚҒе№ҙеүҚеҸҲеӣһеҪ’еҲ°е®¶еәӯиҖ•дҪңпјҢиІҢдјјвҖңдёҖеӨңеӣһеҲ°и§Јж”ҫеүҚвҖқгҖӮе°Ҹ规模зҡ„家еәӯиҖ•дҪңиҖҢд»Ҡиө°еҲ°дәҶе°ҪеӨҙпјҢжүҖд»ҘйҮҚжҸҗ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гҖҒ规模иҖ•дҪңгҖӮиҖҢд»Ҡзҡ„规模иҖ•дҪңеҪ“然дёҚеҗҢдәҺ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е®ҢжҲҗдәҶе…Ёйқўе·ҘдёҡеҢ–еҹәзЎҖдёҠзҡ„规模иҖ•дҪңгҖӮжңәжў°гҖҒеҢ–иӮҘгҖҒеҶңиҚҜгҖҒз§ҚеӯҗгҖҒзҒҢжәүпјҢзҺ°д»Јзҡ„еҶңиҖ•жүӢж®өж—©е·Ід»Ҡйқһжҳ”жҜ”гҖӮ
иҖ•ең°йӣҶдёӯжңүдёүз§ҚеҸ°йқўдёҠзҡ„ж–№жЎҲгҖӮ第дёҖпјҢиҖ•ең°з§ҒжңүеҢ–гҖӮдҪҶйқ з§ҒжңүеҢ–йӣҶдёӯеңҹең°пјҢи®©еҹҺйҮҢиҝҮеү©зҡ„иө„жң¬дёӢ乡并иҙӯдёӘдҪ“еҶңж°‘зҡ„жүҝеҢ…ең°пјҢ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зҡ„йҖҹеәҰжҳҫ然дјҡеҫҲж…ўпјҢеӨҡж•°жңүжүҝеҢ…ең°зҡ„еҶңж°‘жҲ–йқһеҶңж°‘дёҚдјҡеӮ»еҲ°е»үд»·ж”ҫејғеңҹең°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дәә们жңүзҗҶз”ұжҖҖз–‘иҖ•ең°з§ҒжңүеҢ–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йӣҶдёӯеңҹең°пјҢз”ҡиҮідёҺеҶңдёҡд№ҹж— е…іпјҢиҖҢжҳҜдёәдәҶи®©еҹҺйҮҢиө„жң¬еҺ»зӮ’дҪңеҶңең°пјҢи®©еҶңең°еҗёзәіеҹҺйҮҢйҖҡиҙ§иҶЁиғҖзҡ„еҺӢеҠӣгҖӮйӮЈдёҚд»…жһҒдёҚйҒ“еҫ·пјҢиҝқиғҢе·ҘеҶңиҒ”зӣҹд№ӢеӣҪжң¬пјҢиҝҳиҝқиғҢдәҶжҲ‘еӣҪвҖңиҖ•иҖ…жңүе…¶з”°вҖқзҡ„дәҳеҸӨйҒ“д№үгҖӮжҠҠеҶңз”°еҸҳжҲҗиө„жң¬зӮ’дҪңе·Ҙе…·жӣҙдјҡжҜҒзҒӯжҲ‘еӣҪеҶңдёҡгҖӮ第дәҢпјҢвҖңзЎ®жқғйўҒиҜҒвҖқгҖӮиҷҡеҢ–еңҹең°еҸ‘еҢ…ж–№вҖ”вҖ”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пјҢи®©жүҝеҢ…ең°жҲҗдёәе°ҸеҶңвҖңж°ёд№…иҙўдә§вҖқпјҢе°ҸеҶң们жҲ–и®ёдјҡжҠҠеңҹең°иҪ¬з§ҹз»ҷвҖңз§Қз”°еӨ§жҲ·вҖқгҖӮдҪҶиҝҷз§ҚйӣҶдёӯдёҚд»…зј“ж…ўпјҢиҖҢдё”еҫҲдёҚзЁіе®ҡвҖ”вҖ”жүҝеҢ…дәәеҸҜйҡҸж—¶иҰҒеӣһеңҹең°жҲ–жҸҗй«ҳең°з§ҹгҖӮеҶөдё”пјҢйҡҸзқҖеҶңжқ‘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иҝҳдјҡдә§з”ҹеӨ§йҮҸвҖңдёҚеңЁең°вҖқең°дё»пјҢдҫқж—§иҝқиғҢвҖңиҖ•иҖ…жңүе…¶з”°вҖқзҡ„еӨ©зҗҶгҖӮ第дёүпјҢж №жҚ®гҖҠе®Әжі•гҖӢе’ҢгҖҠеңҹең°з®ЎзҗҶжі•гҖӢпјҢйҮҚз”іиҖ•ең°еҪ’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жүҖжңүгҖӮиҝҷж ·пјҢ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жңүжқғж №жҚ®жң¬ең°жқЎд»¶дёҚж–ӯиҝӣиЎҢеўһдәәеўһең°е’ҢеҮҸдәәеҮҸең°зҡ„еҸ‘еҢ…и°ғж•ҙпјҢйҳ»жӯўеӨ§йҮҸдә§з”ҹвҖңдёҚеңЁең°вҖқең°дё»гҖӮзҫҺеӣҪеҶңеңәзҡ„е№іеқҮ规模зәҰдёүеҚғдә©гҖӮиӢҘжҢүиЎҢж”ҝжқ‘з®—пјҢжҲ‘еӣҪ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е№іеқҮжӢҘжңүдёүеҚғдә©д»ҘдёҠзҡ„规模пјҢ规模иҖ•дҪңеңЁжҲ‘еӣҪжң¬жқҘжҳҜзҺ°жҲҗзҡ„гҖҒжі•е®ҡзҡ„гҖӮз•ҷеңЁз”°ең°йҮҢиҖ•дҪңзҡ„и¶ҠжқҘи¶Ҡе°‘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ә”еҪ“жӢҘжңү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иҖ•ең°пјҢеғҸеҹҺйҮҢдәәдёҖж ·иҝҮи¶ҠжқҘи¶ҠеҜҢиЈ•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ҹзӯ”жЎҲжҳҜиӮҜе®ҡзҡ„гҖӮи®©зңҹжӯЈзҡ„еҶңж°‘зңҹжӯЈи„ұиҙ«дёҚеҸҜиғҪйқ ж…Ҳе–„гҖӮ既然改йқ©ж°ёиҝңеңЁи·ҜдёҠпјҢе…¶иҝӣеұ•е°ұйҡҫе…Қе‘Ҳиһәж—ӢзҠ¶гҖӮжӢ’з»қж”№йқ©е‘ҲзҺ°зҡ„иһәж—ӢзҠ¶пјҢдёҚд»Һе®һйҷ…еҮәеҸ‘пјҢд»ҺеёӮеңәеҢ–зӯүвҖңи§ӮеҝөвҖқеҮәеҸ‘пјҢж— ејӮдәҺжӢ’з»қж”№йқ©жң¬иә«гҖӮйӮЈеҸҲдҪ•жқҘвҖңж–°ж—¶д»ЈвҖқпјҹ
еңЁеҹҺд№ЎеҹәеұӮзӨҫеҢәдёҖеҲҖеҲҮең°жҗһвҖңж”ҝдјҒеҲҶејҖвҖқ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ж”№йқ©еӣӣеҚҒе№ҙйҮҢ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•ҷи®ӯгҖӮеҹҺеёӮзӨҫеҢәжҳҜйқһз»ҸжөҺзӨҫеҢәпјҢдҪҶеҶңжқ‘зӨҫеҢәдё»иҰҒжҳҜз»ҸжөҺзӨҫеҢәгҖӮжІЎжңүз»ҸжөҺе°ұжІЎжңүеҶңжқ‘зӨҫеҢәгҖӮжҲ‘们дёҚиғҪеҝҳи®°пјҢиҖ•ең°еұһдәҺеҶңжқ‘йӣҶдҪ“жҳҜжі•е®ҡзҡ„пјҢеҸҚеҜ№иҖ•ең°йӣҶдёӯеңЁе°‘ж•°дёӘдәәжүӢйҮҢжҳҜ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йўҶеҜјдәәж°‘йқ©е‘Ҫзҡ„жңҖеҹәжң¬зҡ„жӯЈеҪ“жҖ§жқҘжәҗгҖӮ
еӣӣгҖҒеҶңжқ‘ж”№йқ©жңҖеҝҢвҖңдёҖеҲҖеҲҮвҖқ
жҗһеҶңең°е®¶еәӯжүҝеҢ…дёҚжҳҜйЎ¶еұӮи®ҫи®Ў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д№Ўжқ‘дјҒдёҡзҡ„ејӮеҶӣвҖңзӘҒиө·вҖқ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пјҢ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й—®йўҳзҡ„еҝҪ然ж¶ҲеӨұжӣҙжҳҜдёӘж„ҸеӨ–гҖӮе…ЁеӣҪеҶңжқ‘вҖңзЎ®жқғйўҒиҜҒвҖқзҡ„йЎ¶еұӮи®ҫи®ЎиҰҒжұӮеҶңжқ‘еңҹең°жөҒиҪ¬йӣҶдёӯпјҢиҠұдәҶеҫҲеӨҡй’ұпјҢеҚҙеҹәжң¬ж— ж•Ҳ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пјҹеӣ дёәжҲ‘еӣҪеҶңжқ‘иҮӘ然жқЎд»¶е’ҢзӨҫеҢәжқЎд»¶еҚғе·®дёҮеҲ«гҖӮе”ҜдёҖиғҪзЎ®е®ҡзҡ„жҳҜпјҢдёҖдёӘеҮәиүІзҡ„жң¬ең°зӨҫеҢәйўҶеӨҙдәәиғҪеҲӣйҖ еҘҮиҝ№гҖӮ然иҖҢпјҢеҮәиүІзҡ„зӨҫеҢәйўҶеӨҙдәәеҗ‘жқҘеҸҜйҒҮдёҚеҸҜжұӮгҖӮ
дёҫдёӘжһҒз«ҜеҚҙеҪұе“ҚеҲ°е…ЁеӣҪзҡ„дҫӢеӯҗгҖӮж–°з–ҶеҚ—йғЁзҡ„з»ҝжҙІжңүжҲ‘еӣҪе”ҜдёҖеӯҳз•ҷзҡ„иҖҒејҸ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й—®йўҳпјҢиҖҢдё”дёҘйҮҚеҲ°вҖңзҲҶзӮёвҖқзҡ„зЁӢеәҰгҖӮйҡҸзқҖдёӯеӣҪеёӮеңәеҢ–ж”№йқ©зҡ„иҝӣеұ•вҖ”вҖ”е°Ҫз®ЎеҚ—з–Ҷзҡ„ж”№йқ©и„ҡжӯҘжҜ”еҶ…ең°ж…ўдәҶдёҚжӯўдёӨдёүжӢҚпјҢйӮЈйҮҢеҚғдёҮ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дәәзҡ„з”ҹжҙ»ж°ҙе№ійқһдҪҶжІЎдёҠеҚҮпјҢеҸҚиҖҢдёӢйҷҚгҖӮеңЁдёҖдёӘдёӘйҡ”зҰ»зҡ„е°Ҹз»ҝжҙІйҮҢпјҢ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дәәжҜ”жұүж—ҸдәәжӣҙзІҫиҖ•з»ҶдҪңгҖӮдҪҶйӮЈйҮҢеҶңдҪң规模йқһеёёе°ҸпјҢдёҺеёӮеңәи·қзҰ»йҒҘиҝңеҲ°еҹәжң¬дёҚеҸҜеҸҠпјҢеҶңиҖ•жҠҖжңҜзҡ„иҝӣжӯҘиў«дәәеҸЈеўһй•ҝеҗһеҷ¬ж®Ҷе°ҪгҖӮиҝҷз§ҚдәәеӨҡең°е°‘зҡ„з»Ҹе…ёвҖңдёүеҶңвҖқй—®йўҳз”ұдәҺ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еҶңж°‘зјәд№ҸйқһеҶңеҮәеҸЈиҖҢж—ҘжёҗдёҘйҮҚгҖӮеҺҹжң¬иғҪеҗёзәіе…¶е°ұдёҡзҡ„ж–°з–ҶеӣҪдјҒжІЎжңүдәҶпјҢеӣ дёәиҜӯиЁҖгҖҒе®—ж•ҷгҖҒд№ дҝ—пјҢдёҚзЁіе®ҡзҡ„з§ҒдјҒд№ҹеҮ д№ҺжІЎжі•жҺҘеҸ—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йӣҮе·ҘгҖӮдёҺеҶ…ең°е’ҢеҢ—з–ҶзӣёжҜ”иҫғпјҢзҫӨдҪ“иҙ«еӣ°жҲҗдёәеЎ‘йҖ еҚ—з–Ҷж—ҸиЈ”и®ӨеҗҢзҡ„жңҖеӨ§жҺЁжүӢгҖӮж–°еҪўжҲҗзҡ„ж—ҸиЈ”и®ӨеҗҢеҸҲжҲҗдёәеўғеӨ–еҗ„з§ҚеҠҝеҠӣзҡ„йҰҷйҘҪйҘҪпјҢжҲҗдёәжҡҙжҒҗдәӢ件зҡ„жё©еәҠгҖӮеҰӮжӯӨпјҢиҝһе°‘йҮҸжөҒе…ҘеҶ…ең°зҡ„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е°Ҹжң¬з”ҹж„Ҹдәәд№ғиҮіз–ҶеҶ…еҜ№жң¬ж—ҸиЈ”еүҚйҖ”еҝғжҖҘеҰӮз„ҡзҡ„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д№ҹйҡҫе…ҚжҲҗдёәжҖҖз–‘еҜ№иұЎгҖӮж— е·ҘдёҚеҜҢпјҢж•ҙдҪ“зҡ„иҙ«еӣ°жқҘиҮӘйқһдҪҶжІЎеҮҸе°‘еҸҚиҖҢеҝ«йҖҹеўһеҠ зҡ„еҚ—з–ҶеҠЎеҶңдәәеҸЈгҖӮиҝҷжҳҫ然дёҚжҳҜйқ йј“еҠұвҖңеәӯйҷўз»ҸжөҺвҖқжҲ–иҖ…вҖңжү¶иҙ«вҖқж…Ҳе–„иғҪи§ЈеҶізҡ„гҖӮеңЁеёӮеңәеҢ–йҮҢпјҢеҚ—з–Ҷ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дәәиў«ж•ҙдҪ“жҠӣеҮәдәҶпјӣж’’иғЎжӨ’йқўејҸзҡ„ж…Ҳе–„иҮіеӨҡиө·вҖңз»ҙжҢҒвҖқдҪңз”ЁгҖӮ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еёӮеңәеҢ–дёҚжҳҜи§ЈеҶіеҚ—з–Ҷй—®йўҳзҡ„жүӢж®өпјҢиҖҢжҳҜеҚ—з–Ҷй—®йўҳжҢҒз»ӯжҒ¶еҢ–зҡ„еҺҹеӣ гҖӮжҖҺж ·жүҚиғҪи®©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дәәзҰ»еңҹзҰ»д№ЎпјҢжҲҗдёәеҹҺеёӮдәәпјҢиҝӣиҖҢжӢҘжңүеҮәиүІзҡ„еӨ§еӯҰз”ҹгҖҒеҢ»з”ҹгҖҒе·ҘзЁӢеёҲгҖҒж•ҷеёҲгҖҒиҝҗеҠЁе‘ҳгҖҒиүәжңҜ家пјҹеҸ‘жү¬жҲ‘еӣҪ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еҲ¶еәҰйӣҶдёӯеҠӣйҮҸеҠһеӨ§дәӢзҡ„дјҳеҠҝпјҢеңЁеҚ—з–Ҷж–°е»әдёӨеә§зҺ°д»ЈеҢ–еӨ§еҹҺеёӮпјҢе ӘжҜ”иҝӘжӢңгҖҒйҳҝеёғжүҺжҜ”з”ҡиҮідјҠж–ҜеқҰеёғе°”пјҢеҗёзәідёҖеҚҠз»ҝжҙІеҶңж°‘пјҢз»ҙеҗҫе°”ж—Ҹдәәе°ұдјҡж„ҹеҸ—еҲ°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зҡ„ж— жҜ”ејәеӨ§пјҢ并д»ҘиҝҷдёӘеӨ§е®¶еәӯзҡ„дёҖе‘ҳиҖҢиҮӘиұӘгҖӮ
еҪ“е®Ӣдәҡе№іеёҰжҲ‘们周游湖еҢ—д№ЎдёӢж—¶пјҢжҲ‘жғҠ讶ең°еҸ‘зҺ°пјҢз§Ұе§ӢзҡҮз»ҹдёҖеәҰйҮҸиЎЎйғҪдёӨеҚғеӨҡе№ҙдәҶпјҢиҖҢж№–еҢ—зҡ„вҖңеұұең°дә©гҖҒд№ жғҜдә©вҖқиҝҳжҳҜжҜ”вҖңж ҮеҮҶдә©вҖқеӨ§дёҖеҚҠ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дёҖ家дёҖжҲ·зҡ„вҖңе®…еҹәең°вҖқеұ…然еҚ ең°иҝ‘еҚҒдә©пјҢжӢҘжңүиҮӘ家зҡ„йЈҺж°ҙжһ—е’Ңжұ еЎҳгҖӮеҸҜйӮЈйҮҢзҡ„еҶңж°‘еҚҙдҫқ然иҙ«з©·гҖӮиҖҢеңЁж·®жІід»ҘеҢ—пјҢжҲ‘еҸҲи§ҒеҲ°иҝҮеҚ«жҳҹе®ҡдҪҚзҡ„иҒ”еҗҲ收еүІжңәдёҖеӯ—жҺ’ејҖпјҢеғҸиқ—иҷ«йӮЈж ·йҡҸдҪңзү©жҲҗзҶҹжёҗж¬Ўеҗ‘еҢ—жҺЁиҝӣпјҢзӣҙжҠөеұұжө·е…іеҲ°еӨ©еұұд»ҘеҢ—зҡ„дёҖзәҝпјҢд»ӨдәәеҸ№дёәи§Ӯжӯў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е°ұеңЁжқҺжҳҢе№ізҡ„зӣ‘еҲ©еҺҝеҶ…пјҢвҖңеҚҒйҮҢдёҚеҗҢйҹівҖқгҖҒиҜӯиЁҖдёҚйҖҡпјҢд№ҹжҳҜеёёи§ҒпјҢйҒ‘и®әеңЁе…¶дёҚиҝңзҡ„еӨ§еҲ«еұұи„ҡдёӢвҖңзӣӣдә§вҖқйҖ еҸҚзҡ„е°ҶеҶӣгҖӮ
дҪ•дёәвҖңеӨ§дёҖз»ҹвҖқпјҹеӣ дёәжүҝи®Өе·®еҲ«пјҢе®Ҫе®№е·®ејӮпјҢжҲ‘еӣҪе°ұе№ҝжңүвҖңдә”ж№–еӣӣжө·вҖқгҖӮж ёеҝғдёҚжҳҜвҖңдёҖз»ҹвҖқпјҢиҖҢеңЁвҖңеӨ§вҖқгҖӮжңүе®№д№ғеӨ§пјҢе°ұжңүдәҶеӨ§дёҖз»ҹгҖӮеҚғе·®дёҮеҲ«зҡ„жҲ‘еӣҪеҶңжқ‘е°ұжҳҜвҖңеӨ§вҖқ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ејәжұӮдёҖиҮҙпјҢејәжұӮеӣҪжі•д№ӢжІ»пјҢдёҚзҗҶи§ЈдёәдҪ•дёӨеҚғеӨҡе№ҙжқҘиҰҒе®һиЎҢвҖңжқ‘ж°‘иҮӘжІ»вҖқпјҢеӨ§дёӯеҚҺе°ұдјҡеҸҳжҲҗе°ҸдёӯеҚҺпјҢеӨ§дёҖз»ҹе°ұдјҡеҸҳжҲҗе°ҸдёҖз»ҹгҖӮ
жҲ‘们зҷҫ姓зҡ„дәәз”ҹдёҚиҝҮеӣӣеӨ§йҳ¶ж®өпјҡиў«е…»гҖҒе…»е°ҸгҖҒйҖҒиҖҒгҖҒиў«йҖҒгҖӮвҖңдәәж°‘ж—ҘзӣҠеўһй•ҝзҡ„зҫҺеҘҪз”ҹжҙ»йңҖиҰҒвҖқе°ұеӣҙз»•иҝҷеӣӣеӨ§еҶ…е®№еұ•ејҖпјҢж— йқһж•ҷиӮІгҖҒеҢ»з–—гҖҒе…»иҖҒгҖӮеҪ“жҲ‘们йҖҗжёҗиҝӣе…ҘдәҶвҖңиў«йҖҒвҖқйҳ¶ж®өпјҢе°ұи¶ҠжқҘи¶ҠзҗҶи§ЈвҖңеҢ…е®№вҖқдәҶгҖӮиӢҘеҪ“е№ҙеҮӯдёҖиӮЎеӯҗд№Ұз”ҹж„Ҹж°”пјҢдёҚеҺ»е®һең°и°ғз ”пјҢеҮӯдёүеҜёдёҚзғӮд№ӢиҲҢеңЁдјҡдёҠз—ӣж–ҘдёҖйЎҝе®Ӣж°ҸвҖңе’ёе®үж–°ж”ҝвҖқпјҢд№ҹжҳҜеҸҜиғҪзҡ„пјҢеҚҙдёҚдјҡжңүжҲ‘дҝ©д»Ҡж—Ҙзҡ„е…„ејҹд№Ӣи°ҠгҖӮдёҮеҸӨй«ҳеұұпјҢеҚғз§ӢжөҒж°ҙпјҢзҹҘйҹізјҳиө·дёҚзҒӯгҖӮж„ҝиҝҷж®өд»ЈеәҸеҜ№еҗҺеӯҰжңүзӣҠпјҢд№ҹз»ӯеҶҷжҲ‘们зҡ„зӣёзҹҘгҖӮ
|  йғӯзЈҠпјҡеҰӮдҪ•зҗҶи§ЈдёҖеӯЈеәҰ
йғӯзЈҠпјҡеҰӮдҪ•зҗҶи§ЈдёҖеӯЈеәҰ дјҚжҲҲпјҡз»ҸжөҺпјҢд»Һе№је„ҝеӣӯ
дјҚжҲҲпјҡз»ҸжөҺпјҢд»Һе№је„ҝеӣ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з»ҸжөҺвҖңжё©е·®вҖқ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з»ҸжөҺвҖңжё©е·®вҖқ е‘Ёжө©пјҡзҫҺеҖәеҲ©зҺҮдёҠиЎҢпјҡ
е‘Ёжө©пјҡзҫҺеҖәеҲ©зҺҮдёҠиЎҢпјҡ 第е…ӯе·Ўи§Ҷз»„еӣҪ家粮йЈҹе’Ң
第е…ӯе·Ўи§Ҷз»„еӣҪ家粮йЈҹе’Ң зЁӢе®һпјҡд»Һи¶…йўқ收зӣҠзҡ„и§Ҷ
зЁӢе®һпјҡд»Һи¶…йўқ收зӣҠзҡ„и§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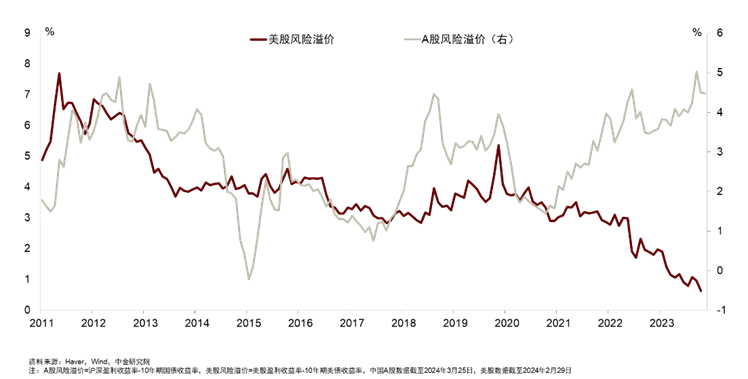 еҪӯж–Үз”ҹпјҡд»ҺйҮ‘иһҚе‘ЁжңҹзңӢ
еҪӯж–Үз”ҹпјҡд»ҺйҮ‘иһҚе‘ЁжңҹзңӢ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йҮ‘иһҚж•°жҚ®еҮҸйҖҹ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йҮ‘иһҚж•°жҚ®еҮҸйҖҹ еӨ§е®—е•Ҷе“ҒиЎҢжғ…зҒ«зҲҶпјҢеҸІ
еӨ§е®—е•Ҷе“ҒиЎҢжғ…зҒ«зҲҶпјҢеҸІ еј жҳҺгҖҒзҺӢе–ҶпјҡзЁіж…ҺжүҺе®һ
еј жҳҺгҖҒзҺӢе–ҶпјҡзЁіж…ҺжүҺе®һ иҙўзЁҺдҪ“еҲ¶дёҺй«ҳиҙЁйҮҸеҸ‘еұ•
иҙўзЁҺдҪ“еҲ¶дёҺй«ҳиҙЁйҮҸеҸ‘еұ•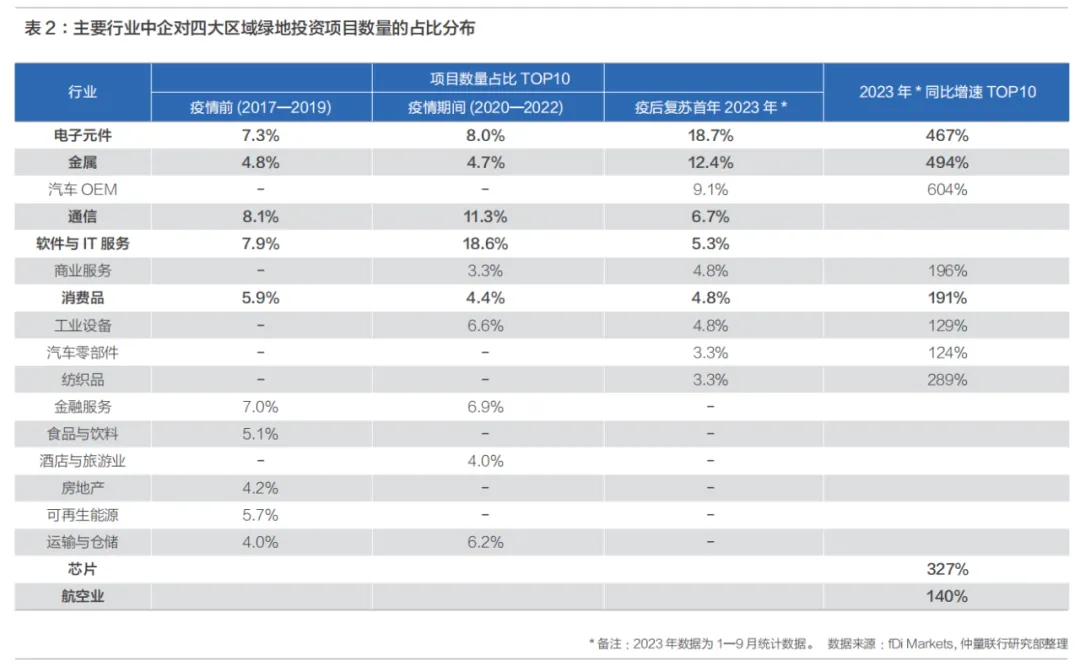 еәһжәҹпјҡеҚҒе№ҙеҫҒзЁӢвҖ”вҖ”жө…
еәһжәҹпјҡеҚҒе№ҙеҫҒзЁӢвҖ”вҖ”жө…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