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и®ёеҶ¬йҳіпјҢеҘіпјҢеұұдёңеӨ§еӯҰж–ҮеӯҰйҷўеҚҡеЈ«з”ҹгҖӮжқҺжЎӮеҘҺпјҢз”·пјҢ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ӣҪйҷ…ж–ҮеҢ–дәӨжөҒ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гҖҒеҚҡеЈ«з”ҹеҜјеёҲгҖӮ
еҸӨд»Је°ҸиҜҙзҡ„ж–ҮдҪ“ең°дҪҚжҖ»дҪ“дёҠжҜ”иҫғдҪҺпјҢеҫҖеҫҖиў«еҶ д»ҘвҖңе°ҸйҒ“вҖқвҖңй„ҷиҜҙвҖқзӯүз§°и°“пјҢе…¶жө…зҷҪгҖҒдҝҡдҝ—гҖҒиҷҡе№»зӯүзү№зӮ№д№ҹж—¶еёёеҸ—дәәиҜҹз—…гҖӮдҪңдёәеҸӨд»Је°ҸиҜҙжү№иҜ„зҡ„дё»иҰҒеҪўејҸд№ӢдёҖпјҢеәҸи·ӢжҳҜеҺҶд»Је°ҸиҜҙ家е’Ңе°ҸиҜҙжү№иҜ„家表иҫҫи§ӮзӮ№гҖҒе»әжһ„зҗҶи®әзҡ„йҮҚиҰҒиҪҪдҪ“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–ңзҲұе°ҸиҜҙзҡ„ж–ҮдәәеҫҖеҫҖеҖҹеҠ©еәҸи·ӢжқҘж ҮжҰңе°ҸиҜҙзҡ„д»·еҖје’ҢеҠҹз”ЁгҖӮеүҚиҙӨж—¶еҪҰиҷҪе·ІжіЁж„ҸеҲ°дәҶеәҸи·Ӣзҡ„иҝҷдёҖеҠҹиғҪ并еҠ д»ҘжҺўи®ЁпјҢдҪҶе…¶и®әиҝ°еҫҖеҫҖд»…е°ұжҹҗдёҖи§Ҷи§’е…ҘжүӢпјҢйІңжңүеҜ№е…¶дҪңеҮәе…ЁйқўгҖҒзі»з»ҹжўізҗҶиҖ…гҖӮе®һйҷ…дёҠпјҢеәҸи·ӢеҜ№е°ҸиҜҙзҡ„д»·еҖјиҫ©жҠӨе’Ңең°дҪҚж ҮжҰңеҫҖеҫҖжҳҜйҖҡиҝҮвҖңдҫқз»ҸеӮҚеҸІвҖқзҡ„ж–№ејҸжқҘе®һзҺ°зҡ„гҖӮ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йҖҡиҝҮеҜ№з»ҸеҸІзҡ„ж”Җйҷ„гҖҒ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еҶ…йғЁзҡ„иҜ„иөҸд»ҘеҸҠеҜ№дҪңиҖ…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зҡ„жҢ–жҺҳзӯүеӨҡз§Қжё йҒ“пјҢжқҘе……еҲҶеҪ°жҳҫе°ҸиҜҙзҡ„д»·еҖјгҖҒжҸҗеҚҮе°ҸиҜҙ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е…¶и®әиҝ°дёӯжүҖдҪ“зҺ°еҮәзҡ„и§ӮеҝөдёҺзҗҶи®әеҜҢжңүеұӮж¬Ўдё”жһҒе…·еј еҠӣгҖӮеҗ„зұ»еәҸи·ӢеҜ№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иҝӣиЎҢи®Ёи®әпјҢзӣ®зҡ„еңЁдәҺжҸҗй«ҳиҮӘиә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еңЁ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дёӯ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иҝӣиҖҢ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еңЁж•ҙдёӘж–ҮеӯҰйўҶеҹҹ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жңҖз»Ҳд»Өе°ҸиҜҙж‘Ҷи„ұе°ҸйҒ“жң«жөҒзҡ„зӘҳеўғпјҢеҫ—еҲ°жӯЈзЎ®зҡ„иҜ„дј°е’Ңеә”жңүзҡ„йҮҚи§ҶгҖӮдёҖгҖҒд»Ҙз»ҸеҸІдёәй•ңеғҸиҜ„иҜҙ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д»·еҖј з»ҸеҸІеңЁеҸӨд»Је…ёзұҚеҸҠж–ҮеҢ–иҜӯеўғдёӯжңүзқҖиҮій«ҳж— дёҠзҡ„жӯЈз»ҹең°дҪҚпјҢиҖҢе°ҸиҜҙзҙ жқҘжңүвҖңдёҚз»ҸвҖқвҖңйҮҺеҸІвҖқд№Ӣз§°пјҢе…¶жңүжӮ–дәҺз»ҸеҸІзҡ„жө…дҝ—дёҺиҚ’иҜһжҲҗдёәеҺҶд»ЈйҒ“еӯҰ家жү№еҲӨ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зҡ„йҮҚиҰҒи®әжҚ®гҖӮдёәдәҶж”№еҸҳиҝҷдёҖеұҖйқўпјҢеӨ§йҮҸ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д»Ҙз»ҸеҸІдёәй•ңеғҸеҜ№е°ҸиҜҙиҝӣиЎҢд»·еҖјиҜ„дј°гҖӮ他们дҫқйҷ„з»ҸеҸІеұ•ејҖи®әиҜҒпјҢеҜ№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зӣёе…ізү№жҖ§иҝӣиЎҢжҜ”иҫғпјҢжҢҮеҮә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зӣёйҖҡд№ӢеӨ„пјҢ并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зӣёжҜ”з»ҸеҸІзҡ„дјҳеҠҝжүҖеңЁгҖӮиҝҷз§ҚеҒҡжі•зҡ„дё»иҰҒж„ҸеӣҫеңЁдәҺеҖҹеҠ©з»ҸеҸІзҡ„жқғеЁҒжҖ§дёҺжӯЈз»ҹжҖ§жқҘ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д»Өе°ҸиҜҙж‘Ҷи„ұвҖңдёҚз»ҸвҖқвҖңйҮҺеҸІвҖқд№ӢеҗҚзҡ„жЎҺжўҸгҖӮпјҲдёҖпјүеңЁ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зұ»жҜ”дёӯиҜҒжҳҺе°ҸиҜҙзҡ„еҗҲзҗҶжҖ§дёҺжӯЈз»ҹжҖ§дёҖдәӣ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дјҡ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з«Ӣж„Ҹз¬ҰеҗҲз»ҸеӯҰиҰҒд№үпјҢеҰӮжңұеә·еҜҝгҖҠжөҮж„ҒйӣҶеҸҷгҖӢдә‘вҖңиҰҒзҡҶеҸ–д№үе…ӯз»ҸпјҢеҸ‘жәҗзҫӨзұҚвҖқпјҢеҫҗжүҝжҒ©гҖҠиҖійЈҹеҪ•еәҸгҖӢдә‘вҖңиҖғдҝЎеҝ…жң¬дәҺе…ӯз»ҸвҖқгҖӮеҸҰжңүеӨ§йҮҸи®ІеҸІзұ»е°ҸиҜҙ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ж ҮжҰңиҮӘиә«йҒөеҫӘжӯЈеҸІпјҢеҰӮзҪ—зғЁгҖҠйҶүзҝҒи°ҲеҪ•иҲҢиҖ•В·еҸҷеј•гҖӢз§°вҖңеҫ—е…¶е…ҙеәҹпјҢи°ЁжҢүеҸІд№ҰвҖқпјҢгҖҠйҡӢзӮҖеёқиүіеҸІВ·еҮЎдҫӢгҖӢз§°е…¶вҖңеј•з”Ёж•…е®һпјҢжӮүйҒөжӯЈеҸІпјҢ并дёҚе·§еҖҹдёҖдәӢпјҢеҰ„и®ҫдёҖиҜӯпјҢд»Ҙж»Ӣдё–дәәд№Ӣжғ‘вҖқгҖӮиҖҢеңЁжӣҙеӨҡ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әҸи·Ӣеёёе°Ҷ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йўҳжқҗе’Ңз«Ӣж„ҸиҝӣиЎҢзұ»жҜ”пјҢд»ҘжңҹиҜҒжҳҺе…¶дё»ж—Ёз¬ҰеҗҲз»ҸеҸІгҖӮе…¶еҒҡжі•дё»иҰҒжңүдёӨз§ҚпјҡдёҖжҳҜж”ҖжҜ”з»ҸеҸІпјҢе°Ҷ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зҲұжғ…дёҺжҖӘеҘҮзӯүйўҳжқҗеҗҲзҗҶеҢ–пјӣдәҢжҳҜдҫқйҷ„з»ҸеҸІпјҢ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еҠқжғ©йўҳжқҗзҡ„жӯЈз»ҹжҖ§е’ҢжҖқжғіж·ұеәҰгҖӮ1.ж”ҖжҜ”з»ҸеҸІе°ҸиҜҙйўҳжқҗзҡ„иҜІж·«гҖҒжө…дҝ—гҖҒиҷҡеҰ„е’ҢиҚ’иҜһеҺҶжқҘдёәдәәиҜҹз—…пјҢжҳҜеҜјиҮҙе°ҸиҜҙеұ…дәҺвҖңе°ҸйҒ“вҖқвҖңй„ҷиҜҙвҖқвҖңжң«еӯҰвҖқең°дҪҚзҡ„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еҠӣиҜҒз»ҸеҸІдёӯд№ҹжңүзұ»дјјйўҳжқҗпјҢд»ҺиҖҢдёәзӣёе…іе°ҸиҜҙдёӯжӯӨзұ»йўҳжқҗзҡ„иҝҗз”ЁжҸҗдҫӣзҗҶз”ұгҖӮиғӯзІүзұ»е°ҸиҜҙеёёд»Ҙ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дёӯеҶҷжғ…зҲұзҡ„гҖҠе…ійӣҺгҖӢдёҺеҶҷж·«еҘ”зҡ„гҖҠиқғгҖӢзӯүзҜҮзӣ®дёәдҫӢпјҢжҲ–еҲ—дёҫе…¶д»–з»Ҹдј е…ёзұҚдёӯдёҺеӨ«еҰҮгҖҒдәәдјҰгҖҒеӨ©жҖ§зӣёе…ізҡ„и®әиҝ°пјҢжқҘиҜҒжҳҺзҲұжғ…йўҳжқҗеӯҳеңЁзҡ„еҗҲзҗҶжҖ§дёҺеҝ…иҰҒжҖ§гҖӮеүҚиҖ…пјҢеҰӮж¬Јж¬ЈеӯҗгҖҠйҮ‘瓶梅иҜҚиҜқеәҸгҖӢз”ЁгҖҠе…ійӣҺгҖӢжқҘеӣһеә”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дҝҡдҝ—и„ӮзІүзҡ„дәүи®®пјҢз»ҙйЈҺиҖҒдәәгҖҠеҘҪйҖ‘дј еҸҷгҖӢз§°иҜҘзҜҮеҸҜдёҺгҖҠе…ійӣҺгҖӢеҗҢиҜ»пјҢжҶЁжҶЁеӯҗгҖҠз»ЈжҰ»йҮҺеҸІеәҸгҖӢжҸҗеҲ°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дёӯеҗҢж ·дҝқз•ҷдәҶжҸҸеҶҷ鹑еҘ”гҖҒй№ҠеҪҠгҖҒйғ‘йЈҺгҖҒж Әжһ—зӯүеҶ…е®№зҡ„зҜҮз« пјӣеҗҺиҖ…пјҢеҰӮж°ҙ箬散дәәгҖҠй©»жҳҘеӣӯе°ҸеҸІеәҸгҖӢз”ЁгҖҠеӨ§еӯҰгҖӢдёҺгҖҠжҳ“з»ҸгҖӢжқҘиҜҒжҳҺжҖ§дёҺжғ…д№ғеұһдәәдјҰпјҢиҢӮиӢ‘жғңз§Ӣз”ҹгҖҠжө·еӨ©йёҝйӣӘи®°еәҸгҖӢеј•з”ЁгҖҠжҳ“гҖӢдёӯзҡ„йҘ®йЈҹз”·еҘіеҸҠ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ӯвҖңйЈҹиүІжҖ§д№ҹвҖқзҡ„дҫӢиҜҒжқҘиҜҒжҳҺз»ҸзұҚдёӯд№ҹжңүвҖңиүІвҖқ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ҒеҘҪиүІзҡ„жңӘеҝ…дёҚжҳҜеҗӣеӯҗгҖӮжңҖе…ёеһӢзҡ„еҪ“еұһгҖҠжғ…еҸІеҸҷгҖӢпјҢйҖҡиҝҮвҖңгҖҠжҳ“гҖӢе°ҠеӨ«еҰҮпјҢгҖҠиҜ—гҖӢжңүгҖҠе…ійӣҺгҖӢпјҢгҖҠд№ҰгҖӢеәҸе«”иҷһд№Ӣж–ҮпјҢгҖҠзӨјгҖӢи°ЁиҒҳеҘ”д№ӢеҲ«пјҢ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дәҺ姬е§ңд№Ӣйҷ…иҜҰ然иЁҖд№ӢвҖқиҖҢеҫ—еҮәвҖңе…ӯз»ҸзҡҶд»Ҙжғ…ж•ҷвҖқзҡ„з»“и®әпјҢзӣҙжҺҘе°Ҷжғ…дёҠеҚҮеҲ°дёҺзӨјд№җ并й©ҫйҪҗй©ұзҡ„вҖңж•ҷвҖқзҡ„й«ҳеәҰгҖӮдёҺд№Ӣзұ»дјјпјҢжңүжҖӘеҘҮйўҳжқҗзҡ„е°ҸиҜҙд№ҹдјҡз”ЁеҗҢж ·зҡ„ж–№жі•жқҘдёәиҮӘиә«зҡ„вҖңжҖӘвҖқвҖңеҘҮвҖқеӣ зҙ еҜ»жүҫзҗҶи®әж №жҚ®гҖӮеҰӮйҷҶеҜҝеҗҚгҖҠз»ӯеӨӘе№іе№ҝи®°еәҸгҖӢз”Ёеӯ”еӯҗвҖңеҲ гҖҠиҜ—гҖӢгҖҠд№ҰгҖӢиҖҢдёҚеәҹйёҹе…ҪиҚүжңЁд№ӢејӮпјҢдҝ®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иҖҢжӮүдј зҒҫзҘҘеҸҳејӮд№Ӣз«ҜвҖқжқҘиҜҒжҳҺеңЈдәә并дёҚйҒҝеҝҢжҖӘејӮд№ӢдәӢпјҢиҜһеҰ„д№ӢиҜҙ并йқһдёҚз»ҸгҖӮеҸҲеҰӮеҚўиҒ”зҸ гҖҠ第дёҖеҝ«жҙ»еҘҮд№ҰеәҸгҖӢз”ЁвҖңгҖҠжҳ“гҖӢеӨҮе…ӯз»Ҹд№ӢдҪ“пјҢиҖҢйҹ©жҳҢй»Һд»ҘвҖҳеҘҮвҖҷжӢ¬д№ӢвҖқжқҘиҜҒжҳҺз»Ҹд»ҘеҘҮдёәзү№еҫҒгҖҒд№Ұд№ӢжүҖиҙөиҖ…еҘҮгҖӮзһҝдҪ‘еңЁгҖҠеүӘзҒҜж–°иҜқеәҸгҖӢдёӯжҸҗеҲ°пјҢиҮӘе·ұз”ЁвҖңгҖҠжҳ“гҖӢиЁҖйҫҷжҲҳдәҺйҮҺпјҢгҖҠд№ҰгҖӢиҪҪйӣүйӣҠдәҺйјҺпјҢгҖҠеӣҪйЈҺгҖӢеҸ–ж·«еҘ”д№ӢиҜ—пјҢ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зәӘд№ұиҙјд№ӢдәӢвҖқжқҘи§ЈйҮҠгҖҠеүӘзҒҜж–°иҜқгҖӢзҡ„вҖңж¶үдәҺиҜӯжҖӘпјҢиҝ‘дәҺиҜІж·«вҖқпјҢиҝҷж ·ж—ўжҳҜдёәдәҶвҖңиҮӘи§ЈвҖқ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еҫ—еҲ°дәҶвҖңе®ўвҖқзҡ„и®ӨеҸҜ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әҸи·Ӣдёӯзҡ„иҝҷдёҖзұ»и®әиҝ°пјҢж—ўеҸҜд»Ҙдҝғиҝӣе°ҸиҜҙдёӯзҲұжғ…дёҺжҖӘеҘҮйўҳжқҗзҡ„еҗҲзҗҶеҢ–пјҢеҸҲеҸҜд»Ҙеӣһеә”иҙЁз–‘иҖ…пјҢд»Ҙз»ҸеҸІдёәзӣҫдҝқжҠӨе…¶жүҖиҜ„и®әзҡ„е°ҸиҜҙдёҚеҸ—йўҳжқҗж–№йқўзҡ„жү№еҲӨгҖӮ2.дҫқйҷ„з»ҸеҸІеҠқе–„жғ©жҒ¶дёҺиЈЁзӣҠйЈҺж•ҷзҡ„жҰӮеҝөиҮӘз»ҸеҸІиҖҢе§ӢпјҢеүҚиҖ…жәҗиҮӘгҖҠе·Ұдј гҖӢдёӯвҖң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д№Ӣз§°пјҡеҫ®иҖҢжҳҫпјҢеҝ—иҖҢжҷҰпјҢе©үиҖҢжҲҗз« пјҢе°ҪиҖҢдёҚжұҷпјҢжғ©жҒ¶иҖҢеҠқе–„вҖқд№Ӣи®әпјҢеҗҺиҖ…еҲҷжәҗиҮӘгҖҠжҜӣиҜ—еәҸгҖӢдёӯвҖңйЈҺд»ҘеҠЁд№ӢпјҢж•ҷд»ҘеҢ–д№ӢвҖқвҖңз»ҸеӨ«еҰҮпјҢжҲҗеӯқ敬пјҢеҺҡдәәдјҰпјҢзҫҺж•ҷеҢ–пјҢ移йЈҺдҝ—вҖқд№Ӣи®әгҖӮ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жҷ®йҒҚе…¬и®ӨпјҢеҠқжғ©жһңжҠҘзҗҶеҝөеңЁз»ҸеҸІе°Өе…¶жҳҜеҸІд№ҰдёӯжңүзқҖе……еҲҶзҡ„дҪ“зҺ°гҖӮиөөејјгҖҠж•ҲйўҰйӣҶеҗҺеәҸгҖӢеҚіиЁҖ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дёҺ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жңүвҖңжҲ’вҖқвҖңиӯҰвҖқдҪңз”ЁпјҢи®ёе®қе–„гҖҠеҢ—еҸІжј”д№үеәҸгҖӢдәҰиЁҖвҖңеҺҶжңқдәҢеҚҒдәҢеҸІжҳҜдёҖйғЁеӨ§жһңжҠҘд№Ұ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дёҚйҒ—дҪҷеҠӣең°ж ҮжҰң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еҠқжғ©д№Ӣж—ЁпјҢ并称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зҡ„еҠқжғ©зҗҶеҝөеҫ—еҲ°дәҶз»ҸеҸІе°Өе…¶жҳҜеҸІд№Ұзҡ„зІҫй«“гҖӮеҰӮй’ұжЈЁгҖҠи°җй“ҺеәҸгҖӢз§°е…¶вҖңеҫ—еҸІж°ҸеҠқжғ©д№Ӣж—ЁвҖқпјҢж•…иҖҢдёҚеҸҜдёҺжқӮд№ҰеҗҢеҲ—пјӣйҮҮйҰҷеұ…еЈ«гҖҠз»ӯеҪӯе…¬жЎҲеҸҷгҖӢз§°вҖңжӯЈеҸІд№ӢдёҺдј еҘҮпјҢиҷҪжңүйӣ…дҝ—д№ӢеҲ«пјҢиҖҢе…¶ж„ҹдәәеҝғд»ҘжҲҗйЈҺеҢ–еҲҷдёҖд№ҹвҖқгҖӮз”ұжӯӨеҮәеҸ‘пјҢ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иҝӣдёҖжӯҘејәи°ғпјҢдёҺз»ҸеҸІдёҖж ·еҠқе–„жғ©жҒ¶гҖҒжңүиЎҘйЈҺеҢ–зҡ„е°ҸиҜҙз”ҡиҮіеҸҜд»ҘдёҺз»ҸеҸІзӣёжҸҗ并и®әгҖӮеҰӮжҙӘжЈЈе…ғгҖҠй•ңиҠұзјҳеҺҹеәҸгҖӢз§°е…¶вҖңжӯЈдәәеҝғпјҢз«ҜйЈҺеҢ–вҖқпјҢеҸҜвҖңд»Ҙз»Ҹд№үиҜ»д№ӢвҖқпјҢдёҚеҸҜвҖңд»Ҙ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иҖҢеҝҪд№ӢвҖқпјӣжөӘиҝ№з”ҹгҖҠйёійёҜжўҰеҸҷгҖӢз§°е…¶вҖңйҡҗжңүдәәжғ…дё–йЈҺеңЁвҖқпјҢж•…иҖҢвҖңи°“дёәйҪҗд№ӢеҚ—еҢ—еҸІеҸҜпјӣи°“дёәжҷӢд№Ӣд№ҳжҘҡд№ӢжўјжқҢпјҢдәҰж— дёҚеҸҜвҖқгҖӮе°ҸиҜҙеҜ№з»ҸеҸІеҠқжғ©еҠҹиғҪзҡ„延з»ӯвҖңжҳҜе°ҸиҜҙжү№иҜ„家们鼓еҗ№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зҡ„еә•ж°”вҖқпјҢеәҸи·ӢеҜ№е°ҸиҜҙеҠқжғ©зҗҶеҝөзҡ„ејәи°ғпјҢжӯЈжҳҜеҖҹеҠ©дәҶз»ҸеҸІзҡ„жӯЈз»ҹжҖ§е’ҢеҙҮй«ҳең°дҪҚпјҢд»ҺиҖҢд»Өе°ҸиҜҙеңЁиҝҷдёҖеұӮйқўдёҠиҺ·еҫ—з»ҸеҸІзҡ„йҷ„еұһд»·еҖјпјҢд№ғиҮіж‘Ҷи„ұвҖңдёҚжӯЈз»ҸвҖқдёҺвҖңйҮҺеҸІвҖқзӯүжү№еҲӨд№ӢиҜӯгҖӮпјҲдәҢпјүеңЁ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еҸҚеҗ‘еҜ№жҜ”дёӯеҮёжҳҫе°ҸиҜҙзҡ„дјҳеҠҝеңЁ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зҡ„йўҳжқҗеҸҠдё»ж—ЁдёҺз»ҸеҸІзӣёйҖҡд№ӢдҪҷпјҢжӣҙеӨҡ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еҲҷзғӯиЎ·дәҺе°Ҷ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иҝӣиЎҢеҸҚеҗ‘еҜ№жҜ”пјҢзӘҒжҳҫз»ҸеҸІзҡ„зјәйҷ·е’Ңе°ҸиҜҙзҡ„дјҳеҠҝпјҢд»ҺиҖҢеҫ—еҮәе°ҸиҜҙеҸҜиЈЁиЎҘз»ҸеҸІз”ҡиҮідјҳдәҺз»ҸеҸІзҡ„з»“и®әпјҢд»Ҙжңҹ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зҡ„ең°дҪҚгҖӮиҝҷз§ҚеҜ№жҜ”еҫҖеҫҖд»Һд»ҘдёӢдёӨдёӘеұӮйқўеұ•ејҖгҖӮ1.еҜ№жҜ”з»ҸеҸІдёҺе°ҸиҜҙзҡ„еҸҜиҜ»жҖ§дёҚе°‘еәҸи·ӢжҢҮеҮәпјҢдёҺз»ҸеҸІзӣёжҜ”пјҢе°ҸиҜҙжӣҙеҠ йҖҡдҝ—жҳ“жҮӮгҖӮеҰӮиўҒе®ҸйҒ“гҖҠдёңиҘҝжұүйҖҡдҝ—жј”д№үеәҸгҖӢз§°пјҡвҖңдәҲжҜҸжЈҖеҚҒдёүз»ҸжҲ–дәҢеҚҒдёҖеҸІпјҢдёҖеұ•еҚ·пјҢеҚіеҝҪеҝҪж¬ІзқЎеҺ»пјҢжңӘиӢҘгҖҠж°ҙжө’гҖӢд№ӢжҳҺзҷҪжҷ“з•…пјҢиҜӯиҜӯ家常гҖӮвҖқгҖҠйҮҚеҲҠжқӯе·һиҖғиҜҒдёүеӣҪеҝ—дј еәҸгҖӢз§°пјҡвҖңзҪ—иҙҜдёӯж°ҸеҸҲзј–дёәйҖҡдҝ—жј”д№үпјҢдҪҝд№ӢжҳҺзҷҪжҳ“жҷ“пјҢиҖҢж„ҡеӨ«дҝ—еЈ«пјҢдәҰеә¶еҮ зҹҘжүҖи®ІиҜ»з„үгҖӮвҖқи®ёеӨҡ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и®ІеҸІзұ»дҪңе“ҒпјҢйғҪз§үжҢҒвҖңд»ҘдёҠеҸӨйҡҗеҘҘд№Ӣж–Үз« пјҢдёәд»Ҡж—ҘеҲҶжҳҺд№Ӣи®®и®әвҖқзҡ„еҲӣдҪңж–№й’ҲпјҢеӣ жӯӨпјҢйҖҡдҝ—еңЁдҪңдёәе°ҸиҜҙиҝҪжұӮ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жҲҗдёәе®ғ们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дјҳдәҺз»ҸеҸІзҡ„дёҖеӨ§еҚ–зӮ№гҖӮдёҺйҖҡдҝ—зӣёеә”пјҢиҫғд№ӢжһҜзҮҘйҡҫиҜ»зҡ„з»ҸеҸІпјҢе°ҸиҜҙжңүзқҖжӣҙејәзҡ„и¶Је‘іжҖ§гҖӮгҖҠеҝ«еҝғзј–еәҸгҖӢз§°е°ҸиҜҙд»ӨдәәвҖңеҝҳжҡ‘жӯўйҘҘвҖқпјҢйҷ¶е®¶й№ӨгҖҠз»ҝйҮҺд»ҷиёӘеәҸгҖӢз§°е°ҸиҜҙеҸҜвҖңеЁұзӣ®йҖӮжғ…вҖқпјҢйӮ№еӯҳж·ҰгҖҠеҲ иЎҘе°ҒзҘһжј”д№үиҜ и§ЈеәҸгҖӢеҲҷжӣҙжҳҜжҸҗеҲ°вҖңиҜ»жӯЈеҸІиҖ…пјҢжҜҸдёҚз»ҲеҚ·пјӣеҫ—е°ҸиҜҙиҜ»д№ӢпјҢеҲҷжҙҘжҙҘжңүе‘івҖқпјҢиҝҷдәӣи®әиҝ°йғҪеҜ№жҜ”дәҶеҸІд№ҰдёҺе°ҸиҜҙзҡ„йҳ…иҜ»ж•ҲжһңгҖӮи¶Је‘іжҖ§иөӢдәҲе°ҸиҜҙд»Ҙеҝ…иҰҒзҡ„еӯҳеңЁд»·еҖјпјҢжЁөдә‘еұұдәәеңЁгҖҠйЈһиҠұиүіжғіеәҸгҖӢдёӯ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пјҢеҰӮдәәй—ҙ家常иҢ¶йҘӯпјҢж—Ҙз”ЁдёҚеҸҜзјәпјӣ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пјҢеҰӮдё–дёҠеұұжө·зҸҚйҰҗпјҢзҲҪеҸЈдәҰдёҚеҸҜе°‘гҖӮеҰӮеҝ…и°“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ж–№еҸҜиҜ»пјҢиҖҢ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дёҚи¶ійҳ…пјҢжҳҜзҠ№ж—Ҙ用家常иҢ¶йҘӯпјҢиҖҢзҲҪеҸЈж— зҸҚйҰҗзҹЈгҖӮвҖқд»–е°Ҷ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жҜ”дҪңдёҚеҸҜжҲ–зјәзҡ„家常иҢ¶йҘӯпјҢиҖҢе°Ҷе°ҸиҜҙжҜ”дҪңеҸҜдҫӣзҲҪеҸЈзҡ„еұұжө·зҸҚйҰҗгҖӮзҸҚйҰҗзҡ„вҖңзҲҪеҸЈвҖқзү№еҫҒеҚідёәе°ҸиҜҙи¶Је‘іжҖ§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дҪңиҖ…и®ӨдёәпјҢеҒҘеә·зҡ„иҢ¶йҘӯиҮӘ然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пјҢдҪҶеўһиүІзҡ„зҸҚйҰҗд№ҹдёҚеҸҜеәҹејғ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»–дё»еј пјҢ并йқһеҸӘжңү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еҸҜиҜ»пјҢ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д№ҹ并йқһдёҚи¶ійҳ…пјҢдёҚиғҪеӣ жӯЈи·ҜиҖҢеҒҸеәҹж”ҜжөҒпјҢеә”жӯЈи§Ҷи¶Је‘іжҖ§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д»·еҖјгҖӮе°ҸиҜҙзҡ„йҖҡдҝ—жҖ§е’Ңи¶Је‘іжҖ§еңЁжҳҺзҷҪжҷ“з•…гҖҒд»ӨдәәиҜ»еҫ—жҙҘжҙҘжңүе‘ід№ӢдҪҷпјҢиҝҳдә§з”ҹдәҶжҜ”з»ҸеҸІжӣҙеҘҪзҡ„дј ж’ӯж•ҲжһңгҖӮдҝһдёҮжҳҘзҡ„гҖҠз»“ж°ҙжө’е…Ёдј еј•иЁҖгҖӢеҚіз§°пјҡвҖңиҺ«йҒ“е°ҸиҜҙй—Ід№ҰдёҚе…ізҙ§иҰҒпјҢйЎ»зҹҘи¶ҠжҳҜе°ҸиҜҙй—Ід№Ұи¶ҠеҸ‘ж’ӯдј еҫ—еҝ«пјҢиҢ¶еқҠй…’иӮҶпјҢзҒҜеүҚжңҲдёӢпјҢдәәдәәе–ңиҜҙпјҢдёӘдёӘзҲұеҗ¬гҖӮвҖқжҒ¬жҫ№дәәзҡ„гҖҠзҺүиҹҫи®°еҸҷгҖӢдәҰз§°пјҡвҖңд»–еҰӮйҮҺд№ҳзЁ—е®ҳгҖҒж·«иҜҚе°ҸиҜҙпјҢеҮЎжңүиҜҶеӯ—д№ӢеҶңеӨ«пјҢзӣ®йҒҮд№ӢпјҢеҚіи¶ід»ҘдҪҡеҝ—пјӣзҹҘжғ…д№ӢеҘіеӯҗпјҢиҖіеҫ—д№ӢпјҢдәҰи¶ід»ҘеҠЁеҝғ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дёҚд»…иҜ„д»·дәҶе°ҸиҜҙзҡ„дј ж’ӯйҖҹеәҰпјҢиҖҢдё”жҢҮеҮәе°ҸиҜҙеҜ№зҷҫ姓зҡ„жҖқжғіжңүзқҖиҫғеӨ§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гҖӮ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жіЁж„ҸеҲ°дәҶе°ҸиҜҙзҡ„йҖҡдҝ—жҖ§дёҺдј ж’ӯдјҳеҠҝпјҢ并д»ҘжӯӨеҮәеҸ‘пјҢжҢҮеҮәдәҶиҜҘзү№иҙЁдёәе°ҸиҜҙеёҰжқҘзҡ„дёӨеӨ§з§ҜжһҒеҠҹиғҪгҖӮдёҖжҳҜе°ҸиҜҙзҡ„йҖҡдҝ—жҖ§дёҺдј ж’ӯдјҳеҠҝеҸҜеё®еҠ©з»ҸеҸІжҺЁе№ҝеҠқжғ©пјҢд»ҺиҖҢжӯЈдәәеҝғгҖҒ移йЈҺдҝ—гҖҒиЈЁзӣҠйЈҺж•ҷгҖӮеҸҜдёҖеұ…еЈ«гҖҠйҶ’дё–жҒ’иЁҖеҸҷгҖӢеҚіз§°е…ӯз»ҸеӣҪеҸІвҖңе°ҡзҗҶжҲ–з—…дәҺиү°ж·ұпјҢдҝ®иҜҚжҲ–дјӨдәҺи—»з»ҳпјҢеҲҷдёҚи¶ід»Ҙи§ҰйҮҢиҖіиҖҢжҢҜжҒ’еҝғвҖқпјҢвҖңдёүиЁҖвҖқеҲҷеҸҜвҖңеҜјж„ҡвҖқвҖңйҖӮдҝ—вҖқпјҢдёәвҖңе…ӯз»ҸеӣҪеҸІд№Ӣиҫ…вҖқгҖӮйқҷжҒ¬дё»дәәгҖҠйҮ‘зҹізјҳеәҸгҖӢ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е°ҸиҜҙдҪ•дёәиҖҢдҪңд№ҹпјҹжӣ°пјҡд»ҘеҠқе–„д№ҹпјҢд»Ҙжғ©жҒ¶д№ҹгҖӮеӨ«д№Ұд№Ӣи¶ід»ҘеҠқжғ©иҖ…пјҢиҺ«иҝҮдәҺз»ҸеҸІпјҢиҖҢд№үзҗҶиү°ж·ұпјҢйҡҫд»Ө家喻иҖҢжҲ·жҷ“пјҢеҸҚдёҚиӢҘзЁ—е®ҳйҮҺд№ҳпјҢзҰҸе–„зҘёж·«д№ӢзҗҶжӮүеӨҮпјҢеҝ дҪһиҙһйӮӘд№ӢжҠҘжҳӯ然пјҢиғҪдҪҝдәәи§Ұзӣ®жғҠеҝғпјҢеҰӮеҗ¬жҷЁй’ҹпјҢеҰӮй—»еӣ жһңпјҢе…¶дәҺ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дёҚдёәж— иЎҘд№ҹгҖӮвҖқ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жҷ®йҒҚи®ӨдёәпјҢз»ҸеҸІиҷҪ然足д»ҘеҠқжғ©пјҢдҪҶжҷҰ涩йҡҫжҮӮпјҢж— жі•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пјӣе°ҸиҜҙеҲҷйҖҡдҝ—жңүи¶ЈпјҢеҸҜдҪҝдәәвҖңеҚ·дёҚйҮҠжүӢ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Һз»ҸеҸІзӣёжҜ”пјҢе°ҸиҜҙеҸҜд»ҘжӣҙеҘҪең°ж•ҷеҢ–ж„ҡж°“пјҢ并еҜ№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жңүжүҖиЈЁзӣҠгҖӮдәҢжҳҜе°ҸиҜҙзҡ„йҖҡдҝ—жҖ§дёҺи¶Је‘іжҖ§еҸҜд»Ҙеё®еҠ©иҜ»иҖ…жҳҺзҷҪең°дәҶи§ЈеҸІд№Ұзҡ„иү°ж¶©еҶ…е®№пјҢд»ҺиҖҢиө·еҲ°е№ҝдәәи§Ғй—»з”ҡиҮіеҠ©дәәжІ»еӯҰ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и®ёе®қе–„гҖҠеҢ—еҸІжј”д№ү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»ҠиҜ•иҜӯдәәжӣ°пјҡе°”ж¬ІзҹҘеҸӨд»Ҡд№ӢдәӢд№Һпјҹдәәж— дёҚиёҠи·ғжұӮзҹҘиҖ…гҖӮеҸҲиҜ•иҜӯдәәжӣ°пјҡе°”ж¬ІзҹҘеҸӨд»Ҡд№ӢдәӢпјҢзӣҚиҜ»еҸІпјҹдәәзҪ•жңүиёҠи·ғжұӮиҜ»иҖ…гҖӮе…¶ж•…дҪ•д№ҹпјҹеҸІд№ӢиЁҖиҙЁиҖҢеҘҘпјҢдәәдёҚиҖҗиҜ»пјҢиҜ»дәҰзҪ•и§ЈгҖӮж•…е”ҜеӯҰеЈ«еӨ§еӨ«жҲ–иғҪжҠ«и§ҲпјҢеӨ–жӯӨеҲҷжңӣжңӣ然еҺ»д№ӢзҹЈгҖӮеҒҮдҪҝе…¶д№ҰдёҖзӣ®дәҶ然пјҢжҷәж„ҡе…ұи§ҒпјҢдәәеӯ°дёҚдәүе…Ҳзқ№д№Ӣдёәеҝ«д№Һ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§°дәәзҡҶж¬ІзҹҘеҸӨд»Ҡд№ӢдәӢпјҢдҪҶеӨ§йғҪзўҚдәҺеҸІд№Ұиү°ж·ұиҖҢдёҚж„ҝиҜ»д№ӢпјҢеҸҜвҖңдёҖзӣ®дәҶ然пјҢжҷәж„ҡе…ұи§ҒвҖқзҡ„е°ҸиҜҙеҲҷеҫҲеҘҪең°и§ЈеҶідәҶ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гҖӮи”Ўе…ғж”ҫзҡ„гҖҠдёңе‘ЁеҲ—еӣҪеҝ—еәҸгҖӢжӣҙжҳҜжҸҗеҮәвҖңдәәеӨҡдёҚиғҪиҜ»еҸІпјҢиҖҢж— дәәдёҚиғҪиҜ»зЁ—е®ҳгҖӮзЁ—е®ҳеӣәдәҰеҸІд№Ӣж”ҜжҙҫпјҢзү№жӣҙжј”з»Һе…¶иҜҚиҖігҖӮе–„иҜ»зЁ—е®ҳиҖ…пјҢдәҰеҸҜиҝӣдәҺиҜ»еҸІпјҢж•…еҸӨдәәдёҚеәҹвҖқпјҢи®ӨдёәеҺҶеҸІжј”д№үж—ўеҸҜдҪҝдәәйҖҡжҷ“еҸІе®һпјҢеҸҲеҸҜеҠ©дәәвҖңиҝӣдәҺиҜ»еҸІвҖқпјҢиғҪеӨҹдҪңдёәиҝӣе…ҘеҸІеӯҰйўҶеҹҹзҡ„еӘ’д»ӢпјҢеӣ иҖҢеҜ№еҸІеӯҰжңүвҖңе°ҸиЈЁвҖқгҖӮ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们д№җдәҺвҖң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е…·жңүжҜ”з»ҸеӯҰжӣҙеҘҪзҡ„иүәжңҜйӯ…еҠӣе’Ңе®ЎзҫҺж•ҲжһңпјҢеҮёжҳҫиҜ»иҖ…еҜ№дәҺ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ӯҰзҡ„дёҚеҗҢжҺҘеҸ—жҖҒеәҰпјҢеҜ№жҜ”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ӯҰжҺҘеҸ—ж•Ҳжһңж–№йқўзҡ„е·ЁеӨ§еҸҚе·®пјҢд»ҺиҖҢе ӮиҖҢзҡҮд№Ӣең°иӮҜе®ҡе°ҸиҜҙзҡ„д»·еҖјж„Ҹд№үвҖқпјҢеҜ№еҸІд№ҳдәҰ然гҖӮ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зҡ„еҸҜиҜ»жҖ§дёҺдј ж’ӯж•ҲжһңеҜ№жҜ”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еҚҒеҲҶеёёи§ҒпјҢ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еҜ№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е°ҸиҜҙзҡ„дјҳеҠҝдҫҝеҸҜеҫ—д»ҘзӘҒжҳҫгҖӮиҝҷз§ҚеҒҡжі•жҳҜ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дёәж ҮжҰң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жүҖйҮҮеҸ–зҡ„иҫғдёәжҲҗеҠҹзҡ„зӯ–з•ҘгҖӮ2.еҜ№жҜ”еҸІд№ҳдёҺе°ҸиҜҙзҡ„е®Ңж•ҙжҖ§е°ҸиҜҙеҺҶжқҘжңүвҖң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вҖқвҖңжӯЈеҸІд№ӢдҪҷвҖқвҖңеҸІд№Ӣж”ҜжөҒвҖқзӯүдёҺеҸІд№ҳжңүе…ізҡ„еҲ«з§°пјҢеҸІзЁ—е…ізі»д№ҹжҳҜеҺҶд»Ј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жүҖзғӯиЎ·жҺўи®Ёзҡ„йҮҚиҰҒиҜқйўҳ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е°Өе…¶жҳҜи®ІеҸІзұ»е°ҸиҜҙзҡ„еәҸи·ӢпјҢдјҡиҜҰз»ҶеҜ№жҜ”е°ҸиҜҙдёҺжӯЈеҸІзҡ„дёҚеҗҢзү№иҙЁгҖӮеҰӮжҶЁжҶЁеӯҗгҖҠз»ЈжҰ»йҮҺеҸІ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жӯЈеҸІжҲ–дёҚж•ўи®ҪеҲәпјҢдҪҶе°ҸиҜҙе№¶ж— жӯӨз§ҚйЎҫеҝҢгҖӮеҗүиЎЈдё»дәәгҖҠйҡӢеҸІйҒ—ж–Ү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жӯЈеҸІиҙөзңҹгҖҒйҒ—еҸІиҙөе№»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жҜ”иҫғдёӯиӮҜ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әҸи·ӢдёӯжңҖеёёжҸҗеҸҠзҡ„д№ғжҳҜеҸІзЁ—зҡ„е®Ңж•ҙжҖ§еҜ№жҜ”пјҢи®ӨдёәеҸІд№Ұиҫғдёәз®Җз•ҘпјҢе°ҸиҜҙеҲҷжӣҙеҠ иҜҰе°ҪгҖӮе‘Ёд№Ӣж ҮгҖҠж®Ӣе”җдә”д»ЈеҸІдј еҸҷгҖӢеҚізӣҙиЁҖвҖңжӯЈеҸІз•ҘвҖқвҖңйҮҺеҸІиҜҰвҖқпјӣжқҺйӣЁе ӮгҖҠдёҮиҠұжҘјжқЁеҢ…зӢ„жј”д№үеҸҷгҖӢжӣҙжҳҜжҸҗеҮәпјҢеҸІд№ҳвҖңз®ҖиҖҢзәҰ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иҮӘ然дјҡеҮәзҺ°вҖңз§ү笔йҡҫиҜҰвҖқвҖңеӨ§йўҳе°ҸдҪңвҖқзҡ„зү№еҫҒпјҢеҜјиҮҙвҖңжһҜеҜӮвҖқпјҢиҖҢдј еҘҮиҷҪвҖңж— й—®дәҺзЁҪиҖғжү¶жӨҚд№ӢйҮҚвҖқпјҢдҪҶиҙөеңЁвҖңиҜҰеҚҡвҖқ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әҸи·ӢиҝӣдёҖжӯҘзӮ№жҳҺпјҢжӯЈеӣ дёәеҸІд№ҳз®ҖзәҰгҖҒе°ҸиҜҙиҜҰеҚҡ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и®ІеҸІзұ»е°ҸиҜҙдёӯж¶үеҸҠи®ёеӨҡжӯЈеҸІжүҖвҖңйҮҮж‘ӯжңӘеӨҮвҖқ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Ңиҫғд№ӢжӯЈеҸІпјҢ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жҸҸиҝ°жӣҙеҠ иҜҰз»Ҷе®Ңе–„пјҢж•…иҖҢеҸҜд»ҘиЎҘжӯЈеҸІд№ӢйҳҷгҖӮеҰӮзҶҠеӨ§жңЁеңЁгҖҠеӨ§е®ӢжӯҰз©ҶзҺӢжј”д№үеәҸгҖӢдёӯ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жҲ–и°“е°ҸиҜҙдёҚеҸҜзҙҠд№Ӣд»ҘжӯЈеҸІпјҢдҪҷж·ұжңҚе…¶и®әпјӣ然иҖҢ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е®һи®°жӯЈеҸІд№ӢжңӘеӨҮпјҢиӢҘдҪҝзҡ„д»ҘдәӢиҝ№жҳҫ然дёҚжіҜиҖ…еҫ—еҪ•пјҢеҲҷжҳҜд№Ұз«ҹйҡҫд»ҘжҲҗйҮҺеҸІд№ӢдҪҷж„ҸзҹЈгҖӮвҖқд»–жүҝи®Өе°ҸиҜҙйҡҫд»ҘеҢ№ж•ҢжӯЈеҸІ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дҪҶеҗҢж—¶и®Өдёәе°ҸиҜҙдёӯи®°иҪҪдәҶи®ёеӨҡжӯЈеҸІдёӯжІЎжңү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дёҺд№Ӣзӣёзұ»пјҢе°Ҹзҗ…зҺҜдё»дәәзҡ„гҖҠдә”иҷҺе№іеҚ—еҗҺдј еәҸгҖӢдәҰжҸҗеҮәвҖңеӨ–еҸІйҮҺеҸІдәҰеҸҜеӨҮеӣҪеҸІжүҖжңӘеӨҮвҖқ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е°ҸиҜҙзҡ„еҠҹиғҪдҫҝеҸҜеӣ жӯӨеҫ—д»ҘдҪ“зҺ°пјҢеҰӮгҖҠиҝҳеҶӨи®°гҖӢеәҸз§°е…¶вҖңй—ҙжңүејӮй—»еҸҜиЎҘеҸІдј д№ӢйҳҷвҖқпјҢгҖҠи¶Ҡз»қд№ҰгҖӢеәҸз§°е…¶вҖңдәӢиЈЁеҸІзјәвҖқпјҢгҖҠжё…жіўжқӮеҝ—гҖӢеәҸз§°е…¶вҖңеҸҜиЎҘжӯЈеҸІжүҖйҳҷйҒ—вҖқпјҢгҖҠе®Ӣдәәе°ҸиҜҙгҖӢеәҸз§°е…¶вҖңдәӢеҸҜиЎҘжӯЈеҸІд№ӢдәЎпјҢиЈЁжҺҢж•…д№ӢйҳҷвҖқзӯүпјҢеқҮ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е…·жңүвҖңиЎҘеҸІйҳҷвҖқзҡ„еҠҹиғҪгҖӮйғЁеҲҶеәҸи·Ӣиҝҳи®Өдёәе°ҸиҜҙеңЁиЎҘеҸІд№ӢдҪҷдәҰеҸҜиЎҘз»ҸпјҢеҰӮйҷҲ继儒称гҖҠеҲ—еӣҪдј гҖӢдёәвҖңдё–е®ҷй—ҙдёҖеӨ§иҙҰз°ҝвҖқпјҢи®Өдёәе…¶вҖңдәҰи¶іиЎҘз»ҸеҸІд№ӢжүҖжңӘиө…вҖқпјҢвҖңиҷҪдёҺз»ҸеҸІе№¶дј еҸҜд№ҹвҖқпјӣжқЁжҫ№жёёгҖҠй¬ји°·еӣӣеҸӢеҝ—еәҸгҖӢз§°иҮӘе·ұе–ңиҜ»зҷҫ家е°Ҹдј 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дәӣе°Ҹдј еҸҜд»ҘвҖңдёҫз»Ҹдј зјәз•ҘпјҢжңүиЈЁдәҺжӯЈйҒ“вҖқ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д»…еҮӯе°ҸиҜҙеҸҜвҖңи®°жӯЈеҸІд№ӢжңӘеӨҮвҖқдҫҝз§°е…¶еҜ№еҸІд№ҳжңүиЈЁиЎҘдҪңз”ЁпјҢжҳҜжңүзүөејәд№Ӣе«Ңзҡ„гҖӮеӣ дёәиҙөеңЁдј дҝЎзҡ„жӯЈеҸІеҺҹжң¬е°ұдјҡиҲҚејғдёҖдәӣж— е…ізҙ§иҰҒзҡ„е°ҸдәӢжҲ–еҸҜдҝЎеәҰдёҚи¶ізҡ„дј й—»пјҢе°ҸиҜҙеҲҷдёҚ然пјҢдёҖеҲҮиҪ¶дәӢж— и®әеӨ§е°Ҹзңҹе№»еқҮеҸҜж•·иЎҚжҲҗзҜҮгҖӮ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зҡ„дҪңиҖ…е…¶е®һд№ҹж„ҸиҜҶеҲ°дәҶиҝҷдёҖзӮ№пјҢеҰӮжҹұзҹіж°Ҹзҡ„гҖҠзҷҪзүЎдё№е°ҸеәҸгҖӢе°ұиЁҖжҳҺжӯЈеҫ·зҡҮеёқдёҺзҷҪзүЎдё№д№ӢдәӢвҖңеҸІж— й—»зҹЈгҖӮеҸІж— й—»пјҢеҲҷдҪ•дёҚеҸҜдёәд№ӢиҜҙвҖқ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еңЁеҜ№жҜ”гҖҒиҜ„еҲӨе°ҸиҜҙдёҺеҸІд№ҳзҡ„е®Ңж•ҙжҖ§ж—¶пјҢжңүж„Ҹең°жҗҒзҪ®дәҶжӯЈеҸІзҡ„йҮҮжӢ©ж ҮеҮҶпјҢиҖҢд»…иҖғеҜҹе…¶дё°еҜҢзЁӢеәҰгҖӮ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иҜ„еҲӨж ҮеҮҶдёӢпјҢе°ҸиҜҙиҮӘ然дјҡеӣ е…¶жӣҙеӨ§зҡ„зҜҮе№…е’Ңжӣҙе……е®һзҡ„еҶ…е®№иҖҢеңЁдёҺеҸІд№ҳзҡ„еҜ№жҜ”дёӯиғңеҮәпјҢиҝҷж ·д№ҹе°ұиҫҫеҲ°дәҶеәҸи·Ӣд»ҘжӯӨжқҘеҪ°жҳҫ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зҡ„зӣ®зҡ„гҖӮз»јдёҠжүҖиҝ°пјҢеҖҹеҠ©з»ҸеҸІзҡ„ең°дҪҚе’Ңж„Ҹд№үпјҢ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зҫҪзҝјз»ҸеҸІд№ғиҮідјҳдәҺз»ҸеҸІпјҢеҸҜи°“ж ҮжҰң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зҡ„з»қдҪійҖ”еҫ„гҖӮ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пјҢ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既еҠӣиҜҒе°ҸиҜҙзҡ„йҖүжқҗдёҺз«Ӣж„Ҹз¬ҰеҗҲз»ҸеҸІзҡ„жҖқжғіеўғз•Ңе’Ң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пјҢеҸҲи®Өдёәе°ҸиҜҙеӣ е…¶дјҳдәҺз»ҸеҸІзҡ„еҸҜиҜ»жҖ§е’Ңе®Ңж•ҙжҖ§иҖҢе…·еӨҮи¶…и¶Ҡз»ҸеҸІзҡ„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пјҢд»ҺиҖҢиҫҫеҲ°еҖҹеҠ©з»ҸеҸІд№ӢеҠӣжқҘжҠ¬й«ҳе°ҸиҜҙең°дҪҚзҡ„зӣ®зҡ„гҖӮдәҢгҖҒвҖңдҫқз»ҸеӮҚеҸІвҖқиҜ„иҜҙе°ҸиҜҙиҮӘиә«д»·еҖј йҷӨдәҶдҫқз»ҸеӮҚеҸІгҖҒеҖҹеҠ©з»ҸеҸІзҡ„жӯЈз»ҹжҖ§ж ҮжҰңиҮӘиә«д»·еҖјпјҢеӨ§йҮҸ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иҝҳд№җдәҺеҖҹеҠ©еәҸи·ӢзӘҒжҳҫе…¶жүҖиҜ„дҪңе“ҒеңЁе°ҸиҜҙиҝҷдёҖж–ҮдҪ“дёӯзҡ„дјҳз§Җж°ҙе№іе’ҢеҚ“и¶Ҡең°дҪҚпјҢж ҮжҰңиҜҘдҪңе“Ғд№ғжҳҜ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дёҠд№ҳд№ӢдҪңгҖӮпјҲдёҖпјүеңЁдёҺдјҳз§ҖдҪңе“Ғзҡ„жҜ”иҫғдёӯеҪ°жҳ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зҡ„зү№иҙЁи®ёеӨҡе°ҸиҜҙзҡ„еәҸи·Ӣеёёеёёе°ҶиҮӘе·ұдёҺе…¶д»–дјҳз§Җе°ҸиҜҙиҝӣиЎҢжҜ”иҫғпјҢеҰӮзғҹйңһеӨ–еҸІгҖҠйҹ©ж№ҳеӯҗеҸҷгҖӢдёӯз§°гҖҠйҹ©ж№ҳеӯҗе…Ёдј гҖӢвҖңжңү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д№ӢжЈ®дёҘпјҢгҖҠж°ҙжө’дј гҖӢд№ӢеҘҮеҸҳпјӣж— гҖҠиҘҝжёёи®°гҖӢд№Ӣи°‘иҷҗпјҢ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д№Ӣдәөж·«вҖқпјҢжңүеӣӣеӨ§еҘҮд№Ұзҡ„дјҳзӮ№пјҢдё”ж— е…¶и°‘иҷҗдәөж·«зҡ„ејҠз—…пјҢжҳҜдёҖйғЁдҪідҪңгҖӮйҷ¶е®¶й№ӨгҖҠз»ҝйҮҺд»ҷиёӘеәҸгҖӢжҸҗеҮәпјҡвҖңж„ҝе–„иҜ»иҜҙйғЁиҖ…пјҢе®ңз–ҫеҸ–гҖҠж°ҙжө’гҖӢ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гҖҠз»ҝйҮҺд»ҷиёӘгҖӢдёүд№ҰиҜ»д№ӢпјҢеҪјзҡҶи°ҺеҲ°е®¶д№Ӣж–Үеӯ—д№ҹпјҢи°“д№ӢдёәеӨ§еұұгҖҒеӨ§ж°ҙгҖҒеӨ§еҘҮд№ҰпјҢдёҚдәҰе®ңд№ҺпјҹвҖқиҝҷйҮҢзӣҙжҺҘе°ҶгҖҠз»ҝйҮҺд»ҷиёӘгҖӢдёҺгҖҠж°ҙжө’дј гҖӢ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иҝҷдёӨйғЁеҘҮд№ҰйҪҗеҗҚ并дёҫгҖӮи§Ӯд№ҰдәәгҖҠжө·жёёи®°еәҸгҖӢиЁҖгҖҠжө·жёёи®°гҖӢвҖңжң«еҚ·ж¶үдәҺиҚ’жёәжўҰд№ҹпјҢжўҰдёӯдҪ•жүҖдёҚжңүе“үпјҒд»ҘжўҰз»“иҖ…пјҢгҖҠиҘҝеҺўи®°гҖӢгҖҠж°ҙжө’дј гҖӢпјҢеҫ—жӯӨиҖҢдёүзҹЈвҖқпјҢзӮ№жҳҺгҖҠжө·жёёи®°гҖӢдёҺгҖҠиҘҝеҺўи®°гҖӢгҖҠж°ҙжө’дј гҖӢдёҖж ·жңүд»ҘжўҰдҪңз»“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еӣ иҖҢеҸҜдёҺеҗҺдёӨиҖ…并称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еәҸи·ӢжүҖйҖүжӢ©зҡ„жҜ”иҫғеҜ№иұЎеҹәжң¬йӣҶдёӯеңЁгҖҠж°ҙжө’дј гҖӢ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гҖҠиҘҝжёёи®°гҖӢзӯүдё–жүҖе…¬и®Өзҡ„з»Ҹе…ёеҗҚи‘—дёӯпјҢ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们жӯЈжҳҜеёҢжңӣеҲ©з”Ёз»Ҹе…ёд№ӢеҗҚпјҢи®әиҜҒ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жңүзқҖдёҺз»Ҹе…ёдҪңе“ҒзӣёеҗҢзҡ„зү№еҫҒпјҢд»ҺиҖҢиҜҒжҳҺ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е…·еӨҮжҲҗдёәеҗҚи‘—зҡ„жҪңиҙЁгҖӮпјҲдәҢпјүеңЁдёҺеҸҚйқўдҫӢеӯҗзҡ„еҜ№жҜ”дёӯеҮёжҳ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зҡ„дјҳеҠҝжӣҙеӨҡеәҸи·ӢеҲҷеҖҹеҠ©е…·жңүеҸҚйқўжЎҲдҫӢеҠҹиғҪзҡ„еҮ йғЁе°ҸиҜҙжҲ–дёҖзұ»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пјҢйҖҡиҝҮдёҺе…¶еҜ№жҜ”жқҘзӘҒеҮәиҮӘиә«зҡ„дјҳеҠҝгҖӮеҜ№жҜ”ж–№ејҸеӨ§иҮҙеҸҜеҲҶдёәеҰӮдёӢеӣӣзұ»гҖӮ1.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йЈҺйӣ…дёҚе®Јж·«иҜҘж–№жі•дё»иҰҒиҝҗз”ЁдәҺе“ҒиҜ„иғӯзІүзұ»е°ҸиҜҙгҖӮеҰӮеҸӨеҗҙеӯҗгҖҠдәәй—ҙд№җ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жүҚеӯҗдҪідәәе°ҸиҜҙвҖңеҠЁеӨҡй„ҷзҗҗйҫҢйҫҠд№Ӣи°ҲвҖқпјҢиҖҢгҖҠдәәй—ҙд№җгҖӢиҙөеңЁвҖңжүҚеӯҗд№Ӣд№җпјҢдёҚе®ідәҺйӣ…пјӣдҪідәәд№Ӣд№җпјҢдёҚеӨұе…¶жӯЈвҖқпјӣжқҺжҳҘиҚЈгҖҠж°ҙзҹізјҳеҗҺеәҸгҖӢз§°вҖңеҸӨжқҘдј еҘҮдёҚеӨ–д№ҺдҪідәәжүҚеӯҗпјҢжҖ»д»ҘеҗҹиҜ—дёәеӘ’пјҢзүөеј•иӢҹеҗҲпјҢжёҗиҮіж·«иҚЎиҚ’д№ұпјҢеӨ§еқҸе“ҒиЎҢпјҢж®ҠдјӨйЈҺеҢ–вҖқпјҢиҖҢгҖҠж°ҙзҹізјҳгҖӢвҖңеҸӘиҖғиҜ—и®әиҜ—пјҢз»қж— жҢ‘иҜұд№Ӣжғ…вҖқпјӣж ‘жЈ гҖҠйҮ‘еҸ°е…Ёдј еәҸгҖӢеҲҷиҝӣдёҖжӯҘи®әиҜҒдәҶдёҖдәӣй—Ід№Ұиў«з„ҡзҰҒзҡ„еҺҹеӣ еңЁдәҺвҖңй„ҷдҝҡж·«иҜҚпјҢе№ҪжңҹеҜҶзәҰпјҢй—әеЁғзЁҡеӯҗйҳ…д№ӢпјҢеҝ…иҮҙж•Ҳз”ұвҖқпјҢ并д»ҘжӯӨйҳҗжҳҺгҖҠйҮ‘еҸ°е…Ёдј гҖӢвҖңйҖҡзҜҮеҲ°еә•пјҢе№¶ж— дёҖиҜӯиҝ°еҸҠж·«йӮӘпјҢзҪ®д№ӢжЎҲеӨҙзҝ»йҳ…пјҢдёҚж— зЁҚиЎҘвҖқзҡ„дјҳзӮ№гҖӮ他们声称пјҢд»ҘеҫҖ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йЈҺжңҲж•…дәӢеёёжңүвҖңй„ҷзҗҗйҫҢйҫҠвҖқвҖңе®Јз§ҪеҜјж·«вҖқзҡ„ејҠз—…пјҢиҝҷзұ»е°ҸиҜҙдёҖеҲҷдёҚдёҠеҸ°йқўпјҢдәҢеҲҷ移дәәжҖ§жғ…пјҢиҖҢиҮӘе·ұ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дёқжҜ«ж— ж¶үж·«з§Ҫд№ӢиҜӯпјҢж•…иҖҢеҸҜи·»иә«йЈҺйӣ…пјҢз”ҡиҮіиғҪдҪңдёәй—әйҳҒеҘіеӯҗвҖңж·‘жҖ§йҷ¶жғ…д№Ӣеҝ«зқ№вҖқпјҢиө·еҲ°иүҜеҘҪзҡ„еј•еҜјдҪңз”ЁгҖӮ2.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зңҹе®һдёҚиҚ’иҜһ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еҫҖеҫҖжһҒеҠӣж ҮжҰңиҮӘиә«жүҖеҸҷд№ғзңҹдәәзңҹдәӢгҖӮеҰӮйҷҲзҘҲж°ёгҖҠеҸ°ж№ҫеӨ–и®°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ҳҜд№Ұд»Ҙй—ҪдәәиҜҙй—ҪдәӢпјҢиҜҰе§Ӣжң«пјҢе№ҝжҗңиҫ‘пјҢиҝҘејӮдәҺзЁ—е®ҳе°ҸиҜҙпјҢдҝЎи¶іеӨҮеӣҪеҸІйҮҮжӢ©з„үгҖӮвҖқгҖҠеҸ°ж№ҫеӨ–и®°гҖӢдёәи®ІеҸІзұ»е°ҸиҜҙпјҢиҜҘеәҸдҪңи®Өдёәе…¶зңҹе®һжҖ§з”ҡиҮіеҸҜжҜ”иӮ©жӯЈеҸІпјҢеӣ иҖҢиҝңејәдәҺе…¶дҪҷзЁ—е®ҳе°ҸиҜҙд№ӢжөҒгҖӮеҸҲеҰӮжў…жәӘдё»дәәгҖҠжё…йЈҺй—ё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Ҡ‘жҲ–жңүеҮӯиҷҡз»“ж’°пјҢйҡҗе…¶дәәпјҢдјҸе…¶дәӢпјҢиӢҘ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гҖҠзәўжҘјжўҰгҖӢиҖ…пјҢ究д№ӢдёҚзҹҘе®һжҢҮдҪ•дәәпјҢи§ӮиҖ…дәҰдёҚиҝҮдә’зӣёдј дёәжҹҗжҹҗиҖҢе·ІгҖӮе”ҜгҖҠжё…йЈҺй—ёгҖӢдёҖд№ҰпјҢж—ўе®һжңүе…¶дәӢпјҢеӨҚе®һжңүе…¶дәәпјҢдёәе®Ӣж°‘дёҖеӨ§еҶӨзӢұпјҢеҖҹзҡ®еҘүеұұд»ҘйӣӘд№ӢгҖӮвҖқгҖҠжё…йЈҺй—ёгҖӢдёәе…¬жЎҲе°ҸиҜҙпјҢж”№зј–иҮӘгҖҠиӯҰдё–йҖҡиЁҖгҖӢпјҢеҶҷеҢ…е…¬жүҖж–ӯеҶӨжЎҲд№ӢдёҖпјҢеҢ…е…¬е®һжңүе…¶дәәпјҢиҜҘжЎҲд№ҹжңүиҝ№еҸҜиҖғпјҢиҜҘеәҸдҪңеӣ жӯӨз§°е…¶дјҳдәҺ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гҖҠзәўжҘјжўҰгҖӢд№Ӣзұ»зңӢдјјжңүеҪұе°„дҪҶдёҚзҹҘжүҖжҢҮдҪ•дәәзҡ„е°ҸиҜҙгҖӮиҫғдёәзү№ж®Ҡзҡ„пјҢеҲҷеҰӮе§ҡиҒҳдҫҜзҡ„еәҸдҪңжүҖдә‘вҖңзІӨиҮӘй»„е·һиҜҙй¬јпјҢз»ҲдёҪдәҺиҷҡпјӣе№Іе®қгҖҠжҗңзҘһгҖӢпјҢе°Өе«Ңе…¶е№»гҖӮиҮіж¬ІжӯЈдәәеҝғпјҢеҢ–дё–йҒ“пјҢи®ІеҫӘзҺҜжһңжҠҘпјҢеҲҶеҲ«е–„жҒ¶пјҢжүҖи°“е®һиҖҢдёҚиҷҡпјҢзңҹиҖҢдёҚе№»иҖ…пјҢе…¶жғҹжӯӨгҖҠжөҺе…¬дј гҖӢдёҖд№Ұд№ҺвҖқпјҢз§°е…¶жүҖеәҸд№ӢгҖҠиҜ„жј”жөҺе…¬дј гҖӢд№ғзңҹе®һд№ӢдҪңгҖӮжӯӨеӨ„жүҖи®әзҡ„вҖңзңҹе®һвҖқдёҺзңҹдәәзңҹдәӢдёҚеҗҢпјҢд№ғжҳҜз§°иөһе…¶жүҖиҝ°иӯҰж„ҡеҠқе–„ж•…дәӢиҙҙиҝ‘дё–дҝ—гҖҒиӨ’еҝ иҙ¬дҪһйЈҺж°”з¬ҰеҗҲдәәеҝғпјҢеӣ иҖҢд»Өдәәи®ӨеҸҜ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ңЁдёҖдәӣ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зҡ„зңјдёӯпјҢе°ҸиҜҙеҺҶеҸІ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зңҹе®һдёҺжҖқжғі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дёҚиҚ’иҜһеқҮдёәе…¶дјҳеҠҝжүҖеңЁгҖӮ3.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ж–°еҘҮдёҚиҗҪдҝ—еҘ—е°ҸиҜҙиҙөеҘҮпјҢеҚғзҜҮдёҖеҫӢзҡ„йҖүжқҗдёҺ笔法еҫҖеҫҖдјҡдҪҝдәәж„ҹеҲ°д№Ҹе‘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йҖҡиҝҮеҜ№иҮӘиә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ж–°еҘҮд№ӢеӨ„зҡ„жҸӯзӨәдёҺејәи°ғжқҘеҗёеј•иҜ»иҖ…гҖӮеҰӮжҙӘжЈЈе…ғгҖҠй•ңиҠұзјҳеҺҹ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пјҡвҖңд»ҺеҸӨиҜҙйғЁпјҢж— иҷ‘ж•°еҚғзҷҫз§ҚпјҢе…¶з”Ёж„ҸйҖүиҫһпјҢйқһеӨұд№Ӣиҷҡж— е…Ҙе№»пјҢеҚіеӨұд№ӢеҘҘжҠҳйҡҫжҳҺпјҢйқһеӨұд№ӢеӯӨйҷӢеҜЎй—»пјҢеҚіеӨұд№ӢиӮӨеәёиҝӮйҳ”пјҢд»ӨдәәдёҚиҖҗеҜ»е‘іпјҢдёҖи§Ҳж— дҪҷгҖӮвҖқгҖҠй•ңиҠұзјҳгҖӢеҲҷдёҚиҗҪзӘ иҮјпјҢзҷҫиҜ»дёҚеҺҢгҖӮи®ёд№”жһ—гҖҠй•ңиҠұзјҳеәҸгҖӢдәҰдә‘гҖҠй•ңиҠұзјҳгҖӢвҖңж— дёҖеӯ—жӢҫд»–дәәзүҷж…§пјҢж— дёҖеӨ„иҗҪеүҚдәәзӘ иҮјвҖқпјҢз§°е…¶жӢҘжңүйӣҶеӨ§жҲҗзҡ„зү№иҙЁгҖӮи§Ӯд№ҰдәәгҖҠжө·жёёи®°еәҸгҖӢз§°вҖңе°ҸиҜҙ家иЁҖпјҢжңӘжңүдёҚжҢҮз§°жңқд»ЈпјҢеҰ„и®әеҗӣиҮЈпјҢжҲ–еӨёжүҚеӯҗдҪідәәпјҢжҲ–еҒҮзҘһд»ҷй¬јжҖӘвҖқпјҢиҜҘд№ҰеҲҷвҖңжҙ—е°Ҫж•…еҘ—пјҢж—¶ж— еҸҜзЁҪвҖқгҖӮдјҜиүҜж°ҸгҖҠд№үеӢҮеӣӣдҫ й—әеӘӣдј 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вҖңе°ҸиҜҙдёҖд№ҰпјҢеӨ§жҠөдҪідәәжүҚеӯҗгҖҒйЈҺеҚҺйӣӘжңҲд№ӢдҪңпјҢжұ—зүӣе……ж ӢпјҢеҚғжүӢйӣ·еҗҢпјҢйҳ…иҖ…ж— дёҚи®ЁеҺҢвҖқпјҢиҜҘд№ҰеҲҷвҖңејӮжғіеӨ©ејҖпјҢйҷҶзҰ»е…үжҖӘпјҢжһ„жҖқд№Ӣе·§пјҢ用笔д№ӢзҒөпјҢзңҹи¶ід»Өйҳ…иҖ…жғҠеҝғеӨәзӣ®вҖқгҖӮд»ҘдёҠеәҸи·Ӣж„ҸеңЁеҪ°жҳҫ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з«Ӣж„Ҹжһ„жҖқгҖҒи°ӢзҜҮеёғеұҖж–№йқўзҡ„зӢ¬зү№д№ӢеӨ„пјҢеҸҜи°“еҫҲеҘҪең°жҺҢжҸЎдәҶе°ҸиҜҙиҜ»иҖ…зҡ„зҢҺеҘҮеҝғзҗҶгҖӮ4.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е…·жңүж•ҷеҢ–еҠҹиғҪ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иҜ•еӣҫејәи°ғиҮӘиә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дёҚд»…ж— е®ідәҺйЈҺдҝ—пјҢеҸҚиҖҢиғҪеҠқдәәеҗ‘е–„гҖҒж•ҷдәәеӯҰеҘҪгҖӮеҰӮж–Үе…үжҘјдё»дәәгҖҠе°Ҹдә”д№ү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вҖңж·«иҜҚиүіжӣІжңүе®ізәІеёёпјҢеҝ—жҖӘдј еҘҮж— е…іеҗҚж•ҷвҖқпјҢиҖҢжӯӨд№ҰвҖңиҷҪзі»е°ҸиҜҙпјҢжүҖиЁҖзҡҶеҝ зғҲдҫ д№үд№ӢдәӢпјҢжңҖжҳ“ж„ҹеҸ‘дәәд№ӢжӯЈж°”вҖқгҖӮж•Ҹж–Ӣеұ…еЈ«гҖҠиӯҰеҜҢж–°д№ҰеәҸгҖӢиҜ„д»·вҖңеҸӨд»Ҡе°ҸиҜҙвҖқдёәвҖңйқһеәҸж·«дәөпјҢеҲҷиҪҪиҚ’е”җпјӣдёҚе•»жұ—зүӣе……ж ӢпјҢдҪҝйҳ…иҖ…зӣ®д№ұзҘһиҝ·пјҢдёҖж—Ұдё§е…¶жүҖе®ҲвҖқпјҢиҖҢгҖҠиӯҰеҜҢж–°д№ҰгҖӢвҖңж„ҸеҪ°иҜҚжҷ°пјҢеәҹеҚ·йҡҫеҝҳпјҢеҸҜд»Ҙйј“иҲһе…¶з–ҫжҒ¶еҘӢд№үд№ӢеҝғпјҢеӯҳдҫ§йҡҗе“Җз—ӣд№ӢеҝөвҖқгҖӮжҷҙе·қеұ…еЈ«гҖҠзҷҪеңӯеҝ—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гҖҠиҘҝжёёи®°гҖӢгҖҠйҮ‘瓶梅гҖӢд№Ӣзұ»вҖңж— зӣҠдәҺдё–йҒ“пјҢдҪҷеёёжҖӘд№ӢвҖқпјҢдёҚеҸҠиҜҘд№ҰвҖңеҸҜд»ҘдёәеҗҺдё–жі•вҖқгҖӮиғҪеӨҹж„ҹеҢ–дё–дәәгҖҒеҜ№йЈҺдҝ—дәәеҝғжңүзӣҠзҡ„е°ҸиҜҙжңүзқҖиҫғй«ҳзҡ„зӨҫдјҡд»·еҖјпјҢеңЁ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们зңӢжқҘпјҢд»…еҮӯиҝҷдёҖзӮ№пјҢиҝҷдәӣе°ҸиҜҙдҫҝеҸҜдёҺжҖқжғіеўғз•ҢиҫғдҪҺзҡ„е°ҸиҜҙзӣҙжҺҘжӢүејҖе·®и·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ҚідҫҝеҗҺиҖ…жӣҙеҠ ж–°еҘҮжңүи¶ЈгҖҒжӮҰдәәиҖізӣ®пјҢд№ҹдёҚеҸҠеүҚиҖ…ејҳжү¬жӯЈйҒ“гҖҒж„Ҹд№үж·ұиҝңгҖӮдёҠиҝ°еӣӣзұ»еҜ№жҜ”дёӯжүҖжҸҗеҲ°зҡ„е®Јз§ҪеҜјж·«гҖҒиҚ’иҜһиҷҡеҰ„гҖҒиҗҪе…ҘеӣәеҘ—е’ҢиҚЎдәәеҝғеҝ—еӣӣз§ҚзјәзӮ№пјҢйғҪжҳҜеҺҶд»Јж–Үдәәжү№еҲӨе°ҸиҜҙж—¶жүҖеёёеёёжҸҗеҲ°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зқҖйҮҚйҖүжӢ©иҝҷеӣӣз§ҚзјәзӮ№жқҘеұ•ејҖеҜ№жҜ”пјҢ并дёҚжғңйҖҡиҝҮиҙ¬дҪҺе…¶д»–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жқҘеё®еҠ©иҮӘиә«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ж‘Ҷи„ұдёҠиҝ°ејҠз—…гҖҒйҒҝе…ҚеҸ—еҲ°йқһи®®гҖӮпјҲдёүпјүйҮҮеҸ–з§ҜжһҒж–№ејҸиЎҘж•‘жңүзјәйҷ·зҡ„дҪңе“ҒеҸҰжңүдёҖдәӣ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иҮӘзҹҘдҪңе“ҒжңүжҳҺжҳҫзҡ„зјәйҷ·д№ӢеӨ„пјҢдҪҶ并дёҚжғіеӣ жӯӨиҖҢеҪұе“Қж—ҒдәәеҜ№иҜҘе°ҸиҜҙ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дәҺжҳҜйҖүжӢ©еҖҹеҠ©еәҸи·ӢеҠ д»ҘиЎҘж•‘гҖӮе…·дҪ“иЎҘж•‘ж–№ејҸдёҚеӨ–д№Һд»ҘдёӢдёӨз§ҚгҖӮ1.йҳҗжҳҺзјәзӮ№еӯҳеңЁеҺҹеӣ зҡ„еҗҢж—¶е°Ҷе…¶еҗҲзҗҶеҢ–иҝҷз§Қж–№ејҸеӨҡиҝҗз”ЁеңЁеҜ№вҖңж·«вҖқзҡ„и®әиҝ°дёӯгҖӮйЈҺжңҲйўҳжқҗйҡҫе…ҚдјҡеҸ—еҲ°дҪҺдҝ—гҖҒиҜІж·«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ҢеәҸи·ӢеҲҷеҫҖеҫҖд»ҘвҖңдәәж¬ІвҖқдҪңдёәжҢЎз®ӯзүҢгҖӮзҹҘдёҚи¶іж–Ӣдё»дәәгҖҠйҮҺеҸҹжӣқиЁҖеәҸгҖӢдёӯеҚіејәи°ғпјҢвҖңжӯЈеӨ§иҖ…еӨ©зҗҶпјҢзҢҘдәөиҖ…дәәжғ…гҖӮеӨ©зҗҶеҚіеҜ“д№Һдәәжғ…д№ӢдёӯпјҢйқһеҚідәәжғ…иҖҢйҖҸиҫҹд№ӢпјҢеҚіеӨ©зҗҶдёҚиғҪжҳҢжҳҺиҮіеҚҒдәҢеҲҶд№ҹвҖқпјҢз§°ж·«ж¬Ід№ғжҳҜдёҚеҸҜзЈЁзҒӯзҡ„дәәжғ…гҖӮжҶЁжҶЁеӯҗгҖҠз»ЈжҰ»йҮҺеҸІеәҸгҖӢдёӯеҲҷжҸҗеҮәдәҶжӣҙиҝӣдёҖжӯҘзҡ„и§ЈйҮҠпјҢз§°е…¶дёӯзҡ„ж·«з§Ҫжғ…иҠӮжҳҜвҖңдёәдё–иҷ‘ж·ұиҝңвҖқпјҢеӣ дёәвҖңдҪҷе°ҶжӯўеӨ©дёӢд№Ӣж·«пјҢиҖҢеӨ©дёӢе·Іи¶ӢзҹЈпјҢдәәеҝ…дёҚеҸ—гҖӮдҪҷд»ҘиҜІд№ӢиҖ…жӯўд№ӢпјҢеӣ е…¶еҠҝиҖҢеҲ©еҜјз„үпјҢдәәдёҚеҝ…дёҚеҸҳд№ҹвҖқпјҢиҜІж·«д№ғжҳҜжҠҠжҸЎдәәеҝғгҖҒеӣ еҠҝеҲ©еҜјд№ӢдёҫгҖӮжңүдәӣеәҸи·Ӣз”ҡиҮід»ҺеҸ—дј—и§Ҷи§’е…ҘжүӢпјҢе®Јз§°еҸӘжңүеәёдҝ—д№ӢдәәжүҚдјҡиҝҮеҲҶжіЁж„Ҹд№ҰдёӯвҖңж·«вҖқ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з§Ӣж–ӢгҖҠиҪҪйҳіе Ӯж„ҸеӨ–зјҳиҫЁгҖӢдёӯеҚіиЁҖпјҡвҖңжӯӨд№Ұж–ӯдёҚеҸҜз»ҸдёӨз§Қдәәд№ӢзңјпјҡиӢҘдёҺеҶ¬зғҳеӨҙи„‘е…Ҳз”ҹи§ҒпјҢжҒјж–ҮзҗҶдёҚйҖҡпјҢж·«иЎҢеҸҜз§ҪиҖҢе·ІпјҢдёҚе®Ўе…¶ж•…пјҢжҳҜд»Ҙж–Үе®іеҝ—д№ҹд№ӢпјӣдҪҶдёҺиҚЎжЈҖйҖҫй—Ід№Ӣеҫ’и§Ғд№ӢпјҢеӣәдёҚй—®ж–ҮзҗҶдёҚйҖҡпјҢдәҰдёҚзҗҶд№Ұдёӯд№Ӣжң¬ж„ҸпјҢдҪҶе°ҶеәҠ笫д№ӢдәӢеӣһзҺҜ笑йҳ…пјҢд»ҘдёәгҖҠйҶӢи‘«иҠҰгҖӢд№ӢеӨ–д№Ұдә‘пјҢдҪҷжӣҙжҶҫз„үгҖӮвҖқ2.жүҝи®Өжңүеҫ®з‘•зҡ„еҗҢж—¶ејәи°ғз‘•дёҚжҺ©з‘ң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е…Ҳз•Ҙж–ҪдёҖ笔жүҝи®Ө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жңүзјәзӮ№пјҢ继иҖҢжө“еўЁйҮҚеҪ©ең°ејәи°ғе…¶й•ҝеӨ„пјҢеҠӣеӣҫиҜҒжҳҺиҜҘе°ҸиҜҙиҷҪжңүеҫ®з‘•пјҢдҪҶз‘•дёҚжҺ©з‘ңгҖӮеҰӮйҫҡжҷӢгҖҠиҪҪйҳіе Ӯж„ҸеӨ–зјҳ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…¶дәӢиҷҪиҝ‘ж·«ж·«пјҢиҖҢз« жі•гҖҒ笔法гҖҒеҸҘжі•гҖҒеӯ—жі•пјҢж— дёҖдёҚи¶іеҗҜеҸ‘еҗҺдәәгҖӮвҖқеҖҡдә‘ж°ҸгҖҠеҚҮд»ҷдј ејҒиЁҖ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ҷҪдәӢзҡҶеҘҮејӮпјҢз–‘дҝЎеҸӮеҚҠпјҢиҖҢе…¶жү¶е–„иүҜгҖҒйҷӨеҘёйӮӘпјҢе…¶и¶ід»Ҙе…ҙиө·дәәеҘҪе–„жҒ¶жҒ¶д№ӢеҝғиҖ…пјҢдёҺеҸӨд»ҠеҸІеҶҢж— ејӮз„үгҖӮвҖқжЁҠеҜҝеІ©гҖҠж°ёеәҶеҚҮе№іеәҸгҖӢз§°е…¶иҷҪдёәвҖңй„ҷдҝҡд№ӢиЁҖвҖқпјҢдҪҶвҖңдёҚд»Ҙж–Үе®іиҫһпјҢдёҚд»Ҙиҫһе®іеҝ—вҖқпјҢвҖңд№Ұд№ӢеҘҮд№ҹдёҚеңЁж–ҮвҖқгҖӮиҝҷдёҖзұ»еәҸи·Ӣзҡ„дҪңиҖ…еӨ§йғҪеЈ°з§°пјҢе°ҸиҜҙй«ҳж·ұзҡ„д№үзҗҶеҸҜд»Ҙж¶Ҳи§Јж–ҮиҫһеҸҠжғ…иҠӮзҡ„дҝҡдҝ—иҚ’иҜһд№ӢеӨ„пјҢе°ҸиҜҙз»ҷдәәеёҰжқҘзҡ„еҗҜеҸ‘ж„Ҹд№үи¶ід»ҘжҺ©зӣ–ж·«з§ҪгҖҒиҷҡеҰ„гҖҒй„ҷдҝҡзӯүзјәзӮ№гҖӮ然иҖҢпјҢеҸҷдәӢж–№жі•дёҺжҖқжғіж·ұеәҰ并йқһеҗҢдёҖеұӮйқўзҡ„иҜ„еҲӨж ҮеҮҶпјҢеӣ жӯӨпјҢиҝҷз§Қи®әиҝ°ж–№ејҸд»…д»…жҳҜиҪ¬з§»и§ҶзәҝгҖӮжҖ»иҖҢиЁҖд№Ӣ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еңЁи®әиҝ°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ж—¶пјҢеҫҖеҫҖдјҡиҝӣиЎҢ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еҶ…йғЁзҡ„жҜ”иҫғгҖӮе®ғ们з§ҜжһҒжҸҗеҮәиҜҘ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…ёеҗҚи‘—зҡ„зӣёеҗҢзү№иҙЁпјҢд»ҘжңҹдёҺз»Ҹе…ёжҜ”иӮ©гҖӮеңЁдёҺе…¶д»–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е’ҢиҮӘиә«ж–Үжң¬зҡ„еҜ№жҜ”ж—¶пјҢжҷ®йҒҚйҮҮеҸ–жү¬й•ҝйҒҝзҹӯзҡ„зӯ–з•ҘпјҢж—ўдёҺе…¶д»–дёҠдёҚеҫ—еҸ°йқўзҡ„дҪңе“ҒеҲ’жё…з•ҢйҷҗпјҢеҸҲеңЁеҸ‘жү¬е…үеӨ§иҮӘиә«дјҳзӮ№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Ҝ№зјәзӮ№еҗ«зіҠиЁҖд№ӢжҲ–дёәе…¶еҜ»жүҫзҗҶз”ұгҖӮдёҠиҝ°еҒҡжі•еқҮжҳҜдёәдәҶж ҮжҰңе…¶жүҖиҜ„и®әдҪңе“ҒеңЁ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еҶ…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д»ҘжңҹиҺ·еҫ—дёҠд№ҳд№ӢдҪңзҡ„зІҫе“Ғд»·еҖјгҖӮдёүгҖҒдҫқжҚ®з»ҸеҸІд»·еҖјж ҮеҮҶиҜ„иҜҙ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ж„Ҹеӣҫ дҪңдёәеҪұе“ҚдҪңе“ҒеҶ…ж¶өгҖҒж·ұеәҰе’ҢжҲҗе°ұзҡ„йҮҚиҰҒеӣ зҙ пјҢ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еҺҶжқҘжҳҜж–ҮеӯҰз ”з©¶дёӯзҡ„йҮҚиҰҒиҜқйўҳпјҢ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дәҰ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еңЁеҺҶд»Ј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дёӯпјҢзӣёеҪ“дёҖйғЁеҲҶдҪңиҖ…дёҚзҪІзңҹеҗҚпјҢе…¶зңҹе®һиә«д»Ҫж— д»ҺзЁҪиҖғ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ҫғд№ӢиҜ—ж–ҮпјҢе°ҸиҜҙзҡ„вҖңзҹҘдәәи®әдё–вҖқзӣёеҜ№еӣ°йҡҫпјҢдҪҶе…¶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жҲ–еҸҜйҖҡиҝҮе°ҸиҜҙж–Үжң¬еҠ д»ҘжҸЈжө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д»ҺдҪңиҖ…зҡ„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е…ҘжүӢпјҢжҢ–жҺҳдҪңиҖ…дёәе°ҸиҜҙеёҰжқҘзҡ„зӢ¬зү№жҖқжғід»·еҖјгҖӮд»ҺжҖ»дҪ“дёҠзңӢпјҢеәҸи·ӢеҜ№д»ҘдёӢдёүз§ҚеҲӣдҪңзӣ®зҡ„е°ӨдёәйҮҚи§ҶпјҢ并иҝӣиЎҢдәҶдё“й—Ёејәи°ғгҖӮпјҲдёҖпјүејәи°ғдҪңиҖ…дёәдәҶз«ӢиЁҖеһӮеҗҺеҲӣдҪңе°ҸиҜҙвҖңз«ӢиЁҖвҖқдёҖиҜҙжәҗеҮәгҖҠе·Ұдј гҖӢпјҡвҖңвҖҳеӨ§дёҠжңүз«Ӣеҫ·пјҢе…¶ж¬Ўжңүз«ӢеҠҹпјҢе…¶ж¬Ўжңүз«ӢиЁҖгҖӮвҖҷиҷҪд№…дёҚеәҹпјҢжӯӨд№Ӣи°“дёҚжңҪгҖӮвҖқ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и®ӨдёәпјҢеңЁиҝҷдёүиҖ…дёӯпјҢз«ӢиЁҖжҜ”з«ӢеҠҹгҖҒз«Ӣеҫ·жӣҙеҠ йҮҚиҰҒгҖӮз®Әз“ўдё»дәәгҖҠйҮ‘й’ҹдј еәҸгҖӢдә‘вҖңиЁҖдјјеҗҺдәҺеҠҹпјҢиҖҢеҠҹдјјеҗҺдәҺеҫ·зҹЈгҖӮдёҚзҹҘйқһиЁҖж— д»ҘжҲҗе…¶еҠҹпјҢйқһеҠҹж— д»ҘжҲҗе…¶еҫ·д№ҹвҖқпјҢж•…иҖҢвҖңж¬Іи§Ӯеҫ·дёҺеҠҹиҖ…пјҢеҝ…д»Ҙи§ӮиЁҖе§ӢвҖқгҖӮгҖҠиҜ„еҲ»ж°ҙжө’еҗҺдј еҸҷгҖӢдәҰдә‘вҖңз«ӢиЁҖиҖ…пјҢиҜҡдёәйҮҚеӨ§д№ӢжүҖеҜ„пјҢйқһд»…ж–Үеӯ—д№Ӣй•ҝвҖқпјҢ并称гҖҠж°ҙжө’еҗҺдј гҖӢвҖңдҪңиҖ…з«ӢиЁҖд№Ӣжң¬и¶ЈпјҢеә¶еҮ д№ҺжңүеҪ“дәҺеңЈиҙӨеҪ°еә еҠқжғ©д№ӢиЁҖд№ҹеӨ«вҖқгҖӮиҝҷйҮҢи®Өдёәз«ӢиЁҖд№ғж–Үдәәд№ӢдәӢпјҢеҸҜдёҺеңЈиҙӨд№Ӣз«Ӣеҫ·гҖҒиӢұйӣ„д№Ӣз«ӢеҠҹ并дёҫдёәдёү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ҫ·гҖҒеҠҹйңҖиҰҒз”ұиЁҖжқҘи®°еҪ•ж–№иғҪдёәдәәжүҖзҹҘпјҢдё”еҫ·гҖҒеҠҹд»…жғ жіҪдёҖж—¶пјҢдёҚеҸҠиЁҖеҸҜж•°зҷҫдё–дёҚзҒӯпјҢжһҒиЁҖз«ӢиЁҖ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дёҚе°‘еәҸи·ӢжҸҗеҮәпјҢе°ҸиҜҙзҡ„еҲӣдҪңд№ғжҳҜз«ӢиЁҖд№ӢдҪңпјҢи‘—д№Ұз«ӢиҜҙжҳҜдёәдәҶжҲҗдёҖ家д№ӢиЁҖгҖӮеҰӮеҗҙи¶јдәәиҮӘз§°еҲӣдҪңгҖҠиҝ‘еҚҒе№ҙд№ӢжҖӘзҺ°зҠ¶гҖӢд№ғвҖңз«ӢиЁҖд»ҘиҮӘиЎЁвҖқпјӣйҷҲжң—иҮӘз§°еҲӣдҪңгҖҠйӣӘжңҲжў…дј гҖӢд№ғеӣ вҖңеҝөз«ӢиЁҖеұ…дёҚжңҪд№ӢдёҖвҖқпјҢж•…иҖҢдёҚж„ҝвҖңеҷӨдёҚеҸ‘дёҖиҜӯвҖқгҖӮиҖҢжҲҗдёҖ家д№ӢиЁҖзҡ„зӣ®зҡ„еңЁдәҺжөҒдј еҗҺдё–пјҢз®Җеәөеұ…еЈ«гҖҠй’ҹжғ…дёҪйӣҶеәҸгҖӢеҚіиЁҖпјҡвҖңеӨ§дёҲеӨ«з”ҹдәҺдё–д№ҹпјҢиҫҫеҲҷжҠҪйҮ‘еҢ®зҹіе®Өд№Ӣд№ҰпјҢеӨ§д№Ұзү№д№ҰпјҢд»ҘеӨҮдёҖд»Јд№Ӣе®һеҪ•пјӣжңӘиҫҫеҲҷжі„жҖқйЈҺжңҲж№–жө·д№Ӣж°”пјҢй•ҝе’Ҹзҹӯе’ҸпјҢд»ҘеҶҷдёҖж—¶д№Ӣжғ…зҠ¶гҖӮжҳҜиҷҪжңүеӨ§е°Ҹд№Ӣж®ҠпјҢе…¶жүҖд»ҘеһӮеҗҺд№Ӣж·ұж„ҸеҲҷдёҖиҖҢе·ІгҖӮвҖқ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еёёеј•з”Ёеә„еӯҗзҡ„вҖңйҒ“еңЁеұҺжәәвҖқиҜҙжқҘдёәе°ҸиҜҙз«ӢиЁҖжҸҗдҫӣеҸҜиғҪгҖӮйҷҲе…ғд№ӢгҖҠе…ЁзӣёиҘҝжёёи®°еәҸгҖӢз§°пјҡвҖңеӨӘеҸІе…¬жӣ°пјҡвҖҳеӨ©йҒ“жҒўжҒўпјҢеІӮдёҚеӨ§е“үпјҒи°ӯиЁҖеҫ®дёӯпјҢдәҰеҸҜд»Ҙи§Јзә·гҖӮвҖҷеә„еӯҗжӣ°пјҡвҖҳйҒ“еңЁеұҺжәәгҖӮвҖҷе–„д№Һз«ӢиЁҖпјҒжҳҜж•…вҖҳйҒ“жҒ¶д№ҺеҫҖиҖҢдёҚеӯҳпјҢиЁҖжҒ¶д№ҺеӯҳиҖҢдёҚеҸҜвҖҷгҖӮвҖқдҝһжЁҫгҖҠе°ҒзҘһиҜ и§ЈеәҸгҖӢдәҰз§°пјҡвҖңеӨ«йҒ“ж— жүҖдёҚеңЁд№ҹгҖӮеә„еӯҗдёҚдә‘д№ҺпјҹйҒ“еңЁиқјиҡҒпјҢеңЁзЁҺзЁ—пјҢеңЁз“Ұз’§пјҢеңЁеұҺжәәгҖӮеӨ«иҮіеұҺжәәзҠ№еҸҜд»Ҙи§ҒйҒ“пјҢеҶөжӯӨжҙӢжҙӢж•°еҚҒдёҮиЁҖд№Ӣж–Үеӯ—д№ҺгҖӮвҖқ他们ејәи°ғ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жңҖдҪҺиҙұгҖҒжңҖз»Ҷеҫ®зҡ„дәӢзү©дёӯд№ҹжңүйҒ“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жүҖд»ҘдҪңдёәвҖңй„ҷиҜҙвҖқзҡ„е°ҸиҜҙдәҰеҸҜи°ҲйҒ“пјҢдёҚвҖңеҝ…д»Ҙеә„йӣ…д№ӢиЁҖжұӮд№Ӣ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жө…зҷҪдҝҡдҝ—гҖҒиә«дёәе°ҸйҒ“жң«жөҒзҡ„е°ҸиҜҙпјҢд№ҹеҸҜдёҺз»ҸеҸІеӯҗйӣҶдёҖж ·пјҢжҲҗдёәз«ӢиЁҖд№Ӣд№ҰпјҢжүҝиҪҪдҪңиҖ…ж¬Ідј д№ӢеҗҺдё–зҡ„вҖңдёҖ家д№ӢиЁҖвҖқгҖӮпјҲдәҢпјүејәи°ғдҪңиҖ…еӣ еҸ‘ж„Өи‘—д№ҰеҲӣдҪңе°ҸиҜҙвҖңеҸ‘ж„Өи‘—д№ҰвҖқиҜҙпјҢжәҗиҮӘеӯ”еӯҗзҡ„вҖңиҜ—еҸҜд»ҘжҖЁвҖқдёҺеҸёй©¬иҝҒзҡ„вҖңеҸ‘ж„Өд№ӢжүҖдҪңвҖқпјҢиҙҜз©ҝеҸӨд»ЈеҸІд№ҳдёҺиҜ—ж–Үзҡ„еҲӣдҪңе’ҢиҜ„и®ә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зҫҺеӯҰе‘ҪйўҳгҖӮеңЁ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дёҺе°ҸиҜҙжү№иҜ„йҖҗжёҗе…ҙиө·д№ӢеҗҺпјҢе°ҸиҜҙ家е’Ңе°ҸиҜҙзҗҶи®ә家们е°ҶиҝҷдёҖе‘Ҫйўҳеј•е…Ҙе°ҸиҜҙд№ӢдёӯпјҢжҸҗеҮәе°ҸиҜҙеҗҢж ·иғҪеӨҹеҸ‘ж„ӨжҠ’жғ…гҖҒеҸ‘ж„ӨиЎЁеҝ—гҖӮдёҖдәӣ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еҖҹиҮӘеәҸйҳҗжҳҺиҮӘе·ұзҡ„еҲӣдҪңзӣ®зҡ„пјҢеҰӮзҺӢйҹ¬з§°е…¶еҲӣдҪңгҖҠж·һйҡҗжј«еҪ•гҖӢд№ғеӣ вҖңиҜҡеЈ№е“Җз—ӣжҶ”жӮҙе©үз¬ғиҠ¬иҠіжӮұжҒ»д№ӢжҖҖпјҢдёҖеҜ“д№ӢдәҺд№ҰиҖҢе·ІвҖқпјҢеҗҙз’ҝеҲ и®ўгҖҠйЈһйҫҷе…Ёдј гҖӢд№ғеӣ вҖңеҝҶеҫҖж— иҒҠпјҢдёҚзҰҒзһҝ然жңүж„ҹгҖӮд»Ҙдёәж—ўдёҚеҫ—йҒӮе…¶еҲқеҝғпјҢеҲҷ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пјҢдәҰеҸҜд»ҘеҜ„йғҒз»“д№ӢжҖқвҖқзӯүпјҢйҷҲиҝ°е…¶з”ҹе№ізҡ„дёҚеҫ—еҝ—д№ӢеӨ„пјҢиЎЁжҳҺе…¶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жҳҜдёәдәҶеҜ„жғ…йҖӮеҝ—гҖӮеҸҰжңү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еҜ№дҪңиҖ…зҡ„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еҠ д»ҘжҸЈжөӢпјҢи®Өдёәе…¶еҲӣдҪңеҺҹеӣ жҳҜдёҚе№іеҲҷйёЈгҖӮеҰӮи’ӢзҶҠжҳҢгҖҠе®ўзӘ—еҒ¶з¬”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ҫ—жҜӢеӣ жҖҖжҠұеҲ©еҷЁпјҢе°ҡжңӘйҖўж—¶пјҢеҒ¶жүҳжӯӨд»ҘеҶҷиғёиҮҶиҖ¶гҖӮвҖқдёңеұұдё»дәәгҖҠдә‘еҗҲеҘҮиёӘ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–Үй•ҝжҠұеҘҮжүҚпјҢйғҒйғҒдёҚеҫ—еҝ—вҖҰвҖҰе…¶жёёжҲҸдәҺж–ҮиҖ¶гҖӮвҖқ他们и®ӨдёәпјҢдҪңиҖ…д№ӢжүҖд»ҘеҖҹе°ҸиҜҙд№Ұж„ӨпјҢжҳҜеӣ дёәвҖңж–ҮдәәеӨҡдҫҳеӮәпјҢеқ—еһ’иғёдёӯжЁӘвҖқпјҢе…¶жӮұжҒ»зј з»өд№ӢйҡҗгҖҒеҝ§ж„ӨйғҒз»“д№Ӣз§Ғж— жүҖе®Јжі„пјҢеҝ…ж¬ІдёҖеҗҗдёәеҝ«пјҢе°ҸиҜҙеҲҷдёә他们жҸҗдҫӣдәҶиүҜеҘҪзҡ„жғ…ж„ҹиЎЁиҫҫжё йҒ“пјҢиҝҷе°ұе……еҲҶиӮҜе®ҡдәҶе°ҸиҜҙеңЁж»Ўи¶ідҪңиҖ…зІҫзҘһйңҖжұӮж–№йқўзҡ„еӯҳеңЁд»·еҖј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Ҹ‘ж„Өи‘—д№ҰиҝҷдёҖ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иҝҳдёәе°ҸиҜҙиөӢдәҲејәеӨ§зҡ„ж„ҹжҹ“еҠӣпјҢжқҺиҙҪеңЁгҖҠиҜ»гҖҲеҝ д№үж°ҙжө’е…Ёдј гҖүеәҸгҖӢдёӯжҸҗйҒ“пјҡвҖңеҸӨд№ӢеңЈиҙӨпјҢдёҚж„ӨеҲҷдёҚдҪңзҹЈгҖӮдёҚж„ӨиҖҢдҪңпјҢиӯ¬еҰӮдёҚеҜ’иҖҢйўӨпјҢдёҚз—…иҖҢе‘»еҗҹд№ҹпјҢеҸҜиҖ»еӯ°з”ҡз„үпјҹиҷҪдҪңдҪ•и§Ӯд№ҺпјҒвҖқд»–е°Ҷжғ…ж„ҹи§Ҷдёәж–ҮдәәеҲӣдҪңзҡ„жәҗеҠЁеҠӣпјҢи®ӨдёәеҸ‘ж„Өд№ӢдҪңж–№еҸҜеҠЁдәә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ңЁеәҸи·Ӣзҡ„и®әиҝ°дёӯпјҢ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д№Ұж„Өеӣ зҙ дёҚд»…еҸҜд»Ҙеё®еҠ©дҪңиҖ…е®һзҺ°жғ…ж„ҹе®Јжі„пјҢиҝҳеҸҜд»ҘдҪҝиҜ»иҖ…дә§з”ҹеҗҢж„ҹдёҺе…ұжғ…пјҢеӣ иҖҢе…·жңүиҫғй«ҳзҡ„жғ…ж„ҹд»·еҖје’ҢзҫҺеӯҰд»·еҖјгҖӮпјҲдёүпјүејәи°ғдҪңиҖ…еӣ жҖҖжңүж•‘дё–е©ҶеҝғеҲӣдҪңе°ҸиҜҙвҖңе©ҶеҝғвҖқдёҖиҜҚжәҗеҮәдҪӣж•ҷпјҢдёәвҖңиҖҒе©ҶеҝғвҖқд№Ӣз•ҘпјҢжҢҮж…ҲжӮІеҝғиӮ гҖӮгҖҠжҷҜеҫ·дј зҒҜеҪ•гҖӢжүҖиҪҪд№үзҺ„зҰ…еёҲвҖңеҸӘдёәиҖҒе©ҶеҝғеҲҮвҖқдёҺйҒ“еҢЎзҰ…еёҲвҖңйҒ®дёӘжҳҜиҖҒе©ҶеҝғвҖқзҡҶдёәжӯӨж„ҸгҖӮеәҸи·Ӣдёӯж—¶еёё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жҖҖжңүе©ҶеҝғпјҢжЎғиҠұеәөдё»дәәгҖҠйҶүиҸ©жҸҗ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•…жҠұеәҰдё–е©ҶеҝғиҖ…пјҢжҲ–жүҳд№Ӣз–Ҝз—ҙпјҢеә¶жңүд»ҘжғҠе…¶иҒӢиҒ©иҖҢиҪ¬е…¶ж„ҡи’ҷпјҢзӨәд»ҘеҘҮжҖӘиҖҢеҸ‘дәәж·ұзңҒгҖӮвҖқе…¶дёӯвҖңеәҰдё–е©ҶеҝғвҖқ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ж—ўжҢҮеңЁжһҒж„ҸдҪҜзӢӮдёӯжҷ®еәҰдј—з”ҹзҡ„жөҺйў зҰ…еёҲпјҢд№ҹжҢҮи®°еҪ•дәҶжөҺе…¬жҙ»жіјзҰ…еҝғзҡ„гҖҠжөҺйў еӨ§еёҲйҶүиҸ©жҸҗе…Ёдј гҖӢжң¬иә«гҖӮи§ӮйүҙжҲ‘ж–ӢгҖҠе„ҝеҘіиӢұйӣ„дј еәҸгҖӢдә‘вҖңиҮӘйқһиӢҰеҸЈпјҢеҸҜиғҪе”ӨйҶ’з—ҙдәәпјӣдёҚжңүе©ҶеҝғпјҢдҪ•д»Ҙз»ҙжҢҒеҗҚж•ҷвҖқпјҢз§°дҪңиҖ…зҡ„иӢҰеҸЈе©Ҷеҝғд№ғеҢ–дҝ—еҜјж„ҡгҖҒз»ҙжҢҒеҗҚж•ҷд№ӢдёҫгҖӮеәҸи·ӢдёӯеҸҰжңүе…¶д»–зұ»дјјиҜҚжұҮз”Ёд»ҘйҳҗжҳҺдҪңиҖ…жӯӨз§ҚеҲӣдҪңзӣ®зҡ„пјҢеҰӮзғҹйңһж•ЈдәәгҖҠж–©й¬јдј иҮӘеәҸгҖӢиҮӘз§°вҖңжҳҜдёҖеүҜеӨ§ж…ҲжӮІеҝғиЎҢж…ҲжӮІдәӢвҖқпјҢеҸҜвҖңдҪҝдәәзҹҘжүҖз•ҸиҖҢдёәе–„вҖқпјӣйҡәеёӮйҒ“дәәгҖҠйҶ’йЈҺжөҒгҖӢиҮӘеәҸз§°зј–ж¬ЎиҜҘе°ҸиҜҙжҳҜеӣ дёәвҖңеӨ©дёӢд№Ӣдәәе“ҒпјҢжң¬д№ҺеҝғжңҜпјҢеҝғжңҜдёҚиғҪиҮӘжӯЈпјҢеҖҹд№Ұд»ҘжӯЈд№ӢвҖқпјҢж•…иҖҢвҖңдҪңиҖ…д№ӢеҲқеҝғпјҢдәҰиүҜиӢҰзҹЈпјҢе–„зҹЈвҖқзӯүгҖӮвҖңе©ҶеҝғвҖқвҖңж…ҲжӮІеҝғвҖқвҖңиүҜиӢҰеҝғвҖқзӯүз§°и°“пјҢе…¶еҶ…ж¶өзұ»дјјпјҢеқҮжҢҮдҪңиҖ…д»Ҙж„ҹеҢ–дё–дәәдёәеҲӣдҪңзӣ®зҡ„пјҢе…¶е°ҸиҜҙеҶҷдҪңд№ғеҮәдәҺеҠқдё–д№Ӣе–„еҝғ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әҸи·ӢиҝӣдёҖжӯҘжҸҗеҮәе°ҸиҜҙжңүиЎҘдәҺдё–пјҢиөӢдәҲе…¶ејәеӨ§зҡ„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гҖӮеҰӮиҜ„гҖҠеүӘзҒҜдҪҷиҜқгҖӢвҖңжңүиЈЁдәҺж—¶вҖқвҖңжңӘеҝ…ж— иЎҘдәҺдё–вҖқпјҢгҖҠз”ҹз»ЎеүӘгҖӢиҮӘз§°вҖңжңүеҠҹдәҺдё–вҖқпјҢз§°гҖҠйҶ’дё–жҒ’иЁҖгҖӢвҖңжңЁй“ҺйҶ’дё–вҖқгҖҒгҖҠеӣӣжёёеҗҲдј гҖӢвҖңи°Ҷи°Ҷи§үдё–вҖқгҖҒгҖҠеҪӯе…¬жЎҲгҖӢдёәвҖңж•‘дё–д№Ӣд№ҰвҖқгҖҒгҖҠиҜҙе”җе…Ёдј гҖӢдёәвҖңиЈЁдё–д№ӢиүҜд№ҰвҖқгҖҒгҖҠж— еЈ°жҲҸгҖӢвҖңз»ҙжҢҒ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вҖқгҖҒгҖҠиҜҙе‘је…Ёдј гҖӢвҖңдёҚж— иЈЁдәҺдё–ж•ҷвҖқгҖҒгҖҠиҜ„жј”жөҺе…¬дј гҖӢвҖңеҹ№жӨҚдё–йҒ“вҖқгҖҒгҖҠйҮ‘иҺІд»ҷеҸІгҖӢдёәвҖңжёЎдё–д№Ӣж…ҲиҲӘвҖқпјҢеҮЎжӯӨз§Қз§Қпј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гҖӮиҝҷж ·з”ұдҪңиҖ…е©ҶеҝғйҖ е°ұзҡ„жңүиЎҘдәҺдё–пјҢе°ұдёҚд»…д»…жӯўдәҺ继жүҝеҸ‘жү¬з»ҸеҸІзҡ„еҠқе–„жғ©жҒ¶дј з»ҹпјҢиҖҢжҳҜзӣҙжҺҘдёҠеҚҮеҲ°дәҶдҪңиҖ…жҖҖзқҖдёҖзүҮж…ҲжӮІеҝғиӮ пјҢеёҢжңӣд»Ҙе°ҸиҜҙйҶ’дё–гҖҒж•‘дё–зҡ„й«ҳеәҰгҖӮзұ»дјјзҡ„зӨҫдјҡж„ҸиҜҶиҝҳ被延з»ӯиҮіеҮәзүҲиҖ…иә«дёҠпјҢгҖҠз»ӯж°ёеәҶеҚҮе№іеҸҷгҖӢз§°пјҢеӣ гҖҠж°ёеәҶеҚҮе№ігҖӢдёәж•‘дё–д№Ӣд№ҰпјҢдёә继жүҝе…¶ж•ҷеҢ–еҠҹиғҪпјҢвҖңд»Ҡжң¬е ӮдёҚжғңйҮҚиө„пјҢиҙӯи§…иҪҪзәӘпјҢйҮҮи®ҝйҒ—еҸІпјҢеҖ©дәәз»ӯжј”е…¶д№ҰвҖқгҖӮдёңзҜұеұұдәәгҖҠйҮҚеҲ»иҚЎеҜҮеҝ—еҸҷгҖӢдәҰз§°пјҢеӣ гҖҠиҚЎеҜҮеҝ—гҖӢвҖңжңүе…і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вҖқпјҢеә”еҪ“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пјҢж•…иҖҢвҖңзҲ°ж Ўе…¶иҲӣи®№пјҢйҮҚд»ҳеүһеҠӮпјҢе®ӣжҲҗиў–зҸҚпјҢдҝҫиЎҢиҖ…жҳ“зәіе·ҫз®ұпјҢеұ…дәҰдҫҝдәҺжЈҖйҳ…пјҢжөҒдј йҒҚи§ҲвҖқ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йҮҚйҮ‘иҜ·дәәз»ӯеҶҷпјҢиҝҳжҳҜеҲҠеҲ»иў–зҸҚжң¬пјҢе…¶йҰ–иҰҒеҠЁжңәеқҮдёәе•Ҷдёҡзӣ®зҡ„пјҢеҮәзҺ°еңЁеәҸи·Ӣдёӯд№ҹжҳҜдёәдәҶиҺ·еҫ—е№ҝе‘Ҡж•Ҳеә”гҖӮдҪҶеңЁ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笔дёӢпјҢжӯӨз§ҚиЎҢдёәе°ұжҲҗдәҶеҮәзүҲиҖ…ж¬Іе°Ҷж•‘дё–д№Ӣд№Ұдј ж’ӯе№ҝиҝңд»ҘиЈЁзӣҠдё–йҒ“йЈҺдҝ—зҡ„е–„еҝғд№ӢдёҫгҖӮиҝҷдёҖзұ»и®әиҝ°иөӢдәҲе°ҸиҜҙд»Ҙе……еҲҶзҡ„зӨҫдјҡиҙЈд»»ж„ҹпјҢеңЁжҖқжғіж·ұеәҰдёҺзӨҫдјҡд»·еҖјеұӮйқўзӘҒжҳҫдәҶе°ҸиҜҙзҡ„еҠҹж•ҲпјҢеҜ№е°ҸиҜҙең°дҪҚзҡ„жҸҗй«ҳдёҚж— дҪңз”ЁгҖӮ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пјҢж— и®әз«ӢиЁҖгҖҒд№Ұж„ӨиҝҳжҳҜд»Ҙд№ҰйҶ’дё–пјҢдёҠиҝ°еәҸи·ӢжүҖи®Ёи®әзҡ„вҖңе°ҸиҜҙвҖқйғҪдёҚеҶҚжҳҜеҚ•зәҜзҡ„ж•…дәӢйӣҶеҗҲпјҢд№ҹдёҚеҶҚжҳҜвҖңдёӣж®Ӣе°ҸиҜӯвҖқвҖңе°ҸйҒ“жң«жөҒвҖқпјҢиҖҢжӣҙеӨҡең°иў«иөӢдәҲдәҶж–Үз« зҡ„жҰӮеҝөгҖҒд»·еҖје’ҢеҠҹиғҪгҖӮдёәжӯӨпјҢиҝҷдәӣеәҸи·ӢдёҚи°Ҳ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зҡ„еҘҮи¶ЈиҝҪжұӮпјҢйҡҗеҺ»дәҶе°ҸиҜҙеҲҠиЎҢзҡ„е•Ҷдёҡзӣ®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д»ҺдҪңиҖ…зҡ„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еҮәеҸ‘пјҢд»Һз«ӢиЁҖжұӮйҒ“гҖҒеҸ‘ж„Өи‘—д№ҰгҖҒе©Ҷеҝғж•‘дё–зӯүж–№йқўжҢ–жҺҳе°ҸиҜҙзҡ„жҖқжғіж·ұеәҰпјҢж„ҸеңЁжүӯиҪ¬еҺҶд»Јж–Үи®ә家еҜ№е°ҸиҜҙжө…и–„дҝҡдҝ—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еҪ°жҳҫе°ҸиҜҙзҡ„зҗҶи®әд»·еҖјгҖҒжғ…ж„ҹд»·еҖје’ҢзӨҫдјҡд»·еҖј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еңЁи®әеҸҠ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ж—¶пјҢдјҡзқҖж„Ҹејәи°ғдҪңиҖ…дәҺиҜ—ж–ҮзӯүжӯЈйҒ“еқҮеҚҒеҲҶж“…й•ҝпјҢ并дёҚжҳҜеҸӘдјҡеҶҷе°ҸиҜҙгҖӮеҰӮйҳ®е…ғзҡ„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з¬әз–ҸеәҸгҖӢдёӯжҸҗеҲ°йғқжҮҝиЎҢвҖңжүҖи‘—е°ҡжңүгҖҠе°”йӣ…з–ҸгҖӢиҜёд№ҰвҖқпјӣи’Із«ӢжғӘзҡ„гҖҠиҒҠж–Ӣеҝ—ејӮи·ӢгҖӢиҜ„д»·и’Іжқҫйҫ„зҡ„иҜ—ж–ҮдҪңе“ҒдёәвҖңй—ҙдёәиҜ—иөӢжӯҢиЎҢпјҢдёҚ愧дәҺеҸӨдҪңиҖ…пјӣж’°еҸӨж–ҮиҫһпјҢдәҰеҫҖеҫҖж Үж–°йўҶејӮпјҢдёҚеүҝиўӯе…Ҳж°‘вҖқпјӣй’ұеҫҒзҡ„гҖҠйҒҒзӘҹи°°иЁҖи·ӢгҖӢз§°зҺӢйҹ¬вҖңе°ҡжңүгҖҠејўеӣӯж–Ү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иҳ…еҚҺйҰҶиҜ—й’һгҖӢгҖҒгҖҠжҳҘз§Ӣжң”й—°иҖғгҖӢгҖҒгҖҠзҖӣеЈ–жқӮиҜҶгҖӢгҖҒгҖҠз“®зү–дҪҷи°ҲгҖӢзӯүи‘—пјҢдёҡе·Ід»ҳд№ӢжүӢж°‘пјҢе°ҶеҚіеҲҠеҚ°гҖӮд»–ж—ҘжұҮдёәе…ЁйӣҶпјҢдј ж’ӯзҺҜзҖӣпјҢжӯӨдёҚзӢ¬зәёиҙөжҙӣйҳіпјҢжҠ‘е°ҶйёЎжһ—дәүиҙӯзҹЈвҖқпјҢ并称其е°ҸиҜҙгҖҠйҒҒзӘҹи°°иЁҖгҖӢдёәдёҠиҝ°иҜ—ж–ҮйӣҶзҡ„вҖңеҡҶзҹўвҖқгҖӮ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зӣҙжҺҘжҢҮеҮәпјҢдҪңиҖ…зҡ„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д»…д»…жҳҜй—ІжҡҮд№Ӣж—¶зҡ„жёёжҲҸпјҢиҖҢ并йқһжӯЈдәӢгҖӮеҰӮзҺӢиӢұзҡ„гҖҠеүӘзҒҜдҪҷиҜқеәҸгҖӢжҸҗеҲ°вҖңдҝҫдё–д№ӢеЈ«зҡҶзҹҘжҳҢзҘәжүҚиҜҶд№Ӣе№ҝпјҢиҖҢеӢҝ讶其жүҖи‘—д№ӢдёәејӮд№ҹгҖӮжҳҢзҘәжүҖдҪңд№ӢиҜ—иҜҚз”ҡеӨҡпјҢжӯӨзү№е…¶жёёжҲҸиҖівҖқпјҢиЁҖжҳҺжқҺжҳҢзҘәеҶҷе°ҸиҜҙд»…дёәжёёжҲҸпјҢдёҺе…¶иҜ—иҜҚеҲӣдҪңж— жі•зӣёжҜ”гҖӮз®Җеәөеұ…еЈ«зҡ„гҖҠй’ҹжғ…дёҪйӣҶеәҸгҖӢжҸҗеҲ°пјҡвҖңдҪҷеҸӢзҺүеі°з”ҹжҠұйў–ж•Ҹд№Ӣиө„пјҢеҲқй”җеҝ—иҜҚз« д№ӢеӯҰпјҢеҚҡиҖҢжұӮд№ӢпјҢиҜёеӯҗзҷҫ家пјҢиҺ«дёҚ究жһҒпјӣеҸҠжҪңеҝғ科第д№ӢдёҡпјҢзәҰиҖҢдјҡд№ӢпјҢе…ӯз»Ҹеӣӣд№ҰиҺ«дёҚиһҚиҙҜгҖӮдјҹе“үеҚ“и¶Ҡд№ӢйҖҡпјҢиҜҡжңүејӮд№ҺжіӣиҖҢж— иҠӮпјҢжӢҳиҖҢж— зӣёиҖ…гҖӮжҡҮж—ҘжүҖдҪңгҖҠй’ҹжғ…дёҪйӣҶгҖӢд»ҘзӨәдҪҷ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§°зҺүеі°дё»дәәеӯҰиҜҶжёҠеҚҡпјҢе°ҸиҜҙгҖҠй”әжғ…дёҪйӣҶгҖӢд»…дёәвҖңжҡҮж—ҘжүҖдҪңвҖқ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ңЁдёҖдәӣд№җдәҺдёәе°ҸиҜҙеҶҷдҪңеәҸи·Ӣзҡ„ж–ҮдәәзңјдёӯпјҢе°ҸиҜҙдҪңдёәвҖңеӨ§йҒ“жүҖеҝҢвҖқвҖңдёӣж®Ӣе°ҸиҜӯвҖқзҡ„жң«жөҒж–ҮдҪ“зҡ„и§Ӯеҝөдҫқж—§ж №ж·ұи’ӮеӣәпјҢиҝҷжҳҜеӨ§йҮҸе–ңзҲұе°ҸиҜҙзҡ„ж–Үдәәй•ҝд№…д»ҘжқҘйҮҮеҸ–еҗ„з§Қзӯ–з•Ҙд»Ҙжңҹ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ең°дҪҚ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еӣӣгҖҒдҫқжҚ®з»ҸеҸІвҖңеҠқжғ©вҖқи§ӮеҝөиҜ„иҜҙ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зҡ„еҸҜдҝЎеәҰе’ҢиҷҡеӨёжҖ§ жҖ»дҪ“жқҘзңӢпјҢдҪңдёәеҸӨд»Је°ҸиҜҙжү№иҜ„зҡ„дё»иҰҒеҪўејҸд№ӢдёҖпјҢеәҸи·Ӣзҡ„зҗҶи®әжҖ§жҳҜдјҳдәҺиҜ„зӮ№зҡ„гҖӮе…¶еҺҹеӣ еңЁдәҺпјҢиҜ„зӮ№вҖңжҳҜдёҖз§ҚеҚіе…ҙеҸ‘жҢҘпјҢжңүж„ҹиҖҢеҸ‘пјҢйҡҸйҳ…йҡҸжү№пјҢеёҰжңүжһҒеӨ§зҡ„йҡҸж„ҸжҖ§вҖқгҖӮиҜ„зӮ№иҖ…зҪ®иә«дәҺзҜҮз« еӯ—еҸҘд№Ӣй—ҙпјҢеӣ иҖҢе…¶и§ӮзӮ№йҖҡеёёиҫғдёәзҗҗзўҺж„ҹжҖ§пјӣиҖҢеәҸи·Ӣзҡ„дҪңиҖ…з«Ӣи¶іж–Үжң¬д№ӢеӨ–пјҢеҸҜд»Ҙз”Ёз»ји§Ӯе…ЁеұҖзҡ„и§ҶйҮҺдҝҜзһ°жҹҗдёҖе°ҸиҜҙж–Үжң¬д№ғиҮіж•ҙдёӘ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әҸи·ӢеҫҖеҫҖдјҡжіЁж„ҸеҲ°ж–Үжң¬д№ӢеӨ–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ҢеҜ№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дёӯзҡ„жҹҗдёҖж–ҮеӯҰзҺ°иұЎжҲ–еҜ№е°ҸиҜҙиҝҷдёҖдҪ“иЈҒиҝӣиЎҢи§ӮеҜҹпјҢд»ҺиҖҢеұ•ејҖзі»з»ҹжҖ§гҖҒж•ҙдҪ“жҖ§зҡ„и®әиҝ°гҖӮеҰӮз»ҝеӨ©йҰҶдё»дәәгҖҠеҸӨд»Ҡе°ҸиҜҙеҸҷгҖӢдёӯжүҖи®әвҖңе§Ӣд№Һе‘ЁеӯЈпјҢзӣӣдәҺе”җпјҢиҖҢжөёж·«дәҺе®ӢгҖӮйҹ©йқһгҖҒеҲ—еҫЎеҜҮиҜёдәәпјҢе°ҸиҜҙд№ӢзҘ–д№ҹвҖқпјҢиҖғй•ң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д№ӢжәҗжөҒпјӣ笑иҠұдё»дәәгҖҠд»ҠеҸӨеҘҮи§ӮеәҸгҖӢз§°вҖңе°ҸиҜҙиҖ…пјҢжӯЈеҸІд№ӢдҪҷд№ҹгҖӮгҖҠеә„гҖӢгҖҒгҖҠеҲ—гҖӢжүҖиҪҪеҢ–дәәгҖҒдјӣеҒ»дёҲдәәпјҢжҳ”дәӢдёҚеҲ—дәҺеҸІпјӣ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гҖӢгҖҒгҖҠеӣӣе…¬дј гҖӢгҖҒгҖҠеҗҙи¶ҠжҳҘз§ӢгҖӢзҡҶе°ҸиҜҙд№Ӣзұ»д№ҹвҖқпјҢд»ҘжӯӨжқҘи®Ёи®әеҸІзЁ—е…ізі»пјӣи”Ўе…ғж”ҫгҖҠдёңе‘ЁеҲ—еӣҪеҝ—еәҸгҖӢи®ӨдёәвҖңд№Ұд№ӢеҗҚпјҢдәЎиҷ‘ж•°еҚҒзҷҫз§ҚпјҢиҖҢ究其е®һпјҢдёҚиҝҮз»ҸдёҺеҸІдәҢиҖ…иҖҢе·ІгҖӮз»ҸжүҖд»ҘиҪҪйҒ“пјҢеҸІжүҖд»ҘзәӘдәӢиҖ…д№ҹгҖӮе…ӯз»ҸејҖе…¶жәҗпјҢеҗҺдәәиёөеўһз„үгҖӮи®ӯжҲ’и®әи®®иҖғиҫЁд№ӢеұһпјҢзҡҶз»Ҹд№Ӣеұһд№ҹгҖӮйүҙи®°зәӘдј еҸҷеҝ—д№ӢеұһпјҢзҡҶеҸІд№Ӣеұһд№ҹвҖқпјҢд»ҘжӯӨжқҘи®Ёи®әж–ҮдҪ“еұһжҖ§гҖӮиҝҷз§ҚеҜҢжңүйҖ»иҫ‘жҖ§зҡ„гҖҒиҫғдёәж·ұеҲ»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ңЁиҜ„зӮ№дёӯжҳҜе°‘и§Ғзҡ„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әҸи·ӢвҖңеҜ№е°ҸиҜҙиүәжңҜзҡ„зҗҶжҖ§и®ӨиҜҶжӣҙиғҪжҳҫеҮәдҪ“зі»жҖ§е’Ңе®Ңж•ҙжҖ§пјҢжҜ”иө·жӣҙеӨҡзҡ„еёҰжңүж„ҹжҖ§йүҙиөҸжҖ§иҙЁзҡ„е°ҸиҜҙиҜ„зӮ№пјҢзҗҶи®әиүІеҪ©жӣҙжө“пјҢиҝҷжҳҜеәҸи·Ӣзҡ„зІҫй«“жүҖеңЁвҖқгҖӮ然иҖҢпјҢдёҺгҖҠж–ҮиөӢгҖӢгҖҠж–Үеҝғйӣ•йҫҷгҖӢзӯүж–ҮеӯҰзҗҶи®әдё“и®әдёҚеҗҢзҡ„жҳҜпјҢе°ҸиҜҙзҡ„еәҸи·ӢиҝҳжүҝжӢ…зқҖйҮҚиҰҒзҡ„е®Јдј еҠҹиғҪгҖӮ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йңҖиҰҒйҖҡиҝҮж ҮжҰң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еҸҠ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зҡ„д»·еҖјпјҢжҸҗй«ҳе…¶еңЁе°ҸиҜҙйўҶеҹҹ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д№ғиҮі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еңЁж–ҮеӯҰйўҶеҹҹ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её®еҠ©иҜҘе°ҸиҜҙиҺ·еҫ—иөһиӘүжҲ–е®һзҺ°з•…й”Җ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әҸи·ӢеҫҖеҫҖдјҡз§ҜжһҒжҢҮеҮә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зҡ„дјҳеҠҝжүҖеңЁпјҢеҰӮи¶Је‘іжҖ§ејәгҖҒдј ж’ӯеәҰй«ҳзӯүпјӣиҖҢжһҒе°‘жҸҗеҸҠе…¶зҹӯеӨ„пјҢеҚідҫҝжҸҗеҸҠд№ҹйҖҡеёёдјҡйҮҮеҸ–规йҒҝжҖ§зҡ„иҜӯиЁҖзӯ–з•ҘгҖӮжҲ–е°ҶиҜҘзҹӯеӨ„иҝӣиЎҢеҗҲзҗҶеҢ–зҡ„и§ЈйҮҠпјҢжҲ–ејәи°ғй•ҝеӨ„д»ҘжҺ©зӣ–зҹӯеӨ„пјҢеүҚж–ҮжҸҗеҲ°зҡ„вҖңдёҚжӯўж·«жҳҜдёәдәҶеӣ еҠҝеҲ©еҜјвҖқвҖңд№үзҗҶй«ҳж·ұеҸҜжҺ©зӣ–з”ЁиҜӯдҝҡдҝ—вҖқзӯүиҜ„д»·еҚі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иҝҷж ·е°ұеҜјиҮҙ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еңЁ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зҗҶи®әй«ҳеәҰ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йҡҫд»ҘйҒҝе…ҚеӨёеӨ§жҲ–еӨұе®һд№Ӣе«Ң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дёҚе°‘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йғҪз§°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иЁҖиҝ‘ж—ЁиҝңпјҢеҸҜдёҺз»ҸеҸІзӣёеӘІзҫҺпјҢжҲ–иҖ…и®Өдёәе…¶дёҚиҗҪзӘ иҮјгҖҒдјҳдәҺе°ҸиҜҙдёӯе…¬и®Өзҡ„з»Ҹе…ёеҗҚи‘—гҖӮдҪҶдәӢе®һжұӮжҳҜең°иҜҙпјҢе°ҸиҜҙзҡ„ең°дҪҚе§Ӣз»Ҳж— жі•дёҺз»ҸеҸІжҜ”иӮ©пјҢе°ҸиҜҙеҸІдёҠжөҒдј е№ҝиҝңзҡ„з»Ҹе…ёдҪңе“Ғд№ҹ并йқһи§Ұзӣ®зҡҶжҳҜгҖӮйҷӨжӯӨд№ӢеӨ–пјҢжңҖе…ёеһӢзҡ„еҪ“еұһ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дёӯжңүе…івҖңеҠқжғ©вҖқзҡ„и®әиҝ°гҖӮеңЁеҺҶд»Јеҗ„зұ»е°ҸиҜҙзҡ„еәҸи·ӢдёӯпјҢз§°жүҖиҜ„дҪңе“ҒжңүеҠқжғ©д№Ӣж—Ёзҡ„иҝңдёҚжӯўзҷҫзҜҮпјҢиҷҪз”ЁиҜӯдёҚе°ҪзӣёеҗҢпјҢеҰӮвҖңеҜ“иЁҖвҖқвҖңйҶ’дё–вҖқвҖңеҠқе–„жғ©жҒ¶вҖқвҖңйЎәдё–еҢ–дҝ—вҖқвҖңеҜјдәәдәҺжӯЈвҖқзӯүпјҢдҪҶжҖқжғідё»ж—ЁеӨ§еҗҢе°ҸејӮпјҢзҡҶз§°иҜҘе°ҸиҜҙд№ғиҮі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еҸҜд»Ҙе–„жҒ¶жһңжҠҘжғ…иҠӮж„ҹеҢ–дё–дәәпјҢиҝӣиҖҢвҖңиө·иЎ°ж•‘з—…вҖқпјҢжңүзӣҠдәҺдё–йҒ“пјҢжҲҗдёәвҖңж•‘дё–д№Ӣд№ҰвҖқгҖӮиҜҡ然пјҢжңүдәӣе°ҸиҜҙзҡ„дҪңиҖ…гҖҒз»“йӣҶиҖ…жҲ–еҲҠеҲ»иҖ…зЎ®е®һжңүеҖҹе°ҸиҜҙеҠқжғ©ж•‘дё–д№Ӣж„ҸпјҢиҝҷдёҖзұ»еҲӣдҪңж„ҸеӣҫжҲ–еҸҜеңЁе°ҸиҜҙзҡ„е‘ҪеҗҚгҖҒдҪңиҖ…зҡ„иҮӘеәҸе’ҢйҖүжң¬зҡ„йҖүз”Ёж ҮеҮҶзӯүж–№йқўеҫ—еҲ°еҚ°иҜҒгҖӮеҰӮвҖңдёүиЁҖвҖқеҲҶеҲ«йўҳдёәгҖҠе–»дё–еҗҚиЁҖгҖӢгҖҠиӯҰдё–йҖҡиЁҖгҖӢгҖҠйҶ’дё–жҒ’иЁҖгҖӢпјҢеҸҲеҰӮгҖҠеһӢдё–иЁҖгҖӢгҖҠз…§дё–жқҜгҖӢзҡ„е‘ҪеҗҚпјӣзһҝдҪ‘иҮӘеәҸе…¶гҖҠеүӘзҒҜж–°иҜқгҖӢвҖңиҷҪдәҺдё–ж•ҷж°‘еҪқпјҢиҺ«д№ӢжҲ–иЎҘпјҢиҖҢеҠқе–„жғ©жҒ¶пјҢе“Җз©·жӮјеұҲпјҢе…¶дәҰеә¶д№ҺиЁҖиҖ…ж— зҪӘпјҢй—»иҖ…и¶ід»ҘжҲ’д№ӢдёҖд№үвҖқпјӣиғЎж–Үз„•гҖҠ稗家粹编гҖӢзҡ„зӣ®ж¬ЎиҮӘвҖңдјҰзҗҶйғЁвҖқе§ӢгҖҒиҮівҖңжҠҘеә”йғЁвҖқз»ҲгҖӮдҪҶдёҚеҸҜеҗҰи®Өзҡ„жҳҜпјҢеңЁе°ҸиҜҙжҳҜеҗҰзңҹжӯЈдё»еҠЁең°гҖҒжңүж„ҸиҜҶең°еҠқжғ©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дёҠпјҢдёҖдәӣеәҸи·Ӣд»ҚжңүеӨёеӨ§е…¶иҫһд№Ӣе«ҢгҖӮжҜ•з«ҹжңүе°ҸиҜҙдҫҝжңүдәәзү©пјҢжңүдәәзү©дҫҝжҳ“жңүе–„жҒ¶д№ӢеҲҶпјҢжңүе–„жҒ¶д№ӢеҲҶдҫҝеҸҜиғҪдә§з”ҹдёәе–„еҺ»жҒ¶зҡ„жғ…иҠӮпјҢиҝҷ并дёҚдёҖе®ҡжҳҜжңүж„Ҹдёәд№ӢпјҢжӣҙдёҚдёҖе®ҡиғҪдёҠеҚҮеҲ°дҪңиҖ…ж„Ҹеӣҫз”ЁиҜҘе°ҸиҜҙж•‘ж°‘жөҺдё–зҡ„й«ҳеәҰгҖӮиҜёеҰӮз§°зҢҘдәөе°ҸиҜҙгҖҠз»ЈжҰ»йҮҺеҸІгҖӢйҖҡиҝҮе®Јж·«еӣ еҠҝеҲ©еҜјд»ҺиҖҢиҫҫеҲ°жӯўж·«зҡ„зӣ®зҡ„пјҢгҖҠйЈһиҠұиүіжғігҖӢиҷҪдёәйЈҺжңҲйўҳжқҗдҪҶеӣ еҪ’дәҺеҝ еӯқиҠӮд№үжүҖд»ҘвҖңжҳҜд№ҰдёҖеҮәпјҢи°“д№Ӣйҳ…зЁ—е®ҳйҮҺеҸІд№ҹеҸҜпјҢеҚіи°“д№ӢиҜ»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д№ҹдәҰеҸҜвҖқпјҢиҝҷдәӣи®әи°ғзҡ„иҜҙжңҚеҠӣе°ұеҚҒеҲҶжңүйҷҗ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дёҖе‘іеҪ°жҳҫеҠқжғ©гҖҒиҝҪжұӮж•ҷеҢ–пјҢеҸҚиҖҢеҸҜиғҪеҜ№е°ҸиҜҙзҡ„зҫҺж„ҹйҖ жҲҗжҚҹе®іпјҢз”ҡиҮідҪҝе°ҸиҜҙеҸҳеҫ—зЁӢејҸеҢ–гҖҒиҝӮи…җеҢ–гҖӮдәҺе…ҙжұүи®ӨдёәвҖңж•ҷеҢ–жҖқжғі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иҝқиғҢдәҶе°ҸиҜҙеҲӣдҪң规еҫӢвҖқпјҢиҝҷдёҖиҜҙжі•иҷҪ然жңүдәӣз»қеҜ№пјҢдҪҶе°ұе°ҸиҜҙиүәжңҜзү№жҖ§иҖҢиЁҖпјҢжҳҜжңүдёҖе®ҡйҒ“зҗҶзҡ„гҖӮжҜ•з«ҹе°ҸиҜҙжңүе…¶зӢ¬зү№зҡ„ж–ҮдҪ“зү№еҫҒдёҺиүәжңҜиҝҪжұӮпјҢиӢҘеӣ еҠӣжұӮеҠқжғ©иҖҢеӨұеҺ»е°ҸиҜҙеә”жңүзҡ„еҸҜиҜ»жҖ§е’Ңе®ЎзҫҺд»·еҖјпјҢеҪ»еә•жІҰдёәж•ҷеҢ–зҡ„е·Ҙе…·пјҢйӮЈд№ҲеҚідҫҝе…¶йҶ’дё–ж•‘дё–д№Ӣж—ЁеҚҒеҲҶйІңжҳҺпјҢд№ҹйҡҫд»ҘжҲҗдёәдҪідҪң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з”ЁеҠқжғ©жқҘиҜ„д»·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ејәи°ғ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зҡ„еҙҮй«ҳ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пјҢеҪ°жҳҫе°ҸиҜҙзҡ„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гҖӮйҖҡиҝҮжҢҮеҮә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ҸІеңЁиҝҷдёҖеұӮйқўзҡ„зӣёйҖҡд№ӢеӨ„жқҘж ҮжҰңиҜҘе°ҸиҜҙзҡ„д»·еҖјдёҺдјҳеҠҝпјҢдҪҝиҜҘе°ҸиҜҙеҸҳеҫ—з•…й”ҖгҖҒеҸ—еҲ°йҮҚи§ҶжҲ–е…ҚйҒӯзҰҒжҜҒпјҢиҝӣиҖҢ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д»Өе°ҸиҜҙж‘Ҷи„ұвҖңе°ҸйҒ“жң«жөҒвҖқзҡ„зӘҳеўғгҖӮж»Ӣжһ—иҖҒдәәгҖҠиҜҙе‘је…Ёдј еәҸгҖӢз§°пјҡвҖңе°ҸиҜҙ家еҚғжҖҒдёҮзҠ¶пјҢз«һз§ҖдәүеҘҮпјҢдҪ•жӯўжұ—зүӣе……ж ӢгҖӮ然еҝ…жңүе…іжғ©еҠқжү¶жӨҚзәІеёёиҖ…пјҢж–№еҸҜеҲҠиҖҢиЎҢд№ӢгҖӮвҖқгҖҠйҡӢзӮҖеёқиүіеҸІеҮЎдҫӢгҖӢ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и‘—д№Ұз«ӢиЁҖпјҢж— и®әеӨ§е°ҸпјҢеҝ…жңүе…ідәҺдәәеҝғдё–йҒ“иҖ…дёәиҙөгҖӮвҖқйғ‘й№Өйҫ„гҖҠеўһеӣҫз»ӯе°Ҹдә”д№үдј еә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ҮЎз®Җзј–жүҖеӯҳпјҢж— и®әжӯЈеҸІе°ҸиҜҙпјҢе…¶ж— е…ідәҺ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иҖ…пјҢзҡҶеҪ“д»ҳд№ӢдёҖзӮ¬пјӣе…¶жңүе…ідәҺдё–йҒ“дәәеҝғиҖ…пјҢеҲҷеӨҡеӨҡзӣҠе–„гҖӮвҖқжңүеҠқжғ©д№Ӣж—Ёж–№еҸҜеҲҠиЎҢпјҢж— е…ідәҺеҠқжғ©еҲҷзҡҶеҪ“зҰҒжҜҒпјҢиҝҷзұ»и§ӮзӮ№еӣә然иҝҮдәҺжһҒз«ҜпјҢеҚҙд№ҹеҗҢж—¶иЎЁжҳҺпјҢеҠқжғ©еҸҜиөӢдәҲе°ҸиҜҙд»ҘиҫғеӨ§зҡ„жҖқжғіж·ұеәҰе’Ңиҫғй«ҳзҡ„зӨҫдјҡд»·еҖјиҝҷдёҖи§ӮеҝөпјҢе·ІжҲҗдёәеӨҡж•°е°ҸиҜҙдҪңиҖ…е’Ң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зҡ„е…ұиҜҶгҖӮиҝҷж ·дёҖжқҘпјҢд№ҹе°ұж— жҖӘд№ҺеӨ§йҮҸеәҸи·Ӣж ҮжҰңеҠқжғ©пјҢз§°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еҸҜд»ҘйҶ’дё–гҖҒж•‘дё–гҖӮз»“ иҜӯ жҰӮиҖҢиЁҖд№ӢпјҢеҸӨд»Је°ҸиҜҙзҡ„еәҸи·ӢеёёйҖҡиҝҮдёҺз»ҸеҸІжҲ–е…¶д»–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зҡ„жҜ”иҫғеҸҠеҜ№дҪңиҖ…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зҡ„ејәи°ғжқҘж ҮжҰң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д№ғиҮіж•ҙдёӘе°ҸиҜҙж–ҮдҪ“зҡ„д»·еҖјгҖӮд»Ҙз»ҸеҸІдёәеҸӮз…§пјҢеҗ„зұ»е°ҸиҜҙеәҸи·ӢжҲ–йҖҡиҝҮзұ»жҜ”жҢҮеҮәе°ҸиҜҙзҫҪзҝјз»ҸеҸІзҡ„жӯЈз»ҹжҖ§пјҢжҲ–йҖҡиҝҮеҜ№жҜ”зӘҒжҳҫе°ҸиҜҙиЈЁиЎҘз»ҸеҸІзҡ„дјҳи¶ҠжҖ§гҖӮдёҺе…¶д»–е°ҸиҜҙдҪңе“ҒзӣёжҜ”пјҢеәҸи·ӢжҲ–е°Ҷе…¶жүҖиҜ„е°ҸиҜҙдёҺз»Ҹе…ёе°ҸиҜҙжҜ”иӮ©пјҢжҢҮеҮәе…¶дёҺеҗҚи‘—зӣёеҗҢзҡ„зү№иҙЁпјӣжҲ–ејәи°ғе…¶дјҳзӮ№пјҢдҪҝе…¶дёҺдҪҺдҝ—д№Ҹе‘ізҡ„е°ҸиҜҙеҲ’жё…з•ҢйҷҗгҖӮеңЁеҲӣдҪңеҠЁжңәеұӮйқўпјҢеәҸи·ӢжҲ–з§°е°ҸиҜҙд№ғз«ӢиЁҖд№ӢдҪңпјҢжҲ–з§°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дёәеҸ‘ж„Өи‘—д№ҰпјҢжҲ–з§°е°ҸиҜҙжҳҜдҪңиҖ…жҖҖзқҖеҠқе–„е©ҶеҝғеҶҷдёӢзҡ„жөҺдё–ж–Үз« гҖӮеңЁеәҸи·ӢдҪңиҖ…зҡ„笔дёӢпјҢе°ҸиҜҙж—ўејҳжү¬йҒ“д№үгҖҒйҒөеҫӘжӯЈз»ҹпјҢеҸҲеҢ еҝғзӢ¬иҝҗгҖҒзү№иүІжҳҫи‘—пјӣж—ўеҸҜеҜ“зӣ®жёёеҝғгҖҒеЁұд№җеӨ§дј—пјҢеҸҲеҸҜиЈЁзӣҠйЈҺж•ҷгҖҒжңүиЎҘдәҺдё–гҖӮдҪҶеҸ—е…¶еҠҹиғҪжүҖйҷҗпјҢеәҸи·Ӣж— жі•еҒҡеҲ°е®Ңе…Ёзңҹе®һе®ўи§ӮпјҢйғЁеҲҶеәҸи·ӢиҝҳдјҡжңүеӨёеј жҲ–еӨұе®һзҡ„жҲҗеҲҶпјҢеӣ иҖҢдёҚеҸҜе…ЁзӣҳйҮҮдҝЎпјҢдҪҶеәҸи·ӢеҜ№е°ҸиҜҙе°Өе…¶жҳҜйҖҡдҝ—е°ҸиҜҙзҡ„иҜёеӨҡи®Ёи®әе’ҢиҜ„д»·пјҢеҜ№ж ҮжҰңе°ҸиҜҙд»·еҖјгҖҒжҸҗй«ҳе°ҸиҜҙең°дҪҚе…·жңү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йҮҮи–Ү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2жңҹвҖңж–ҮеӯҰдёҺиүәжңҜз ”з©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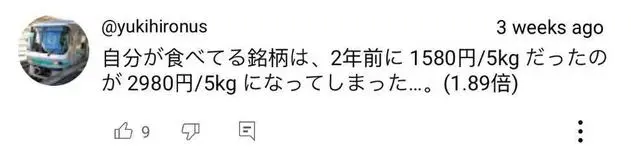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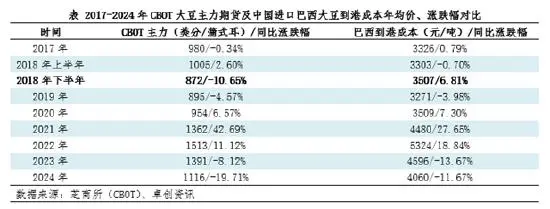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