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еҲҳе®—зҒөпјҢз”·пјҢз”өеӯҗ科жҠҖеӨ§еӯҰ马е…ӢжҖқдё»д№үеӯҰйҷўеүҜйҷўй•ҝпјҢж•ҷжҺҲгҖҒеҚҡеЈ«з”ҹеҜјеёҲпјҢеӣӣе·қзңҒ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вҖңзҷҫдәә专家еә“вҖқжҲҗе‘ҳгҖӮйғ‘зҘҘж–ҮпјҢз”·пјҢдёӯе…ұжіёе·һеёӮйҫҷ马жҪӯеҢә委е…ҡж Ўе№ІйғЁгҖӮ
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жҳҜзәўеҶӣе’ҢиӢҸеҢәе»әи®ҫзҡ„йҮҚиҰҒеҶ…е®№пјҢжҳҜз»ҙзі»йқ©е‘ҪеҶӣйҳҹжҲҳж–—еҠӣе’Ң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жқғжңүеәҸиҝҗиҪ¬зҡ„е…ій”®дёҖзҺҜгҖӮвҖңе……е®һзәўеҶӣзҡ„з»ҷе…»дёҺдҫӣз»ҷпјҢз»„з»ҮиҒ”з»ңеүҚзәҝдёҺеҗҺж–№зҡ„еҶӣдәӢиҝҗиҫ“пјҢз»„з»ҮеҶӣдәӢзҡ„еҚ«з”ҹжІ»з–—пјҢеҗҢжҳҜеҜ№йқ©е‘ҪжҲҳдәүжңүеҶіе®ҡж„Ҹд№үзҡ„дәӢдёҡгҖӮвҖқеҹәдәҺжӯӨпјҢеңЁжҝҖзғҲзҡ„йқ©е‘Ҫж–—дәүдёӯпјҢ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йўҶеҜјзҡ„зәўиүІжӯҰиЈ…ж јеӨ–жіЁйҮҚ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әӢдёҡзҡ„е»әи®ҫпјҢйҖҡиҝҮеҗ„з§Қж–№ејҸе…ЁеҠӣеҢ»жІ»жҲҳдәүз»ҷ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еёҰжқҘзҡ„иӮүдҪ“еҲӣдјӨе’Ңең°ж–№иҝһе№ҙжөҒиЎҢзҡ„еҗ„з§Қз–«з—…зҒҫе®ігҖӮиҝ„д»ҠеӯҰз•Ңе·Іе°ұ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еұ•ејҖ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зҺ°жңүи‘—иҝ°е°ұ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гҖҒзҫӨдј—жҲ’зғҹиҝҗеҠЁзӯүеҹәжң¬еҸІе®һиҝӣиЎҢдәҶ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зҡ„жўізҗҶе’ҢжҺўи®ЁпјҢдҪҶеҜ№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»әз«ӢеүҚеҗҺ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еҸҳеҢ–гҖҒжј”иҝӣеҸҠе…¶еӣ°еўғзӯүиҝҗиЎҢе®һжҖҒпјҢжңүеҫ…жӣҙдёәж·ұе…ҘгҖҒеҠЁжҖҒзҡ„жҺўи®ЁдёҺеҲҶжһҗгҖӮжң¬ж–ҮжӢҹеңЁеүҚдәәз ”з©¶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°Ҷ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еӨҚжқӮжҖ§гҖҒеӣ°йҡҫжҖ§еҸҠе…¶еҠЁжҖҒеҸҳеҢ–е°ҪйҮҸдәҲд»ҘеҺҶеҸІең°е‘ҲзҺ°пјҢд»ҘиҖғеҜҹеңҹең°йқ©е‘Ҫж—¶жңҹзәўеҶӣдё»еҠӣйғЁйҳҹеңЁе»әи®ҫ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еҪ“дёӯжүҖйқўдёҙзҡ„еўғеҶөеҸҠе…¶иҝҗдҪңе®һжҖҒгҖӮдёҖгҖҒ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…Ҙе·қеүҚеҗҺ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ўғеҶө 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ңЁиҘҝеҫҒйҖ”дёӯпјҢйқўеҜ№ж•ҢеҶӣзҡ„еӣҙиҝҪе өжҲӘе’Ңй•ҝйҖ”иЎҢеҶӣпјҢеёёеёёйқўдёҙ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еҢ»жІ»е’Ңе®үзҪ®й—®йўҳгҖӮвҖңжҒ¶д»—дёҖеңәжҺҘзқҖдёҖеңәпјҢиҷҪ然жӯјзҒӯдәҶеӨ§йҮҸж•ҢдәәпјҢиҮӘе·ұд№ҹжңүдёҚе°‘дјӨдәЎгҖӮвҖқзәўеҶӣдёӯдјӨз—…е‘ҳж•°йҮҸж—ҘзӣҠеўһеҠ 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вҖңжһЈйҳігҖҒж–°йӣҶдёҖд»—дёӢжқҘвҖқпјҢвҖңеҢ»йҷўйҮҢдјӨе‘ҳеҸҲеўһеҠ дәҶдёҖеӨ§е ҶвҖқгҖӮеңЁдјӨе‘ҳеўһеӨҡ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йғЁйҳҹиҝҳеӯҳеңЁзјәеҢ»е°‘иҚҜзӯүеӣ°еўғпјҢвҖңиҚҜе“ҒгҖҒеҷЁжқҗеҘҮзјәгҖӮйә»иҚҜеҫҲе°‘пјҢжңүж—¶ж №жң¬е°ұжІЎжңүпјҢжӣҙжІЎжңүеҘҪзҡ„еҷЁжў°вҖқгҖӮжҚ®зҺӢе®ҸеқӨеӣһеҝҶпјҢе…¶дҪңжҲҳиҙҹдјӨеҗҺпјҢвҖңеӣ дјӨеҸЈеҸ‘зӮҺвҖқпјҢвҖңйҡҫеҸ—еҫ—дёҚеҫ—дәҶпјҢ马д№ҹжІЎжі•йӘ‘вҖқпјҢеёҲеҢ»еҠЎдё»д»»е‘Ёеҗүе®үвҖңжқҘдәҶпјҢиҜҙжІЎжңүйә»иҚҜпјҢжҲ‘иҜҙжІЎжңүйә»иҚҜд№ҹиҰҒеҸ–вҖқгҖӮз”ұдәҺеҢ»з–—иө„жәҗеҢ®д№ҸпјҢйғЁйҳҹйҮҚдјӨе‘ҳдәәж•°жҝҖеўһгҖӮвҖңиҰҒиҚҜжІЎиҚҜпјҢиҰҒеҢ»зјәеҢ»пјҢиҪ»дјӨжӢ–жҲҗдәҶйҮҚдјӨгҖӮвҖқеңЁиҪ¬жҲҳеҫҒйҖ”дёӯпјҢзәўдәҢеҚҒдә”еҶӣеҶӣй•ҝи”Ўз”ізҶҷдёҚе№ёиә«иҙҹйҮҚдјӨпјҢиҷҪз»ҸиӢҸдә•и§Ӯе…ЁеҠӣжҠўж•‘пјҢдҪҶз»Ҳеӣ дјӨеҠҝиҝҮйҮҚе’ҢеҢ»з–—жқЎд»¶йҷҗеҲ¶иҖҢеЈ®зғҲзүәзүІгҖӮ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І»з–—е’Ңе®үзҪ®жҳҜ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ж’ӨзҰ»й„Ӯиұ«зҡ–иӢҸеҢәеҗҺйқўдёҙзҡ„е…Ёж–°й—®йўҳгҖӮдёӯеӨ®йқ©е‘ҪеҶӣдәӢ委е‘ҳдјҡйҖҡд»Өеҗ„иӢҸеҢәйғЁйҳҹе°Ҫеҝ«е»әз«ӢйҮҺжҲҳеҢ»йҷўпјҢ并е®һиЎҢвҖңеҜ„е…»вҖқж”ҝзӯ–гҖӮвҖңе…ідәҺжІ»з–—дјӨз—…жҲҳеЈ«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йҷӨдәӨз”ұе·Іжңүзҡ„еҗҺж–№еҢ»йҷўеӨ–пјҢеҗ„дҪңжҲҳең°еҹҹжҖ»жҢҮжҢҘйғЁпјҢеә”зӯ№еӨҮжң¬иә«зҡ„йҮҺжҲҳеҢ»йҷўе’Ңеҝ…иҰҒж—¶еҜ„еҢ»ж°‘家зҡ„и®ЎеҲ’гҖӮвҖқеңЁиҝҷдёҖж”ҝзӯ–жҢҮеҜјдёӢпј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йҮҮеҸ–дәҶвҖңеҜ„е…»вҖқзҡ„ж–№ејҸжІҝйҖ”е®үзҪ®дјӨз—…е‘ҳгҖӮжҚ®еҫҗеҗ‘еүҚеӣһеҝҶпјҡвҖңйҮҚдјӨеҸ·иө°дёҚеҠЁпјҢе°ҪйҮҸз”ЁжӢ…жһ¶гҖҒ马еҢ№еёҰиө°пјҢе®һеңЁеёҰдёҚдәҶзҡ„вҖқпјҢвҖңз•ҷеңЁиҖҒзҷҫ姓家йҮҢвҖқгҖӮзәўеҶӣиЎҢиҮійҮҺзӢҗеІӯж—¶пјҢвҖңдјӨе‘ҳж— жі•еёҰиө°пјҢе°ұе®үзҪ®еңЁйҷ„иҝ‘иҖҒзҷҫ姓家йҮҢвҖқгҖӮеҶҚеҰӮпјҢвҖңжҲ‘еҶӣз»Ҹз”ұйҡҸеҺҝд»ҘеҚ—жҙӣйҳіеә—дёҖеёҰең°еҢәпјҢдё”иЎҢдё”жҲҳпјҢеҗ‘иҘҝ移еҠЁгҖӮжІҝйҖ”е®үзҪ®дјӨз—…е…өвҖқгҖӮеңЁжӢҘжңүиҗҪи„ҡд№Ӣең°еҗҺпјҢзәўеҶӣз«ӢеҚізқҖжүӢи§ЈеҶійғЁйҳҹеҶ…йғЁзҡ„дјӨз—…й—®йўҳпјҢвҖңжҲ‘们д№ҹжңүдҪҷеҠӣжіЁж„Ҹжё…жҙҒеҚ«з”ҹпјҢеҜ№дәҺз”ҹеҶ»з–®д»ҘеҸҠдјӨз—…зҡ„е…өеЈ«з§ҜжһҒеҢ»з–—пјҢйўҮе…·жҲҗж•ҲвҖқ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д№ҹејҖе§ӢиҮӘдёҠиҖҢдёӢе»әз«ӢеӨҡеұӮж¬Ў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пјҢд»Ҙж»Ўи¶і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зҡ„еҢ»з–—дҝқеҒҘйңҖжұӮгҖӮйҰ–е…ҲпјҢз»„е»әиҘҝеҢ—йқ©е‘ҪеҶӣдәӢ委е‘ҳдјҡжҖ»еҢ»йҷўпјҢжү©е……еҗ„зә§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гҖӮ1932е№ҙ12жңҲеә•пј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жҖ»жҢҮжҢҘйғЁеҶіе®ҡд»Ҙе…Ҙе·қзҡ„иҘҝеҢ—йқ©е‘ҪеҶӣдәӢ委е‘ҳдјҡжҖ»еҢ»йҷўдёәеҹәзЎҖпјҢжҠҪи°ғеӣӣдёӘеёҲеҢ»йҷўзҡ„йғЁеҲҶ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жҲҗз«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гҖӮвҖңжҲ‘们еҘүе‘ҪеңЁйҖҡжұҹеҺҝзҡ„жіҘжәӘеңәпјҢе°ҶжҖ»жҢҮжҢҘйғЁеҢ»йҷўж”№зј–дёәиҘҝеҢ—йқ©е‘ҪеҶӣдәӢ委е‘ҳдјҡжҖ»еҢ»йҷўгҖӮвҖқ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иҝҳе…·иЎҢж”ҝжҖ§иҙЁпјҢиҙҹиҙЈе…Ё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пјҢвҖңзәў4ж–№йқўеҶӣи®ҫеҚ«з”ҹйғЁпјҢжҖ»еҢ»йҷўж—ўжҳҜеҢ»йҷўпјҢеҸҲжҳҜеҚ«з”ҹйғЁжҖ§иҙЁзҡ„еҚ•дҪҚвҖқгҖӮеңЁз»„е»ә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жҖ»еҢ»йҷўиҝҳж №жҚ®жҲҳеңәеҪўеҠҝжҠҪи°ғйғЁеҲҶзІҫе№ІеҠӣйҮҸз»„жҲҗдәҶдёҙж—¶зҡ„йҮҺжҲҳеҢ»йҷўгҖӮжңЁй—Ёдјҡи®®еҗҺпј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з”ұ4дёӘеёҲжү©зј–дёә4дёӘеҶӣпјҢдёәдҪҝеҢ»йҷўе·ҘдҪңйҖӮеә”йғЁйҳҹеҸ‘еұ•зҡ„йңҖиҰҒпјҢжҖ»еҢ»йҷўеҜ№еҗ„йғЁйҳҹеҺҹжңүеҗ„зә§еҢ»з–—жңәжһ„иҝӣиЎҢжү©е……пјҢеҰӮе°ҶеёҲеҢ»йҷўжү©е……дёәеҶӣеҢ»йҷўпјҢе°Ҷеӣўзҡ„еҢ»еҠЎжүҖжү©е……дёәеёҲеҢ»йҷўпјҢеңЁеҶӣйҳҹеҶ…йғЁе»әз«ӢдәҶеӣҠжӢ¬жҖ»еҢ»йҷўгҖҒеҶӣеҸҠеёҲеҢ»йҷўгҖҒеҚ«з”ҹйҳҹпјҲжүҖпјүгҖҒеҚ«з”ҹе®ӨпјҲжүҖпјүгҖҒеҚ«з”ҹе‘ҳеңЁеҶ…зҡ„6зә§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гҖӮжӯӨеҗҺпјҢз”ұдәҺ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з»Ҹеёёжҗ¬иҝҒпјҢдёәж»Ўи¶іеҗ„ең°еҶӣж°‘еҢ»з–—йңҖиҰҒ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иҝҳжҠҪи°ғдәҶйғЁеҲҶ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еңЁиӢҸеҢәзҡ„зҺӢеқӘгҖҒеј е®¶жІҹгҖҒжіҘжәӘеңәгҖҒжё…жұҹжёЎзӯүең°е…ҲеҗҺи®ҫз«ӢдәҶ7дёӘеҲҶйҷўгҖӮе…¶ж¬ЎпјҢе»әз«ӢдёәиӢҸз»ҙеҹғжңәе…іеӣўдҪ“е’Ң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жңҚеҠЎзҡ„еҗ„зә§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жңәжһ„гҖӮзәўеҶӣе…Ҙе·қеүҚпјҢеҸ—ең°зҗҶдҪҚзҪ®гҖҒз»ҸжөҺжқЎд»¶гҖҒж”ҝжІ»з»“жһ„д»ҘеҸҠеҚ«з”ҹж„ҸиҜҶзӯүеҲ¶зәҰпјҢ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еҚ«з”ҹеҒҘеә·зҠ¶еҶөе Әеҝ§гҖӮе·қеҢ—зҫӨдј—вҖңиҜҶеӯ—зҡ„дәәжһҒе°‘пјҢж–ҮзӣІеңЁ90%д»ҘдёҠвҖқгҖӮз”ұдәҺж–ҮеҢ–ж°ҙе№ідҪҺпјҢ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еҜ№еҚ«з”ҹеёёиҜҶзҹҘд№Ӣз”ҡе°‘пјҢвҖңеұ…ж°‘дёҚйҮҚжё…жҙҒпјҢдёҚйҮҚеҚ«з”ҹвҖқгҖӮиҝҷеҜјиҮҙе·қеҢ—еҗ„ең°еӨ©иҠұгҖҒйңҚд№ұгҖҒдјӨеҜ’зӯүзғҲжҖ§е’ҢжҖҘжҖ§дј жҹ“з—…иӮҶиҷҗпјҢжӯ»дәЎзҺҮжһҒй«ҳгҖӮдҫӢеҰӮ1932е№ҙпјҢе·ҙдёӯвҖңдёүжұҮеңәзәҰ800дәәжҹ“ж№ҝзҳҹз—ҮпјҲдёӯеҢ»з—…еҗҚпјүпјҢиҖҢжӯ»дәҺиҜҘз—…иҖ…зәҰ700дәәвҖқгҖӮж¬Ўе№ҙпјҢвҖңејҖеҺҝгҖҒе®ЈжұүгҖҒејҖжұҹзӯүеҺҝзӣӣз–«еӨ§жөҒиЎҢпјҢејҖеҺҝеҸ‘з—…зҺҮиҫҫ70%д»ҘдёҠпјҢиҫҫеҺҝйңҚд№ұжӯ»дәЎз”ҡеӨҡ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зҫӨдј—жӮЈз—…еҗҺж— й’ұе°ұеҢ»пјҢйҘұеҸ—з—…з—ӣжҠҳзЈЁгҖӮ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е·қеҢ—жөҒдј иҝҷж ·дёҖйҰ–ж°‘и°ЈпјҡвҖңз©·еҫ—зӢ—еңЁй”…йҮҢеҚ§пјҢе“ӘйҮҢжңүй’ұеҺ»еҗғиҚҜпјҢжңүз—…е”Ҝж„ҝж—©дәӣжӯ»пјҢе…Қеҫ—жҙ»иө·еҸ—жҠҳзЈЁгҖӮвҖқеӣ иҖҢпјҢйҡҸзқҖ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жү©еӨ§е’Ңе·©еӣәпјҢ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ж•‘жІ»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зҡ„е·ҘдҪңйҮҸж—ҘзӣҠеҠ йҮҚпјҢеҗ„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зҡ„жңҚеҠЎеҜ№иұЎжһҒдёәе№ҝжіӣпјҢвҖңйҷӨжІ»з–—зәўеҶӣдјӨз—…е‘ҳеӨ–пјҢиҝҳдёәе№ҝеӨ§е·ҘеҶңзҫӨдј—жңҚеҠЎвҖқпјҢвҖңйҮҚз—…дёҚиғҪеҲ°еҢ»йҷўй—ЁиҜҠзҡ„пјҢеҢ»з”ҹиҝҳдәІиҮӘеҲ°д»–家еҺ»иҜҠж–ӯвҖқгҖӮ1933е№ҙ8жңҲпјҢйҡҸзқҖ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пјҢдёәиҝӣдёҖжӯҘж»Ўи¶і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зҫӨдј—иҜҠз–—йңҖжұӮпјҢе·қйҷ•зңҒ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е°ҶйҖҡжұҹеҺҝиҙўз»Ҹ委е‘ҳдјҡзҡ„еҢ»еҠЎжүҖе’Ң1дёӘз§ҒиҗҘзҡ„дёӯиҘҝиҚҜе°ҸиҚҜжҲҝеҗҲ并组е»әдёәе·қйҷ•зңҒе·ҘеҶңпјҲжҖ»пјүеҢ»йҷўпјҢз”ұзңҒ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еҶ…еҠЎе§”е‘ҳдјҡзӣҙжҺҘйўҶеҜјгҖӮжӯӨеҗҺпјҢвҖңеҗ„еҺҝзӣёз»§жҲҗз«ӢеҺҝе·ҘеҶңпјҲеҲҶпјүеҢ»йҷўвҖқпјҢвҖңеҢәгҖҒд№ЎеӨ§еңәй•ҮеңЁ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еҶ…ејҖи®ҫе·ҘеҶңиҚҜжҲҝпјҲиҚҜй“әпјүвҖқгҖӮ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е·ҘеҶңиҚҜжҲҝеӨ§йғҪз”ұеҪ“ең°еҺҹжңүзҡ„иҚҜжҲҝж”№е»әиҖҢжқҘгҖӮвҖңеҪ“ж—¶еҳүйҷөгҖҒзәўеқӘгҖҒиөӨеҢ–зӯүеҺҝжүҖиҫ–зҡ„еҢәеңәй•ҮдёҠзҡ„дёӯиҚҜй“әеӨ§йғҪж”№еҗҚдёәвҖҳе·ҘеҶңиҚҜжҲҝвҖҷгҖӮвҖқеҲ°1933е№ҙз§Ӣ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жҲҗж•Ҳжҳҫи‘—пјҢеҲқжӯҘжһ„е»әдәҶе®ҢеӨҮдё”еәһеӨ§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пјҢеҹәжң¬и§ЈеҶідәҶзәўеҶӣе’ҢиӢҸеҢәж°‘дј—зҡ„е°ұеҢ»й—®йўҳ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…ұеҲӣеҠһдәҶ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1жүҖгҖҒеҲҶеҢ»йҷў7жүҖгҖҒеҶӣеҢ»йҷў5жүҖгҖҒеӣўеҢ»еҠЎжүҖ44жүҖпјӣ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1жүҖгҖҒеҲҶеҢ»йҷў6жүҖгҖҒеҺҝе·ҘеҶңеҲҶеҢ»йҷў23жүҖгҖҒе·ҘеҶңиҚҜеә—жҲ–иҚҜй“ә160еӨҡдёӘгҖӮеҗ„еҢ»з–—жңәжһ„收容иғҪеҠӣд№ҹйҡҸд№ӢжҸҗеҚҮ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дёӢиҫ–зҡ„7дёӘеҲҶеҢ»йҷўвҖңе…ұжңүеәҠдҪҚеҮ еҚғеј вҖқгҖӮ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дәҰжңүвҖңз—…еәҠпјҲйҖҡй“әжӢјеҗҲпјү3000дҪҷеј вҖқгҖӮдәҢгҖҒ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зҡ„жқҘжәҗеҸҠеҹ№е…» 然иҖҢпјҢеӣҝдәҺиӢҸеҢәеҶ…йғЁжңүйҷҗзҡ„еҢ»з–—иө„жәҗе’Ңзҙ§еј дёҘй…·зҡ„ж–—дәүзҺҜеўғпјҢ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жңәжһ„е»әз«ӢеҗҺд»Қ然йқўдёҙиҜёеӨҡеӣ°йҡҫгҖӮйҰ–иҰҒзҡ„й—®йўҳдҫҝжҳҜзјәд№Ҹ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пјҢвҖң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зҡ„еҘҮзјәпјҢжҳҜеҪ“ж—¶еҢ»йҷўе»әи®ҫдёӯжңҖзӘҒеҮәзҡ„й—®йўҳ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дәҰеҚҒеҲҶеҢ®д№ҸпјҢвҖңжҳҜжҖ»еҢ»йҷўе·ҘдҪңдёӯзҡ„еҸҲдёҖдёӘзӘҒеҮә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вҖңе°ұиҝһдёҖиҲ¬зҡ„зәўжұһгҖҒзўҳй…’д№ҹжҳҜзЁҖжңүзҡ„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Ң»йҷўзҡ„еҗҺеӢӨзү©иө„дҫӣз»ҷе’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зІҫзҘһжҠҡж…°зӯүе·ҘдҪңд№ҹеӯҳеңЁиҜёеӨҡдёҚи¶ігҖӮ1933е№ҙ8жңҲ13ж—Ҙпј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第дёҖж¬Ўе…ЁеҶӣеҢ»еҠЎдјҡи®®жЈҖжҹҘдәҶиҝҮеҺ»еҢ»еҠЎе·ҘдҪңдёӯзҡ„зјәзӮ№пјҢи®Өдёәе…ЁеҶӣеҢ»еҠЎе·ҘдҪңиҝҳеӯҳеңЁвҖңеҜ№зІ®йЈҹзҡ„еҮҶеӨҮпјҢжІ№зӣҗзҡ„еҮҶеӨҮпјҢжЈүзө®жЈүиў«зҡ„еҮҶеӨҮйқһеёёдёҚеӨҹвҖқпјҢд»ҘеҸҠвҖңеҜ№дјӨз—…еҸ·зҡ„ж•ҷиӮІе’Ңе®үж…°е·ҘдҪңпјҢеҒҡеҫ—йқһеёёдёҚе……еҲҶвҖқзӯүиҜёеӨҡзјәзӮ№гҖӮжӯӨж¬Ўдјҡи®®еҗҺпјҢзәўеҶӣеҗ„еҢ»йҷўзҡ„еҢ»еҠЎе·ҘдҪңйҖҗжӯҘиҝӣе…ҘжӯЈиҪЁ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әӢдёҡжҳҜдёҖйЎ№еҠЁжҖҒдё”еӨҚжқӮ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иҝҷиҰҒжұӮдҪңдёәйқ©е‘ҪиҖ…зҡ„иӢҸеҢәе…ұдә§е…ҡдәәеҸҠе…¶йўҶеҜјдёӢзҡ„еҶӣдәӢеҠӣйҮҸе–„дҪңе–„дёәпјҢдёҚж–ӯйҮҮеҸ–еӨҡз§ҚдёҫжҺӘи§ЈеҶіеңЁж–°иӢҸеҢәйҒҮеҲ°зҡ„ж–°й—®йўҳпјҢеҠӘеҠӣеә”еҜ№ж–°жҢ‘жҲҳпјҢйҖҗжӯҘе…ӢжңҚ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дёҚи¶ігҖҒ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зҹӯзјәгҖҒдјӨе‘ҳз…§жҠӨеҺӢеҠӣеӨ§зӯүеҲ¶зәҰеӣ зҙ пјҢд»ҘзЎ®дҝқ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жңүеәҸејҖеұ•гҖӮеңЁ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йўҶеҜјзҡ„жӯҰиЈ…йқ©е‘ҪиҝӣзЁӢдёӯпјҢе·ҘеҶңзҫӨдј—жҳҜдё»дҪ“пјҢдё»еҠЁжҠ•иә«йқ©е‘Ҫзҡ„еҢ»жҠӨжҠҖжңҜдәәе‘ҳиҫғе°‘пјҢеӣ иҖҢе…ҡе’ҢиӢҸеҢәдёӯеҢ»жҠӨеҸҠеҢ»з–—йўҶеҹҹзҡ„дё“дёҡдәәжүҚжһҒдёәзЁҖзјәгҖӮеҪјж—¶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жқҘжәҗеӨ§иҮҙеҸҜеҲҶдёәд»ҘдёӢдёүеӨ§зұ»гҖӮ第дёҖзұ»дёәйҡҸзәўеҶӣд»Һй„Ӯиұ«зҡ–иӢҸеҢәиҪ¬жҲҳе…Ҙе·қзҡ„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е’ҢеӣҪж°‘е…ҡеҶӣйҳҹдёӯжҠ•йҷҚиҖҢжқҘзҡ„еҢ»е®ҳгҖӮиҝҷзұ»дәәе‘ҳдё»иҰҒжҳҜд»ҘиӢҸдә•и§ӮгҖҒйҡ°з§Ҝеҫ·гҖҒзҺӢеӯҗе…ғгҖҒе‘Ёеҗүе®үгҖҒи’ІиҚЈй’Ұзӯүдәәдёәд»ЈиЎЁзҡ„иҘҝеҢ»пјҢж•°йҮҸиҫғе°‘пјҢдҪҶжһ„жҲҗиҫғдёәеӨҚжқӮпјҢеҢ…жӢ¬еҢ»еӯҰдё“дёҡзҡ„жҜ•дёҡз”ҹгҖҒй„Ӯиұ«зҡ–иӢҸеҢәж—¶жңҹзәўеҶӣеҹ№е…»зҡ„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д»ҘеҸҠд»ҺеӣҪж°‘е…ҡйғЁйҳҹжҠ•йҷҚиҖҢжқҘзҡ„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зӯү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жҲҗз«Ӣд№ӢеҲқпјҢвҖңе…Ёйҷўжңү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30дҪҷдәәвҖқпјҢеҗ„еёҲгҖҒеӣўеҢ»йҷўд№ҹд»…жңү3вҖ”4еҗҚдёӯиҘҝеҢ»е’Ң6вҖ”7еҗҚзңӢжҠӨе‘ҳ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и·ҹйҡҸзәўеҶӣе…Ҙе·қдё”е…·жңүеҢ»еӯҰиғҢжҷҜиҖ…д»…жңүиӢҸдә•и§ӮгҖҒе‘Ёеҗүе®үзӯүеҜҘеҜҘж•°дәәгҖӮй„Ӯиұ«зҡ–иӢҸеҢәеҹ№е…»зҡ„зңӢжҠӨдәәе‘ҳеҲҷжңүзҺӢжҒ©еҺҡгҖҒз§ҰеӯҗзҸҚгҖҒжұӘеҝғж„ҸгҖҒи©№дё–ејјзӯүдәәгҖӮеӣҪж°‘е…ҡеҶӣйҳҹдёӯжҠ•йҷҚиҖҢжқҘзҡ„еҢ»еҠЎжҠҖжңҜдәәе‘ҳпјҢжңүеҗҚ姓еҸҜиҖғиҖ…жңүзҺӢеӯҗе…ғгҖҒи’ІиҚЈй’ҰгҖҒжқЁжҲҗзҰҸгҖҒеҗ‘жЎӮжһ—зӯү10дҪҷдәәпјҢзәҰеҚ иҘҝеҢ»йғЁ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жҖ»ж•°зҡ„дёҖеҚҠгҖӮеҰӮзҺӢеӯҗе…ғжӣҫжҳҜеӣҪж°‘е…ҡе…ӯеҚҒд№қеёҲйҡҸеҶӣеҢ»йҷўзҡ„дёҖеҗҚжҠӨеЈ«й•ҝпјҢеңЁй„Ӯиұ«зҡ–иӢҸеҢәж—¶жңҹвҖңиў«дҝҳеҗҺеҸӮеҠ дәҶзәўеҶӣвҖқгҖӮвҖңи’ІиҚЈй’ҰпјҢжқЁеҢ»е®ҳгҖҒе®ӢеҢ»е®ҳгҖҒй»„еҢ»е®ҳвҖқзӯү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еҲҷжҳҜеңЁ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…Ҙе·қд№ӢеҗҺиў«дҝҳ并еҸӮеҠ зәўеҶӣзҡ„гҖӮеҶҚеҰӮпјҢзәўеҶӣвҖңеңЁжү“иҫҫеҺҝж—¶дҝҳиҷҸзҷҪеҶӣдёӯзҡ„дёҖдёӘжқҺеҢ»з”ҹгҖҒдёҖдёӘжқЁеҢ»з”ҹвҖқгҖӮиҝҷдәӣдәәе‘ҳеӨ§йғҪеҸӮеҠ дәҶзәўеҶӣпјҢдҪҶеҢ»жңҜеҸӮе·®дёҚйҪҗпјҢвҖңйҷӨе°‘ж•°еҮ дёӘдәәиғҪиЎҢжҲӘиӮўгҖҒеү–и…№зӯүжүӢжңҜеӨ–пјҢе…¶дҪҷеҸӘиғҪжІ»дёҖиҲ¬з—…вҖқгҖӮдҪҶеңЁеҢ»з–—иө„жәҗжһҒеәҰеҢ®д№Ҹзҡ„йқ©е‘ҪжҲҳдәүе№ҙд»ЈпјҢиҝҷе·Іе®һеұһйҡҫеҫ—дәҶгҖӮиҘҝеҢ»зҫӨдҪ“жҳҜ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…Ҙе·қеҲқжңҹеҢ»жІ»еӨ–科еҲӣдјӨзҡ„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пјҢ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зәўеҶӣдёӯз»ҸйӘҢдё°еҜҢзҡ„иҘҝеҢ»жһҒе°‘пјҢйҷӨиӢҸдә•и§ӮеӨ–пјҢжңүз»ҸйӘҢзҡ„иҘҝеҢ»еҸӘжңүйҡ°з§Ҝеҫ·гҖҒе‘Ёеҗүе®үпјҢвҖңд»ҘеҸҠи’ІиҚЈй’ҰзӯүеҮ дҪҚеҢ»е®ҳе’Ңй„Ӯиұ«зҡ–ж №жҚ®ең°еҹ№е…»зҡ„з§ҰеӯҗзҸҚгҖҒжұӘеҝғж„ҸгҖҒи©№дё–ејје’ҢеҚ•жүҝзҢӣзӯүзәўиүІеҢ»е®ҳвҖқгҖӮиғҪеҒҡеӨ–科жүӢжңҜзҡ„еҢ»з”ҹжӣҙеҠ зЁҖзјәгҖӮ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вҖңеӨ§еһӢжүӢжңҜз”ұиӢҸдә•и§Ӯдё»еҲҖпјҢе°ҸеһӢжүӢжңҜз”ұе‘Ёеҗүе®үгҖҒйҷҲ银еұұдё»еҲҖвҖқгҖӮжҳҫ然пјҢд»…йқ жңүйҷҗзҡ„иҘҝеҢ»иө„жәҗйҡҫд»ҘжүҝжӢ…иӢҸеҢәе·ЁеӨ§зҡ„еҢ»з–—еҺӢеҠӣгҖӮ第дәҢзұ»еҲҷжҳҜеҪ“ең°дј з»ҹзҡ„дёӯеҢ»иө„жәҗгҖӮдёәи§ЈеҶі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дёҚи¶і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жҖ»ж”ҝжІ»йғЁиҰҒжұӮеҗ„ең°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е’ҢзәўеҶӣеӨ§йҮҸжӢӣиҒҳеҢ»з”ҹпјҢвҖңиҜ·еҗ„ең°жӢӣеӢҹдёӯиҘҝеҢ»з”ҹпјҢеҸӘиҰҒеҝ еҝғйқ©е‘ҪпјҢж„ҝдёәе·ҘеҶңжңҚеҠЎпјҢжҢүжҠҖжңҜй«ҳдёӢпјҢзү№еҲ«дјҳеҫ…вҖқгҖӮ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е·қеҢ—еҗ„еҺҝеҫҲе°‘жңүжӯЈи§„зҡ„еҢ»иҚҜеӯҰж ЎпјҢиҘҝеҢ»дәәжүҚеҘҮзјәпјҢеӣ иҖҢиӢҸеҢәжӢӣиҒҳзҡ„еҜ№иұЎдё»иҰҒдёә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ҮҮеҸ–еӨ§йҮҸиҒҳиҜ·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еҲ°еҢ»йҷўжІ»з—…зҡ„дёҫжҺӘд№ҹжңүеҸҰеӨ–дёҖеұӮеҺҹеӣ гҖӮжӯӨж—¶жӯЈеҖјиӢҸеҢәвҖңдјӨеҜ’гҖҒз—ўз–ҫе’Ңз–ҹз–ҫзӯүең°ж–№жҖ§з–ҫз—…зҢ–зӢӮжіӣж»ҘгҖӮзәўеҶӣжҲҳеЈ«жҲ–иҪ»жҲ–йҮҚең°еҲҶеҲ«жҹ“дёҠеҗ„з§Қз–ҫз—…зҡ„дәәеҮ д№ҺиҰҒеҚ еҚҒеҲҶд№ӢдёҖгҖӮз”ұдәҺеҢ»з–—жқЎд»¶и·ҹдёҚдёҠпјҢдёҚиғҪеҸҠж—¶жІ»з–—пјҢиҮҙдҪҝз—…дәәж—ҘжёҗеўһеӨҡпјҢжӯ»дәЎзҺҮж„ҲжқҘж„ҲеӨ§гҖӮиҰҒеҲ¶жӯўз–ҫз—…жөҒиЎҢпјҢжҢҪж•‘и®ёи®ёеӨҡеӨҡеһӮеҚұзҡ„з—…дәәпјҢиҘҝеҢ»дёҚд»…зјәд№ҸеҢ»иҚҜпјҢиҖҢдё”еӨ§еӨҡж•°еҢ»з”ҹйғҪдёҚзҶҹжӮүиҝҷз§ҚеёҰжңүең°ж–№жҖ§зҡ„жөҒиЎҢз—…пјҢйқўеҜ№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пјҢе”ҜдёҖзҡ„еҠһжі•е°ұеҸӘжңүиҜ·ең°ж–№дёӯеҢ»жқҘи§ЈеҶівҖқгҖӮзәўеҶӣжӢӣиҒҳеҢ»з”ҹ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зҡ„ж–№ејҸе’ҢйҖ”еҫ„иҫғеӨҡгҖӮдёҖжҳҜеҗҢжғ…йқ©е‘Ҫзҡ„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дјҡдё»еҠЁйҖүжӢ©дёәзәўеҶӣжңҚеҠЎгҖӮжҚ®гҖҠе·ҙдёӯеҺҝеҚ«з”ҹеҝ—гҖӢжүҖиҪҪпјҢ1933е№ҙ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жҲҗз«Ӣж—¶пјҢйјҺеұұеҢәдёӯеҢ»зҺӢеӨ©еҫ·еҚідё»еҠЁ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гҖӮеҗҢе№ҙпјҢ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зЁӢзҺүеҗүд№ҹвҖңе…Ҙе·қйҷ•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еҢ»иҚҜеҗҲдҪңзӨҫпјҢж—¶йҖўз—ўз–ҫжөҒиЎҢпјҢдҫҝйҡҸеҶӣжІ»з—…вҖқгҖӮиҖҒзәўеҶӣжқҺдёүеӨҡеңЁ1933е№ҙ9жңҲзәўеҶӣеҲ°жё еҺҝеӢҹе…өж—¶еҸӮеҠ дәҶйқ©е‘Ҫ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и·ҹеӨ–зҘ–зҲ¶еӯҰиҝҮеҢ»пјҢе°ұе°Ҷе…¶вҖңеҲҶй…ҚеҲ°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дёӯеҢ»жүҖеҪ“иҚҜеүӮе‘ҳвҖқпјҢе…¶еҗҺжқҺдёүеӨҡеҸҲеңЁ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зі»з»ҹеӯҰд№ зңӢз—…ејҖж–№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зәўиүІеҢ»е®ҳгҖӮдәҢжҳҜзәўеҶӣе……еҲҶеҲ©з”ЁеӯҰзјҳгҖҒдәІеҸӢзӯүдәәйҷ…зҪ‘з»ңе°ҪеҠӣжҢ–жҺҳпјҢз”ұжӯӨиҒҳиҜ·еҲ°еӨ§йҮҸеҗҚдёӯеҢ»гҖӮ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е·қеҢ—дёӯеҢ»зҡ„еҹ№е…»ж–№ејҸдё»иҰҒжҳҜвҖңе®¶дј еёҲжҺҲвҖқгҖӮиҝҷз§Қеҹ№е…»жЁЎејҸдёӢпјҢ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гҖҒзҲ¶еӯҗе…ізі»гҖҒеӯҰеҸӢе…ізі»зәҪеёҰиҒ”зі»жһҒдёәзҙ§еҜҶпјҢиӢҸеҢәеңЁиҒҳиҜ·еҲ°дёҖеҗҚдёӯеҢ»еҗҺпјҢеҫҖеҫҖдҫҝиғҪйҡҸд№ӢеҸ‘жҺҳдёҖеӨ§жү№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пјҢ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ҸҜд»Ҙжңүж•ҲејҘиЎҘиӢҸеҢә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дёҚи¶і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йҳҺж–Үд»ІдҪңдёәжңҖж—©еҲ°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е·ҘдҪңзҡ„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пјҢвҖңд»–жІ»еҘҪдәҶдёҚе°‘з–ҹз–ҫз—…дәәпјҢж·ұеҸ—ж¬ўиҝҺвҖқпјҢ并еҫ—еҲ°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ж”ҝжІ»йғЁдё»д»»еј зҗҙз§Ӣзҡ„иөһжү¬пјҢеҸ—жӯӨжҝҖеҠұпјҢйҳҺж–Үд»ІдҫҝжҺЁиҚҗжҺҲдёҡжҒ©еёҲжқЁжҲҗе…ғеҲ°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еҸӮдёҺиҜҠз–—е·ҘдҪңгҖӮеҗҺеј зҗҙз§ӢзӯүжҖ»еҢ»йҷўйўҶеҜје§”жүҳжІҷжәӘеҢә委д№Ұи®°йҳҺд»•е…ЁвҖңдёүйЎҫиҢ…еәҗвҖқиҒҳиҜ·жқЁжҲҗе…ғпјҢжңҖз»ҲжҲҗеҠҹдәүеҸ–еҲ°жқЁж°Ҹе…ҘиҒ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гҖӮжқЁж°Ҹ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еҗҺдёҚд№…пјҢвҖңеҸҲз§ҜжһҒжҺЁиҚҗеҢ»з”ҹпјҢеҰӮж–Үиғңзҡ„е‘ЁиҮҙе’ҢгҖҒдҪ•е…үж—¬пјҢд№қеұӮзҡ„йҳҺеҗ•дё°пјҢејҜжҹҸж ‘зҡ„жҲҡдә‘иҠізӯүдёӯеҢ»й«ҳжүӢвҖқгҖӮдёүжҳҜзәўеҶӣжҜҸеҲ°дёҖең°дҫҝжҙҫдәәеҜ»еҢ»пјҢ然еҗҺеҶҚдәІиҮӘдёҠй—ЁиҒҳиҜ·е…¶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вҖңж—әиӢҚеәҷдәҢж№ҫжңүдҪҚйўҮиҙҹзӣӣиӘүзҡ„ж°‘й—ҙдёӯеҢ»еҲҳж°ҸпјҢзәўдёүеҚҒдёҖеҶӣеҢ»йҷўеҚіеүҚеҺ»иҜ·жқҘдёәзәўеҶӣжІ»дјӨжІ»з—…вҖқгҖӮеҸҰжҚ®ж—¶дәәжқҺж°ёеҲҡеӣһеҝҶпјҡвҖң1933е№ҙж Ҫ秧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ңүдёӨдёӘзәўеҶӣеҲ°е®¶жүҫжҲ‘пјҢиҜҙж–°еңәеққжҲҗз«ӢдәҶдәҢеҲҶйҷўпјҢйҮҢйқўеҸӘжңүиҘҝеҢ»пјҢжІЎжңүдёӯеҢ»пјҢиҜ·еҲ°йӮЈйҮҢеҺ»зңӢз—…гҖӮжҲ‘е’Ңд»»жқғд»ІгҖҒеј жё…жү¬3дәәеҲ°дәҶж¶ӘйҳіеққгҖӮвҖқдёәж”№е–„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жқЎд»¶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жұӮиҙӨиӢҘжёҙпјҢеҜ»иҒҳеҢ»з”ҹзҡ„ж–№ејҸжӣҙжҳҜзҒөжҙ»еӨҡж ·пјҢеҠ д№Ӣ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зҡ„зғӯжғ…иҫғй«ҳпјҢзәўеҶӣеҫ—д»ҘеңЁйҖҡжұҹгҖҒеҚ—жұҹгҖҒе·ҙдёӯгҖҒд»ӘйҷҮзӯүеҺҝжӢӣиҒҳиҖҒдёӯеҢ»96дәәпјҢеҠ дёҠ他们зҡ„еҫ’ејҹе…ұ150еӨҡдәәпјҢжһҒеӨ§ең°е……е®һдәҶеҢ»йҷўзҡ„еҢ»з–—еҠӣйҮҸпјҢеҢ»йҷўзҡ„еҢ»з–—ж°ҙе№ід№ҹеҫ—еҲ°жҳҫи‘—жҸҗй«ҳгҖӮд»ҺдёҠиҝ°дәӢдҫӢ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еңЁзү№е®ҡ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йқ©е‘ҪдәӢдёҡеҜ№еҪ“ең°дёҖдәӣеҢ»з”ҹжңүзқҖиҫғејәзҡ„еҗёеј•еҠӣгҖӮ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еҫ—зӣҠдәҺиӢҸеҢәйҮҚи§Ҷжңүдё“дёҡжҠҖжңҜиғҪеҠӣзҡ„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пјҢеӣўз»“дёҖеҲҮеҸҜд»Ҙеӣўз»“зҡ„еҠӣйҮҸд»Ҙе……е®һиӢҸеҢәеҢ»еҠЎеҠӣйҮҸзҡ„ж–№й’Ҳж”ҝзӯ–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д№ҹеҫ—зӣҠдәҺ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Ҝ№дёӯеҢ»е’ҢиҘҝеҢ»гҖҒзәўиүІеҢ»е®ҳе’Ңе…¶д»–еҢ»е®ҳзҫӨдҪ“е®һиЎҢзҡ„ж— е·®еҲ«жҷӢеҚҮеҲ¶еәҰе’Ңе…Ёж–№дҪҚзҡ„дјҳеҫ…ж”ҝзӯ–гҖӮеңЁе…·дҪ“е®һи·өдёӯпјҢзәўеҶӣз»ҷдәҲдё“дёҡеҢ»е®ҳ们充еҲҶзҡ„дҝЎд»»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иӢҸдә•и§Ӯе°ұжӣҫеҸҚеӨҚе‘ҠиҜ«еҗ„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пјҢеҜ№е…¶д»–вҖңеҢ»е®ҳзҫӨдҪ“вҖқпјҢвҖңж”ҝжІ»дёҠиҰҒеё®еҠ©пјҢе·ҘдҪңдёҠиҰҒдҝЎд»»пјҢз”ҹжҙ»дёҠиҰҒз»ҷдәҲз…§йЎҫгҖӮжҠҖжңҜеҘҪзҡ„иҝҳиҰҒеҗ‘他们еӯҰд№ вҖқгҖӮеңЁж”ҝжІ»еҫ…йҒҮдёҠпјҢеҮЎжңүдё“й•ҝзҡ„еҢ»е®ҳвҖңзә§еҲ«зӣёеҪ“дәҺеҶӣйҳҹзҡ„иҝһзә§вҖқгҖӮеңЁеҜ№еҢ»е®ҳзҡ„жҸҗжӢ”е’ҢдҪҝз”ЁдёҠпјҢеқҡжҢҒвҖңд»Ҙдәәе°Ҫе…¶жүҚгҖҒйҮҸжүҚеҪ•з”ЁвҖқзҡ„еҺҹеҲҷгҖӮеҰӮжқЁжҲҗе…ғе…ҘиҒҢжҖ»еҢ»йҷўдёҚд№…пјҢдҫҝиў«жҸҗжӢ”дёәвҖңзӣёеҪ“еүҜеёҲзә§зҡ„дёӯеҢ»йғЁеүҜдё»д»»вҖқпјҢи’ІиҚЈй’ҰгҖҒжқЁжҲҗзҰҸвҖңжҲҗдёәиҘҝеҢ»йғЁзҡ„йӘЁе№ІвҖқпјҢеҗ‘жЎӮжһ—еҲҷеңЁвҖң1934е№ҙиў«жҸҗеҚҮдёәзәў33еҶӣеҶӣеҢ»йҷўйҷўй•ҝ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Ң»з”ҹзҡ„и–Әиө„еҫ…йҒҮд№ҹжҜ”иҫғдјҳеҺҡпјҢиҝҷж— з–‘еҜ№з»ҸжөҺзӘҳиҝ«зҡ„еҪ“ең°дёӯеҢ»е…·жңүеҗёеј•еҠӣгҖӮжқҺж°ёеҲҡгҖҒд»»жқғд»ІдёӨдәәвҖңжҜҸжңҲз»ҸжөҺ32е…ғвҖқгҖӮжқЁжҲҗе…ғжҜҸжңҲе·Ҙиө„еҲҷй«ҳиҫҫ120е…ғ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вҖңеӨ–йғЁеҢ»з”ҹпјҲиҒҳиҜ·гҖҒеҪ•з”ЁеҢ»з”ҹпјүиЎҢеҶӣгҖҒеҮәиҜҠиҝҳеҸҜд»ҘйӘ‘йӘЎй©¬вҖқгҖӮдёәж¶ҲйҷӨеҢ»е®ҳ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е°ұйҡҫд»Ҙе…јйЎҫ家еәӯзҡ„йЎҫиҷ‘пјҢеҢ»йҷўвҖңиҝҳе…Ғи®ёеёҰ家еұһвҖқпјҢйҷӨдјҷйЈҹиҙ№еӨ–пјҢвҖңжҜҸжңҲиҝҳеҸ‘з»ҷеӨ§жҙӢ10е…ғпјҲдёҖиҲ¬е·ҘдҪңдәәе‘ҳйҖўйҮҚеӨ§иҠӮж—ҘжүҚеҸ‘еӨ§жҙӢ1е…ғпјүвҖқгҖӮд»Һж•ҙдҪ“жқҘзңӢпјҢеңЁиӢҸеҢәеҗ„йЎ№ж”ҝзӯ–зҡ„еј•еҜјдёӢпјҢиў«дҝҳиҖҢ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зҡ„еҺҹеӣҪж°‘е…ҡйғЁйҳҹеҢ»е®ҳе’ҢеңЁжң¬еңҹ延иҜ·зҡ„дёӯеҢ»зҫӨдҪ“пјҢеӨ§йғҪиғҪеҜ№йқ©е‘ҪдәӢдёҡдә§з”ҹдёҖе®ҡзҡ„и®ӨеҗҢпјҢз§ҜжһҒжҠ•е…ҘзәўеҶӣе’Ң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дёӯгҖӮеӣ иҖҢпјҢеҚідҪҝиә«еӨ„еҶӣдәӢдёҠзҡ„йҖҶеўғпјҢе…ҡе’ҢзәўеҶӣдҫқж—§иғҪеҫ—еҲ°з»қеӨ§еӨҡж•°иӢҸеҢәеҢ»з”ҹзҫӨдҪ“зҡ„дҝЎд»°е’ҢиҝҪйҡҸ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вҖң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јҖе§Ӣй•ҝеҫҒ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қЁжҲҗе…ғиҖҒе…Ҳз”ҹиҷҪе·Іе№ҙйҖҫеҸӨзЁҖпјҢдҪҶд»–еқҡеҶіиЎЁзӨәдёҚжғңзҰ»ејҖж•…еңҹпјҢж„ҝйҡҸзәўеҶӣеүҚеҫҖвҖқгҖӮеңЁе…¶дёҙз»Ҳд№Ӣйҷ…пјҢдҫқж—§йҒ—иЁҖж„ҹи°ўе…ҡвҖңеҜ№жҲ‘жңүзқҖзҹҘйҒҮд№ӢжҒ©пјҢдҪҝжҲ‘е№ёеҫ—жҠ•иә«йқ©е‘ҪвҖқпјҢвҖңжҲ‘жӯ»иҖҢж— жҶҫпјҢеӣ дёәжҲ‘жҳҜйқ©е‘Ҫд№ӢдәәвҖқ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йқ©е‘ҪдәӢдёҡеҜ№еҢ»еҠЎдё“дёҡжҠҖжңҜзҫӨдҪ“е…·жңүзҡ„жғ…ж„ҹеҗёзәіеҠӣгҖӮ第дёүзұ»жҳҜ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иҮӘе·ұеҹ№е…»зҡ„еҢ»з–—жҠҖжңҜдәәе‘ҳгҖӮзәўеҶӣиҮӘе…Ҙе·қдјҠе§ӢпјҢе°ұеҚҒеҲҶйҮҚи§ҶйҖҡиҝҮйҖҹжҲҗеҠһжі•еҹ№е…»иҮӘе·ұзҡ„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гҖӮ1933е№ҙеҲқпјҢз”ұдәҺжҲҳж–—йў‘з№ҒпјҢзңӢжҠӨдәәе‘ҳзјәд№Ҹ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дҫҝејҖеҠһдәҶзңӢжҠӨи®ӯз»ғзҸӯпјҢиҰҒжұӮзәўеҶӣе’Ңеҗ„ең°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жӢӣ收йҳ¶зә§жҲҗеҲҶеҘҪпјҢвҖңзӨҫдјҡе…ізі»жё…зҷҪвҖқпјҢвҖңиә«дҪ“еҒҘеә·пјҢжІЎжңүе—ңеҘҪпјҢзІ—зҹҘж–Үеӯ—пјҢжңүеӯҰд№ зІҫзҘһвҖқзҡ„йқ’е№ҙ40еҗҚпјҢйӣҶдёӯеӯҰд№ 3дёӘжңҲзҡ„зңӢжҠӨеӯҰгҖҒеҢ»иҚҜеӯҰгҖҒз”ҹзҗҶеӯҰгҖҒжҲҳдјӨзҹҘиҜҶе’ҢеҶӣдәӢж”ҝжІ»зӯүеҹәжң¬еёёиҜҶеҗҺпјҢдҫҝеҲҶй…ҚиҮі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дёӯжңҚеҠЎ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йҡҸзқҖиӢҸеҢәж—ҘзӣҠжү©еӨ§пјҢдёәж»Ўи¶ійғЁйҳҹе’ҢиӢҸеҢәеҜ№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зҡ„йңҖиҰҒ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еҶіе®ҡеңЁзңӢжҠӨи®ӯз»ғзҸӯ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з»„е»әзәўиүІ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пјҢдё“й—ЁиҙҹиҙЈеҹ№е…»зңӢжҠӨе‘ҳе’ҢеҢ»з”ҹгҖӮ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жӢӣз”ҹиҢғеӣҙиҫғе№ҝпјҢйҷӨйқўеҗ‘иӢҸеҢәжӢӣ收иҜҶеӯ—зҡ„йқ’е№ҙе’ҢеҺҹжқҘеңЁжҖ»еҢ»йҷўе·ҘдҪңзҡ„зңӢжҠӨдәәе‘ҳдҪңдёә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еӯҰе‘ҳд№ӢеӨ–пјҢеӯҰж ЎиҝҳвҖңд»Һеҗ„еҶӣеҗ„еёҲйҖүжӢ”иә«дҪ“еҒҘеЈ®гҖҒе№ҙиҪ»жңәзҒөгҖҒзЁҚжңүж–ҮеҢ–зҡ„зәўе°Ҹй¬јпјҢжқҘ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еӯҰд№ вҖқгҖӮиӢҸдә•и§ӮзӯүдәәвҖңиҝҳеҲ°еҗ„еҶӣгҖҒеёҲеҢ»йҷўзҡ„е·ҘдҪңдәәе‘ҳдёӯжҢ‘йҖүеӯҰе‘ҳпјҢеңЁжҖ»еҢ»йҷўдҪҸйҷўзҡ„дјӨз—…е‘ҳдёӯйҖүз•ҷеӯҰе‘ҳвҖқ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жҲҗз«Ӣд№ӢеҲқеҲҶи®ҫиҘҝеҢ»е’ҢдёӯеҢ»дёӨдёӘзҸӯпјҢе…ұжӢӣ收еӯҰе‘ҳ200еӨҡеҗҚпјҢдёӯеҢ»зҸӯжңүеӯҰе‘ҳ40дәәпјҢвҖңйғҪжҳҜжӣҫз»ҸзңӢиҝҮз—…зҡ„еҢ»з”ҹпјҢеӯҰд№ жңҹйҷҗ3дёӘжңҲвҖқгҖӮеӯҰд№ ж–№ејҸдё»иҰҒдёәеҚҠе·ҘеҚҠиҜ»пјҢвҖңдёҠеҚҲз”ұеҢ»з”ҹеёҰеҲ°еҗ„дјӨз—…иҝһеҢ»дјӨжІ»з—…пјҢдёӢеҚҲдёҠиҜҫгҖӮжҜҸеӨ©еӯҰд№ 4дёӘе°Ҹж—¶вҖқгҖӮе…¶еҗҺ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и§„жЁЎйҖҗжёҗжү©еӨ§пјҢз”ұжңҖеҲқзҡ„200дҪҷдәәеҸ‘еұ•еҲ°400еӨҡдәәпјҢзҹӯж—¶й—ҙеҶ…е°ұдёә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ҹ№е…»дәҶ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2000дҪҷдәәпјҢзӣёеҪ“зЁӢеәҰдёҠеЈ®еӨ§дәҶ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еҠЎдәәжүҚйҳҹдј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зәўеҶӣеҗ„еҶӣгҖҒеёҲеҢ»йҷўд№ҹзӣёз»§жҲҗз«ӢдәҶеҚ«з”ҹдәәе‘ҳи®ӯз»ғзҸӯпјҢе……е®һдәҶеҗ„йғЁйҳҹзҡ„еҢ»жҠӨеҠӣйҮҸ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з»ҸиҝҮдёҚж–ӯеҹ№и®ӯпјҢеҗ„еҶӣгҖҒеёҲеқҮеӮЁеӨҮдәҶж•°еҚҒеҗҚеҚ«з”ҹдәәе‘ҳпјҢе…¶дёӯвҖңзәў31еҶӣ91еёҲзҡ„еҚ«з”ҹдәәе‘ҳжңҖеӨҡпјҢ1933е№ҙеә•иҫҫеҲ°дәҶ100еӨҡдәәвҖқгҖӮ1933е№ҙ10жңҲпјҢз»Ҹе·қйҷ•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жү№еҮҶпјҢе·қйҷ•зңҒе·ҘеҶңеҢ»йҷўиҝҳејҖеҠһдәҶ3жңҹзәўиүІдёӯеҢ»и®ӯз»ғзҸӯгҖӮдёӯеҢ»и®ӯз»ғзҸӯе…ұеҹ№е…»дёӯеҢ»150еҗҚпјҢжҠӨзҗҶдәәе‘ҳ200дәә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ёәеә”еҜ№жөҒиЎҢжҖ§з–«з—…пјҢеҗ„ең°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д№ҹз§ҜжһҒеҲӣе»ә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и®ӯз»ғзҸӯпјҢеҹ№е…»дәҶдёҖеӨ§жү№ең°ж–№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гҖӮеҰӮзәўеҶӣзӣҗдёҡз»ҸзҗҶйғЁеӨ§зў‘йҷўз¬¬дёғеҢәиӢҸз»ҙеҹғејҖеҠһзҡ„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и®ӯз»ғзҸӯпјҢз”ұеҗ„д№ЎжҺЁиҚҗиҜ»иҝҮдёӯеҢ»иҚҜд№Ұе’ҢеҶіеҝғеӯҰеҢ»зҡ„иҝӣжӯҘйқ’е№ҙеҸӮеҠ еҹ№и®ӯгҖӮ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ҖҡиҝҮеҗ„з§ҚдёҫжҺӘеҹ№е…»дәҶеӨ§жү№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пјҢдҪҶз”ұдәҺ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еҹ№е…»е‘Ёжңҹиҫғй•ҝгҖҒиӢҸеҢәж•ҷеӯҰжқЎд»¶е’ҢеҢ»еҠЎдәәе‘ҳиҮӘиә«ж–ҮеҢ–ж°ҙе№іжңүйҷҗпјҢ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иӢҸеҢәеҹ№е…»зҡ„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ж•ҙдҪ“дёҡеҠЎж°ҙ平并дёҚз®—й«ҳпјҢдҪҶз»ҸиҝҮеҗҺз»ӯзҡ„дё“дёҡеҹ№и®ӯе’ҢеІ—дҪҚй”»зӮјпјҢ他们дҫқж—§еңЁзәўеҶӣе’Ңең°ж–№зҡ„еҚ«з”ҹдәӢдёҡдёӯ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пјҢз”ҡиҮіжңүдёҚе°‘еҲқеҠ е…ҘиҖ…йҖҗжёҗжҲҗй•ҝдёәеҢ»з–—йӘЁе№ІгҖӮеҰӮ1933е№ҙеӨҸеӨ©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Қ«з”ҹеӯҰж Ўд»Һдјҳз§ҖеӯҰе‘ҳдёӯвҖңжҸҗжӢ”дәҶе…«еҗҚзәўиүІеҢ»е®ҳпјҢд»ҘйҖӮеә”еҢ»з–—е·ҘдҪңзҡ„йңҖиҰҒгҖӮиҝҷе…«дёӘдәәдёӯжңүйҷҲ银еұұгҖҒйҷҲж°ёеҜҝгҖҒиӮ–йӮҰе®Ғе’ҢиөөеӯҗжҒ’вҖқзӯүдәәпјҢ他们еқҮиў«еҲҶй…ҚеҲ°жҖ»еҢ»йҷўеҲҶйҷўжҲ–еёҲзә§зәўеҶӣеҢ»йҷўеҒҡеҢ»еҠЎдё»д»»гҖӮдёүгҖҒ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з”Ёе“Ғдҫӣеә” 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жҳҜз»ҙжҠӨ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иә«дҪ“еҒҘеә·гҖҒжІ»з–—жҲҳдәүеҲӣдјӨзҡ„зү№ж®Ҡе•Ҷе“ҒгҖӮд»Һең°зҗҶеҢәдҪҚжқЎд»¶жқҘзңӢпјҢе·қеҢ—дәӨйҖҡй—ӯеЎһгҖҒеұұй«ҳжһ—ж·ұпјҢеңЁеҶӣдәӢдёҠйҖӮеҗҲзәўеҶӣжҚ®йҷ©иҖҢе®ҲпјҢеҸҜдёҖж—ҰеҸ—еҲ°ж•Ңдәәзҡ„е…Ёйқўе°Ғй”ҒпјҢе°ұе®№жҳ“жҡҙйңІеҮәиө„жәҗдҫӣз»ҷдёҠзҡ„жһҒз«Ҝи„ҶејұжҖ§гҖӮвҖңе·қеҢ—йҖҡгҖҒеҚ—гҖҒе·ҙдёҖеёҰдәӨйҖҡй—ӯеЎһпјҢеҠ дёҠж•Ңдәәзҡ„вҖҳеӣҙеүҝвҖҷгҖҒе°Ғй”ҒпјҢжҳҜеҫҲйҡҫжҗһеҲ°иҚҜзү©зҡ„пјҢжңүж—¶зјҙиҺ·ж•ҢдәәдёҖдәӣиҚҜе“ҒпјҢйӮЈз®ҖзӣҙжҳҜеҰӮиҺ·иҮіе®қгҖӮвҖқеҗҢж—¶пјҢиӢҸеҢәеҗ„зә§еҢ»йҷўзҡ„еҢ»з–—и®ҫеӨҮд№ҹжһҒдёәз®ҖйҷӢе’ҢеҢ®д№ҸгҖӮз”ұдәҺеӣҪж°‘е…ҡж”ҝжқғдёҘеҜҶзҡ„е°Ғй”ҒзҰҒиҝҗпјҢдҝқйҡңеҢ»з–—з”Ёе“Ғзҡ„дҫӣеә”дҝЁз„¶жҲҗдёә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дё»иҰҒеҶ…е®№гҖӮдёәи§ЈеҶізӣёе…ій—®йўҳ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қ©е‘ҪеҠӣйҮҸеӨҡжҺӘ并дёҫпјҢдёҚж–ӯжӢ“еұ•еҢ»з–—з”Ёе“Ғзӯ№йӣҶжё йҒ“пјҢе…ЁеҠӣдҝқйҡң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зү©иө„дҫӣеә”гҖӮе…¶дёҖпјҢеңЁжҲҳдәүе’Ңйқ©е‘Ҫж–—дәүдёӯзјҙиҺ·ж•Ңдәәзҡ„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д»ҘиЎҘе……иҮӘиә«гҖӮ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°Ҷ收зјҙ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дҪңдёәзәўеҶӣе№ҝеӨ§жҢҮжҲҳе‘ҳеҚ йўҶеҹҺеёӮеҗҺзҡ„дёҖйЎ№еҹәжң¬д»»еҠЎ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зәўеҶӣеңЁгҖҠзәўиүІжҲҳеЈ«еҝ…иҜ»пјҲ第дёҖз§ҚпјүгҖӢдёӯпјҢе°ұе°ҶвҖңеҚ еҹҺеёӮжіЁж„Ҹ收йӣҶжңәеҷЁеҢ»иҚҜвҖқдҪңдёәжҜҸдҪҚзәўеҶӣжҲҳеЈ«еҝ…йЎ»зҹҘжҷ“зҡ„йҮҚиҰҒдәӢйЎ№гҖӮеҗҺеҸҲеңЁгҖҠеҶӣдәӢе№ІйғЁдјҡи®®еҗ„з§ҚжҠҘе‘ҠеӨ§зәІгҖӢдёӯиҰҒжұӮеҗ„йғЁйҳҹйҰ–й•ҝеҠ ејәвҖңдёӯиҘҝиҚҜе“Ғзҡ„收йӣҶ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№ҝеӨ§зәўеҶӣжҢҮжҲҳе‘ҳеңЁжү“жү«жҲҳеңәж—¶еҚҒеҲҶжіЁж„Ҹ收йӣҶиҚҜе“Ғзӯүзү©иө„пјҢвҖңжҜҸж¬ЎеӨ§зҡ„жҝҖзғҲжҲҳж–—ж”»еҚ дёҖеҹҺд»ҘеҗҺпјҢжҖ»жҳҜиҰҒзјҙиҺ·йғЁеҲҶзү©е“Ғзҡ„пјҢеҰӮиҘҝиҚҜгҖҒжһӘеј№гҖҒиў«жңҚгҖҒйЈҹзӣҗзӯүвҖқгҖӮеҶҚеҰӮпјҢзәўеҶӣж”»дёӢз»Ҙе®ҡеҹҺпјҲд»Ҡиҫҫе·һпјүеҗҺзјҙиҺ·дәҶеӨ§йҮҸиҚҜе“ҒпјҢвҖңеӨ§жү№зҡ„иҚҜзү©д»Һз»Ҙе®ҡиҝҗгҖӮдёҖж¬ЎдёҖзҷҫеҢ№зүІеҸЈй©®пјҢй©®дәҶеҘҪеҮ еӣһ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иҝҳйҖҡиҝҮеҗ‘еңҹиұӘеҠЈз»…еҫҒеҸ‘гҖҒ没收зӯүж–№ејҸзӯ№йӣҶиҚҜе“ҒгҖӮ1933е№ҙ6жңҲпјҢе·қйҷ•зңҒ委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иҚҜжқҗзӯүзү©иҙЁд»ҘеҸҠеҢ»йҷўдјӨз—…зӯүзҡ„йңҖиҰҒпјҢеә”дёҖйқўеӨ§еӨ§зҡ„еҠЁе‘ҳзҫӨдј—жқҘеё®еҠ©дёҺжӢҘжҠӨпјҢдёҖйқўеҸҲиҰҒжңүи®ЎеҲ’зҡ„收买еҫҒеҸ‘дёҺйӣҶдёӯ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д№ҹеҲ©з”ЁдҝҳиҷҸзҡ„ж•ҢеҶӣе®ҳй•ҝгҖҒеңҹиұӘеҠЈз»…зӯүжқҘдәӨжҚўиӢҸеҢәжҖҘйңҖзҡ„иҚҜе“ҒгҖҒжӯҰеҷЁзӯүзү©иө„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йҖҡиҝҮзјҙиҺ·гҖҒеҫҒ收гҖҒ没收е’ҢеҲ©з”ЁдҝҳиҷҸдәӨжҚў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зҡ„ж–№ејҸиҷҪ然иғҪеңЁзҹӯж—¶й—ҙеҶ…зӯ№йӣҶеҲ°иҫғеӨҡеҢ»иҚҜзү©иө„пјҢдҪҶйҡҫд»ҘжҢҒз»ӯгҖӮе…¶дәҢ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иҝҳйҖҡиҝҮз§ҳеҜҶйҮҮиҙӯпјҢеҸ‘еұ•еҜ№еӨ–иҙёжҳ“пјҢдёҫеҠһ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зӯүж–№ејҸжӢ“е®Ҫзӯ№йӣҶеҢ»з–—зү©иө„зҡ„жё йҒ“гҖӮ1933е№ҙеӨҸпјҢеӣҪж°‘е…ҡеҚҒдёғи·ҜеҶӣжқЁиҷҺеҹҺгҖҒеӯҷи”ҡеҰӮйғЁдёҺзәўеҶӣе»әз«ӢдәҶз»ҹжҲҳе…ізі»пјҢж„ҝж„ҸдёәзәўеҶӣжҸҗдҫӣйҖӮйҮҸзҡ„еҶӣйңҖзү©иө„пјҢвҖңз»ҷзәўеҶӣиө йҖҒдәҶиҝ‘дёӨеҚғе…ғзҡ„еҢ»иҚҜзӯүзү©вҖқпјҢеӯҷи”ҡеҰӮеҸҲе…ҲеҗҺвҖңз»ҷзәўеҶӣиө йҖҒдәҶ10жү№иҚҜе“Ғ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зәўеҶӣеҸҲеңЁжұүдёӯиҮіе·қеҢ—д№Ӣй—ҙе»әз«ӢдәҶ3жқЎз§ҳеҜҶзәўиүІдәӨйҖҡзәҝе’Ң1жқЎеӨҚзәҝпјҢд»ҘвҖңеҚҸеҠ©еҗҺеӢӨжҖ»йғЁйҮҮиҙӯжҖ»йғЁжүҖйңҖзү©иө„еҸҠиҪ¬иҝҗвҖқзӯүдәӢйЎ№гҖӮдҫӢеҰӮ1933е№ҙ6жңҲпјҢзәўеҶӣе°ұжӣҫйҖҡиҝҮзәўиүІдәӨйҖҡзәҝе°ҶвҖңиҙӯеҫ—ж— зәҝз”өеҷЁжқҗгҖҒиҚҜе“ҒгҖҒ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е’Ңз”өжұ зӯү20еӨҡжӢ…вҖқйҖҒиҮійҖҡжұҹгҖӮеӯҷи”ҡеҰӮйғЁдёәзәўеҶӣжҸҗдҫӣзҡ„иҚҜе“Ғе’ҢзәўеҶӣд»Һйҷ•еҚ—иҙӯд№°зҡ„иҘҝиҚҜ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зӯүзү©иө„жҖ»йҮҸиҫғе°ҸпјҢиҷҪиғҪеӢүејәж»Ўи¶іеҢ»жІ»йғЁеҲҶйҮҚдјӨе‘ҳзӯүзү№ж®ҠйңҖиҰҒпјҢдҪҶдәҺж•ҙдёӘиӢҸеҢәзҡ„еәһеӨ§йңҖжұӮиҖҢиЁҖж— ејӮдәҺжқҜж°ҙиҪҰи–ӘгҖӮдёәжӯӨ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иҝҳйҖҡиҝҮдёҫеҠһ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гҖҒйј“еҠұеҜ№еӨ–иҙёжҳ“зӯүж–№ејҸ收иҙӯиҚҜе“ҒгҖӮеңЁ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зҡ„жңәжһ„и®ҫи®ЎдёӯпјҢ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жҳҜ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жқғзҡ„е•Ҷдёҡжңәе…іе’ҢйҮҚиҰҒзҡ„иҙёжҳ“жңәе…іпјҢе…¶дё»иҰҒиҒҢиғҪжҳҜиҙҹиҙЈд»ҺзҫӨдј—жүӢдёӯиҙӯд№°зІ®йЈҹгҖҒзӣҗгҖҒиҚҜе“ҒзӯүиӢҸеҢәзҙ§зјәзү©иө„пјҢд»Ҙдҫӣз»ҷ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пјҢвҖң银иҖігҖҒзү№иҙ§з”ұ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з®ЎпјҢд»Һ收иҙӯгҖҒйӣҶдёӯгҖҒз»„з»ҮиҝҗеҫҖзҷҪеҢәпјҢеҺ»жҚўиҙӯеҶӣйңҖе“ҒгҖҒйЈҹзӣҗгҖҒиҘҝиҚҜзӯүеӣһжқҘдҫӣз»ҷиӢҸеҢәе№ҝеӨ§еҶӣж°‘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·қйҷ•зңҒ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иҝҳйј“еҠұиҚҜе“ҒгҖҒзІ®йЈҹзӯүеҝ…йңҖе“Ғзҡ„иҝӣеҸЈпјҢ并еҜ№е…¶дәҲд»Ҙе…ҚзЁҺж”ҜжҢҒпјҢвҖңдёӯиҘҝиҚҜжқҗгҖҒиҖ•зүӣгҖҒе°ҸзҢӘгҖҒжҙӢжІ№гҖҒз”ҹеҸ‘жІ№зӯүпјҢзҡҶеҫ—е…ҚзЁҺ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иӢҸеҢәдәҰйј“еҠұзҷҪеҢәзҡ„е•Ҷиҙ©иҝҗйҖҒвҖңдёӯиҘҝиҚҜжқҗгҖҒйЈҹзӣҗвҖқвҖңзӯүзү©еҲ°иӢҸеҢәиҙ©еҚ–вҖқгҖӮе…¶дёүпјҢзҷҪеҢәзҡ„ең°дёӢе…ҡе‘ҳе’Ңе№ҝеӨ§зҫӨдј—ж— еҒҝжҚҗиө гҖӮзәўеҶӣе…Ҙе·қеҗҺпјҢжҲҗз«Ӣе…ҡзҡ„вҖңз§ҳеҜҶзҡ„еӨ–еңҲз»„з»ҮвҖқвҖ”вҖ”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зӨҫгҖӮ1933е№ҙ1жңҲ6ж—ҘпјҢйҷ•иҘҝжұүеҚ—зү№е§”еҶіи®®вҖңжү©еӨ§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зӨҫзҡ„з»„з»ҮпјҢз§ҜжһҒиҝӣиЎҢеӢҹжҚҗиҝҗеҠЁвҖқпјҢвҖңеӢҹжҚҗдёҖеҲҮж…°еҠіе“ҒпјҢж…°еҠізәўеҶӣвҖқгҖӮеҗҺеӣӣе·қзңҒ委д№ҹжҢҮзӨәеҗ„ең°е…ҡгҖҒеӣўз»„з»ҮпјҢвҖңиҰҒеҲ°ж— з»„з»Үзҡ„зҫӨдј—дёӯеҺ»еӢҹжҚҗпјҢжҠҠеҮәдәҶжҚҗзҡ„зҫӨдј—з»„з»ҮжҲҗвҖҳ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вҖҷвҖқгҖӮеңЁеҗ„ең°е…ҡгҖҒеӣўз»„з»Үзҡ„йўҶеҜјдёӢпјҢеҗ„ең°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зӨҫзә·зә·ејҖеұ•еӢҹжҚҗжҙ»еҠЁпјҢ并еӢҹйӣҶеҲ°дёҚе°‘иӢҸеҢәзҙ§зјәзҡ„зү©иө„пјҢз»ҷдәҲдәҶзәўеҶӣд»ҘжңүеҠӣж”ҜжҸҙгҖӮеҰӮжұүдёӯзәўеҸӢд№ӢеҸӢзӨҫдёәзәўеҶӣвҖңеӢҹеҲ°жІ№еҚ°жңәгҖҒеҸ·и§’гҖҒз”өжұ гҖҒеҢ»иҚҜз”Ёе“ҒзӯүеҶӣйңҖзү©иө„вҖқгҖӮеҚҒдёғи·ҜеҶӣ第38еҶӣзҡ„вҖңеҢ»еҠЎдё»д»»иөөжҹҗпјҲең°дёӢе…ҡе‘ҳпјүдёҖдәәжҚҗеӢҹзҡ„еҢ»иҚҜе°ұжңүеҚҒеӨҡз§ҚвҖқ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еңЁ1933е№ҙ4жңҲиҮі6жңҲпјҢ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зӨҫеӢҹйӣҶеҲ°зҡ„зү©иө„з»ҸзәўиүІдәӨйҖҡзәҝвҖңиҪ¬йҖҒеҲ°е·қйҷ•ж №жҚ®ең°зҡ„еҢ»иҚҜе°ұжңүдәҢеҚҒдҪҷз§ҚвҖқгҖӮеӣӣе·қе…ҡз»„з»Үе’ҢзәўеҶӣд№ӢеҸӢзӨҫд№ҹзӯ№йӣҶеҲ°дәҶйғЁеҲҶиҚҜе“Ғ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·қеҢ—ең°дёӢе…ҡз»„з»ҮжӣҫжҚҗиө вҖң3жӢ…еҗҚиҙөиҚҜе“ҒвҖқгҖӮ1933е№ҙеӨҸеӨ©пјҢзәўеҶӣиҝҳжҲҗз«ӢдәҶд»Ҙеҗҙз‘һжһ—дёәйҰ–зҡ„жӯҰиЈ…е°ҸеҲҶйҳҹпјҢвҖңдёҚд»…жҗһдәҶеҚҒеӨҡдёҮж–Өзӣҗе·ҙпјҢиҝҳжҗһдәҶеҮ еҚҒеҸӘиҲ№е’ҢдёҚе°‘зҡ„иҚҜе“ҒгҖҒеёғеҢ№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йғЁеҲҶ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зҡ„дёӯеҢ»еңЁе…ҡе’ҢзәўеҶӣзҡ„ж„ҹеҸ¬дёӢд№ҹзә·зә·жҚҗзҢ®иҮӘе·ұеӮЁи—Ҹзҡ„иҚҜе“ҒпјҢеҰӮжқЁжҲҗе…ғеҸӮеҠ йқ©е‘ҪдёҚд№…пјҢйҒӮвҖңжүҳдәәеҸ–еӣһд»–еҺҹжқҘйҡҗи—Ҹд№ӢиҚҜпјҢ并еҸ‘еҠЁдәІжңӢеҢ»еҸӢеңЁеҶңжқ‘收йӣҶж•ЈеӯҳиҚҜзү©пјҢеҸҲеёҰйўҶжӢӣе‘јйҳҹе‘ҳдёҠеұұйҮҮжҢ–пјҢзј“и§ЈдәҶиҚҜзү©зҡ„дҫӣжұӮзҹӣзӣҫвҖқгҖӮиҝҷ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ж”№е–„дәҶ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зү©иө„еҢ®д№Ҹзҡ„зҠ¶еҶөгҖӮз»јдёҠжүҖиҝ°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»әз«ӢеҲқжңҹе…¶жүҖйңҖзҡ„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дёҘйҮҚеҢ®д№Ҹдё”жқҘжәҗжһҒдёҚзЁіе®ҡгҖӮдёәз ҙи§Јеӣ°еўғ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ҖҡиҝҮйҮҮеҸ–з§ҳеҜҶйҮҮеҠһгҖҒеҸ‘еұ•з»ҸжөҺе…¬зӨҫгҖҒйј“еҠұеҶ…еӨ–иҙёжҳ“гҖҒеҸ‘еҠЁзҫӨдј—жҚҗиҚҜзӯүдёҫжҺӘзӯ№жҺӘеҢ»з–—зү©иө„пјҢ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ҮҸиҪ»дәҶж•Ңдәәз»ҸжөҺе°Ғй”Ғ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иҙҹйқўеҪұе“ҚпјҢжңүж•Ҳзј“и§ЈдәҶиӢҸеҢәиҘҝиҚҜ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еҢ®д№ҸзҠ¶еҶөпјҢйғЁеҲҶдҝқйҡңдәҶ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зҡ„иҜҠз–—йңҖжұӮгҖӮе…¶еӣӣпјҢжҢ–жҺҳе·қеҢ—дёӯеҢ»иҚҜжҪңеҠӣпјҢиҮӘдё»з”ҹдә§е’ҢеҲ¶дҪңжӣҝд»ЈиҚҜе“Ғ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гҖӮе·қеҢ—ең°еӨ„еұұеҢәпјҢжЈ®жһ—еҜҶеёғпјҢйҮҺз”ҹдёӯиҚҜжқҗиө„жәҗдё°еҜҢпјҢдёәиӢҸеҢәеӨ§йҮҸйҮҮйӣҶдёӯиҚүиҚҜжҸҗдҫӣдәҶзү©иҙЁжқЎд»¶гҖӮд»ҘеҚ—жұҹеҺҝдёәдҫӢпјҢиҜҘеҺҝвҖңеҗҚиҙөиҚҜжқҗжңүй№ҝиҢёгҖҒйәқйҰҷгҖҒзҶҠиғҶгҖҒзҢҙиӮқгҖҒиұ№йӘЁгҖҒеӨ©йә»гҖҒе…ҡеҸӮгҖҒжқңд»ІгҖҒжһЈзҡ®гҖҒзәўиҠұгҖҒжһёжқһзӯүвҖқгҖӮдёҠиҝ°иҚҜжқҗйҷӨж»Ўи¶іеҪ“ең°йңҖиҰҒеӨ–пјҢиҝҳвҖңиҝңй”ҖзңҒеҶ…еҸҠиҘҝеә·гҖҒйҷ•иҘҝгҖҒиҙөе·һгҖҒз”ҳиӮғгҖҒж№–еҢ—зӯүең°вҖқгҖӮиҗҘеұұзӯүеҺҝеҹҹдәҰ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жё…жң«вҖңиҗҘеұұеҺҝеўғжңүдёӯиҚҜжқҗ204з§ҚгҖӮе…¶дёӯйҮҺз”ҹ143з§ҚпјҢ家з§Қ61з§ҚвҖқгҖӮз”ұдәҺиҘҝеҢ»е’ҢиҘҝиҚҜеҢ®д№Ҹ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ҮҮеҸ–дәҶдёӯиҘҝз»“еҗҲзҡ„жІ»з–—ж–№жі•пјҢе……еҲҶеҲ©з”ЁдёӯеҢ»дёӯиҚҜдёәдјӨз—…е‘ҳжІ»з–—пјҢвҖңеҜ№еҝ…йЎ»ејҖеҲҖеҠЁжүӢжңҜзҡ„жҖҘйҮҚдјӨе‘ҳпјҢйҮҮеҸ–иҘҝеҢ»иҘҝиҚҜжІ»з–—пјӣеӨ§еӨҡж•°з—…е‘ҳе’ҢиҪ»дјӨе‘ҳпјҢд»ҘдёӯеҢ»дёӯиҚҜдёәдё»жІ»з–—вҖқгҖӮдёәзӯ№йӣҶдёӯиҚҜжқҗ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жӣҫжҙҫйҒЈвҖңдёүеҚҒдәәе·ҰеҸіеңЁеҗ„ең°иҝӣиЎҢйҮҮиҙӯиҚҜжқҗвҖқпјҢдҪҶдҫқж—§йҡҫд»Ҙж»Ўи¶і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еәһеӨ§зҡ„з”ЁиҚҜйңҖжұӮпјҢвҖңе°ұжҳҜдёӯиҚҜд№ҹжҳҜйҡҫеј„еҲ°жүӢвҖқпјҢвҖңжңүж—¶еҮәеҺ»дёӨдёүдёӘжңҲиҝҳд№°дёҚеҲ°еҮ зҷҫж–ӨиҚҜеӣһжқҘвҖқгҖ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ҖҡиҝҮеңЁеҗ„еҢ»йҷўз»„з»ҮжҢ–иҚҜйҳҹпјҢеҠЁе‘ҳзҫӨдј—жҢ–иҚҜжқҗзӯүж–№ејҸиҺ·еҸ–дәҶиҫғеӨҡзҡ„дёӯиҚүиҚҜ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дё“й—Ёз»„з»ҮдәҶ60дҪҷдәәзҡ„жҢ–иҚҜйҳҹдјҚпјҢвҖңжңүдәәжҠҠгҖҠжң¬иҚүзәІзӣ®гҖӢеёҰеҲ°йҮҺең°еҺ»пјҢжҢүд№ҰдёҠжүҖжҸҸз»ҳзҡ„еӣҫж ·еңЁеңҹдёӯжҠҠе®ғжҢ–еӣһжқҘпјҢз»ҸиҝҮиҜ•йӘҢиҜҒжҳҺжҳҜжӯӨиҚҜзҡ„иҜқпјҢе°ұеӨ§йҮҸзҡ„жҢ–вҖқпјҢвҖңеңЁе·қеҢ—йҖҡеҚ—жұҹдёҖеёҰеӨ§зәҰиғҪжүҫеҲ°дёҖзҷҫеӨҡз§ҚдёӯиҚҜгҖӮеҪ“ең°иғҪдә§зҡ„иҚҜжҳҜеҸҜд»Ҙи§ЈеҶідәҶ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ёәи§ЈеҶіиӢҸеҢәжҡҙеҸ‘з–«з—…еҗҺдёӯиҚүиҚҜдҫӣз»ҷдёҚи¶і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пјҢ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иҝҳе№ҝжіӣең°еҸ‘еҠЁзҫӨдј—йҮҮиҚҜзҢ®иҚҜгҖӮвҖңз”ұеҢ»з”ҹжҚ®гҖҠжң¬иҚүзәІзӣ®гҖӢдёӯиҚҜжқҗзҡ„еҪўзҠ¶з»ҳеҲ¶жҲҗеӣҫж ·еј иҙҙеҗ„еӨ„пјҢж•ҷзҫӨдј—иҜҶеҲ«пјҢеҶҚеҸ‘еҠЁзҫӨдј—дёҠеұұйҮҮйӣҶгҖӮеҫҲеӨҡеҢәгҖҒд№ЎиӢҸз»ҙеҹғ规е®ҡжҜҸжңҲз”ұжқ‘иӢҸз»ҙеҹғз»„з»ҮзҫӨдј—пјҢиғҢдёҠиҚҜжқҗпјҢжү“дёҠзәўж——пјҢж•Ій”Јжү“йј“еҗ‘еҶӣйҳҹеҢ»йҷўе’Ңең°ж–№еҢ»йҷўзҢ®иҚҜдёҖж¬ЎгҖӮвҖқеҜ№жҢ–жҺҳеҲ°зҡ„дёӯиҚүиҚҜпјҢеҗ„еҢ»йҷўйҷӨз”Ёд»ҘзӮ®еҲ¶й…Қж–№зҡ„иҚҜжқҗеӨ–пјҢиҝҳжҲҗз«ӢдәҶеҲ¶иҚҜжңәжһ„д»ҘеҲ¶дҪңдёӯжҲҗиҚҜ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вҖңиҮӘеҲ¶дәҶеҶ…жңҚе’ҢеӨ–з”Ёзҡ„ж„ҹеҶ’дёёгҖҒеҚҒе…ЁеӨ§иЎҘдёёгҖҒжё…зӮҺж•ЈгҖҒзәўеҚҮдё№гҖҒзҷҪйҷҚдё№гҖҒй»‘иҚҜиҶҸзӯүеҮ еҚҒз§ҚдёӯжҲҗиҚҜгҖӮ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иҮӘеҲ¶зҡ„иҚҜе“ҒйҷӨж»Ўи¶іжң¬йҷўеӨ–пјҢиҝҳз»Ҹеёёж”ҜжҸҙеҗ„еҲҶеҢ»йҷўе’ҢзәўеҶӣеҗ„йғЁйҳҹзҡ„еҶӣгҖҒеёҲеҢ»йҷўвҖқгҖӮ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еҲҷеңЁеҲ¶дҪңдёӯжҲҗиҚҜ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иҝҳиҮӘеҲ¶дәҶйғЁеҲҶиӢҸеҢәжҖҘйңҖзҡ„иҘҝиҚҜгҖӮвҖңзәўеҶӣжҖ»еҢ»йҷўиҮӘеҲ¶зҡ„иҚҜе“ҒжңүйҳҝзүҮй…ҠгҖҒеӨҚж–№жЁҹи„‘й…ҠгҖҒиҝңеҝ—й…ҠгҖҒйҷҲзҡ®й…ҠгҖҒеӨҚж–№иұҶи”»й…ҠгҖҒзўҳеҢ–й’ҫж¶ІгҖҒзўҳй…Ҡе’ҢеӨ§й»„жөёеүӮгҖҒеӨ§й»„ж•ЈгҖҒзўій…ёй’ҷзӯүгҖӮвҖқжӯӨеӨ–пјҢиӢҸеҢә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иҝҳеӣ ең°еҲ¶е®ңпјҢеҲ©з”ЁдёӯиҚҜжӣҝд»ЈиӢҸеҢәзјәд№Ҹзҡ„йә»иҚҜгҖҒж¶ҲзӮҺиҚҜгҖҒжӯўз—ӣиҚҜзӯүиҘҝиҚҜпјҢ并е°ұең°еҸ–жқҗеҲ¶дҪңдәҶеҗ„з§Қз®Җжҳ“зҡ„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гҖӮиӯ¬еҰӮпјҢ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дёәдәҶз»ҷйҮҚдјӨе‘ҳеҠЁжүӢжңҜеҸ–еӯҗеј№пјҢвҖңе°ұз”ЁзҷҪй…’гҖҒзӣҗж°ҙж¶ҲжҜ’пјҢе°Ҷе·қз©№гҖҒеҚҠеӨҸеҪ“йә»йҶүиҚҜеүӮпјҢз”ЁзҢӘжІ№гҖҒзүӣжІ№еҒҡиҫ…ж–ҷй…ҚеҲ¶иҚҜиҶҸпјҢз”ЁеӨ§й»„жөёеүӮгҖҒеӨ§й»„жІ«дҪңдёәж¶ҲзӮҺиҚҜеүӮпјҢеҲ©з”Ёеәҹй“ҒгҖҒй“ңзәҝгҖҒй“ңзӯ·зӯүеҲ¶жҲҗй•ҠеӯҗгҖҒеҸ—ж°ҙеҷЁгҖҒж¶ҲжҜ’зў—гҖҒжҚўиҚҜзӣҳпјҢе°Ҷ银еёҒгҖҒ银йҰ–йҘ°жү“еҲ¶жҲҗжҺўй’ҲгҖҒиҖійј»й•ңзӯүвҖқпјҢжІЎжңүйҳІжІ»з ҙдјӨйЈҺзҡ„иҚҜе“ҒпјҢе°ұз”ЁвҖңзҺүзңҹж•ЈвҖқж•·дјӨеҸЈ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д№Ўжқ‘зӨҫдјҡеңЁжүҝиҪҪ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йқ©е‘ҪдәӢдёҡ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ж—ўеӣ е…¶зҺ°д»Јиө„жәҗеҢ®д№Ҹз»ҷйқ©е‘ҪиҖ…еёҰжқҘдәҶиҜёеӨҡеӣ°жү°пјҢд№ҹеӣ е…¶дј з»ҹиө„жәҗзҡ„дё°еҜҢиөӢдәҲдәҶйқ©е‘ҪиҖ…дёҖе®ҡзҡ„иЎҢдёәеј№жҖ§з©әй—ҙпјҢжңүж•Ҳзј“и§ЈдәҶе…¶иҝңзҰ»дәҺеҸ‘иҫҫеҹҺеёӮж–ҮжҳҺзҡ„зӘҳиҝ«дёҺз—ӣиӢҰгҖӮ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ҖҡиҝҮе№ҝжіӣеҲ©з”ЁдёӯеҢ»дёӯиҚҜпјҢ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ж»Ўи¶ідәҶ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әӢдёҡеҸ‘еұ•зҡ„йңҖжұӮпјҢвҖңж—ўйҖӮеә”еҪ“ж—¶зҫӨдј—е°ұеҢ»зҡ„дҝЎд»»е’Ңд№ жғҜпјҢд№ҹи§ЈеҶідәҶдёҙеәҠдёҠиҚҜжқҗдҫӣеә”зҡ„еӣ°йҡҫвҖқгҖӮеӣӣгҖҒиӢҸеҢә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зҺ°е®һеӨ„еўғ д»Һе®Ҹи§Ӯж–№йқўжқҘзңӢпј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•‘жІ»гҖҒзңӢжҠӨдәҰжҳҜеҜ№еҢ»йҷўеҗҺеӢӨдҝқйҡңиғҪеҠӣд№ғиҮіж•ҙдёӘиӢҸеҢәеҗҺеӢӨе·ҘдҪңзҡ„йҮҚиҰҒиҖғйӘҢгҖӮеӣ иҖҢ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йҷӨжһ„е»әзі»з»ҹе®ҢеӨҮзҡ„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пјҢдёәдјӨз—…е‘ҳжҸҗдҫӣеҝ…иҰҒзҡ„еҢ»з–—зү©иө„е’ҢеҢ»жҠӨиө„жәҗзӯүеҢ»з–—дҝқйҡңеӨ–пјҢиҝҳд»Һ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иҪ¬иҝҗгҖҒйҘ®йЈҹгҖҒзІҫзҘһжҠҡж…°е’Ңзү©иҙЁдјҳжҠҡзӯүйўҶеҹҹзқҖжүӢпјҢйҖҡиҝҮеҠӘеҠӣд»ҘжұӮж”№еҸҳ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иү°йҡҫз”ҹеӯҳеӨ„еўғгҖӮе…¶дёҖ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ж—¶жңҹ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е°ҪеҠӣдҪҝдјӨз—…е‘ҳеӨ§йғҪиғҪеҫ—еҲ°еҸҠж—¶зҡ„иҪ¬иҝҗе’ҢжІ»з–—гҖӮзәўеҶӣе…Ҙе·қеҗҺе»әз«ӢдәҶзі»з»ҹзҡ„дјӨз—…е‘ҳиҪ¬иҝҗдёҺжҠўж•‘дҪ“зі»пјҢвҖңдјӨз—…еҗҢеҝ—д№ӢеҗҺйҖҒйҒ“и·ҜеҸҠеҗ„еёҲгҖҒеӣўеҢ»еҠЎеӨ„гҖҒжүҖпјҢжҲҳж–—ж—¶д№ӢдҪҚзҪ®йЎ»жҳҺзҷҪжҢҮзӨәвҖқгҖӮйҷӨжҳҺзЎ®еҢ»йҷўеҸҠеҗ„жҲҳж–—йғЁйҳҹзҡ„еҮҶзЎ®ең°еқҖеӨ–пјҢзәўеҶӣиҝҳ规иҢғдәҶ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иҪ¬иҝҗжөҒзЁӢгҖӮвҖңдёҖиҲ¬з”ұеӣўйҖҒеёҲгҖҒеёҲйҖҒеҶӣпјҢеҶӣеҢ»йҷўеҲҷйҡҸйғЁйҳҹеңЁеүҚж–№ејҖи®ҫеҢ»йҷўгҖӮйғЁйҳҹиҪ¬з§»ж—¶пјҢжңүеҶӣеҢ»йҷўеҗ‘еҗҺж–№еҢ»йҷўиҪ¬йҖҒзҡ„пјҢд№ҹжңүеёҲеӣўзӣҙжҺҘиҪ¬йҖҒеҗҺж–№еҶӣеҢ»йҷўзҡ„пјҢеҶӣеҢ»йҷўзҡ„йҮҚдјӨз—…е‘ҳе°ұиҪ¬йҖҒеҲ°жҖ»еҢ»йҷўгҖӮвҖқеӣ иҖҢпј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иҪ¬иҝҗе’Ңж•‘жІ»иҫғдёәеҸҠж—¶гҖӮвҖңйӮЈж—¶пјҢеҮ д№ҺеӨ©еӨ©йғҪеңЁжү“д»—пјҢйҡҸж—¶йғҪжңүд»ҺеүҚзәҝйҖҒдёӢжқҘзҡ„дјӨз—…е‘ҳпјҢеҝ…йЎ»йҡҸеҲ°йҡҸ收пјӣйҒҮжңүйҮҚдјӨе‘ҳпјҢиҝҳиҰҒз«ӢеҚіз»„з»ҮжҠўж•‘гҖӮвҖқе…¶дәҢпјҢ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еҗ„зә§жңәе…ід№ҹеҚҒеҲҶйҮҚи§ҶеҢ»йҷўзҡ„зІ®йЈҹгҖҒиҗҘе…»е“Ғзӯүз”ҹжҙ»зү©иө„зҡ„дҫӣеә”пјҢз«ӯеҠӣдёә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еә·еӨҚжҸҗдҫӣе……и¶ізҡ„иҗҘе…»дҝқйҡңгҖӮеҰӮпјҢдёәи§ЈеҶіеҢ»йҷўзҡ„зү©иө„дҫӣеә”пјҢе·қйҷ•зңҒ委е’Ңж”ҝеәңеҸ·еҸ¬зҫӨдј—зғӯзғҲжӢҘжҠӨеҢ»йҷўпјҢвҖңжӢҘжҠӨдјӨз—…еҸ·вҖқгҖӮеңЁеҗ„зә§е…ҡз»„з»Үе’ҢиӢҸз»ҙеҹғж”ҝеәңзҡ„еҸ·еҸ¬дёӢпјҢ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жӢҘжҠӨеҢ»йҷўзҡ„зғӯжғ…й«ҳж¶ЁгҖӮвҖңжҜҸеҪ“еҢ»йҷўдјӨз—…е‘ҳеўһеӨҡпјҢзҫӨдј—е°ұиҮӘеҠЁеё®еҠ©еҢ»йҷўжҠ¬жӢ…жһ¶пјҢи…ҫжҲҝеӯҗпјҢжү“жү«еҚ«з”ҹгҖӮ他们йҖҒжқҘзІ®йЈҹгҖҒзҢӘиӮүгҖҒйёЎиӣӢд»ҘеҸҠеёғйһӢгҖҒиўңеә•гҖҒиҚүйһӢзӯүз”ҹжҙ»з”Ёе“ҒпјҢж…°й—®дјӨз—…е‘ҳе’ҢеҢ»йҷўзҡ„еҗҢеҝ—гҖӮвҖқе…ҡе’ҢзәўеҶӣзҡ„еҗ„зә§йўҶеҜје№ІйғЁд№ҹвҖңеңЁз”ҹжҙ»дёҠеӨҡж–№з…§йЎҫпјҢеҮЎиҮӘе·ұз”ҹдә§зҡ„жҲ–жү“еңҹиұӘе’ҢжҲҳеңәзјҙиҺ·жқҘзҡ„йЈҹзү©пјҢйғҪжіЁж„Ҹдјҳе…Ҳз…§йЎҫдҪҸйҷўдјӨз—…е‘ҳвҖқгҖӮеҪјж—¶пј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йЈҹе“Ғдҫӣеә”д№ҹиҫғдёәе……и¶ігҖӮвҖңеҢ»йҷўжңү规е®ҡпј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иҗҘе…»зү©иө„е°Ҫз®Ўйҡҫд»ҘдҝқиҜҒпјҢдҪҶеҗғйҘұдёүйӨҗйҘӯиҰҒдҝқиҜҒпјҢиҰҒйҖӮеҪ“з»ҷйҮҚз—…еҸ·еҠ ејәйёЎиӣӢгҖҒйЈҹзі–зӯүйҘ®йЈҹж–№йқўзҡ„з…§йЎҫгҖӮвҖқеҗҢж—¶пјҢеҢ»йҷўиҝҳйҮҚи§Ҷз…§йЎҫ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йҘ®йЈҹд№ жғҜпјҢвҖңжҲ‘们зҡ„дјӨз—…е‘ҳпјҢеӨҡеҚҠжҳҜжң¬ең°дәәпјҢд»–д»¬д№ жғҜеҗғй…ёзҡ„пјҢиҝҷжҳҜ他们жңҖдҪҺзҡ„еҗҲзҗҶиҰҒжұӮпјҢжҳҜе®Ңе…ЁиғҪеҠһеҲ°зҡ„вҖқгҖӮе…¶дёүпјҢзІҫзҘһжҠҡж…°е’Ңзү©иҙЁдёҠзҡ„дјҳеҫ…дәҰжҳҜдёҚеҸҜжҲ–зјәзҡ„гҖӮ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Җқжғіж”ҝжІ»ж•ҷиӮІдё»иҰҒдҫқжүҳе…ҡж”ҜйғЁејҖеұ•пјҢеҗ„еҢ»йҷўвҖңж №жҚ®з—…жҲҝжғ…еҶөз»„з»ҮдәҶдј‘е…»иҝһпјҢжҲҗз«ӢдәҶдј‘е…»е‘ҳе…ҡеӣўж”ҜйғЁпјҢиҝҮз»„з»Үз”ҹжҙ»вҖқпјҢвҖңжҲ‘们иҝҳеңЁдјӨз—…е‘ҳдёӯйҖүеҮәиҝһй•ҝгҖҒжҢҮеҜје‘ҳпјҢз—…жҲҝдёӯзҡ„жҖқжғіж•ҷиӮІе·ҘдҪңз”ұ他们иҙҹиҙЈжҠ“гҖӮеҜ№йҮҚдјӨз—…е‘ҳиҝһпјҢеҲҷз”ұеҢ»йҷўж”ҝжІ»йғЁжҙҫе№ІдәӢиҙҹиҙЈз—…жҲҝдёӯзҡ„жҖқжғіе·ҘдҪңвҖқгҖӮдёәдё°еҜ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–ҮеҢ–з”ҹжҙ»пјҢжҖ»еҢ»йҷўиҝҳз»„з»Үеҗ„з§ҚеЁұд№җжҙ»еҠЁпјҢд»ҘиҲ’зј“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ғ…з»Ә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ј зҗҙз§ӢвҖңжҠҠеҢ»йҷўйҮҢзҡ„е°ҸеҗҢеҝ—з»„з»Үиө·жқҘпјҢеҠһиө·е®Јдј йҳҹпјҢдәІиҮӘж•ҷеҘ№д»¬и·ій«ҳеҠ зҙўиҲһпјҢе”ұгҖҠе…«жңҲжЎӮиҠұгҖӢгҖҒгҖҠж…°й—®дјӨе‘ҳе°Ҹе”ұгҖӢзӯүжӯҢжӣІпјҢжҺ’з»ғеҘҪеҗҺпјҢеҸҲеёҰзқҖ他们ж·ұе…ҘеҲ°еҗ„еҢ»йҷўз—…жҲҝж…°й—®жј”еҮәгҖӮжңүж—¶еҘ№иҝҳдәІиҮӘдёәдјӨз—…е‘ҳжӯҢе”ұпјҢдҪҝдјӨз—…е‘ҳж„ҹеҸ—еҲ°еҗҢеҝ—й—ҙзҡ„дәІеҲҮжғ…и°Ҡе’Ңйқ©е‘ҪеӨ§е®¶еәӯзҡ„жё©жҡ–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жҖ»еҢ»йҷўиҝҳзү№еҲ«йҮҚи§Ҷд»ҺзІҫзҘһдёҠеҮҸиҪ»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ҖқжғіиҙҹжӢ…гҖӮвҖңеј зҗҙз§Ӣдё»д»»з»Ҹеёёж·ұе…Ҙз—…жҲҝпјҢе’ҢдјӨз—…е‘ҳи°ҲиҜқгҖҒж‘Ҷйҫҷй—ЁйҳөпјҢиҜўй—®д»–们зҡ„家еәӯжғ…еҶөпјҢе®ү慰他们еҘҪеҘҪе…»дјӨжІ»з—…гҖӮвҖқиӢҸдә•и§ӮзӯүдәәеҲҷеҲӣеҠһдәҶгҖҠиЎҖиҠұжҠҘгҖӢпјҢвҖңйј“еҠұдјӨз—…е‘ҳз§ҜжһҒй…ҚеҗҲ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жІ»з–—жҠӨзҗҶпјҢиЎЁжү¬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е’Ңдј‘е…»е‘ҳдёӯзҡ„еҘҪдәәеҘҪдәӢпјҢиҝҳе®Јдј еҚ«з”ҹдҝқеҒҘе’Ңз–ҫз—…йҳІжІ»зҹҘиҜҶвҖқгҖӮе…¶еӣӣпјҢиӢҸеҢәиҝҳеҲ¶е®ҡдәҶзәўеҶӣдјӨдәЎжҠҡжҒӨеҲ¶еәҰпјҢи§ЈеҶіеҸ—дјӨжҲҳеЈ«зҡ„еә·еӨҚз–—е…»й—®йўҳгҖӮеҰӮ规е®ҡпјҢвҖңзәўеҶӣеңЁжңҚеҠЎжңҹй—ҙпјҢеӣ дјӨз—…йЎ»дј‘е…»ж—¶пјҢеә”йҖҒеҲ°жңҖйҖӮе®ңд№Ӣдј‘е…»жүҖдј‘е…»пјҢеңЁдј‘е…»жңҹй—ҙдёҖеҲҮиҙ№з”Ёз”ұеӣҪ家дҫӣз»ҷвҖқпјҢвҖңеӣҪ家и®ҫз«Ӣж®ӢеәҹйҷўпјҢеҮЎеӣ жҲҳдәүеңЁзәўеҶӣжңҚеҠЎдёӯиҖҢж®ӢеәҹиҖ…е…Ҙйҷўдј‘е…»пјҢдёҖеҲҮз”ҹжҙ»иҙ№з”Ёз”ұеӣҪ家дҫӣз»ҷгҖӮдёҚж„ҝеұ…ж®ӢеәҹйҷўиҖ…пјҢжҢүе№ҙз»ҷз»Ҳиә«дјҳжҒӨйҮ‘пјҢз”ұеҗ„еҺҝиӢҸз»ҙеҹғжҢүеҪ“ең°з”ҹжҙ»жғ…еҪўиҖҢе®ҡпјҢдҪҶзҺ°ж—¶жҜҸе№ҙиҮіе°‘дә”еҚҒе…ғеӨ§жҙӢвҖқгҖӮиҝҷдәӣж”ҝзӯ–е’ҢдёҫжҺӘзҡ„ж–ҪиЎҢдҪҝдјӨз—…е‘ҳеӨҮеҸ—йј“иҲһпјҢеқҮиғҪз§ҜжһҒй…ҚеҗҲжІ»з–—пјҢд»ҺиҖҢиҫғеҝ«ең°жҒўеӨҚиә«дҪ“еҒҘеә·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иӢҸеҢәзҡ„еҢ»з–—жңәжһ„еңЁж•‘жІ»жҲҳдәүеҲӣдјӨгҖҒжү‘зҒӯжөҒиЎҢжҖ§з–«з—…гҖҒеҮҸиҪ»зәўеҶӣе’Ң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зҡ„дјӨдәЎ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Ҹ‘жҢҘдәҶдёҚеҸҜжӣҝд»Ј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йҡҸзқҖ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Ҫ“зі»зҡ„е»әз«Ӣе’Ңе®Ңе–„пјҢжӮЈз–ҫе’ҢеҸ—дјӨзҡ„еҶӣж°‘еӨ§еӨҡиғҪеҫ—еҲ°жңүж•Ҳзҡ„жІ»з–—пјҢи®ёеӨҡ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д№ҹдёҚз”ЁеҶҚйҘұеҸ—з–ҫз—…иӮҶиҷҗиҖҢж— еҢ»ж— иҚҜд№ӢиӢҰ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1934е№ҙиӢҸеҢәжөҒиЎҢжҖ§з–ҫз—…зҢ–зҚ—пјҢд»…вҖң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дҪҸйҷўз—…дәәеӨҡиҫҫ2200дәәпјҢеҗ„еҺҝе·ҘеҶңеҲҶеҢ»йҷўдҪҸйҷўз—…дәәд№ҹиҫҫеҲ°500дәәгҖӮйҖҡиҝҮеҢ»йҷўиү°иӢҰеҠӘеҠӣпјҢз»қеӨ§йғЁеҲҶиў«жІ»ж„ҲвҖқгҖӮзәўеҶӣеңЁеӣӣе·қзҡ„дёӨе№ҙеӨҡж—¶й—ҙйҮҢпјҢвҖңд»…еңЁе·ҘеҶңжҖ»еҢ»йҷўеҸҠе…¶дёӢеұһеҲҶеҢ»йҷўе…ұжІ»ж„ҲдјӨз—…е‘ҳ2.3дёҮеҗҚпјҢ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дҝқйҡңдәҶеҶӣж°‘иә«дҪ“еҒҘеә·вҖқгҖӮеҲ°зәўеӣӣж–№йқўеҶӣиҘҝжёЎеҳүйҷөжұҹд№Ӣж—¶пјҢзәўеҶӣжүҖеұһзҡ„жҖ»еҢ»йҷўе’ҢдёғдёӘеҲҶйҷўе…ұжңү1.1дёҮдҪҷеҗҚдјӨз—…е‘ҳпјҢвҖңе…Ёз”ұеҰҮеҘіжӢ…жһ¶йҳҹе’ҢзҫӨдј—жӢ…жһ¶йҳҹиҝҗйҖҒгҖӮеңЁеү‘йҳҒеҒңз•ҷдёҖдёӘжңҲпјҢз§ҜжһҒејҖеұ•жІ»з–—пјҢеӨ§еӨҡж•°дјӨз—…е‘ҳжІ»ж„ҲеҮәйҷўеҪ’йҳҹвҖқгҖӮеҸҚи§ӮеӣҪж°‘е…ҡеЈ«е…өе’ҢзҷҪеҢәзҫӨдј—зҡ„дёӘдәәйҒӯйҒҮпјҢжҲ‘们жҲ–еҸҜд»ҘзӘҘи§ҒеӣҪе…ұеҸҢж–№еңЁејҖеұ•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еҠӣеәҰдёҺеҝғжҖҒдёҠеӯҳеңЁзҡ„е·®и·қгҖӮ1934е№ҙ9жңҲпјҢгҖҠзәўиүІдёӯеҚҺгҖӢжӣҫжҠҘйҒ“иҝҮеӣӣе·қзҷҪеҢәеҸҠеӣҪж°‘е…ҡеҶӣйҳҹеЈ«е…өзҡ„еҢ»з–—еўғеҶөпјҢеҪјж—¶дёҮжәҗзӯүеҺҝж—¶з–«еӨ§еҸ‘пјҢз”ұдәҺвҖңеҢ»иҚҜдёӨзјәвҖқпјҢиў«дј жҹ“иҖ…вҖңеҸӘжңүеқҗиҖҢеҫ…дәЎпјҢеӣ жӯӨжӯ»иҖ…蔓延дёҚжӯўпјҢзҺ°е№іеқҮжҜҸжҲ·жңүдәҢдәәд»ҘдёҠжӯ»дәЎвҖқпјҢвҖңе…өеӨ«зҡ„жӯ»дәЎпјҢд№ҹеҲ°еӨ„йғҪжҳҜпјҢе°Өд»ҘеӨ«еҪ№дёәеӨҡвҖқ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дјӨз—…е‘ҳзҡ„ж•‘жҠӨжҳҜеӣҪе…ұеҸҢж–№еңЁжҲҳдәүдёӯйқўдёҙзҡ„е…ұжҖ§й—®йўҳпјҢ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д№ҹжҳҜйқ©е‘ҪиҝӣзЁӢзҡ„дёҖдёӘдҫ§йқўпјҢиҖҢж”ҝжІ»зҗҶеҝөд№Ӣй—ҙзҡ„е·®ејӮпјҢеҲҷжҳҜйҖ жҲҗеӣҪе…ұеҸҢж–№еңЁж•‘жҠӨдјӨз—…е‘ҳдёҠ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ҒжҲҗж•Ҳеҗ„ејӮзҡ„ж №жәҗгҖӮд»ҘвҖңдёәж°‘и°ӢзҰҸеҲ©вҖқдҪңдёәж №жң¬ж”ҝжІ»дҝЎеҝөзҡ„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пјҢиғҪжё…жҘҡи®ӨиҜҶеҲ°иҮӘиә«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дёӯеӯҳеңЁзҡ„зјәйҷ·дёҺе…ҲеӨ©дёҚи¶іпјҢеқҡжҢҒд»ҘдҝқйҡңиӢҸеҢәеҶӣж°‘зҡ„иә«дҪ“еҒҘеә·дёәе·ұд»»пјҢ并еңЁе»әи®ҫиӢҸеҢә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дәӢдёҡзҡ„иү°йҡҫиҝӣзЁӢдёӯзӯҡи·Ҝи“қзј•гҖҒеӨҡз®ЎйҪҗдёӢпјҢз«ӯеҠӣиЎҘйҪҗеҢ»з–—жңәжһ„дёҚеҒҘе…ЁгҖҒеҢ»жҠӨдәәе‘ҳдёҚи¶ігҖҒеҢ»з–—з”Ёе“ҒеҢ®д№ҸгҖҒдјӨз—…е‘ҳж•‘жІ»з…§жҠӨдёҚе‘Ёзӯүж—ўеӯҳзҹӯжқҝпјҢ并еҸ–еҫ—дәҶзӣёеҪ“зҡ„ж•ҲжһңгҖӮд»ҺеҢ»з–—еҚ«з”ҹе·ҘдҪңзҡ„и§’еәҰжқҘзңӢпјҢиҝҷжҲ–и®ёд№ҹжҳҜе·қйҷ•иӢҸеҢәиғҪеңЁж•ҢжҲ‘иө„жәҗдёҘйҮҚдёҚеҜ№зӯү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е§Ӣз»ҲдҝқжҢҒзәўеҶӣж—әзӣӣзҡ„жҲҳж–—ж„Ҹеҝ—пјҢиөўеҫ—иӢҸеҢәзҫӨдј—е…ЁеҠӣж”ҜжҸҙе’ҢжӢҘжҠӨпјҢиҝӣиҖҢе…ҲеҗҺдёӨж¬ЎзІүзўҺж•ҢдәәйҮҚе…өвҖңеӣҙеүҝвҖқзҡ„йҮҚиҰҒеҺҹеӣ д№ӢдёҖ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зҺӢиҪІ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5жңҹвҖңеҺҶеҸІдёҺж–ҮеҢ–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 зҪ—еҝ—жҒ’пјҡ2025е№ҙиҙўж”ҝеҰӮ
зҪ—еҝ—жҒ’пјҡ2025е№ҙиҙўж”ҝеҰӮ е‘Ёжө©пјҡвҖңејәзҫҺе…ғвҖқиҝҳиғҪ
е‘Ёжө©пјҡвҖңејәзҫҺе…ғвҖқиҝҳиғҪ зҷҫдә©ж°ёд№…еҶңз”°ж”№з§ҚжҷҜи§Ӯ
зҷҫдә©ж°ёд№…еҶңз”°ж”№з§ҚжҷҜи§Ӯ еӨҜе®һзІ®йЈҹдә§иғҪ з«Ҝзүўдёӯ
еӨҜе®һзІ®йЈҹдә§иғҪ з«Ҝзүўдёӯ ж–°еҸ‘еұ•йҳ¶ж®өжҺЁеҠЁд№Ўжқ‘жҢҜ
ж–°еҸ‘еұ•йҳ¶ж®өжҺЁеҠЁд№Ўжқ‘жҢҜ еҲҳз…ңиҫүжңҖж–°жј”и®Іе…Ёж–Үпјҡ
еҲҳз…ңиҫүжңҖж–°жј”и®Іе…Ёж–Үпјҡ еҲҳй”ӢпјҡеӯҳйҮҸиө„дә§иҜҒеҲёеҢ–
еҲҳй”ӢпјҡеӯҳйҮҸиө„дә§иҜҒеҲёеҢ–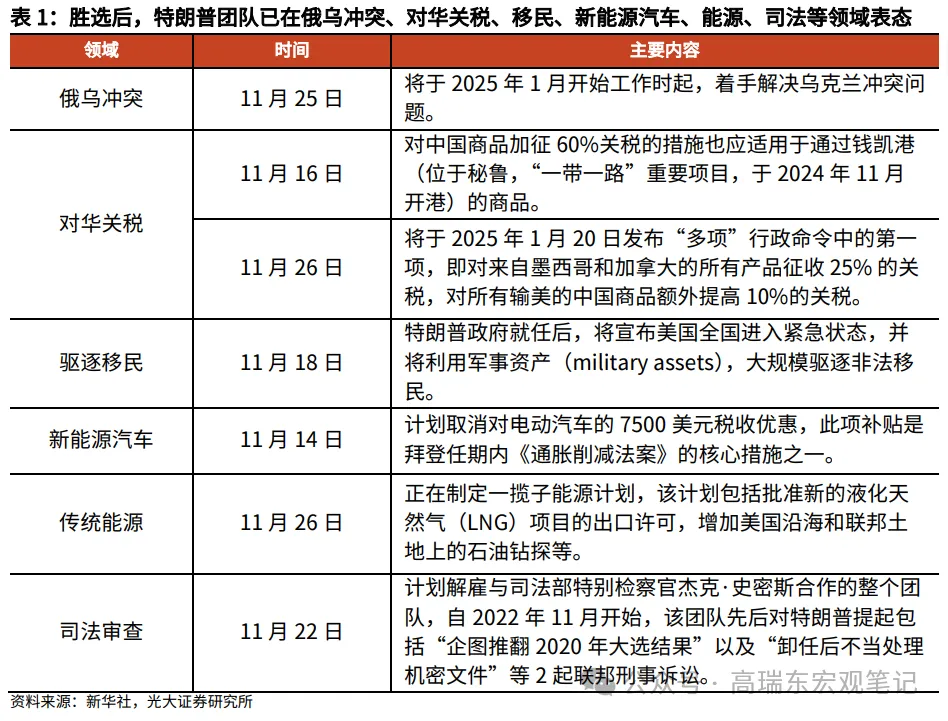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д»ҺжӢңзҷ»еҲ°зү№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д»ҺжӢңзҷ»еҲ°зү№ и°·зү©зЈЁеҲ¶йҮҚеӨ§дәӢж•…йҡҗжӮЈ
и°·зү©зЈЁеҲ¶йҮҚеӨ§дәӢж•…йҡҗжӮЈ д»ҳжҢҜеҘҮпјҡ家жҲ·е…ізі»и§Ҷи§’
д»ҳжҢҜеҘҮпјҡ家жҲ·е…ізі»и§Ҷи§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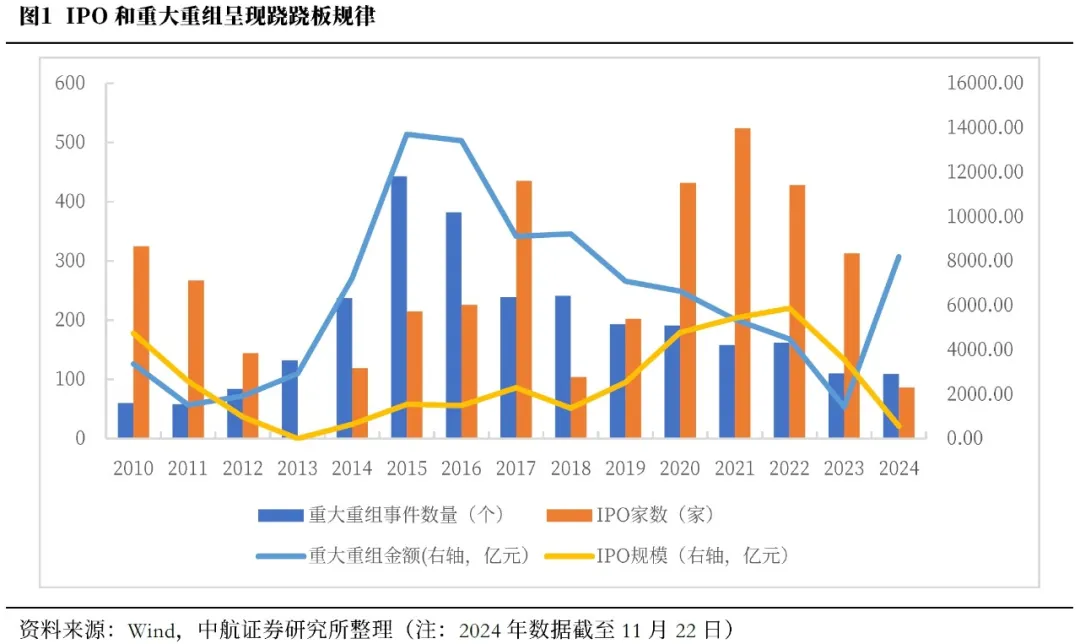 и‘Јеҝ дә‘зӯүпјҡе…іжіЁж–°дёҖиҪ®
и‘Јеҝ дә‘зӯүпјҡе…іжіЁж–°дёҖиҪ® зҪ—еҝ—жҒ’зӯүпјҡеҶ…йҳҒжҲҗе‘ҳжҖқ
зҪ—еҝ—жҒ’зӯүпјҡеҶ…йҳҒжҲҗе‘ҳжҖқ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