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е°№иҚЈж–№пјҢз”·пјҢдёҠжө·жө·е…іеӯҰйҷўе…¬е…ұж•ҷеӯҰйғЁж•ҷжҺҲгҖӮ
гҖҠеҸ¬еҚ—В·иЎҢйңІгҖӢжҳҜ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дёӯзҡ„еҗҚзҜҮд№ӢдёҖпјҢиҜҘиҜ—е…ід№ҺзӢұи®је№¶ж— з–‘д№үгҖӮдҪҶз”ұдәҺжӯӨиҜ—йҰ–з« еўғз•Ңзҡ„иҝ·зҰ»жғқжҒҚпјҢд»ҘеҸҠдәҢгҖҒдёүз« вҖңйӣҖж— и§’вҖқвҖңйј ж— зүҷвҖқж„ҸиұЎзҡ„иҜҳеұҲиҙ№и§ЈзӯүпјҢиҮҙдҪҝе…¶дё»ж—ЁдёҖзӣҙиҒҡи®јзә·зәӯгҖӮеӨ§иҮҙиҜҙжқҘпјҢжңүвҖң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вҖқвҖңеҘіеӯҗе®ҲзӨјиҮҙи®јвҖқвҖңз”іеҘіе®ҲзӨјиҮҙи®јвҖқвҖңзҗҶе®ҳеҲӨзӢұд№ӢиҫһвҖқвҖңеҜЎеҰҮжү§иЎҢдёҚиҙ°вҖқвҖңеӘ’еҰҒд№ӢиЁҖдёҚе’ҢвҖқвҖңиҙ«еЈ«еҚҙжҳҸиҮҙи®јвҖқвҖңжӢ’з»қе·Іе©ҡз”·еӯҗвҖқвҖңжҠ—и®®ејәиҝ«дҪңеҰҫвҖқвҖңеӨ«еҰ»зә зә·иҮҙи®јвҖқвҖңжңӘе©ҡдёҲеӨ«иҫ©и§ЈвҖқвҖңеҘіеӯҗ家й•ҝзӯ”еӨҚвҖқзӯүеӨҡз§ҚиҜҙжі•гҖӮе…¶дёӯд»ҘгҖҠиҜ—еәҸгҖӢзҡ„вҖң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вҖқиҜҙеҪұе“ҚжңҖеӨ§пјҡв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д№ҹгҖӮиЎ°д№ұд№Ӣдҝ—еҫ®пјҢиҙһдҝЎд№Ӣж•ҷе…ҙпјҢ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дёҚиғҪдҫөеҮҢиҙһеҘід№ҹгҖӮвҖқжҲ‘们иҜҰе‘ігҖҠиҜ—еәҸгҖӢеҸҠжҜӣгҖҒйғ‘зҡ„з”іи®әзӯүпјҢеҸ‘зҺ°жӯӨиҜҙеҸҠеҸӨд»ҠеӯҰиҖ…д№ӢиҜҙзҡҶжңүеҫ…е•ҶжҰ·гҖӮжӯӨиҜ—еҪ“жҚ®д»ӘејҸиҲһи№Ҳж”№еҶҷиҖҢжҲҗпјҢеҸҚжҳ дәҶиҜ—гҖҒд№җгҖҒиҲһдёүдҪҚдёҖдҪ“зҡ„вҖңиҜ—ж•ҷвҖқиЎЁзҺ°еҪўејҸгҖӮдёҖгҖҒ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дёҺвҖң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қд№ӢвҖң鹑йҰ–вҖқ е…ідәҺ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дёҖиҜ—зҡ„дё»ж—ЁпјҢдәүи®әиҫғеӨҡзҡ„жҳҜеҜ№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дёӨеҸҘзҡ„зҗҶи§ЈгҖӮжҜӣгҖҒйғ‘и§ЈжӯӨдёӨеҸҘпјҢеҸҜи°“з…һиҙ№иӢҰеҝғгҖӮжҜӣгҖҠдј 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ёҚжҖқзү©еҸҳиҖҢжҺЁе…¶зұ»пјҢ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пјҢдјјжңүи§’иҖ…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гҖҠз¬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пјҢеҸҳејӮд№ҹгҖӮдәәзҡҶи°“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дјјжңүи§’пјҢ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пјҢеҸ¬жҲ‘иҖҢзӢұпјҢдјјжңүе®Ө家д№ӢйҒ“дәҺжҲ‘д№ҹгҖӮзү©жңүдјјиҖҢдёҚеҗҢпјҢ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дёҚд»Ҙи§’пјҢд№ғд»Ҙе’®пјҢд»Ҡ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еҸ¬жҲ‘иҖҢзӢұпјҢдёҚд»Ҙе®Ө家д№ӢйҒ“дәҺжҲ‘пјҢд№ғд»ҘдҫөеҮҢгҖӮзү©дёҺдәӢжңүдјјиҖҢйқһиҖ…пјҢеЈ«еёҲжүҖеҪ“е®Ўд№ҹгҖӮвҖқжҜӣгҖҒйғ‘зҡҶи°“вҖңдјјжңүи§’вҖқпјҢжҳҜеҗҰе®ҡйӣҖжңүи§’пјҢд»ҘжӯӨиҜҙжҳҺ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дҫөеҮҢдјјжҳҜиҖҢйқһгҖӮй’ұй’ҹд№Ұе…Ҳз”ҹдјји®ӨеҗҢжҜӣгҖҒйғ‘д№ӢиҜҙдә‘пјҡвҖңжҳҺзҹҘдәӢд№ӢдёҚ然пјҢиҖҢеҸҚиҜҚиҙЁиҜҳпјҢд»ҘиҜҒ其然пјҢжӯӨжӯЈиҜ—дәәеҰҷз”ЁгҖӮвҖқдҪҶ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пјҢвҖң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пјҢдјјжңүи§’иҖ…вҖқд№Ӣи§ЈйҮҠпјҢи®©дәәи§үеҫ—дёҚеҸҜзҗҶи§ЈпјҢжҜӣгҖҒйғ‘д№ӢжіЁи§ЈпјҢдјјзҡҶиҝӮжӣІйҡҫйҖҡгҖӮ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пјҢе…ід№ҺеҜ№иҜ—ж—Ё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дёҚиғҪдёҚиҫЁгҖӮеҗҺжқҘдёҚе°‘еӯҰиҖ…д»ҘвҖңйёҹе–ҷвҖқи§ЈиҜ—дёӯзҡ„вҖңйӣҖи§’вҖқгҖӮеҰӮдҝһжЁҫгҖҠзҫӨз»Ҹе№іи®®гҖӢеҚ·е…«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дј гҖӢгҖҒгҖҠз¬әгҖӢд№Ӣж„ҸпјҢзҡҶи°“йӣҖе®һж— и§’пјҢж•…е…¶иҜҙеҰӮжӯӨгҖӮ然дёӢз« дә‘пјҡвҖҳи°Ғи°“йј ж— зүҷ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ўүвҖҷпјҢйј д№Ӣз©ҝеўүпјҢиӢҘдёҚд»ҘзүҷпјҢеӨҚд»ҘдҪ•зү©д№ҺпјҹдёӨз« ж–Үд№үдёҖеҫӢпјҢйј е®һжңүзүҷпјҢеҲҷйӣҖдәҰе®һжңүи§’гҖӮзӘғз–‘жүҖи°“и§’иҖ…пјҢеҚіе…¶е–ҷд№ҹгҖӮйёҹе–ҷе°–й”җпјҢж•…и°“д№Ӣи§’гҖӮвҖқдҝһжЁҫд»Ҙйёҹе–ҷи§ЈвҖңйӣҖи§’вҖқпјҢдёәдёҚе°‘еӯҰиҖ…иөһеҗҢгҖӮдҝһжЁҫд№ӢеүҚпјҢжҜӣеҘҮйҫ„зӯүе·Ід»ҘвҖңйӣҖи§’вҖқдёәвҖңйёҹе–ҷвҖқ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Ҳ‘们дҪ•жӣҫи§ҒиҝҮйёҹйӣҖеҰӮйј зұ»йӮЈж ·з©ҝеўҷе…ҘеұӢпјҹйә»йӣҖгҖҒзҮ•еӯҗзӯүе·ўдәәеұӢжӘҗпјҢд»ҺжңӘи§Ғжңүдәәз”ЁйӣҖи§’з©ҝеұӢжқҘеҪўе®№пјҢеҸҜи§ҒиҜ—дәәиҝҷйҮҢиҜҙзҡ„з»қйқһзҮ•йӣҖе·ўдәәеұӢжӘҗд№ӢдәӢгҖӮдҝһжЁҫд»Ҙйј д№Ӣз”Ёзүҷз©ҝеўүдёәжҳҺзҷҪж— иҜҜпјҢеҲҷвҖңж–Үж„ҸдёҖеҫӢвҖқзҡ„еүҚз« еҸҲдҪ•д»Ҙз”Ёд»Өдәәиҙ№и§Јзҡ„йӣҖи§’з©ҝеұӢдҪңжҜ”е‘ўпјҹжҜ”иҫғеҗҲзҗҶзҡ„и§ЈйҮҠжҳҜпјҢйӣҖи§’з©ҝеұӢеҸҜиғҪд№ҹжҳҜеҪјж—¶дәәд»¬д№ и§Ғд№Ӣжғ…жҷҜпјҢеҸӘжҳҜеҗҺдәәдёҚи§ЈжӯӨжғ…жӯӨжҷҜзҪўдәҶгҖӮ笔иҖ…д»ҘдёәпјҢд»ҘвҖңдјјжңүи§’вҖқеҸҠвҖңйёҹе–ҷвҖқи§ЈйҮҠ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вҖқпјҢе°ҡжңӘиҫҫе…¶ж—ЁгҖӮжӯӨиҜ—д№ӢвҖңйӣҖвҖқпјҢд№ғеӨ©дёҠвҖң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қд№ӢвҖң鹑йҰ–вҖқд№ҹгҖӮвҖң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қдёәдә•гҖҒй¬јгҖҒжҹігҖҒжҳҹгҖҒеј гҖҒзҝјгҖҒиҪёдёғдёӘжҳҹе®ҝгҖӮе…¶дёӯдә•гҖҒй¬јдёӨе®ҝдёәвҖң鹑йҰ–вҖқгҖӮең°дёҠйёҹ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иҖҢеӨ©дёҠзҡ„жҳҹеә§еҚҙеҸҜд»ҘвҖңи§’вҖқеҗҚд№ӢпјҢеҰӮи§ңе®ҝд№ӢвҖңи§ңвҖқеҚід»Һи§’гҖӮйӣҖд№Ӣз©ҝеұӢпјҢеҫҲеҸҜиғҪжҳҜз”ЁжқҘжҸҸиҝ°вҖң鹑йҰ–вҖқиҝҗиЎҢйҖҡиҝҮе®ӨеұӢж—¶зҡ„жғ…жҷҜгҖӮгҖҠеӨ§жҲҙзӨји®°В·еӨҸе°ҸжӯЈгҖӢдёғжңҲдә‘пјҡвҖңжұүжЎҲжҲ·гҖӮеҚўиҫ©жіЁпјҡвҖҳжұүд№ҹиҖ…пјҢжІід№ҹгҖӮжЎҲжҲ·д№ҹиҖ…пјҢзӣҙжҲ·д№ҹпјҢиЁҖжӯЈеҚ—еҢ—д№ҹгҖӮвҖҷвҖқжұүжҢҮ银河пјҢжҲ·жҳҜе®ӨеұӢд№Ӣй—ЁжҲ·пјҢдёғжңҲ银河еҪ“жҲ·гҖӮеӯ”е№ҝжЈ®иҜҙпјҡвҖңеҸӨиҖ…дёәжҲ·дәҺе®ӨдёңеҚ—йҡ…пјҢеӨ©жұүжҳҸи§ҒеҪ“жҲ·пјҢеҲҷеҚ—еҢ—зӣҙиҖҢеҒҸдёң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е°”йӣ…В·йҮҠе®«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ҘҝеҚ—йҡ…и°“д№ӢеҘҘгҖӮвҖқйӮўжҳәз–ҸпјҡвҖңеҸӨиҖ…дёәе®ӨпјҢжҲ·дёҚеҪ“дёӯиҖҢиҝ‘дёңгҖӮвҖқгҖҠиҜ—В·е”җйЈҺВ·з»ёзјӘгҖӢдёӯжңүвҖңз»ёзјӘжқҹжҘҡпјҢдёүжҳҹеңЁжҲ·вҖқд№ӢеҸҘпјҢжҜӣгҖҠдј 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ҸӮжҳҹжӯЈжңҲдёӯзӣҙжҲ·д№ҹ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иҷҪ然и®ӨдёәвҖңдёүжҳҹвҖқдёҚжҳҜеҸӮе®ҝпјҢиҖҢжҳҜеҝғе®ҝдёүжҳҹпјҢдҪҶд№ҹд»ҘдёүжҳҹеңЁжҲ·дёәзӣҙжҲ·гҖӮгҖҠжұүд№ҰВ·и‘Јд»ІиҲ’дј гҖӢеј•и‘Јд»ІиҲ’еҜ№зӯ–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д№ҰгҖӢжӣ°пјҡвҖҳзҷҪйұје…ҘдәҺзҺӢиҲҹпјҢжңүзҒ«еӨҚдәҺзҺӢеұӢпјҢжөҒдёәд№ҢгҖӮвҖҷвҖқ马иһҚгҖҠд№ҰеәҸгҖӢдә‘д»Ҡж–ҮгҖҠе°ҡд№ҰгҖӢд№ӢгҖҠжі°иӘ“гҖӢжңүпјҡвҖңзҒ«еӨҚдәҺдёҠпјҢиҮідәҺзҺӢеұӢпјҢжөҒдёәпјҢдә”иҮід»Ҙи°·дҝұжқҘ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ҡ„вҖңзҒ«вҖқпјҢжҳҜеҝғе®ҝд№ӢеҗҚгҖӮвҖңеӨҚдәҺзҺӢеұӢвҖқ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еҝғе®ҝзӣҙжҲ·д№Ӣж„ҸгҖӮеӨ©дёҠ银河гҖҒеҝғе®ҝзӯүвҖңзӣҙжҲ·вҖқпјҢеҚідёәжҳҸдёӯжҳҹиұЎпјҢдәә们дәҺй—ЁжҲ·еҚіеҸҜд»Ҙи§ӮеҜҹпјҢж•…дёә他们жүҖд№ и§ҒгҖӮеӨ©дёҠдҪңдёәвҖң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қеӨҙи§’зҡ„дә•е®ҝвҖңзӣҙжҲ·вҖқеҝ…д№ҹдёәдәә们жүҖзҶҹзҹҘгҖӮе‘ЁеҲқе©ҡеЁ¶д№ӢзӨјдё»иҰҒиЎҢдәҺд»ІжҳҘж—¶иҠӮпјҢгҖҠеӨҸе°ҸжӯЈгҖӢдәҢжңҲдә‘пјҡвҖңз»ҘеӨҡеЈ«еҘігҖӮвҖқеҚўиҫ©жіЁпјҡвҖңз»ҘпјҢе®үд№ҹгҖӮеҶ еӯҗеҸ–еҰҮд№Ӣж—¶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е‘ЁзӨјВ·ең°е®ҳВ·еӘ’ж°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ёӯжҳҘд№ӢжңҲпјҢд»Өдјҡз”·еҘі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жіЁпјҡвҖңдёӯжҳҘпјҢйҳҙйҳідәӨпјҢд»ҘжҲҗжҳҸзӨјпјҢйЎәеӨ©ж—¶д№ҹгҖӮвҖқи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йҰ–з« вҖңеҺҢжөҘиЎҢйңІвҖқдә‘дә‘пјҢйғ‘зҺ„гҖҠз¬әгҖӢиҜҙеҫ—еҚҒеҲҶжҳҺзҷҪпјҡвҖңеҺҢжөҘ然ж№ҝпјҢйҒ“дёӯе§ӢжңүйңІпјҢи°“дәҢжңҲдёӯе«ҒеҸ–ж—¶д№ҹгҖӮвҖқе‘Ёд»ЈеҲқе№ҙпјҢдәҢжңҲзҡ„жҳҸдёӯжҳҹжӯЈеҘҪдёә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ң鹑йҰ–вҖқзҡ„дә•е®ҝгҖӮгҖҠзӨји®°В·жңҲд»ӨгҖӢд»ІжҳҘд№ӢжңҲдә‘пјҡвҖңжҳҸеј§дёӯпјҢж—Ұе»әжҳҹдёӯ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жіЁпјҡвҖңеј§еңЁиҲҶй¬јеҚ—пјҢе»әжҳҹеңЁж–—дёҠ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ҡ„еј§жҳҹпјҢжҳҹ家зҪ®дёәдә•е®ҝеұһжҳҹ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гҖҠжңҲд»ӨгҖӢд»ҘвҖңеј§жҳҹвҖқдёәжҳҸдёӯжҳҹпјҢиҖҢдёҚзӣҙжҺҘиҜҙжҳҜдә•е®ҝе‘ўпјҹеӯ”йў–иҫҫгҖҠжӯЈд№үгҖӢжңүйқһеёёеҗҲзҗҶзҡ„и§ЈйҮҠпјҡеј§дёҺе»әжҳҹпјҢйқһдәҢеҚҒе…«е®ҝпјҢиҖҢжҳҸжҳҺдёҫд№ӢиҖ…пјҢз”ұеј§жҳҹиҝ‘дә•пјҢе»әжҳҹиҝ‘ж–—гҖӮдә•жңүдёүеҚҒдёүеәҰпјҢж–—жңүдәҢеҚҒе…ӯеәҰпјҢе…¶еәҰж—ўе®ҪпјҢиӢҘдёҫдә•ж–—пјҢдёҚзҹҘдҪ•ж—Ҙзҡ„иҮідә•ж–—д№ӢдёӯпјҢж•…дёҫеј§жҳҹе»әжҳҹд№ҹгҖӮ然жҳҘеҲҶд№Ӣж—¶ж—ҘеӨңдёӯпјҢи®ЎжҳҘеҲҶжҳҸдёӯд№ӢжҳҹпјҢеҺ»ж—Ҙд№қеҚҒдёҖеәҰгҖӮд»Ҡж—ҘеңЁеҘҺдә”еәҰпјҢеҘҺдёҺй¬јд№ӢеҲқд№ғдёҖзҷҫд№қеәҰгҖӮжүҖд»ҘдёҚеҗҢиҖ…пјҢйғ‘иҷҪдә‘еј§еңЁй¬јеҚ—пјҢе…¶е®һд»ҚеҪ“дә•д№ӢеҲҶеҹҹпјҢж•…зҡҮж°Ҹдә‘д»ҺеҘҺ第дә”еәҰдёәдәҢжңҲиҠӮпјҢж•°иҮідә•з¬¬еҚҒдә”еәҰпјҢеҫ—д№қеҚҒдёҖеәҰпјҢеҲҷеј§жҳҹеҪ“дә•д№ӢеҚҒе…ӯеәҰд№ҹгҖӮ иҝҷж®өиҜқиҜҙеҫ—еҚҒеҲҶжё…жҘҡпјҢгҖҠжңҲд»ӨгҖӢдёҫеј§жҳҹдёәд»ІжҳҘд№ӢжҳҸдёӯжҳҹ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ј§жҳҹиҝ‘дә•е®ҝпјҢиҖҢдә•е®ҝжңүдёүеҚҒдёүеәҰпјҢдёәе…ЁеӨ©жңҖе®ҪиҖ…пјҢиӢҘдёҫдә•е®ҝдёәд»ІжҳҘжҳҸдёӯжҳҹпјҢйҡҫд»ҘжҳҺзЎ®ж–ӯе®ҡе“Әж—ҘеҲ°иҫҫдә•е®ҝд№ӢдёӯгҖӮиҖҢеј§жҳҹжӯЈеҪ“дә•е®ҝд№ӢеҚҒе…ӯеәҰпјҢжүҖд»Ҙе°ұд»Ҙеј§жҳҹдҪңдёәд»ІжҳҘзҡ„жҳҸдёӯжҳҹдәҶгҖӮдә•е®ҝжҳҜвҖң鹑йҰ–вҖқпјҢдёәд»ІжҳҘдәә们е«ҒеЁ¶д№Ӣж—¶зҡ„жҳҸдёӯжҳҹпјҢиҝҷеңЁеҪ“ж—¶жҳҜдёҖз§Қеёёи§Ғзҡ„жҳҹиұЎпјҢжӯӨжҳҹе®ҝеҝ…дёәе«ҒеЁ¶дёӯдәәжүҖе…іжіЁе’ҢзҶҹзҹҘгҖӮ然еҲҷ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әҢз« дёӯзҡ„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дёҺдёүз« дёӯзҡ„вҖңи°Ғи°“йј ж— зүҷ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ўүвҖқеқҮжҳҜиЎЁзӨәдәәдәәжҳҺзҷҪгҖҒж— еҸҜзҪ®з–‘д№ӢдәӢпјҢеҚіеӨ©дёҠд№ӢвҖңжңұйӣҖвҖқжҳҹиұЎжңүйҰ–пјҲи§’пјүз©ҝи¶Ҡй—ЁжҲ·пјҢең°дёҠд№Ӣйј з”ЁзүҷйҪҝз©ҝеўҷпјҢйғҪжҳҜжҳҺзҷҪж— иҜҜд№ӢдәӢгҖӮжңүдәәиҖғиҜҒиҖҒйј ж— зүҷпјҢе°ҶзүҷдёҺйҪҝеҲҶејҖи§ЈйҮҠпјҢи°“зүҷеӨ§йҪҝе°ҸпјҢиҖҒйј йҪҝе°Ҹж•…и°“д№Ӣж— зүҷгҖӮиҝҷз§Қи§ЈйҮҠжңүдәӣзүөејәпјҢйҪҝгҖҒзүҷдёӨеӯ—ж—©е°ұйҖҡз”ЁпјҢиҖҒйј зүҷйҪҝд№Ӣе°–еҲ©дәәдәәжүҖзҹҘпјҢжӯЈеҰӮдҝһжЁҫ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йј д№Ӣз©ҝеўүпјҢиӢҘдёҚд»ҘзүҷпјҢеӨҚд»ҘдҪ•зү©д№ҺвҖқпјҹ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№ӢдҪңиҖ…з”Ё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е’ҢвҖңи°Ғи°“йј ж— зүҷ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ўүвҖқиҝҷдёӨз§ҚдёҚе®№зҪ®з–‘зҡ„дәӢе®һ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зӘҒжҳҫдёӢж–Үд№ӢвҖңи°Ғи°“еҘіж— 家вҖқгҖӮеҰӮеҗҢйӣҖжңүи§’гҖҒйј жңүзүҷдёҖж ·пјҢжҳҺзҷҪж‘ҶеңЁиҝҷйҮҢзҡ„жҳҜпјҢдҪ еҲҷжңүвҖң家вҖқпјҢжӯӨвҖң家вҖқеҸҜдҪң家е®ӨгҖҒеҰ»е®Өи§ЈгҖӮеҺҹжқҘеҘіеӯҗжӢҹе«Ғд№Ӣз”·жҳҜе·ІжңүеҰ»е®ӨиҖ…пјҢиҝҷеӨ§зәҰе°ұжҳҜиҮҙи®јзҡ„зҗҶз”ұдәҶгҖӮйҷҲеӯҗеұ•гҖҠиҜ—з»Ҹзӣҙи§ЈгҖӢе°ұиҜҙпјҡв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дёәдёҖеҘіеӯҗжӢ’з»қдёҺдёҖе·Іжңүе®Ө家д№Ӣз”·еӯҗйҮҚе©ҡиҖҢдҪңгҖӮвҖқжқҺй•ҝд№ӢгҖҠеӣҪйЈҺиҜ•иҜ‘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еқҡејәзҡ„еҘіеӯҗжӢ’з»қдёҖдёӘжңү家е®Өзҡ„з”·дәәејәиҝ«жҲҗе©ҡзҡ„иҜ—пјҢеҘ№дёҚйЎҫжі•еҫӢзҡ„иҝ«е®іпјҢдёәиҮӘе·ұзҡ„зӢ¬з«ӢиҮӘз”ұиҖҢиҝӣиЎҢзқҖеҸҚжҠ—гҖӮвҖқжё…дәәдәҺй¬ҜгҖҠйҰҷиҚүж Ўд№ҰгҖӢеҚ·еҚҒдёҖеҲҷд»ҘдёәжӯӨиҜ—еҶҷз”·еӯҗејәиҝ«еҘіеӯҗдҪңеҰҫпјҡжӯӨ家еӯ—зӣ–и°“е…¶еҰ»пјҢ家жңүеҰ»и®ӯгҖӮгҖҠе·Ұеғ–еҚҒдә”е№ҙгҖӢдј еӯ”д№үдә‘пјҡвҖңеӨ«и°“еҰ»дёә家гҖӮвҖқеҸҲгҖҠжҘҡиҫһВ·зҰ»йӘҡгҖӢзҺӢйҖёз« еҸҘдә‘пјҡвҖңеҰҮи°“д№Ӣ家гҖӮвҖқгҖҠеҗ•ж°ҸжҳҘз§ӢВ·дёҚеұҲи§ҲгҖӢй«ҳиҜұжіЁдә‘пјҡвҖң家ж°ҸеҰҮж°ҸгҖӮвҖқеҰҮеҚіеҰ»д№ҹпјӣдёҠж–Үдә‘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вҖқпјҢдҝһиҚ«з”«еӨӘеҸІгҖҠе№іи®®гҖӢи°“и§’еҚіе…¶е–ҷгҖӮиғЎжүҝзҸҷгҖҠеҗҺз¬әгҖӢеј•дҪ•ж°ҸгҖҠеҸӨд№үгҖӢе·ІжңүжӯӨиҜҙгҖӮеҸҲжҜӣеҘҮйҫ„гҖҠз»ӯиҜ—дј В·йёҹеҗҚгҖӢ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и§’иҖ…пјҢйёҹеҷЈд№Ӣй”җеҮәиҖ…гҖӮвҖқзӣ–йӣҖе®һжңүи§’пјҢйқһж— и§’пјҢж•…жӣ°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вҖқпјҢйғ‘з¬әдә‘пјҡвҖңеҘіпјҢеҘі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гҖӮвҖқеҲҷжӯӨ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пјҢе®һжңүеҰ»пјҢйқһж— еҰ»пјҢж•…жӣ°вҖңи°Ғи°“еҘіж— 家вҖқпјҢиӢҘжӣ°и°Ғи°“еҘіж— еҰ»д№ҹгҖӮзҺ©жӯӨиҜ—д№Ӣж„ҸпјҢзӣ–жӯӨ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ж¬ІејәжӯӨеҘідёәеҰҫпјҢиҖҢеҘідёҚж„ҝд»ҘиҮідәҺи®јпјҢж•…дёӢж–Үдә‘вҖңе®Ө家дёҚи¶івҖқпјҢвҖңе®Ө家дёҚи¶івҖқиҖ…пјҢжӯЈд»Ҙе…¶дёәеҰҫгҖӮеҰҫд№Ӣй…ҚеӨ«дёҚи¶ідәҺеӨ«еҰҮд№ӢйҒ“д№ҹгҖӮиӢҘдёәеҰ»пјҢеҚіе®Ө家足зҹЈгҖӮгҖҠжҜӣдј гҖӢи§ЈвҖңе®Ө家дёҚи¶івҖқпјҢи°“жҳҸзӨјзәҜеёӣдёҚиҝҮдә”дёӨпјҢдё»зәҜеёӣиЁҖпјҢдјјжңӘеҫ—д№үгҖӮ дәҺй¬ҜжӯӨиҜҙпјҢдёҺйҷҲгҖҒжқҺд№ӢиҜҙе…¶е®һжңүзұ»дјјд№ӢеӨ„пјҢдјјд№ҺдјҳдәҺжҜӣдј зҡ„вҖңжҳҸзӨјзәҜеёӣдёҚиҝҮдә”дёӨвҖқпјҢеҚівҖңзӨјдёҚи¶івҖқпјҲиҒҳзӨјдёҚи¶ізӨји§„е®ҡд№Ӣж•°пјүд№ӢиҜҙгҖӮе‘ЁзӨје°ҡз®ҖпјҢдә”дёӨзәҜеёӣзәҰзӣёеҪ“дәҺеӣӣеҚҒе°әпјҢе®№жҳ“зҪ®еҠһгҖӮеӣ жӯӨпјҢйғ‘зҺ„дёҚи®ӨеҗҢжҜӣдј жӯӨи§ЈпјҢдә‘пјҡвҖңеёҒеҸҜеӨҮд№ҹгҖӮе®Ө家дёҚи¶іпјҢи°“еӘ’еҰҒд№ӢиЁҖдёҚе’ҢпјҢе…ӯзӨјд№ӢжқҘејә委д№ӢгҖӮвҖқд»–и®ӨдёәеҘіж–№ејәи°ғвҖңе®Ө家дёҚи¶івҖқпјҢжҳҜеӣ дёәз”·еӯҗзҡ„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е’ҢеҪ“ж—¶еӘ’дәәжүҖдә‘дёҚзӣёз¬ҰеҗҲпјҢиҖҢйҖҡиҝҮеӘ’еҰҒж¬ІејәеЁ¶еҘ№гҖӮеӯ”йў–иҫҫжӯЈд№үдә‘пјҡзҹҘдёҚдёәеёҒдёҚи¶іиҖ…пјҢд»Ҙз”·йҖҹеҘіиҖҢзӢұпјҢеёҒиӢҘдёҚеӨҮпјҢдёҚеҫ—и®јд№ҹгҖӮд»Ҙи®јжӢ’д№ӢпјҢжҳҺеҘідёҚиӮҜеҸ—пјҢз”·еӯҗејә委其зӨјпјҢ然еҗҺи®јд№ӢпјҢиЁҖеҘіеҸ—е·ұд№ӢзӨјиҖҢдёҚд»Һе·ұпјҢж•…зҹҘеёҒеҸҜеӨҮгҖӮиҖҢдә‘дёҚи¶іпјҢжҳҺз”·еҘіиҙӨдёҺдёҚиӮ–еҗ„жңүе…¶иҖҰпјҢеҘіжүҖдёҚд»ҺпјҢз”·еӯҗејәжқҘпјҢж•…дә‘вҖңи°“еӘ’еҰҒд№ӢиЁҖдёҚе’ҢпјҢе…ӯзӨјд№ӢжқҘејә委д№ӢвҖқпјҢжҳҜе…¶е®Ө家дёҚи¶ід№ҹгҖӮ еӯ”йў–иҫҫд№ҹи®ӨдёәжӯӨиҜ—дё»ж—ЁеңЁдәҺз”·еӯҗзҡ„вҖңејә委вҖқпјҢиҖҢеҘіеӯҗдёҚд»ҺпјҢдәҺжҳҜжңүиҜүи®јд№ӢдәӢгҖӮ笔иҖ…д»ҘдёәпјҢжҜӣгҖҒйғ‘гҖҒеӯ”еҢ…жӢ¬еҗҺжқҘзҡ„йҷҲеӯҗеұ•гҖҒжқҺй•ҝд№ӢеҸҠдәҺй¬Ҝзӯүдәәзҡ„и§ЈиҜҙе°Ҹжңүе·®ејӮпјҢдҪҶе№¶ж— е®һиҙЁеҢәеҲ«пјҢ他们йғҪд»ҘдёәжӯӨиҜ—жҸҸиҝ°зҡ„жҳҜе®һйҷ…еӯҳеңЁзҡ„иҜүи®јд№ӢдәӢгҖӮдҪҶиҝҷз§ҚиҜҙжі•жҳҜеҖјеҫ—жҖҖз–‘е’Ңе•ҶжҰ·зҡ„гҖӮдәҢгҖҒе…ідәҺ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зҡ„дҪңиҖ…еҸҠе…¶йўҳж—Ё 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зҡ„дҪңиҖ…й—®йўҳпјҢе…ізі»еҲ°еҜ№жң¬иҜ—дё»ж—Ё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жүҖд»ҘеҺҶжқҘиҜҙиҜ—иҖ…еҜ№жӯӨйғҪдәҲд»Ҙе…іжіЁпјҢжӯӨдәҰдёҚиғҪдёҚиҫЁгҖӮеӨ§иҮҙиҜҙжқҘпјҢдё»иҰҒжңүд»ҘдёӢеҮ з§ҚиҜҙжі•гҖӮ1.вҖңеә”и®јвҖқеҘіеӯҗдҪңжұүд»ЈвҖңдёү家иҜ—вҖқзҡ„йІҒиҜ—жӣ°пјҡгҖҠеҸ¬еҚ—гҖӢпјҢз”іеҘіиҖ…пјҢз”ідәәд№ӢеҘід№ҹпјҢж—ўи®ёе«ҒдәҺй…ҶпјҢеӨ«е®¶зӨјдёҚеӨҮиҖҢж¬ІиҝҺд№ӢгҖӮеҘідёҺе…¶дәәиЁҖпјҢд»ҘдёәеӨ«еҰҮиҖ…дәәдјҰд№Ӣе§Ӣд№ҹпјҢдёҚеҸҜдёҚжӯЈгҖӮгҖҠдј гҖӢжӣ°пјҡжӯЈе…¶жң¬еҲҷдёҮзү©зҗҶпјҢеӨұд№ӢжҜ«еҺҳпјҢе·®д№ӢеҚғйҮҢпјҢжҳҜд»Ҙжң¬з«ӢиҖҢйҒ“з”ҹпјҢжәҗе§ӢиҖҢжөҒжё…гҖӮж•…е«ҒеЁ¶иҖ…пјҢжүҖд»Ҙдј йҮҚжүҝдёҡпјҢ继з»ӯе…ҲзҘ–пјҢдёәе®—еәҷдё»д№ҹгҖӮеӨ«е®¶иҪ»зӨјиҝқеҲ¶пјҢдёҚеҸҜд»ҘиЎҢгҖӮйҒӮдёҚиӮҜеҫҖгҖӮеӨ«е®¶и®јд№ӢдәҺзҗҶпјҢиҮҙд№ӢдәҺзӢұгҖӮеҘіз»Ҳд»ҘдёҖзү©дёҚе…·гҖҒдёҖзӨјдёҚеӨҮпјҢе®ҲиҠӮжҢҒд№үпјҢеҝ…жӯ»дёҚеҫҖпјҢиҖҢдҪңиҜ—жӣ°пјҡвҖңиҷҪйҖҹжҲ‘зӢұпјҢе®Ө家дёҚи¶ігҖӮвҖқиЁҖеӨ«е®¶д№ӢзӨјдёҚеӨҮи¶ід№ҹгҖӮеҗӣеӯҗд»Ҙдёәеҫ—еҰҮйҒ“д№Ӣе®ңпјҢж•…дёҫиҖҢжү¬д№ӢпјҢдј иҖҢжі•д№ӢпјҢд»Ҙз»қж— зӨјд№ӢжұӮпјҢйҳІж·«жіҶд№ӢиЎҢгҖӮеҸҲжӣ°пјҡвҖңиҷҪйҖҹжҲ‘и®јпјҢдәҰдёҚеҘід»ҺгҖӮвҖқжӯӨд№Ӣи°“д№ҹгҖӮ з”іеҘіи®ёе«ҒдәҺй…Ҷд№ӢиҜҙпјҢжҒҗжҖ•жҳҜеҗҺиө·зҡ„дј иҜҙпјҢдёҚиғҪеҪ“зңҹгҖӮжңұзҶ№гҖҠиҜ—йӣҶдј 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ҘіеӯҗдёҚдёәејәжҡҙжүҖжұЎпјҢиҮӘиҝ°е·ұеҝ—пјҢдҪңжӯӨиҜ—д»Ҙз»қдәәгҖӮвҖқд»Һеӯ—йқўиҜӯж°”зңӢпј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зҡ„дҪңиҖ…дјјеҸҜи§Јдёәеә”и®јзҡ„еҘіеӯҗ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ә”и®јеҘіеӯҗдҪңжӯӨиҜ—зҡ„иҜҙжі•дёәеҫҲеӨҡдәәзӣёдҝЎгҖӮ2.вҖңеҗӣеӯҗвҖқйўӮжү¬вҖңиҙһеҘівҖқдҪңвҖңдёү家иҜ—вҖқдёӯзҡ„йҹ©иҜ—еҲҷд»Ҙдёә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дёәвҖңеҗӣеӯҗвҖқжүҖдҪңпјҢгҖҠйҹ©иҜ—еӨ–дј гҖӢеҚ·дёҖдә‘пјҡдј жӣ°пјҡеӨ«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д№Ӣдәәж—ўи®ёе«ҒзҹЈпјҢ然иҖҢжңӘеҫҖд№ҹгҖӮдёҖзү©дёҚе…·пјҢдёҖзӨјдёҚеӨҮпјҢе®Ҳеҝ—иҙһзҗҶпјҢе®Ҳжӯ»дёҚеҫҖгҖӮеҗӣеӯҗд»Ҙдёәеҫ—еҰҮйҒ“д№Ӣе®ңпјҢж•…дёҫиҖҢдј д№ӢпјҢжү¬иҖҢжӯҢд№ӢпјҢд»Ҙз»қж— зӨјд№ӢжұӮпјҢйҳІжұЎйҒ“д№ӢиЎҢд№ҺпјҹгҖҠиҜ—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иҷҪйҖҹжҲ‘и®јпјҢдәҰдёҚе°”д»ҺгҖӮвҖқ еӯ”йў–иҫҫд№ӢиҜҙдёҺжӯӨзӣёеҗҢпјҡвҖңз»ҸзҡҶйҷҲеҘідёҺз”·и®јд№ӢиҫһиҖіпјҢд»Ҙж–ҮзҺӢд№Ӣж•ҷпјҢеҘізҡҶиҙһдҝЎпјҢйқһзӨјдёҚеҠЁпјҢж•…иғҪжӢ’ејәжҡҙд№Ӣз”·пјҢдёҺд№Ӣдәүи®јгҖӮиҜ—дәәеҖҹе…¶дәӢиҖҢдёәд№ӢиҫһиҖігҖӮвҖқеӨ§дҪ“иҜҙе‘ЁеҲқеҸ¬е…¬д№Ӣж—¶пјҢиҜ—дәәдәІи§ҒдёҖиҙһдҝЎд№ӢеҘіе’Ңж¬ІејәеЁ¶еҘ№зҡ„з”·еӯҗдәүи®јпјҢдәҺжҳҜдҪңдәҶиҝҷж ·дёҖйҰ–иҜ—гҖӮиҜ—дәәдҪңжӯӨиҜ—зҡ„зӣ®зҡ„жҳҜиӨ’жү¬иҙһеҘігҖӮ3.еҸ¬дјҜ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д№ӢиҫһгҖҠе°ҸеәҸгҖӢе·Іжңүв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вҖқд№ӢиҜҙпјҢдҪҶжңӘдҪңе…·дҪ“еҲҶжһҗгҖӮиҮійғ‘зҺ„е§ӢжҳҺзЎ®жҸҗеҮәиҜҘиҜ—жҳҜеҶҷвҖңз”·еҘіеҜ№и®јвҖқгҖӮйғ‘зҺ„д№ӢиҜҙи§ҒдәҺеӯ”йў–иҫҫгҖҠжҜӣиҜ—жӯЈд№үгҖӢеҚ·дёҖеј•йғ‘зҺ„зӯ”еј йҖёй—®пјҡгҖҠйғ‘еҝ—гҖӢеј йҖёй—®пјҡв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пјҢеҜҹж°‘ж„Ҹд№ӢеҢ–иҖіпјҢдҪ•и®јд№ҺпјҹвҖқзӯ”жӣ°пјҡвҖңе®һи®јд№Ӣиҫһд№ҹгҖӮвҖқж°‘иў«еҢ–д№…зҹЈпјҢж•…иғҪжңүи®јгҖӮй—®иҖ…и§ҒиҙһдҝЎд№Ӣж•ҷе…ҙпјҢжҖӘдёҚеҪ“жңүи®јпјҢж•…дә‘еҜҹж°‘д№Ӣж„ҸиҖҢеҢ–д№ӢпјҢдҪ•дҪҝиҮідәҺи®јд№Һпјҹзӯ”жӣ°пјҡжӯӨзҜҮе®һжҳҜи®јд№Ӣиҫһд№ҹгҖӮз”ұж—¶ж°‘иў«еҢ–ж—Ҙд№…пјҢиҙһеҘідёҚд»ҺпјҢз”·еҘіж•…зӣёдёҺи®јгҖӮеҰӮжҳҜж°‘иў«еҢ–ж—Ҙд№…пјҢжүҖд»Ҙеҫ—жңүејәжҡҙиҖ…пјҢзәЈдҝ—йҡҫйқ©ж•…д№ҹгҖӮиЁҖејәжҡҙиҖ…пјҢи°“ејәиЎҢж— зӨјиҖҢеҮҢжҡҙдәҺдәәгҖӮз»Ҹдёүз« пјҢдёӢдәҢз« йҷҲз”·еҘіеҜ№и®јд№ӢиҫһгҖӮйҰ–з« иЁҖжүҖд»Ҙжңүи®јпјҢз”ұеҘідёҚд»Һз”·пјҢдәҰжҳҜеҗ¬и®јд№ӢдәӢд№ҹгҖӮ йғ‘зҺ„и®ӨдёәпјҢжӯӨиҜ—ж—ўйқһеҘіеӯҗиҮӘдҪң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еҗӣеӯҗдёәиӨ’жү¬иҙһеҘіжүҖ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еҸ¬е…¬еҗ¬и®јд№ӢиҫһгҖӮйҰ–з« еҶҷиҮҙи®ј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жҳҜеҘідёҚд»Һз”·пјӣ第дәҢгҖҒдёүдёӨз« еҶҷз”·еҘіеҜ№и®јгҖӮжӯӨиҜҙиҷҪ然еҗҺдәәд№ҹжңүдёҚеҗҢж„Ҹи§ҒпјҢдјјиҫғеүҚдәҢиҜҙжӣҙдёәе…·дҪ“пјҢ然дәҰжңүиҙ№и§Јд№ӢеӨ„пјҡеҰӮж–ӯдёә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д№ӢиҜҚпјҢжӯӨиҜ—жҳҜз”ұеҸ¬дјҜдәІеҪ•пјҢиҝҳжҳҜеҸ¬дјҜжүӢдёӢжүҖеҪ•пјҹйғ‘зҺ„дәҺжӯӨиҜӯз„үдёҚиҜҰгҖӮеҗҺжқҘеӯҰиҖ…д№ҹжңү并дёҚи®ӨеҗҢйғ‘иҜҙзҡ„пјҢжҸҗеҮәд»ҘдёӢиҙЁз–‘пјҡеҸ¬дјҜдёәе‘ЁеҲқдёҺе‘Ёе…¬йҪҗеҗҚзҡ„вҖңдәҢдјҜвҖқд№ӢдёҖпјҢдјҡдәІиҮӘе®ЎзҗҶж°‘й—ҙз”·еҘіи®јдәӢпјҹйғ‘зҺ„д№ҹејәи°ғвҖңдәҢеҚ—вҖқзӯүең°еҸ—ж–ҮзҺӢзӯүж•ҷеҢ–пјҢж•…жңүиҙһеҘідёҚз•ҸејәжҡҙиҖҢеҜ№и®јд№ӢдёҫпјҢ然男еӯҗд№ӢдҫөжҡҙеҸҲдҪ•д»ҘдҪ“зҺ°вҖң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вҖқпјҹй»„йңҮгҖҠй»„ж°Ҹж—Ҙй’һгҖӢеҚ·еӣӣвҖңиЎҢйңІвҖқжқЎжӣ°пјҡеІ·йҡҗи°“з”·жңүејә委иҒҳиҖ…пјҢеҘідёҚд»ҺиҖҢи®јпјҢеј•гҖҠеҲ—еҘідј гҖӢдёәиҜҒгҖӮйӣӘеұұжӣ°пјҡвҖңжҡҙз”·дҫөиҙһеҘіпјҢеҘіеӣәеҸҜе°ҡгҖӮз”·дёәдҪ•дәәпјҹеІӮ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зӢ¬еҸҠеҘіиҖҢдёҚеҸҠз”·йӮӘпјҹвҖқеҗҲжӯӨдәҢиҜҙпјҢеҲҷгҖҠиҜ—еәҸгҖӢдҫөеҮҢд№ӢиҜҙж®Ҷйқһд№ҹпјҢзү№дёҚжҲҗе©ҡиҖҢи®јиҖігҖӮ зҺӢиЈігҖҠзҹҘж–°еҪ•гҖӢеҚ·дәҢд№ҹдә‘пјҡгҖҠжЁ—еӣӯиҜ—иҜ„гҖӢпјҡвҖңеҘіиҙһеҰӮжӯӨпјҢеІӮзңҹжңүејәжҡҙдҫөеҮҢпјҹеҰӮжүҖз§°еӨҡйңІиҖ…пјҢиҖҢдё”иҮідәҺи®јзӢұпјҢжҳҜ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еҸӘеҸҜиЎҢдәҺеҘіеӯҗиҖҢдёҚеҸҜиЎҢдәҺдёҲеӨ«д№ҹгҖӮйј йӣҖж·«иҙӘпјҢеҖҹиЁҖдёҚиғҪз©ҝе…¶зү–еұӢгҖӮзӣ–иә¬иЎҢиҙһжҲ’пјҢеҝ—ж°”жё…жҳҺпјҢе·ІеҶідәҺиөӢиҜ—и§Ғеҝ—д№Ӣж—ҘзҹЈгҖӮвҖқ зҺӢиЈіиҷҪд№ҹи®ӨдёәжӯӨиҜ—дҪңиҖ…дёәвҖңиҙһеҘівҖқпјҢдҪҶ他并дёҚи®ӨеҗҢвҖң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вҖқиҜҙпјҡеҒҮеҰӮ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еҢ…жӢ¬гҖҠе‘ЁеҚ—гҖӢгҖҠеҸ¬еҚ—гҖӢеҰӮжҜӣгҖҒйғ‘зӯүиҜҙе…ід№ҺвҖң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вҖқпјҢйӮЈд№Ҳдёәд»Җд№Ҳиҝҷз§Қж•ҷеҢ–зҡ„жҲҗжһңеҸӘйҷҗдәҺеҘіеӯҗе‘ў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иҝҳдјҡеҮәзҺ°йӮЈд№ҲеӨҡзҡ„вҖңејәжҡҙдҫөеҮҢвҖқе‘ўпјҹйЎ»зҹҘз”·еӯҗжҳҜеҪјж—¶зӨҫдјҡзҡ„дё»еҜјиҖ…гҖӮиҝҷд№ҹжҳҜдҪҝйғ‘зҺ„зҡ„еӯҰз”ҹеј йҖёз”ҹз–‘пјҢиҖҢеҗ‘иҖҒеёҲеҸ‘й—®зҡ„зјҳз”ұгҖӮдёҺеј йҖёжҺҘеҸ—иҖҒеёҲзҡ„и§Ғи§ЈдёҚеҗҢпјҢй»„йңҮгҖҒзҺӢиЈізӯүдәәеҲҷз”ұжӯӨеј•еҸ‘дәҶ他们еҜ№жӯӨиҜ—иҜ—ж—Ёзҡ„дёҚеҗҢзҗҶи§ЈгҖӮеҰӮй»„йңҮи®ӨдёәпјҢжӯӨиҜ—е№¶ж— жүҖи°“з”·ж–№дҫөеҮҢд№ӢдәӢпјҢеҸӘжҳҜз”·еҘід№Ӣй—ҙеӣ е©ҡдәӢиҖҢжү“зҡ„дёҖеңәе®ҳеҸёгҖӮ4.еҚҙе©ҡз”·еӯҗдҪңжңүдәәзӣёдҝЎгҖҠеҸ¬еҚ—гҖӢеҸҚжҳ дәҶвҖң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вҖқпјҢд»ҺиҖҢеҗҰе®ҡ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зҡ„з”·еӯҗвҖңејәжҡҙдҫөеҮҢвҖқиҜҙгҖӮжңүдәәз”ҡиҮіеҸҚе…¶йҒ“иҖҢиЎҢд№ӢпјҢд»ҘдёәжӯӨиҜ—иЎЁзҺ°зҡ„жҳҜвҖңеҗӣеӯҗеҚҙе©ҡд»Ҙиҝңе«ҢвҖқгҖӮж–№зҺүж¶ҰгҖҠиҜ—з»ҸеҺҹе§ӢгҖӢеҚ·дәҢдә‘пјҡвҖңеӨ§жҠөдёүд»Јзӣӣж—¶пјҢиҙӨдәәеҗӣеӯҗе®ҲжӯЈдёҚйҳҝпјҢиҖҢйЈҹиҙ«иҮӘз”ҳпјҢдёҚж•ўеҰ„еҶҖйқһзӨјгҖӮеҪ“ж—¶еҝ…жңүеҠҝ家巨ж—ҸпјҢд»ҘеҘіејәеҰ»иҙ«еЈ«гҖӮжҲ–еүҚе·Іи®ёеӯ—дәҺдәәпјҢдёӯеӨҚиҮӘжӮ”пјҢеҸҰеӣҫеҲ«е«ҒиҖ…гҖӮеЈ«ж—ўд»ҘзӨјиҮӘе®ҲпјҢеІӮиӮҜиҝқеҲ¶зӣёд»ҺпјҹеҲҷдёҚе…ҚжңүиҜүи®јзӣёиҝ«д№ӢдәӢпјҢж•…дҪңжӯӨиҜ—д»Ҙи§Ғеҝ—гҖӮвҖқж–№ж°ҸжӯӨиҜҙжҒҗжңүдәӣзүөејәпјҢжҲ‘们д»ҺжӯӨиҜ—зҡ„еӯ—йҮҢиЎҢй—ҙе®һеңЁзңӢдёҚеҮәиҝҷеұӮж„ҸжҖқгҖӮдәҰжңүеӯҰиҖ…жҢҮеҮә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зҡ„主旨并йқһиЎЁзҺ°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пјҢиҖҢжҳҜиЎЁзҺ°иҙўдә§д№ӢиҜүгҖӮеҰӮе·Ұе®қжЈ®гҖҠиҜҙз»Ҹе‘“иҜӯВ·иЎҢйңІиҜҙгҖӢдә‘пјҡжӯӨиҜ—ж¬ЎгҖҠз”ҳжЈ гҖӢзҜҮеҗҺпјҢж®ҶеҸ¬е…¬еҶізӢұз”ҳжЈ д№ӢдёӢпјҢжҳҺдәҺеҗ¬ж–ӯпјҢиҜ—дәәдёәдәәжүҖжһ„пјҢдҪңжӯӨиҜ—д»ҘеҲәе…¶дәәиҖ…ж¬ӨпјҹвҖҰвҖҰеҸӨдәә家жӣ°вҖңеҜҢ家вҖқпјҢе®Өжӣ°вҖңеұ…е®ӨвҖқпјҢзӣ–жҢҮиҙўиҙ§жңүж— иЁҖд№Ӣд№ҹгҖӮиҷһгҖҒиҠ®е°ҡжңүеңҹз”°д№Ӣи®јеҶід№ӢдәҺе‘ЁпјҢе®үи§ҒеҪ“ж—Ҙд№Ӣж°‘пјҢеҝ…ж— дәүз«ҜпјҢеҰӮгҖҠе‘ЁзӨјгҖӢжүҖи°“вҖңд»ҘиҙўзӢұи®јвҖқиҖ…д№Һпјҹе…¶дёүз« иЁҖжұқиҷҪиғҪиҮҙжҲ‘дәҺзӢұи®јпјҢеҪјеҗ¬и®јиҖ…еҝ дҝЎжҳҺеҶіпјҢйқһд»Һжғҹжұқд»ҺиҖ…д№ҹпјҢз»ҲдёҚд»ҺжұқдёҖеҒҸд№ӢиҜҚпјҢиҖҢиҮҙжҲ‘дәҺзӢұи®јд№ҹгҖӮ е·Ұе®қжЈ®д»ҘдёәжӯӨиҜ—иЎЁзҺ°зҡ„жҳҜиҙўдә§д№Ӣи®јпјҢдёҺ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ж— е…ігҖӮиҝҷжҒҗжҖ•дёҺеҪ“ж—¶зҡ„зӨјеҲ¶зӣёйҫғйҫүпјҢд№ҹйҡҫд»ҘжҲҗз«ӢгҖӮж–№гҖҒе·ҰдәҢдәәд№ӢиҜҙиҷҪ然жңӘеҝ…иғҪеӨҹжҲҗз«ӢпјҢдҪҶ他们д»Һ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ж–Үжң¬еҮәеҸ‘дҪңеҮәзҡ„еӨҡе…ғи§ЈиҜ»пјҢд№ҹд»Һдҫ§йқўеҸҚжҳ дәҶжҜӣгҖҒйғ‘зӯүжұүд»ЈеӯҰиҖ…зҡ„иҜҙжі•жңӘеҝ…жҳҜе®ҡи®әпјҢиҖҢжҳҜеҖјеҫ—е•ҶжҰ·зҡ„гҖӮдёүгҖҒ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зҡ„еҲӣдҪңдёҺдёҠеҸӨд»ІжҳҘ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зӨјеҲ¶ 笔иҖ…д»ҘдёәпјҢд»Һе‘ЁеҲқд№ӢиҜ—еҫҖеҫҖи„ұиғҺдәҺд»ӘејҸзҡ„и§’еәҰзңӢпј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еҪ“йқһзәӘе®һд№Ӣ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е‘ЁеҲқеҸІе®ҳпјҲд№җе®ҳпјүж №жҚ®зӣёе…ізҡ„д»ӘејҸд№җиҲһеҲӣдҪңиҖҢжҲҗ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з§Қж•ҷеҢ–ж–№ејҸпјҢе®ҳж–№дәҺжҳҘеӯЈвҖңдјҡз”·еҘівҖқзҡ„ж—¶иҠӮпјҢз»„з»Үжј”зӨәдёҖдәӣиҠӮзӣ®пјҢж—©жңҹзҡ„иҜ—жҳҜдёҺиҫһгҖҒд№җгҖҒиҲһеҗҲдёәдёҖдҪ“зҡ„гҖӮгҖҠеўЁеӯҗВ·е…¬еӯҹзҜҮ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йўӮиҜ—дёүзҷҫпјҢејҰиҜ—дёүзҷҫпјҢжӯҢиҜ—дёүзҷҫпјҢиҲһиҜ—дёүзҷҫ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иҜҙзҡ„иҮӘ然дёҚдјҡжҳҜеҸӘиҜөиҜ»иҖҢжІЎжңүжӯҢиҲһзӣёй…ҚеҗҲзҡ„вҖңиҜ—вҖқ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еҸӘжңүиҲһи№Ҳзҡ„жүҖи°“вҖңиҲһиҜ—вҖқзӯүгҖӮеўЁеӯҗжүҖиҜҙжӯЈеҸҚжҳ дәҶвҖңиҜ—дёүзҷҫвҖқиҜ—гҖҒд№җгҖҒиҲһдёүдҪҚдёҖдҪ“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ёҺеүҚдёҖйҰ–гҖҠз”ҳжЈ гҖӢпјҢйғҪиў«и®Өдёәе…ід№ҺеҸ¬дјҜеҗ¬и®јгҖӮдёҠеҸӨзҡ„е·Ўе®ҲеҲ¶жңүжүҖи°“вҖңеӨӘеёҲйҷҲиҜ—вҖқпјҢвҖңйҷҲиҜ—вҖқе°ұжҳҜз”ЁиҜ—пјҲжӯҢгҖҒиҲһпјүжқҘзӨәпјҲйҷҲпјүпјҢжүҖзӨәиҖ…дёәжңҲд»ӨзӨјеҲ¶пјҢеҢ…жӢ¬зӣёе…ізҡ„е‘ҠзӨәгҖҒе‘ҠиҜ«зӯүгҖӮеҜ№з”·еҘізҡ„ж•ҷеҢ–пјҢеҚіжүҖи°“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пјҢеә”иҜҘжҳҜвҖңйҷҲиҜ—вҖқзҡ„еҶ…е®№д№ӢдёҖгҖӮгҖҠе‘ЁзӨјВ·жҳҘе®ҳВ·еӨӘеёҲ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ҮЎд№җе®ҳпјҢжҺҢе…¶ж”ҝд»ӨпјҢеҗ¬е…¶жІ»и®јгҖӮвҖқе‘ЁеҲқдҪңдёәд№җе®ҳзҡ„еӨӘеёҲең°дҪҚеҫҲй«ҳпјҢе‘Ёе…¬е°ұжӣҫд»»еӨӘеёҲд№ӢиҒҢгҖӮжңҖеҲқе·Ўе®Ҳз”ұеӨӘеёҲгҖҒеӨӘдҝқпјҲжҲ–еҸёеҫ’гҖҒеҸёз©әгҖҒеҸёй©¬зӯүпјүиҝҷдәӣжңқе»·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дәәе‘ҳжӢ…д»»йўҒж”ҝгҖҒж•ҷиҜІеҢ…жӢ¬еҗ¬и®јд№ӢиҙЈпјҢеҗҺжқҘпјҢйҡҸзқҖзҺӢжңқз–Ҷеҹҹзҡ„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пјҢе°Ғе»әйӮҰеӣҪзҡ„дёҚж–ӯеҮәзҺ°пјҢйңҖиҰҒзҡ„е·Ўе®Ҳдәәе‘ҳд№ҹеҝ…然еўһеӨҡпјҢдёҖиҲ¬зҡ„еҚҝеӨ§еӨ«д№ҹејҖе§ӢжӢ…д»»е·Ўе®Ҳд№ӢиҙЈгҖӮе…ідәҺвҖңеӨ§еӨ«вҖқеҗ¬и®јпјҢиҝҷеңЁ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дёӯдәҰжңүжүҖиЎЁзҺ°пјҢеҰӮгҖҠиҜ—з»ҸВ·зҺӢйЈҺВ·еӨ§иҪҰгҖӢе°ҸеәҸдә‘пјҡвҖңеҲәе‘ЁеӨ§еӨ«д№ҹгҖӮзӨјд№үйҷөиҝҹпјҢз”·еҘіж·«еҘ”пјҢж•…йҷҲеҸӨд»ҘеҲәд»ҠеӨ§еӨ«дёҚиғҪеҗ¬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д№ҹгҖӮвҖқеӯ”йў–иҫҫз–Ҹ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еӨ§иҪҰгҖӢдә‘еҸӨиҖ…еӨ§еӨ«еҮәеҗ¬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гҖӮвҖқ1.гҖҠзҺӢйЈҺВ·еӨ§иҪҰгҖӢиҜ—еҸҚжҳ зҡ„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зӨјеҲ¶жұүгҖҒе”җеӯҰиҖ…еӨ§еӨҡзӣёдҝЎдёҠеҸӨжңүе…¬еҚҝеӨ§еӨ«е·Ўе®Ҳ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зӨјеҲ¶пјҢи®ӨдёәгҖҠеӨ§иҪҰгҖӢиҜ—ж¶үеҸҠжӯӨзӨјеҲ¶гҖӮгҖҠеӨ§иҪҰгҖӢе…ЁиҜ—еҰӮдёӢпјҡеӨ§иҪҰж§ӣж§ӣпјҢжҜіиЎЈеҰӮиҸјгҖӮеІӮдёҚе°”жҖқпјҢз•ҸеӯҗдёҚж•ўгҖӮеӨ§иҪҰе“је“јпјҢжҜіиЎЈеҰӮз’ҠгҖӮеІӮдёҚе°”жҖқпјҢз•ҸеӯҗдёҚеҘ”гҖӮжҰ–еҲҷејӮе®ӨпјҢжӯ»еҲҷеҗҢз©ҙгҖӮи°“дәҲдёҚдҝЎпјҢжңүеҰӮжӣ’ж—ҘгҖӮе…ідәҺжӯӨиҜ—йҰ–з« пјҢжҜӣгҖҠдј гҖӢдә‘пјҡ еӨ§иҪҰпјҢеӨ§еӨ«д№ӢиҪҰгҖӮж§ӣж§ӣпјҢиҪҰиЎҢеЈ°д№ҹгҖӮжҜіиЎЈпјҢеӨ§еӨ«д№ӢжңҚгҖӮиҸјпјҢ д№ҹпјҢиҠҰд№ӢеҲқз”ҹиҖ…д№ҹгҖӮеӨ©еӯҗеӨ§еӨ«еӣӣе‘ҪпјҢе…¶еҮәе°Ғдә”е‘ҪпјҢеҰӮеӯҗз”·д№ӢжңҚгҖӮд№ҳе…¶еӨ§иҪҰж§ӣж§ӣ然пјҢжңҚжҜіеҶ•д»ҘеҶіи®јгҖӮгҖҠеӨ§иҪҰгҖӢиҜ—дёӯжүҖдә‘д№ӢвҖңеӨ§иҪҰвҖқвҖңжҜіжңҚвҖқйғҪжҳҜе…·жңүвҖңеӨ§еӨ«вҖқиә«д»Ҫзҡ„дәәжүҚжңүиө„ж јжңҚз”ЁпјҢеҜ№жӯӨгҖҠе‘ЁзӨјгҖӢгҖҠзӨји®°гҖӢзӯүд№ҰжңүжҳҺж–Ү规е®ҡпјҢиҝҷйҮҢдёҚиҜҰи®әгҖӮдёҠеҸӨе®һиЎҢе·Ўе®ҲзӨјеҲ¶пјҢе·Ўе®ҲзӨјеҲ¶еҢ…жӢ¬еӯЈиҠӮжҖ§зҡ„вҖңйўҒж”ҝвҖқдёҺвҖңе‘ҠзӨәвҖқпјҲеҗҺд»ЈзҗҶи§Јдёәж•ҷеҢ–пјүпјҢеңЁж–Үеӯ—еҸӘжҳҜжһҒе°‘ж•°дәәжҺҢжҸЎзҡ„ж—¶д»ЈпјҢвҖңйўҒж”ҝвҖқдёҺвҖңе‘ҠзӨәвҖқжҳҫ然дёҚиғҪйҖҡиҝҮж–Үжң¬ж–Үд№ҰеҠ д»Ҙи§ЈеҶіпјҢиҜүиҜёжӯҢиҲһд»ӘејҸеҲҷжҳҜеҪ“ж—¶зҡ„жңҖеҘҪйҖүйЎ№гҖӮеңЁе·Ўе®ҲвҖңйўҒж”ҝвҖқвҖңе‘ҠзӨәвҖқ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·ЎиЎҢе®ҳе‘ҳпјҲж—©жңҹеӨ§еӨҡдёәд№җе®ҳжӢ…д»»пјүд№ҹдјҡ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пјҢж°‘й—ҙе©ҡ姻зә зә·зҡ„еӯҳеңЁеҸҜи°“жӯЈеёёзҺ°иұЎгҖӮеӣҪ家жҙҫйҒЈе®ҳе‘ҳе®ЎзҗҶиҝҷдәӣзә зә·пјҢеҜ№дәҺз»ҙжҢҒзӨҫдјҡжӯЈд№үдёҺ秩еәҸ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гҖӮиҝҷзұ»е®ЎзҗҶдәәе‘ҳзҡ„еҮәзҺ°еҸҠе…¬жӯЈжү§жі•пјҢжҳҜж–ҮжҳҺиҝӣжӯҘзҡ„иЎЁзҺ°пјҢд№ҹжҳҜдёәжҷ®йҖҡзҷҫ姓жүҖж¬ўиҝҺзҡ„гҖӮгҖҠеҸ¬еҚ—В·з”ҳжЈ гҖӢдёҖиҜ—пјҢе°ұеҸҚжҳ дәҶж°‘дј—еҜ№еҸ¬дјҜж•ҷеҢ–еҸҠеҗ¬ж–ӯ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зҡ„жӯҢйўӮгҖӮжҳҺдәҶдёҠеҸӨе…¬еҚҝеӨ§еӨ«е·Ўе®ҲвҖңеҗ¬и®јвҖқзӨјеҲ¶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жҲ‘们ж·ұе…ҘзҗҶи§Ј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зҡ„дё»ж—ЁеҸҠе…¶дҪңдёәеҪјж—¶зӨјеҲ¶иҪҪдҪ“зҡ„е®һиҙЁгҖӮдҪҶ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дёҺгҖҠз”ҳжЈ гҖӢдёҖж ·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еҶҷдёҖжЎ©е…·дҪ“зҡ„з”·еҘіиҜүи®јжЎҲ件пјҢиҖҢжҳҜиЎЁзҺ°д»ІжҳҘж—¶иҠӮеҸ¬дјҜпјҲжҲ–е…¶д»–е·ЎиЎҢе®ҳе‘ҳпјүеҜ№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жүҖдҪңзҡ„вҖңе‘ҠзӨәвҖқжҲ–вҖңе‘ҠиҜ«вҖқгҖӮд»ІжҳҘе©ҡй…Қж—¶иҠӮпјҢ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иҒҡдјҡдәҺвҖңзӨҫвҖқзӯүе®Ҫйҳ”ең°еёҰпјҢеӣҪ家жҙҫйҒЈзҡ„вҖңдәҢдјҜвҖқжҲ–вҖңеӨ§еӨ«вҖқд№Ӣзұ»зҡ„е·Ўе®Ҳе®ҳе‘ҳеңЁжӯӨдёҫиЎҢжӯҢиҲһиЎЁжј”пјҢжӯҢиҲһеұ•зӨәзҡ„еҶ…е®№е…·жңүвҖңжӯЈз”·еҘівҖқдәҰеҚівҖңд»ҘзӨјиҖҢиЎҢвҖқзҡ„е‘ҠиҜ«гҖҒж•ҷиӮІжҖ§иҙЁгҖӮдәҢжңҲзҡ„е·Ўе®ҲвҖңе‘ҠзӨәвҖқжҳҜеҪјж—¶еҜ№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иҝӣиЎҢж•ҷеҢ–зҡ„дёҖз§Қе…·дҪ“ж–№ејҸпјҢеӨ§зәҰеҢ…еҗ«еҗҺдәәжҙҘжҙҘд№җйҒ“зҡ„вҖңж–ҮзҺӢд№ӢеҢ–вҖқзҡ„дёҖдәӣеҶ…е®№гҖӮ2.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вҖңйӣҖи§’вҖқдёҺвҖңдә•е®ҝвҖқдё»вҖңжі•еҲ¶вҖқгҖҠиЎҢйңІгҖӢ第дәҢз« дёӯзҡ„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пјҢжҳҜиЎЁжј”иҖ…жӯҢиҲһдёӯзҡ„жӯҢиҜҚпјҢдёҚжҳҜеҰӮйғ‘зҺ„иҜҙзҡ„жҳҜз”·ж–№и®јиҜҚпјҢжӣҙдёҚеҸҜиғҪжҳҜеҘіж–№жүҖжӯҢиҖ…гҖӮжӯҢиҜҚдёӯжҳҫ然еҢ…еҗ«дәҶе‘ҠиҜ«пјҢдәҰеҚівҖңж•ҷеҢ–вҖқ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иҜ—дёӯйӣҖжңүи§’д№ӢйӣҖпјҢ并йқһжҢҮдәәй—ҙд№ӢйёҹйӣҖпјҢиҖҢжҳҜжҢҮвҖңеҚ—ж–№жңұйёҹвҖқдёӯд»ЈиЎЁвҖң鹑йҰ–вҖқзҡ„дә•гҖҒй¬јдёӨдёӘжҳҹе®ҝгҖӮгҖҠејҖе…ғеҚ з»ҸгҖӢеҚ·е…ӯеҚҒдёүеј•гҖҠй»„еёқеҚ 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дёңдә•пјҢеӨ©еәңжі•д»Өд№ҹгҖӮвҖҰвҖҰдёңдә•дё»ж°ҙпјҢз”Ёжі•жё…е№іеҰӮж°ҙпјҢзҺӢиҖ…еҝғжӯЈпјҢеҫ—еӨ©зҗҶпјҢеҲҷдә•жҳҹжӯЈиЎҢдҪҚпјҢдё»жі•еҲ¶и‘—жҳҺгҖӮвҖқеј•з”ҳж°Ҹжӣ°пјҡвҖңз”Ёжі•е№іпјҢзҺӢиҖ…еҝғжӯЈпјҢеҲҷдә•жҳҹжҳҺпјҢиЎҢдҪҚзӣҙгҖӮй’әжҳҹжҳҺпјҢеҲҷиҮЈеӨҡзҠҜзҪӘиҖ…гҖӮвҖқеј•зҹіж°Ҹиөһжӣ°пјҡвҖңдёңдә•дё»ж°ҙиЎЎд»Ҙе№іж—¶пјҢж•…зҪ®й’әжҳҹж–©ж·«еҘўгҖӮдёңдә•е…«жҳҹдё»ж°ҙиЎЎпјҢдә•иҖ…иұЎжі•ж°ҙпјҢжі•ж°ҙе№іе®ҡпјҢжү§жҖ§дёҚж·«пјҢж•…дё»иЎЎгҖӮвҖқеј•гҖҠеҚ—е®ҳеҖҷ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иҲҶй¬јдёҖеҗҚеӨ©й”§пјҢдёҖеҗҚеӨ©и®јпјҢдё»еҜҹеҘёгҖӮвҖқеј•зҹіж°Ҹиөһжӣ°пјҡвҖңиҲҶй¬ји§ҶжҳҺеҜҹеҘёи°ӢпјҢж•…еҲ¶дә”иҜёдҫҜд»ҘеҲәд№ӢгҖӮиҲҶй¬јдә”жҳҹдё»и§ҶжҳҺпјҢд»Һйҳҙи§ҶйҳідёҚеӨұзІҫгҖӮвҖқгҖҠеҸІи®°В·еӨ©е®ҳд№Ұ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ёңдә•дёәж°ҙдәӢгҖӮе…¶иҘҝжӣІжҳҹжӣ°й’әгҖӮвҖқеј е®ҲиҠӮжӯЈд№үдә‘пјҡвҖңдёңдә•е…«жҳҹпјҢй’әдёҖжҳҹпјҢиҲҶй¬јеӣӣжҳҹпјҢдёҖжҳҹдёәиҙЁпјҢдёәвҖҳ鹑йҰ–вҖҷпјҢдәҺиҫ°еңЁжңӘпјҢзҡҶз§Ұд№ӢеҲҶйҮҺгҖӮдёҖеӨ§жҳҹпјҢй»„йҒ“д№ӢжүҖз»ҸпјҢдёәеӨ©д№ӢдәӯеҖҷпјҢдё»ж°ҙиЎЎдәӢпјҢжі•д»ӨжүҖеҸ–е№ід№ҹгҖӮзҺӢиҖ…з”Ёжі•е№іпјҢеҲҷдә•жҳҹжҳҺиҖҢз«ҜеҲ—гҖӮвҖҳй’әвҖҷдёҖжҳҹйҷ„вҖҳдә•вҖҷд№ӢеүҚпјҢдё»дјәеҘўж·«иҖҢж–©д№ӢгҖӮвҖқгҖҠжҷӢд№ҰВ·еӨ©ж–Үеҝ—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ҲҶй¬јдә”жҳҹпјҢеӨ©зӣ®д№ҹпјҢдё»и§ҶпјҢжҳҺеҜҹеҘёи°ӢгҖӮвҖқеҸҜи§ҒпјҢдә•гҖҒй¬јдёӨе®ҝз»„жҲҗзҡ„вҖң鹑йҰ–вҖқпјҢжҳҹеҚ дёҠжүҖдё»иҖ…дёәжі•д»ӨгҖҒиҜүи®јзӯүпјҢиұЎеҫҒеӨ©йҒ“зҡ„е…¬жӯЈдёҺжҳҺеҜҹгҖӮд»ҺгҖҠеӨ§иҪҰгҖӢиҜ—дј иҫҫеҮәзҡ„дҝЎжҒҜзңӢпјҢиЎЁжј”иҖ…жҲ–и®ёиЈ…жү®жҲҗйёҹзҡ„ж ·еӯҗпјҢд»ҘжЁЎд»ҝеӨ©дёҠзҡ„йёҹжҳҹпјҢд»ҘзҘһйҒ“и®ҫж•ҷпјҢеҸҜд»ҘжӣҙеҘҪең°иө·еҲ°ж•ҷеҢ–дёҺе‘ҠиҜ«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гҖҠзӨји®°В·зӨјиҝҗгҖӢжүҖдә‘вҖңеӨ«зӨјпјҢе…ҲзҺӢд»ҘжүҝеӨ©д№ӢйҒ“пјҢд»ҘжІ»дәәжғ…вҖқпјҢгҖҠеӨ§жҲҙзӨји®°В·иҷһжҲҙеҫ·гҖӢжүҖи°“вҖңжҳҺжі•дәҺеӨ©жҳҺпјҲиұЎпјүпјҢејҖж–Ҫж•ҷдәҺж°‘вҖқпјҢйғҪжңүзҘһйҒ“и®ҫж•ҷзҡ„ж„Ҹе‘ігҖӮеӨ§еӨ«е·ЎиЎҢгҖҒеҶіи®јж—¶з©ҝзҡ„вҖңжҜіиЎЈвҖқпјҢжҜӣдј пјҡвҖңд№ҹпјҢиҠҰд№ӢеҲқз”ҹиҖ…д№ҹгҖӮвҖқд»ҘвҖңвҖқеҪўе®№жҜіиЎЈпјҢеҪ“жҳҜеҸӨжқҘдј жүҝпјҢ并йқһз”Ёд№ӢйўңиүІзҠ¶жҜіиЎЈгҖӮвҖңжҜіиЎЈеҰӮиҸјвҖқеҰӮиҜҙжҲҗжҳҜжҜіиЎЈеҰӮжҹҗз§ҚйўңиүІпјҢжҳҫ然дёҚйҖҡпјӣеҰӮжһңиҜҙжҜіиЎЈеғҸжҹҗдёӘйёҹзұ»пјҢеҲҷйЎәзҗҶжҲҗз« гҖӮйғ‘зҺ„гҖҠз¬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ҸјпјҢд№ҹгҖӮеҸӨиҖ…пјҢеӨ©еӯҗеӨ§еӨ«жңҚжҜіеҶ•д»Ҙе·ЎиЎҢйӮҰеӣҪпјҢиҖҢеҶіз”·еҘід№Ӣи®јпјҢеҲҷжҳҜеӯҗз”·е…ҘдёәеӨ§еӨ«иҖ…гҖӮвҖқвҖңжҜіиЎЈд№ӢеұһпјҢиЎЈиҖҢиЈіз»ЈпјҢзҡҶжңүдә”иүІз„үпјҢе…¶йқ’иҖ…еҰӮ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иҷҪдәҰд»ҘиҸјдёәпјҢ然жҚ®гҖҠе°ҡд№ҰВ·зҡӢйҷ¶и°ҹгҖӢвҖңеҸӨдәәд№ӢиұЎвҖқд№ӢиҜҙжҢҮеҮәпјҢжҜіиЎЈд№Ӣзұ»з”ЁдәҺе·Ўе®Ҳзҡ„иЎЈиЈіе…¶дёҠжңүз»ҳз”»жҲ–еҲәз»ЈпјҢзҡҶжңүдә”иүІпјҢе…¶дёӯйқ’иүІиҖ…дјјгҖӮйғ‘зҺ„д№ӢиҜҙиҷҪ然жңүдәӣеҗ«зіҠпјҢеҚҙиҜҙжҳҺдәҶжҜіиЎЈйқ’иүІеҰӮзҡ„зү№зӮ№гҖӮйқ’иүІдёҺжҳҘеӨ©еҜ№еә”пјҢжӯЈжҳҜз”·еҘіиҒҡдјҡжӢ©еҒ¶зҡ„ж—¶иҠӮгҖӮ3.вҖңвҖқдёәвҖңзҘқйё вҖқвҖ”вҖ”е‘ЁеҲқд№җиҲһвҖңж•ҷеҢ–вҖқд№ӢиҢғеҲ°еә•жҳҜд»Җд№ҲйёҹпјҢгҖҠиҜ—В·е°Ҹйӣ…В·еӣӣзүЎ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зҝ©зҝ©иҖ…гҖӮвҖқжҜӣгҖҠдј гҖӢпјҡвҖңпјҢеӨ«дёҚд№ҹгҖӮвҖқйғ‘гҖҠз¬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Ө«дёҚпјҢйёҹд№ӢжӮ«и°ЁиҖ…пјҢдәәзҡҶзҲұд№ӢгҖӮвҖқгҖҠе°”йӣ…В·йҮҠйё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йҡ№е…¶пјҢгҖӮвҖқйғӯз’һжіЁпјҡвҖңд»Ҡйё гҖӮвҖқйӮўжҳәз–Ҹдә‘пјҡвҖңжқҺе·Ўжӣ°пјҡвҖҳд»ҠжҘҡйё д№ҹгҖӮвҖҷжҹҗж°Ҹеј•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дә‘пјҡвҖҳзҘқйё ж°ҸеҸёеҫ’гҖӮвҖҷзҘқйё пјҢеҚіе…¶гҖҒеӨ«дёҚпјҢеӯқпјҢж•…дёәеҸёеҫ’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йёҹйғЁдә‘пјҡвҖңпјҢзҘқйё д№ҹгҖӮд»Һйёҹйҡ№еЈ°гҖӮжҲ–д»Һйҡ№дёҖгҖӮдёҖжӣ°й№‘еӯ—гҖӮвҖқвҖңвҖқдёҖжӣ°вҖң鹑вҖқеӯ—д№ӢиҜҙж„Ҹе‘іж·ұй•ҝпјҢеӨ©дёҠд№Ӣдә•гҖҒй¬јдёӨжҳҹе®ҝжӯЈдёәвҖң鹑йҰ–вҖқгҖӮжҲ–д»ҘвҖңд»Һйҡ№дёҖвҖқдёәй№°йҡјд№ӢвҖңйҡјвҖқпјҢжҒҗжҳҜи®№иҜҜпјҢй№°йҡјеҪ“дёҚеҫ—вҖңеӯқйёҹвҖқд№Ӣз§°пјҢеҜ№жӯӨжё…д»ЈеӯҰиҖ…жЎӮйҰҘжңүз»ҶиҮҙзҡ„иҫЁжһҗпјҡвҖң жҲ–д»Һйҡ№дёҖвҖқиҖ…пјҢгҖҠиҜ—В·йҮҮиҠ‘гҖӢжӯЈд№үеј•дә‘пјҡвҖңйҡјпјҢйё·йёҹ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е…ӯд№Ұж•…гҖӢеј•е”җжң¬вҖңд»ҺйёҹпјҢд»Һйҡ№гҖӮйҡјд»Һйҡ№д»ҺеҚӮзңҒгҖӮвҖқжқҺйҳіеҶ°жӣ°пјҡвҖңйҡјеҚӮзңҒеЈ°гҖӮвҖқдҫ—жҢүпјҡвҖң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дёҚд»Ҙйҡјдёәйё·йёҹпјҢиҖҢгҖҠиҜ—В·з–ҸгҖӢеј•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д№ғжӣ°вҖҳйҡјпјҢйё·йёҹд№ҹгҖӮвҖҷ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еӣәеӨҡејӮжң¬йӮӘгҖӮвҖқйҷҲеӨ§з« гҖҠиҜ—дј еҗҚзү©йӣҶи§ҲгҖӢжЎҲпјҡвҖңвҖҳ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дёҚд»Ҙйҡјдёәйё·йёҹиҖҢгҖҠиҜ—В·з–ҸгҖӢеј•д№ӢвҖҷдә‘пјҡвҖҳ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йё·йёҹеҸҜзҹҘгҖӮ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йҡҸдәәйҷ„дјҡпјҢй—ҙжңүи®№иҖ…пјҢйқһе°Ҫе…¶жң¬ж–Үд№ӢеӨұд№ҹгҖӮвҖҷвҖқйҰҘжЎҲпјҡвҖңгҖҠд№қ家жҳ“гҖӢдә‘вҖҳйҡјпјҢйё·йёҹд№ҹгҖӮе…¶жҖ§з–ҫе®ігҖӮвҖҷйҹҰжіЁгҖҠеӣҪиҜӯгҖӢвҖҳйҡјпјҢйё·йёҹпјҢд»Ҡд№Ӣй№—д№ҹгҖӮвҖҷвҖқйғ‘жіЁгҖҠжңҲд»ӨгҖӢвҖңй№°йҡјж—©йё·вҖқдә‘пјҡвҖңеҫ—з–ҫеҺүд№Ӣж°”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дәўд»“еӯҗгҖӢжіЁпјҡвҖңйё·йҡјпјҢйӣ•й№—д№Ӣзұ»гҖӮвҖқиҜёд№ҰзҡҶд»Ҙйҡјдёәйё·йёҹгҖӮжқңйў„и°“зҘқйё еӯқпјҢж•…дёәеҸёеҫ’пјҢдё»ж•ҷж°‘гҖӮйё·йёҹдёҚеҫ—з§°еӯқпјҢдёҚеҸҜд»Ҙж•ҷж°‘гҖӮгҖҠзҰҪз»ҸгҖӢвҖңдёҠж— еҜ»вҖқпјҢиЁҖдёҚиғҪй«ҳйЈһгҖӮйҡјдёҺзҘқйё дёҚеҗҢзү©гҖӮжң¬д№ҰдёәдәәжүҖд№ұгҖӮжЎӮйҰҘиҫЁжһҗйқһйё·йёҹпјҢи®әиҜҒжһҒдёәжңүеҠӣпјҢд»–еҸҲи®ӨеҗҢжқңйў„зҘқйё д№ӢиҜҙпјҢ笔иҖ…дәҰиөһеҗҢе…¶иҜҙгҖӮ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гҖҠе°”йӣ…гҖӢжүҖиҪҪд№ӢвҖңвҖқйёҹпјҢжңӘи§Ғе…¶жңүиүІйқ’д№Ӣзү№еҫҒпјҢдё”вҖңвҖқ究з«ҹдёәдҪ•йёҹпјҢеүҚдәәиҜҙжі•еӨҡз«ҜгҖӮгҖҠиҜ—зјүгҖӢи°“жңүеҚҒеӣӣз§ҚпјҢиҖҢгҖҠе·Ұдј В·жҳӯе…¬еҚҒдёғе№ҙгҖӢдёӯжҸҗеҲ°вҖңзҘқйё ж°ҸвҖқпјҢеҪ“дёәе…¶еҺҹеһӢпјҡвҖңпјҢйё д№ҹгҖӮеҚійғҜеӯҗвҖҳзҘқйё ж°ҸеҸёеҫ’вҖҷд№ҹгҖӮдёҖйёҹиҖҢеҚҒеӣӣеҗҚпјҢд№ҹпјҢйҡ№е…¶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зҘқйё д№ҹпјҢ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жҘҡ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иҚҶ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пјҢйё д№ҹгҖӮгҖҠе·Ұдј гҖӢжқңйў„жіЁжӣ°пјҡвҖҳзҘқйё еӯқпјҢж•…дё»дәҺж•ҷж°‘гҖӮвҖҷвҖқгҖҠе·Ұдј В·жҳӯе…¬еҚҒдёғе№ҙгҖӢйғҜеӯҗдә‘пјҡвҖңзҘқйё ж°ҸпјҢеҸёеҫ’д№ҹгҖӮвҖқжқңйў„жіЁпјҡвҖңзҘқйё пјҢйё д№ҹгҖӮйё еӯқпјҢж•…дёәеҸёеҫ’пјҢдё»ж•ҷж°‘гҖӮвҖқеҸҲдә‘пјҡвҖңдә”йё пјҢйё ж°‘иҖ…д№ҹгҖӮвҖқжқңйў„жіЁпјҡвҖңйё пјҢиҒҡд№ҹгҖӮжІ»ж°‘дёҠиҒҡпјҢж•…д»Ҙйё дёәеҗҚгҖӮвҖқжІ»ж°‘ж•ҷж°‘йңҖиҰҒиҒҡйӣҶж°‘дј—пјҢеӣ жӯӨд»Ҙйё дёәеҗҚгҖӮ然еҲҷвҖңзҘқйё вҖқжҳҜдёҠеҸӨеҸёеҫ’д№ӢвҖңиұЎвҖқпјҢ并йқһе®һжңүд№ӢйёҹгҖӮе‘Ёдәә继жүҝдәҶиҝҷж ·зҡ„дј з»ҹпјҢеңЁд»ІжҳҘж—¶иҠӮпјҢеңЁвҖңзӨҫвҖқзӯүзү№е®ҡеңәжүҖйӣҶдёӯ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пјҢз”Ёжү®жҲҗвҖңзҘқйё вҖқзҡ„еҸёеҫ’иЎЁжј”жӯҢиҲһзҡ„еҪўејҸпјҢеҜ№д»–们иҝӣиЎҢзӣҙи§ӮејҸзҡ„дјҰзҗҶж•ҷиӮІпјҢеҸҜиғҪд№ҹдјҡе®Јдј дёҺе©ҡ姻зӣёе…ізҡ„зӨјеҲ¶пјҢд»ҘйҒҝе…Қејәжҡҙж— зӨјзҡ„зҺ°иұЎеҮәзҺ°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жүҖеҶҷеҶ…е®№жңӘеҝ…жҳҜе®һжңүд№ӢдәӢ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иҘҝе‘ЁеҗҺжңҹжҲ–дёңе‘ЁеүҚжңҹзҡ„еҸІе®ҳж №жҚ®еҺҹе§Ӣд№җиҲһж”№дҪңиҖҢжҲҗгҖӮиҝҷзұ»еҺҹе§Ӣд№җиҲһжҳҜвҖңеҸ¬е…¬вҖқд№Ӣзұ»зҡ„е…¬еҚҝеӨ§еӨ«жүҖеҲӣдҪң并表演пјҢз”ЁдәҺд»ІжҳҘж—¶иҠӮеҜ№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зҡ„ж•ҷеҢ–гҖӮгҖҠиЎҢйңІгҖӢ第дәҢгҖҒдёүз« йғҪдёәеҸ¬е…¬жҲ–еҸёеҫ’д№Ӣзұ»зҡ„е·Ўе®ҲеӨ§еӨ«жүҖжӯҢжүҖжј”пјҢйҰ–дәҢеҸҘиҜҙвҖңи°Ғи°“йӣҖж— и§’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ұӢвҖқдёҺвҖңи°Ғи°“йј ж— зүҷпјҢдҪ•д»Ҙз©ҝжҲ‘еўүвҖқпјҢеҲҶеҲ«з”ЁжқҘејәи°ғвҖңеӨ©зҗҶвҖқе’ҢвҖңең°д№үвҖқгҖӮ4.йј вҖ”вҖ”зӨјд»Әзҡ„иұЎеҫҒйј еңЁеҪ“ж—¶жҳҜзӨјд»Ә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гҖҠиҜ—В·й„ҳйЈҺВ·зӣёйј 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зӣёйј жңүзҡ®пјҢдәәиҖҢж— д»ӘгҖӮдәәиҖҢж— д»ӘпјҢдёҚжӯ»дҪ•дёәпјҹзӣёйј жңүйҪҝпјҢдәәиҖҢж— жӯўгҖӮдәәиҖҢж— жӯўпјҢдёҚжӯ»дҪ•дҝҹпјҹзӣёйј жңүдҪ“пјҢдәәиҖҢж— зӨјгҖӮдәәиҖҢж— зӨјпјҢиғЎдёҚйҒ„жӯ»пјҹвҖқгҖҠе°ҸеәҸгҖӢи°“вҖңеҲәж— зӨјвҖқпјҢжҜӣгҖҒйғ‘д№ҹзҡҶи°“гҖҠзӣёйј гҖӢиҜ—дёӯд№Ӣйј жҳҜзӨјд»Ә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иҜ—дёӯжүҖеҶҷд№Ӣйј зҺ°д»ЈеҠЁзү©еӯҰ家称дёәвҖңиӨҗе®¶йј вҖқпјҢжҳҜвҖңдҪ“еһӢжҜ”иҫғзІ—еӨ§зҡ„дёҖз§ҚпјҢдҪ“й•ҝжңҖеӨ§еҸҜиҫҫ20еҺҳзұігҖӮиҖіиҫғзҹӯгҖӮе°ҫжҜ”иә«дҪ“зҹӯгҖӮеҗҺи¶іиҫғзІ—еӨ§вҖқгҖӮеӣ е…¶еҗҺи¶ізІ—еӨ§пјҢжүҖд»Ҙз«ҷз«Ӣ并дёҚеӣ°йҡҫгҖӮйј дҪ•д»ҘиғҪжҲҗдёәзӨјд»Ә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зҪ—ж„ҝзҡ„гҖҠе°”йӣ…зҝјВ·йҮҠе…ҪгҖӢиҜҙеҫ—еҫҲжҳҺзҷҪпјҡгҖҠиҜ—гҖӢз§°вҖңзӣёйј вҖқпјҢд»ҘеҲәдәәд№Ӣж— зӨјиҖ…гҖӮд»ҠжІідёңжңүеӨ§йј пјҢиғҪдәәз«ӢпјҢдәӨдёӨи„ҡдәҺйўҲдёҠпјҢжҲ–и°“д№ӢйӣҖйј пјҢйҹ©йҖҖд№ӢжүҖи°“вҖңзӨјйј жӢұиҖҢз«ӢвҖқиҖ…д№ҹгҖӮзӣёйј вҖңжңүзҡ®вҖқпјҢеҸҲвҖңжңүйҪҝвҖқгҖҒвҖңжңүдҪ“вҖқгҖӮзҡ®пјҢеӨ–йҘ°д№ҹпјҢж•…иұЎдәәд№Ӣжңүд»ӘгҖӮйҪҝжңүж—¶д»Ҙе•®пјҢжңүж—¶д»ҘжӯўпјҢеңЁгҖҠжҳ“гҖӢвҖңиү®дёәйј вҖқпјҢж•…йҪҝиұЎжӯўгҖӮдҪ“иҖ…пјҢзҷҫдҪ“д№ӢеҠЁд№ҹпјҢгҖҠиҜҙж–ҮгҖӢдҪ“еӯ—дә‘пјҡвҖңжҖ»еҚҒдәҢеұһд№ҹгҖӮвҖқзӣ–йј дёәеҚҒдәҢеұһд№ӢйҰ–пјҢеҸҲеҘҪж‘©еј„е…¶й«ӯпјҢзӣёж—¶иҖҢиҝӣпјҢж•…дҪ“иұЎзӨјгҖӮгҖҠеҗ•ж°ҸжҳҘз§Ӣ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е‘ЁйјҺи‘—йј пјҢд»Ө马еұҘд№ӢпјҢдёәе…¶дёҚйҳід№ҹгҖӮвҖқгҖҠе…іе°№еӯҗ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еёҲжӢұйј еҲ¶зӨјгҖӮвҖқ дёҚд»…зҪ—ж„ҝпјҢеүҚд»ЈеӯҰиҖ…д№ҹеӨҡи®ӨдёәжңүвҖңзӨјйј вҖқиҖ…гҖӮеӯ”йў–иҫҫз–ҸгҖҠиҜ—В·зЎ•йј гҖӢж—¶еј•йҷҶзҺ‘гҖҠиҚүжңЁйёҹе…Ҫиҷ«йұјз–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»ҠжІідёңжңүеӨ§йј пјҢиғҪдәәз«ӢпјҢдәӨеүҚдёӨи„ҡдәҺйўҲдёҠи·іиҲһпјҢе–„йёЈпјҢйЈҹдәәзҰҫиӢ—гҖӮдәәйҖҗеҲҷиө°е…Ҙж ‘з©әдёӯгҖӮдәҰжңүдә”жҠҖпјҢжҲ–и°“д№ӢйӣҖйј гҖӮжҲ–и°“д№ӢйӣҖйј пјҢе…¶еҪўеӨ§пјҢж•…еәҸдә‘вҖҳеӨ§йј вҖҷд№ҹгҖӮвҖқжҜӣжҷӢдә‘пјҡгҖҠж–Үеӯҗ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ңЈдәәеёҲжӢұйј еҲ¶зӨјгҖӮвҖқгҖҠеҪ•ејӮи®°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Ӣұйј еҪўеҰӮеёёйј пјҢиЎҢз”°йҮҺдёӯпјҢи§ҒдәәеҚіжӢұжүӢиҖҢз«ӢгҖӮдәәиҝ‘ж¬ІжҚ•д№ӢпјҢеҚіи·іи·ғиҖҢиө°еҺ»гҖӮвҖқ жІідёңеӨ§йј пјҢиғҪеғҸдәәйӮЈж ·з«ҷз«ӢпјҢдё”и§Ғдәәе°ұвҖңжӢұжүӢиҖҢз«Ӣ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еҸӨдәәеҸҲеҗҚд№ӢдёәвҖңжӢұйј вҖқгҖӮзҪ—ж„ҝгҖҒжҜӣжҷӢзҡҶи°“гҖҠе…іе°№еӯҗгҖӢдёҖд№Ұе·Іи®°иҪҪеҸӨеңЈдәәвҖңеёҲжӢұйј еҲ¶зӨјвҖқгҖӮдё”йҷҶзҺ‘жңүиҜҙпјҢйҹ©ж„ҲжңүиҜ—пјҢиҜҙжҳҺеҸӨдәәвҖңеёҲжӢұйј еҲ¶зӨјвҖқжңӘеҝ…жІЎжңүж №жҚ®гҖӮд№ҹжңүдәәи®ӨдёәзӨјйј жҢҮй»„йј зӢјпјҢеҲҳжҜ“еәҶеј•еј еӯҳз»…гҖҠеўһи®ўйӣ…дҝ—зЁҪиЁҖгҖӢеҚ·дәҢеҚҒдёүвҖңзӣёйј вҖқжқЎдә‘пјҡвҖңдёҖжӣ°й»„йј з©ҙеұ…пјҢеҗ„жңүжӯЈеҢ№пјҢжҜҸеҮәз©ҙпјҢи§ҒдәәеҲҷжӢұеүҚи…ӢиҖҢжҸ–пјҢжүҖи°“вҖҳзӨјйј жӢұиҖҢз«ӢвҖҷиҖ…д№ҹгҖӮвҖқй»„йј зӢјеҘҪеҗғйј зұ»гҖҒиӣҷзұ»е’ҢжҳҶиҷ«пјҢжІЎжңүйЈҹдәәзҰҫиӢ—зӯүзү№еҫҒпјҢеҸҲеӨҡз©ҙеұ…дәҺеІ©зҹігҖҒж ‘жҙһзӯүеӨ„пјҢ并дёҚз©ҙдәҺз”°й—ҙпјҢжӯӨиҜҙжҒҗйқһжҳҜ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жӢұйј еҸҲеҗҚвҖңйӣҖйј вҖқпјҢеӯ—жҲ–еҶҷдҪңвҖңвҖқпјҢжҜӣжҷӢгҖҠе№ҝиҰҒгҖӢеј•гҖҠеҚҡйӣ…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пјҢпјҢйј«йј гҖӮвҖқгҖҠж–№иЁҖгҖӢеҚ·е…«дә‘пјҡвҖңе®ӣгҖҒйҮҺи°“йј дёәгҖӮвҖқйғӯз’һжіЁпјҡвҖңе®ӣгҖҒж–°йҮҺпјҢд»ҠзҡҶеңЁеҚ—йҳігҖӮвҖқиҝҷи®©жҲ‘们иҒ”жғіиө·гҖҠеӨ§жҲҙзӨји®°В·еӨҸе°ҸжӯЈгҖӢдёүжңҲзҡ„вҖңжңҲд»ӨвҖқпјҡвҖңз”°йј еҢ–дёәгҖӮвҖқеҚўиҫ©жіЁпјҡвҖңпјҢй№Ңд№ҹгҖӮеҸҳиҖҢд№Ӣе–„пјҢж•…е°Ҫе…¶иҫһд№ҹгҖӮдёәйј пјҢеҸҳиҖҢдёҚиҮіе–„пјҢж•…дёҚе°Ҫе…¶иҫһд№ҹгҖӮвҖқеҗҢд№ҰвҖңе…«жңҲвҖқдә‘пјҡвҖңдёәйј гҖӮвҖқгҖҠзӨји®°В·жңҲд»ӨгҖӢжүҖиҪҪдёҺжӯӨзӣёеҗҢпјҢиҝҷз§ҚйёҹгҖҒйј дә’еҸҳзҡ„и§ӮеҝөжҳҜдёҚжҳҺеҖҷйёҹзӯүзҡ„иҝҒеҫҷзү№еҫҒжүҖиҮҙгҖӮеңЁеҸӨдәәзҡ„и§ӮеҝөдёӯпјҢйј е…·жңүжҢҮзӨәж—¶д»Ө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гҖҠеӨҸе°ҸжӯЈгҖӢжӯЈжңҲеҚі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з”°йј еҮәгҖӮвҖқеҚўиҫ©жіЁпјҡвҖңз”°йј иҖ…пјҢе—ӣйј д№ҹгҖӮи®°ж—¶д№ҹгҖӮвҖқжӯӨеҚізҪ—ж„ҝжҰӮжӢ¬зҡ„вҖңжңүж—¶д»ҘжӯўвҖқвҖңзӣёж—¶иҖҢиҝӣвҖқгҖӮйј и§ҒдәәвҖңжӢұжүӢиҖҢз«ӢвҖқд»ҘеҸҠжҢүж—¶иҖҢеҮәпјҢжҢүж—¶еҸҳеҢ–зҡ„вҖңжңүиЎҢжӯўвҖқпјҢиҪҪдәҺгҖҠжңҲд»ӨгҖӢпјҢз”ЁдәҺи®°ж—¶гҖӮд№ҹжңүдәәи®Өдёәйј дёәжҳҹиҫ°д№ӢвҖңж•ЈзІҫвҖқпјҢеҰӮгҖҠеӨӘе№іеҫЎи§ҲгҖӢеј•гҖҠжҳҘз§Ӣиҝҗж–—жһўгҖӢжӣ°вҖңзҺүиЎЎжҳҹж•ЈиҖҢдёәйј вҖқпјҢжүҖи°“вҖңзҺүиЎЎвҖқжҳҜжҢҮеҢ—斗第дә”жҳҹпјҢгҖҠејҖе…ғеҚ з»ҸгҖӢеҚ·е…ӯеҚҒдёғеј•з”ҳж°Ҹжӣ°пјҡвҖңиЎЎжҳҹеҲҶж°‘пјҢеҲҷжі•д»Өд»ҺпјҢеҫ®з»ҶеҲҷжі•д»ӨдёҚиЎҢгҖӮиЎЎжҳҹзӣёз–ҸпјҢжі•д»Өзј“пјӣзӣёеҺ»ж•°пјҢжі•д»ӨжҖҘгҖӮвҖқиҝҷжҝҖеҸ‘иө·вҖңеҸӨеңЈдәәвҖқеҲ¶зӨјзҡ„зҒөж„ҹпјҢжҳҜе®Ңе…ЁжңүеҸҜиғҪзҡ„гҖӮ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ёӯд»Ҙйј з©ҝеўҷдёәе–»пјҢеҗҢж ·еҜҢжңүж·ұж„ҸгҖӮеӣ дёәйј жҳҜзӨјд»Ә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иҜ—дәәз”ЁжӯӨдёӨдёӘвҖңе…ҙиұЎвҖқ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е‘ҠиҜ«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дәҺе©ҡ姻еӨ§дәӢиҰҒе®Ҳжі•е®ҲзӨјгҖӮеӣ дёәеӨ©дёҠжңүзҘһжҳҺпјҢдәәй—ҙжңүзӨјд№үгҖӮеҗҺдәҢеҸҘвҖңи°Ғи°“еҘіж— 家пјҢдҪ•д»ҘйҖҹжҲ‘зӢұвҖқдёҺвҖңи°Ғи°“еҘіж— 家пјҢдҪ•д»ҘйҖҹжҲ‘и®јвҖқеҗҢж ·дёәиЎЁжј”иҖ…жүҖе”ұпјҢж„Ҹдёәпјҡи°ҒиҜҙеҘіпјҲдҪ пјүжІЎжңү家е®ӨпјҢдёәдҪ•еҲ°жҲ‘иҝҷйҮҢжү“е®ҳеҸёпјҹиҝҷйҮҢзҡ„вҖңжҲ‘вҖқеҪ“жҢҮе·Ўе®ҲеӨ§еӨ«пјҢдәҰеҚіиЎЁжј”иҖ…иҖҢиЁҖгҖӮжӯӨдёӨеҸҘпјҢдјјд№Һй’ҲеҜ№з”·еҘідёӨж–№иҖҢиЁҖпјҢжҳҺзЎ®е‘ҠиҜ«з”·еҘійқ’е№ҙеңЁе©ҡ姻еӨ§дәӢдёҠиҰҒе®һдәӢжұӮжҳҜпјҢжүӘеҝғиҮӘй—®пјҢдёҚиҰҒйҡҗзһ’е®һжғ…пјҢиҝқеҸҚзӨјд№үгҖӮдәҢгҖҒдёүз« жңҖеҗҺдәҢеҸҘвҖңиҷҪйҖҹжҲ‘зӢұпјҢе®Ө家дёҚи¶івҖқеҸҠвҖңиҷҪйҖҹжҲ‘и®јпјҢдәҰдёҚеҘід»ҺвҖқеҲҷжҳҜиЎЁжј”иҖ…зҡ„вҖңиӘ“иЁҖвҖқпјҢж„ҸжҖқжҳҜпјҡеҚідҪҝдҪ зЎ¬иҰҒжү“е®ҳеҸёпјҢд№ҹдёҚдјҡи®©дҪ еҫ—йҖһгҖӮиҝҷйўҮжңүдёҖзӮ№еҗҺжқҘеӯ”еӯҗзҡ„вҖңеҝ…д№ҹж— и®јд№ҺвҖқзҡ„ж„Ҹе‘ігҖӮ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йҰ–з« вҖңеҺҢжөҘиЎҢйңІпјҢеІӮдёҚеӨҷеӨңпјҹи°“иЎҢеӨҡйңІвҖқзӮ№жҳҺж—¶иҠӮпјҢйӣҶдёӯз”·еҘізҡ„ж—¶й—ҙдјјд№ҺжҳҜжҷҡдёҠпјҢжҷҡй—ҙжүҚжңүйңІж°ҙгҖӮвҖңиЎҢвҖқжҢҮйҒ“и·ҜпјҢдјјд№ҺжҳҜжҸҸиҝ°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иө¶иөҙйӣҶдёӯең°зӮ№д№Ӣжғ…жҷҜгҖӮиҝҷеӨ§зәҰжҳҜдҪңжӯӨиҜ—иҖ…жүҖдёәгҖӮйҖүжӢ©жҷҡдёҠжҒҗжҖ•д№ҹжҳҜдёәдәҶжңүеҲ©дәҺжҳҫзӨәеӨ©йҒ“зҡ„еЁҒеҠӣпјҢжҷҡдёҠдәә们еҸҜд»Ҙжё…жҷ°ең°зңӢеҲ°еӨ©дёҠй—ӘзғҒзҡ„вҖңйӣҖи§’вҖқпјҢжӣҙиғҪеӨҹж„ҹи§үиҝҷдәӣжҳҹиҫ°жҳҺеҜҹдёҖеҲҮзҡ„зҘһеҠӣгҖӮеӣӣгҖҒдёҠеҸӨвҖңзҘқйё вҖқпјҲеҸёеҫ’пјүзҡ„ж•ҷж°‘д»ӘзӨј еӯ”еӯҗжӣҫж•ҷеҜјеӯҰз”ҹиҜҙпјҡвҖңе°ҸеӯҗдҪ•иҺ«еӯҰд№ҺиҜ—пјҹиҜ—еҸҜд»Ҙе…ҙпјҢеҸҜд»Ҙи§ӮпјҢеҸҜд»ҘзҫӨпјҢеҸҜд»ҘжҖЁпјӣиҝ©д№ӢдәӢзҲ¶пјҢиҝңд№ӢдәӢеҗӣпјӣеӨҡиҜҶдәҺйёҹе…ҪиҚүжңЁд№ӢеҗҚгҖӮвҖқпјҲгҖҠи®әиҜӯВ·йҳіиҙ§гҖӢпјүеҜ№жӯӨпјҢ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еӨҸеҗ«еӨ·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вҖҳеӨҡиҜҶдәҺйёҹе…ҪиҚүжңЁд№ӢеҗҚвҖҷ并дёҚжҳҜжҢҮеҠЁзү©еӯҰжҲ–иҖ…жӨҚзү©еӯҰзҡ„зҹҘиҜҶпјҢиҖҢжҳҜиҜҙйҖҡиҝҮгҖҠиҜ—гҖӢжҲ‘们еҸҜд»Ҙи®ӨиҜҶйёҹе…ҪиҚүжңЁзҡ„иұЎеҫҒжҖ§иҙЁпјҢ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еұұйҷөдёәд»Җд№ҲеҚұйҷ©гҖҒйёҝйӣҒдёәд»Җд№Ҳе’Ңе©ҡ姻问йўҳжңүе…ізі»гҖӮвҖқиҷҪ然еӨҸж°ҸеӨҡд»ҺвҖңеҚ еҚңвҖқеҸҠвҖңзҘһе–»вҖқи§’еәҰи°Ҳ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зҡ„иҚүжңЁиҷ«йұјпјҢдҪҶд»–д»Ҙдёә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з”ЁжқҘиө·е…ҙзҡ„еҠЁгҖҒжӨҚзү©е…·жңүиұЎеҫҒж„Ҹд№үпјҢжҳҜеҚҒеҲҶжӯЈзЎ®зҡ„гҖӮз”Ёиҝҷж ·зҡ„еҪўејҸж•ҷеҢ–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пјҢеңЁе‘ЁеҲқдјјд№ҺеҸ–еҫ—дәҶиүҜеҘҪзҡ„ж•ҲжһңпјҢиҝҷд№ҹжҳҜеҗҺдәәеҜ№ж–ҮзҺӢгҖҒе‘Ёе…¬зӯүзҡ„ж•ҷеҢ–жҙҘжҙҘд№җйҒ“зҡ„еҺҹеӣ гҖӮеӣ дёәеӯқеңЁеҗҺжқҘжҲҗдәҶйҒ“еҫ·д№ӢйҰ–пјҢжүҖд»ҘжңүвҖңзҘқйё еӯқвҖқзҡ„йҷ„дјҡд№ӢиҜҙгҖӮе…¶е®һж•ҷеҢ–зҡ„еҶ…е®№дё»иҰҒеӨ§жҰӮжҳҜжүҖи°“зҡ„дә”дјҰжҲ–жӣ°дә”зӨјпјҢиҖҢз”·еҘід№Ӣй—ҙзҡ„е©ҡ姻д№ӢзӨјеҚ жңүйҮҚиҰҒзҡ„ең°дҪҚгҖӮдёҠеҸӨд»ҘеҸёеҫ’д№ӢиҒҢдёәвҖңж•ҷж°‘вҖқпјҢеҸҲи§ҒдәҺгҖҠе°ҡд№ҰВ·иҲңе…ёгҖӢпјҡеёқжӣ°пјҡвҖңеҘ‘пјҡзҷҫ姓дёҚдәІпјҢдә”е“ҒдёҚйҖҠпјҢжұқдҪңеҸёеҫ’пјҢ敬敷дә”ж•ҷпјҢеңЁе®ҪгҖӮвҖқеӯ”дј пјҡвҖңдә”е“ҒпјҢи°“дә”еёёгҖӮйҖҠпјҢйЎәд№ҹгҖӮеёғдә”еёёд№Ӣж•ҷпјҢеҠЎеңЁе®ҪпјҢжүҖд»Ҙеҫ—дәәеҝғгҖӮвҖқ гҖҠеҸІи®°В·дә”еёқжң¬зәӘгҖӢйӣҶи§Јеј•йғ‘зҺ„жӣ°пјҡвҖңдә”е“ҒпјҢзҲ¶жҜҚе…„ејҹеӯҗд№ҹ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д№ӢиҜҙжҚ®гҖҠе·Ұдј гҖӢж–Үе…¬еҚҒе…«е№ҙпјҡвҖңдёҫе…«е…ғпјҢдҪҝеёғдә”ж•ҷдәҺеӣӣж–№пјҢзҲ¶д№үжҜҚж…Ҳе…„еҸӢејҹжҒӯеӯҗеӯқгҖӮвҖқдҪңдёәиҲңд№ӢеҸёеҫ’зҡ„еҘ‘пјҢдёҺвҖңйёҹвҖқжңүдёҚи§Јд№ӢзјҳпјҢгҖҠиҜ—В·е•ҶйўӮВ·зҺ„йё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Ө©е‘ҪзҺ„йёҹпјҢйҷҚиҖҢз”ҹе•ҶгҖӮвҖқйғ‘зҺ„з¬әпјҡвҖңйҷҚпјҢдёӢд№ҹгҖӮеӨ©дҪҝдёӢиҖҢз”ҹе•ҶиҖ…пјҢи°“йҒ—еҚөпјҢеЁҖж°Ҹд№ӢеҘіз®ҖзӢ„еҗһд№ӢиҖҢз”ҹеҘ‘пјҢдёәе°§еҸёеҫ’пјҢжңүеҠҹгҖӮе°Ғе•ҶгҖӮе°§зҹҘе…¶еҗҺе°Ҷе…ҙпјҢеҸҲ锡其姓з„үгҖӮиҮӘеҘ‘иҮіжұӨе…«иҝҒпјҢе§ӢиҝҒдәід№Ӣж®·ең°иҖҢеҸ—е‘ҪпјҢеӣҪж—Ҙд»Ҙе№ҝеӨ§иҠ’иҠ’然гҖӮжұӨд№ӢеҸ—е‘ҪпјҢз”ұеҘ‘д№ӢеҠҹпјҢж•…жң¬е…¶еӨ©ж„ҸгҖӮвҖқеҘ‘дҪңдёәеҸёеҫ’дё»ж•ҷеҢ–пјҢеҗҺдё–дёҖзӣҙдј жүҝгҖӮгҖҠеӣҪиҜӯВ·йғ‘иҜӯ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•ҶеҘ‘иғҪе’ҢеҗҲдә”ж•ҷпјҢд»ҘдҝқдәҺзҷҫ姓иҖ…д№ҹгҖӮвҖқйҹҰжҳӯжіЁпјҡвҖңдә”ж•ҷпјҡзҲ¶д№үпјҢжҜҚж…ҲпјҢе…„еҸӢпјҢејҹжҒӯпјҢеӯҗеӯқгҖӮвҖқж•ҷеҢ–зҷҫ姓еҪ“жҳҜж®·е•Ҷд»ҘжқҘзҡ„дј з»ҹпјҢе‘ЁдәәеҸҜиғҪжҳҜеӣ иўӯдәҶе•Ҷдәәзҡ„зӨјеҲ¶е№¶еҠ д»ҘеҸ‘жү¬е…үеӨ§пјҢеҰӮйғ‘зҺ„гҖҠе‘ЁеҚ—еҸ¬еҚ—и°ұгҖӢдёӯ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ж–ҮзҺӢеҸ—е‘ҪпјҢдҪңйӮ‘дәҺдё°пјҢд№ғеҲҶеІҗйӮҰгҖӮе‘ЁеҸ¬д№Ӣең°пјҢдёәе‘Ёе…¬ж—ҰгҖҒеҸ¬е…¬еҘӯд№ӢйҮҮең°пјҢж–Ҫе…Ҳе…¬д№Ӣж•ҷдәҺе·ұжүҖиҒҢд№ӢеӣҪгҖӮвҖқеҸёеҫ’ж•ҷеҢ–зҡ„еҶ…е®№дёҚд»…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дә”ж•ҷвҖқпјҢд»Һ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е°Өе…¶жҳҜгҖҠе‘ЁеҚ—гҖӢгҖҠеҸ¬еҚ—гҖӢж–Үжң¬зңӢпјҢж•ҷеҢ–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гҖҒе®Ңе–„е©ҡ姻зӨјеҲ¶жҳҜе…¶йҮҚиҰҒзҡ„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иҝҷеңЁгҖҠиҜ—еәҸгҖӢдёӯеҸҜд»ҘзңӢеҫ—еҚҒеҲҶжё…жҘҡпјҡвҖңйЈҺд№Ӣе§Ӣд№ҹпјҢжүҖд»ҘйЈҺеӨ©дёӢиҖҢжӯЈеӨ«еҰҮд№ҹпјҢж•…з”Ёд№Ӣд№Ўдәәз„үпјҢз”Ёд№ӢйӮҰеӣҪз„үгҖӮйЈҺпјҢйЈҺд№ҹпјҢж•ҷд№ҹгҖӮйЈҺд»ҘеҠЁд№ӢпјҢж•ҷд»ҘеҢ–д№ӢгҖӮвҖҰвҖҰж•…жӯЈеҫ—еӨұпјҢеҠЁеӨ©ең°пјҢж„ҹй¬јзҘһпјҢиҺ«иҝ‘дәҺиҜ—гҖӮе…ҲзҺӢд»ҘжҳҜз»ҸеӨ«еҰҮпјҢжҲҗеӯқ敬пјҢеҺҡдәәдјҰпјҢзҫҺж•ҷеҢ–пјҢ移йЈҺдҝ—гҖӮвҖқвҖңз»ҸеӨ«еҰҮвҖқзҪ®дәҺвҖңжҲҗеӯқ敬вҖқд№ӢеүҚпјҢеҸҜи§ҒдёҠеҸӨж—¶жңҹеңЈдәәеҜ№йқ’е№ҙз”·еҘіж•ҷеҢ–зҡ„йҮҚи§ҶгҖӮдҪҷ и®ә 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жҹҜ马дёҒеңЁгҖҠдҪңдёәиЎЁжј”ж–Үжң¬зҡ„иҜ—вҖ”вҖ”д»ҘгҖҲе°Ҹйӣ…В·жҘҡиҢЁгҖүдёәдёӘжЎҲ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жҢҮеҮәпјҢгҖҠе°Ҹйӣ…В·жҘҡиҢЁгҖӢж–Үжң¬жҳҜж №жҚ®зҘӯд»Әж”№еҶҷиҖҢжҲҗпјҡжҲ‘и®ӨдёәиҝҷзҜҮиҜ—жӯҢеҢ…еҗ«дәҶдёҠеҸӨпјҲжҲ–и®ёз”ҡиҮіжҳҜиҘҝе‘Ёж—¶жңҹпјүзҘӯд»ӘжүҖзңҹе®һйҮҮз”Ёзҡ„иҜ—жӯҢпјҢиҷҪ然е®ғд№ҹз»ҸиҝҮдәҶеҗҺдәәзҡ„зј–иҫ‘пјҢ并йҖҡиҝҮеҗҺдәәзҡ„и§Ҷи§’з»ҷиҝҷйғЁеҲҶеҺҹе§ӢиҜ—жӯҢи®ҫе®ҡдәҶжЎҶжһ¶гҖӮжҲ‘зҢңжғіпјҢиҝҷдёӘеҚҠеҸҷдәӢжҖ§зҡ„жЎҶжһ¶еӨ§зәҰжҲҗеһӢдәҺдёңе‘Ёжҹҗж—¶пјҢеҪ“ж—¶ж—§зҡ„зҘӯд»ӘиҝҳдҝқеӯҳеңЁи®°еҝҶеҪ“дёӯпјҢеҚҙдёҚеҶҚд»ҘеҺҹе§ӢеҪўжҖҒиЎЁжј”гҖӮ 笔иҖ…и®ӨдёәиҝҷдёҖиҜҙжі•еӨ§иҮҙеҸҜд»ҘжҲҗз«ӢгҖӮд»Ҡжң¬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жҳҜдёӘж–Үеӯ—ж–Үжң¬пјҢиҝҷдёӘж–Үеӯ—ж–Үжң¬жәҗдәҺеҺҹе§Ӣзҡ„жӯҢиҲһпјҲиЎЁжј”пјүд»ӘејҸпјҢз»ҸиҝҮеҗҺдәә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зҡ„еҠ е·Ҙж•ҙзҗҶгҖӮдёҚд»…йўӮиҜ—гҖҒйӣ…иҜ—еҰӮжӯӨпјҢеҫҲеӨҡйЈҺиҜ—д№ҹеҗҢж ·жәҗдәҺд»ӘејҸжӯҢиҲһгҖӮиҝҷз§Қд»ӘејҸжӯҢиҲһжҳҜеӣҪ家巡е®ҲзӨјд»Ә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жүҖд»ҘдёҖзӣҙеҫ—еҲ°дј жүҝпјҢзӣҙеҲ°е·Ўе®ҲзӨјд»ӘеҪ»еә•з“Ұи§Јд№ӢеҗҺпјҢдј жүҝиҖ…жүҚе°Ҷе®ғ们改编жҲҗзҺ°еңЁзҡ„ж ·еӯҗгҖӮд»Һ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зҡ„жғ…еҶөжқҘзңӢпјҢе…¶з»ҸиҝҮеҗҺдәәж”№зј–зҡ„з—•иҝ№дјје№¶йқһжІЎжңүиЎЁйңІгҖӮдәҢгҖҒдёүз« еҪ“дёәеҺҹжқҘиЎЁжј”дёӯжүҖе”ұпјҢиҖҢ第дёҖз« вҖңеҺҢжөҘиЎҢйңІпјҢеІӮдёҚеӨҷеӨңпјҹи°“иЎҢеӨҡйңІвҖқдёҺдәҢгҖҒдёүз« жүҖиҝ°еҸҘжі•дёҚзұ»пјҢеҶ…е®№дёҚиҝһиҙҜпјҢз»ҷдәәзӘҒе…Җзҡ„ж„ҹи§ү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№ҹжңүдәәжҖҖз–‘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жңүи„ұж–ҮжҲ–вҖңд№ұе…ҘвҖқзҡ„зҺ°иұЎпјҡвҖҰвҖҰжӯӨдёүеҸҘдёәиҜ—д№ӢйҰ–з« гҖӮзҺӢиҙЁгҖҠиҜ—жҖ»й—»гҖӢи°“жӯӨз« вҖңжҲ–дёҠдёӢд№Ӣй—ҙпјҢжҲ–дёӨеҸҘдёүеҸҘпјҢжҖ•жңүжүҖйҳҷпјӣдёҚиҖҢпјҢдәҰеҝ…йҳҷдёҖеҸҘгҖӮзӣ–ж–ҮеҠҝжңӘиғҪе…ҘйӣҖиҜҚиҖівҖқгҖӮзҺӢжҹҸгҖҠиҜ—з–‘гҖӢ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йҰ–з« дёҺдәҢз« ж„Ҹе…ЁдёҚзӣёиҙҜпјҢеҸҘжі•дҪ“ж јдәҰејӮпјҢжҜҸзӘғз–‘д№ӢгҖӮеҗҺи§ҒеҲҳеҗ‘дј еҲ—еҘіи°“пјҡеҸ¬еҚ—з”ідәәд№ӢеҘіпјҢи®ёе«ҒдәҺй…ҶпјҢеӨ«е®¶зӨјдёҚеӨҮиҖҢж¬ІеЁ¶д№ӢпјҢи®јд№ӢдәҺзҗҶпјҢйҒӮдҪңдәҢз« пјҢиҖҢж— еүҚдёҖз« д№ҹгҖӮд№ғзҹҘеүҚз« д№ұе…Ҙж— з–‘гҖӮвҖқ зҺӢиҙЁгҖҒзҺӢжҹҸзңје…үеҰӮзӮ¬пјҢеҸ‘зҺ°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йҰ–з« дёҺдәҢгҖҒдёүз« еҸҘжі•гҖҒдҪ“ж јзҡ„дёҚеҗҢгҖӮеӯҷдҪңдә‘гҖҠиҜ—з»Ҹзҡ„й”ҷз®ҖгҖӢдёҖж–Үд№ҹ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ж„ҸжҖқеүҚеҗҺдёҚзӣёиҝһиҙҜпјҢеҸЈж°”дёҠдёӢдёҚзӣёиЎ”жҺҘпјҢжҳҫ然жҳҜдёӨйҰ–иҜ—иҜҜеҗҲдёәдёҖйҰ–иҜ—гҖӮвҖқдҪҶ笔иҖ…д»ҘдёәпјҢиҝҷд№ҹеҸҜиғҪжҳҜеҗҺжқҘж”№зј–иҖ…жүҖдёәпјҢеҠ дёҠвҖңеҺҢжөҘиЎҢйңІвҖқзӯүдҪңдёәж•ҙйҰ–иҜ—зҡ„иғҢжҷҜ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ж ҮжҳҺд»ІжҳҘж—¶д»ӨпјҢ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пјҢз”ЁвҖңеҺҢжөҘиЎҢйңІвҖқејәи°ғжҷҡй—ҙпјҢеҫҲжңүеҸҜиғҪжҳҜеӣ дёәвҖңеҸёеҫ’вҖқйӣҶеҗҲйқ’е№ҙиЎЁжј”жӯҢиҲһзҡ„ж—¶й—ҙд№ҹеңЁжҷҡй—ҙпјҢжҷҡдёҠжҳҹжұүзҒҝзғӮпјҢжңүеҲ©дәҺзӣҙи§Ӯең°е®һзҺ°зҘһйҒ“и®ҫж•ҷзҡ„ж•ҷеҢ–зӣ®ж ҮгҖӮгҖҠе·Ұдј В·иҘ„е…¬дёғе№ҙ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еҶ¬еҚҒжңҲпјҢжҷӢйҹ©зҢ®еӯҗе‘ҠиҖҒгҖӮе…¬ж—Ҹз©Ҷеӯҗжңүеәҹз–ҫпјҢе°Ҷз«Ӣд№ӢгҖӮиҫһжӣ°пјҡвҖңгҖҠиҜ—гҖӢжӣ°пјҡвҖҳеІӮдёҚеӨҷеӨңпјҹи°“иЎҢеӨҡйңІпјҒвҖҷеҸҲжӣ°пјҡвҖҳеј—иә¬еј—дәІпјҢеә¶ж°‘еј—дҝЎгҖӮвҖҷж— еҝҢдёҚжүҚпјҢи®©пјҢе…¶еҸҜд№ҺпјҹиҜ·з«Ӣиө·д№ҹгҖӮвҖқ з©ҶеӯҗдёәжҷӢеӣҪе…¬еҚҝеӨ§еӨ«йҹ©еҺҘд№Ӣй•ҝеӯҗпјҢйҹ©еҺҘе‘ҠиҖҒйҖҖдј‘пјҢжғіз«Ӣз©ҶеӯҗдёәеҚҝеӨ§еӨ«пјҢдҪҶз©Ҷеӯҗеј•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әҢеҸҘжҺЁиҫһпјҢеҺҹеӣ жҳҜиҮӘе·ұжңүвҖңеәҹз–ҫвҖқпјҢдёҚиғҪиә¬дәІеӨ„зҗҶж°‘дәӢгҖӮгҖҠе·Ұдј В·иҘ„е…¬дёғе№ҙгҖӢеҚіжңүдәәеј•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пјҢз”ұжӯӨеҸҜзҹҘпјҢд»Ҡжң¬гҖҠиЎҢйңІгҖӢиҜ—д№Ӣе®ҢжҲҗпјҢжңҖжҷҡеңЁдёңе‘ЁдёӯжңҹпјҢд№ҹжңүеҸҜиғҪе®ғеңЁиҘҝе‘ЁжҷҡжңҹеҚіе·Іе®ҢжҲҗгҖӮдҪңдёәе·Ўе®Ҳж—¶иЎЁжј”д»ӘејҸвҖңжӯҢиҲһвҖқзҡ„и„ҡжң¬пјҢдәә们зҡ„е…іжіЁзӮ№еңЁе…¶жӯҢиҲһпјҢе…¶дј жүҝйҖҡиҝҮиә«дј еҸЈжҺҲгҖӮеңЁе·Ўе®ҲзӨјеҲ¶дёҚеҶҚйҒөе®Ҳзҡ„ж—¶д»ЈпјҢеҰӮе№ҪзҺӢж—¶д»ЈпјҢдёҖдәӣеҺҹжқҘзҡ„иЎЁжј”иҖ…еҸҠдј жүҝиҖ…пјҢеҫҲеҸҜиғҪжҳҜвҖңеӨӘеёҲвҖқвҖңеӨӘеҸІвҖқжҲ–е‘ЁзҺӢжңқзҡ„вҖңеҚҝеӨ§еӨ«вҖқдёҖзұ»зҡ„дәәзү©пјҢ他们еҮәдәҺеҜ№е‘ЁзҺӢжңқзӣӣж—¶зҡ„ж— йҷҗеҗ‘еҫҖпјҢж„ҹеҸ№дәҺе·Ўе®ҲзӨјеҲ¶зҡ„еҙ©еқҸпјҢе°ҶеҺҹжқҘз”ЁдәҺиЎЁжј”зҡ„д»ӘејҸд№җиҲһеҠ д»Ҙж•ҙзҗҶж”№зј–гҖӮиҝҷдәӣж”№зј–жң¬еҗҺжқҘз§°дёәгҖҠиҜ—дёүзҷҫгҖӢпјҢжҲҗдёәиҙөж—Ҹеӯҗејҹзҡ„ж•ҷжң¬пјҢеҸӨиҖҒзҡ„е·Ўе®ҲзӨјеҲ¶еңЁиҝҷдәӣж–Үжң¬дёӯеҫ—еҲ°дәҶйғЁеҲҶдј жүҝ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йҮҮи–Ү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5жңҹвҖңж–ҮеӯҰдёҺиүәжңҜз ”з©¶вҖқж Ҹзӣ®вҖң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ж–°и§ЈвҖқдё“йўҳ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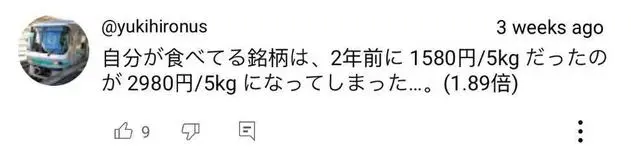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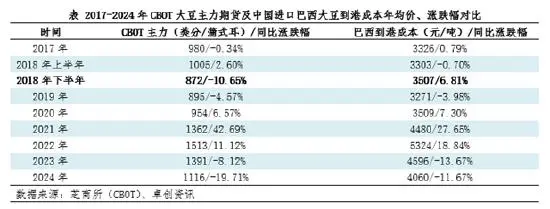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