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зүӣ继清пјҢз”·пјҢж·®еҢ—еёҲиҢғеӨ§еӯҰе®үеҫҪж–ҮзҢ®ж•ҙзҗҶдёҺ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ж•ҷжҺҲгҖӮ
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пјҢж—Ҙжң¬дҫөеҚҺжҲҳдәүдёҺдёҚж–ӯеҠ ж·ұзҡ„ж°‘ж—ҸеҚұжңәпјҢиҝ«дҪҝеӣҪеҶ…жңүиҜҶд№ӢеЈ«ж—ҘзӣҠи®ӨиҜҶеҲ°иҘҝеҢ—ең°еҢә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пјҢеңЁж•‘дәЎеӣҫеӯҳзҡ„еӨ§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жҺҖиө·дәҶиҖғеҜҹиҘҝеҢ—зҡ„зғӯжҪ®гҖӮд»Һи‘—еҗҚеӯҰиҖ…гҖҒж–°й—»и®°иҖ…еҲ°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й«ҳзә§е®ҳе‘ҳпјҢ他们жҲ–иҖ…д»Ҙе®ҳж–№зҡ„еҗҚд№үпјҢжҲ–иҖ…д»ҘдёӘдәәзҡ„иә«д»ҪпјҢзә·зә·еүҚеҫҖз”ҳгҖҒйқ’гҖҒе®ҒгҖҒж–°зӯүиҘҝеҢ—иҜёзңҒиҖғеҜҹгҖӮ1932е№ҙпјҢ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иҖғиҜ•йҷўй•ҝжҲҙеӯЈйҷ¶иҖғеҜҹиҘҝеҢ—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ж”№йҖ еӨ§иҘҝеҢ—вҖқзҡ„и®ЎеҲ’гҖӮ1934е№ҙ4вҖ”5жңҲпјҢе®Ӣеӯҗж–Үд»Ҙе…ЁеӣҪз»ҸжөҺ委е‘ҳдјҡ常委зҡ„иә«д»ҪиҖғеҜҹдәҶйҷ•гҖҒз”ҳгҖҒе®ҒгҖҒйқ’еӣӣзңҒгҖӮеҗҢе№ҙ10жңҲпјҢ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委е‘ҳй•ҝи’Ӣд»ӢзҹіеҸҠеӨ«дәәдәІиҮіз”ҳиӮғиҖғеҜҹгҖӮ1935е№ҙиҮӘжҳҘеҫӮз§ӢпјҢеӣҪж°‘е…ҡдёӯеӨ®жү§иЎҢ委е‘ҳйӮөе…ғеҶІеҲ°з”ҳиӮғгҖҒйқ’жө·гҖҒе®ҒеӨҸзӯүең°иҖғеҜҹвҖңж”ҝдҝ—ж–Үж•ҷвҖқгҖӮдҪҷеҰӮжһ—й№Ҹдҫ еҘіеЈ«д»Ҙи®°иҖ…иә«д»ҪдәҺ1932вҖ”1933е№ҙй—ҙиҖғеҜҹйҷ•гҖҒз”ҳгҖҒйқ’гҖҒе®ҒеӣӣзңҒгҖӮгҖҠз”іжҠҘгҖӢи®°иҖ…йҷҲиө“йӣ…дәҺ1934вҖ”1935е№ҙй—ҙпјҢиҖғеҜҹдәҶе®ҒеӨҸгҖҒз”ҳиӮғгҖҒйқ’жө·гҖҒж–°з–ҶгҖҒйҷ•иҘҝзӯүзңҒ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дёҖиЎҢеҲҷд»ҘдёӯиӢұеәҡж¬ҫи‘ЈдәӢдјҡзҡ„еҗҚд№үпјҢдәҺ1937вҖ”1938е№ҙеүҚеҫҖз”ҳиӮғгҖҒйқ’жө·иҖғеҜҹж•ҷиӮІ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иҝҷдәӣдәәеңЁиҖғеҜҹ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°Ҷи§ӮеҜҹдёҺи®ҝй—®жүҖеҫ—пјҢиҜүд№ӢдәҺ笔墨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дёәж•°дёҚе°‘зҡ„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пјҲжёёи®°пјүпјҢжҲ–еҸ‘иЎЁдәҺжҠҘеҲҠпјҢжҲ–иҫ‘еҪ•жҲҗд№ҰеҮәзүҲеҸ‘иЎҢгҖӮдёҫеҮЎиҫ№з–ҶеӣҪйҳІгҖҒж°‘ж—Ҹе…ізі»гҖҒзӨҫдјҡзҠ¶еҶөгҖҒж–ҮеҢ–ж•ҷиӮІгҖҒзү©дә§з»ҸжөҺгҖҒйЈҺеңҹдәәжғ…зӯүйғҪеңЁе…¶е…іжіЁд№ӢеҲ—пјҢеҗҢ时他们иҝҳжҠ’еҸ‘жңүе…іиҘҝеҢ—зӨҫдјҡз»ҸжөҺгҖҒиҫ№з–ҶгҖҒж°‘ж—ҸиҜёй—®йўҳзҡ„ж„ҹжғіпјҢжҸҗеҮә规еҲ’дёҺе»әи®®гҖӮжҚ®зҺӢе®ҮеЁҹз»ҹи®ЎпјҢ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иҖғеҜҹиҘҝеҢ—并еҶҷжңүиЎҢи®°зҡ„е…ұжңү18дәәпјҢеҶҷдҪңиЎҢи®°19з§ҚпјҢе…¶дёӯз»қеӨ§йғЁеҲҶйӣҶдёӯдәҺ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еүҚеҗҺпјҢиҝҷдёӘз»ҹи®ЎжҳҜеңЁгҖҠ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дёӣиҗғгҖӢжүҖиҫ‘йҖүзҡ„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еҹәзЎҖдёҠеҒҡеҮәзҡ„пјҢжңӘ收е…ҘгҖҠ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дёӣиҗғгҖӢдёӯзҡ„гҖҠеҲ°йқ’жө·еҺ»гҖӢзӯүеҸҠеҸ‘иЎЁеңЁеҗ„з§ҚжқӮеҝ—жҠҘзәёдёҠзҡ„зҹӯзҜҮиЎҢи®°пјҲжёёи®°пјү并жңӘз»ҹи®Ўе…ҘеҶ…пјҢеӣ жӯӨе°ҡдёҚжҳҜеҫҲе®Ңе…ЁгҖӮиҝҷдәӣ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пјҢж— дёҖдҫӢеӨ–йғҪжіЁж„ҸеҲ°дәҶеҪ“ең°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дәәеҸЈж•°зӣ®гҖҒдәәеҸЈеҲҶеёғгҖҒзӨҫдјҡ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еҸҠеҗ„ж°‘ж—Ҹзӣёдә’й—ҙзҡ„дәӨеҫҖгҖҒдәӨжөҒдёҺиһҚеҗҲпјҢиҝҷд№ҹдёҺдҪңиҖ…们йқўеҜ№ж°‘ж—ҸеҚұжңәж—¶еҜ№дәҺеӣҪ家гҖҒж°‘ж—ҸеүҚйҖ”е‘Ҫиҝҗзҡ„ж·ұж·ұжӢ…еҝ§еҜҶдёҚеҸҜеҲҶ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иҘҝеҢ—иҖғеҜҹзҡ„зӣҙжҺҘеҜ№иұЎжҳҜз”ҳгҖҒйқ’гҖҒе®ҒдёүзңҒж•ҷиӮІпјҢдҪҶеҺҶеҸІеӯҰ家зҡ„дҪҝе‘ҪдёҺиҙЈд»»и®©д»–еҝғеҝғеҝөеҝөдәҺиҫ№з–ҶдёҺж°‘ж—Ҹй—®йўҳпјҡвҖңжҳҜиЎҢд№ҹпјҢдёәж¬Іи®ӨиҜҶиҘҝеҢ—зӨҫдјҡд№Ӣеҹәжң¬й—®йўҳпјҢж•…иҲҚеә·еә„д№ӢйҷҮдёңеҚ—еҸҠжІіиҘҝдёҚжёёпјҢиҖҢжғҹжёёдәҺе…¬и·Ҝе°ҡжңӘйҖҡиҫҫд№ӢйҷҮиҘҝпјҢзӣ–з§Қж—ҸгҖҒе®—ж•ҷиҜёй—®йўҳжғҹжӯӨдёҖеҢәдёәзә зә·иҖҢйҡҫзҗҶд№ҹгҖӮвҖқд»–еңЁдёҙжҙ®иҜ•еҠһеҜ’еҒҮе°ҸеӯҰж•ҷеёҲи®Ід№ дјҡпјҢдё“и®ҫвҖңиҫ№з–Ҷй—®йўҳвҖқи®Іеә§пјҢи®ІвҖңз§Қж—ҸдёҺж°‘ж—Ҹзҡ„еҢәеҲ«вҖқвҖңи°ғеҚҸиҫ№ж°‘ж—Ҹд№Ӣж–№зӯ–вҖқзӯүй—®йўҳгҖӮеҲ°йқ’жө·еҗҺпјҢд»–еҸҲеә”йӮҖеңЁвҖңеӣһж•ҷдҝғиҝӣдјҡвҖқдёә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еӯҰдјҡи®Іжј”пјҢйўҳзӣ®жҳҜвҖңеҰӮдҪ•еҸҜдҪҝ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еӣўз»“иө·жқҘвҖқпјҢйЎҫж°ҸиҮӘиЁҖпјҡвҖңиҮӘж°‘еӣҪдәҢеҚҒдёүе№ҙжёёзҷҫзҒөеәҷпјҢдёҺеҫ·зҺӢеҸҠе…¶йғЁдёӢдҪңж•°ж—Ҙи°ҲпјҢеҝғдёӯеҚіжў—жӯӨйўҳпјҢд»ҠиҮіиҘҝеҢ—пјҢжӣҙеӨҡжҖ…и§ҰгҖӮвҖқиҘҝеҢ—иҖғеҜҹиҜёдәәдёӯпјҢд»Ҙ马й№ӨеӨ©еңЁиҘҝеҢ—еҺҶж—¶жңҖй•ҝпјҢдёҺз”ҳйқ’дёҠеұӮдәӨжёёжңҖж·ұпјҢжёёеҺҶж¶үеҸҠең°еҹҹжңҖе№ҝпјҢж’°иҝ°жңҖеӨҡгҖӮеңЁгҖҠйқ’жө·иҖғеҜҹи®°гҖӢвҖңиҮӘеәҸвҖқдёӯпјҢд»–и°ҲеҲ°иҖғеҜҹзҡ„зјҳз”ұдёҺзӣ®зҡ„пјҡйқ’жө·дёәдҪҷд№…жҖқиҖғеҜҹд№Ӣең°пјҢиҖҢиӢҰж— жңәгҖӮж°‘еӣҪеҚҒе…ӯе№ҙз”ұи’ҷеҸӨиҝ”з”ҳиӮғеҗҺпјҢеӨҮе‘ҳзңҒ委пјҢе…јдё»ж•ҷиӮІиЎҢж”ҝпјҢи§үиҘҝеҢ—ж•ҷиӮІпјҢеә”жіЁж„Ҹж°‘ж—Ҹй—®йўҳпјҢд»Һж•ҷиӮІж–№йқўпјҢжҸҗй«ҳ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–ҮеҢ–пјҢжіҜйҷӨеҗ„ж°‘ж—Ҹз•ҢйҷҗпјҢиҒ”з»ң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„ҹжғ…пјҢи°ғе’Ңеҗ„ж°‘ж—ҸдёӘжҖ§пјҢд»ҘжңҹйҖҗжёҗе№ізӯүпјҢеҗҢж ·иҝӣеҢ–гҖӮзҠ№ж¬ІиҖғеҜҹеӣһгҖҒи—Ҹеҗ„ж—Ҹд№Ӣз”ҹжҙ»д№ жғҜпјҢеҸҠж–ҮеҢ–жғ…еҪўгҖӮ еӣ жӯӨпјҢиҝҷдәӣеңЁе®һең°иҖғеҜҹе’Ңи°ғз ”еҹәзЎҖдёҠеҪўжҲҗзҡ„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дёӯпјҢдҝқз•ҷдәҶеӨ§йҮҸзӣҙжҺҘеҸҚжҳ 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дәӨеҫҖдәӨжөҒдәӨиһҚзҡ„зҸҚиҙөеҸІж–ҷгҖӮжң¬ж–ҮжӢҹд»Ҙиҝҷжү№иҘҝеҢ—иЎҢи®°дёәж ёеҝғпјҢеҜ№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еүҚеҗҺ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пјҲеҸҲз§°жІіж№ҹ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пјү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дәӨеҫҖдәӨжөҒдәӨиһҚеҒҡдёҖзІ—жө…и®Ёи®әпјҢд»Ҙе°ұжӯЈдәҺ方家гҖӮйңҖиҰҒзү№еҲ«ејәи°ғзҡ„жҳҜпјҢз”ұдәҺеҗ„з§Қеӣ зҙ пјҢеҪ“ж—¶зҡ„еӯҰиҖ…еҜ№дәҺйқ’жө·зҡ„ж°‘ж—ҸжқҘжәҗгҖҒжҲҗеҲҶгҖҒзӣёдә’е…ізі»дәҶи§ЈдёҚе°Ҫз¬ҰеҗҲе®һйҷ…пјҢдҪҶ并дёҚеҪұе“Қжң¬ж–Үдё»ж—ЁгҖӮдёҖгҖҒ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зҡ„е©ҡ姻 з”ұдәҺ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дёҺеҺҶеҸІ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еңЁд»Ҡ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з”ҹжҙ»зқҖдј—еӨҡзҡ„ж°‘ж—ҸпјҢдё»иҰҒжңүжұүгҖҒ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гҖҒеӣһгҖҒж’’жӢүгҖҒеңҹгҖҒдёңд№ЎгҖҒдҝқе®үзӯүж°‘ж—ҸпјҢиҝҷдәӣдёҚеҗҢж°‘ж—ҸеңЁеҺҶеҸІж—¶жңҹй•ҝжңҹе…ұеҗҢз”ҹжҙ»еңЁеҗҢдёҖең°еҢәпјҢдә’зӣёзў°ж’һгҖҒдәӨеҫҖпјҢйҖҗжёҗи¶Ӣеҗ‘иһҚеҗҲпјҢеҪўжҲҗдҪ дёӯжңүжҲ‘гҖҒжҲ‘дёӯжңүдҪ зҡ„еұҖйқўпјҢ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зҡ„зӣёдә’йҖҡе©ҡе°ұжҳҜжңҖдёәзӘҒеҮәзҡ„дҪ“зҺ°гҖӮжұүж—ҸдёҺеҪ“ең°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зҡ„йҖҡе©ҡзҺ°иұЎиө·жәҗеҫҲж—©пјҢйҡҸзқҖе…ғжңқи’ҷеҸӨж—ҸеӨ§йҮҸиҝӣе…ҘиҝҷдёҖеҢәеҹҹд»ҘеҸҠжҳҺд»ЈеҚ«жүҖеұҜз”°еҲ¶еәҰзҡ„е®һиЎҢпјҢеҗ„ж°‘ж—ҸйҖҡе©ҡдёҚж–ӯжү©еұ•пјҢдёҚе°‘й©»е®ҲеұҜз”°зҡ„еҶ…ең°жұүдәәпјҢеЁ¶еҪ“ең°и—Ҹж—ҸжҲ–е…¶д»–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ҘіеӯҗдёәеҰ»пјҢжҲҗ家з”ҹеӯҗ并е®ҡеұ…пјҢ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йҖҗжёҗи¶ӢеҗҢгҖӮ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пјҢеҺҹжқҘеңЁеҪ“ең°й©»е®Ҳзҡ„жё…еҶӣиў«иЈҒж’ӨпјҢдёҚе°‘е…өеЈ«йҖүжӢ©е°ұең°е®ҡеұ…пјҢеЁ¶еҪ“ең°и—Ҹж—ҸеҘіжҖ§жҲҗ家пјҢжҜ”еҰӮе“ҲжӢүеә“еӣҫпјҲд»Ҡж№ҹжәҗеҺҝж—ҘжңҲи—Ҹж—Ҹд№Ўе“ҲеҹҺжқ‘пјүеңЁжё…д»ЈеҺҹжңүвҖңе…өйўқдәҢзҷҫеӣӣеҚҒеҗҚпјҢж°‘еӣҪдёүе№ҙе§ӢеҸ–ж¶ҲпјҢеҺҹй©»д№Ӣе…өпјҢйҒӮеЁ¶з•ӘеҘіжҲҗ家пјҢж•…зҺ°жңүеұ…ж°‘еӣӣеҚҒдҪҷжҲ·вҖқгҖӮиҖҢжүҺд»Җе·ҙе ЎпјҲд»ҠеҢ–йҡҶеҺҝжүҺе·ҙд№Ўпјүйҷ„иҝ‘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еҹәжң¬дёҠйғҪжҳҜдёҺжұүгҖҒеӣһжҺҘи§ҰиҫғеӨҡзҡ„жүҖи°“вҖңзҶҹз•ӘвҖқпјҢе…¶з”ҹжҙ»ж–№ејҸеҸ—жұүж°‘еҪұе“ҚеҫҲж·ұпјҢжҜ”еҰӮе»әеңҹеұӢеұ…дҪҸпјҢзғ§еңҹзӮ•иҖҢеҜқеӨ„пјҢз”ҡиҮіиҝһзүІз•ңд№ҹйғҪеңҲе…»еңЁеңҹеұӢд№ӢдёӯпјҢвҖңз”·еӯҗи“„еҸ‘иҫ«пјҢж“ҚжұүиҜқиҖ…зәҰеҚҒеҲҶд№Ӣдә”е…ӯпјҢеҸҜзҹҘе·Іж—©жұүеҢ–зҹЈвҖқгҖӮиҝҷдәӣи—Ҹж°‘зҡ„жұүеҢ–дёҚд»…жҳҜз”ұдәҺдёҺжұүж°‘зҡ„ж—ҘеёёдәӨеҫҖ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еӣ зҙ жҳҜйҖҡе©ҡпјҢи—Ҹж—ҸеҰҮеҘіе«Ғз»ҷжұүдәәзҡ„з”ҡеӨҡпјҢз”ұдәҺе©ҡ姻关系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еҗ„з§ҚзӨҫдјҡдәӨеҫҖиҮӘ然д№ҹдёҚе°‘гҖӮжӢүеҚңжҘһең°еҢәзҡ„ж°‘ж—ҸзҠ¶еҶөзӣёеҜ№еӨҚжқӮпјҢ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гҖҒеӣһгҖҒжұүзӯүж°‘ж—ҸиҒҡйӣҶпјҢзӣёеҗҢзҡ„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дҪҝеҫ—еҗ„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дә’зӣёдәӨеҫҖйў‘з№ҒпјҢйҖҡе©ҡзҺ°иұЎд№ҹиҫғжҷ®йҒҚгҖӮ1933е№ҙпјҢдёҠжө·гҖҠж–°й—»жҠҘгҖӢи®°иҖ…йЎҫжү§дёӯгҖҒйҷҶиҜ’зӯүдәәеҜ№еӨҸжІіеҺҝз«Ӣ第дёҖе°ҸеӯҰеӯҰз”ҹзҠ¶еҶөеҒҡдәҶж·ұе…Ҙи°ғжҹҘпјҢиҜҘж ЎеӯҰз”ҹйҷӨдәҶжұүж—Ҹе’Ңеӣһж—ҸеӨ–пјҢе°ҡжңүж··иЎҖеӯҰз”ҹи¶…иҝҮ7еҗҚпјҢе…¶дёӯзҲ¶дәІеӣһж—ҸгҖҒжҜҚдәІи—Ҹж—ҸеӯҰз”ҹи¶…иҝҮ4еҗҚпјҢзҲ¶дәІжұүж—ҸгҖҒжҜҚдәІи—Ҹж—ҸеӯҰз”ҹ3еҗҚгҖӮеҸҜи§ҒеңЁжӢүеҚңжҘһпјҢжұүи—ҸгҖҒеӣһи—ҸйҖҡе©ҡзҡ„зҺ°иұЎиҫғеӨҡгҖӮзҮ•дә¬еӨ§еӯҰеӯҰз”ҹеҲҳе…Ӣи®©йҡҸйЎҫйўүеҲҡиҖғеҜҹжӢүеҚңжҘһжңҹй—ҙпјҢиў«еҸ·з§°вҖңжӢүеҚңжҘһзҡҮеҗҺвҖқзҡ„и—Ҹж—ҸеҘізҝ зҗ…й”ҷзӣёдёӯпјҢж„Ҹж¬ІжӢӣе©ҝгҖӮйҒЈе…¶еҘід»ҶжӢӣе…Ӣи®©еҫҖпјҢд№…д№ӢдёҚеҪ’пјҢеҲҷиҚҗжһ•еёӯзҹЈпјӣз•ӘеҘіеҰӮжӯӨиҮӘз”ұз®ҖжҚ·пјҢж®Ҡд»ӨжҲ‘иҫҲеҲқиҮіиҖ…е’ӢиҲҢгҖӮй—»жӯӨеҘіж…•жұүдәәж–ҮеҢ–з¶ҰеҲҮпјҢд№…ж¬ІжӢ©дёҖеҶ…ең°йқ’е№ҙиҖҢе«Ғд№ӢгҖӮ д»Ҡе…Ӣи®©иҮіпјҢе№ҙдәҢеҚҒдҪҷпјҢдё”дёәдёҖеӨ§еӯҰз”ҹпјҢдёҫжӯўжё©дҝҠпјҢйҒӮеҪ“е…¶йҖүгҖӮ зҝ зҗ…й”ҷеҸ—жұү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иҫғж·ұпјҢз•ҘйҖҡжұүиҜӯпјҢе…¶еұ…жүҖвҖңеЈҒдёҠжӮ¬иғЎзҗҙеҸҠз¬ӣпјҢзҹҘе…¶ж“…йҹід№җпјӣжЎҲдёҠиҠұйңІж°ҙгҖҒйӣӘиҠұиҶҸзҡҶеӨҮз„үвҖқ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еҲҳе…Ӣи®©еңЁеҫҒеҫ—家дәәеҗҢж„ҸеҗҺдёҺд№ӢжҲҗе©ҡпјҢз•ҷеңЁз”ҳиӮғжңҚеҠЎпјҢ继з»ӯиҖғеҜҹе№¶з ”з©¶з”ҳиӮғж°‘ж—Ҹе…ізі»гҖҒ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еҸҠзӨҫдјҡеҸ‘еұ•гҖӮдҝЎеҘү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зҡ„еӣһгҖҒж’’жӢүзӯүж°‘ж—ҸпјҢиҷҪ然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гҖҒиҜӯиЁҖзӯүе·Із»ҸжұүеҢ–пјҢдҪҶз”ұдәҺж•ҷд№үгҖҒж•ҷ规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дёҺе…¶д»–ж°‘ж—ҸйҖҡе©ҡеҸ—еҲ°жҳҺжҳҫйҷҗеҲ¶пјҢвҖңиЎЈжңҚдёҺжұүдәәеҗҢвҖқпјҢвҖңдёҡе•ҶиҖ…еӨҡпјҢеҠЎеҶңиҖ…е°‘вҖқгҖӮвҖңе…¶дәәжҖ§ејәжӮҚеҘҪжӯҰпјҢиҷ”дҝЎд»°пјҢеӣәеӣўз»“пјҢдёҚдёҺд»–ж—ҸеӘҫе©ҡе…ұйЈҹпјҢзҹ«з„¶зӢ¬ејӮгҖӮе…¶ж—ҸеӨ§жҠөеҸҜеҲҶдёәжұүеӣһгҖҒж’’жӢүгҖҒжүҳжҜӣдёүз§ҚгҖӮжұүеӣһдёҺжұүдәәжқӮеӨ„пјҢиҜӯиЁҖж–Үеӯ—йҷӨз»Ҹе…ёеӨ–пјҢзҡҶдёҺжұүдәәж— ејӮгҖӮвҖқдёҚиҝҮдҝЎеҘү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зҡ„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пјҢзӣёдә’йҖҡе©ҡзҺ°иұЎе°ұжҜ”иҫғжҷ®йҒҚдәҶ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ӣһж—ҸдёҺж’’жӢүж—ҸпјҢвҖңжңҖж—©йғҪжҳҜд»ҺиҘҝеҹҹиҫ—иҪ¬иҝҒеҫҷеҲ°йқ’жө·ең°еҢәзҡ„пјҢиҝҷдёӨдёӘж°‘ж—Ҹе…ұеҗҢдҝЎд»°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пјҢйғҪжҳҜз©Ҷж–Ҝжһ—зҫӨдј—пјҢзӣёдә’д№Ӣй—ҙйҖҡе©ҡжҜ”иҫғж–№дҫҝгҖӮзү№еҲ«жҳҜйҘ®йЈҹд№ жғҜзӣёеҗҢпјҢз”ҹжҙ»дёҠе…·жңүдҫҝеҲ©жқЎд»¶вҖқгҖӮеӣ дёәи—Ҹ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дё»иҰҒйЈҹзү©жқҘжәҗжҳҜзүӣзҫҠиӮүпјҢдёҺ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зҡ„йҘ®йЈҹд№ дҝ—жІЎжңүж №жң¬еҶІзӘҒпјҢеӣ жӯӨ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иҜёж°‘ж—ҸдёҺи—Ҹж—ҸйҖҡе©ҡзӣёеҜ№иҫғеӨҡгҖӮеҰӮж’’жӢүж—Ҹзҡ„е…ҲзҘ–еҲ°иҫҫеҫӘеҢ–ең°еҢәд№ӢеҗҺпјҢйҰ–е…ҲдёҺеҺҹдҪҸжӯӨең°зҡ„и—Ҹж—ҸжқӮеұ…пјҢйҖҗжёҗдёҺд№ӢйҖҡе©ҡпјҢд»ҺиҖҢеҗёж”¶дәҶи—Ҹж—ҸжҲҗеҲҶпјҢеүҚдёҫеӨҸжІіеҺҝз«Ӣ第дёҖе°ҸеӯҰжңүзҲ¶еӣһжҜҚи—Ҹзҡ„еӯҰз”ҹи¶…иҝҮ4еҗҚпјҢзҡҶеұһжӯӨдҫӢгҖӮз”ҹжҙ»еңЁйқ’жө·зҡ„жүҳиҢӮпјҲжүҳжҜӣпјүдәәпјҢдј з»ҹи®ӨиҜҶдёәвҖңжүҳжҜӣиҖ…еҚіи’ҷгҖҒи—Ҹдәәж°‘д№Ӣеӣһж•ҷеҫ’д№ҹпјҢдёҖйғЁеұ…еҫӘеҢ–еҺҝеўғпјҢе…¶иЁҖиҜӯжңҚйҘ°йҘ®йЈҹеұ…дҪҸеқҮи’ҷеҸӨеҢ–пјӣдёҖйғЁеұ…еҗҢд»Ғд№ӢдёҖйҡ…пјҢеҲҷз”ҹжҙ»дёәи—ҸејҸпјҢзӣ–и’ҷгҖҒи—ҸеҢ–д№Ӣеӣһдәәд№ҹвҖқгҖӮзҺ°д»ЈеӯҰиҖ…з ”з©¶зҡ„з»“жһңжҳҜпјҢжүҳиҢӮдәәзҡ„дё»дҪ“жҳҜиҝӣе…Ҙйқ’жө·зҡ„и’ҷеҸӨж—ҸпјҢйҖҗжёҗиһҚе…ҘдәҶз»ҙеҗҫе°”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гҖҒжұүж—ҸпјҢдҝЎеҘү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пјҢдҪҶд»Қж—§ж“Қи’ҷеҸӨиҜӯпјҢз©ҝи’ҷеҸӨжңҚиЈ…пјҢвҖңдҪңдёәи’ҷи—ҸеӣһпјҢж—ўжҳҜи’ҷи—ҸдәәеӣһеҢ–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д№ҹжҳҜеӣһеӣһи’ҷи—ҸеҢ–зҡ„з»“жһңвҖқгҖӮиҮідәҺйқ’жө·еңҹж—ҸпјҢвҖңжңҚиЈ…д№ дҝ—ејӮдәҺеҗ„ж—ҸпјҢиҜӯиЁҖеҲҷжқӮд»Ҙи’ҷгҖҒи—ҸиҜӯпјҢзҡҶдёҡеҶңвҖқпјҢвҖңж—Ҙи§ҒеҗҢеҢ–дәҺжұүдәәвҖқгҖӮиҖҢеңҹж—ҸдёҺжұүгҖҒи—Ҹж°‘ж—Ҹзҡ„е…ізі»зӣёеҜ№иҫғдёәзҙ§еҜҶпјҢдёҺжұүж—Ҹдә’и®ӨдәІжҲҝеҪ“家пјҢеҸ—жұү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еҫҲж·ұпјҢд№ҹдёҺжұүж—ҸжңүйҖҡе©ҡзҺ°иұЎпјҢдҪҶвҖңеңҹгҖҒи—Ҹд№Ӣй—ҙзҡ„йҖҡе©ҡпјҢжҜ”еңҹгҖҒжұүд№Ӣй—ҙзҡ„жӣҙдёәжҷ®йҒҚвҖқпјҢвҖңжұүеңҹйҖҡе©ҡзҡ„еҫҲе°‘пјҢжңүзҡ„пјҢеҸӘжңүеңҹдәәеЁ¶жұүдәәпјҢеӣ дёәеҘіе®¶йңҖзҙўзҡ„иҙўзӨјеҫҲйҮҚвҖқгҖӮ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йҖҡе©ҡпјҢ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еҠ ејәдәҶзӣёдә’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ӨеҫҖгҖҒдәӨжөҒдёҺдәӨиһҚпјҢеңЁиҘҝе®ҒпјҢжұүж—ҸзәҰеҚ 70%пјҢеӣһж—ҸзәҰеҚ 26%пјҢи—Ҹж—ҸзәҰеҚ 4%пјҢиҖҢдё”вҖңиҝ‘е№ҙеӨҡиў«жұүж—ҸеҗҢеҢ–вҖқгҖӮжӯЈеҰӮ马й№ӨеӨ©ж„ҹж…Ёзҡ„пјҡ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пјҢе®һзҡҶеҗҢжәҗгҖӮдё”ж•°еҚғе№ҙжқҘпјҢеҗ„ж°‘ж—ҸжҺҘи§ҰжҝҖиҚЎпјҢйЈҺдҝ—гҖҒиҜӯиЁҖдә’зӣёеҗҢеҢ–пјҢеҪјжӯӨйҖҡе©ҡпјҢиЎҖз»ҹдәҰж··пјҢжёҗжҲҗдёәж•ҙдёӘ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пјҢе·ІйҡҫдёәжҳҺзЎ®д№ӢеҲҶеҲ«зҹЈгҖӮ дәҢгҖҒ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зҡ„з»ҸжөҺдёҺзӨҫдјҡдәӨеҫҖ 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Ө„дәҺй»„еңҹй«ҳеҺҹиҫ№зјҳдёҳйҷөең°иІҢеҗ‘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зҡ„иҝҮжёЎеёҰпјҢдё»иҰҒз»ҸжөҺжЁЎејҸеҲҷжҳҜеҶңиҖ•дёҡеҗ‘еҶңзү§з»“еҗҲгҖҒеҶҚеҗ‘зү§дёҡзҡ„иҝҮжёЎпјҢз”ҹжҙ»еңЁиҝҷдёҖең°еҢәзҡ„еҗ„ж°‘ж—ҸпјҢе…¶з»ҸжөҺжЁЎејҸеҝ…然еҸ—еҲ°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зҡ„еҪұе“Қе’ҢеҲ¶зәҰгҖӮ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пјҢжұүж—ҸгҖҒеңҹж—Ҹдё»иҰҒз»ҸиҗҘеҶңдёҡпјҢ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и—Ҹж—Ҹдё»иҰҒд»ҺдәӢз•ңзү§дёҡпјҢиҖҢеӣһж—ҸгҖҒж’’жӢүж—ҸгҖҒдҝқе®үж—ҸеҲҷд»ҘеҶңдёҡдёәдё»пјҢе…јиҗҘжүӢе·Ҙдёҡе’Ңе•ҶдёҡгҖӮ马й№ӨеӨ©еҜ№жӯӨжңүиҜҰз»ҶжҸҸиҝ°пјҡйқ’жө·ең°еҹҹиҫҪйҳ”пјҢдәәеҸЈзЁҖе°‘пјҢжұүдәәгҖҒеӣһж°‘пјҢиҒҡз„ҰдәҺйқ’жө·дёңеҢ—йғЁпјҢеӣ ж°”еҖҷеңҹе®ңеҸҠж°ҙеҲ©д№ӢдҫҝпјҢдё“дәӢеҶңдёҡгҖӮи’ҷгҖҒи—Ҹдәәж°‘пјҢеҸ—еӨ©ж—¶д№ӢйҷҗеҲ¶пјҢдёҺд№ жғҜд№ӢзӣёжІҝпјҢд»Ҙжёёзү§дёәз”ҹжҙ»пјҢйҖҗж°ҙиҚүиҖҢеұ…гҖӮ 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•ҝжңҹдәӨеҫҖпјҢ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пјҢз»ҸжөҺжЁЎејҸдёҚж–ӯеҸҳеҢ–пјҢд№ҹжңүдёҚе°‘ең°ж–№зҡ„и—Ҹ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ж°‘дј—еҸ—жұүгҖҒеӣһзӯүж—Ҹж„ҹжҹ“пјҢејҖе§Ӣд»ҺдәӢеҶңдёҡиҖ•дҪңгҖӮиҝһиҝңеңЁжө·иҘҝзҡ„йғҪе…°еҺҝпјҢйғҪеҮәзҺ°дәҶвҖңи’ҷз•Әд№Ӣж°‘жёҗзҹҘиҲҚеёҗе°ұеұӢпјҢжҲ–ејғзү§з•ңпјҢиҖҢдәӢиә¬иҖ•вҖқзҡ„зҺ°иұЎгҖӮиҘҝе®ҒеёӮйғҠзҡ„зҷҪ马еҜәжқ‘пјҲд»Ҡдә’еҠ©еҺҝзҷҪ马еҜәпјүеҫҲжңүд»ЈиЎЁжҖ§пјҢиҜҘжқ‘еӨ„дәҺе…°е·һеҲ°иҘҝе®Ғзҡ„дәӨйҖҡиҰҒйҒ“пјҢеұһдәҺи—ҸгҖҒеӣһжқӮеұ…зҡ„жқ‘иҗҪгҖӮ1933е№ҙпјҢйЎҫжү§дёӯзӯүдәәи®ҝй—®дәҶдҪҚдәҺзҷҪ马еҜәж—Ғзҡ„жқ‘иҗҪпјҢиҜҘжқ‘е…ұжңү25жҲ·дәә家пјҢе…¶дёӯ19жҲ·и—Ҹж°‘пјҢ6жҲ·еӣһж°‘пјҢиҷҪ然жҳҜи—ҸгҖҒеӣһж··еұ…пјҢдҪҶи—Ҹж°‘еҚ дәҶжҖ»жҲ·ж•°зҡ„иҝ‘е…«жҲҗпјҢиҖҢдё”жқ‘еә„зҡ„дә§дёҡд№ҹе…ЁеҪ’еҺҹдҪҸж°‘и—Ҹж—ҸжүҖжңүпјҢвҖңжқ‘еә„дёҠжүҖжңүзҡ„еҶңз”°жҲҝеұӢпјҢе®Ңе…ЁжҳҜз•Әеӯҗзҡ„дә§дёҡпјҢе°ұжҳҜе°‘ж•°еҒҡд№°еҚ–зҡ„еӣһж•ҷеҫ’дҪҸзҡ„жҲҝеұӢпјҢд№ҹжҳҜеҗ‘з•Әеӯҗз§ҹжқҘзҡ„вҖқгҖӮиҖҢиҝҷдёӘжқ‘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еҲҷвҖңеӨ§йғЁеҲҶе·Із»Ҹжұүж—ҸеҢ–дәҶгҖӮйғҪд»ҺдәӢдәҺиҖ•дҪңпјҢеңЁиЁҖиҜӯдёҠпјҢ他们йҷӨдәҶиҜҙз•ӘиҜқд№ӢеӨ„пјҢд№ҹиғҪи®ІжұүиҜӯгҖӮжңҚиЈ…дёҠпјҢз”·зҡ„е®Ңе…Ёе’ҢжұүдәәдёҖж ·пјҢдёҚиҝҮеҘізҡ„д»ҚиЎЈз•Әеӯҗзҡ„еҺҹжңүжңҚиЈ…вҖқпјҢвҖңд»ҺдәӢз§Қз§ҚеҶңдёҡиҖ•дҪңпјҢеҰӮжү“йәҰгҖҒиҙҹи–ӘгҖҒй”„з”°зӯүиү°иӢҰзҡ„е·ҘдҪңвҖқгҖӮ第дәҢе№ҙпјҢдёҠжө·гҖҠз”іжҠҘгҖӢи®°иҖ…йҷҲиө“йӣ…еүҚеҫҖиҘҝе®ҒйҖ”дёӯпјҢеңЁзҷҪ马еҜә第дёҖж¬Ўи§ҒеҲ°и—Ҹж—ҸеҰҮеҘіпјҢз»ҸеҗҢиЎҢзҡ„иӢұзҫҺзғҹе…¬еҸёзҡ„зғ§йҘӯеҸёеҠЎеј жҹҗиҜҙжҳҺпјҢж–№зҹҘжҳҜи—ҸеҘіпјҢвҖңдәҢдәәеңЁй©¬й“ғи–Ҝең°дёӯиҖҳиҚүгҖӮи®°иҖ…д»…и§үе…¶жңҚиЈ…дҪ“жҖҒеҸҲдёҺи’ҷдәәдёҚеҗҢвҖқпјҢвҖңеҘіж“ҚжұүиҜӯ笑зӯ”вҖқгҖӮеҸҜи§ҒзҷҪ马еҜәеҸҠе…¶е‘Ёиҫ№ең°еҢәзҡ„и—Ҹж°‘е·Із»Ҹе®Ңе…Ёи„ұзҰ»дәҶеҺҹжңүзҡ„з»ҸжөҺжЁЎејҸпјҢиҪ¬иҖҢд»ҺдәӢеҶңдёҡиҖ•дҪңдәҶгҖӮиҝҷз§Қеҹәжң¬жұүеҢ–дәҶ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еҸҲиў«з§°дҪңвҖңеҚҠи—ҸвҖқпјҢвҖңжүҖи°“еҚҠи—ҸиҖ…пјҢдҝ—з§°еҚҠз•ӘпјҢд№…е·Іеҗ‘еҢ–еҶ…йҷ„пјҢдёҺжұүдәәеҫҖжқҘз”ҡеҜҶпјҢдё”ж··жңүжұүдәәиЎҖз»ҹпјҢеұ…е·қдёӯпјҢжҲҗеҶңжқ‘пјҢз”ҹжҙ»д№ жғҜпјҢжөёжҹ“еҚҺйЈҺпјҢиҝ‘е№ҙдё”еӨҡж”№еңҹеҪ’жөҒпјҢеҰӮеІ·еҺҝгҖҒдёҙжҙ®дёҖеёҰеңҹеҸёжүҖеұһд№Ӣи—Ҹж°‘зҡҶ然вҖқгҖӮиҖҢи·қзҰ»жұүж°‘еұ…дҪҸеҢәзЁҚиҝң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д№ҹ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Ҹ—жұүж—Ҹз»ҸжөҺжЁЎејҸ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еңЁеҺҹжңүз•ңзү§дёҡ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д»ҺдәӢйғЁеҲҶеҶңдёҡиҖ•дҪңпјҢиҝӣе…ҘдәҶеҚҠзү§еҚҠеҶңгҖҒеҚҠжёёзү§еҚҠе®ҡеұ…зҡ„з”ҹжҙ»гҖӮвҖңиҝ‘и—Ҹдҝ—з§°зҶҹз•ӘпјҢеҸҲз§°йҫҷеЁғпјҢиҝ‘еҹҺеёӮпјҢйҖҡжұүиҜӯпјҢеҚҠиҖ•еҚҠзү§пјҢжёҗжҲҗзҶҹең°пјҢеұ…еңҹеұӢпјҢиҫғеҜҢиҖ…дәҰеұ…жңЁжқҝеұӢпјҢй«ҳжҘјзғӯзӮ•пјҢд»“еӮЁе……ж®·пјҢжғҹжңҚйҘ°д»Қеӯҳи—Ҹдҝ—гҖӮжҙ®жІідёҠжөҒдёҙжҪӯеҺҝеҚ“е°јйҷ„иҝ‘д№Ӣи—Ҹж°‘пјҢдәҰеұһжӯӨзұ»гҖӮвҖқйқ’жө·и—Ҹж—ҸпјҢвҖңз”ҹжҙ»д»ҚеӨҡжёёзү§пјҢеұ…дәҺиҘҝе®Ғйҷ„иҝ‘еҗ„еҺҝиҖ…пјҢдәҰжңүж”№еҠЎеҶңдёҡвҖқиҖ…гҖӮдёҙеӨҸеҲ°д№°еҗҫпјҲд»ҠеӨҸжІіеҺҝзҫҺжӯҰд№ЎпјүйҖ”дёӯвҖңеҮ еӨ„и—Ҹж°‘иҒҡеұ…зҡ„жқ‘иҗҪпјҢ他们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Ңе·Із»Ҹиҝӣе…ҘеҺҹе§Ӣзҡ„еҶңдёҡ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зҶҷзҶҷе—Ҙе—Ҙең°жӯЈеңЁж”¶еүІйәҰеӯҗгҖӮдёҖжҚҶжҚҶзҡ„收иҺ·зү©пјҢд»ҺзүӣиғҢдёҠиҪҪеҲ°жҷ’еңәдёҠеҺ»вҖқгҖӮйҷӨжӯӨиҖҢеӨ–пјҢиҝҳжңүйғЁеҲҶи—Ҹ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ж’’жӢүж—Ҹж°‘дј—пјҢеӣ ең°еҲ©дёҺиө„жәҗд№ӢдҫҝпјҢејҖе§Ӣд»ҺдәӢеүҜдёҡгҖҒе•Ҷдёҡз»ҸиҗҘгҖӮеҰӮйқ’жө·иҢ¶еҚЎпјҲеҜҹеҚЎпјүжҳҜи‘—еҗҚзҡ„йқ’зӣҗдә§ең°пјҢеҺҹеұһи’ҷеҸӨзҺӢе…¬жүҖжңүпјҢд»…и®ёи’ҷеҸӨиҙ«ж°‘йўҶеҸ–зҘЁз…§жҢ–е”®гҖӮ收еҪ’еӣҪжңүеҗҺпјҢдә§йҮҸеўһеҠ пјҢй”Җи·Ҝжү©еұ•пјҢйҒҚеёғиҘҝеҢ—е·қйҷ•пјҢдё»иҰҒзҡ„иҝҗиҫ“ж–№ејҸжҳҜз”ұ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и—Ҹж—Ҹзҷҫ姓й©ұдҪҝзүІз•ңй©®иҝҗпјҢвҖңй”Җе”®ең°дёәйқ’жө·вҖқпјҢвҖңз”ҳиӮғд№Ӣжҙ®еІ·пјҢеӣӣе·қд№ӢжқҫиҢӮпјҢеҸҠйҷ•иҘҝд№Ӣжұүдёӯзӯүең°вҖқпјҢиҖҢвҖңжӯӨз§Қй©®жҲ·пјҢдҝұзі»и’ҷгҖҒи—Ҹдәәж°‘вҖқгҖӮи—Ҹж°‘еҹәдәҺ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дёҺ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пјҢдёҚжҚ•йЈҹйұјзұ»гҖӮйқ’жө·ж№–зӣӣдә§ж№ҹйұјпјҲйқ’жө·ж№–иЈёйІӨпјүпјҢж№ҹйұјеұһеҶ·ж°ҙйұјзұ»пјҢе‘ійҒ“йІңзҫҺпјҢеңЁиҘҝе®ҒгҖҒе…°е·һзӯүең°еёӮеңәйўҮе№ҝпјҢдәҺжҳҜж№–еҢәйҷ„иҝ‘зҡ„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ж°‘дј—еңЁжұүж—Ҹзҡ„еҪұе“ҚдёӢпјҢйҖҗжёҗйҖӮеә”еёӮеңәйңҖжұӮпјҢејҖе§ӢжҚ•йұјиҝҗй”ҖгҖӮйқ’жө·дә§йұјпјҢжғңеңҹдәәеӣ е®—ж•ҷиҝ·дҝЎпјҢдёҚйЈҹпјҢдәҰдёҚжҚ•гҖӮжғҹеҶ¬ж—ҘжңүжұүдәәжҲ–жұүеҢ–зҡ„и’ҷдәәгҖҒз•ӘдәәпјҢеҮҝеҶ°еҸ–йұјпјҢиҝҗиҮіиҘҝе®ҒгҖҒе…°е·һпјҢеҚіеҗҚеҶ°йұјгҖӮ 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пјҢжҳҜеҶ…ең°е•Ҷе“ҒдёҺ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еҗ„ж°‘ж—Ҹзү©дә§дәӨжҳ“зҡ„йҮҚиҰҒеӯ”йҒ“д№ӢдёҖпјҢеҺҶеҸІж—¶жңҹпјҢеңЁвҖңжІіе·һгҖҒжҙ®е·һгҖҒеІ·е·һеқҮи®ҫиҢ¶й©¬еҸёпјҢд»Ҙзү§жҳ“еҶңвҖқгҖӮдј з»ҹдёҠзҡ„вҖңйқ’жө·е•ҶдёҡпјҢеӣ еұ…ж°‘еӨ§йғЁдёәи’ҷгҖҒи—Ҹж°‘ж—ҸпјҢж•…дәӨжҳ“е°ҡеӨҡд»Ҙзү©жҳ“зү©д№Ӣж–№ејҸвҖқпјҢдҪҶжҳҜпјҢйҡҸзқҖеҶ…ең°е•ҶдәәдёҺе•Ҷе“Ғзҡ„дёҚж–ӯж¶Ңе…ҘпјҢд№ҹжңүдёҚе°‘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и—Ҹж—Ҹж°‘дј—ејҖе§Ӣд»ҺдәӢе•Ҷе“ҒдәӨжҳ“жҙ»еҠЁпјҢз”ұдәҺиҜӯиЁҖдәӨжөҒж–№йқўеӯҳеңЁзҡ„йҡңзўҚпјҢеӮ¬з”ҹдәҶвҖңжӯҮ家вҖқеҲ¶еәҰпјҢеҚіз”ұйҖҡжҷ“и—ҸиҜӯжҲ–и’ҷеҸӨиҜӯзҡ„жұүдәәжқҘе……еҪ“жұүе•ҶдёҺ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е•ҶдәәдәӨжҳ“зҡ„дёӯд»ӢдәәпјҢвҖңи’ҷгҖҒи—ҸдәәиҗҘе•ҶиҖ…пјҢиҝ‘дәҰдёҚе°‘вҖқпјҢвҖңжұүе•ҶдёҺи’ҷгҖҒи—ҸдәәдәӨжҳ“е°ҡеӯҳдёӯд»ӢдәәеҲ¶пјҢеҗҚжӣ°жӯҮ家вҖқпјҢвҖңеӨҡдёәйҖҡи’ҷгҖҒи—ҸиҜӯд№ӢжұүдәәвҖқгҖӮеҗ„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е•Ҷдёҡиҙёжҳ“жҜ”иҫғз№Ғзӣӣ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жҳҜеҲҶеёғеңЁз”ҳвҖ”йқ’вҖ”и—ҸдәӨйҖҡиҰҒйҒ“дёҠиҫғеӨ§зҡ„еұ…ж°‘зӮ№д»ҘеҸҠ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йҮҚиҰҒеҜәйҷўйҷ„иҝ‘пјҢеүҚиҖ…зҡ„д»ЈиЎЁеҰӮж№ҹжәҗеҺҝпјҢеҗҺиҖ…еҲҷд»ҘеЎ”е°”еҜәжүҖеңЁзҡ„йІҒж’’пјҲйІҒжІҷе°”пјүй•ҮжңҖдёәе…ёеһӢгҖӮж№ҹжәҗеҺҝеӨ„дәҺиҘҝе®ҒдёҺйқ’жө·ж№–д№Ӣй—ҙпјҢжҳҜз”ҳгҖҒйқ’йҖҡеҫҖиҘҝи—Ҹзҡ„дәӨйҖҡиҰҒеҶІпјҢеҸҲжҳҜйқ’жө·дёңйғЁеҶңеҢәдёҺиҘҝйғЁзү§еҢәгҖҒй»„еңҹй«ҳеҺҹдёҺ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гҖҒи—Ҹж–ҮеҢ–дёҺжұүж–ҮеҢ–зҡ„з»“еҗҲйғЁпјҢеҫҲж—©д»ҘжқҘе°ұжҳҜвҖңжұүгҖҒеңҹгҖҒи’ҷгҖҒеӣһ并з•ӘдәәдәӨжҳ“д№ӢжүҖвҖқпјҢе°Өе…¶д»Ҙжё…еҳүеәҶгҖҒйҒ“е…үд№Ӣйҷ…жңҖдёәз№ҒзӣӣпјҢвҖңеҪ“ж—¶и’ҷгҖҒи—Ҹд№Ӣиҙ§пјҢеӨ§йғЁд»Ҙж№ҹжәҗдёәй”ҖеңәвҖқгҖӮиҝ‘д»Јд»ҘжқҘпјҢз”ұдәҺиҘҝж–№еҠҝеҠӣзҡ„иҝӣе…ҘпјҢж”№еҸҳдәҶиҜҘең°и’ҷеҸӨгҖҒиҘҝи—Ҹең°еҢәиҙ§зү©зҡ„иҙёжҳ“иө°еҗ‘пјҢвҖңи—Ҹиҙ§иҘҝжі„дәҺеҚ°еәҰпјҢзҺүж ‘д№Ӣиҙ§пјҢеҚ—жі„дәҺе·қиҫ№пјҢи’ҷдәәд№Ӣиҙ§пјҢеҢ—жі„дәҺз”ҳгҖҒеҮүвҖқпјҢдҪҝеҫ—ж№ҹжәҗдҪңдёәеҢәеҹҹе•Ҷдёҡдёӯеҝғзҡ„ең°дҪҚеҸ—еҲ°еҫҲеӨ§еҪұе“ҚпјҢжёҗи¶ӢиЎ°иҗҪгҖӮдёҚиҝҮ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пјҢеӣ дёәзҡ®жҜӣиҙёжҳ“дёҡзҡ„еҙӣиө·пјҢиҜҘең°е•ҶдёҡйҮҚиҺ·ж–°з”ҹпјҢж—Ҙжёҗз№ҒиҚЈпјҢжҚ®й©¬й№ӨеӨ©дј°и®ЎпјҢеҺҝеҹҺеҶ…жңүе•Ҷдәә1000дҪҷ家пјҢеҠ дёҠеҹҺе…ізҡ„е•ҶдәәпјҢжҖ»е…ұжңү3000дҪҷ家гҖӮиҖҢиҝҷдәӣе•Ҷ家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еӣһж°‘дёҺжұүж°‘пјҢ他们收иҙӯеҪ“ең°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и—Ҹж—Ҹзҷҫ姓зҡ„зҡ®жҜӣдёҺең°ж–№зү№дә§пјҢиҝҗй”Җдә§дәҺеҶ…ең°зҡ„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еҝ…йңҖе“Ғ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—Ҹзү§ж°‘жүҖйңҖзҡ„з –иҢ¶гҖӮе…¶д»–жҜ”иҫғйҮҚиҰҒзҡ„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гҖҒеңҹзӯүж°‘ж—ҸжқӮеұ…зҡ„йҮҚиҰҒеұ…ж°‘зӮ№пјҢд№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еҰӮдёҙжҪӯеҺҝпјҢжң¬жқҘжҳҜи—Ҹж°‘ең°еҢәпјҢеңЁй•ҝжңҹзҡ„дәӨжөҒдәӨиһҚ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…ўж…ўеҸҳдёә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жқӮеұ…ең°еҢәгҖӮ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пјҢж–°еҹҺдё»иҰҒдёәжұүж°‘еұ…дҪҸеҢәпјҢж—§еҹҺд»Ҙеӣһж°‘дёәдё»пјҢе№ҝиўӨзҡ„д№ЎйҮҺеҲҷжҳҜи—Ҹж°‘зҡ„зү§еҢәгҖӮеҺҝеҹҺдҪңдёәең°еҹҹиЎҢж”ҝгҖҒз»ҸжөҺдёӯеҝғпјҢе•Ҷдёҡд№ҹжҜ”иҫғеҸ‘иҫҫпјҡвҖңе…Ҙе…¶иӮҶпјҢйҷӨиӢҘе№ІжҙӢгҖҒе№ҝиҙ§еӨ–пјҢдәҰжңүе•ҶеҠЎгҖҒдёӯеҚҺдёӨеұҖд№Ӣеӣҫд№ҰеҲ—дәҺжһ¶дёҠгҖӮвҖқиҮідәҺ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и…№ең°пјҢиҷҪ然д№ҹжңүеӨ–ең°е•ҶдәәдёҚз•Ҹиү°йҡҫпјҢеүҚеҫҖиҙёжҳ“пјҢдҪҶжҖ»дҪ“е№…еәҰдёҚеӨ§пјҢдё”еӨҡеұһеӯЈиҠӮжҖ§иЎҢдёәгҖӮйғҪе…°еҺҝвҖңеӨ–жқҘжұүеӣһе•ҶдәәпјҢзҡҶжқҘиҮӘиҘҝе®ҒгҖҒж№ҹжәҗдёҖеёҰпјҢеӨҸеӯЈжҗәи’ҷз•Әеҝ…йЎ»д№Ӣзү©еҰӮиҢ¶гҖҒзғҹгҖҒй…’гҖҒеёғгҖҒй’ҲгҖҒзәҝгҖҒзі–зӯүе…ҘеўғпјҢеҫҖеҗ„еёҗиҙ©еҚ–пјҢеҸҠеҶ¬ж—¶еҲҷ收еҗ„зұ»жҜӣзҡ®еҸҠй№ҝиҢёгҖҒйәқйҰҷзӯүд»ҘеҪ’пјҢе№ҙеҸӘдёҖж¬ЎвҖқгҖӮз”ҹжҙ»еңЁ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зҡ„и—Ҹ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зӯүж—Ҹдәәж°‘пјҢеҜ№дәҺ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зҡ„дҝЎд»°еҚҒеҲҶиҷ”иҜҡпјҢ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йҮҚиҰҒеҜәйҷўпјҢж—ўжҳҜе®—ж•ҷдёӯеҝғпјҢд№ҹжҳҜдј з»ҹдё–дҝ—дәӢеҠЎзҡ„дёӯеҝғпјҢжүҖеңЁең°еҫҖеҫҖдјҡеҪўжҲҗжҜ”иҫғеӨ§зҡ„еұ…ж°‘еҢәпјҢиЎҢж—…зә·иҮіпјҢе®ўе•ҶеҫҖжқҘпјҢиҝӣиҖҢеҸ‘еұ•жҲҗдёәең°еҹҹе•ҶиҙёдёӯеҝғгҖӮеЎ”е°”еҜәжүҖеңЁзҡ„йІҒжІҷе°”й•ҮпјҢе°ұжҳҜеҪ“ең°жұүгҖҒи—Ҹж°‘д№Ӣй—ҙзҡ„йҮҚиҰҒдәӨжҳ“еңәжүҖгҖӮи—Ҹж°‘еҮәеҚ–д№Ӣиҙ§пјҢйҰ–жҺЁе®¶з•ңгҖҒйҮҺе…Ҫд№Ӣзҡ®жҜӣпјҢж¬Ўдёәи—ҸйҰҷгҖҒжҜЎгҖҒдҪӣеғҸд»ҘеҸҠиҚҜз”Ёй№ҝиҢёгҖҒйәқйҰҷгҖҒзәўиҠұзӯүпјҢд№°е…ҘеҲҷдёәзІ®йЈҹгҖҒеёғеҢ№гҖҒиҢ¶гҖҒз»ёзјҺгҖҒжҙӢиҙ§гҖҒзғҹж–ҷгҖҒ马йһҚзӯүгҖӮеұ…ж°‘зәҰдәҢзҷҫдҪҷ家пј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жқӮеӨ„пјҢеұӢе®Үж үжҜ”гҖӮ иҝҷз§Қе•Ҷдёҡиҙёжҳ“жҙ»еҠЁпјҢеҝ…然дҪҝеҫ—еұ…дҪҸеңЁиҝҷдёҖеҢәеҹҹеҶ…зҡ„еҗ„ж—Ҹдәәж°‘дёҺеӨ–жқҘе®ўе•Ҷзҡ„дәӨеҫҖдёҚж–ӯеўһејәпјҢиҖҢеҢәеҹҹеҶ…еҗ„ж°‘ж—Ҹзӣёдә’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ӨеҫҖдәӨжөҒд№ҹжӣҙеҠ йў‘з№ҒпјҢдё”ж—ҘзӣҠж·ұе…ҘгҖӮдёҖдәӣд»ҺдәӢе•ҶдёҡжҲ–й•ҝйҖ”иҙ©иҝҗ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з”ұдәҺжқҘеҫҖеҗ„ең°пјҢдёҺеҶ…ең°жұүгҖҒеӣһзӯүж°‘ж—ҸдәӨеҫҖпјҢеӯҰдјҡдәҶе…¶д»–ж°‘ж—Ҹзҡ„иҜӯиЁҖгҖӮжһ—з«һеңЁе…°е·һйғҠеҢәпјҢйҒҮеҲ°й©ұиө¶зүҰзүӣзҫӨеҫҖе…°е·һиҙ©еҚ–зҡ„е№із•ӘеҺҝпјҲд»Ҡж°ёзҷ»еҺҝпјүи—Ҹж°‘пјҢеұһдәҺйІҒеңҹеҸёжүҖиҫ–иҢғеӣҙпјҢдёҺжұүж°‘дәӨеҫҖеҺҶеҸІжӮ д№…пјҢеҸ—жұүж—ҸеҪұе“ҚеҫҲеӨ§пјҢвҖңдёҺд№Ӣи°ҲпјҢзҹҘжӯӨиҫҲзұ»иғҪж“ҚжұүгҖҒи’ҷиҜӯиЁҖпјҢдё–еұ…жқҫеұұпјҢдәәдј—ж•°еҚғпјҢд»Ҙзү§з•ңдёәдёҡпјҢдә§зүҰзүӣз”ҡеӨҡвҖқпјҢвҖңзӣ–жӯӨд№ғзҶҹз•ӘвҖқгҖӮиҖҢеңЁжқҫеұұжӣҙеҫҖеӨ–зҡ„еҢәеҹҹпјҢжҳҜдёҚеұһдәҺйІҒеңҹеҸёзҡ„и—Ҹж—ҸиҒҡеұ…еҢәпјҢдёҺжұүж—ҸеҢәеҹҹзӣёйҡ”зЁҚиҝңпјҢвҖңдҪҶеҗҢж ·зҡ„е·ІеҸ—дәҶжұүж—Ҹзҡ„иӢҘе№ІеҗҢеҢ–гҖӮ他们еңЁжқҫеұұеҢәеҹҹд№ӢеҶ…з§ҚдәӣзІ®йЈҹпјҢиҖҢдё”е…»жңүеҘҪзҡ„иө°й©¬пјҢж—¶еёёжӢҝ他们зҡ„еҮәдә§е“ҒеҲ°еІ”еҸЈй©ҝгҖҒж°ёзҷ»дёҖеёҰеёӮеңәдёҠдәӨжҚўз –иҢ¶гҖҒйЈҹзӣҗе’Ңе…¶д»–еҝ…йңҖзҡ„ж—Ҙз”Ёе“ҒвҖқгҖӮдёҺз»ҸжөҺиҒ”зі»ж—ҘзӣҠзҙ§еҜҶзӣёйҖӮеә”пјҢеңЁеҫҲеӨҡе…¬ејҖеңәеҗҲ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йҮҚиҰҒиҠӮж—ҘжҲ–зӣӣеӨ§иҒҡдјҡпјҢеҗ„ж°‘ж—ҸзҫӨдј—ж··жқӮеҸӮдёҺпјҢдёҚеҲҶеҪјжӯӨгҖӮеҰӮд№җйғҪеҺҝжҜҸе№ҙдёҖеәҰзҡ„йӘЎй©¬еӨ§дјҡпјҢдё»йўҳжҳҜзүІз•ңдәӨжҳ“жҙ»еҠЁпјҢдҪҶйғҪдјҡйӮҖиҜ·жҲҸзҸӯеӯҗжј”е”ұз§Ұи…”пјҢд»Ҙзғҳжүҳж°”ж°ӣпјҢеҗёеј•е®ўе•ҶпјҢ1934е№ҙзҡ„йӘЎй©¬еӨ§дјҡпјҢжј”е”ұзҡ„еү§зӣ®жҳҜз§Ұи…”гҖҠзІҫеҝ гҖӢпјҢзңӢжҲҸиҖ…вҖңи’ҷи—Ҹз”·еҘіпјҢеҲҷжқӮжІ“дәҺеҗ„еӨ„пјҢиЎЈзқҖзәўз»ҝпјҢзҺҜдҪ©зҗ…зҸ°пјҢйўҮжңүеҗ„ж—ҸеӣўиҒҡгҖҒд№җеәҶеҚҮе№ід№ӢиұЎвҖқгҖӮж°ёзҷ»еҺҝеІ”еҸЈй©ҝпјҲд»ҠеӨ©зҘқи—Ҹж—ҸиҮӘжІ»еҺҝеӨ©и—ҸеҜәй•ҮеІ”еҸЈй©ҝжқ‘пјүжҳҜдёқз»ёд№Ӣи·ҜдёҺиҢ¶й©¬еҸӨйҒ“дёҠйҮҚиҰҒзҡ„еҸӨй©ҝз«ҷгҖӮдҪҚдәҺйҮ‘ејәе·қзҡ„ж ёеҝғең°еёҰпјҢиҮӘеҸӨд»ҘжқҘеҮәдә§е–„иө°еҝ«жӯҘгҖҒиҖҗеҠӣжҢҒд№…зҡ„еІ”еҸЈй©ҝ马пјҢжҜҸе№ҙжҳҘгҖҒз§ӢдёӨеӯЈйғҪиҰҒдёҫеҠһиөӣ马еӨ§дјҡпјҢвҖңиҝңиҝ‘жұүгҖҒз•ӘйӘ‘马иөҙиөӣиҖ…пјҢиҮіж•°еҚғеҢ№пјҢз”·еҘіиҒҡи§ӮпјҢжј«еұұйҒҚи°·пјҢзӣӣжһҒдёҖж—¶вҖқгҖӮ1935е№ҙ5жңҲ12ж—ҘпјҢйқ’жө·еҗ„з•ҢеңЁ100еёҲеёҲйғЁеҸ¬ејҖж¬ўиҝҺйӮөе…ғеҶІеҸҠзҸӯзҰ…еӨ§дјҡпјҢж•ЈдјҡеҗҺж¬ўе®ҙпјҢвҖңеҸ°дёҠжј”з§Ұеү§еҠ©е…ҙпјҢеҶӣд№җеҘҸдәҺеәӯвҖқпјҢвҖңи—ҸгҖҒи’ҷгҖҒеӣһгҖҒжұүгҖҒеңҹдәәпјҢиҒҡи§ӮиҖ…иҫҫеҚғдҪҷдәәпјҢеҰҮеҘіжңҚйҘ°пјҢе°ӨеӨҡеҘҮејӮпјҢеҸҜи°“дёҖж°‘ж—Ҹеұ•и§Ҳдјҡд№ҹвҖқгҖӮеЎ”е°”еҜәжүҖеңЁйІҒжІҷе°”й•ҮпјҢз”ұйқ’жө·зңҒж”ҝеәңдё»жҢҒпјҢеҖҹжҜҸе№ҙйҳҙеҺҶжӯЈжңҲеҚҒдёүж—ҘиҮіеҚҒдә”ж—ҘиҜҘеҜәдёҫиЎҢи·ізҘһжёёзҒҜдјҡзҡ„ж—¶жңәпјҢеҸ¬ејҖж°‘ж—ҸиҒ”ж¬ўеӨ§дјҡдёҖж¬ЎпјҢз”ЁжқҘиҒ”з»ң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„ҹжғ…пјҢеұҠж—¶дјҡжңү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гҖҒжұүгҖҒеӣһеҗ„ж—ҸзҫӨдј—зғӯжғ…еҸӮдёҺпјҢж—ӢжӯҢж—ӢиҲһпјҢвҖңеҗ„и°ғйҪҗеҮәвҖқгҖӮ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д№ҹ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пјҢдёҚж–ӯиһҚйҖҡгҖӮжһ—й№Ҹдҫ еңЁиҘҝе®Ғж—¶ж„ҹж…ЁйўҮж·ұпјҡвҖңиҝһж—ҘдёҺеӣһж°‘еҰҮеҘізӣёеӨ„пјҢеӨҮзҹҘе…¶зҠ¶еҶөгҖӮеӣ е…¶дёҺжұүдәәеҗҢеҢ–е·Ід№…пјҢдёҖеҲҮйЈҺдҝ—пјҢдёҖеҰӮжұүдәәгҖӮвҖқиҝҷз§ҚиһҚйҖҡдҪ“зҺ°еңЁзӨҫдјҡз”ҹжҙ»зҡ„ж–№ж–№йқўйқўгҖӮиҜёеҰӮж—ҘеёёйҘ®йЈҹпјҢе°ұиЎЁзҺ°еҫ—ж·Ӣжј“е°ҪиҮҙпјҢеӣһж°‘еӣ е®—ж•ҷеҺҹеӣ пјҢзҙ зҲұжҙҒеҮҖпјҢеҸҲе–„дәҺиҗҘе•ҶпјҢ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дёҚе°‘йЈҹеә—йғҪжҳҜеӣһж°‘ејҖи®ҫзҡ„пјҢжӢӣеҫ…еҫҖжқҘзҡ„еҗ„ж°‘ж—ҸиЎҢж—…дёҺе®ўе•ҶгҖӮж°ёзҷ»еҺҝе№іе®үе ЎвҖңйЈҹй“әпјҢзҡҶеӣһдәәжүҖи®ҫпјҢдё“е”®еҮүйқўеҸҠеӨ§йҘјвҖқпјҢвҖңжүҖе”®йЈҹзү©пјҢе°ҡз§°жҙҒеҮҖгҖӮжұүдәәеҠЎеҶңиҖ…з”ҡеӨҡпјҢз»Ҹе•ҶиҖ…еҲҷз»қе°‘пјҢжңүд№ӢпјҢдәҰд»…ејҖе°Ҹе®ҝеә—иҖҢе·ІгҖӮеӣһе•Ҷе–„з»ҸиҗҘпјҢеӣ д»Ҙж—ҘеҜҢпјӣжұүеҶңеҸ—еүҘеүҠпјҢеӣ д»Ҙж—Ҙиҙ«вҖқгҖӮйҷҲиө“йӣ…еңЁзҷҪ马еҜәиҝҷдёӘеӣһгҖҒжұүгҖҒи—ҸжқӮеұ…зҡ„жқ‘еӯҗи§ҒеҲ°зҡ„жҷҜи§Ӯе°ұйқһеёёе’Ңи°җгҖӮеҗ„иҢ¶иӮҶйқўеә—пјҢиҙҙжңүжқ‘规дёҖзәёпјҢз•Ҙи°“пјҡвҖ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дәәзӯүпјҢиӢҘжңүдәүеҗөиҖ…пјҢзҪҡ银еҚҒдәҢе…ғгҖӮж— и®әеұ…ж°‘жҲ–иЎҢдәәпјҢиӢҘеңЁиҝ‘жқ‘е”ұжӯҢжӣІиҖ…пјҢжү§жү“жҹійһӯдёҖзҷҫдәҢеҚҒдёӢгҖӮвҖқиҝҷиҜҙжҳҺиҢ¶иӮҶйқўеә—жҳҜеҪ“ең°еҗ„ж°‘ж—Ҹеұ…ж°‘зӣёдә’дәӨеҫҖзҡ„йҮҚиҰҒеңәжүҖпјҢиҖҢжқ‘规зҡ„еҶ…е®№иҜҙжҳҺеҜ№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ж°‘жқҘиҜҙпјҢеӨ„зҪҡжҳҜдёҖж ·зҡ„пјҢж°‘ж—Ҹз•Ңйҷҗе·ІдёҚеҲҶжҳҺгҖӮз»ҸиҝҮй•ҝжңҹзҡ„зҶҸжҹ“пјҢеӣһж°‘дј з»ҹйҘ®йЈҹдёӯзҡ„е“Ғз§ҚеҰӮжІ№йҰ“зӯүйғҪжҲҗдәҶеҪ“ең°еҗ„ж—Ҹж°‘дј—е–ңзҲұзҡ„зҫҺйЈҹпјҢиҖҢеҺҹжң¬дё»иҰҒдҫқйқ иӮүгҖҒеҘ¶з»ҙжҢҒз”ҹжҙ»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д№ҹејҖе§Ӣд»ҝж•ҲжұүгҖҒеӣһж°‘пјҢеҗғиө·дәҶйқўйЈҹз”ҡиҮіи”¬иҸңгҖӮжӢүеҚңжҘһ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дёҺеҪ“ең°еӣһгҖҒжұүж°‘жқӮеұ…е·Ід№…пјҢж·ұеҸ—еӣһгҖҒжұүж°‘йҘ®йЈҹд№ дҝ—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вҖңдәҰжңүйЈҹйқўзүҮжҲ–йқўеқ—гҖҒйҘ®йқўжұӨиҖ…гҖӮеҚҠжұүеҢ–д№Ӣи—Ҹж°‘пјҢ并жңүзӮ’иҸңе№ІиҸңпјҢжҲ–дәҺйқўдёӯе…ҘиӮүеқ—иҖ…вҖқгҖӮеҰӮйҒҮи—Ҹдҝ—иҠӮж—ҘпјҢеҲҷвҖңеҗ„и—Ҹж°‘ж— дёҚзҫҺиЎЈйІңйЈҹпјҢжҲ–и’ёиӮүеҢ…пјҢжҲ–з…ҺжІ№йҘјпјҢз”ҡжҲ–ж•Ҳжұүдәәд№ӢйқўйҘәвҖқ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дёҖиЎҢд»ҺдёҙжҪӯеҲ°еҗҲдҪңйҖ”дёӯз»ҸиҝҮйҷҢеҠЎпјҲеҸҲдҪңд№°еҗҫпјүпјҢеҪ“ең°зҡ„дә”ж——еңҹе®ҳжқЁеҚ иӢҚпјҢжұү姓еҚҙвҖңдёҚиғҪдҪңжұүиҜӯвҖқпјҢдҪҶ其家вҖңеҶ…ең°иҜёеҮәе“ҒиӢҘжұҹиҘҝз“·еҷЁгҖҒдёҠжө·зҪҗеӨҙйЈҹе“ҒдәҰ粲然йҷҲеҲ—вҖқгҖӮи—Ҹ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дёҠеұӮдәәеЈ«пјҢеңЁдёҺжұүж—ҸеЈ«з»…дәӨеҫҖж—¶пјҢеҫҖеҫҖд№ҹдјҡиә«зқҖжұүжңҚпјҢеҰӮжӢүеҚңжҘһдҝқе®үеҸёд»Өй»„жӯЈжё…еҺҹдёәеӣӣе·қзҗҶеЎҳи—Ҹж—ҸпјҢйҡҸеҗҢе…¶ејҹеҳүжңЁж ·дә”дё–жҙ»дҪӣеҲ°жӢүеҚңжҘһпјҢдё»з®Ў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жүҖиҫ–еҢәеҹҹдҝ—еҠЎпјҢжҚ®й©¬й№ӨеӨ©зҡ„и§ӮеҜҹпјҢвҖңй»„еҗӣз”ҹжҙ»пјҢе®Ңе…ЁеҗҢеҢ–дәҺжұүдәәпјҢдё”жһҒеҠӣж‘№д»ҝйғҪеёӮд№Ӣж–ҮжҳҺгҖӮе№іж—ҘиЎЈжңҚпјҢдәҰеҗҢжұүдәәвҖқгҖӮйқ’жө·и’ҷеҸӨе’ҢзЎ•зү№й»„жІіеҚ—йҰ–ж——дёәжё…еҲқйқ’жө·и’ҷеҸӨ29ж——д№ӢдёҖпјҢз”ұдәҺй•ҝжңҹдёҺи—Ҹж—Ҹе…ұеұ…е…ұеӯҳдәҺй»„жІід»ҘеҚ—ең°еҢәпјҢж——дёӢж°‘дј—еҗ„з§Қд№ дҝ—е·Із»ҸдёҺи—Ҹж—ҸжІЎжңүеӨҡе°‘еҢәеҲ«пјҢ第д№қд»ЈжІіеҚ—дәІзҺӢвҖңиІҢжһҒжё…з§ҖпјҢиЎЈжұүжңҚпјҢејұдёҚиғңиЎЈпјҢе®Ңе…Ёжұүдәәд№ҹвҖқгҖӮд»Ҡйқ’жө·дҝқе®үгҖҒеҗҢд»Ғзӯүең°зҡ„еңҹж—ҸжҳҜз”ұеҺҹжқҘеұ…дҪҸжӯӨең°зҡ„и—Ҹж—ҸдёҺе…ҲеҗҺиҝҒе…Ҙзҡ„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жұүж—ҸзӯүдёҚж–ӯйҖҡе©ҡдәӨиһҚжүҖдә§з”ҹзҡ„ж–°ж°‘ж—ҸпјҢ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д»ҘвҖңеҗҫеұҜж—ҸвҖқиҮӘеұ…гҖӮ他们зҡ„жқҘеҺҶпјҢгҖҠеҫӘеҢ–еҺ…еҝ—гҖӢзҡ„и®°иҪҪдёҺеҪ“ең°ж°‘дј—зҡ„еҸЈеӨҙдј иҜҙйғҪдёҚеҚҒеҲҶеҮҶзЎ®пјҢдёҚиҝҮеҶ…ең°еүҚеҫҖиҖғеҜҹиҖ…е·Із»Ҹж•Ҹй”җең°жіЁж„ҸеҲ°дәҶ他们既дёҺи—Ҹж°‘дёҚеҗҢпјҢеҸҲдёҺжұүдәәдёҚеҗҢзҡ„иҜӯиЁҖгҖҒеұ…еӨ„е’ҢжңҚйҘ°йЈҺж јпјҢеҚівҖңе…¶дәәз”·еҘіеқҮзқҖиЈӨпјҢеҘіжӢ–еҚ•еҸ‘иҫ«пјҢејӮдәҺи—Ҹж°‘пјҢиҖҢиҝ‘дәҺжұүдәәд№ҹвҖқпјҢвҖңеҰҮеҘіеқҮзқҖеҚҠиә«зҹӯиЎЈпјҢжңүиЈӨпјҲжҷ®йҖҡз•Әж—ҸеҰҮеҘій•ҝиўҚж— иЈӨпјүвҖқпјҢвҖңеұ…еұӢйқһеёҗжЈҡиҖҢдёәеңҹжҲҝвҖқпјҢвҖңжҚ®еұ…еұӢеҸҠз”·еҘіиЈ…йҘ°зӯүи§Ӯд№ӢпјҢеҗҫеұҜж—Ҹе®һеҚҠеҗҢеҢ–дәҺжұүдәәд№Ӣи—Ҹж—ҸиҖівҖқгҖӮиҝҷз§ҚеҸҳеҢ–пјҢеңЁйқ иҝ‘еҢәеҹҹ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еҸҠйҖҡйҖ”еӨ§йҒ“зҡ„ең°ж–№жӣҙеҠ жҳҺжҳҫпјҢйЎҫйўүеҲҡд»ҺеӨҸжІіз»ҸиҝҮдёүеӨ©ж—…иЎҢжҠөиҫҫдёҙеӨҸеҗҺпјҢжӣҫжҠ’еҸ‘ж„ҹеҸ—пјҡдёүж—ҘжқҘжүҖз»ҸдәҰзҡҶз•ӘеҢәпјҢиҖҢдёҚж„ҹе…¶зү№ж®ҠпјҢеҲҷд»ҘдёәеҫҖжқҘеӨ§йҒ“пјҢеҗҢеҢ–иҮӘжҳ“пјҢзҠ№д№Ӣе№із»Ҙи·ҜдёҠдёҚи§Ғи’ҷеҸӨдәәд№ӢеҺҹжқҘз”ҹжҙ»д№ҹгҖӮ й•ҝжңҹдёҺ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зӯү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жқӮеұ…пјҢдёҚе°‘жұүдәәд№ҹж…ўж…ўеҸ—еҲ°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зҡ„жөёжҹ“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зү№еҲ«жіЁйҮҚи§ӮеҜҹж°‘ж—Ҹзӣёдә’дәӨеҫҖиһҚйҖҡ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д»–дёҺжҙӘи°ЁиҪҪзӯүдәәеңЁдёҙжҪӯиҘҝеӨ§еҜЁжқ‘иҜўй—®еҶңжқ‘еҗҲдҪң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пјҢеҸ‘зҺ°еҪ“ең°зҙ§иҝ©и—Ҹж°‘иҒҡеұ…еҢәпјҢеҗҲдҪңзӨҫзӨҫе‘ҳдёҚе°‘дәәзҡ„姓еҗҚжҳҜ4еӯ—пјҢдё”иҜӯж„ҸдёҚиҜҰпјҢвҖңжңүеҶҜжүҺд»ҖдҝқгҖҒжқҺзҘһд»ҷд»ЈгҖҒи’ҷеӨӘеұұдҝқгҖҒеҲҳеҚҒзҘһдҝқгҖҒзҺӢзҷҫзҰҸиҜҰиҜёеҗҚпјҢеҖҳдәҰз•ӘеҢ–д№ӢеҫҒд№ҺпјҹвҖқиҖҢеңЁйҷҢеҠЎпјҢ他们дҪҸе®ҝеңЁй“ңеҢ зҺӢж–Ү清家пјҢвҖңдәҰйўҮж•ҙжҙҒпјҢзӣ–жұүдәәиҖҢз•ӘеҢ–иҖ…вҖқпјҢйЎҫж°ҸиҷҪжңӘиҜҙжҳҺзҺӢж–Үжё…вҖңз•ӘеҢ–вҖқзҡ„зҗҶз”ұпјҢдҪҶжҚ®дёҖиҲ¬жҖ§еҲӨж–ӯпјҢеә”иҜҘиҝҳжҳҜз»ҸиҝҮи§ӮеҜҹпјҢеҸ‘зҺ°д»–们зҡ„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д№ дҝ—е·Із»ҸдёҺжұүж—ҸжңүдәҶжҳҺжҳҫеҢәеҲ«пјҢеҸҚиҖҢдёҺи—Ҹж—ҸжӣҙеҠ жҺҘиҝ‘пјҢиҝҷжҳҜж°‘ж—ҸжқӮеұ…еҢәеҹҹ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дәӨжөҒ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马й№ӨеӨ©дёҺ马йә’еҺ»йқ’жө·ж№–зҘӯжө·пјҢеңЁжҠӨиЎҢ马йҳҹдёӯпјҢжңүдёҖз»„вҖңиә«з©ҝзҙ«иўҚпјҢи¶ізқҖзҡ®йқҙпјҢеӨҙжҲҙжҜЎеёҪпјҢиӮ©иҚ·еҸҢжҸ’жһӘпјҢи…°еёҰиҚҜзӯ’зҒ«й•°зӯүвҖқзҡ„и—ҸжңҚ马йҳҹпјҢдҪҶеҚҙдёҚжҳҜи—Ҹж—Ҹдәәз»„жҲҗзҡ„пјҢвҖңзӣ–еӣһгҖҒжұүдәәиҖҢдёәи—ҸиЈ…иҖ…вҖқпјҢзӣ®зҡ„жҳҜйҖӮеә”иҝӣе…Ҙи—Ҹж°‘еҢәжүҖйқўдёҙзҡ„иҮӘ然дёҺдәәж–ҮзҺҜеўғгҖӮдёүгҖҒ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зҡ„иҜӯиЁҖиһҚйҖҡ еҗ„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ӨеҫҖе’ҢдәӨжөҒпјҢйҰ–е…ҲжҳҜиҜӯиЁҖж–№йқўзҡ„жІҹйҖҡпјҢеӣ жӯӨеҗ„ж°‘ж—Ҹж°‘дј—й—ҙиҜӯиЁҖзҡ„дә’йҖҡжҳҜжңҖдёәе…ій”®зҡ„иҰҒзҙ пјҢйҳ»зўҚдёҚеҗҢж—ҸзҫӨй—ҙж·ұе…ҘдәӨжөҒзҡ„иҜӯиЁҖеұҸйҡңдёҖж—Ұиў«жү“з ҙпјҢ马дёҠе°ұдјҡе‘ҲзҺ°дёҖдёӘе…Ёж–°зҡ„дё–з•ҢгҖӮи—ҸдәәиҖҢйҖҡжұүиҜӯпјҢд»Ҙй»„жӯЈжё…жңҖдёәе…ёеһӢгҖӮзҗҶеЎҳи—Ҹж—ҸдёҺжұүж—ҸдәӨеҫҖйў‘з№ҒпјҢеҸ—жұү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иҫғж·ұпјҢй»„жӯЈжё…з«Ҙе№ҙж—¶еңЁзҗҶеЎҳеӯҰж ЎеӯҰд№ иҝҮжұүиҜӯгҖӮиҮі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д№ӢеҗҺпјҢеҸҲй•ҝжңҹеңЁе…°е·һеҗ‘зңҒеәңжҺ§иҜү马йә’еҜ№жӢүеҚңжҘһзҡ„дҫөжү°пјҢеҗҢ时继з»ӯеӯҰд№ жұүж–ҮпјҢ并еңЁе®Јдҫ зҲ¶зӯүзҡ„её®еҠ©дёӢпјҢжҲҗз«ӢдәҶи—Ҹж°‘ж–ҮеҢ–дҝғиҝӣдјҡгҖӮ马й№ӨеӨ©еӣһеҝҶ第дёҖж¬Ўи§ҒеҲ°й»„жӯЈжё…пјҢжӯЈжҳҜй»„ж°Ҹиөҙе…°е·һеӯҰд№ жұүиҜӯж—¶пјҢеҪ“ж—¶й»„ж°ҸеңЁеҗ„ж–№йқўиҝҳеҹәжң¬дҝқжҢҒи—Ҹж—Ҹзҡ„д№ дҝ—гҖӮдҪҶеҚҒе№ҙеҗҺеҸҳеҢ–йқһеёёжҳҺжҳҫпјҢвҖңд»ҠеҲҷдёҚзү№жұүиҜӯеЁҙзҶҹпјҢдё”жұүж–ҮдәҰдҪіпјҢжҜҸж—Ҙйҳ…иҜ»жұүж–Үд№ҰзұҚпјҢеӯҰиҜҶи§Ғи§ЈеқҮејӮеёёиҝӣжӯҘвҖқгҖӮй»„жӯЈжё…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дёҚд»…з”ұдәҺе…¶еңЁе…°е·һзҡ„жұүиҜӯеӯҰд№ з»ҸеҺҶпјҢжӣҙеңЁдәҺиҝҷеҚҒе№ҙй—ҙпјҢд»–жёёеҺҶи®ҝй—®дәҶдёҚе°‘еҶ…ең°йҮҚиҰҒйғҪеёӮпјҢдёҺеҫҲеӨҡжұүж°‘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дәӨдәҶжңӢеҸӢпјҢеҜ№дәҺзҺ°д»Јж–ҮжҳҺжңүдәҶжҜ”иҫғжё…жҷ°зҡ„и®ӨзҹҘпјҢд№ҹи®ӨиҜҶеҲ°ж•ҷиӮІеҜ№зҺ°д»Јж–ҮжҳҺдёҺзӨҫдјҡеҸ‘еұ•зҡ„йҮҚиҰҒжҺЁеҠЁдҪңз”ЁпјҢжүҖд»Ҙд»–дёҚдҪҶиҮӘе·ұиҜҙжұүиҜӯпјҢиҜ»жұүж–Үд№ҰзұҚпјҢиҝҳеңЁ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дёҫеҠһи—Ҹж°‘е°ҸеӯҰпјҢйј“еҠұи—Ҹж—Ҹеӯҗејҹе…ҘеӯҰпјҢеӯҰд№ и—Ҹж–Үзҡ„еҗҢж—¶д№ҹеӯҰд№ жұүж–ҮпјҢиө·еҲ°дәҶеј•йўҶйЈҺж°”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жӯЈеҰӮйЎҫйўүеҲҡжүҖиҜҙпјҢй»„жӯЈжё…вҖңжӣҫеҺҶе№ігҖҒжҙҘгҖҒжІӘгҖҒжқӯгҖҒжұүиҜёең°пјҢеҸҲжӣҫеңЁе…°е·һж•ҷи—Ҹж–ҮпјҢе…¶жҖқжғіз”ҡејҖйҖҡпјҢжҖҘж¬Із•Җз•Әж°‘д»Ҙ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пјҢеҲӣз«Ӣи—Ҹж°‘ж–ҮеҢ–дҝғиҝӣдјҡпјҢеҸҲз«Ӣи—Ҹж°‘е°ҸеӯҰиҜ»жұүгҖҒи—Ҹж–Үеӯ—пјҢдёҚ收еӯҰиҙ№вҖқгҖӮдҪңдёәи—ҸеҢәжңҖдё»иҰҒзҡ„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йҳ¶еұӮпјҢ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зҡ„е–ҮеҳӣжҮӮжұүиҜӯзҡ„д№ҹдёҚе°‘пјҢз”ҡиҮіиғҪз”ЁжұүиҜӯе’ҢеҶ…ең°е®ўдәәдәӨжөҒгҖӮеҰӮдҪҚдәҺеӨҸжІізҡ„зҒ«е°”и—Ҹд»“пјҲйңҚе°”и—Ҹпјүжҙ»дҪӣпјҢвҖңз•ҘиҜҶжұүеӯ—пјҢдәҰе–ңд№ жұүиҜӯвҖқпјҢ马й№ӨеӨ©еҒҡе®ўж—¶пјҢеҸ‘зҺ°жҙ»дҪӣдҪҸеӨ„жңүи®ёеӨҡжұү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зҡ„з—•иҝ№пјҢжЎҲдёҠж”ҫзҪ®зқҖеӣҪж–Үж•ҷ科д№ҰпјҢеўҷеЈҒдёҠиҙҙжңүеҶ…ең°еҸҚжҳ еҝ гҖҒеӯқзӯүдј з»ҹи§Ӯеҝөзҡ„дәәзү©еҪ©з”»пјҢжҲ–зҗҙжЈӢд№Ұз”»гҖҒеұұж°ҙиҠұйёҹзӯүгҖӮдҪҚдәҺй»‘й”ҷпјҲд»Ҡз”ҳиӮғзңҒз”ҳеҚ—и—Ҹж—ҸиҮӘжІ»е·һеҗҲдҪңеёӮпјүзҡ„й”Ғи—ҸдҪӣе…„й•ҝпјҢеӣ дёәз»ҸеёёеӨ–еҮәжёёеҺҶпјҢ并вҖңжӣҫиҘҝиҮіж–°з–ҶпјҢж•…иғҪдҪңжұүиҜӯвҖқгҖӮжҷ®йҖҡзҡ„и—Ҹж—Ҹж°‘дј—иғҪйҖҡжұүиҜӯзҡ„д№ҹдёҚе°‘пјҢеңЁиҘҝе®ҒпјҢ马жӯҘиҠіжҙҫз»ҷжһ—й№Ҹдҫ жёёжө·еҝғеұұзҡ„еҗ‘еҜјжқҺеҚҺпјҢжң¬жҳҜи—Ҹж—ҸдәәпјҢдҪҶвҖңзІҫжұүиҜӯпјҢдёәдәәжһҒеҝ е®һпјҢеҮЎжёёз•Әең°иҖ…пјҢеӨҡд»Ҙдёәд№ЎеҜјвҖқ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еңЁз”ҳйқ’ең°еҢәиҖғеҜҹж—¶пјҢзү№еҲ«з•ҷж„ҸеҜ№ж°‘ж—Ҹе…ізі»зҡ„дәҶи§ЈпјҢеңЁгҖҠиҘҝеҢ—иҖғеҜҹж—Ҙи®°гҖӢдёӯи®°еҪ•дәҶдёҚе°‘и—Ҹж°‘йҖҡжұүиҜӯзҡ„дҫӢеӯҗгҖӮд»ҺдёҙжҪӯеҲ°еҗҲдҪңзҡ„йҖ”дёӯпјҢйҒҮеҲ°дёҖдҪҚи—Ҹж°‘пјҢеҸҢж–№вҖңд»ҘжұүиҜӯзӣёй…¬зӯ”пјӣж—ўиҖҢиҮӘйҷҲдёәз•Әж°‘пјҢжӣҫиҜөгҖҠдёүеӯ—з»ҸгҖӢеҸҠгҖҠеӣӣд№ҰгҖӢпјҢеҲҷз•Әж°‘д№Ӣеұ…иҝ‘жұүең°иҖ…пјҢж•…йқһжңүдёҚиҜ»жұүд№Ұд№ӢжҲҗи§Ғд№ҹвҖқгҖӮеҲ°иҫҫжӢүеҚңжҘһд№ӢеҗҺпјҢжӣҫдәҺвҖңйҘӯеҗҺиҮідёҖз•ӘеҘіе®¶и®ҝй—®пјҢжӯӨеҘіеүҚжӣҫдёәеҰ“пјҢиғҪж“ҚжұүиҜӯпјҢд»Ҡе«ҒдёҖе•ҶдәәвҖқгҖӮеңЁеӨҸжІіеҺҝж—¶пјҢеҺҝеәңжҙҫдёҖеҗҚеҸ«зҷҪз‘ңзҡ„жҠӨе…өдёәйЎҫж°ҸдёҖиЎҢжңҚеҠЎпјҢе…јдҪңжң¬ең°еҜјжёёпјҢзҷҪз‘ңдёәвҖңз•ӘзұҚиҖҢиғҪжұүиҜӯпјҢдәҰз•ҘиҜҶеӯ—вҖқгҖӮйҷӨдәҶдёӘдҪ“д»ҘеӨ–пјҢд№ҹжңүжҹҗдёҖзү№е®ҡеҢәеҹҹ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дёҺжұүж°‘зҙ§йӮ»иҖҢеӨ„жҲ–ж··жқӮеұ…дҪҸпјҢзӣёдә’д№Ӣй—ҙй•ҝжңҹдәӨеҫҖпјҢеҸ—жұүж–ҮеҢ–зҡ„жөёжҹ“жӣҙж·ұпјҢе·Із»ҸеҸӘиғҪиҜҙжұүиҜӯпјҢеҸҚиҖҢдёҚйҖҡи—ҸиҜӯгҖӮеҰӮ马й№ӨеӨ©еңЁд»Һж№ҹжәҗиөҙжӢүеҚңжҘһйҖ”дёӯпјҢз»ҸиҝҮиҚҜж°ҙд№ЎпјҲд»ҠиҘҝе®ҒеёӮж№ҹдёӯеҢәиҚҜж°ҙж»©пјүпјҢжӯӨең°и·қзҰ»иҘҝе®ҒдёҚиҝңпјҢеҸҲжңүе……жІӣзҡ„ең°зғӯиө„жәҗпјҢйҖӮеҗҲеҶңиҖ•пјҢжүҖд»ҘжҳҜжұүж—ҸеҶңж°‘иҫғж—©иҝӣе…Ҙ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Ҫ“ең°и—Ҹж°‘еҸ—жұү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иҫғд№…пјҢвҖңеұ…ж°‘жңүи—Ҹж—ҸдёүеҚҒдҪҷжҲ·пјҢдҝұжұүеҢ–дёҚйҖҡи—ҸиҜӯзҹЈгҖӮеҶңзү§дёҡе…јиҗҘвҖқгҖӮиҮідәҺиҝҷдёҖең°еҢәзү№жңүзҡ„еңҹж—ҸгҖҒж’’жӢүж—ҸгҖҒдҝқе®үж—ҸгҖҒдёңд№Ўж—Ҹзӯүж—Ҹзҡ„иҜӯиЁҖпјҢжң¬жқҘе°ұжҳҜеңЁжұүгҖҒ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гҖҒзӘҒеҺҘзӯүеӨҡж°‘ж—ҸиҜӯиЁҖдёҚж–ӯдәӨжөҒгҖҒ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иҝҮзЁӢдёӯеҪўжҲҗзҡ„гҖӮеҪ“然д№ҹжңүжұүж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иў«и—Ҹж—ҸйҖҗжёҗеҗҢеҢ–пјҢйҖҡи—Ҹж–ҮгҖҒиҜҙи—ҸиҜӯзҡ„дҫӢеӯҗгҖӮд»ҠжІіеҚ—и’ҷеҸӨж—ҸиҮӘжІ»еҺҝең°еӨ„з”ҳиӮғгҖҒйқ’жө·гҖҒеӣӣе·қдёүзңҒдәӨз•ҢпјҢеҪ“ең°и’ҷеҸӨж—Ҹдё»иҰҒжҳҜиҘҝи’ҷеҸӨеҺ„дҫҝзү№йғЁзҡ„е’ҢзЎ•зү№гҖҒеңҹе°”жүҲзү№дёӨйғЁеҸҠжј еҚ—и’ҷеҸӨеңҹй»ҳзү№йғЁзҡ„иҫҫе°”еҗҫгҖҒзҒ«иҗҪиөӨдёӨйғЁзҡ„еҗҺд»ЈпјҢе‘Ёиҫ№з”ҹжҙ»зҡ„йғҪжҳҜи—Ҹж—ҸгҖӮиҝӣе…ҘжІіеҚ—ең°еҢәеҗҺпјҢи’ҷеҸӨж—ҸдёҠеұӮиҙөж—ҸеҸ—и—Ҹж–ҮеҢ–еҪұе“ҚпјҢдҝЎеҘү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ж јйІҒжҙҫпјҢйҖүжҙҫеӯҗејҹиҝӣе…ҘеҜәйҷўдёәеғ§пјҢеӯҰд№ и—ҸиҜӯи—Ҹж–ҮпјҢдёҺи—Ҹж—ҸйҖҡе©ҡгҖӮй•ҝжңҹзҡ„жҪң移й»ҳеҢ–пјҢдҪҝеҫ—иҮӘдәІзҺӢд»ҘдёӢпјҢжҷ®йҒҚдҪҝз”Ёи—Ҹж–Үи—ҸиҜӯпјҢз”ҡиҮіеҸӘз”Ёи—Ҹж–Үи—ҸиҜӯгҖӮеҰӮ马й№ӨеӨ©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йқ’жө·дёҖйғЁеҲҶи’ҷдәәпјҢеҸҚдёәи—ҸдәәжүҖеҗҢеҢ–пјҢзҹҘи—ҸиҜӯиҖҢдёҚзҹҘи’ҷиҜӯгҖӮвҖқеҰӮ第д№қд»ЈжІіеҚ—дәІзҺӢпјҢвҖң其家еұӢеҲҷдёәи—ҸејҸпјҢй—»е…¶дәәдәҰиҜҙи—ҸиҜӯвҖқпјҢе…¶е®һдәІзҺӢд№ҹд№ жұүж–ҮгҖҒдјҡжұүиҜӯпјҢж—¶иҖҢжұүжңҚжұүиҜӯпјҢж—¶иҖҢе–ҮеҳӣжңҚи—ҸиҜӯгҖӮ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дҪңдёә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жңҖи‘—еҗҚзҡ„еҜәйҷўд№ӢдёҖпјҢеҜәеҶ…е–ҮеҳӣжқҘжәҗзӣёеҪ“еӨҚжқӮпјҢд»Һең°еҹҹдёҠзңӢпјҢйҷӨз”ҳиӮғгҖҒйқ’жө·гҖҒиҘҝеә·еӨ–пјҢе°ҡжңүжқҘиҮӘж–°з–ҶгҖҒеҶ…и’ҷеҸӨгҖҒдёңеҢ—дёүзңҒзӯүең°иҖ…пјҢж°‘ж—ҸйҷӨ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д№ӢеӨ–пјҢиҝҳжңүжұүж°‘е–Үеҳӣ50еӨҡдәәпјҢд»ҘжӢ…д»»жӢүеҚңжҘһдҝқе®үеҸёд»ӨйғЁеҶӣжі•еӨ„й•ҝзҡ„жқЁзңҹеҰӮе–ҮеҳӣжңҖе…·д»ЈиЎЁжҖ§пјҢжқЁе–ҮеҳӣвҖңдёәжІіе·һжұүдәәпјҢе№ҙе…ӯеҚҒдҪҷпјҢд№…еңЁеҜәеҸёжӢӣеҫ…иҖ…д№ҹвҖқпјҢе…ҘжӢүеҚңжҘһдёәеғ§е·Із»Ҹ40еӨҡе№ҙ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дёҖиЎҢеңЁеҚ“е°јзӣҳжЎ“ж—Ҙд№…пјҢдёҺеҚ“е°јзҰ…е®ҡеҜәе®Ӣе ӘеёғдәӨеҫҖз”ҡеӨҡпјҢжҚ®йЎҫж°Ҹи®°иҪҪпјҢе Әеёғжң¬дёәвҖңжұүдәәпјҢе®Ӣ姓пјҢд»Ҡе№ҙе…ӯеҚҒд№қпјҢдёҚз”ҡиҜҶжұүеӯ—иҖҢзІҫз ”и—Ҹж–ҮпјҢиҮӘе№јзҡҲдҫқе–Үеҳӣж•ҷпјҢжёёеӯҰиҘҝи—ҸпјҢеҪ’дё»йҳҺ家еҜәпјӣйў‘е№ҙеҲ°жұҹгҖҒжөҷгҖҒе№ігҖҒжҙҘиҜёең°иҖғеҜҹпјҢеҺ»е№ҙеҚ“е°јжқЁеңҹеҸёз§ҜеәҶиў«жқҖпјҢзҰ…е®ҡеҜәж— дё»пјҢд»Ҙе Әеёғеҫ·жңӣй«ҳпјҢиҝҺдёәдҪҸжҢҒвҖқгҖӮд№ҹжңүжұүж—Ҹй«ҳзә§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еӯҰд№ и—Ҹж–ҮпјҢз ”з©¶дҪӣеӯҰзҡ„гҖӮйӮ“йҡҶпјҲ1884вҖ”1938е№ҙпјүпјҢз”ҳиӮғжІіе·һпјҲд»ҠдёҙеӨҸпјүдәәпјҢеӯ—еҫ·иҲҶпјҢеҸ·зҺүе ӮпјҢдәҰеҸ·зқ«е·ўеӯҗгҖҒзқ«е·ўеұ…еЈ«гҖӮжё…е…үз»ӘдёүеҚҒе№ҙпјҲ1904е№ҙпјүиҝӣеЈ«пјҢе…Ҙж°‘еӣҪеҗҺеҠ е…ҘеӣҪж°‘е…ҡпјҢд»»з”ҳиӮғзңҒи®®дјҡи®®е‘ҳпјҢеҺҶе®ҳ银еҸ·еқҗеҠһгҖҒзҰҒзғҹеұҖеұҖй•ҝгҖҒйҖ еёҒеҺӮзӣ‘зқЈгҖҒжҰ·иҝҗеұҖеұҖй•ҝзӯүпјҢеҗҺеұ…е®¶й’»з ”дҪӣз»ҸпјҢиҮҙеҠӣе®—ж•ҷпјҢд»»з”ҳиӮғдҪӣж•ҷдјҡдјҡй•ҝгҖӮвҖңйҖҡи—Ҹж–ҮпјҢз ”дҪӣеӯҰпјҢи‘—жңүгҖҠеҜҶи—Ҹй—®жҙҘ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еҜҶе®—еӣӣдёҠеёҲдј гҖӢгҖҒгҖҠз•ӘдҪӣеҗҚд№үйӣҶгҖӢгҖҒгҖҠж–Үеӯ—иҲ¬иӢҘйӣҶгҖӢгҖҒгҖҠи—Ҹж–ҮжіЁи§ЈгҖӢеҸҠиҜ—ж–ҮйӣҶгҖҒиҖғеҸӨеҪ•зӯүд№ҰгҖӮвҖқйЎҫйўүеҲҡеҲ°е…°е·һеҗҺпјҢзү№еҲ«з•ҷж„ҸеҜ№йҷҮеҸіж–ҮзҢ®зҡ„жҗңжұӮпјҢзҹҘйӮ“йҡҶдёәйҷҮеҸіж–ҮзҢ®дёүеӨ§е®¶д№ӢдёҖпјҲеҸҰдёӨдәәдёәж…•еҜҝзҘәгҖҒеј з»ҙпјүпјҢйҖӮйҖўйӮ“йҡҶйҖқдё–пјҢеҚҙжңӘиғҪи®ҝеҫ—е…¶йҒ—и‘—пјҢзҰ»ејҖе…°е·һд№Ӣйҷ…пјҢд»Қ然引д»ҘдёәжҒЁдәӢгҖӮеӣӣгҖҒ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жҳҜдҝғиҝӣж°‘ж—ҸиһҚеҗҲзҡ„йҮҚиҰҒдёҫжҺӘ иҝӣе…Ҙ20дё–зәӘд»ҘеҗҺпјҢ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еҜ№еҗҜеҸ‘ж°‘жҷәгҖҒдҝғиҝӣзӨҫдјҡиҝӣжӯҘзҡ„дҪңз”Ёж—ҘзӣҠеҮёжҳҫпјҢи¶ҠжқҘи¶ҠеҸ—еҲ°еӣҪдәә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иҖҢиҖғеҜҹиҘҝеҢ—зҡ„е®ҳе‘ҳгҖҒеӯҰиҖ…们д№ҹйғҪйқһеёёжіЁйҮҚиҖғеҜҹж•ҷиӮІзҠ¶еҶөпјҢж„ҹеҸ№з—ӣжғңиҘҝеҢ—ж•ҷиӮІзҡ„иҗҪеҗҺпјҢиҺ«дёҚд»Ҙе…ҙеҠһж•ҷиӮІдёәж”№йҖ иҘҝеҢ—гҖҒејҖеҸ‘иҘҝеҢ—д№ӢйҰ–еҠЎгҖӮйҷҲдёҮйҮҢиҘҝиЎҢж•Ұз…ҢпјҢйҖ”з»Ҹз”ҳиӮғеҸӨжөӘи—Ҹж°‘иҒҡеұ…еҢәйҫҷжІҹе ЎпјҢвҖңи§ҒдёҖз•ӘеҰҮпјҢзәҰеӣӣеҚҒдҪҷпјҢжҗәдёҖеӯҗеҚҒдәҢеІҒпјҢжқҘе Ўд»ҘжүҖеҲ¶зүӣжІ№жҳ“з –иҢ¶пјҢе…¶еӯҗиІҢйўҮиҒӘйў–пјҢжғңж— дәәжҸҗеҖЎз•Әж°‘ж•ҷиӮІпјҢдёҖд»»е…¶иҮӘз”ҹиҮӘзҒӯпјҢи§ҶеҗҢеҢ–еӨ–пјҢдёәеҸҜжӮІиҖівҖқгҖӮ马й№ӨеӨ©жӣҫд»»з”ҳиӮғзңҒж•ҷиӮІеҺ…еҺ…й•ҝгҖҒе…°е·һдёӯеұұеӨ§еӯҰпјҲе…°е·һеӨ§еӯҰеүҚиә«пјүж Ўй•ҝзӯүпјҢзү№еҲ«йҮҚи§Ҷж•ҷиӮІе°Өе…¶жҳҜ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пјҢи®Өдёәж•ҷиӮІжҳҜиһҚжҙҪ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„ҹжғ…гҖҒж¶ҲйҷӨж°‘ж—ҸзҹӣзӣҫдёҺеҶІзӘҒзҡ„жңҖжңүж•ҲйҖ”еҫ„гҖӮж•…е…¶жһҒеҠӣдё»еј вҖңеӣһж•ҷдәәеӨҡе…ҘеӯҰж ЎвҖқпјҢе°Ҷжё…зңҹеӯҰж ЎдёҖеҫӢж”№еҗҚпјҢжӢӣ收жұүз”ҹпјҢ并е…ҘжұүдәәеӯҰж ЎпјҢд»Ҙжңҹ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ж¶ҲйҷӨж„Ҹи§ҒпјҢиһҚеҗҲж„ҹжғ…пјҢз»ҹдёҖжҖқжғіпјҢжіҜзҒӯз•Ңйҷҗ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дёҖиЎҢзҡ„зӣ®зҡ„жҳҜдёәдёӯиӢұеәҡж¬ҫиЎҘеҠ©иҘҝеҢ—ж•ҷиӮІеҒҡи°ғжҹҘеҸҠзј–и®ўи®ЎеҲ’пјҢз»ҸиҝҮж·ұе…Ҙи°ғз ”пјҢд»–еңЁеҶҷз»ҷжҖ»е№ІдәӢжқӯз«ӢжӯҰзҡ„дҝЎдёӯејәи°ғпјҡвҖңеӣһж°‘ж•ҷиӮІд№ӢжҸҗеҖЎпјҢе®һдёәи§ЈеҶіиҘҝеҢ—й—®йўҳдёӯд№Ӣж №жң¬й—®йўҳгҖӮвҖқвҖңйҷӨж—ҘиҜҫйҳҝж–Үз»Ҹе…ёеӨ–пјҢеҺҹеҸҜж–Ҫд»ҘдёҺжұүдәәеҗҢж ·д№Ӣж•ҷиӮІгҖӮвҖқеҜ№дәҺ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°‘пјҢвҖңйҷӨж•ҷд»Ҙе•ҶдёҡжҠҖжңҜдёҺйҒ“еҫ·еӨ–пјҢжӣҙеҪ“жҺҲдёүж°‘дё»д№үпјҢи’ҷгҖҒи—ҸиҜӯж–ҮпјҢеӣҪйҷ…еҪўеҠҝпјҢж°‘дј—ж•ҷиӮІпјҢеҚ«з”ҹж•ҷиӮІзӯүиҜҫпјҢдҪҝд№Ӣе…·жңүеӣҪ家и§ӮеҝөпјҢеӣўз»“ж„ҸиҜҶвҖқпјҢвҖ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з•Әдёүж–№иҮӘиғҪд»Ҙж•ҷиӮІзӣёеҗҢиҖҢжҖқжғіеҗҢпјҢеӣ жҖқжғіеҗҢиҖҢжғ…ж„ҹдә’йҖҡпјҢеӣ жғ…ж„ҹдә’йҖҡиҖҢеӣўз»“дёәдёҖдҪ“вҖқгҖӮж°‘еӣҪд»ҘжқҘпјҢз”ҳйқ’ең°еҢәејҖе§ӢдәҶз”ұдј з»ҹж•ҷиӮІеҗ‘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зҡ„иү°йҡҫиҪ¬еһӢпјҢ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пјҢиҷҪ然д»ҚжңүдёҚе°‘д№Ўжқ‘еЎҫеёҲд»ҘгҖҠдёүеӯ—з»ҸгҖӢгҖҠзҷҫ家姓гҖӢгҖҠеҚғеӯ—ж–ҮгҖӢеҸҠгҖҠеӣӣд№ҰгҖӢгҖҠдә”з»ҸгҖӢзӯүж•ҷжҺҲз”ҹеҫ’гҖӮдҪҶ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е·Із»Ҹиө·жӯҘпјҢ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зҡ„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д№ҹе‘ҠејҖз«ҜгҖӮеӣһж—ҸдёҺеҶ…ең°жұүж—ҸиҒ”зі»дёҺдәӨеҫҖжңҖдёәеҜҶеҲҮпјҢеӣһж—ҸдёҠеұӮеҰӮеҶӣж”ҝдё»е®ҳеҸҠеҗ„ең°ж•ҷдё»пјҢдёҚе°‘дәәеҸ—еҶ…ең°ж–ҮеҢ–дёҺж•ҷиӮІеҪұе“ҚиҫғеӨ§пјҢйҮҚи§Ҷж•ҷиӮІдәӢдёҡпјҢ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ејҖе§Ӣж—©пјҢд№ҹзӣёеҜ№е®Ңе–„гҖӮеңЁйқ’жө·иҘҝе®ҒпјҢе…ҲеүҚз”ұ马йә’жҚҗиө„еҚғе…ғдёәеӣһж°‘еӯҗејҹеҲӣеҠһзҡ„жё…зңҹеӯҰж ЎпјҢеӣ 马й№ӨеӨ©гҖҒжһ—з«һгҖҒй»Һдё№зӯүдәәеқҮдё»еј еӣһжұүж•ҷиӮІдёҖдҪ“пјҢдёҚеҝ…зӢ¬з«Ӣи®ҫзҪ®еӣһж°‘еӯҰж ЎпјҢйҒҝе…ҚеҠ ж·ұж°‘ж—ҸзҹӣзӣҫпјҢеӣ жӯӨж”№еҗҚдёәеҗҢд»ҒеӯҰж ЎпјҢеӣһж°‘д№ӢеӨ–пјҢ兼收жұүдәәеӯҗејҹе…ҘеӯҰпјҢ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дёӯеҸ¶пјҢжңүеҲқе°ҸеӣӣзҸӯпјҢй«ҳе°ҸдёӨзҸӯпјҢе…ұ160дҪҷеҗҚеӯҰз”ҹпјҢвҖңзҺ°жұүз”ҹеҚ е…ЁдҪ“еӯҰз”ҹеӣӣеҲҶд№ӢдёҖвҖқгҖӮеӣһж•ҷдҝғиҝӣдјҡйҷ„и®ҫзҡ„иҘҝе®ҒдёӯеӯҰж ЎпјҢеҲҶеӣӣзә§е…ұ185еҗҚеӯҰз”ҹ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иЎҘд№ зҸӯ20еҗҚеӯҰз”ҹпјҢе…¶дёӯ150дәәеҜ„е®ҝгҖӮиҜҫзЁӢжңүеӣҪж–ҮпјҢжңүз®—еӯҰпјҢдҫҜйёҝйүҙи§ҶеҜҹеҪ“еӨ©пјҢдёҖе№ҙзә§еӣҪж–ҮйҖүжҺҲзҡ„жҳҜжқҺз…ңгҖҠиҷһзҫҺдәәгҖӢпјҢдёүе№ҙзә§еӣҪж–ҮйҖүжҺҲзҡ„жҳҜе…ЁзҘ–жңӣгҖҠжў…иҠұеІӯи®°гҖӢпјҢзЁӢеәҰйғҪдёҚз®—дҪҺгҖӮеҲӣз«ӢдәҺ1928е№ҙзҡ„д№җйғҪдёӯеӯҰпјҢеҲҶеҲқдёӯгҖҒе°ҸеӯҰдәҢйғЁпјҢвҖңиҜҫжң¬еӨ§жҠөйҮҮз”ЁдёӯеҚҺд№ҰеұҖж–°ж ҮеҮҶиҜҫжң¬вҖқгҖӮиҖҢз”ұеҪ“ең°еӣһж•ҷдҝғиҝӣдјҡйҷ„и®ҫдёӨзә§е°ҸеӯҰпјҢеҲҶдёәдә”зҸӯпјҢй«ҳзә§дёҖзҸӯпјҢеҲқзә§еӣӣзҸӯпјҢвҖңиҜҫзЁӢжҜҸж—Ҙеҝ…жңүдёҖй’ҹзӮ№еӣһж–ҮпјҢдҪҷдәҰз”ЁдёӯеҚҺд№ҰеұҖж–°ж ҮеҮҶиҜҫжң¬вҖқгҖӮжңүеӣҪж–ҮиҜҫпјҢеӯҰз”ҹиҜҫжЎҢдёҠиҝҳжңүеҺҶеҸІгҖҒең°зҗҶзӯүиҜҫжң¬гҖӮз”ҳиӮғдёҙеӨҸдёәеӣһж°‘иҒҡеұ…еҢәпјҢд№ҹжҳҜз”ҳйқ’е®ҒиҜёй©¬зҡ„家乡пјҢ马зҰҸзҘҘпјҲеӯ—дә‘дәӯпјүеҲӣеҠһдәҶдә‘дәӯе°ҸеӯҰпјҢ并еңЁеҗ„д№Ўй•Үи®ҫз«ӢеҲҶж Ўе…ӯеӨ„гҖӮйҹ©е®¶йӣҶеҲҶж Ўдёә马зҰҸзҘҘд№Ӣеӯҗ马йёҝйҖөжүҖеҠһпјҢж•…еҗҚз§Ғз«ӢйёҝйҖөе°ҸеӯҰж ЎпјҢвҖңжңүж–°е»әеұӢеҚҒдҪҷй—ҙпјҢеӯҰз”ҹе…«еҚҒдҪҷдәәпјҢеҲқе°Ҹеӣӣе№ҙзә§пјҢеҲҶдәҢзҸӯж•ҷжҺҲпјҢж•ҷе®ӨдәҢпјҢе°ҡзі»ж–°ејҸпјҢж•ҷе‘ҳеӣӣдәәпјҢдәҢдәәдёәеұұдёңдәәвҖқпјҢвҖңжҲҗз«Ӣд»…ж•°е№ҙпјҢеӯҰз”ҹеӣһгҖҒжұүеӯҗејҹеқҮжңүгҖӮжҜҸе‘ЁйҷӨйҳҝж–ҮдәҢиҠӮпјҲжҜҸиҠӮеҚҠе°Ҹж—¶пјүеӨ–пјҢе…¶дҪҷеӯҰ科пјҢеқҮжҢүж•ҷйғЁе®ҡз« пјҢз”Ёж–°ж•ҷ科д№ҰвҖқгҖӮдә‘дәӯе°ҸеӯҰе…¶д»–еҲҶж Ўзҡ„жғ…еҪўеә”иҜҘеӨ§иҮҙзӣёеҪ“гҖӮдёҙжҪӯиҘҝйҒ“е ӮеҲӣз«ӢиҖ…马еҗҜиҘҝпјҢжӣҫд»ҺиҙЎз”ҹиҢғз»іжӯҰеӯҰд№ е„’е®¶з»Ҹ典并иҖғдёӯз§ҖжүҚпјҢж·ұеҸ—儒家еӯҰиҜҙзҶҸйҷ¶пјҢиҮӘеҲӣиҘҝйҒ“е ӮпјҢд»ҘеҲҳжҷәзӯүдәәзҝ»иҜ‘зҡ„жұүж–Ү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з»Ҹе…ёдј ж•ҷпјҢжҸҙе„’е…ҘеӣһпјҢе…¶жүҖдҪңжҘ№иҒ”жңүпјҡвҖңиҜ»д№Ұеҫ—еҰҷж„ҸпјҢзҗҶдјҡеӨ©з»ҸдёүеҚҒйғЁпјӣе…»ж°”йҖҡзҘһжҳҺпјҢйҒ“з»ҹеҸӨеңЈеҚғзҷҫе№ҙгҖӮвҖқвҖңеұ…е№ҝеұ…пјҢз”ұжӯЈи·ҜпјҢж–№еҫ—дҝқе’Ңе…ғж°”пјӣеҸӢиүҜеҸӢпјҢдәІеҗҚеёҲпјҢдёҚе•»е·ҰеҸіжҳҘйЈҺгҖӮвҖқеҸ—е…¶еҪұе“ҚпјҢиҘҝйҒ“е ӮеҮәиө„еҲӣеҠһдёӯе°ҸеӯҰпјҢйј“еҠұйҒ“е ӮеҶ…е’ҢеҪ“ең°еҗ„ж—Ҹз”·еҘіе„ҝз«Ҙе…ҘеӯҰпјҢ并йҖүжӢ”жҲҗз»©еҘҪзҡ„йқ’е№ҙдёҠеӨ§еӯҰгҖӮеә·д№җи®ҫжІ»еұҖж•ҷе Ӯ第еҚҒдёүд»Јж•ҷ主马延еҜҝж–ҮеҢ–ж°ҙе№ій«ҳпјҢе…јзІҫйҳҝгҖҒжұүж–ҮпјҢжӣҫе°ҶйҳҝжӢүдјҜж–ҮдјҠж–Ҝе…°з»Ҹе…ёиҜ‘дёәжұүж–ҮпјҢ并жңүж”№иҜөжұүж–Үз»Ҹе…ёзҡ„жҸҗи®®пјҢеҪ“ең°еӣһжұүе…ізі»д№ҹзӣёеҜ№иһҚжҙҪгҖӮеңЁд»–зҡ„еҖЎи®®дёҺдё»жҢҒдёӢпјҢеә·д№җе…ҙеҠһеӣһж°‘е°ҸеӯҰпјҢвҖңиҜ»жұүж–Үе…јиҜ»йҳҝж–Үпјӣжғҹд»Ҙеӣһж°‘еҗ‘дёҚиҝӣжұүж ЎпјҢж— еҗҲдәҺдҪңе°ҸеӯҰж•ҷе‘ҳд№Ӣиө„ж јиҖ…пјҢж•…е…¶ж Ўй•ҝж•ҷе‘ҳзҡҶз”ұе®ҒеӨҸиҒҳиҜ·иҖҢжқҘвҖқгҖӮдҪҶз”ұдәҺе®—ж•ҷеӣ зҙ пјҢд»Қ然жңүдёҚе°‘еӣһж°‘еӯҰж ЎпјҢдё»иҰҒеӯҰд№ йҳҝжӢүдјҜиҜӯдёҺдјҠж–Ҝе…°ж•ҷз»Ҹе…ёпјҢжүҖд»ҘйЎҫйўүеҲҡеңЁиҘҝе®ҒеҸӮи§ӮдәҶйҳҝж–ҮдёӯеӯҰеҸҠйҳҝж–ҮеҘіеӯҗе°ҸеӯҰгҖҒеҸ¶ж°Ҹйҳҝж–Үз§ҒеЎҫзӯүд№ӢеҗҺпјҢдёҚз”ұж…ЁеҸ№пјҡвҖңиҘҝе®Ғйҳҝж–ҮеӯҰж Ўз”ҡеӨҡпјҢз”·еҘіз”ҹ并众пјҢжғҹеҸӘеҝөз»ҸпјҢдёҚиҜ»д№ҰпјҢдёҺзҺ°д»Јз”ҹжҙ»еӨӘж— е…ізі»гҖӮвҖқзӣёеҜ№дәҺеӣһж—Ҹж•ҷиӮІпјҢ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зҡ„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зӯү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жӣҙдёәиҗҪеҗҺпјҢжӣҫй•ҝжңҹжӢ…д»»з”ҳиӮғж•ҷиӮІеҺ…еҺ…й•ҝзҡ„ж°ҙжў“жӣҫеҜ№йҷҲиө“йӣ…и°ҲеҸҠз”ҳиӮғ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зҡ„зҺ°зҠ¶еҸҠе…¶еҜ№зӯ–пјҡвҖңз”ҳзңҒж°‘ж—ҸеӨҚжқӮпјҢдәәж°‘еҗ‘жқҘдёҚйҮҚиҜ»д№ҰгҖӮж°‘е…ғд»ҘеүҚпјҢеӣһи—ҸдёӨж—ҸеҗҢиғһпјҢжӣҙз»қдёҚдҪҝеӯҗејҹе…ҘеӯҰгҖӮиҝ‘е№ҙеӣһж•ҷйўҶиў–пјҢе·ІзҹҘжҸҗеҖЎж•ҷиӮІпјҢиҖҢи—Ҹж°‘д№ӢзҹҘиҜ»д№ҰиҖ…пјҢд»ҚеұһеҜҘеҜҘгҖӮвҖқвҖңж•…жң¬зңҒеҜ№дәҺеӣһгҖҒи—Ҹж•ҷиӮІпјҢд»Ҡе·Ізү№еҲ«жіЁи§ҶпјҢе№ёеӣһгҖҒи—ҸйўҶиў–пјҢдәҰжһҒеҠӣиөһжҲҗпјҢжҲ–еҸҰи®ҫеӣһгҖҒи—ҸеӯҰж ЎпјҢжҲ–дәҺеҗ„ж Ўйҷ„и®ҫзү№еҲ«зҸӯеқҮеҸҜгҖӮвҖқ1930е№ҙеүҚеҗҺпјҢйқўдёҙдёҘеі»зҡ„иҫ№з–ҶдёҺж°‘ж—Ҹй—®йўҳпјҢ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йҮҮеҸ–дәҶдёҖзі»еҲ—е·©еӣәиҫ№з–ҶгҖҒеҠ ејәж°‘ж—Ҹеӣўз»“зҡ„жҺӘж–ҪпјҢеҰӮж”№з»„еҺҹи’ҷи—Ҹйҷўдёәи’ҷи—Ҹ委е‘ҳдјҡпјҢе…ҲжҳҜзӣҙеұһдәҺ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пјҢеҗҺж”№йҡ¶иЎҢж”ҝйҷўпјҢдҪңдёәжү§жҺҢи’ҷеҸӨиҘҝи—Ҹзӯүиҫ№з–Ҷж°‘ж—ҸдәӢеҠЎзҡ„жңҖй«ҳиЎҢж”ҝжңәжһ„гҖӮеҮәзүҲгҖҠи’ҷи—Ҹ委е‘ҳдјҡе…¬жҠҘгҖӢпјҢеҲ¶е®ҡгҖҠи’ҷи—Ҹ委е‘ҳдјҡ法规жұҮзј–гҖӢпјҢдёҫеҠһи’ҷи—Ҹж”ҝжІ»и®ӯз»ғзҸӯеҹ№е…»и’ҷеҸӨиҘҝи—Ҹе№ІйғЁпјҢ并з”ұж•ҷиӮІйғЁеҸ‘еёғжҢҮд»ӨпјҢеңЁи’ҷеҸӨж—ҸгҖҒи—Ҹж—ҸиҒҡеұ…ең°еҢәпјҢеҗ„дёӯзӯүеӯҰж ЎйғҪиҰҒеўһеҠ 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–ҮиҜҫзЁӢпјҢеҠ ејә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гҖӮж°ҙжў“дёҺйҷҲиө“йӣ…зҡ„и°ҲиҜқпјҢе°ұжҳҜ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еұ•ејҖзҡ„гҖӮж №жҚ®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ж•ҷиӮІйғЁзҡ„жҢҮзӨәпјҢз”ҳиӮғзңҒж•ҷиӮІеҺ…йҖҡд»Өж°‘ж—Ҹең°еҢәеҗ„еҺҝеҗ„дёӯзӯүеӯҰж ЎйғҪиҰҒеўһеҠ и’ҷеҸӨиҜӯгҖҒи—ҸиҜӯж–ҮиҜҫзЁӢпјҢ并дәҺ第дә”дёӯеӯҰдёҫеҠһдәҶвҖңи’ҷи—Ҹзү№еҲ«зҸӯвҖқпјҢвҖңд»ҘеҖҹж•ҷиӮІдёәејҖеҸ‘иҘҝеҢ—гҖҒдҝғиҝӣж–ҮеҢ–д№ӢйҖ”еҫ„вҖқгҖӮиҝҳеҮҶеӨҮвҖңеңЁеӣһж°‘иҫғеӨҡзҡ„зҡӢе…°гҖҒдёҙеӨҸгҖҒе®Ғе®ҡгҖҒеҢ–е№ігҖҒжө·еҺҹгҖҒеӣәеҺҹгҖҒжё…ж°ҙзӯүеҺҝеҗ„и®ҫеӣһж°‘е°ҸеӯҰдёҖжүҖпјҢеңЁи—Ҹж°‘иҫғеӨҡд№ӢеӨҸжІігҖҒеІ·еҺҝгҖҒдёҙжҪӯзӯүеҺҝпјҢеҗ„и®ҫи—Ҹж°‘е°ҸеӯҰдёҖжүҖвҖқпјҢзҡӢе…°гҖҒдёҙеӨҸгҖҒе®Ғе®ҡгҖҒеӨҸжІігҖҒеІ·еҺҝгҖҒдёҙжҪӯиҜёеҺҝеқҮеӨ„дәҺ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д№ӢеҶ…гҖӮ1927е№ҙпјҢйқ’жө·еңЁеҺҹе®Ғжө·и’ҷз•ӘеёҲиҢғеӯҰж ЎеҹәзЎҖдёҠж”№и®ҫдәҶе®Ғжө·зӯ№иҫ№еӯҰж ЎпјҢеҲҶи®ҫдёӯеӯҰе’ҢеёҲиҢғдёӨйғЁпјҢеҸҲйҷ„и®ҫиҒҢдёҡеӯҰж ЎпјҢйҷӨ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规е®ҡзҡ„иҜҫзЁӢеӨ–пјҢиҝҳж•ҷжҺҲиҫ№дәӢгҖҒи—Ҹж–ҮзӯүиҜҫзЁӢпјҢиЎЈгҖҒйЈҹгҖҒе®ҝе…ЁйғЁе…¬иҙ№гҖӮдҪҶж Ўй•ҝжңұз»ЈеқҰиЁҖеӯҰж ЎжӢӣз”ҹжһҒе…¶еӣ°йҡҫпјҢйқ’жө·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зҺӢе…¬гҖҒеҚғжҲ·дёҚж„ҝи®©еӯҗејҹе…ҘеӯҰпјҡвҖңи§үжӮҹдёҚжҳ“пјҢеӣ ж•°е№ҙеүҚпјҢжӣҫејәд»Өе…¶жҜҸйғЁйҖҒеӯҗејҹдёҖдәҢдәәиҮіиҘҝе®Ғе…ҘеӯҰж ЎпјҢдёҚж„Ҹеҗ„дёҚиӮҜжҙҫйҖҒиҮӘе·ұеӯҗејҹпјҢз«ҹеҮәиө„йӣҮдёҖиҙ«еҜ’еӯҗејҹпјҢиӢҘеә”差然пјӣ第дәҢж¬Ўд»ӨйҖҒе…«еҚҒдәәпјҢз»“жһңд»…йҖҒдәҢеҚҒдәәпјҢдё”дәҺжҡ‘еҒҮж—¶пјҢдёҖеҺ»дёҚиҝ”гҖӮвҖқ马й№ӨеӨ©еңЁйқ’жө·жө·зҘһеәҷжӣҫеҠқиҜҙдёҖеҗҚжҠ•иҜүзҠ¶зҡ„и—Ҹж—Ҹйқ’е№ҙеҲ°иҘҝе®ҒдёҠеӯҰпјҢиў«жӢ’з»қпјҢеҸҜи§Ғ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иө·жӯҘд№Ӣиү°йҡҫгҖӮ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иҝҳеңЁйқ’жө·еҠһдәҶдёӯеӨ®ж”ҝжІ»еӯҰж ЎиҘҝе®ҒеҲҶж ЎпјҢиҜҘж ЎжҳҜдё“й—ЁвҖңдёәиҫ№з–Ҷж°‘ж—ҸиҖҢзү№и®ҫиҖ…гҖӮз»ҘиҝңгҖҒе®ҒеӨҸгҖҒз”ҳиӮғгҖҒиҘҝеә·гҖҒйқ’жө·еҗ„жңүдёҖеҲҶж ЎпјҢжӯӨж ЎжіЁж„Ҹи’ҷгҖҒи—Ҹж—Ҹж•ҷиӮІгҖӮзҺ°еёҲиҢғеӣӣзә§пјҢеӯҰз”ҹзҷҫж•°еҚҒеҗҚпјҢеӨҡжұүгҖҒеӣһдәәпјҢдҪҶд№ и—Ҹж–ҮпјҢеҮҶеӨҮеҚ’дёҡеҗҺеңЁи—Ҹж°‘иҒҡеұ…д№Ӣең°еҠһе°ҸеӯҰиҖ…вҖқгҖӮиҖҢеёӮз«ӢиҘҝе®ҒеҲқзә§дёӯеӯҰжҳҜе…ёеһӢзҡ„еӨҡж°‘ж—ҸеӯҰж ЎпјҢеӯҰз”ҹжңүжұүгҖҒи’ҷеҸӨ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еҸҠж’’жӢүгҖҒзҫҢж—Ҹ6дёӘж°‘ж—ҸпјҢе№ҙйҫ„жңҖеӨ§иҖ…24еІҒпјҢ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—ҸдёҠеұӮиҙөж—ҸпјҲзҺӢе…¬иҙқеӢ’пјүзҡ„еӯҗејҹе°ұжңү10дҪҷдәәгҖӮеҗ„еҺҝеҸҠд№Ўй•ҮжҲ–и®ҫжңү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—Ҹе°ҸеӯҰпјҢд№ҹжңү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—ҸеҸҠе…¶д»–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ӯҗејҹе…Ҙжұүдәәе°ҸеӯҰжҺҘеҸ—ж•ҷиӮІгҖӮйқ’жө·еҚ—йғЁиҫ№еҢәиӯҰеӨҮеҸёд»ӨйғЁйҷ„и®ҫжңүи’ҷи—Ҹе°ҸеӯҰж ЎпјҢиҜҘж ЎеӯҰз”ҹжқҘжәҗжҳҜи—ҸгҖҒи’ҷеҸӨж—ҸеӯҗејҹпјҢеҢ…жӢ¬и’ҷеҸӨзҺӢе…¬еӯҗејҹпјҢеӣҪиҜӯиҜҫзЁӢдё»иҰҒеӯҰд№ жұүгҖҒи—ҸдёӨз§ҚиҜӯиЁҖеҸҠзӣёдә’зҝ»иҜ‘пјҢзү№еҲ«жіЁйҮҚж—Ҙеёёе®һз”ЁжҖ§гҖӮдёҖе№ҙзә§еӯҰз”ҹз”Ёи—ҸиҜӯи§ЈйҮҠжұүж–ҮпјҢж•ҷеёҲеҲҷд»Ҙжұүж–Үи§ЈйҮҠи—ҸиҜӯпјҢеёҲз”ҹеҪјжӯӨиғҪд»Ҙжұүи—ҸдёӨз§ҚиҜӯиЁҖдә’дёәи§ЈйҮҠпјӣдәҢе№ҙзә§дҫ§йҮҚдәҺи®°еҝҶгҖҒиғҢиҜөе’Ңй»ҳеҶҷгҖӮеңЁй»„жӯЈжё…зҡ„дё»жҢҒдёӢпјҢеӨҸжІіеҺҝеҸҠжӢүеҚңжҘһең°еҢәеңЁ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ж–№йқўеҒҡдәҶдёҚе°‘е·ҘдҪңпјҢжҲҗж•Ҳд№ҹзӣёеҪ“жҳҫи‘—гҖӮж—©еңЁ1927е№ҙејҖеҠһдәҶи—Ҹж°‘еӯҰж ЎпјҢдҪҶеҲқжңҹеҸ‘еұ•еҫҲдёҚйЎәеҲ©пјҢиҝһе№ҙеҸӘиғҪжӢӣеҲ°20дҪҷеҗҚеӯҰз”ҹгҖӮ1933е№ҙйЎҫжү§дёӯзӯүдәәеҲ°иҫҫжӢүеҚңжҘһеҗҺпјҢеҜ№и—Ҹж°‘ж–ҮеҢ–дҝғиҝӣдјҡз«Ӣ第дёҖе°ҸеӯҰзҲ¶жҜҚйғҪжҳҜи—Ҹж°‘зҡ„13еҗҚеңЁж ЎеӯҰз”ҹиҝӣиЎҢдәҶжөӢйӘҢпјҢи®Өдёәз»“жһңеңЁж°ҙе№ізәҝд»ҘдёҠпјҢвҖң他们зҺ°еңЁйғҪиғҪиҜҙжұүиҜқпјҢиғҪиҜ»жұүд№ҰпјҢйғҪдёҚзҲұеҒҡе–ҮеҳӣвҖқгҖӮиҖҢеӨҸжІіеҺҝз«Ӣ第дёҖе°ҸеӯҰпјҢеӯҰз”ҹжқҘжәҗзӣёеҜ№иҫғеҘҪпјҢвҖңжңүзҲ¶жҳҜеӣһж°‘жҜҚжҳҜз•Әж°‘пјҢд№ҹжңүзҲ¶жҳҜжұүж°‘жҜҚжҳҜз•Әж°‘зҡ„вҖқпјҢжҲҗз»©жҖ»дҪ“дёҠиҰҒжҜ”и—Ҹж°‘е°ҸеӯҰеҘҪгҖӮ1935е№ҙ马й№ӨеӨ©еҲ°еӨҸжІіж—¶пјҢеҪ“ең°е°ҸеӯҰе·Із»ҸжңүдәҶжҳҺжҳҫзҡ„еҸ‘еұ•пјҢеӯҰз”ҹж•°йҮҸеўһеҠ еҲ°60дҪҷеҗҚпј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ж°‘еқҮжңүпјҢиҷҪ然и—Ҹж°‘еқҮдёҚж„ҝеӯҗејҹиҜ»д№ҰпјҢдҪҶе·Із»ҸжңүзәҜзІ№и—Ҹж—ҸеӯҰз”ҹ17еҗҚпјҢдё”вҖңи—Ҹз”ҹжұүиҜӯеӨ§еҚҠз”ҡеҘҪвҖқпјҢвҖңиҝӣжӯҘдәҰз”ҡйҖҹпјҢзӣ–дёҖж ЎеҶ…жұүгҖҒи—Ҹе„ҝз«ҘиҒҡеұ…пјҢи§Ӯж‘©иҫғжҳ“вҖқгҖӮжүҖд»Ҙ马й№ӨеӨ©дё»еј иҘҝеҢ—еҗ„ж°‘ж—ҸиҒҡеұ…д№Ӣең°пјҢе°ҸеӯҰж Ўд»ҘеҗҢж ЎдёәжңҖе®ңпјҢдёҖеҲҷиҜӯиЁҖеҸҜд»Ҙз»ҹдёҖпјҢдәҢеҲҷж„ҹжғ…иһҚжҙҪпјҢж°‘ж—Ҹз•Ңйҷҗжҳ“жіҜпјҢдёүеҲҷд№ жғҜжҳ“ж”№гҖӮвҖңж•ҷ科д№ҰйҮҮе•ҶеҠЎеҚ°д№ҰйҰҶжң¬пјҢз”ЁжұүиҜӯж•ҷжҺҲпјҢжңүж—¶з”Ёи—ҸиҜӯзҝ»иҜ‘пјҢеӯҰ科еӨ§иҮҙжҢүйғЁз« пјҢжғҹеҲқдёүе№ҙзә§д»ҘдёҠпјҢжҜҸе‘Ёжңүи—Ҹж–ҮдәҢе°Ҹж—¶гҖӮвҖқд»–иҝҳйҷ„и—Ҹж°‘й«ҳе№ҙзә§еӯҰз”ҹдҪңж–ҮдёӨзҜҮпјҢдёҖзҜҮйўҳдёәгҖҠи°Ҳи°ҲжӢүеҚңжҘһзҡ„йЈҺдҝ—гҖӢпјҢдёҖзҜҮйўҳдҪңгҖҠжӢүеҚңжҘһеҰҮеҘізҡ„иЈ…йҘ°гҖӢпјҢзҡҶж–Үд»Һеӯ—йЎәпјҢеӨ§иҮҙеҸҜи§ӮпјҢе…¶еӣҪж–ҮзЁӢеәҰдёҺж•ҷиӮІжҲҗж•ҲеқҮеҸҜи§ҒдёҖж–‘гҖӮеҲ°1938е№ҙпјҢйЎҫйўүеҲҡдёҖиЎҢеңЁжӢүеҚңжҘһеҸӮи§ӮдәҶеҪ“ең°е°ҸеӯҰпјҢзңӢеҲ°вҖңжӯӨй—ҙжұүдәәе°ҸеӯҰдёӯжңүи—ҸдәәпјҢи—Ҹдәәе°ҸеӯҰдёӯдәҰжңүжұүдәәпјҢеҸҜи§ҒдёӨж—Ҹд№ӢиһҚе’ҢвҖқгҖӮзҹӯзҹӯеҚҒ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еҜ№жӢүеҚңжҘһең°еҢә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зӯүж°‘ж—ҸжҖқжғіи§Ӯеҝөзҡ„ж”№йҖ е’Ңеҗ„ж°‘ж—Ҹе…ізі»зҡ„ж”№е–„пјҢиө·еҲ°дәҶ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„жҺЁеҠЁдҪңз”Ё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иҮӘдёҙжҪӯиҮіеҗҲдҪңйҖ”дёӯпјҢеңЁжҳҺд»ЈжүҖзӯ‘иҫ№еўҷзҡ„жҡ—й—ЁйҒҮеҲ°дёҖдёӘи—Ҹж°‘пјҢиғҪеӨҹзҶҹз»ғең°з”ЁжұүиҜӯе’ҢйЎҫж°ҸдёҖиЎҢй—®зӯ”пјҢиҮӘз§°жӣҫз»ҸиҜ»иҝҮгҖҠдёүеӯ—з»ҸгҖӢеҸҠгҖҠеӣӣд№ҰгҖӢпјҢиҝҷеҜ№жҷ®йҖҡи—Ҹж°‘жқҘиҜҙпјҢе·Із»ҸжҳҜзӣёеҪ“й«ҳзҡ„жұүж–ҮеҢ–ж°ҙе№ідәҶпјҢвҖңеҲҷз•Әж°‘д№Ӣеұ…иҝ‘жұүең°иҖ…пјҢж•…йқһжңүдёҚиҜ»жұүд№Ұд№ӢжҲҗи§Ғд№ҹвҖқгҖӮеңЁжө·дёңзӣёеҜ№жҜ”иҫғеҸ‘иҫҫзҡ„ең°еҢәпјҢеҚіе°Ҹжқ‘иҗҪпјҢд№ҹжңүж°‘ж—Ҹе°ҸеӯҰжҲ–з§ҒеЎҫгҖӮеҢ–йҡҶеҺҝд»Җи¶іж—Ҹзҡ„жҳӮй”ҷжӣҫеңЁеҶ…ең°жёёеҺҶпјҢдәҶи§Јж–ҮеҢ–ж•ҷиӮІдәӢдёҡеҜ№дәҺзӨҫдјҡеҸ‘еұ•зҡ„йҮҚиҰҒдҝғиҝӣдҪңз”ЁпјҢжүҖд»Ҙзү№еҲ«жіЁж„ҸеҠһеӯҰпјҢеӣ жӯӨд»Җи¶іи—Ҹж°‘иҷҪ然仅жңү800дҪҷжҲ·3000дҪҷдәәпјҢеҚҙжӢҘжңүдёӨжүҖе°ҸеӯҰе…ұ100еӨҡеҗҚеңЁж ЎеӯҰз”ҹгҖӮзҷҝжҖқи§ӮпјҲд»Ҡжө·дёңе№іе®үеҢәеҚ—пјү100дҪҷжҲ·дәә家пјҢжңүз§ҒеЎҫдёҖжүҖпјҢж•ҷе‘ҳдёҖеҗҚпјҢдёәиҘҝе®Ғи’ҷз•ӘеёҲиҢғеӯҰж ЎжҜ•дёҡз”ҹпјҢжүҖж•ҷдёәйғЁйўҒж•ҷ科д№ҰпјҢд№ҹжңүгҖҠеӣӣд№ҰгҖӢ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гҖҠеЈ°еҫӢеҗҜи’ҷгҖӢзӯүдј з»ҹж•ҷжқҗгҖӮеӯҰз”ҹ28дәәпјҢе…¶дёӯи—Ҹж—ҸеӯҰз”ҹе…«д№қеҗҚпјҢзҡҶиғҪжұүиҜӯпјҢиЎЈжңҚдәҰдёҺжұүдәәж— ејӮгҖӮжңүдёҖдәӣжҖқжғіејҖжҳҺзҡ„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е®—ж•ҷдәәеЈ«е·Із»Ҹи®ӨиҜҶеҲ°ж•ҷиӮІеҸҠжұүиҜӯеӯҰд№ 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пјҢеҰӮеҚ“е°јзҰ…е®ҡеҜәе®Ӣе Әеёғжң¬дёәжұүдәәпјҢеӣ жӯӨжҖқжғіжҜ”иҫғејҖйҖҡпјҢж„ҸиҜҶеҲ°е–ҮеҳӣдёҚйҖҡжұүиҜӯпјҢдёҚдҫҝдәҺеұҘиЎҢж•ҷиӮІж°‘дј—зҡ„иҒҢиҙЈпјҢвҖңж¬ІеңЁеәҷдёӯи®ҫз«ӢеҚҠж—ҘеӯҰж ЎпјҢдҪҝе–ҮеҳӣеҚҠж—ҘиҜөз»ҸпјҢеҚҠж—ҘиҜ»д№ҰвҖқпјҢвҖңе–Үеҳӣж—ўиҜҶжұүж–ҮпјҢе…·жңүзҺ°д»ЈзҹҘиҜҶпјҢе°ҶжқҘеҶҚз”ұеҪјиҫҲж•ҷиӮІз•Әж°‘пјҢз•Әж°‘зҡҶжғҹе–Үеҳӣд№Ӣе‘ҪжҳҜеҗ¬иҖ…пјҢж”№йҖ е…¶жҖқжғіз”ҹжҙ»иҮӘеҝ…йЎәеҲ©вҖқгҖӮдҪҶеҸ—дј з»ҹд№ дҝ—дёҺ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дёҚе°‘и—ҸеҢәеӯҰж ЎдёҺеҜәйҷўжңүеҚғдёқдёҮзј•зҡ„иҒ”зі»пјҢжңүдәӣеӯҰж ЎеҚідёәеҜәйҷўжүҖеҠһпјҢжҲ–йҡ¶еұһдәҺеҜәйҷўпјҢеҰӮеӨ§йҖҡеҺҝдё°зЁ”е Ўи’ҷи—Ҹе°ҸеӯҰж Ўе°ұеұһдәҺдё°зЁ”е ЎеҢ—еҜәпјҢдёҺеҜәйҷўжңүеҜҶеҲҮиҒ”зі»гҖӮ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зҡ„еҸ‘еұ•пјҢжңүжҳҫи‘—зҡ„жҖқжғіеҗҜи’ҷдҪңз”ЁпјҢеҸ—иҝҮж–°ејҸж•ҷиӮІзҡ„и’ҷеҸӨгҖҒи—Ҹж—ҸеӯҗејҹпјҢдјҡжңүжӣҙиҝңеӨ§зҡ„дәәз”ҹзӣ®ж ҮпјҢдёҚеҶҚе°ҶеҮә家еҪ“е–Үеҳӣи§ҶдҪңзҗҶжүҖеҪ“然зҡ„иҒҢдёҡйҖүжӢ©пјҢзӣҙжҺҘеЁҒиғҒеҲ°еҜәйҷўзҡ„еүҚйҖ”пјҢеӣ жӯӨйғЁеҲҶж–°ејҸж°‘ж—ҸеӯҰж Ўеҝ…然еҸ—еҲ°жқҘиҮӘеҜәйҷўзҡ„жҺ’жҢӨе’Ңжү“еҺӢгҖӮеӨҸжІіеҚЎеҠ пјҲд»ҠеӨҸжІіеҺҝдёӢеҚЎеҠ д№Ўпјүжң¬дёәи—Ҹж°‘иҒҡеұ…еҢәпјҢжңүеӨҸжІіеҺҝз«Ӣе°ҸеӯҰдёҖжүҖпјҢеҗҢж—¶жӢӣ收周иҫ№еҗ„ең°жқҘжӯӨйҒҝд№ұзҡ„жұүгҖҒеӣһ民家еӯҗејҹпјҢвҖңжӯӨй—ҙе–Үеҳӣж·ұзҹҘж–°ејҸж•ҷиӮІеҸ‘иҫҫеҲҷеӯҗејҹеҮә家иҖ…еҝ…ж—Ҙе°‘пјҢе°ҶеҚұеҸҠеҜәйҷўеүҚйҖ”пјҢж•…йў‘ж–Ҫжү“еҮ»вҖқгҖӮ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иғҪеңЁеҰӮжӯӨзҺҜеўғдёӯиү°йҡҫиө·жӯҘ并жңүдәҶеҲқжӯҘжҲҗж•ҲпјҢдёә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иҝӣдёҖжӯҘиһҚеҗҲеҒҡеҘҪдәҶж–ҮеҢ–й“әеһ«пјҢеүҚжҷҜеҸҜжңҹгҖӮз»“ иҜӯ з»јдёҠжүҖи®әпјҢ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еҺҶеҸІжӮ д№…зҡ„е©ҡ姻关系пјҢй•ҝжңҹзҡ„зӨҫдјҡгҖҒз»ҸжөҺгҖҒж–ҮеҢ–дәӨжөҒпјҢдҪҝеҫ—еҗ„ж°‘ж—Ҹд№Ӣй—ҙзҡ„иҒ”зі»ж—ҘзӣҠеҠ ејәпјҢж„ҹжғ…д№ҹйҖҗжёҗиһҚжҙҪпјҢеңЁжҠөи§ҰгҖҒеҜ№жҠ—зҡ„еҗҢж—¶дә’еҠ©гҖҒе…ұеӯҳпјҢ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е…ұеҗҢдҪ“ж„ҸиҜҶејҖе§ӢиҗҢиҠҪпјҢиҝӣе…ҘдәҶж°‘ж—ҸиһҚеҗҲзҡ„ж–°йҳ¶ж®өгҖӮйЎҫйўүеҲҡж №жҚ®иҮӘе·ұзҡ„и§ӮеҜҹдёҺи°ғз ”пјҢиҜҙжӢүеҚңжҘһиЎ—еёӮвҖңйўҮз№Ғзӣӣпј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з•ӘдәәдҝұжңүпјҢеҗ„жңҚе…¶иЎЈеҶ пјҢеҗ„еәҰе…¶з”ҹжҙ»пјҢиҷҪиҜӯиЁҖд№ жғҜйўҮжңүе·®жұ иҖҢж— жҚҹдәҺжғ…ж„ҹд№ӢиһҚжҙҪвҖқгҖӮжһ—й№Ҹдҫ д№ҹи®ӨдёәпјҡвҖңд№җйғҪеҺҹдёәзўҫдјҜеҺҝпјҢжұүгҖҒеӣһгҖҒи’ҷгҖҒи—Ҹеҗ„ж—ҸжқӮеұ…пјҢиҷҪеҗ„ж—ҸдҝЎд»°йЈҺдҝ—жңүж®ҠпјҢиҖҢж„ҹжғ…з”ҡжҙҪпјҢд»Һж— зҢңз–‘гҖӮвҖқеҚідҪҝеңЁеҸ‘з”ҹжҲҳд№ұ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җ„ж°‘ж—Ҹй—ҙзӣёдә’ж•‘еҠ©пјҢжңүдёҚе°‘ж°‘дј—д№үж— еҸҚйЎҫең°з»ҙжҠӨж°‘ж—Ҹе…ұеӯҳдёҺеӣўз»“гҖӮж—©еңЁжё…жңқеҗҢжІ»гҖҒе…үз»ӘпјҲ1862вҖ”1908е№ҙпјүе№ҙй—ҙпјҢжҙ®е·һпјҲд»Ҡз”ҳиӮғдёҙжҪӯпјүеұЎйҒӯе…өзҮ№пјҢеҫҲеӨҡжұүж°‘е°ұеҫ—еҲ°и—Ҹж°‘зҡ„дҝқжҠӨпјҢвҖңеҗҢжІ»е…өзҮ№пјҢеҹҺжұ е ЎеҜЁе°ҪжҲҗзҒ°зғ¬пјҢиҖҢжҙ®ең°дәәж°‘иҮід»ҠзҠ№жңүеӯ‘йҒ—иҖ…пјҢзҡҶз•ӘдәәдҝқжҠӨд№ӢеҠҹеұ…еӨҡвҖқпјҢвҖңдәҺжӯӨеҸҜи§ҒжұүгҖҒз•Әжғ…и°Ҡд№Ӣз¬ғвҖқгҖӮе…үз»ӘдәҢеҚҒдёҖе№ҙпјҲ1895е№ҙпјүпјҢжҙ®е·һеӣһж°‘еҸ—жІіж№ҹеӣһж°‘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еҜҶи°Ӣиө·дәӢпјҢеҪ“ең°еӣһгҖҒжұүеЈ«з»…ж¶ҲйҷӨж°‘ж—ҸејӮи§ҒпјҢиҒ”еҗҲи°ғеҒңпјҢжӯўдәүз«ҜдәҺиҗҢиҠҪгҖӮ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еүҚеҗҺпјҢйҡҸзқҖеҗ„ж°‘ж—ҸдәӨеҫҖзҡ„иҝӣдёҖжӯҘеҠ ж·ұпјҢз”ҳйқ’ж°‘ж—Ҹиө°е»Ҡең°еҢәж°‘ж—Ҹе…ізі»жӣҙи¶ӢиһҚжҙҪгҖӮйғЁеҲҶеӣһгҖҒжұүжқӮеұ…ең°еҢәдёӨж—Ҹж°‘дј—д№ҹиғҪе’Ңе№іе…ұеӨ„пјҢдә’зӣёдҝқжҠӨпјҢеҰӮдёҙеӨҸжқЁе®¶еҸ°еӯҗпјҲд»ҠдёҙеӨҸеҺҝ马йӣҶй•ҮжқЁеҸ°жқ‘пјүйҷ„иҝ‘дә”е…ӯдёӘжқ‘еә„йғҪжҳҜеӣһгҖҒжұүж°‘жқӮеұ…зҡ„пјҢвҖңиҝҷдёӘжқЁе®¶еҸ°еӯҗзҡ„еӣһжұүдәәж°‘пјҢеҫҲиғҪдә’зӣёз»ҙжҠӨпјҢеҢӘжқҘпјҢеӣһж°‘жҺ©жҠӨжұүж°‘пјҢеҶӣжқҘпјҢжұүж°‘жҺ©жҠӨеӣһж°‘вҖқгҖӮ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ж•ҷиӮІзҡ„е…ҙиө·дёҺеҸ‘еұ•пјҢдҪҝеҫ—дј—еӨҡ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ӯҗејҹеӯҰд№ дәҶж–ҮеҢ–е’Ң科еӯҰзҹҘиҜҶпјҢжҺҘи§ҰдәҶзҺ°д»Јж–ҮжҳҺпјҢзңјз•ҢйҖҗжёҗејҖйҳ”пјҢжҖқжғіж—ҘзӣҠи§Јж”ҫпјҢејҖе§Ӣж‘Ҷи„ұзӢӯйҡҳзҡ„ж°‘ж—Ҹз•ҢйҷҗдёҺе®—ж•ҷзҗҶеҝөзҡ„жқҹзјҡпјҢдёәиҝҷдёҖ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иҝӣдёҖжӯҘдәӨеҫҖгҖҒдәӨжөҒгҖҒдәӨиһҚеҘ е®ҡдәҶеқҡе®һ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зҺӢиҪІ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10жңҹвҖңеҺҶеҸІдёҺж–ҮеҢ–вҖқж Ҹзӣ®вҖң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°‘ж—ҸдәӨеҫҖдәӨжөҒдәӨиһҚеҸІвҖқдё“йўҳ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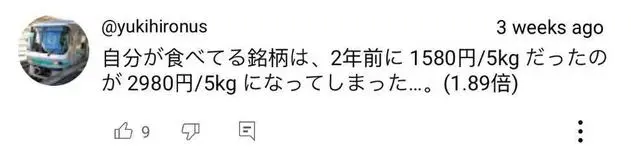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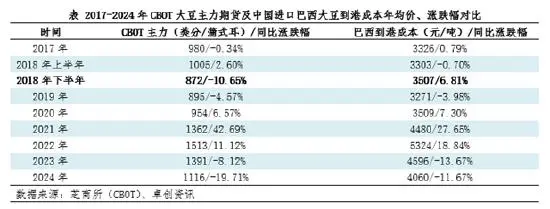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