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зҺӢй‘«пјҲзҫҺеӣҪдјҒдёҡз ”з©¶жүҖзӨҫдјҡеҸҠз»ҸжөҺ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пјү дёҖгҖҒдёәд»Җд№ҲиҰҒйҖүжӢ©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пјҹ
йүҙдәҺиҙЁз–‘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зҡ„еЈ°йҹіеҫҲзӘҒеҮәпјҢжҜ”еҰӮе“ҲдҪӣеӨ§еӯҰзҡ„Dani Rodrik(Rodrik 2018)е’Ңеү‘жЎҘеӨ§еӯҰзҡ„Ha-JoonChang(Chang 2008)пјҢеҫҲе®№жҳ“еӨёеӨ§з»ҸжөҺеӯҰ家д№Ӣй—ҙеӯҳеңЁзҡ„еҲҶжӯ§гҖӮжҖҖз–‘и®әиҖ…йҖҡеёёеЈ°з§°е·ҘдёҡеҢ–еҜ№зҺ°д»Ј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иҮіе…ійҮҚиҰҒгҖӮз”ұдәҺе·ҘдёҡеҢ–иҝҮзЁӢйҖҡеёёжҳҜеңЁзӣёеҪ“зЁӢеәҰзҡ„з»ҸжөҺдҝқжҠӨдёӢиҝӣиЎҢзҡ„пјҢе°ұеғҸ18дё–зәӘжң«зҡ„иӢұеӣҪгҖҒ19дё–зәӘзҡ„зҫҺеӣҪе’Ң第дәҢ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еҗҺзҡ„дёңдәҡз»ҸжөҺдҪ“дёҖж ·пјҢ他们и®ӨдёәпјҢз»ҷ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жҸҗдҫӣзҡ„з»Ҹе…ёпјҲcanonicalпјүе»әи®®жҳҜй”ҷиҜҜзҡ„пјҢеҚіз®ҖеҚ•ең°еҗ‘иҙёжҳ“ејҖж”ҫеёӮеңәгҖӮ
йҷӨдәҶжҜҸдёҖйЎ№зңӢдјјжҲҗеҠҹзҡ„дҫқиө–иҝӣеҸЈдҝқжҠӨзҡ„дә§дёҡж”ҝзӯ–йғҪеҸҜд»ҘжүҫеҲ°еҮ дёӘеӨұиҙҘзҡ„дҫӢеӯҗеӨ–пјҢ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е’ҢеҲ¶йҖ дёҡд№Ӣй—ҙзҡ„иҒ”зі»д№ҹжҳҜеҖјеҫ—жҖҖз–‘зҡ„гҖӮе°Ҫз®Ў18дё–зәӘеӯҳеңЁйҮҚиҰҒзҡ„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пјҢдҪҶеҫҲе°‘жңүз»ҸжөҺеҸІеӯҰ家и®ӨдёәиҝҷдәӣжҳҜиӢұеӣҪе·Ҙдёҡйқ©е‘Ҫзҡ„еҺҹеӣ гҖӮеҗҢж ·пјҢеңЁй«ҳеәҰ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зҡ„еҚҒд№қдё–зәӘжң«зҡ„зҫҺеӣҪпјҢ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жҳҜз”ұдәәеҸЈе’Ңиө„жң¬з§ҜзҙҜзҡ„еўһй•ҝжҺЁеҠЁзҡ„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иҙёжҳ“ж”ҝзӯ–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жӯЈеҰӮйҒ“ж јжӢүж–Ҝ·欧ж–Ү(Douglas Irwin)еҜ№зҫҺеӣҪ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зҡ„з ”з©¶жүҖжҳҫзӨәзҡ„йӮЈж ·пјҢвҖңе…ізЁҺеҸҜиғҪйҖҡиҝҮжҸҗй«ҳиҝӣеҸЈиө„жң¬е•Ҷе“Ғзҡ„д»·ж јйҳ»зўҚдәҶиө„жң¬з§ҜзҙҜвҖқпјҢеңЁе…¬з”ЁдәӢдёҡе’ҢжңҚеҠЎзӯүжңӘеҸ—е…ізЁҺеҪұе“Қзҡ„иЎҢдёҡдёӯпјҢи§ӮеҜҹеҲ°зҡ„з”ҹдә§зҺҮеўһй•ҝдјјд№Һд№ҹжҳҜжңҖејәеҠІзҡ„(欧ж–Ү2001)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·ҘдёҡеҢ–并дёҚжҳҜйҖҡеҗ‘й«ҳ收е…Ҙзҡ„е”ҜдёҖйҖ”еҫ„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йҰҷжёҜгҖҒйҹ©еӣҪе’Ңж–°еҠ еқЎзҡ„з»ҸжөҺеҙӣиө·еӣҙз»•зқҖеҠіеҠЁеҠӣиҫ“еҮәвҖ”вҖ”еҠіеҠЁеҜҶйӣҶеһӢеҲ¶йҖ дёҡ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йҖҡиҝҮ常规и®ҫжғізҡ„е·ҘдёҡеҢ–гҖӮж–°иҘҝе…°гҖҒжҫіеӨ§еҲ©дәҡе’ҢзҲұе°”е…°еңЁеҗ„иҮӘзҡ„з»ҸжөҺиө·йЈһжңҹй—ҙд№ҹйҒҝе…ҚдәҶдј з»ҹзҡ„е·ҘдёҡеҢ–еҪўејҸпјҢ并дҝқжҢҒдәҶжһҒй«ҳзҡ„з»ҸжөҺејҖж”ҫеәҰгҖӮ
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зҡ„зҗҶз”ұдҫқиө–дәҺдёҖзі»еҲ—и®әзӮ№пјҢд»ҺдәҡеҪ“В·ж–ҜеҜҶ(Adam Smith)е’ҢеӨ§еҚ«В·жқҺеҳүеӣҫ(DavidRicardo)еҲҶеҲ«жҸҗеҮәзҡ„з»Ҹе…ёеҲҶе·Ҙе’ҢжҜ”иҫғдјҳеҠҝжҰӮеҝөпјҢйҖҡиҝҮе°Ҷиҙёжҳ“ејҖж”ҫдёҺз»ҸжөҺиЎЁзҺ°иҒ”зі»иө·жқҘзҡ„е……и¶ізҡ„з»ҸйӘҢиҜҒжҚ®пјҢеҲ°еңЁжүҖи°“зҡ„ж–°иҙёжҳ“зҗҶи®ә(New Trade They)зҡ„дҝқжҠӨдјһдёӢеҸ‘еұ•еҮәжқҘзҡ„ж–°и§Ғи§ЈгҖӮеҗҺиҖ…дҪҝз”Ёе…ідәҺдә§е“Ғе·®ејӮеҢ–е’Ң规模з»ҸжөҺзҡ„зҺ°е®һеҒҮи®ҫжқҘи§ЈйҮҠзҺ°е®һдё–з•Ңиҙёжҳ“жөҒеҠЁзҡ„дё°еҜҢжҖ§гҖӮ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зҡ„жҳҜпјҢж–°иҙёжҳ“зҗҶи®әдёӢзҡ„иҙёжҳ“жғ…еҶөжҜ”д»ҘеүҚзҡ„жғ…еҶөжӣҙеӨҚжқӮ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йҷҗеҲ¶гҖӮе°Ҫз®ЎеҰӮжӯӨпјҢз»қеӨ§еӨҡж•°з»ҸжөҺдё“дёҡдәәеЈ«йғҪдјҡеҗҢж„ҸпјҢеҜ№дәҺзҺ°е®һдё–з•ҢдёӯеӯҳеңЁзҡ„еӨҚжқӮеӣ зҙ пјҢ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жһ„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еҸҜд»ҘдҝЎиө–зҡ„еҹәзәҝж”ҝзӯ–еҲ¶еәҰгҖӮ
еӣ жӯӨпјҢ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йқўдёҙзҡ„дё»иҰҒжҢ‘жҲҳдёҚжҳҜжҷәеҠӣдёҠ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ж”ҝжІ»дёҠзҡ„гҖӮжүҖжңүж”ҝжқғдёӢзҡ„ж”ҝжІ»йўҶеҜјдәәйғҪйқўдёҙзқҖеҗ‘жңүз»„з»Үзҡ„еҲ©зӣҠйӣҶеӣўжҸҗдҫӣеҲ©зӣҠеәҮжҠӨд»ҘжҚўеҸ–е…¶ж”ҜжҢҒзҡ„иҜұжғ‘пјҢеҗҢж—¶е°ҶжӯӨзұ»ж”ҝзӯ–зҡ„жҲҗжң¬еҲҶж•ЈеҲ°жӣҙе№ҝжіӣзҡ„дәәеҸЈдёӯгҖӮе…ізЁҺгҖҒй…Қйўқе’Ңе…¶д»–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жҺӘж–Ҫе°ұжҳҜеҫҲеҘҪзҡ„дҫӢеӯҗгҖӮеӣҪеҶ…з”ҹдә§е•Ҷзҡ„收зӣҠеҫҖеҫҖжҳҜеҸҜи§Ӯзҡ„пјҢиҖҢеӣҪеҶ…ж¶Ҳиҙ№иҖ…е’ҢеӨ–еӣҪз”ҹдә§е•Ҷд№Ӣй—ҙзҡ„иҙёжҳ“еӣ жӯӨеёҰжқҘзҡ„收зӣҠжҚҹеӨұеҚҙеҫҲеӨ§пјҢе°Ҫз®Ўд»ҺеҚ•дёӘж¶Ҳиҙ№иҖ…дёӘдҪ“зҡ„и§’еәҰжқҘзңӢ收зӣҠжҚҹеӨұеҫҲе°ҸгҖӮ19дё–зәӘз»ҸжөҺеӯҰ家兼记иҖ…еј—йӣ·еҫ·йҮҢе…ӢВ·е·ҙж–Ҝи’Ӯдәҡзү№(FrГ©dГ©ric Bastiat)еңЁе…¶и‘—еҗҚзҡ„ж–Үз« вҖңзңӢеҲ°дәҶд»Җд№Ҳе’ҢзңӢдёҚеҲ°д»Җд№ҲвҖқ(What Is Seed And What Is Not Seed)дёӯжҸҗ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и‘—еҗҚ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ж”ҝзӯ–зҡ„收зӣҠеҫҖеҫҖжҳҜеҸҜи§Ғзҡ„пјҢиҖҢе®ғ们зҡ„жҲҗжң¬(еҚіпјҢеӨұеҺ»зҡ„жңәдјҡ)еҲҷжҳҜдёҚеҸҜи§Ғзҡ„(Bastiat1850)гҖӮ
еӣ жӯӨпјҢ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зҡ„жҢ‘жҲҳжң¬иҙЁдёҠдё»иҰҒжҳҜеӣҪеҶ…зҡ„пјҡдёҖжҳҜйҒҸеҲ¶з»„з»ҮдёҘеҜҶзҡ„еӣҪеҶ…еҲ©зӣҠйӣҶеӣў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жҲ–иҖ…пјҢжӯЈеҰӮе…ӢйІҒж јжӣјжүҖиҜҙпјҢвҖңжҲ‘们иҫҫжҲҗ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еҚҸи®®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дҝқжҠӨжҲ‘们дёҚеҸ—е…¶д»–еӣҪ家дёҚе…¬е№іиҙёжҳ“иЎҢдёә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зңҹжӯЈзҡ„зӣ®ж ҮжҳҜдҝқжҠӨжҲ‘们дёҚеҸ—иҮӘиә«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ҡйҷҗеҲ¶иҝҮеҺ»дё»еҜјиҙёжҳ“ж”ҝзӯ–зҡ„зү№ж®ҠеҲ©зӣҠж”ҝжІ»е’ҢеҪ»еӨҙеҪ»е°ҫзҡ„и…җиҙҘгҖӮвҖқ(е…ӢйІҒж јжӣј2018е№ҙ)гҖӮ
е°ұдёӘ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йқўдёҙзҡ„йҖүжӢ©жҳҜпјҢжҳҜеҗҰдёәжң¬еӣҪз”ҹдә§е•ҶжҸҗдҫӣе…ҚеҸ—еӨ–еӣҪз«һдәүзҡ„дҝқжҠӨпјҢеҗҢж—¶е°Ҷж•ҙдҪ“иҙҹжӢ…ејәеҠ з»ҷз»ҸжөҺзҡ„е…¶д»–йғЁй—ЁгҖӮж №жҚ®е…·дҪ“жғ…еҶөпјҢиҝҷдёҖйҖүжӢ©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дёәеӣҡеҫ’еӣ°еўғ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дёәзҢҺй№ҝжёёжҲҸгҖӮж— и®әе“Әз§Қж–№ејҸпјҢжӯӨзұ»йӣҶдҪ“иЎҢеҠЁй—®йўҳзҡ„еӯҳеңЁйғҪдёәеӣҪйҷ…жңәжһ„еңЁж”ҝжІ»дёҠз»ҙжҢҒиҙёжҳ“ејҖж”ҫжҸҗдҫӣдәҶејәжңүеҠӣзҡ„дҝқйҡңгҖӮ
дәҢгҖҒиҮӘз”ұдёҺдёҚиҮӘз”ұзҡ„иҙёжҳ“еҸІ
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дёҚжҳҜеҺҶеҸІеёёжҖҒгҖӮж–ҜеҜҶеңЁд»–1776е№ҙзҡ„йҮҢзЁӢзў‘ејҸи‘—дҪңгҖҠеӣҪеҜҢи®әгҖӢдёӯ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жңҹжңӣеңЁеӨ§дёҚеҲ—йў е®Ңе…ЁжҒўеӨҚ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пјҢе°ұеғҸжңҹжңӣеңЁйӮЈйҮҢе»әз«ӢдёҖдёӘеӨ§жҙӢжҙІжҲ–д№ҢжүҳйӮҰдёҖж ·иҚ’и°¬гҖӮвҖқ(Smith1979пјҢ第471йЎө)гҖӮиӢұеӣҪе’Ң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вҖ”вҖ”з”ҡиҮіжҳҜе…Ёдәәзұ»вҖ”вҖ”д»ҺйӮЈж—¶иө·пјҢе·Із»Ҹиө°иҝҮдәҶеҫҲй•ҝдёҖж®өи·ҜгҖӮж–ҜеҜҶжІЎжңүйў„и§ҒеҲ°пјҢд»–зҡ„ж•ҷд№үе’Ңе…¶д»–еҸӨе…ёз»ҸжөҺеӯҰ家зҡ„ж•ҷд№үеҫҲеҝ«е°ұдјҡжҝҖиө·дёҖиӮЎж”ҝжІ»жҝҖиҝӣдё»д№үжөӘжҪ®гҖӮејҖж”ҫиҙёжҳ“зҡ„иҝҗеҠЁеҜјиҮҙдәҶ1846е№ҙи°·зү©жі•зҡ„еәҹйҷӨпјҢиҝҷйЎ№жі•еҫӢзҡ„еј•е…ҘжҳҜдёәдәҶдҝқжҢҒеӣҪеҶ…и°·зү©д»·ж јзҡ„дёҠж¶Ё(д»ҘеҸҠең°дё»еә”收зҡ„з§ҹйҮ‘)гҖӮ欧жҙІйҡҸеҗҺеҮәзҺ°дәҶдёҖжіў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жөӘжҪ®пјҢе…¶дёӯеӨ§йғЁеҲҶжҳҜйҖҡиҝҮеӣҪдёҺеӣҪд№Ӣй—ҙзҡ„еҸҢиҫ№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е®һзҺ°зҡ„гҖӮ1860е№ҙиӢұеӣҪе’Ңжі•еӣҪзј”з»“зҡ„вҖң科еёғзҷ»вҖ”вҖ”и°ўз“ҰеҲ©еҹғиҙёжҳ“жқЎзәҰвҖқдёәи®ёеӨҡ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ҡ„ж”ҝеәң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дёӘиҢғжң¬гҖӮеҸ–ж¶ҲдәҶеҜ№жі•еӣҪиҝӣеҸЈзҡ„зҰҒд»ӨпјҢеҸ–иҖҢд»Јд№Ӣзҡ„жҳҜдёҚи¶…иҝҮ30%зҡ„е…ізЁҺгҖӮиӢұеӣҪеӨ§е№…йҷҚдҪҺдәҶи‘Ўиҗ„й…’е…ізЁҺпјҢ并ејҖе§Ӣе…Ғи®ёи®ёеӨҡжі•еӣҪдә§е“Ғе…ҚзЁҺгҖӮвҖң科еёғзҷ»вҖ”вҖ”и°ўз“ҰеҲ©еҹғжқЎзәҰвҖқеңЁж•ҙдёӘ欧жҙІеӨ§йҷҶеј•еҸ‘дәҶдёҖжіўзұ»дјјз»“жһ„зҡ„еҸҢиҫ№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пјҢе…¶дёӯи®ёеӨҡеҚҸе®ҡе…·жңүвҖңжңҖжғ еӣҪвҖқжқЎж¬ҫвҖ”вҖ”ејҖеҲӣдәҶдёҖдёӘ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„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ж—¶жңҹпјҢ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ә·зә·ж•Ҳд»ҝ(KindlebergerпјҢ1975)гҖӮжңҖжғ еӣҪеҫ…йҒҮжқЎж¬ҫиҰҒжұӮеҗ„еӣҪдёҚеҲҶйқ’зәўзҡӮзҷҪең°йҖӮз”Ёе®ғ们еҗ‘д»»дҪ•е…¶д»–еӣҪ家жҸҗдҫӣзҡ„зӣёеҗҢжқЎж¬ҫгҖӮ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з”ҡиҮіжңҖз»ҲеҲ°иҫҫдәҶжӣҫз»ҸдёҺдё–йҡ”з»қзҡ„ж—Ҙжң¬е’ҢдёӯеӣҪеёқеӣҪпјҢе®ғ们дёҺиҘҝж–№дё»иҰҒз»ҸжөҺдҪ“зӯҫи®ўдәҶ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вҖ”вҖ”е°ұж—Ҙжң¬иҖҢиЁҖжҲ–иҖ…иў«иҝ«е…Ғи®ёеӨ–еӣҪеҲ—ејәеҲ¶е®ҡ他们зҡ„иҙёжҳ“еҲ¶еәҰвҖ”вҖ”е°ұеғҸйёҰзүҮжҲҳдәүеҗҺзҡ„дёӯеӣҪдёҖж ·гҖӮ
然иҖҢпјҢејҖж”ҫзҡ„иҙёжҳ“дҪ“еҲ¶е№¶жІЎжңүжҢҒз»ӯеҫҲй•ҝж—¶й—ҙгҖӮеҲ°еҪ“ж—¶ж—ўжңүзҡ„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еҲ°жңҹйҮҚж–°зӯҫзҪІж—¶пјҢ欧жҙІзҡ„з»ҸжөҺе’Ңж”ҝжІ»ж°”еҖҷе·Із»Ҹж”№еҸҳ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жҖқжғіеҸҲйҮҚж–°жөҒиЎҢиө·жқҘ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йҖҡиҝҮеҫ·еӣҪеҺҶеҸІеӯҰжҙҫ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д»ҘеҸҠе®ғзҡ„вҖңе№јзЁҡе·ҘдёҡвҖқи®әзӮ№еңЁж¬§жҙІиҝҹжқҘзҡ„е·ҘдёҡеҢ–еӣҪ家дёӯзҡ„зӘҒеҮәиЎЁзҺ°гҖӮеҫ·еӣҪеҺҶеҸІеӯҰжҙҫйў„иЁҖдәҶеҪ“д»Ҡиҙёжҳ“жҖҖз–‘и®әиҖ…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жӢ’з»қжҺҘеҸ—дәҡеҪ“В·ж–ҜеҜҶ(Adam Smith)е’Ңи®©-е·ҙи’Ӯж–Ҝзү№(Jean-Baptiste)зӯүз»Ҹе…ёж”ҝжІ»з»ҸжөҺеӯҰ家ж”ҜжҢҒ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зҡ„и®әзӮ№дёӯйҡҗеҗ«зҡ„дё–з•Ңдё»д№ү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е®ғж”ҜжҢҒдёҖз§ҚзӢӯйҡҳзҡ„гҖҒд»ҘеӣҪ家дёәдёӯеҝғзҡ„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и§ӮзӮ№пјҢиҝҷз§Қи§ӮзӮ№еңЁж¬§жҙІж°‘ж—ҸеӣҪ家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ҫ·ж„Ҹеҝ—еёқеӣҪе’Ңж„ҸеӨ§еҲ©зҡ„е·©еӣәиҝҮзЁӢдёӯиҮӘ然дә§з”ҹдәҶе…ұйёЈгҖӮ
1871е№ҙеҫ·еӣҪжҲҳиғңжі•еӣҪеҗҺпјҢдҝҫж–ҜйәҰеҗ‘жі•еӣҪејәеҠ дәҶдёҖ笔еҸҜи§Ӯзҡ„жҲҳдәүиө”еҒҝйҮ‘гҖӮжі•еӣҪжҸҗеүҚиҝҳж¬ҫеҗҺпјҢеҫ·еӣҪз»ҸжөҺйҷ·е…Ҙ1873е№ҙжҒҗж…Ңеј•еҸ‘зҡ„еҚұжңәгҖӮиҝҷдәӣеӣ°йҡҫж”ҫеӨ§дәҶеҫ·еӣҪз”ҹдә§е•ҶиҰҒжұӮе…ізЁҺдҝқжҠӨзҡ„е‘јеЈ°гҖӮж”ҝеәңиҝҳеңЁеҜ»жүҫж–°зҡ„收е…ҘжқҘжәҗпјҢд»ҘејҘиЎҘжі•еӣҪжҸҗеүҚиҝҳж¬ҫйҖ жҲҗзҡ„зјәеҸЈгҖӮ1879е№ҙпјҢдҝҫж–ҜйәҰеј•е…ҘдәҶй“Ғе’Ңй»‘йәҰе…ізЁҺпјҢеҜ№еҗ„з§ҚеҶңдёҡе’Ңе·Ҙдёҡдә§е“ҒеҫҒ收иҝӣеҸЈзЁҺпјҡзІ®йЈҹгҖҒиӮүзұ»гҖҒзҢӘгҖҒзәәз»Үе“ҒгҖҒжңәжў°д»ҘеҸҠеҗ„з§ҚеҚҠжҲҗе“ҒгҖӮ1882е№ҙпјҢжі•еӣҪз»ҸеҺҶдәҶдёҖеңәдёҘйҮҚзҡ„银иЎҢдёҡеҚұжңәпјҢеҜјиҮҙиҜҘеӣҪз»ҸжөҺйҷ·е…ҘиЎ°йҖҖпјҢжҢҒз»ӯдәҶиҝҷдёӘдё–зәӘеү©дҪҷзҡ„еҚҒ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еӨ§е®—е•Ҷе“Ғд»·ж јдёӢи·ҢеҠ еү§дәҶиЎ°йҖҖгҖӮеңЁ19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җҺеҚҠж®өпјҢиҝҷдәӣй—®йўҳдә§з”ҹдәҶи¶іеӨҹзҡ„ж”ҝжІ»еҺӢеҠӣпјҢиҰҒжұӮйҮҚж–°еј•е…Ҙ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пјҢеҢ…жӢ¬еңЁдј з»ҹдёҠд»ҘеҮәеҸЈдёәеҜјеҗ‘зҡ„иЎҢдёҡгҖӮ1892е№ҙпјҢдёҖз§Қж–°зҡ„е…ізЁҺеҲ¶еәҰиў«еј•е…ҘпјҢд»Ҙе…¶дё»иҰҒеҖЎеҜјиҖ…жңұе°”ж–ҜВ·жў…жһ—(Jules MГ©line)зҡ„еҗҚеӯ—е‘ҪеҗҚгҖӮ
еңЁз¬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зҲҶеҸ‘д№ӢеүҚпјҢдёҖзі»еҲ—зҡ„иҙёжҳ“еҶІзӘҒе’ҢйҖҗжӯҘзҡ„жҠҘеӨҚжҖ§е…ізЁҺдёҠеҚҮгҖӮ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зҡ„жҳҜпјҢе…Ёзҗғиҙёжҳ“еңЁеҗҺжқҘиў«з§°дёәвҖң第дёҖд»Је…ЁзҗғеҢ–вҖқзҡ„жңҹй—ҙ继з»ӯжү©еӨ§пјҢе°Ҫз®ЎжІЎжңүиҫҫеҲ°зӣ®еүҚдё–з•Ңеҗ„ең°з»ҸжөҺдёҖдҪ“еҢ–зҡ„ж°ҙе№ігҖӮ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иҙёжҳ“зҡ„еўһй•ҝдё»иҰҒжҳҜиҝҗиҫ“жҲҗжң¬дёӢйҷҚе’Ңд»ҘйҮ‘жң¬дҪҚ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дёҖдҪ“еҢ–йҮ‘иһҚдҪ“зі»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еҪ“жҲҳдәүжқҘдёҙж—¶пјҢеҜ№иҙёжҳ“зҡ„еҪұе“ҚжҳҜе·ЁеӨ§зҡ„гҖӮ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еј•е…ҘдәҶж–°зҡ„е…ізЁҺгҖҒеӨ–жұҮз®ЎеҲ¶е’Ңе…¶д»–йҷҗеҲ¶жҺӘж–ҪпјҢ并иҜ•еӣҫйҮҚж–°и°ғж•ҙ他们зҡ„з»ҸжөҺж–№еҗ‘пјҢиҪ¬еҗ‘жҲҳдәүз”ҹдә§гҖӮиҙёжҳ“жүҖйңҖзҡ„жңүеҪў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вҖ”вҖ”е…¬и·ҜгҖҒй“Ғи·Ҝе’ҢжёҜеҸЈвҖ”вҖ”жӯЈеңЁиў«ж‘§жҜҒпјҢдәӨжҲҳеҸҢж–№йў‘з№ҒиҝӣиЎҢе°Ғй”Ғе’ҢжҪңиүҮжҲҳеҪ№пјҢд»Ҙдёӯж–ӯеҪјжӯӨзҡ„иҙёжҳ“жөҒеҠЁгҖӮ
еҸҜжӮІзҡ„жҳҜпјҢ1918е№ҙзҡ„е’Ң平并没жңүйҳ»жӯў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зҡ„жөӘжҪ®гҖӮйҷӨдәҶ1927е№ҙиҮі1928е№ҙд№Ӣй—ҙзҡ„дёҙж—¶е…ізЁҺдј‘жҲҳеӨ–пјҢе№іеқҮе…ізЁҺзЁҺзҺҮеңЁ20дё–зәӘ20е№ҙд»Јжңҹй—ҙ继з»ӯж”ҖеҚҮпјҢ然еҗҺйҡҸзқҖеӨ§иҗ§жқЎзҡ„еҲ°жқҘиҖҢе‘ҲзҲҶзӮёејҸеўһй•ҝвҖ”вҖ”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1930е№ҙж–Ҝз©Ҷзү№вҖ”вҖ”йңҚеҲ©е…ізЁҺжі•жЎҲ(Smoot-Hawley Tariff Act)еҮәеҸ°еҗҺпјҢзҫҺеӣҪжӢ’з»қ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(Mad-sen 2001пјҢp.850)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»ҺеӨ§иҗ§жқЎејҖе§ӢеҲ°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йҮҸ收缩дәҶзәҰ40%пјҢдҪҝ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жҒўеӨҚеҲ°з¬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еүҚзҡ„ж°ҙе№ігҖӮ
еңЁдёҺйҮ‘жң¬дҪҚеҲ¶жҢӮй’©зҡ„еӣҪ家пјҢжҖҘдәҺжҺЁиЎҢ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зҡ„зҺ°иұЎе°ӨдёәжҳҺжҳҫпјҢеӣ дёәиҝҷдәӣеӣҪе®¶ж— жі•йҖҡиҝҮиҙ§еёҒж”ҝзӯ–еә”еҜ№з»ҸжөҺеҶІеҮ»(Eichen-Greenе’ҢIrwinпјҢ2009)гҖӮ然иҖҢпјҢжңӘиғҪз»ҙжҢҒ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дҪ“еҲ¶зҡ„дё»иҰҒеҺҹеӣ жҳҜж”ҝжІ»еӣ зҙ гҖӮеёҰжңүжңҖжғ еӣҪжқЎж¬ҫзҡ„еҸҢиҫ№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зҡ„иӣӣзҪ‘йҖ жҲҗдәҶйӣҶдҪ“иЎҢеҠЁ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жІЎжңүеҸӮдёҺ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пјҢиҖҢжҳҜзӯүеҫ…е…¶д»–еӣҪ家жүҝжӢ…иҙёжҳ“и°ҲеҲӨзҡ„ж”ҝжІ»йҮҚд»»пјҢ然еҗҺ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жңҖжғ еӣҪжқЎж¬ҫиҺ·еҫ—еҘҪеӨ„гҖӮ1932е№ҙпјҢиҒ”еҗҲзҺӢеӣҪеҜ№иӢұиҒ”йӮҰеӣҪ家е®һиЎҢдјҳжғ е…ізЁҺеҲ¶еәҰпјҢж Үеҝ—зқҖйқһжӯ§и§ҶжҖ§иҙёжҳ“еҲ¶еәҰзҡ„жңүж•Ҳз“Ұи§Ј(дё–з•Ңиҙёжҳ“з»„з»ҮпјҢ2007е№ҙпјҢ第39-43йЎө)гҖӮ
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иҮӘ1945е№ҙд»ҘжқҘеҸ–еҫ—зҡ„иҝӣеұ•д»ӨдәәйңҮжғҠгҖӮдё»иҰҒе·ҘдёҡеҢ–з»ҸжөҺдҪ“еңЁ20дё–зәӘ40е№ҙд»Јжң«е®һж–Ҫзҡ„е№іеқҮе…ізЁҺзЁҺзҺҮзәҰдёә20%пјҢж—©е…Ҳзҡ„дёҖдәӣдј°и®Ўй«ҳиҫҫ40%(Bownе’ҢIrwin 2015)гҖӮд»ҠеӨ©пјҢеңЁз»ҸеҺҶдәҶ70е№ҙзҡ„жҢҒз»ӯ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д№ӢеҗҺпјҢиҝҷдёҖжҜ”зҺҮзЁіе®ҡеңЁ5%д»ҘдёӢгҖӮиҝҷдёҖдёӢйҷҚжҳҜе…іиҙёжҖ»еҚҸе®ҡе’Ң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дё»жҢҒдёӢзҡ„еӨҡиҫ№е…ізЁҺеүҠеҮҸд»ҘеҸҠдјҳжғ зҡ„гҖҒдё»иҰҒжҳҜеҢәеҹҹз»„з»Үзҡ„иҙёжҳ“е®үжҺ’жҝҖеўһ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
е…іиҙёжҖ»еҚҸе®ҡ/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и°ҲеҲӨеҲҶеҮ иҪ®иҝӣиЎҢгҖӮжңҖиҝ‘зҡ„дёҖж¬ЎжҳҜеӨҡе“ҲеӣһеҗҲпјҢдәҺ2001е№ҙеҗҜеҠЁпјҢиҮӘ2015е№ҙеҶ…зҪ—жҜ•йғЁй•ҝзә§дјҡи®®д»ҘжқҘе®һйҷ…дёҠе·Із»Ҹжӯ»дәЎгҖӮиҷҪ然жңҖеҲқзҡ„еҮ иҪ®и°ҲеҲӨеҢ…жӢ¬еҮ еҚҒдёӘеӣҪ家пјҢиҖ—ж—¶ж•°жңҲпјҢеҸӘж¶үеҸҠе…ізЁҺи®©жӯҘпјҢдҪҶ159дёӘеӣҪ家жӯЈеңЁеҸӮдёҺеҪ“еүҚзҡ„еӨҡе“ҲеӣһеҗҲвҖ”вҖ”иҝҷиҪ®и°ҲеҲӨеҺӢеҖ’жҖ§ең°йӣҶдёӯеңЁзӣ‘з®Ўе’Ңйқһе…ізЁҺеЈҒеһ’зӯүеӨҚжқӮй—®йўҳдёҠгҖӮеңЁжҹҗз§ҚзЁӢеәҰдёҠпјҢ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дҪ“зі»жҳҜе…¶иҮӘиә«жҲҗеҠҹзҡ„зүәзүІе“ҒгҖӮеңЁеӨ§еӨҡж•°е…ізЁҺе’Ңй…Қйўқе·Із»Ҹ移йҷӨ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ү©дёӢзҡ„йғҪжҳҜж”ҝжІ»ж•Ҹж„ҹйғЁй—Ё(еҰӮеҶңдёҡ)зҡ„жЈҳжүӢй—®йўҳпјҢзӣ‘з®ЎеҲ¶еәҰзҡ„еӨҡж ·жҖ§пјҢзҹҘиҜҶдә§жқғй—®йўҳзӯүзӯүгҖӮжӯЈеҰӮж„Ҳжј”ж„ҲзғҲдё”жҜ«ж— з»“жһңзҡ„и°ҲеҲӨжүҖиЎЁжҳҺзҡ„йӮЈж ·пјҢдёҖдёӘз”ұдё–з•ҢдёҠеӨ§еӨҡж•°еӣҪ家ж”ҝеәңеҸӮдёҺзҡ„е…ұеҗҢи®әеқӣпјҢеқҡжҢҒд»ҘвҖңеҚ•дёҖжүҝиҜәвҖқ(иҰҒжұӮе°ұжүҖжңүдәӢжғ…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еҗҰеҲҷе°ұд»Җд№ҲйғҪдёҚеҒҡ)зҡ„еҪўејҸиҝӣиЎҢи°ҲеҲӨпјҢеҸҜиғҪдёҚеҶҚжҳҜеҸ–еҫ—иҝӣдёҖжӯҘиҝӣеұ•зҡ„жңҖеҗҲйҖӮеңәжүҖгҖӮ
然иҖҢпјҢд»…д»…йҖҡиҝҮзҺ°е·ІеҒңж»һдёҚеүҚзҡ„еӨҡиҫ№и°ҲеҲӨзҡ„жЈұй•ңжқҘзңӢеҫ…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жҳҜй”ҷиҜҜзҡ„гҖӮе®ғзҡ„дё»иҰҒиҙЎзҢ®жҳҜйқһжӯ§и§ҶжҖқжғіпјҢиҝҷе·ІжҲҗдёәе…ЁзҗғйҖӮз”Ёзҡ„дёҖйЎ№еҹәжң¬иҙёжҳ“ж”ҝзӯ–еҺҹеҲҷгҖӮйқһжӯ§и§ҶжҢҮзҡ„жҳҜдёӨдёӘ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„жҰӮеҝөгҖӮйҰ–е…ҲпјҢйқһжӯ§и§Ҷж„Ҹе‘ізқҖ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з»ҷдәҲеӣҪеҶ…е’ҢеӨ–еӣҪе•Ҷе“Ғ(жҲ–жҠ•иө„иҖ…)еҗҢзӯүзҡ„жі•еҫӢе’Ңзӣ‘з®Ўеҫ…йҒҮгҖӮ第дәҢпјҢдёҚжӯ§и§Ҷж¶үеҸҠжңҖжғ еӣҪеҫ…йҒҮзҡ„жҰӮеҝөпјҡеҗ„еӣҪдёҚеҫ—еңЁжі•еҫӢдёҠжӯ§и§ҶжқҘиҮӘдёҚеҗҢеӣҪ家зҡ„иҝӣеҸЈ(жҲ–жҠ•иө„)пјҢеҝ…йЎ»еҜ№д»Һд»»дҪ•еӣҪ家еҗ‘жүҖжңүеӣҪ家иҝӣеҸЈзҡ„е•Ҷе“Ғе®һиЎҢжңҖдјҳжғ еҫ…йҒҮгҖӮиҝҷдёҖеҺҹеҲҷдёҚжҳҜз»қеҜ№зҡ„вҖ”вҖ”еҰӮжһңжҳҜз»қеҜ№зҡ„пјҢйӮЈд№Ҳ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д»ҘеӨ–зҡ„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е°Ҷ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зҡ„гҖӮж №жҚ®GATT第24жқЎпјҢеҸӘиҰҒдёҚеўһеҠ е…¶д»–еӣҪ家йқўдёҙзҡ„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пјҢејҖж”ҫжүҖжңүиҙёжҳ“(д»ҘйҒҝе…ҚжүӯжӣІ)пјҢ并йҖӮеҪ“ең°еҗ‘WTOжҠҘе‘ҠпјҢе°ұеҸҜд»Ҙе…Ғи®ёиҫҫжҲҗдјҳжғ 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ҜҘз»„з»Үе…Ғи®ёеҗ„еӣҪе°ұи¶…еҮәеӨҡиҫ№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иҢғеӣҙзҡ„иҙёжҳ“д№үеҠЎиҫҫжҲҗдёҖиҮҙгҖӮ
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жқЎзәҰжҸҗдҫӣзҡ„дёҖз§ҚйҖүжӢ©жҳҜпјҢйҖҡиҝҮеңЁеҗ„еӣҪиҮӘиЎҢйҖүе®ҡзҡ„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жҲҗе‘ҳд№Ӣй—ҙиҝӣиЎҢи°ҲеҲӨпјҢйҖҡиҝҮи°ҲеҲӨиҫҫжҲҗж–°зҡ„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пјҢеңЁ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规еҲҷжЎҶжһ¶еҶ…зҡ„вҖң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+вҖқзҡ„ж–№ејҸиҝӣиЎҢпјҢиҝҷдәӣеҚҸи®®еўһеҠ дәҶзҺ°жңүзҡ„д№үеҠЎпјҢ并дёәйӮЈдәӣйҖүжӢ©йҖҡиҝҮжҲҗдёәеҚҸи®®зј”зәҰж–№иҖҢжҺҘеҸ—д№үеҠЎзҡ„жҲҗе‘ҳжҸҗдҫӣйўқеӨ–зҡ„д»·еҖј(е·ҙе…Ӣж–ҜпјҢ2018е№ҙ)гҖӮ
еӣҙз»•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е»әз«Ӣзҡ„е…Ёзҗғиҙёжҳ“дҪ“зі»д№ҹжҸҗдҫӣдәҶи®ёеӨҡеҸҜд»Ҙи§ЈеҶіеҶІзӘҒзҡ„еңәжүҖпјҢйӮҖиҜ·еҗ„еӣҪ(жңүж—¶жҳҜе…¬еҸё)вҖңжҢ‘йҖүвҖқеҗҲйҖӮзҡ„еңәжүҖжқҘи§ЈеҶіе®ғ们зҡ„дәүз«Ҝ(Busch 2007)гҖӮе®№жҳ“зҡ„й—®йўҳйҖҡеёёд»ҘеҸҢиҫ№ж–№ејҸи§ЈеҶіпјҢиҖҢиҫғеӣ°йҡҫзҡ„й—®йўҳеҲҷеңЁ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еұӮйқўдёҠд»ҘеӨҡиҫ№ж–№ејҸи§ЈеҶі(David 2009)гҖӮ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жңүдёҖдёӘз”ұ专家组е’ҢдёҠиҜүжңәжһ„з»„жҲҗзҡ„дёӨдёӘйҳ¶ж®өзҡ„зі»з»ҹпјҢжҲҗз«ӢдәҺ1995е№ҙпјҢзӣ®зҡ„жҳҜи§ЈеҶіеӣҪ家д№Ӣй—ҙзҡ„еҲҶжӯ§гҖӮ
WTOжҖҖз–‘и®әиҖ…жңүж—¶жҢҮеҮәпјҢжҲҗе‘ҳеӣҪзҡ„иҙёжҳ“йўқ并дёҚжҜ”иҜҘз»„з»Үд»ҘеӨ–зҡ„еӣҪ家еӨҡ(RoseпјҢ2004)гҖӮеңЁдёҖдёӘд»Ҙ规еҲҷ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е…ЁзҗғзҺҜеўғдёӯпјҢPTAеҸҜд»ҘйҖҡиҝҮиЎҘе……еӨҡиҫ№дҪ“зі»иҖҢдёҚжҳҜз ҙеқҸеӨҡиҫ№дҪ“зі»иҖҢжңүж•Ҳең°иҝӣиЎҢвҖ”вҖ”жӯЈеҰӮе®ғ们еңЁ1930е№ҙд»ЈжүҖеҒҡзҡ„йӮЈж ·гҖӮиҝҷеҫҲйҮҚиҰҒпјҢеӣ дёәеҚідҪҝд»ҺзҗҶи®әдёҠи®ІпјҢз»ҸжөҺеӯҰ家д№ҹдјҡеҜ№PTAжҢҒжҖҖз–‘жҖҒеәҰгҖӮеңЁвҖңж¬ЎдјҳвҖқз»ҸжөҺзҗҶи®әдёӢпјҢжңүйҖүжӢ©ең°еҸ–ж¶Ҳ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дјҡйҖ жҲҗж–°зҡ„жүӯжӣ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йғЁеҲҶ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з ҙеқҸзҡ„иҙёжҳ“йўқеҸҜиғҪдјҡи¶…иҝҮиҙёжҳ“еҲӣйҖ зҡ„зҰҸеҲ©ж”¶зӣҠгҖӮеҚідҪҝжҳҜдёҘйҮҚзҡ„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пјҢеҸӘиҰҒе®ғжҳҜйқһжӯ§и§ҶжҖ§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дёҖе®ҡдјҡж”№еҸҳзӣёеҜ№д»·ж јгҖӮ然иҖҢпјҢжңүйҖүжӢ©ең°еҸ–ж¶Ҳд»Һе°‘ж•°еӣҪ家иҝӣеҸЈзҡ„е…ізЁҺпјҢеҸҜиғҪдјҡд»ҘзүәзүІе…¶д»–еӣҪ家дёәд»Јд»·пјҢеҠ ејәдёҺиҝҷдәӣз»ҸжөҺдҪ“зҡ„иҙёжҳ“гҖӮеҰӮжһңз”ұжӯӨеҜјиҮҙзҡ„иҙёжҳ“жөҒеҠЁжүӯжӣІзЁӢеәҰиҝңиҝңи¶…еҮәжҪңеңЁз»ҸжөҺеҹәжң¬йқўжүҖиғҪи§ЈйҮҠзҡ„иҢғеӣҙпјҢе°ұеҸҜиғҪеҜјиҮҙж•ҙдҪ“ж•ҲзҺҮйҷҚдҪҺгҖӮ
дёҺиҝҮеҺ»еҫҖеҫҖз”ұзӣёдә’з«һдәүзҡ„ж®–ж°‘еӨ§еӣҪе»әз«Ӣзҡ„дәӨжҲҳиҙёжҳ“йӣҶеӣўдёҚеҗҢпјҢд»ҠеӨ©зҡ„PTAдёҚдјҡдә§з”ҹиҝҷз§ҚеҸҚеёё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йҷӨдәҶиҝҷдәӣеҚҸе®ҡеҸ‘з”ҹеңЁ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еЎ‘йҖ зҡ„еӣҪйҷ…зҺҜеўғд№ӢеӨ–пјҢиҝҷдәӣеҚҸе®ҡеҫҖеҫҖеңЁең°зҗҶдёҠжҲ–з”ұдәҺе…¶д»–жҪңеңЁиҒ”зі»пјҢеҰӮе…ұеҗҢзҡ„еҺҶеҸІгҖҒиҜӯиЁҖжҲ–иҝҮеҺ»зҡ„з»ҸжөҺе’Ңе•ҶдёҡиҒ”зі»пјҢеңЁе·Із»ҸжҳҜиҮӘ然иҙёжҳ“дјҷдјҙзҡ„еӣҪ家д№Ӣй—ҙжңүжңәең°дә§з”ҹгҖӮ
PTAзҡ„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жҳҜеӣҪ家дёҺеӣҪ家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үз«Ҝи§ЈеҶіжңәеҲ¶пјҢдёҺзҺ°жңүзҡ„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еұӮйқўзҡ„жңәеҲ¶зӣёиҫ…зӣёжҲҗ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ҲҳеҗҺж—¶д»ЈиҝҳеҮәзҺ°дәҶжҠ•иө„иҖ…е’ҢеӣҪ家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үз«Ҝи§ЈеҶіжңәеҲ¶пјҢеҚіжҠ•иө„иҖ…дёҺеӣҪ家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үз«Ҝи§ЈеҶіжңәеҲ¶(ISDS)гҖӮзӣ®еүҚеӨ§зәҰжңү3000еӨҡдёӘ (Wellhausen2016)пјҢйҖҡеёёжҳҜйҷӨеҸҢиҫ№жҠ•иө„жқЎзәҰд№ӢеӨ–зҡ„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иҝҷдәӣ规е®ҡе…Ғи®ёеӨ–еӣҪе…¬еҸёеҗ‘еӣҪйҷ…жі•йҷўжҲ–дёҙж—¶д»ІиЈҒжңәжһ„еҜ»жұӮй’ҲеҜ№еӣҪеҶ…ж”ҝеәңзҡ„иЎҘж•‘жҺӘж–ҪгҖӮISDSжңҖеҲқзҡ„зҗҶи®әеҹәзЎҖжқҘиҮӘдәҺеҗҺж®–ж°‘ж—¶д»Ј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з»ҸжөҺж”ҝзӯ–зҡ„дёҚзЁіе®ҡпјҢеңЁиҝҷдәӣеӣҪ家пјҢеӨ–еӣҪжҠ•иө„иҖ…з»Ҹеёёйқўдёҙиў«еҫҒз”Ёзҡ„еЁҒиғҒгҖӮдёәдәҶзј“и§Јиҝҷз§ҚжӢ…еҝ§пјҢ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жүҝиҜәйҒөе®Ҳиҝҷдәӣжңәжһ„зҡ„еҶіе®ҡгҖӮйҡҸзқҖж—¶й—ҙзҡ„жҺЁз§»пјҢжңҖеҲқзҡ„зҗҶз”ұе·Із»ҸеҸҳеҫ—и–„ејұвҖ”вҖ”жҲ–и®ёжҳҜеӣ дёәISDSзҡ„жү©ж•Је’ҢжҲҗеҠҹвҖ”вҖ”然иҖҢпјҢйҡҸзқҖдё–з•Ңеҗ„ең°(еҢ…жӢ¬еҢҲзүҷеҲ©е’Ңжіўе…°зӯү欧жҙІеӣҪ家)з»ҸжөҺ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зҡ„еҚ·еңҹйҮҚжқҘпјҢеҫҲйҡҫиҫ©з§°ISDSе·Із»ҸиҝҮж—¶гҖӮISDSи¶…и¶ҠдәҶ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зҡ„йқһжӯ§и§Ҷ规еҲҷпјҢиҰҒжұӮз»ҷдәҲеӨ–еӣҪжҠ•иө„иҖ…вҖңе…¬жӯЈе’Ңе№ізӯүвҖқзҡ„еҫ…йҒҮгҖӮдёҖдәӣдәәжӢ…еҝғISDSз»ҷдәҲеӨ–еӣҪе…¬еҸёдёҚе…¬е№ізҡ„зү№жқғпјҢиҖҢеӣҪеҶ…е…¬еҸёеҲҷжІЎжңүгҖӮ然иҖҢпјҢиөўеҫ—ISDSзә зә·е№¶дёҚжҳҜдёҖеёҶйЈҺйЎәзҡ„пјҡжңҖиҝ‘еҜ№ISDSеӨҮжЎҲж–Ү件зҡ„дёҖйЎ№з ”з©¶жҳҫзӨәпјҢж”ҝеәңиөўеҫ—иҜүи®јзҡ„жҜ”дҫӢдёә37.7%пјҢжҠ•иө„иҖ…иҺ·иғңзҡ„жҜ”дҫӢдёә29.1%пјҢ33.1%зҡ„жЎҲ件иҫҫжҲҗе’Ңи§ЈгҖӮеҚідҪҝе…¬еҸёиғңиҜүпјҢ他们д№ҹеҸӘиғҪ收еӣһжңҖеҲқзҙўиө”зҡ„30%еҲ°40%(Wellhausen 2016пјӣFranck 2007)гҖӮ
дёүгҖҒе…ізЁҺд»ҘеӨ–зҡ„еӣ зҙ
еңЁе…ізЁҺеЈҒеһ’еӨ„дәҺеҺҶеҸІдҪҺзӮ№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зҡ„иҙёжҳ“жҠ•иө„иҮӘз”ұеҢ–дё»иҰҒжҳҜеӣҪеҶ…ж”№йқ©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е…¶дёӯи®ёеӨҡж”№йқ©жҳҜдёҚеҸ—еҪұе“Қзҡ„гҖӮеңЁTTIP(и·ЁеӨ§иҘҝжҙӢиҙёжҳ“е’ҢжҠ•иө„дјҷдјҙе…ізі»)и°ҲеҲӨжңҹй—ҙпјҢ欧жҙІе’ҢзҫҺеӣҪзҡ„и°ҲеҲӨд»ЈиЎЁеҜ»жұӮе°ұе»әзӯ‘еёҲгҖҒе·ҘзЁӢеёҲе’Ңе®Ўи®ЎеёҲзҡ„иө„ж јпјӣеҠЁзү©зҰҸеҲ©е’ҢйЈҹе“Ғе®үе…Ёж ҮеҮҶпјӣд»ҘеҸҠзҹҘиҜҶдә§жқғиҫҫжҲҗдёҖиҮҙ(欧зӣҹ委е‘ҳдјҡ2016)гҖӮиҷҪ然иҝҷдәӣйўҶеҹҹзҡ„жі•еҫӢе’Ңзӣ‘з®Ўж ҮеҮҶзҡ„е·®ејӮйғҪдјҡеҜјиҮҙиҙёжҳ“ж‘©ж“ҰпјҢдҪҶе®ғ们зҡ„еӯҳеңЁд№ҹеҸҜиғҪжңүд»ӨдәәдҝЎжңҚзҡ„зҗҶз”ұгҖӮиҜ•еӣҫеңЁиҝҷдәӣйўҶеҹҹеҰҘеҚҸ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дёҚйҖҸжҳҺ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жңүеҸҜиғҪеј•еҸ‘еҸҚеј№пјҢдә’иҒ”зҪ‘ж—¶д»Јзҡ„еӨёеӨ§е…¶иҜҚиҝӣдёҖжӯҘеӮ¬еҢ–дәҶиҝҷдёҖйЈҺйҷ©гҖӮ
дҫӢеҰӮпјҢTTIPдёӯзҡ„зҹҘиҜҶдә§жқғй—®йўҳе°ұеҢ…жӢ¬ең°зҗҶж Үеҝ—й—®йўҳгҖӮиҝҷдәӣеҸҚжҳ дәҶеӨ§иҘҝжҙӢдёӨеІёзҡ„дёҖз§ҚзңҹжӯЈзҡ„еҲҶжӯ§пјҢ欧жҙІдәәжҜ”зҫҺеӣҪдәәжӣҙжү§зқҖдәҺең°зҗҶзҡ„жғіжі•гҖӮеҜ№дәҺжі•еӣҪдәәгҖҒж„ҸеӨ§еҲ©дәәжҲ–еёҢи…Ҡ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и®ӨдёәйҰҷж§ҹи‘Ўиҗ„й…’гҖҒеё•е°”зҺӣзҶҸзҒ«и…ҝжҲ–иҸІеЎ”еҸҜд»Ҙз”ұ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ҡ„з”ҹдә§е•Ҷз”ҹдә§зҡ„жғіжі•жҳҜејӮз«ҜгҖӮеҗҢж ·пјҢеңЁиӢұеӣҪпјҢеҗ‘зҫҺеӣҪејҖж”ҫж”ҝеәңйҮҮиҙӯзҡ„еүҚжҷҜ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еј•еҸ‘дәҶеҜ№еӣҪ家еҢ»з–—жңҚеҠЎ(National Health ServiceпјҢQuinn 2016)вҖңз§ҒжңүеҢ–вҖқзҡ„жӢ…еҝ§пјҢиҝҷ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жҳҜжІЎжңүж №жҚ®зҡ„пјҢдҪҶе®Ңе…ЁеҸҜд»Ҙйў„и§ҒпјҢеҗҢж—¶иҝҳеј•еҸ‘дәҶе№ҝжіӣи®Ёи®әзҡ„еҜ№еҚіе°Ҷд»ҺзҫҺеӣҪиҝӣеҸЈзҡ„вҖңж°ҜеҢ–йёЎиӮүвҖқзҡ„еҚұиЁҖиҖёеҗ¬гҖӮ
еӣҪеҶ…ж”ҝзӯ–е·®ејӮзҡ„еӯҳеңЁ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и§ЈйҮҠдәҶдёәд»Җд№Ҳе°Ҫз®Ўе…ізЁҺдёӢйҷҚпјҢдё–з•ҢеҸҳеҫ—и¶ҠжқҘи¶ҠвҖңе№іеқҰвҖқпјҢең°зҗҶдҪҚзҪ®д»Қ然еҫҲйҮҚиҰҒгҖӮдёҺзүӣйЎҝзҡ„еј•еҠӣжЁЎеһӢзұ»дјјпјҢдё–з•ҢдёҠд»»дҪ•дёӨдёӘз»ҸжөҺдҪ“д№Ӣй—ҙзҡ„иҙёжҳ“йҮҸпјҢеҸӘиҰҒзҹҘйҒ“е®ғ们зҡ„еӨ§е°Ҹе’Ңи·қзҰ»е°ұеҸҜд»ҘзӣёеҪ“зІҫзЎ®ең°дј°и®ЎеҮәжқҘгҖӮз»ҸжөҺеӯҰ家乔зәіжЈ®В·дјҠйЎҝ(Jonathan Eaton)е’ҢеЎһзјӘ尔·科尔еӣҫе§Ҷ(Samuel Kor-tum)еңЁ2002е№ҙеҸ‘иЎЁзҡ„дёҖзҜҮи®әж–Үз ”з©¶дәҶдёҖз§ҚдёҚеӯҳеңЁиҝҷз§ҚвҖңеј•еҠӣвҖқзҡ„иҙёжҳ“еҒҮжғіжЁЎеһӢгҖӮеңЁиҝҷж ·дёҖдёӘиҷҡжһ„зҡ„дё–з•ҢйҮҢпјҢдё–з•Ңиҙёжҳ“йҮҸе°ҶжҳҜзҺ°е®һдё–з•Ңзҡ„5еҖҚгҖӮеҸҰдёҖйЎ№з ”з©¶дј°и®ЎпјҢеҸ‘иҫҫеӣҪ家зҡ„иҙёжҳ“ж‘©ж“Ұ规模зӣёеҪ“дәҺй«ҳиҫҫ170%зҡ„зЁҺ收вҖ”вҖ”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жӣҙжҳҜеҰӮжӯӨ(Andersonе’Ңvan WincoopпјҢ2004е№ҙ)гҖӮ
и·қзҰ»дёҚеғҸиҝҮеҺ»йӮЈд№ҲйҮҚиҰҒпјҢдҪҶе®ғзҡ„жҢҒз»ӯзӣёе…іжҖ§д№ӢжүҖд»ҘеҰӮжӯӨеј•дәәжіЁзӣ®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ңЁ20дё–зәӘдёӢеҚҠеҸ¶пјҢиҝҗиҫ“жҲҗжң¬еӨ§е№…дёӢйҷҚпјҢд»ҘиҮідәҺи®ёеӨҡз»ҸжөҺеӯҰ家еҸӘжҳҜдёәдәҶж–№дҫҝиҖҢз®ҖеҚ•ең°е°Ҷиҝҗиҫ“жҲҗжң¬зӯүеҗҢдәҺйӣ¶(Harford 2017)гҖӮ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зҡ„жҳҜпјҢеү©дёӢзҡ„дёҖдәӣ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еҫҲеҸҜиғҪж—ўдёҚеҸ—жҠҖжңҜеӣ зҙ 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д№ҹдёҚеҸ—е…¬е…ұж”ҝзӯ–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иҜӯиЁҖйҡңзўҚдёҚд»…еҸҚжҳ дәҶзӣҙжҺҘжІҹйҖҡзҡ„дҫҝеҲ©жҖ§(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еҸҜд»ҘйҖҡиҝҮжҠҖжңҜи§ЈеҶі)пјҢиҝҳеҸҚжҳ дәҶдҝЎд»»е’Ңе…ұеҗҢзҡ„е•Ҷдёҡж–ҮеҢ–зҡ„еӯҳеңЁ(Melitz 2003пјӣMelitz and Toubal 2012)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…ідәҺж•Јеұ…дёңеҚ—дәҡзҡ„дёӯеӣҪдәәеҲӣе»әзҡ„иҙёжҳ“зҪ‘з»ң(RauchпјҢ2001)жҲ–дјҒдёҡз®ЎзҗҶе®һи·өдёӯзҡ„е·®ејӮжүҖиө·зҡ„дҪңз”Ё(EstrinпјҢBagdasaryanе’ҢMeyerпјҢ2009)пјҢе·Із»ҸеҶҷдәҶеҫҲеӨҡж–Үз« гҖӮ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жӯЈеҰӮз»ҸжөҺеӯҰ家зҗҶжҹҘеҫ·В·йІҚеҫ·жё©(Richard BaldwinпјҢ2016)жүҖиҜҙпјҢеҪ“д»Ҡз»ҸжөҺдёҖдҪ“еҢ–зҡ„йҷҗеҲ¶жҖ§зәҰжқҹжҳҜдј ж’ӯжҖқжғізҡ„жҲҗжң¬гҖӮ
жӯӨзұ»ж‘©ж“Ұ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жәҗдәҺжі•еҫӢ规еҲҷзҡ„е·®ејӮгҖӮеӣ дёәйҒөе®Ҳ法规зҡ„жҲҗжң¬еҫҲй«ҳпјҢдёҖ家дјҒдёҡйңҖиҰҒйҒөеҫӘзҡ„дёҚеҗҢ规еҲҷи¶ҠеӨҡпјҢе…¶еҗҲ规жҲҗжң¬е°ұи¶Ҡй«ҳгҖӮеңЁжҹҗз§ҚзЁӢеәҰдёҠ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жҲҗжң¬е°Ҷйҳ»жӯўе…¬еҸёиҝӣе…Ҙжң¬жқҘеҸҜд»ҘзӣҲеҲ©зҡ„еёӮеңәгҖӮжңүдёҖдәӣиҜҒжҚ®иЎЁжҳҺпјҢйҡҸзқҖе…ізЁҺеЈҒеһ’зҡ„ж¶ҲеӨұ(OreficeгҖҒPiermartiniе’ҢRocha 2012)пјҢиҝҷз§ҚжҠҖжңҜе’Ңзӣ‘з®ЎеЈҒеһ’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д№ҹеңЁеўһеҠ пјҢиҝҷиЎЁжҳҺ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жӯЈеңЁз§ҜжһҒеҜ»жұӮж–°зҡ„е·Ҙе…·пјҢе°ҶеӨ–еӣҪз«һдәүжӢ’д№Ӣй—ЁеӨ–гҖӮ
еңЁжңҚеҠЎдёҡпјҢзӣ‘з®ЎеЈҒеһ’зҡ„иҙҹжӢ…дј°и®ЎзӣёеҪ“дәҺ20%иҮі75%зҡ„е…ізЁҺ(з»ҸеҗҲз»„з»Ү2017е№ҙ)гҖӮеңЁеҲ¶йҖ дёҡдёӯпјҢйҒөе®ҲдёҚеҗҢзҡ„ж ҮеҮҶйңҖиҰҒжҳӮиҙөзҡ„йҮҚж–°и®ҫи®Ў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ңЁжұҪиҪҰеҲ¶йҖ е•ҶиҒ”зӣҹеј•з”Ёзҡ„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дёӯпјҢдёҖ家зҫҺеӣҪе…¬еҸёиҜ•еӣҫеҗ‘欧жҙІеҮәеҸЈдёҖж¬ҫе№ҝеҸ—ж¬ўиҝҺзҡ„иҪ»еһӢеҚЎиҪҰпјҢеҝ…йЎ»еҲ¶йҖ 100дёӘзӢ¬зү№зҡ„йғЁд»¶пјҢйўқеӨ–иҠұиҙ№4200дёҮзҫҺе…ғиҝӣиЎҢи®ҫи®Ўе’ҢејҖеҸ‘пјҢ并еҜ№33дёӘдёҚеҗҢзҡ„иҪҰиҫҶзі»з»ҹиҝӣиЎҢдёҘж јжөӢиҜ•вҖ”вҖ”вҖңеңЁе®үе…ЁжҲ–жҺ’ж”ҫж–№йқўжІЎжңүд»»дҪ•жҖ§иғҪе·®ејӮвҖқгҖӮ(Akhtarе’ҢJones 2014пјҢ第8йЎө)гҖӮ
дё–з•Ң银иЎҢзҡ„жҠҖжңҜжҖ§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и°ғжҹҘжұҮжҖ»дәҶдёң欧гҖҒжӢүдёҒзҫҺжҙІгҖҒдёӯдёңгҖҒеҚ—дәҡе’Ңж’’е“ҲжӢүд»ҘеҚ—йқһжҙІ16дёӘеӣҪ家зҡ„е…¬еҸёеҸ‘з”ҹзҡ„дёҖж¬ЎжҖ§еӣәе®ҡжҲҗжң¬пјҢеҸ‘зҺ°жҲҗжң¬д»Һ3.57дәҝзҫҺе…ғеҲ°1230дёҮзҫҺе…ғдёҚзӯүпјҢе№іеқҮдёә42.5дёҮзҫҺе…ғпјҢеҚ е№ҙеўһеҠ еҖјзҡ„4.7%(MaskusпјҢOtsukiе’ҢWilson2005пјҢ第22йЎө)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җҲ规жҖ§еўһеҠ дәҶйўқеӨ–зҡ„жҲҗжң¬пјҢеӣ дёәз®ЎзҗҶжөӢиҜ•е’Ңи®ӨиҜҒйңҖиҰҒж–°зҡ„е‘ҳе·ҘжҲ–жңҚеҠЎгҖӮжҖ»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дёҺжӢҘжңүеӨ§йҮҸжі•еҫӢе’ҢеҗҲ规йғЁй—Ёзҡ„иҖҒзүҢеӨ§е…¬еҸёзӣёжҜ”пјҢжҲҗжң¬еҜ№е°ҸдјҒдёҡжқҘиҜҙжҳҜдёҖдёӘжӣҙеӨ§зҡ„йҡңзўҚгҖӮ
ж №жҚ®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вҖңжҠҖжңҜжҖ§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еҚҸе®ҡвҖқе’ҢвҖңеҚ«з”ҹдёҺжӨҚзү©еҚ«з”ҹжҺӘж–ҪеҚҸе®ҡвҖқдёӯзҡ„规е®ҡпјҢ17дёӘжҲҗе‘ҳеӣҪжүҝиҜә其法规гҖҒж ҮеҮҶе’ҢеҗҲж јиҜ„е®ҡзЁӢеәҸжҳҜйқһжӯ§и§ҶжҖ§зҡ„пјҢдёҚдјҡеҜ№иҙёжҳ“йҖ жҲҗдёҚеҝ…иҰҒзҡ„йҡңзўҚгҖӮдёҚз”ЁиҜҙпјҢзӣ‘з®Ўзҡ„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и®ҫи®ЎеҫҲе°‘е…¬ејҖеұ•зӨәгҖӮеҚідҪҝиҝҷж ·зҡ„WTOиҜүи®јиғңиҜүпјҢ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еҫҖеҫҖд№ҹдёҚж„ҝеҸ–ж¶ҲиҝҷдәӣеҸ—еҲ°жҢ‘жҲҳзҡ„жҺӘж–ҪпјҢиҖҢжҳҜеҸӘеҒҡдёҖдәӣеҫ®е°Ҹзҡ„и°ғж•ҙпјҢеҗҰеҲҷе°ұдјҡйқўдёҙз»ҸжөҺеӨ„зҪҡгҖӮжӣҙж №жң¬зҡ„жҳҜпјҢжІЎжңүе…¬ејҖзҡ„зӣ‘з®Ўжӯ§и§Ҷжң¬иә«е№¶дёҚиғҪж¶ҲйҷӨеҗҲ规жҲҗжң¬гҖӮжӯЈжҳҜжі•еҫӢеҲ¶еәҰзҡ„е·®ејӮдҪҝеҫ—жҹҗдәӣдәӨжҳ“зҡ„жү§иЎҢжҲҗжң¬иҝҮй«ҳвҖ”вҖ”еҚідҪҝиҝҷз§Қе·®ејӮжҳҜеҮәдәҺе®Ңе…ЁиүҜжҖ§зҡ„еҺҹеӣ еҮәзҺ°зҡ„гҖӮ
иҰҒеҪ»еә•ж¶ҲйҷӨзӣ‘з®ЎйҡңзўҚпјҢдё–з•Ңе°Ҷеҝ…йЎ»еҸ—еҲ°дёҖеҘ—жі•еҫӢ规еҲҷзҡ„з®Ўиҫ–пјҢе°ұеғҸеҗ„еӣҪеёӮеңәдёҖж ·гҖӮйҷӨжӯӨд№ӢеӨ–пјҢй—®йўҳеңЁдәҺ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з”ұи®ёеӨҡдёҚеҗҢж”ҝдҪ“з»„жҲҗзҡ„дё–з•ҢйҮҢпјҢеҰӮдҪ•жүҚиғҪеҮҸе°‘дёҚеҗҢзӣ‘з®ЎеҲ¶еәҰйҖ жҲҗзҡ„ж‘©ж“ҰгҖӮжҳҫ然пјҢ并дёҚжҳҜжүҖжңүзҡ„法规йғҪдјҡеңЁиҝҷдәӣеҠӘеҠӣдёӯеҸ‘жҢҘеҗҢж ·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
еҮҸе°‘зӣ‘з®ЎеЈҒеһ’зҡ„е·Ҙе…·жҳҜеӨҡж ·зҡ„гҖҒйҮҚеҸ зҡ„пјҢиҖҢдё”еӨ§еӨҡжҳҜеҲҶж•Јзҡ„гҖӮж”ҝеәңжң¬иә«еҸҜд»ҘеҜ№ж–°з«Ӣжі•зҡ„иҙёжҳ“еҪұе“ҚиҝӣиЎҢжӣҙдёҘж јзҡ„е®ЎжҹҘгҖӮеҜ№иў«з§°дёәзӣ‘з®ЎеҪұе“ҚиҜ„дј°(RIA)зҡ„ж–°жі•еҫӢ规еҲҷзҡ„з»ҸжөҺеҪұе“ҚиҝӣиЎҢе®ЎжҹҘе·Із»ҸзӣёеҪ“жҷ®йҒҚвҖ”вҖ”дҫӢеҰӮпјҢеңЁзҫҺеӣҪпјҢжҸҗеҮә新规еҲҷзҡ„иҒ”йӮҰжңәжһ„иў«иҰҒжұӮиҜҒжҳҺе…¶дә§з”ҹзҡ„з»ҸжөҺж•ҲзӣҠи¶…иҝҮжҲҗжң¬пјҢиҖҢдё”иҜҘжҺӘж–ҪзӣёеҜ№дәҺе…¶жӣҝд»ЈжҺӘж–ҪжқҘиҜҙдјјд№ҺжҳҜжңүеҲ©зҡ„пјҢеҢ…жӢ¬д»Җд№ҲйғҪдёҚеҒҡгҖӮ
然иҖҢ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е°‘ж•°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иҝҷз§ҚиҜ„дј°жүҚжҳҺзЎ®дҫ§йҮҚдәҺзӣ‘з®ЎйҖ жҲҗзҡ„иҙёжҳ“еҪұе“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з»ҸжөҺеҗҲдҪңдёҺеҸ‘еұ•з»„з»Ү(з»ҸеҗҲз»„з»Ү)жҠҘе‘ҠиҜҙпјҢвҖңд»Һи®ҫи®Ўе’Ңзӣ®зҡ„дёҠи®ІпјҢеӣҪеҶ…RIAжҳҜдёҖз§ҚдҪҝеӣҪ家зҰҸеҲ©жңҖеӨ§еҢ–зҡ„е·Ҙе…·гҖӮдёәжӯӨпјҢRIAйҖҡеёёеңЁеӣҪеҶ…еұӮйқўеҜ№зӣ‘з®ЎжҸҗжЎҲзҡ„еҪұе“ҚиҝӣиЎҢиҜ„дј°е’Ңе»әжЁЎгҖӮе®ғ们еҫҲе°‘иҜ„дј°и¶…и¶ҠеӣҪз•Ң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жӣҙж №жң¬зҡ„жҳҜпјҢе®ғ们еҫҖеҫҖдёҚиҜ„дј°й’ҲеҜ№е…¶д»–еҸёжі•з®Ўиҫ–еҢәзұ»дјјжі•и§„зҡ„зӣ‘з®Ўе»әи®®вҖңгҖӮ
жӯӨеӨ–пјҢе°Ҫз®ЎRIAжҳҜдёәиҜ„дј°еҚ•дёӘзӣ‘з®Ўе»әи®®иҖҢиҝӣиЎҢзҡ„пјҢдҪҶиҙёжҳ“е•ҶйҖҡеёёе…іеҝғзӣ‘з®ЎзҺҜеўғ(еҚіпјҢзү№е®ҡиЎҢдёҡзҡ„法规гҖҒж ҮеҮҶе’Ңжі•еҫӢзҡ„жҖ»е’Ң)еҜ№иҙёжҳ“зҡ„ж•ҙдҪ“еҪұе“ҚгҖӮ
з§ҒиҗҘйғЁй—ЁйҖҡиҝҮж¶өзӣ–и®ёеӨҡдёҚеҗҢиЎҢдёҡзҡ„еӣҪйҷ…ж ҮеҮҶйҷҚдҪҺдәҶдёҖдәӣеҗҲ规жҲҗжң¬пјҢд»Һз”өеҷЁеҲ°йЈҹе“ҒеҠ е·ҘпјҢиҒ”еҗҲеӣҪзІ®йЈҹеҸҠеҶңдёҡз»„з»Үе’Ңдё–з•ҢеҚ«з”ҹз»„з»Үе…ұеҗҢеҲ¶е®ҡдәҶдёҖд»Ҫе…Ёйқўзҡ„гҖҒе…ЁзҗғдёҖиҮҙйҒөе®Ҳзҡ„йЈҹе“Ғжі•е…ёгҖӮжҠҖжңҜж ҮеҮҶеҢ–жҳҜиҮӘж„ҝзҡ„пјҢж—ЁеңЁзЎ®дҝқйҒөе®ҲдёҚеҗҢеӣҪ家зҺ°жңүзҡ„жӣҙй«ҳзә§еҲ«зҡ„гҖҒе…·жңүжі•еҫӢзәҰжқҹеҠӣзҡ„法规гҖӮдёәдәҶдҪҝиҙёжҳ“жӣҙдҫҝеҲ©пјҢж ҮеҮҶдёҚд»…еҝ…йЎ»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дё”иҝҳеҝ…йЎ»еҫ—еҲ°еӣҪ家法规зҡ„жүҝи®ӨпјҢдҪңдёәйҒөе®Ҳзҡ„е……еҲҶжқЎд»¶гҖӮе…¬еҸёеҸҜд»ҘиҮӘз”ұең°дҫқиө–иҝҷж ·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еҝҪз•Ҙе®ғ们пјҢзӣҙжҺҘйҒөе®ҲйҖӮз”ЁдәҺжҜҸдёӘеӣҪ家зҡ„жі•еҫӢ规еҲҷпјҢиҝҷйҖҡеёёиҰҒжҳӮиҙөеҫ—еӨҡгҖӮ
жҠҖжңҜж ҮеҮҶжңүеҪұе“Қеҗ—пјҹеӣҪйҷ…ж ҮеҮҶеҢ–з»„з»Ү(ISO)9000ж ҮеҮҶзҡ„жҺЁе№ҝеҜ№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зҡ„еҮәеҸЈдә§з”ҹ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з§ҜжһҒеҪұе“Қ(Cloughertyе’ҢGrajekпјҢ2008е№ҙ)гҖӮOECD 2010е№ҙзҡ„дёҖд»ҪжҠҘе‘Ҡз ”з©¶дәҶOECDдә”дёӘжҲҗе‘ҳеӣҪ(еҠ жӢҝеӨ§гҖҒ欧зӣҹгҖҒйҹ©еӣҪгҖҒеўЁиҘҝе“Ҙе’ҢзҫҺеӣҪ)зҡ„家用з”өеҷЁгҖҒеӨ©з„¶ж°”е’Ңз”өиҜқеҗ¬зӯ’пјҢеҸ‘зҺ°еҗ„еӣҪзӣ‘з®Ўжңәжһ„(FliessгҖҒGonzalesгҖҒKimе’ҢSchon-Field2010)еҜ№жҠҖжңҜж ҮеҮҶзҡ„е®һиҙЁжҖ§и®ӨеҸҜжҳҜжңүиҜҒжҚ®зҡ„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з”өзЈҒеңәеёҰжқҘзҡ„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е’Ңз”өзЈҒе…је®№жҖ§зӣ‘з®Ўж–№йқўпјҢиҝҷдәӣйғҪеҸҚжҳ дәҶеӣҪйҷ…з”өе·Ҙ委е‘ҳдјҡзҡ„ж ҮеҮҶгҖӮиҷҪ然иҝҷиЎЁжҳҺж ҮеҮҶзҡ„еӯҳеңЁзЎ®е®һдҝғиҝӣдәҶиҙёжҳ“пјҢдҪҶе®ғд№ҹжҸҗйҶ’дәә们пјҢ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еҫҲе°‘жүҝи®Өеҗ„з§ҚдёҚеҗҢ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д»ҺиҖҢжҺ’йҷӨдәҶе®ғ们д№Ӣй—ҙзҡ„з«һдәүпјҢ并巩еӣәдәҶж ҮеҮҶеҢ–жңәжһ„дҪңдёәдәӢе®һдёҠзҡ„еһ„ж–ӯиҖ…зҡ„ең°дҪҚгҖӮ
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еҸҜз”ЁжқҘеҮҸе°‘иҙёжҳ“з®ЎеҲ¶еЈҒеһ’зҡ„дёӨдёӘдё»иҰҒжӯЈејҸе·Ҙе…·жҳҜеҚҸи°ғпјҲharmonizationпјү(е’Ңзӣёе…ізҡ„и°ғж•ҙпјҲalignmentпјүзҗҶеҝө)е’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пјҲmutualrecognitionпјүгҖӮеҚҸи°ғиҰҒжұӮеҗ„еӣҪж”ҝеәңе°ұе…¶з®Ўиҫ–иҢғеӣҙеҶ…йҖҡз”Ёзҡ„гҖҒз»ҹдёҖйҖӮз”Ёзҡ„规еҲҷиҫҫжҲҗдёҖиҮҙгҖӮи°ғж•ҙж¶үеҸҠеҲ°еӣҪеҶ…зӣ‘з®Ўзі»з»ҹйҖҗжӯҘжҺҘиҝ‘еӨ–еӣҪжҲ–еӣҪйҷ…规иҢғ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зҡ„жғіжі•ж—ўеҸҜд»Ҙеә”з”ЁдәҺз¬ҰеҗҲжҖ§иҜ„дј°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жӣҙйӣ„еҝғеӢғеӢғең°еә”з”ЁдәҺжі•еҫӢ规еҲҷжң¬иә«гҖӮеҚҸи°ғе’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йғҪжҳҜеңЁдёҚеҗҢ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дә§з”ҹзҡ„пјҢдҪҶеҫҖеҫҖжҳҜPTAзҡ„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гҖӮ然иҖҢпјҢеҺҹеҲҷдёҠпјҢд»»дҪ•дёҖз§ҚзҺ°иұЎйғҪеҸҜиғҪеҚ•ж–№йқўеҸ‘з”ҹпјҢж”ҝеәңиҮӘиЎҢеҶіе®ҡиҰҒд№Ҳжүҝи®Ө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иҰҒд№Ҳе°Ҷе…¶з«Ӣжі•дёҺ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Һ°жңүзҡ„з«Ӣжі•зӣёз»“еҗҲгҖӮ
йҷӨдәҶдҝғиҝӣиҙёжҳ“(OreficeзӯүдәәпјҢ2012е№ҙ)пј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иҝҳе…·жңүдҝқеӯҳдёҚеҗҢзӣ‘管规иҢғеӨҡж ·жҖ§е’Ңдҝғиҝӣе®ғ们д№Ӣй—ҙиүҜжҖ§з«һдәүзҡ„йўқеӨ–дјҳеҠҝгҖӮ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еҚҸи°ғеҫҲе®№жҳ“еҸҳеҫ—з¬ЁжүӢз¬Ёи„ҡпјҢиҖҢдё”дәӢдёҺж„ҝиҝқ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ңЁ20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пјҢ欧зӣҹз»Ҹеёёеӣ е…¶жӢҶйҷӨиҙёжҳ“еЈҒеһ’зҡ„ж–№жі•иҖҢеҸ—еҲ°еҳІз¬‘пјҢиҝҷз§Қж–№жі•ж¶үеҸҠеҲ°еҜ№дә§е“ҒеёӮеңәиҝӣиЎҢиҜҰз»Ҷзҡ„жҠҖжңҜзӣ‘з®ЎгҖӮйҡҸзқҖ1985е№ҙж–°зӣ‘з®Ўж”ҝзӯ–зҡ„еҮәеҸ°пјҢ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е·Із»ҸеҮҸе°‘пјҢ欧жҙІз«Ӣжі•еҸӘжҳҫзӨәдәҶе…¬е…ұж”ҝзӯ–зӣ®ж Үзҡ„еӨ§иҮҙиҪ®е»“пјҢиҖҢеҪ“ж—¶зҡ„з»ҶиҠӮйҖҡеёёз•ҷз»ҷиҮӘж„ҝзҡ„жҠҖжңҜж ҮеҮҶ(Pelkmans1987)гҖӮжҲ–иҖ…пјҢеңЁж¬§зӣҹжі•еҫӢи®ҫе®ҡзҡ„е№ҝжіӣеҸӮж•°иҢғеӣҙеҶ…пјҢжҲҗе‘ҳеӣҪеҸҜд»ҘиҮӘиЎҢз«Ӣжі•пјҢе°Ҫз®Ўе®ғ们вҖңдёҚиғҪе°ҶеӣҪ家зӣ‘з®Ўзҡ„жҹҗдәӣе…·дҪ“з»ҶиҠӮеә”з”ЁдәҺ欧зӣҹеҶ…йғЁзҡ„е•Ҷе“ҒиҝӣеҸЈпјҢеүҚжҸҗжҳҜе…¶д»–жҲҗе‘ҳеӣҪзҡ„зӣёе…іжі•еҫӢзҡ„зӣ®ж ҮжҲ–ж•ҲжһңдёҺиҝӣеҸЈеӣҪзҡ„зӣ®ж ҮжҲ–ж•ҲжһңзӣёеҪ“гҖӮвҖқ(Pelkmans2002пјҢ第3йЎө)гҖӮ
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е’ҢеҚҸи°ғдёҚжҳҜзҰ»ж•Јзҡ„гҖҒжҺ’д»–жҖ§зҡ„йҖүжӢ©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е®ғ们жҳҜзӣёиҫ…зӣёжҲҗзҡ„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дёҖеұӮе…ұеҗҢзҡ„欧жҙІи§„еҲҷпјҢе»әз«ӢеңЁ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еҺҹеҲҷдёҠзҡ„欧зӣҹеҚ•дёҖеёӮеңәеңЁж”ҝжІ»дёҠжҳҜдёҚеҸҜжҢҒз»ӯзҡ„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еңЁжҲҗе‘ҳеӣҪзӣ‘з®Ўж–№ејҸеӯҳеңЁйҮҚеӨ§е·®ејӮзҡ„иЎҢдёҡ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ңҚеҠЎдёҡпјҢ欧зӣҹзҡ„еёӮеңәд»Қ然ж”ҜзҰ»з ҙзўҺгҖӮеңЁйҒөе®ҲеӨ§зӣёеҫ„еәӯзҡ„规еҲҷзҡ„дёҚеҗҢжі•еҹҹд№Ӣй—ҙпјҢжҲҗеҠҹзҡ„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е®үжҺ’зҡ„дҫӢеӯҗеҜҘеҜҘж— еҮ гҖӮдҫӢеҰӮпјҢ1998е№ҙпјҢзҫҺеӣҪе’Ң欧зӣҹзј”з»“дәҶдёҖйЎ№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еҚҸи®®пјҢж¶өзӣ–з”өдҝЎи®ҫеӨҮгҖҒз”өзЈҒе…је®№жҖ§гҖҒз”өж°”е®үе…ЁгҖҒеЁұд№җе·Ҙиүәе“ҒгҖҒеҲ¶иҚҜе’ҢеҢ»з–—еҷЁжў°гҖӮ然иҖҢпјҢеңЁе®һи·өдёӯпјҢиҜҘеҚҸи®®зҡ„ж•Ҳз”Ёе·Іиў«иҜҒжҳҺжҳҜжңүйҷҗ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еӨ§иҘҝжҙӢдёӨеІёзҡ„зӣ‘з®ЎеҒҡ法继з»ӯеӯҳеңЁеҲҶжӯ§гҖӮ
йҷӨдәҶ欧зӣҹзҡ„еҚ•дёҖеёӮеңәпјҢи·ЁеЎ”ж–ҜжӣјпјҲTrans-Tasmanпјү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е®үжҺ’еҸҜиғҪжҸҗдҫӣдәҶе…ідәҺиҙ§зү©и§„еҲҷ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зҡ„е”ҜдёҖеҸҰдёҖдёӘдҫӢеӯҗгҖӮе…¶е…ій”®еҺҹеҲҷдёҺ欧зӣҹеҚ•дёҖеёӮеңәзҡ„жғ…еҶөзӣёеҗҢпјҡвҖңеңЁд»»дҪ•жҫіеӨ§еҲ©дәҡеҪ“дәӢдёҖж–№зҡ„з®Ўиҫ–иҢғеӣҙеҶ…еҸҜд»ҘеҗҲжі•й”Җе”®зҡ„е•Ҷе“ҒеҸҜд»ҘеңЁж–°иҘҝе…°й”Җе”®пјҢеңЁж–°иҘҝе…°еҗҲжі•й”Җе”®зҡ„е•Ҷе“ҒеҸҜд»ҘеңЁд»»дҪ•жҫіеӨ§еҲ©дәҡдёҖж–№зҡ„з®Ўиҫ–иҢғеӣҙеҶ…й”Җе”®гҖӮиҙ§зү©еҸӘйңҖз¬ҰеҗҲе…¶з”ҹдә§ең°жҲ–иҝӣеҸЈең°йҖӮз”Ёзҡ„ж ҮеҮҶжҲ–法规гҖӮвҖқ
иҷҪ然еӯҳеңЁдёҖдәӣдҫӢеӨ–пјҢдҪҶиҝҷдёҖе®үжҺ’жҳҜд»Һеҹәжң¬дёҠж— жқЎд»¶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зҡ„жҺЁе®ҡејҖе§Ӣзҡ„гҖӮдҪҶжҫіеӨ§еҲ©дәҡе’Ңж–°иҘҝе…°зҡ„жғ…еҶөеҫҲзӢ¬зү№гҖӮдёҺеҜ»жұӮеӨҚеҲ¶жӯӨзұ»е®үжҺ’зҡ„е…¶д»–иҙёжҳ“йӣҶеӣўдёҚеҗҢпјҢдёӨеӣҪжӢҘжңүе…ұеҗҢзҡ„жі•еҫӢе’Ңж”ҝжІ»дј з»ҹпјҢ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ж°ҙе№ізӣёеҪ“пјҢжІЎжңүиҜӯиЁҖжҲ–ж–ҮеҢ–йҡңзўҚпјҢ并дҝғиҝӣдәҶзӣ‘з®Ўжңәжһ„д№Ӣй—ҙзҡ„з§ҜжһҒиҒ”зі»гҖӮ
еҪ“еҹәзЎҖзӣ‘з®Ўе·Із»ҸеҫҲдёҘеҜҶж—¶пјҢжҲ–иҖ…еҪ“е®ғйҖӮз”ЁдәҺзӣ‘з®Ўиҫғе®Ҫжқҫзҡ„з»ҸжөҺйғЁй—Ёж—¶пј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ж•ҲжһңжңҖеҘҪгҖӮйӮЈж—¶пјҢ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зҡ„з»ҸжөҺеҲ©зӣҠд№ҹе°ҶжҳҜйҖӮеәҰзҡ„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еҪ“зӣёдә’жүҝи®Өиў«ејәеҠ еңЁ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„зӣ‘з®ЎеҲ¶еәҰдёҠж—¶пјҢеҫҖеҫҖдјҡз“Ұи§ЈжҲ–дә§з”ҹеҚҸи°ғзҡ„еҺӢеҠӣ(Davies 2006)гҖӮ
然иҖҢпјҢзӣ‘з®ЎејӮиҙЁжҖ§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дёҖдёӘйңҖиҰҒжңҖе°ҸеҢ–зҡ„жҲҗжң¬гҖӮдёҚеҗҢзҡ„зӣ‘管规иҢғе’ҢеҒҡжі•йҖҡеёёжңүе®Ңе…ЁиүҜжҖ§зҡ„зҗҶз”ұвҖ”вҖ”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дёҚеҗҢзҡ„ж”ҝзӯ–еҒҸеҘҪгҖӮиҝҷз§ҚеӨҡж ·жҖ§иҝҳеҲӣйҖ дәҶиҮӘ然е®һйӘҢпјҢеё®еҠ©еӯҰиҖ…е’Ңж”ҝзӯ–еҲ¶е®ҡиҖ…дәҶи§Јд»Җд№ҲжҳҜжңүж•Ҳзҡ„пјҢд»Җд№ҲжҳҜж— ж•Ҳзҡ„гҖӮ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е…Ёзҗғзӣ‘з®ЎеҚ•дёҖж–ҮеҢ–еҸҜиғҪжҲҗдёәж„ҸжғідёҚеҲ°зҡ„и„ҶејұжҖ§зҡ„жқҘжәҗпјҢе°ұеғҸ2008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жңҹй—ҙдёҖж ·гҖӮ
еӣӣгҖҒеҚұйҷ©зҡ„иҙёжҳ“ж”ҝжІ»
дё№е°јВ·зҪ—еҫ·йҮҢе…Ӣ(DaniRodrik)еңЁд»–зҡ„ж–°д№Ұдёӯи®Ёи®әдәҶд»–дёҺеӯҰз”ҹ们дёҖиө·иҝӣиЎҢзҡ„дёҖдёӘжҖқз»ҙе®һйӘҢгҖӮеҒҮи®ҫзҪ—еҫ·йҮҢе…ӢвҖңжңүиғҪеҠӣд»Һе°јеҸӨжӢүж–Ҝ(д»–зҡ„дёҖдёӘеӯҰз”ҹ)зҡ„银иЎҢиҙҰжҲ·дёҠиөҡеҲ°200зҫҺе…ғ--з °пјҒ--еҗҢж—¶еҸҲз»ҷзәҰзҝ°(еҸҰдёҖдёӘеӯҰз”ҹ)еўһеҠ дәҶ300зҫҺе…ғпјҢиҝҷе°ҶдҪҝж•ҙдёӘзҸӯзә§зҡ„收е…ҘеўһеҠ 100зҫҺе…ғгҖӮвҖқ(зҪ—еҫ·йҮҢе…ӢпјҢ2018е№ҙ)жҜ«дёҚеҘҮжҖӘпјҢиҝҷз§ҚжӯҰж–ӯзҡ„收е…ҘеҶҚеҲҶй…ҚпјҢеҚідҪҝе®ғдҪҝж•ҙдёӘзӨҫдјҡеҸҳеҫ—жӣҙеҘҪпјҢд№ҹдјҡдёҺеӨ§еӨҡж•°дәәзҡ„йҒ“еҫ·зӣҙи§үж јж јдёҚе…ҘгҖӮе…ій”®й—®йўҳжҳҜиҝҷз§ҚеҸҳеҢ–жҳҜеҰӮдҪ•еҸ‘з”ҹзҡ„гҖӮеҰӮжһңе°јеҸӨжӢүж–Ҝе’ҢзәҰзҝ°з»ҸиҗҘз«һдәүжҝҖзғҲзҡ„дјҒдёҡпјҢиҖҢзәҰзҝ°е·ҘдҪңжӣҙеҠӘеҠӣпјҢжҠ•иө„жӣҙеӨҡпјҢжӣҙе…·еҲӣж–°жҖ§пјҢ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дәәдјҡд»Ӣж„Ҹе°јеҸӨжӢүж–ҜжҚҹеӨұ200зҫҺе…ғпјҢиў«иө¶еҮәдјҒдёҡгҖӮдҪҶвҖңеҒҮи®ҫзәҰзҝ°д»Һеҫ·еӣҪиҝӣеҸЈжӣҙй«ҳиҙЁйҮҸзҡ„жҠ•е…Ҙе“ҒпјҢеҜјиҮҙе°јеҸӨжӢүж–Ҝз ҙдә§е‘ўпјҹвҖқйҖҡиҝҮеӨ–еҢ…з»ҷеҠіе·ҘжқғзӣҠеҫ—дёҚеҲ°еҫҲеҘҪдҝқжҠӨзҡ„еӣҪ家пјҹеңЁеҚ°е°јйӣҮдҪЈз«Ҙе·ҘпјҹйҡҸзқҖиҝҷдәӣйҖүжӢ©дёӯзҡ„жҜҸдёҖдёӘпјҢеҜ№жҸҗи®®зҡ„ж”№еҸҳзҡ„ж”ҜжҢҒзҺҮ(еңЁзҸӯзә§дёӯ)йғҪдёӢйҷҚдәҶ(еҗҢдёҠпјҢ第121йЎө)гҖӮ
еҪ“然пјҢиҝҷ并дёҚж„Ҹе‘ізқҖиҝҷз§ҚеӨ–еҢ…жҳҜдёҚеҸҜеҸ–зҡ„пјҢеҸӘжҳҜе®ғеҸҜд»ҘеҗҜеҠЁйҡҫд»ҘжҺ§еҲ¶зҡ„ж”ҝжІ»еҠЁжҖҒгҖӮ
жҜ«ж— з–‘й—®пјҢдёӯеӣҪеҮәеҸЈеҜјеҗ‘еһӢеҲ¶йҖ дёҡзҡ„еҙӣиө·з»ҷ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зҡ„дҪҺи–Әе·Ҙдәәе’Ңиҙ«з©·еӣҪ家зҡ„дҪҺ收е…Ҙж¶Ҳиҙ№иҖ…еёҰжқҘ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еҘҪеӨ„гҖӮжІғе°”зҺӣдёҘйҮҚдҫқиө–дёӯеӣҪеҲ¶йҖ дёҡзҡ„е•ҶдёҡжЁЎејҸпјҢеңЁж•ҙдёӘ21дё–зәӘеӨҙ10е№ҙйҮҢпјҢеңЁзҫҺеӣҪеҮҸе°‘иҙ«еӣ°ж–№йқў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(FurmanпјҢ2005)гҖӮж №жҚ®дёҖйЎ№з ”з©¶пјҢвҖңдёӯеӣҪеҠ е…Ҙ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дҪҝзҫҺеӣҪеҲ¶жҲҗе“Ғд»·ж јжҢҮж•°дёӢйҷҚдәҶгҖӮ7.6%пјҢ2000еҲ°2006е№ҙй—ҙе№іеқҮжҜҸе№ҙеңЁ1%е·ҰеҸігҖӮ(AmitiпјҢDaiпјҢFeenstraпјҢand Romalis 2018пјҢ第3йЎө)гҖӮ
然иҖҢпјҢеҶҚеҠ дёҠиҮӘеҠЁеҢ–пјҢдёӯеӣҪеҮәеҸЈз»ҷзҫҺеӣҪзҡ„е·Ҙиө„е’ҢеҲ¶йҖ дёҡеёҰжқҘдәҶдёӢиЎҢеҺӢеҠӣпјҢ1999е№ҙиҮі2011е№ҙй—ҙпјҢеҸҜиғҪжңүеӨҡиҫҫ240дёҮдёӘзҫҺеӣҪе·ҘдҪңеІ—дҪҚиў«жҜҒгҖӮе°Ҫз®ЎзҫҺеӣҪжңҚеҠЎеҮәеҸЈзҡ„еўһй•ҝзӣ–иҝҮдәҶиҝҷдёҖеҺӢеҠӣпјҢеҜјиҮҙдәҶеҠіеҠЁеҠӣйңҖжұӮзҡ„еҮҖеўһй•ҝ(Feenstraе’ҢSasahara 2017)пјҢдҪҶе®ғ并没жңүеҜјиҮҙе·Ҙдәәд»ҺеҲ¶йҖ дёҡеҗ‘жңҚеҠЎдёҡзҡ„з®ҖеҚ•иҝҮжёЎвҖ”вҖ”зӣёеҸҚпјҢе®ғз•ҷдёӢдәҶзҫҺеӣҪзӣёеҪ“еӨ§дёҖйғЁеҲҶеӨ„дәҺеҠіеҠЁе№ҙйҫ„дәәеҸЈзҡ„еӨұдёҡгҖӮ
иҝҷдёҖз»“жһң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дёӯеӣҪеӣәжңүзҡ„жҲҗжң¬дјҳеҠҝжҲ–дјҒдёҡ家зҡ„зІҫжҳҺжүҖиҮҙгҖӮз”ұдәҺйҡҗжҖ§е’ҢжҳҫжҖ§зҡ„иЎҘиҙҙпјҢд»ҘеҸҠз»ҷдәҲдёӯеӣҪеӣҪжңүе’ҢдёҺеӣҪ家жңүе…іиҒ”зҡ„е…¬еҸёзҡ„еҗ„з§Қзү№жқғпјҢиҘҝж–№е…¬еҸёеҫҖеҫҖдёҚеҸҜиғҪеңЁдёӯеӣҪеёӮеңәдёҠз«һдәүгҖӮдёӯеӣҪдҪҝз”Ёзҡ„ж”ҜжҢҒеҪўејҸвҖ”вҖ”д»ҺеӣҪжңү银иЎҢж…·ж…Ёзҡ„дҝЎиҙ·ж”ҝзӯ–пјҢеҲ°з ҙдә§дјҒдёҡдёҚдјҡз ҙдә§иҖҢжҳҜдёҺе…¶д»–еӣҪжңүе®һдҪ“еҗҲ并гҖҒдә«жңүеӣҪ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зү№жқғдҪҝз”ЁжқғпјҢеҶҚеҲ°жҷ®йҒҚиҝқеҸҚзҹҘиҜҶдә§жқғ规еҲҷвҖ”вҖ”еңЁзӢӯйҡҳзҡ„WTO规еҲҷдёӢдёҚе®№жҳ“еҸ—еҲ°жҢ‘жҲҳгҖӮ
ж”ҜжҢҒ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зҡ„дәәеҸҜиғҪдјҡеҜ№иҝҷдәӣжү№иҜ„дёҚеұ‘дёҖйЎҫгҖӮзҡ„зЎ®пјҢеҰӮжһңдёӯеӣҪж”ҝеәңжғіиҰҒжүӯжӣІеӣҪ家з»ҸжөҺпјҢзҫҺеӣҪдәәдёәд»Җд№ҲиҰҒеңЁж„Ҹе‘ўпјҹдҪҶйҖүж°‘еҜ№дәӢжғ…зҡ„зңӢжі•дёҚеҗҢгҖӮ2017е№ҙзҡ„дёҖйЎ№з ”з©¶еҸ‘зҺ°пјҢеңЁдёҖзі»еҲ—еӣҪдјҡе’ҢжҖ»з»ҹйҖүдёҫдёӯпјҢвҖңжңҖеҲқзҷҪдәәеҚ еӨҡж•°жҲ–жңҖеҲқжҺҢжҸЎеңЁе…ұе’Ңе…ҡжүӢдёӯзҡ„еҸ—иҙёжҳ“еҪұе“Қзҡ„йҖүеҢәпјҢеңЁе®һиҙЁдёҠжӣҙжңүеҸҜиғҪйҖүдёҫдҝқе®Ҳжҙҫе…ұе’Ңе…ҡдәәпјҢиҖҢжңҖеҲқеҚ еӨҡж•°зҡ„е°‘ж•°ж—ҸиЈ”дәәеҸЈжҲ–жңҖеҲқжҺҢжҸЎеңЁж°‘дё»е…ҡжүӢдёӯзҡ„еҸ—иҙёжҳ“еҪұе“Қзҡ„йҖүеҢәпјҢд№ҹеҸҳеҫ—жӣҙжңүеҸҜиғҪйҖүдёҫиҮӘз”ұж°‘дё»е…ҡдәәвҖқпјҢд»ҺиҖҢеҸ–д»Јжӣҙжё©е’Ңзҡ„еҖҷйҖүдәә(Autorе’ҢMajlesi 2017)гҖӮдёҚд»…еӣ дёәдёӯеӣҪзҡ„з«һдәү(Bisbee 2018)пјҢиҙёжҳ“й—®йўҳйҮҚж–°еӣһеҲ°дәҶйҖүдёҫзҡ„иҒҡе…үзҒҜдёӢпјҢжӣҙд»ӨдәәдёҚе®үзҡ„жҳҜпјҢдёӯеӣҪиҝӣеҸЈе•Ҷе“Ғеј•еҸ‘зҡ„з»ҸжөҺеҶІеҮ»вҖң(й©ұдҪҝ)дәҶдәә们еҜ№з§»ж°‘е’Ңе°‘ж•°ж—ҸиЈ”зҡ„иҙҹйқўжҖҒеәҰгҖӮвҖқ(CerratoпјҢFerraraе’ҢRuggieri2018)гҖӮ
иҝҷдәӣдәӢжҖҒеҸ‘еұ•зҡ„ж•ҷи®ӯд№ӢдёҖпјҢдёҺе…¶иҜҙдёҺдёӯеӣҪжңүе…іпјҢдёҚеҰӮиҜҙжҳҜеңЁз»ҸжөҺзҺҜеўғеҸ‘з”ҹйҮҚеӨ§е’ҢжҪңеңЁз ҙеқҸжҖ§еҸҳеҢ–ж—¶пјҢи®©е…¬дј—жӢҘжңүеҸӮдёҺеҸҠеҸ‘иЁҖзҡ„жқғеҲ©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гҖӮеңЁж”Ҝж’‘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зҡ„зҺ°жңүжңәжһ„еҶ…еҹ№е…»еҹәжң¬зҡ„е…¬е№іж„ҹе’ҢйҖҸжҳҺеәҰд№ҹиҮіе…ійҮҚиҰҒгҖӮдҫӢеҰӮпјҢISDSжІЎжңүзҗҶз”ұдёҚеҗ‘еӨ–еӣҪе…¬еҸёд»ҘеӨ–зҡ„е…¶д»–еҸ—еҪұе“ҚиҖ…ејҖж”ҫпјҢеҢ…жӢ¬еӣҪеҶ…е…¬еҸёгҖҒж¶Ҳиҙ№иҖ…жҲ–жңүз»„з»Үзҡ„еҠіе·Ҙ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иҰҶзӣ–еӨ§йҮҸеӣҪеҶ…ж”ҝзӯ–зҡ„еҪұе“Қж·ұиҝңзҡ„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дёҚиғҪиў«и§ҶдёәзәҜзІ№зҡ„жҠҖжңҜжј”д№ пјҢйў„и®Ўе…¬дј—дјҡй»ҳи®ёгҖӮ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пјҢдҝқжҢҒе…¬дј—еҜ№иҮӘз”ұиҙёжҳ“зҡ„ж”ҜжҢҒйңҖиҰҒжӣҙеҘҪзҡ„еӣҪеҶ…ж”ҝзӯ–пјҢд»ҘзЎ®дҝқжІЎжңүдәәвҖңжҺүйҳҹвҖқгҖӮжңҖзӘҒеҮәзҡ„жҳҜпјҢиҝҷеҢ…жӢ¬ж…·ж…Ёзҡ„зӨҫдјҡдҝқйҡңзҪ‘з»ңпјҢж—ўиЎҘеҒҝиҙёжҳ“зҡ„иҫ“家(е°ұиҝҷдёҖзӮ№иҖҢиЁҖпјҢд№ҹеҢ…жӢ¬жқҘиҮӘжҷәиғҪжңәеҷЁзҡ„з«һдәү)пјҢ并帮еҠ©д»–们йҮҚе»әиҒҢдёҡз”ҹжҙ»гҖӮ
иҮӘ第дәҢ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з»“жқҹд»ҘжқҘпјҢејҖж”ҫе…ЁзҗғеёӮеңәз»ҷдәәзұ»еёҰжқҘдәҶйқһеҮЎзҡ„з»ҸжөҺеҲ©зӣҠпјҢиҝҷдёҖзӮ№жҜӢеәёзҪ®з–‘гҖӮиҝҷз§ҚејҖж”ҫжҳҜеҸІж— еүҚдҫӢзҡ„пјҢжҳҜжӯЈејҸжңәжһ„е»әз«Ӣ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…іиҙёжҖ»еҚҸе®ҡгҖҒдё–иҙёз»„з»Үе’ҢеҢәеҹҹз»ҸжөҺдёҖдҪ“еҢ–йЎ№зӣ®зҡ„еӨҡиҫ№дҪ“зі»гҖӮеңЁжҢҒз»ӯдёҚж–ӯзҡ„еҺӢеҠӣдёӢпјҢеҲ°зӣ®еүҚдёәжӯўпјҢзҺ°жңүзҡ„еҲ¶еәҰиў«иҜҒжҳҺжҳҜжңүйҹ§жҖ§зҡ„вҖ”вҖ”еҢ…жӢ¬йӮЈдәӣзңҹжӯЈж„ҡи ўзҡ„ж”ҝзӯ–пјҢжҜ”еҰӮзҺ°д»»зҷҪе®«дё»дәәпјҲзү№жң—жҷ®пјүеҖЎеҜјзҡ„йӮЈдәӣж”ҝзӯ–гҖӮдёҺиҝҮеҺ»зҡ„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жөӘжҪ®вҖ”вҖ”е°Өе…¶жҳҜдёҠ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зҡ„дҝқжҠӨдё»д№үвҖ”вҖ”е°Ҷ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жөҒеҠЁеҮҸе°‘еҲ°жҳ”ж—Ҙзҡ„йҳҙеҪұдёҚеҗҢпјҢзү№жң—жҷ®ж”ҝеәңеҒ¶е°”йҮҮеҸ–зҡ„е…ізЁҺжҺӘж–ҪеҸӘжҳҜи§ҰеҸҠдәҶеӣҪйҷ…иҙёжҳ“жөҒеҠЁзҡ„зҡ®жҜӣ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зҺ°жңүзҡ„иҙёжҳ“дҪ“зі»жҳҜеҗҰиғҪеӨҹжүҝеҸ—жҢҒз»ӯзҡ„з–«жғ…еј•еҸ‘зҡ„з»ҸжөҺеҚұжңә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еҺӢеҠӣпјҢеҲҷе®Ңе…ЁжҳҜеҸҰ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гҖӮ
|  зҫҺиҒ”еӮЁдё»еёӯйҮҚзЈ…еҸ‘еЈ°
зҫҺиҒ”еӮЁдё»еёӯйҮҚзЈ…еҸ‘еЈ°  2024е№ҙзҺүзұіеёӮеңәдҫӣйңҖеҪў
2024е№ҙзҺүзұіеёӮеңәдҫӣйңҖеҪў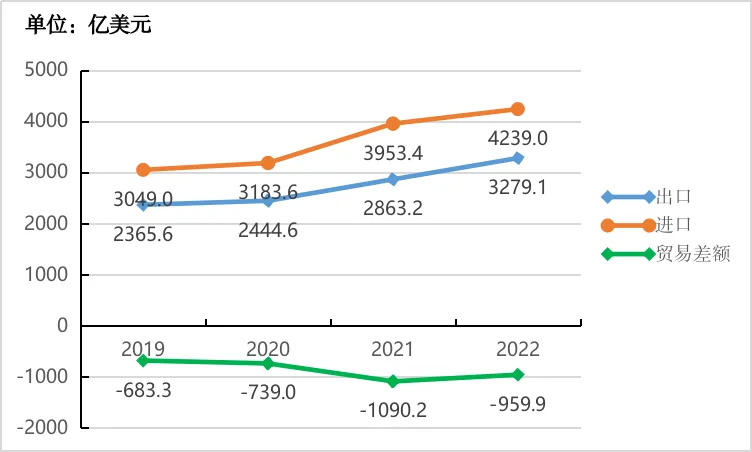 дёӯеӣҪдёҺйҮ‘з –еӣҪ家еҶңдә§е“Ғ
дёӯеӣҪдёҺйҮ‘з –еӣҪ家еҶңдә§е“Ғ еҪӯж–Үз”ҹпјҡд»Һ规模з»ҸжөҺзңӢ
еҪӯж–Үз”ҹпјҡд»Һ规模з»ҸжөҺзңӢ д№ иҝ‘е№ідё»еёӯ第е…ӯж¬ЎеҲ°и®ҝ
д№ иҝ‘е№ідё»еёӯ第е…ӯж¬ЎеҲ°и®ҝ еј дә‘еҚҺпјҡе…ідәҺзІ®йЈҹе®үе…Ё
еј дә‘еҚҺпјҡе…ідәҺзІ®йЈҹе®үе…Ё е…ЁзҗғиҪ¬еҹәеӣ зҺ°зҠ¶
е…ЁзҗғиҪ¬еҹәеӣ зҺ°зҠ¶ иҝһе№іпјҡж¶Ҳиҙ№жҸҗжҢҜпјҡйЈҺзү©
иҝһе№іпјҡж¶Ҳиҙ№жҸҗжҢҜпјҡйЈҺзү© еҲҳйҷҲжқ°пјҡ2025е№ҙе®Ҹи§Ӯз»Ҹ
еҲҳйҷҲжқ°пјҡ2025е№ҙе®Ҹи§Ӯз»Ҹ жқҺеҘҮйң–пјҡM1еўһйҖҹе№ҙеҶ…йҰ–
жқҺеҘҮйң–пјҡM1еўһйҖҹе№ҙеҶ…йҰ– еҰӮдҪ•жһ„е»әејҳжү¬ж•ҷиӮІе®¶зІҫ
еҰӮдҪ•жһ„е»әејҳжү¬ж•ҷиӮІе®¶зІҫ дёӯеӣҪе·ҘзЁӢйҷўйҷўеЈ«еӯҷе…¶дҝЎ
дёӯеӣҪе·ҘзЁӢйҷўйҷўеЈ«еӯҷе…¶дҝ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