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еј жҷ“жҷ¶пјҲ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з»ҸжөҺз ”з©¶жүҖеүҜжүҖй•ҝпјү д»Һжқ жқҶзҺҮеҸҳеҢ–зңӢ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еҠЁжҖҒе№іиЎЎ
д»Һжқ жқҶзҺҮеҸҳеҢ–жқҘзңӢпјҢ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еҠЁжҖҒ平衡并йқһжҳ“дәӢгҖӮжҲ‘们估算дәҶ1993е№ҙиҮід»Ҡ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гҖӮж №жҚ®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еҸҳеҠЁжҖҒеҠҝпјҢеҸҜе°Ҷе…¶еҲҶдёәеӣӣдёӘйҳ¶ж®өгҖӮ
дёҖжҳҜе№ізЁіеҠ жқ жқҶйҳ¶ж®өпјҲ1993пҪһ2003е№ҙпјүгҖӮжңҹй—ҙжқ жқҶзҺҮе…ұдёҠеҚҮ41.6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е№іеқҮжҜҸе№ҙеўһй•ҝ4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иҝҷж®өж—¶й—ҙеҖәеҠЎе’Ңе№ҝд№үиҙ§еёҒзҡ„еўһйҖҹиҫғй«ҳпјҢиҖҢеҗҚд№үGDPеўһйҖҹиҮӘ1997е№ҙд»ҘжқҘеҫҳеҫҠеңЁ10%йҷ„иҝ‘пјҢ1998е№ҙгҖҒ1999е№ҙжӣҙжҳҜи·ҢеҲ°7%д»ҘдёӢпјҢз”ұжӯӨеҜјиҮҙжқ жқҶзҺҮжҝҖеўһгҖӮжңҹй—ҙзҡ„дәҡжҙІ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гҖҒдә’иҒ”зҪ‘жіЎжІ«з ҙиЈӮд»ҘеҸҠйқһе…ёжҳҜиҫғеӨ§зҡ„иҙҹйқўеҶІеҮ»пјҢеҜ№зЁіеўһй•ҝеёҰжқҘиҫғеӨ§еҺӢеҠӣпјҢеӣ жӯӨжҲ‘们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ж”ҝзӯ–зҡ„з§ҜжһҒеӣһеә”д»ҘеҸҠз”ұжӯӨеёҰжқҘ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ж”ҖеҚҮгҖӮ
дәҢжҳҜвҖңиҮӘдё»вҖқеҺ»жқ жқҶйҳ¶ж®өпјҲ2003пҪһ2008е№ҙпјүгҖӮжңҹй—ҙжқ жқҶзҺҮдёӢйҷҚдәҶ8.2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иҝҷж®өж—¶й—ҙеҗҚд№үGDPй«ҳйҖҹеўһй•ҝпјҲйҷӨдәҶ2003е№ҙпјүпјҢеўһйҖҹжңҖдҪҺзҡ„е№ҙд»Ҫд№ҹиҫҫеҲ°дәҶ16%пјҢжңҖй«ҳиҫҫеҲ°23%пјҢеҗҚд№үGDPеўһйҖҹи¶…иҝҮдәҶиҙ§еёҒе’ҢеҖәеҠЎеўһйҖҹпјҢе®һдҪ“з»ҸжөҺжқ жқҶзҺҮдёӢйҷҚгҖӮиҝҷжҳҜе…Ёзҗғз»ҸжөҺеӨ§з№ҒиҚЈдёҺ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дёҠеҚҮе‘ЁжңҹзӣёйҮҚеҗҲзҡ„йҳ¶ж®өгҖӮзӣёжҜ”дәҺзҺ°йҳ¶ж®өзҡ„вҖңејәеҲ¶вҖқеҺ»жқ жқҶпјҢ2008е№ҙд№ӢеүҚзҡ„еҺ»жқ жқҶ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иҮӘдё»вҖқ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зңӢеҒҡиҫҫйҮҢеҘҘ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жјӮдә®еҺ»жқ жқҶвҖқпјҢдё»иҰҒдҫқиө–еҲҶжҜҚжү©еј еҺӢдҪҺ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ж”ҖеҚҮйҖҹеәҰпјҢиҝҷжҳҜ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еҠЁжҖҒе№іиЎЎзҡ„жңҖдҪізҠ¶жҖҒгҖӮдҪҶиҰҒеҒҡеҲ°иҝҷдёҖзӮ№е№¶дёҚе®№жҳ“гҖӮ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еҫҖеҫҖжҳҜ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з»ҸжөҺжҪңеңЁеўһйҖҹеңЁдёӢеҸ°йҳ¶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иҙ§еёҒжү©еј еҲәжҝҖеўһй•ҝзҡ„иҫ№йҷ…ж•Ҳеә”еңЁйҖ’еҮҸпјҢе®Ңе…ЁжҢҮжңӣе®Ҫжқҫиҙ§еёҒеҠ з ҒжқҘеҠ еҝ«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гҖҒеҒҡеӨ§еҲҶжҜҚйҷҚжқ жқҶдёҚе•»дёҖз§Қе№»жғігҖӮ
дёүжҳҜеҝ«йҖҹеҠ жқ жқҶйҳ¶ж®өпјҲ2008пҪһ2015е№ҙпјүгҖӮжңҹй—ҙжқ жқҶзҺҮеўһй•ҝдәҶ86.2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е№іеқҮжҜҸе№ҙеўһй•ҝи¶…иҝҮ12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2009е№ҙпјҢз”ұдәҺвҖңеӣӣдёҮдәҝвҖқзҡ„еҗҜеҠЁпјҢеҖәеҠЎеҮәзҺ°дәҶи·ғеҚҮпјҢеҪ“е№ҙеҖәеҠЎеўһйҖҹй«ҳиҫҫ34%пјҢиҖҢеҗҚд№үGDPеўһйҖҹеҲҷеӣһиҗҪиҮі9.2%пјҢйҡҸеҗҺеҖәеҠЎеўһйҖҹжҢҒз»ӯдёӢж»‘дҪҶеҗҚд№үGDPеўһйҖҹдёӢж»‘йҖҹеәҰжӣҙеҝ«пјҢ2015е№ҙеҗҚд№үGDPеўһйҖҹи·ҢеҲ°дәҶ7.0%гҖӮжң¬иҪ®еӣҪйҷ…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д»ҘжқҘзҡ„еҝ«йҖҹеҠ жқ жқҶпјҢд»ҺеҫҲеӨҡеұӮйқўжқҘзңӢпјҢйғҪжҳҜдёҖз§ҚвҖңиҝ«дёҚеҫ—е·ІвҖқпјӣдҪҶзЎ®е®һд№ҹеӯҳеңЁеңЁзЁіеўһй•ҝиҝҮзЁӢдёӯеҝҪз•ҘдәҶзЁіжқ жқҶй—®йўҳпјҢеӣ дёәзӣҙиҮі2015е№ҙ10жңҲпјҢйҷҚжқ жқҶжүҚеҮәзҺ°еңЁдёӯеӨ®еұӮйқўзҡ„и®®зЁӢдёҠгҖӮ
еӣӣжҳҜвҖңејәеҲ¶вҖқеҺ»жқ жқҶйҳ¶ж®өпјҲ2015е№ҙиҮід»ҠпјүгҖӮ2015е№ҙ10жңҲдёӯеӨ®жҸҗеҮәйҷҚжқ жқҶд»»еҠЎпјҢдҪҶ2016е№ҙжқ жқҶзҺҮд»ҚдёҠеҚҮдәҶ12.9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究其еҺҹеӣ пјҢ2016е№ҙ第дёҖеӯЈеәҰGDPеўһй•ҝ6.7%пјҢеҲӣ28дёӘеӯЈеәҰд»ҘжқҘж–°дҪҺпјҢд№ҹи®©зӣёе…іж”ҝеәңйғЁй—ЁеңЁжү§иЎҢеҺ»жқ жқҶд»»еҠЎж—¶дә§з”ҹйЎҫеҝҢпјҢжңүвҖңж”ҫж°ҙвҖқд№Ӣе«ҢгҖӮиҝҷд№ҹеҮёжҳҫеҮә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д№Ӣй—ҙзҡ„зҹӣзӣҫгҖӮ2017е№ҙжқ жқҶзҺҮд»…еўһй•ҝ3.8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2018е№ҙеҲҷеӣһиҗҪ0.3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жқ жқҶзҺҮеҝ«йҖҹж”ҖеҚҮзҡ„еұҖйқўеҫ—еҲ°дәҶжңүж•ҲжҠ‘еҲ¶гҖӮ
еҖјеҫ—ејәи°ғзҡ„жҳҜпјҢеңЁдёӯзҫҺз»Ҹиҙёж‘©ж“ҰеҠ еү§гҖҒз»ҸжөҺдёӢиЎҢеҺӢеҠӣеҠ еӨ§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2019е№ҙ第дёҖеӯЈеәҰжқ жқҶзҺҮеӨ§е№…ж”ҖеҚҮ5.1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дёҺд№ӢзӣёеҜ№еә”зҡ„жҳҜ第дёҖеӯЈеәҰ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зҡ„вҖңи¶…йў„жңҹвҖқгҖӮиҖҢ第дәҢеӯЈеәҰжқ жқҶзҺҮд»…дёҠеҚҮ0.7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жқ жқҶзҺҮеўһе№…зҡ„еӨ§е№…еӣһиҗҪпјҢе°Ҷз»ҷеҗҺз»ӯеўһй•ҝеёҰжқҘеҺӢеҠӣпјҢеҚ•еӯЈжқ жқҶзҺҮеўһе№…0.7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зҡ„жҖҒеҠҝжҒҗиҫғйҡҫжҢҒз»ӯгҖӮд»ҺжҠҠжҸЎ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е№іиЎЎзҡ„и§’еәҰпјҢйңҖиҰҒе®№еҝҚжқ жқҶзҺҮзү№еҲ«жҳҜ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ҖӮеәҰжҠ¬еҚҮпјҢеўһејәзЁіеўһй•ҝзҡ„еҠ©еҠӣгҖӮ
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дё»иҰҒй—®йўҳеңЁз»“жһ„иҖҢдёҚеңЁж°ҙе№і
еҲӨж–ӯ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ЈҺйҷ©пјҢдёҖиҲ¬еҸҜд»Ҙд»Һ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ж°ҙе№ігҖҒеўһйҖҹдёҺз»“жһ„дёүдёӘз»ҙеәҰжқҘзңӢгҖӮ
е°ұж°ҙе№іиҖҢиЁҖпјҢ2018е№ҙжҲ‘еӣҪе®һдҪ“з»ҸжөҺ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дёҚеҲ°250%пјҢдёҺзҫҺеӣҪеҫҲжҺҘиҝ‘пјҢдҪҶжҜ”еҸ‘еұ•дёӯз»ҸжөҺдҪ“е№іеқҮ190%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ж°ҙе№іиҰҒй«ҳеҫҲеӨҡгҖӮе°ұеўһйҖҹиҖҢиЁҖпјҢ2008пҪһ2016е№ҙпјҢжҲ‘еӣҪжқ жқҶзҺҮе№ҙеқҮж”ҖеҚҮ12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е·®дёҚеӨҡжҳҜеҗҢжңҹе…Ёзҗғжқ жқҶзҺҮж”ҖеҚҮйҖҹеәҰзҡ„дёӨеҖҚгҖӮ
д»Һж°ҙе№ідёҺеўһйҖҹжқҘзңӢпјҢжҲ‘еӣҪ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е·Із»ҸеҖјеҫ—е…іжіЁпјҢдҪҶжӣҙеӨ§зҡ„й—®йўҳеңЁ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з»“жһ„гҖӮ2018е№ҙпјҢжҲ‘еӣҪеұ…ж°‘жқ жқҶзҺҮ53.2%пјҢж”ҝеәңпјҲжҳҫжҖ§пјүжқ жқҶзҺҮ37%пјҢ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дёә153.6%гҖӮе’ҢеӣҪйҷ…жҜ”иҫғпјҢжңҖвҖңдёҚжӯЈеёёвҖқзҡ„еҪ“еұһдјҒдёҡжқ жқҶзҺҮпјҢеҹәжң¬дёҠдҪҚеҲ—е…Ёзҗғд№ӢеҶ гҖӮиЎЁйқўдёҠй—®йўҳе’ҢйЈҺйҷ©йғҪеңЁ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пјҢдҪҶж·ұе…ҘеҲҶжһҗеҸҜзҹҘз—Үз»“еңЁ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гҖӮиҝҷжҳҜеӣ дёәпјҡ第дёҖпјҢеңЁ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дёӯ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еҚ жҜ”и¶…иҝҮе…ӯжҲҗпјҢиҖ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дёӯ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еҚҠе·ҰеҸіжҳҜжүҖи°“зҡ„иһҚиө„е№іеҸ°еҖәеҠЎгҖӮеҰӮжһңжүЈйҷӨиһҚиө„е№іеҸ°еҖәеҠЎпјҢ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д№ҹе°ұдёҚйӮЈд№ҲеҮёжҳҫдәҶгҖӮ第дәҢпјҢжҲ‘们еҜ№жқ жқҶзҺҮиҝӣиЎҢйҮҚжһ„пјҢе°Ҷ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гҖҒ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дёҺ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дҪңдёә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пјҢе°Ҷеұ…ж°‘еҸҠйқһ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Ҫңдёә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пјҢйӮЈд№Ҳ2018е№ҙеә•пјҢ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дёә140%пјҢиҖҢ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дёә100%еӨҡдёҖзӮ№гҖӮ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й«ҳеҮә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еҫҲеӨҡпјҢиҝҷеңЁеӣҪйҷ…дёҠжҳҜзҪ•и§Ғзҡ„гҖӮйҷӨдәҶж—Ҙжң¬пјҢе…¶д»–еӣҪ家йғҪжҳҜ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иҝңй«ҳдәҺ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гҖӮиҝҷйҮҢдҪ“зҺ°еҮәдёӯеӣҪзҡ„зү№ж®ҠжҖ§пјҢз”ұдәҺ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дёӯжңүеӨ§йҮҸ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д»ҺиҖҢеҮәзҺ°дәҶдәҢиҖ…зҡ„вҖңеҸҚиҪ¬вҖқ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й«ҳдәҺ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гҖӮ第дёүпјҢдёӯеӣҪ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«ҳдјҒдё»иҰҒжҳҜеӣ дёә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Һ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еҖәеҠЎжү©еј зјәд№ҸзәҰжқҹпјҢд»ҺиҖҢеҸҚжҳ еҮәдёӯеӣҪеҖәеҠЎз§ҜзҙҜзҡ„вҖңдҪ“еҲ¶зү№иүІвҖқгҖӮ
дёӯеӣҪжқ жқҶзҺҮж”ҖеҚҮзҡ„дҪ“еҲ¶зү№иүІпјҢеҸҜз”ЁвҖңеӣӣдҪҚдёҖдҪ“вҖқжқҘжҰӮжӢ¬пјҢеҚі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зҡ„з»“жһ„жҖ§дјҳеҠҝгҖҒ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зҡ„еҸ‘еұ•иҙЈд»»дёҺиҪҜйў„з®—зәҰжқҹгҖҒ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зҡ„дҪ“еҲ¶жҖ§еҒҸеҘҪпјҢд»ҘеҸҠ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зҡ„жңҖеҗҺе…ңеә•иҙЈд»»гҖӮ
第дёҖ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зҡ„вҖңз»“жһ„жҖ§дјҳеҠҝвҖқгҖӮдҪңдёәе…ұе’ҢеӣҪзҡ„й•ҝеӯҗ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Җзӣҙд»ҘжқҘжүҝжӢ…зқҖеҫҲеӨҡзӨҫдјҡиҙЈд»»е№¶дә«жңүзү№еҲ«зҡ„вҖңз»“жһ„жҖ§дјҳеҠҝвҖқгҖӮиҝҷдёӘиҙЈд»»пјҢе°ұжҳҜе®һзҺ°зӨҫдјҡжҖ§зӣ®ж ҮпјҢж—ўеҢ…жӢ¬жүҝжӢ…зқҖеқҡжҢҒеҹәжң¬з»ҸжөҺеҲ¶еәҰгҖҒ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ж–№еҗ‘иҝҷж ·зҡ„е®ҸеӨ§д»»еҠЎпјҢд№ҹеҢ…жӢ¬зЁіе®ҡе®Ҹи§Ӯз»ҸжөҺгҖҒе®һзҺ°зӨҫдјҡе…¬е№ігҖҒдҝқйҡңз»ҸжөҺе®үе…Ёзӯүж–№йқўзҡ„е…·дҪ“иҙЈд»»гҖӮжӯЈеӣ дёәиҙЈд»»йҮҚеӨ§пјҢжүҚдҪҝеҫ—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ңЁзЁҺ收гҖҒдҝЎиҙ·гҖҒеёӮеңәеҮҶе…Ҙзӯүж–№йқўдә«жңүдјҳжғ ж”ҝзӯ–пјӣе°Өе…¶жҳҜ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зҡ„иҪҜйў„з®—зәҰжқҹеҸҠж”ҝеәңеҜ№д№Ӣзҡ„йҡҗжҖ§жӢ…дҝқгҖӮиҝҷдәӣжҒ°жҒ°жҳҜе…¶д»–еёӮеңәдё»дҪ“жүҖдёҚиғҪеӨҹдә«жңүзҡ„вҖңз»“жһ„жҖ§дјҳеҠҝвҖқгҖӮеҖјеҫ—дёҖжҸҗзҡ„жҳҜ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Қд»…еңЁеёӮеңәеҮҶе…Ҙж–№йқўеҫ—еҲ°дјҳе…Ҳз…§йЎҫпјҢеңЁеёӮеңәйҖҖеҮәж–№йқўд№ҹдә«жңүиҜёеӨҡдҝқжҠӨгҖӮзӣ®еүҚеӨ§йҮҸеғөе°ё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жңӘиғҪйҖҖеҮәеёӮеңәпјҢе°ұжҳҜеӣ дёәеҸ—еҲ°зү№ж®Ҡдјҳеҫ…гҖӮ
第дәҢпјҢ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зҡ„еҸ‘еұ•иҙЈд»»дёҺиҪҜйў„з®—зәҰжқҹгҖӮ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иӮ©иҙҹзқҖеҸ‘еұ•ең°ж–№з»ҸжөҺзҡ„д»»еҠЎ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е»әи®ҫе’Ңе…¬е…ұжңҚеҠЎжҸҗдҫӣж–№йқўпјҢиҙҹжңүдёҚеҸҜжҺЁеҚёзҡ„иҙЈд»»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еҸҲзјәд№Ҹи¶іеӨҹзҡ„иҙўж”ҝ收е…Ҙе’ҢжӯЈи§„жё йҒ“иө„йҮ‘зҡ„ж”ҜжҢҒпјҢдәҺжҳҜеҗ„з§ҚвҖңеҲӣж–°вҖқеә”иҝҗиҖҢз”ҹгҖӮзҺ°еңЁзңӢеҲ°зҡ„еҫҲеӨҡиһҚиө„е№іеҸ°еҖәеҠЎпјҢд»ҘеҸҠж”ҝеәңжҠ•иө„еҹәйҮ‘гҖҒPPPйЎ№зӣ®гҖҒж”ҝеәңиҙӯд№°жңҚеҠЎзӯүпјҢйғҪжҲҗдәҶж”ҝеәңиҺ·еҸ–иө„йҮ‘зҡ„жё йҒ“пјҢеҪўжҲҗ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зҡ„йҡҗжҖ§еҖәеҠЎгҖӮиҷҪ然дёӯеӨ®дёүд»Өдә”з”ідёҚиғҪиҝқ规еҖҹеҖәпјҢдҪҶеҮәдәҺеҸ‘еұ•йңҖиҰҒзҡ„еҖҹеҖәеҸҲзҗҶзӣҙж°”еЈ®пјҢжңҖеҗҺиҝҳдёҚдёҠй’ұиҝҳиҰҒжүҫдёӯеӨ®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иҜҙпјҢ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йқўдёҙзҡ„е°ұжҳҜиҪҜйў„з®—зәҰжқҹгҖӮ
第дёүпјҢ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зҡ„дҪ“еҲ¶жҖ§еҒҸеҘҪгҖӮжӯЈжҳҜ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зҡ„дҪ“еҲ¶жҖ§еҒҸеҘҪпјҢжүҚдҪҝеҫ—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Һ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зҡ„вҖңд»»жҖ§вҖқжү©еј иғҪеӨҹйЎәеҲ©е®һзҺ°гҖӮиҝҷз§ҚеҒҸеҘҪпјҢжң¬иҙЁдёҠжәҗдәҺ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зҡ„зҗҶжҖ§иЎҢдёәпјҢеӣ дёәе®ғ们и§үеҫ—иҙ·ж¬ҫз»ҷжӢҘжңүеӣҪиө„жҲ–ж”ҝеәңиғҢжҷҜзҡ„йЎ№зӣ®пјҢеҸҜд»ҘиҺ·еҫ—ж”ҝеәңзҡ„йҡҗжҖ§жӢ…дҝқе’ҢжңҖеҗҺе…ңеә•гҖӮеҰӮжһ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ҚдјҡйҖҖеҮәгҖҒиһҚиө„е№іеҸ°дёҚдјҡз ҙдә§пјҢиҝҷз§ҚдҪ“еҲ¶жҖ§еҒҸеҘҪе°ұеҫ—дёҚеҲ°ж”№еҸҳгҖӮз”ҡиҮіж”ҝеәңеЈ°жҳҺдёҚдјҡе…ңеә•пјҢ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д№ҹд»Қеӯҳжңүиҝҷз§Қе№»и§үгҖӮ
第еӣӣпјҢ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зҡ„жңҖеҗҺе…ңеә•иҙЈд»»гҖӮе…¶е®һеңЁд»»дҪ•еӣҪ家пјҢеҮәзҺ°дәҶз»ҸжөҺ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пјҢжңҖеҗҺж”ҝеәңйғҪдјҡеҮәйқўж•‘еҠ©пјҢйғҪиҰҒжқҘе…ңеә•пјҢдёҚдјҡ任其蔓延гҖӮдҪҶй—®йўҳжҳҜе…ңеӨҡе°‘гҖӮзјәе°‘еёӮеңәеҢ–зҡ„йЈҺйҷ©еҲҶжӢ…жңәеҲ¶пјҢеҸ‘еұ•еһӢж”ҝеәңе°ҶвҖңжүҖжңүзҡ„йЈҺйҷ©йғҪиҮӘе·ұжүӣвҖқпјҢд»ҺиҖҢеҜјиҮҙйЈҺйҷ©йӣҶиҒҡ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пјҢеңЁеҸ‘еұ•д№ӢеҲқпјҢз»ҸжөҺзҡ„еҝ«йҖҹеўһй•ҝдҪҝеҫ—ж”ҝеәңе…ңеә•жңүи¶іеӨҹзҡ„еә•ж°”пјҢйӮЈд№ҲпјҢеңЁз»ҸжөҺеўһйҖҹдёҺиҙўж”ҝ收е…ҘеўһйҖҹж”ҫзј“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…ЁйғЁе…ңеә•е·ІжҳҜеҠӣжңүдёҚйҖ®гҖӮ
дёҚе®№еҗҰи®ӨпјҢвҖңеӣӣдҪҚдёҖдҪ“вҖқеҸ‘еұ•жЁЎејҸжӣҫз»ҸжҳҜ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еҝ«йҖҹеўһй•ҝзҡ„йҮҚиҰҒжі•е®қпјӣдҪҶеҝ…йЎ»жё…йҶ’ең°зңӢеҲ°пјҢе®ғеҗҢж ·д№ҹжҳҜеҪ“еүҚжқ жқҶзҺҮж”ҖеҚҮдёҺйЈҺйҷ©з§ҜзҙҜзҡ„дҪ“еҲ¶ж №жәҗгҖӮ
зЁіжқ жқҶдҝғеўһй•ҝжҳҜеҰӮдҪ•жҲҗдёәеҸҜиғҪзҡ„пјҡз»“жһ„жҖ§еҺ»жқ жқҶзҡ„йҖ»иҫ‘
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—®йўҳдё»иҰҒеңЁз»“жһ„пјҢиҝҷдёҖйҮҚиҰҒеҸ‘зҺ°жҲҗдёәз»“жһ„жҖ§еҺ»жқ жқҶзҡ„еҹәжң¬ж”Ҝж’‘гҖӮи§ӮеҜҹиҝ‘е№ҙжқҘжҲ‘еӣҪ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жҖ»дҪ“жқ жқҶзҺҮж”ҖеҚҮжҖҒеҠҝжңүжүҖи¶Ӣзј“пјҢиҖҢ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еҚҙжҳҜжӯӨж¶ҲеҪјй•ҝгҖӮжқ жқҶиҪ¬з§»ж—ЁеңЁзә жӯЈжқ жқҶй”ҷй…ҚпјҢиҝҷжҳҜеӣҪйҷ…йҖҡиЎҢеҒҡжі•гҖӮ并且пјҢжқ жқҶеңЁйғЁй—Ёй—ҙзҡ„иҪ¬з§»пјҢиғҪеӨҹжңүж•ҲйҷҚдҪҺжҖ»дҪ“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ЈҺйҷ©гҖӮе…¶зҗҶи®әйҖ»иҫ‘еңЁдәҺпјҡ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жӣҙеӨҡдҪ“зҺ°зҡ„жҳҜ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й”ҷй…Қд»ҘеҸҠз”ұжӯӨеј•иө·зҡ„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ж•ҲзҺҮзҡ„дёӢйҷҚпјҢиҖҢдёҚеҚ•зәҜеңЁдәҺжқ жқҶзҺҮж°ҙе№ізҡ„й«ҳдҪҺгҖӮжӯЈжҳҜз”ұдәҺдёҚеҗҢйғЁй—ЁгҖҒдёҚеҗҢдё»дҪ“иҝҗиЎҢж•ҲзҺҮдёҺиҙҹеҖәиғҪеҠӣзҡ„е·®ејӮеҜјиҮҙе…¶жүҝжӢ…йЈҺйҷ©зҡ„иғҪеҠӣдёҚеҗҢпјҢд»ҺиҖҢеңЁз»ҙжҢҒжҖ»жқ жқҶзҺҮе№ізЁізҡ„еүҚжҸҗдёӢпјҢе®һзҺ°жқ жқҶзҺҮеҶ…йғЁз»“жһ„зҡ„и°ғж•ҙе’ҢдјҳеҢ–пјҢжҳҜеҸҜд»Ҙе®һзҺ°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дёӢйҷҚзҡ„гҖӮ
йҰ–е…ҲпјҢеҶ…еҖәе’ҢеӨ–еҖәзҡ„еҲҶеҲ«гҖӮеӨ–еҖәдёҖиҲ¬жқҘи®ІжҜ”еҶ…еҖәйЈҺйҷ©жӣҙеӨ§пјҢеҺҹеӣ еңЁдәҺеӨ–еҖәжҳҜеҲҡжҖ§зҡ„пјҢйңҖиҰҒжңүзЎ¬иө„дә§пјҲдёәеӨ–еӣҪжүҖжҺҘеҸ—пјүд»ҘеҸҠеҮәеҸЈеҲӣжұҮиғҪеҠӣгҖӮиҖҢеҶ…еҖәеҲҡжҖ§иҫғејұпјҢжҜ•з«ҹж”ҝеәңеҸҜд»ҘйҮҮеҸ–еӨҡз§ҚжүӢж®өжқҘеә”еҜ№пјҢеҰӮеҸ‘ж–°еҖәиҝҳж—§еҖәпјҢжҲ–иҖ…жҳҜд»ҘйҖҡиҙ§иҶЁиғҖж–№ејҸжқҘзЁҖйҮҠеҖәеҠЎгҖӮж— и®әжҳҜжӢүзҫҺеҖәеҠЎеҚұжңәиҝҳжҳҜдәҡжҙІ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пјҢйғҪе’ҢеӨ§йҮҸзҡ„еӨ–еҖәж— жі•еҒҝиҝҳжңүеҫҲеӨ§е…ізі»гҖӮзҫҺеӣҪжңүеӨ§йҮҸеӨ–еҖәпјҢдҪҶзҫҺе…ғжҳҜеӣҪйҷ…еӮЁеӨҮиҙ§еёҒ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…¶еӨ–еҖәзӣёеҪ“дәҺеҶ…еҖәпјҢеҚ°й’һзҘЁе°ұеҸҜд»Ҙи§ЈеҶіпјӣж—Ҙжң¬еҶ…еҖәеӨҡиҖҢеӨ–еҖәе°‘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°Ҫз®ЎжҖ»жқ жқҶзҺҮеҫҲй«ҳпјҢдҪҶе…¶йЈҺйҷ©е№¶жІЎжңүе…¶жқ жқҶзҺҮжүҖе‘ҲзҺ°зҡ„йӮЈд№Ҳй«ҳ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и§’еәҰзңӢпјҢеҰӮжһңеҶ…еҖәеўһеҠ пјҢеӨ–еҖәеҮҸе°‘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дјҡеёҰжқҘйЈҺйҷ©зҡ„дёӢйҷҚгҖӮ
е…¶ж¬ЎпјҢе…¬е…ұйғЁй—ЁдёҺ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зҡ„еҲҶеҲ«гҖӮж”ҝеәңеӣ е…¶иҮӘиә«зҡ„дҝЎз”Ёд»ҘеҸҠе…¶жҺҢжҺ§зҡ„иө„жәҗпјҢдёҖиҲ¬жқҘи®ІжүҝеҸ—еҖәеҠЎзҡ„иғҪеҠӣжҜ”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иҰҒејәпјҢиҝҷд»ҺеҺҶж¬ЎеҚұжңәйғҪиҰҒз”ұж”ҝеәңжқҘж•‘еёӮеҸҜи§ҒдёҖж–‘гҖӮжҜ”еҰӮзҫҺиҒ”еӮЁиө„дә§иҙҹеҖәиЎЁзҡ„жү©еј пјҢд»ҘеҸҠиөӨеӯ—еўһеҠ гҖҒеҖәеҠЎдёҠйҷҗзҡ„жҸҗй«ҳпјҢйғҪжҳҜйҖҡиҝҮдёҖдёӘжӣҙ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ж”ҝеәң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ж”ҝеәң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жҸҗй«ҳпјҢжқҘзј“и§Ј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иў«иҝ«еҺ»жқ жқҶ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з»ҸжөҺдёӢиЎҢйЈҺйҷ©гҖӮеҜ№дәҺжҲ‘еӣҪиҖҢиЁҖпјҢжӣҙ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вҖңеӣӣдёҮдәҝвҖқд»ҘеҸҠдёҺд№ӢзӣёеҢ№й…Қзҡ„银иЎҢдҝЎиҙ·е’ҢеӣҪжңүз»ҸжөҺзҡ„жү©еј пјҢд»ҺиҖҢе№ҝд№үж”ҝеәңиө„дә§иҙҹеҖәиЎЁжү©еј пјҢжӯЈжҳҜжҲ‘еӣҪеә”еҜ№еҚұжңәзҡ„еҹәжң¬жүӢж®өгҖӮеҪ“然пјҢж•‘еёӮж–№ејҸзҡ„йҖүжӢ©пјҢжңҖз»Ҳдјҡж¶үеҸҠжҲҗжң¬ж”¶зӣҠгҖӮдҪҶжҖ»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ж”ҝеәңеңЁдёәиө„жәҗиҜҜй…ҚзҪ®еёҰжқҘзҡ„еҗҺжһңпјҲеҢ…жӢ¬еқҸиҙҰгҖҒдёҚзЁіе®ҡз”ҡиҮіеҚұжңәпјүд№°еҚ•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зӣёеҜ№дәҺеҸ‘иҫҫз»ҸжөҺдҪ“пјҢжҲ‘еӣҪж”ҝеәңжҺҢжҺ§зқҖжӣҙеӨҡзҡ„иө„жәҗ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…¶еңЁж•‘еёӮдёӯжӣҙжңүиғҪеҠӣе’ҢиҮӘдҝЎгҖӮд»ҺиҖҢпјҢз§ҒдәәйғЁй—ЁпјҲеҰӮ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пјүжқ жқҶзҺҮдёӢйҷҚпјҢиҖҢж”ҝеәңпјҲзү№еҲ«жҳҜ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пјүжқ жқҶзҺҮдёҠеҚҮпјҢжңүеҲ©дәҺзј“йҮҠз»ҸжөҺдҪ“зҡ„йЈҺйҷ©гҖӮ
еҶҚж¬ЎпјҢеұ…ж°‘дёҺдјҒдёҡзҡ„еҲҶеҲ«гҖӮеұ…ж°‘жҳҜзӨҫдјҡеҮҖеӮЁи“„зҡ„жҸҗдҫӣиҖ…пјҢиҖҢдјҒдёҡеҹәжң¬дёҠжҳҜйқ иҙҹеҖәз»ҸиҗҘпјҢйқ жқ жқҶжқҘеҸ‘еұ•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ҖиҲ¬иҖҢиЁҖпјҢ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еҖәеҠЎжүҝеҸ—иғҪеҠӣиҰҒејәдәҺдјҒдёҡ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еңЁ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ж°ҙе№ізӣёеҜ№пјҲеӣҪйҷ…пјүиҫғдҪҺгҖҒиҙҹеҖәз©әй—ҙиҫғеӨ§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йҖӮеәҰеҠ жқ жқҶгҖҒ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еҺ»жқ жқҶжңүеҲ©дәҺйҷҚдҪҺжҖ»дҪ“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гҖӮеҪ“然пјҢд№ҹиҰҒе…іжіЁ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иҮӘиә«зҡ„йЈҺйҷ©гҖӮиҷҪ然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жҖ»дҪ“дёҠжҳҜеҮҖеӮЁи“„зҡ„жҸҗдҫӣиҖ…пјҢдҪҶеңЁз»“жһ„дёҠпјҢд№ҹдјҡеҮәзҺ°жңүдёҚе°‘иҙҹиө„дә§зҡ„家еәӯпјҲеӣ дёәиҙ«еҜҢе·®и·қзҡ„еӯҳеңЁпј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йЈҺйҷ©дё»иҰҒжҳҜз»“жһ„жҖ§зҡ„гҖӮ
жңҖеҗҺ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Һж°‘дјҒзҡ„еҲҶеҲ«гҖӮдјҒдёҡд№ҹжңүй«ҳж•ҲдҪҺж•Ҳд№ӢеҲҶгҖӮдёҖиҲ¬иҖҢиЁҖ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ж•ҲзҺҮзӣёеҜ№иҰҒдҪҺдәӣпјҢиҖҢж°‘дјҒж•ҲзҺҮзӣёеҜ№иҫғй«ҳдәӣгҖӮдҪҶеңЁиҺ·еҫ—дҝЎиҙ·ж”ҜжҢҒдёҠеҚҙеҸҚиҝҮжқҘ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иғҪеӨҹжӣҙе®№жҳ“д»ҘжӣҙдҪҺзҡ„жҲҗжң¬иҺ·еҫ—дҝЎиҙ·иө„жәҗпјҢиҖҢж°‘дјҒеҚҙеӯҳеңЁиһҚиө„йҡҫгҖҒиһҚиө„иҙө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з»“жһңеҜјиҮҙеңЁж•ҙдёӘ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еҖәеҠЎдёӯ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еҚ жҜ”иҫҫе…ӯеҲ°дёғжҲҗгҖӮеҰӮжһңиғҪеӨҹе°ҶдҝЎиҙ·иө„жәҗпјҲжҲ–жқ жқҶзҺҮпјүжӣҙеӨҡй…ҚзҪ®еҲ°й«ҳж•Ҳзҡ„дјҒдёҡпјҲеҰӮж°‘дјҒпјүпјҢе°ұжңүеҸҜиғҪдҪҝдә§еҮәжӣҙеҝ«ең°еўһй•ҝгҖӮ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жҲ‘们е°ұжңүеҸҜиғҪеңЁ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®һзҺ°зЁіеўһй•ҝгҖӮ
жҖ»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жҲ‘们еҰӮжһңжІҝзқҖж•ҲзҺҮзҡ„и·Ҝеҫ„пјҢжҢүз…§йЈҺйҷ©дёҺ收зӣҠеҢ№й…Қзҡ„жҖқи·ҜжқҘйҮҚж–°й…ҚзҪ®жқ жқҶзҺҮе’Ңи°ғж•ҙ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еҶ…йғЁз»“жһ„пјҢе°ұеҸҜиғҪеңЁ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®һзҺ°дҝғеўһй•ҝгҖӮ
е°Ҷ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дёҺ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Ң№й…Қиө·жқҘпјҢдҝғиҝӣ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еҠЁжҖҒе№іиЎЎ
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пјҢдёҖе®ҡж„Ҹд№үдёҠеұһдәҺзҹӯжңҹе®Ҹи§ӮзЁіе®ҡж”ҝзӯ–пјҢжҳҜдҫ§йҮҚдәҺйңҖжұӮйқўзҡ„гҖӮдҪҶдәҢиҖ…д№Ӣй—ҙзҡ„зҹӣзӣҫд»ҘеҸҠзҹӣзӣҫи§ЈеҶізҡ„йҖ”еҫ„пјҢжңҖз»Ҳж №жӨҚдәҺж•ҲзҺҮгҖҒз»“жһ„дёҺдҪ“еҲ¶пјҢжҳҜеұһдәҺдҫӣз»ҷйқўзҡ„гҖӮ
йҰ–е…ҲпјҢејәи°ғжқ жқҶзҺҮй…ҚзҪ®зҡ„ж•ҲзҺҮеҺҹеҲҷпјҲеҪ“然иҝҷдёҚжҳҜе”ҜдёҖеҺҹеҲҷпјүпјҢзә жӯЈжқ жқҶзҺҮй”ҷй…ҚгҖӮжң¬иҪ®еҺ»жқ жқҶ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дёҺж°‘дјҒзҡ„вҖңеҫ…йҒҮвҖқжҳҜ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зҡ„гҖӮеңЁиҝ‘дёӨе№ҙдёҘеҺүеҺ»жқ жқҶж”ҝзӯ–дёӢпјҢ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еҮәзҺ°дәҶдёӢйҷҚпјҡ2017е№ҙеӣһиҗҪ0.3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2018е№ҙжӣҙжҳҜйӘӨйҷҚ4.6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иҝҷеҸҜд»ҘзңӢеҒҡ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еҜ№ж•ҙдҪ“еҺ»жқ жқҶзҡ„иҙЎзҢ®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з»Ҷ究еҸ‘зҺ°пјҢиҝҷж–№йқўзҡ„иҙЎзҢ®дё»иҰҒжҳҜз”ұж°‘иҗҘдјҒдёҡдҪңеҮәзҡ„гҖӮ2015е№ҙд»ҘжқҘ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еңЁе…ЁйғЁдјҒдёҡеҖәеҠЎдёӯзҡ„еҚ жҜ”дёҖи·Ҝж”ҖеҚҮпјҢз”ұ2015е№ҙ第дәҢеӯЈеәҰзҡ„57%пјҢдёҠеҚҮеҲ°2019е№ҙ第дәҢеӯЈеәҰзҡ„69%гҖӮиҝҷ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зӣ®еүҚ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й…ҚзҪ®дёӯпјҢжңүдёғжҲҗе·ҰеҸій…ҚзҪ®з»ҷдәҶ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гҖӮдёҖиҲ¬иҖҢиЁҖпј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ж•ҲзҺҮиҰҒдҪҺдәҺж°‘дјҒ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й…ҚзҪ®дјҡеҜјиҮҙиө„жәҗзҡ„иҜҜй…ҚзҪ®пјҢд»ҺиҖҢеҲ¶зәҰдә§еҮәдёҠеҚҮ并еёҰжқҘзЁіеўһй•ҝзҡ„еҺӢеҠӣгҖӮз ҙи§ЈиҝҷдёҖеӣ°еўғпјҢйңҖиҰҒзӘҒеҮәз«һдәүдёӯжҖ§пјҢд»Һж•ҲзҺҮеҮәеҸ‘пјҢе°Ҷжқ жқҶдёҺж•ҲзҺҮеҢ№й…Қиө·жқҘпјҢжүӯиҪ¬жқ жқҶзҺҮй”ҷй…ҚеұҖйқўпјҢдјҳеҢ–еҖәеҠЎиө„йҮ‘й…ҚзҪ®пјҢе®һзҺ°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еҠЁжҖҒе№іиЎЎгҖӮ
е…¶ж¬ЎпјҢ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еҸ‘еҠӣпјҢжҠҠеҠҹеӨ«дёӢеңЁжқ жқҶз»“жһ„зҡ„дјҳеҢ–дёҠгҖӮд»ҺзЁіжқ жқҶзҡ„и§’еәҰпјҢеҰӮжһңжңүзҡ„йғЁй—ЁпјҲеҰӮ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гҖҒ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пјүйңҖиҰҒеҺ»жқ жқҶпјҢйӮЈд№Ҳе°ұеҝ…йЎ»иҰҒжңүйғЁй—ЁеҠ жқ жқҶгҖӮд»ҺиҝҮеҺ»еҮ е№ҙжқҘзңӢпјҢиҝҷдёӘеҠ жқ жқҶзҡ„д»»еҠЎдё»иҰҒз”ұ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жқҘжүҝжӢ…гҖӮд»Һ2016е№ҙ第еӣӣеӯЈеәҰеҲ°2019е№ҙ第дәҢеӯЈеәҰпјҲе…ұи®Ў10дёӘеӯЈеәҰпјүпјҢдјҒдёҡ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дёӢйҷҚ2.8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жқ жқҶзҺҮеҫ®еҚҮ0.4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пјҲжҳҫжҖ§пјүжқ жқҶзҺҮд№ҹд»…дёҠеҚҮ1.4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иҖҢ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жқ жқҶзҺҮеҚҙеӨ§е№…ж”ҖеҚҮ10.3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жүҖи°“зӢ¬жңЁйҡҫж”ҜпјҢд»…йқ еұ…ж°‘йғЁй—ЁжқҘе®һзҺ°жҖ»дҪ“жқ жқҶзҺҮзҡ„зЁіе®ҡжҳҜйқһеёёеҚұйҷ©зҡ„гҖӮеҚ•д»Һ2016е№ҙд»ҘжқҘзҡ„ж•°жҚ®зңӢпјҢеұ…ж°‘жқ жқҶзҺҮ10дёӘеӯЈеәҰдёҠеҚҮ10.3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жҜҸдёӘеӯЈеәҰдёҠеҚҮ1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дёҖе№ҙе°ұжҳҜ4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иҖҢиҝҷдёӘйҖҹеәҰдёҺзҫҺеӣҪ第дәҢ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д»ҘжқҘеұ…ж°‘жқ жқҶзҺҮеўһйҖҹжңҖеҝ«зҡ„дёҖж®өж—¶жңҹпјҲ2000пҪһ2007е№ҙпјүе№ҙеқҮеўһйҖҹ4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жҢҒе№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йңҖиҰҒ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жңүжүҖдҪңдёә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йҖӮеәҰжҠ¬еҚҮ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зҡ„жқ жқҶзҺҮпјӣеҗҢж—¶пјҢеҠ еҝ«еғөе°ёдјҒдёҡжё…зҗҶпјҢжҺЁиҝӣеӣҪжңүдјҒдёҡеҺ»жқ жқҶпјҢд»ҘеҸҠ规иҢғзәҰжқҹ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дёҫеҖәиЎҢдёәпјҢд»ҘеёӮеңәеҢ–жі•жІ»еҢ–зҡ„ж–№жі•еӨ„зҪ®ең°ж–№йҡҗжҖ§еҖәеҠЎгҖӮ
жңҖеҗҺпјҢжһ„е»әйЈҺйҷ©е…ұжӢ…жңәеҲ¶пјҢе°Ҷ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дёҺ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Ң№й…Қиө·жқҘгҖӮ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иө¶и¶…зҡ„е…ёеһӢзү№еҫҒжҳҜпјҲдёӯеӨ®пјүж”ҝеәңйҖҡиҝҮиЎҢж”ҝе№Ійў„е’ҢйҡҗжҖ§жӢ…дҝқпјҢеҮ д№ҺжүҝжӢ…дәҶжүҖжңүзҡ„еҸ‘еұ•йЈҺйҷ©гҖӮзү№еҲ«жҳҜпјҢиө„жәҗгҖҒеҸ‘еұ•жңәдјҡдёҺеҸ‘еұ•ж”¶зӣҠжӣҙеӨҡең°й…ҚзҪ®з»ҷдәҶеӣҪжңүз»ҸжөҺпјҢдҪҶ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еҚҙжңӘиғҪе°Ҷзӣёеә”зҡ„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ҮәеҺ»пјҢеҜјиҮҙеӣҪжңү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иҝҮзЁӢдёӯзҡ„йЈҺйҷ©ж”¶зӣҠдёҚеҢ№й…ҚпјҢеҪўжҲҗиҪҜйў„з®—зәҰжқҹе’ҢејәзғҲзҡ„жү©еј еҶІеҠЁгҖӮжңӘжқҘзңӢпјҢйңҖиҰҒе°Ҷ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дёҺ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Ң№й…Қиө·жқҘгҖӮжқ жқҶжҳҜдёҖз§Қиө„жәҗпјҢиҺ·еҫ—дәҶиҝҷз§Қиө„жәҗпјҢе°ұиҰҒжүҝжӢ…зӣёеә”зҡ„йЈҺйҷ©гҖӮи§ЈеҶійЈҺйҷ©ж”¶зӣҠдёҚеҢ№й…Қзҡ„ж №жң¬пјҢеңЁдәҺеҸ–ж¶ҲйҡҗжҖ§жӢ…дҝқгҖҒеҲҡжҖ§е…‘д»ҳд»ҘеҸҠйҮ‘иһҚжңәжһ„зҡ„дҪ“еҲ¶жҖ§еҒҸеҘҪгҖӮеҸӘжңүеҸ–ж¶ҲдәҶиҝҷдәӣеҲ¶еәҰжҖ§жүӯжӣІпјҢжүҚиғҪдҪҝеҫ—йЈҺйҷ©е®ҡд»·еӣһеҪ’жӯЈиҪЁпјҢйЈҺйҷ©дёҺ收зӣҠзҡ„еҢ№й…ҚжүҚе…·еӨҮдәҶеҹәзЎҖпјҢйЈҺйҷ©зҡ„еёӮеңәеҢ–еҲҶжӢ…жүҚжңүеҸҜиғҪгҖӮ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пјҢе®һзҺ°йЈҺйҷ©дёҺ收зӣҠзҡ„еҢ№й…ҚпјҢйңҖиҰҒе°Ҷж”ҝеәңжҲ–еӣҪжңүз»ҸжөҺеһ„ж–ӯзҡ„иө„жәҗгҖҒеҸ‘еұ•жңәдјҡжӢҝеҮәжқҘпјҢжҺЁиҝӣеёӮеңәејҖж”ҫпјҢи®©зӨҫдјҡиө„жң¬иғҪеӨҹзңҹжӯЈеҲҶдә«еҸ‘еұ•ж”¶зӣҠпјҢиҝҷдәӣзӨҫдјҡиө„жң¬жүҚиғҪеӨҹжӣҙеҘҪең°еҺ»еҲҶжӢ…зӣёеә”зҡ„йЈҺйҷ©гҖӮдјҳеҢ–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еҲ©дәҺзЁіеўһй•ҝпјҢдјҳеҢ–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Ҳ©дәҺзЁіжқ жқҶпјӣз”ұжӯӨзңӢжқҘпјҢйҖҡиҝҮдҪ“еҲ¶ж”№йқ©е°Ҷ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дёҺйЈҺйҷ©й…ҚзҪ®еҢ№й…Қиө·жқҘпјҢе°ҶжҳҜе®һзҺ°зЁіеўһй•ҝдёҺзЁіжқ жқҶд№Ӣй—ҙеҠЁжҖҒе№іиЎЎзҡ„е…ій”®дёҖжӢӣ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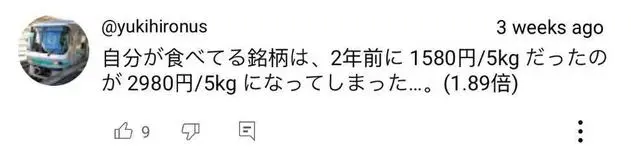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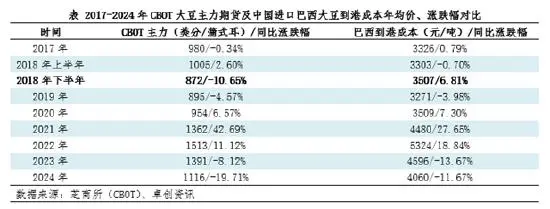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