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жқЁеӨ©дҝқпјҢз”·пјҢе№ҝиҘҝж°‘ж—ҸеӨ§еӯҰж”ҝжІ»дёҺе…¬е…ұз®ЎзҗҶ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гҖӮ
иҝ‘е№ҙжқҘпјҢеӯҰз•ҢеҜ№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зҡ„з ”з©¶ж—Ҙи¶Ӣй«ҳж¶ЁпјҢдёӯеӨ–еӯҰиҖ…е°ҶеҸІж–ҷжү№еҲӨгҖҒеҸІеӯҰеҲҶжһҗе’Ңж–Үжң¬иҖғеҸӨзӯүеј•е…Ҙдј з»ҹеҺҶеҸІзј–зәӮеӯҰпјҢйҖҡиҝҮзі»з»ҹиҫЁжһҗвҖңеҺҶеҸІдёүи°ғвҖқпјҲз»ҸеҺҶгҖҒдәӢ件е’ҢзҘһиҜқпјүпјҢж·ұе…Ҙжҙһи§ҒеҸІзӣёдёҺеҸІе®һгҖҒжқғеҠӣдёҺж–Үжң¬зҡ„йҖ»иҫ‘е…ізі»пјҢжӣҙе…·зҗҶжҖ§ең°жҸӯйңІеҮә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дё»дҪ“дёҺе®ўдҪ“зҡ„дә’еҠЁгҖӮеӯҰиҖ…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дәәзұ»зҡ„еҺҶеҸІвҖқйғҪвҖңеҸҜд»ҘеңЁе®ғе·Із»ҸеҸ‘з”ҹеҗҺжүҚиў«еҶіе®ҡжҳҜжҖҺж ·еҸ‘з”ҹзҡ„вҖқ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иҫ№з–Ҷең°еҢәзҡ„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й—®йўҳпјҢеӨ§е®¶жҷ®йҒҚи®ӨдёәпјҢеҸӨд»ЈзҺӢжңқеӣҪ家жҖ»дҪ“дёҠзҡҶдё»еҠЁйҮҮз”Ё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иҢғејҸйҮҚе»әиҝҮеҺ»пјҢз§ҜжһҒи°ӢжұӮдёӯеӨ®дёҺең°ж–№вҖңе…ұеҗҢзҡ„еҺҶеҸІи®°еҝҶвҖқпјҢжңҖз»Ҳд»Ҙж–ҮеҢ–еҪўејҸе®һзҺ°иҫ№з–Ҷж•ҙеҗҲ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ҸӨд»Јеӣҙз»•вҖңиҫ№з–ҶвҖ”еҶ…ең°вҖқдёҖдҪ“еҢ–дё»йўҳзҡ„еӨҡз§Қ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пјҢеңЁиЎЁиҫҫзҺӢжңқеӣҪ家зҡ„ж„Ҹеҝ—е’Ңд№ҰеҶҷиҖ…ж”ҝжІ»иҜүжұӮ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®ғ们жӣҙжҳ з…§еҮә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и®ӨзҹҘиҫ№з–Ҷзҡ„е…ҲеҗҺиҝӣзЁӢпјҢд»ҘеҸҠжІ»иҫ№зӯ–з•ҘдёҠзҡ„йҖүжӢ©е·®ејӮгҖӮд»ҘдёӢпјҢйҖүеҸ–е”җд»ЈжқҺеӨҚжІ»зҗҶе®№е·һдәӢдҫӢеҸҠе…¶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пјҢз•ҘдҪңеҲҶжһҗгҖӮдёҖгҖҒзҹіеҲ»ж–ҮгҖҠжқҺе…¬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дёҺ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и®°дәӢе·®ејӮ е”җд»ЈеҲқе№ҙпјҢгҖҠеҚҒйҒ“еҝ—гҖӢжҲҗд№ҰгҖӮе…¶вҖңеІӯеҚ—йҒ“вҖқд№ҰеҶҷзҡ„е®№е·һвҖңеӣҫеғҸвҖқпјҢжҚ®е®Ӣд»ЈгҖҠиҲҶең°зәӘиғңгҖӢиҫ‘е…¶дҪҡж–ҮпјҢеӨ§дҪ“е°ұжҳҜпјҡвҖңеӨ·еӨҡеӨҸе°‘пјҢйј»йҘ®и·ЈиЎҢгҖӮеҘҪеҗ№и‘«иҠҰз¬ҷпјҢеҮ»й“ңйј“пјҢд№ е°„еј“еј©гҖӮж— иҡ•жЎ‘пјҢзјүи•үи‘ӣд»ҘдёәеёғгҖӮдёҚд№ ж–ҮеӯҰпјҢе‘јеёӮдёәеўҹпјҢдә”ж—ҘдёҖйӣҶгҖӮдәәжҖ§еҲҡжӮҚпјҢйҮҚжӯ»иҪ»з”ҹгҖӮвҖқдәәеҸЈжһ„жҲҗдёҺдёӯеҺҹж®ҠејӮпјҢ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дј—еӨҡпјҢдё”з”ҹи®Ўд№ жҖ§зҲұеҘҪзӢ¬зү№пјҢж•…е…¶ең°ж–№жІ»зҗҶжҳҫ然дёҚиғҪеӣ еҫӘж—§дҫӢпјҢжӣҙдёҚеҸҜе®Ңе…Ёз…§жҗ¬еҶ…ең°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е”җд»ЈеңЁеІӯеҚ—ең°еҢәзҡ„иҫ№з–ҶжІ»зӯ–пјҢе·Із»Ҹи®ҫи®ЎеҮәиҰҒе·һдёҺиҫ№е·һгҖҒиҰҒеәңпјҲиҰҒеҶІйғҪзқЈеәңпјүдёҺиҫ№еәңпјҲиҫ№з–ҶйғҪзқЈеәңпјүзҡ„еҲ¶еәҰе·®еҲ«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пјҢйӮ•еәңйҮҚеңЁејҖжӢ“еүҚжІҝз–ҶеңҹпјҢжҠөеҫЎеӨ–ж•ҢпјҢжҳҜвҖңеҠ©жҺЁеҷЁвҖқжҲ–вҖңжЎҘеӨҙе ЎвҖқпјӣйӮЈд№Ҳе®№еәңе°ұжҳҜвҖңзЁіеҺӢеҷЁвҖқжҲ–вҖңй•ҮжІіеЎ”вҖқпјҢиҒҢиҙЈе°ұжҳҜдҝқйҡңжҲҳз•ҘеҗҺж–№гҖӮиҰҒд№ӢпјҢжІ»е®№ж—ўеҠӣдё»ең°ж–№еҲӣж–°еҸҲ关系家еӣҪе®үе…ЁпјҢйқһдёҖиҲ¬иҖ…жүҖиғҪдёәд№ӢгҖӮжқҺеӨҚпјҲ739вҖ”797пјүпјҢеӯ—еҲқйҳіпјҢжҳҜе”җд»Јж·®е®үзҺӢжқҺзҘһйҖҡпјҲ576вҖ”630пјүзҡ„еҗҺдәәпјҢе…ҲеҗҺд»»иҒҢжұҹйҷөеҺҝд»ӨгҖҒйҘ¶е·һеҲәеҸІгҖҒиӢҸе·һеҲәеҸІгҖҒжұҹйҷөе°‘е°№е…јеҫЎеҸІдёӯдёһгҖӮиҙһе…ғдәҢе№ҙпјҲ786е№ҙпјүпјҢжқҺеӨҚеҚ—дёӢеІӯиЎЁпјҢеңЁиҫ№ең°д»ЈзҗҶжІ»жқғгҖӮдёҖжҳҜвҖңзҡҮж—Ҹиҝӣиҫ№з–ҶиЎҷй—ЁвҖқпјҢиә«д»ҪйІңдә®дё”иЎҖз»ҹвҖңй«ҳиҙөвҖқпјҢеј•дәәе…іжіЁгҖӮдәҢжҳҜжұүе”җж—¶д»ЈпјҢжӯҰе°Ҷ家ж—ҸжҳҜдёӯеӣҪж”ҝжІ»иҲһеҸ°дёҠзҡ„дё»и§’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иә«дёәвҖңиҠӮеё…вҖқпјҢд»–е°ҶжӯҰе°Ҷ世家ж–ҮеҢ–иһҚе…ҘеІӯеҚ—иҫ№ж”ҝпјҢиҝӣиҖҢжҺЁеҠЁең°ж–№ж”ҝжІ»еҸ‘еұ•пјҢдәҰеҖјеҫ—жңҹеҫ…гҖӮж–Үд»ҘиҪҪйҒ“пјҢзҹҘдәәи®әдё–гҖӮжё…еҲқжұӘжЈ®гҖҠзІӨиҘҝж–ҮиҪҪгҖӢеҪ•иҪҪгҖҠе”җжЈҖж ЎеҸіж•ЈйӘ‘еёёдҫҚе®№е·һеҲәеҸІжқҺе…¬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пјҢеҸҜдёҖзқ№е…¶жІ»е®№еҸІгҖӮжҚ®жӯӨеҚғеӯ—йўӮж–ҮеҸҜзҹҘпјҢжқҘе®№е·һе°ұиҒҢеҗҺпјҢжқҺеӨҚвҖңдәІеё…е…¶дёӢпјҢд»ҘжҠҡеҗҫдәәпјӣж…°и—үдјӨз—ҚпјҢе®үйӣҶз–ІиҖ—вҖқ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еҒҡдәҶ10件дәӢпјҡдёҖжҳҜвҖңжғ§иҙ§иҙЎд№ӢйҳҷпјҢиҮіеҠ©д№Ӣд»Ҙ家иҙўпјӣжӮҜеҫӯдәӢд№Ӣз№ҒпјҢиҮід»Јд№Ӣд»Ҙз§ҒеұһвҖқпјӣдәҢжҳҜвҖңйҖүжӯҰиүәпјҢеҪ’иҖҒз–ҫпјҢзҪўеҮҸеЎһеҚ’еӣӣеҚғдҪҷдәәпјҢд»Ҙи¶ӢеҶңж—¶вҖқпјӣдёүжҳҜвҖңзҺҮжө®е •пјҢиҫҹжұЎиҺұпјҢејҖзҪ®еұҜз”°дә”зҷҫдҪҷйЎ·пјҢд»Ҙи¶іеҶӣе®һвҖқпјӣеӣӣжҳҜвҖңиҲҚеҜҮиҙјд№Ӣдёәзј§еӣҡиҖ…пјҢйҮҠиҖҢйҒЈд№ӢпјҢд»ҘйҷӨе…¶жҖЁпјҢиҖҢзӢҷзҠ·д»ҘйЎәвҖқпјӣдә”жҳҜвҖңзҰҒдәәж°‘д№ӢзӣёжҺіеҚ–иҖ…пјҢжү§иҖҢиҜӣд№ӢпјҢд»ҘеҺ»е…¶е®іпјҢиҖҢз«ҘжҳҸд»Ҙе®үвҖқпјӣе…ӯжҳҜвҖңеёёеІҒжңүзҒҫпјҢж»ҘзӮҺиҖҢиҝһзғ§дәҺеәҗиҲҚпјҢе…¬еҲӣе…¶еҲ¶пјҢд»ҘеҫЎе…¶йғҒж”ёпјҢиҖҢйӮ‘еұ…д»Ҙи‘әвҖқпјӣдёғжҳҜвҖңж—§дҝ—еӨҡжҖЁпјҢзқҡзңҰиҖҢиҮҙжҜ’дәҺйҘ®йЈҹпјҢе…¬з«Ӣе…¶йҳІпјҢд»Ҙи§Је…¶жӮҒеҝҝпјҢиҖҢд№Ўе…ҡд»Ҙе’ҢвҖқпјӣе…«жҳҜвҖңж ‘жқҝе№ІиҖҢеҗҜй—ӯжҜ•дҝ®пјҢеҲ—дәӯзҮ§иҖҢеҺ„е®іж–ҜжҺ§вҖқпјӣд№қжҳҜвҖңе·®йҮҚиҪ»д»ҘиЎҢеҫҒд»ӨпјҢж— дёҚеқҮд№Ӣи®ҘвҖқпјӣеҚҒжҳҜвҖңйҮҸиҝңиҝ‘д»ҘзәіиҙЎиҒҢпјҢж— дёҚдҫӣд№ӢиҙЈпјҢдәәз”ЁеҜҢеә¶пјҢ家жңүеӮЁеіҷвҖқгҖӮжӯӨзҹіеҲ»зў‘ж–ҮжҖ»дҪ“иҝҪеҝҶгҖҒжҸҸж‘№еҮәжқҺеӨҚеҲәйғЎе®№е·һзҡ„дёҖиҲ¬еҸІзӣёвҖ”вҖ”иҫ№ең°жІ»ж”ҝпјҢеҚ“жңүе®Ұз»©гҖӮеҪ“д»ЈдәәеҲ»еҶҷеҪ“д»ЈеҸІпјҢвҖңдҪҝиҙӨеЈ«еӨ§еӨ«д№ӢдәӢдёҡпјҢдёҚжІЎдәҺеҗҺвҖқпјҢеёҢжңӣжңүеҲ©дәҺең°ж–№и®°еҝҶе’ҢеҗҺдәәеҸӮиҖғ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җҺжҷӢе®°зӣёеҲҳжҳ«дё»дҝ®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пјҢеңЁеҚ·дёҖзҷҫдёҖеҚҒдәҢгҖҠжқҺжҡ дј йҷ„жқҺеӨҚгҖӢдёӯеҜ№е…¶е®№е·һжІ»иҝ№з”ЁеўЁйўҮе°‘пјҡвҖңе…Ҳж—¶иҘҝдә¬еҸӣд№ұпјҢеүҚеҗҺз»Ҹз•ҘдҪҝеҫҒи®ЁеҸҚиҖ…пјҢиҺ·е…¶дәәзҡҶжІЎдёәе®ҳеҘҙе©ўпјҢй…ҚдҪңеқҠйҮҚеҪ№пјҢпјҲжқҺпјүеӨҚд№ғд»Өи®ҝе…¶дәІеұһпјҢжӮүеҪ’иҝҳд№ӢгҖӮеңЁе®№е·һдёүеІҒпјҢеҚ—дәәе®үжӮҰгҖӮиҝҒе№ҝе·һеҲәеҸІгҖҒе…јеҫЎеҸІеӨ§еӨ«гҖҒеІӯеҚ—иҠӮеәҰи§ӮеҜҹдҪҝгҖӮвҖқ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еҲ—еҮәзҡ„ж•ҙж•ҙ10件еӨ§дәӢпјҢз»“жһңеҚҙеҸӘжңү第4件йҮҠйҒЈвҖңзј§еӣҡиҖ…вҖқпјҢдёҺеҪ’иҝҳвҖңжІЎдёәе®ҳеҘҙе©ўвҖқиҖ…зҡ„жӯЈеҸІеҸҷдәӢз•Ҙжңүе…іиҒ”пјҢиҖҢеҜ№дәҺиҙ§иҙЎзәіиҙЎгҖҒеҫӯдәӢиЎҢеҫҒгҖҒзҪўеҮҸеЎһеҚ’гҖҒејҖзҪ®еҶӣеұҜгҖҒзҰҒж°‘жҺіеҚ–гҖҒи‘әеұ…йҖ еәҗгҖҒйқ©йҷӨж—§дҝ—гҖҒе®Ңе–„дәӨйҖҡзӯүеӨҡж–№йқўзҡ„з–ҶеҹёеҲӣеҲ¶дёҺжІ»зҗҶеҸ‘жҳҺпјҢжӯЈеҸІзҡҶејғд№ӢдёҚйЎҫ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жқҺеӨҚжӯ»еҗҺжүҚзҷҫдҪҷе№ҙпјҢдё–й—ҙе°ұе·Іж— е®Ңж•ҙзҡ„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еҸІгҖӮдәҢгҖҒвҖңеҖәеё…вҖқпјҡе®ҳж–№е»әжһ„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зҡ„еҸҰдёҖеҸІзӣё иҙһе…ғеҚҒдәҢе№ҙпјҢжқҺеӨҚеҠ е®ҳжЈҖж Ўе·Ұд»Ҷе°„пјҢж¬Ўе№ҙйҖқдё–пјҢзҡҮдёҠдёәе…¶жІ»дё§пјҢеәҹжңқ3еӨ©пјҲжҜ”е…¶зҲ¶жқҺйҪҗзү©иҝҳеӨҡ2еӨ©пјүпјҢдё”вҖңиө еҸёз©әпјҢиөҷеёғеёӣзұізІҹжңүе·®вҖқпјҢи°Ҙжӣ°вҖңжҳӯвҖқпјҢжҳҫ然дҪҚеҲ—дёҖд»ЈеҗҚиҮЈ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В·жқҺжҡ дј гҖӢеңЁжңҖеҗҺжҖ»иҜ„е…¶дәә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пјҲжқҺпјүеӨҚд№…е…ёж–№йқўпјҢз§ҜиҙўйўҮз”ҡпјҢдёәж—¶жүҖи®ҘгҖӮвҖқзңӢжқҘпјҢзӢ¬ж–ӯдёҖеҹҹпјҢд»Ҙжқғи°Ӣз§ҒпјҢеӨ§ж®–家дә§пјҢиҙўжәҗе№ҝиҝӣпјҢз»ҲжҲҗеҜҢз”ІдёҖж–№зҡ„еӨ§иҙӘе®ҳпјҢиҝҷеҸҲжҳҜжқҺеӨҚеҲәйғЎең°ж–№гҖҒиҠӮй•ҮеІӯеҚ—зҡ„еҸҰдёҖеҸІзӣёгҖӮ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еҰӮжӯӨд№ҰеҶҷиҠӮеё…пјҢе°ҡеҸҜеңЁжң¬д№Ұе…¶д»–зҡ„еҲ—дј дёӯеҜ»еҲ°дәӣеҺҹ委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Қ·дёҖе…ӯдәҢгҖҠй«ҳз‘Җдј 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иҮӘеӨ§еҺҶе·ІжқҘпјҢиҠӮеҲ¶д№ӢйҷӨжӢңпјҢеӨҡеҮәзҰҒеҶӣдёӯе°үгҖӮеҮЎе‘ҪдёҖеё…пјҢеҝ…е№ҝиҫ“йҮҚиөӮгҖӮзҰҒеҶӣе°Ҷж ЎеҪ“дёәеё…иҖ…пјҢиҮӘж— е®¶иҙўпјҢеҝ…еҸ–иө„дәҺдәәпјӣеҫ—й•Үд№ӢеҗҺпјҢеҲҷиҶҸиЎҖз–Іж°‘д»ҘеҒҝд№ӢгҖӮеҸҠпјҲй«ҳпјүз‘Җд№ӢжӢңпјҢд»ҘеҶ…еӨ–е…¬и®®пјҢжҗўз»…зӣёеәҶжӣ°пјҡвҖҳйҹҰе…¬дҪңзӣёпјҢеҖәеё…йІңзҹЈпјҒвҖҷвҖқеҸҜзҹҘпјҢе…¶еҸҷдәӢйҖ»иҫ‘е°ұжҳҜпјҡе”җд»ЈеӨ§еҺҶе®ҳеңәпјҢиҠӮеҲ¶йҷӨжӢңпјҢзҺҮзҡҶвҖңиҙҝйҖүвҖқгҖӮж—¶еұҖж”ҝйЈҺеҰӮжӯӨпјҢе…¶дёӯзҡ„жҜҸдёҖдёӘдёӘдҪ“пјҢиҮӘ然еңЁжүҖйҡҫе…ҚгҖӮиҷҪ然жӯӨеӨ„иЎҢж–Ү并没жңүжҢҮеҗҚйҒ“姓пјҢзӣҙиҜҙжқҺеӨҚдёҖеҰӮй«ҳз‘ҖвҖңеҫ—й•ҮвҖқпјҢдҪҶйҒӯйҖўжӯӨйҷ…пјҢд»ҘзҡҮж—Ҹе’Ңе°Ҷй—ЁеҸҢйҮҚиә«д»ҪеҮәжҺҢең°ж–№йҮҚй•Үзҡ„жқҺеӨҚпјҢд»–дёӘдәәзҡ„д»•йҖ”еҸІжӯЈеҘҪеҸҜдёәеҸІе®ҳд№ҰеҶҷгҖҒжҠЁеҮ»жӯӨиҲ¬ж”ҝжІ»дё‘иұЎжҸҗдҫӣз»қдҪівҖңжіЁи„ҡвҖқгҖӮиҝӣе…ҘеҢ—е®ӢеҗҺпјҢжӯӨдёҖиҜҙжі•еҶҚеәҰеј•иө·е…іжіЁгҖӮе…Ҳжңү欧йҳідҝ®гҖҠж–°е”җд№ҰВ·жқҺеӨҚдј гҖӢдәҲд»ҘйҮҚеӨҚ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пјҲжқҺпјүеӨҚжӣҙж–№й•ҮпјҢжүҖеңЁз§°жІ»пјҢ然йўҮе—ңиҙўпјҢдёәдё–жүҖи®ҘгҖӮвҖқдҪңдёәвҖңе”җе®Ӣе…«еӨ§е®¶вҖқд№ӢдёҖпјҢ欧ж°Ҹж–ҮеҸІзӯүиә«пјҢд»–д»ҘвҖңе—ңиҙўвҖқж–°иҜӯпјҢи°ғжҚўдәҶ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жүҖдёҚйҪҝзҡ„вҖңз§ҜиҙўвҖқиЎҢеҫ„пјҢе°ҶеүҚдәәйўҮе…·жғ…ж„ҹиүІеҪ©зҡ„иЎЁиҝ°пјҢжӯЈејҸдёҠеҚҮдёәеҜ№е®ҳе‘ҳеҝғжҖ§йҒ“еҫ·зҡ„еҶ…еңЁжЈҖи®Ё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еҗҺиҖ…д»ҺиЎҢдёәжҙ»еҠЁеұӮйқўиҪ¬еҗ‘дәәжҖ§и®әпјҢдәҰи¶іи§ҒејәеӨ§зҡ„иҜқиҜӯйңёжқғгҖӮжҺҘзқҖпјҢеҸёй©¬е…ү继з»ӯе°ҶжӯӨиҜқйўҳзәіе…ҘгҖҠиө„жІ»йҖҡйүҙгҖӢ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еӨ§е’Ңе…ғе№ҙпјҲ827е№ҙпјүеӨҸеӣӣжңҲвҖңдёҷиҫ°пјҢеҝ жӯҰиҠӮеәҰдҪҝзҺӢжІӣи–ЁгҖӮеәҡз”іпјҢд»ҘеӨӘд»ҶеҚҝй«ҳз‘Җдёәеҝ жӯҰиҠӮеәҰдҪҝгҖӮиҮӘеӨ§еҺҶд»ҘжқҘпјҢиҠӮеәҰдҪҝеӨҡеҮәзҰҒеҶӣпјҢе…¶зҰҒеҶӣеӨ§е°Ҷиө„й«ҳиҖ…пјҢзҡҶд»ҘеҖҚз§°д№ӢжҒҜиҙ·й’ұдёҺеҜҢе®ӨпјҢд»ҘиөӮдёӯе°үпјҢеҠЁйҖҫдәҝдёҮпјҢ然еҗҺеҫ—д№ӢпјҢжңӘе°қз”ұжү§ж”ҝпјӣиҮій•ҮпјҢеҲҷйҮҚж•ӣд»ҘеҒҝжүҖиҙҹгҖӮеҸҠжІӣи–ЁпјҢиЈҙеәҰгҖҒйҹҰеӨ„еҺҡе§ӢеҘҸд»Ҙз‘Җд»Јд№ӢгҖӮдёӯеӨ–зӣёиҙәжӣ°пјҡвҖҳиҮӘд»ҠеҖәеё…йІңзҹЈпјҒвҖҷвҖқеҸёй©¬е…үд»ҘеүҚжңқе”җеҸІдёәйүҙпјҢ继з»ӯжј”з»ҺвҖңеҖәеё…и®әвҖқпјҢдёәеҸӨд»ЈдёӯеӣҪж”ҝжІ»е»әжһ„еҮәдёҖдёӘеҸҚи…җж–°жҰӮеҝөвҖ”вҖ”вҖңеҖәеё…вҖқпјҢдё“жҢҮйӮЈдәӣе…Ҳеҗ‘е·ЁеҜҢеҘёе•ҶеҖҹеҖәпјҢиҙҝиөӮеҶӣж–№пјҲиҖҢйқһе®°зӣёпјүпјҢдҝҳиҺ·ең°ж–№йҮҚиҒҢе’ҢжІ»жқғпјҢд»»иҒҢеҗҺеҶҚж•ӣеүҘжүҖйғЁд№Ӣж°‘пјҢеҒҝиҝҳеҖҹж¬ҫзҡ„иҠӮй•Үеәң帅们гҖӮиҝҷж ·дёҖз§ҚвҖңйүҙдәҺеҫҖдәӢпјҢжңүиө„дәҺжІ»йҒ“вҖқзҡ„вҖңжҳҘз§Ӣ笔法вҖқе’ҢеҸІе®¶жү№еҲӨжҖқз»ҙпјҢзҡ„зЎ®жңүиө„дәҺеҢ—е®ӢжІ»ж”ҝе’Ңеҫ·иӮІе»әи®ҫе·ҘдҪңгҖӮеңЁеҸёй©¬е…үзҠҖеҲ©зҡ„笔й”ӢдёӢпјҢеҝ жӯҰиҠӮеәҰдҪҝзҺӢжІӣеҸӘиғҪз®—жҳҜдёҖдҪҚвҖңжң«д»ЈеҖәеё…вҖқгҖӮеӣ дёәеңЁдёҖдёӘиҝһз»ӯдёҚж–ӯзҡ„жқҺе”җвҖңеҖәеё…вҖқдәәзү©и°ұзі»йҮҢпјҢжқҺеӨҚзҡ„ж”ҝжІ»е®ҡдҪҚй—®йўҳпјҢе®һдёҚиЁҖиҮӘжҳҺпјҒе®һиҙЁдёҠпјҢдёҖжҳҜеҗҺдәәе§Ӣз»ҲйғҪжІЎжңүзңӢеҲ°зӣёе…іж–ҮзҢ®пјҢжҳҺиҪҪжқҺеӨҚж•ӣиҙўжңүж–№пјҢд»ҘжқғеҜ»з§ҹпјӣдәҢжҳҜд№ҹжңӘеҮәзҺ°еҗҢж—¶д»Јзҡ„дәәзү©пјҢи®Ёи®әгҖҒжҸӯеҸ‘жҲ–жҢҮиҜҒд»–з”ҹжҙ»дёҚжЈҖпјҢиҙӘиҙўзҲұзү©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дёҖеҲҷжһҒжҳ“зҝ»йҳ…еҲ°жүӢзҡ„е”җд»ЈзҹіеҲ»ж–Ү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дёӯпјҢеҚ•е°ұи®°еҪ•зҡ„第дёҖ件治дәӢиҖҢи®әвҖ”вҖ”вҖңжғ§иҙ§иҙЎд№ӢйҳҷпјҢиҮіеҠ©д№Ӣд»Ҙ家иҙўпјӣжӮҜеҫӯдәӢд№Ӣз№ҒпјҢиҮід»Јд№Ӣд»Ҙз§ҒеұһвҖқпјҢе°ұиғҪиҜҙжҳҺй—®йўҳгҖӮжқҺеӨҚиғҪдё»еҠЁжӢҝеҮәиҮӘ家зҡ„з§Ғиҙўз§ҒеұһпјҢеҺ»ејҘиЎҘең°ж–№зәіиҙЎгҖҒжңҚеҪ№д№ӢдёҚи¶іпјҢд»Ҙе……жқҺе”җеӣҪз”ЁпјҢжҷ®еӨ©д№ӢдёӢпјҢе”җе®ӢиғҪжңүеҮ дәәпјҹжүҖд»ҘпјҢдёҖж—ҰеҜ№жӯӨе……иҖідёҚй—»пјҢиҪ¬иҖҢеҺ»и°ӢжұӮж–°зҡ„ж„Ҹд№үе»әжһ„пјҢиҝҳи°Ҳд»Җд№Ҳд№ҰеҶҷе’Ңи®°еҝҶпјҢи°ҒеҸҲиғҪиҜҙиҝҷж ·еҒҡдёҚжҳҜйў еҖ’й»‘зҷҪгҖҒж··ж·ҶжҳҜйқһпјҹе°ұ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зҡ„ж–Үжң¬з”ҹжҲҗиҖҢи®әпјҢе®ғе…Ҳз”ұе·һиЎҷеҗҢеғҡвҖңеІӯеҚ—з»Ҹз•ҘдҪҝеҲӨе®ҳгҖҒжқғзҹҘе®№е·һз•ҷеҗҺдәӢзӣ‘еҜҹеҫЎеҸІйҮҢиЎҢвҖқжқҺзүўиҚүжӢҹпјҢеҗҺйҖҒеҫҖдә¬еҹҺпјҢз”ұи‘—еҗҚеҸІе®ҳдәҺйӮөж’°е®ҡпјҢйғҪжҳҜйҒөз…§еҪ“ж—¶и§„з« еҲ¶еәҰеҠһдәӢгҖӮиҷҪ然жқҺеӨҚгҖҒжқҺзүўж—ўеҗҢ姓еҗҢд№ЎеҸҲеҗҢиЎҷе…ұдәӢпјҢз§ҒдәәдәӨжғ…ж·ұеҺҡпјҢдҪҶзҺӢжңқеӣҪ家зӨјеҲ¶й©¬иҷҺдёҚеҫ—гҖӮеҠ д№ӢйҖ’иҪ¬дәҺеӨҡдёӘйғЁй—ЁпјҢйҖҗзә§дёҠжҠҘпјҢдәәз№ҒеҸЈжқӮпјҢиӢҘе…¶и®°иҝ°иҜ„и®әзЁҚжңүдёҚе®һпјҢеҲҷеҝ…йҒӯж—¶дәәйқһи®®пјҢз”ҡжҲ–дёәз”ҹеүҚж”ҝж•ҢжҠ“дҪҸжҠҠжҹ„пјҢй…ҝжһ„дәӣж–ҮзӢұд№ӢзҘёгҖӮжӣҙдёҚз”ЁиҜҙпјҢе®ғжңҖз»ҲиҝҳиҰҒеҲ»е…ҘзҹіеӨҙпјҢз•ҷжҳӯеҗҺдё–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ҝҷзҜҮеҚғеӯ—ж–ҮпјҢиҷҪдёәжӯ»иҖ…и®іпјҢеүҚеүҚеҗҺеҗҺзҡ„д№ҰеҶҷдё»дҪ“йҡҫе…ҚеӨҡжңүжәўзҫҺд№ӢиҜҚпјҢдҪҶе®ғеңЁеҪ“е№ҙйЎәеҲ©йҖҡиҝҮеҗ„зұ»е®ЎжҹҘпјҢжңҖз»ҲжҲҗдёәжӯЈејҸзҡ„е®ҳж–№ж–Үд№ҰпјҢдәҺдәӢгҖҒдәҺжғ…гҖҒдәҺзҗҶгҖҒдәҺжі•пјҢзҡҶжҳҜеҗҲзҗҶеҗҲжі•зҡ„дә§зү©пјҢд№ҹжҳҜеҗҺдәәеҖјеҫ—е°ҠйҮҚзҡ„вҖңдҝЎеҸІвҖқгҖӮ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еңЁе”җе®Ӣд№Ӣйҷ…зӨҫдјҡиҪ¬еһӢзҡ„иҝӣзЁӢдёӯпјҢиөөе®ӢдёҖд»ЈпјҢеҙҮж–ҮжҠ‘жӯҰпјҢдёҖжҳҜеҲ¶еәҰ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жҙҫж–ҮиҮЈиҝӣеЈ«еҒҡең°ж–№зҹҘе·һпјҢеЈ«еӨ§еӨ«еҸӮж”ҝжҒ’жңүдҝқйҡңпјӣдәҢжҳҜд»·еҖј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жұүе”җе°ҡжӯҰзІҫзҘһе·Іж—Ҙи¶ӢдёҚеҪ°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Ҹӯжү№гҖҒжЈҖи®ЁеҺҶд»ЈжӯҰдәәзҡ„жІ»ж”ҝеҸІпјҢиҗҘе»әвҖңзҡҮеёқдёҺеЈ«еӨ§еӨ«е…ұжІ»еӨ©дёӢвҖқзҡ„дәәж–ҮжІ»ж”ҝж–°еұҖпјҢе·ІеұһеҢ—е®Ӣ欧йҳідҝ®гҖҒеҸёй©¬е…үзӯүвҖңе®ӢеӯҰ家们вҖқе»әжһ„ж–°ж”ҝжІ»ж–ҮеҢ–жңҖйңҖз”ЁеҠҹе’ҢеҠӘеҠӣ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еҖҹеҠ©д»ҘзҺӢжңқеӣҪ家дёәдёӯеҝғзҡ„жӯЈеҸІд№ҰеҶҷиҢғејҸпјҢеңЁйҮҚе»әиҝҮеҺ»дёӯе·§еҰҷвҖңеҸӮдёҺиҝҮеҺ»вҖқвҖңеҚҸе•ҶиҝҮеҺ»вҖқпјҢиҮӘ然е°ұжҳҜжңҖж–№дҫҝеҸҜеҸ–зҡ„зӯ–з•Ҙ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дёҖеҰӮйҫҡиҮӘзҸҚгҖҠеҸӨеҸІй’©жІүи®әдәҢгҖӢ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зҒӯдәәд№ӢеӣҪпјҢеҝ…е…ҲеҺ»е…¶еҸІгҖӮйҡідәәд№ӢжһӢпјҢиҙҘдәәд№ӢзәІзәӘпјҢеҝ…е…ҲеҺ»е…¶еҸІгҖӮз»қдәәд№ӢжүҚпјҢж№®еЎһдәәд№Ӣж•ҷпјҢеҝ…е…ҲеҺ»е…¶еҸІгҖӮеӨ·дәәд№ӢзҘ–е®—пјҢеҝ…е…ҲеҺ»е…¶еҸІгҖӮвҖқдјҙйҡҸзқҖжұүе”җжӯҰе°Ҷ世家йҖҗж¬ЎиЎ°иҙҘпјҢд»Һж”ҝжІ»дёӯеҝғдҪҚзҪ®иө°еҗ‘иҫ№зјҳеҢәпјҢеҗҺдё–еҜ№дәҺжӯҰе°Ҷ世家зҡ„иә«д»Ҫи®ӨеҗҢдёҺ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пјҢд№ҹеңЁжү№еҲӨе’ҢиҙЁз–‘еЈ°дёӯпјҢеҗҢж ·иө°еҗ‘жІүжІҰпјҒдёүгҖҒе”җе®ӢиҪ¬еһӢи§ҶеҹҹдёӢжӯҰе°Ҷ世家зҡ„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пјҡд»ҺгҖҠжқҺйҪҗзү©дј гҖӢеҲ°зҲ¶еӯҗвҖңеҗҲдј вҖқ жҚ®жӯЈеҸІиҪҪпјҢжқҺеӨҚжҳҜзӣ‘е·һеҲәеҸІгҖҒзҒөе·һйғҪзқЈжқҺеӯқиҠӮпјҲжё…жІізҺӢпјүзҡ„жӣҫеӯҷпјҢејҳеҶңйғЎеӨӘе®ҲжқҺз’ҹд№ӢеӯҷпјҢвҖңе……еӨӘеҺҹе·ІеҢ—иҜёеҶӣиҠӮеәҰдҪҝвҖқжқҺжҡ д№Ӣдҫ„пјҢвҖңжҢҒиҠӮе……жң”ж–№й•ҮиҘҝеҢ—еәӯе…ҙе№ійҷҲйғ‘зӯүиҠӮеәҰиЎҢиҗҘе…ө马еҸҠжІідёӯиҠӮеәҰйғҪз»ҹеӨ„зҪ®дҪҝвҖқпјҢвҖңеҠ е……з®ЎеҶ…жІідёӯжҷӢз»ӣж…Ҳйҡ°жІҒзӯүе·һи§ӮеҜҹеӨ„зҪ®зӯүдҪҝвҖқжқҺеӣҪиҙһд№Ӣе Ӯдҫ„пјҢвҖңеҺҶд»»жҖҖйҷ•дәҢе·һеҲәеҸІвҖқпјҢвҖңжҷҡе№ҙйҷӨеӨӘеӯҗеӨӘеӮ…е…је®—жӯЈеҚҝвҖқжқҺйҪҗзү©д№ӢеӯҗгҖӮжүҖд»ҘпјҢ家ж—ҸзҙҜдё–дёәе®ҳпјҢд»Јд»ЈзҡҶе…·ж”ҝжІ»дҪңдёәгҖӮ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иҜ„д»·иҝҷдёҖй«ҳй—ЁеӨ§ж—Ҹ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зҡ“пјҢеӯқеҸӢжё…ж…ҺпјҢеұ…е®ҳжңүз§°пјӣйҪҗзү©иҙһе»үж•ҙиӮғпјҢеӨҚиҠӮеҲ¶жқғи°ӢпјӣеӣҪиҙһжё…зҷҪе®Ҳжі•пјҢзҡҶзҘһйҖҡд№ӢжӣҫзҺ„пјҢе®—е®Өд№ӢзҝҳжҘҡгҖӮвҖқиөһиӘүжһҒйҮҚгҖӮиҝҷж®өиҜ„иҜӯд№ҹеӨ§иҮҙеӢҫз”»еҮәжқҺж°Ҹ家ж—ҸжІ»ж”ҝзҡ„еҲқжӯҘй•ңеғҸпјҡд»ҺжқҺзҘһйҖҡд»ҘдёӢпјҢиҝҷдёӘзҡҮе®Өиҙөж—Ҹе·ІжҳҜе®—е®ӨжҰңж ·пјҢдёӘдёӘйғҪиғҪдё»ж”ҝдёҖж–№пјҢиҙЎзҢ®з”ҡе·Ё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иҙөиҖҢдёҚйӘ„пјҢиҝңзҰ»дҫҲйқЎпјҢйўҮеӨҡжё…е»үд№ ж°”пјҢ他们дёә家ж—Ҹз§ҜзҙҜеҮәдёҖд»ҪиҙөйҮҚзҡ„иұЎеҫҒиө„жң¬гҖӮиҮіеҫ·е…ғиҪҪпјҲ756е№ҙпјүе”җиӮғе®—жқҺдәЁзҷ»еҹәеҗҺпјҢжқҺеӨҚд№ӢзҲ¶жқҺйҪҗзү©пјҲеӯ—йҒ“з”ЁпјүвҖңжӢңеӨӘеӯҗе®ҫе®ўпјҢиҝҒеҲ‘йғЁе°ҡд№ҰгҖҒеҮӨзҝ”е°№гҖҒеӨӘеёёеҚҝгҖҒдә¬е…Ҷе°№вҖқгҖӮеҶ…еӨ–жңқж”ҝпјҢе·ІеӨҡеҸӮдёҺи°ӢеҲ’гҖӮе°ұжІ»ж”ҝйЈҺж јиҖҢи®әпјҢ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иҜҙжқҺйҪҗзү©пјҢвҖңж— еӯҰжңҜпјҢеңЁе®ҳдёҘж•ҙвҖқпјҢвҖңдёәж”ҝеҸ‘е®ҳеҗҸйҳҙдәӢпјҢд»ҘеҜҹдёәиғҪпјҢдәҺзү©е°‘жҒ©пјҢиҖҢжё…е»үиҮӘйҘ¬пјҢдәәеҗҸиҺ«ж•ўжҠөзҠҜвҖқгҖӮеҗҺжқҘпјҢ欧йҳідҝ®гҖҠж–°е”җд№ҰгҖӢиҝӣдёҖжӯҘи®әжӣ°пјҡвҖңжҖ§иӢӣеҜҹе°‘жҒ©пјҢе–ңеҸ‘дәәз§ҒпјҢ然жҙҒе»үиҮӘе–ңпјҢеҗҸж— ж•ўж¬әиҖ…гҖӮвҖқжҖ»д№ӢпјҢжқҺйҪҗзү©иә«дёәжңқе»·йҮҚиҮЈпјҢеқҡжҢҒе»үжҙҒиҮӘеҫӢдёҚиҜҙпјҢиҝҳжӢје‘ҪжҸӯеҸ‘иҙӘе®ҳжұЎеҗҸзҡ„дё‘иЎҢпјӣеңЁеҲ‘йғЁеӨ„зҗҶжЎҲ件时пјҢеёёеёёдёҚи®Іжғ…йқўпјҢжҚ®дәӢи®әзҪҡпјҢиҝ‘д№ҺдәҺеҲ»и–„еҜЎжҒ©зҡ„法家дҪңйЈҺгҖӮж–°ж—§вҖңе”җд№ҰвҖқеҰӮжӯӨи®°дәӢиЎҢж–ҮпјҢжҳҫжҳҜдёҚиөһеҗҢвҖңд»ҘеҜҹдёәиғҪвҖқвҖңе–ңеҸ‘дәәз§ҒвҖқзҡ„жқҺж°Ҹдёәе®ҳе“ІеӯҰгҖӮиҝҷд№Ӣдёӯзҡ„зјҳз”ұпјҢеҗҢж ·жҳҜе”җе®ӢиҪ¬еһӢд№Ӣйҷ…пјҢе„’еӯҰеӨҚе…ҙжөӘжҪ®жұ№ж¶ҢпјҢиә«д»Ҫи®ӨеҗҢеү§еҸҳпјҢеҸІеӯҰж—Ҙи¶ӢвҖңд№үзҗҶеҢ–вҖқпјҢжӯЈеҸІд№ҰеҶҷиҖ…еңЁвҖңеҶ…еңЈвҖқвҖңеӨ–зҺӢвҖқзҡ„д»·еҖјйҖүжӢ©дёҠпјҢж„ҸжңүжүҖеұһвҖ”вҖ”еқҡдҝЎдј з»ҹ儒家д»ҘзҺӢйҒ“иғңйңёйҒ“зҡ„дёәж”ҝд№ӢйҒ“пјҢе°‘и°ҲеҶӣеҠҹд№Ӣзұ»зҡ„з»Ҹдё–иҮҙз”Ёпјӣ讲究д»ҘзӨјжІ»ж”ҝгҖҒд»Ҙд»Ғе…»еҫ·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ә«дёәдёҠзә§пјҢжқҺйҪҗзү©зҗҶеҪ“вҖңе»үиҖҢдёҚеҲҝвҖқпјҢе°ҪеҠӣеҪ°жҳҫеҮәеҸӮж”ҝд№Ӣе„’зҡ„йЈҺиҢғгҖҒдҪ“йҮҸгҖҒиғҶиҜҶе’Ңд»Ғж…ҲпјҢдҪ“жҒӨдёӢжғ…пјҢдёәдёӢеұһеҗҢеғҡе‘Ёж—ӢжҠӨзҹӯгҖҒжҺ©жҒ¶жү¬е–„пјӣз”ҡиҮідәҺеҸҳйҖҡеҲ¶еәҰпјҢжі•еӨ–ж–Ҫжғ…пјҢд№ҹиҰҒз»ҙзі»еҘҪиЎҷй—Ёзҡ„е’Ңи°җж”ҝжІ»з”ҹжҖҒгҖӮз ”жІ»дј з»ҹдёӯеӣҪж”ҝжІ»жҖқжғіеҸІиҖ…пјҢд»ҠеӨ©еӨ§дҪ“йғҪжҢҒжңүдёҖз§ҚвҖңеӨ–е„’еҶ…жі•вҖқзҡ„иҜҙжі•гҖӮз®ҖиЁҖд№ӢпјҢе®ғжҳҜдёҖз§ҚжқӮеҗҲвҖңеҫ·жІ»вҖқе’ҢвҖңжі•жІ»вҖқзҡ„еҸӨд»Јз»ҹжІ»зӯ–з•ҘпјҢд№ҹжҳҜдёӯеӣҪдј з»ҹж”ҝжІ»зҡ„еҹәжң¬еҶ…ж ё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ҺҶд»ЈзҺӢжқғеӨ–зӨәд»Ғж”ҝпјҢеҶ…еҙҮжі•е…ёпјҢе®ғдё»иҰҒиҝҳжҳҜй’ҲеҜ№зЁіе®ҡеҹәеұӮ秩еәҸжқҘи®Ізҡ„гҖӮеҸӨд»ЈвҖңжІ»ж°‘вҖқдёҺвҖңжІ»е®ҳвҖқзҡ„жІ»зҗҶеҜ№иұЎгҖҒеңәеҹҹеҸҠзҗҶеҝөж–№жі•пјҢеҗ„дёҚзӣёеҗҢпјҢдё”иҮӘжҲҗдёҖеҘ—дҪ“зі»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еңЁз®ЎзҗҶиҮӘиә«зҡ„е®ҳеғҡзі»з»ҹж—¶пјҢеӣ вҖңеҲ‘дёҚдёҠеӨ§еӨ«вҖқзҡ„йҒ—дј ж·ұеҺҡпјҢж•…вҖңеҶ…жі•вҖқеӨ§дҪ“д»…е…·иҷҡж–ҮгҖӮз”ұжӯӨпјҢе”җд»ЈеҲ‘йғЁе°ҡд№ҰжқҺйҪҗзү©зҡ„еҸҜиҙөе°ұеңЁдәҺпјҢд»ҘжқҺ家зҡҮж—ҸеҲ©зӣҠдёәйҮҚпјҢиҮӘдё»йҖүз”Ёж–ҮдәәеЈ«еӨ§еӨ«жүҖдёҚеұ‘зҡ„法家зҗҶеҝөпјҢе°ҶиЎҷй—Ёе®ҳеңәдёҺеҹәеұӮзӨҫдјҡзӯүиҖҢи§Ҷд№ӢпјҢдёҚз•ҷжғ…йқўгҖӮдҪҶиҝҷж ·еҒҡпјҢд»–е°ұеҝҪи§ҶдәҶвҖңж°‘вҖқдёҺвҖңе®ҳвҖқзҡ„иә«д»ҪеҢәеҲ«пјҢеҝ…然引иө·еҗҢзұ»зҡ„дёҚж»Ўе’Ңжү№иҜ„гҖӮеңЁејәи°ғеҝғжҖ§йҒ“еҫ·зҡ„вҖңе®ӢеӯҰвҖқи§ҶеҹҹдёӢпјҢд»–еҰӮжӯӨжІ»дәӢзҗҶж”ҝпјҢе®һеұһеҒҸзҰ»е„’家жӯЈйҒ“гҖӮйҷӨдәҶиў«ж–ҘдёәвҖңж— еӯҰжңҜвҖқпјҢе…¶дәәе…¶дәӢиҮӘ然жӣҙдёҚе…·еӨҮи®°еҝҶдёҺд№ҰеҶҷ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д»·еҖјпјҒеӨ©е®қдә”иҪҪпјҲ746е№ҙпјүпјҢжқҺйҪҗзү©еӣ еҫ—зҪӘжқғзӣёжқҺжһ—з”«пјҢиў«иҙ¬дёәз«ҹйҷөеӨӘе®ҲпјҲд»Ҡж№–еҢ—зңҒеӨ©й—ЁеёӮпјүпјҢдҪҶвҖңи°Әе®ҰвҖқд»Қж—§дёҚж”№еҫҖжҳ”зҡ„法家дёҫжҺӘгҖӮжқҺйҪҗзү©дёҖеҲ°д»»е°ұдёӢд»ӨпјҡвҖңе®ҳеҗҸжңүз° з°ӢдёҚдҝ®иҖ…пјҢеғ§йҒ“жңүжҲ’еҫӢдёҚзІҫиҖ…пјҢзҷҫ姓жңүжіӣй©ҫ蹶ејӣиҖ…пјҢжңӘиҮід№ӢеүҚпјҢдёҖж— жүҖй—®пјӣиҖҢд»ҠиҖҢеҗҺпјҢд№үдёҚзӣёе®№пјҒвҖқж——еёңйІңжҳҺең°иҰҒдёҺвҖңз° з°ӢдёҚдҝ®вҖқзҡ„иҙӘе®ҳжұЎеҗҸж–—дәүеҲ°еә•гҖӮйҡҫжҖӘд»–жңҖеҗҺзҰ»д»»ж—¶пјҢз«ҹйҷөвҖңиҖҒе№јйҒ®жӢҘпјҢдёҚеҫ—еҸ‘иҖ…дёүиҫ°вҖқгҖӮдёҠе…ғдәҢе№ҙпјҲ761е№ҙпјүдә”жңҲпјҢжқҺйҪҗзү©еҚ’пјҢзҡҮеёқиҫҚжңқдёҖж—ҘгҖӮеҪ“ж—¶жңқе»·иҚүиҜҸ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е®—е®ӨзҸӘз’ӢпјҢеЈ«жһ—жЎўе№Іпјӣжё…е»үзӢ¬ж–ӯпјҢеҲҡжҜ…дёҚзҫӨпјӣеҺҶи·өе‘ЁиЎҢпјҢеӨҮз»ҸдёӯеӨ–пјӣеЁҒеҗҚзӣҠжҢҜпјҢеҝ ж•ҲејҘеҪ°пјӣдёүе°№зҘһе·һпјҢдёҖзҷ»дјҡеәңпјӣж“’еҘёжҺ©й’©и·қд№ӢжңҜпјҢжҒӨзӢұжӯЈе–үиҲҢд№Ӣе®ҳпјӣйҒӮд»Өи°ғжҠӨеӮЁй—ұпјҢеҶҚзҷ»еёҲеӮ…пјӣд»Һе®№е®ҫеҸӢпјҢеёҲй•ҝе®ҳеғҡпјӣжЎ‘жҰҶд№Ӣж—¶пјҢеЈ®еҝ—йҖҫеҠұпјӣжқҫжҹҸд№ӢжҖ§пјҢжҷҡеІҒеёёеқҡгҖӮвҖқзңӢжқҘпјҢеҜ№дәҺиҝҷз§Қзү№з«ӢзӢ¬иЎҢгҖҒеҲҡжҜ…дёҚзҫӨзҡ„е®—е®ӨйІ зӣҙеӨ§иҮЈпјҢеҪ“жңқзҡҮдёҠиҝҳжҳҜзңје…үзӢ¬еҲ°пјҢеҗҢеғҡзңјдёӯзҡ„ејӮзұ»еҘҮи‘©пјҢеҜ№дәҺжңқе»·еҸҜе°ұжҳҜдёҖд»ҪеҸҜиҙөзҡ„ж”ҝжІ»иҙўеҜҢгҖӮеңЁж»ЎеҸЈд»Ғд№үйҒ“еҫ·зҡ„жұүе”җ儒家е®ҳеғҡзі»з»ҹдёӯпјҢж”ҫе…»еҮәиҝҷз§ҚдёҚеҸ—ж¬ўиҝҺзҡ„法家еһӢвҖңйі—йұјвҖқпјҢжңүдҫҝдәҺеҲәжҝҖзҷҫе®ҳпјҢеҘҪи®©йӮЈдёӘж…өеҖҰзҡ„йҷҲж—§зі»з»ҹ继з»ӯдҝқжҢҒдёҖд»Ҫзҙ§еј еәҰе’ҢиӯҰжғ•ж„ҹпјҢиҝӣиҖҢдҝғдҪҝзҺӢжңқеӣҪ家иЎҢж”ҝеҠӣзҡ„ж•ҙдҪ“жҸҗй«ҳе’ҢиҝҗиЎҢжңәеҲ¶зҡ„йІңжҙ»дёҚиЎ°гҖӮеҸҰпјҢзҲ¶еӯҗвҖңеҗҲдј вҖқпјҢиҝҷжҳҜдёӯеӣҪжӯЈеҸІд№ҰеҶҷзҡ„дј з»ҹдҪ“дҫӢгҖӮеҰӮжӯӨи®ҫзҪ®пјҢзӣ®зҡ„д№ӢдёҖе°ұжҳҜдҝғдҪҝиҜ»иҖ…дёә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жүҫеҜ»е®¶ж—ҸжёҠжәҗ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з§°пјҡвҖңзҡ“еҸ‘дәәйҳҙз§ҒпјҢйҪҗзү©з§Ҝиҙўе…ҙи®®пјҢеӣҪиҙһжҖҘдәҺж“ҚдёӢгҖӮвҖқиЁҖдёӢд№Ӣж„Ҹе°ұжҳҜдёӨд»ЈеҗҢж¬ҫпјҢдёҠжўҒдёҚжӯЈдёӢжўҒжӯӘпјҢжқҺеӨҚз”ұвҖңиҠӮеё…вҖқжІҰдёәвҖңеҖәеё…вҖқпјҢжҳҜ家ж—Ҹеҹәеӣ еңЁиө·дҪңз”ЁгҖӮиҝҷдёҖд№ҰеҶҷе»әжһ„пјҢи¶іи§ҒеҗҺдё–ж–Үдәәиҝҗ笔зҡ„ж·ұж„ҸгҖӮеҸҲеҰӮпјҢж–°ж—§вҖңе”җд№ҰвҖқе®Јжү¬вҖңд»ҘеҜҹдёәиғҪвҖқвҖңжҖ§иӢӣеҜҹе°‘жҒ©вҖқзӯүдёҠд»ЈжІ»ж”ҝйЈҺиҢғпјҢе®ғиҮӘ然е°ұдёәе…¶еҗҺд»Јд»Ҙ法家зҗҶеҝөй•Үиҫ№зҡ„ж”ҝжІ»йҖүжӢ©пјҢйў„зҪ®дәҶжҖ»иғҢжҷҜ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е·ІзӣҙжҺҘжҸҗдҫӣдәҶеҸҚи®әпјҡвҖңжҳҺи¶ід»Ҙз…§йҒҒжғ…йҡҗж…қиҖҢдёҚдёәеҜҹпјҢеЁҒи¶ід»ҘеҲ¶зҢҫдәәжҡҙеҗҸиҖҢдёҚдёәиӢӣгҖӮвҖқжүҖд»ҘпјҢзңҹе®һзҡ„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еҸІпјҢжҳҜеңЁе”җд»ЈжӯҰе°Ҷ家ж—ҸиғҢжҷҜе’ҢзҲ¶ж•ҷзҶҸйҷ¶дёӢпјҢвҖңжҙӘз»Әдё•з»©д№ӢдҪҷиЈ•пјҢе®Ҹдј‘зәҜжҮҝд№ӢдёӢй’ҹвҖқпјҢе®—е®ӨеҗҺдәәжқҺеӨҚеҚҙеҮәиҗҪеҫ—йқһеҗҢеҫҖиҖ…вҖ”вҖ”вҖңе®ҪеҚҡиҖҢжҹ”иүҜпјҢй«ҳжҳҺиҖҢз–ҸиҝңпјҢж №дәҺз»Ҹд№үпјҢйҘ°д»Ҙиүәж–ҮвҖқгҖӮеҪ°жҳҫеҮәе”җе®ӢиҪ¬еһӢиҝӣзЁӢдёӯдёӘдҪ“з”ҹе‘Ҫзҡ„йҖүжӢ©еҸҳеҠЁгҖӮз”ҹй•ҝдәҺжӯҰе°Ҷ世家пјҢдҪҶд»–еҸҲиғҪдёҺж—¶дҝұиҝӣпјҢи¶ҠеҮә家йҒ“дј з»ҹзҡ„йҷҗе®ҡпјҢй•ҝеҮәж–°ж„Ҹ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»Јйҷ…еҸҳеҢ–пјҢжүҚзҗҶеҪ“жҳҜзҲ¶еӯҗвҖңеҗҲдј вҖқзҡ„д№ҰеҶҷиҰҒзӮ№гҖӮжҚ®з« зӮійәҹгҖҠеҺҹеӯҰгҖӢиҖғеҜҹжҖқжғіз”ҹжҲҗеҸ‘еұ•зҡ„йҖ»иҫ‘жқҘзңӢпјҢ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зҡ„жҲҗеҠҹпјҢжҳҜжқҺе”җвҖңж”ҝдҝ—вҖқгҖҒжӯҰе°Ҷдё–е®¶дј з»ҹе’ҢдёӘдәәвҖңжқҗжҖ§вҖқз»јеҗҲеҸ‘еұ•зҡ„жҖ»з»“жһңгҖӮ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вҖңдёҖжҠҠжүӢвҖқзҡ„еЁҒйҮҚдёҺеҗҸжІ»жҳҜе…¶й•ҝпјҢж•…вҖңдәІеё…е…¶дёӢвҖқпјҢжҠҠеҘҪиҫ№ең°вҖңиЎҷй—Ёе…івҖқпјҢд»Ҙиә«зӨәиҢғпјҢз”ұе·ұеҸҠдәәпјҢдҝғжҲҗе®ҳеңәдёҠдёӢдёҖеҝғеҠЎж”ҝпјҢд»ҺвҖңеҗҸйҒ“вҖқжңқеҗ‘вҖңж”ҝйҒ“вҖқпјҢжңҖз»ҲеҗҸжё…ж”ҝжҲҗгҖӮжқҺеӨҚзҡ„иҝҷдёҖжІ»иҫ№йҖ»иҫ‘пјҢд№ҹеҲҡеҘҪжҺҘиҝ‘дәҶеҸӨд»Јиҫ№з–Ҷж”ҝжІ»еҸ‘еұ•зҡ„ж ёеҝғвҖ”вҖ”ж— еҫ·дёҚиҫ№пјҢжІ»иҫ№йҰ–йҮҚеҗҸжІ»гҖӮдёҖж—ҰеҗҸйЈҺдёҚжҢҜпјҢдҝЎд»°иҝ·еӨұпјҢе®ғеҚіеҲ»еҠЁж‘Үж°‘еҝғпјҢжҝҖеҢ–ж°‘ж—ҸеҶІзӘҒпјҢз”ҡжҲ–еј•е…ҘеӨ–жқҘдҫөз•ҘеҠҝеҠӣпјҢеҲҶиЈӮзҘ–еӣҪпјҢзӮ№зҮғжҲҳзҒ«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ҫ№йҷІзӨҫдјҡе§Ӣз»Ҳе°ұжҳҜдёҖеқ—йҒ“еҫ·иҜ•йҮ‘зҹіпјҡе®ҲдёҚдҪҸиҙ«з©·пјҢиҖҗдёҚдҪҸеҜӮеҜһпјҢжҠҠжҢҒдёҚдҪҸеҝғжҖ§пјҢзӮје°ұдёҚеҮәжё…е»үзҡ„еҶ…йӘЁгҖҒиғҶиҜҶе’Ңдәәж јпјҢе°ұдёҚй…ҚеҒҡиҫ№з–ҶеӨ§иҮЈпјҒиҝңеңЁиҫ№йҷІзҡ„е№ҝиҘҝпјҢе®һиҙЁе°ұжҳҜзҺӢжңқеӣҪ家зҡ„дёҖзүҮзҗҶжғіеһӢеҫ·иӮІеңәеҹҹгҖӮ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дҪңиҖ…еҸ—йҷҗдәҺвҖңж–Ҝж–ҮвҖқз«Ӣеңәе’Ңиә«д»Ҫжғ…з»“пјҢе°Ҡе„’и®Ҙжі•пјҢз»“жһңе°ұж— жі•еҜ№дәҺжӯҰе°Ҷ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зҡ„ж”ҝжІ»йҒ—дә§вҖ”вҖ”иҫ№з–Ҷеҫ·жІ»иҙЎзҢ®пјҢдәҲд»Ҙж·ұжҸӯ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жқҺеӨҚиҷҪ然е°ҶжӯҰе°Ҷ世家ж–ҮеҢ–еёҰе…ҘеІӯеҚ—пјҢдҪҶйҖҡиҝҮе…·дҪ“зҡ„жІ»е®№е®һи·өпјҢдё»дҪ“жҖ§е·ІеӨҡж–°еҸ‘еұ•гҖӮ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иҖҢеҗҺиҮіжҳҜе·һпјҢжҒ©з»“дәҺдәәпјҢеҠҹеҠ дәҺзү©пјҢеҝ…й—»зҗҶж•ҲиҖҢе…ҙйўӮеЈ°гҖӮвҖқдёҺе…¶зҲ¶иҫҲзӣёжҜ”пјҢд»–дёҚеҶҚж•ҙеӨ©еңЁиЎҷй—ЁйҮҢжқҝзқҖи„ёпјҢеҲ°еӨ„жүҫеҲ«дәәзҡ„зјәзӮ№е’ҢиҝҮеӨұпјҢи®©дәәи§ҒиҖҢйҒҝд№ӢпјҢз»·зҙ§дәҶеҗҢиЎҷзҡ„е…ұдәӢе…ізі»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е„’жі•е…јдҝ®пјҢд»–иҪ¬иҖҢйҮҮз”Ёж–ҮдәәеЈ«еӨ§еӨ«зҡ„еҫ·иӮІж–№жі•и®әпјҢвҖңжҒ©з»“дәҺдәәвҖқпјҢдҝ®еҘҪдәәйҷ…е…ізі»пјҢз§ҜжһҒиҗҘе»әиҫ№з–ҶиЎҷй—Ёз»„з»Ү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зҲ¶дәІжқҺйҪҗзү©дёҚз»“е…ҡиҗҘз§ҒпјҢдёҚеҗҢжөҒеҗҲжұЎпјҢвҖңеҲҡжҜ…дёҚзҫӨвҖқзҡ„法家еҸӮж”ҝйЈҺйӘЁпјҢд№ҹдёҚзӯүдәҺиҜҙд»–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и°ҷдәәжғ…дё–йҒ“зҡ„й“Ғеҝғжұү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з«ҹйҷөеӨӘе®Ҳд»»дёҠпјҢд»–ж…§зңјиҜҶиӢұпјҢеңЁең°ж–№д№җйҳҹзҡ„ж•ҷеёӯдёӯпјҢз»“иҜҶеҪ“ең°дәәйҷҶзҫҪгҖӮжҚ®гҖҠйҷҶж–ҮеӯҰиҮӘдј гҖӢиҪҪпјҡйҷҶзҫҪвҖңжңүд»Іе®ЈгҖҒеӯҹйҳід№ӢиІҢйҷӢпјҢзӣёеҰӮгҖҒеӯҗдә‘д№ӢеҸЈеҗғпјҢиҖҢдёәдәәжүҚиҫ©пјҢдёәжҖ§иӨҠиәҒпјҢеӨҡиҮӘз”Ёж„ҸпјҢжңӢеҸӢ规и°ҸпјҢиұҒ然дёҚжғ‘гҖӮеҮЎдёҺдәәе®ҙеӨ„пјҢж„ҸжңүжүҖйҖӮпјҢдёҚиЁҖиҖҢеҺ»гҖӮдәәжҲ–з–‘д№ӢпјҢи°“з”ҹеӨҡе—”гҖӮеҸҲдёҺдәәдёәдҝЎпјҢиҷҪеҶ°йӣӘеҚғйҮҢпјҢиҷҺзӢјеҪ“йҒ“пјҢдёҚж„Ҷд№ҹгҖӮдёҠе…ғеҲқпјҢз»“еәҗдәҺиҢ—жәӘд№Ӣ湄пјҢй—ӯй—ҫиҜ»д№ҰпјҢдёҚжқӮйқһзұ»гҖӮеҗҚеғ§й«ҳеЈ«пјҢи°ҲзҮ•ж°ёж—ҘгҖӮеёёжүҒиҲҹеҫҖжқҘеұұеҜәпјҢйҡҸиә«е”Ҝзәұе·ҫи—ӨйһӢзҹӯиӨҗзҠҠйј»пјҢеҫҖеҫҖзӢ¬иЎҢйҮҺдёӯпјҢиҜөдҪӣз»ҸпјҢеҗҹеҸӨиҜ—пјҢжқ–еҮ»жһ—жңЁпјҢжүӢеј„жөҒж°ҙпјҢеӨ·зҠ№еҫҳеҫҠпјҢиҮӘжӣҷиҫҫжҡ®пјҢиҮіж—Ҙй»‘е…ҙе°ҪпјҢеҸ·жіЈиҖҢеҪ’пјҢж•…жҘҡдәәзӣёи°“пјҡйҷҶеӯҗзӣ–д»Ҡд№ӢжҺҘиҲҶд№ҹгҖӮвҖқжң¬жқҘе°ұжҳҜдёӘвҖңдёҚжӯЈеёёвҖқзҡ„ејӮдәә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Қ®е‘Ёж„ҝгҖҠзү§е®Ҳз«ҹйҷөеӣ жёёиҘҝеЎ”и‘—дёүж„ҹиҜҙгҖӢз§°пјҢжқҺйҪҗзү©з«ҹ然вҖңи§ҒејӮпјҢжҚүжүӢжӢҠиғҢпјҢдәІжҺҲиҜ—йӣҶпјҢдәҺжҳҜжұүжІ”д№Ӣдҝ—дәҰејӮз„үвҖқпјҢз®ҖзӣҙеҰӮиҺ·иҮіе®қпјҢзҲұдёҚйҮҠжүӢгҖӮйҷӨдәҶжӢҝеҮәиҮӘе·ұз§ҳдёҚзӨәдәәзҡ„зҸҚиҙөиҜ—ж–ҮйӣҶпјҢдәІиҮӘдј жҺҲж–ҮеӯҰпјҢи®©е…¶д№ЎеңҹзІ—йҮҺд№Ӣж°”ж—Ҙе°‘д№ӢеӨ–пјҢиҝҳеҝҷзқҖжҠҠд»–жҺЁиҚҗеҲ°зҒ«й—ЁеұұпјҲд»ҠеӨ©й—ЁеёӮдҪӣеӯҗеұұпјүйӮ№еӨ«еӯҗеӨ„еӯҰд№ ж·ұйҖ гҖӮеҖҹжӯӨжҸҙеҠ©пјҢйҷҶзҫҪйҒҚиҜ»еңЈиҙӨд№ҰпјҢе®Ңе…Ёи„ұиғҺжҚўйӘЁпјҢдёҖж”№еҫҖжҳ”жҖӘзҷ–пјҢвҖңзҷҫж°Ҹд№Ӣе…ёеӯҰпјҢй“әеңЁжүӢжҺҢпјҢеӨ©дёӢиҙӨеЈ«еӨ§еӨ«еҚҠдёҺд№ӢжёёвҖқпјҢдёәе…¶ж—ҘеҗҺжҲҗдёәвҖңиҢ¶еңЈвҖқпјҢеҘ е®ҡдәҶеҹәзЎҖгҖӮжӯЈжҳҜжқҺгҖҒйҷҶдәҢдәәжңүдәҶиҝҷдёҖж®өзңҹжҢҡеҸӢжғ…пјҢдәҺжҳҜпјҢвҖңз”ҹдәҺе®Ҳд№Ӣж—ҘвҖқзҡ„жқҺеӨҚпјҢй•ҝеӨ§еҗҺеҺ»еҒҡе®№е·һеҲәеҸІж—¶пјҢвҖңиҢ¶еңЈдәәвҖқе°ұд»Ҙй…¬жҒ©д№Ӣж•…пјҢдёҺе‘Ёж„ҝпјҲдәҰдёәеІӯеҚ—иҠӮеәҰд»ҺдәӢпјүгҖҒ马жҖ»зӯүдәәдёҖиө·пјҢдё»еҠЁеҚ—дёӢвҖңдҪҗе…¬д№Ӣ幕вҖқпјҢдёҖе®ҡиҰҒдәІиҮӘи·‘еҲ°е®№е·һпјҢеҺ»еҒҡжқҺеӨҚзҡ„幕еғҡ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йқһжҳҜзҲ¶иҫҲе№ҝз»“е–„зјҳпјҢйқһжҳҜдёҠд»ЈдәӨжғ…ж·ұиҝңпјҢдҪ•иҮідәҺжӯӨпјҒжӯЈжҳҜжңүдәҶйҷҶзҫҪиҝҷеё®вҖңеІӯеҚ—иҠӮеәҰд»ҺдәӢвҖқ们зҡ„еҸӮдёҺпјҢжқҺеӨҚжІ»ж”ҝиҫ№з–Ҷжҳҫ然еҸҲжңүдәҶжӣҙеӨҡж–°иө„жәҗеҸҠе…¶ж–°ж•…дәӢ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үҚдәәж Ҫж ‘пјҢеҗҺдәәж‘ҳжһңпјҒдј з»ҹжқғеҠҝд№Ӣ家е№ҝжӨҚй—Ёе®ўгҖҒ幕еғҡжҲ–з§ҒеұһпјҢиҚ«еәҮдәҶдёҖеё®вҖңйёЎйёЈзӢ—зӣ—вҖқд№Ӣеҫ’пјҢе®ғе°ұдёәеҗҺдәә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зҗҶж”ҝжҸҗдҫӣдәҶжӣҙеӨҡж”ҜжҢҒгҖӮ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еҰӮжӯӨд№ҰеҶҷзҲ¶еӯҗвҖңеҗҲдј вҖқпјҢе®ғжүҚиғҪиөӢдәҲдёҖз§Қж–°зҡ„еҺҶеҸІд»·еҖјгҖӮеӣӣгҖҒвҖңж”ҝйҒ“вҖқдёҺвҖңеҗҸйҒ“вҖқпјҡвҖңиҠӮеё…вҖқжІ»иҫ№зҡ„еҺҶеҸІе®Ўи§Ҷ 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иҜ„д»·жқҺеӨҚд№Ӣж”ҝ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еӨҚжҷ“дәҺж”ҝйҒ“пјҢжүҖеңЁз§°зҗҶгҖӮвҖқиӢҘе°ұ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жүҖиҪҪ10件иҫ№з–ҶжІ»дәӢиҖҢи®әпјҢиҝҷдёҖжҖ»иҜ„иҝҳз®—жңүж–ҮеҸҜеҫҒпјҡйҖүжӯҰиүәгҖҒејҖеұҜз”°гҖҒзәіиҙЎиҒҢд№ҹеҘҪпјҢж ‘жқҝе№ІгҖҒеҲ—дәӯзҮ§гҖҒиЎҢеҫҒд»Өд№ҹзҪўпјҢе®ғ们йғҪжҳҜиҠӮеҲ¶й•Үиҫ№гҖҒд»ҘеҶӣдәӢдёәйҮҚзҡ„еҝ…然йҖүйЎ№гҖӮдҪҶ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еҚ•еҮӯеҪ’иҝҳвҖңжІЎдёәе®ҳеҘҙе©ўвҖқиҖ…дёҖдәӢпјҢе°ұж–ӯ然дҪңеҮәвҖңжҷ“дәҺж”ҝйҒ“вҖқзҡ„иҜ„и®®пјҢж—ўжҳҫиӢҚзҷҪпјҢеҸҲиЁҖиҝҮе…¶е®һгҖӮе”җжңқж”ҝеәңжү“еҮ»иұӘж—ҸеӨ§жҲ·пјҢи§Јж”ҫеҘҙйҡ¶пјҢжё…зҗҶиҗҪеҗҺзҡ„е°Ғе»әдәәиә«дҫқйҷ„е…ізі»пјҢдёәзҺӢжңқеӣҪ家еўһеҠ дәәеҸЈе’ҢеҠіеҠЁеҠӣпјҢиҝҷзҡ„зЎ®жҳҜе”җе®ӢзӨҫдјҡиҪ¬еһӢжңҹзҡ„дёәж”ҝдё»йҒ“гҖӮжқҺеӨҚеҮәиә«зҡҮж—ҸпјҢеҸҲжҳҜе°Ҷй—ЁвҖң世家еӯҗвҖқпјҢиғҪеҗҰиҮӘиЎҢе°ҶдёӯеҺҹејҖе§Ӣзҡ„и§Јж”ҫеҘҙе©ўиҝҗеҠЁпјҢеҚ—жҺЁеІӯиЎЁпјҢиҝҷзҡ„зЎ®жҳҜжЈҖйӘҢвҖңжҷ“дәҺж”ҝйҒ“вҖқзҡ„жңҖеҘҪиҜ•еүӮгҖӮз”ҡжғңзҡ„жҳҜпјҢ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зў‘ж–ҮвҖңжӮҜеҫӯдәӢд№Ӣз№ҒпјҢиҮід»Јд№Ӣд»Ҙз§ҒеұһвҖқдёҖиҜӯпјҢеҲҡеҘҪеҸҲйҖҸйңІеҮәеҪ“йҷ…и§Јж”ҫеҘҙйҡ¶зҡ„зңҹе®һйқўзӣёпјҡжқҺеӨҚвҖңиҲҚеҜҮиҙјд№Ӣдёәзј§еӣҡиҖ…пјҢйҮҠиҖҢйҒЈд№ӢпјҢд»ҘйҷӨе…¶жҖЁпјҢиҖҢзӢҷзҠ·д»ҘйЎәвҖқпјҢйҮҠж”ҫеІӯеҚ—е®ҳеҘҙ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ј з»ҹжӯҰе°Ҷ世家иҮӘ家зҡ„дё»д»ҶдҪ“зі»дҫқ然еҒҘеңЁж— жҚҹпјҢеҸӘжҳҜйҒҮеҲ°ең°ж–№еҫӯеҪ№еҫҒеҸ‘жңүеӣ°йҡҫпјҢд»–е°ұзј©еҮҸ家дёӯжқӮеҠЎпјҢжҠҪеҮәдәӣз§Ғ家еҠӣйҮҸеҺ»е®ҢжҲҗеӣҪ家任еҠЎ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жқҺеӨҚдёҖж–№йқўи§Јж”ҫеҮәдёҖеӨ§жү№еңЁиӢҰйҡҫдёӯжұӮз”ҹзҡ„е®№е·һе®ҳеҘҙпјҢ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»–并没жңүжё…йҶ’ең°иҰҒд»ҺиҮӘ家ејҖе§ӢпјҢе…Ҳе®ҢжҲҗдёҖж¬ЎеҪ»еә•зҡ„вҖң家еәӯйқ©е‘ҪвҖқд№ӢеҗҺпјҢеҶҚе°Ҷе…¶жү©еұ•гҖҒжј”з»ҺдёәдёҖеңәж·ұеҲ»зҡ„зӨҫдјҡйқ©е‘ҪгҖӮдёӘдҪ“зҡ„ж”ҝжІ»и®ӨзҹҘеҺҹжң¬еҰӮжӯӨпјҢд»Қд»ҘеҠҝ家жҺ§еҲ¶дәәиә«дёәеҗҲжі•пјҢеҸҲдҪ•ж•ўз§°е…¶вҖңжҷ“дәҺж”ҝйҒ“вҖқпјҹе……е…¶йҮҸпјҢд»–йӮЈд№ҲеҒҡд№ҹеҸӘжҳҜйЎәеә”еҪ“ж—¶е®ҳеңәд№ ж°”иҖҢе·ІпјҢ并дёҚе…·жңүж”ҝжІ»дёҠзҡ„иҮӘи§үгҖӮи®ҫиӢҘе°Ҷе…¶д№ҰеҶҷи°ғж•ҙдёәвҖңжҷ“дәҺеҗҸйҒ“вҖқвҖ”вҖ”д»ҘвҖңеҗҸйҒ“вҖқжҚўвҖңж”ҝйҒ“вҖқпјҢиҷҪдёҖеӯ—д№Ӣе·®пјҢд№ҹи®ёжӣҙеҘ‘еҗҲе…¶дёҠд»ЈйҮҚжі•жІ»еҗҸгҖҒвҖңд»ҘеЁҒйҮҚи§Ғз§°вҖқзӯүиЎҢж–Үдёӯзҡ„еҶ…еңЁж„Ҹи•ҙдәҶ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жң¬дј ејҖзҜҮе°ұиҜҙжқҺеӨҚвҖңзІҫжҷ“еҗҸйҒ“вҖқвҖңжҖ§иӢӣеҲ»вҖқвҖңзҡҶи‘—ж”ҝеЈ°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ҺҶеҸІд№ҰеҶҷиҖ…дёҚи°ЁдәҺеҲқж–ҮпјҢиҮӘд№ұз« жі•пјҢз»“жһңе°ұи®©ж–Үжң¬ж— жі•е®һзҺ°йҖ»иҫ‘иҮӘжҙҪпјҢж— еҠ©дәҺеӨҚзҺ°еҺҶеҸІзңҹзӣёгҖӮеҗҢж ·пјҢ欧йҳідҝ®йҮҚдҝ®гҖҠе”җд№ҰгҖӢпјҢеҸёй©¬е…үдёәиөөе®Ӣе®ҳеңәвҖңи®ІйҒ“жҺҲиҜҫвҖқпјҢд»…д»…дҫқиө–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зҡ„е®ҳж–№и®°иҪҪпјҢз»“жһңйғҪзҠҜдәҶе…¶жі•дёҚе‘Ёзҡ„й”ҷиҜҜгҖӮиә«дёәжұҹеҚ—ең°ж–№ж–°е…ҙж–ҮеЈ«е’Ңж–°жҷӢзҡ„вҖңиҝӣ士公们вҖқпјҢ欧йҳідҝ®гҖҒеҸёй©¬е…үзӯүдәәеңЁе®Ји®ІвҖңж–Ҝж–ҮвҖқд№ӢйҒ“гҖҒзІҫеҝғе»әжһ„еЈ«еӨ§еӨ«дёҺжІ»жқғ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е…ізі»ж—¶пјҢеҜ№дәҺжұүе”җжӯҰдәәеҲәйғЎгҖҒвҖңиҠӮеҲ¶жқғи°ӢвҖқзӯүжІ»зҗҶиҢғејҸпјҢиҮӘ然еҝғеӯҳиҠҘи’ӮгҖӮдҪҶ他们иҪ»дҝЎеүҚдәәиЁҖи®әпјҢејәи°ғиә«д»Ҫе·®ејӮпјҢ继з»ӯзқҖжү№дјҗжӯҰе°ҶжІ»иҫ№пјҢе®һеҸҲзңҹдёҚиҜҶе”җд»Јзҡ„вҖңиҫ№з–Ҷж”ҝжІ»вҖқгҖӮеӣ дёәдј з»ҹжІ»зҗҶиҫ№з–Ҷжңүе…¶иҮӘ然еҺҶеҸІйҖ»иҫ‘пјҢз®ҖиЁҖд№ӢпјҡеҶӣдәӢжҺ§еҲ¶вҶ’ж”ҝжІ»е»әеҲ¶вҶ’з»ҸжөҺеҲ‘еҗҚвҶ’ж–Үж•ҷйҒ“еҫ·пјҢеӣҪ家еңЁеңәпјҢжӯҘжӯҘдёәиҗҘпјҢж–№иғҪдҝғжҲҗиҫ№з–ҶвҖңеҶ…ең°еҢ–вҖқпјҢиҝӣиҖҢзЁіиҫ№еӣәиҫ№гҖҒе…ҙиҫ№ејәиҫ№гҖӮдёҖж—Ұд»»ж„Ҹйў еҖ’гҖҒжү°д№ұзЁӢеәҸеҸҠе…¶ж—¶з©әжі•еәҰпјҢеҲҷеҝ…然з”ҹйҡҷпјҢж”ҝйҒ“еӨұзәІгҖӮзү№еҲ«жҳҜпјҢжҚ®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В·ең°зҗҶеҝ—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ж°ёеҫҪеҗҺпјҢд»Ҙе№ҝгҖҒжЎӮгҖҒе®№гҖҒйӮ•гҖҒе®үеҚ—еәңпјҢзҡҶйҡ¶е№ҝеәңйғҪзқЈз»ҹж‘„пјҢи°“д№Ӣдә”еәңиҠӮеәҰдҪҝпјҢеҗҚеІӯеҚ—дә”з®ЎгҖӮвҖқдёәеҠ ејәеҜ№иҘҝеҚ—ең°еҢәзҡ„жҺ§еҲ¶пјҢжқҺе”җзҺӢжңқеңЁеІӯеҚ—жҺЁиЎҢвҖңдә”з®ЎвҖқд№ӢеҲ¶пјҢжңҖжҳҫжІ»зҗҶеҸ‘жҳҺ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вҖңе®№з®ЎвҖқеұ…е…¶дёҖпјҢдё”зҙ§жүјжө·дёҠдёқз»ёд№Ӣи·ҜпјҢең°дҪҚйҷ©иҰҒпјҢжҳҜиҘҝеҚ—д№Ӣе…ій”®жһўзәҪгҖӮең°ж–№ж—§еҝ—иҪҪпјҡвҖңе®№д»ӢжЎӮгҖҒе№ҝд№Ӣй—ҙпјҢзӣ–зІӨеҫјд№ҹгҖӮвҖқжұүиҜӯз©әй—ҙжҰӮеҝөвҖңеҫјвҖқпјҢжҢҮеҗ‘зҡ„е°ұжҳҜиҫ№зјҳеҢәгҖӮе®№е·һд»ҘвҖңзІӨеҫјвҖқпјҲеҚідёӨе№ҝзҡ„иҫ№з–ҶпјүиҮӘз§°иҮӘиҜ©пјҢжҳҫе·ІжҠҳе°„еҮәе®ғеҜ№дәҺзҪ®иә«вҖңдә”з®ЎвҖқдҪ“зі»зҡ„зӢ¬еҲ°и®ӨзҹҘвҖ”вҖ”е®№е·һжӣҙжҳҜиҫ№з–Ҷдёӯзҡ„вҖңиҫ№з–Ҷ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ёәжңүж•Ҳе®һзҺ°еӣҪ家еңЁеңәе’ҢйңҮж…‘еўғеӨ–пјҢе”җд»ЈйҖүе°ҶжІ»е®№пјҢејәи°ғжӯҰеҠӣе®һиҫ№пјҢе®һжңүиҫ№з–ҶжІ»зҗҶзҡ„зӢ¬еҲ°ж„Ҹи•ҙгҖӮдҪҶжҳҜе…Ҙе®ӢеҗҺпјҢеҲ¶еәҰйқ©ж–°пјҢжҚҹзӣҠйқһеёёпјҢе·ІдёҚеӨҚжҳЁж—Ҙ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ҸІиҪҪзҶҷе®Ғе…«е№ҙпјҲ1075е№ҙпјүпјҢдәӨеқҖвҖңе…ҘеҜҮпјҢдј—еҸ·е…«дёҮпјҢйҷ·й’ҰгҖҒе»үпјҢз ҙйӮ•еӣӣеҜЁвҖқгҖӮж¬Ўе№ҙдёүжңҲеҲқдёүпјҢвҖңеҹҺйҒӮйҷ·вҖқ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зҹҘпјҢе®Ӣд»Јз”Ёж–Үж”№жӯҰвҖ”вҖ”зҢқ然改еҸҳе”җд»ЈвҖңйғҪзқЈвҖқвҖңеҶӣеәңвҖқдҪ“еҲ¶пјҢйҮҮз”Ёж•ҙйҪҗеҲ’дёҖзҡ„ж–ҮиҮЈзҹҘе·һгҖҒд№Ұз”ҹй•Үиҫ№пјҢд»ҘжүҒе№іеҢ–зҡ„ең°ж–№жІ»зҗҶиҢғејҸеҸ–д»Јзү№ж®ҠжҖ§зҡ„иҫ№з–ҶжІ»зҗҶж ·ејҸпјҢзЎ®е®һдёәж—¶иҝҮж—©гҖӮиҫ№ең°иҜёе·һиЎҢж”ҝи¶ӢеҗҢеҢ–пјҢдҪҶеҗ„иҮӘдёәиҗҘ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еҝҳеҚҙе’Ңж¶ҲйҷӨе®№гҖҒйӮ•зӯүиҫ№иҰҒе·һйғЎзҡ„е·®ејӮеҢ–жІ»зҗҶеҸІпјҢи®©ж—§жңүзҡ„ж•ҙдҪ“жҖ§иҫ№йҳІжӯҰеӨҮеҪ»еә•жҚҹжҜҒгҖӮиҫ№з–Ҷең°еҢәдёҖдҪ“еҢ–зҡ„еҶӣдәӢйҳІеӨҮе°ҡжңӘжҲҗеҠҹпјҢе°ұеҝҷзқҖжҺЁиЎҢдёҖдҪ“еҢ–зҡ„ж–Үе®ҳж”ҝжІ»пјҢе№»жғізқҖж—©ж—Ҙе®һзҺ°еІӯеҚ—иЎҢж”ҝзҡ„вҖңеҶ…ең°еҢ–вҖқпјҢз»“жһңе°ұдёҚеҫ—дёҚдёәжӯӨд»ҳеҮәд»Јд»·вҖ”вҖ”иҮӘвҖңзҶҷе®Ғе®үеҚ—д№ӢеҪ№вҖқеҗҺпјҢе®үеҚ—еҪ»еә•и„ұзҰ»и—©еұһдҪ“зі»гҖӮжӯӨжғ…жӯӨжҷҜпјҢзӣёиҫғдәҺдә”д»ЈеҢ—е®ӢеҸІеӯҰ家们д№ҰеҶҷжӯҰе°ҶдёҚжі•гҖҒи®Ҙж–ҘвҖңеҖәеё…вҖқпјҢеҸҲдҪ•е…¶еӨ§зҹЈпјҒд»ҘеҸІдёәйүҙпјҢеҗҺдё–д№үзҗҶеҢ–еҸІеӯҰеӣ дәәи®әж”ҝпјҢеӣ е…¶жӯҰе°Ҷиә«д»ҪиҖҢи®ҘиҜӢе…¶ж”ҝпјҢж—ўйҷҗе®ҡдәҶиҮӘиә«зҡ„ж”ҝжІ»и®ӨзҹҘпјҢеҸҲз»ҲдёҚжҳҺеҜҹдәҺеІӯеҚ—вҖңж”ҝйҒ“вҖқпјҢдёҚиғҪзңҹе®һжҙһи§ҒеҸӨд»ЈдёӯеӣҪиҫ№з–ҶжІ»зҗҶзҡ„зү№ж®ҠжҖ§гҖӮдҪҷ и®ә д№ҰеҶҷз”ҹжҲҗеҗҺзҡ„ж–Үжң¬пјҢж— и®әжӯЈеҸІйҮҺи°ҲпјҢзҡҶжүҝиҪҪдёҚеҗҢи®°еҝҶиҖ…е’Ңд№ҰеҶҷдё»дҪ“зҡ„жқғеҠӣгҖҒж„Ҹеҝ—дёҺжғіиұЎгҖӮеҸІе®һгҖҒж–Үжң¬гҖҒж„ҸиҜҶдёүиҖ…е…ұз»ҮпјҢе»әжһ„еҮәжңҖдёҖиҲ¬зҡ„еңәеҹҹгҖӮжң¬ж–ҮйҖүеҸ–жқҺеӨҚжІ»е®№жЎҲдҫӢпјҢдё»иҰҒж¶үеҸҠгҖҠеҺ»жҖқйўӮгҖӢгҖҠж–°е”җд№ҰгҖӢгҖҠж—§е”җд№ҰгҖӢгҖҠиө„жІ»йҖҡйүҙгҖӢзӯүдёҚеҗҢж–Үжң¬гҖӮе®ғ们йҖҡиҝҮд№ҰеҶҷжқҺеӨҚзҡ„е®№е·һж”ҝдәӢгҖҒиә«д»Ҫе’Ң家йҒ“зӯүпјҢеҗ„иҮӘиҮҙеҠӣдәҺе®һзҺ°дё»жөҒеҸҷдәӢгҖҒејәеҢ–и®ӨеҗҢе’ҢдҝғжҲҗж–°зҡ„ж„Ҹд№үе»әжһ„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ҝҷдёҖд№ҰеҶҷе®һи·өжЎҲдҫӢпјҢе®һжңүеҠ©дәҺеү–жһҗдә”д»ЈеҢ—е®ӢеҸІеӯҰвҖңд№үзҗҶеҢ–вҖқзҡ„е…·дҪ“ејҖеұ•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пјҢзӣёиҫғдәҺ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и”Ўй»ҳж¶өе·Із»Ҹдё“й—ЁжҺўи®ЁеҸ—йҒ“еӯҰеҪұе“ҚдёӢзҡ„вҖңеҚ—е®ӢеҸІеӯҰвҖқпјҢдёӯеӣҪеӯҰз•ҢйҮҚж–°еҺ»е°ҶвҖңдә”д»ЈеҢ—е®ӢеҸІеӯҰвҖқзҪ®дәҺе”җе®ӢиҪ¬еһӢи§ҶеҹҹдёӢиҜҰеҠ и®Ёи®әпјҢзҠ№еҫ…жӣҙеӨҡе…іжіЁ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зҺӢиҪІ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3е№ҙ第10жңҹвҖңеҺҶеҸІз ”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 вҖңдёӯзҫҺеӨ§иұҶиҙёжҳ“йў„жңҹвҖқ
вҖңдёӯзҫҺеӨ§иұҶиҙёжҳ“йў„жңҹвҖқ иұҶзІ•пјҡеҲ©з©әеҮәе°ҪжӢҗзӮ№жңҖ
иұҶзІ•пјҡеҲ©з©әеҮәе°ҪжӢҗзӮ№жңҖ дёӯеӣҪйҮҮиҙӯжҫіжҙІеӨ§йәҰз§ҜжһҒ
дёӯеӣҪйҮҮиҙӯжҫіжҙІеӨ§йәҰз§ҜжһҒ зҺӢж¶ө пјҡж¬ІвҖңзҘёж°ҙеӨ–еј•
зҺӢж¶ө пјҡж¬ІвҖңзҘёж°ҙеӨ–еј•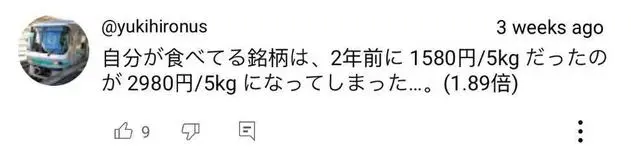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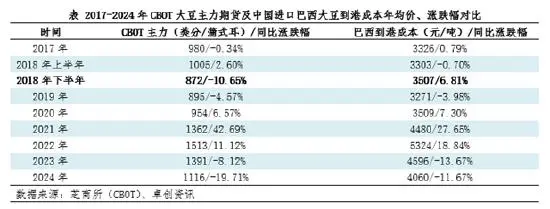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