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еј е°ҸзЁіпјҢеҘіпјҢдёңеҚ—еӨ§еӯҰдәәж–Ү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гҖӮ 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
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жҳҜдёӯеӣҪж–ҮеҢ–еҸ‘еұ•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йҳ¶ж®өпјҢд№ҹжҳҜ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”ұе®ӢеӯҰеҗ‘жё…еӯҰиҪ¬еҗ‘зҡ„йҮҚиҰҒж—¶жңҹпјҢдҪҶзӣ®еүҚ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ӯҰжңҜеҸІз ”究пјҢеӨҡйӣҶдёӯдәҺжұүд»ЈгҖҒе®Ӣд»Је’Ңжё…д»ЈпјҢ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жҳҜ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ӯҰжңҜеҸІз ”究дёӯзҡ„дёҖдёӘи–„ејұзҺҜиҠӮпјҢе’Ңе®ғжң¬иә«жүҖе…·жңүзҡ„ең°дҪҚе’Ңж„Ҹд№үжһҒдёҚзӣёз§°гҖӮеӯҰжңҜз•Ңе·Іжңүзҡ„е…ідәҺ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пјҢйӣҶдёӯеңЁдёӨ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ҢдёҖжҳҜи®әиҝ°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жҹҗдёҖжҖқжғідёҺе®ӢжҳҺзҗҶеӯҰ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дәҢжҳҜеҜ№еӯҹеӯҗеңЁ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ең°дҪҚеҸҳеҢ–еҸҠе…¶еҺҹеӣ иҝӣиЎҢиҖғеҜҹгҖӮиҝҷдәӣз ”з©¶пјҢжҲ–еҜ№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иҝӣиЎҢзҪ—еҲ—пјҢжҲ–еұҖйҷҗдәҺеұҖйғЁз ”究гҖҒдёӘжЎҲз ”з©¶пјҢйғҪжңӘиғҪи®әеҸҠе…¶еҸ‘еұ•и„үз»ңдёҺеҹәжң¬и¶ӢеҠҝгҖӮжң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笔иҖ…дёҚжҸЈи°«йҷӢпјҢеңЁе·Іжңүз ”з©¶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°Ҷ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Ҫ®дәҺе…ғжҳҺж–ҮеҢ–еҸ‘еұ•зҡ„еӨ§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еҜ№е…¶еҸ‘еұ•и„үз»ңгҖҒеҹәжң¬и¶ӢеҠҝеҸҠе…¶дёҺж–ҮеҢ–еҸ‘еұ•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иҝӣиЎҢеӢҫеӢ’еҲҶжһҗпјҢд»Ҙеұ•зҺ°иҜҘж—¶жңҹ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ҡ„еҸ‘еұ•жҰӮиІҢдёҺеҺҶеҸІең°дҪҚгҖӮдёҖгҖҒе…ғеҸҠжҳҺеҲқ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пјҡзҗҶеӯҰжЎҶжһ¶дёӢзҡ„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еҚ—е®ӢжңұзҶ№гҖҠеӣӣд№Ұз« еҸҘйӣҶжіЁгҖӢзҡ„е®ҢжҲҗ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зҗҶеӯҰдҪ“зі»зҡ„жңҖз»ҲеҪўжҲҗпјҢе…¶зҗҶи®әжҲҗе°ұеҫ—еҲ°е®ӢзҗҶе®—зҡ„и®ӨеҸҜ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з« еҸҘйӣҶжіЁгҖӢд№ҹдҪңдёәе®ҳеӯҰзҡ„ж•ҷ科д№ҰиҖҢйҖҡиЎҢе…ЁеӣҪпјҢдҪҶжҳҜ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并没жңүж•ҙдҪ“иў«зәіе…Ҙ科дёҫиҖғиҜ•зі»з»ҹпјҢд»…жңүгҖҠи®әиҜӯгҖ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ңЁеҲ—пјҢең°дҪҚдәҰеңЁвҖңдә”з»ҸвҖқд№ӢдёӢгҖӮе…ғжңқе»әз«Ӣд№ӢеҗҺпјҢдёҖеәҰеәҹжӯўз§‘дёҫпјҢд»Ғ宗延зҘҗдәҢе№ҙпјҲ1315е№ҙпјүйҮҚж–°жҒўеӨҚпјҢ规е®ҡ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дёәиҖғиҜ•зҡ„дё»иҰҒеҶ…е®№пјҢд»ҘжңұзҶ№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з« еҸҘйӣҶжіЁгҖӢдҪңдёәеҮҶз»іпјҢ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•ҙдҪ“иў«зәіе…Ҙ科дёҫиҖғиҜ•зі»з»ҹпјҢ科дёҫиҖғиҜ•з”ұвҖңдә”з»Ҹж—¶д»ЈвҖқиҝӣе…ҘвҖңеӣӣд№Ұж—¶д»ЈвҖқгҖӮжҳҺд»ЈжІҝиўӯе…ғ代科дёҫеҲ¶еәҰпјҢд»Қ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и®ҫ科еҸ–еЈ«гҖӮжҳҺеӨӘзҘ–йқһеёёйҮҚи§Ҷ儒家жҖқжғіпјҢжҙӘжӯҰдёүе№ҙпјҲ1370е№ҙпјүжҒўеӨҚ科дёҫпјҢ规е®ҡвҖңеҲ¶з§‘еҸ–еЈ«пјҢдёҖд»Ҙз»Ҹд№үдёәе…ҲвҖқпјҢ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дә”з»ҸвҖқе‘ҪйўҳпјҢ并д»Ҙ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зҡ„и§ЈйҮҠдёәеҮҶпјҢиҰҒжұӮеӯҰиҖ…вҖңдёҖе®—жңұж°Ҹд№ӢеӯҰпјҢйқһдә”з»Ҹеӯ”еӯҹд№Ӣд№ҰдёҚиҜ»пјҢйқһжҝӮжҙӣе…ій—Ҫд№ӢеӯҰдёҚи®ІвҖқгҖӮдёәиҝӣдёҖжӯҘжҺЁе№ҝ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пјҢз»ҹдёҖ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пјҢеҠ ејәжҖқжғіз»ҹжІ»пјҢжҳҺжҲҗзҘ–е‘Ҫд»Өзҝ°жһ—еӯҰеЈ«иғЎе№ҝзӯүдәәиҙҹиҙЈзј–зәӮгҖҠдә”з»ҸеӨ§е…ЁгҖӢгҖҠеӣӣд№ҰеӨ§е…ЁгҖӢе’ҢгҖҠжҖ§зҗҶеӨ§е…ЁгҖӢпјҢжҲҗдёә科дёҫиҖғиҜ•зҡ„жқғеЁҒж ҮеҮҶпјҢжҺЁиЎҢе…ЁеӣҪгҖӮз”ұдәҺеҪ“时科дёҫ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дёәйҮҚпјҢгҖҠдә”з»ҸеӨ§е…ЁгҖӢиў«жқҹд№Ӣй«ҳйҳҒ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еӨ§е…ЁгҖӢжҲҗдёәеЈ«еӯҗжүӢеӨҙеҝ…иҜ»д№Ӣд№ҰгҖӮеңЁжӯӨиғҢжҷҜд№ӢдёӢпјҢеӯҹеӯҗең°дҪҚеҫ—д»ҘдёҚж–ӯжҸҗеҚҮпјҢзӣҙиҮіиў«е°ҠдёәдәҡеңЈ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дәҰдё§еӨұ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зӢ¬з«ӢжҖ§пјҢз”ұзӢ¬з«Ӣз ”з©¶йҳ¶ж®өиҝӣе…ҘвҖңеӣӣд№ҰеӯҰвҖқд№ӢдёӢзҡ„з ”з©¶йҳ¶ж®өпјҢе…ғд»ЈеҸҠжҳҺеҲқ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пјҢеӨ§еӨҡжҳҜ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еӯҰвҖқзҡ„йқўзӣ®еҮәзҺ°зҡ„гҖӮиҜҘ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жүҝиўӯе®ӢеӯҰ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еңЁз»§жүҝ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еҸҲжңүжүҖеҸ‘еұ•пјҢдҪҶз”ұдәҺжңұзҶ№зҗҶеӯҰе®ҳж–№ең°дҪҚзҡ„зЎ®з«ӢпјҢиҝҷдәӣз ”з©¶жІЎжңүдәҰдёҚиғҪзӘҒз ҙзҗҶеӯҰзҡ„жҖқжғіжЎҶжһ¶пјҢеӣ иҖҢеҸӘиғҪжҳҜеңЁзҗҶеӯҰжЎҶжһ¶дёӢзҡ„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пјҢдё»иҰҒзҡ„д»ЈиЎЁжҖ§жҲҗжһңжңүйҮ‘еұҘзҘҘ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йӣҶжіЁиҖғиҜҒгҖӢгҖҒи®ёи°Ұзҡ„гҖҠиҜ»еӣӣд№ҰдёӣиҜҙгҖӢгҖҒиўҒдҝҠзҝҒ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иҠӮгҖӢе’Ңи”Ўжё…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и’ҷеј•гҖӢгҖӮйҮ‘еұҘзҘҘжҳҜжңұзҶ№зҡ„дёүдј ејҹеӯҗпјҢи®ёи°ҰжҳҜйҮ‘еұҘзҘҘзҡ„еӯҰз”ҹпјҢ他们йғҪжҳҜжңұзҶ№еӯҰжҙҫзҡ„дј дәәпјҢеҠӣжұӮеңЁжңұзҶ№еӯҰиҜҙ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жңүжүҖеҸ‘еұ•пјҢ他们зҡ„еҸ‘еұ•дё»иҰҒиЎЁзҺ°еңЁеҜ№жңұзҶ№гҖҠеӯҹеӯҗйӣҶжіЁгҖӢзҡ„и§ЈиҜҙе’ҢиЎҘе……дёҠгҖӮйҮ‘еұҘзҘҘи®ӨдёәиҮӘе·ұжүҖдҪң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йӣҶжіЁиҖғиҜҒгҖӢжҳҜдёәжңұзҶ№гҖҠеӯҹеӯҗйӣҶжіЁгҖӢжүҖдҪңзҡ„з–ҸпјҢд»–еңЁиҜҘд№ҰгҖҠеәҸгҖӢдёӯиҜҙиҮӘе·ұеҶҷдҪңзҡ„зӣ®зҡ„жңүдәҢпјҡдёҖжҳҜеҜ№жңұжіЁдёӯзҡ„з–‘йҡҫй—®йўҳиҝӣиЎҢйҳҗйҮҠпјҢдәҢжҳҜеҜ№иў«жңұзҶ№еҝҪз•Ҙзҡ„ең°ж–№иҝӣиЎҢиЎҘе……иҜҙжҳҺгҖӮд»–еӨҡжңүиҮӘе·ұзӢ¬еҲ°зҡ„и§Ғи§ЈпјҢд»ҘеҜ№еӯҹеӯҗвҖңд»Ғд№Ӣе®һпјҢдәӢдәІжҳҜд№ҹвҖқзҡ„и§ЈйҮҠдёәдҫӢпјҡ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ж–Үе…¬е°қдёҺеҗ•жҲҗе…¬иЁҖпјҡвҖңвҖҳе®һвҖҷеӯ—жңүеҜ№вҖҳеҗҚвҖҷиҖҢиЁҖиҖ…пјҢи°“еҗҚе®һд№Ӣе®һпјӣжңүеҜ№вҖҳзҗҶвҖҷиҖҢиЁҖиҖ…пјҢи°“дәӢе®һд№Ӣе®һпјӣжңүеҜ№вҖҳеҚҺвҖҷиҖҢиЁҖиҖ…пјҢи°“еҚҺе®һд№Ӣе®һгҖӮзӣ–д»Ғд№Ӣе®һдёҚиҝҮвҖҳдәӢдәІвҖҷпјҢд№үд№Ӣе®һеҲҷжҳҜвҖҳд»Һе…„вҖҷпјҢжҺЁе№ҝд№ӢпјҢзҲұдәәеҲ©зү©пјҢеҝ еҗӣејҹй•ҝпјҢд№ғжҳҜд»Ғд№үд№ӢеҚҺйҮҮгҖӮвҖқеұҘзҘҘжҢүпјҡжӯӨвҖңе®һвҖқеҪ“дҪңж–Үе®һд№Ӣе®һгҖӮдәӢдәІд»Һе…„иҖ…пјҢд»Ғд№үд№Ӣе®һпјӣиҖҢжҺЁд№Ӣд»Ғж°‘еҲ©зү©пјҢеҝ еҗӣејҹй•ҝпјҢеҲҷзҡҶд»Ғд№үд№Ӣж–ҮгҖӮ вҖңе®һвҖқжңүеҫҲеӨҡзӣёеҜ№д№үпјҢжңүеҗҚе®һд№Ӣе®һпјҢжңүзҗҶе®һд№Ӣе®һпјҢжңүеҚҺе®һд№Ӣе®һзӯүгҖӮжңұзҶ№и®Өдёә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д»Ғд№Ӣе®һзҡ„вҖңе®һвҖқжҳҜеҚҺе®һд№Ӣе®һпјҢеҚід»Ғзҡ„жң¬иҙЁжҳҜдәӢдәІпјҢдҪңдёәд»Ғзҡ„жү©еұ•зҡ„зҲұдәәеҲ©зү©гҖҒеҝ еҗӣжӮҢй•ҝеҸӘдёҚиҝҮжҳҜйҷ„еңЁд»ҒдёҠзҡ„иЈ…йҘ°пјҢжҳҜеҚҺйҮҮпјҢжҳҜеӨ–еңЁдәҺд»Ғзҡ„гҖӮйҮ‘еұҘзҘҘеҲҷи®ӨдёәпјҢ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е®һжҳҜж–Үе®һзҡ„е®һпјҢеҚізҲұдәәеҲ©зү©гҖҒеҝ еҗӣжӮҢй•ҝжҳҜз”ұеҶ…еңЁзҡ„д»ҒиҖҢиЎЁзҺ°еҮәжқҘзҡ„зә№и·ҜгҖҒзә№зҗҶпјҢжҳҜд»Ғжң¬иә«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жҳҜеҶ…еңЁзҡ„гҖӮйҮ‘еұҘзҘҘзҡ„и§ЈйҮҠдёҺжңұзҶ№дёҚеҗҢпјҢдҪҶжӣҙжҺҘиҝ‘еӯҹеӯҗзҡ„жң¬ж„ҸпјҢеӯҹеӯҗи®Өдёәз”ұд»ҒжүҖеҸҠзҡ„зҲұдәәгҖҒзҲұзү©з”ҡиҮіеӣҪеҗӣзҡ„д»Ҙд»Ғеҫ—еӨ©дёӢйғҪжҳҜд»Ғзҡ„иҮӘ然з”ҹеҸ‘е’Ңеҝ…然结жһңгҖӮи®ёи°Ұзҡ„гҖҠиҜ»еӣӣд№ҰдёӣиҜҙгҖӢжҳҜд»–ж•ҙзҗҶиҮӘе·ұиҜ»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зҡ„笔记пјҢе…¶дёӯгҖҠиҜ»еӯҹеӯҗдёӣиҜҙгҖӢжңү200еӨҡжқЎпјҢйҮҢйқўжңүдёҚе°‘и§ӮзӮ№пјҢеҸ‘еүҚдәәжүҖжңӘеҸ‘пјҢйўҮе…·еҗҜеҸ‘жҖ§пјҢдҫӢеҰӮд»–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В·жўҒжғ зҺӢдёҠгҖӢдёӯеӯҹеӯҗиҜҙеӨ©дёӢвҖңе®ҡдәҺдёҖвҖқзҡ„и§ЈйҮҠжҳҜпјҡ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дёҖвҖқпјҢеҗ«д№үжҳҜз»ҹдёҖеӨ©дёӢдёәдёҖдёӘж•ҙдҪ“пјҢе°ұеғҸз§Ұжұүж—¶жңҹзҡ„зӨҫдјҡйӮЈж ·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ғҸеӨҸе•Ҷе‘Ёж—¶д»Јзҡ„е°ҒйӮҰе»әеӣҪпјҢиҝҷжҳҜеӯҹеӯҗзңӢеҲ°дәҶеҪ“ж—¶еӨ©дёӢеҸ‘еұ•зҡ„еҝ…然и¶ӢеҠҝиҖҢеҒҡеҮәзҡ„еҲӨж–ӯгҖӮд»ҺдёҠеҸӨж—¶жңҹжңүеҗӣй•ҝејҖе§ӢпјҢе®һиЎҢзҡ„йғҪжҳҜе°ҒйӮҰе»әеӣҪд№ӢеҲ¶гҖӮй»„еёқж—¶жңүдёҮеӣҪпјҢеӨҸзҰ№ж—¶дәҰжңүдёҮеӣҪпјҢзӯүеҲ°е•ҶжұӨж—¶жңҹпјҢиҝҳжңүдёүеҚғеӨҡеӣҪгҖӮеҲ°еӯҹеӯҗ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зӣёдә’д№Ӣй—ҙиғҪеӨҹдәүйӣ„зҡ„пјҢеҸӘеү©дёӢдёғеӣҪдәҶпјҢжңҖз»ҲдёҖе®ҡжҳҜз»ҹдёҖдёәдёҖдёӘе®Ңж•ҙзҡ„еӣҪпјҢеӨ©дёӢе®һиЎҢйғЎеҺҝеҲ¶гҖӮеҲ°дәҶз§ҰжұүпјҢеӯҹеӯҗвҖңе®ҡдәҺдёҖвҖқзҡ„иҜқеә”йӘҢдәҶпјҢдҪҶжҳҜз§Ұжңқзҡ„з»ҹжІ»иҖ…ж®Ӣй…·е—ңжқҖпјҢиҷҪ然з»ҹдёҖдәҶпјҢдҪҶжҳҜеӨ©дёӢеҚҙдёҚиғҪе®үе®ҡпјҢеҲ°дәҶжұүд»ЈжүҚзңҹжӯЈе®һзҺ°дәҶвҖңе®ҡдәҺдёҖвҖқгҖӮи®ёи°Ұзҡ„и§ЈйҮҠз«ҷеңЁеҗҺдё–зҡ„з«ӢеңәдёҠйҮҚж–°зҗҶи§Јеӯҹеӯҗзҡ„иҜқпјҢж—ўз¬ҰеҗҲеӯҹеӯҗжүҖеӨ„ж—¶д»Јзҡ„еҺҶеҸІеҸ‘еұ•и¶ӢеҠҝпјҢд№ҹз¬ҰеҗҲеӯҹеӯҗжҖқжғізҡ„е®һйҷ…пјҢи¶…и¶ҠдәҶеүҚиҫҲеӯҰиҖ…еҜ№иҝҷеҸҘиҜқзҡ„и§ЈйҮҠгҖӮиўҒдҝҠзҝҒ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иҠӮгҖӢжҳҜ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гҖӢзҡ„еҲ иҠӮжң¬гҖӮз»Ҹз–‘жҳҜе…ғ代科дёҫиҖғиҜ•зҡ„дёҖз§ҚеҪўејҸпјҢд»Ҙй—®зӯ”зҡ„ж–№ејҸеҮәзҺ°гҖӮз»Ҹз–‘зҡ„еҪўејҸжәҗиҮӘжңұзҶ№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жҲ–й—®гҖӢ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жҲ–й—®гҖӢдё»иҰҒжҳҜи§ЈйҮҠз–‘й—®пјҢйҳҗеҸ‘гҖҠеӣӣд№Ұз« еҸҘйӣҶжіЁгҖӢдёӯзҡ„жіЁйҮҠгҖӮ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гҖӢжҳҜ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дё“й—Ёдёәеә”еҜ№з§‘дёҫиҖғиҜ•дёӯзҡ„з»Ҹз–‘иҖҢдҪңзҡ„дёҖзұ»и‘—дҪңзҡ„еҗҚз§°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иҠӮгҖӢеә”жҳҜиҝҷзұ»д№Ұзҡ„з»Ҹе…ёй—®йўҳжұҮзј–гҖӮе…Ёд№Ұе…ұ12еҚ·пјҢе…¶дёӯжңү3еҚ·жҳҜгҖҠеӯҹеӯҗз–‘иҠӮгҖӢ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з–‘иҠӮгҖӢжҳҜдёҖйғЁе…је…·е®һз”ЁжҖ§е’Ңз ”з©¶жҖ§зҡ„и‘—дҪңгҖӮдҪңдёәеә”еҜ№з§‘дёҫд№ӢдҪңпјҢиҜҘд№ҰеңЁеҗҚзү©и®ӯиҜӮе’ҢжҖқжғід№үзҗҶзҡ„и§ЈйҮҠдёҠдёҺжңұзҶ№е®Ңе…ЁдёҖиҮҙпјҢдёҚж•ўи¶Ҡйӣ·жұ дёҖжӯҘпјҢдҪҶд№ҹжҸҗеҮәдәҶдёҖдәӣж–°йІң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并еҠ д»Ҙи§Јзӯ”жҲ–иЎЁжҳҺиҮӘе·ұ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еҰӮеҚ·д№қдёӯй—®пјҡвҖңгҖҠд№ҰгҖӢз»ҸеӨ«еӯҗд№ӢжүҖе®ҡпјҢеӯҹеӯҗд№ғжӣ°вҖҳе°ҪдҝЎгҖҠд№ҰгҖӢпјҢеҲҷдёҚеҰӮж— гҖҠд№ҰгҖӢвҖҷпјҢдҪ•ж¬ӨпјҹвҖқзӯ”жӣ°пјҡвҖңеҗӣеӯҗз«ӢиЁҖпјҢжҲ–жңүжүҖдёәиҖҢеҸ‘иҖ…пјҢжңӘеҸҜйҒҪд»ҘдёәйҖҡи®әд№Ӣиҫһд№ҹгҖӮеӯҹеӯҗе°қжӣ°вҖҳе°ҪдҝЎгҖҠд№ҰгҖӢпјҢдёҚеҰӮж— гҖҠд№ҰгҖӢвҖҷпјҢжӯӨзӣ–жӯЈдёәиЎҖжөҒжјӮжқөдёҖиҜӯиҖҢеҸ‘пјҢеІӮиҜҡд»Ҙд»Ҡд№ӢгҖҠд№ҰгҖӢдёәдёҚеҸҜе°ҪдҝЎиҖ¶пјҹиҜ»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Җ…пјҢйҖҡдёҠдёӢз« иҖҢи®әд№ӢеҲҷеҸҜи§Ғе…¶з«ӢиЁҖд№Ӣжң¬ж„ҸзҹЈгҖӮвҖқеҚ·д№қеҚі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вҖңе°ҪдҝЎгҖҠд№ҰгҖӢпјҢдёҚеҰӮж— гҖҠд№ҰгҖӢвҖқеҸӘжҳҜзңӢеҲ°вҖңиЎҖжөҒжјӮжқөвҖқеҗҺзҡ„дёҖж—¶ж„ҹж…ЁиҖҢе·ІпјҢдёҚиғҪеҪ“дҪңеӯҹеӯҗеҜ№еҫ…ж•ҙжң¬гҖҠд№ҰгҖӢз»Ҹзҡ„жҖҒеәҰпјҢиҰҒзңҹжӯЈзҗҶи§Ј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иҜқ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йңҖиҰҒйҖҡиҜ»дёҠдёӢж–ҮжүҚеҸҜд»ҘжҠҠжҸЎгҖӮи”Ўжё…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и’ҷеј•гҖӢжҳҜжҳҺд»ЈдёҖйғЁд»ҘйҳҗйҮҠд№үзҗҶдёәдё»зҡ„и‘—дҪңгҖӮиҝҷйғЁд№ҰиҷҪ然д№ҹжҳҜдёә科дёҫиҖғиҜ•иҖҢдҪңпјҢд»ҘжңұеӯҰдёәе®—пјҢдҪҶжҳҜж·ұеҫ—е®ӢдәәеӯҰйЈҺд№Ӣзңҹи°ӣпјҢжүҖи®Ід№үзҗҶпјҢж·ұеҲ»йҖҸеҪ»пјҢжңүдёҚе°‘зІҫиҫҹзӢ¬еҲ°зҡ„и§Ғи§ЈпјҢиҜ•дёҫдёҖдҫӢпјҡгҖҠеӯҹеӯҗВ·ж»•ж–Үе…¬дёҠгҖӢ第1з« жңүвҖңеӯҹеӯҗйҒ“жҖ§е–„пјҢиЁҖеҝ…з§°е°§иҲңвҖқгҖӮеҜ№е…¶дёӯвҖңжҖ§е–„вҖқдёҖиҜҚпјҢжңұзҶ№еј•з”ЁзЁӢеӯҗзҡ„иҜқи§ЈйҮҠдёәпјҡвҖңжҖ§еҚізҗҶд№ҹгҖӮеӨ©дёӢд№ӢзҗҶпјҢеҺҹе…¶жүҖиҮӘпјҢж— жңүдёҚе–„гҖӮе–ңгҖҒжҖ’гҖҒе“ҖгҖҒд№җжңӘеҸ‘пјҢдҪ•е°қдёҚе–„гҖӮеҸ‘иҖҢдёӯиҠӮпјҢеҚіж— еҫҖдёҚе–„пјӣеҸ‘дёҚдёӯиҠӮпјҢ然еҗҺдёәдёҚе–„гҖӮвҖқж„ҸжҖқжҳҜпјҢжҖ§е°ұжҳҜзҗҶпјҢеӨ©дёӢд№ӢзҗҶпјҢд»Һж №жәҗдёҠиҜҙпјҢжІЎжңүдёҚе–„зҡ„пјҢе–ңжҖ’е“Җд№җжІЎжңүд»ҺеҝғдёӯеҸ‘еҮә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“ӘжңүдёҚе–„зҡ„пјӣд»ҺеҝғдёӯеҸ‘еҮәжқҘз¬ҰеҗҲзӨјиҠӮ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дёҚе–„зҡ„гҖӮеҸӘжңүеҸ‘еҮәжқҘдёҚз¬ҰеҗҲзӨјиҠӮзҡ„пјҢжүҚжҳҜдёҚе–„зҡ„гҖӮи”Ўжё…и®ӨдёәжңұзҶ№зҡ„и§ЈйҮҠдёҚеӨҹзЎ®еҲҮ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вҖҳд»Ғд№үвҖҷдәҢеӯ—д»ҺдҪ•жқҘпјҹд»ҺвҖҳе–„вҖҷеӯ—жқҘд№ҹгҖӮжҖ§жңүд»Ғд№үпјҢжүҖд»Ҙдёәе–„гҖӮеӯҹеӯҗи®әйҒ“зҗҶпјҢеҸӘд»ҘвҖҳд»Ғд№үвҖҷдәҢеӯ—иҜҘд№ӢгҖӮвҖқж„ҸжҖқжҳҜпјҢ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йҒ“вҖқе’ҢвҖңзҗҶвҖқпјҢйғҪжҳҜд»Ҙд»Ғд№үдёәж ёеҝғпјҢжҖ§е–„д№ҹжҳҜд»Ҙд»Ғд№үдёәж ёеҝғпјҢиҖҢд»Ғд№үе°ұжҳҜдәәе’Ңдәә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жқҘиҮӘдәәеҶ…еҝғзҡ„дәІжғ…пјҢжүҖд»ҘвҖңжҖ§еҚізҗҶвҖқдёӯзҡ„вҖңзҗҶвҖқдёҚжҳҜеӨ©дёӢзҡ„жҷ®йҒҚд№ӢзҗҶпјҢиҖҢжҳҜдәәеҶ…еҝғд№ӢзҗҶгҖӮе®Ӣд»ЈзҗҶеӯҰжҳҜдёәдәҶеӣһеә”дҪӣйҒ“дәҢж•ҷеҜ№е„’еӯҰз»ҹжІ»ең°дҪҚзҡ„еҶІеҮ»иҖҢйҮҚж–°жһ„е»әе„’еӯҰзҡ„е“ІеӯҰдҪ“зі»пјҢд»Һе®ӢеҲқиҜёе„’з»Ҹз”ұеј иҪҪгҖҒдәҢзЁӢзӯүдәәзҡ„дј жүҝпјҢзӣҙеҲ°еҚ—е®ӢжңұзҶ№е§Ӣе®ҢжҲҗеҺҶеҸІдҪҝе‘ҪпјҢжһ„е»әдәҶд»ҘвҖңзҗҶвҖқдёәж ёеҝғжҰӮеҝөпјҢз”ұзҗҶж°”дәҢе…ғзҡ„жң¬дҪ“и®әгҖҒзҗҶдёҖеҲҶж®Ҡзҡ„з”ҹжҲҗи®әгҖҒеӨ©е‘Ҫд№ӢжҖ§дёҺж°”иҙЁд№ӢжҖ§зҡ„жҖ§дәҢе…ғи®әе’Ңеҝғз»ҹжҖ§жғ…зҡ„и®ӨиҜҶи®әгҖҒж јзү©иҮҙзҹҘзҡ„ж–№жі•и®әзӯүдёәдё»иҰҒеҶ…е®№зҡ„зҗҶеӯҰ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гҖӮзҗҶеӯҰд»Ҙ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дёәдё»иҰҒж–ҮзҢ®дҫқжҚ®пјҢд»ҘйҳҗеҸ‘д№үзҗҶгҖҒжһ„е»әиҮӘе·ұзҡ„жҖқжғізҗҶи®әдёәдё»гҖӮе…ғеҸҠжҳҺеҲқпјҢз”ұдәҺе„’еӯҰйҮҚжһ„зҡ„д»»еҠЎе·Із»Ҹе®ҢжҲҗпјҢдё”зҗҶеӯҰе·Із»Ҹиў«е®ҳж–№е®ҡдёәдёҖе°ҠпјҢдёҚжҳ“дё”дёҚиғҪзӘҒз ҙпјҢдҪҶе®ӢеӯҰеӯҰжңҜйЈҺж°”зҡ„еҪұе“ҚдәҰдёҚдјҡдёҖж—¶ж¶ҲеӨұпјҢеӯҰиҖ…们д»Қжңүйҳҗиҝ°д№үзҗҶзҡ„еӯҰжңҜиҝҪжұӮпјҢж•…еҪўжҲҗдәҶж—ўиҰҒеҸ‘еұ•иҖҢеҸҲдёҚиғҪзӘҒз ҙзҡ„ж—¶д»Јзү№зӮ№гҖӮз”ұдәҺжңұзҶ№дё»иҰҒзІҫеҠӣеңЁзҗҶи®әжһ„е»әпјҢеҜ№вҖңеӣӣд№ҰвҖқж–ҮзҢ®зҡ„и§ЈйҮҠдёҚиғҪе…ЁйқўйЎҫеҸҠпјҢд№ҹз»ҷеҗҺдәәз•ҷдёӢ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еҸ‘жҢҘз©әй—ҙпјҢжүҖд»Ҙ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ҡ„еҸ‘еұ•еҸӘиғҪжҳҜзҗҶеӯҰжЎҶжһ¶дёӢзҡ„жңүйҷҗеҸ‘еұ•пјҢжӯЈеҰӮйҮ‘еұҘзҘҘжүҖиҜҙжҳҜеҜ№жңұжіЁзҡ„йҮҠйҡҫе’ҢиЎҘе……гҖӮ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дәҢгҖҒ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пјҡ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еҸ‘еұ• зҗҶеӯҰеҶ…йғЁпјҢд»Һе®Ӣд»ЈејҖе§Ӣе°ұжңүзҗҶеӯҰдёҺеҝғеӯҰзҡ„еҲҶжӯ§пјҢжңҖж—©зҡ„еҲҶжӯ§еҸҜд»ҘиҝҪжәҜеҲ°дәҢзЁӢпјҢзЁӢйўўжҸҗеҮәвҖңеҝғеҚізҗҶвҖқзҡ„е‘ҪйўҳпјҢзЁӢйўҗжҸҗеҮәвҖңжҖ§еҚізҗҶвҖқзҡ„е‘ҪйўҳпјӣзЁӢйўҗзҡ„зҗҶеӯҰз»Ҹз”ұжқЁж—¶гҖҒзҪ—д»ҺеҪҰгҖҒжқҺдҫ—пјҢиҮіеҚ—е®ӢжңұзҶ№ж—¶еҪўжҲҗжҲҗзҶҹзҡ„зҗҶеӯҰдҪ“зі»пјҢз§°дёәвҖң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вҖқпјҢз®Җз§°вҖңзҗҶеӯҰвҖқпјӣеҚ—е®ӢйҷҶд№қжёҠжүҝиўӯеҸ‘еұ•дәҶзЁӢйўўзҡ„еҝғеӯҰпјҢжҲҗдёәе®Ӣд»ЈеҝғеӯҰзҡ„д»ЈиЎЁгҖӮж— и®әзҗҶеӯҰиҝҳжҳҜеҝғеӯҰ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йғҪжҳҜе…¶йҮҚиҰҒзҡ„жҖқжғіжқҘжәҗгҖӮзҗҶеӯҰ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жҖқжғізҡ„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дё»иҰҒеңЁдәәжҖ§и®әе’ҢеҝғжҖ§и®әдёҠгҖӮеӯҹеӯҗдё»еј дәәжҖ§е–„пјҢдҪҶеӯҹеӯҗеҜ№е–„д»ҺдҪ•еӨ„жқҘгҖҒдәәжҖ§дҪ•д»ҘжңүжҒ¶еҚҙдёҚиғҪз»ҷеҮәеңҶж»Ўзҡ„и§ЈйҮҠпјҢжүҖд»ҘдёҚиғҪ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жҲҳиғңжҖ§жҒ¶и®әгҖӮжңұзҶ№еңЁеӯҹеӯҗжҖ§е–„и®ә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з»јеҗҲд»ҘеҫҖзҡ„дәәжҖ§и®әжҖқжғіпјҢз»“еҗҲиҮӘе·ұзҗҶж°”дәҢе…ғзҡ„е®Үе®ҷи®әпјҢжҸҗеҮәеӨ©е‘Ҫд№ӢжҖ§е’Ңж°”иҙЁд№ӢжҖ§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з”ЁеӨ©е‘Ҫд№ӢжҖ§жқҘи§ЈйҮҠе–„зҡ„жқҘжәҗпјҢз”Ёж°”жқҘи§ЈйҮҠжҒ¶зҡ„жқҘжәҗпјҢз”Ёж°”зҡ„дёҚеҗҢжқҘи§ЈйҮҠдәәзҡ„иҙӨж„ҡеҜҝеӨӯиҙ«иҙұеҜҢиҙөзӯүеӨҡж ·жҖ§зҡ„еҢәеҲ«пјҢдё°еҜҢеҸ‘еұ•дәҶеӯҹеӯҗзҡ„дәәжҖ§и®әгҖӮеңЁеҝғжҖ§и®әдёҠпјҢеӯҹеӯҗи®Өдёәеҝғе…·жңүи®ӨиҜҶеҠҹиғҪпјҢжңұзҶ№з»јеҗҲеӯҹеӯҗжҖ§е–„и®әе’ҢеҝғжҖ§и®әпјҢжҸҗеҮәеҝғз»ҹжҖ§жғ…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жҢҮеҮәеҝғе…·жңүдё»дҪ“е’Ңе®ўдҪ“зҡ„дәҢйҮҚжҖ§пјҢ并жҸҗеҮәж јзү©иҮҙзҹҘзҡ„и®ӨиҜҶж–№жі•пјҢеҚійҖҡиҝҮдёҖдёҖи®ӨиҜҶдёҮдәӢдёҮзү©дёӯзҡ„зҗҶпјҢжңҖеҗҺиҫҫеҲ°еҜ№е®Үе®ҷз»ҲжһҒд№ӢзҗҶзҡ„и®ӨиҜҶгҖӮйҷҶд№қжёҠеҝғеӯҰ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ҡ„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дё»иҰҒдҪ“зҺ°еңЁжң¬еҝғзҗҶи®әдёҠгҖӮжң¬еҝғзҡ„жҰӮеҝөжҳҜеңЁгҖҠеӯҹеӯҗВ·е‘ҠеӯҗдёҠгҖӢдёӯжҸҗеҮәзҡ„пјҢжҢҮдәәдёҺз”ҹдҝұжқҘзҡ„жҒ»йҡҗгҖҒзҫһжҒ¶гҖҒиҫһи®©гҖҒжҳҜйқһеӣӣеҝғдёҺд»Ғд№үзӨјжҷәеӣӣз«ҜгҖӮйҷҶд№қжёҠеҜ№еӯҹеӯҗжң¬еҝғзҗҶи®әзҡ„еҸ‘еұ•дё»иҰҒдҪ“зҺ°еңЁдёӨ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ҡ第дёҖпјҢеҺҳжё…дәҶ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ӯ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еӨ©гҖҒзҗҶиҜёжҰӮеҝө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并жҠҠвҖңеҝғеҚізҗҶвҖқзҡ„е‘Ҫйўҳз»ҹдёҖеҲ°вҖңжң¬еҝғвҖқзҡ„жҰӮеҝөдёҠгҖӮеңЁеӯҹеӯҗзҡ„жҖқжғідёӯпјҢ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еӨ©е…·жңүеҶ…еңЁзҡ„дёҖиҮҙжҖ§пјӣеҝғгҖҒзҗҶгҖҒд№үе…·жңүеҶ…е®№дёҠзҡ„еҗҢзӯүжҖ§пјҢе…·дҪ“еҰӮдҪ•пјҢеҲҷжІЎжңүжӣҙеӨҡи®әиҝ°гҖӮйҷҶд№қжёҠеҖҹеҠ©е®Үе®ҷгҖҒеҗҫеҝғзӯүжҰӮеҝөпјҢжІҹйҖҡдәҶ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зҗҶзҡ„е…ізі»гҖӮйҷҶд№қжёҠи®Өдёәеҝғзҡ„и®ӨиҜҶеҜ№иұЎжҳҜжҷ®йҒҚеӯҳеңЁдәҺеӨ©ең°й—ҙзҡ„зҗҶпјҢеӨ©ең°еҚіе®Үе®ҷпјҢе®Үе®ҷжҳҜж— з©·зҡ„пјҢйӮЈд№ҲдҪңдёәи®ӨиҜҶдё»дҪ“еҗҫеҝғзҡ„и®ӨиҜҶеҜ№иұЎд№ҹжҳҜж— з©·зҡ„пјҢеҗҫеҝғеҸҜд»Ҙи¶…и¶ҠдёҖеҲҮдәәгҖҒдәӢгҖҒзү©зҡ„йҷҗеҲ¶пјҢеҺ»и®ӨиҜҶж— з©·ж— е°Ҫзҡ„е®Үе®ҷпјҢи®ӨиҜҶеӯҳеңЁдәҺе®Үе®ҷдёӯзҡ„жҷ®йҒҚд№ӢзҗҶпјҢеӣ иҖҢжҸҗеҮәвҖңе®Үе®ҷдҫҝжҳҜеҗҫеҝғпјҢеҗҫеҝғдҫҝжҳҜе®Үе®ҷвҖқгҖӮиҝӣиҖҢпјҢйҷҶд№қжёҠи®ӨдёәпјҢе®Үе®ҷдёӯзҡ„зҗҶжҳҜи¶…и¶Ҡж—¶з©әзҡ„пјҢе®ғдёҚд»…жҳҜвҖңеҗҫеҝғвҖқи®ӨиҜҶ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д№ҹжҳҜеҸӨеҫҖд»ҠжқҘ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йңҖиҰҒи®ӨиҜҶ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жүҖд»ҘжҜҸдёӘдәәйңҖиҰҒи®ӨиҜҶзҡ„зҗҶйғҪжҳҜзӣёеҗҢзҡ„пјҢдҪңдёәжҜҸдёӘдәәи®ӨиҜҶз»“жһңзҡ„вҖңеҗҫеҝғвҖқд№ҹжҳҜзӣёеҗҢзҡ„пјҢиҝҷзӣёеҗҢзҡ„вҖңеҗҫеҝғвҖқе°ұжҳҜеӯҹ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жң¬еҝғгҖӮ第дәҢпјҢе°Ҷеӯҹеӯҗд»ҘвҖңе…»еҝғвҖқдёәдё»зҡ„ж¶өе…»ж–№жі•еҸ‘еұ•дёәвҖңеҸ‘жҳҺжң¬еҝғвҖқи®әгҖӮеӯҹеӯҗи®ӨдёәпјҢдәәжҖ§жң¬е–„пјҢдҪҶжҳҜз”ұдәҺеӨ–з•ҢзҺҜеўғ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дәә们еҫҖеҫҖдјҡеҒҸзҰ»жҲ–дё§еӨұжҖ§е–„зҡ„жң¬жҖ§пјҢеҰӮдҪ•дҪҝдәәдҝқжҢҒгҖҒжҒўеӨҚжҖ§е–„зҡ„жң¬жҖ§пјҢеӯҹеӯҗжҸҗеҮәдәҶеӯҳеҝғгҖҒе…»еҝғгҖҒжұӮж”ҫеҝғгҖҒеҜЎж¬Ізӯүж–№жі•гҖӮйҷҶд№қжёҠиөһеҗҢеӯҹеӯҗзҡ„ж–№жі•пјҢи®ӨдёәвҖңжӯӨд№ғдёәеӯҰд№Ӣй—ЁпјҢиҝӣеҫ·д№Ӣең°вҖқпјҢе№¶ж №жҚ®иҮӘе·ұеҜ№вҖңжң¬еҝғвҖқжҰӮеҝө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еҸ‘жҳҺжң¬еҝғвҖқзҡ„дё»еј пјҢдё»еј з ”з©¶еҝғдёӯд№ӢзҗҶпјҢзӣҙжҺҘдҪ“и®Өжң¬еҝғпјҢд»ҺиҖҢиҫҫеҲ°и®ӨиҜҶзҗҶгҖҒи·өиЎҢзҗҶзҡ„зӣ®зҡ„гҖӮе®Ӣд»ЈзҗҶеӯҰе’ҢеҝғеӯҰд№ӢдәүпјҢзҗҶеӯҰдёҖзӣҙеҚ жҚ®дёҠйЈҺпјҢзӣҙиҮі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җҶеӯҰиў«е®ҡдёәдёҖе°ҠпјҢдҪҶеҝғ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е№¶жңӘеҒңж»һгҖӮ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е°ҶеҝғеӯҰеҸ‘еұ•еҲ°дәҶй«ҳеі°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еңЁйҷҶд№қжёҠжң¬еҝғжҖқжғі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еҝғеӨ–ж— зҗҶвҖқзҡ„е‘Ҫйўҳе’ҢвҖңиҮҙиүҜзҹҘвҖқзҡ„дҝ®е…»ж–№жі•пјҢдё°еҜҢеҸ‘еұ•дәҶеӯҹеӯҗзҡ„ж јеҝғзҗҶи®әе’ҢиүҜзҹҘзҗҶи®әгҖӮ第дёҖпјҢеҸ‘еұ•дәҶеӯҹеӯҗзҡ„ж јеҝғзҗҶи®әгҖӮеӯҹеӯҗи®Өдёәд»Ғд№үзӨјжҷәдә§з”ҹдәҺжҒ»йҡҗгҖҒзҫһжҒ¶гҖҒиҫһи®©гҖҒжҳҜйқһеӣӣеҝғпјҢжҳҜж №жӨҚдәҺдәәзҡ„еҶ…еҝғиҖҢиЎЁзҺ°еңЁдәәзҡ„еӨ–еңЁиЎҢдёәдёҠпјҢз”ҡиҮіе……зӣҲдәҺдәәзҡ„зҘһжғ…еӨ–иІҢпјҢдёҖжңӣдҫҝзҹҘпјҢд»–иҜҙвҖңеҗӣеӯҗжүҖжҖ§пјҢд»Ғд№үзӨјжҷәж №дәҺеҝғпјҢе…¶з”ҹиүІд№ҹзқҹ然пјҢи§ҒдәҺйқўпјҢзӣҺдәҺиғҢпјҢж–ҪдәҺеӣӣдҪ“пјҢеӣӣдҪ“дёҚиЁҖиҖҢе–»вҖқгҖӮиҰҒиҫҫеҲ°иҝҷж ·зҡ„зҗҶжғізҠ¶жҖҒпјҢе°ұиҰҒдҝқжңүжӯӨеҝғпјҢеҰӮжһңжӯӨеҝғиў«еӨ–еңЁдәӢзү©жүҖжғ‘иҖҢжңүжүҖеҒҸзҰ»пјҢдҫҝиҰҒеҺ»йҷӨеҝғдёӯзҡ„жҳҜйқһжқӮеҝөпјҢеӯҹеӯҗиҜҙвҖңеӨ§дәәиҖ…пјҢдёҚеӨұе…¶иөӨеӯҗд№ӢеҝғиҖ…д№ҹвҖқпјҢвҖңе”ҜеӨ§дәәдёәиғҪж јеҗӣеҝғд№ӢйқһвҖқ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ңЁеӯҹеӯҗзҡ„жҖқжғідёӯпјҢеҸӘжңү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ҚіжңүйҒ“еҫ·зҡ„дәәжүҚиғҪеҒҡеҲ°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йҖҡиҝҮвҖңеҝғеӨ–ж— зҗҶвҖқзҡ„е‘ҪйўҳпјҢе°Ҷе…¶еҸ‘еұ•дёәвҖңеҸӘеңЁиә«еҝғдёҠеҒҡвҖқпјҢдҫҝдәәдәәзҡҶеҸҜиҫҫеҲ°зҡ„еўғз•ҢгҖӮвҖңеҝғеӨ–ж— зҗҶвҖқж„ҸжҖқжҳҜеҝғдёӯжң¬жңүзҗҶпјҢеӨ–еңЁдәӢзү©дёӯзҡ„зҗҶе’Ңеҝғдёӯжң¬жңүзҡ„зҗҶжҳҜеҗҢдёҖзҡ„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еӨ–еңЁдәӢзү©зҡ„зҗҶжҳҜеҝғжүҖиөӢдәҲзҡ„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вҖңеҸӘеңЁиә«еҝғдёҠеҒҡпјҢеҶіз„¶д»ҘеңЈдәәдёәдәәдәәеҸҜеҲ°пјҢдҫҝиҮӘжңүжӢ…еҪ“дәҶвҖқгҖӮ第дәҢпјҢеҸ‘еұ•дәҶеӯҹеӯҗзҡ„иүҜзҹҘзҗҶи®әгҖӮ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жәҗиҮӘгҖҠеӯҹеӯҗВ·е°ҪеҝғдёҠгҖӢ第15з« пјҡ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еӯҹеӯҗжӣ°пјҡвҖңдәәд№ӢжүҖдёҚеӯҰиҖҢиғҪиҖ…пјҢе…¶иүҜиғҪд№ҹпјӣжүҖдёҚиҷ‘иҖҢзҹҘиҖ…пјҢе…¶иүҜзҹҘд№ҹгҖӮеӯ©жҸҗд№Ӣз«Ҙж— дёҚзҹҘзҲұе…¶дәІиҖ…пјҢеҸҠе…¶й•ҝд№ҹпјҢж— дёҚзҹҘ敬其兄д№ҹгҖӮвҖқ еңЁеӯҹеӯҗзңӢжқҘпјҢиүҜзҹҘе°ұжҳҜдәәеӨ©з”ҹе°ұе…·жңүзҡ„д»ҒгҖҒд№үе“Ғеҫ·гҖӮзҺӢйҳіжҳҺжңҖеҲқд№ҹ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继жүҝиҝҷдёҖжҰӮеҝөзҡ„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ҝғиҮӘ然дјҡзҹҘпјҡи§ҒзҲ¶иҮӘ然зҹҘеӯқпјҢи§Ғе…„иҮӘ然зҹҘејҹпјҢи§Ғеӯәеӯҗе…Ҙдә•иҮӘ然зҹҘжҒ»йҡҗпјҢжӯӨдҫҝжҳҜиүҜзҹҘпјҢдёҚеҒҮеӨ–жұӮгҖӮвҖқжҷҡе№ҙпјҢйҡҸзқҖйҳ…еҺҶзҡ„еўһеҠ е’ҢеҝғеӯҰ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зҡ„йҖҗжёҗжҲҗзҶҹпјҢд»–зҡ„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йҖҗжёҗж¶өж‘„дәҶеҝғдёҺзҗҶпјҢеҢ…еҗ«е№ҝжіӣпјҢжҲҗдёәд»–еҝғеӯҰ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дёӯжң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жҰӮеҝөгҖӮе…·дҪ“иҖҢиЁҖеҢ…жӢ¬еҰӮдёӢдёүдёӘж–№йқўзҡ„еҗ«д№үгҖӮе…¶дёҖпјҢиүҜзҹҘжҳҜеӨ©зҗҶеңЁеҝғдёӯзҡ„иҮӘ然жҳҫзҺ°гҖӮеңЁзҺӢйҳіжҳҺзҡ„зҗҶи®әдёӯпјҢ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зҗҶжҳҜеҗҢдёҖзҡ„гҖҒдёҖдҪ“зҡ„пјҢиүҜзҹҘдҫҝжҳҜиҝҷдёӘеҗҢдёҖдҪ“зҡ„дҪ“зҺ°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зҹҘжҳҜзҗҶд№ӢзҒөеӨ„гҖӮе°ұе…¶дё»е®°еӨ„иҜҙпјҢдҫҝи°“д№Ӣеҝғпјӣе°ұе…¶зҰҖиөӢеӨ„иҜҙпјҢдҫҝи°“д№ӢжҖ§гҖӮеӯ©жҸҗд№Ӣз«Ҙж— дёҚзҹҘзҲұе…¶дәІпјҢж— дёҚзҹҘ敬其兄пјҢеҸӘжҳҜиҝҷдёӘзҒөиғҪдёҚдёәз§Ғж¬ІйҒ®йҡ”пјҢе……жӢ“еҫ—е°ҪпјҢдҫҝе®Ңе®ҢжҳҜд»–жң¬дҪ“пјҢдҫҝдёҺеӨ©ең°еҗҲеҫ·гҖӮвҖқеҸӘиҰҒиүҜзҹҘиғҪе®Ңе…ЁжҳҫзҺ°пјҢдҫҝжҳҜиҙҜз©ҝдәҺеӨ©ең°д№Ӣй—ҙзҡ„зҗҶпјҢеҚіиүҜзҹҘе°ұжҳҜ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зҗҶпјҢдёүдҪҚдёҖдҪ“гҖӮе…¶дәҢпјҢиүҜзҹҘжҳҜжҳҜйқһд№ӢеҝғгҖӮжҳҜйқһд№Ӣеҝғжң¬жҳҜеӯҹеӯҗжҸҗеҮәзҡ„еӣӣеҝғд№ӢдёҖ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е°Ҷд№ӢзӯүеҗҢдәҺиүҜзҹҘпјҢе°Ҷд№ӢдҪңдёәеҲӨж–ӯеҜ№й”ҷ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д»–иҜҙпјҢдҪ йӮЈдёҖзӮ№иүҜзҹҘпјҢжҳҜдҪ иҮӘ家зҡ„еҮҶеҲҷгҖӮдҪ ж„ҸеҝөжүҖеҲ°д№ӢеӨ„пјҢеҜ№зҡ„дҫҝзҹҘйҒ“жҳҜеҜ№зҡ„пјҢй”ҷзҡ„дҫҝзҹҘйҒ“жҳҜй”ҷзҡ„пјҢдёҖзӮ№д№ҹйҡҗзһ’дёҚеҫ—гҖӮиҝҷиүҜзҹҘдҫҝжҳҜдҪ зҡ„жҳҺеёҲгҖӮе…¶дёүпјҢиүҜзҹҘе…·жңүзӣ‘еҜҹ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дәәзҡ„жҖқжғіеҠЁжңәпјҢеҰӮжһңз¬ҰеҗҲеӨ©зҗҶпјҢиүҜзҹҘиҮӘ然дјҡзҹҘйҒ“пјӣеҰӮжһңжҳҜз§Ғж¬Із§Ғж„ҸпјҢиүҜзҹҘиҮӘ然д№ҹдјҡеҲҶиҫЁеҫ—еҮәжқҘпјҢвҖңзӣ–жҖқд№ӢжҳҜйқһйӮӘжӯЈпјҢиүҜзҹҘж— жңүдёҚзҹҘиҖ…вҖқпјҢ并иғҪиҮӘи§үзҹ«жӯЈпјҢеҺ»йҷӨиҝҷд»Ҫжү§зқҖпјҢиҝҳиүҜзҹҘд»Ҙжё…жҳҺпјҢвҖңиүҜзҹҘдәҰиҮӘдјҡи§үпјҢи§үеҚіи”ҪеҺ»пјҢеӨҚе…¶дҪ“зҹЈвҖқгҖӮеӯҹеӯҗзҡ„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пјҢзӯүеҗҢдәҺжҖ§е–„зҡ„жң¬жҖ§пјҢзӯүеҗҢдәҺд»Ғд№үзӨјжҷәзӯүйҒ“еҫ·е“ҒиҙЁпјҢжҳҜеӯҳеңЁ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е°Ҷд№ӢдёҺ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зҗҶзӯүеҝғеӯҰзү№жңүзҡ„жҰӮеҝөзӣёз»“еҗҲпјҢеңЁеӯҳеңЁж„Ҹд№үдёҠе°Ҷд№ӢзӯүеҗҢдәҺеҝғгҖҒжҖ§гҖҒзҗҶпјҢдёүдҪҚдёҖдҪ“пјӣжӯӨеӨ–иҝҳеңЁе®һи·өж„Ҹд№үдёҠжү©еұ•дәҶ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зҡ„еҶ…ж¶өпјҢдҪҝд№Ӣе…·жңүеҲӨж–ӯгҖҒзӣ‘еҜҹгҖҒзҹ«жӯЈзҡ„еҠҹиғҪпјҢжҳҫзӨәеҮәзҹҘиЎҢеҗҲдёҖзҡ„еҖҫеҗ‘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еҸҲ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иҮҙиүҜзҹҘвҖқ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жӣҙеҠ зӘҒеҮәдәҶ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зҹҘиЎҢеҗҲдёҖ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е°Ҷеӯҹеӯҗзҡ„иүҜзҹҘжҰӮеҝөеҸ‘еұ•еҲ°дёҖдёӘж–°зҡ„йҳ¶ж®өгҖӮиҮҙиүҜзҹҘжҳҜгҖҠеӨ§еӯҰгҖӢвҖңиҮҙзҹҘвҖқжҰӮеҝөе’ҢеӯҹеӯҗвҖңиүҜзҹҘвҖқжҰӮеҝөзҡ„зі…еҗҲгҖӮжңүж—¶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зҺӢйҳіжҳҺжҷҡе№ҙжүҖиҜҙзҡ„иҮҙзҹҘе°ұжҳҜиҮҙиүҜзҹҘгҖӮиҮҙиүҜзҹҘдё»иҰҒжңүдёӨеұӮеҗ«д№үпјҡе…¶дёҖпјҢиҮҙдёәеҲ°иҫҫ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иҮҙиүҜзҹҘе°ұжҳҜеҺ»йҷӨз§Ғж„Ҹз§Ғж¬Ізҡ„йҒ®и”ҪпјҢеҲ°иҫҫиүҜзҹҘзҡ„еўғз•ҢгҖӮеҜ№жӯӨпјҢд»–еӨҡжңүи®әиҝ°пјҢеҰӮвҖңдәәеҝғжҳҜеӨ©жёҠгҖӮеҝғд№Ӣжң¬дҪ“ж— жүҖдёҚиҜҘпјҢеҺҹжҳҜдёҖдёӘеӨ©гҖӮеҸӘдёәз§Ғж¬ІйҡңзўҚпјҢеҲҷеӨ©д№Ӣжң¬дҪ“еӨұдәҶгҖӮеҝғд№ӢзҗҶж— з©·е°ҪпјҢеҺҹжҳҜдёҖдёӘжёҠгҖӮеҸӘдёәз§Ғж¬ІзӘ’еЎһпјҢеҲҷжёҠд№Ӣжң¬дҪ“еӨұдәҶгҖӮеҰӮд»ҠеҝөеҝөиҮҙиүҜзҹҘпјҢе°ҶжӯӨйҡңзўҚзӘ’еЎһдёҖйҪҗеҺ»е°ҪпјҢеҲҷжң¬дҪ“е·ІеӨҚпјҢдҫҝжҳҜеӨ©жёҠдәҶвҖқгҖӮе…¶дәҢпјҢиҮҙдёәе®һи·ө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иҮҙиүҜзҹҘе°ұжҳҜе°ҶиүҜзҹҘз”ЁдәҺе…·дҪ“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зҡ„е®һи·өдёӯгҖ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жүҖи°“иҮҙзҹҘж јзү©иҖ…пјҢиҮҙеҗҫеҝғд№ӢиүҜзҹҘдәҺ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д№ҹгҖӮеҗҫеҝғд№ӢиүҜзҹҘпјҢеҚіжүҖи°“еӨ©зҗҶд№ҹгҖӮиҮҙеҗҫеҝғиүҜзҹҘд№ӢеӨ©зҗҶдәҺ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пјҢеҲҷ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зҡҶеҫ—е…¶зҗҶзҹЈгҖӮвҖқеҚіиҮҙзҹҘж јзү©е°ұжҳҜе°Ҷеҝғдёӯзҡ„иүҜзҹҘз”ЁдәҺз”ҹжҙ»дёӯзҡ„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гҖҒдёҖиЁҖдёҖиЎҢгҖҒдёҖдёҫдёҖеҠЁд№ӢдёӯгҖӮиүҜзҹҘе°ұжҳҜеӨ©зҗҶпјҢе°ҶиүҜзҹҘз”ЁдәҺз”ҹжҙ»дёӯзҡ„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пјҢйӮЈд№ҲдәӢдәӢзү©зү©е°ұйғҪиғҪеӨҹжҳҫзҺ°еҮәе®ғзҡ„зҗҶдәҶпјҢдәә们зҡ„дёҖиЁҖдёҖиЎҢгҖҒдёҖдёҫдёҖеҠЁд№ҹйғҪз¬ҰеҗҲзҗҶдәҶ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еңЁзҗҶеӯҰең°дҪҚдёҖе°Ҡ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дјҡеҮәзҺ°еҝғеӯҰзҗҶи®әзҡ„еҸ‘еұ•й«ҳеі°пјҹ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дёҺзҺӢйҳіжҳҺдёӘдәәвҖңж јзү©еӨұиҙҘвҖқвҖңйҫҷеңәд№ӢжӮҹвҖқзҡ„зҗҶи®әжҖқиҖғе’Ңе®һи·өжңүе…і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зҡ„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еҮәзҺ°дәҶйҮҚеӨ§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ж»Ӣз”ҹдәҶеҝғеӯҰзӘҒз ҙжҖ§еҸ‘еұ•зҡ„жҖқжғіеңҹеЈӨпјҢиҝҳжңүеӯҰжңҜеҸ‘еұ•зҡ„еҶ…еңЁеӣ зҙ пјҢжҳҜдәҢиҖ…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гҖҒзӣёдә’е‘јеә”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е°ұ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зҡ„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иҖҢиЁҖпјҢйҰ–е…ҲпјҢж”ҝжІ»дёҠзәІзәӘеәҹејӣпјҢ秩еәҸж¶Јж•ЈпјҢгҖҠжҳҺеҸІгҖӢдёӯиЁҖвҖңжҳҺиҮӘдё–е®—иҖҢеҗҺпјҢзәІзәӘж—Ҙд»ҘйҷөеӨ·пјҢзҘһе®—жң«е№ҙпјҢеәҹеқҸжһҒзҹЈвҖқгҖӮзҡҮеёқеӨҡжҖ ж”ҝпјҢдёҚйғҠгҖҒдёҚзҰҳгҖҒдёҚжңқгҖҒдёҚи®ІпјҢзәөжғ…дә«д№җпјҢе–ңжҖ’ж— еёёпјҢеҠЁиҫ„е»·жқ–еӨ§иҮЈпјҢиҝҷдҪҝзҡҮеёқзҡ„е°ҠдёҘжү«ең°гҖҒжқғеЁҒдё§еӨұпјҢеӨ§иҮЈд»¬еҜ№зҡҮеёқжү№иҜ„зҡ„еҘҸз–ҸиҝһзҜҮзҙҜзүҚпјҢжңқйҮҺдёҠдёӢеҮәзҺ°дәҶйқһеҗӣжҖқжҪ®гҖӮдёҺд№Ӣзӣёдјҙзҡ„жҳҜйқһз»ҸгҖҒйқһеңЈжҖқжҪ®зҡ„еҮәзҺ°пјҢеҰӮвҖңгҖҠе…ӯз»ҸгҖӢгҖҠиҜӯгҖӢгҖҠеӯҹгҖӢпјҢд№ғйҒ“еӯҰд№ӢеҸЈе®һпјҢеҒҮдәәд№ӢжёҠи–®д№ҹвҖқгҖӮеҗҢж—¶еҮәзҺ°дәҶи§ҶеҠҹеҗҚеҲ©зҰ„дёәжқҹзјҡпјҢиҝҪжұӮиҖізӣ®еЈ°иүІзҡ„жғ…ж¬ІжҖқжғіпјҢеҰӮиўҒе®ҸйҒ“жҖ»з»“дәҶдәәз”ҹдә”д№җпјҢ第дёҖд№җдҫҝжҳҜвҖңзӣ®жһҒдё–й—ҙд№ӢиүІпјҢиҖіжһҒдё–й—ҙд№ӢеЈ°пјҢиә«жһҒдё–й—ҙд№ӢйІңпјҢеҸЈжһҒдё–й—ҙд№Ӣи°ӯвҖқпјҢ并表зӨәдәәз”ҹзҹӯжҡӮпјҢз»қдёҚдјҡз”ЁеҒҡе®ҳзҡ„ж— жқҘз”ұд№ӢиӢҰжҚўжӯӨдәәз”ҹд№Ӣд№җпјҢвҖңдәәз”ҹеҮ ж—ҘиҖіпјҢиҖҢд»ҘжІЎжқҘз”ұд№ӢиӢҰпјҢжҳ“еҗҫж— з©·д№Ӣд№җе“үвҖқгҖӮе…¶ж¬ЎпјҢ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е•Ҷе“Ғз»ҸжөҺиҝ…йҖҹеҸ‘еұ•пјҢе•Ҷе“ҒдәӨжҳ“ж—ҘзӣҠз№ҒиҚЈпјҢжө·еӨ–иҙёжҳ“и¶ӢдәҺйјҺзӣӣпјҢзӨҫдјҡдёҠз»Ҹе•Ҷд№ӢйЈҺзӣӣиЎҢгҖӮж №жҚ®йЎҫзӮҺжӯҰзҡ„и§ӮеҜҹпјҢжҳҺеҲқиҮіејҳжІ»жңҹй—ҙпјҢж°‘йЈҺж·іеҺҡпјҢдәәж°‘е®үеұ…д№җдёҡпјҢвҖңеҜ»иҮіжӯЈеҫ·жң«еҳүйқ–еҲқеҲҷзЁҚејӮзҹЈпјҢеҮәиҙҫж—ўеӨҡпјҢеңҹз”°дёҚйҮҚпјҢж“ҚиөҖдәӨжҚ·пјҢиө·иҗҪдёҚеёёвҖқгҖӮдҪ•иүҜдҝҠдәҰиҜҙпјҢжӯЈеҫ·д№ӢеүҚвҖңйҖҗжң«д№Ӣдәәе°ҡе°‘вҖқпјҢеҳүйқ–д№Ӣж—¶вҖңеҺ»еҶңиҖҢж”№дёҡдёәе·Ҙе•ҶиҖ…дёүеҖҚдәҺеүҚзҹЈвҖқпјҢз”ҡиҮіеЈ«еӨ§еӨ«д№ҹеҠ е…Ҙз»Ҹе•ҶиЎҢеҲ—пјҢвҖңдёҖжү№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и„ұзҰ»е„’жңҜжҠ•иә«е•Ҷдёҡжҙ»еҠЁпјҢз”ҡиҮіжңүеЈ«еӨ§еӨ«жҠҠдёәиҙҫдҪңдёәвҖҳжӣІзәҝе…Ҙд»•вҖҷзҡ„дёҖжқЎйҖ”еҫ„вҖқпјҢвҖңз»Ҹе•Ҷж—ўеҸҜд»ҘеўһеҠ зү©иҙЁиҙўеҜҢпјҢеҸҲеҸҜд»Ҙе…Ҙд»•дёәе®ҳпјҢиҝҷ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иҜұеҸ‘дәҶеЈ«еӨ§еӨ«д»Һе•Ҷзҡ„ж¬ІжңӣвҖқгҖӮдјҙйҡҸзқҖе•Ҷдёҡзҡ„е·ЁйўқеҲ©ж¶ҰпјҢеҜҢе•ҶеӨ§иҙҫж—ҘзӣҠеўһеӨҡпјҢзӨҫдјҡдёҠеҘўйқЎжҲҗйЈҺпјҢиҝқзӨјйҖҫеҲ¶иЎҢдёәеұЎи§ҒдёҚйІңпјҢд»ҺиЎЈзқҖжңҚйҘ°еҲ°еұ…е®…з”Ёе…·пјҢеҶҚеҲ°е©ҡ姻зӨјд»Әзӯүж— еӨ„дёҚеңЁпјҢеҚідҪҝжңқе»·дёүд»Өдә”з”іпјҢд»Қ然收ж•Ҳз”ҡеҫ®пјҢзӨҫдјҡзҡ„иә«д»Ҫзӯүзә§з§©еәҸйҒӯеҲ°жһҒеӨ§зҡ„з ҙеқҸгҖӮе°ұеӯҰжңҜеҸ‘еұ•зҡ„еҶ…еңЁеӣ зҙ иҖҢиЁҖпјҢйҰ–е…ҲпјҢжңұзҶ№зҗҶеӯҰж—ҘзӣҠиө°еҗ‘еғөеҢ–гҖӮжңұзҶ№дё»еј зҗҶж°”дәҢе…ғи®әпјҢзҗҶжҳҜе®ўи§Ӯ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дәәзҡ„жҖқжғіиЎҢдёәиҰҒиҫҫеҲ°зҗҶзҡ„иҰҒжұӮпјҢеҲҷиҰҒйҖҡиҝҮдё»и§Ӯзҡ„еҠӘеҠӣе®һи·өпјҢдё»е®ўдәҢе…ғжҖ§жһ„жҲҗдәҶзҗҶеӯҰе®һи·өзҡ„еҶ…еңЁзҹӣзӣҫгҖӮжңұзҶ№жҸҗеҮәж јзү©иҮҙзҹҘзҡ„е®һи·өж–№жі•пјҢеҚійҖҡиҝҮеҜ№дёҮзү©д№ӢзҗҶзҡ„е№ҝжіӣз ”з©¶пјҢиҖҢиҫҫеҲ°еҜ№жҷ®йҒҚд№ӢзҗҶ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ж–№жі•иү°иӢҰжј«й•ҝпјҢдё”дёҚдёҖе®ҡиғҪеӨҹжҲҗеҠҹпјҢзҺӢйҳіжҳҺвҖңж јз«№вҖқеӨұиҙҘ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еҫҲеҘҪзҡ„дҫӢеӯҗгҖӮзҗҶеӯҰзҗҶи®әйңҖиҰҒиҝӣдёҖжӯҘең°еҸ‘еұ•е®Ңе–„пјҢдҪҶжҳҜжңұзҶ№зҗҶеӯҰе®ҳеӯҰең°дҪҚзҡ„зЎ®з«ӢпјҢвҖңд»Ҙеӣәе®ҡзҡ„зҗҶи§ЈжЁЎејҸе’Ңи®ӨзҹҘиҢғеӣҙжҠ‘еҲ¶дәҶжҖқжғіиҮӘз”ұеҲӣйҖ зҡ„жҙ»еҠӣвҖқпјҢдҪҝд№ӢеҒңж»һдёҚеүҚпјҢж—ҘзӣҠеғөеҢ–гҖӮжүҖд»ҘйҒӯеҲ°дёҚе°‘еӯҰиҖ…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Ңз”ҹжҙ»дәҺжҳҺдёӯжңҹзҡ„зҪ—й’ҰйЎәеҰӮжҳҜиҜҙпјҡвҖңдҪҷиҮӘе…Ҙе®ҳеҗҺпјҢеёёи§Ғиҝ‘ж—¶еҚҒж•°з§Қд№ҰпјҢдәҺе®ӢиҜёеӨ§е„’иЁҖи®әжңүжҳҺиҜӢиҖ…пјҢжңүжҡ—иҜӢиҖ…пјҢзӣҙжҳҜеҸҜжҖӘгҖӮвҖқе…¶ж¬ЎпјҢиҮӘйҷҶд№қжёҠд»ҘжқҘпјҢеҝғеӯҰеҸ‘еұ•дёҖзј•дёҚз»қпјҢдёә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еҸ‘еұ•еҘ е®ҡдәҶеҹәзЎҖ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д»ҘеҗҙдёҺејјгҖҒиғЎеұ…д»Ғе’ҢйҷҲзҢ®з« дёәд»ЈиЎЁгҖӮеҗҙдёҺејјжңүи®ёеӨҡжҺҘиҝ‘еҝғеӯҰзҡ„и®әиҝ°пјҢеҰ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Ө«еҝғпјҢиҷҡзҒөд№ӢеәңпјҢзҘһжҳҺд№ӢиҲҚпјҢеҰҷеҸӨд»ҠиҖҢиҙҜз©№еЈӨпјҢдё»е®°дёҖиә«иҖҢж №жҹўдёҮдәӢгҖӮвҖқзӘҒеҮәеҝғзҡ„дё»е®°жҖ§пјӣеңЁдҝ®е…»ж–№жі•дёҠпјҢд»–д№ҹи®ӨеҗҢжң¬еҝғиҜҙпјҡвҖңдәәиӢҹеҫ—жң¬еҝғпјҢйҡҸеӨ„зҡҶд№җпјҢз©·иҫҫдёҖиҮҙгҖӮвҖқвҖңж¶өе…»жӯӨеҝғпјҢдёҚдёәдәӢзү©жүҖиғңпјҢз”ҡеҲҮж—Ҙз”Ёе·ҘеӨ«гҖӮвҖқиғЎеұ…д»ҒдәҰжңүзӣёдјји®әиҝ°гҖӮйҷҲзҢ®з« зӣҙжҺҘжҸҗеҮәйқҷеқҗдҪ“жӮҹзҡ„дҝ®е…»ж–№жі•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иҲҚеҪјд№Ӣз№ҒпјҢжұӮеҗҫд№ӢзәҰпјҢжғҹеңЁйқҷеқҗгҖӮд№…д№ӢпјҢ然еҗҺи§ҒеҗҫжӯӨеҝғд№ӢдҪ“пјҢйҡҗ然е‘ҲйңІпјҢеёёиӢҘжңүзү©пјҢж—Ҙз”Ёй—ҙз§Қз§Қеә”й…¬пјҢйҡҸеҗҫжүҖж¬ІпјҢеҰӮ马д№ӢеҫЎиЎ”еӢ’д№ҹпјӣдҪ“и®Өзү©зҗҶпјҢзЁҪиҜёеңЈи®ӯпјҢеҗ„жңүеӨҙз»ӘжқҘеҺҶпјҢеҰӮж°ҙд№Ӣжңүжәҗ委д№ҹгҖӮдәҺжҳҜ涣然иҮӘдҝЎжӣ°пјҡвҖҳдҪңеңЈд№ӢеҠҹпјҢе…¶еңЁе…№д№ҺпјҒвҖҷвҖқе·ІжңүйЎҝжӮҹзҡ„ж„Ҹе‘іпјҢиў«и§ҶдёәзҺӢ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зҡ„е…Ҳй©ұгҖӮзәІзәӘеәҹејӣз»ҷдәҶдәә们иҮӘз”ұжҖқжғізҡ„з©әй—ҙпјҢз»ҸжөҺзҡ„з№ҒиҚЈгҖҒз”ҹжҙ»зҡ„еҜҢи¶із»ҷдәәж°‘жҸҗдҫӣдәҶж‘Ҷи„ұзӨјж•ҷжқҹзјҡгҖҒиҝҪжұӮеҝ«ж„Ҹдәәз”ҹзҡ„зү©иҙЁжқЎд»¶пјҢж—ҘзӣҠеғөеҢ–зҡ„жңұзҶ№зҗҶеӯҰе·ІдёҚз¬ҰеҗҲ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зҡ„жҪ®жөҒпјҢиҖҢејәи°ғдәәзҡ„дё»и§ӮиғҪеҠЁжҖ§пјҢдё»еј еҝғзҗҶеҗҲдёҖгҖҒеҝғеӨ–ж— зү©пјҢжҸҗеҮәж¶өе…»гҖҒйқҷеқҗгҖҒдҪ“жӮҹзӯүз®ҖзәҰдҝ®е…»ж–№ејҸзҡ„еҝғеӯҰеҲҷдёҺжӯӨжҪ®жөҒдёҖиҮҙгҖӮ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е°ұеңЁиҝҷдёҖ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дёҺеӯҰжңҜдәӨз»Үдә’еҠЁ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еә”иҝҗиҖҢз”ҹгҖӮ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дёүгҖҒжҳҺд»ЈеҗҺ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пјҡйҖҗжӯҘиө°еҗ‘иҖғжҚ®еӯҰ иҖғжҚ®е’Ңд№үзҗҶжҳҜ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ҡ„дёӨз§Қдё»иҰҒж–№ејҸгҖӮиҖғжҚ®еҚіиҖғиҜҒпјҢжҳҜйҖҡиҝҮиҖғж ёдәӢе®һе’ҢеҪ’зәідҫӢиҜҒпјҢжҸҗдҫӣеҸҜдҝЎжқҗж–ҷиҖҢеҫ—еҮәз»“и®әзҡ„з ”з©¶ж–№жі•пјҢеҢ…жӢ¬еҜ№ж–ҮзҢ®зҡ„еӯ—йҹігҖҒеӯ—д№үгҖҒиҜҚд№үзҡ„жіЁйҮҠпјҢдҪңиҖ…зҡ„з”ҹе№ідәӢиҝ№гҖҒж–ҮзҢ®жүҖж¶үеҸҠзҡ„ж—¶й—ҙгҖҒең°зҗҶгҖҒеҗҚзү©еҲ¶еәҰзӯү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е№ҝд№үзҡ„иҖғжҚ®иҝҳеҢ…жӢ¬иө„ж–ҷ收йӣҶгҖҒзүҲжң¬ж ЎеӢҳзӯүж–№йқў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д№үзҗҶжҳҜеҜ№ж–ҮзҢ®зҡ„жҖқжғіеҶ…ж¶өиҝӣиЎҢйҳҗйҮҠжҲ–еҸ‘еұ•гҖӮдёҚеҗҢзҡ„ж—¶жңҹпјҢз”ұдәҺж”ҝжІ»зӨҫдјҡгҖҒж–ҮеҢ–зҺҜеўғгҖҒеӯҰжңҜйЈҺж°”зӯүзҡ„дёҚеҗҢпјҢе‘ҲзҺ°еҮәдёҚеҗҢзҡ„еҖҫеҗ‘пјҢжңүж—¶д»ҘиҖғжҚ®дёәдё»пјҢжңүж—¶д»Ҙд№үзҗҶдёәдё»гҖӮжұүе”җж—¶жңҹд»ҘиҖғжҚ®дёәдё»пјҢд№үзҗҶдёәиҫ…гҖӮжұүжӯҰеёқз«Ӣдә”з»ҸеҚҡеЈ«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жҳҜвҖңдә”з»ҸвҖқйҮҚиҰҒзҡ„иҫ…еҠ©иҜ»зү©пјҢз”ұдәҺз»Ҹд№ҰжҲҗдёәеҲ©зҰ„д№ӢйҖ”пјҢжүҖд»ҘеңЁдј жҺҲдёҠйҮҚеёҲ法家法пјҢејҹеӯҗеҸӘиғҪжҒӘе®Ҳз« еҸҘпјҢеңЁеӯ—иҜҚеҗҚзү©зҡ„и®ӯиҜӮдёҠдёӢе·ҘеӨ«пјҢдҪҶдәҰжңүдёҚд»ҘеҠҹеҗҚдёәзҙҜиҖ…пјҢеңЁз« еҸҘдёӯеҠ е…ҘдёҖе®ҡзҡ„д№үзҗҶйҳҗйҮҠгҖӮйӯҸжҷӢеҚ—еҢ—жңқйҡӢе”җж—¶жңҹпјҢдҪӣйҒ“дәҢж•ҷзӣӣиЎҢпјҢеӨ§еӨ§еҶІеҮ»дәҶе„’еӯҰзҡ„е®ҳж–№ең°дҪҚпјҢз»ҹжІ»жҖқжғійўҶеҹҹе‘ҲзҺ°дёүи¶ійјҺз«Ӣзҡ„еұҖйқўпјҢе„’еӯҰжңүж—¶еұҲеұ…дҪӣйҒ“д№ӢеҗҺгҖӮиҝҷдёҖеұҖйқўзҡ„еҮәзҺ°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дҪӣйҒ“дәҢж•ҷиҝҺеҗҲдәҶеҪ“ж—¶зӨҫдјҡзҡ„йңҖжұӮ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жұүд»Је„’еӯҰжүҖзЎ®з«Ӣзҡ„еӨ©дәәеҗҲдёҖзҡ„е“ІеӯҰдҪ“зі»е·Із»Ҹиў«ж—¶д»ЈжүҖжҠӣејғпјҢдёәдәҶеӣһеә”дҪӣйҒ“дәҢж•ҷзҡ„еҶІеҮ»пјҢе„’еӯҰеҝ…йЎ»йҮҚе»әе“ІеӯҰдҪ“зі»гҖӮ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ӣ е…¶дәәжҖ§и®әгҖҒеҝғжҖ§и®әиө„жәҗз¬ҰеҗҲе„’еӯҰйҮҚе»әзҡ„йңҖжұӮиҖҢжҲ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жҖқжғіиө„жәҗпјҢжүҖд»Ҙе”җдёӯжңҹд№ӢеҗҺпјҢд»Ҙйҹ©ж„ҲгҖҒжқҺзҝұдёәе…Ҳй©ұ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иҪ¬еҗ‘еҲӣйҖ жҖ§еҸ‘еұ•пјҢд№үзҗҶдёәдё»пјҢиҖғжҚ®дёәиҫ…пјҢиҝҷдёҖеҖҫеҗ‘延з»ӯиҮі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гҖӮе…ғеҸҠжҳҺеҲқпјҢеңЁжүҝ继жңұеӯҰ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әҰжңүиҖғжҚ®и‘—дҪңзҡ„еҮәзҺ°пјҢеҰӮиөөеҫ·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з¬әд№үгҖӢгҖӮиҜҘд№Ұзҡ„еҶҷдҪңзјҳз”ұжҳҜиөөеҫ·еңЁиҜ»гҖҠеӣӣд№Ұз« еҸҘйӣҶжіЁгҖӢ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дә§з”ҹдәҶеҫҲеӨҡз–‘жғ‘пјҢиҖҢдёҚиғҪеҫ—еҲ°и§Јзӯ”пјҢеҜ№дәҺеӯҰз”ҹжҸҗеҮә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д»–жңүж—¶д№ҹзӯ”дёҚдёҠжқҘпјҢдәҺжҳҜеҸ‘ж„ӨиҜ»д№ҰпјҢе№ҝи§Ҳз»ҸеҸІд№ӢдҪңгҖҒеҸӨдәәжіЁз–ҸпјҢз”ЁеҠҹ20дҪҷе№ҙпјҢж’°жҲҗжӯӨд№ҰгҖӮиөөеҫ·еңЁиҮӘеәҸдёӯиҜҙд»–зҡ„дё»иҰҒе·ҘдҪңжҳҜвҖңеӣ е…¶иЁҖд»ҘжұӮжүҖжң¬пјҢиҖғе…¶ејӮд»Ҙи®ўжүҖз–‘вҖқгҖӮвҖңеӣ е…¶иЁҖд»ҘжұӮжүҖжң¬вҖқе°ұжҳҜеҜ№жңұзҶ№гҖҠйӣҶжіЁгҖӢд№ғиҮ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жң¬д№ҰдёӯжүҖжҸҗеҸҠзҡ„еҗҚзү©еҲ¶еәҰгҖҒеҺҶеҸІдәӢе®һе’ҢжүҖеј•д№ҰзұҚпјҢжҺўз©¶жң¬жәҗпјҢжҢҮеҮәеҮәеӨ„гҖӮеҰӮгҖҠеӯҹеӯҗВ·е…¬еӯҷдё‘дёҠгҖӢ第7з« жңүвҖңд»ҒиҖ…еҰӮе°„вҖқпјҢиөөеҫ·жҢҮеҮәвҖңжң¬дәҺгҖҠзӨји®°В·е°„д№үгҖӢвҖқ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В·зҰ»еЁ„дёҠгҖӢ第1з« жңүвҖңж•…жӣ°дёәй«ҳеҝ…еӣ дёҳйҷөпјҢдёәдёӢеҝ…еӣ е·қжіҪвҖқпјҢиөөеҫ·жҢҮеҮәвҖңеҮәиҮӘгҖҠзӨји®°В·зӨјеҷЁгҖӢпјҢжүҖд»ҘжңүвҖҳж•…жӣ°вҖҷдәҢеӯ—вҖқгҖӮвҖңиҖғе…¶ејӮд»Ҙи®ўжүҖз–‘вҖқжҳҜ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ҸҠжңұжіЁдёӯзҡ„з–‘йҡҫй—®йўҳиҝӣиЎҢиҖғи®ўпјҢжҲ–иҖ…еҜ№жңұжіЁдёӯжңӘж¶үеҸҠзҡ„еӯ—иҜҚиҝӣиЎҢиЎҘе……жіЁйҮҠгҖӮеҰӮгҖҠеӯҹеӯҗВ·ж»•ж–Үе…¬дёҠгҖӢдёӯжңүвҖңд»Ҡд№ҹдёҚе№ёиҮідәҺеӨ§ж•…вҖқпјҢжңұжіЁдёәвҖңеӨ§ж•…пјҢеӨ§дё§д№ҹвҖқпјҢгҖҠеӣӣд№Ұз¬әд№үгҖӢдёәпјҡ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гҖҠе‘ЁзӨјВ·еӨ§е®—дјҜгҖӢпјҡвҖңеӣҪжңүеӨ§ж•…гҖӮвҖқйғ‘жіЁпјҡвҖңж•…и°“еҮ¶зҒҫд№ҹгҖӮвҖқеҸҲгҖҠд№җи®°гҖӢпјҡвҖңе…ҲзҺӢжңүеӨ§дәӢгҖӮвҖқйғ‘жіЁпјҡвҖңеӨ§дәӢи°“жӯ»дё§д№ҹгҖӮвҖқж„ҡжҢүеӨ§ж•…еҚіеӨ§дәӢд№Ӣд№үгҖӮеҸҲгҖҠжӣІзӨјгҖӢвҖңеҗӣеӯҗйқһжңүеӨ§ж•…вҖқжіЁпјҢгҖҠе‘ЁзӨјгҖӢжҜҸдә‘еӣҪжңүеӨ§ж•…пјҢзҡҶжҚ®еҶ жҲҺзҒҫзҘёпјҢ然еҲҷдәҰдёҚдё“жҢҮеӨ§дё§иҖҢиЁҖд№ҹгҖӮ иөөеҫ·еј•з”ЁгҖҠе‘ЁзӨјгҖӢгҖҠд№җи®°гҖӢгҖҠжӣІзӨјгҖӢдёӯзҡ„з»Ҹж–ҮеҸҠйғ‘зҺ„зҡ„жіЁйҮҠпјҢжҢҮеҮәвҖңеӨ§ж•…вҖқзҡ„ж„ҸжҖқжҳҜвҖңеӨ§дәӢвҖқпјҢеҢ…жӢ¬вҖңеӨ§дё§вҖқпјҢдҪҶдёҚдё“жҢҮвҖңеӨ§дё§вҖқгҖӮж—ўжҢҮеҮәдәҶжңұжіЁзҡ„еҮәеӨ„пјҢеҸҲиҖғиҜҒдәҶвҖңеӨ§ж•…вҖқзҡ„е…¶д»–еҗ«д№үпјҢдё°еҜҢдәҶжңұзҶ№зҡ„жіЁж–ҮгҖӮ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д№ӢеҗҺпјҢжӯӨзұ»и‘—дҪңжӣҙжҳҜеӨ§йҮҸж¶ҢзҺ°пјҢеҰӮи”Ўжё…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еӣҫеҸІеҗҲиҖғгҖӢгҖҒи–ӣеә”ж—Ӯ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дәәзү©иҖғгҖӢгҖҒй’ҹжғәзҡ„гҖҠиҜ ж¬Ўеӣӣд№ҰзҝјиҖғгҖӢгҖҒйҷҲзҰ№и°ҹ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еҗҚзү©иҖғгҖӢгҖҒйҷҲд»Ғй”Ў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дәәзү©еӨҮиҖғгҖӢгҖҒеҫҗйӮҰдҪҗзҡ„гҖҠеӣӣд№Ұз»ҸеӯҰиҖғгҖӢзӯүгҖӮиҝҷдәӣиҖғжҚ®зұ»и‘—дҪңпјҢдёҚеұҖйҷҗдәҺеҜ№еӯ—йҹігҖҒеӯ—д№ү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иҖҢжҳҜе°ҶиҖғиҜҒеҶ…е®№жӢ“еұ•иҮ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ҸҠжңұжіЁдёӯжүҖж¶үеҸҠзҡ„ж–ҮзҢ®жқҘжәҗгҖҒеӨ©ж–Үең°зҗҶгҖҒеҗҚзү©еҲ¶еәҰгҖҒеҺҶеӯҰз®—жңҜгҖҒдҪҡж–Үж Ўеј•зӯүеҗ„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ҢиҖғй•ңжәҗжөҒпјҢй’©жІүзҙўйҡҗпјҢиҫЁжһҗи§Јз–‘пјҢиө„ж–ҷдё°еҜҢпјҢиҖғиҜҒиҜҰз»ҶгҖӮиҜҘж—¶жңҹиҝҳеҮәзҺ°дәҶд»Ҙеӯҹеӯҗз”ҹ平家世дёәдё»зҡ„иҖғжҚ®жҖ§и‘—дҪңпјҢд»ҘйҷҲеЈ«е…ғ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жқӮи®°гҖӢе’ҢеҺҶжҳҺжё…дёӨд»Јзј–жҲҗзҡ„гҖҠдёүиҝҒеҝ—гҖӢдёәд»ЈиЎЁгҖӮгҖҠеӯҹеӯҗжқӮи®°гҖӢе…ұ4еҚ·гҖӮжҜҸеҚ·ж¶үеҸҠдёҚеҗҢзҡ„ж–№йқўпјҢ第дёҖеҚ·иҖғи®ўеӯҹеӯҗзҡ„з”ҹ平家世пјҢеҢ…жӢ¬зі»жәҗгҖҒйӮ‘йҮҢгҖҒеҗҚеӯ—гҖҒеӯҹжҜҚгҖҒеӯҹеҰ»гҖҒе—Јиғ„гҖҒеҸ—дёҡгҖҒдёғзҜҮгҖҒз”ҹеҚ’гҖҒиЎҘдј 10дёӘжқЎзӣ®пјӣ第дәҢеҚ·жҳҜ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№ҰдёӯжүҖеј•гҖҠиҜ—гҖӢгҖҠд№ҰгҖӢгҖҠзӨјгҖӢзӯүд№Ұе’ҢеҺҶеҸІдәӢе®һзҡ„иҖғиҜҒд»ҘеҸҠ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Ҫҡж–Ү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еҢ…жӢ¬зЁҪд№ҰгҖҒеҮҶиҜ—гҖҒжҸҶзӨјгҖҒеҫҒдәӢгҖҒйҖёж–Ү5дёӘжқЎзӣ®пјӣ第дёүеҚ·жҳҜеҜ№д»–д№ҰдёӯжүҖеј•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Һ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Җд№ҰдёӯеҺҹж–Үзҡ„ејӮеҗҢжҜ”иҫғе’Ң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ж–№иЁҖгҖҒдәәеҗҚ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еҢ…жӢ¬ж Ўеј•гҖҒж–№иЁҖгҖҒиҫЁеҗҚ3дёӘжқЎзӣ®пјӣ第еӣӣеҚ·жҳҜ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еӯ—иҜҚгҖҒиҜӯжі•еҸҠдёҚеҗҢжіЁи§Ј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еҢ…жӢ¬еӯ—еҗҢгҖҒеӯ—и„ұгҖҒж–ӯеҸҘгҖҒжіЁејӮгҖҒиҜ„иҫһ5дёӘжқЎзӣ®гҖӮиҜҘд№ҰеҜ№еӯҹеӯҗз”ҹе№ідәӢиҝ№зӯүзҡ„иҖғиҜҒгҖҒиҫЁжһҗеӨҡжңүзІҫеҪ©д№ӢеӨ„гҖӮгҖҠдёүиҝҒеҝ—гҖӢд»Ҙи®°иҪҪеӯҹж°Ҹ家ж—ҸгҖҒеҗҺдё–з»ҹжІ»иҖ…еҜ№еӯҹеӯҗзҡ„еҠ е°ҒгҖҒиЎЁеҪ°е’ҢеҺҶд»Ј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еҜ№еӯҹеӯҗзҡ„иҜ„д»·дёәдё»пјҢжҳҜдёҖйғЁеӯҹеӯҗзҡ„жЎЈжЎҲиө„ж–ҷгҖӮиҝҷдәӣиҖғжҚ®зұ»и‘—дҪңејҖеҗҜдәҶжё…д»Ј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ҖғжҚ®и‘—дҪңзҡ„е…ҲжІіпјҢдёәжё…д»Ј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ҖғжҚ®зұ»и‘—дҪңзҡ„иҫүз…ҢжҲҗе°ұеҘ е®ҡдәҶеӯҰжңҜгҖҒеӯҰйЈҺгҖҒеҶ…е®№е’Ңж–№жі•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жё…д»Ј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ҖғжҚ®зұ»и‘—дҪңжҲҗжһңдё°зЎ•пјҢеҶ…е®№е№ҝжіӣпјҢж— жүҖдёҚеҢ…пјҢд»Һеӯҹеӯҗзҡ„з”ҹе№ідәӢиҝ№еҰӮз”ҹеҚ’е№ҙжңҲгҖҒе®Ұжёёз»ҸеҺҶгҖҒеёҲжүҝгҖҒејҹеӯҗзӯүпјҢеҲ°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ёҖд№Ұзҡ„дҪңиҖ…гҖҒзј–жҺ’йЎәеәҸпјҢеҶҚеҲ°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д№ҰдёӯдәәгҖҒдәӢгҖҒж—¶гҖҒең°гҖҒе…ёз« еҲ¶еәҰзҡ„иҖғиҜҒпјҢж— дёҚж¶үзҢҺпјӣеҸҰеӨ–пјҢиҝҳеҮәзҺ°дәҶ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ҫ‘дҪҡзұ»и‘—дҪңе’ҢеҜ№еүҚд»Ј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и‘—дҪңзҡ„иЎҘжӯЈзұ»и‘—дҪңпјҢеҸҜи°“ејӮеҪ©зә·е‘ҲпјҢиҖғиҜҒз»ҶеҜҶпјҢе№ҝеҫҒеҚҡеј•пјҢеҰӮз„ҰеҫӘ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жӯЈд№үгҖӢе…ұеј•еҗ„зұ»д№ҰзұҚ826з§Қ10796ж¬ЎпјҢеҫҒеј•и‘—дҪңзұ»еһӢж— жүҖдёҚеҢ…пјҢеҚҒдёүз»ҸгҖҒе®ҳдҝ®еҸІд№ҰдёҖеә”дҝұе…ЁпјҢиҜёеӯҗи‘—дҪңдәҰеҮ д№Һе…ЁйғЁеӣҠжӢ¬пјҢдёӣд№ҰгҖҒзұ»д№Ұж— дёҖйҒ—жјҸпјҢеҚідҪҝдёҚеёёи§Ғзҡ„д№ҰзұҚпјҢд№ҹе°ҪйҮҸе…ЁйғЁж”¶йӣҶгҖӮиҝҷйғҪжҳҜжҳҺд»Ј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иҖғжҚ®еӯҰзҡ„延з»ӯдёҺж·ұе…ҘгҖӮжҳҺд»ЈеҗҺжңҹ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д№ӢжүҖд»ҘеҮәзҺ°иҝҷж ·зҡ„иҪ¬еҗ‘пјҢжҳҜеҪ“ж—¶зҡ„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иғҢжҷҜе’ҢеӯҰжңҜиҮӘиә«еҸ‘еұ•и§„еҫӢе…ұеҗҢдҪңз”Ё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е°ұеҪ“ж—¶зҡ„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иғҢжҷҜиҖҢиЁҖпјҢ15вҖ”16дё–зәӘпјҢиҘҝж–№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иҗҢиҠҪеҮәзҺ°пјҢдёәдәҶејҖжӢ“еёӮеңәпјҢиҘҝж–№жҺҖиө·дәҶең°зҗҶеӨ§еҸ‘зҺ°зҡ„зғӯжҪ®гҖӮиҘҝж–№дј ж•ҷеЈ«иҝӣе…ҘдёӯеӣҪпјҢд»ҘиҮӘ然科еӯҰжҠҖжңҜдҪңдёәдј ж•ҷзҡ„жүӢж®өпјҢе®ўи§ӮдёҠдҝғиҝӣдәҶжҷҡжҳҺеҜ№з§‘еӯҰжҠҖжңҜ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еӮ¬з”ҹдәҶд»Ҙз»Ҹдё–иҮҙз”Ёдёәж ёеҝғзҡ„е®һеӯҰжҖқжҪ®пјҢеҮәзҺ°дәҶиҜёеҰӮгҖҠеӨ©е·ҘејҖзү©гҖӢгҖҠеҶңж”ҝе…Ёд№ҰгҖӢгҖҠжң¬иҚүзәІзӣ®гҖӢзӯүиҮӘ然科еӯҰзҡ„е·Ёи‘—гҖӮеңЁзӨҫдјҡйўҶеҹҹпјҢеЈ«еӨ§еӨ«д»¬жҸҗеҖЎжұӮзңҹеҠЎе®һпјҢжІ»еӣҪжөҺж°‘пјҢеҸҚеҜ№з©әе№»иҷҡж— пјҢи°Ҳз©әиҜҙзҺ„гҖӮдёңжһ—еӯҰдәәеҸҚеҜ№вҖңдёҖеҝғеҸӘиҜ»еңЈиҙӨд№ҰвҖқпјҢдё»еј вҖң家дәӢеӣҪдәӢеӨ©дёӢдәӢдәӢдәӢе…іеҝғвҖқпјҢеҰӮйЎҫзӮҺжӯҰи®ӨдёәеҒҡеӯҰй—®зҡ„еҪ“еҠЎд№ӢжҖҘеңЁдәҺжҺўзҙўвҖңеӣҪ家治д№ұд№ӢжәҗгҖҒз”ҹж°‘ж №жң¬д№Ӣи®ЎвҖқгҖӮ然иҖҢпјҢ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еңЁ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еҚҙж—ҘзӣҠжөҒеҗ‘з©әиҷҡгҖӮйҳіжҳҺеҗҺеӯҰеҲҶеҢ–еҮәеӨҡдёӘеӯҰжҙҫпјҢе…¶дёӯеҪұе“ҚжңҖеӨ§зҡ„жҳҜжі°е·һеӯҰжҙҫгҖӮжі°е·һеӯҰжҙҫзҡ„еҲӣе§ӢдәәзҺӢиү®е°ҶеҝғеӯҰз®Җжҳ“еҢ–пјҢдё»еј вҖңзҷҫ姓ж—Ҙз”ЁеҚійҒ“вҖқпјҢеҚіеңЈдәәе’Ңзҷҫ姓йғҪеңЁ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дёӯи·өиЎҢйҒ“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еңЈдәәж„ҸиҜҶеҲ°йҒ“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зҷҫ姓没жңүж„ҸиҜҶеҲ°йҒ“зҡ„еӯҳеңЁиҖҢе·ІгҖӮзҺӢиү®еҝғеӯҰдёҚд»…еҗёеј•дәҶеӨ§жү№дёӢеұӮж°‘дј—пјҢиҖҢдё”иҝҺеҗҲдәҶеёӮеңәе’Ңе•ҶдёҡеҸ‘еұ•жүҖеј жү¬зҡ„дёӘдәәдё»д№үе’ҢиҮӘ然主д№үпјҢд»–зҡ„еҗҺеӯҰдҪ•еҝғйҡҗжҸҗеҮәвҖңжҖ§д№ҳж¬ІвҖқ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дё»еј еЈ°гҖҒиүІгҖҒжҖ§гҖҒе‘ігҖҒе®үйҖёйғҪжҳҜдәәжҖ§пјҢдәәжҖ§еӣ дәәзҡ„ж¬ІжңӣиҖҢиө·пјҢжҳҜеӨ©з„¶еҗҲзҗҶзҡ„пјҢиҝҷзӘҒз ҙдәҶзҗҶеӯҰеӨ©е‘Ҫд№ӢжҖ§дёәйҒ“еҫ·д№ӢжҖ§зҡ„з•ҢйҷҗпјҢд№ҹзӘҒз ҙдәҶзҺӢйҳіжҳҺиүҜзҹҘеҚіжҖ§зҡ„з•ҢйҷҗпјҢе°Ҷд№Ӣеј•еҗ‘зҺҮжҖ§иҖҢдёәгҖҒж”ҫиҚЎдёҚзҫҒгҖҒи”‘и§ҶзӨјжі•д№Ӣи·ҜгҖӮ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дё»еј йЎҝжӮҹпјҢжң¬жңүзҰ…еӯҰжҲҗеҲҶпјҢе…¶еҗҺдәәж··иҝ№дәҺеғ§йҒ“д№Ӣй—ҙпјҢе°Ҷд№ӢиҝӣдёҖжӯҘеҸ‘жҢҘгҖӮеңЁжі°е·һеӯҰжҙҫзҡ„еҪұе“ҚдёӢпјҢжҳҺжңқжң«е№ҙзҡ„еЈ«еӨ§еӨ«вҖңжөҒдәҺзҰ…иҖ…еҚҒд№қзҹЈвҖқпјҢеңЁзҰ…еӯҰзҡ„жҺ©зӣ–дёӢпјҢеј жү¬дёӘдәәдё»д№үпјҢвҖңжқҹд№ҰдёҚи§ӮвҖқвҖңз©әи°ҲеҝғжҖ§вҖқпјҢеңЁеӣҪ家е’Ңж°‘ж—ҸеҚұйҡҫд№Ӣйҷ…пјҢд»Қ然зҶҹи§Ҷж— зқ№пјҢй«ҳи°Ҳйҳ”и®әпјҢжҜ«дёҚдҪңдёәпјҢеҝғеӯҰжөҒејҠиҮіжӯӨиҖҢжһҒгҖӮзҺӢеӨ«д№ӢеҜ№д№Ӣз—ӣеҠ ж–ҘиҙЈпјҡзҺӢж°Ҹд№Ӣеҫ’вҖңеәҹе®һеӯҰпјҢеҙҮз©әз–ҸпјҢ蔑规зҹ©пјҢжҒЈзӢӮиҚЎпјҢд»Ҙж— е–„ж— жҒ¶е°Ҫеҝғж„ҸзҹҘд№Ӣз”ЁпјҢиҖҢи¶Ӣе…ҘдәҺж— еҝҢжғ®д№ӢеҹҹвҖқгҖӮйЎҫзӮҺжӯҰжӣҙжҳҜе°Ҷд№ӢдёҠеҚҮеҲ°жҳҺжңқзҒӯдәЎзҡ„еҺҹеӣ д№ӢдёҖпјҢи®ӨдёәжҳҺжң«зҡ„еҝғеӯҰз©әи°Ҳжңүз”ҡдәҺиҘҝжҷӢзҡ„жё…и°ҲпјҢиҘҝжҷӢзҡ„жё…и°ҲеҜјиҮҙвҖңдә”иғЎд№ұеҚҺвҖқпјҢиҖҢжҳҺжң«зҡ„жё…и°ҲдәҰеҜјиҮҙвҖңзҘһе·һиҚЎиҰҶпјҢе®—зӨҫдёҳеўҹ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д»–жҸҗеҖЎе®һеӯҰпјҢжҸҗеҮәвҖңзҗҶеӯҰпјҢз»ҸеӯҰд№ҹвҖқ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°Ҷз»ҸеӯҰи§Ҷдёәе„’еӯҰзҡ„жӯЈз»ҹпјҢи®ӨдёәеҗҺдё–зҡ„зҗҶеӯҰиҖ…дёҚй’»з ”дә”з»ҸпјҢиҖҢжІүиҝ·дәҺжүҖи°“зҗҶеӯҰ家зҡ„иҜӯеҪ•пјҢжң¬иҙЁдёҠжҳҜзҰ…еӯҰ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„’еӯҰпјҢ并жҸҗеҮәд»ҺйҹійҹөгҖҒж–Үеӯ—зҡ„и§’еәҰз ”з©¶з»Ҹд№ҰпјҢвҖңиҜ»д№қз»ҸиҮӘиҖғж–Үе§ӢпјҢиҖғж–ҮиҮӘзҹҘйҹіе§ӢвҖқпјҢејҖеҲӣдәҶжё…д»ЈиҖғжҚ®еӯҰзҡ„е…ҲжІігҖӮе°ұеӯҰжңҜиҮӘиә«еҸ‘еұ•и§„еҫӢиҖҢиЁҖпјҢзҗҶеӯҰеҝғеӯҰд№ӢдәүдҪҝеӯҰиҖ…们йҮҚеӣһз»Ҹе…ёгҖӮзҗҶеӯҰдёҺеҝғеӯҰиҮӘдәҢзЁӢж—¶дҫҝеҮәзҺ°еҲҶжӯ§пјҢеҚ—е®Ӣж—¶жңүжңұгҖҒйҷҶзҡ„й№…ж№–д№Ӣдјҡпјӣе…ғд»ЈпјҢзҗҶеӯҰдёҺеҝғеӯҰд№ӢдәүдәҰжңӘеҒңжӯўпјӣ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еҗҺпјҢеҝғеӯҰеҸ‘еұ•еҫ—и”ҡдёәеӨ§и§ӮпјҢеҸҢж–№еҗ„жү§дёҖиҜҚгҖҒдә’дёҚзӣёи®©гҖӮиҰҒ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и§ЈеҶізҗҶеӯҰе’ҢеҝғеӯҰд№Ӣдәү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еҝ…йЎ»йҮҚеӣһз»Ҹе…ёпјҢиҖғйҮҠз»Ҹе…ёеҺҹж„ҸпјҢдәҺжҳҜиҖғжҚ®еӯҰдҫҝиҜһз”ҹдәҶпјҢиҝҷжҳҜеӯҰжңҜеҸ‘еұ•еҶ…еңЁзҗҶи·Ҝзҡ„иҰҒжұӮгҖӮдҪҷиӢұж—¶е…Ҳз”ҹзҡ„гҖҠи®әжҲҙйңҮдёҺз« еӯҰиҜҡгҖӢдҫҝжҳҜдёәдәҶеӣһзӯ”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иҖҢдҪң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ҺҹжқҘзЁӢгҖҒжңұдёҺйҷҶгҖҒзҺӢд№Ӣй—ҙеңЁеҪўиҖҢдёҠеұӮйқўзҡ„дәүи®әпјҢиҮіжӯӨе·Іеұұз©·ж°ҙе°ҪпјҢдёҚиғҪдёҚеӣһеҗ‘еҸҢж–№йғҪжҚ®д»Ҙз«ӢиҜҙзҡ„еҺҹе§Ӣз»Ҹе…ёгҖӮжҲ‘з”ұжӯӨиҖҢжғіеҲ°пјҡдёәд»Җд№ҲзҺӢйҳіжҳҺпјҲ1427вҖ”1529пјүдёәдәҶе’ҢжңұзҶ№дәүи®әвҖҳж јзү©вҖҷгҖҒвҖҳиҮҙзҹҘвҖҷ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ңҖеҗҺеҝ…йЎ»иҜүиҜёгҖҠеӨ§еӯҰеҸӨжң¬гҖӢпјҢиёҸиҝӣдәҶж–Үжң¬иҖғи®ўзҡ„йўҶеҹҹгҖӮвҖқвҖңиҝҷеІӮдёҚиҜҙжҳҺпјҡд»ҺзҗҶеӯҰиҪ¬е…Ҙз»Ҹе…ёиҖғиҜҒжҳҜ16гҖҒ17дё–зәӘе„’еӯҰеҶ…йғЁзҡ„е…ұеҗҢиҰҒжұӮеҗ—пјҹвҖқ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з»“ иҜӯ 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жҳҜеӣӣд№Ұз»ҸеӯҰзҡ„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д№ҹжҳҜж–ҮеҢ–зҡ„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е®ғзҡ„еҸ‘еұ•еҸҳеҢ–еҸ—еҲ°ж–ҮеҢ–еӨ§зҺҜеўғ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д№ҹеҸ—еҲ°еӯҰжңҜеҸ‘еұ•еҶ…еңЁи§„еҫӢзҡ„ж”Ҝй…ҚпјҢеҗҢж—¶дәҰеҪұе“ҚзқҖж–ҮеҢ–зҺҜеўғзҡ„еҸ‘еұ•еҸҳеҢ–пјҢдәҢиҖ…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гҖҒзӣёдә’дҝғиҝӣпјҢеҪўжҲҗеӯҰжңҜдёҺж–ҮеҢ–зҡ„дәӨз»Үдә’еҠЁгҖӮе…ғеҸҠжҳҺеҲқпјҢеӣҪ家еҠ ејәеҲ¶еәҰе»әи®ҫпјҢжҸҗеҖЎ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пјҢе°Ҷд№ӢдҪңдёә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жӯӨж—¶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еҸӘиғҪ收ж•ӣжҖқжғізҡ„зҝ…иҶҖпјҢдёҚж•ўдәҰдёҚиғҪи¶ҠеҮәзҗҶеӯҰзҡ„иҢғз•ҙпјӣдҪҶеңЁеӯҰжңҜиҝҪжұӮдёҠпјҢеӯҰиҖ…们иҝҳ延з»ӯзқҖе®Ӣд»ЈйҮҚи§Ҷд№үзҗҶйҳҗеҸ‘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жүҖд»ҘиҜҘ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е‘ҲзҺ°еҮәзҗҶеӯҰжЎҶжһ¶дёӢзҡ„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зҡ„ж—¶д»Јзү№зӮ№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еҝғеӯҰдҪңдёәдёҖиӮЎжҪңжөҒе§Ӣз»ҲеӯҳеңЁпјҢ并дёҚж–ӯдё°еҜҢеҸ‘еұ•пјҢзӣҙеҲ°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еҪўжҲҗ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пјҢе°Ҷеӯҹеӯҗзҡ„иүҜзҹҘзҗҶи®әжҺЁеҗ‘ж–°зҡ„йҳ¶ж®өпјҢе®һзҺ°дәҶ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еҸ‘еұ•пјҢ并еңЁзӨҫдјҡдёҠе№ҝжіӣжөҒдј пјҢејәзғҲеҶІеҮ»зқҖ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гҖӮ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еҝғеӯҰеӯҰиҖ…们дёҚжҮҲеҠӘеҠӣ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жҳҺд»ЈдёӯжңҹзӨҫдјҡж–ҮеҢ–зҺҜеўғеҸ‘з”ҹ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дёәе…¶жҸҗдҫӣдәҶж—¶д»Јзҡ„еңҹеЈӨгҖӮжҳҺдёӯжңҹд№ӢеҗҺпјҢзҺӢзәІеәҹејӣпјҢ秩еәҸж¶Јж•ЈпјҢдёәдәә们иҮӘз”ұең°жҖқжғіжҸҗдҫӣдәҶе№ҝйҳ”зҡ„з©әй—ҙпјӣе•Ҷе“Ғз»ҸжөҺиҝ…йҖҹеҸ‘еұ•пјҢе•ҶдёҡеёҰжқҘзҡ„е·ЁеӨ§еҲ©ж¶Ұж”№еҸҳдәҶдәә们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пјҢйҮҚе•Ҷд№ӢйЈҺзӣӣиЎҢпјҢдәә们дёҚеҶҚеҺӢжҠ‘иҮӘе·ұзү©иҙЁгҖҒжғ…ж¬Ідә«еҸ—зҡ„ж¬ІжңӣпјҢз”ҹжҙ»еҘўйқЎгҖҒиҝқзӨјйҖҫеҲ¶жҲҗдёәзӨҫдјҡж–°йЈҺе°ҡгҖӮзғҰзҗҗеғөеҢ–зҡ„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ж—ҘзӣҠжҲҗдёәдәә们жҖқжғідёҠе’ҢиЎҢдёәдёҠзҡ„жқҹзјҡпјҢйҒӯеҲ°жҲ–жҳҺжҲ–жҡ—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ӣиҖҢдё»еј еҝғеӨ–ж— зү©гҖҒе°ҠйҮҚдәәеҝғпјҢжҸҗеҖЎиҮҙзҹҘгҖҒйЎҝжӮҹзӯүз®ҖзәҰдҝ®иЎҢж–№ејҸзҡ„еҝғеӯҰеҲҷжӣҙеҠ з¬ҰеҗҲдәә们зҡ„йңҖжұӮгҖӮйҳіжҳҺеҝғеӯҰйҮҚи§Ҷдәәзҡ„дё»и§ӮиғҪеҠЁжҖ§пјҢеҸҚиҝҮжқҘеҸҲиҝӣдёҖжӯҘдҝғиҝӣдәҶдәә们зҡ„жҖқжғіи§Јж”ҫдёҺиҮӘжҲ‘ж„ҸиҜҶзҡ„и§үйҶ’пјҢдҪҝиҜҘж—¶жңҹзҡ„ж–ҮеҢ–еҜҢжңүдёӘдәәдё»д№үе’ҢиҮӘ然主д№үиүІеҪ©гҖӮ然иҖҢпјҢйҳіжҳҺеҗҺеӯҰиҝҮеәҰејәи°ғдәәзҡ„еЈ°иүІжҖ§е‘ізӯүж¬ІжңӣпјҢйҖҗжёҗжөҒдәҺз©әиҷҡпјҢиө°еҲ°дәҶзҗҶеӯҰзҡ„еҸҚйқўгҖӮжҳҺд»ЈеҗҺжңҹпјҢе®һеӯҰжҖқжҪ®е…ҙиө·пјҢе®һеӯҰеҸҚеҜ№еҝғеӯҰзҡ„з©әи°ҲпјҢдё»еј еӣһеҪ’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пјҢеӣһеҪ’ж јзү©иҮҙзҹҘзҡ„и®ӨиҜҶж–№ејҸпјҢеҝғеӯҰдёҺзҗҶеӯҰзҡ„еӯҰжңҜд№Ӣдәүд№ҹдҪҝеӯҰиҖ…们йҮҚж–°е®Ўи§ҶеҜ№е…ғе…ёзҡ„и§ЈйҮҠпј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ж–ҮеҢ–жҪ®жөҒе’ҢеӯҰжңҜи¶ӢеҠҝдёӯж—ҘзӣҠиө°еҗ‘иҖғжҚ®гҖӮе…ғжҳҺж—¶жңҹзҡ„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з ”з©¶дёҠжүҝе®ӢеӯҰпјҢдёӢеҗҜжё…еӯҰпјҢжҳҜдәҢиҖ…д№Ӣй—ҙиҮӘ然зҡ„гҖҒдёҚеҸҜжҲ–зјәзҡ„иҝҮжёЎйҳ¶ж®өгҖӮ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зј–иҫ‘пјҡзҺӢиҪІ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3жңҹвҖңеҺҶеҸІдёҺж–ҮеҢ–вҖқж Ҹзӣ®вҖңжҳҺд»Јж–ҮеҢ–вҖқдё“йўҳ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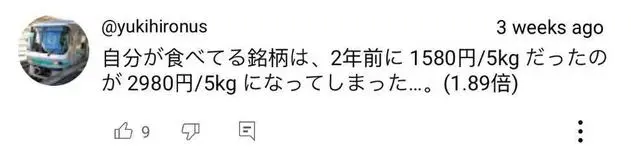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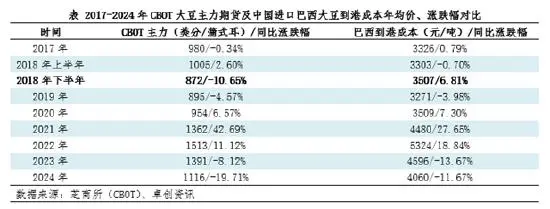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