ه”هگو—¢وک¯ه„’ه¦هˆ›ه§‹ن؛؛,ن¹ںوک¯ن¼ ç»ںو–‡هŒ–çڑ„继و‰؟者,è؟™é‡Œو‰€è¯´çڑ„“ن¼ ç»ںو–‡هŒ–â€وŒ‡çڑ„وک¯ه”هگ视角ن¸‹çڑ„ه¤ڈه•†ه‘¨ن¸‰ن»£ç¤¼ن¹گو–‡وکژم€‚ه”هگوٹٹه¤ڈه•†ه‘¨ن¸‰ن»£ç¤¼ن¹گو–‡وکژو‰€è•´هگ«çڑ„éپ“ه¾·ه…ƒç´ çھپوک¾ه‡؛و¥ï¼Œه¼€هˆ›ن؛†ه„’ه®¶ه¦و´¾م€‚هœ¨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ن¸ï¼Œوœ‰و²،وœ‰éپ“ه¾·وک¯ن؛؛ن¸ژ禽ه…½çڑ„و ¹وœ¬هŒ؛هˆ«ï¼Œéپ“ه¾·è·µه±¥و°´ه¹³çڑ„é«کن½ژوک¯هگ›هگن¸ژه°ڈن؛؛çڑ„هˆ†و°´ه²م€‚هںهگ说“ن؛؛ن¹‹و‰€ن»¥ه¼‚ن؛ژ禽ه…½è€…ه‡ ه¸Œ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ç¦»ه¨„ن¸‹م€‹ï¼‰ï¼Œن؛؛ن¸ژ禽ه…½çڑ„ه·®هˆ«ن»…“ه‡ ه¸Œâ€م€‚ه…³ن؛ژè؟™â€œه‡ ه¸Œâ€ï¼Œèچ€هگçڑ„看و³•وک¯ï¼ڑ“و°´çپ«وœ‰و°”而و— ç”ں,èچ‰وœ¨وœ‰ç”ں而و— çں¥ï¼Œç¦½ه…½وœ‰çں¥è€Œو— ن¹‰ï¼Œن؛؛وœ‰و°”م€پوœ‰ç”ںم€پوœ‰çں¥م€پن؛¦ن¸”وœ‰ن¹‰ï¼Œو•…وœ€ن¸؛ه¤©ن¸‹è´µن¹ں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چ€هگآ·çژ‹هˆ¶م€‹ï¼‰ن؛؛ن¸ژ禽ه…½ç›¸و¯”ن¹ںو— éه°±وک¯ه¤ڑن؛†ن¸€ن¸ھ“ن¹‰â€ï¼Œو‰€è°““ن¹‰â€ه°±وک¯çں¥éپ“è‡ھه·±è¯¥ه¹²ن»€ن¹ˆم€پن¸چ该ه¹²ن»€ن¹ˆï¼Œه±ن؛ژéپ“ه¾·è§‚ه؟µèŒƒç•´م€‚و£ه› ن¸؛ه„’ه®¶وٹٹن؛؛看ن½œوک¯éپ“ه¾·و€§çڑ„هکهœ¨ï¼Œو‰€ن»¥ن»–ن»¬ن¸»ه¼ “ن»¥ه¾·ن؟®è؛«â€م€‚
ه„’ه®¶ه¯¹éپ“ه¾·ن؟®ه…»ه¾ˆوœ‰ن؟،ه؟ƒï¼Œهœ¨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è§†é‡ژن¸ï¼Œéپ“ه¾·ن؟®ه…»è؟™ن»¶ن؛‹وƒ…ه®Œه…¨هڈ–ه†³ن؛ژن¸ھن½“çڑ„选و‹©ï¼Œم€ٹهںهگآ·ه‘ٹهگن¸‹م€‹وœ‰ن؛‘ï¼ڑ“هگوœچه°§ن¹‹وœچ,诵ه°§ن¹‹è¨€ï¼Œè،Œه°§ن¹‹è،Œï¼Œوک¯ه°§è€Œه·²çں£م€‚هگوœچو،€ن¹‹وœچ,诵و،€ن¹‹è¨€ï¼Œè،Œو،€ن¹‹è،Œï¼Œوک¯و،€è€Œه·²çں£م€‚â€ن¹ںو£وک¯هœ¨è؟™ن¸ھو„ڈن¹‰ن¸ٹ,ه„’ه®¶وڈگه‡؛ن؛†â€œن¸؛ن»پç”±ه·±â€â€œن؛؛çڑ†هڈ¯ن»¥ن¸؛ه°§èˆœâ€çڑ„观点م€‚虽然وڈگه‡؛ن؛†â€œن؛؛çڑ†هڈ¯ن»¥ن¸؛ه°§èˆœâ€çڑ„观点,ن½†è؟™ن¹ںهڈھوک¯é¢„ç¤؛ç€ن؛؛وڈگهچ‡éپ“ه¾·ه¢ƒç•Œçڑ„هڈ¯èƒ½و€§ï¼Œè‹¥è¦پوٹٹهڈ¯èƒ½و€§هڈکوˆگçژ°ه®و€§ï¼Œè؟ک需è¦پو‰ژو‰ژه®ه®çڑ„هٹھهٹ›م€‚ن¸؛و¤ï¼Œه„’ه®¶ه»؛و„ن؛†ن¸€ه¥—细致م€پç³»ç»ںçڑ„éپ“ه¾·ن؟®ه…»و–¹و³•م€‚هœ¨è؟™é‡Œï¼Œوˆ‘ن»ژن¸و‹©هڈ–ن¸€ن؛›ن»چوœ‰è¾ƒه¼؛çژ°ه®و„ڈن¹‰çڑ„è¦پ点ن¸؛ه¤§ه®¶ن½œن¸€ç•ھ讲解م€‚
و³¨é‡چو€è€ƒه’Œهڈچو€
هگو›°ï¼ڑ“ن¸چو›°â€که¦‚ن¹‹ن½•ï¼Œه¦‚ن¹‹ن½•â€™è€…,هگ¾وœ«ه¦‚ن¹‹ن½•ن¹ںه·²çں£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چ«çپµه…¬م€‹ï¼‰ه”هگ说,ن¸€ن¸ھن؛؛ه¦‚وœن¸چçں¥éپ“ç»ڈه¸¸é—®é—®è‡ھه·±â€œè¯¥و€ژن¹ˆهٹه•ٹ,该و€ژن¹ˆهٹه•ٹâ€ï¼Œن»–ن¹ںن¸چçں¥éپ“该و‹؟è؟™و ·çڑ„ن؛؛“و€ژن¹ˆهٹâ€ن؛†م€‚ه› ن¸؛,ن¸€ن¸ھن؛؛能ه¤ںé—®ه‡؛“ه¦‚ن¹‹ن½•ï¼Œه¦‚ن¹‹ن½•â€ï¼Œهچ³è¯´وکژن»–ه¯¹è‡ھè؛«وک¯وœ‰هڈچو€çڑ„,ن»–هœ¨è°‹و±‚çھپç ´ه’Œو”¹هڈک,而è؟™و£وک¯ن¸€ن¸ھن؛؛وˆگé•؟è؟›و¥çڑ„هٹ¨هٹ›م€‚هڈچن¹‹ï¼Œه¦‚وœن¸€ن¸ھن؛؛é—®ن¸چه‡؛“ه¦‚ن¹‹ن½•â€ï¼Œهˆ™è¯´وکژن»–ç¼؛ن¹ڈè؟™ç§چè‡ھوˆ‘وˆگé•؟çڑ„هٹ¨هٹ›ï¼Œè€Œه¯¹ن؛ژç¼؛ن¹ڈè‡ھوˆ‘وˆگé•؟هٹ¨هٹ›çڑ„ن؛؛,ه”هگن¹ںن¸چçں¥éپ“该و€ژو ·هژ»ه¼•ه¯¼و•™è‚²ن»–ن؛†م€‚
هœ¨ه„’ه®¶çœ‹و¥ï¼Œو€è€ƒه’Œهڈچو€وک¯وڈگهچ‡éپ“ه¾·ن؟®ه…»ه’Œç²¾ç¥ه¢ƒç•Œçڑ„é‡چè¦پو–¹ه¼ڈ,那ن¹ˆï¼Œه…·ن½“ه؛”该ه¾€ه“ھن؛›و–¹هگ‘هژ»و€è€ƒه’Œهڈچو€ه‘¢ï¼ں
هœ¨م€ٹè®؛è¯م€‹ن¸ï¼Œو›¾هگه’Œه”هگ都هپڑن؛†وڈگç¤؛م€‚و›¾هگوڈگهˆ°ن؛†â€œن¸‰çœپâ€ï¼ڑ“هگ¾و—¥ن¸‰çœپهگ¾è؛«â€”—ن¸؛ن؛؛谋而ن¸چه؟ ن¹ژï¼ںن¸ژوœ‹هڈ‹ن؛¤è€Œن¸چن؟،ن¹ژï¼ںن¼ ن¸چن¹ ن¹ژï¼ں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¦è€Œم€‹ï¼‰â€œن¸‰çœپâ€و„ڈن¸؛ه¤ڑو¬،çœپه¯ں,و›¾هگه¤ڑو¬،çœپه¯ںçڑ„ه†…ه®¹وک¯ï¼ڑن¸؛هˆ«ن؛؛هپڑن؛‹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وœ‰و²،وœ‰هپڑهˆ°ه°½ه؟ƒه°½هٹ›ï¼ںن¸ژوœ‹هڈ‹ن؛¤ه¾€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وœ‰و²،وœ‰هپڑهˆ°è¯ڑه®ه®ˆن؟،ï¼ںè€په¸ˆو•™çڑ„ن¸؛ن؛؛ه¤„ن¸–çڑ„éپ“çگ†ï¼Œè‡ھه·±وœ‰و²،وœ‰هژ»â€œن¹ â€ï¼ںè؟™é‡Œçڑ„“ن¹ â€وŒ‡çڑ„ن¸چوک¯ç®€هچ•çڑ„ه¤چن¹ ,而وک¯وŒ‡ه®ن¹ م€پ练ن¹ م€پو¼”ن¹ ,هچ³èگ½ه®هˆ°ه®è·µن¸هژ»م€‚ه”هگهˆ™è®²هˆ°ن؛†â€œن¹و€â€ï¼ڑ“هگ›هگوœ‰ن¹و€ï¼ڑ视و€وکژ,هگ¬و€èپھ,色و€و¸©ï¼Œè²Œو€وپ,言و€ه؟ ,ن؛‹و€و•¬ï¼Œç–‘و€é—®ï¼Œه؟؟و€éڑ¾ï¼Œè§په¾—و€ن¹‰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£و°ڈم€‹ï¼‰çœ‹ن¸œè¥؟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وƒ³وƒ³è‡ھه·±وک¯هگ¦çœ‹و¸…و¥ڑن؛†ï¼›هگ¬é—®é¢ک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问问è‡ھه·±وک¯هگ¦هگ¬وکژ白ن؛†ï¼›ه¾…ن؛؛وژ¥ç‰©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هڈچçœپè‡ھه·±وœ‰و²،وœ‰هپڑهˆ°ç¥è‰²و¸©ه’Œم€په®¹è²Œوپو•¬ï¼›è¯´è¯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وƒ³وƒ³è‡ھه·±و‰€è¯´çڑ„è¯وک¯هگ¦ç،®ه®هڈ¯é ï¼›هپڑن؛‹وƒ…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问问è‡ھه·±وک¯هگ¦هپڑهˆ°ن؛†ن¸¥è‚ƒè®¤çœں;碰هˆ°ç–‘é—®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هڈچو€è‡ھه·±وœ‰و²،وœ‰هژ»ه¯»و±‚çœںçگ†ï¼›هڈ‘و€’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考虑هگژوœï¼›ه¾—هˆ°ه¥½ه¤„çڑ„و—¶ه€™ï¼Œè¦پهڈچçœپè‡ھه·±وک¯هگ¦è¯¥ه¾—م€‚
ن؛؛هœ¨و€è€ƒه’Œهڈچو€çڑ„è؟‡ç¨‹ن¸ï¼Œه¾ˆهڈ¯èƒ½ن¼ڑهڈ‘çژ°è‡ھه·±وœ‰هپڑé”™çڑ„هœ°و–¹م€‚و¯•ç«ںوˆ‘ن»¬و¯ڈن¸ھن؛؛都هکهœ¨ه±€é™گ,ن¾‹ه¦‚هژںç”ںه®¶ه؛çڑ„ه±€é™گم€پوˆگé•؟ç»ڈهژ†çڑ„ه±€é™گم€پçں¥è¯†ç»“و„çڑ„ه±€é™گم€پو€§و ¼è„¾و°”çڑ„ه±€é™گç‰م€‚وˆ‘ن»¬ه¸¦ç€è؟™ن؛›ه±€é™گهژ»وƒ³é—®é¢کم€پهپڑن؛‹وƒ…,وœ€هگژه‡؛çژ°è؟‡ه¤±ن¹ںن¸چ足ن¸؛ه¥‡ï¼Œو‰€ن»¥و‰چوœ‰ن؛†â€œن؛؛éهœ£è´¤ï¼Œه°èƒ½و— è؟‡â€è؟™و ·çڑ„说و³•م€‚هپڑé”™ن؛†ه¾ˆو£ه¸¸ï¼Œçں¥éپ“هڈٹو—¶و”¹و£ه°±هڈ¯ن»¥ن؛†ï¼Œو£ه¦‚ه”هگو‰€è¨€ï¼Œâ€œè؟‡ï¼Œهˆ™ه‹؟وƒ®و”¹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¦è€Œم€‹ï¼‰ï¼Œâ€œè؟‡è€Œن¸چو”¹ï¼Œوک¯è°“è؟‡çں£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چ«çپµه…¬م€‹ï¼‰ï¼Œçں¥éپ“è‡ھه·±هپڑé”™ن؛†هچ´ن¸چو”¹و£ï¼Œو‰چوک¯çœںو£çڑ„è؟‡é”™م€‚
و—¢ç„¶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و³¨é‡چو€è€ƒه’Œهڈچو€ï¼Œé‚£ن¹ˆï¼Œوˆ‘ن»¬و—¥ه¸¸ç”ںو´»ن¸ه¸¸è®²çڑ„“ن¸‰و€è€Œهگژè،Œâ€ï¼Œه„’ه®¶وک¯هگ¦è®¤هڈ¯ه‘¢ï¼ںهڈ¯èƒ½وœ‰ن؛؛ن¼ڑç»™ه‡؛肯ه®ڑçڑ„ه›ç”,ن½†ه®é™…ن¸ٹ,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ه¯¹و¤وک¯وŒپهڈچه¯¹و€په؛¦çڑ„م€‚وچ®م€ٹè®؛è¯آ·ه…¬ه†¶é•؟م€‹è®°è½½ï¼Œه£و–‡هگè؟™ن¸ھن؛؛“ن¸‰و€è€Œهگژè،Œâ€ï¼Œه”هگهگ¬è¯´ه£و–‡هگçڑ„è،Œن؛‹é£ژو ¼ن¹‹هگژ,点评ن؛†ن¸€هڈ¥ï¼ڑ“ه†چ,و–¯هڈ¯çں£م€‚â€è؟™هڈ¥è¯çڑ„و„ڈو€وک¯ï¼Œن¸؛ن»€ن¹ˆè¦پوƒ³é‚£ن¹ˆه¤ڑه‘¢ï¼Œوƒ³ن¸¤و¬،ه°±هڈ¯ن»¥ن؛†م€‚ه”هگن¹‹و‰€ن»¥هڈچه¯¹â€œن¸‰و€è€Œهگژè،Œâ€ï¼Œوک¯ه› ن¸؛“ن¸‰و€è€Œهگژè،Œâ€è‡³ه°‘ن¼ڑن؛§ç”ںن¸¤و–¹é¢çڑ„é—®é¢کï¼ڑن¸€و–¹é¢ï¼Œه¦‚وœه¯¹è؟‡هژ»çڑ„ن؛‹وƒ…و€è™‘è؟‡ه¤ڑ,那ن¹ˆن¾؟ه®¹وک“ه›°ن؛ژè؟‡هژ»è€Œéڑ¾ن»¥è‡ھو‹”,ه¯¼è‡´و— و³•ه¼€ه±•و–°çڑ„ç”ںو´»وˆ–ن؛‹ن¸ڑï¼›هڈ¦ن¸€و–¹é¢ï¼Œه¦‚وœه¯¹هچ³ه°†è¦پهپڑçڑ„ن؛‹وƒ…و€è™‘è؟‡ه¤ڑ,那ن¹ˆن¾؟ه®¹وک“é€ وˆگè،Œهٹ¨ن¸ٹçڑ„ن¼کوں”ه¯،و–م€‚
و³¨é‡چçژ¯ه¢ƒçڑ„ه½±ه“چ
م€ٹهںهگآ·و»•و–‡ه…¬ن¸‹م€‹è®°è½½ن؛†هںهگه’Œوˆ´ن¸چ胜ن¹‹é—´çڑ„ن¸€و®µه¯¹è¯م€‚هںهگé—®وˆ´ن¸چ胜ï¼ڑو¥ڑه›½وœ‰ن¸€ن¸ھه¤§ه¤«ï¼Œوƒ³و•™è‡ھه·±çڑ„ه©هگ说é½گه›½è¯ï¼Œن»–ه؛”该هژ»و‰¾ن¸€ن½چé½گه›½ن؛؛و¥و•™ه‘¢ï¼Œè؟کوک¯هژ»و‰¾ن¸€ن½چو¥ڑه›½ن؛؛و¥و•™ï¼ںوˆ´ن¸چ胜ه›ç”说,ه½“然وک¯و‰¾ن¸€ن½چé½گه›½ن؛؛و¥و•™م€‚هںهگوژ¥ن¸‹و¥è¯´â€œن¸€é½گن؛؛ه‚…ن¹‹ï¼Œن¼—و¥ڑن؛؛ه’»ن¹‹â€ï¼Œن¸€ن¸ھé½گه›½ن؛؛هœ¨é‚£é‡Œو•™è؟™ن¸ھه°ڈه©è¯´é½گه›½è¯ï¼Œن¸€ç¾¤و¥ڑه›½ن؛؛هœ¨و—پ边起ه“„,“虽و—¥وŒè€Œو±‚ه…¶é½گن¹ں,ن¸چهڈ¯ه¾—çں£â€ï¼Œهچ³ن½؟و¯ڈه¤©è´£و‰“è؟™ن¸ھه°ڈه©و•¦ن؟ƒن»–说é½گه›½è¯ï¼Œن»–ن¹ںوک¯ه¦ن¸چن¼ڑçڑ„ï¼›هڈچن¹‹ï¼Œâ€œه¼•è€Œç½®ن¹‹ه؛„ه²³ن¹‹é—²و•°ه¹´â€ï¼Œه؛„م€په²³وŒ‡çڑ„وک¯ه½“و—¶é½گه›½éƒ½هںژن¸´و·„ن¸¤و،وœ€ç¹په؟™çڑ„è،—éپ“——ه؛„è،—ه’Œه²³é‡Œï¼Œه¦‚وœوٹٹè؟™ن¸ھه°ڈه©ه¸¦هژ»ه؛„è،—ه’Œه²³é‡Œه¾…ن¸ٹه‡ ه¹´ï¼Œâ€œè™½و—¥وŒè€Œو±‚ه…¶و¥ڑ,ن؛¦ن¸چهڈ¯ه¾—çں£â€ï¼Œهچ³ن¾؟و¯ڈه¤©هژ»è´£و‰“è؟™ن¸ھه°ڈه©é€¼ن»–ه†چ说ه›و¥ڑه›½è¯ï¼Œن¹ںوک¯و— و³•هپڑهˆ°ن؛†م€‚هںهگن»¥و¤و•…ن؛‹ï¼Œéکگè؟°ن؛†ه„’ه¦è§†é‡ژن¸‹çژ¯ه¢ƒه¯¹ن؛؛ç”ںوˆگé•؟çڑ„و„ڈن¹‰م€‚
ه…³ن؛ژçژ¯ه¢ƒçڑ„é‡چè¦پو€§ï¼Œم€ٹèچ€هگآ·هٹه¦م€‹ن¹ںن¸¾ن؛†ن¸€ç³»هˆ—ن¾‹هگن؛ˆن»¥è¯´وکژï¼ڑهچ—و–¹وœ‰ن¸€ç§چهگچن¸؛è’™é¸ çڑ„é¸ں,è؟™ç§چé¸ں用è‡ھه·±çڑ„ç¾½و¯›هپڑه·¢م€پ用è‡ھه·±çڑ„هڈ‘ن¸وٹٹه·¢و‹´èµ·و¥ï¼Œه¹¶â€œç³»ن¹‹è‹‡è‹•â€ï¼Œç»“وœâ€œé£ژ至苕وٹک,هچµç ´هگو»â€ï¼Œن¹‹و‰€ن»¥ه‡؛çژ°è؟™ç§چو‚²وƒ¨çڑ„结ه±€ï¼Œه¹¶éه› ن¸؛é¸ںه·¢ن¸چهڑه›؛,而وک¯ه› ن¸؛وٹٹé¸ںه·¢ç³»é”™ن؛†هœ°و–¹ï¼›è¥؟و–¹وœ‰ن¸€ç§چهگچن¸؛“ه°„ه¹²â€çڑ„و ‘,è؟™ç§چو ‘و‰چه››ه¯¸é•؟,ن½†وک¯ه› ن¸؛“ç”ںن؛ژé«که±±ن¹‹ن¸ٹâ€ï¼Œن¹ںèژ·ه¾—ن؛†â€œن¸´ç™¾ن»ن¹‹و¸ٹâ€çڑ„视é‡ژ,è؟™ن¸چوک¯ه› ن¸؛ه®ƒوœ¬è؛«é•؟ه¾—é«ک,而وک¯ه› ن¸؛ه®ƒç”ںé•؟ه¯¹ن؛†هœ°و–¹ï¼›ه…°و§گçڑ„و ¹وœ¬و¥وک¯هڈ¯ن»¥هپڑ香و–™çڑ„,ن½†وک¯ه¦‚وœوٹٹه®ƒو³،ه…¥و±،وµٹçڑ„و¶²ن½“ن¸ï¼Œه¤§ه®¶ن¹ں都ن¼ڑ离ه®ƒè؟œè؟œçڑ„,“هگ›هگن¸چè؟‘,ه؛¶ن؛؛ن¸چوœچâ€ï¼Œè؟™ه¹¶éه› ن¸؛ه…°و§گçڑ„و ¹هڈکè´¨هڈ‘è‡ï¼Œè€Œوک¯ه› ن¸؛ه‘¨ه›´çڑ„çژ¯ه¢ƒو±،وں“ن؛†ه®ƒم€‚é€ڑè؟‡è؟™ن؛›ن¾‹هگ,èچ€هگç»™ه‡؛ن؛†ن¸€ن¸ھه؟ ه‘ٹï¼ڑ“هگ›هگه±…ه؟…و‹©ن¹،,و¸¸ه؟…ه°±ه£«ï¼Œو‰€ن»¥éک²é‚ھè¾ں而è؟‘ن¸و£ن¹ںم€‚â€هگ›هگن»¥هڈٹوœ‰ه؟—ن؛ژوˆگن¸؛هگ›هگçڑ„ن؛؛,ه؛”该ه¾…هœ¨è‡ھه·±è¯¥ه¾…çڑ„هœ°و–¹ï¼Œç»“ن؛¤ه€¼ه¾—结ن؛¤çڑ„ن؛؛,è؟™و ·و‰چهڈ¯ن»¥ç¦»ن¸و£ن¹‹éپ“و›´è؟‘ن¸€ن؛›م€‚
çں¥è،Œهگˆن¸€
م€ٹè®؛è¯م€‹ه¼€ç¯‡هچ³è®²â€œه¦è€Œو—¶ن¹ ن¹‹â€ï¼Œâ€œه¦â€وک¯èژ·ه¾—“çں¥â€çڑ„é‡چè¦پ途ه¾„م€‚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çœ‹é‡چه¦ن¹ هٹ¨وœ؛,ه¹¶و ¹وچ®ه¦ن¹ هٹ¨وœ؛çڑ„ن¸چهگŒï¼Œه°†â€œه¦â€هˆ†ن¸؛ن¸¤ç§چï¼ڑ“هگ›هگن¹‹ه¦â€ه’Œâ€œه°ڈن؛؛ن¹‹ه¦â€م€‚
ه…³ن؛ژن؛Œè€…ن¹‹é—´çڑ„هŒ؛هˆ«ï¼Œم€ٹèچ€هگآ·هٹه¦م€‹ن½œن؛†ç•Œه®ڑï¼ڑ“هگ›هگن¹‹ه¦ن¹ں,ه…¥ن¹ژ耳,箸ن¹ژه؟ƒï¼Œه¸ƒن¹ژه››ن½“,ه½¢ن¹ژهٹ¨é™م€‚â€â€œهگ›هگن¹‹ه¦â€وŒ‡çڑ„وک¯ن؛؛用耳وœµهگ¬هˆ°هگژ,ه؟ƒن¸ٹه°±وک¾çژ°ه‡؛و¥ï¼Œç„¶هگژه°±ن»ژن؛؛çڑ„ن¸€è¨€ن¸€è،Œم€پن¸€ن¸¾ن¸€هٹ¨ن¸ن½“çژ°ه‡؛و¥ï¼›â€œه°ڈن؛؛ن¹‹ه¦ن¹ں,ه…¥ن¹ژ耳,ه‡؛ن¹ژهڈ£م€‚هڈ£è€³ن¹‹é—´هˆ™ه››ه¯¸è€³ï¼Œو›·è¶³ن»¥ç¾ژن¸ƒه°؛ن¹‹è؛¯ه“‰â€ï¼Œâ€œه°ڈن؛؛ن¹‹ه¦â€هˆ™وک¯وŒ‡ن؛؛用耳وœµهگ¬è§پن؛†م€پé€ڑè؟‡هڈ£ن¸هچ–ه¼„ه‡؛و¥ï¼Œç„¶è€Œï¼Œهڈ£è€³ن¹‹é—´هڈھوœ‰ه››ه¯¸é•؟,وŒ‡وœ›é€ڑè؟‡è؟™â€œه››ه¯¸é•؟â€è®©و•´ن½“ن؛؛و ¼ه¾—هˆ°وڈگهچ‡م€پç¾ژهŒ–,那وک¯ن¸چهڈ¯èƒ½çڑ„م€‚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ه€،ه¯¼â€œهگ›هگن¹‹ه¦â€ï¼Œهڈچه¯¹â€œه°ڈن؛؛ن¹‹ه¦â€م€‚ه„’ه®¶è®¤ن¸؛,ن¸€ن¸ھن؛؛é€ڑè؟‡ه¦ن¹ èژ·ه¾—çڑ„éپ“ه¾·çگ†ه؟µï¼Œه¦‚وœن¸چ能ه†…هŒ–ن؛ژه؟ƒن¸ه¹¶ه¤–هŒ–ن¸؛è،Œن¸؛,那ن¹ˆç؛µن½؟ن»–ه¦هˆ°çڑ„ن¸œè¥؟ه†چه¤ڑم€په¦ه¾—çڑ„ه†…ه®¹ه†چه¥½ï¼Œن¹ںوک¯و²،وœ‰و„ڈن¹‰çڑ„م€‚
ن»€ن¹ˆو—¶ه€™و‰چهڈ¯ن»¥ه°†ه¦ن¹ ه‘ٹن¸€و®µèگ½ه‘¢ï¼ںé‚£ه°±وک¯ه°†و‰€ه¦èگ½ه®هˆ°ه®è·µن¸هژ»ï¼Œهچ³â€œه¦è‡³ن؛ژè،Œن¹‹è€Œو¢çں£â€ï¼ˆم€ٹèچ€هگآ·ه„’و•ˆم€‹ï¼‰م€‚ه„’ه®¶ن¹‹و‰€ن»¥ه¼؛调“çں¥è،Œهگˆن¸€â€ï¼Œوک¯ه› ن¸؛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و•™ç»™ن؛؛çڑ„首è¦په†…ه®¹ه¹¶éن¹¦وœ¬ن¸ٹçڑ„çں¥è¯†ï¼Œè€Œوک¯هپڑن؛؛هپڑن؛‹çڑ„éپ“çگ†م€‚è؟™ن؛›هپڑن؛؛هپڑن؛‹çڑ„éپ“çگ†ï¼Œهڈھوœ‰é€ڑè؟‡èگ½ه®هˆ°ه®è·µن¸هژ»و‰چوœ‰و„ڈن¹‰م€‚و£ه¦‚ه®‹ن»£ه¤§ه„’程é¢گهœ¨ç‚¹è¯„ه¦‚ن½•è¯»م€ٹè®؛è¯م€‹و—¶و‰€è¨€ï¼ڑ“ه¦‚读م€ٹè®؛è¯م€‹ï¼Œوœھ读و—¶وک¯و¤ç‰ن؛؛,读ن؛†هگژهڈˆهڈھوک¯و¤ç‰ن؛؛,ن¾؟وک¯ن¸چو›¾è¯»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ه››ن¹¦ç« هڈ¥é›†و³¨م€‹ï¼‰
هœ¨çں›ç›¾ه†²çھپن¸ه½°وک¾éپ“ه¾·ه¢ƒç•Œ
ه¯¹ن؛ژه¤§ه¤ڑو•°ن؛؛و¥è¯´ï¼Œهœ¨و³¢و¾œن¸چوƒٹçڑ„و—¥ه¸¸ç”ںو´»ن¸è·µè،Œéپ“ه¾·è§„范وˆ–许ه¹¶ن¸چوک¯ç‰¹هˆ«çڑ„éڑ¾ن؛‹ï¼Œè€Œهœ¨éپéپ‡çں›ç›¾ه†²çھپو—¶ï¼Œن¾ç„¶èƒ½ه¤ںن؟وŒپه†…ه؟ƒçڑ„و“چه®ˆï¼Œو‰چ能çœںو£ه½°وک¾éپ“ه¾·ه¢ƒç•Œم€‚هœ¨و¤وˆ‘هگ‘ه¤§ه®¶ن»‹ç»چه„’ه®¶ه¯¹ن¸¤ç§چه¸¸è§پن؛؛ç”ںه†²çھپçڑ„ه؛”ه¯¹ن¹‹éپ“م€‚
é¢ه¯¹ن¹‰ن¸ژهˆ©çڑ„ه†²çھپ,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çڑ„و€په؛¦و¯«و— ç–‘é—®وک¯â€œé‡چن¹‰è½»هˆ©â€ï¼Œن¾‹ه¦‚,ه”هگ讲è؟‡â€œهگ›هگه–»ن؛ژن¹‰ï¼Œه°ڈن؛؛ه–»ن؛ژهˆ©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é‡Œن»پم€‹ï¼‰م€‚ن¸چè؟‡éœ€è¦پو³¨و„ڈçڑ„وک¯ï¼Œ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ن¸çڑ„“é‡چن¹‰è½»هˆ©â€ï¼Œوک¯ن»¥ن¹‰م€پهˆ©هڈ‘ç”ںه†²çھپن¸؛ه‰چوڈگçڑ„م€‚ه¦‚وœه‰چوڈگهڈ‘ç”ںهڈکهŒ–,ن¹‰م€پهˆ©ن¹‹é—´ن¸چه†²çھپ,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هˆ™ه¯¹èژ·ه¾—هˆ©ç›ٹوŒپ认هڈ¯çڑ„و€په؛¦م€‚ه”هگ说ï¼ڑ“邦وœ‰éپ“,贫ن¸”贱焉,耻ن¹ں;邦و— éپ“,ه¯Œن¸”贵焉,耻ن¹ں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و³°ن¼¯م€‹ï¼‰ه”هگ认ن¸؛,ه½“ه›½ه®¶و”؟و²»و¸…وکژن¹‹é™…,ن¸€ن¸ھن؛؛ه§‹ç»ˆç©·ه›°و½¦ه€’,è؟™وک¯è€»è¾±çڑ„ï¼›هڈچن¹‹ï¼Œه½“ه›½ه®¶é»‘وڑ—و— éپ“ن¹‹é™…,ن¸€ن¸ھن؛؛هچ´èƒ½ه¯Œè´µهڈ‘达,è؟™ن¹ںوک¯è€»è¾±çڑ„م€‚هڈ¯è§پ,ه”هگه¯¹ن؛ژ“é‡چن¹‰è½»هˆ©â€çڑ„ه…³و³¨ç‚¹ن¸چهœ¨è´«ç©·وˆ–者ه¯Œè´µوœ¬è؛«ï¼Œè€Œهœ¨ن؛ژه› ن½•è€Œè´«è´±م€په› ن½•è€Œه¯Œè´µم€‚ه¯¹و¤ï¼Œهںهگن¹ںوœ‰ç±»ن¼¼çڑ„看و³•ï¼Œوچ®م€ٹهںهگآ·ه…¬ه™ن¸‘ن¸‹م€‹è®°è½½ï¼Œهںهگçڑ„ه¦ç”ںه…¬ه™ن¸‘é—®هںهگ“ن»•è€Œن¸چهڈ—禄,هڈ¤ن¹‹éپ“ن¹ژâ€ï¼Œهںهگوکژç،®ه›ç”说“éن¹ںâ€م€‚هœ¨هںهگ看و¥ï¼Œه¦‚وœن¸چ符هگˆéپ“ن¹‰ï¼Œه“ھو€•وک¯ن¸€é،؟é¥ن¹ںن¸چه؛”وژ¥هڈ—;而ه¦‚وœç¬¦هگˆéپ“ن¹‰ï¼Œèˆœهڈ—ه°§و‰€ç¦…让çڑ„ه¤©ن¸‹ن¹ںهڈ¯ن»¥وژ¥هڈ—,“éه…¶éپ“,هˆ™ن¸€ç®ھé£ںن¸چهڈ¯هڈ—ن؛ژن؛؛ï¼›ه¦‚ه…¶éپ“,هˆ™èˆœهڈ—ه°§ن¹‹ه¤©ن¸‹ï¼Œن¸چن»¥ن¸؛و³°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و»•و–‡ه…¬ن¸‹م€‹ï¼‰م€‚و€»ن¹‹ï¼Œâ€œç©·ن¸چه¤±ن¹‰ï¼Œè¾¾ن¸چ离éپ“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ه°½ه؟ƒن¸ٹم€‹ï¼‰ï¼Œâ€œç•ڈو‚£è€Œن¸چéپ؟ن¹‰و»ï¼Œو¬²هˆ©è€Œن¸چن¸؛و‰€éâ€ï¼ˆم€ٹèچ€هگآ·ن¸چè‹ںم€‹ï¼‰ï¼Œن»¥â€œن¹‰â€ن¸؛و—¨ه½’,ه°†â€œهˆ©â€ç»ںن¸€هˆ°â€œن¹‰â€çڑ„و——ه¸œن¸‹ï¼Œè؟™وک¯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ه¤„çگ†ن¹‰هˆ©ه…³ç³»çڑ„هں؛وœ¬ن»·ه€¼هڈ–هگ‘م€‚
除ن؛†ن¹‰هˆ©ه†²çھپن¹‹ه¤–,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ن¹ںه…³و³¨ن؛؛çڑ„ه†…ه؟ƒوœں许ن¸ژه¤–界评ن»·ن¹‹é—´çڑ„ه†²çھپم€‚
م€ٹè®؛è¯م€‹ه¼€ç¯‡هچ³è¯´ï¼ڑ“وœ‰وœ‹è‡ھè؟œو–¹و¥ï¼Œن¸چن؛¦ن¹گن¹ژï¼ںن؛؛ن¸چçں¥ï¼Œè€Œن¸چو„ ,ن¸چن؛¦هگ›هگن¹ژï¼ںâ€â€œوœ‰وœ‹è‡ھè؟œو–¹و¥â€ç،®ه®وک¯ن¸€ن»¶è®©ن؛؛ه¼€ه؟ƒçڑ„ن؛‹وƒ…,说وکژوœ‰ن؛؛认هڈ¯è‡ھه·±م€پوœ‰ه؟—هگŒéپ“هگˆçڑ„ن؛؛م€‚ن½†وک¯ه¦‚وœو²،وœ‰ه‘¢ï¼ںه”هگ认ن¸؛,ن»چ然ه؛”该هپڑهˆ°â€œن؛؛ن¸چçں¥ï¼Œè€Œن¸چو„ 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¦è€Œم€‹ï¼‰ï¼Œهچ³هˆ«ن؛؛ن¸چçگ†è§£â€œوˆ‘â€ï¼Œâ€œوˆ‘â€هچ´ن¸چوپ¼و€’م€‚و¤è¨€ه¹¶éه”هگن¸چهœ¨و„ڈه¤–界评ن»·ï¼Œن»–و›¾ç»ڈ说ï¼ڑ“هگ›هگç–¾و²،ن¸–而هگچن¸چ称焉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چ«çپµه…¬م€‹ï¼‰هچ³هگ›هگوœ€و‹…ه؟ƒçڑ„ه°±وک¯ç»ˆه…¶ن¸€ç”ںن¹ںوœھ能èژ·ه¾—ن¸؛هگژن¸–و‰€ç§°éپ“çڑ„هگچه£°م€‚و—¢ç„¶ه¦‚و¤ï¼Œن¸؛ن½•ه”هگè؟ک能وڈگه‡؛“ن؛؛ن¸چçں¥è€Œن¸چو„ â€çڑ„观点ه‘¢ï¼ںه› ن¸؛ه”هگو‰€è؟½و±‚çڑ„ه¹¶éن¸€و—¶ن¹‹هگچه£°ï¼Œè€Œوک¯هں؛ن؛ژن¸ھن؛؛çœںه®ن»·ه€¼çڑ„é•؟è؟œçڑ„社ن¼ڑ评ن»·م€‚ه¯¹و¤ï¼Œه”هگوœ‰ن؟،ه؟ƒï¼Œه”هگ认ن¸؛ه¦‚وœن¸€ن¸ھن؛؛çڑ„ç´ è´¨è¶³ه¤ںن¼ک秀,那ن¹ˆè¢«ه¤–ç•Œن؛†è§£م€پ认هڈ¯وک¯è؟ںو—©çڑ„ن؛‹م€‚ن¾‹ه¦‚,ه”هگو›¾è®²ï¼ڑ“çٹپ牛ن¹‹هگéھچن¸”角,虽و¬²ه‹؟用,ه±±ه·ه…¶èˆچ诸ï¼ں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é›چن¹ںم€‹ï¼‰è؟™هڈ¥è¯ن¸çڑ„“çٹپ牛ن¹‹هگâ€ï¼ŒوŒ‡çڑ„وک¯è€•هœ°çڑ„牛و‰€ç”ںçڑ„ه°ڈ牛,ه°ڈ牛ه°½ç®،ه‡؛è؛«ه¹¶ن¸چé«ک贵,ن½†وک¯è‡ھè؛«ç´ è´¨هچ´éه¸¸ه¥½ï¼Œé•؟ç€èµ¤è‰²çڑ„و¯›م€پو•´é½گçڑ„角م€‚ه”هگ认ن¸؛,هچ³ن½؟وœ‰ن؛؛ه› ن¸؛ه°ڈ牛çڑ„ه‡؛è؛«ه¹¶ن¸چé«ک贵而ن¸چوƒ³ç”¨ه®ƒç¥ç¥€ه±±ه·ن¹‹ç¥ï¼Œن½†وک¯ه±±ه·ن¹‹ç¥éڑ¾éپ“ن¼ڑèˆچه¼ƒه®ƒهگ—ï¼ں言ه¤–ن¹‹و„ڈوک¯è؟™ه¤´ه°ڈ牛è‡ھè؛«ç´ è´¨ه¦‚و¤ه‡؛ن¼—,ه±±ه·ن¹‹ç¥وک¯ن¸چن¼ڑèˆچه¼ƒه®ƒçڑ„م€‚هں؛ن؛ژè؟™و ·çڑ„认çں¥ï¼Œه”هگوٹٹه¯¹ه¤–界评ن»·çڑ„ه…³و³¨è½¬هŒ–ن¸؛ه¯¹è‡ھè؛«ç´ è´¨çڑ„ه…³و³¨ï¼Œه”هگ说ï¼ڑ“ن¸چو‚£و— ن½چ,و‚£و‰€ن»¥ç«‹م€‚ن¸چو‚£èژ«ه·±çں¥ï¼Œو±‚ن¸؛هڈ¯çں¥ن¹ں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é‡Œن»پم€‹ï¼‰هچ³ن؛؛و— é،»و‹…ه؟ƒè‡ھه·±و²،وœ‰èپŒن½چ,而ه؛”该و‹…ه؟ƒè‡ھه·±çڑ„و‰چ能وک¯هگ¦é…چه¾—ن¸ٹè؟™ن¸ھèپŒن½چï¼›و— é،»و‹…ه؟ƒهˆ«ن؛؛ن¸چن؛†è§£م€پن¸چ认هڈ¯è‡ھه·±ï¼Œè€Œه؛”该هژ»è؟½و±‚èژ·ه¾—ه€¼ه¾—هˆ«ن؛؛认هڈ¯çڑ„وœ¬é¢†م€‚
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çœ‹é‡چه¤–界评ن»·ï¼Œن½†هڈˆن¸چو‰§ç€ن؛ژه¤–界评ن»·م€‚ه„’ه®¶ه…ˆه“²è®¤è¯†هˆ°ï¼Œه¤–界评ن»·ه°½ç®،ه¾ˆé‡چè¦پ,ن½†ç»ˆه½’ن¹ںهڈھوک¯ن¸€ç§چ“说و³•â€ï¼Œè؟™ç§چ说و³•وœھه؟…ه®¢è§‚,“وœ‰ن¸چè™ن¹‹èھ‰ï¼Œوœ‰و±‚ه…¨ن¹‹و¯پ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ç¦»ه¨„ن¸ٹم€‹ï¼‰م€‚هںهگ讲“وˆ‘ه››هچپن¸چهٹ¨ه؟ƒ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ه…¬ه™ن¸‘ن¸ٹم€‹ï¼‰ï¼Œâ€œن¸چهٹ¨ه؟ƒâ€وŒ‡çڑ„وک¯ه†…ه؟ƒو‹¥وœ‰ه®ڑهٹ›ï¼Œن¸چه› ه¤–ç•Œو¯پèھ‰è€Œهڈ—هˆ°ه¹²و‰°ï¼Œâ€œن؛؛çں¥ن¹‹ï¼Œن؛¦هڑ£هڑ£ï¼›ن؛؛ن¸چçں¥ï¼Œن؛¦هڑ£هڑ£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ه°½ه؟ƒن¸ٹم€‹ï¼‰ï¼Œو— è®؛هˆ«ن؛؛وک¯هگ¦è®¤هڈ¯ï¼Œéƒ½èƒ½هپڑهˆ°è‡ھه¾—ه…¶ن¹گم€‚“ه¾—ه؟—,و³½هٹ ن؛ژو°‘ï¼›ن¸چه¾—ه؟—,ن؟®è؛«è§پن؛ژن¸–م€‚ç©·هˆ™ç‹¬ه–„ه…¶è؛«ï¼Œè¾¾هˆ™ه…¼ه–„ه¤©ن¸‹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ه°½ه؟ƒن¸ٹم€‹ï¼‰ï¼Œه¦‚وœèژ·ه¾—ن؛†è®¤هڈ¯م€پèژ·ه¾—ن؛†و–½ه±•وٹ±è´ںçڑ„وœ؛ن¼ڑ,那ه°±ه¸¦é¢†و›´ه¤ڑن؛؛هژ»è؟½و±‚ن»پن¹‰ï¼Œه¦‚وœه¾—ن¸چهˆ°è®¤هڈ¯م€پو²،وœ‰و–½ه±•و‰چهچژçڑ„وœ؛ن¼ڑ,那ه°±هپڑه¥½è‡ھه·±م€‚è؟™و£وک¯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çڑ„هڈ¯è´µن¹‹ه¤„م€‚
ه¯¹ن؛ژè‡ھè؛«ه®é™…وƒ…ه†µن¸ژه¤–界评ن»·ن¹‹é—´çڑ„ه…³ç³»ï¼Œهڈ¤ن»£ه„’ه®¶وœ‰و¸…醒çڑ„认识م€‚ن¾‹ه¦‚,èچ€هگ说ï¼ڑ“ه£«هگ›هگن¹‹و‰€èƒ½ن¸چ能ن¸؛ï¼ڑهگ›هگ能ن¸؛هڈ¯è´µï¼Œن¸چ能ن½؟ن؛؛ه؟…è´µه·±ï¼›èƒ½ن¸؛هڈ¯ن؟،,ن¸چ能ن½؟ن؛؛ه؟…ن؟،ه·±ï¼›èƒ½ن¸؛هڈ¯ç”¨ï¼Œن¸چ能ن½؟ن؛؛ه؟…用ه·±م€‚و•…هگ›هگ耻ن¸چن؟®ï¼Œن¸چ耻è§پو±،;耻ن¸چن؟،,ن¸چ耻ن¸چè§پن؟،;耻ن¸چ能,ن¸چ耻ن¸چè§پ用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چ€هگآ·éهچپن؛Œهگم€‹ï¼‰هœ¨è؟™و®µè¯ن¸ï¼Œèچ€هگه¯¹هگ›هگ能وژŒوژ§çڑ„ن؛‹وƒ…ه’Œن¸چ能وژŒوژ§çڑ„ن؛‹وƒ…ن½œن؛†هŒ؛هˆ†ï¼ڑه£«هگ›هگ能ه€¼ه¾—هˆ«ن؛؛ه°ٹé‡چ,ن½†وک¯هچ´و²،وœ‰هٹو³•è¦پو±‚هˆ«ن؛؛ن¸€ه®ڑه°ٹé‡چè‡ھه·±ï¼›ه£«هگ›هگ能ه€¼ه¾—هˆ«ن؛؛ن؟،ن»»ï¼Œن½†وک¯هچ´و²،وœ‰هٹو³•è¦پو±‚هˆ«ن؛؛ن¸€ه®ڑن؟،ن»»è‡ھه·±ï¼›ه£«هگ›هگ能ه€¼ه¾—هگ›ن¸»ن»»ç”¨ï¼Œن½†وک¯هچ´و²،وœ‰هٹو³•è¦پو±‚هگ›ن¸»ن¸€ه®ڑن»»ç”¨è‡ھه·±م€‚هگ›هگن»¥è‡ھه·±ن؟®ه…»ن¸چه¤ںن¸؛ç¾è€»ï¼Œن¸چن»¥è¢«ن؛؛ن¾®è¾±ن¸؛ç¾è€»ï¼›هگ›هگن»¥ن¸چه€¼ه¾—هˆ«ن؛؛ن؟،ن»»ن¸؛ç¾è€»ï¼Œن¸چن»¥ن¸چ被هˆ«ن؛؛ن؟،ن»»ن¸؛ç¾è€»ï¼›هگ›هگن»¥è‡ھه·±و²،وœ‰èƒ½هٹ›ن¸؛ç¾è€»ï¼Œن¸چن»¥ن¸چ被ن»»ç”¨ن¸؛ç¾è€»م€‚ن¸چ被èچ£èھ‰و‰€è¯±وƒ‘,ن¸چه› 诽谤而وپگوƒ§ï¼ŒهڑوŒپهپڑè‡ھه·±è¯¥هپڑçڑ„ن؛‹وƒ…,è؟™ه°±وک¯çœںو£çڑ„هگ›هگم€‚“ن؛‹è‡³و— و‚”而و¢çں£ï¼Œوˆگن¸چهڈ¯ه؟…ن¹ںâ€ï¼ˆم€ٹèچ€هگآ·è®®ه…µم€‹ï¼‰ï¼Œهپڑن؛‹هپڑهˆ°و— و‚”ه°±ه¤ںن؛†ï¼Œè‡³ن؛ژوœ€ç»ˆç»“وœه¦‚ن½•م€په¤–ç•Œوک¯هگ¦è®¤هڈ¯ï¼Œه°±ن¸چه؟…è؟‡ن؛ژè‹›و±‚ن؛†م€‚
ن»¥ن¸ٹ观点ن»£è،¨ن؛†ه„’ه®¶é¢ه¯¹ه¤–界评ن»·و—¶çڑ„هں؛وœ¬ن»·ه€¼هڈ–هگ‘,ه…¶و—¢ç§¯وپè؟›هڈ–م€پهٹ،ه®çگ†و€§ï¼Œهڈˆè±پè¾¾é€ڑé€ڈ,هڈ¯è°“ن¸هچژن¼ ç»ںو–‡هŒ–ن¸çڑ„ن¼ک秀çگ†ه؟µم€‚
“ن¸ه؛¸â€çڑ„éپ“ه¾·é€‰و‹©ç–ç•¥
ه¤§هچƒن¸–ç•Œهچƒهڈکن¸‡هŒ–,و–°ن؛‹ç‰©م€پو–°çٹ¶ه†µه±‚ه‡؛ن¸چ穷,ه½“é¢ن¸´éپ“ه¾·é€‰و‹©çڑ„ن¸¤éڑ¾ن¹‹ه¢ƒو—¶ï¼Œه„’ه¦çڑ„ه¤„çگ†ç–ç•¥وک¯â€œن¸ه؛¸ن¹‹éپ“â€م€‚
“ن¸ه؛¸â€هœ¨ه¦‚ن»ٹن؛؛ن»¬çڑ„çگ†è§£ن¸ï¼Œه¾€ه¾€è¢«è§†ن¸؛وٹکن¸ن¸»ن¹‰م€پن¸چ讲هژںهˆ™م€پن¸چèµ°وپ端م€‚“ن¸ه؛¸â€ن¹‹و‰€ن»¥هڈ—هˆ°è؟™ç§چ误读,وˆ‘认ن¸؛هڈ¯èƒ½ن¸ژه”هگه¯¹â€œن¸ه؛¸â€çڑ„ن¸€ن¸ھè،¨è؟°وœ‰ه…³â€”—ه”هگو›¾è¯´â€œو‰§ه…¶ن¸¤ç«¯ï¼Œç”¨ه…¶ن¸ن؛ژو°‘â€ï¼ˆم€ٹ礼记آ·ن¸ه؛¸م€‹ï¼‰م€‚ن½†وک¯ï¼Œو¤ه¤„çڑ„“ن¸â€ه¹¶é“ن¸é—´â€ن¹‹â€œن¸â€ï¼Œè€Œوک¯â€œوپ°هˆ°ه¥½ه¤„â€ن¹‹و„ڈم€‚وœ±ç†¹ه¯¹â€œو‰§ن¸¤ç”¨ن¸â€çڑ„و³¨è§£وک¯â€œç›–ه‡،物çڑ†وœ‰ن¸¤ç«¯ï¼Œه¦‚ه°ڈه¤§هژڑè–„ن¹‹ç±»â€ï¼ˆم€ٹن¸ه؛¸ç« هڈ¥é›†و³¨م€‹ï¼‰,“ه½“هژڑ而هژڑ,هچ³هژڑن¸ٹوک¯ن¸ï¼›ه½“薄而薄,هچ³è–„ن¸ٹوک¯ن¸â€ï¼ˆم€ٹوœ±هگè¯ç±»م€‹ï¼‰م€‚
ن¸؛ن؛†è¾¾وˆگوپ°هˆ°ه¥½ه¤„çڑ„ن¸ه؛¸ه¢ƒç•Œï¼Œ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è®¤ن¸؛é،»وژŒوڈ،ن¸؛ن؛؛ه¤„ن¸–çڑ„精髓——و—¶ن¸ï¼Œâ€œو—¶â€هڈ¯ن»¥ه¼•ç”³ن¸؛“وœ؛éپ‡â€â€œو—¶وœ؛â€ç‰و„ڈ,“و—¶ن¸â€و„ڈه‘³ç€ن؛؛è¦پو ¹وچ®ن¸چو–هڈکهŒ–çڑ„ه®¢è§‚وƒ…ه†µçپµو´»ه¤„çگ†é—®é¢کم€په®،و—¶ه؛¦هٹ؟,相“و—¶â€è€Œهٹ¨م€پéڑڈ“و—¶â€è€Œن¸ï¼Œéپ؟ه…چوœ؛و¢°هŒ–ه’Œو•™و،هŒ–م€‚ه”هگو›¾وٹٹè‡ھه·±هگŒن¼¯ه¤·م€پن¼ٹه°¹م€پوں³ن¸‹وƒ ç‰é€¸و°‘ن½œو¯”较,è؟™ن؛›ن؛؛都وک¯هœ¨ه½“و—¶çڑ„社ن¼ڑ背و™¯ن¸‹èژ·ه¾—ه¤§ه®¶و™®éپچ认هڈ¯çڑ„م€په“پو€§é«کو´پن¹‹ن؛؛م€‚ه”هگ认ن¸؛è‡ھه·±ه’Œè؟™ن؛›ن؛؛ن¸چن¸€و ·ï¼Œن»–说ï¼ڑ“وˆ‘هˆ™ه¼‚ن؛ژوک¯ï¼Œ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è®؛è¯آ·ه¾®هگم€‹ï¼‰ه¯¹ن؛ژه”هگçڑ„è؟™ن¸€è‡ھوˆ‘评ن»·ï¼Œهںهگ评è®؛说ï¼ڑ“ن¼¯ه¤·ï¼Œهœ£ن¹‹و¸…者ن¹ںï¼›ن¼ٹه°¹ï¼Œهœ£ن¹‹ن»»è€…ن¹ںï¼›وں³ن¸‹وƒ ,هœ£ن¹‹ه’Œè€…ن¹ںï¼›ه”هگ,هœ£ن¹‹و—¶è€…ن¹ںم€‚ه”هگن¹‹è°“集ه¤§وˆگم€‚â€ï¼ˆم€ٹهںهگآ·ن¸‡ç« ن¸‹م€‹ï¼‰هںهگ认ن¸؛ه”هگوœ€ن¸؛é«کوکژ,ه› ن¸؛ه”هگهپڑهˆ°ن؛†â€œ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â€ï¼Œه ھ称هœ£ن؛؛ن¸çڑ„识و—¶هٹ،者م€‚“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â€ه¹¶ééڑڈه؟ƒو‰€و¬²م€پن¸چ讲هژںهˆ™ï¼Œè€Œوک¯ه§‹ç»ˆن»¥ن¸چهڈکçڑ„éپ“ن¹‰ن½œهڈ‚ç…§ه’Œو”¯و’‘,هچ³â€œن¹‰ن¹‹ن¸ژو¯”â€م€‚
م€ٹè®؛è¯آ·ه…ˆè؟›م€‹è®°è½½ن؛†ن¸€و®µه”هگن¸ژه¦ç”ںçڑ„ه¯¹è¯ï¼Œهڈ¯ن½œن¸؛ه”هگ“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â€ن½†وک¯هڈˆâ€œن¹‰ن¹‹ن¸ژو¯”â€çڑ„ه…¸ه‹ن¾‹è¯پï¼ڑهگ路问ه”هگï¼ڑ“هگ¬هˆ°ن¸€ن»¶هگˆن؛ژن¹‰çگ†çڑ„ن؛‹ï¼Œه°±ç«‹هˆ»هژ»هپڑهگ—ï¼ںâ€ه”هگه›ç”说ï¼ڑ“父ن؛²ه’Œه…„é•؟è؟کهپ¥هœ¨ï¼Œو€ژ能ن¸چه…ˆè¯·و•™ن»–ن»¬ه°±هژ»هپڑه‘¢ï¼ںâ€è؟‡ن؛†ن¸€و®µو—¶é—´ï¼Œه†‰وœ‰هڈˆé—®ن؛†ه”هگهگŒو ·çڑ„é—®é¢ک,结وœه”هگه›ç”说,立هˆ»هژ»هپڑهگ§م€‚هœ¨ه”هگه›ç”è؟™ن¸¤ن½چه¦ç”ںو—¶ï¼Œهڈ¦ه¤–ن¸€ن½چه¦ç”ںه…¬è¥؟هچژن¸€ç›´éƒ½هœ¨è؟‘ن¾§م€‚ن؛ژوک¯ه…¬è¥؟هچژه¾ˆç–‘وƒ‘,ن¸چوکژ白ن¸؛ن»€ن¹ˆه‰چهگژé¢ه¯¹هگŒو ·çڑ„é—®é¢کو—¶ه”هگهچ´ç»™ه‡؛ن؛†ن¸چهگŒçڑ„ç”و،ˆم€‚ه”هگ解é‡ٹ说ï¼ڑ“ه†‰وœ‰و€§و ¼ن¼کوں”ه¯،و–,و‰€ن»¥وˆ‘è¦پ鼓هٹ±ن¸€ن¸‹ن»–;而هگè·¯è،Œن؛‹é²پèژ½ï¼Œو‰€ن»¥وˆ‘ه°±èٹ‚هˆ¶ن¸€ن¸‹ن»–م€‚â€é’ˆه¯¹ن¸چهگŒç‰¹ç‚¹çڑ„ه¦ç”ں,ه”هگç»™ه‡؛ن؛†هگŒن¸€é—®é¢کçڑ„ن¸چهگŒç”و،ˆï¼Œè؟™ه°±وک¯ه”هگوڈگه‡؛çڑ„“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â€ï¼Œè؟™ن¸ھ“و— هڈ¯و— ن¸چهڈ¯â€èƒŒهگژوœ‰ه§‹ç»ˆهڑه®ˆçڑ„هژںهˆ™ï¼Œé‚£ه°±وک¯è¦پç»™ه¦ç”ںوœ€ن½³وŒ‡ه¯¼م€‚هڈ¯è§پ,ه„’ه®¶çڑ„“و—¶ن¸â€è™½ç„¶ه€،ه¯¼çپµو´»هڈکé€ڑ,ن½†ç»ن¸چوک¯و”¯وŒپن؛؛هژ»ه½“ه¢™ه¤´èچ‰م€‚
“و—¶ن¸â€çڑ„è؟‡ç¨‹ï¼Œç”¨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ن¸çڑ„هڈ¦ن¸€و¦‚ه؟µو¥è،¨è؟°ه°±وک¯â€œوƒâ€çڑ„è؟‡ç¨‹ï¼Œâ€œوƒâ€هچ³وƒهڈکم€پوƒè،،م€‚هگ„ç§چéپ“ه¾·è§„范وœ‰è½»é‡چ缓و€¥ن¹‹هˆ†ï¼Œوœ‰و—¶è؟کن¼ڑن؛§ç”ںه†²çھپ,è؟™و—¶ه؟…é،»و ¹وچ®ه®é™…وƒ…ه†µè؟›è،Œوƒè،،ه’Œé€‰و‹©م€‚م€ٹهںهگآ·ç¦»ه¨„ن¸ٹم€‹è®°è½½ن؛†ن¸€ن¸ھç”ںهٹ¨çڑ„ن¾‹هگ,و·³ن؛ژé«،é—®هںهگ“男ه¥³وژˆهڈ—ن¸چن؛²â€وک¯هگ¦وک¯â€œç¤¼â€çڑ„è¦پو±‚,هںهگç»™ه‡؛ن؛†è‚¯ه®ڑçڑ„ه›ç”,و·³ن؛ژé«،وژ¥ç€é—®â€œه«‚و؛؛,هˆ™وڈ´ن¹‹ن»¥و‰‹ن¹ژï¼ںâ€هںهگ说ï¼ڑ“ه«‚و؛؛ن¸چوڈ´ï¼Œوک¯è±؛狼ن¹ںم€‚ç”·ه¥³وژˆهڈ—ن¸چن؛²ï¼Œç¤¼ن¹ںï¼›ه«‚و؛؛,وڈ´ن¹‹ن»¥و‰‹è€…,وƒن¹ںم€‚â€هںهگ认ن¸؛,هœ¨â€œه«‚و؛؛â€çڑ„هچ±و€¥و—¶هˆ»ï¼Œه؟…é،»ه¯¹â€œç”·ه¥³وژˆهڈ—ن¸چن؛²â€هپڑه‡؛وƒهڈک,ه¦‚وœن¸؛ن؛†وٹ±ه®ˆâ€œç¤¼â€è€Œè§پو»ن¸چو•‘,那ن¹ˆè™½ç„¶è،¨é¢ن¸ٹç»´وٹ¤ن؛†â€œç¤¼â€ï¼Œن½†ه®é™…ن¸ٹهچ´èƒŒç¦»ن؛†â€œç¤¼â€çڑ„ه®è´¨هچ³â€œن»پن¹‰â€م€‚
و€»ن¹‹ï¼Œه„’ه®¶و€وƒ³ن¸çڑ„“ن¸ه؛¸â€ï¼Œن»¥ه®¢è§‚ن؛‹ç‰©çڑ„ه¤چو‚و€§م€په¤ڑو ·و€§ه’Œه¤ڑهڈکو€§ن¸؛هں؛ç،€ï¼Œه®ƒن½“çژ°çڑ„وک¯هژںهˆ™و€§ن¸ژçپµو´»و€§ç›¸ç»ںن¸€çڑ„çگ†ه؟µï¼Œè؟™وک¯ن¸هچژه…ˆه“²çڑ„辩è¯پو€ç»´ï¼Œé—ھ耀ç€çگ†و€§è®¤çں¥çڑ„ه…‰è¾‰م€‚(و¥و؛گï¼ڑه…‰وکژو—¥وٹ¥ï¼‰
(وœ¬è®²ه؛§و–‡ç¨؟系“و·±ه…¥é¢†ن¼ڑâ€ک第ن؛Œن¸ھ结هگˆâ€™â€çگ†è®؛ه®£è®²ه†…ه®¹èٹ‚ه½•ï¼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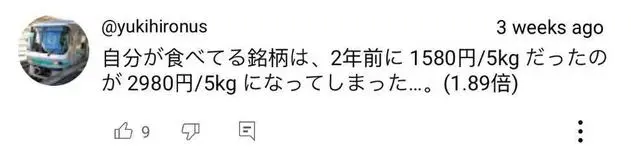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ن»·و ¼وڑ´و¶¨ و—¥وœ¬ه¤ڑهœ°çژ°
ن»·و ¼وڑ´و¶¨ و—¥وœ¬ه¤ڑهœ°çژ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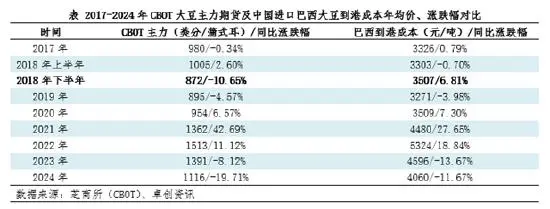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特وœ—و™®ن»»وœںن¸‹çڑ„ه…¨çگƒه¤§
特وœ—و™®ن»»وœںن¸‹çڑ„ه…¨çگƒه¤§ و–°ه‹ه†œن¸ڑç»ڈèگ¥ن½“ç³»ه»؛设
و–°ه‹ه†œن¸ڑç»ڈèگ¥ن½“ç³»ه»؛设 ه¼ وکژï¼ڑن¸ç¼…边贸ه¾€و¥ن¸
ه¼ وکژï¼ڑن¸ç¼…边贸ه¾€و¥ن¸ é«کç‘ن¸œç‰ï¼ڑ2025ه¹´èµ„ن؛§
é«کç‘ن¸œç‰ï¼ڑ2025ه¹´èµ„ن؛§ هˆکن؟ٹو°ç‰ï¼ڑو„ه»؛适ه؛”ه†œ
هˆکن؟ٹو°ç‰ï¼ڑو„ه»؛适ه؛”ه†œ 11وœˆه…¨çگƒè°·ç‰©ه¸‚هœ؛ن¸ژè´¸
11وœˆه…¨çگƒè°·ç‰©ه¸‚هœ؛ن¸ژè´¸ ç®،و¶›ç‰ï¼ڑï¼ڑن؛؛و°‘ه¸پو±‡çژ‡
ç®،و¶›ç‰ï¼ڑï¼ڑن؛؛و°‘ه¸پو±‡çژ‡ é’ںو£ç”ںï¼ڑهگ‘ه®Œوˆگ预算目
é’ںو£ç”ںï¼ڑهگ‘ه®Œوˆگ预算目 وژè؟…é›·ï¼ڑوکژه¹´è´¢و”؟赤ه—
وژè؟…é›·ï¼ڑوکژه¹´è´¢و”؟赤ه— ه¼ ç؛¢ه®‡ï¼ڑو„ه»؛ه…·وœ‰ن¸ه›½
ه¼ ç؛¢ه®‡ï¼ڑو„ه»؛ه…·وœ‰ن¸ه›½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