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жҪҳеҠЎжӯЈпјҢз”·пјҢе®үеҫҪеёҲиҢғеӨ§еӯҰдёӯеӣҪиҜ—еӯҰз ”з©¶дёӯеҝғж•ҷжҺҲгҖӮ
еҸӨд»ЈиҜ—дәәдёӯ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жңҖжҺЁеҙҮжқңз”«пјҢжқңиҜ—дҪңдёәж–№ж°ҸгҖҒе§ҡж°ҸзӯүеӨ§е®¶ж—Ҹзҡ„家еӯҰдё–д»Јдј жүҝпјҢе…¶ж¬ЎжҺЁеҙҮйҷ¶жёҠжҳҺгҖҒйҹ©ж„ҲгҖҒзҷҪеұ…жҳ“гҖҒиӢҸиҪјгҖҒй»„еәӯеқҡзӯүдәәгҖӮиҮідәҺжқҺе•Ҷйҡҗ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жҠұжҢҒйқһеёёзҹӣзӣҫзҡ„жҖҒеәҰпјҢжҲ–зҲұд№ӢеҗҢжқңз”«пјҢжҲ–еҺҢд№ӢеҰӮзҺӢеҪҰжі“пјҢдәҰжңүзҲұжҒЁдәӨз»ҮиҖ…гҖӮйҡҸзқҖж—¶д»Јзҡ„еҸҳиҝҒ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Ҝ—дәәеҜ№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иҜ„д»·д№ҹеңЁдёҚж–ӯж”№еҸҳгҖӮе…ідәҺжЎҗеҹҺжҙҫиҜ—дәәеҜ№жқҺиҜ—зҡ„жҺҘеҸ—пјҢеҲҳеӯҰй”ҙгҖҒеҗҙи°ғе…¬еҸҠзұіеҪҰйқ’зӯүеңЁе…¶и‘—дҪңдёӯеқҮжңүжүҖж¶үеҸҠ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Ҝ№дәҺе…¶дёӯи‘—еҗҚиҖ…пјҢеҰӮй’ұжҫ„д№ӢгҖҒе§ҡйјҗгҖҒж–№дёңж ‘гҖҒжӣҫеӣҪи—©зӯүдәә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қҮжңүжҲ–еӨҡжҲ–е°‘зҡ„и®әиҝ°пјҢжң¬ж–ҮжӢҹд»ҺжҖ»дҪ“дёҠеҜ№жЎҗеҹҺжҙҫзҡ„д№үеұұиҜ—иҜ„и®әеҠ д»ҘиҖғеҜҹгҖӮдёҖгҖҒжқңиҜ—е—Је“Қ жЎҗеҹҺжҙҫе®—е°ҡжқңиҜ—пјҢеӣ жӯӨпјҢдҪҶеҮЎе–„еӯҰжқңиҖ…пјҢеҰӮйҹ©ж„ҲгҖҒзҷҪеұ…жҳ“гҖҒй»„еәӯеқҡзӯүдәәпјҢеқҮеҫ—еҲ°е…¶жҺЁеҙҮгҖӮ他们иӮҜе®ҡ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пјҢдё»иҰҒд№ҹжҳҜеңЁжӯӨж–№йқўгҖӮз”ұе°ҠжқңиҖҢеҙҮжқҺпјҢзҺӢе®үзҹіејҖе…¶е…ҲеЈ°пјҢи®Ө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зӣҙжүҝжқңз”«гҖӮе®ӢдәәиҜ—иҜқ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зҺӢиҚҶе…¬жҷҡе№ҙдәҰе–ңз§°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Ңд»Ҙдёәе”җдәәзҹҘеӯҰиҖҒжқңиҖҢеҫ—е…¶и—©зҜұиҖ…пјҢжғҹд№үеұұдёҖдәәиҖҢе·ІгҖӮвҖқдёҺзҺӢе®үзҹізұ»дјј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д№ҹжҳҜе°Ҷд№үеұұдҪңдёәиҖҒжқңдј дәәзңӢеҫ…гҖӮе§ҡйјҗи®ӨдёәпјҢжҷҡе”җиҜёиҜ—дәәдёӯвҖңжғҹзҺүжәӘз”ҹд№ғз•Ҙжңүжқңе…¬йҒ—е“ҚвҖқпјҢ并жҢҮеҮ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дә”еҫӢгҖҒдёғеҫӢгҖҒжҺ’еҫӢеқҮж•Ҳжі•жқңиҜ—пјҡвҖңдёғеҫӢдҪіиҖ…пјҢеҮ ж¬ІиҝңиҝҪжӢҫйҒ—вҖқпјҢвҖңй•ҝеҫӢжғҹд№үеұұзҠ№ж¬ІеӯҰжқңвҖқгҖӮе§ҡиҺ№иҜҙпјҡвҖңдё–зҹҘзҺүжәӘз”ҹе–„еӯҰжқңиҜ—пјҢиҖҢдёҚзҹҘжқңиҜ—жңүй…·дјјд№үеұұиҖ…гҖӮвҖқ并иҝӣдёҖжӯҘи§ЈйҮҠйҒ“пјҡвҖңгҖҠжӣІжұҹеҜ№й…’гҖӢдёҖзҜҮеҚіиҘҝжҳҶд№Ӣе…ҲеЈ°д№ҹгҖӮвҖҳйҫҷжӯҰж–°еҶӣж·ұй©»иҫҮпјҢиҠҷи“үеҲ«ж®ҝжј«з„ҡйҰҷвҖҷпјҢйқһд№үеұұдҪіеҸҘд№ҺпјҹиҮіиӢҘвҖҳиҠұиҗјеӨ№еҹҺйҖҡеҫЎж°”пјҢиҠҷи“үе°ҸиӢ‘е…Ҙиҫ№ж„ҒвҖҷпјҢеҲҷжқҺжҲ–жңӘд№Ӣжңүд№ҹгҖӮвҖқеӣ дёәд№үеұұиҜ—дёҺжқңиҜ—зҡ„еҜҶеҲҮе…ізі»пјҢе§ҡж°Ҹеӣ иҖҢиӮҜе®ҡжқҺиҜ—зҡ„жҲҗе°ұгҖӮеҲҳеӯҰй”ҙе…Ҳз”ҹи®ӨдёәпјҢжқңиҜ—д»ҺжҖқжғіж„ҹжғ…еҸҠеҲӣдҪңзІҫзҘһгҖҒжІүйғҒйЎҝжҢ«зҡ„йЈҺж јгҖҒиҜ—жӯҢйўҳжқҗдёүдёӘж–№йқўеҜ№жқҺиҜ—дә§з”ҹеҪұе“ҚгҖӮжЎҗеҹҺжҙҫдәҰжңүд»ҺжҖқжғіжғ…ж„ҹеҸҠеҲӣдҪңзІҫзҘһж–№йқўиӮҜе®ҡжқҺиҜ—иҖ…пјҢе§ҡиҺ№гҖҠи®әиҜ—з»қеҸ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й”Ұз‘ҹгҖӢеҲҶжҳҺжҳҜжӮјдәЎпјҢеҗҺдәәжһүиҮӘиҙ№е№із« гҖӮзүҷж——зҺүеёҗзңҹеҝ§еӣҪпјҢиҺ«еҗ‘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и§…з“ЈйҰҷгҖӮвҖқжҳҫ然пјҢе§ҡж°ҸеҜ№дәҺ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дёӯгҖҠйҮҚжңүж„ҹгҖӢд№Ӣзұ»е…іжіЁе”җзҺӢжңқзҺ°е®һзҡ„иҜ—жӯҢз»ҷдәҲжһҒй«ҳ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зӣёеҪўд№ӢдёӢпјҢгҖҠй”Ұз‘ҹгҖӢ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иҜёиҜ—еҲҷйҒӯеҲ°д»–们зҡ„жҺ’ж–ҘгҖӮдҪҶеҚідҪҝжҳҜвҖңжҳ”дәәзҡҶд»ҺдёҠйҖүвҖқзҡ„гҖҠйҮҚжңүж„ҹгҖӢпјҢдёҺе§ҡиҺ№еҗҢдёәвҖңе§ҡй—Ёеӣӣжқ°вҖқзҡ„ж–№дёңж ‘еҚҙвҖңз»ҶжҢүд№Ӣз»ҲжңӘжҙҪвҖқгҖӮиҷҪ然其зҲ¶ж–№з»©жҢҮеҮәжӯӨиҜ—жүҝжқңз”«гҖҠиҜёе°ҶгҖӢд№Ӣж„ҸпјҢдҪҶд»Қи®Өдёәе…¶вҖңдёҚеҸҠжқңвҖқгҖӮеҺҹеӣ еңЁдәҺе®ғвҖңйӘЁзҗҶдёҚжё…пјҢеӯ—еҸҘз”ЁдәӢпјҢдәҰдјјжңүзҡ®еӮ…дёҚзІҫеҲҮд№Ӣз—…вҖқпјҢеҰӮ第еӣӣеҸҘдёҺж¬ЎеҸҘеӨҚпјҢеҸҲдёҺ第е…ӯеҸҘеӨҚпјҢжӯӨдёәж— з« жі•пјӣжқңиҜ—еҲҷж— жӯӨвҖңеҝҷд№ұжІ“еӨҚй”ҷеұҘвҖқд№ӢеӨ„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и®ӨдёәпјҢеҜјиҮҙжӯӨз§ҚзҠ¶еҶөеҮәзҺ°зҡ„ж №жң¬еҺҹеӣ пјҢжҳҜвҖңжңүжң¬йўҶдёҺж— жң¬йўҶвҖқд№ӢвҖңжӮ¬з»қвҖқгҖӮжқңз”«вҖңжңүжң¬йўҶд»ҺиӮәи…‘дёӯжөҒеҮә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е…¶иҜ—вҖңжҺӘжіЁз”Ёж„ҸпјҢиҜӯеҠҝжө©з„¶пјҢиҖҢеҸҲеҮәд№Ӣд»Ҙж–Үд»Һеӯ—йЎәпјҢдёҺз»ҸгҖҒйӘҡгҖҒеҸӨж–ҮйҖҡжәҗвҖқпјӣжқҺе•ҶйҡҗеҸҠжҳҺдёғеӯҗеҲҷеұһдәҺвҖңж— жң¬йўҶвҖқиҖ…пјҢж•…е…¶иҜ—вҖңдёҚиҝҮдёңзүөиҘҝиЎҘпјҢж¶ӮйҘ°жҗҳжҹұд»ҘжҲҗе®ӨиҖҢе·ІвҖқгҖӮжқҺиҜ—вҖңж— жң¬йўҶвҖқпјҢж•…е…¶йҡҫдёҺжқңиҜ—жҜ”иӮ©гҖӮвҖңж— жң¬йўҶвҖқж„Ҹе‘ізқҖе…¶дәәйҒ“еҫ·дҝ®е…»дёҚеӨҹе……е®һгҖӮжЎҗеҹҺжҙҫе°ҶйҒ“еҫ·еўғз•Ңи§ҶдёәиҜ—жӯҢжҲҗе°ұзҡ„ж №еҹәпјҢеҲҳеӨ§ж«Ҷи®ӨдёәпјҡвҖңж–Үз« д№Ӣдј дәҺеҗҺдё–пјҢжҲ–д№…жҲ–жҡӮпјҢдёҖи§Ҷе…¶зІҫзҘһд№ӢеӨ§е°Ҹи–„еҺҡиҖҢдёҚйҖҫзҙҜй»ҚгҖӮвҖқе§ҡйјҗеҲҷеҸ‘зҺ°вҖңеҸӨд№Ӣе–„дёәиҜ—иҖ…вҖҰвҖҰе…¶иғёдёӯжүҖи“„пјҢй«ҳзҹЈгҖҒе№ҝзҹЈгҖҒиҝңзҹЈпјҢиҖҢеҒ¶еҸ‘д№ӢдәҺиҜ—пјҢеҲҷиҜ—дёҺд№Ӣдёәй«ҳе№ҝдё”иҝңз„үпјҢж•…жӣ°е–„дёәиҜ—д№ҹвҖқзҡ„规еҫӢ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еӨ§зәҰиғёиҘҹй«ҳпјҢз«Ӣеҝ—й«ҳпјҢи§Ғең°й«ҳпјҢеҲҷе‘Ҫж„ҸиҮӘй«ҳгҖӮвҖқжҖ»д№Ӣ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®ӨдёәпјҢиҜ—жӯҢжҲҗе°ұеӨ§е°ҸдёҺиҜ—дәәзҡ„зІҫзҘһеўғз•Ңй«ҳдҪҺ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пјҢиғёиҘҹй«ҳпјҢдёәжңүжң¬йўҶпјӣеҸҚд№ӢпјҢеҲҷдёәж— жң¬йўҶгҖӮеңЁж–№дёңж ‘еҝғзӣ®дёӯ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д№ғиғёиҘҹдёҚй«ҳиҖ…гҖӮйҮҠзҹіжһ—дә‘пјҡвҖңиҜ—дәәи®әе°‘йҷөеҝ еҗӣзҲұеӣҪпјҢдёҖйҘӯдёҚеҝҳпјҢиҖҢзӣ®д№үеұұдёәжөӘеӯҗпјҢд»Ҙз»®дёҪеҚҺиүіпјҢжһҒгҖҠзҺүеҸ°гҖӢгҖҒгҖҠйҮ‘жҘјгҖӢд№ӢдҪ“д№ҹгҖӮвҖқж–№ж°Ҹеј•жӯӨиҜӯпјҢ并еҠ жҢүиҜӯдә‘пјҡвҖңи®әзҡҶжңүи§ҒпјҢдәҰе№іе…Ғеҫ—е®һгҖӮвҖқ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д»–жҳҜеҗҢж„ҸиҝҷдёҖи§ӮзӮ№зҡ„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®Ө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并没жңүеңЁзІҫзҘһеҶ…ж ёеұӮйқўз»§жүҝжқңиҜ—гҖӮжқҺиҜ—вҖңе—Је“Қжқңе…¬вҖқпјҢжӣҙеӨҡжҳҜд»ҺиүәжңҜеұӮйқўдёҠжқҘиҜҙзҡ„гҖӮеңЁжЎҗеҹҺжҙҫзңӢжқҘпјҢжқңиҜ—вҖңжүҖд»ҘеҶ з»қеҸӨд»ҠиҜёе®¶вҖқпјҢвҖңеҸӘжҳҜжІүйғҒйЎҝжҢ«пјҢеҘҮжЁӘжҒЈиӮҶпјҢиө·з»“жүҝиҪ¬пјҢжӣІжҠҳеҸҳеҢ–пјҢз©·жһҒ笔еҠҝпјҢиҝҘдёҚз”ұдәәвҖқгҖӮиҝҷз§ҚзңӢжі•иҷҪ然жҳҜиҜ„д»·жқңз”«зҡ„дёғеҫӢ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д№ҹеҸҜд»ҘдҪңдёәжқңиҜ—еҗ„дҪ“зҡ„е®ҡиҜ„гҖӮиҮідәҺд№үеұұеӯҰжқңпјҢе§ҡйјҗд»Ҙдёәд»–вҖңдҪҶж‘№е…¶еҸҘж јпјҢдёҚеҫ—е…¶дёҖж°”е–·и–„гҖҒйЎҝжҢ«зІҫзҘһгҖҒзәөжЁӘеҸҳеҢ–еӨ„вҖқгҖӮжЎҗеҹҺжҙҫи®Өдё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иҜ—жӯҢ并жңӘзңҹжӯЈжҠҠжҸЎжқңиҜ—жІүйғҒйЎҝжҢ«гҖҒзәөжЁӘеҸҳеҢ–зӯүзІҫеҰҷд№ӢеӨ„пјҢиҖҢд»…д»…еңЁеҸҘжі•гҖҒз« жі•еҸҠиҜ—дәәдёӘжҖ§еұ•зӨәзӯүж–№йқўжңүжүҖдҪ“зҺ°гҖӮйҰ–е…Ҳ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зҡ„еҸҘжі•ж•Ҳжі•жқңиҜ—гҖӮе§ҡйјҗи®Өдёәд№үеұұеӨҡеӯҰжқңиҜ—д№ӢвҖңеҸҘж јвҖқ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еҜ№д№үеұұиҜ—зҡ„иҜ„д»·д№ҹжіЁйҮҚ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гҖӮеҰӮд№үеұұиҜ—гҖҠеҶҷж„ҸгҖӢйў”иҒ”вҖңдәәй—ҙи·ҜжңүжҪјжұҹйҷ©пјҢеӨ©еӨ–еұұжғҹзҺүеһ’ж·ұвҖқдәҢеҸҘпјҢдёәдёүдёҖдәҢдёҖд№Ӣз»“жһ„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иҜҙжӯӨдәҢеҸҘеҸҘжі•вҖңдјјжқңвҖқгҖӮи§Ӯжқңз”«гҖҠд№қж—Ҙи“қз”°еҙ”ж°Ҹеә„гҖӢйўҲиҒ”вҖңи“қж°ҙиҝңд»ҺеҚғ涧иҗҪпјҢзҺүеұұй«ҳ并дёӨеі°еҜ’вҖқдёҺгҖҠе°ҸеҜ’йЈҹиҲҹдёӯеқҗгҖӢйў”иҒ”вҖңжҳҘж°ҙиҲ№еҰӮеӨ©дёҠеқҗпјҢиҖҒе№ҙиҠұдјјйӣҫдёӯзңӢвҖқпјҢеҸҘејҸйғҪжҳҜеүҚдёүеӯ—дёҖйЎҝпјҢ第еӣӣеӯ—дёәиҷҡеӯ—пјҢдә”е…ӯдёӨеӯ—дёәж–№дҪҚеҗҚиҜҚпјҢ第дёғеӯ—дёәе®һиҜҚгҖӮеҸҲеҰӮжқңз”«гҖҠйҮҺиҖҒгҖӢйў”иҒ”вҖңжё”дәәзҪ‘йӣҶжҫ„жҪӯдёӢпјҢиҙҫе®ўиҲ№йҡҸиҝ”з…§жқҘвҖқдёҺгҖҠйҖҒйҹ©еҚҒеӣӣжұҹдёңзңҒи§җгҖӢйўҲиҒ”вҖңй»„зүӣеіЎйқҷж»©еЈ°иҪ¬пјҢзҷҪ马жұҹеҜ’ж ‘еҪұзЁҖвҖқпјҢе…¶дёӯзҡ„第еӣӣеӯ—иҷҪ然йғҪдёҚжҳҜиҷҡеӯ—пјҢдҪҶдёүдёҖдәҢдёҖд№ӢеҸҘејҸдәҰеҗҢ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–№ж°Ҹд»Ҙ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е®үе®ҡеҹҺжҘјгҖӢвҖңеҸҘж јдјјжқңвҖқгҖӮе…¶ж¬Ў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зҡ„з« жі•еӯҰд№ жқңиҜ—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и®Өдё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гҖҠеҶҷж„ҸгҖӢдёҚд»…дёүеӣӣеҸҘз« жі•дјјжқңпјҢиҖҢдё”вҖңжң«еҸҘзӮ№йўҳпјҢз« жі•з”Ёз¬”з•ҘдјјжқңвҖқгҖӮжӯӨиҜ—йҰ–дәҢеҸҘвҖңзҮ•йӣҒиҝўиҝўйҡ”дёҠжһ—пјҢй«ҳз§Ӣжңӣж–ӯжӯЈй•ҝеҗҹвҖқжҖ»иө·пјҢдёӯй—ҙдёӨиҒ”вҖңдәәй—ҙи·ҜжңүжҪјжұҹйҷ©пјҢеӨ©еӨ–еұұжғҹзҺүеһ’ж·ұгҖӮж—Ҙеҗ‘иҠұй—ҙз•ҷиҝ”з…§пјҢдә‘д»ҺеҹҺдёҠз»“еұӮйҳҙвҖқеҶҷжҷҜпјҢеҜ“жҖқд№Ўд№Ӣжғ…пјҢжң«дәҢеҸҘвҖңдёүе№ҙе·ІеҲ¶жҖқд№ЎжіӘпјҢжӣҙе…Ҙж–°е№ҙжҒҗдёҚзҰҒвҖқзӮ№йўҳпјҢдҪ•з„Ҝи°“вҖңеҚіиҖҒжқңжүҖи°“вҖҳдёӣиҸҠдёӨејҖд»–ж—ҘжіӘвҖҷд№ҹвҖқгҖӮжқңз”«д№ӢгҖҠз§Ӣе…ҙе…«йҰ–гҖӢпјҢдёӯй—ҙдёӨиҒ”жҲ–еҶҷжҷҜпјҢжҲ–з”Ёе…ёж•…е…іиҒ”ж—¶дәӢпјҢжң«иҒ”зӮ№йўҳпјҢз»“жһ„дёҺжӯӨиҫғдёәзӣёдјјгҖӮиҖҢж–№ж°Ҹд№ӢжүҖд»ҘиҜҙвҖңз•ҘдјјвҖқ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Ҝ№жқҺиҜ—дёӯйҰ–еҸҘз”ЁвҖңдёҠжһ—вҖқд»ЈжҢҮж•…д№ЎдёҚеӨӘж»Ўж„ҸгҖӮж–№ж°Ҹи®ӨдёәпјҡвҖңдёҚзҹҘжӯӨиҜ—дҪңдәҺдҪ•ең°пјҢдјјжҳҜеңЁиңҖеҸҠеҲӨе®ҳж—¶пјҢиҖҢд»ҘзҮ•йӣҒдёҠжһ—дёәд№ЎпјҢж”Ҝжіӣж— и°“гҖӮдә”е…ӯеҶҷжҖқд№Ўд№ӢжҷҜпјҢеҸҘдәҰе№іж»һгҖӮвҖқгҖҠеҶҷж„ҸгҖӢйҰ–еҸҘз”ЁиӢҸжӯҰеҪ’еӣҪд№Ӣе…ёпјҢеӨ§жҰӮж–№дёңж ‘и§үеҫ—иӢҸжӯҰжҳҜз”ұеҢ—ж–№еҢҲеҘҙеҪ’еӣҪпјҢиҖҢд№үеұұжӯӨж—¶еңЁжҹід»Ійў–дёңе·қиҠӮеәҰдҪҝ幕дёӢпјҢеӣ жӯӨз”Ёе…ёдёҚеҲҮпјҢж•…и§үвҖңж”ҜжіӣвҖқгҖӮеҠ д№Ӣдә”е…ӯдёӨеҸҘеҶҷжҖқд№ЎиҖҢеҸҘејҸе№іж·Ўж»һ涩пјҢдёҚжҜ”жқңиҜ—д№Ӣйӣ„жқ°пјҢж•…и®ӨдёәжқҺиҜ—з« жі•иҷҪеӯҰжқңпјҢдҪҶдёҺжқңиҜ—е·®и·қз”ҡеӨ§пјҢжүҖд»ҘеҸӘжҳҜвҖңз•ҘдјјвҖқжқңиҜ—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д№үеұұжҹҗдәӣиҜ—дҪңиғҪеҶҷеҮәиҜ—дәәзҡ„зІҫзҘһйқўиІҢпјҢзҘһйҹөеҸҜдёҺжқңиҜ—еӘІзҫҺ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з»ҷдәҲ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гҖҠзӯ№з¬”й©ҝгҖӢй«ҳеәҰиҜ„д»·пјҡвҖңд№үеұұжӯӨзӯүиҜ—пјҢиҜӯж„Ҹжө©з„¶пјҢдҪңз”ЁзҘһйӯ„пјҢзңҹдёҚ愧жқңе…¬гҖӮеүҚдәәжҺЁдёәдёҖеӨ§е®—пјҢеІӮиҷҡд№ҹе“үпјҒвҖқеңЁд»–зңӢжқҘпјҢд№үеұұжӯӨиҜ—д№ӢвҖңиҜӯж„Ҹжө©з„¶вҖқеҸҠвҖңдҪңз”ЁзҘһйӯ„вҖқйғҪеҸҜд»ҘдёҺжқңиҜ—зӣёеӘІзҫҺгҖӮжүҖи°“вҖңиҜӯж„Ҹжө©з„¶вҖқпјҢе°ұжҳҜжҢҮжқңиҜ—д№ӢвҖңеҘҮжЁӘжҒЈиӮҶвҖқзҡ„йЈҺиІҢпјҢж–№еӣһиҜ„жӯӨиҜ—вҖңиө·еҸҘеҚҒеӣӣеӯ—еЈ®е“үвҖқпјҢдәҰжҳҜвҖңжө©з„¶вҖқд№Ӣи°“гҖӮвҖңдҪңз”ЁзҘһйӯ„вҖқеҲҷжҢҮиҜ—дёӯжңүдҪңиҖ…еңЁ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е°ҶиҜ—д№ӢзҘһз§°дёәвҖңйӯӮвҖқпјҢвҖңйӯӮвҖқд№ӢиҪҪдҪ“еҚіиҜӯиЁҖж–Үеӯ—еұӮйқўз§°дёәвҖңйӯ„вҖқпјҢеҘҪиҜ—иҮӘжңүйӯӮйӯ„гҖӮд»–иҜ„еҲҳй•ҝеҚҝзҡ„гҖҠзҷ»дҪҷе№ІеҸӨеҺҝеҹҺ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ЁҖеӨ–еҸҘеҸҘжңүзҷ»еҹҺдәәеңЁпјҢеҸҘеҸҘжңүдҪңиҜ—дәәеңЁпјҢжүҖд»Ҙз§°дёәдҪңиҖ…пјҢжҳҜи°“йӯӮйӯ„еҒңеҢҖгҖӮвҖқиҜ—д№ӢйӯӮеҚіиҜ—дәәд№ӢйӯӮпјҢдёҖйҰ–иҜ—жңҖе®ҢзҫҺзҡ„иЎЁзҺ°еә”иҜҘжҳҜйӯӮдёҺйӯ„зҡ„жңүжңәз»“еҗҲ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д№үеұұиҜ—вҖңеӨҡдҪҝж•…дәӢпјҢиЈ…иҙҙи—»йҘ°пјҢжҺ©е…¶жҖ§жғ…йқўзӣ®пјҢеҲҷдҪҶи§Ғйӯ„ж°”иҖҢж— йӯӮж°”вҖқпјӣдҪңдёәвҖңеҚғеҸӨдёҖдәәвҖқзҡ„жқңз”«вҖңеҸӘжҳҜзәҜд»ҘйӯӮж°”дёәз”ЁвҖқпјҢиҖҢвҖңйӯӮж°”еӨҡеҲҷжҲҗз”ҹжҙ»зӣёпјҢйӯ„ж°”еӨҡеҲҷдёәжӯ»ж»һвҖқгҖӮжҳҫ然еңЁж–№дёңж ‘зңӢжқҘ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еӨҡвҖңжӯ»ж»һвҖқпјҢдёҚиғҪдёҺиҖҒжқңзӣёжҸҗ并и®әгҖӮдҪҶд»–и®Ө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гҖҠзӯ№з¬”й©ҝгҖӢйӯӮйӯ„еҒңеҢҖпјҢдёҺжқңиҜ—дёҚзӣёдёҠдёӢгҖӮжІҲеҫ·жҪңдәҰдә‘жӯӨиҜ—вҖңз“ЈйҰҷиҖҒжқңпјҢж•…иғҪзҘһе®Ңж°”и¶іпјҢиҫ№е№…дёҚзӘҳвҖқпјҢиҝҷдёҺж–№дёңж ‘зҡ„ж„Ҹи§Ғзӣёиҝ‘гҖӮдәәеӨҡд»ҘжӯӨиҜ—дёҺгҖҠиңҖзӣёгҖӢ并жҸҗпјҢиҖҢеҲҳеӯҰй”ҙе…Ҳз”ҹи®ӨдёәпјҢе°ұжӯӨиҜ—д№ӢеҶ…е®№иҖҢиЁҖпјҢжӣҙжҺҘиҝ‘гҖҠе’ҸжҖҖеҸӨиҝ№гҖӢе…¶дә”пјҢвҖңдјҜд»Ід№Ӣй—ҙи§ҒдјҠеҗ•пјҢжҢҮжҢҘиӢҘе®ҡеӨұиҗ§жӣ№вҖқеҚівҖңз®Ўд№җжңүжүҚзңҹдёҚеҝқвҖқд№Ӣж„ҸпјҢиҖҢвҖңиҝҗ移жұүзҘҡз»ҲйҡҫеӨҚвҖқдёҖиҜӯпјҢвҖңжӣҙзӣҙеҸҜ移дҪңжӯӨиҜ—дё»йўҳвҖқгҖӮжӯЈжҳҜз”ұдәҺдәҢиҖ…еҰӮжӯӨзӣёзұ»пјҢж•…ж–№ж°Ҹиөһе…¶вҖңзңҹдёҚ愧жқңе…¬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иҝҳи®Ө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дәҢжңҲдәҢж—ҘгҖӢвҖңдјјжқңе…¬вҖқпјҢгҖҠжқңе·ҘйғЁиңҖдёӯзҰ»еёӯгҖӢвҖңжӢҹжқңдҪ“вҖқпјҢеҸӘжҳҜвҖңж·ұеҺҡжӣІжҠҳеӨ„дёҚеҸҠвҖқпјҢ然вҖңеЈ°и°ғдјјд№ӢвҖқгҖӮеңЁиҜ„и®әд№үеұұиҜ—ж—¶пјҢж–№ж°Ҹи„‘жө·дёӯжҖ»жҳҜжңүдёӘжқңиҜ—зҡ„ж ҮеҮҶжЁӘдәҳе…¶дёӯгҖӮж–№иҙһи§ӮеңЁиҜ„и®әе”җд»ЈиҜ—дәәж—¶пјҢдәҰеёёе°Ҷд№үеұұдёҺиҖҒжқңзӣёжҸҗ并и®әпјҡвҖңжүҖи°“вҖҳиҜӯдёҚжғҠдәәжӯ»дёҚдј‘вҖҷиҖ…пјҢйқһеҘҮйҷ©жҖӘиҜһд№Ӣи°“д№ҹпјҢжҲ–иҮізҗҶеҗҚиЁҖпјҢжҲ–зңҹжғ…е®һжҷҜпјҢеә”жүӢз§°еҝғпјҢеҫ—жңӘжӣҫжңүпјҢдҫҝеҸҜйңҮжғҠдёҖдё–гҖӮеӯҗзҫҺйӣҶдёӯпјҢеңЁеңЁзҡҶжҳҜпјҢеӣәж— и®әзҹЈгҖӮд»–еҰӮвҖҰвҖҰжқҺе•Ҷйҡҗд№ӢвҖҳдәҺд»Ҡи…җиҚүж— иҗӨзҒ«пјҢз»ҲеҸӨеһӮжқЁжңүжҡ®йёҰвҖҷпјҢдёҚиҝҮеҶҷжҷҜеҸҘиҖіпјҢиҖҢз”ҹеүҚдҫҲзәөпјҢжӯ»еҗҺиҚ’еҮүпјҢдёҖдёҖжүҳеҮәпјҢеҸҲеӨҚе…үеҪ©еҠЁдәәпјҢйқһжғҠдәәиҜӯд№ҺпјҹвҖқеңЁжЎҗеҹҺжҙҫзңӢжқ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жҳҜжқңз”«зҡ„继жүҝиҖ…пјҢеӣ иҖҢжҖ»жҳҜжңүж„ҸеҲҶиҫЁдәҢиҖ…й«ҳдёӢгҖӮдәҢгҖҒдёғеҫӢжҲҗжҙҫж–№дё–дёҫгҖҠе…°дёӣиҜ—иҜқ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зҺӢиҚҶе…¬д»Ҙдёәе…Ҳд»ҺжқҺд№үеұұе…ҘпјҢдјјеҸӘи°“дёғеҫӢгҖӮвҖқи§ӮзҺӢе®үзҹіе–ңиҜөд№үеұұвҖңйӣӘеІӯжңӘеҪ’еӨ©еӨ–дҪҝпјҢжқҫе·һзҠ№й©»ж®ҝеүҚеҶӣвҖқвҖңж°ёеҝҶжұҹж№–еҪ’зҷҪеҸ‘пјҢж¬ІеӣһеӨ©ең°е…ҘжүҒиҲҹвҖқдёҺвҖңжұ е…үдёҚеҸ—жңҲпјҢжҡ®ж°”ж¬ІжІүеұұвҖқвҖңжұҹжө·дёүе№ҙе®ўпјҢд№ҫеқӨзҷҫжҲҳеңәвҖқиҜёеҸҘпјҢеҲҷе…¶жүҖиөҸиҖ…пјҢдёҚжғҹдёғеҫӢпјҢдәҰжңүдә”иЁҖгҖӮ然жЎҗеҹҺжҙҫжңҖжҺЁеҙҮд№үеұұд№ӢдёғеҫӢпјҢжӯЈеҰӮж–№дёңж ‘жүҖдә‘вҖңзҺүжәӘдёғеҫӢпјҢеүҚдәәи°“иғҪе—Је“Қжқңе…¬пјҢеҲҷиҜҡжңӘеҸҜиҪ»и§ҶвҖқгҖӮеңЁд»–зңӢжқҘ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жңҖиғҪеҫ—жқңд№ӢзІҫй«“иҖ…еңЁдёғеҫӢпјҢиҝҷеңЁжЎҗеҹҺжҙҫеҹәжң¬иҫҫжҲҗе…ұиҜҶгҖӮд»ҺйҖүжң¬жқҘиҜҙ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жңҖзҲұиҖ…дёә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гҖӮеҲҳеӨ§ж«Ҷзј–гҖҠеҺҶд»ЈиҜ—зәҰйҖүгҖӢж—¶пјҢдәҺд№үеұұиҜ—з”„йҖүйўҮеӨҡпјҡеҚ·дәҢеҚҒдёҖйҖүе…¶дёғиЁҖеҸӨиҜ—гҖҠйҹ©зў‘гҖӢ1йҰ–пјҢеҚ·дёүеҚҒд№қйҖүе…¶дә”иЁҖеҫӢиҜ—20йҰ–пјҢеҚ·дә”еҚҒдёҖйҖүе…¶дёғиЁҖеҫӢиҜ—46йҰ–пјҢеҚ·е…ӯеҚҒе…«йҖүе…¶дә”иЁҖз»қеҸҘ2йҰ–пјҢеҚ·дёғеҚҒдёғйҖүе…¶дёғиЁҖз»қеҸҘ38йҰ–пјҢжүҖйҖүжңҖеӨҡиҖ…дёәдёғеҫӢгҖӮе§ҡйјҗ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йҖүе…¶дә”иЁҖеҫӢиҜ—еҚҒе…ӯйўҳ17йҰ–пјҢдёғеҫӢ32йҰ–пјҢдёғиЁҖз»қеҸҘ13йҰ–пјҢдәҰйҮҚе…¶дёғеҫӢгҖӮеҜ№дәҺе§ҡйјҗжүҖйҖүдёғеҫӢ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ж°ҸиҮӘ然йҰ–иӮҜпјҢз§°е…¶вҖңжңҖдёәдёҘжҙҒвҖқпјҢвҖңдҪҶеӯҳжӯӨзӯүдёүеҚҒдәҢйҰ–пјҢиҖҢеҲ е…¶жҷҰеғ»ж”ҜзҰ»гҖҒиҪ»иүіжөҒеҘ•иҖ…пјҢеІӮдёҚжҙ—жё…йқўзӣ®пјҢдёҺеӨ©дёӢзӣёи§ҒвҖқгҖӮдҪҶд»–еҜ№дәҺеҲҳеӨ§ж«Ҷеҗ„дҪ“еқҮйҖүжқҺиҜ—зҡ„еҒҡжі•пјҢеҲҷжү№иҜ„дёәвҖңжө·еі°еӨҡзҲұпјҢдёҚе…Қж»Ҙзҷ»иҖівҖқгҖӮиҮідәҺжӣҫеӣҪи—©йҖүгҖҠеҚҒ八家иҜ—й’һгҖӢж—¶пјҢд»…йҖүжқҺе•ҶйҡҗдёғеҫӢ117йҰ–пјҢдәҰеҸҜи§Ғд»–еҜ№жӯӨдҪ“зҡ„еҒҸзҲұгҖӮеңЁжЎҗеҹҺжҙҫзңӢжқҘ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жҲҗе°ұжңҖй«ҳиҖ…дёәдёғеҫӢпјҢиғҪеӨҹ继жүҝжқңиҜ—иҖ…дәҰеңЁжӯӨдҪ“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жӣҫиЁҖвҖңиҜ—иҺ«йҡҫдәҺдёғеҸӨвҖқпјҢеӣ дёәжӯӨдҪ“вҖңд»ҘжүҚж°”дёәдё»пјҢзәөжЁӘеҸҳеҢ–пјҢйӣ„иө·жө‘йўўпјҢдәҰз”ұеӨ©жҺҲпјҢдёҚеҸҜејәиғҪвҖқ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ңЁи°Ҳи®әдёғеҫӢж—¶пјҢд»–еҸҲиҜҙпјҡвҖңиҜ—д№ӢиҜёдҪ“пјҢдёғеҫӢдёәжңҖйҡҫпјҢе°ҡеңЁдёғиЁҖеҸӨиҜ—д№ӢдёҠгҖӮвҖқеӣ дёәжӯӨдҪ“вҖңжқҹдәҺе…«еҸҘд№ӢдёӯпјҢд»ҘзҹӯзҜҮиҖҢйЎ»е…·зәөжЁӘеҘҮжҒЈејҖйҳ–йҳҙйҳід№ӢеҠҝпјҢиҖҢеҸҲеҝ…иө·з»“иҪ¬жҠҳз« жі•и§„зҹ©дә•з„¶пјҢжүҖд»ҘдёәйҡҫвҖқгҖӮдёғеҸӨеҸҜд»ҘжүҚж°”дёәд№ӢпјҢд»»иҜ—дәәд№Ӣж„Ҹд»Ҙдёәиө·з»“пјӣиҖҢдёғеҫӢеҝ…йЎ»еңЁи§„е®ҡзҡ„ж јеҫӢеҸҠз»“жһ„дёӯж–Ҫеұ•жүҚж°”пјҢеӣ жӯӨе…¶йҡҫеәҰиҮӘ然еңЁдёғеҸӨд№ӢдёҠгҖӮж–№ж°Ҹе°ҶиҜ—еҸІдёҠзҡ„дёғеҫӢеҗҚ家жҖ»з»“дёәвҖңдәҢжҙҫдёғ家вҖқпјҢжүҖи°“вҖңдәҢжҙҫвҖқпјҢеҚіжқңз”«дёҺзҺӢз»ҙпјӣжүҖи°“вҖңдёғ家вҖқпјҢйҰ–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пјҢеҗҺйқўдҫқж¬Ўдёәй»„еәӯеқҡгҖҒйҷҶжёёгҖҒжқҺжўҰйҳігҖҒжқҺж”ҖйҫҷгҖҒйҷҲеӯҗйҫҷгҖҒй’ұи°ҰзӣҠгҖӮиҮідәҺеӨ§еҺҶеҚҒжүҚеӯҗгҖҒеҲҳй•ҝеҚҝгҖҒзҷҪеұ…жҳ“зӯүиҷҪдәҰи¶ід»Ҙз§°е®—пјҢдҪҶйғҪдёҚеҸҠд№үеұұвҖңеҲ«дёәдёҖжҙҫвҖқгҖӮз”ұжӯӨж—ў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ж–№ж°ҸеҜ№дёғ家иЈҒйҮҸд№ӢдёҘж јпјҢдәҰеҸҜи§Ғе…¶еҜ№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д№ӢжҺЁеҙҮгҖӮе§ҡйјҗдә‘пјҡвҖңзҺүжәӘз”ҹиҷҪжҷҡеҮәпјҢиҖҢжүҚеҠӣе®һдёәеҚ“з»қгҖӮдёғеҫӢдҪіиҖ…пјҢеҮ ж¬ІиҝңиҝҪжӢҫйҒ—пјӣе…¶ж¬ЎиҖ…пјҢзҠ№и¶іиҝ‘жҺ©еҲҳзҷҪгҖӮвҖқж–№дёңж ‘д№Ӣи®әпјҢ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жүҝе…¶еёҲд№Ӣи§ӮзӮ№гҖӮ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пјҢеңЁжқңгҖҒзҺӢдәҢжҙҫд№ӢеҗҺеҸҰжҲҗдёҖжҙҫпјҢдё”вҖңе®һе…јдёҠдәҢжҙҫвҖқ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зҺүжәӘдёғеҫӢе…јжңүжқңиҜ—еҸҠзҺӢиҜ—д№ӢеҰҷ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е“Ғе‘іжқңз”«дёғеҫӢеҰҷеңЁвҖңеҰӮеӨӘеҸІе…¬ж–ҮпјҢд»Ҙз–Ҹж°”дёәдё»пјӣйӣ„еҘҮйЈһеҠЁпјҢзәөжҒЈеЈ®жөӘпјҢеҮҢи·ЁеҸӨд»ҠпјҢеҢ…дёҫеӨ©ең°вҖқпјҢжӯӨдёәвҖңжһҒеўғвҖқпјӣзҺӢз»ҙдёғеҫӢеҰҷеңЁвҖңеҰӮзҸӯеӯҹеқҡж–ҮпјҢд»ҘеҜҶеӯ—дёәдё»пјӣеә„дёҘеҰҷеҘҪпјҢеӨҮдёүеҚҒдәҢзӣёпјӣ瑶жҲҝз»ӣйҳҷпјҢд»ҷе®ҳд»Әд»—пјҢйқһеӨҚе°ҳй—ҙиүІзӣёвҖқгҖӮжҚ®жӯӨжҸҸиҝ°пјҢжқңгҖҒзҺӢдәҢжҙҫпјҢе®һеҚійҳіеҲҡдёҺйҳҙжҹ”дёӨз§Қе®ЎзҫҺеўғз•ҢпјҡжқңиҜ—вҖңйӣ„еҘҮйЈһеҠЁпјҢзәөжҒЈеЈ®жөӘвҖқпјҢеҚіе…·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пјӣзҺӢиҜ—вҖң瑶жҲҝз»ӣйҳҷпјҢд»ҷе®ҳд»Әд»—вҖқпјҢе®һе…·йҳҙжҹ”д№ӢзҫҺгҖӮе§ҡйјҗи®әж–ҮжңүдёӨз§Қеўғз•ҢпјҡдёҖдёә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пјҢдёҖдёәйҳҙжҹ”д№ӢзҫҺгҖӮд»–иҝҪжұӮзҡ„жңҖй«ҳеўғз•ҢжҳҜвҖңйҳіеҲҡйҳҙжҹ”пјҢ并иЎҢиҖҢдёҚе®№еҒҸеәҹвҖқзҡ„зҫҺеӯҰзҗҶжғіпјҢиҖҢиӢҘвҖңжңүе…¶дёҖз«ҜиҖҢз»қдәЎе…¶дёҖвҖқпјҢе®ҡ然жҳҜвҖңеҝ…ж— дёҺдәҺж–ҮиҖ…вҖқгҖӮ然иҖҢпјҢд»–еҸҲи®ӨиҜҶеҲ°пјҢеҸӨд»ЈжңҖдјҹеӨ§зҡ„ж–ҮеӯҰ家пјҢд№ҹеҫҲйҡҫеҒҡеҲ°дәҢиҖ…жҜ«ж— вҖңеҒҸеәҹвҖқпјҢеҝ…еҒҸдәҺдёҖз«ҜпјҢеӣ дёәеӨ©ең°д№ӢйҒ“е°ҡйҳіиҖҢдёӢйҳҙпјҢйӮЈд№ҲвҖңж–Үд№Ӣйӣ„дјҹиҖҢеҠІзӣҙиҖ…пјҢеҝ…иҙөдәҺжё©ж·ұиҖҢеҫҗе©ү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§ҡй—ЁејҹеӯҗеңЁзҫҺеӯҰиҝҪжұӮдёҠеҙҮе°ҡ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гҖӮз®ЎеҗҢдә‘пјҡвҖңеҸӨжқҘж–ҮдәәйҷҲд№үеҗҗиҫһпјҢеҫҗе©үдёҚеӨұжҖҒеәҰпјҢеҺҶд»ЈеӨҡжңүпјӣиҮіиӢҘйӘҸжЎҖе»үжӮҚпјҢз§°йӣ„жүҚиҖҢи¶іеҸ·дёәеҲҡиҖ…пјҢеҚғзҷҫе№ҙиҖҢеҗҺдёҖйҒҮз„үиҖігҖӮвҖқжң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д»–жҸҗеҖЎвҖңдёҺе…¶еҒҸдәҺйҳҙд№ҹпјҢеҲҷж— е®ҒеҒҸдәҺйҳівҖқ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еңЁжӯӨж–№йқўдёҺз®Ўж°ҸеҗҢпјҢж•…жҺЁжқңиҜ—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дёәвҖңжһҒеўғвҖқгҖӮж–№ж°Ҹи®Өдёәд№үеұұиҜ—е…јжңүжқңгҖҒзҺӢдәҢжҙҫд№ӢеҰҷпјҢеӨ§жҰӮе°ұжҳҜжҢҮе…¶иҜ—е…је…·йҳіеҲҡдёҺйҳҙжҹ”д№ӢзҫҺгҖӮеңЁжІҲеҫ·жҪңзңӢжқҘпјҢжқңиҜ—вҖңзәөжЁӘеҮәжІЎдёӯпјҢеӨҚеҗ«и•ҙи—үеҫ®иҝңд№ӢиҮҙгҖӮзӣ®дёәвҖҳеӨ§жҲҗвҖҷпјҢйқһиҷҡиҜӯд№ҹвҖқ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жқңиҜ—д№ҹжҳҜдәҢзҫҺе…је…·зҡ„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ж–№ж°Ҹе°Ҷе…¶и§Ҷдёә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зҡ„жңҖй«ҳиЎЁзҺ°гҖӮд№үеұұиҜ—е…је…·дәҢжҙҫпјҢдәҺеЈ®зҫҺд№ӢдёӯеҸҲе…јзҶ”йҳҙжҹ”д№ӢзҫҺгҖӮж–№з»©иҜ„гҖҠиҢӮйҷө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—Ҹй”Ӣж•ӣй”·дәҺе®ҸйҹіеЈ®йҮҮд№ӢдёӯпјҢдёғеҫӢж— жӯӨжі•й—ЁгҖӮвҖқжүҖи°“вҖңи—Ҹй”Ӣж•ӣй”·вҖқеҚіеҒҸдәҺйҳҙжҹ”дёҖйқўпјҢвҖңе®ҸйҹіеЈ®йҮҮвҖқеҲҷеұһйҳіеҲҡд№ӢзҫҺпјҢжӯӨиҜ—жңҖеӨ§жҲҗе°ұеңЁдәҺзәійҳҙжҹ”дәҺйҳіеҲҡпјҢе®һзҺ°дәҢиҖ…зҡ„иһҚеҗҲгҖӮеҜ№дәҺжӯӨиҜ—зҡ„дё»ж—ЁпјҢиҜ„и®әиҖ…жңүдёҚеҗҢзҡ„зңӢжі•пјҢдёҖжҙҫи®ӨдёәжҳҜж…ЁжӯҰе®—пјҢдёҖжҙҫи®ӨдёәжҳҜи®ҪжӯҰе®—пјҢиҖҢж–№ж°ҸжҢҒеҗҺдёҖз§Қи§ӮзӮ№пјҢжүҖд»Ҙж–№з»©иҜҙвҖңжӯӨиҜ—е…ЁдёҺжӯҰе®—еҜ№з°ҝвҖқгҖӮйҰ–иҒ”вҖңжұү家еӨ©й©¬еҮәи’ІжўўпјҢиӢңи“ҝжҰҙиҠұйҒҚиҝ‘йғҠвҖқжҳҜиЁҖвҖңз©·е…өз•ҘиҝңвҖқпјӣйў”иҒ”вҖңеҶ…иӢ‘еҸӘзҹҘеҗ«еҮӨи§ңпјҢеұһиҪҰж— еӨҚжҸ’йёЎзҝҳвҖқпјҢдёҠеҸҘиЁҖз”°зҢҺпјҢдёӢеҸҘиЁҖеҫ®иЎҢпјӣйўҲиҒ”вҖңзҺүжЎғеҒ·еҫ—жҖңж–№жң”пјҢйҮ‘еұӢдҝ®жҲҗиҙ®йҳҝеЁҮвҖқпјҢдёҠеҸҘиЁҖжұӮд»ҷпјҢдёӢеҸҘиЁҖиҝ‘иүІпјӣе°ҫиҒ”вҖңи°Ғж–ҷиӢҸеҚҝиҖҒеҪ’еӣҪпјҢиҢӮйҷөжқҫжҹҸйӣЁиҗ§иҗ§вҖқпјҢжӯӨвҖң收е°ӨеҰҷвҖқгҖӮж–№ж°ҸжңӘжҳҺиЁҖеҰҷеңЁдҪ•еӨ„пјҢдҪ•з„Ҝдә‘пјҡвҖңиҗҪеҸҘеҸӘеҖҹеӯҗеҚҝдёҖиЎ¬пјҢйЈҺеҲәиҮӘи§ҒдәҺиЁҖеӨ–гҖӮвҖқ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ж–№з»©жүҖиЁҖеҰҷеӨ„еҚіеңЁдәҺжӯӨгҖӮжӯӨиҜ—йҖ иҜӯйӣ„еҘҮжҒЈиӮҶпјҢеӯ—йҮҢиЎҢй—ҙж— дёҚеҢ…еҗ«зқҖеҜ№е”җжӯҰе®—зҡ„и®ҪеҲәпјҢдё”жӯӨз§Қи®ҪеҲәдәҺиЁҖеӨ–и§Ғд№ӢпјҢеҗ«и“„еҮәд№ӢпјҢж•…д»ҘвҖңи—Ҹй”Ӣж•ӣй”·дәҺе®ҸйҹіеЈ®йҮҮд№ӢдёӯвҖқеҠ д»ҘжҰӮжӢ¬пјҢе…је…·жқңгҖҒзҺӢдёғеҫӢзҡ„й•ҝеӨ„пјҢд№ҹжӯЈеӣ жӯӨпјҢжӯӨиҜ—еҫ—еҲ°д»–们жңҖй«ҳзҡ„иҜ„д»·гҖӮеңЁж–№з»©зңӢжқ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д№ӢеүҚзҡ„дёғеҫӢдёӯж— жӯӨдёҖжҙҫпјҢ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зҡ„жҲҗе°ұдёҺд»·еҖјжӯЈеңЁдәҺжӯӨ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з»§жүҝе…¶зҲ¶и§ӮзӮ№пјҢд»ҘеҲҡжҹ”зӣёжөҺдёә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д№ӢжңҖеӨ§зү№иүІпјҢе…¶еҜ№гҖҠд№қжҲҗе®«гҖӢзҡ„иҜ„д»·дәҰиғҪиҜҙжҳҺиҝҷдёҖи§ӮзӮ№гҖӮиҜ—дә‘пјҡвҖңеҚҒдәҢеұӮеҹҺйҳҶиӢ‘иҘҝпјҢе№іж—¶йҒҝжҡ‘жӢӮиҷ№йң“гҖӮдә‘йҡҸеӨҸеҗҺеҸҢйҫҷе°ҫпјҢйЈҺйҖҗе‘ЁзҺӢе…«йӘҸ蹄гҖӮеҗҙеІіжҷ“е…үиҝһзҝ пјҢз”ҳжіүжҷҡжҷҜдёҠдё№жўҜгҖӮиҚ”жһқеҚўж©ҳжІҫжҒ©е№ёпјҢйёҫй№ҠеӨ©д№Ұж№ҝзҙ«жіҘгҖӮвҖқж–№з»©иҜ„дә‘пјҡвҖңиҚ”ж©ҳеӨҸзҶҹпјҢж•…иҙЎдәҺд№қжҲҗе®«пјҢвҖҳзҙ«жіҘвҖҷвҖҳеӨ©д№ҰвҖҷпјҢеҸӘдёәдәҢзү©пјҢи®ҪеҲәжһҒеҲ»пјҢ然дёҚи§үпјҢж•…еҰҷгҖӮвҖқеҸҲдә‘пјҡвҖңиҒ”еҜ№д№Ӣе·ҘпјҢжқЁгҖҒеҲҳжүҖиғҪгҖӮе…¶е№іе№іеҶҷеҺ»пјҢдёҚжҒӨж°‘дҫқд№Ӣж„ҸиҮӘи§ҒпјҢиЁҖд№Ӣж— зҪӘпјҢй—»д№Ӣи¶іжҲ’пјҢеҲҷжқЁгҖҒеҲҳж— жӯӨдҪңз”ЁгҖӮвҖқиҝҷдёӨеҸҘиҜқжқҘиҮӘдҪ•з„Ҝ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еј•д№ӢеҶ д»ҘвҖңе…Ҳеҗӣдә‘вҖқпјҢе°ҶжӯӨи§Ҷдёәе…¶зҲ¶д№Ӣи§ӮзӮ№гҖӮдҪ•гҖҒж–№жҢҮеҮәжӯӨиҜ—и®ҪеҲәж„Ҹе‘із”ҡжө“пјҢ然дёҚзӣҙжҺҘи®ҪеҲә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ң«еҸҘпјҢеӨ©еӯҗд»Ҙзҙ«жіҘе°ҒеӨ©д№ҰпјҢеҰӮжӯӨйғ‘йҮҚе…¶дәӢпјҢеҚҙеҸӘжҳҜдёәдәҶиЎЁеҪ°иҝӣиҙЎиҚ”жһқгҖҒеҚўж©ҳд№ӢдәәпјҢи®ҪеҲәжһҒдёәе°–еҲ»пјҢ然еҸҲи®©дәәдёҚи§үпјҢиҜ—д№ӢеҰҷжӯЈеңЁдәҺжӯӨгҖӮйҷҶжҳҶжӣҫдә‘пјҡвҖңе®«еңЁеҮӨзҝ”пјҢеҺ»дә¬еёҲдёүзҷҫйҮҢпјҢжҜҸеІҒйҒҝжҡ‘дәҺжӯӨпјҢеҫҖжқҘй©ҝйӘҡеҸҜзҹҘпјҢеҰҷеңЁеҗ«иҖҢдёҚйңІпјҢдҪҝиҜ»иҖ…иҮӘдјҡдәҺеӯ—еҸҘд№ӢеӨ–гҖӮвҖқжӯӨиҜ—дёҺгҖҠиҢӮйҷөгҖӢеҗҢпјҢйғҪжҳҜе°Ҷи®ҪеҲәеҜ“дәҺжҸҸеҶҷд№Ӣдёӯ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иҜ„гҖҠд№қжҲҗе®«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ӯӨж–№жҳҜд№үеұұжң¬иүІжӯЈе®—пјҢеҰӮе»әз« е®«ж®ҝпјҢ规еҲ¶еә”з»ігҖӮвҖқвҖңе»әз« е®«ж®ҝвҖқж— з–‘жҳҜеҪўе®№жӯӨиҜ—д№Ӣж°”иұЎи§„жЁЎе®ҸеӨ§пјҢ然еҰӮжӯӨе®ҸеӨ§д№Ӣе·ҘзЁӢпјҢеҸҲиғҪеҒҡеҲ°вҖң规еҲ¶еә”з»івҖқпјҢеҶ…йғЁз»“жһ„дёҺеёғеұҖжңүжқЎдёҚзҙҠпјҢе°ұиҜ—жң¬иә«иҖҢиЁҖпјҢйҰ–е°ҫејҖйҳ–иҪ¬жҠҳжҳ з…§еҲҶжҳҺпјҢе°ҶжүҚж°”иһҚдәҺ规зҹ©д№ӢдёӯпјҢд№үеұұд№ӢиғҪдәӢе…·дәҺжӯӨ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ҰӮвҖңе»әз« е®«ж®ҝвҖқиҲ¬зҡ„е®ҸеӨ§ж°”иұЎпјҢеҸҲиғҪдёҺеҗ«и“„дёҚйңІзҡ„и®ҪеҲәзӣёз»ҹдёҖпјҢдәҰжҳҜвҖңж•ӣй”Ӣи—Ҹй”·дәҺе®ҸйҹіеЈ®йҮҮвҖқд№ӢдёӯпјҢеҗҢж ·еҒҡеҲ°йҳіеҲҡдёҺйҳҙжҹ”зҡ„иһҚеҗҲпјҢд№ҹдҪ“зҺ°еҮә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дҪңдёәжқңз”«гҖҒзҺӢз»ҙд№ӢеҗҺ第дёүжҙҫзҡ„зү№иүІгҖӮдёүгҖҒи—»йҘ°иҪ»иүі 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иһҚеҗҲйҳіеҲҡдёҺйҳҙжҹ”пјҢеңЁе§ҡйјҗжүҖиҝҪжұӮзҡ„е®ЎзҫҺеўғз•ҢдёӯпјҢеҪ“еұһжңҖдёҠдёҖеұӮ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ЎҗеҹҺжҙҫ并жңӘе°ҶжқҺе•ҶйҡҗзҪ®дәҺжқңз”«д№ӢйҳіеҲҡгҖҒзҺӢз»ҙд№Ӣйҳҙжҹ”д№ӢдёҠпјҢиҖҢжҳҜе°Ҷе…¶еҲ—дёәйҖҠдәҺ他们зҡ„第дёүжҙҫ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еӣ дёәжқҺиҜ—д№Ӣи—»йҘ°дёҚз¬ҰеҗҲжЎҗеҹҺжҙҫзҡ„е®ЎзҫҺиҝҪжұӮгҖӮж–№з»©дә‘пјҡвҖңдёғеҫӢдёӯпјҢд»Ҙж–ҮиЁҖеҸҷдҝ—жғ…е…ҘеҰҷиҖ…пјҢеҲҳе®ҫе®ўд№ҹпјӣж¬ЎеҲҷд№үеұұпјҢд№үеұұиө„д№Ӣд»Ҙи—»йҘ°гҖӮвҖқеҰӮжһңиҜҙж–№з»©жӯӨиЁҖ并жңӘеӣ дёәи—»йҘ°иҖҢиҙ¬дҪҺд№үеұұиҜ—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ж–№дёңж ‘еҲҷжҳҺзЎ®ең°иЎЁиҫҫеҮәеҜ№жқҺиҜ—и—»йҘ°зҡ„еҸҚж„ҹдёҺдёҚж»ЎпјҡвҖңж ‘и°“жүҖе«ҢдәҺд№үеұұиҖ…пјҢж”ҝз—…е…¶и—»йҘ°гҖӮвҖқеңЁиҝҷдёҖзӮ№дёҠ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йҡҫеҫ—ең°дёҺе…¶зҲ¶и§ӮзӮ№дёҚеҗҢгҖӮжЎҗеҹҺжҙҫиӯҰжғ•и—»йҘ°иҜ—йЈҺпјҢжңүзқҖжӮ д№…зҡ„дј з»ҹдёҺж·ұеҲ»зҡ„жҖқжғіеҹәзЎҖгҖӮйҰ–е…Ҳ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еҸ—зЁӢжңұзҗҶ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иҜ—ж–ҮиҝҪжұӮжңҙе®һж— еҚҺзҡ„жң¬иүІд№ӢзҫҺпјҢиҖҢеҸҚеҜ№вҖңиҷҡиҪҰд№ӢйҘ°вҖқгҖӮж–№иӢһе…ідәҺеҸӨж–Үзҡ„з§Қз§ҚзҰҒеҝҢдёӯпјҢжңүдёҖжқЎе°ұжҳҜеҸҚеҜ№вҖңе…ӯжңқи—»дёҪеҫҳиҜӯвҖқиҝӣе…ҘеҸӨж–ҮгҖӮеңЁвҖңиҜ—ж–ҮдёҖзҗҶвҖқзҡ„и§ӮеҝөдёӢ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Ҝ—жӯҢдәҰеҸҚеҜ№е…ӯжңқи—»дёҪд№ӢйЈҺпјҢиҖҢд№үеұұиҜ—д№Ӣи—»йҘ°жӯЈжәҗдәҺйҪҗжўҒгҖӮеҶҜзҸӯгҖҠй’қеҗҹжқӮеҪ•гҖӢеҚ·дёғдә‘пјҡвҖңжқҺзҺүжәӘе…Ёжі•жқңпјҢж–Үеӯ—иЎҖи„үпјҢеҚҙдёҺйҪҗжўҒдәәзӣёжҺҘгҖӮвҖқжЎҗеҹҺжҙҫи®ӨдёәпјҢиҜ—ж–ҮиҝҮдәҺж–ҮеҚҺдјҡжү°д№ұеҝғжҖ§пјҢеӣ жӯӨеҝ…йЎ»еҜ№жӯӨдёҘеҠ жҸҗйҳІгҖӮзЁӢжўҰжҳҹз¬әжіЁд№үеұұиҜ—ж—¶пјҢжӣҫйӮҖиҜ·иЎЁе…„ж–№дё–дёҫеҚҸеҠ©пјҢеҗҺиҖ…еҜ№жӯӨдәӢи®°иҪҪйҒ“пјҡвҖңеҚ—еҪ’иҲҹиҝҮжү¬е·һпјҢиЎЁејҹзЁӢзј–дҝ®еҚҲжЎҘз•ҷз¬әжіЁжқҺд№үеұұйӣҶгҖӮвҖқжңүжӯӨжёҠжәҗпјҢж–№ж°Ҹжң¬еә”еҪ“еҜ№жқҺиҜ—жңүзү№еҲ«зҡ„жғ…ж„ҹпјҢ然иҖҢпјҢд»–еҚҙжһҒдёәеҺҢжҒ¶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ҡвҖңеӨ§жҠөеӯҰй•ҝеҗүиҖҢдёҚеҫ—е…¶е№Ҫж·ұеӯӨз§ҖиҖ…пјҢжүҖдёәйҒӮе •жҒ¶йҒ“гҖӮд№үеұұеӨҡеӯҰд№ӢпјҢдәҰзҡҶжҒ¶гҖӮвҖқдёҖдёӘвҖңжҒ¶вҖқеӯ—жөҒйңІе…¶еҝғеЈ°пјҢд№ӢжүҖд»ҘеҰӮжӯӨпјҢжӯЈеңЁдәҺд№үеұұиҜ—зҡ„и—»йҘ°гҖӮд»–и®ӨдёәпјҡвҖңе…¶ж–ҮеӨӘз№ҒзјӣпјҢеҸҚжҒҗдә”иүІд№ұзӣ®пјҢдә”еЈ°д№ұиҒӘд№ҹгҖӮвҖқеӣ дёәжқҺиҜ—вҖңз№ҒзјӣвҖқпјҢжҒҗжғ‘д№ұдәәд№ӢеҝғжҷәпјҢз”ұжҳҜиҖҢжҺ’ж–Ҙе…¶иҜ—гҖӮй’ұжҫ„д№Ӣи®әиҜ—еҙҮе°ҡжң¬иүІпјҢеӣ иҖҢеҜ№жңүвҖңжё©жқҺд№ӢйҒ—е“ҚвҖқд№Ӣз§°зҡ„й’ұи°ҰзӣҠеҸҠиҷһеұұиҜ—жҙҫе—ңеҘҪжқҺиҜ—иЎЁзҺ°еҮәдёҚи§ЈгҖӮд»–и§ЈйҮҠвҖңз©·иҖҢеҗҺе·ҘвҖқж—¶дә‘пјҡвҖңжҳ”дәәи°“иҜ—иғҪз©·дәәпјҢйқһд№ҹпјҢжғҹз©·иҖҢиҜ—д№ғе·ҘиҖігҖӮиҖҢд»Ҡд№ӢиҫҫиҖ…пјҢзұ»еҘҪдёәиҜ—пјҢеҲҷеҝ…е…¶иғҪеӨ–еЈ°еҲ©пјҢи–„е—ңж¬ІпјҢж„ҸжҖқиҗ§й—ІпјҢдёҚд»Ҙдҝ—и§ҒзҙҜе…¶иғёпјҢиҷҪиҫҫпјҢиҰҒдёҚеӨұз©·иҖігҖӮвҖҰвҖҰеҗҫи§ҒеҗҙдјҡдәәиҜ—пјҢеҘҪдёәз»®дёҪиҜӯпјҢе…¶дәәжңӘеҝ…иғҪе°Ҫиҫҫд№ҹпјҢд»ҘеҜ’й…ёд№ иҙөдәәе®№пјҢеҫ’иҮӘеӨұе…¶жң¬иүІгҖӮвҖқеңЁд»–зңӢжқҘпјҢз»®дёҪд№ӢиҜӯеҢ…еҗ«зқҖеҜ№еЈ°еҲ©зҡ„еҗ‘еҫҖпјҢиҖҢиҜ—д№ӢжұӮе·ҘпјҢйҰ–иҰҒд»»еҠЎеңЁжҖ§жғ…зҡ„жҒ¬ж·ЎпјҢж•…йЎ»жҺ’ж–Ҙе—ңж¬ІгҖҒж‘’ејғз»®иҜӯпјҢжң¬иүІдёәжңҖдёҠгҖӮжү§е®Ҳжң¬иүІзҡ„е®ЎзҫҺзҗҶеҝөпјҢд»–иҮӘ然дёҚж»Ўд№үеұұиҜ—д№Ӣи—»йҘ°гҖӮе…¶ж¬ЎпјҢи—»йҘ°еӨӘз”ҡеҲҷжҜ”е…ҙйҡҗиҖҢдёҚеҪ°гҖӮжқҺе•ҶйҡҗиҮӘйҒ“е…¶дёәиҜ—вҖңжҘҡиҜӯеҗ«жғ…зҡҶжңүжүҳвҖқпјҢж•…еҗҺдәәи§Је…¶иҜ—пјҢдәҰе–ңжҸЈж‘©е…¶еҜ„жүҳд№Ӣж„ҸгҖӮй’ұи°ҰзӣҠжӯЈжҳҜеңЁжӯӨеұӮйқўжҺЁеҙҮжқҺиҜ—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д№үеұұеҪ“еҚ—еҢ—ж°ҙзҒ«пјҢдёӯеӨ–з®қз»“пјҢиӢҘе–‘иҖҢж¬ІиЁҖд№ҹпјҢиӢҘйӯҮиҖҢжұӮеҜӨд№ҹпјҢдёҚеҫ—дёҚзәЎжӣІе…¶жҢҮпјҢиҜһи°©е…¶иҫһпјҢе©үеЁҲжүҳеҜ„пјҢи°ңиҝһжҜ”пјҢжӯӨдәҰйЈҺдәәд№ӢйҒҗжҖқпјҢе°Ҹйӣ…д№ӢеҜ„дҪҚд№ҹгҖӮеҗҫд»Ҙдёәд№үеұұд№ӢиҜ—пјҢжҺЁеҺҹе…¶еҝ—д№үпјҢеҸҜд»Ҙйј“еҗ№е°‘йҷөгҖӮвҖқжқҺе•Ҷйҡҗз”ҹжҙ»еңЁж”ҝжІ»еҠЁиҚЎдёҚе®үзҡ„жҷҡе”җж—¶жңҹпјҢж•…дёҚеҫ—дёҚд»ҘжҜ”е…ҙеҜ„жүҳзҡ„ж–№ејҸдёәиҜ—пјӣй’ұи°ҰзӣҠеӨ„еңЁзӣёиҝ‘зҡ„ж—¶дё–пјҢж•…дәҺжқҺиҜ—ж„ҹеҗҢиә«еҸ—пјҢеӣ жӯӨжҺЁеҙҮеӨҮиҮігҖӮиў«и§Ҷдёәиҙ°иҮЈзҡ„й’ұи°ҰзӣҠйҒӯеҲ°ж·ұеҸ—зҗҶеӯҰжҖқжғіеҪұе“Қзҡ„жЎҗеҹҺжҙҫд№Ӣй„ҷеӨ·пјҢд»–жүҖжҺЁеҙҮзҡ„жқҺе•ҶйҡҗдәҰеӣ жӯӨиҝһеёҰеҸ—еұҲгҖӮй’ұжҫ„д№Ӣ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й”Ұз‘ҹгҖӢпјҢжӮјдәЎиҜ—д№ҹпјҢжғ…жҖқйўҮж·ұпјҢиҖҢдёәж•…е®һжүҖжҺ©пјҢиҮід»Өи§ЈиҖ…дёҚзҹҘйўҳд№үжүҖеңЁгҖӮ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иҜ—зҜҮпјҢе®«еӘӣд»ҷеҰғй”ҷеҮәдә’и§ҒпјҢеҸӘжҳҜжғ…жҳөйҰҷеҘҒпјҢиҜҚеҸ–иүіејӮпјҢжңӘе°қжңүж„ҹдәәдәҺеҫ®пјҢйЈҺдәәиЁҖеӨ–иҖ…пјҢиҖҢдёәд№Ӣ委жӣІз”ҹи§ЈпјҢиЁҖжңүжүҳеҜ„иҖ…пјҢеҰ„д№ҹгҖӮвҖқеҲҳеӯҰй”ҙе…Ҳз”ҹи®ӨдёәжӯӨиҜӯжңүеҸҜиғҪжҳҜй’ҲеҜ№жңұй№Өйҫ„д№Ӣз¬әжіЁиҖҢеҸ‘пјҢз”ҡжҳҜгҖӮй’ұж°ҸеҸҚеҜ№и®әиҖ…д»Ҙдёәд№үеұұзҲұжғ…иҜ—жңүеҜ„жүҳпјҢйҖҖдёҖжӯҘиҖҢиЁҖпјҢеҚідҪҝжңүеҜ„жүҳпјҢжңүжғ…жҖқпјҢдҪҶиҝҷдәӣеқҮиў«ж•…е®һдёҺи—»йҘ°йҒ®жҺ©пјҢеҫҲйҡҫзҙўи§ЈгҖӮиҙәиЈідә‘пјҡвҖңйӯҸжҷӢд»ҘйҷҚпјҢеӨҡе·ҘиөӢдҪ“пјҢд№үеұұзҠ№е…јжҜ”е…ҙгҖӮвҖқеҜ№жӯӨ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жҸҗеҮәејӮи®®пјҡвҖңж„ҡи°“и—»йҘ°еӨӘз”ҡпјҢеҲҷжҜ”е…ҙйҡҗиҖҢдёҚи§ҒзҹЈгҖӮвҖқд»–и®Өдёәи—»йҘ°еҰЁзўҚжҜ”е…ҙеҜ„жүҳзҡ„е‘ҲзҺ°пјҢиҝҷз§ҚзңӢжі•дёҺй’ұжҫ„д№ӢдёҖиҮҙ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и—»йҘ°жҺ©зӣ–зңҹжҖ§жғ…гҖӮй’ұи°ҰзӣҠжҺЁеҙҮ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зӯүзҲұжғ…иҜ—е…·жңүж„ҹеҠЁдәәеҝғзҡ„еҠӣйҮҸпјҡвҖңд№үеұұ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иҜёд»ҖпјҢжҳҘеҘіиҜ»д№ӢиҖҢе“ҖпјҢз§ӢеЈ«иҜ»д№ӢиҖҢжӮІгҖӮвҖқдҪҶй’ұжҫ„д№Ӣ并дёҚи®ӨеҗҢиҝҷдёҖи§ӮзӮ№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жқҺе•Ҷйҡҗиҝҷзұ»иҜ—вҖңжғ…жҳөйҰҷеҘҒпјҢиҜҚеҸ–иүіејӮвҖқпјҢеӣ жӯӨвҖңжңӘе°қжңүж„ҹдәәдәҺеҫ®пјҢйЈҺдәәиЁҖеӨ–иҖ…вҖқгҖӮд»–еҗҰе®ҡиҝҷзұ»иҜ—зҡ„ж„ҹжҹ“еҠӣпјҢи®Өдёәе°Ҫз®Ўиҝҷзұ»иҜ—вҖңжң¬дёәжғ…иҜӯвҖқпјҢдҪҶвҖңиҜ»д№Ӣж— дёҖиҜӯи¶іеҠЁдәәжғ…вҖқпјҢе°ұеҘҪжҜ”еҜҢ家еҘівҖңдәҰжңүеӨ©е§ҝпјҢиҖҢзІүй»ӣзҸ зҝ е…ЁйҒ®жң¬иүІпјҢд№Ңи¶ід»ҘдёәдҪідёҪе“үвҖқгҖӮеңЁд»–зңӢжқҘпјҢеҰҶе®№йҒ®и”ҪдәҶеҜҢ家еҘізҡ„еӨ©з”ҹдёҪиҙЁпјҢи—»йҘ°д№ҹж·№жІЎдәҶиҜ—жӯҢзҡ„зңҹжҖ§жғ…гҖӮиҖҢй’ұжҫ„д№ӢжүҖиҝҪжұӮзҡ„вҖңжң¬иүІвҖқпјҢдёҚд»…еңЁдәҺиҜӯиЁҖзҡ„иҙЁжңҙпјҢжӣҙејәи°ғжҖ§жғ…зҡ„зңҹжҢҡпјҢ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зҡ„и—»йҘ°еҸ—еҲ°д»–зҡ„жҺ’ж–Ҙ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д№ҹжҢҮеҮә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зҹӯжҡӮиҖҢеқҺеқ·зҡ„дёҖз”ҹи¶ід»Ҙи®©дәәвҖңжөҒ涕вҖқпјҢдҪҶжҳҜвҖңиҜ»е…¶иҜ—пјҢдёҚиғҪдҪҝдәәиҖғе…¶еҝ—дәӢд»Ҙе…ҙж•ҷиҖҢиө·е“ҖвҖқпјҢе…ій”®еңЁдәҺвҖңеҚҺи—»жҺ©жІЎе…¶жҖ§жғ…йқўзӣ®д№ҹвҖқгҖӮз”ұдәҺиҜ—жӯҢиҝҮеҲҶиҝҪжұӮи—»йҘ°пјҢиҜ—дәәзҡ„жҖ§жғ…йҡҫд»ҘжҳҫзҺ°пјҢж„ҹжҹ“еҠӣд№ҹдјҡйҡҸд№ӢеҮҸејұ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е°Ҫз®Ў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е°Өе…¶жҳҜе…¶дёғеҫӢиҝҪиёӘжқңз”«пјҢдҪҶд»ҚдёәиҝҪжұӮзңҹжҖ§жғ…зҡ„жЎҗеҹҺжҙҫжүҖдёҚж»ЎгҖӮдёҺи—»йҘ°зӣёиҒ”зі»зҡ„пјҢжҳҜ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дёӯеӨҡеҶҷеҘіжҖ§пјҢдё”е…іеҗҲз”·еҘіжғ…дәӢпјҢеҜ№жӯӨжЎҗеҹҺжҙҫдәҰжһҒдёәжҠ—жӢ’гҖӮжҷҡжҳҺе…¬е®үжҙҫеҸҠжё…дёӯжңҹд»ҘиўҒжһҡдёәд»ЈиЎЁзҡ„жҖ§зҒөиҜ—жҙҫжҸҸеҶҷз§Ғз”ҹжҙ»пјҢиҝҷжҳҜжЎҗеҹҺжҙҫж— жі•жҺҘеҸ—зҡ„пјҢдёәжҠөеҲ¶жӯӨйЈҺпјҢ他们еҜ№дәҺжқҺиҜ—дёӯзҡ„зӣёе…іеҶ…е®№дәҰиҫғеӨҡжү№иҜ„гҖӮй’ұжҫ„д№Ӣдә‘пјҡвҖңиӢҘе”җжқҺд№үеұұпјҢеҘҪдёәиүідҪ“пјҢеҗҫж— еҸ–з„үгҖӮвҖқй’ұж°Ҹж— жі•жҺҘеҸ—д№үеұұжғ…иҜ—дёӯвҖңе®«еӘӣд»ҷеҰғй”ҷеҮәдә’и§ҒпјҢеҸӘжҳҜжғ…жҳөйҰҷеҘҒвҖқзҡ„жҸҸеҶҷгҖӮе§ҡйјҗдәҰжҳҜеҰӮжӯӨпјҢд»–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гҖҠзў§еҹҺгҖӢгҖҠж·ұе®«гҖӢгҖҠеңЈеҘізҘ гҖӢпјҢзҡҶеҲәе®«жҺ–д№ӢиҜӯпјҢдҪҶд»ҘгҖҠзў§еҹҺгҖӢдёәеҲәиҙөдё»пјҢд»ҘгҖҠж·ұе®«гҖӢдёәе®«жҖЁпјҢзҠ№жңӘе°Ҫе…¶ж—ЁиҖігҖӮжӯӨзӯүдәӢпјҢеІӮж–ҮеЈ«жүҖеҪ“д»Ҙе…Ҙеҗҹе’Ҹпјҹд№үеұұиҪ»и–„пјҢж•…дёҫи§ҒдәҺжӯӨгҖӮвҖқд»–еҸҚеҜ№еңЁиҜ—жӯҢдёӯеҗҹе’Ҹз”·еҘід№ӢдәӢпјҢжҢҮиҙЈжқҺж°ҸдҪңжӯӨзӯүиҜ—дёәвҖңиҪ»и–„вҖқгҖӮжӯӨдёүйҰ–иҜ—дёӯпјҢе§ҡж°Ҹе°Өе…¶еҸҚж„ҹгҖҠзў§еҹҺгҖӢгҖҠж·ұе®«гҖӢпјҢж•…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жңӘйҖүиҝҷдёӨйҰ–пјҢд»…йҖүгҖҠеңЈеҘізҘ гҖӢгҖҠйҮҚиҝҮеңЈеҘізҘ гҖӢдәҢйҰ–пјҢеҸҠгҖҠй”Ұз‘ҹгҖӢдёҺгҖҠж— йўҳгҖӢпјҲвҖңжқҘжҳҜз©әиЁҖвҖқдёҺвҖңжҳЁеӨңжҳҹиҫ°вҖқпјүдёүйҰ–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зҡ„еҒҡжі•иҫғе…¶еёҲжӣҙз”ҡпјҢдёҚд»…зӣҙжҺҘж— и§Ҷе§ҡж°Ҹ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йҖүдёӯзҡ„еҗҺдёүйҰ–иҜ—пјҢиҖҢдё”еҜ№гҖҠеңЈеҘізҘ гҖӢиҜ„д»·дә‘пјҡвҖңиө·дәҢеҸҘзҘ гҖӮдёүеӣӣеңЈеҘігҖӮдә”е…ӯеҸҠ收иҪ»и–„пјҢдёҚдёәдҪігҖӮвҖқеҜ№гҖҠйҮҚиҝҮеңЈеҘізҘ гҖӢиҜ„д»·дә‘пјҡвҖңиө·еҸҘзҘ гҖӮж¬ЎеҸҘеңЈеҘігҖӮдёүеӣӣеҗҲеҶҷгҖӮдә”е…ӯеҸҠ收д»ҘеҸӨдәәиЎ¬иҙҙпјҢдәҰжңӘи¶іжі•пјҢеҸҲж— и°“гҖӮжӯӨиҜ—еҸҜд»ҘдёҚйҖүгҖӮвҖқ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°Ҫз®Ўд»–и®Өдёәе§ҡйјҗ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жүҖйҖү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32йҰ–иҜ—вҖңдёҘжҙҒвҖқпјҢдҪҶд»Қ然жңүжүҖдёҚж»Ў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Ҝ№дәҺйӮЈдәӣж¶үеҸҠеҘіжҖ§еҸҠз”·еҘізҲұжғ…зҡ„иҜ—жӯҢпјҢд»–йғҪдәҲд»ҘжһҒдҪҺ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з”ҡиҮізӣҙжҺҘж— и§ҶиҖҢдёҚдәҲиҜ„д»·гҖӮжӣҫеӣҪи—©иҷҪдёәжЎҗеҹҺжҙҫдј дәәпјҢдәҰе®—зҗҶеӯҰпјҢдҪҶе…¶ж–ҮеӯҰи§ӮеҝөиҫғиҜҘжҙҫе…¶д»–дәәејҖж”ҫгҖӮд»–и®ӨдёәиҜҙзҗҶд№Ӣж–ҮдёҺиүәжңҜеҸӨж–ҮжңүеҲ«пјҡвҖңй„ҷж„Ҹж¬ІеҸ‘жҳҺд№үзҗҶпјҢеҲҷеҪ“жі•гҖҠз»ҸиҜҙгҖӢгҖҠзҗҶзӘҹгҖӢеҸҠеҗ„иҜӯеҪ•гҖҒжңӯи®°пјӣж¬ІеӯҰдёәж–ҮпјҢеҲҷеҪ“жү«иҚЎдёҖеүҜж—§д№ пјҢиөӨең°ж–°з«ӢпјҢе°ҶжӯӨеүҚ家еҪ“пјҢиҚЎз„¶иӢҘдё§е…¶жүҖжңүпјҢд№ғе§ӢеҲ«жңүдёҖз•Әж–ҮеўғгҖӮжңӣжәӘжүҖд»ҘдёҚеҫ—е…ҘеҸӨдәәд№ӢйҳғеҘҘиҖ…пјҢжӯЈдёәдёӨдёӢе…јйЎҫпјҢд»ҘиҮіж— еҸҜжҖЎжӮҰгҖӮвҖқд»–жү№иҜ„ж–№иӢһд»Ҙйҹ©ж¬§еҸӨж–ҮиЁҖиҜҙзЁӢжңұд№үзҗҶ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з§ҚеҒҡжі•иҷҪдёӨдёӢе…јйЎҫеҚҙж— жі•д»ӨиҜ»иҖ…вҖңжҖЎжӮҰвҖқпјҢиҝҷз§ҚзңӢжі•жӯЈжҳҫзӨәеҮәе…¶дёҺжЎҗеҹҺжҙҫдёҚеҗҢзҡ„и§Ӯеҝө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ҺжЎҗеҹҺжҙҫжү№иҜ„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и—»йҘ°дёҺиүіжғ…зӣёеҸҚпјҢжӣҫеӣҪи—©д»ҺвҖңжҖЎжӮҰвҖқзҡ„и§’еәҰж¬ЈиөҸд№үеұұиҜ—гҖӮе…¶гҖҠиҜ»жқҺд№үеұұиҜ—йӣҶ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ёәз»өеҮәеЈ°е“ҚпјҢеҘҘзј“з”ҹе…үиҺ№гҖӮеӨӘжҒҜж¶ӘзҝҒеҺ»пјҢж— дәәдјҡжӯӨжғ…гҖӮвҖқд»–д»ҘвҖңжёәз»өвҖқз»ҳе…¶вҖңеЈ°е“ҚвҖқпјҢд»ҘвҖңеҘҘзј“вҖқзҠ¶е…¶вҖңе…үиҺ№вҖқпјҢ并ж„ҹеҸ№иҮӘй»„еәӯеқҡд№ӢеҗҺпјҢеҶҚд№ҹж— дәәж¬ЈиөҸжқҺиҜ—д№Ӣи—»йҘ°пјҢз”ұжӯӨ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е…¶еҖҫеҗ‘жүҖеңЁгҖӮжӣҫеӣҪи—©гҖҠеҚҒ八家иҜ—й’һгҖӢжүҖйҖү117йҰ–жқҺиҜ—дёӯпјҢеӨ§йҮҸйҖүе…ҘжҸҸеҶҷеҘіжҖ§жҲ–з”·еҘід№Ӣжғ…зҡ„иҜ—дҪңпјҢеҰӮе…¶дёӯйҰ–йҖүгҖҠй”Ұз‘ҹгҖӢпјҢжҚ®жңұй№Өйҫ„д№ӢжіЁеҸҜзЎ®е®ҡе…¶дё»йўҳдёәжӮјдәЎпјӣж¬ЎйҖүгҖҠйҮҚиҝҮеңЈеҘізҘ гҖӢпјҢжҚ®зЁӢжўҰжҳҹд№ӢжіЁеҸҜзЎ®е®ҡе…¶дё»йўҳдёәеҲәеҘійҒ“еЈ«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жӮјдәЎеҸҠеҲәеҘійҒ“еЈ«иҝҳиғҪдёәжӯӨзұ»иҜ—ж¶ӮжҠ№дёҖеұӮдҝқжҠӨиүІ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пјҢжӣҫеӣҪи—©гҖҠеҚҒ八家иҜ—й’һгҖӢдёӯйҖүе…Ҙдёәе§ҡйјҗжүҖжҺ’ж–Ҙзҡ„гҖҠж·ұе®«гҖӢгҖҠзў§еҹҺгҖӢпјҢиҝҳжҜ«дёҚйЎҫеҝҢең°е°ҶдёҖдәӣиў«и®ӨдёәжҳҜжҢҹеҰ“гҖҒеҶ¶жёёгҖҒиүіиҜ—гҖҒж·«еӘҹд№ӢдҪңзәіе…Ҙе…¶дёӯпјҢиҝҷз§ҚеҒҡжі•е°ұжһҒдёәеӨ§иғҶгҖӮиҝҷдәӣиҜ—дёӯдёҚд№ҸеҰӮвҖңеҰ“еёӯжғңеҲ«вҖқзҡ„гҖҠйҘ®еёӯжҲҸиө еҗҢиҲҚгҖӢпјҢвҖңж·«еӘҹд№ӢиҫһвҖқзҡ„гҖҠиҚҜиҪ¬гҖӢпјҢвҖңеҶ¶жёёжғңеҲ«д№ӢиҜ—вҖқгҖҠжҳЁж—ҘгҖӢпјҢвҖңдёәеҘіеҶ иҖҢдҪңвҖқзҡ„гҖҠ银河еҗ№з¬ҷгҖӢпјҢвҖңдёәе®«еҰ“жөҒиҗҪеңЁдәәй—ҙиҖ…иҖҢдҪңвҖқзҡ„гҖҠй—»жӯҢгҖӢпјҢвҖңдёәе®«жҖЁвҖқзҡ„гҖҠж·ұе®«гҖӢпјҢвҖңеҶ¶жёёжғңеҲ«д№ӢиҜ—вҖқгҖҠжӣІжұ гҖӢпјҢвҖңиүіиҜ—вҖқгҖҠзүЎдё№гҖӢпјҢвҖңжҢҹеҰ“д№ӢиҜ—вҖқгҖҠй…¬еҙ”е…«иҡӨжў…жңүиө е…јзӨәд№ӢдҪңгҖӢпјҢвҖңеҸ№й•ҝе®үж•…еҰ“жөҒиҗҪеӣһдёӯиҖ…вҖқгҖҠеӣһдёӯзүЎдё№дёәйӣЁжүҖиҙҘдәҢйҰ–гҖӢзӯүгҖӮжӣҫеӣҪи—©еңЁиҮӘе·ұж¬ЈиөҸ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иҝҳж•ҷеҜје…¶еӯҗжӣҫзәӘжіҪиҜ»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ҡвҖңе°”иҜ»жқҺ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ҢдәҺжғ…йҹөж—ўжңүжүҖеҫ—пјҢеҲҷе°ҶжқҘдәҺе…ӯжңқж–ҮдәәиҜ—ж–ҮпјҢдәҰеҝ…жҳ“дәҺеҘ‘еҗҲгҖӮвҖқд»–иҝҳж•ҷеҜје„ҝеӯҗеӯҰ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Ңд»Һе…¶дёӯдҪ“дјҡжғ…йҹөзҡ„иЎЁиҫҫж–№ејҸпјҡвҖңе°”дёғеҫӢеҚҒдә”йҰ–еңҶйҖӮж·ұзЁіпјҢжӯҘи¶Ӣд№үеұұпјҢиҖҢеҠІж°”еҖ”ејәеӨ„йўҮдјјеұұи°·пјҢе°”дәҺжғ…йҹөгҖҒи¶Је‘ідәҢиҖ…зҡҶз”ұеӨ©еҲҶдёӯеҫ—д№ӢгҖӮвҖқвҖңжғ…йҹөвҖқдёҺвҖңж°”еҠҝвҖқвҖңиҜҶеәҰвҖқвҖңи¶Је‘івҖқеұһдәҺвҖңеҸӨж–ҮеӣӣиұЎвҖқпјҢжӣҫеӣҪи—©е°Ҷд№үеұұиҜ—и§ҶдёәвҖңжғ…йҹөвҖқзҡ„е…ёеһӢд»ЈиЎЁпјҢз”ұжӯӨдёҚйҡҫи§ҒеҮәжҺЁеҙҮд№Ӣж„ҸгҖӮеңЁиҝҷз•Әж•ҷиҜІд№ӢдёӢпјҢжӣҫзәӘжіҪд№ӢиҜ—д№ҹжҺҘеҸ—дәҶд№үеұұ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еӣӣгҖҒеғ»жҷҰж”ҜзҰ» 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д№Ӣйҡҫи§ЈпјҢдј—жүҖе‘ЁзҹҘгҖӮд№ӢжүҖд»ҘеҰӮжӯӨпјҢд»Һе…¶жң¬дәәз»ҸеҺҶжқҘиҜҙпјҢеӣә然жҳҜз”ұе…¶жүҖеӨ„зҡ„дёӨйҡҫеўғең°еҸҠиү°еҚұж—¶дё–жүҖйҖ жҲҗпјӣд»ҺиҜ—еҸІеҸ‘еұ•жқҘиҜҙпјҢеҲҷжҳҜе…¶жңүзә жӯЈжҷҡе”җиҜ—еқӣжөҒејҠзҡ„з”Ёж„ҸгҖӮеҲҳзҰ№й”ЎгҖҒзҷҪеұ…жҳ“е°Өе…¶жҳҜеҗҺиҖ…зҡ„жө…иҝ‘иҜ—йЈҺиҮіжҷҡе”җж—¶жңҹжөҒдёәж»‘жҳ“пјҢдёәж•‘жӯӨејҠпјҢжқҺе•ҶйҡҗиҮӘ然иҝҪжұӮиҜ—жӯҢиЎЁзҺ°ж–№ејҸзҡ„еҗ«и“„йҡҗжҷҰеҸҠжғ…ж„ҹж„Ҹи•ҙзҡ„ж·ұеҲ»дё°еҺҡгҖӮе®ӢдәәеҜ№жӯӨжңүзқҖжё…йҶ’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и®ёдә‘пјҡвҖңдҪңиҜ—жө…жҳ“й„ҷйҷӢд№Ӣж°”дёҚйҷӨпјҢеӨ§еҸҜжҒ¶гҖӮе®ўй—®дҪ•д»ҺеҺ»д№ӢпјҢд»Ҷжӣ°пјҡвҖҳзҶҹиҜ»е”җжқҺд№үеұұиҜ—дёҺжң¬жңқй»„йІҒзӣҙиҜ—иҖҢж·ұжҖқз„үпјҢеҲҷеҺ»д№ҹгҖӮвҖҷвҖқе®ӢеҲқзҷҪдҪ“жөҒиЎҢпјҢиҜ—йЈҺи¶ӢдәҺж»‘дҝ—пјҢдёәж•‘жӯӨејҠпјҢжқЁдәҝгҖҒеҲҳзӯ зӯүйҰҶйҳҒиҜёе…¬иҝҪиёӘд№үеұұиҜ—иҖҢжҲҗиҘҝжҳҶдҪ“пјӣй»„еәӯеқҡдёәиҜ—вҖңд»Ҙдҝ—дёәйӣ…вҖқпјҢдәҰжңүеҸҚдҝ—еҢ–еҖҫеҗ‘гҖӮи®ёи®ӨиҜҶеҲ°еӯҰд№үеұұиҜ—еҸҜд»ҘеҺ»йҷӨжө…жҳ“й„ҷйҷӢд№Ӣд№ пјҢеӣ иҖҢжҠ¬й«ҳе…¶иҜ—еҸІең°дҪҚгҖӮжҳҺжё…ж–ҮеӯҰдё–дҝ—еҢ–еҸ‘еұ•зҡ„еҖҫеҗ‘жӣҙдёәжҳҫи‘—пјҢе…¬е®үжҙҫдёҺиўҒжһҡзҡ„жҖ§зҒөиҜ—еӯҰеҚідёәд»ЈиЎЁгҖӮйқўеҜ№иҝҷдёҖи¶ӢеҠҝпјҢд»Ҙ儒家жӯЈз»ҹж–ҮеҢ–дј дәәиҮӘеұ…зҡ„жЎҗеҹҺжҙҫиҮӘ然дёҚиғҪеқҗи§ҶдёҚз®Ў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дёҚзӮ№еҗҚең°жү№иҜ„йҒ“пјҡвҖңеҰӮиҝ‘дәәжҹҗжҹҗпјҢйҡҸеҸЈзҺҮж„ҸпјҢиҚЎзҒӯе…ёеҲҷпјҢйЈҺиЎҢжөҒдј пјҢдҪҝйЈҺйӣ…д№ӢйҒ“пјҢеҮ дәҺж–ӯз»қгҖӮвҖқжҳҺзңјдәәдёҖзңӢпјҢе°ұзҹҘйҒ“жӯӨиҜӯжҳҜй’ҲеҜ№иўҒжһҡжҖ§зҒөиҜ—жҙҫеҸҠе…¶жң«жөҒзҡ„гҖӮе§ҡйјҗе°ҶеҜ№вҖңжө…жҳ“иҜўзҒ¶еҰӘвҖқзҡ„иўҒжһҡжҖ§зҒөиҜ—жҙҫд№ӢејҠзҡ„жү№еҲӨпјҢдёҠеҚҮеҲ°еҜ№е…¶иҜ—йЈҺиҝңзҘ–зҡ„иӯҰжғ•гҖӮд»–зј–зәӮ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пјҢзӣ®зҡ„е°ұеңЁдәҺвҖңжӯЈйӣ…зҘӣйӮӘ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»–еңЁйҖүзј–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Ҝ№дәҺиҜ—еҸІдёҠдҝҡдҝ—иҜ—йЈҺзҡ„е§ӢдҪңдҝ‘иҖ…пјҢж…ҺеҠ еҺ»еҸ–гҖӮеҰӮе…¶иҜ„зҷҪеұ…жҳ“иҜ—дә‘пјҡвҖңйҰҷеұұд»ҘжөҒжҳ“д№ӢдҪ“пјҢжһҒеҜҢиөЎд№ӢжҖқпјҢйқһзӢ¬дҝ—еЈ«еӨәйӯ„пјҢдәҰдҪҝиғңжөҒеҖҫеҝғгҖӮ然滑дҝ—д№Ӣз—…пјҢйҒӮиҮіжҒ¶ж»ҘпјҢеҗҺзҡҶд»ҘеӨӘеӮ…дёәзұҚеҸЈзҹЈгҖӮйқһж…ҺеҸ–д№ӢпјҢдҪ•д»Ҙз»ҙжҢҒйӣ…жӯЈе“үпјҹвҖқгҖҠд»ҠдҪ“иҜ—й’һгҖӢйҖүе…¶3йҰ–дә”еҫӢпјҢ10йҰ–дёғеҫӢпјҢж•°йҮҸд№Ӣе°‘пјҢдёҺе…¶иҜ—еҸІең°дҪҚе®Ңе…ЁдёҚиғҪеҢ№й…ҚгҖӮиҖҢе§ҡйјҗд№ӢжүҖд»ҘеҰӮжӯӨиӢӣеҲ»пјҢе°ұжҳҜдёәдәҶд»ҺжәҗеӨҙдёҠйҒҸеҲ¶дҝ—дҪ“иҜ—гҖӮе§ҡйјҗеҜ№дәҺйӮЈдәӣеңЁжҠөеҲ¶дҝҡдҝ—еҢ–иҝҮзЁӢдёӯиө·иҮіе…і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зҡ„иҜ—дәәпјҢеҲҷдәҲд»Ҙй«ҳеәҰиӮҜе®ҡгҖӮеҰӮе…¶иҜ„иӢҸиҪјдә‘пјҡвҖңдёңеқЎеӨ©жүҚпјҢжңүдёҚеҸҜжҖқи®®еӨ„гҖӮе…¶дёғеҫӢеҸӘз”ЁжўҰеҫ—гҖҒйҰҷеұұж ји°ғпјҢе…¶еҰҷеӨ„еІӮеҲҳгҖҒзҷҪжүҖиғҪжңӣе“үпјҒвҖқд»–еҸҲжҺЁеҙҮй»„еәӯеқҡдә‘пјҡвҖңеұұи°·еҲ»ж„Ҹе°‘йҷөпјҢиҷҪдёҚиғҪеҲ°пјҢ然其е…ҖеӮІзЈҠиҗҪд№Ӣж°”пјҢи¶ідёҺеҸӨд»ҠдҪңдҝ—иҜ—иҖ…жҫЎжҝҜиғёиғғпјҢеҜјеҗҜжҖ§зҒөгҖӮвҖқд»–иӮҜе®ҡиӢҸиҪјеҲ©з”ЁеҲҳзҰ№й”ЎгҖҒзҷҪеұ…жҳ“иҜ—д№Ӣж ји°ғиҖҢи¶…и¶ҠеҲҳгҖҒзҷҪ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°Ҷй»„еәӯеқҡжҺЁдёҫдёәзә жӯЈдҝ—дҪ“иҜ—зҡ„е…ёиҢғгҖӮеҗҢж ·пјҢд»–иөһиөҸжқҺе•ҶйҡҗдёғеҫӢвҖңзҠ№и¶іиҝ‘жҺ©еҲҳзҷҪвҖқпјҢжҠүеҸ‘е…¶з”ЁжҖқд№Ӣж·ұж„ҸеңЁвҖңзҹ«ж•қж»‘жҳ“вҖқпјҢеёҢжңӣд»ҘжӯӨжҢҪж•‘еҲҳгҖҒзҷҪеҸҠе…¶жң«жөҒе№іж»‘жө…жҳ“иҜ—йЈҺзҡ„ејҠз«ҜгҖӮеңЁиўҒжһҡжҖ§зҒөиҜ—йЈҺжөҒиЎҢзҡ„д№ҫеҳүж—¶жңҹ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еҲ©з”Ёд№үеұұд№Ӣж·ұеҲ»з”ЁжҖқеҠ д»Ҙзә ејҠ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д»ҺиҝҷдёҖзӮ№еҮәеҸ‘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жҺЁеҙҮ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д№ӢзІҫзӮјйҖ иҜӯеҸҠж·ұеҲ»жғ…ж„ҹгҖӮеҪ“ж—¶дёҺвҖңжө…жҳ“иҜўзҒ¶еҰӘвҖқзҡ„жҖ§зҒөиҜ—жҙҫ并еӯҳзҡ„пјҢиҝҳжңүвҖңйҷ©жҖӘи¶Ӣиҷ¬жҲ·вҖқзҡ„жөҷжҙҫгҖӮжөҷжҙҫд»ҘеҺүй№—дёәд»ЈиЎЁпјҢе…¶иҜ—жӯҢдёәдәҶиҝҪжұӮйҷҢз”ҹеҢ–зҡ„ж•ҲжһңпјҢиӢҰеҝғз»ҸиҗҘиҜ—ж„ҸпјҢз”Ёеӯ—иҝҘдёҚзҠ№дәәпјҢжҠӣејғеёёи§Ғе…ёж•…пјҢеӨ§йҮҸдҪҝз”Ёе®ӢгҖҒе…ғдәәе°ҸиҜҙдёӯзҡ„еғ»е…ёпјҢд»ҺиҖҢеҪўжҲҗвҖңйҷ©жҖӘвҖқзҡ„иҜ—йЈҺгҖӮе§ҡйјҗе°ҶиўҒжһҡгҖҒеҺү鹗并称дёәвҖңиҜ—家д№ӢжҒ¶жҙҫвҖқпјҢеҸҚж„ҹд№Ӣжғ…жәўдәҺиЁҖиЎЁгҖӮеҜ№дәҺвҖңйҷ©жҖӘвҖқзҡ„иҜ—йЈҺпјҢж–№иҙһи§ӮдәҰжҠЁеҮ»дә‘пјҡвҖңиҝ‘жңүдҪңиҖ…пјҢи°“е…ӯз»ҸгҖҒгҖҠеҸІгҖӢгҖҠжұүгҖӢзҡҶзіҹзІ•йҷҲиЁҖпјҢй„ҷдёүе”җеҗҚ家дёәзҶҹзғӮд№ еҘ—пјҢеҲ«жңүеёҲдј пјҢеҸҰжҲҗиҜӯеҸҘпјҢеҸ–е®ӢгҖҒе…ғдәәе°ҸиҜҙйғЁд№Ұдё–жүҖдёҚжөҒдј иҖ…пјҢз”Ёдёәжһ•дёӯз§ҳе®қпјҢйҮҮе…¶дәӢе®һпјҢж‘ӯе…¶иҜҚеҚҺпјҢиҝҒе°ұеӢүејәд»Ҙз”Ёд№ӢпјҢиҜ—жҲҗеӨҡдёҚеҸҜи§ЈгҖӮд»Өе…¶иҮӘдёәз–ҸиҜҙпјҢеҲҷзҡҶйҖҗеҸҘжҲҗж–ҮпјҢж— дёҖж„ҸиҙҜдёүиҜӯиҖ…пјҢж— дёҖж°”иҙҜдёүиҜӯиҖ…пјҢд№ғ然иҮӘд»ҘдёәеҚҡеҘҘеҘҮеҸӨгҖӮжӯӨзңҹеӨ§йҒ“д№Ӣжіўж—¬пјҢдёҮйҡҫеҢ»иҚҜиҖ…д№ҹгҖӮдҪҶж„ҝеӨ©ең°еӨҡз”ҹжҳҺзңјдәәпјҢдёҚдёәе…¶жүҖиҝ·жғ‘пјҢдҪҝжөҒжҜ’дёҚиҝңпјҢжҳҜеҺҡе№ёзҹЈгҖӮвҖқд»–дёҘеҺүжү№иҜ„еҺүй№—иҜ—жӯҢжүҖз”Ёе…ёж•…зҡ„жқҘжәҗеҸҠз”Ёе…ё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д»ҘеҸҠз”ұжӯӨеҪўжҲҗзҡ„вҖңдёҚеҸҜи§ЈвҖқзҡ„иҜ—йЈҺгҖӮеҺүиҜ—з”Ёе…ёзјҳдәҺе®ӢиҜ—пјҢиҖҢе®ӢиҜ—д№Ӣз”Ёе…ёеҸҲжҲ–еӨҡжҲ–е°‘еҸ—еҲ°жқҺе•Ҷйҡҗ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еӣ жӯӨ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Ҝ—дәәеҜ№дәҺ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зҡ„з”Ёе…ёд»ҘеҸҠз”ұжӯӨиҖҢеҜјиҮҙзҡ„иҜ—йЈҺд№ӢејҠз«ҜеӨҡжңүжё…йҶ’зҡ„и®ӨиҜҶгҖӮжӯЈеҰӮе§ҡйјҗжүҖдә‘пјҢд№үеұұвҖң第д»Ҙзҹ«ж•қж»‘жҳ“пјҢз”ЁжҖқеӨӘиҝҮпјҢиҖҢеғ»жҷҰд№Ӣж•қеҸҲз”ҹвҖқгҖӮ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з”ұдәҺзә жӯЈе№іжө…ж»‘жҳ“д№ӢиҜ—йЈҺпјҢиҖҢиҝҪжұӮеҗ«и“„ж·ұйҡҗпјҢз»“жһңиө°еҗ‘еҸҰдёҖдёӘжһҒз«ҜпјҢеҚіжҷҰ涩йҡҫжҮӮгҖӮ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иҷҪ然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иҜ—жӯҢз”Ёе…ёзҡ„зјҳж•…пјҢдҪҶз”Ёе…ёеҚҙжҳҜ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еӣ зҙ 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еҜ№дәҺд№үеұұиҜ—д№Ӣз”Ёе…ёеӨҡжңүжү№иҜ„пјҢдё»иҰҒйӣҶдёӯеңЁд»ҘдёӢ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гҖӮйҰ–е…Ҳ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з”Ёе…ёиҝӮжҷҰж·ұйҡҗгҖӮе®Ӣдәәжғ жҙӘжү№иҜ„д№үеұұиҜ—вҖңз”ЁдәӢеғ»ж¶©вҖқпјҢи”Ўз»ҰдәҰжҢҮеҮәе…¶зҹӯеӨ„еңЁдәҺвҖңз”ЁдәӢж·ұеғ»пјҢиҜӯе·ҘиҖҢж„ҸдёҚеҸҠвҖқпјҢйӣҶзҹўдәҺжқҺиҜ—з”Ёе…ёжҷҰ涩йҡҫжҮӮпјӣжЎҗеҹҺжҙҫд№ҹжҳҜеңЁжӯӨеұӮйқўдёҚж»Ўд№үеұұиҜ—гҖӮе§ҡйјҗиҜ„гҖҠд№қжҲҗе®«гҖӢжң«дәҢеҸҘдә‘пјҡвҖңиҚ”жһқгҖҒеҚўж©ҳзҡҶеӨҸзҶҹпјҢеҲҮйҒҝжҡ‘гҖӮжң«еҸҘдҪҶи°“иҜҸжұӮжӯӨжһңиҖіпјҢиҖҢиҜӯд№ғиҝӮжҷҰпјҢжӯӨд№үеұұд№Ӣз—…гҖӮвҖқиҜҘиҜ—жң¬ж„ҸеңЁдёӢиҜҸжұӮиҚ”жһқдёҺеҚўж©ҳпјҢдҪҶд№үеұұеҒҸдә‘вҖңйёҫй№ҠеӨ©д№Ұж№ҝзҙ«жіҘвҖқпјҢз”ЁвҖңйёҫй№ҠвҖқвҖңеӨ©д№ҰвҖқжҢҮиҜҸд№ҰпјҢд»ҘвҖңж№ҝзҙ«жіҘвҖқжҢҮе°ҒеҚ°пјҢиҜ»иҖ…йңҖиҰҒйҖҡиҝҮеӨҡеұӮиҪ¬жҚўжүҚиғҪдҪ“жӮҹпјҢж•…е§ҡйјҗжү№иҜ„е…¶вҖңиҝӮжҷҰвҖқпјҢ并е°ҶжӯӨдёҠеҚҮдёәжқҺиҜ—зҡ„йҖҡз—…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иҜ„гҖҠжӣІжұ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收еҸҘж¬Іж·ұеҸҚжҷҰгҖӮвҖқжӯӨиҜ—жң«дәҢеҸҘвҖңеӨ©иҚ’ең°еҸҳеҝғиҷҪжҠҳпјҢиӢҘжҜ”дјӨжҳҘж„ҸжңӘеӨҡвҖқпјҢиҜёе®¶дәҺжӯӨдәүи®әйўҮеӨҡпјҢжңұй№Өйҫ„жіЁеҗҺиҜ„дә‘пјҡвҖңеҗҺеӣӣеҸҘеҲҷиЁҖзҺӢж¶Ҝзӯүиў«зҘёпјҢеҝ§еңЁзҺӢе®ӨиҖҢдёҚиғңеӨ©иҚ’ең°еҸҳд№ӢжӮІд№ҹгҖӮвҖқдҪ•з„ҜдёҚж»Ўжңұж°ҸжӯӨиҜ„пјҢи®Өдёәе…¶вҖңжңӘе°ҪдҪңиҖ…д№Ӣж„ҸвҖқгҖӮзЁӢжўҰжҳҹдәҰжү№иҜ„йҒ“пјҡвҖңеҸӘд»ҘвҖҳеҝ§еңЁзҺӢе®ӨиҖҢдёҚиғңеӨ©иҚ’ең°еҸҳд№ӢжӮІвҖҷдёҖиҜӯдәҶд№ӢпјҢдәҺжң¬еҸҘд№ӢвҖҳеҝғиҷҪжҠҳвҖҷпјҢдёӢеҸҘд№ӢвҖҳдјӨжҳҘеӨҡвҖҷдёҖиҜӯзҡҶиӢҘдёҚеҸҜи§ЈиҖ…гҖӮвҖқжңұжіЁеҸҠиҜ„жңӘиғҪжё…жҷ°йҳҗжҳҺгҖҠжӣІжұҹгҖӢзҡ„иҜ—ж„ҸпјҢиҖҢж–№дёңж ‘еҸӮиҖғжңұж°Ҹи§ӮзӮ№пјҢж•…дәҰйҡҫжҳҺжң¬ж—Ё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жү№иҜ„д№үеұұдёәиҝҪжұӮж·ұеҲ»еҸҚиҖҢиө°еҗ‘еғ»жҷҰзҡ„дёҖйқўгҖӮе…¶ж¬Ў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з”Ёе…ёжө“иүіиҪ»еҲ©гҖӮд№үеұұе–ңз”ЁдёҺеҘіжҖ§зӣёе…ізҡ„е…ёж•…пјҢжӯӨдәҰдёәжЎҗеҹҺжҙҫдёҚж»ЎгҖӮй’ұжҫ„д№Ӣдә‘пјҡвҖңе…¶иҜ—дҪҝдәӢж‘ӣиҫһпјҢз§ҫеҺҡж»һйҮҚпјҢеҫ’еҸ–е·ҘдёҪиҖі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дҪҝдәӢвҖқзҡ„вҖңз§ҫеҺҡвҖқпјҢеҚідёҺеҘіжҖ§зӣёе…ігҖӮеҰӮ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еҚ—жңқгҖӢдёӯзҡ„йўҲиҒ”вҖңи°ҒиЁҖзҗјж ‘жңқжңқи§ҒпјҢдёҚеҸҠйҮ‘иҺІжӯҘжӯҘжқҘвҖқдёҺе°ҫиҒ”вҖңж»Ўе®«еӯҰеЈ«зҡҶйўңиүІпјҢжұҹд»ӨеҪ“е№ҙеҸӘиҙ№жүҚвҖқпјҢе°ұз”ЁдәҶйҷҲеҗҺдё»д№Ӣеј иҙөеҰғгҖҒеӯ”иҙөе«”еҸҠдёғдҪҚеҘіеӯҰеЈ«гҖҒйҪҗеәҹеёқд№ӢжҪҳеҰғзӯүеӨҡдёӘеҘіжҖ§зҡ„е…ёж•…пјҢдё”з”ЁвҖңз»ЈиҘҰвҖқвҖңзҗјж ‘вҖқвҖңйҮ‘иҺІвҖқвҖңйўңиүІвҖқзӯүжө“иүізҡ„иҫһи—»пјҢе…¶вҖңз§ҫеҺҡж»һйҮҚвҖқдёҚиЁҖиҖҢе–»гҖӮж–№з»©дә‘пјҡвҖңжӯӨиҜ—з•Ҙиҝ‘гҖҠйҡӢе®«гҖӢгҖӮвҖқж–№дёңж ‘и®ӨдёәвҖңгҖҠйҡӢе®«гҖӢеҸҲйҖҠгҖҠзӯ№з¬”й©ҝгҖӢвҖқпјҢеҺҹеӣ еңЁдәҺвҖңз”ЁдәӢеӨӘжө“пјҢдёӢ笔еӨӘиҪ»еҲ©пјҢејҖдҪңдҝ—иҜ—жҙҫвҖқгҖӮе®һйҷ…дёҠпјҢгҖҠйҡӢе®«гҖӢдәҰз”ЁдәҶгҖҠзҺүж ‘еҗҺеәӯиҠұгҖӢзӯүе…ёж•…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дёҚдјјгҖҠеҚ—жңқгҖӢйӮЈд№Ҳжө“иүігҖӮгҖҠзӯ№з¬”й©ҝгҖӢиҷҪдәҰж…ЁеҸ№иңҖжұүд№ӢзҒӯдәЎпјҢ然дёҚз”ЁеҘіжҖ§е…ёж•…жёІжҹ“ж°”ж°ӣ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ңЁгҖҠеҚ—жңқгҖӢгҖҠйҡӢе®«гҖӢгҖҠзӯ№з¬”й©ҝгҖӢиҝҷдёүйҰ–иҜ—дёӯпјҢж–№ж°ҸжҺЁе…¶жҲҗе°ұжңҖй«ҳ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д№үеұұиҜ—з”Ёе…ёжө®жіӣж”ҜзҰ»гҖӮж–№дёңж ‘иҜ„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д№қж—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№үеұұиҙӘз”ЁдәӢеӨҡпјҢдёҚеҝҚеүІпјҢеҰӮжӯӨвҖҳиӢңи“ҝвҖҷпјҢдҪ•жүҖжҢҮд№ҹпјҹвҖқжӯӨиҜ—еҮ д№ҺеҸҘеҸҘз”Ёе…ёпјҢдёҚд»…жңүвҖңиҙӘеӨҡвҖқд№ӢејҠпјҢиҖҢдё”еҜјиҮҙиҜ—ж„ҸйҡҗжҷҰдёҚжҳҺгҖӮжӯӨиҜ—е°ҫиҒ”вҖңдёҚеӯҰжұүиҮЈж ҪиӢңи“ҝпјҢз©әж•ҷжҘҡе®ўе’Ҹжұҹи“ вҖқдёӯзҡ„вҖңиӢңи“ҝвҖқд№Ӣи§ЈпјҢеј•еҸ‘иҜёеӨҡдәүи®®гҖӮйҷҶжҳҶжӣҫи®ӨдёәпјҢиҝҷжҳҜдёәдәҶиЎЁиҫҫвҖңпјҲд»ӨзӢҗз»№пјүеҠҹеңЁзӨҫзЁ·пјҢдёҚеҫ’еҰӮжұүиҮЈд№ӢеҒ¶дёҖеҘүдҪҝпјҢйҮҮеҸ–иӢңи“ҝеҪ’ж Ҫе·Ід№ҹвҖқгҖӮиҖҢеј йҮҮз”°еҸҚй©ідә‘пјҡвҖңеҸӘеҸ–移з§ҚдёҠиӢ‘д№Ӣд№үпјҢиЁҖд»ӨзӢҗдёҚиӮҜжҸҙжүӢпјҢдҪҝд№ӢжІүжІҰдҪҝеәңпјҢдёҚеҫ—еӨҚе®ҳзҰҒиҝ‘д№ҹгҖӮвҖҰвҖҰеІӮд»Ҙж•ҢеӣҪеҜ“ж…Ёе“үпјҹвҖқд»Һд»ҘдёҠиҜёе®¶зҡ„дәүи®әдёӯпјҢдәҰеҸҜи§ҒжӯӨе…ёе®№жҳ“еј•иө·еӨҡйҮҚи§ЈйҮҠгҖӮеңЁиҜ—дёӯз”Ёе…ёеҜҶйӣҶпјҢ并且дёҚеҗҢе…ёж•…д№Ӣй—ҙи·ЁеәҰжҜ”иҫғеӨ§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иҜ—дәәеҰӮжһңдёҚиғҪе°Ҷе…¶жө‘иһҚдёҖдҪ“пјҢе°ұе®№жҳ“з»ҷдәәе Ҷеһӣд№Ӣе«ҢгҖӮж–№ж°ҸдёҚж»Ўд№үеұұеңЁгҖҠеҶҷж„ҸгҖӢдёӯз”ЁвҖңзҮ•йӣҒдёҠжһ—вҖқд»ЈжҢҮж•…д№ЎпјҢи°“е…¶з—…еңЁвҖңж”ҜзҰ»ж— и°“вҖқгҖӮеҸҜиғҪд»–и§үеҫ—дёҠжһ—жҳҜеёқзҺӢд№Ӣжһ—иӢ‘пјҢд№үеұұд»ҘжӯӨд»ЈжҢҮиҜ—дәәж•…д№ЎпјҢж•…дёҚе…ҚвҖңж”ҜзҰ»вҖқгҖӮе§ҡйјҗиҜ„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йғ‘е·һзҢ®д»ҺеҸ”иҲҚдәәиӨ’гҖӢдёӯвҖңз»ӣз®Җе°ҡеҸӮй»„зәёжЎҲпјҢдё№зӮүзҠ№з”Ёзҙ«жіҘе°ҒвҖқд№ӢеҸҘдә‘пјҡвҖңдёңйӨҗиҘҝе®ҝд№ӢиҜӯпјҢж„ҸиӨ’д№ғжүҳзҘһд»ҷиҜҙд»ҘеҸ–иҙөиҖ…пјҢж•…д»ҘжҳҜи®Ҫд№ӢдёҺпјҹвҖқе§ҡж°Ҹз”ұиҜ—дёӯз”ЁиҜӯжҺЁжөӢжқҺиӨ’д№ғйҒ“ж•ҷдёӯдәәпјҢж–№дёңж ‘жүҝе…¶еёҲд№Ӣж„ҸпјҢ并иҝӣдёҖжӯҘеқҗе®һдә‘пјҡвҖңеӨ§зәҰжқҺиӨ’еҘҪйҒ“пјҢиө·еҚівҖҳзғҹйңһвҖҷдёҺвҖҳй’ҹйјҺвҖҷпјҢиҝңд»Ҙз§°д№ӢгҖӮвҖҳйҮ‘йҫҷвҖҷиҷҪз”ЁйҒ“家пјҢд»ҚеҲҮиҲҚдәәдё»ж’°ж–ҮзүӢеҘҸгҖӮвҖҰвҖҰдә”е…ӯз”ЁвҖҳй»„зәёвҖҷвҖҳзҙ«жіҘвҖҷдёҺжӯӨеҗҢпјҢзҡҶеҸҢе…ід№ҹгҖӮвҖқеҜ№дәҺиҝҷйҰ–иҜ—зҡ„з”Ёе…ёпјҢж–№ж°ҸиҷҪдәҰиӮҜе®ҡе…¶вҖңдјјзІҫеҲҮвҖқпјҢ然еҸҲжү№д№Ӣдә‘пјҡвҖңдёҚе…ҚдёңйӨҗиҘҝе®ҝпјҢејҖдҝ—иҜ—ж¶ӮйҘ°д№Ӣжҙҫ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дёҺе…¶еёҲеҗҢз”ЁвҖңдёңйӨҗиҘҝе®ҝвҖқиЎЁиҫҫеҜ№жӯӨиҜ—з”Ёе…ёзҡ„дёҚж»Ў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жҢҮиҙЈжқҺе•ҶйҡҗеҘҪз”Ёд»ЈиҜҚдёәе…ёпјӣ并且жҢҮеҮәеҰӮжӯӨз”ЁдәӢпјҢжңүејҖеҗҜдҝ—иҜ—жҙҫж¶ӮйҘ°д№ӢејҠзҡ„еҚұйҷ©гҖӮе…¶иЁҖеӨ–д№Ӣж„ҸпјҢе°ұжҳҜй’ҲеҜ№жөҷжҙҫеҘҪд»Ҙд»ЈиҜҚдёәиҜ—зҡ„йЈҺж°”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еңЁжҳҺжё…иҜ—еқӣеҸ‘еұ•зҡ„еӨ§иғҢжҷҜдёӯ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еҜ№дәҺд№үеұұиҜ—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ж—ўзҲұеҸҲжҒЁгҖӮзҲұе…¶дёәжқңиҜ—д№ӢвҖңе—Је“ҚвҖқпјҢиӮҜе®ҡе…¶дёғеҫӢеңЁжқңз”«гҖҒзҺӢз»ҙд№ӢеҗҺиҮӘжҲҗдёҖжҙҫпјҢз”ЁжҖқж·ұеҲ»иҖҢиғҪвҖңзҹ«ж•қжөҒжҳ“вҖқпјӣжҒЁе…¶д»ҘеҚҺзҫҺзҡ„иҫһи—»жҸҸз»ҳз”·еҘіз§Ғжғ…пјҢз”ЁйҡҗжҷҰзҡ„е…ёж•…иЎЁиҫҫеӨҚжқӮзҡ„жғ…ж„ҹпјҢйқ©жөҒжҳ“д№ӢејҠиҖҢеҸҲз”ҹж¶ӮйҘ°д№Ӣз—…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ӮҜе®ҡд№үеұұдёғеҫӢеӯҰжқңд№ӢеӨ–пјҢиҝҳжіЁж„ҸеҲ°е…¶е…јжңүзҺӢз»ҙ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иҝҷ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зӘҒз ҙдәҶзҺӢе®үзҹіиЁҖи®әзҡ„жқҹзјҡпјҢжӢ“еұ•дәҶеҗҺдәәеҜ№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жёҠжәҗиҝҪжәҜзҡ„и§Ҷеҹҹ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жЎҗеҹҺжҙҫиҷҪеҮәдәҺжӯЈз»ҹи§ӮеҝөиҖҢжҢҮиҙЈд№үеұұиҜ—д№ӢвҖңи—»йҘ°вҖқе’ҢвҖңиҪ»и–„вҖқпјҢдёҚиҝҮпјҢдёҖж—Ұе…¶жҠӣејҖиҝҷеұӮеӣ зҙ зҡ„е№Іжү°пјҢеҸҲиғҪеҰӮжӣҫеӣҪи—©йӮЈж ·дә«еҸ—д№үеұұиҜ—еёҰжқҘзҡ„вҖңжҖЎжӮҰвҖқе®ЎзҫҺж„ҹеҸ—пјҢеҮёжҳҫд№үеұұиҜ—жӯҢзҡ„ж–ҮеӯҰиҙЁжҖ§гҖӮиҝҷдәӣиҜ„д»·еңЁжқҺе•ҶйҡҗиҜ—жӯҢжҺҘеҸ—еҸІдёҠеқҮе…·жңүйҮҚиҰҒзҡ„ж„Ҹд№ү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йҮҮи–Ү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4жңҹвҖңж–ҮеӯҰдёҺиүәжңҜз ”з©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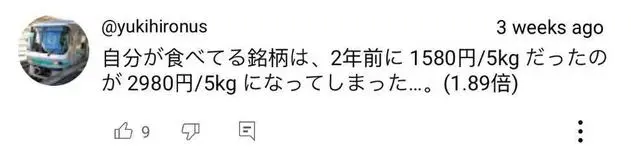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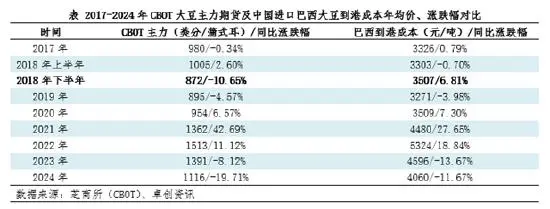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