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и’ӢжҢҜеҚҺпјҢз”·пјҢж№–еҚ—еёҲиҢғеӨ§еӯҰж–Ү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гҖҒеҚҡеЈ«з”ҹеҜјеёҲгҖӮ
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жңүзқҖдё°еҜҢ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з”ҡиҮіеҮәзҺ°дәҶжҹҗз§Қ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гҖӮз ”з©¶иЎЁжҳҺпјҢ儒家дә”з»Ҹ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дё»иҰҒжңүгҖҠд№ҰгҖӢгҖҠжҳ“гҖӢгҖҠиҜ—гҖӢпјҢеҸІдј ж•Јж–Ү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дё»иҰҒжңүгҖҠе·Ұдј гҖӢгҖҠжҷҸеӯҗжҳҘз§ӢгҖӢгҖҠеӣҪиҜӯгҖӢ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гҖҠжҲҳеӣҪзӯ–гҖӢпјҢиҜёеӯҗж•Јж–Ү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дё»иҰҒжңүгҖҠеўЁеӯҗгҖӢгҖҠи®әиҜӯгҖӢгҖҠз®ЎеӯҗгҖ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гҖҠе°ёеӯҗгҖӢ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гҖҠиҚҖеӯҗгҖӢгҖҠеҗ•ж°ҸжҳҘз§ӢгҖӢпјҢе…¶д»–е…ёзұҚ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жң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гҖҠжҘҡиҫһгҖӢзӯүгҖӮж №жҚ®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д№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®ҡд№үжқҘеҲ’еҲҶпјҢе…Ҳз§Ұ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д№ҰеҶҷзҡ„зұ»еһӢеҸҜд»ҘеҲҶдёәиә«жёёгҖҒзҘһжёёдёӨз§ҚгҖӮиә«жёёеҫҖеҫҖдёҺдәәзҡ„еҲҮиә«дҪ“йӘҢ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пјҢзҘһжёёеҲҷдёҺд№ӢжңүжҳҺжҳҫдёҚеҗҢгҖӮзҘһжёёзҡ„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ёәзҘһжҖ§д№ӢзҒөжҲ–иҷҡи®ҫзҡ„е…·жңүеҺҹе§Ӣе®—ж•ҷиүІеҪ©зҡ„зҘһжҲ–д»ҷзү©пјҢе…¶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ҫҖеҫҖдјҡдёҺзҘһй¬јд»ҷзҒөеҸ‘з”ҹжҹҗз§Қз“ңи‘ӣжҲ–е…ізі»пјҢ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ж—…жёёиҖ…еҫҖеҫҖдёҺи¶…зҺ°е®һгҖҒи¶…иҮӘ然зҡ„зҘһжҲ–д»ҷзӣёдәӨеҘ‘гҖӮзҘһжёёжҳҜжёёи§Ҳдё»дҪ“д№ӢзІҫзҘһжүҖе®ҢжҲҗзҡ„ж—…жёёиҝҮзЁӢпјҢжёёзҡ„ең°ж–№жӣҙдёәйҒҘиҝңиҷҡе»“пјҢеҸҜд»ҘдёҠиҮіеӨ©еәӯзҗје®ҮпјҢдёӢиҮіеӨ§ең°д№ӢжһҒпјҢзңҹеҸҜи°“вҖңдёҠз©·зў§иҗҪдёӢй»„жіүвҖқгҖӮдёҺдёҖиҲ¬зҡ„иә«жёёд№ҰеҶҷзӣёжҜ”пјҢ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Ҷ…ж¶өжӣҙеҠ дё°еҜҢпјҢи•ҙеҗ«зқҖ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ұұж°ҙе“ІжҖқгҖҒзҫҺдё‘е®Ўи§ҶгҖҒзҘһд»ҷиҝҪжұӮзӯүеӨҡйҮҚ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пјҢжӣҙиғҪиЎЁзҺ°еҸӨдәәеҜ№ж—¶з©әзҡ„и®ӨиҜҶгҖҒеҜ№еұұж°ҙиҮӘ然зҡ„дҪ“жӮҹгҖҒеҜ№з”ҹе‘Ҫж°ёжҒ’зҡ„жёҙжңӣдёҺиҝҪжұӮзӯүпјҢиҝҷе…·жңүйҮҚиҰҒзҡ„ж–ҮеӯҰжҜҚйўҳж„Ҹд№үпјҢеҜ№еҗҺдё–ж–ҮеӯҰдә§з”ҹдәҶж·ұиҝңеҪұе“ҚгҖӮдёҖгҖҒ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“ІжҖқеҶ…ж¶ө 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еҜ№иұЎж— з–‘жҳ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жёёеҺҶзҡ„е®ўи§Ӯеұұж°ҙпј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ҮӘ然д№ҹдёҚдҫӢеӨ–гҖӮ然иҖҢпјҢеңЁжҸҸеҶҷж—…жёёе®ўдҪ“з»ҷдәҲ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ж„ҹеҸ—ж–№йқўпјҢиә«жёёд№ҰеҶҷдёҺ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ҲҷжңүзқҖжҳҺжҳҫдёҚеҗҢгҖӮиә«жёёжҸҸеҶҷжүҖеёҰжқҘзҡ„з»қеӨ§еӨҡж•°жҳ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жҳҫжҖ§зҡ„е®ЎзҫҺж„ҹеҸ—гҖҒеҝғзҒөиҺ·еҫ—пјҢеҚіеҰӮж—…жёёеңЈиҙӨеӯ”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зҹҘиҖ…д№җж°ҙпјҢд»ҒиҖ…д№җеұұвҖқпјҢдәҰеҰӮж—…жёёеӨ§еёҲеә„еӯҗ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еұұжһ—дёҺпјҢзҡӢеЈӨдёҺпјҢдҪҝжҲ‘欣欣然иҖҢд№җдёҺвҖқгҖӮдҪҶе…Ҳз§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Қҙж— дёҖдҫӢеӨ–ең°е°ҶйҡҗжҖ§зҡ„е“ІжҖқеҶ…ж¶өеҢ…и•ҙе…¶дёӯпјҢе…¶е“ІжҖқеҶ…ж¶өдё»иҰҒеҢ…жӢ¬ж—¶з©әиҢғз•ҙгҖҒжңүж— зӣёз”ҹгҖҒеҠЁжңәж•Ҳжһңзӯү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пјҢд»ҘжӯӨжҳҫзӨәдҪңдёәж—…жёёеҜ№иұЎзҡ„еұұж°ҙеҶ…иҙЁгҖӮеұұж°ҙж—…жёёеҖҹеҠ©ж—¶й—ҙзҡ„延з»ӯеҫ—д»Ҙе®ҢжҲҗпј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Ҝ№дәҺеұұж°ҙзҡ„ж„ҹеҸ—жҲ–иҖ…д»Ҙж—¶й—ҙзҡ„жҳ“йҖқеҪўжҲҗжҹҗз§Қи®ӨзҹҘе’Ңи®°еҝҶпјҢжҲ–иҖ…еңЁж—¶е…үзҡ„жөҒйҖқдёӯйҒ—еҝҳи®°еҝҶпјҢиҝҷз§ҚеҜ№дәҺеұұж°ҙзҡ„ж·ұеҲ»йўҶдјҡд»Ҙ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жңҖдёәе…ёеһӢгҖӮгҖҠеә„еӯҗВ·еӨ©ең°гҖӢдә‘пјҡй»„еёқжёёд№ҺиөӨж°ҙд№ӢеҢ—пјҢзҷ»д№ҺжҳҶд»‘д№ӢдёҳиҖҢеҚ—жңӣгҖӮиҝҳеҪ’пјҢйҒ—е…¶зҺ„зҸ гҖӮдҪҝзҹҘзҙўд№ӢиҖҢдёҚеҫ—пјҢдҪҝзҰ»жңұзҙўд№ӢиҖҢдёҚеҫ—пјҢдҪҝеҗғиҜҹзҙўд№ӢиҖҢдёҚеҫ—д№ҹгҖӮд№ғдҪҝиұЎзҪ”пјҢиұЎзҪ”еҫ—д№ӢгҖӮй»„еёқжӣ°пјҡвҖңејӮе“үпјҒиұЎзҪ”д№ғеҸҜд»Ҙеҫ—д№Ӣд№ҺпјҹвҖқ й»„еёқд№ӢжёёжҳҜеә„еӯҗиҷҡи®ҫзҡ„дёҖж¬ЎзҘһзҒөд№Ӣж—…гҖӮд»Һз©әй—ҙиҢғеӣҙжқҘзңӢпјҢйҒҘиҝңеҜҘе»“пјҢеҲ°иҫҫе№ҝиўӨиҫҪйҳ”зҡ„иөӨж°ҙд№ӢеҢ—гҖҒжҳҶд»‘д№ӢдёҳпјҢж¶үеҸҠеҚҺеӨҸжңҖе№ҝйҳ”зҡ„д»ҷж°ҙгҖҒзҘһеұұгҖӮд»Һж—¶й—ҙиҢғеӣҙжқҘзңӢ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ж¬Ўжј«й•ҝзҡ„ж—…жёёгҖӮйҡҸзқҖж—¶й—ҙзҡ„жөҒйҖқпјҢиҝҷз§Қе®Ҫе№ҝз©әй—ҙе’ҢжӮ й•ҝж—¶й—ҙзҡ„зҘһжёёдјҡеҜјиҮҙ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и®°еҝҶж¶ҲеӨұпјҢй»„еёқйҒ—еҝҳе…¶зҺ„зҸ жҲҗдёәйҖ»иҫ‘д№Ӣеҝ…然гҖӮиҝҷз§ҚйҒ—еҝҳе°ұжҳҜдёҖз§Қи®°еҝҶзҡ„ж¶ҲеӨұпјҢж—¶й—ҙеңЁиҝҷйҮҢе……еҪ“дәҶйІңжҙ»зҡ„з”ҹжҲҗеҠӣйҮҸпјҢе®ғжҜҒзҒӯдәҶдәәзұ»еҜ№дәҺе‘Ёиҫ№дёҮиұЎзҡ„еҗ„з§ҚеҠӘеҠӣи®ӨзҹҘпјҢй»„еёқпјҲзҘһпјүдҫҝжҳҫеҫ—йқһеёёжёәе°ҸгҖӮдҪңдёә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зҡ„ж–ҮеӯҰд№ҰеҶҷжҲ–еҸҷдәӢж–Үжң¬пјҢиҝҷдёӘзҘһжёёж•…дәӢеҜ№д№ӢеҗҺзҡ„ж–ҮеӯҰд№ҰеҶҷдә§з”ҹдәҶйҮҚиҰҒеҪұе“ҚпјҢжұүд»Јж— еҗҚж°ҸгҖҠеҸӨиҜ—еҚҒд№қйҰ–гҖӢеҸҠе…¶д»ҘеҗҺж–Үдәәе’ҸеҸ№дёӯеҜ№дәҺж—¶й—ҙзҡ„жҒҗжғ§пјҢд»ҘеҸҠз”ұжӯӨеҪўжҲҗзҡ„еҸҠж—¶иЎҢд№җжҖқжғіе’Ңж—¶й—ҙи№үи·Һд№Ӣж„ҹпјҢж— дёҚеҪ°жҳҫзқҖе…Ҳз§Ұеұұж°ҙзҘһжёёеҶ…йҡҗзҡ„е“ІеӯҰжҖқиҫЁзҡ„йӯ…еҠӣе’Ңзү№иҙЁгҖӮдёҚд»…еҰӮжӯӨпјҢ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иұЎзҪ”вҖқвҖңиөӨж°ҙвҖқд№ҹжҲҗдёәеҗҺдё–ж–Үдәәд№ҰеҶҷзҡ„йҮҚиҰҒйўҳжқҗеҶ…е®№гҖӮеҲҳе®үгҖҠж·®еҚ—еӯҗгҖӢдә‘пјҡжңүзҹҘеҫҗд№Ӣдёәз–ҫпјҢиҝҹд№ӢдёәйҖҹиҖ…пјҢеҲҷеҮ дәҺйҒ“зҹЈгҖӮж•…й»„еёқдәЎе…¶зҺ„зҸ пјҢдҪҝзҰ»жңұгҖҒжҚ·еүҹзҙўд№ӢпјҢиҖҢеј—иғҪеҫ—д№Ӣд№ҹпјҢдәҺжҳҜдҪҝеҝҪжҖіиҖҢеҗҺиғҪеҫ—д№ӢгҖӮ еҝҪжҖіпјҢй»„еёқд№ӢиҮЈпјҢе–„еҝҳд№ӢдәәпјҢе…¶дёҺ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жүҖдә‘иұЎзҪ”е®һеұһдёҖд№үгҖӮеҲҳе®үеңЁжӯӨз”Ёе–„еҝҳд№ӢдәәеҸҚиҖҢеҜ»еҫ—йҒ—еҝҳд№ӢзҸ пјҢйҷӨдәҶйҳҗйҮҠеүҚйқўвҖңеҮ дәҺйҒ“вҖқзҡ„жғ…еҶөпјҲеҚіеҫҗд№Ӣдёәз–ҫгҖҒиҝҹд№ӢдёәйҖҹд№ӢзҗҶпјү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з»ҷдёӯеӣҪ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жіЁе…ҘдәҶж—¶й—ҙзҡ„ж°ёжҒ’жөҒеҠЁдјҡдҪҝи®°еҝҶж¶ҲиҡҖдёҺж·ЎеҢ–зҡ„е“ІзҗҶжҖ§и®ӨзҹҘгҖӮеңЁиөӨж°ҙгҖҒжҳҶд»‘зҡ„и§ҒиҜҒдёӢпјҢиұЎзҪ”жҲ–еҝҪжҖіжҲҗдёәи®°еҝҶеңЁж—¶й—ҙжөҒйҖқдёӯиў«йҒ—еҝҳзҡ„з¬ҰеҸ·пјҢе®ҡж јеңЁж–ҮдәәеҜ№дәҺж—¶й—ҙж°ёжҒ’иҖҢз”ҹе‘ҪеҰӮеҜ„зҡ„ж„ҹеҸ№д№Ӣдёӯ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йҷ¶жёҠжҳҺиҜҙпјҡвҖңзІІзІІдёүж Әж ‘пјҢеҜ„з”ҹиөӨж°ҙйҳҙгҖӮвҖқжқҺзҷҪгҖҠйҮ‘й—Ёзӯ”иӢҸз§ҖжүҚгҖӢдёӯ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жңӘжһңдёүеұұжңҹпјҢйҒҘж¬ЈдёҖдёҳд№җгҖӮзҺ„зҸ еҜ„зҪ”иұЎпјҢиөӨж°ҙйқһеҜҘе»“гҖӮвҖқ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зҡ„ж•…дәӢжҲҗдәҶд»Ҙйҷ¶жёҠжҳҺгҖҒжқҺзҷҪдёәд»ЈиЎЁзҡ„ж–ҮдәәеҲӣдҪңзҡ„йўҳжқҗжқҘжәҗпјҢй»„еёқгҖҒиөӨж°ҙгҖҒзҺ„зҸ гҖҒиұЎзҪ”пјҲеҝҪжҖіпјүиҝһзјҖжҲҗдёҖз»„е“ІеӯҰ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иҖҢжІүж·ҖеңЁж–ҮеӯҰд№ӢдёӯпјҢжҲҗдёәж–ҮдәәйқўеҜ№ж—¶й—ҙжҠ’еҸ‘еҗ„з§Қж„ҹж…Ёзҡ„ж·ұеҲ»ж„ҸиұЎпјҢжІүж·ҖеңЁж·ұйӮғзҡ„дёӯеӣҪ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д№ӢдёӯгҖӮе…Ҳз§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зҡ„еұұж°ҙпјҢеҫҖеҫҖд№ҹи§ҒиҜҒдәҶ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жүҖйңҖж—¶й—ҙзҡ„ж°ёжҒ’жҖ§еҶ…иҙЁпјҢиҝҷзӘҒеҮәең°иЎЁзҺ°еңЁ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еҜ№зҘһжёёзӣ®зҡ„ең°дёҚжӯ»еұұд»ҘеҸҠдёҚжӯ»ж ‘гҖҒдёҚжӯ»ж°‘гҖҒдёҚжӯ»еӣҪзҡ„еҸҷиҝ°д№ӢдёӯпјҢд№ҹеҢ…еҗ«еңЁ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жүҖеҶҷж—…жёёд№Ӣеёқе‘Ёз©ҶзҺӢеҜ№ж—¶й—ҙж°ёй©»зҡ„еҗ‘еҫҖд№ӢдёӯгҖ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дә‘пјҡжөҒжІҷд№ӢдёңпјҢй»‘ж°ҙд№Ӣй—ҙпјҢжңүеұұеҗҚдёҚжӯ»д№ӢеұұгҖӮејҖжҳҺеҢ—жңүи§ҶиӮүпјҢзҸ ж ‘пјҢж–ҮзҺүж ‘пјҢзҺ—зҗӘж ‘пјҢдёҚжӯ»ж ‘гҖӮдёҚжӯ»ж°‘еңЁе…¶дёңпјҢе…¶дёәдәәй»‘иүІпјҢеҜҝпјҢдёҚжӯ»гҖӮжңүдёҚжӯ»д№ӢеӣҪпјҢйҳҝ姓пјҢз”ҳжңЁжҳҜйЈҹгҖӮ дёҠеј•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жүҖиҝ°дёҚжӯ»еұұгҖҒдёҚжӯ»ж ‘гҖҒдёҚжӯ»ж°‘гҖҒдёҚжӯ»еӣҪпјҢеӯҳеңЁдәҺзҘһжёёжүҖи§Ғд№Ӣеұұж°ҙд№Ӣй—ҙпјҢдәә们еҜ№дәҺж—¶й—ҙзҡ„ж°ёжҒ’жҖ§и®ӨзҹҘе’Ңж„ҝжҷҜйҡҗеҗ«еңЁеұұж°ҙж„ҸиұЎд№ӢдёӯпјҢз”ұжӯӨеҸҜд»Ҙжҷ®йҒҚеҢ–дёәдәәзұ»дёӘдҪ“еҜ№дәҺз”ҹе‘Ҫй•ҝд№…гҖҒеҜҝйҪҝж°ёжҒ’зҡ„зӣјжңӣпјҢд»ҺиҖҢеҮқз»“дёәдәәзұ»зҡ„з”ҹе‘Ҫе“ІзҗҶгҖӮеӣ иҖҢйҷ¶жёҠжҳҺжңүиҜ—дә‘пјҡвҖңиҮӘеҸӨзҡҶжңүжІЎпјҢдҪ•дәәеҫ—зҒөй•ҝпјҹдёҚжӯ»еӨҚдёҚиҖҒпјҢдёҮеІҒеҰӮе№іеёёгҖӮиөӨжіүз»ҷжҲ‘йҘ®пјҢе‘ҳдёҳи¶іжҲ‘зІ®гҖӮж–№дёҺдёүиҫ°жёёпјҢеҜҝиҖғеІӮжё еӨ®пјҒвҖқиҝҷз§ҚеҜ№з”ҹе‘Ҫж°ёжҒ’зҡ„жёҙжңӣпјҢе·Іжһ„жҲҗ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–ҮеӯҰзҡ„жҷ®йҒҚжҖ§дё»йўҳпјҢ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гҖӮ 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ж—…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д»ЈиЎЁдҪңж— з–‘йҰ–жҺЁ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пјҢе…¶дёӯе‘Ёз©ҶзҺӢзҘһжёёжҳҶд»‘жҲ–иҖ…иҜҙзҘһдәӨиҘҝзҺӢжҜҚпјҢжҳҜ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ҮәеҪ©д№Ӣз« пјҢе…¶дёӯжңүдә‘пјҡжҲҠеҚҲвҖҰвҖҰеӨ©еӯҗйҘ®иҖҢиЎҢпјҢйҒӮе®ҝдәҺжҳҶд»‘д№ӢйҳҝпјҢиөӨж°ҙд№ӢйҳігҖӮ иҫӣеҚҜпјҢеӨ©еӯҗеҢ—еҫҒпјҢдёңиҝҳпјҢд№ғеҫӘй»‘ж°ҙпјҢзҷёе·іпјҢиҮідәҺзҫӨзҺүд№ӢеұұгҖӮ еҗүж—Ҙз”ІеӯҗпјҢеӨ©еӯҗе®ҫдәҺиҘҝзҺӢжҜҚпјҢд№ғжү§зҷҪеңӯзҺ„з’§д»Ҙи§ҒиҘҝзҺӢжҜҚпјҢзҢ®й”Ұз»„зҷҫзәҜпјҢиҘҝзҺӢжҜҚеҶҚжӢңеҸ—д№ӢгҖӮд№ҷдё‘пјҢеӨ©еӯҗи§һиҘҝзҺӢжҜҚдәҺ瑶жұ д№ӢдёҠгҖӮиҘҝзҺӢжҜҚдёәеӨ©еӯҗи°Јжӣ°пјҡвҖңзҷҪдә‘еңЁеӨ©пјҢеұұйҷөиҮӘеҮәгҖӮйҒ“йҮҢжӮ иҝңпјҢеұұе·қй—ҙд№ӢгҖӮе°Ҷеӯҗж— жӯ»пјҢе°ҡиғҪеӨҚжқҘгҖӮвҖқеӨ©еӯҗзӯ”д№Ӣжӣ°пјҡвҖңдәҲеҪ’дёңеңҹпјҢе’ҢжІ»иҜёеӨҸгҖӮдёҮж°‘е№іеқҮпјҢеҗҫйЎҫи§ҒжұқгҖӮжҜ”еҸҠдёүе№ҙпјҢе°ҶеӨҚиҖҢйҮҺгҖӮвҖқеӨ©еӯҗйҒӮй©ұеҚҮдәҺејҮеұұгҖӮ иҝҷдәӣжҸҸеҶҷи®°еҸҷдәҶеұұж°ҙд№ӢжёёеҺҶгҖҒжӮ иҝңз©әй—ҙдёҺжј«й•ҝж—¶й—ҙзҡ„дәӨжӣҝпјҢд»ҘеҸҠж—¶з©әиҪ¬жҚўе”Өиө·зҡ„еҜ№дәҺвҖңж— жӯ»вҖқпјҲеҚідёҚжӯ»пјүзҡ„жёҙжңӣгҖӮ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дҪ“зҺ°дәҶе…Ҳж°‘дәҺеұұж°ҙжёёеҺҶд№Ӣдёӯз„•еҸ‘зҡ„ж„үжӮҰд№Ӣжғ…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№ҹдҪ“зҺ°еҮәе…Ҳж°‘еҜ№дәҺз”ҹе‘Ҫж°ёжҒ’гҖҒж—¶е…үж°ёй©»зҡ„дҝЎд»°иҝҪжұӮгҖӮиҒҢжҳҜд№Ӣж•…пјҢз©ҶзҺӢзҘһжёёиҘҝзҺӢжҜҚдҫҝжҲҗдёәд№ӢеҗҺж–Үдәәе’Ҹе”ұ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иҝӣиҖҢеҮқеӣәдёәдёҖз§ҚвҖңз©ҶзҺӢжғ…з»“вҖқд»ҘзӨәеҜ№з”ҹе‘ҪжҒ’д№…зҡ„еҗ‘еҫҖгҖӮж•…йҷ¶жёҠжҳҺжңүиҜ—дә‘пјҡвҖңиҝўиҝўж§җжұҹеІӯпјҢжҳҜдёәзҺ„еңғдёҳгҖӮиҘҝеҚ—жңӣжҳҶеўҹпјҢе…үж°”йҡҫдёҺдҝҰгҖӮдәӯдәӯжҳҺзҺ•з…§пјҢжҙӣжҙӣ清瑶жөҒгҖӮжҒЁдёҚеҸҠе‘Ёз©ҶпјҢжүҳд№ҳдёҖжқҘжёёгҖӮвҖқе”җе®Ӣж–ҮдәәйӘҡе®ўеҰӮжқҺе•ҶйҡҗгҖҒиӢҸиҪјзӯүеӨ§и§„жЁЎз»Үз»©вҖңз©ҶзҺӢжғ…з»“вҖқпјҢдҪҝе…¶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еӨ§дё»йўҳгҖӮеҰӮжқҺзҷҪгҖҠеҸӨйЈҺгҖӢпјҲе…¶еӣӣеҚҒдёүпјүдә‘пјҡвҖңе‘Ёз©Ҷе…«иҚ’ж„ҸпјҢжұүзҡҮдёҮд№ҳе°ҠгҖӮвҖқгҖҠеӨ©й©¬жӯҢ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Ҝ·еҗӣиөҺзҢ®з©ҶеӨ©еӯҗпјҢзҠ№е Әеј„еҪұиҲһ瑶жұ гҖӮвҖқжқҺе•ҶйҡҗгҖҠ瑶жұ 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瑶жұ йҳҝжҜҚз»®зӘ—ејҖпјҢй»„з«№жӯҢеЈ°еҠЁең°е“ҖгҖӮе…«йӘҸж—ҘиЎҢдёүдёҮйҮҢпјҢз©ҶзҺӢдҪ•дәӢдёҚйҮҚжқҘгҖӮвҖқиӢҸиҪјгҖҠж•…жқҺиҜҡд№Ӣеҫ…еҲ¶е…ӯдёҲжҢҪиҜҚ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ҸҲж— з©ҶеӨ©еӯҗпјҢиҘҝеҫҒзҮ•з‘¶жұ гҖӮвҖқ他们еҜ№дәҺз”ҹе‘Ҫж°ёеӯҳзҡ„жёҙзӣј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–ҮеӯҰзҡ„йҮҚиҰҒе…ғзҙ пјҢдё°еҜҢдәҶдёӯеҚҺдјҳз§Җ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зҡ„е®қеә“пјҢ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дёӯзҘһжёёиҘҝзҺӢжҜҚд№ӢжҳҶд»‘еұұж°ҙзҡ„ж–ҮеӯҰд№ҰеҶҷжүҖеҶ…йҡҗзҡ„еұұж°ҙеҗ«д№ү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иҝҷз§Қ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жүҖи•ҙеҗ«зҡ„еұұж°ҙж„Ҹд№үжҲ–еұұж°ҙеҶ…иҙЁпјҢеҚіеұұж°ҙдҪңдёәе®ўдҪ“ж„ҹеҠЁдәҺдё»дҪ“еҜ№дәҺз”ҹе‘Ҫж—¶е…үзҡ„ж°ёжҒ’зҘҲзҘ·пјҢеңЁгҖҠжҘҡиҫһВ·иҝңжёёгҖӢдёӯдәҰжңүе……еҲҶзҡ„иЎЁзҺ°пјҡвҖңжӮІж—¶дҝ—д№Ӣиҝ«йҳЁе…®пјҢж„ҝиҪ»дёҫиҖҢиҝңжёёвҖҰвҖҰжғҹеӨ©ең°д№Ӣж— з©·е…®пјҢе“Җдәәз”ҹд№Ӣй•ҝеӢӨвҖҰвҖҰй—»иөӨжқҫд№Ӣжё…е°ҳе…®пјҢж„ҝжүҝйЈҺд№ҺйҒ—еҲҷгҖӮиҙөзңҹдәәд№Ӣдј‘еҫ·е…®пјҢзҫҺеҫҖдё–д№Ӣзҷ»д»ҷгҖӮвҖқеңЁеӨ©ең°зҡ„жӮ иҝңиҫҪйҳ”йқўеүҚпјҢиҜ—дәәж„ҹеҸ№зҺ°е®һз”ҹе‘Ҫзҡ„жёәе°ҸдёҺзҹӯжҡӮпјҢж•…иҖҢеҖҹиҝңжёёпјҲзҘһжёёпјүеҗ‘еӨ©ең°зҘһзҒөзҘҲжұӮзҷ»д»ҷпјҢ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иЎЁиҫҫеёҢеҶҖз”ҹе‘Ҫж°ёжҒ’еӯҳеңЁзҡ„ж„ҝжҷҜгҖӮж•…иҜ—дәәдә‘пјҡвҖңиҒҠд»ҝдҪҜиҖҢйҖҚйҒҘе…®пјҢж°ёеҺҶе№ҙиҖҢж— жҲҗгҖӮвҖқеұҲеҺҹеёҢжңӣеңЁеұұж°ҙйҖҚйҒҘеҫңеҫүд№ӢдёӯпјҢдёҺж°ёжҒ’зҡ„ж—¶е…үеҗҢеңЁпјҢдҪҶдәӢдёҺж„ҝиҝқгҖӮеҜ№дәҺвҖңдёҚжӯ»вҖқзҡ„ж—¶й—ҙзҡ„еҗ‘еҫҖпјҢдҫқ然жҳҜгҖҠжҘҡиҫһгҖ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“ІжҖқеҶ…ж¶өд»ҘеҸҠеұұж°ҙе®ўдҪ“жүҖиөӢдәҲзҡ„еҶ…иҙЁпјҢжӯЈжүҖи°“вҖңд»ҚзҫҪдәәдәҺдё№дёҳе…®пјҢз•ҷдёҚжӯ»д№Ӣж—§д№ЎвҖқгҖӮдё№дёҳжҳҜзҘһеұұд№ӢжүҖпјҢд№ҹжҳҜиҜ—дәәзҘһжёёзҡ„еңЈең°гҖҒвҖңдёҚжӯ»вҖқзҡ„ж°ёжҒ’д№Ӣд№ЎгҖҒз”ҹе‘Ҫеӯҳж”ҫзҡ„й•ҝе®үд№ӢеӨ„гҖӮ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д»Һ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зҡ„дёҚжӯ»еұұгҖҒдёҚжӯ»ж ‘гҖҒдёҚжӯ»ж°‘гҖҒдёҚжӯ»еӣҪпјҢеҲ°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зҡ„дёҚжӯ»дәәпјҢеҶҚеҲ°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зҡ„дёҚжӯ»д№ЎпјҢдёҚж–ӯз”ұз©әй—ҙзҡ„еұұгҖҒд№Ўйҡҗе–»ж—¶й—ҙдёҚжӯ»пјҲж°ёжҒ’пјүпјҢ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ж–ҮеӯҰеҸІдёҠжңҖж—©д»Ҙеұұж°ҙдҪңдёәж—¶й—ҙжҰӮеҝөзҡ„йҡҗе–»дҪ“пјҢеҶ…иҒҡзқҖе…·жңүжҖқиҫЁзү№еҫҒзҡ„йҡҗжҖ§ж–ҮеҢ–еҗ«д№үпјҢд»ҺиҖҢдҪҝжҲ‘еӣҪж—©жңҹ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з„•еҸ‘еҮәз’Җз’Ёзҡ„е…үиҠ’пјҢз…§дә®дәҶе®ғдҪңдёәж–ҮеӯҰеҲҶж”Ҝзҡ„еүҚиҝӣйҒ“и·ҜгҖӮжңүж— зӣёз”ҹд№ҹжҳҜ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“ІжҖқеҶ…ж¶өд№ӢдёҖгҖӮеұұж°ҙж—…жёёпјҢи§Ҳзү©и§ӮжҷҜпјҢиҮӘ然з•Ңз»ҷдәә们е‘ҲзҺ°зҡ„еҫҖеҫҖжҳҜиүІз©әзӣёеҖҡгҖҒжңүж— зӣёз”ҹзҡ„е®ўи§ӮеӯҳеңЁпјҢиҝҷдәӣе®ўи§ӮеӯҳеңЁеҜ“еҗ«зқҖеҜ№з«Ӣз»ҹдёҖзҡ„жҰӮеҝөеҪўжҖҒпјҢдҪң家们д»Ҙж•Ҹй”җзҡ„е“ІеӯҰеӨҙи„‘е°Ҷе®ғ们编з»ҮеңЁ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№ӢдёӯпјҢд»ҘжӯӨеҸҚжҳ 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зӢ¬зү№зҡ„ж–ҮеҢ–йӯ…еҠӣгҖӮгҖҠеә„еӯҗВ·еә”еёқзҺӢгҖӢдә‘пјҡеӨ©ж №жёёдәҺж®·йҳіпјҢиҮіи“јж°ҙд№ӢдёҠпјҢйҖӮйҒӯж— еҗҚдәәиҖҢй—®з„ү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иҜ·й—®дёәеӨ©дёӢгҖӮвҖқ ж— еҗҚдәәжӣ°пјҡвҖңеҺ»пјҒжұқй„ҷдәәд№ҹпјҢдҪ•й—®д№ӢдёҚиұ«д№ҹпјҹдәҲж–№е°ҶдёҺйҖ зү©иҖ…дёәдәәпјҢеҺҢпјҢеҲҷеҸҲд№ҳеӨ«иҺҪзңҮд№ӢйёҹпјҢд»ҘеҮәе…ӯжһҒд№ӢеӨ–пјҢиҖҢжёёж— дҪ•жңүд№Ӣд№ЎпјҢд»ҘеӨ„ең№еҹҢд№ӢйҮҺгҖӮжұқеҸҲдҪ•еёӣд»ҘжІ»еӨ©дёӢж„ҹдәҲд№ӢеҝғдёәпјҹвҖқеҸҲеӨҚй—®гҖӮж— еҗҚдәәжӣ°пјҡвҖңжұқжёёеҝғдәҺж·ЎпјҢеҗҲж°”дәҺжј пјҢйЎәзү©иҮӘ然иҖҢж— е®№з§Ғз„үпјҢиҖҢеӨ©дёӢжІ»зҹЈгҖӮвҖқ ж— ж №еңЁжӯӨж¬Ўеұұж°ҙд№ӢжёёдёӯпјҢеҜ№жүҖйҒҮгҖҒжүҖй—®иҖ…йҳҗиҝ°жІ»еӨ©дёӢд№ӢйҒ“пјҢд»Ҙж— еҫЎжңүпјҢжңүпјҲжІ»пјүеҫ…дәҺж— пјҲиҮӘ然пјүпјҢеұұж°ҙд№Ӣжёёй—ҙиҝёеҸ‘еҮәжңүж— зӣёз”ҹзҡ„е“ІеӯҰжҖқиҫЁпјҢеҪ°жҳҫдәҶж—…жёёиЎҢдёәзҡ„е·ЁеӨ§йӯ…еҠӣдёҺж–ҮеҢ–еә•и•ҙгҖӮеӨ©ж №д№ӢжёёжҳҜеә„еӯҗйў„и®ҫзҡ„зҘһжёёд№ӢдёҫпјҢе…¶е“ІжҖқеҗ«и•ҙеұұж°ҙиҖҢеҶ…и“„д№ӢпјҢеұұж°ҙд№ӢеҜ“пјҢдәҺе…№еҸҜи§ҒгҖӮеҗҢзҜҮеҸҲдә‘пјҡеҚ—жө·д№Ӣеёқдёәе„өпјҢеҢ—жө·д№ӢеёқдёәеҝҪпјҢдёӯеӨ®д№Ӣеёқдёәжө‘жІҢгҖӮе„өдёҺеҝҪж—¶зӣёдёҺйҒҮдәҺжө‘жІҢд№Ӣең°пјҢжө‘жІҢеҫ…д№Ӣз”ҡе–„гҖӮе„өдёҺеҝҪи°ӢжҠҘжө‘жІҢд№Ӣеҫ·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дәәзҡҶжңүдёғзӘҚд»Ҙи§Ҷеҗ¬йЈҹжҒҜпјҢжӯӨзӢ¬ж— жңүпјҢе°қиҜ•еҮҝд№ӢгҖӮвҖқж—ҘеҮҝдёҖзӘҚпјҢдёғж—ҘиҖҢжө‘жІҢжӯ»гҖӮ дҪңдёәиҷҡжһ„зҡ„дёүеёқпјҲзҘһпјүпјҢеҚ—еҢ—дәҢеёқеҗ„иҮӘж—…жёёпјҢ并дәҺдёӯеӨ®зӣёйҒҮпјҢдәҺжҳҜеҸ‘з”ҹдәҶжңүж— и§Ӯеҝөзҡ„е…ізі»и®әпјҢжңүзҡ„дә§з”ҹжҳҜеҫ…дәҺж— зҡ„пјҢжө‘жІҢд№Ӣжӯ»зҡ„з»“жһңжҳҜ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зҡ„й“ҒиҜҒ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ж·ұеұӮе“ІжҖқйғҪеңЁжңүж–№еҗ‘зҡ„иҝҗиЎҢпјҲж—…жёёпјүдёӯдә§з”ҹпјҢеҶҚж¬ЎиҜҙжҳҺдәҶ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ңЁжҖқиҫЁеҶ…ж¶өдёҠ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дёҚиҝҮжӯӨд№ӢжүҖи°“зҡ„зҘһжёёпјҢжҳҜд»Һ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Қ—еҢ—дёӯеӨ®д№Ӣеёқзҡ„иә«д»ҪдёҠе®ҡжҖ§зҡ„пјҢдёҚеғҸжӯӨеүҚзҡ„зҒөйӯӮжҲ–зІҫзҘһд№ӢжёёжҲ–д»ҷжёёгҖӮеңЁе…Ҳз§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з§Қе‘ҲзҺ°еұұж°ҙеҶ…иҙЁзҡ„йҡҗд№үжҖ§е“ІжҖқж–ҮеҢ–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еҠЁжңәж•Ҳжһңзҡ„иҫ©иҜҒе…ізі»гҖӮ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ҪңдёәиҜёеӯҗе“ІзҗҶж•Јж–Үзҡ„е…ёиҢғд№ӢдҪңпјҢи®әеҸҠдәҶжҲ‘еӣҪж—©жңҹе“ІеӯҰзҡ„иҜёеӨҡй—®йўҳгҖӮеңЁе…¶жүҖж¶үе“ІеӯҰиҢғз•ҙдёӯпјҢжңүи®әеҸҠеҠЁжңәдёҺж•ҲжһңиҢғз•ҙиҖ…дё»иҰҒжңүдёүз§Қжғ…еҶөпјҡдёҖжҳҜеҠЁжңәдёҺж•ҲжһңдёҚз»ҹдёҖпјҢеҰӮгҖҠеә„еӯҗВ·еӨ©иҝҗгҖӢд№ӢвҖңдёңж–Ҫж•ҲйўҰвҖқпјӣдәҢжҳҜеҠЁжңәзӣёеҗҢдҪҶж•ҲжһңдёҚдёҖпјҢеҰӮгҖҠйҖҚйҒҘжёёгҖӢд№ӢвҖңе®Ӣдәәиө„з« з”«вҖқпјӣдёүжҳҜеҠЁжңәдёҚдёҖдҪҶж•ҲжһңзӣёеҗҢпјҢеҰӮгҖҠйӘҲжӢҮгҖӢд№ӢвҖңиҮ§и°·дәЎзҫҠвҖқгҖӮеүҚиҝ°вҖңй»„еёқйҒ—зҺ„зҸ вҖқпјҢеұһдәҺ第дёҖз§Қжғ…еҪўгҖӮй»„еёқжҙҫеӣӣеӯҗеҺ»еҜ»жүҫйҒ—зҸ зҡ„еҠЁжңәжҳҜдёҖж ·зҡ„пјҢдҪҶж•ҲжһңдёҚдёҖж ·пјҢдҪңдёәж•Ҳжһңзҡ„и§ҒиҜҒеҲҷжҳҜзҘһжёёдёӯзҡ„еұұж°ҙвҖ”вҖ”иөӨж°ҙд№ӢеҢ—гҖҒжҳҶд»‘д№Ӣдёҳ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зҹҘпјҢеұұж°ҙдҪңдёәйҡҗе–»жҖ§зҡ„зү©иұЎпјҢеңЁ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жүҖеј•еҸ‘зҡ„ж–ҮеҢ–з¬ҰеҸ·д»·еҖјйқһеҗҢдёҖиҲ¬пјҢдәҹеҫ…жҲ‘们еҺ»еҸ‘жҺҳгҖӮдәҢгҖҒ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®ЎзҫҺи§Ӯз…§ ж—…жёёжң¬иә«жҳҜдёәдәҶеҺ»ж¬ЈиөҸе’ҢеҸ‘зҺ°иҮӘ然д№ӢзҫҺпјҢдҪҶеңЁ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пј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ңЁзІҫзҘһдё–з•ҢдёӯиҝҳеҲӣйҖ дәҶеӨҡз§Қе®ЎзҫҺж–№ејҸпјҢиөӢдәҲиҮӘ然еұұж°ҙд»Ҙдё»дҪ“ж„Ҹеҝ—е’ҢиҜ„еҲӨжҖҒеәҰпјҢдҪҝеҫ—дёӯеӣҪж—©жңҹзҡ„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д»ҺдёҖејҖе§Ӣе°ұеҶ…ж¶өдё°еҜҢгҖӮгҖҠеә„еӯҗВ·йҖҚйҒҘжёёгҖӢжҳҜ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жқ°дҪңпјҢеҮ иҝ‘зҘһеҢ–ејҸең°жҸҸеҶҷдәҶйІІй№Ҹд№Ӣжёёе’ҢзҘһд»ҷд№ӢжёёпјҢйҖҡиҝҮиҝҷдёӨз§ҚзҘһжёёе‘ҲзҺ°дәҶеә„е‘ЁиҝҪжұӮзҡ„еЈ®йҳ”зЈ…зӨҙд№ӢзҫҺе’ҢзјҘзјҲз»°зәҰд№ӢзҫҺпјҢдёәдёӯеӣҪзҫҺеӯҰеҲӣз«Ӣе’ҢиҙЎзҢ®дәҶдёӨеӨ§зҫҺеӯҰиҢғз•ҙпјҢд»ҺиҖҢиөӢдәҲеұұж°ҙд»Ҙе®ЎзҫҺеҶ…и•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иў«еҠЁең°еҺ»ж¬ЈиөҸеұұж°ҙе®ўи§ӮеӯҳеңЁзҡ„зҫҺгҖӮеҢ—еҶҘжңүйұјпјҢе…¶еҗҚдёәйІІгҖӮйІІд№ӢеӨ§пјҢдёҚзҹҘе…¶еҮ еҚғйҮҢд№ҹгҖӮеҢ–иҖҢдёәйёҹпјҢе…¶еҗҚдёәй№ҸпјҢй№Ҹд№ӢиғҢпјҢдёҚзҹҘе…¶еҮ еҚғйҮҢд№ҹпјӣжҖ’иҖҢйЈһпјҢе…¶зҝјиӢҘеһӮеӨ©д№Ӣдә‘гҖӮжҳҜйёҹд№ҹпјҢжө·иҝҗеҲҷе°ҶеҫҷдәҺеҚ—еҶҘгҖӮеҚ—еҶҘиҖ…пјҢеӨ©жұ д№ҹгҖӮ еңЁиҝҷж®өжғҠиүі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»Ҹе…ёдёӯпјҢдҪңиҖ…и§ЈйҮҠдәҶйІІй№ҸжҳҜи®°еҪ•дәҺеҪ“ж—¶еҝ—жҖӘиҖ…гҖҠйҪҗи°җгҖӢдёӯзҡ„жҖӘи°Ід№Ӣзү©гҖӮеңЁе…Ҳз§ҰжіӣзҘһи®әжҖқз»ҙдёӯпјҢеҮЎиҜЎи°Ід№Ӣзү©зҡҶзҘһжҖ§д№ӢдҪ“пјҢж•…йІІй№Ҹд№ӢжёёеҚ—еҶҘе®һдёәзҘһжёёгҖӮ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»ҘзЈ…зӨҙеЈ®йҳ”гҖҒиө«з„¶й«ҳеӨ§гҖҒжіўж¶ӣжұ№ж¶Ңзӯүйӣ„дјҹд№ӢзҫҺе‘ҲзҺ°дәҺд»ҺеҢ—еҶҘеҲ°еҚ—еҶҘзҡ„еұұж°ҙз©әй—ҙпјҢеҚіеңЁзҘһжёёдёӯе……еҲҶеҲӣйҖ дё»дҪ“ж„ҸиҜҶ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ё»еҠЁд»Ҙеұұж°ҙдёәдҫқжүҳе‘ҲзҺ°е…¶и§ӮеҝөеҪўжҖҒдёӢзҡ„е®ЎзҫҺиҝҪжұӮгҖӮжҳҫ然пјҢиҝҷдёҖзІҫзҘһжҙ»еҠЁд№ҹеұ•зӨәдәҶдҪңдёәзҘһжёёжүҚе…·жңүзҡ„ж—…жёёдјҳеҠҝгҖӮиҒҢжҳҜд№Ӣж•…пјҢдҪңиҖ…еңЁйІІй№Ҹиҝңжёёз”ҡиҮізҘһдәәеҲ—еӯҗеҫЎйЈҺиҖҢжёёд№ӢеҗҺ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йҳҗеҸ‘зҘһжёёзҡ„ж·ұеҲ»еҗ«д№үпјҡвҖңиӢҘеӨ«д№ҳеӨ©ең°д№ӢжӯЈпјҢиҖҢеҫЎе…ӯж°”д№Ӣиҫ©пјҢд»Ҙжёёж— з©·иҖ…пјҢеҪјдё”жҒ¶д№Һеҫ…е“үпјҒвҖқзҘһжёёзҡ„еҲӨж–ӯж ҮеҮҶжҲ–иҖ…иҜҙжҰӮеҝөз•Ңе®ҡеҝ…йЎ»жҳҜд№ҳеӨ©ең°д№ӢжӯЈгҖҒеҫЎе…ӯж°”д№Ӣиҫ©иҖҢжёёдәҺж— иҫ№ж— йҷ…зҡ„е®Үе®ҷз©әй—ҙ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еә„еӯҗжүҖеҸ‘жҳҺзҡ„зҘһжёёеҲҶдёәдёӨдёӘеұӮж¬ЎпјҡдёҖжҳҜйІІй№ҸејҸзҡ„зҘһжёёпјҢдәҢжҳҜй©ҫй©ӯдәҶйҒ“зҡ„зҘһжёёпјҢдёӨиҖ…зҡ„еҲ’еҲҶж ҮеҮҶжҳҜе“ІеӯҰеұӮйқўзҡ„вҖңйҒ“вҖқжҲ–дҪ“йҒ“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ҫқз…§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зҡ„еҲӨж–ӯж ҮеҮҶеҺ»иЎЎйҮҸпјҢиҝҷдёӨз§ҚзҘһжёёжӣҙе…іжіЁе…¶ж–ҮеӯҰиүәжңҜеҗ«д№үжҲ–зҫҺеӯҰд»·еҖјгҖӮ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иҝҳж¶үеҸҠ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Ҫңдёәд»ҷзҡ„иә«д»ҪжүҖе®ҢжҲҗзҡ„ж—…жёёз»ҸеҺҶгҖӮдҪҶд»Һ科еӯҰе®ўи§Ӯзҡ„ж„Ҹд№үжқҘиҜҙпјҢвҖңд»ҷвҖқжҳҜдәәзұ»дҝЎд»°дёҠзҡ„зҗҶжғіиҷҡжһ„пјҢиҝҷз§ҚеҖҹеҠ©дәҺвҖңд»ҷвҖқжқҘжЁЎд»ҝзҺ°е®һдёӯзҡ„дәәзҡ„жёёеҺҶпјҢе…¶е®һжҳҜдәәзұ»зІҫзҘһж”ҫйЈһзҡ„йҡҗе–»пјҢгҖҠеә„еӯҗВ·йҖҚйҒҘжёёгҖӢдёӯзҡ„и—җ姑射д№ӢжёёдҫҝеұһдәҺжӯӨгҖӮе…¶ж–Үжӣ°пјҡи—җ姑射д№ӢеұұпјҢжңүзҘһдәәеұ…з„үпјҢиӮҢиӮӨиӢҘеҶ°йӣӘпјҢз»°зәҰиӢҘеӨ„еӯҗгҖӮдёҚйЈҹдә”и°·пјҢеҗёйЈҺйҘ®йңІгҖӮд№ҳдә‘ж°”пјҢеҫЎйЈһйҫҷпјҢиҖҢжёёд№Һеӣӣжө·д№ӢеӨ–гҖӮ иҝҷйҮҢеҜ№дәҺ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ҪўиІҢжҸҸеҶҷе’ҢзҘһжҖҒжҸҸеҶҷпјҢжіЁйҮҚе®ЎзҫҺж„ҹеҸ—зҡ„е‘ҲзҺ°пјҢдҪҝжҺҘеҸ—иҖ…иғҪжҠҪиұЎеҮәзјҘзјҲз»°зәҰзҡ„е®ЎзҫҺиҢғз•ҙжҲ–зҫҺж„ҹеҗ«и•ҙпјҢе°ҶзҫҺзҡ„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пјҲзҘһдәәпјүдёҺзҫҺзҡ„ж—…жёёе®ўдҪ“пјҲеӣӣжө·д№ӢеӨ–вҖ”вҖ”еұұж°ҙеҶ…еӨ–пјүз»ҹдёҖиө·жқҘпјҢе…¶е®һжҳҜиөӢдәҲдәҶеұұж°ҙеҶ…еңЁзҡ„зҫҺеӯҰеҗ«д№үгҖӮ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иҜҙпјҢеұұж°ҙеҲӣйҖ дәҶеҶ°иӮҢзҺүйӘЁгҖҒзјҘзјҲз»°зәҰзӯүзҫҺеӯҰиҢғз•ҙпјҢеұұж°ҙдҪңдёәйҡҗе–»жҖ§з¬ҰеҸ·е……ж»ЎдәҶиҝ·дәәзҡ„еҶ…еңЁиҙЁжҖ§пјҢиҝҷжҳҜ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д»·еҖјжҢҮеҗ‘д№ӢдёҖгҖӮеҗҢж ·е…·жңүе®ЎзҫҺеҗ«и•ҙ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еңЁгҖҠжҘҡиҫһВ·иҝңжёёгҖӢдёӯдәҰиЎЁзҺ°еҫ—дё°еҜҢеӨҡеҪ©гҖӮиҜ—жӯҢдёҖејҖе§Ӣе°ұеұ•зҺ°еҮәдёҖдёӘиҪ»дёҫйЈҳеҝҪзҡ„иҝңжёёиҖ…еҪўиұЎпјҢз»ҷдәәд»ҘзҫҺеҰҷиҪ»зӣҲзҡ„еҪўжҖҒзҫҺпјҢвҖңж„ҝиҪ»дёҫиҖҢиҝңжёёвҖқпјҢвҖңз„үжүҳд№ҳиҖҢдёҠжө®вҖқгҖӮиҝҷз§ҚеҪўжҖҒзҫҺдёҺиҜ—дәәжғіиҰҒж‘Ҷи„ұжҘҡеӣҪиӮ®и„Ҹй»‘жҡ—зҡ„зҺ°е®һзӨҫдјҡпјҢж”ҫйЈһй•ҝжңҹиў«иҝ«е®ізҡ„еҝғжғ…жңүжһҒеӨ§е…іиҒ”гҖӮиҝҷд№ҹиҜҒжҳҺдәҶзҘһжёёиҝңж–№еұұж°ҙз»ҷ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ёҰжқҘзҡ„е®ЎзҫҺеЁұд№җпјҢж—ўжңүеӨ–еңЁеҪўжҖҒзҡ„иЎЁзҺ°д№ӢзҫҺпјҢд№ҹжңүеҶ…еңЁж„ҹи§үзҡ„и“„ж•ӣд№ӢзҫҺгҖӮеӣ жӯӨ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зҘһжёёд»ҘжҸҗдҫӣе®ЎзҫҺдёәзӣ®зҡ„пј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Ҳҷд»ҘиЎЁзҺ°зҫҺдёәдҪҝе‘ҪгҖӮеңЁиҝҷйҰ–иҜ—дёӯпј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ҪўжҖҒзҫҺд»ҺдёҖејҖе§ӢзҘһжёёдҫҝиЎЁзҺ°еҮәжқҘпјҢиҖҢеҪ“е…¶вҖңиҘҝеҫҒвҖқж—¶пјҢеҚізҘһжёёиҝӣдёҖжӯҘеҸ‘еұ•ж—¶пјҢеҲҷе‘ҲзҺ°еҮәеҸҰдёҖз§Қе®ЎзҫҺеҪўжҖҒпјҡвҖңжҒҗеӨ©ж—¶д№Ӣд»ЈеәҸе…®пјҢиҖҖзҒөжҷ”иҖҢиҘҝеҫҒгҖӮеҫ®йңңйҷҚиҖҢдёӢжІҰе…®пјҢжӮјиҠіиҚүд№Ӣе…Ҳйӣ¶гҖӮиҒҠеҫңеҫүиҖҢйҖҚйҒҘе…®пјҢж°ёеҺҶе№ҙиҖҢж— жҲҗгҖӮи°ҒеҸҜдёҺзҺ©ж–ҜйҒ—иҠіе…®пјҢй•ҝеҗ‘йЈҺиҖҢиҲ’жғ…гҖӮвҖқиӮғиӮғйңңйЈҺпјҢиҠіиҚүеҮӢйӣ¶пјҢжҳҜдёҖз§ҚеҮ„еҶ·иҗҪеҜһд№ӢзҫҺпјҢиӢҰ涩зҡ„иҜ—жӯҢж„Ҹеўғж·ұи—ҸзқҖ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жҲ–жҠ’жғ…дё»дҪ“ж— йҷҗзҡ„дәәз”ҹйҳ…еҺҶд№Ӣж…ЁпјҢеұұж°ҙйЈҺзү©еҶ…йҡҗзҡ„е–»д№үи§ҰжүӢеҸҜеҸҠгҖӮе…¶д»–еҰӮеҗ‘еҚ—зҡ„зҘһжёёпјҡвҖңйЎәеҮҜйЈҺд»Ҙд»Һжёёе…®пјҢиҮіеҚ—е·ўиҖҢеЈ№жҒҜвҖқпјҢвҖңжҢҮзӮҺзҘһиҖҢзӣҙй©°е…®пјҢеҗҫе°ҶеҫҖд№ҺеҚ—з–‘вҖқпјӣеҗ‘еҢ—зҡ„зҘһжёёпјҡвҖңиҲ’并иҠӮд»Ҙй©°йӘӣе…®пјҢйҖҙз»қеһ д№ҺеҜ’й—ЁгҖӮиҪ¶иҝ…йЈҺдәҺжё…жәҗе…®пјҢд»ҺйўӣйЎјд№ҺеўһеҶ°гҖӮеҺҶзҺ„й—Ёд»ҘйӮӘеҫ„е…®пјҢд№ҳй—ҙз»ҙд»ҘеҸҚйЎҫвҖқпјҢеңЁеҚ—еҢ—зҘһжёёдёӯпјҢиҜ—дәәйӮЈз§ҚдёҠеӨ©ж— и·ҜдёӢең°ж— й—Ёзҡ„з»қжңӣдёҺжңҰиғ§иҝ·жғҳгҖҒеҮ„иҝ·ж·ұйӮғзҡ„ж–ҮеӯҰе®ЎзҫҺж„ҸеўғдәӨз»Ү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дё»дҪ“жғ…ж„ҹдёҺе®ЎзҫҺжҙ»еҠЁзҡ„еҸ еҠ дҪҝ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ж•ЈеҸ‘еҮәжө“йғҒзҡ„еұұж°ҙйҹөе‘іпјҢж·ұеҺҡзҡ„зҫҺеӯҰ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з”ұжӯӨиў«еҸ‘жҺҳеҮәжқҘгҖӮд»ҺзҫҺеӯҰеҺҹзҗҶжқҘи®ІпјҢж—…жёёж–ҮеӯҰзҡ„е®ЎзҫҺе‘ҲзҺ°иҝҳеҢ…жӢ¬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жҲ–е®ЎзҫҺдё»дҪ“еҜ№дё‘зҡ„еҸ‘зҺ°пјҢеҜ№зҫҺдёҺдё‘зҡ„е®Ўи§ҶжүҚжҳҜе®Ңж•ҙ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е®ЎзҫҺжҙ»еҠЁгҖӮ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№ҹйҒөеҫӘиҝҷдёҖзҫҺеӯҰеҺҹзҗҶжҸҸеҶҷдәә们зҡ„е®Ўдё‘пјҢдё»иҰҒдҪ“зҺ°еңЁ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еҜ№еұұе·қжҷҜзү©зҡ„жҸҸеҶҷд№ӢдёӯгҖӮе…¶иЎЁзҺ°ж–№ејҸдё»иҰҒжҳҜеңЁеұұж°ҙжҸҸеҶҷдёӯе Ҷз ҢеӨ§йҮҸжҖӘејӮи°ІиҜЎзҡ„зү©гҖҒдәәгҖҒзҘһдҪңдёәеұұж°ҙ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д»ҺиҖҢдҪҝеұұж°ҙе…·жңүж·ұеҺҡзҡ„зҫҺеӯҰ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пјҢжӯӨзұ»д№ҰеҶҷж–Үеӯ—ж №жҚ®еүҚиҝ°зҘһжёёж–ҮеӯҰзҡ„е®ҡд№үжқҘеҲӨж–ӯпјҢжҳҜе…ёеһӢ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гҖӮеҰ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В·еҚ—еұұз»ҸгҖӢж•°жқЎпјҡеҚ—еұұвҖҰвҖҰдёңдёүзҷҫйҮҢпјҢжӣ°е Ӯеәӯд№ӢеұұпјҢеӨҡжЈӘжңЁпјҢеӨҡзҷҪзҢҝпјҢеӨҡж°ҙзҺүпјҢеӨҡй»„йҮ‘гҖӮ еҸҲдёңдёүзҷҫе…«еҚҒйҮҢпјҢжӣ°зҢЁзҝјд№ӢеұұпјҢе…¶дёӯеӨҡжҖӘе…ҪпјҢж°ҙеӨҡжҖӘйұјпјҢеӨҡзҷҪзҺүпјҢеӨҡиқ®иҷ«пјҢеӨҡжҖӘиӣҮпјҢеӨҡжҖӘжңЁпјҢдёҚеҸҜд»ҘдёҠгҖӮ еҸҲдёңдёүзҷҫдёғеҚҒйҮҢпјҢжӣ°жқ»йҳід№ӢеұұпјҢе…¶йҳіеӨҡиөӨйҮ‘пјҢе…¶йҳҙеӨҡзҷҪйҮ‘гҖӮжңүе…Ҫз„үпјҢе…¶зҠ¶еҰӮ马иҖҢзҷҪйҰ–пјҢе…¶ж–ҮеҰӮиҷҺиҖҢиөӨе°ҫпјҢе…¶йҹіеҰӮи°ЈпјҢе…¶еҗҚжӣ°й№ҝиңҖпјҢдҪ©д№Ӣе®ңеӯҗеӯҷгҖӮжҖӘж°ҙеҮәз„үпјҢиҖҢдёңжөҒжіЁдәҺе®Әзҝјд№Ӣж°ҙгҖӮе…¶дёӯеӨҡзҺ„йҫҹпјҢе…¶зҠ¶еҰӮйҫҹиҖҢд№ҢйҰ–иҷәе°ҫпјҢе…¶еҗҚжӣ°ж—ӢйҫҹпјҢе…¶йҹіеҰӮеҲӨжңЁпјҢдҪ©д№ӢдёҚиҒӢпјҢеҸҜд»Ҙдёәеә•гҖӮ еҸҲдёңеӣӣзҷҫйҮҢпјҢжӣ°дә¶зҲ°д№ӢеұұпјҢеӨҡж°ҙпјҢж— иҚүжңЁпјҢдёҚеҸҜд»ҘдёҠпјҢжңүе…Ҫз„үпјҢе…¶зҠ¶еҰӮзӢёиҖҢжңүй«ҰпјҢе…¶еҗҚжӣ°зұ»пјҢиҮӘдёәзүқзүЎпјҢйЈҹиҖ…дёҚеҰ’гҖӮ еҸҲдёңдёүзҷҫйҮҢпјҢжӣ°еҹәеұұпјҢе…¶йҳіеӨҡзҺүпјҢе…¶йҳҙеӨҡжҖӘжңЁпјҢжңүе…Ҫз„үпјҢе…¶зҠ¶еҰӮзҫҠпјҢд№қе°ҫеӣӣиҖіпјҢе…¶зӣ®еңЁиғҢпјҢе…¶еҗҚжӣ°зҢјиЁ‘пјҢдҪ©д№ӢдёҚз•ҸгҖӮ дёҠеј•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жүҖеҶҷеҚ—еұұдёңйқўд№Ӣдә”з§Қеұұж°ҙпјҢжҲ–зӣҙиЁҖжҖӘе…ҪгҖҒжҖӘйұјгҖҒжҖӘиӣҮгҖҒжҖӘж°ҙгҖҒжҖӘжңЁпјҢжҲ–жҸҸеҶҷжҹҗзү©жҖӘд№ӢжүҖеңЁпјҢиҝҷз§Қең°жҜҜејҸгҖҒж»ҡеҠЁејҸжҸҸеҶҷпјҢеғҸиҝһзҸ зӮ®дёҖж ·иҪ°еҮ»еңЁзҘһ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®ЎзҫҺеҝғзҗҶдёҠпјҢйҖ жҲҗдёҖз§ҚеҜ№вҖңжҖӘвҖқд№Ӣдё‘зҡ„жҒҗжғ§еҝғзҗҶпјҢдә§з”ҹ敬з•Ҹжғ…з»ӘпјҢд»Өе®ЎзҫҺдё»дҪ“жңӣиҖҢз”ҹз•ҸпјҢ敬иҖҢиҝңд№ӢпјҢеҚівҖңдёҚеҸҜд»ҘдёҠвҖқгҖӮиҝҷз§ҚжҒҗжғ§ж„ҹеёҰжқҘзҡ„е®ЎзҫҺж•ҲжһңжҲ–е®ЎзҫҺзӣ®зҡ„жҳҜе”Өиө·дәәзұ»еҜ№дәҺвҖңжҖӘвҖқзҡ„иӯҰжғ•гҖҒйҳІеҫЎпјҢ规йҒҝе…¶жүҖйҖ жҲҗзҡ„зҒҫйҡҫеҜ№дәәзұ»иҮӘиә«зҡ„еҚұе®ігҖӮйҖҡи§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иҝҷз§ҚеҜ№дәҺеұұж°ҙжҖӘејӮд№ӢеӨ„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еӨҡжңүжҢҮзӨәе…Ҳж°‘еҜ№жҹҗдёҖжҖӘзү©зҡ„еҲ©з”Ёдјҡдә§з”ҹжҹҗз§ҚзӢ¬зү№ж•Ҳеә”д№Ӣж„ҸгҖӮеҰӮдёҠ引第дёүжқЎдә‘вҖңе…¶дёӯеӨҡзҺ„йҫҹпјҢе…¶зҠ¶еҰӮйҫҹиҖҢд№ҢйҰ–иҷәе°ҫвҖҰвҖҰдҪ©д№ӢдёҚиҒӢвҖқпјҢ第еӣӣжқЎдә‘вҖңе…¶еҗҚжӣ°зұ»пјҢиҮӘдёәзүқзүЎпјҢйЈҹиҖ…дёҚеҰ’вҖқпјҢ第дә”жқЎдә‘вҖңдҪ©д№ӢдёҚз•ҸвҖқпјҢеҮЎжӯӨз§Қз§ҚпјҢе…¶дёӯжҪңи—Ҹзҡ„ж·ұд№үжҳҫ然жҳҜиЎЁиҫҫе…Ҳж°‘еӣҫз”ҹеӯҳгҖҒжұӮз№ҒиЎҚзҡ„зҫҺеҘҪж„ҝжңӣгҖ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дёӯе°Ҷиҝҷдәӣдё°еҜҢж·ұеҺҡзҡ„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йҡҗеҗ«еңЁеұұж°ҙдёӯзҡ„и°ІжҖӘд№Ӣзү©иә«дёҠжҳҜеҚҒеҲҶжҷ®йҒҚзҡ„гҖӮйҷӨдёҠиҝ°жүҖеј•еӨ–пјҢж•ҙйғЁ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дёӯеҮ д№ҺйҖҡз”ЁвҖңГ—д№ӢдёҚГ—вҖқжҲ–вҖңеҸҜд»ҘГ—Г—вҖқзҡ„иЎЁиҫҫеҪўејҸпјҢеүҚиҖ…еҰӮгҖҠиҘҝ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йЈҹд№ӢдёҚжғ‘вҖқгҖҒвҖңжңҚд№ӢдёҚз•Ҹйӣ·вҖқпјҢгҖҠеҢ—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йЈҹд№ӢдёҚйӘ„вҖқгҖҒвҖңйЈҹд№ӢдёҚйҘҘвҖқпјҢгҖҠдёң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йЈҹиҖ…дёҚз–ЈвҖқпјҢгҖҠдёӯ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жңҚд№ӢдёҚеҝҳвҖқпјҢгҖҠдёӯ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жңҚд№ӢдёҚзңҜвҖқпјӣеҗҺиҖ…еҰӮгҖҠеҚ—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еҸҜд»ҘйҮҠеҠівҖқпјҢгҖҠиҘҝ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еҸҜд»Ҙе·Іи…ҠвҖқвҖңеҸҜд»Ҙе·ІиҒӢвҖқгҖҒвҖңеҸҜд»ҘеҫЎзҒ«вҖқпјҢгҖҠеҢ—еұұз»ҸгҖӢдә‘вҖңеҸҜд»ҘжӯўиЎ•вҖқ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иҝҷз§Қд№ҰеҶҷйҖҡејҸж—ўеҸҜд»ҘйІңжҳҺеұ•зӨәжҲ‘еӣҪдёҠеҸӨзҘһиҜқзҡ„еҲӣдҪңиө·жәҗе’Ңзӣ®зҡ„пјҢжӣҙжҳҜдёәдәҶиЎЁиҫҫ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өӢдәҲеұұж°ҙзҡ„еҠҹеҲ©жҖ§иҰҒжұӮпјҢдҪ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ңЁйўҶз•Ҙеұұж°ҙйҡҗд№үж—¶иҺ·еҫ—е®ЎзҫҺж»Ўи¶ігҖ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жүҖйҮҚеҸ зҡ„жҖӘзү©жҸҸеҶҷпјҢиҷҪ然еёҰжқҘзҡ„жҳҜжҒҗжғ§д№Ӣж„ҹпјҢдҪҶеңЁиҝҷз§ҚеҸ еҠ зҡ„жҖӘејӮдё‘еҢ–иғҢеҗҺпјҢеҚҙеҪўжҲҗдәҶз”ұжҒҗжғ§йҖ жҲҗзҡ„зҫҺеӯҰеҺҹзҗҶдёҠзҡ„еЈ®зҫҺеҙҮй«ҳзҡ„д»·еҖјз»ҙеәҰпјҢд»ҺиҖҢдҪҝеҫ—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ұұж°ҙеҶ…ж¶өи¶…еҮәдәҶдҪңдёәең°зҗҶеӯҰж„Ҹд№үзҡ„еұұж°ҙпјҢжҗӯиҪҪеңЁ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Ҡзҡ„зҘһиҜқиЎЁиҝ°жӣҙдҪҝеұұж°ҙзғҷдёҠдәҶж·ұеҲ»зҡ„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гҖӮиҒҢжҳҜд№Ӣж•…пјҢ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жүҚжҲҗдёәдёҠеҸӨж–ҮзҢ®дёӯжңҖе…·йӯ…еҠӣжҲ–йӯ”еҠӣзҡ„ж–ҮзҢ®д№ӢдёҖгҖӮдёүгҖҒ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д»ҷйҒ“еҗ«и•ҙ 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жҳҜзҸҚзҲұз”ҹе‘ҪгҖҒеҗ‘еҫҖеҒҘеә·й•ҝеҜҝзҡ„ж°‘ж—ҸпјҢе…Ҳдәә们иҝңеңЁдёҠеҸӨж—¶жңҹе°ұиЎЁиҫҫдәҶеҜ№з”ҹе‘Ҫй•ҝеҜҝзҡ„жёҙжңӣд№Ӣжғ…пјҢеҲӣйҖ дәҶзҒҝзғӮзҡ„еҒҘеә·з”ҹе‘Ҫж–ҮеҢ–гҖӮгҖҠиҜ—з»ҸВ·е°Ҹйӣ…В·еӨ©дҝқ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ҰӮжңҲд№ӢжҒ’пјҢеҰӮж—Ҙд№ӢеҚҮпјҢеҰӮеҚ—еұұд№ӢеҜҝпјҢдёҚйӘһдёҚеҙ©гҖӮеҰӮжқҫжҹҸд№ӢиҢӮпјҢж— дёҚе°”жҲ–жүҝгҖӮвҖқвҖңеҜҝжҜ”еҚ—еұұвҖқвҖңиҢӮеҰӮжқҫжҹҸвҖқпјҢжҳҜе…Ҳж°‘зҡ„зҫҺеҘҪзҘҲзҘ·гҖӮиҝҷз§Қз”ҹе‘Ҫж„ҸиҜҶеңЁ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иў«е№ҝжіӣең°йҡҗеҗ«еңЁж—…жёёе®ўдҪ“вҖ”вҖ”еұұж°ҙжҷҜзү©д№ӢдёӯпјҢ并е°Ҷе…Ҳж°‘й•ҝжңҹеӣәеҢ–зҡ„йҹ©дј—гҖҒзҺӢд№”гҖҒиөӨжқҫзӯүзҘһд»ҷеҪўиұЎдҪңдёәеұұж°ҙжёёи§ҲдёӯиҝҪеҜ»зҡ„й•ҝз”ҹзӣ®ж ҮгҖӮеүҚеј•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В·жө·еӨ–еҚ—з»ҸгҖӢжүҖи®°дёҚжӯ»д№ӢеұұвҖ”вҖ”е‘ҳдёҳеұұжңүй•ҝеҜҝдёҚжӯ»ж°‘пјҢеҸҲ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и®°е‘Ёз©ҶзҺӢйҖ и®ҝиҘҝзҺӢжҜҚпјҢзҺӢжҜҚзҘҲзҘқз©ҶзҺӢвҖңе°Ҷеӯҗж— жӯ»вҖқеҚій•ҝе‘ҪдёҚжӯ»пјҢиҖҢиҘҝзҺӢжҜҚжӯЈжҳҜжҳҶд»‘еұұдёҠдёҖзҘһд»ҷ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гҖҠеә„еӯҗВ·йҖҚйҒҘжёёгҖӢе…ідәҺи—җ姑射еұұзҡ„зҘһд»ҷжҸҸеҶҷпјҢе…¶дёӯжүҖи®°еӣӣзҘһд»ҷзҺӢеҖӘгҖҒе•®зјәгҖҒиў«иЎЈгҖҒи®ёз”ұдәҰжҳҜдҫқеұұеӮҚж°ҙиҖҢй•ҝеҜҝгҖӮж— и®әжҳҜ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дёӯзҡ„дёҚжӯ»ж°‘пјҢиҝҳжҳҜ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дёӯзҡ„иҘҝзҺӢжҜҚпјҢз”ҡжҲ–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еӣӣеӯҗвҖқпјҢйғҪеҮәзҺ°еңЁдҪңдёә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еұұж°ҙд№ӢдёӯпјҢеұұж°ҙ已然жҲҗдёәз”ҹе‘Ҫй•ҝеҜҝ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өӢдәҲдәҶеұұж°ҙд»Ҙз”ҹе‘Ҫж°ёжҒ’зҡ„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гҖӮеҗҺдё–йҒ“ж•ҷе°Ҷе…¶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зҡ„ж ёеҝғд»·еҖји®ҫзҪ®еңЁй•ҝз”ҹдёҚжӯ»зҡ„зҘһд»ҷзӣ®ж ҮдёҠпјҢзҘһд»ҷзҡ„зҗҶжғізҪ®иә«д№Ӣең°еҲҷжҳҜеҰӮ蓬иҺұдёүеІӣгҖҒжҳҶд»‘иөӨж°ҙд№Ӣзұ»зҡ„ж Үеҝ—жҖ§ең°еҹҹгҖӮдёҚд»…еҰӮжӯӨпјҢеұұж°ҙд№ҹжҲҗдёәе…Ҳз§Ұд№ӢеҗҺж–ҮдәәжҠ’жғ…йҒЈжҖҖгҖҒж¬ўж„үиә«еҝғзҡ„зҷ»дёҙд№ӢеӨ„жҲ–ж –еұ…д№ӢжүҖд№ғиҮійҡҗеұ…д№Ӣең°гҖӮд»ҺйҰ–еҲӣд№ӢеҠҹжқҘиҜҙпјҢ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дёҠиҝ°еұұж°ҙйҡҗд№үпјҢејҖеҗҜдәҶеҗҺдё–д»ҷйҒ“ж–ҮеҢ–д»·еҖјиҜүжұӮзҡ„е…ҲеЈ°гҖӮдёҠиҝ°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•ҙеҗ«зҡ„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пјҢе°Өе…¶зӘҒеҮәең°иЎЁзҺ°еңЁеұҲеҺҹжүҖдҪң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№ӢдёӯгҖӮ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й—»иөӨжқҫд№Ӣжё…е°ҳе…®пјҢж„ҝжүҝйЈҺд№ҺйҒ—еҲҷгҖӮвҖқиөӨжқҫпјҢгҖҠеҲ—д»ҷдј 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иөӨжқҫеӯҗпјҢзҘһеҶңж—¶дёәйӣЁеёҲпјҢжңҚеҶ°зҺүпјҢж•ҷзҘһеҶңпјҢиғҪе…ҘзҒ«иҮӘзғ§гҖӮиҮіжҳҶеұұдёҠпјҢеёёжӯўиҘҝзҺӢжҜҚзҹіе®ӨгҖӮйҡҸйЈҺйӣЁдёҠдёӢгҖӮзӮҺеёқе°‘еҘіиҝҪд№ӢпјҢдәҰеҫ—д»ҷдҝұеҺ»гҖӮвҖқиҝңеҸӨд»ҷдәәиөӨжқҫпјҢеұ…д»ҷеұұжҳҶд»‘д№ӢдёҠгҖӮ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ҘҮеӮ…иҜҙд№ӢжүҳжҷЁжҳҹе…®пјҢзҫЎйҹ©дј—д№Ӣеҫ—дёҖгҖӮвҖқйҹ©дј—пјҢеҚійҹ©з»ҲпјҢгҖҠеҲ—д»ҷдј 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йҪҗдәәйҹ©з»ҲпјҢдёәзҺӢйҮҮиҚҜдә”жҹһеұұдёӯпјҢзҺӢдёҚиӮҜжңҚпјҢз»ҲиҮӘжңҚд№ӢпјҢйҒӮеҫ—д»ҷиҖҢеҺ»гҖӮвҖқйҹ©з»Ҳеҫ—д»ҷеҺ»дәҶдә”жҹһеұұгҖӮ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Ҫ©иҫ•дёҚеҸҜж”ҖжҸҙе…®пјҢеҗҫе°Ҷд»ҺзҺӢд№”иҖҢеЁұжҲҸгҖӮвҖқзҺӢд№”пјҢеҚізҺӢеӯҗд№”пјҢжҳҜжёёи§Ҳе’Ңз”ҹжҙ»дәҺеұұж°ҙй—ҙзҡ„еҗҚд»ҷгҖӮгҖҠеҲ—д»ҷдј 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зҺӢеӯҗд№”иҖ…пјҢе‘ЁзҒөзҺӢеӨӘеӯҗжҷӢд№ҹгҖӮеҘҪеҗ№з¬ҷпјҢдҪңеҮӨеҮ°йёЈгҖӮжёёдјҠгҖҒжҙӣд№Ӣй—ҙгҖӮйҒ“еЈ«жө®дёҳе…¬жҺҘд»ҘдёҠеө©й«ҳеұұгҖӮдёүеҚҒдҪҷе№ҙеҗҺпјҢжұӮд№ӢдәҺеұұдёҠпјҢи§ҒжҹҸиүҜжӣ°пјҡвҖҳе‘ҠжҲ‘家дёғжңҲдёғж—Ҙеҫ…жҲ‘дәҺзј‘ж°Ҹеұұе·…гҖӮвҖҷиҮіж—¶пјҢжһңд№ҳй№Өй©»еұұеӨҙпјҢжңӣд№ӢдёҚеҸҜеҲ°гҖӮдёҫжүӢи°ўж—¶дәәпјҢж•°ж—ҘиҖҢеҺ»гҖӮвҖқ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д»ҚзҫҪдәәдәҺдё№дёҳе…®пјҢз•ҷдёҚжӯ»д№Ӣж—§д№ЎгҖӮвҖқиҜ—дәәжғіиҝҪж…•зҫҪдәәеҚід»ҷдәәдәҺдё№дёҳд№ӢеұұпјҢй•ҝз”ҹдёҚжӯ»гҖӮ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дҪңдёәдёҖзҜҮжқ°еҮә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№ӢдҪңпјҢеӨҡж¬ЎиЎЁиҫҫеұұж°ҙжёёеҺҶдёӯзҫЎд»ҷгҖҒжҲҗд»ҷд№Ӣж„ҝпјҢе»әжһ„дәҶдёҖеұұдёҖд»ҷжҲ–дёҖж°ҙдёҖд»ҷжҲ–еұұж°ҙе…ұд»ҷзҡ„еҜ№еә”е…ізі»пјҢжҲҗдёә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»ҷеұұеҗҲдёҖж–ҮеӯҰжЁЎејҸзҡ„е…ёиҢғгҖӮеҗҺжқҘйҒ“ж•ҷдҝЎд»°дёӯзҡ„д»ҷдёҺеұұзҡ„д»ҷйҒ“ж–ҮеҢ–еҗ«и•ҙпјҢе…¶жёҠжәҗеҸҜд»ҘеңЁ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ҜёеҰӮ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гҖҠз©ҶеӨ©еӯҗдј гҖӢ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гҖҠжҘҡиҫһгҖӢзӯү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дёӯжүҫеҲ°пјҢе…¶дёӯвҖңеә„вҖқвҖңйӘҡвҖқеұ…еҠҹз”ҡдјҹгҖӮдёӯеӣҪйҒ“ж•ҷеҸ‘еұ•еҲ°дёӨжҷӢпјҢз”ұдәҺеӨ§жү№еЈ«йҳ¶еұӮдәәзү©зҡ„еҸӮдёҺпјҢејҖе§Ӣе°ҶйҒ“ж•ҷ规иҢғеҢ–гҖҒзҗҶи®әеҢ–пјҢе…¶дёӯеҜ№жӯӨеҒҡеҮәеҺҶеҸІжҖ§ж”№йқ©зҡ„йҮҚиҰҒдәәзү©дҫҝжҳҜи‘ӣжҙӘгҖӮд»–еҲӣе»әзҡ„зі»з»ҹеҢ–зҡ„зҘһд»ҷйҒ“ж•ҷзҗҶи®әпјҢжӯЈејҸжҠҠйҒ“ж•ҷеј•еҗ‘д»ҷеӯҰзҡ„иҪЁйҒ“пјҢеҜ№вҖңд»ҷвҖқзҡ„зҗҶи®әеҶ…ж¶өиҝӣиЎҢдәҶеӨҡе…ғеҢ–зҡ„йҳҗйҮҠгҖӮе…¶жүҖдҪңгҖҠжҠұжңҙеӯҗВ·еҶ…зҜҮгҖӢејҖзҜҮзҡ„гҖҠз•…зҺ„гҖӢдҫҝеҸ‘жҳҺиҖҒеә„д№ӢзҺ„йҒ“пјҢи®ӨдёәдҪ“и®Өе’ҢжӮҹеҫ—зҺ„йҒ“еҚіжҳҜжҲҗд»ҷзҡ„йҰ–иҰҒеүҚжҸҗгҖӮж•…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Ө«жұӮй•ҝз”ҹпјҢеңЁдҝ®иҮійҒ“гҖӮвҖқдҝ®иҮійҒ“пјҢеҚіжҳҜжҢҮжёҙжұӮй•ҝз”ҹзҡ„дәәеҝ…йЎ»дҪ“жӮҹиҮійҒ“пјҢдәҰеҚіиҺ·еҸ–е®Үе®ҷдёҮзү©д№ӢиҮізҗҶпјҢйЎәжӯӨиҮізҗҶеҲҷиғҪй•ҝз”ҹжҲҗд»ҷгҖӮиҮідәҺжҖҺж ·дҝ®иҮійҒ“пјҢи‘ӣжҙӘеҸҲ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еҗ«ж·іе®ҲжңҙпјҢж— ж¬Іж— еҝ§пјӣе…ЁзңҹиҷҡеҷЁпјҢеұ…е№іе‘іж·ЎпјҢжҒўжҒўиҚЎиҚЎпјҢдёҺжө‘жҲҗзӯүе…¶иҮӘ然пјӣжө©жө©иҢ«иҢ«пјҢдёҺйҖ еҢ–й’§е…¶з¬ҰеҘ‘гҖӮвҖқе®Ҳжңҙе…ЁзңҹпјҢиҮӘ然з¬ҰеҘ‘пјҢйЎәзү©д№ӢжҖ§пјҢйЎәз”ҹд№ӢжҖ§пјҢеҝ…иғҪй•ҝз”ҹд№…и§ҶгҖӮеҰӮжһңеҸҚе…¶йҒ“иҖҢиЎҢд№ӢпјҢеҲҷеҝ…дёҚиғҪзӣҠеҜҝ延е№ҙпјҢжүҖд»Ҙд»–еҸҲжү№иҜ„йӮЈдәӣеҰӮвҖңж“ҚйҡӢзҸ д»Ҙеј№йӣҖпјҢжііеҗ•жўҒд»ҘжұӮйұјвҖқд№Ӣзұ»зҡ„иҝқеҸҚиҮӘ然гҖҒиҝқиғҢеӨ©жҖ§зҡ„жң¬жң«еҖ’зҪ®иЎҢдёәгҖӮвҖңжііеҗ•жўҒд»ҘжұӮйұјвҖқд№Ӣе…ёеҮәиҮӘгҖҠеә„еӯҗВ·иҫҫз”ҹгҖӢдёӯдёҖдёӘжңүе…і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ж–Үжң¬гҖӮе…¶ж–Үжӣ°пјҡеӯ”еӯҗи§ӮдәҺеҗ•жўҒпјҢжӮ¬ж°ҙдёүеҚҒд»һпјҢжөҒжІ«еӣӣеҚҒйҮҢпјҢйјӢйјҚйұјйі–д№ӢжүҖдёҚиғҪжёёд№ҹгҖӮи§ҒдёҖдёҲеӨ«жёёд№ӢпјҢд»ҘдёәжңүиӢҰиҖҢж¬Іжӯ»д№ҹпјҢдҪҝејҹеӯҗ并жөҒиҖҢжӢҜд№ӢгҖӮж•°зҷҫжӯҘиҖҢеҮәпјҢжҠ«еҸ‘иЎҢжӯҢиҖҢжёёдәҺеЎҳдёӢгҖӮеӯ”еӯҗд»ҺиҖҢй—®з„үпјҢжӣ°пјҡвҖңеҗҫд»Ҙеӯҗдёәй¬јпјҢеҜҹеҲҷдәәд№ҹгҖӮиҜ·й—®пјҢи№Ҳж°ҙжңүйҒ“д№ҺпјҹвҖқжӣ°пјҡвҖңдәЎпјҢеҗҫж— йҒ“гҖӮеҗҫе§Ӣд№Һж•…пјҢй•ҝд№ҺжҖ§пјҢжҲҗд№Һе‘ҪгҖӮдёҺйҪҗдҝұе…ҘпјҢдёҺжұ©еҒ•еҮәпјҢд»Һж°ҙд№ӢйҒ“иҖҢдёҚдёәз§Ғз„үпјҢжӯӨеҗҫжүҖд»Ҙи№Ҳд№Ӣд№ҹгҖӮвҖқеӯ”еӯҗжӣ°пјҡвҖңдҪ•и°“е§Ӣд№Һж•…пјҢй•ҝд№ҺжҖ§пјҢжҲҗд№Һе‘ҪпјҹвҖқжӣ°пјҡвҖңеҗҫз”ҹдәҺйҷөиҖҢе®үдәҺйҷөпјҢж•…д№ҹпјӣй•ҝдәҺж°ҙиҖҢе®үдәҺж°ҙпјҢжҖ§д№ҹпјӣдёҚзҹҘеҗҫжүҖд»Ҙ然иҖҢ然пјҢе‘Ҫд№ҹгҖӮвҖқ еӯ”еӯҗжёёеҗ•жўҒжҳҜеә„еӯҗиҷҡжһ„зҡ„дёҖдёӘж—…жёёж•…дәӢпјҢдё”ж–ҮдёӯжүҖи°“вҖңд»Ҙеӯҗдёәй¬јвҖқпјҢд№ғжҢҮз§°зҘһй¬јжҲ–й¬јзҘһд№Ӣзұ»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еҢ…еҗ«дёҖз§ҚеҮәзҘһе…ҘеҢ–зҡ„жҠҠжҸЎдё–з•Ңзҡ„жҠҪиұЎж„Ҹд№үпј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ӯ”еӯҗдёҺй¬јзҘһдә§з”ҹдәҶдёҖе®ҡе…ізі»пјҢиҝҷз§Қе…ізі»дәҰжһ„жҲҗиҫғдёәе®Ҫжіӣзҡ„зҘһжёёжң¬дәӢгҖӮд»ҺжҖқжғіеҶ…ж¶өзңӢпјҢеә„еӯҗи®©еӯ”еӯҗйҖҡиҝҮе®һең°ж„ҹеҸ—гҖҒйқўеҜ№йқўзҡ„и§ӮеҜҹд»ҘдҪ“и®Өеҗ•жўҒдёҲеӨ«и№Ҳж°ҙд№ӢйҒ“пјҢиҝӣиҖҢдёҠеҚҮеҲ°з”ҹе‘Ҫд№ӢйҒ“еҚіиҫҫз”ҹд№ӢйҒ“пјҡйЎәд№ҺиҮӘ然д№ӢжҖ§гҖӮи‘ӣжҙӘж·ұи°ҷжӯӨиҖҒеә„е…»з”ҹд№ӢзҗҶпјҢж•…еңЁгҖҠз•…зҺ„гҖӢдёӯжү№иҜ„йӮЈдәӣеҸӘд»ҺиЎЁйқўдёҠеҺ»и®ӨзҹҘеҗ•жўҒдёҲеӨ«и№Ҳж°ҙд»ҘдёәиҺ·йұјзҡ„дәәпјҢеҢ…жӢ¬еғҸеӯ”еӯҗиҝҷж ·зҡ„еңЈдәәйғҪдјҡжңүеңЁи®ӨзҹҘзҡ„еҲқжӯҘйҳ¶ж®өзҠҜй”ҷиҜҜ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д»ҺиҖҢдёәе…¶зҘһд»ҷ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еўһж·»дәҶжҖқжғіеҺҹж–ҷ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гҖҠеә„еӯҗВ·иҫҫз”ҹгҖӢвҖңеӯ”еӯҗи§ӮдәҺеҗ•жўҒвҖқ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пјҢд»Һеҗ•жўҒеұұж°ҙзҡ„йҡҗд№үж–ҮеҢ–и§Ҷи§’жқҘи§ЈеҜҶпјҢи•ҙеҗ«дәҶеҗҺжқҘзҘһд»ҷйҒ“ж•ҷзҡ„ж·ұеұӮз”ҹе‘Ҫж–ҮеҢ–ж„Ҹд№үгҖӮжҲ‘们е°Ҷеә„еӯҗзҡ„вҖңеӯ”еӯҗи§ӮдәҺеҗ•жўҒвҖқдёҺеүҚиҝ°йІІй№Ҹд№ӢжёёгҖҒи—җ姑射еұұд»ҷдәәд№Ӣжёёзӯү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»“еҗҲиө·жқҘиҖғеҜҹпјҢ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еә„еӯҗ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д»ҷйҒ“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иЎЁзҺ°дёәдёӨз§Қжғ…еҶөпјҡдёҖжҳ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ңЁиә«д»ҪдёҠеҚіжҳҜзҘһд»ҷжҲ–д»ҷдәәи§’иүІпјҢ他们иә«еӨ„еұұжһ—д№ӢдёӯпјҢдҪңдёәеҮЎдәәдҝ—зү©иҝҪж…•зҡ„зӣ®ж ҮпјӣдәҢжҳ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№Ӣиә«д»ҪдёҚжҳҜзҘһд»ҷжҲ–д»ҷдәәпјҢдҪҶе…¶зІҫзҘһжҲ–еҝғзҒөеҚҙжёёдәҺйҒҘиҝңзҡ„еұұж°ҙй—ҙжҲ–жёәиҢ«зҡ„е°ҳдё–еӨ–пјҢеёҢеҶҖи¶…и¶ҠзҺ°е®һпјҢж”ҫйЈһиҮӘжҲ‘пјҢиҫҫеҲ°еҝҳжҲ‘пјҲеқҗеҝҳпјүж— жҲ‘гҖҒйҖҚйҒҘиҮӘз”ұзҡ„иҮіеўғгҖӮеҜ№дәҺеҗҺиҖ…пјҢеә„еӯҗжҳҜиҝҷж ·иЎЁиҝ°зҡ„пјҡвҖңд№ҳзү©д»ҘжёёеҝғвҖқпјҢвҖңжёёеҝғдәҺзү©вҖқгҖӮиҝҷйҮҢеә„еӯҗ第дёҖж¬Ўе®ҡд№үдәҶжңҖй«ҳеўғз•Ңзҡ„зҘһжёёгҖӮе®ғжҳҜдёҖз§ҚдёҚеҸ—зҺ°е®һжқЎд»¶йҷҗеҲ¶гҖҒиғҪеӨҹе…ӢжңҚиҜёеӨҡж—…жёёеӣ°йҡҫгҖҒ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дёҺвҖңйҒ“вҖқеҶҘеҗҲзҡ„зІҫзҘһд№Ӣж—…пјҢ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®ўи§Ӯиә«иәҜеҸҜд»Ҙе®үж”ҫеңЁжҹҗдёӘеӨ„жүҖпјҢиҖҢе…¶еҝғзҒөжҲ–зҒөйӯӮгҖҒзІҫзҘһеҚҙи„ұзҰ»дәҶеҪўдҪ“пјҢдёҺеұұж°ҙгҖҒе®Үе®ҷдёҮзү©иһҚдёәдёҖдҪ“пјҢиҺ·еҫ—е®ЎзҫҺж„ҹеҸ—гҖҒзІҫзҘһж„үжӮҰе’Ңжғ…ж„ҹе®Јжі„гҖӮдҪҶеҗҢж—¶пјҢеә„еӯҗеҸҲи®ӨдёәдёҚжҳҜжүҖжңү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йғҪеҸҜд»ҘзҘһжёёпјҢдёҖе®ҡиҰҒжңүеҜ№дәҺвҖңйҒ“вҖқдҪңдёәе®Үе®ҷд№Ӣжң¬гҖҒдёҮзү©д№ӢжәҗгҖҒзү©иҙЁжһ„жҲҗд№ӢжүҖд»ҘеҸҠзҘһз§ҳиҺ«жөӢд№Ӣжң¬жҖ§зҡ„ж·ұеҲ»зҗҶи§ЈпјҢжңҖеҗҺжүҚиғҪиҫҫеҲ°й©ҫй©ӯвҖңйҒ“вҖқеҚівҖңд№ҳеӨ©ең°д№ӢжӯЈпјҢиҖҢеҫЎе…ӯж°”д№Ӣиҫ©пјҢд»ҘжёёдәҺж— з©·вҖқзҡ„еўғз•ҢгҖӮ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еҜ№дәҺвҖңйҒ“вҖқзҡ„дҝ®зӮјжҳҜзҘһжёёеұұж°ҙзҡ„е…ҲеҶіжқЎд»¶пјҢеҸӘжңүдҪ“йҒ“д№ӢдәәгҖҒеҫ—йҒ“д№ӢдәәжүҚиғҪиҮӘз”ұиҮӘеңЁйҒЁжёёдәҺеұұж°ҙжҷҜи§Ӯд№Ӣдёӯ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…·жңүд»ҷйҒ“ж°”жҒҜзҡ„зҘһзҒөд№ӢеңәгҖӮиҝҷдёӘж—…жёёиҝҮзЁӢжҳҜ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иҮӘжҲ‘и§Јж”ҫзҡ„иЎЁзҺ°пјҢвҖңд»–еҸҜд»Ҙе°Ҷе®һдҪ“з©әй—ҙ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е®ўдҪ“е®Ңе…ЁиҪ¬еҢ–дёәиҷҡжӢҹз©әй—ҙдёӯзҡ„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пјҢд»ҺиҖҢй©°йӘӢеңЁжӣҙеӨ§зҡ„ж—…жёёз©әй—ҙвҖқпјҢзІҫзҘһиҮӘз”ұеңЁиҝҷдёӘиҷҡжӢҹзҡ„ж—…жёёз©әй—ҙе……еҲҶе®һзҺ°гҖӮиҝҷдёӘж—…жёёз©әй—ҙз”ұдәҺи’ҷдёҠдәҶиҷҡжӢҹзҡ„иүІеҪ©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з§ҚзҺ°е®һдёӯж— жі•еҒ¶йҒҮзҡ„вҖңд№ҢжүҳйӮҰвҖқжҲ–вҖңзҗҶжғіеӣҪвҖқпјҢеӣ иҖҢеҸӘиғҪиў«и§ҶдёәдёҖз§ҚиүәжңҜеҢ–гҖҒе®ЎзҫҺеҢ–зҡ„зІҫзҘһеўғз•ҢпјҢеӣ жӯӨпјҢвҖңзҘһжёёвҖқд№ҹе°ұе®Ңе…ЁеҸ–еҫ—дәҶжҰӮеҝөжҲҗз«Ӣзҡ„еҪ“然иө„ж јгҖӮиҝҷз§ҚвҖңзҘһжёёвҖқйҷӨдәҶиөӢдәҲдёҖиҲ¬зҡ„д»ҷйҒ“еҶ…ж¶өеӨ–пјҢејҖе§Ӣеҗ‘иүәжңҜд№ӢеўғгҖҒе®ЎзҫҺд№ӢеўғеҸ‘еұ•пјҢд»ҺиҖҢжҸҗеҚҮдәҶз”ҹе‘Ҫж„Ҹд№үзҡ„е“Ғж јгҖӮеӣӣгҖҒ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Ҝ№еҗҺдё–ж–ҮеӯҰзҡ„еҪұе“Қ д»ҺдёҠиҝ°и®әжһҗдёӯжҲ‘们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ж–Үжң¬еҮәеӨ„дё»иҰҒжҳҜгҖҠеұұжө·з»ҸгҖӢ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гҖҠжҘҡиҫһгҖӢпјҢиҝҷдәӣж–ҮеӯҰж–Үжң¬е…ұеҗҢжһ„е»әдәҶзҘһжёёзҡ„дё»йўҳгҖҒж„ҸиұЎгҖҒжғ…иҠӮжЁЎејҸжҲ–иҖ…иҜҙвҖңеҺҹеһӢвҖқпјҢеҜ№еҗҺдё–жёёд»ҷж–ҮеӯҰгҖҒзҺ„жҖқж–ҮеӯҰгҖҒ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зӯүдә§з”ҹдәҶж·ұеҲ»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йҰ–е…ҲеҸ—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Ҫұе“Қзҡ„жҳҜжұүд»Јзҡ„жёёд»ҷиөӢпјҢеҸёй©¬зӣёеҰӮзҡ„гҖҠеӨ§дәәиөӢгҖӢдёәзӘҒеҮәд»ЈиЎЁгҖӮиҜҘиөӢеңЁжһ„жҖқз«Ӣж„Ҹе’ҢдәәеҗҚеҗ«д№үдёҠйғҪеҸ—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иөӢж–ҮејҖзҜҮе°ұеҖҹз”Ё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еҲӣе»әзҡ„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ҪўиұЎпјҡдё–жңүеӨ§дәәе…®пјҢеңЁдәҺдёӯе·һгҖӮе®…ејҘдёҮйҮҢе…®пјҢжӣҫдёҚи¶ід»Ҙе°‘з•ҷгҖӮжӮІдё–дҝ—д№Ӣиҝ«йҡҳе…®пјҢжң…иҪ»дёҫиҖҢиҝңжёёгҖӮеһӮз»ӣе№Ўд№Ӣзҙ иңәе…®пјҢиҪҪдә‘ж°”иҖҢдёҠжө®гҖӮ гҖҠеә„еӯҗВ·еңЁе®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Ө§дәәд№Ӣж•ҷпјҢиӢҘеҪўд№ӢдәҺеҪұпјҢеЈ°д№ӢдәҺе“ҚпјҢжңүй—®иҖҢеә”д№ӢпјҢе°Ҫе…¶жүҖжҖҖпјҢдёәеӨ©дёӢй…ҚгҖӮеӨ„д№Һж— е“ҚпјҢиЎҢд№Һж— ж–№гҖӮжҢҲжұқйҖӮеӨҚд№ӢжҢ жҢ пјҢд»Ҙжёёж— з«ҜгҖӮеҮәе…Ҙж— ж—ҒпјҢдёҺж—Ҙж— е§ӢпјҢйўӮи®әеҪўиәҜпјҢеҗҲд№ҺеӨ§еҗҢпјҢеӨ§еҗҢиҖҢж— е·ұгҖӮвҖқ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ңЁиҝҷйҮҢжҳҜдёҖдёӘдјҒеӣҫж‘Ҷи„ұдәәз”ҹз—ӣиӢҰиҖҢи¶…и„ұдәҺдәәдё–гҖҒзҘһжёёдәҺж— иҫ№ж— йҷ…зҡ„иҮӘз”ұз©әй—ҙзҡ„зҗҶжғідәәж јпјҢжҳҜиҝҪжұӮз”ҹе‘Ҫд№ӢзІҫзҘһеҝ«д№җзҡ„дјҹеӨ§дәәж јгҖӮ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Ҹёй©¬зӣёеҰӮеҖҹз”Ё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ҪўиұЎпјҢж—ЁеңЁиҜҙжҳҺеҪўиұЎжүҖеҶ…йҡҗзҡ„йҒ“家зҗҶжғідәәж јж„Ҹи•ҙ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иҝҷдёӘеӨ§дәәеҪўиұЎж„ҸеңЁжҡ—зӨә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°ұжҳҜдҪңдёәзҺ°дё–з»ҹжІ»иҖ…зҡ„еёқзҺӢ既然已з»Ҹз»ҹжІ»дәҶеӨ©дёӢпјҢдҪҶд»ҚдёҚж»Ўи¶ідәҺвҖңжҷ®еӨ©д№ӢдёӢпјҢиҺ«йқһзҺӢеңҹпјӣзҺҮеңҹд№Ӣж»ЁпјҢиҺ«йқһзҺӢиҮЈвҖқзҡ„еұҖдҝғпјҢе°Өе…¶еңЁзІҫзҘһйңҖжұӮдёҠеҫ—дёҚеҲ°ж»Ўи¶іпјҢеӣ жӯӨпјҢвҖңеӨ§дәәвҖқеёҢеҶҖиҪ»дёҫиҝңжёёпјҢжүҝж°”дёҠжө®гҖӮиҝҷз§Қиҝңжёёзҡ„еҶ…ж¶өи¶…и¶ҠдәҶеұҲеҺҹ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зҡ„дё»ж—ЁпјҢгҖҠиҝңжёёгҖӢжүҖеҶҷжҳҜиҜ—дәәзҗҶжғідёҚиғҪеңЁзҺ°е®һдёӯе®һзҺ°ж•…иҖҢзҘһжёёд»ҷз•Ңе’ҢеӨ©еәӯд»ҘжұӮе®һзҺ°пјӣиҖҢеңЁеҸёй©¬зӣёеҰӮзҡ„гҖҠеӨ§дәәиөӢгҖӢйӮЈйҮҢпјҢеёқзҺӢзҡ„жёёд»ҷжҳҜдёәдәҶ延伸他еңЁдәәдё–й—ҙзҡ„еЁҒжқғдёҺзҘһеңЈпјҢдј—д»ҷжҲҗдәҶеёқзҺӢй©ӯдҪҝз»ҹжІ»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зҘһд»ҷд№ҹеӨұеҺ»дәҶзҘһеңЈи¶…иғҪзҡ„жҖ§иҙЁпјҢдәҺжҳҜеёқзҺӢеҫ—еҲ°жӣҙеӨ§зЁӢеәҰзҡ„ж¬Іжңӣж»Ўи¶іе’ҢзІҫзҘһеҝ«д№җгҖӮжҲ‘们жқҘзңӢиөӢдёӯзҡ„е…·дҪ“жҸҸеҶҷпјҡйӮӘз»қе°‘йҳіиҖҢзҷ»еӨӘйҳҙе…®пјҢдёҺзңҹдәәд№ҺзӣёжұӮгҖӮдә’жҠҳзӘҲзӘ•д»ҘеҸіиҪ¬е…®пјҢжЁӘеҺүйЈһжіүд»ҘжӯЈдёңгҖӮжӮүеҫҒзҒөеңүиҖҢйҖүд№Ӣе…®пјҢйғЁд№ҳдј—зҘһдәҺ瑶е…үгҖӮдҪҝдә”еёқе…ҲеҜје…®пјҢеҸҚеӨӘдёҖиҖҢд»ҺйҷөйҳігҖӮе·ҰзҺ„еҶҘиҖҢеҸіеҗ«йӣ·е…®пјҢеүҚйҷҶзҰ»иҖҢеҗҺжҪҸж№ҹгҖӮеҺ®еҫҒдјҜдҫЁиҖҢеҪ№зҫЎй—Ёе…®пјҢеұһеІҗдјҜдҪҝе°ҡж–№гҖӮзҘқиһҚжғҠиҖҢи·ёеҫЎе…®пјҢжё…йӣ°ж°”иҖҢеҗҺиЎҢгҖӮеұҜдҪҷиҪҰе…¶дёҮд№ҳе…®пјҢзІ№дә‘зӣ–иҖҢж ‘еҚҺж——гҖӮдҪҝеҸҘиҠ’е…¶е°ҶиЎҢе…®пјҢеҗҫж¬ІеҫҖд№ҺеҚ—е¬үгҖӮ жӯӨеӨ„жүҖеҶҷеӨ§дәәеӣӣж–№жёёд»ҷпјҢе…¶дёӯдј—д»ҷдәәдёҚе…·жңү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дёӯзҡ„еҙҮй«ҳзҘһеңЈиүІеҪ©пјҢиҖҢжҳҜжҲҗдёәиў«еӨ§дәәзҡ„жқғеЁҒжүҖй©ұдҪҝе’Ңж”Ҝй…Қзҡ„еҜ№иұЎгҖӮиөӢдҪңзҡ„дё»йўҳеңЁе…Ҳз§ҰйӘҡдҪ“зҘһжёёж–ҮеӯҰ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иҪ¬еҢ–жҲҗжӯҢйўӮеёқзҺӢз»қеҜ№жқғеЁҒе’ҢзҘһеңЈе…үзҺҜзҡ„дё»йўҳгҖӮжӣҙжңүз”ҡиҖ…пјҢеӨ§дәәи—җи§Ҷд»ҷз•ҢпјҢзқҘзқЁдј—д»ҷпјҢиҪ»ж…ўзҺӢжҜҚпјҢи®Ҙи®ҪеҘ№зҡ„еҜӮеҜһиӢҚиҖҒпјҢд»ҘзӨәзҘһд»ҷдёҚжӯ»еҲҶж–ҮдёҚеҖјпјҢзҺ°е®һдё–з•ҢжүҚжҳҜеҖјеҫ—з•ҷжҒӢзҡ„пјҡеҘ„жҒҜжҖ»жһҒжіӣж»Ҙж°ҙе¬үе…®пјҢдҪҝзҒөеЁІйј“з‘ҹиҖҢиҲһеҶҜеӨ·гҖӮж—¶иӢҘи–Ҷи–Ҷе°Ҷж··жөҠе…®пјҢеҸ¬еұҸзҝіиҜӣйЈҺдјҜиҖҢеҲ‘йӣЁеёҲгҖӮиҘҝжңӣжҳҶд»‘д№ӢиҪ§жІ•жҙёеҝҪе…®пјҢзӣҙеҫ„й©°д№ҺдёүеҚұгҖӮжҺ’йҳҠйҳ–иҖҢе…Ҙеёқе®«е…®пјҢиҪҪзҺүеҘіиҖҢдёҺд№ӢеҪ’гҖӮзҷ»йҳҶйЈҺиҖҢйҒҘйӣҶе…®пјҢдәўйёҹи…ҫиҖҢдёҖжӯўгҖӮдҪҺеӣһйҳҙеұұзҝ”д»ҘзәЎжӣІе…®пјҢеҗҫд№ғд»Ҡзӣ®зқ№иҘҝзҺӢжҜҚгҖӮзҡ“然зҷҪйҰ–жҲҙиғңиҖҢз©ҙеӨ„е…®пјҢдәҰе№ёжңүдёүи¶ід№Ңдёәд№ӢдҪҝгҖӮвҖҰвҖҰдёӢеіҘеөҳиҖҢж— ең°е…®пјҢдёҠеҜҘе»“иҖҢж— еӨ©гҖӮи§Ҷзң©зң иҖҢж— и§Ғе…®пјҢеҗ¬жғқжҒҚиҖҢж— й—»гҖӮд№ҳиҷҡж— иҖҢдёҠеҒҮе…®пјҢи¶…ж— еҸӢиҖҢзӢ¬еӯҳгҖӮ зҘһд»ҷдё–з•ҢеңЁиҝҷйҮҢиў«жҸҸиҝ°еҫ—еҜӮеҜһиҚ’иҠңпјҢдј—д»ҷд№Ӣдё»иҘҝзҺӢжҜҚеӯӨзӢ¬иЎ°иҖҒпјҢеҗ„и·ҜзҘһзҒөиў«еӨ§дәәй©ұдҪҝеҫ—зҷҫиҲ¬жңҚеё–пјҢиҝҷз§ҚеҜ№зҘһд»ҷеҸҠзҘһд»ҷдё–з•Ңзҡ„еҗҰе®ҡпјҢ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еҜ№еёқзҺӢжүҖз»ҹжІ»зҡ„зҺ°е®һдё–з•Ңзҡ„иӮҜе®ҡпјҢж— жҖӘд№ҺжұүжӯҰеёқиҜ»дәҶжӯӨиөӢвҖңеӨ§жӮҰпјҢйЈҳйЈҳжңүеҮҢдә‘д№Ӣж°”пјҢдјјжёёеӨ©ең°д№Ӣй—ҙж„ҸвҖқгҖӮиҖҢдҪңдёәдёҖз§ҚжұүеӨ§иөӢдҪ“ејҸпјҢеҸёй©¬зӣёеҰӮвҖңеҠқзҷҫи®ҪдёҖвҖқзҡ„ж—Ёж„Ҹд№ҹе……еҲҶдҪ“зҺ°еҮәжқҘ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еӨ§дәәжёёд»ҷжүҖи§Ғзҡ„д»ҷз•ҢиҝҺеҗҲдәҶдәәй—ҙеёқзҺӢиёҢиәҮж»Ўеҝ—зҡ„еҝғзҗҶ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еҜ№ж·«еЁҒзҘһж°”зҡ„з»ҹжІ»иҖ…зҡ„иҷҡдјӘж— зҹҘиҝӣиЎҢдәҶе°–й”җзҡ„и®ҪеҲәгҖӮ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Ҝ№еҗҺдё–ж–ҮеӯҰеҪұе“Қжҷ®йҒҚиҖҢе·ЁеӨ§зҡ„жҳҜз§Ұжұүд»ҘйҷҚ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пјҢиҝҷз§ҚеҪұе“ҚеҲҶдёӨжқЎи·Ҝеҫ„еҸ‘з”ҹгҖӮ第дёҖжқЎи·Ҝеҫ„жҳҜдё–дҝ—ж–ҮдәәеҲӣдҪң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гҖӮз§Ұжңқзҡ„гҖҠд»ҷзңҹдәәиҜ—гҖӢиў«йІҒиҝ…е…Ҳз”ҹз§°дёәвҖңе…¶иҜ—зӣ–еҗҺдё–жёёд»ҷиҜ—д№ӢзҘ–вҖқпјҢиҝҷдәӣиҜ—е·ІдәЎдҪҡпјҢжҚ®гҖҠеҸІи®°В·з§Ұе§ӢзҡҮжң¬зәӘгҖӢвҖңдҪҝеҚҡеЈ«дёәгҖҠд»ҷзңҹдәәиҜ—гҖӢеҸҠиЎҢжүҖжёёеӨ©дёӢпјҢдј д»Өд№җдәәжӯҢејҰд№ӢвҖқеҸҜзҹҘпјҢиҜ—жӯҢжүҖеҶҷеә”дёәд»ҷжҷҜд№Ӣи§Ӯи§ҲпјҢиЎЁиҫҫжұӮд»ҷд№Ӣж¬ІжңӣжҳҜзҗҶжүҖеҪ“然зҡ„гҖӮжұүд»Јжёёд»ҷиҜ—дё»иҰҒдҝқеӯҳеңЁгҖҠд№җеәңиҜ—йӣҶВ·зӣёе’ҢжӯҢиҫһгҖӢдёӯпјҢгҖҠжӯҘеҮәеӨҸй—ЁиЎҢгҖӢзӯүжҳҜд»ЈиЎЁдҪңпјҢдё»иҰҒжҸҸеҶҷд»ҷз•Ңе’ҢеӨ©з•ҢгҖӮйӯҸжҷӢжҳҜзҘһд»ҷйҒ“ж•ҷжҖқжғіжӯЈејҸеҪўжҲҗе’Ңиҝ…йҖҹеҸ‘еұ•ж—¶жңҹпјҢд№ҹжҳҜ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зҡ„第дёҖдёӘй«ҳеі°жңҹгҖӮвҖңдёүжӣ№вҖқгҖҒйҳ®зұҚгҖҒеөҮеә·гҖҒеј еҚҺгҖҒеј еҚҸгҖҒйҷҶдә‘гҖҒжҲҗе…¬з»ҘгҖҒдҪ•еҠӯгҖҒйғӯз’һзӯүжҳҜйҮҚиҰҒзҡ„д»ЈиЎЁиҜ—дәәпјҢ他们зҡ„иҜ—жӯҢд»Һз•…жёёд»ҷеўғеҲ°зҘһд»ҷе№»жғіпјҢд»ҺжӯҢйўӮзҘһд»ҷеҲ°еҖҹйўҳеҸ‘жҢҘпјҢз”ұжӯЈдҪ“иҪ¬еҗ‘еҸҳдҪ“пјҢдә”еҪ©ж–‘ж–“пјҢе®һдёәжёёд»ҷиҜ—д№ӢеӨ§и§ӮгҖӮеҚ—еҢ—жңқжҳҜ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зҡ„第дәҢдёӘй«ҳеі°жңҹгҖӮйІҚз…§гҖҒзҺӢиһҚгҖҒиҗ§иЎҚгҖҒиҗ§зәІгҖҒжІҲзәҰгҖҒйўңд№ӢжҺЁгҖҒеәҫдҝЎгҖҒеј жӯЈи§ҒгҖҒйҷҶз‘ңгҖҒжұҹжҖ»зӯүжҳҜжӯӨж—¶жңҹ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зҡ„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гҖӮ他们зҡ„иҜ—жӯҢдёҖж–№йқўз»§жүҝ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зҡ„жӯЈдҪ“дј з»ҹпјҢд»ҷжҷҜгҖҒи§Ӯд»ҷгҖҒиҝҪд»ҷд»Қ然жҳҜзңҹжӯЈдё»йўҳ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иЎЁзҺ°еҮәж–Үдәәд»Ҙж¶ҲйҒЈзҡ„жҖҒеәҰеҜ№еҫ…йҒ“ж•ҷзҘһд»ҷдәӢзҡ„еҖҫеҗ‘пјҢдёҺйғӯз’һзҡ„вҖңеҸҳдҪ“вҖқжңүжң¬иҙЁдёҠзҡ„е·®еҲ«гҖӮйҡӢе”җдёӨе®Ӣж—¶жңҹпјҢж–Үдәә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继з»ӯеҸ‘еұ•пјҢд»ҷжёёжҳҜжӯӨж—¶жёёд»ҷиҜ—зҡ„дё»иҰҒйўҳж—ЁгҖӮйҷӨдәҶжқҺиҙәиҝҷдёӘе‘ҪиҝҗеӨҡиҲӣзҡ„иҜ—дәәеҖҹжёёд»ҷжқҘиЎЁиҫҫиҮӘе·ұзҡ„еӨұж„Ҹжғ…ж„ҹеӨ–пјҢе”җе®Ӣжёёд»ҷиҜ—зҡ„дё»йўҳеҹәжң¬жІЎжңүж—ҒйҖёж–ңеҮәгҖӮ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иҜ—дәәйҳҹдјҚйҳөе®№иұӘеҚҺпјҢе”җд»ЈжңүзҺӢз»©гҖҒзҺӢеӢғгҖҒеҚўз…§йӮ»гҖҒжқҺзҷҪгҖҒзҺӢз»ҙгҖҒйҹҰеә”зү©гҖҒиҙҫеІӣгҖҒжқҺиҙәгҖҒеј зҘңгҖҒеҲҳзҰ№й”ЎгҖҒйЎҫеҶөгҖҒеӯҹйғҠгҖҒеҸёз©әеӣҫгҖҒи®ёжө‘зӯүпјӣдёӨе®Ӣжңүе®үжғҮгҖҒе‘ЁиЎҢе·ұгҖҒзҺӢеҚҒжңӢгҖҒжһ—жҷҜзҶҷгҖҒзҝҒеҚ·гҖҒз§Ұи§ӮгҖҒйғӯзҘҘжӯЈгҖҒеҗ•еҚ—е…¬гҖҒжҷҒиҜҙд№ӢзӯүгҖӮе…ғжҳҺжё…ж—¶жңҹжҳҜж–Үдәәжёёд»ҷиҜ—еҲӣдҪңзҡ„дҪҺиҗҪж—¶жңҹпјҢиҝҷдёҺдё–дҝ—зӨҫдјҡеҜ№йҒ“ж•ҷзҡ„дҝЎд»°жңүе…ігҖӮеңЁдё»ж—ЁдёҠпјҢжӯӨж—¶жңҹзҡ„ж–Үдәәжёёд»ҷиҜ—еңЁе……еҲҶж»Ўи¶іж ҮеҮҶжёёд»ҷиҜ—зҡ„жқЎд»¶еӨ–еҸ‘з”ҹдәҶиҫғеӨ§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дё»иҰҒиЎЁзҺ°дёәеҖҹд№ҰеҶҷдҝЎд»°зҘһд»ҷгҖҒжұӮдҪңзҘһд»ҷдёәеҗҚпјҢиЎҢз”Ёж–Үеӯ—еҸҳеҢ–жҠҖе·§еҶҷеұұжһ—йҖёд№җд№Ӣе®һгҖӮиҷһйӣҶгҖҒйҷҲеҹәгҖҒиҙқзҗјгҖҒзҪ—йўҖгҖҒжұӘзҗ¬гҖҒиөөжү§дҝЎгҖҒиўҒжһҡгҖҒжҙӘдә®еҗүгҖҒйҫҡиҮӘзҸҚгҖҒеҶҜзҸӯгҖҒжҹҘж…ҺиЎҢгҖҒеҺүй№—гҖҒеӯҷжҳҹиЎҚзӯүжҳҜжӯӨжңҹйҮҚиҰҒзҡ„д»ЈиЎЁиҜ—дәә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еңЁдёҠиҝ°жёёд»ҷиҜ—дёӯпјҢе®ӢеүҚпјҲеҗ«е®ӢпјүеҫҖеҫҖеңЁж ҮйўҳдёҠжҳҜвҖңеӨ§жёёд»ҷиҜ—вҖқпјҢе®ӢеҗҺеҲҷеҫҖеҫҖзҪІйўҳдёәвҖңе°Ҹжёёд»ҷиҜ—вҖқгҖӮиҝҷиЎЁзҺ°еҮәе…Ҳз§ҰжұүйӯҸе…ӯжңқе”җе®Ӣе’Ңе…ғжҳҺжё…дёӨдёӘеӨ§зҡ„еҺҶеҸІж®өиҗҪдёӯж–ҮдәәеҜ№еҫ…жёёд»ҷйўҳжқҗзҡ„дёӨз§ҚжҖҒеәҰпјҢеүҚиҖ…дёәдёҘиӮғ敬йҮҚзҡ„еҲӣдҪңжҖҒеәҰпјҢеҗҺиҖ…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еҸҜз§°дёәжёёжҲҸж¶ҲйҒЈзҡ„еҲӣдҪңеҖҫеҗ‘гҖӮ第дәҢжқЎи·Ҝеҫ„жҳҜйҒ“ж•ҷдёҡеҶ…дәәеЈ«еҲӣдҪң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гҖӮжұүжң«иҮіе…ӯжңқжҳҜдёӯеӣҪйҒ“ж•ҷеҲӣе»әе’Ңиҝ…йҖҹеҸ‘еұ•ж—¶жңҹ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ңЁйҒ“ж•ҷйўҶиў–и‘ӣжҙӘе»әз«ӢдәҶзҘһд»ҷйҒ“ж•ҷзҡ„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гҖҒйҷ¶ејҳжҷҜеҲӣйҖ дәҶзҘһд»ҷи°ұзі»еҗҺпјҢдёӯеӣҪйҒ“ж•ҷзҡ„еҹәжң¬ж ји°ғдёҖзӣҙе°ұе®ҡдҪҚеңЁзҘһд»ҷдҝЎд»°дёҠпјҢзҘһд»ҷ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°Ғе»әзӨҫдјҡе®ҳж–№е’Ңж°‘й—ҙи¶ӢеҗҢзҡ„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гҖӮдёҺж•ҷеӨ–дё–дҝ—ж–ҮдәәеҲӣдҪң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зӣёжҜ”пјҢйҒ“ж•ҷдёҡеҶ…дәәеЈ«еҲӣдҪң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дё»йўҳ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дҝЎд»ҷпјҢ并没жңүеҖҹжёёд»ҷд№ӢеҗҚжҠ’еқҺеЈҲд№ӢжҖҖзҡ„иЁҖеӨ–д№Ӣж„ҸгҖӮжұүжң«е…ӯжңқйҒ“ж•ҷж–ҮдәәеҰӮи‘ӣжҙӘгҖҒйӯҸеҚҺеӯҳгҖҒжқЁзҫІгҖҒи®ёж°ҸзҲ¶еӯҗгҖҒиҢ…зӣҲе…„ејҹгҖҒйҷҶдҝ®йқҷгҖҒйҷ¶ејҳжҷҜзҡ„жёёд»ҷиҜ—е…·жңүеҲӣеҹәе’Ңе…ёиҢғдҪңз”ЁпјҢзқҖйҮҚеҜ№еӨ–еңЁд»ҷеўғе’Ңд»ҷдәәз”ҹжҙ»зҡ„жҸҸеҶҷпјҢе…¶е®Јж•ҷе’Ңеј•зәізҡ„еҲӣдҪңзӣ®зҡ„еҚҒеҲҶжҳҺжҳҫгҖӮе”җе®ӢйҒ“ж•ҷж–Үдәәжёёд»ҷиҜ—еңЁжұүйӯҸе…ӯжңқжёёд»ҷиҜ—дё»иүІи°ғ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зі…иҝӣдәҶйҒ“ж•ҷеӨ–дё№еӯҰдёҺеҶ…дё№еӯҰзҡ„зҗҶи®әеҶ…ж¶өпјҢйҒ“жңҜжҖ§гҖҒеӯҰзҗҶжҖ§жҳҜе…¶ж—¶д»Јзү№иүІгҖӮжҲҗзҺ„иӢұгҖҒжқҺиҚЈгҖҒеҸёй©¬жүҝзҘҜгҖҒеҗҙзӯ гҖҒжқҺзӯҢгҖҒеӯҷжҖқйӮҲгҖҒжқңе…үеәӯгҖҒйҷҲжҠҹгҖҒйҷҲжҷҜе…ғгҖҒй’ҹзҰ»жқғгҖҒеҗ•жҙһе®ҫгҖҒеј дјҜз«ҜзӯүжҳҜиҝҷзұ»жёёд»ҷиҜ—дҪңзҡ„д»ЈиЎЁдәәзү©гҖӮйҮ‘е…ғжҳҺжё…йҒ“ж•ҷж–Үдәәжёёд»ҷиҜ—дәҰдёҺж—¶дҝұиҝӣпјҢеңЁз»§жүҝжёёд»ҷиҜ—жӯЈз»ҹеҹәи°ғ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°Ҷе…ЁзңҹгҖҒдҝқжҖ§е’Ңдёүж•ҷиһҚеҗҲзҡ„жҖқжғіеҶ…ж¶ө镶еөҢе…¶дёӯпјҢеҸҚжҳ дәҶжңҚеҠЎдәҺйҒ“ж•ҷеҸ‘еұ•иҰҒжұӮзҡ„еҲӣдҪңеҖҫеҗ‘гҖӮзҺӢйҮҚйҳігҖҒвҖңе…ЁзңҹдёғеӯҗвҖқгҖҒе°№еҝ—е№ігҖҒжқҺеҝ—еёёгҖҒеёёеҝ—жё…гҖҒеҗҙе…ЁиҠӮгҖҒеј з•ҷеӯҷгҖҒжһ—зҒөзңҹгҖҒеј дёүдё°гҖҒеј е®ҮеҲқгҖҒйҷҶиҘҝжҳҹзӯүжҳҜжӯӨдёҖж—¶жңҹжёёд»ҷиҜ—зҡ„д»ЈиЎЁдәәзү©гҖӮ继游д»ҷиҜ—еҗҺпјҢйӯҸжҷӢзҺ„иЁҖиҜ—йЎәеә”и°ҲзҺ„и®әйҒ“гҖҒиҝҪжұӮзҺ„иҝңд№Ӣеўғзҡ„зҺ„еӯҰжҖқжҪ®иҖҢдә§з”ҹгҖӮд»Һжң¬иҙЁдёҠи®ІпјҢзҺ„иЁҖиҜ—дё»иҰҒжҠ’еҶҷзҺ„и°Ҳдәәзү©жҲ–зҺ„и°Ҳдё»дҪ“жёёеҝғзҺ„иҝңгҖҒ超然зү©еӨ–зҡ„зІҫзҘһйҒЁжёё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®ғзҡ„жҖқз»ҙж–№ејҸе’ҢиЎЁиҫҫеҪўејҸзӣҙжҺҘи„ұиғҺдәҺе…Ҳз§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гҖӮд»Ій•ҝз»ҹгҖҠиҝ°еҝ—иҜ—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жҠ—еҝ—еұұж –пјҢжёёеҝғжө·е·ҰгҖӮе…ғж°”дёәиҲҹпјҢеҫ®йЈҺдёәиҲөгҖӮж•–зҝ”еӨӘжё…пјҢзәөж„Ҹе®№еҶ¶гҖӮвҖқеөҮеә·гҖҠиө е…„з§ҖжүҚе…ҘеҶӣгҖӢе…¶еҚҒеӣӣдә‘пјҡвҖңзӣ®йҖҒеҪ’йёҝпјҢжүӢжҢҘдә”ејҰгҖӮдҝҜд»°иҮӘеҫ—пјҢжёёеҝғеӨӘзҺ„гҖӮвҖқж— и®әжҳҜжёёеҝғеҸҜеҫ—и§Ғзҡ„жө·е·ҰпјҢиҝҳжҳҜжёёеҝғдёҚеҸҜи§Ғзҡ„еӨӘзҺ„пјҢйғҪжҳҜдё»дҪ“зҘһжёёдәҺзҺ„иҝңжӮ йӮҲд№ӢеўғгҖӮиҝҷз§ҚзҺ„еӯҰиүІеҪ©зҡ„зҘһжёёжҳҜеҜ№е…Ҳз§ҰзҘһжёёе“ІеӯҰж–ҮеҢ–йҡҗд№үзҡ„жүҝз»ӯе’ҢжҸҗеҚҮпјҢиҖҢдё”еҲӣйҖ жҖ§ең°иөӢдәҲдәҶиҜ—ж„Ҹж –еұ…зҡ„иүәжңҜд»·еҖјгҖӮеңЁзҺ„иЁҖиҜ—зҡ„д»ЈиЎЁиҜ—дәәеӯҷз»°йӮЈйҮҢпјҢе®…еҝғзҺ„иҝңгҖҒзҘһжёёеә„з”ҹзҡ„ж— дҪ•жңүд№Ӣд№ЎеҚіиҫҫеҲ°йҒ“зҡ„й«ҳеӨ„еҰҷеўғпјҢжҲҗдёәзҺ„иЁҖиҜ—зҡ„жңҖдҪідё»ж—ЁгҖӮеҰӮе…¶гҖҠзӯ”и®ёиҜўиҜ—гҖӢд№Ӣдёүдә‘пјҡвҖңйҒ—иҚЈиҚЈеңЁпјҢеӨ–иә«иә«е…ЁгҖӮеҚ“е“үе…ҲеёҲпјҢдҝ®еҫ·е°ұй—ІгҖӮж•Јд»ҘзҺ„йЈҺпјҢж¶Өд»Ҙжё…е·қгҖӮжҲ–жӯҘеҙҮеҹәпјҢжҲ–жҒ¬и’ҷеӣӯгҖӮйҒ“и¶іиғёжҖҖпјҢзҘһж –жө©з„¶гҖӮвҖқиҜ—дәәжҖҖйҒ“дәҺе®Ҫе№ҝзҡ„иғёжҖҖд№ӢдёӯпјҢжёёзҘһдәҺиҫҪйҳ”зҡ„ж— дҪ•жңүд№ӢеўғпјҢеҪ“然пјҢиҝҷз§ҚеҝғжёёзҘһжёёзҡ„еҹәзЎҖжҳҜеҜ№иҖҒеә„е“ІеӯҰзҡ„ж·ұеҲ»жҺҘеҸ—пјҢеҶҚз»ҸиҝҮжј«й•ҝзҡ„дҝ®еҫ·иҝҮзЁӢпјҢжңҖеҗҺиҮ»дәҺиҮійҒ“й«ҳйҒ“гҖӮеӯҷз»°еҗҢйўҳиҜ—д№ӢеӣӣдәҰдә‘пјҡвҖңе’ЁдҪҷеҶІдәәпјҢзҰҖжӯӨж•ЈиҙЁгҖӮеҷЁдёҚйҹ¬дҝ—пјҢжүҚдёҚе…јеҮәгҖӮж•ӣиЎҪе‘ҠиҜҡпјҢж•ўи°ўзҹӯиҙЁгҖӮеҶҘиҝҗи¶…ж„ҹпјҢйҒҳжҲ‘зҺ„йҖёгҖӮе®…еҝғиҫҪе»“пјҢе’ҖеҡјеҰҷдёҖ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е°ҶеҝғзҒөжҲ–зҒөйӯӮгҖҒзІҫзҘһе®үж”ҫеңЁиҫҪиҝңз©әйҳ”зҡ„еҰҷдёҖд№ӢеўғпјҢзҘһжёёжҲҗдёәзҺ„иЁҖиҜ—зҡ„жҠ’еҶҷи„үзҗҶгҖӮеӯҷз»°гҖҠиө и°ўе®үиҜ—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¶ідёҚи¶Ҡз–ҶпјҢи°ҲдёҚзҰ»зҺ„гҖӮеҝғеҮӯжө®дә‘пјҢж°”йҪҗжө©з„¶гҖӮд»°е’ҸйҒ“иҜІпјҢдҝҜеә”дҝ—ж•ҷгҖӮвҖқеҝғзҘһеҮӯеҖҹй«ҳйЈһзҡ„жө®дә‘е’Ңжө©з„¶д№ӢеҰҷж°”иҫҫеҲ°йҒ“д№ӢиҮіеўғпјҢжҳҜзҺ„еӯҰгҖҒзҺ„иЁҖиҜ—дёҖиҮҙзҡ„жҖқзҙўз„ҰзӮ№е’ҢеҪ’е®ҝгҖӮд»Һ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Ҳ°жёёд»ҷиөӢгҖҒжёёд»ҷиҜ—пјҢеҶҚеҲ°зҺ„иЁҖиҜ—пјҢиҝҷдәӣ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жңүдёҖдёӘе…ұеҗҢ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е°ұжҳҜжёёеҺҶдё»дҪ“зҡ„зІҫзҘһжҲ–зҒөйӯӮзҰ»ејҖдәҶиӮүдҪ“пјҢеҸӨдәәз§°д№ӢдёәзҘһдёҺеҪўзҡ„еҲҶзҰ»пјҢиҝҷ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ўҰд№ӢиҜҙзҡ„еҪўжҲҗжҸҗдҫӣдәҶжҖқжғіеҹәзЎҖгҖӮдёңжұүзҺӢе……жҠҠжўҰзңӢжҲҗжҳҜдәәзҡ„е№»и§үдә§з”ҹ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гҖҠи®әиЎЎВ·и®ўй¬ј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Ө«зІҫеҝөеӯҳжғіпјҢжҲ–жі„дәҺзӣ®пјҢжҲ–жі„дәҺеҸЈпјҢжҲ–жі„дәҺиҖігҖӮжі„дәҺзӣ®,зӣ®и§Ғе…¶еҪўпјӣжі„дәҺиҖіпјҢиҖій—»е…¶еЈ°пјӣжі„дәҺеҸЈпјҢеҸЈиЁҖе…¶дәӢгҖӮжҳјж—ҘеҲҷй¬ји§ҒпјҢжҡ®еҚ§еҲҷжўҰй—»гҖӮзӢ¬еҚ§з©әе®Өд№ӢдёӯпјҢиӢҘжңүжүҖз•Ҹжғ§пјҢеҲҷжўҰи§ҒеӨ«дәәжҚ®жЎҲе…¶иә«е“ӯзҹЈгҖӮи§үи§ҒеҚ§й—»пјҢдҝұз”ЁзІҫзҘһпјҢз•Ҹжғ§еӯҳжғіпјҢеҗҢдёҖе®һд№ҹгҖӮвҖқиӢұеӣҪдәәзұ»ж–ҮеҢ–еӯҰ家泰еӢ’е°ҶжўҰзҡ„дә§з”ҹеҪ’еӣ дәҺдәәзҡ„зҒөйӯӮжёёзҰ»дәҺиә«дҪ“гҖӮиҝҷдёҺ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йӯӮйӯ„еӯҰжҳҜдёҖиҮҙзҡ„гҖӮйӯӮйӯ„еӯҰи®ӨдёәпјҢеҒҡжўҰиҖ…зҡ„йӯӮйӯ„еңЁжўҰдёӯзҰ»ејҖдәәзҡ„еҪўдҪ“иҖҢиҝңжёёгҖӮеҜ№жӯӨпјҢжқҺй•ҝд»Ғ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дәәзұ»еңЁеҺҹе§ӢзӨҫдјҡж—¶жңҹпјҢдёҚжҮӮзқЎзң зҡ„з”ҹзҗҶдҪңз”ЁпјҢжӣҙдёҚжҮӮеҒҡжўҰзҡ„з”ҹзҗҶдёҺеҝғзҗҶзҡ„еҺҹеӣ гҖӮ他们и®ӨдёәдёҖдёӘдәәе…·жңүдёӨдёӘиә«дҪ“пјҢдёҖдёӘжҳҜиҷҡзҡ„пјҢдёҖдёӘжҳҜе®һзҡ„пјҢиҷҡзҡ„жҳҜ第дәҢдёӘжҲ‘пјҢеҚіжүҖи°“зҒөйӯӮгҖӮе®һзҡ„жҳҜиӮүдҪ“пјҢдәә们зқЎи§ү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第дәҢдёӘжҲ‘еҸҜд»Ҙе’ҢиӮүдҪ“еҲҶзҰ»пјҢжүҖд»ҘеҒҡжўҰгҖӮеҒҡжўҰе°ұжҳҜ第дәҢдёӘжҲ‘зҡ„еҚ•зӢ¬иЎҢеҠЁпјҢзҒөйӯӮжҡӮж—¶зҰ»ејҖиӮүдҪ“иҖҢеҒҡжўҰпјҢе®ғеӣһеҲ°иӮүдҪ“еҶ…е°ұдҪҝдәәи§үйҶ’гҖӮвҖқеӣ жӯӨпјҢд»ҺйҖ»иҫ‘дёҠи®ІпјҢжңүдәҶеҒҡжўҰпјҢеҚізҒөйӯӮзҡ„ж—…жёёпјҢе°ұжңүдәҶжўҰжёёпјҢжңүдәҶзҘһжёёпјҢе°ұжңүдәҶ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пјҢеә„еӯҗе°ұжҳҜе°Ҷ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иҗҪе®һеҲ°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зҡ„第дёҖдәәгҖӮиҷҪ然жӯӨеүҚзҡ„и®ёеӨҡе…ёзұҚеҰӮ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гҖҠе°ҡд№ҰгҖӢгҖҠе·Ұдј гҖӢзӯүжңүе…ідәҺжўҰзҡ„и®°еҪ•пјҢдҪҶеҮҶзЎ®ең°иҜҙпјҢеҸӘжңүеә„еӯҗеҲӣдҪңзҡ„вҖңеә„е‘ЁжўҰиқ¶вҖқзӯүжүҚжҳҜйқһеёёз¬ҰеҗҲжўҰж–ҮеӯҰе®ҡд№үзҡ„ж–ҮеӯҰдҪіжһ„гҖӮд»ҺдёӯеӣҪж–ҮеӯҰеҸІзҡ„еҸ‘еұ•жғ…еҶөзңӢпјҢж–ҮеӯҰеҸІжңүеӨҡй•ҝпјҢ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еҸІе°ұжңүеӨҡй•ҝпјҢе…¶дёӯе…Ҳз§Ұ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Ҝ№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е…·жңүејҖеҲӣжҖ§зҡ„ж„Ҹд№үе’ҢеҪұе“ҚгҖӮз»“ иҜӯ з»јдёҠжүҖиҝ°пјҢ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е…·жңүеӨҡе…ғиҖҢйҮҚиҰҒзҡ„ж„Ҹд№үгҖӮ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дёӯзҡ„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»Ҙеұұж°ҙдҪңдёәж—…жёёе®ўдҪ“пјҢзқҖйҮҚиөӢдәҲеұұж°ҙеҗ„з§ҚйҖҡиҝҮж—…жёёдё»дҪ“зҡ„еӨ–еңЁж„ҹе®ҳе’ҢеҶ…еңЁеҝғиҙЁеҺ»и§Ұзў°е’ҢеҸ‘жҺҳзҡ„ж·ұеҲ»еҗ«д№үгҖӮзҘһжёёзҡ„ж—¶й—ҙдёҺз©әй—ҙе…ғзҙ дҪҝеұұж°ҙеӯ•иӮІе’ҢеӮ¬з”ҹдәҶиҜёеҰӮж—¶й—ҙжҳ“йҖқжҲ–ж—¶е…үж°ёжҒ’зӯүе…·жңүжҖқиҫЁж„Ҹд№үзҡ„е“ІеӯҰжҰӮеҝөе’ҢиҢғз•ҙпјӣзҘһжёёжүҖеҸ‘зҺ°зҡ„еұұж°ҙдёӯеҘҮиҜЎи°ІжҖӘзҡ„е®Үе®ҷдё–з•Ңиў«д№ҰеҶҷдәҺж–ҮеӯҰд№ӢеҶ…пјҢдҪҝе…¶жҲҗдёәжүҝиҪҪе®ЎзҫҺж„ҸиҜҶзҡ„ж–Үжң¬пјҢејҖеҸ‘дәҶдёӯеӣҪеҸӨе…ёзҫҺеӯҰзҡ„зҸҚиҙөзҹҝи—Ҹпјӣ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дёӯ第дёҖж¬Ўе»әжһ„дәҶеұұдёҺд»ҷзҡ„еҜ№еә”гҖҒеӣәе®ҡе…ізі»пјҢејҖдёӯеӣҪжң¬еңҹе®—ж•ҷд»ҷйҒ“ж–ҮеҢ–д№Ӣе…ҲжІігҖӮзҘһжёёзҡ„еҶ…иҙЁд»ҘеҸҠ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зҘһжёёд№ҰеҶҷзҡ„ж–ҮеӯҰи·Ҝеҫ„дёҺж„Ҹи•ҙж·ұеҲ»ең°еҪұе“Қ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жёёд»ҷиөӢгҖҒжёёд»ҷиҜ—гҖҒзҺ„иЁҖиҜ—гҖҒжўҰеўғж–ҮеӯҰзӯүж–ҮеӯҰдҪ“ејҸзҡ„еӨ§и§„жЁЎеҲӣдҪңгҖӮ30еӨҡе№ҙеүҚпјҢй’ұеӯҰжЈ®е…Ҳз”ҹжҸҗеҮәзҡ„вҖңзҒөеўғвҖқиҜҙжҲ–еӨ§жҲҗжҷәж…§дёҺ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еҲӣйҖ зҡ„вҖңзҘһжёёвҖқжҰӮеҝөжңүеҶ…еңЁзҡ„дёҖиҮҙжҖ§гҖӮд»–д»ҺиҷҡжӢҹзҺ°е®һжҠҖжңҜиҒ”жғіпјҢе°Ҷе…¶еә”з”ЁеҲ°дәәжңәз»“еҗҲе’Ңдәәи„‘ејҖеҸ‘йўҶеҹҹпјҢж•…еҸ–еҗҚдёәвҖңзҒөеўғвҖқгҖӮд»–йў„и§ҒеҲ°дәәжңәж·ұеәҰз»“еҗҲе°Ҷз»ҷдәәзұ»зӨҫдјҡеёҰжқҘж·ұеұӮеҸҳйқ©пјҢеӨ§еӨ§жӢ“еұ•дәәи„‘зҡ„зҹҘи§үпјҢдҪҝдәәзұ»иҝӣе…Ҙ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„ж–°еӨ©ең°гҖӮиҝҷдёҖи®ҫжғізҺ°еңЁеҸҜд»Ҙз§°дёәдәәе·ҘжҷәиғҪжҲ–AIжҠҖжңҜпјҢжҳҜз©ҝи¶ҠеҸӨд»ҠгҖҒз©ҝи¶Ҡе®Үе®ҷзҡ„зІҫзҘһжҙ»еҠЁгҖӮд»Һжҹҗз§ҚзЁӢеәҰдёҠиҜҙпјҢиҝҷжҳҜе…Ҳз§Ұж–ҮеӯҰеҸ‘жҳҺзҡ„вҖңзҘһжёёвҖқзҡ„жң¬иҙЁеҶ…ж¶өеңЁд»–еӨҙи„‘дёӯз„•еҸ‘еҮәзҡ„科еӯҰжҖқз»ҙ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ж•°еҚғе№ҙеҗҺзҡ„вҖңзҘһжёёвҖқдҫқ然具жңүејәеӨ§зҡ„з”ҹе‘Ҫжҙ»еҠӣе’Ңж·ұеҲ»ж„Ҹд№үпјҢеҗҜиҝӘзқҖ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йҮҮи–Ү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8жңҹвҖңж–ҮеӯҰдёҺиүәжңҜз ”з©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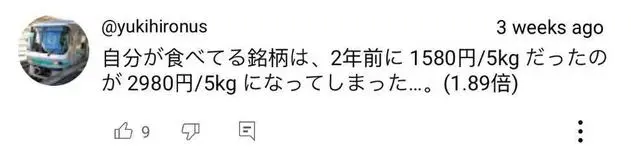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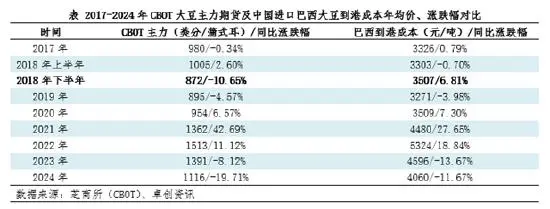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