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е§ңе№ҝиҫүпјҢз”·пјҢж№–еҚ—еӨ§еӯҰеІійә“д№Ұйҷўзү№иҒҳж•ҷжҺҲгҖҒеҚҡеЈ«з”ҹеҜјеёҲгҖӮе”җйҷҲй№ҸпјҢз”·пјҢж№–еҚ—еӨ§еӯҰеІійә“д№ҰйҷўеҚҡеЈ«з”ҹгҖӮ
дҪңдёәдј з»ҹеЈ«еӨ§еӨ«зҡ„е…ёиҢғдәәзү©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пјҲ989вҖ”1052пјүзҡ„дәәе“ҒгҖҒдәӢдёҡеҸҜи°“еҚ“з»қдёҖж—¶гҖӮеҚ—е®Ӣе„’иҖ…еҗ•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е…Ҳе„’и®әе®Ӣжңқдәәзү©пјҢд»ҘиҢғд»Іж·№дёә第дёҖгҖӮвҖқжңұзҶ№д№ҹи®ӨдёәиҢғд»Іж·№д№ғвҖңеӨ©ең°й—ҙж°”пјҢ第дёҖжөҒдәәзү©вҖқпјҢ并称иөһе…¶вҖңеҝғйҮҸд№Ӣе№ҝеӨ§й«ҳжҳҺпјҢеҸҜдёәзҷҫдё–д№ӢеёҲиЎЁвҖқгҖӮе®Ӣд»Јд»ҘиҝҳпјҢеҺҶд»Је„’иҖ…еҜ№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йҒ“еҫ·гҖҒеҠҹдёҡж— дёҚжҺЁеҙҮжңүеҠ пјҢзӣёе…із ”究дёҡе·ІзЎ•жһңзҙҜзҙҜгҖӮдҪҶе®һйҷ…дёҠ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з»ҸеӯҰж–№йқўдәҰйўҮжңүе»әж ‘пјҢе…¶ж–ҮйӣҶдёӯиҮід»Ҡд»ҚеӯҳжңүгҖҠжҳ“д№үгҖӢгҖҠеӣӣеҫ·иҜҙгҖӢзӯүз»ҸеӯҰдё“и®әд»ҘеҸҠеӨ§йҮҸи®Ёи®әз»ҸеӯҰд№үзҗҶзҡ„иҜ—ж–ҮпјҢж¶үеҸҠжҳ“еӯҰгҖҒжҳҘз§ӢеӯҰгҖҒзӨјеӯҰгҖҒеӣӣд№ҰеӯҰзӯүеӨҡдёӘз»ҸеӯҰеӯҰ科гҖӮиҮӘжұүд»Јд»ҘйҷҚпјҢеӯҰиҖ…е–ңж¬ўвҖңд»Ҙз»ҸжңҜзјҳйҘ°еҗҸжІ»вҖқпјҢдҫқжүҳеҜ№з»Ҹдј зҡ„и®Іи§ЈпјҢжқҘеҠқи°Ҹеҗӣдё»гҖӮиҖҢе®Ӣд»Ғе®—еҲҷжҳҜеҺҶеҸІдёҠйҖҡиҝҮз»Ҹзӯөи®ІеёӯеӯҰд№ з»Ҹе…ёж—¶й—ҙжңҖй•ҝзҡ„зҡҮеёқпјҢз”ұжӯӨе…»жҲҗжңқиҮЈйҖҡиҝҮи§Јз»Ҹи°ҸдёҠзҡ„йЈҺж°”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еҪўжҲҗдёҺиҝҷдёҖ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гҖӮиҝ‘е№ҙжқҘпјҢйғЁеҲҶеӯҰиҖ…ејҖе§Ӣе…іжіЁеҲ°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пјҢ并дә§з”ҹдәҶдёҖжү№з ”究жҲҗжһңгҖӮзәөи§Ӯиҝҷдәӣ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пјҢеӨ§еӨҡжҳҜд»Һжҳ“еӯҰгҖҒжҳҘз§ӢеӯҰзӯүеҚ•дёҖз»ҸеӯҰеӯҰ科еҜ№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иҝӣиЎҢжҺўзҙўдёҺйҳҗйҮҠпјҢиҖҢиҫғе°‘д»Һж•ҙдҪ“зҡ„еұӮйқўеҲҶжһҗиҢғд»Іж·№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ж ёеҝғеҶ…е®№еҸҠе…¶еҲӣж–°д№ӢеӨ„гҖӮйҖҡиҝҮе…Ёйқўйҳ…иҜ»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и®әи‘—пјҢ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дёҖдәӣйўҮе…·д»·еҖјзҡ„жҖқжғіе§Ӣз»ҲиҙҜз©ҝдәҺе…¶дёӯпјҢиҝҷдәӣж— з–‘е°ұжҳҜиҢғд»Іж·№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ж ёеҝғдёҺзІҫеҚҺжүҖеңЁ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ң¬ж–ҮжӢҹд»Һд»ҘдёӢ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еҜ№иҢғд»Іж·№з»ҸеӯҰзҡ„ж ёеҝғжҖқжғіеҒҡдёҖе°қиҜ•жҖ§зҡ„жҠүеҸ‘гҖӮдёҖгҖҒ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ж°‘жң¬жҖқжғі 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жҳҜдёӯеҚҺдјҳз§Җ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зҡ„зІҫй«“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еҸҜи°“жәҗиҝңжөҒй•ҝгҖӮе…Ҳз§Ұж—¶жңҹпјҢеӯ”еӯҗеӨ§еҠӣжҸҗеҖЎвҖңд»ҒвҖқеӯҰпјҢдё»еј вҖңиҠӮз”ЁиҖҢзҲұдәәпјҢдҪҝж°‘д»Ҙж—¶вҖқпјҢе°ҶвҖңзҲұж°‘вҖқдҪңдёәеҜ№з»ҹжІ»иҖ…зҡ„еҹәжң¬иҰҒжұӮгҖӮеӯҹеӯҗеңЁз»§жүҝеӯ”еӯҗзӯүеүҚдәәжҖқжғі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еҫ—е…¶ж°‘ж–Ҝеҫ—еӨ©дёӢвҖқвҖңж°‘дёәиҙөпјҢзӨҫзЁ·ж¬Ўд№ӢпјҢеҗӣдёәиҪ»вҖқзӯүзҶ зҶ з”ҹиҫүзҡ„жҖқжғіе‘ҪйўҳпјҢжһҒеӨ§ең°дё°еҜҢдәҶ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зҡ„ж ёеҝғеҶ…е®№гҖӮиҚҖеӯҗдәҰжҢҮеҮәвҖңзҲұж°‘иҖ…ејәпјҢдёҚзҲұж°‘иҖ…ејұвҖқпјҢ并дёӨж¬Ўеј•иҝ°вҖңеҗӣиҖ…пјҢиҲҹд№ҹпјҢеә¶дәәиҖ…пјҢж°ҙд№ҹпјӣж°ҙеҲҷиҪҪиҲҹпјҢж°ҙеҲҷиҰҶиҲҹвҖқзҡ„йҒ“зҗҶпјҢд»ҘиҜҙжҳҺзҷҫ姓жүҚжҳҜеҶіе®ҡеӣҪ家е…ҙиЎ°зҡ„жң¬жәҗжҖ§еӣ зҙ гҖӮеӯ”гҖҒеӯҹгҖҒиҚҖзӯүе…Ҳз§ҰеӨ§е„’еҜ№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зҡ„иҜ йҮҠдёҺжҺЁйҮҚпјҢж—ўеҪўеЎ‘дәҶ儒家вҖңз»Ҹдё–иҮҙз”ЁгҖҒдј йҒ“жөҺж°‘вҖқзҡ„еҹәжң¬е“Ғж јпјҢеҸҲи®©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жҲҗдёә儒家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зІҫзҘһж ҮиҜҶ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гҖҠе°ҡд№ҰВ·дә”еӯҗд№ӢжӯҢгҖӢд№ҹиЎЁзӨәвҖңж°‘жғҹйӮҰжң¬пјҢжң¬еӣәйӮҰе®ҒвҖқпјҢдёҚд»…йҳҗжҳҺдәҶеӣҪд№Ӣж №жң¬еңЁдәҺвҖңж°‘вҖқпјҢиҖҢдё”иҝҳејәи°ғвҖңж°‘вҖқеҜ№з»ҙзі»еӣҪ家е®үе®Ғе…·жңүе…ій”®жҖ§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ҢиҝҷеҜ№еҗҺдё–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зҡ„еҸ‘еұ•дәҰдә§з”ҹдәҶж·ұиҝң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дёӨеІҒеӨұжҖҷпјҢеҮәиә«еӯӨеҜ’пјҢеҜ№еә•еұӮж°‘дј—з”ҹжҙ»д№Ӣеӣ°йЎҝжңүеҲҮиә«зҡ„дҪ“дјҡпјҢиҮіе…¶еҮәд»•дёәе®ҳпјҢд»ҚдёҚеҝҳе…¶жң¬еҝғгҖӮеҰӮ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гҖҠи®©и§ӮеҜҹдҪҝ第дёүиЎЁгҖӢдёӯдҫҝжӣҫиҮӘиҝ°пјҡвҖңиҮЈеҮәеӨ„з©·еӣ°пјҢеҝ§жҖқж·ұиҝңпјҢж°‘д№Ӣз–ҫиӢҰпјҢзү©д№Ӣжғ…дјӘпјҢиҮЈзІ—зҹҘд№ӢгҖӮвҖқеҗҢж—¶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ҮӘе°‘ж—¶еҚівҖңжёёеҝғе„’жңҜпјҢеҶізҹҘеңЈйҒ“д№ӢеҸҜиЎҢвҖқпјҢ并еҜ№д»ҘвҖңе°Ҡж°‘йҮҚж°‘вҖқдёәйІңжҳҺзү№зӮ№зҡ„вҖңеӯҹиҪІд№Ӣеҝ—вҖқе°Өдёәе°Ҡеҙ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дёӯпјҢ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е§Ӣз»ҲеҚ жҚ®зқҖжңҖж ёеҝғзҡ„дҪҚзҪ®гҖӮд»Һ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гҖҠеӣӣж°‘иҜ—гҖӢжқҘзңӢпјҢе…¶зңјдёӯзҡ„вҖңж°‘вҖқ并йқһеҸӘйҷҗе®ҡдәҺд»ҺдәӢз§ҚжӨҚжҲ–е…»ж®–дёҡ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иҖҢжҳҜеӣҠжӢ¬дәҶеЈ«гҖҒеҶңгҖҒе·ҘгҖҒе•ҶеӣӣдёӘзұ»еҲ«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д»ЈиЎЁзқҖйҷӨдәҶз»ҹжІ»иҖ…д№ӢеӨ–зҡ„е№ҝжіӣзҡ„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гҖӮзәөи§Ӯ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вҖңж°‘жң¬вҖқжҖқжғіпјҢе®һд»Ҙ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дёәж ёеҝғе®—ж—Ёпјҡ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пјҢиҚЎиҚЎжҙҪеӨ§еҗҢд№ӢеҢ–пјӣзӨјзҡҶд»Һдҝ—пјҢзҶҷзҶҷж— дёҚиҺ·д№ӢдәәвҖҰвҖҰд»ҘдёәиӮҶдәҲдёҖдәәд№Ӣж„ҸпјҢеҲҷеӣҪеҝ…йў еҚұпјӣдјёе°”дёҮйӮҰд№ӢжҖҖпјҢеҲҷдәәе°Ҷйј“иҲһгҖӮдәҺжҳҜе®Ўж°‘д№ӢеҘҪжҒ¶пјҢеҜҹж”ҝд№ӢеҗҰиҮ§гҖӮжңүз–ҫиӢҰеҝ…дёәд№ӢеҺ»пјҢжңүзҒҫе®іеҝ…дёәд№ӢйҳІвҖҰвҖҰеҪјжғ§зғҰиӢӣпјҢжҲ‘еҲҷеҙҮз®Җжҳ“д№ӢйҒ“пјӣеҪјжӮЈз©·еӨӯпјҢжҲ‘еҲҷдҝ®еҜҢеҜҝд№Ӣж–№гҖӮеӨ«еҰӮжҳҜеҲҷзҲұе°Ҷдј—еҗҢпјҢд№җдёҺдәәе…ұпјҢеҫ·жіҪжөғдәҺж°‘еә¶пјҢд»ҒеЈ°ж’ӯдәҺйӣ…йўӮ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пјҢжҢҮзҡ„жҳҜдёҖеҲҮж”ҝзӯ–зҡ„еҲ¶е®ҡдёҺе®һж–ҪйғҪеҝ…йЎ»йЎәд»Һж°‘ж„ҸгҖӮиҝҷжҳҺжҳҫжҳҜеҜ№гҖҠз®ЎеӯҗВ·зү§ж°‘гҖӢвҖңж”ҝд№ӢжүҖе…ҙпјҢеңЁйЎәж°‘еҝғвҖқжҖқжғі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з»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°Ҷд№ӢеҮқз»“дёә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еӣӣеӯ—пјҢиЎЁиҫҫжӣҙдёәйҶ’иұҒ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еҗӣзҺӢжІ»зҗҶеӣҪ家еҸӘжңүд»ҘвҖңйЎәж°‘еҝғвҖқдёәе®—ж—ЁпјҢжүҚиғҪйј“иҲһдёҮж°‘пјҢй“ёе°ұжҙҪзҶҷе’Ңд№җзҡ„зӨҫдјҡпјӣиӢҘд»ҘвҖңиӮҶдәҲдёҖдәәвҖқвҖңжң•еҚіеӣҪ家вҖқзҡ„зҗҶеҝөдёәиҝҪжұӮпјҢеј„еҫ—ж°‘дёҚиҒҠз”ҹпјҢеҲҷеӣҪ家зӨҫзЁ·еҝ…е°ҶжңүвҖңйў еҚұвҖқд№Ӣйҷ©гҖӮиҝҷйҮҢжүҖйҡҗеҗ«зҡ„ж„ҸжҖқжҳҜпјҢеӨ©дёӢдёҚеә”д»ҘзҡҮеёқдёҖдәәдёәдё»дҪ“пјҢзҡҮеёқд№ҹдёҚеҸҜе”ҜжҲ‘зӢ¬е°ҠгҖҒйҡҸеҝғжүҖж¬Іең°еҸ‘еҸ·ж–Ҫд»ӨеҪ№дҪҝдәәж°‘пјҢиҖҢеә”д»Ҙдәәж°‘еӨ§дј—дёәдё»дҪ“гҖӮ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е…ій”®еңЁдёҖдёӘвҖңйЎәвҖқеӯ—пјҢжү§ж”ҝиҖ…жҳҜиҷҡе·ұйЎәд»Һж°‘еҝғпјҢиҝҳжҳҜе°Ҷж°‘дј—еҸҳжҲҗвҖңйЎәж°‘вҖқпјҢйЎәд»ҺиҮӘе·ұпјҢдёҖеӯ—зҗҶи§ЈдёҚеҗҢпјҢж„Ҹд№үеӨ§еҸҳпјҢе…¶з»“еұҖдәҰжӮ¬йҡ”дёҮйҮҢ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жҺҘзқҖйҳҗиҝ°йҒ“пјҢйЎәд»Һж°‘ж„ҸпјҢе°ұжҳҜиҰҒеҜ№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зҡ„еҘҪжҒ¶жңүжҳҺжҷ°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并д»ҘжӯӨжқҘеҜҹйӘҢжңқж”ҝзҡ„еҫ—еӨұгҖӮе…·дҪ“иҜҙжқҘпјҢеҚідәәж°‘жңүз–ҫиӢҰпјҢеҝ…дёәд№ӢйҷӨеҺ»пјӣдәәж°‘еҸҜиғҪйҒӯзҪ№зҒҫе®іпјҢеҝ…дёәд№ӢжҸҗеүҚйў„йҳІпјӣдәәж°‘жғ§жҖ•з№ҒжқӮиӢӣз»Ҷзҡ„жі•д»ӨпјҢе°ұеә”еҪ“з®Җж”ҝдҫҝж°‘пјӣдәәж°‘йқўдёҙз©·еӣ°ж—©еӨӯзҡ„иү°йҡҫеӨ„еўғпјҢе°ұеҫ—иҝ…йҖҹйҮҮеҸ–жңүж•ҲжҺӘж–Ҫи®©ж°‘дј—иҝҮдёҠеҜҢи¶ій•ҝеҜҝзҡ„з”ҹжҙ»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з»ҹжІ»иҖ…еә”еҪ“вҖңдёҚд»Ҙе·ұж¬Ідёәж¬ІпјҢиҖҢд»Ҙдј—еҝғдёәеҝғвҖқпјҢдёҖеҲҮж”ҝзӯ–зҡ„е…ҙеәҹдёҺи°ғж•ҙпјҢзҡҶд»Ҙзҷҫ姓зҡ„е®һйҷ…йңҖиҰҒдёәеҮҶгҖӮеҰӮжӯӨпјҢж”ҝд»ӨжүҖеҮәпјҢзҡҶйЎәвҖңж°‘еҝғвҖқпјҢеӨ©дёӢе…ұдә«е…¶д№җпјҢзҷҫ姓еҗҢеҸ—е…¶жғ гҖӮеҪ“然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дё»еј е№¶йқһеҸӘжҳҜдёҖеҸҘз©әжҙһзҡ„еҸЈеҸ·пјҢиҖҢжҳҜжңүд»ҘдёӢ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зҡ„е®һйҷ…еҶ…е®№гҖӮ1.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еҹәзЎҖжҳҜвҖңе…»ж°‘вҖқеҹәдәҺе°‘е№ҙж—¶жңҹзҡ„еқҺеқ·з»ҸеҺҶ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Ҝ№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зҡ„з”ҹеӯҳеўғеҶөж јеӨ–йҮҚи§ҶпјҢеұЎеұЎеҠқи°Ҹз»ҹжІ»иҖ…еә”еҪ“е…ЁеҠӣвҖңе…»ж°‘вҖқпјҢеҚідёә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жҸҗдҫӣиғҪж»Ўи¶іеҹәжң¬з”ҹжҙ»зҡ„еҗ„ж–№йқўжқЎд»¶гҖӮгҖҠе°ҡд№ҰВ·еӨ§зҰ№и°ҹ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ҫ·жғҹе–„ж”ҝпјҢж”ҝеңЁе…»ж°‘гҖӮвҖқиҢғд»Іж·№еҜ№жӯӨиҜ йҮҠйҒ“пјҡвҖңеңЈдәәд№Ӣеҫ·пјҢжғҹеңЁе–„ж”ҝпјӣе–„ж”ҝд№ӢиҰҒпјҢжғҹеңЁе…»ж°‘гҖӮвҖқ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еңЈдәәд№Ӣеҫ·жңҖе…ій”®зҡ„е‘ҲзҺ°еңЁдәҺжҺЁиЎҢвҖңе–„ж”ҝвҖқпјҢиҖҢжҺЁиЎҢвҖңе–„ж”ҝвҖқзҡ„зҙ§иҰҒеӨ„еҚіеңЁдәҺвҖңе…»ж°‘вҖқгҖӮеҸҲ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зі»иҫһгҖӢжҸҗеҮәпјҡвҖңеӨ©ең°д№ӢеӨ§еҫ·жӣ°з”ҹпјҢеңЈдәәд№ӢеӨ§е®қжӣ°дҪҚпјҢдҪ•д»Ҙе®ҲдҪҚжӣ°д»ҒгҖӮвҖқиҢғд»Іж·№йЎәжӯӨйҳҗиҝ°иҜҙпјҡвҖңжҳҜд»ҘеӨ©ең°е…»дёҮзү©пјҢж•…е…¶йҒ“дёҚз©·пјӣеңЈдәәе…»дёҮж°‘пјҢж•…е…¶дҪҚдёҚеҖҫ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е°ҶвҖңе…»ж°‘вҖқи§ҶдёәеңЈдәәеҫ—дҪҚгҖҒеӣҪ家еҫ—е®үзҡ„ж №жң¬дҝқиҜҒ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гҖҠйҳ…еҸӨе ӮиҜ—гҖӢдёӯ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иҖ•еӨ«дёҺжЁөеӯҗпјҢйҘұжҡ–зӣёи®ҙеҗҹгҖӮзҺӢйҒ“иҮӘжӯӨе§ӢпјҢ然еҗҺеј зҶҸзҗҙгҖӮвҖқжүҖи°“вҖңзҺӢйҒ“иҮӘжӯӨе§ӢвҖқпјҢжҳҺжҳҫжҳҜеҜ№гҖҠеӯҹеӯҗВ·жўҒжғ зҺӢ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и°·дёҺйұјйі–дёҚеҸҜиғңйЈҹпјҢжқҗжңЁдёҚеҸҜиғңз”ЁпјҢжҳҜдҪҝж°‘е…»з”ҹдё§жӯ»ж— жҶҫд№ҹгҖӮе…»з”ҹдё§жӯ»ж— жҶҫпјҢзҺӢйҒ“д№Ӣе§Ӣд№ҹвҖқдёҖеҸҘзҡ„еҢ–з”ЁгҖӮд»ҘжӯӨеҸҜзҹҘпјҢвҖңе…»ж°‘вҖқ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ңјдёӯе®һе…·жңүвҖңзҺӢйҒ“д№Ӣе§ӢвҖқзҡ„йҮҚиҰҒж„Ҹд№үгҖӮ2.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е…ій”®жҳҜвҖңеҲ©ж°‘вҖқдёәдәҶжӣҙеҘҪең°йҳҗеҸ‘е…¶вҖңеҲ©ж°‘вҖқзҡ„дё»еј 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°Ҷ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жҚҹзӣҠвҖқд№ӢйҒ“еҲӣйҖ жҖ§ең°иҜ йҮҠжҲҗвҖңжҚҹдёҠпјҲеҗӣпјүзӣҠдёӢпјҲж°‘пјүвҖқд№ӢйҒ“гҖӮеҰӮ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жҚҹгҖӢиҜҙпјҡгҖҠжҚҹгҖӢпјҢеұұжіҪйҖҡж°”пјҢиү®дёәеұұпјҢе…‘дёәжіҪгҖӮе…¶ж¶ҰдёҠиЎҢпјҢеҸ–дёӢиө„дёҠд№Ӣж—¶д№ҹвҖҰвҖҰ然еҲҷдёӢиҖ…дёҠд№Ӣжң¬пјҢжң¬еӣәеҲҷйӮҰе®ҒгҖӮд»ҠеҠЎдәҺеҸ–дёӢпјҢд№ғдјӨе…¶жң¬зҹЈпјҢеҚұд№ӢйҒ“д№ҹгҖӮжҚҹд№Ӣжңүж—¶пјҢж°‘зҠ№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№ҹпјҢе…‘дёә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пјӣжҚҹд№Ӣж— ж—¶пјҢжіҪе°Ҷз«ӯз„үпјҢе…‘дёәжіҪгҖӮж•…жӣ°вҖңе·қз«ӯеҝ…еұұеҙ©вҖқпјҢжӯӨд№ӢиұЎд№ҹгҖӮ жҚҹеҚҰд·ЁпјҢе…¶еҚҰеҗҚзҡ„еҸ–иұЎжҳҜд»Һж№–еә•жҢ–еңҹеҫҖеұұдёҠе ҶпјҢеҚівҖңеҸ–дёӢиө„дёҠвҖқ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°Ҷе…¶еј•з”ідёәеүҘж°‘д»ҘеҘүеҗӣгҖӮдҫқжӯӨ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ЎЁзӨәпјҢж°‘иҷҪеӨ„дёӢпјҢиҖҢе®һдёәйӮҰжң¬пјҢж•…дёҚеҸҜиҝҮеәҰеҸ–ж°‘д№ӢиҙўгҖӮеҰӮжһңдёҖе‘іең°жҚҹж°‘д»ҘеҲ©еҗӣпјҢеҝ…然дјҡдҪҝж°‘еҠӣеӣ°з«ӯпјҢиҝҷж— з–‘жҳҜжҜҒеӣҪд№Ӣж №еҹәгҖҒйҷ·еӣҪдәҺйҷ©еўғпјҢжүҖеҜјиҮҙзҡ„е°ҶжҳҜгҖҠеӣҪиҜӯВ·е‘ЁиҜӯгҖӢдёӯжүҖиЁҖзҡ„вҖңе·қз«ӯеұұеҝ…еҙ©вҖқзҡ„еҗҺжһң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жӯЈзЎ®зҡ„еҒҡжі•еә”иҜҘжҳҜжҖҺж ·зҡ„е‘ўпјҹ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иҜ и§ЈвҖңзӣҠвҖқеҚҰж—¶йғ‘йҮҚең°еӣһзӯ”дәҶ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пјҡгҖҠзӣҠгҖӢпјҢеҲҡжқҘиҖҢеҠ©жҹ”пјҢжҚҹжңүдҪҷиҖҢиЎҘдёҚи¶івҖҰвҖҰиҮӘдёҠжғ дёӢд№Ӣж—¶д№ҹгҖӮеӨ©йҒ“дёӢжөҺпјҢе“Ғзү©е’ёдәЁпјӣеңЈдәәдёӢжөҺпјҢдёҮеӣҪе’ёе®ҒгҖӮгҖҠзӣҠгҖӢд№ӢдёәйҒ“еӨ§зҹЈе“үпјҒ然еҲҷзӣҠдёҠжӣ°гҖҠжҚҹгҖӢпјҢжҚҹдёҠжӣ°гҖҠзӣҠгҖӢиҖ…пјҢдҪ•д№ҹпјҹеӨ«зӣҠдёҠеҲҷжҚҹдёӢпјҢжҚҹдёӢеҲҷдјӨе…¶жң¬д№ҹпјҢжҳҜж•…и°“д№ӢгҖҠжҚҹгҖӢгҖӮжҚҹдёҠеҲҷзӣҠдёӢпјҢзӣҠдёӢеҲҷеӣәе…¶жң¬д№ҹпјҢжҳҜж•…и°“д№ӢгҖҠзӣҠгҖӢгҖӮжң¬ж–ҜеӣәзҹЈпјҢе№Іж–ҜиҢӮзҹЈпјӣжәҗж–Ҝж·ұзҹЈпјҢжөҒж–Ҝй•ҝзҹЈгҖӮдёӢд№ӢзӣҠдёҠпјҢеҲҷеҲ©жңүз«ӯз„үпјӣдёҠд№ӢзӣҠдёӢпјҢеҲҷеӣ е…¶еҲ©иҖҢеҲ©д№ӢпјҢдҪ•з«ӯд№Ӣжңүз„үвҖҰвҖҰжҳҺгҖҠзӣҠгҖӢд№ӢйҒ“пјҢдҪ•еҫҖиҖҢдёҚеҲ©е“үпјҹ зӣҠеҚҰд·©пјҢйңҮдёӢе·ҪдёҠпјҢдёҠеҚҰе°ҡдҪҷдәҢйҳіпјҢдёӢеҚҰд»…жңүдёҖйҳіпјҢжүҖд»ҘиҢғд»Іж·№иҜҙвҖңеҲҡжқҘиҖҢеҠ©жҹ”пјҢжҚҹжңүдҪҷиҖҢиЎҘдёҚи¶івҖқпјҢзӣҠеҚҰжүҖе–»зӨәзҡ„жӯЈжҳҜиҝҷвҖңиҮӘдёҠжғ дёӢвҖқд№Ӣж—¶зҡ„жғ…еўғгҖӮеҗӣзҺӢеұ…дёҠпјҢеҜҢжңүеӣӣжө·пјӣж°‘дј—еұ…дёӢпјҢжүҖжӢҘжҲ–жңӘеҸҠдёҖе®ӨгҖӮжҚҹеҗӣдёҠд»ҘзӣҠдёӢж°‘пјҢеҲҷеҗӣдёҠжҚҹиҖ—ж— еҮ пјҢиҖҢдёӢж°‘еҫ—жғ е®һеӨҡпјҢжӯӨеҚівҖңеңЈдәәдёӢжөҺпјҢдёҮеӣҪе’ёе®ҒвҖқ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жҺҘзқҖеҲҶжһҗиҜҙпјҢжҚҹеҚҰеӣ е…¶жҚҹдёӢзӣҠдёҠгҖҒжҚҹж°‘еҲ©еҗӣжңүдјӨвҖңйӮҰжң¬вҖқиҖҢеҫ—еҗҚдёәвҖңжҚҹвҖқпјҢзӣҠеҚҰеӣ е…¶жҚҹдёҠзӣҠдёӢгҖҒжҚҹеҗӣеҲ©ж°‘е·©еӣәвҖңйӮҰжң¬вҖқиҖҢеҫ—еҗҚдёәвҖңзӣҠвҖқгҖӮжҚўиЁҖд№ӢпјҢжҳҜвҖңжҚҹж°‘вҖқиҝҳжҳҜвҖңзӣҠж°‘вҖқпјҢжһ„жҲҗдәҶжҚҹгҖҒзӣҠдәҢеҚҰзҡ„е‘ҪеҗҚж ҮеҮҶгҖӮеҶөдё”пјҢжҚҹеҗӣеҲ©ж°‘жң¬е°ұжҳҜвҖңеҸ–д№ӢдәҺж°‘пјҢз”Ёд№ӢдәҺж°‘вҖқпјҢвҖңеӣ е…¶еҲ©иҖҢеҲ©д№ӢвҖқпјҢжҳҜеҸҜд»ҘжҢҒз»ӯдёҚз«ӯзҡ„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жҲ‘们дҫҝеҸҜд»ҘжҳҺзҷҪпјҢеӨ§вҖңзӣҠвҖқд№ӢйҒ“зҡ„ж ёеҝғиҰҒд№үе°ұеңЁдәҺжҚҹдёҠзӣҠдёӢгҖҒжҚҹеҗӣеҲ©ж°‘гҖӮдёҮж°‘зҡҶеҫ—е…¶еҲ©пјҢеӣҪдҫҝеҸҜеҫ—е…¶е®үпјҢиҝҷеҜ№дәҺз»ҹжІ»иҖ…жқҘиҜҙпјҢйҡҫйҒ“дёҚжҳҜвҖңж— еҫҖдёҚеҲ©вҖқеҗ—пјҹиҖҢеңЁ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е…‘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ҝӣдёҖжӯҘејәи°ғйҒ“пјҢеҸӘжңүеҒҡеҲ°жҺЁжҒ©ж•·жғ гҖҒдёҖеҝғвҖңеҲ©ж°‘вҖқпјҢжүҚиғҪи®©еҗӣж°‘дёҠдёӢе’Ңи°җж¬ЈжӮҰпјҢиҝӣиҖҢеҠ©жҺЁвҖңзҺӢйҒ“д№ӢжІ»вҖқеӨ§еҫ—дәЁйҖҡпјҡгҖҠе…‘гҖӢпјҢжіҪйҮҚж¶ҰиҖҢдёҠдёӢзҡҶ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пјҢеҗӣеӯҗжҺЁжҒ©ж•·жғ д№Ӣж—¶д№ҹгҖӮеӨ«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ёҮзү©иҖ…пјҢиҺ«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№ҺжіҪгҖӮд»ҠеӨҚйҮҚд№ӢпјҢж°‘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иҖҢж— з–ҶиҖ…д№ҹгҖӮеҠқеӨ©дёӢиҖ…пјҢиҺ«еӨ§д№ҺжҺЁжҒ©иҖҢж•·жғ пјҢеҲҷвҖңйЎәд№ҺеӨ©пјҢеә”д№ҺдәәвҖқпјҢиҖҢзҺӢйҒ“дәЁгҖӮдёҚ然иҖ…еҸҚжӯӨгҖӮиӢҘеӨ«еЁҒд»Ҙе…Ҳж°‘пјҢж°‘йҮҚе…¶еҠіпјӣеЁҒд»ҘзҠҜйҡҫпјҢж°‘йҮҚе…¶жӯ»гҖӮ е…‘еҚҰд·№пјҢдёҠдёӢзҡҶе…‘пјҢзҠ№дёӨжіҪзӣёиҝһпјҢеҜ“ж„ҸдёҮзү©еҸ—еҲ°ж№–ж°ҙж»Ӣе…»иҖҢе’ҢжӮҰ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°Ҷе…¶ж–ҪдәҺдәәдәӢпјҢиҜ йҮҠдёәеҗӣж°‘вҖңдёҠдёӢзҡҶжӮҰ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жӯӨеҚҰеңЁе…¶зңјдёӯжүҖе–»зӨәзҡ„дҫҝжҳҜвҖңеҗӣеӯҗжҺЁжҒ©ж•·жғ д№Ӣж—¶вҖқзҡ„жғ…еўғгҖӮ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иҜҙеҚҰ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ёҮзү©иҖ…иҺ«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№ҺжіҪгҖӮвҖқе…‘еҚҰдёӨжіҪзӣёйҮҚпјҢдәӨзӣёжөёж¶ҰпјҢиҝҷж„Ҹе‘ізқҖж°‘дј—жӯӨж—¶иғҪеӨҹйҒҚеҸ—жү§ж”ҝиҖ…ж”ҝзӯ–д№ӢжҒ©жғ пјҢе…¶еҶ…еҝғиҮӘ然дјҡз”ҹеҮәж— йҷҗе–ңжӮҰ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ҫӘжӯӨиҖҢжҢҮеҮәпјҢжү§ж”ҝиҖ…еҝ…йЎ»еӯҰдјҡжҺЁжҒ©ж•·жғ д»ҘеҲ©ж°‘пјҢжүҚиғҪйЎәеӨ©еә”дәәпјҢж•ҰеҠқеӨ©дёӢзҷҫ姓пјҢйҖ е°ұзҺӢйҒ“зӣӣдё–гҖӮеҰӮжһңз»ҹжІ»иҖ…дёҚд»…дёҚвҖңеҲ©ж°‘вҖқпјҢеҸҚиҖҢиҝҳд»ҘиӢӣж”ҝеЁҒжқғејәеҠ дәҺж°‘пјҢи®©ж°‘дј—ж— жі•е®үиә«з«Ӣе‘Ҫ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ж°‘дј—еҸӘдјҡжғізқҖеҰӮдҪ•жғңеҠӣдҝқе‘ҪпјҢиҖҢз»қдёҚдјҡеҝғз”ҳжғ…ж„ҝең°дёәз»ҹжІ»иҖ…ж•ҲеҠіпјҢжӯӨеҚіиҢғд»Іж·№жүҖиӯҰиҜ«зҡ„вҖңеЁҒд»Ҙе…Ҳж°‘пјҢж°‘йҮҚе…¶еҠіпјӣеЁҒд»ҘзҠҜйҡҫпјҢж°‘йҮҚе…¶жӯ»вҖқгҖӮ3.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ж №жң¬жҳҜвҖңзҲұж°‘вҖқиҢғ仲淹继жүҝ并еҸ‘еұ•дәҶе…Ҳз§Ұ儒家зҡ„вҖңзҲұж°‘вҖқжҖқжғіпјҢи®Өдёәз»ҹжІ»иҖ…еҝ…йЎ»еғҸзҲұжҠӨиҮӘе·ұзҡ„иә«дҪ“дёҖж ·еҺ»зҲұжҠӨзҷҫ姓пјҡзҲұж°‘еҲҷеӣ е…¶ж №жң¬пјҢдёәдҪ“еҲҷеҺҡе…¶е…»иӮІвҖҰвҖҰи°“ж°‘д№ӢзҲұд№ҹпјҢиҺ«е…Ҳд№ҺеӣӣдҪ“пјӣи°“еӣҪд№Ӣдҝқд№ҹпјҢиҺ«еӨ§д№ҺзҫӨй»ҺвҖҰвҖҰд»ҠжҲ‘еҗҺеҢ–жҙҪйЈҺиЎҢпјҢйҒ“е…үеӨ©еҗҜгҖӮжҜҸи§Ҷж°‘иҖҢеҰӮеӯҗпјҢеӨҚдҪҝиҮЈиҖҢд»ҘзӨјгҖӮж•…иғҪд»Ҙе…ӯеҗҲиҖҢдёә家пјҢйҪҗдёҮзү©дәҺдёҖдҪ“гҖӮ 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и°ғпјҢеҸӘжңүд»Ҙд»ҒзҲұд№ӢеҝғеҜ№еҫ…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пјҢз»ҷдәҲе…¶зңҹеҲҮзҡ„е…ізҲұдёҺдҝқжҠӨпјҢз»ҹжІ»иҖ…жүҚиғҪзј”йҖ вҖңе…ӯеҗҲдёә家вҖқвҖңдёҮзү©дёҖдҪ“вҖқзҡ„дё°еҠҹдјҹдёҡпјҢиҖҢеӣҪ家д№ҹиғҪз”ұжӯӨй•ҝжңҹдҝқжҢҒз№ҒиҚЈгҖҒе®үе®ҡдёҺз»ҹдёҖгҖӮеңЁгҖҠе°§иҲңзҺҮеӨ©дёӢд»Ҙд»ҒиөӢ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жӣҙжҳҜд»Ҙе°§гҖҒиҲңд№ӢжІ»дёәдҫӢпјҢе°ҶиҝҷдёӘйҒ“зҗҶи®Іеҫ—йқһеёёжҳҺзҷҪпјҡвҖңз©Ҷз©ҶиҷһиҲңпјҢе·Қе·Қеёқе°§гҖӮдјҠдәҢеңЈд№Ӣд»ҒеҢ–пјҢиҮҙеӣӣжө·д№ӢеҜҢйҘ¶гҖӮеҚҸе’ҢдёҮйӮҰпјҢзӣ–е®үдәәиҖҢдёәзҗҶпјӣиӮҶи§җзҫӨеҗҺпјҢдҪҶеӨҚзӨјд»Ҙеұ…жңқгҖӮеҪ“е…¶еҰӮеӨ©иҖ…е°§пјҢ继尧иҖ…иҲңпјҢе®ҲдҪҚиҖҢж—¶ж—ўзӣёжҺҘпјҢиЎҢд»ҒиҖҢжҖ§дәҰзӣёиҝ‘гҖӮвҖқе°§гҖҒиҲңз•…иЎҢд»Ғд№үгҖҒзҲұжҠӨзҷҫ姓пјҢж–№д»Өеӣӣжө·е’Ңе№іеҜҢйҘ¶гҖҒдәәж°‘е’ҢзқҰе®үеә·гҖӮиҖҢжңӘиғҪеғҸе°§гҖҒиҲңдёҖж ·иғёжҖҖвҖңзҲұж°‘вҖқд№Ӣеҝғзҡ„з»ҹжІ»иҖ…пјҢеҝ…з„¶ж— жі•е°Ҷ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ж–Ҫж”ҝе®—ж—Ёй•ҝд№…ең°д»ҳиҜёе®һи·өгҖӮеҰӮжӯӨпјҢиҮӘ然д№ҹе°ұж— жі•иҝҪдёүд»Јд№Ӣй«ҳгҖҒжҲҗе°ұвҖңзҺӢйҒ“д№ӢжІ»вҖқдәҶгҖӮдәҢгҖҒ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 е®Ӣжң«е…ғеҲқзҡ„еӨ§е„’зүҹжӣҫз§°иӘүиҢғд»Іж·№вҖңеҚҡйҖҡе…ӯз»ҸпјҢе°Өй•ҝдәҺгҖҠжҳ“гҖӢвҖқпјҢи§ӮиҜёиҢғд»Іж·№зҺ°еӯҳзҡ„з»ҸеӯҰи®әи‘—пјҢдәҰд»Ҙжҳ“еӯҰдёәжңҖеӨҡ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жҳ“еӯҰ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жҖқжғідёӯе®һе…·жңүжҹұзЎҖиҲ¬зҡ„ең°дҪҚгҖӮдҪңдёәвҖңдә”з»Ҹд№ӢйҰ–вҖқзҡ„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жң¬жқҘе°ұжҳҜдёҖйғЁиЁҖвҖңеҸҳвҖқд№Ӣд№ҰгҖӮеҰӮ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зі»иҫһ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жҳ“гҖӢд№Ӣдёәд№Ұд№ҹдёҚеҸҜиҝңпјҢдёәйҒ“д№ҹеұЎиҝҒгҖӮеҸҳеҠЁдёҚеұ…пјҢе‘ЁжөҒе…ӯиҷҡпјҢдёҠдёӢж— еёёпјҢеҲҡжҹ”зӣёжҳ“пјҢдёҚеҸҜдёәе…ёиҰҒпј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иҜҙпјҢ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иҝҷйғЁд№ҰдёҚеҸҜйЎ»иҮҫиҝңзҰ»пјҢеӨ©ең°дёҮзү©е§Ӣз»ҲеңЁжөҒиҪ¬еҸҳиҝҒпјҢдёҚеҸҜжү§жұӮдәҺ常规пјҢеҸӘжңүеҸҳеҢ–жүҚжҳҜж°ёжҒ’гҖӮ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зі»иҫһгҖӢиҝҳжҢҮеҮәпјҢжҳ“вҖңз©·еҲҷеҸҳпјҢеҸҳеҲҷйҖҡпјҢйҖҡеҲҷд№…вҖқгҖӮжӯӨиҜӯжҸӯзӨәдәҶеӨ©йҒ“гҖҒдәәйҒ“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еҺҹзҗҶгҖӮе°ұеӨ©ең°д№ӢйҒ“иҖҢиЁҖпјҢдёҮдәӢдёҮзү©еҸ‘еұ•еҲ°жһҒз«ҜпјҲе°ҪеӨҙпјүж—¶пјҢдјҡеҸ‘з”ҹж–°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еҸӘжңүеҸҳеҢ–жүҚжҳҜй•ҝд№…д№ӢйҒ“гҖӮе°ұдәәйҒ“иҖҢиЁҖпјҢйҒҮеҲ°еӣ°з©·ж—¶пјҢе°ұиҰҒеӯҰдјҡж”№еҸҳпјҢж”№еҸҳдәҶе°ұиғҪйҖҡиҫҫпјҢйҖҡиҫҫдәҶжүҚиғҪй•ҝд№…гҖӮиҝҷжҳҜ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жҢҮеҜјдәә们и®ӨиҜҶдё–з•Ңзҡ„иҮізҗҶеҗҚиЁҖ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ңЁжҳ“еӯҰзҡ„и§ҶеҹҹдёӯпјҢеҸҳеҢ–жҳҜжҺЁеҠЁдәӢзү©еҸ‘еұ•зҡ„ж №жң¬еҠЁеҠӣгҖӮйҖҡиҝҮж·ұе…ҘеҲҶжһҗ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жҳ“еӯҰи®әи‘—пјҢжҲ‘们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пјҢд»–зҡ„жҳ“еӯҰиҜ йҮҠе§Ӣз»Ҳз¬ғе®ҲзқҖ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зі»иҫһгҖӢжүҖжҸӯзӨәзҡ„вҖңеҸҳжҳ“вҖқе®—ж—ЁпјҢ并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жһ„е»әдәҶе…¶зӢ¬е…·зү№иүІзҡ„жҳ“еӯҰ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гҖӮеҰӮеңЁгҖҠеӣӣж°‘иҜ—В·еЈ«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жӣҫ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йҳҙйҳіжңүеҸҳеҢ–пјҢе…¶зҘһеӣәдёҚжөӢгҖӮвҖқиҖҢеңЁгҖҠз©·зҘһзҹҘеҢ–иөӢ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ҸҲйҳҗиҝ°иҜҙпјҡжғҹзҘһд№ҹж„ҹиҖҢйҒӮйҖҡпјҢжғҹеҢ–д№ҹеҸҳеңЁе…¶дёӯгҖӮ究жҳҺзҘһиҖҢжңӘжҳ§пјҢзҹҘиҮіеҢ–иҖҢж— з©·вҖҰвҖҰеӨ§гҖҠжҳ“гҖӢж јиЁҖпјҢе…ҲеңЈеҫ®ж—ЁгҖӮзҘһеҲҷдёҚзҹҘдёҚиҜҶпјҢеҢ–еҲҷж— з»Ҳж— е§ӢгҖӮеңЁд№Һз©·д№ӢдәҺжӯӨпјҢеҫ—д№ӢдәҺеҪјвҖҰвҖҰзЁҪжҒ¶зӣҲиҖҢжҳҜеҲҷпјҢе°Ҷеә”еҸҳд»ҘдҪ•з–‘пјҹ 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вҖңеҸҳеҢ–вҖқжҳҜдё–з•ҢеӯҳеңЁ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дёҮдәӢдёҮзү©йғҪеӨ„еңЁеҸҳеҢ–зҡ„иҝҮзЁӢеҪ“дёӯгҖӮдәә既然з”ҹеӯҳдәҺиҝҷе……ж»ЎеҸҳеҢ–зҡ„дё–з•ҢпјҢе°ұеә”иҜҘдё»еҠЁең°йҖҡе…¶еҸҳеҢ–гҖҒжҲҗе…¶еҸҳеҢ–гҖӮвҖңзЁҪжҒ¶зӣҲиҖҢжҳҜеҲҷпјҢе°Ҷеә”еҸҳд»ҘдҪ•з–‘вҖқдёӯзҡ„вҖңжҒ¶зӣҲвҖқдәҢеӯ—еҸ–иҮӘ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и°ҰгҖӢеҚҰеҪ–дј вҖңдәәйҒ“жҒ¶зӣҲиҖҢеҘҪи°ҰвҖқгҖӮдёәдәәд№ӢйҒ“пјҢеҺҢжҒ¶иҮӘеӨ§зӣҲж»ЎпјҢиҮӘеӨ§зӣҲж»Ўе°ұдёҚдјҡжңүиҝӣжӯҘгҖӮеӣ жӯӨиҰҒжғідёҚж–ӯиҝӣжӯҘпјҢе°ұиҰҒдёҚж–ӯеҸҳеҢ–жҸҗеҚҮиҮӘе·ұгҖӮеңЁгҖҠжҳ“е…јдёүжқҗиөӢ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и°ғйҒ“пјҢвҖ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вҖқжҳҜжІ»гҖҠжҳ“гҖӢз”ЁгҖҠжҳ“гҖӢзҡ„еҹәжң¬еҺҹеҲҷпјҡжҳ”иҖ…жңүеңЈдәәд№Ӣз”ҹпјҢе»әеӨ§жҳ“д№Ӣж—ЁгҖӮи§ӮеӨ©д№ӢйҒ“пјҢеҜҹең°д№ӢзәӘгҖӮеҸ–дәәдәҺж–ҜпјҢжҲҗеҚҰдәҺеҪјгҖӮе°Ҷд»Ҙе°ҪеҸҳеҢ–дә‘дёәд№Ӣд№үпјҢе°Ҷд»ҘеӯҳжҙҒйқҷзІҫеҫ®д№ӢзҗҶвҖҰвҖҰи§Ӯе…¶иұЎеҲҷеҢәд»ҘеҲ«зҹЈпјҢжҖқе…¶йҒ“еҲҷеҸҳиҖҢйҖҡд№ӢгҖӮдёҠд»Ҙз»ҹзҷҫзҺӢд№ӢдёҡпјҢдёӢд»Ҙж–ӯдёҮзү©д№Ӣз–‘гҖӮеҸҳеҠЁдёҚеұ…пјҢйҖӮеҶ…еӨ–иҖҢж— ж»һпјӣе№ҝеӨ§жӮүеӨҮпјҢеҢ…дёҠдёӢиҖҢеј—йҒ—гҖӮиҮізҹЈе“үпјҒж— е№ҪдёҚйҖҡпј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гҖӮ 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ңӢжқҘпјҢ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дёҖд№Ұж¶өжӢ¬дәҶеӨ©ең°й—ҙдёҮдәӢдёҮзү©иҝҗиЎҢеҸҳеҢ–зҡ„规еҫӢпјҢеҸҜд»ҘдёҠз»ҹвҖңзҷҫзҺӢд№ӢдёҡвҖқгҖҒдёӢж–ӯвҖңдёҮзү©д№Ӣз–‘вҖқпјҢеҸҜи°“жҳҜвҖңе№ҝеӨ§жӮүеӨҮпјҢеҢ…дёҠдёӢиҖҢеј—йҒ—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еңЈдәәйҖҡиҝҮвҖңд»°и§ӮдҝҜеҜҹвҖқеҲӣдҪң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пјҢе…¶зӣ®зҡ„е°ұжҳҜи®©дәәд»¬ж ‘з«ӢеҸҳеҢ–гҖҒеҸҳйҖҡзҡ„дё–з•Ңи§ӮпјҢиғҪи®ӨиҜҶдё–з•ҢеҸ‘еұ•еҸҳеҢ–зҡ„规еҫӢиҖҢжңүжүҖдҪңдёәгҖӮжҳ“йҒ“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жқҘиҜҙжҳҜвҖңеҸҳеҠЁдёҚеұ…вҖқзҡ„пјҢеӣ жӯӨеҸӘжңүйҒөеҫӘвҖ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вҖқзҡ„еҹәжң¬еҺҹеҲҷпјҢдәә们жүҚжңүжңәдјҡиҫҫиҮҙвҖңж— е№ҪдёҚйҖҡвҖқзҡ„еўғз•Ң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Һ°еӯҳзҡ„ж¶үгҖҠжҳ“гҖӢж–ҮзҢ®дёӯпјҢеҜ№вҖ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вҖқеҺҹеҲҷзҡ„жҺўи®ЁжҳҜж•°и§ҒдёҚйІңзҡ„гҖӮеҰӮеңЁгҖҠеӨ©йҒ“зӣҠи°ҰиөӢ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жҖ»з»“иҜҙпјҡвҖңзӣӣиЎ°д№Ӣеә”д№ҹпјҢжғҹеҸҳжүҖйҖӮвҖқпјӣиҖҢеңЁгҖҠй“ёеү‘дёәеҶңеҷЁиөӢгҖӢдёӯпјҢд»–еҸҲжҸҗеҮәпјҡвҖңйңІйў–иҖ…жғҹеҸҳжүҖйҖӮпјҢйҰҖеҲғиҖ…еӨҚеҪ’дәҺж— гҖӮвҖқеңЁжҺЁеҙҮ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вҖңе”ҜеҸҳжүҖйҖӮвҖқеҹәжң¬еҺҹеҲҷ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ҝҳеҲӣйҖ жҖ§ең°е°Ҷ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д№ӢйҒ“пјҢз”ұдәӢзү©еҸ‘еұ•зҡ„е®ўи§Ӯ规еҫӢиҜ йҮҠжҲҗдё“й—Ёй’ҲеҜ№ж”ҝжІ»гҖҒзӨҫдјҡж”№йқ©зҡ„жҢҮеҜјжҖқжғігҖӮиҝҷж—ўжҳҜиҢғд»Іж·№жҳ“еӯҰзҡ„еҲӣж–°д№ӢеӨ„пјҢд№ҹжҳҜе…¶зҺ°еӯҳж–ҮзҢ®дёӯи®Ёи®әжңҖеӨҡзҡ„и®®йўҳд№ӢдёҖгҖӮеҰӮж—©еңЁеӨ©еңЈдёүе№ҙпјҲ1025е№ҙпјүеӣӣжңҲеҶҷз»ҷзҡҮеӨӘеҗҺеҲҳж°ҸдёҺе®Ӣд»Ғе®—зҡ„гҖҠеҘҸдёҠж—¶еҠЎд№Ұ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дҫҝдҫқжүҳ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д№ӢйҒ“пјҢиҜ•еӣҫеҠқи°Ҹз»ҹжІ»иҖ…еҸ‘иө·вҖңж–ҮйЈҺж”№йқ©вҖқиҝҗеҠЁпјҡиҮЈй—»еӣҪд№Ӣж–Үз« пјҢеә”дәҺйЈҺеҢ–гҖӮйЈҺеҢ–еҺҡи–„пјҢи§Ғд№Һж–Үз« гҖӮжҳҜж•…и§ӮиҷһгҖҒеӨҸд№Ӣд№ҰпјҢи¶ід»ҘжҳҺеёқзҺӢд№ӢйҒ“пјӣи§ҲеҚ—жңқд№Ӣж–ҮпјҢи¶ід»ҘзҹҘиЎ°йқЎд№ӢеҢ–гҖӮж•…еңЈдәәд№ӢзҗҶеӨ©дёӢд№ҹпјҢж–ҮејҠеҲҷж•‘д№Ӣд»ҘиҙЁпјҢиҙЁејҠеҲҷж•‘д№Ӣд»Ҙж–ҮвҖҰвҖҰжғҹеңЈеёқжҳҺзҺӢпјҢж–ҮиҙЁзӣёж•‘пјҢеңЁд№Һе·ұпјҢдёҚеңЁд№ҺдәәгҖӮгҖҠжҳ“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з©·еҲҷеҸҳпјҢеҸҳеҲҷйҖҡпјҢйҖҡеҲҷд№…гҖӮвҖқдәҰжӯӨд№Ӣи°“д№ҹгҖӮдјҸжңӣеңЈж…ҲпјҢдёҺеӨ§иҮЈи®®ж–Үз« д№ӢйҒ“пјҢеёҲиҷһгҖҒеӨҸд№ӢйЈҺгҖӮеҶөжҲ‘еңЈжңқеҚғиҪҪиҖҢдјҡпјҢжғңд№ҺдёҚиҝҪдёүд»Јд№Ӣй«ҳпјҢиҖҢе°ҡе…ӯжңқд№Ӣз»ҶвҖҰвҖҰеҸҜж•Ұи°•иҜҚиҮЈпјҢе…ҙеӨҚеҸӨйҒ“пјҢжӣҙ延еҚҡйӣ…д№ӢеЈ«пјҢеёғдәҺеҸ°йҳҒпјҢд»Ҙж•‘ж–Ҝж–Үд№Ӣи–„пјҢиҖҢеҺҡе…¶йЈҺеҢ–д№ҹпјҢеӨ©дёӢе№ёз”ҡпјҒ иҢғд»Іж·№жҢҮеҮәпјҢжҜҸдёҖж—¶д»Јд№Ӣж–ҮйЈҺзҡҶдёҺжӯӨдёҖж—¶д»Јд№Ӣдё–йЈҺзӣёе‘јеә”пјҢеӣ иҖҢжҜҸдёҖж—¶д»Јд№Ӣдё–йЈҺжҳҜж•ҰеҺҡиҝҳжҳҜжөҮи–„пјҢдҫҝдјҡз«ӢеҚідҪ“зҺ°еңЁж–ҮйЈҺдёҠгҖӮиҝҷж ·пјҢйҳ…иҜ»иҷһгҖҒеӨҸдёӨд»Јд№Ӣд№ҰпјҢдҫҝи¶ід»ҘжҳҺжӮүеңЈеёқжҳҺзҺӢзҡ„жІ»еӣҪзҗҶж”ҝд№ӢйҒ“пјӣиҖҢи§Ӯи§ҲеҚ—жңқе®ӢгҖҒйҪҗгҖҒжўҒгҖҒйҷҲд№Ӣж–Үз« пјҢдәҰи¶ід»ҘзҹҘжҷ“иЎ°иҙҘж·«йқЎд№ӢйЈҺзҡ„еҚұе®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ЈдәәжІ»зҗҶеӨ©дёӢпјҢеҫҖеҫҖеҚҒеҲҶжіЁйҮҚеҜ№ж–ҮйЈҺзҡ„规и®ӯдёҺеј•еҜјпјҢж–ҮйҮҮиҝҮеәҰеҲҷд»Ҙжңҙе®һж•‘д№ӢпјҢжңҙе®һиҝҮеәҰеҲҷд»Ҙж–ҮйҮҮж•‘д№ӢгҖӮеңЁвҖңж–ҮејҠвҖқжҲ–вҖңиҙЁејҠвҖқдә§з”ҹд№Ӣж—¶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д»ҘеңЈеёқжҳҺзҺӢдёәе…ёиҢғпјҢеҸҠж—¶ең°йҮҮеҸ–вҖңж–ҮиҙЁзӣёж•‘вҖқзҡ„еҠһжі•иҝӣиЎҢиЎҘж•‘дёҺи°ғж•ҙпјҢд»»з”ұе…¶дёҚж–ӯеҸ‘еұ•дёӢеҺ»пјҢе°ұдјҡеӣ ж–ҮйЈҺд№ӢвҖңејҠвҖқеј•еҸ‘дё–йЈҺд№ӢвҖңејҠвҖқпјҢжңҖз»Ҳз§ҜйҮҚйҡҫиҝ”гҖҒйҡҫд»ҘиҮӘж•‘пјҢд»ҘиҮҙеӨ©дёӢеӨ§д№ұгҖҒе…өзҘёз»ө延гҖӮеҢ—е®Ӣе»әз«Ӣд№ӢеҗҺпјҢеӣҪ家йҮҚеҪ’дёҖз»ҹгҖӮдҪҶиҮӘзңҹе®—жңқејҖе§ӢпјҢз”ұжқЁдәҝжүҖеј•йўҶзҡ„вҖңиҘҝжҳҶдҪ“вҖқзӣӣиЎҢеӨ©дёӢпјҢеЈ«еӨ§еӨ«зә·зә·д»ҘвҖңе…ӯжңқд№Ӣз»ҶвҖқдёәе°ҡпјҢвҖңдё“дәӢи—»йҘ°пјҢз ҙзўҺеӨ§йӣ…вҖқпјҢиҜҡеҸҜи°“жҳҜвҖңж–ҮејҠвҖқз”ҡзҹЈ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з»ҷз»ҹжІ»иҖ…зҡ„дёҠд№Ұдёӯзү№ж„ҸжҸҙеј•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д№ӢйҒ“дҪңдёәзҗҶи®әж №жҚ®пјҢе‘јеҗҒжңқе»·еә”еҪ“еңЁвҖңж–ҮејҠвҖқжңӘиҮідёҚеҸҜж•‘иҚҜд№ӢеүҚиө¶зҙ§иҝӣиЎҢвҖңж–ҮйЈҺж”№йқ©вҖқпјҢеј•еҜјеЈ«еӨ§еӨ«вҖңе…ҙеӨҚеҸӨйҒ“вҖқпјҢд»Һе°ҡвҖңе…ӯжңқд№Ӣз»ҶвҖқеҲ°еёҲвҖңиҷһгҖҒеӨҸд№ӢйЈҺвҖқпјҢиҝҷж ·жүҚжңүеҸҜиғҪж•‘вҖңж–Ҝж–Үд№Ӣи–„вҖқпјҢеҹ№жӨҚеҮәиҝҪиҝ№вҖңдёүд»ЈвҖқзҡ„ж•ҰеҺҡдё–йЈҺгҖӮеҪ“然пјҢйҡҸзқҖиҢғд»Іж·№еҜ№еҢ—е®Ӣж”ҝжІ»гҖҒзӨҫдјҡзҡ„и§ӮеҜҹдёҺжҖқиҖғдёҚж–ӯж·ұе…ҘпјҢд»–ж•Ҹй”җең°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иҰҒеҢ–и§ЈеҪ“ж—¶зҡ„зӨҫдјҡеӣ°еўғпјҢд»…д»…йҖҡиҝҮж”№йқ©ж–ҮйЈҺжҳҜиҝңиҝңдёҚеӨҹзҡ„пјҢиҖҢеә”иҜҘвҖңжҢҒеҸҳйҖҡд№Ӣж•°дәҺеӨ©дёӢвҖқпјҢж–№иғҪжҲҗе°ұвҖңеҪ“дё–д№ӢеҠЎвҖқ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йҖҗжёҗзЎ®дҝЎпјҢеҸӘжңүеҸ‘иө·е…Ёж–№дҪҚзҡ„ж”ҝжІ»ж”№йқ©иҝҗеҠЁпјҢжүҚеҸҜд»Ҙи®©еҢ—е®Ӣе®һзҺ°еҜҢеӣҪејәе…өзҡ„зӣ®ж ҮпјҢд»ҺиҖҢеҪ»еә•ж‘Ҷи„ұз§Ҝиҙ«з§Ҝејұзҡ„еҚұйҷ©еӨ„еўғгҖӮеҸҲеҰӮпјҢеңЁеӨ©еңЈдә”е№ҙеҶ’е“ҖдёҠе‘Ҳе®°жү§зҡ„гҖҠдёҠжү§ж”ҝд№Ұ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ҝғжҖҘеҰӮз„ҡең°иҜҙйҒ“пјҡжҹҗзӘғи§ҲеүҚд№ҰпјҢи§Ғе‘Ёжұүд№Ӣе…ҙпјҢеңЈиҙӨе…ұзҗҶпјҢдҪҝеӨ©дёӢдёәеҜҢдёәеҜҝж•°зҷҫе№ҙпјҢеҲҷеҪ“ж—¶иҮҙеҗӣиҖ…еҠҹеҸҜзҹҘзҹЈгҖӮе‘Ёжұүд№ӢиЎ°пјҢеҘёйӣ„з«һиө·пјҢдҪҝеӨ©дёӢдёәиЎҖдёәиӮүж•°зҷҫе№ҙпјҢеҲҷеҪ“ж—¶иҮҙеҗӣиҖ…зҪӘеҸҜзҹҘзҹЈгҖӮжқҺе”җд№Ӣе…ҙд№ҹпјҢеҰӮе‘Ёжұүз„үпјҢе…¶иЎ°д№ҹпјҢдәҰе‘Ёжұүз„үвҖҰвҖҰ然еҗҰжһҒиҖ…жі°пјҢжі°жһҒиҖ…еҗҰпјҢеӨ©дёӢд№ӢзҗҶеҰӮеҫӘзҺҜз„үгҖӮжғҹеңЈдәәи®ҫеҚҰи§ӮиұЎпјҢвҖңз©·еҲҷеҸҳпјҢеҸҳеҲҷйҖҡпјҢйҖҡеҲҷд№…вҖқгҖӮйқһзҹҘеҸҳиҖ…пјҢе…¶иғҪд№…д№ҺпјҹжӯӨеңЈдәәдҪңгҖҠжҳ“гҖӢд№ӢеӨ§ж—ЁпјҢд»ҘжҺҲдәҺзҗҶеӨ©дёӢиҖ…д№ҹпјҢеІӮеҫ’然е“үпјҹ жӯЈеҰӮе‘ЁгҖҒжұүгҖҒжқҺе”җжңүе…¶е…ҙдәҰжңүе…¶иЎ°дёҖж ·пјҢеӨ©дёӢдәӢзү©жҖ»жҳҜеҗҰжһҒиҖҢжі°гҖҒжі°жһҒеҸҲеҗҰпјҢе‘ҲзҺ°еҮәзӣӣиЎ°еҫӘзҺҜзҡ„规еҫӢ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еҜ№дәҺ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пјҢеңЈдәәж—©е°ұйҖҡиҝҮи§ЈгҖҠжҳ“гҖӢ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гҖӮ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е…ій”®еӨ„еңЁдәҺвҖңеҸҳвҖқпјҢеҸӘжңүдё»еҠЁжү“з ҙйҷҲ规пјҢеӣ еҠҝиҖҢеҠЁпјҢйЎәж—¶иҖҢвҖңеҸҳвҖқпјҢжүҚжңүеҸҜиғҪи·іеҮәзӣӣжһҒеҝ…иЎ°зҡ„вҖңеҺҶеҸІе‘ЁжңҹзҺҮвҖқпјҢиҝӣиҖҢжҲҗе°ұй•ҝд№…д№ӢдёҡгҖӮиӢҘдёҚзҹҘйЎәеә”е…¶вҖңеҸҳвҖқпјҢдҪҝеҫ—жңқж”ҝиө°еҗ‘иҙҘеқҸз©·жһҒпјҢеҸҲжҖҺиғҪе®һзҺ°й•ҝд№…дёҚиЎ°пјҹз”ұжҳҜ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и°ғйҒ“пјҢ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жҳҜеңЈдәәеңЁеҲӣдҪңгҖҒиҜ йҮҠ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дёәеңЁдёҠдҪҚиҖ…жҸҗдҫӣзҡ„жІ»зҗҶеӨ©дёӢзҡ„иҰҒж—ЁпјҢиҝҷеІӮдјҡжҳҜеҫ’з„¶ж— ж•Ҳзҡ„е‘ўпјҒ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йқ©йјҺдёӨеҚҰжҳҜдё“и®ІвҖңеҸҳйқ©вҖқзҡ„еҚҰгҖӮ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жқӮеҚҰ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гҖҠйқ©гҖӢпјҢеҺ»ж•…д№ҹпјӣгҖҠйјҺгҖӢпјҢеҸ–ж–°д№ҹгҖӮвҖқе°Өе…¶жҳҜгҖҠйқ©гҖӢд№ӢгҖҠеҪ–гҖӢиҝҳж——еёңйІңжҳҺең°и®ҙжӯҢдәҶвҖңжұӨжӯҰйқ©е‘ҪвҖқгҖӮеӣ иҖҢеңЁгҖҠжҳ“д№ү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йҖҡиҝҮеҜ№йқ©йјҺдёӨеҚҰзҡ„иҜ йҮҠиҝӣдёҖжӯҘе……е®һе’Ңе®Ңе–„дәҶе…¶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гҖӮеҰӮеңЁ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йқ©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жҢҮеҮәпјҡгҖҠйқ©гҖӢпјҢзҒ«ж°ҙзӣёи–„пјҢеҸҳеңЁе…¶дёӯпјҢеңЈдәәиЎҢжқғйқ©жҳ“д№Ӣж—¶д№ҹвҖҰвҖҰеӨ©дёӢж— йҒ“пјҢеңЈдәәйқ©д№Ӣд»ҘеҸҚеёёд№ӢжқғгҖӮ然иҖҢеҸҚеёёд№ӢжқғпјҢеӨ©дёӢдҪ•з”ұиҖҢд»Һд№Ӣпјҹд»Ҙе…¶еҶ…ж–ҮжҳҺиҖҢеӨ–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д№ҹвҖҰвҖҰд»ҘжӯӨд№Ӣж–ҮжҳҺжҳ“еҪјд№ӢжҳҸд№ұпјҢд»ҘеӨ©дёӢд№Ӣ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жҳ“еӣӣжө·д№ӢжҖЁпјҢд»ҘиҮід»Ғжҳ“дёҚд»ҒпјҢд»ҘжңүйҒ“жҳ“ж— йҒ“пјҢжӯӨжүҖд»ҘеҸҚеёёиҖҢеӨ©дёӢеҗ¬зҹЈпјҢе…¶жұӨжӯҰд№ӢдҪңиҖ¶пјҒ йқ©еҚҰд·°пјҢзҰ»дёӢе…‘дёҠпјҢзҰ»дёәзҒ«пјҢе…‘дёәжіҪпјҢжіҪдёӢжңүзҒ«пјҢжҳҜжһҒеәҰеҸҚеёёд№ӢдәӢпјҢеҝ…дёҚеҸҜй•ҝд№…пјҢиҜҙжҳҺеҸҳйқ©е°ҶиҮіпјҢж•…иҖҢ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жӯӨеҚҰе–»зӨәвҖңеңЈдәәиЎҢжқғйқ©жҳ“д№Ӣж—¶вҖқгҖӮеҜ№дәҺдәәзұ»зӨҫдјҡжқҘиҜҙпјҢжһҒеәҰеҸҚеёёд№ӢдәӢиҺ«иҝҮдәҺвҖңеӨ©дёӢж— йҒ“вҖқпјҢеңЈдәәдәҺжӯӨж—¶дёҚдјҡжӢҳе®ҲжҲҗ规пјҢиҖҢжҳҜзҒөжҙ»ең°йЎәеә”ж—¶еҠҝеҸҳеҢ–еҸ‘иө·йқ©е‘Ҫ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дәә们ж„ҝж„Ҹи·ҹзқҖеңЈдәәиҝӣиЎҢйқ©е‘Ҫе‘ўпјҹиҢғд»Іж·№и§ЈйҮҠйҒ“пјҢйқ©еҚҰеҶ…зҰ»еӨ–е…‘пјҢзҰ»дёәдёҪпјҢиұЎеҫҒж–ҮжҳҺпјҢе…‘дёә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пјҢиЎЁзӨәе–ңжӮҰпјҢиҝҷиҜҙжҳҺеңЈдәәд№ғжҳҜеҮӯеҖҹе…¶еҶ…еңЁзҡ„зҫҺеҫ·иҖҢдҪҝдәәж°‘еҗ‘иҖҢеҫҖд№ӢпјҢж•…иҖҢж„ҝж„Ҹи·ҹйҡҸд»–иҝӣиЎҢйқ©е‘ҪгҖӮиҖҢеҜ№дәҺеңЈдәәиғҪйқ©е‘ҪжҲҗеҠҹзҡ„зјҳз”ұ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д№ҹдҪңдәҶз»ҶиҮҙзҡ„еҲҶжһҗпјҢжҖ»з»“дёәд»ҘвҖңж–ҮжҳҺвҖқйқ©е…¶вҖңжҳҸд№ұвҖқпјҢд»ҘвҖңеӨ©дёӢд№Ӣ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вҖқйқ©е…¶вҖңеӣӣжө·д№ӢжҖЁвҖқпјҢд»ҘвҖңиҮід»ҒвҖқйқ©е…¶вҖңдёҚд»ҒвҖқпјҢд»ҘвҖңжңүйҒ“вҖқйқ©е…¶вҖңж— йҒ“вҖқгҖӮдёҖиЁҖд»Ҙи”Ҫд№ӢпјҢд»ҘвҖңеҫ·ж”ҝвҖқйқ©е…¶вҖңжҡҙж”ҝвҖқпјҢж•…иғҪвҖңйЎәд№ҺеӨ©иҖҢеә”д№ҺдәәвҖқпјҢжҲҗе°ұдјҹдёҡпјҢеҸ–еҫ—жҲҗеҠҹ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и®әиҝ°пјҢж—ўжҢҮжҳҺдәҶжұӨгҖҒжӯҰеҸ‘еҠЁвҖңйқ©е‘ҪвҖқ并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дёҖе·ұз§ҒеҲ©иҖҢжҠўеӨәеӨ§е®қд№ӢдҪҚ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еҸҚеёёд№Ӣдё–дҝ®д»Ғеҫ·гҖҒиЎҢд»Ғж”ҝпјҢвҖңеӨ©дёӢеҪ’еҝғвҖқзҡ„иҮӘ然结жһңпјҢеҸҲйҳҗжҳҺдәҶеңЁеӨ©дёӢж— йҒ“гҖҒејҠж”ҝдёӣз”ҹ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ңЈдәәйўҶеҜјйқ©е‘Ҫд»ҘвҖңеҫ·ж”ҝвҖқжӣҙжӣҝвҖңжҡҙж”ҝвҖқзҡ„дёҫжҺӘжҳҜе®Ңе…ЁжӯЈеҪ“дёҺеҗҲжі•зҡ„гҖӮеҶҚзңӢ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йјҺгҖӢпјҡгҖҠйјҺгҖӢпјҢд»ҘжңЁйЎәзҒ«пјҢйјҺе§Ӣз”Ёз„үпјҢеңЈдәәејҖеҹәз«ӢеҷЁд№Ӣж—¶д№ҹгҖӮеӨ«еӨ©дёӢж— йҒ“пјҢеңЈдәәйқ©д№ӢгҖӮеӨ©дёӢж—ўйқ©иҖҢеҲ¶дҪңе…ҙпјҢеҲ¶дҪңе…ҙиҖҢз«ӢжҲҗеҷЁпјҢз«ӢжҲҗеҷЁиҖҢйјҺиҺ«е…Ҳз„үгҖӮж•…еҸ–йјҺдёәд№үпјҢиЎЁж—¶д№Ӣж–°д№ҹгҖӮжұӨжӯҰжӯЈдҪҚпјҢ然еҗҺж”№жӯЈжң”гҖҒеҸҳжңҚз« гҖҒжӣҙеҷЁз”ЁпјҢд»Ҙж–°еӨ©дёӢд№ӢеҠЎпјҢе…¶жӯӨд№Ӣж—¶ж¬Өпјҹж•…жӣ°вҖңйқ©еҺ»ж•…вҖқиҖҢвҖңйјҺеҸ–ж–°вҖқгҖӮеңЈдәәд№Ӣж–°пјҢдёәеӨ©дёӢд№ҹгҖӮ йјҺдҪңдёәзӨјеҷЁпјҢжҳҜиҮій«ҳжқғеҠӣ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еӣ жӯӨж–°й“ёйјҺеҷЁпјҢд№ғжҳҜж–°з”ҹж”ҝжқғе»әз«Ӣзҡ„е®ЈзӨә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жӯӨеҚҰе–»зӨәвҖңеңЈдәәејҖеҹәз«ӢеҷЁд№Ӣж—¶вҖқгҖӮйқ©еҚҰиЎЁзӨәеҸҳйқ©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йјҺеҚҰеҲҷиҜҙжҳҺеҸҳйқ©е·ІжҲҗпјҢж–°зҡ„жі•еәҰдёҺ秩еәҸйҷҶз»ӯе»әз«ӢпјҢеҚівҖңжұӨжӯҰжӯЈдҪҚпјҢ然еҗҺж”№жӯЈжң”гҖҒеҸҳжңҚз« гҖҒжӣҙеҷЁз”ЁпјҢд»Ҙж–°еӨ©дёӢд№ӢеҠЎвҖқ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зү№ж„Ҹејәи°ғвҖңеңЈдәәд№Ӣж–°пјҢдёәеӨ©дёӢд№ҹвҖқпјҢеңЈдәәйқ©ж—§еҲӣж–°зҡ„зӣ®зҡ„е§Ӣз»ҲжҳҜдёәдәҶеӨ©дёӢзҷҫ姓вҖ”вҖ”иҝҷж—ўжҳҜеңЈдәәеҸ‘еҠЁйқ©е‘Ҫзҡ„еҲқиЎ·пјҢд№ҹжҳҜе…¶йқ©е‘Ҫеҫ—д»ҘжҲҗеҠҹзҡ„ж №жң¬дҝқиҜҒгҖӮз»јеҗҲиҢғд»Іж·№еҜ№йқ©гҖҒйјҺдәҢеҚҰзҡ„иҜ йҮҠпјҢжҲ‘们еҸҜд»ҘжҖ»з»“еҮәеҰӮдёӢи§ӮзӮ№пјҡеңЁжңқж”ҝиө°еҗ‘з©·жһҒгҖҒеӨ©дёӢйҷ·е…Ҙж— йҒ“д№Ӣж—¶пјҢеҸӘжңүд»ҘиҮід»Ғд№ӢеҝғжҺЁиЎҢж”№йқ©жҲ–еҸ‘еҠЁйқ©е‘ҪпјҢжүҚиғҪи§ЈйҷӨеӣ°еўғпјҢйҮҚж–°иө°еҗ‘й•ҝд№…д№ӢжІ»гҖӮиҝҷж ·пјҢеҪ“иҢғд»Іж·№зҪ®иә«дәҺеҢ—е®Ӣд»Ғе®—жңқвҖңзәІзәӘеҲ¶еәҰпјҢж—ҘеүҠжңҲдҫөпјҢе®ҳеЈ…дәҺдёӢпјҢж°‘еӣ°дәҺеӨ–пјҢеӨ·зӢ„йӘ„зӣӣпјҢеҜҮзӣ—жЁӘзӮҪвҖқзҡ„еҶ…еҝ§еӨ–жӮЈд№ӢдёӯпјҢе…¶жүҖеҝөеҝөдёҚеҝҳзҡ„и§ЈеҶід№Ӣзӯ–дҫҝжҳҜйҖҡиҝҮж”№йқ©ејҠж”ҝжқҘйҮҚж–°е®һзҺ°й•ҝжІ»д№…е®үгҖӮеәҶеҺҶдёүе№ҙпјҲ1043е№ҙпјүд№қжңҲпјҢе®Ӣд»Ғе®—ејҖеӨ©з« йҳҒпјҢвҖңеҸ¬еҜ№иөҗеқҗвҖқ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з»ҲдәҺиҝҺжқҘдәҶе°ҶиҮӘиә«зҡ„ж”№йқ©зҗҶи®әд»ҳиҜёе®һи·өзҡ„жңәдјҡгҖӮеңЁвҖңеәҶеҺҶж–°ж”ҝвҖқзҡ„вҖңзәІйўҶжҖ§ж–Ү件вҖқгҖҠзӯ”жүӢиҜҸжқЎйҷҲеҚҒдәӢ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јҖзҜҮеҚіжҢҮеҮәпјҡиҮЈй—»еҺҶд»Јд№Ӣж”ҝпјҢд№…зҡҶжңүејҠгҖӮејҠиҖҢдёҚж•‘пјҢзҘёд№ұеҝ…з”ҹгҖӮдҪ•е“үпјҹзәІзәӘжөёйҡіпјҢеҲ¶еәҰж—ҘеүҠпјҢжҒ©иөҸдёҚиҠӮпјҢиөӢж•ӣж— еәҰпјҢдәәжғ…жғЁжҖЁпјҢеӨ©зҘёжҡҙиө·гҖӮжғҹе°§иҲңиғҪйҖҡе…¶еҸҳпјҢдҪҝж°‘дёҚеҖҰгҖӮгҖҠжҳ“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з©·еҲҷеҸҳпјҢеҸҳеҲҷйҖҡпјҢйҖҡеҲҷд№…гҖӮвҖқжӯӨиЁҖеӨ©дёӢд№ӢзҗҶжңүжүҖз©·еЎһпјҢеҲҷжҖқеҸҳйҖҡд№ӢйҒ“гҖӮж—ўиғҪеҸҳйҖҡпјҢеҲҷжҲҗй•ҝд№…д№ӢдёҡгҖӮ 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д»»дҪ•жңқд»ЈпјҢеҪ“е…¶ж”ҝд»ӨеҲ¶еәҰжІҝиўӯж—Ҙд№…ж—¶пјҢеҝ…然дјҡеӣ дёҚйҖӮеә”ж—¶д»Јзҡ„еҸ‘еұ•иҖҢйҖҗжёҗз”ҹеҮәејҠз«ҜгҖӮејҠз«Ҝж—Ҙз§ҜжңҲзҙҜпјҢе°ұдјҡйҖ жҲҗвҖңдәәжғ…жғЁжҖЁпјҢеӨ©зҘёжҡҙиө·вҖқзҡ„еҚұйҷ©еҗҺжһ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з»ҹжІ»иҖ…еә”иҜҘиҰҒеғҸе°§иҲңдёҖж ·е–„дәҺж”№йқ©йҷҲж—§зҡ„еҷЁз”ЁеҲ¶еәҰпјҢжүҚиғҪдҪҝзҷҫ姓иҝӣеҸ–дёҚжҮҲгҖӮжҺҘзқҖ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зӣҙеј•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д№ӢйҒ“жқҘиҜҙжҳҺеҮЎдәӢз©·еЎһе°ұеҝ…然йңҖиҰҒеҸҳйқ©гҖҒеҸӘжңүеҸҳйқ©жүҚиғҪйҖҡз•…й•ҝд№…зҡ„йҒ“зҗҶпјҢдёәвҖңеәҶеҺҶж–°ж”ҝвҖқзҡ„еҝ…иҰҒжҖ§е’Ңзҙ§иҝ«жҖ§жҸҗдҫӣдәҶе……еҲҶзҡ„зҗҶи®әдҫқжҚ®гҖӮжҚ®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ҡ„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д№ӢйҒ“е§Ӣз»ҲжҳҜ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еҸҠе…¶ж”№йқ©е®һи·өзҡ„ж №жҹўдёҺзҒөйӯӮгҖӮдёүгҖҒ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 иҢғд»Іж·№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еӣ е…¶гҖҠеІійҳіжҘји®°гҖӢдёӯвҖңе…ҲеӨ©дёӢд№Ӣеҝ§иҖҢеҝ§пјҢеҗҺеӨ©дёӢд№Ӣд№җиҖҢд№җвҖқзҡ„еҗҚиЁҖиҖҢеҰҮеӯәзҡҶзҹҘ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ж—©еңЁе…Ҳз§Ұж—¶жңҹпјҢ儒家еӯҰиҖ…дҫҝе·Із»ҸеҜ№вҖңеҝ§д№җвҖқй—®йўҳжңүжүҖи®әиҝ°гҖӮеҰӮеӯ”еӯҗжӣҫж„ҹеҸ№пјҡвҖңиҙӨе“үпјҢеӣһд№ҹпјҒдёҖз®ӘйЈҹпјҢдёҖз“ўйҘ®пјҢеңЁйҷӢе··пјҢдәәдёҚе Әе…¶еҝ§пјҢеӣһд№ҹдёҚж”№е…¶д№җгҖӮиҙӨе“үпјҢеӣһд№ҹпјҒвҖқи®©вҖңеҝ§д№җвҖқдёҚеҸӘжҳҜдҪңдёәдёҖз§Қжғ…ж„ҹиҖҢ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дёҺйҒ“еҫ·дҝ®е…»дә§з”ҹдәҶзҙ§еҜҶ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еӯҹеӯҗеңЁеӯ”еӯҗ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иҝӣдёҖжӯҘж·ұеҢ–дёҺеҸ‘еұ•дәҶвҖңеҝ§д№җвҖқжҖқжғіпјҢеҰӮе…¶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д№җж°‘д№Ӣд№җиҖ…пјҢж°‘дәҰд№җе…¶д№җпјӣеҝ§ж°‘д№Ӣеҝ§иҖ…пјҢж°‘дәҰеҝ§е…¶еҝ§гҖӮд№җд»ҘеӨ©дёӢпјҢеҝ§д»ҘеӨ©дёӢпјҢ然иҖҢдёҚзҺӢиҖ…пјҢжңӘд№Ӣжңүд№ҹгҖӮвҖқе°ҶдёҺеӨ©дёӢзҷҫ姓еҗҢвҖңеҝ§д№җвҖқзЎ®з«Ӣдёәз»ҹжІ»иҖ…вҖңзҺӢеӨ©дёӢвҖқзҡ„еҝ…еӨҮжқЎд»¶пјҢдҪ“зҺ°еҮәйІңжҳҺзҡ„еӨ©дёӢжғ…жҖҖдёҺвҖңдёәж°‘вҖқеҖҫеҗ‘гҖӮйҷӨжӯӨд№ӢеӨ–пјҢеӯҹеӯҗиҝҳ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з”ҹдәҺеҝ§жӮЈиҖҢжӯ»дәҺе®үд№җвҖқзӯүйҮҚиҰҒе‘ҪйўҳпјҢдёәвҖңеҝ§д№җвҖқжҖқжғіжіЁе…ҘдәҶеҝ§жӮЈж„ҸиҜҶзҡ„йІңжҙ»е…ғзҙ 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пјҢжӯЈжҳҜеңЁеҲӣйҖ жҖ§ең°з»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е…Ҳз§Ұ儒家е°Өе…¶жҳҜеӯҹеӯҗзӣёе…іи§ӮзӮ№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еҪўжҲҗзҡ„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ж—ўд»Ҙ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дёәе®—ж—ЁпјҢиҝҷдҫҝж„Ҹе‘ізқҖеңЁе…¶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дёӯвҖңеҝ§вҖқзӣёеҜ№дәҺвҖңд№җвҖқжқҘиҜҙжӣҙе…·дјҳдҪҚжҖ§пјҢвҖңеҝ§вҖқжүҖжүҝиҪҪзҡ„ж„Ҹд№үд№ҹжӣҙдёәж·ұжІү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дёӯзҡ„вҖңеҝ§вҖқпјҢйҰ–е…ҲжҳҜеҝ§еӣҪеҝ§ж°‘д№ӢвҖңеҝ§вҖқпјҢиЎЁзҺ°еҮә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зғҲзҡ„家еӣҪжғ…жҖҖ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°‘жҖҖеӨ§иҠӮпјҢвҖңдәҺеҜҢиҙөгҖҒиҙ«иҙұгҖҒжҜҒиӘүгҖҒж¬ўжҲҡпјҢдёҚдёҖеҠЁе…¶еҝғпјҢиҖҢ慨然жңүеҝ—дәҺеӨ©дёӢвҖқгҖӮиҝҷд»ҪејәзғҲзҡ„вҖңд»ҘеӨ©дёӢдёәе·ұд»»вҖқзҡ„家еӣҪжғ…жҖҖпјҢи®©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иә«еұ…е·һеҺҝе°Ҹе®ҳж—¶еҚідёҚйЎҫе®үеҚұиҚЈиҫұпјҢеұЎеұЎеҗ‘еҪ“жқғиҖ…дёҠд№ҰзӣҙйҷҲжңқж”ҝеҫ—еӨұпјҢд»ҘжұӮж”№йқ©ејҠж”ҝпјҢе®һзҺ°еҜҢеӣҪејәе…өзҡ„зӣ®ж ҮгҖӮеҰӮеңЁгҖҠеҘҸдёҠж—¶еҠЎдёӯ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зӣҙиЁҖд№ӢеЈ«пјҢеҚғеҸӨи°“д№Ӣеҝ пјӣе·§иЁҖд№ӢдәәпјҢеҚғеҸӨи°“д№ӢдҪһгҖӮд»ҠиҮЈеӢүжҖқиҚҜзҹіпјҢеҲҮзҠҜйӣ·йңҶпјҢдёҚйҒөжҳ“иҝӣд№ӢйҖ”пјҢиҖҢеұ…йҡҫз«Ӣд№Ӣең°иҖ…пјҢж¬ІеҖҫиҮЈиҠӮпјҢд»ҘжҠҘеӣҪжҒ©гҖӮвҖқеңЁгҖҠдёҠжү§ж”ҝд№Ұ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ҸҲеқҰиЁҖпјҡвҖңзӣ–й—»еҝ еӯқиҖ…пјҢеӨ©дёӢд№ӢеӨ§жң¬д№ҹвҖҰвҖҰжӯӨжүҖд»ҘеҶ’е“ҖдёҠд№ҰпјҢиЁҖеӣҪ家дәӢпјҢдёҚд»ҘдёҖеҝғд№ӢжҲҡпјҢиҖҢеҝҳеӨ©дёӢд№Ӣеҝ§пјҢеә¶д№Һеӣӣжө·з”ҹзҒөй•ҝи§ҒеӨӘе№ігҖӮвҖқе…Ҙдә¬иә«еұ…и°Ҹд»»д№ӢеҗҺ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жӣҙжҳҜвҖңи° иЁҖзӣҙиҠӮпјҢеҘӢдёҚйЎҫе·ұвҖқпјҢйҒӯйҖўдёүй»ңпјҢдәҰжҜ«дёҚз•Ҹзј©гҖӮеҰӮе…¶иҗҪиҒҢйҘ¶е·һеҲҷиЎЁзӨәпјҡвҖңжҷәиҖ…еҚғиҷ‘иҖҢжңүеӨұпјҢж„ҡиҮЈдёҖеҝғиҖҢеІӮе‘ЁвҖҰвҖҰ然иҖҢжңүзҠҜж— йҡҗпјҢжғҹдёҠеҲҷзҹҘпјӣи®ёеӣҪеҝҳ家пјҢдәҰиҮЈиҮӘдҝЎгҖӮвҖқиҪ¬д»»ж¶Ұе·һеҸҲиҮӘйҷҲеҝғеҝ—дә‘пјҡвҖңеҫ’з«ӯиҜҡиҖҢжҠҘеӣҪпјҢеј—й’іеҸЈд»Ҙе®үиә«гҖӮвҖқеңЁз»ҷеҸӢдәәзҡ„дҝЎ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дәҰиҜҙпјҡжҹҗеҝөе…Ҙжңқд»ҘжқҘпјҢжҖқжҠҘдәәдё»пјҢиЁҖдәӢеӨӘжҖҘпјҢиҙ¬ж”ҫйқһдёҖгҖӮ然д»Ҷи§ӮгҖҠеӨ§иҝҮгҖӢд№ӢиұЎпјҢжӮЈе®Ҳеёёз»ҸгҖӮд№қеӣӣд»ҘйҳіеӨ„йҳҙпјҢи¶ҠдҪҚж•‘ж—¶пјҢеҲҷзҺӢе®Өжңүж ӢйҡҶд№ӢеҗүгҖӮд№қдёүд»ҘйҳіеӨ„йҳіпјҢеӣәдҪҚе®үж—¶пјҢеҲҷеӨ©дёӢжңүж ӢжҢ д№ӢеҮ¶гҖӮйқһеҰӮиү®жӯўд№Ӣж—¶пјҢжҖқдёҚеҮәдҪҚиҖ…д№ҹгҖӮ еӨ§иҝҮеҚҰд·ӣпјҢдёӢе·ҪдёҠе…‘пјҢеҚҰдёӯеӣӣйҳіиҝҮејәпјҢдәҢйҳҙиҝҮејұпјҢд№ғвҖңеӨ§дёәиҝҮз”ҡвҖқд№ӢиұЎгҖӮжӯӨж—¶йЎ»йҳҙйҳідә’жөҺпјҢжүҚиғҪдҝқжҢҒе№іиЎЎдёҺе’Ңи°җпјҢдёҮдёҚеҸҜеҗ„иҮӘеӣәе®ҲвҖңеёёз»ҸвҖқгҖӮеҰӮеӨ§иҝҮеҚҰд№қеӣӣд»ҘйҳіеӨ„йҳҙпјҢд»ҘеҲҡжөҺжҹ”пјҢж•…е…¶зҲ»иҫһжӣ°вҖңж ӢйҡҶпјҢеҗүвҖқпј»8пјҪ84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жҢҮеҮәпјҢиҝҷжҳҜеӣ дёәд№қеӣӣж•ўдәҺзӘҒз ҙ常规гҖҒвҖңи¶ҠдҪҚж•‘ж—¶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зҺӢе®ӨжүҚжңүвҖңж ӢйҡҶд№ӢеҗүвҖқгҖӮиҖҢеӨ§иҝҮеҚҰд№қдёүжң¬еңЁдёӢеҚҰд№ӢжһҒпјҢеҸҲд»Ҙйҳіеұ…йҳіпјҢеҲҡдәўиҝҮз”ҡпјҢж•…е…¶зҲ»иҫһдә‘вҖңж ӢжЎЎпјҢеҮ¶вҖқ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пјҢиҝҷжҳҜеӣ дёәд№қдёүвҖңеӣәдҪҚе®үж—¶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еӨ©дёӢжүҚжңүвҖңж ӢжҢ д№ӢеҮ¶вҖқ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и°ғйҒ“пјҢеңЁжңқж”ҝжңүеӨұзҡ„вҖңеӨ§иҝҮвҖқд№Ӣж—¶пјҢдҪңдёәе„’еЈ«еә”еҪ“еҝғеҝ§еӨ©дёӢпјҢз§ҜжһҒвҖңи¶ҠдҪҚж•‘ж—¶вҖқпјҢиҖҢдёҚиғҪеғҸиү®жӯўд№Ӣж—¶дёҖж ·пјҢеҸӘжҳҜжІүй»ҳдёҚиҜӯгҖҒе®үе®Ҳжң¬дҪҚиҖҢе·І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з§ҚиөӨиҜҡжҠҘеӣҪгҖҒдёҚжғңвҖңи¶ҠдҪҚж•‘ж—¶вҖқзҡ„家еӣҪжғ…жҖҖзҡ„ж”Ҝж’‘дёӢ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д№ӢеҗҺиҘҝе®Ҳиҫ№йҷІеҲҷеҮ»йҖҖејәж•ҢгҖҒе®ҡеҖҫжү¶еҚұпјҢи·»иә«жү§ж”ҝеҲҷжҖқеӣәеӣҪжң¬гҖҒжҺЁиЎҢж–°ж”ҝпјҢзӣҙиҮідёҙз»Ҳд№Ӣж—¶пјҢд»ҚеҝөеҝөдёҚеҝҳвҖңд»Ҙз«ӯйҒ—еҝ вҖқ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дёӯзҡ„вҖңеҝ§вҖқ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жҳҜвҖңз”ҹдәҺеҝ§жӮЈвҖқд№ӢвҖңеҝ§вҖқпјҢеҸҚжҳ еҮәиҢғд»Іж·№ж·ұжІүзҡ„еҝ§жӮЈж„ҸиҜҶгҖӮеҰӮгҖҠжҳ“д№ү·家дәәгҖӢдә‘пјҡвҖңеңЈдәәе°ҶжҲҗе…¶еӣҪпјҢеҝ…жӯЈе…¶е®¶гҖӮдёҖдәәд№Ӣ家жӯЈпјҢ然еҗҺеӨ©дёӢд№Ӣ家жӯЈгҖӮеӨ©дёӢд№Ӣ家жӯЈпјҢ然еҗҺеӯқжӮҢеӨ§е…ҙз„үвҖҰвҖҰ然еҲҷжӯЈе®¶иҖ…пјҢиҙөй—Іе…¶еҲқд№ҹгҖӮвҖқ家дәәеҚҰд·ӨпјҢдё»иҰҒйҳҗеҸ‘вҖң治家вҖқд№ӢйҒ“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ҲӣйҖ жҖ§ең°е°ҶвҖңжӯЈе®¶вҖқдёҺвҖңеӯқжӮҢеӨ§е…ҙпјҲдҝ®иә«пјүвҖқвҖңжҲҗеӣҪвҖқвҖңеӨ©дёӢвҖқиҝһйҖҡиө·жқҘпјҢдҪҝе…¶дёҺгҖҠеӨ§еӯҰгҖӢдҝ®иә«гҖҒйҪҗ家гҖҒжІ»еӣҪгҖҒе№іеӨ©дёӢзҡ„вҖңеҶ…еңЈеӨ–зҺӢвҖқд№ӢйҒ“зӣёеҘ‘ж— й—ҙ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еңЁе…·дҪ“и°ҲеҲ°вҖңжӯЈе®¶вҖқзҡ„жҺӘж–Ҫж—¶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зү№еҲ«ејәи°ғвҖңиҙөй—Іе…¶еҲқд№ҹвҖқгҖӮвҖңй—ІвҖқпјҢйҳІй—Ід№ҹгҖӮиҝҷжҳҜиҜҙеҲқд№қжҳҜ家дәәеҚҰд№Ӣе§ӢпјҢдәҰеҚівҖң治家вҖқд№Ӣе§ӢпјҢжӯӨж—¶жңҖеә”иҜҘйҳІжҒ¶дәҺеҲқпјҢдәҰеҚівҖңйҳІжҒ¶дәҺжңӘиҗҢвҖқгҖӮеңЁ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йҒҜ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ҸҲйҳҗиҝ°йҒ“пјҡвҖңйҳҙиҝӣйҳійҖҖпјҢдәҢйҳҙиҝӣд№ӢдәҺеҶ…пјҢеӣӣйҳійҖҖд№ӢдәҺеӨ–гҖӮжҹ”дҪһе…ҘиҖҢеҲҡжӯЈеҮәпјҢеҗӣеӯҗйҒҜеҺ»д№Ӣж—¶д№ҹвҖҰвҖҰеҗӣеӯҗзҹҘеҗүд№Ӣе…ҲпјҢиҫЁзҘёд№ӢиҗҢпјҢжҖқиҝңе…¶ж—¶д№ҹпјҢеҸҜдёҚйҒҜд№Һпјҹж•…гҖҠйҒҜгҖӢд№Ӣдёәд№үе°ҡд№Һиҝңд№ҹгҖӮжҳҜд»ҘжңҖеңЁеҶ…иҖ…пјҢжңүвҖҳйҒҜе°ҫвҖҷд№ӢеҚұпјӣжңҖеңЁеӨ–иҖ…пјҢжңүиӮҘйҒҜд№ӢеҲ©гҖӮвҖқйҒҜеҚҰд· пјҢд»ҺеҚҰиұЎдёҠзңӢпјҢжҳҜдәҢйҳҙиҝӣд№ӢдәҺеҶ…пјҲеҶ…еҚҰпјүпјҢиҖҢеӣӣйҳійҖҖд№ӢдәҺеӨ–пјҲеӨ–еҚҰпјүпјҢжңүвҖңжҹ”дҪһе…ҘиҖҢеҲҡжӯЈеҮәвҖқзҡ„ж„Ҹе‘іпјҢж•…иҖҢ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жӯӨеҚҰжүҖиұЎеҫҒзҡ„жҳҜвҖңеҗӣеӯҗйҒҜеҺ»д№Ӣж—¶вҖқгҖӮ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жғ…еўғдёӢпјҢеҗӣеӯҗиҰҒж—¶еҲ»дҝқжҢҒй«ҳеәҰиӯҰжғ•пјҢдәҺзҒҫзҘёиҗҢз”ҹд№ӢеҲқдҫҝйЎ»з«ӢеҚіиҫЁеҜҹпјҢеҸҠж—¶йҡҗеҢҝиҖҢеҺ»пјҢж–№иғҪйҒҝзҘёеҫ—еҗү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йҒҜеҚҰд»Ҙеә”ж—¶иҝңйҒҒдёәе°ҡ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йҒҜеҚҰд№ӢеҲқе…ӯеұ…дәҺжңҖеҶ…пјҢеңЁзҘёд№ұеҸ‘з”ҹж—¶жқҘдёҚеҸҠйҒҒеҺ»пјҢе…¶зҲ»иҫһйҒӮиӯҰиҜ«жңүвҖңйҒҜе°ҫвҖқд№ӢеҚұпјӣиҖҢйҒҜеҚҰд№ӢдёҠд№қй«ҳзҝ”иҝңеј•пјҢе…Ёиә«иҖҢйҖҖпјҢе…¶зҲ»иҫһеҲҷеӨ§иЁҖжңүвҖңиӮҘйҒҜвҖқд№ӢеҲ©гҖӮиҝҷйҮҢжүҖеҸҚжҳ зҡ„жҳҜдёҖз§ҚдёҚдёҺеҘёдҪһдёәдјҚгҖҒжҳҺе“Ідҝқиә«зҡ„жҖқжғі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еңЁиҜ и§ЈйңҮеҚҰж—¶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ҝҳ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гҖҠйңҮгҖӢпјҢйӣ·зӣёд»ҺиҖҢе…ҙпјҢеЁҒеҠЁдёҮзү©пјҢеҶ…еӨ–зҡҶйңҮпјҢеҗӣеӯҗеҝғиә«жҲ’жғ§д№Ӣж—¶д№ҹгҖӮдёҮзү©йңҮпјҢе…¶йҒ“йҖҡз„үпјӣеҗӣеӯҗйңҮпјҢе…¶еҫ·еҙҮз„үгҖӮеҗӣеӯҗд№Ӣжғ§дәҺеҝғд№ҹпјҢжҖқиҷ‘еҝ…ж…Һе…¶е§ӢпјҢеҲҷзҷҫеҝ—еј—иҝқдәҺйҒ“пјӣжғ§дәҺиә«д№ҹпјҢиҝӣйҖҖдёҚеұҘдәҺиҝқпјҢеҲҷзҷҫиЎҢеј—зҪ№дәҺзҘёгҖӮвҖқйңҮеҚҰд·ІпјҢдёҠдёӢеҚҰзҡҶдёәйңҮпјҢжңүвҖңеӨ©йӣ·ж»ҡж»ҡвҖқд№ӢиұЎпјҢж•…иҢғд»Іж·№и®ӨдёәжӯӨеҚҰвҖңеЁҒеҠЁдёҮзү©вҖқпјҢжүҖе–»зӨәзҡ„жҳҜвҖңеҗӣеӯҗеҝғиә«жҲ’жғ§д№Ӣж—¶вҖқзҡ„жғ…еўғгҖӮиҝ…йӣ·йңҮж…‘дёҮзү©пјҢдҪҝд№ӢиӯҰжғ§иҖҢдёҚж•ўеҰ„иЎҢпјҢдёҮзү©еӣ иҖҢеҫ—е…¶дәЁйҖҡпјӣеҗӣеӯҗиӢҘжғ¶жҒҗйңҮжғ§пјҢеҝ…дёҚж•ўиғЎдҪңйқһдёәпјҢж•…е…¶йҒ“еҫ·е“ҒиҙЁд№ҹдјҡеӣ жӯӨиҖҢж—ҘиҮ»е®ҢзҫҺгҖӮз”ұжӯӨ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јәи°ғпјҢеҰӮжһңеҗӣеӯҗиә«еҝғеҶ…еӨ–иғҪж—¶ж—¶дҝқжҢҒжҒҗжғ§дҝ®зңҒзҡ„зҠ¶жҖҒпјҢйӮЈд№Ҳд»–иҮӘ然е°ұдјҡе…»жҲҗж…Һе§Ӣжғ§еҲқгҖҒйҒөиЎҢжі•еәҰзҡ„дјҳиүҜе“ҒжҖ§пјҢиҝҷж ·д»–зҡ„жҖқжғіеҝғеҝ—дҫҝдёҚдјҡиҝқиғҢжӯЈйҒ“пјҢд»–зҡ„иЁҖиЎҢдёҫжӯўд№ҹдёҚдјҡжӢӣжқҘзҘёжӮЈгҖӮеңЁиҢғд»Іж·№зңӢжқҘпјҢдәәд»¬ж— и®әиә«еӨ„дҪ•з§Қжғ…еўғпјҢеҸӘжңүеёёжҖҖеҝ§жӮЈд№ӢеҝғгҖҒжҖқиҷ‘еҝ…ж…Һе…¶е§ӢпјҢжүҚиғҪеҒҡеҲ°еә”ж—¶иҖҢеҠЁпјҢе®ҢжҲҗвҖңжӯЈе…¶е®¶вҖқвҖңжҲҗе…¶еӣҪвҖқзӣҙиҮівҖңеӨ©дёӢе®ҡвҖқзҡ„е„’иҖ…дәӢдёҡ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ңЁгҖҠдёҺд№қеӣҪеҚҡгҖӢдёҖдҝЎ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‘ҠиҜ«иҜҙпјҡвҖңгҖҠжҳ“гҖӢжүҖи°“вҖҳеҝ§жӮ”еҗқиҖ…еӯҳд№Һд»ӢвҖҷжҳҜд№ҹгҖӮиҷҪзәӨеҫ®пјҢдәҰиғҪдҪҝдәәеҝ§жӮ”гҖӮвҖқдҝЎдёӯжүҖеј•гҖҠжҳ“гҖӢж–ҮеҮәиҮӘгҖҠе‘Ёжҳ“В·зі»иҫһгҖӢпјҢе…¶ж„ҸжҳҜиҜҙеҝ§еҝөвҖңжӮ”вҖқвҖңеҗқвҖқд№ӢиұЎеңЁдәҺйў„йҳІзәӨд»Ӣе°Ҹз–өгҖӮиҢғд»Іж·№еҖҹжӯӨиҖҢеј•з”іиҜҙ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°Ҹз–өе°ҸеӨұпјҢд№ҹиғҪи®©дәәеҝ§жғ§жӮ”жҒЁпјҢеӣ иҖҢеңЁе№іж—Ҙе®үеұ…д№Ӣж—¶пјҢдәҰйЎ»ж—¶еҲ»дҝқжҢҒеҝ§жӮЈж„ҸиҜҶпјҢд»ҘйҳІеӨҮе°ҸеӨұй…ҝжҲҗеӨ§зҘёгҖӮиҝҷдёҖйҒ“зҗҶж—ўйҖӮз”ЁдәҺдҝ®иә«пјҢдәҰеҸҜжҺЁд№ӢдәҺжІ»еӣҪгҖӮеҰӮеӨ©еңЈдёүе№ҙеӣӣжңҲпјҢе…¶ж—¶е“Ғйҳ¶дҪҺеҫ®зҡ„иҢғд»Іж·№зңӢеҲ°е®Ӣе»·еӣ еӨӘе№іж—Ҙд№…иҖҢеҚіе°Ҷйҷ·е…ҘвҖңдәәдёҚзҹҘжҲҳпјҢеӣҪдёҚиҷ‘еҚұвҖқзҡ„еҚұйҷ©жғ…еҪўпјҢдҫҝдёҚз”ұеҫ—еҝ§еҝғеҝЎеҝЎең°еҗ‘з»ҹжІ»иҖ…дёҠд№ҰеҠӣи°ҸпјҡеңЈдәәд№ӢжңүеӨ©дёӢд№ҹпјҢж–Үз»Ҹд№ӢпјҢжӯҰзә¬д№ӢгҖӮжӯӨдәҢйҒ“иҖ…пјҢеӨ©дёӢд№ӢеӨ§жҹ„д№ҹвҖҰвҖҰж–ҮжӯҰд№ӢйҒ“пјҢзӣёжөҺиҖҢиЎҢпјҢдёҚеҸҜж–ҜйЎ»иҖҢеҺ»з„үгҖӮе”җжҳҺзҡҮд№Ӣж—¶пјҢеӨӘе№іж—Ҙд№…пјҢдәәдёҚзҹҘжҲҳпјҢеӣҪдёҚиҷ‘еҚұпјҢеӨ§еҜҮзҠҜе…іпјҢеҠҝеҰӮз“Ұи§ЈпјҢжӯӨеӨұжӯҰд№ӢеӨҮд№ҹвҖҰвҖҰеңЈдәәеҪ“зҰҸиҖҢзҹҘзҘёпјҢеңЁжІ»иҖҢйҳІд№ұгҖӮж•…е–„е®үиә«иҖ…пјҢеңЁеә·е®Ғд№Ӣж—¶пјҢдёҚи°“з»Ҳж— з–ҫз—…пјҢдәҺжҳҜжңүиҠӮе®Јж–№иҚҜд№ӢеӨҮз„үпјӣе–„е®үеӣҪиҖ…пјҢеҪ“еӨӘе№ід№Ӣж—¶пјҢдёҚи°“з»Ҳж— еҚұд№ұпјҢдәҺжҳҜжңүж•ҷеҢ–з»Ҹз•Ҙд№ӢеӨҮз„үгҖӮ иҢғд»Іж·№жҢҮеҮәпјҢеңЈдәәжІ»зҗҶеӨ©дёӢпјҢйғҪжҳҜж–Үж•ҷдёҺжӯҰеӨҮдёӨиҖ…并йҮҚгҖҒзӣёжөҺиҖҢиЎҢпјҢд»ҺдёҚеҒҸеәҹдёҖж–№пјҢеӣ дёәиҝҷдёӨиҖ…йғҪжҳҜеӨ©дёӢзҡ„ж №жң¬гҖӮеҺҶеҸІдёҠпјҢе”җзҺ„е®—жқҺйҡҶеҹәж—©е№ҙиҷҪејҖиҫҹзӣӣдё–пјҢдҪҶдёӯе№ҙд»ҘеҗҺеӣ иҙӘдә«еӨӘе№іиҖҢеҝҪз•ҘдәҶеҠ ејәжӯҰеӨҮпјҢд»ҘиҮҙе®үеҸІд№Ӣд№ұзҲҶеҸ‘пјҢжңқдёӯж— еҸҜз”Ёд№Ӣе…өпјҢе”җжңқйҒӮз”ұжӯӨйҷ·е…ҘйЈҺйӣЁйЈҳж‘Үд№Ӣдёӯ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җ‘з»ҹжІ»иҖ…еҠқиҜ«йҒ“пјҢеңЈдәәеңЁе®үе®ҡзҘҘе’Ңд№Ӣж—¶пјҢдҫҝејҖе§ӢзқҖжүӢйҳІеӨҮзҘёжӮЈпјҢеңЁзҒҫд№ұжІЎжңүдә§з”ҹд»ҘеүҚпјҢе°ұе·Із»ҸеҒҡеҘҪдәҶе№іе®ҡзҒҫд№ұзҡ„йў„жЎҲпјӣе–„дәҺе…»з”ҹзҡ„дәәпјҢеңЁеҒҘеә·е®үе®Ғ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дёҚдјҡи®Өдёәж°ёж— з–ҫз—…пјҢиҖҢжҳҜйҡҸж—¶еӨҮеҘҪиҚҜе“ҒгҖҒд»ҘйҳІдёҚжөӢпјӣиҖҢе–„дәҺжІ»еӣҪзҡ„дәәпјҢеңЁеӨӘе№іж— дәӢд№Ӣж—¶пјҢдёҚи®Өдёәдјҡж°ёж— еҚұд№ұпјҢиҖҢжҳҜж—¶ж—¶еӢӨж”ҝеҢ–ж°‘гҖҒйҳІзҒҫеӨҮжӮЈгҖӮе…¶иЁҖдёӢд№Ӣж„ҸпјҢдҫҝжҳҜеёҢжңӣз»ҹжІ»иҖ…дёҚеҸҜз«Ҝеұ…еӨӘе№ігҖҒж— жүҖдҪңдёәпјҢиҖҢжҳҜиҰҒеҗёеҸ–еҺҶеҸІж•ҷи®ӯпјҢж—¶еҲ»дҝқжҢҒеҝ§жӮЈж„ҸиҜҶпјҢеӢӨж”ҝжІ»еӣҪпјҢејәе…өеӨҮжҲҳпјҢд»ҘйҳІдёҚиҷһд№ӢзҒҫгҖӮеҸҰеңЁгҖҠж¶Ұе·һи°ўдёҠиЎЁгҖӢдёӯ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иҝҳиҜҙпјҡиҮЈжҢүеӨ§гҖҠжҳ“гҖӢд№Ӣд№үпјҢгҖҠеқӨгҖӢиҖ…пјҢжҹ”йЎәд№ӢеҚҰпјҢиҮЈд№ӢиұЎд№ҹпјҢиҖҢжңүеұҘйңңеқҡеҶ°д№ӢйҳІпјҢд»Ҙе…¶йҳҙдёҚеҸҜй•ҝд№ҹгҖӮгҖҠдё°гҖӢиҖ…пјҢе…үеӨ§д№ӢеҚҰпјҢеҗӣд№ӢиұЎд№ҹпјҢиҖҢжңүж—Ҙдёӯи§Ғж–—д№ӢжҲ’пјҢд»Ҙе…¶жҳҺдёҚеҸҜеҫ®д№ҹгҖӮиҮЈиҖғе…№еүҚи®ӯпјҢиҷ‘дәҺжңӘиҗҢгҖӮеҪ“еҚұиЁҖеҚұиЎҢд№Ӣз§ӢпјҢжңүеҜ–жҳҢеҜ–еҫ®д№ӢиҜҙгҖӮи°“еӨ§иҮЈд№…ж¬ЎпјҢеңЁиҝӣйҖҖиҖҢеҫ—е®ңпјӣи°“зҺӢиҖ…дёҮеҮ пјҢеҝ…иә¬дәІиҖҢж— еҖҰгҖӮ еқӨеҚҰд·ҒпјҢе…ӯзҲ»зҡҶйҳҙпјҢжҳҜзәҜжҹ”д№ӢеҚҰпјҢдёәиҮЈд№ӢиұЎпјҢдҪҶе…¶еҲқзҲ»вҖңеұҘйңңпјҢеқҡеҶ°иҮівҖқиҜҙжҳҺдәҶйҳҙж°”з§ҜжёҗиҖҢиҮіеқҡеҶ°зҡ„йҒ“зҗҶгҖӮеқӨеҚҰгҖҠж–ҮиЁҖдј гҖӢдҫқжӯӨзҲ»д№үиҖҢеҸ‘жҢҘйҒ“пјҡвҖңиҮЈеј‘е…¶еҗӣпјҢеӯҗеј‘е…¶зҲ¶пјҢйқһдёҖжңқдёҖеӨ•д№Ӣж•…пјҢе…¶жүҖз”ұжқҘиҖ…жёҗзҹЈпјҒз”ұиҫЁд№ӢдёҚж—©иҫЁд№ҹ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иҜҙиҮЈеј‘е…¶еҗӣгҖҒеӯҗеј‘е…¶зҲ¶зҡ„еӨ§жҒ¶е№¶йқһдёҖжңқдёҖеӨ•й“ёжҲҗ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з”ұдәҺеҗӣзҲ¶дёҚжӣҫж—©ж—ҘиҫЁеҲ«зҡ„зјҳж•…гҖӮеҸҲдё°еҚҰд·¶пјҢдёӢзҰ»дёҠйңҮпјҢвҖңжҳҺд»ҘеҠЁвҖқпјҢдёәвҖңе…үеӨ§д№ӢеҚҰвҖқпјҢжҳҜеҗӣзҺӢд№ӢиұЎпјҢдҪҶе…¶зҲ»иҫһдёӯеҚҙжңүвҖңж—Ҙдёӯи§Ғж–—вҖқд№ӢжҲ’пјҢеҚіж—ҘжӯЈдёӯеӨ©д№Ӣж—¶еҸ‘з”ҹж—Ҙе…ЁйЈҹпјҢиЎЁжҳҺеҗӣдёҠзҡ„е…үиҠ’йҒӯеҲ°йҒ®и”ҪгҖӮеҖҹеҠ©еҜ№иҝҷдёӨеҚҰзҡ„иҜ йҮҠ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Ҡқи°ҸеҗӣзҺӢпјҢз»ҹзҺҮзҷҫе®ҳиҰҒж—¶еҲ»йҳІеҫ®жқңжёҗпјҢдҪҝд№ӢиҝӣйҖҖеҫ—е®ңпјҢйҒҝе…Қеӣ иҮЈдёӢйӮӘеҝғз§ҜжёҗиҖҢи®©иҮӘиә«йҒӯеҸ—е’Һе®іпјӣжІ»еӣҪзҗҶж”ҝжӣҙйЎ»ж—Ҙж—ҘзІҫеӢӨпјҢеҚідҪҝдәӢеҠЎз№ҒеӨҡд№ҹиҰҒиә¬дәІж— еҖҰпјҢд»Ҙе…Қеӣ жҮҲжҖ жҲ–еҗӣжқғж—ҒиҗҪиҖҢи®©еӣҪ家дә§з”ҹзҘёд№ұгҖӮдёҖиЁҖд»Ҙи”Ҫд№ӢпјҢеҸӘжңүж—¶ж—¶вҖңиҷ‘дәҺжңӘиҗҢвҖқпјҢжүҚиғҪвҖңеӨҡејӯжңӘ然д№ӢжӮЈвҖқгҖӮеҪ“然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дёӯзҡ„вҖңд№җвҖқд№ҹ并йқһеҸӘжҳҜж„ҹе®ҳд№Ӣд№җпјҢиҖҢжҳҜи•ҙеҗ«зқҖвҖңйҒ“д№үд№Ӣд№җвҖқ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гҖҠи°ўиҪ¬зӨјйғЁдҫҚйғҺиЎЁ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иҝӣеҲҷе°Ҫеҝ§еӣҪеҝ§ж°‘д№ӢиҜҡпјҢйҖҖеҲҷеӨ„д№җеӨ©д№җйҒ“д№ӢеҲҶвҖқдёҖеҸҘпјҢдҫҝеҸҜдҪңдёәе…¶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зҡ„жіЁи„ҡжқҘзҗҶи§ЈгҖӮеңЁе®Ӣд»Ј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еӨ§жҰӮжҳҜжңҖж—©еҜ№вҖңеӯ”йўңд№җеӨ„вҖқиҝҷдёҖе‘ҪйўҳиҝӣиЎҢи®Ёи®әзҡ„жҖқжғіе®¶гҖӮеҰӮж—©еңЁеӨ§дёӯзҘҘз¬Ұдёғе№ҙпјҲ1014е№ҙпјүпјҢж—¶е№ҙ26еІҒзҡ„иҢғд»Іж·№е°ҡеңЁзқўйҳід№ҰйҷўиӢҰиҜ»пјҢе°ұжӣҫеҶҷдёӢвҖңз“ўжҖқйўңеӯҗеҝғиҝҳд№җвҖқзҡ„иҜ—еҸҘпјҢиЎЁйңІеҮәи·өиЎҢвҖңеӯ”йўңд№җеӨ„вҖқзҡ„еҝғеҝ—гҖӮвҖңеӯ”йўңд№җеӨ„вҖқзҡ„ж ёеҝғж„Ҹж—ЁеңЁдәҺеҗӣеӯҗвҖңеӣәз©·иҖҢд№җйҒ“вҖқгҖӮеҰӮиҢғд»Іж·№гҖҠжҳ“д№үВ·еӣ°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еӣ°дәҺйҷ©иҖҢдёҚж”№е…¶иҜҙпјҲжӮҰпјүвҖҰвҖҰе…¶жғҹеҗӣеӯҗд№ҺпјҢиғҪеӣәз©·иҖҢд№җйҒ“е“үпјҒвҖқиҝҷжҳҜиҜҙпјҢеңЁеӣ°з©·гҖҒеҚұйҡҫд№Ӣж—¶иҝҳиғҪе§Ӣз»Ҳеқҡе®ҲйҒ“д№үгҖҒдҝ®зҫҺе·ұеҫ·е№¶дё”дёҚж”№е…¶д№җзҡ„дәәпјҢеӨ§жҰӮеҸӘжңүеҗӣеӯҗеҗ§пјҒиҢғд»Іж·№жӯӨиЁҖ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еңЁйҳҗйҮҠжҳ“зҗҶ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№ҹжҳҜеңЁиҮӘиҝ°е…¶дәәз”ҹдҝЎеҝөгҖӮеҰӮе…¶еӣ еҚұиЁҖйІ и®әиҖҢиҮҙж»Ўжңқи§ҒжҖ’пјҢеҚҙдҫқж—§дёҚеҠЁдәҺеҝғпјҢеҸӘжҳҜвҖңжғҹиҙЈе·ұд№җйҒ“вҖқпјҢ并иҜҙвҖңеҗӣеӯҗзҡҶжңүйҖҡеЎһпјҢеӯ”еӯҹдёҚиғҪйҖғпјҢеҶөеҗҫиҫҲиҖ¶вҖқпјӣеҸҲеҰӮе…¶иҷҪвҖң慨然жңүзӣҠеӨ©дёӢд№ӢеҝғпјҢеһӮеҚғеҸӨд№Ӣеҝ—вҖқ,дҪҶеёёе№ҙиў«иҙ¬и°ӘдәҺеӨ–пјҢдёҚеҫ—иЎҢе…¶йҒ“пјҢеҲҷе§Ӣз»ҲиҮӘеҠұдә‘пјҡвҖңжғҹеҗӣеӯҗдёәиғҪд№җйҒ“пјҢжӯЈеңЁжӯӨж—ҘзҹЈгҖӮвҖқжҖ»д№Ӣ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з»ҸиҝҮж—¶й—ҙзҡ„ж·¬зӮјпјҢе·Із»ҸжҲҗдёә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жүҖе…ұеҗҢеҙҮд»°зҡ„зІҫзҘһдё°зў‘пјҢж—¶еҲ»ж„ҹеҸ¬зқҖж— ж•°д»Ғдәәеҝ—еЈ«иғёжҖҖ家еӣҪгҖҒеҝғеҝ§еӨ©дёӢгҖӮз»“ иҜӯ жҜӣжіҪдёңжӣҫжҢҮеҮ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дёҖж–№йқўдёҺиҜёи‘ӣдә®дёҖж ·пјҢжҳҜе…·еӨҮз»Ҹдё–еӨ§жүҚзҡ„вҖңеҠһдәӢд№ӢдәәвҖқ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еҲҷе’Ңеӯ”еӯҗгҖҒеӯҹеӯҗгҖҒжңұзҶ№гҖҒйҷҶд№қжёҠгҖҒзҺӢйҳіжҳҺдёҖиҲ¬пјҢжҳҜзІҫз ”е…ӯз»Ҹзҡ„вҖңдј ж•ҷд№ӢдәәвҖқпјҢе…¶дёҖиә«иҖҢе…јиғҪиҮЈгҖҒеҗҚе„’зӯүеӨҡйҮҚиә«д»ҪгҖӮ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пјҢеҜ№дәҺ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йҒ“еҫ·еҠҹдёҡгҖҒвҖңиғҪиҮЈвҖқеҪўиұЎпјҢвҖңж— и®әеЈ«еӨ§еӨ«дәүдёәдј иҝ°пјҢеҚіеҰҮдәәеҘіеӯҗе…·иғҪиЁҖд№ӢвҖқпјӣиҖҢеҜ№дәҺ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жңҜж–Үз« гҖҒвҖңеҗҚе„’вҖқиә«д»ҪпјҢеӯҰиҖ…们вҖңзңҹиғҪзҹҘиҖ…зӣ–еҜЎвҖқгҖӮйҖҡиҝҮдёҠж–ҮжүҖиҝ°пјҢжҲ‘们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иҢғд»Іж·№еңЁвҖңеҲӣйҖҡз»Ҹд№үвҖқж–№йқўзЎ®жңүдёҚдҝ—жҲҗз»©вҖ”вҖ”д»–йҖҡиҝҮиҜ и§ЈгҖҠе‘Ёжҳ“гҖӢзӯүз»Ҹи‘—еҲӣйҖ жҖ§ең°з»§жүҝдёҺеҸ‘еұ•дәҶе…Ҳе„’зҡ„дёҖдәӣйҮҚиҰҒжҖқжғіпјҢиҝҷдәӣжҖқжғідёҚд»…иҙҜз©ҝдәҺиҢғд»Іж·№зҡ„з»ҸеӯҰи®әи‘—д№Ӣдёӯ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жһ„жҲҗдәҶе…¶з»ҸеӯҰзҡ„ж ёеҝғжҖқжғіпјҢ并主иҰҒе‘ҲзҺ°дёәд»ҘдёӢ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ҡдёҖжҳҜвҖңж”ҝеҝ…йЎәж°‘вҖқзҡ„ж°‘жң¬жҖқжғіпјӣдәҢжҳҜвҖңз©·еҸҳйҖҡд№…вҖқзҡ„ж”№йқ©жҖқжғіпјӣдёүжҳҜвҖңе…Ҳеҝ§еҗҺд№җвҖқзҡ„еҝ§д№җжҖқжғігҖӮдҪңдёәе®Ӣд»ЈеЈ«дәәдёӯйӣҶз»ҸжңҜгҖҒдәӢеҠҹгҖҒйҒ“еҫ·гҖҒж–Үз« дәҺдёҖиә«зҡ„第дёҖдәәпјҢиҢғд»Іж·№з»ҸеӯҰзҡ„ж ёеҝғжҖқжғіи•ҙеҗ«зқҖе…¶еңЁзү№ж®Ҡж—¶д»ЈиғҢжҷҜдёӢзҡ„ж·ұеҲ»жҖқиҖғдёҺдәәз”ҹжҷәж…§пјҢж—ўзҙ§иҙҙз»ҸеӯҰж–Үжң¬пјҢеҸҲеқҡе®һз«Ӣи¶ідәҺеҢ—е®Ӣд»Ғе®—жңқзҡ„ж”ҝжІ»дёҺзӨҫдјҡзҺ°е®һпјҢ并且е§Ӣз»Ҳд»ҘеӨҚиЎҢвҖңзҺӢйҒ“вҖқдёәе®—ж—ЁпјҢдёҚз®ЎжҳҜеҜ№еҪ“ж—¶зҡ„зҺ°е®һж”ҝжІ»пјҢиҝҳжҳҜеҜ№вҖңе®ӢеӯҰвҖқзҡ„е…ҙиө·пјҢеқҮдә§з”ҹдәҶж·ұиҝң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ж¶өеҗ«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4е№ҙ第9жңҹвҖңе“ІеӯҰз ”з©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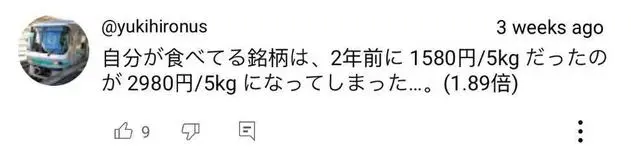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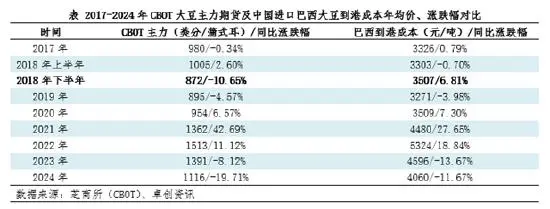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