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зҪ—еҝ…иүҜ еј йңІпјҲеҚҺеҚ—еҶңдёҡеӨ§еӯҰеӣҪ家еҶңдёҡеҲ¶еәҰдёҺеҸ‘еұ•з ”究йҷўйҷўй•ҝгҖҒж•ҷжҺҲпјӣеҚҺдёӯеҶңдёҡеӨ§еӯҰз»ҸжөҺз®ЎзҗҶеӯҰйҷўж•ҷжҺҲпјү д№ иҝ‘е№іжҖ»д№Ұи®°ејәи°ғпјҡвҖңеңЁе…Ёйқўе»әи®ҫ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зҺ°д»ЈеҢ–еӣҪ家新еҫҒзЁӢдёӯпјҢжҲ‘们еҝ…йЎ»жҠҠдҝғиҝӣе…ЁдҪ“дәәж°‘е…ұеҗҢеҜҢиЈ•ж‘ҶеңЁжӣҙеҠ йҮҚиҰҒзҡ„дҪҚзҪ®пјҢи„ҡиёҸе®һең°гҖҒд№…д№…дёәеҠҹпјҢеҗ‘зқҖиҝҷдёӘзӣ®ж ҮжӣҙеҠ з§ҜжһҒжңүдёәең°иҝӣиЎҢеҠӘеҠӣпјҢдҝғиҝӣдәәзҡ„е…ЁйқўеҸ‘еұ•е’ҢзӨҫдјҡе…ЁйқўиҝӣжӯҘпјҢи®©е№ҝеӨ§дәәж°‘зҫӨдј—иҺ·еҫ—ж„ҹгҖҒе№ёзҰҸж„ҹгҖҒе®үе…Ёж„ҹжӣҙеҠ е……е®һгҖҒжӣҙжңүдҝқйҡңгҖҒжӣҙеҸҜжҢҒз»ӯгҖӮвҖқиҝҷдёҖйҮҚиҰҒи®әж–ӯж„Ҹе‘ізқҖпјҢжІ»зҗҶ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иҰҒжӣҙдёәйҮҚи§Ҷе…¬е№іпјҢжӣҙдёәйҮҚи§Ҷдәә们йҖҡиҝҮз§ҜжһҒеҸӮдёҺеҲӣйҖ зҫҺеҘҪз”ҹжҙ»жүҖе®һзҺ°зҡ„зІҫзҘһеҜҢи¶ігҖӮ
1.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ҡжү“з ҙвҖң收е…ҘзҘһиҜқвҖқ
еӣҪ家з»ҹи®ЎеұҖзҡ„ж•°жҚ®иЎЁжҳҺпјҢ2020е№ҙе…ЁеӣҪеұ…ж°‘дәәеқҮеҸҜж”Ҝй…Қ收е…Ҙе·ІиҫҫеҲ°32189е…ғгҖӮдҪҶжҢүдәәеҸЈеёёдҪҸең°еҲҶпјҢ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дәәеқҮеҸҜж”Ҝй…Қ收е…Ҙд»…дёә17131е…ғпјҢзӣёеҪ“дәҺе…ЁеӣҪдәәеқҮж°ҙе№ізҡ„53.22%пјҢд»…дёәеҹҺй•Үеұ…ж°‘дәәеқҮеҸҜж”Ҝй…Қ收е…Ҙзҡ„39.08%гҖӮжҢү照欧зӣҹе°ҶдёӘдҪ“收е…Ҙж°ҙе№ідҪҺдәҺдәәеқҮеҸҜж”Ҝй…Қ收е…ҘдёӯдҪҚж•°зҡ„60%з•Ңе®ҡдёә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„ж ҮеҮҶпјҢдёӯеӣҪеҶңж°‘е°Ҫз®Ўе·Із»ҸеҪ»еә•ж‘Ҷи„ұдәҶз»қеҜ№иҙ«еӣ°пјҢдҪҶеӨҡж•°д»ҚеӨ„дәҺ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¶жҖҒгҖӮиҝӣдёҖжӯҘең°пјҢжң¬иҜҫйўҳз»„еҜ№е…ЁеӣҪ25468дёӘж ·жң¬еҶңжҲ·зҡ„еҲҶжһҗиЎЁжҳҺпјҢеҶңжҲ·е®¶еәӯ收е…ҘдёҺе№ёзҰҸж„ҹд№Ӣй—ҙе‘ҲвҖңеҖ’UвҖқеһӢе…ізі»пјҢиЎЁжҳҺеҶңж°‘зҫӨдҪ“еҮәзҺ°вҖңдјҠж–Ҝзү№жһ—жӮ–и®әвҖқгҖӮвҖңдјҠж–Ҝзү№жһ—жӮ–и®әвҖқж„Ҹе‘ізқҖпјҢеңЁзҹӯжңҹеҶ…пјҢз»қеҜ№ж”¶е…ҘеўһеҠ еңЁж»Ўи¶і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зү©иҙЁйңҖжұӮ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ејәеҢ–е…¶еҜ№жңӘжқҘз”ҹжҙ»зҡ„д№җи§Ӯйў„жңҹ并дҝғиҝӣдәҶе№ёзҰҸж„ҹпјӣд»Һй•ҝжңҹзңӢпјҢз»қеҜ№ж”¶е…Ҙзҡ„жҸҗй«ҳдјҡжҝҖеҸ‘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еҜ№зү©иҙЁзҡ„еҚ жңүж¬ІпјҢйҷҚдҪҺз»қеҜ№ж”¶е…ҘеҜ№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жӯЈеҗ‘еҪұе“ҚгҖӮз”ұжӯӨеҸҜд»ҘеҲӨж–ӯпјҢиҷҪ然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жҳҫи‘—ең°жҸҗеҚҮдәҶ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зҡ„收е…Ҙж°ҙе№іпјҢдҪҶжңӘиғҪжңүж•Ҳең°еўһиҝӣе…¶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
йҖҡеёёдјҠж–Ҝзү№жһ—жӮ–и®әжҳҜеңЁй«ҳ收е…ҘзҫӨдҪ“дёӯжүҚдјҡеҮәзҺ°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然иҖҢжҲ‘еӣҪеҶңж°‘еңЁиҫғдҪҺ收е…Ҙж°ҙе№ідёҺиҫғй«ҳеҹҺ乡收е…Ҙе·®и·қзҡ„жғ…еўғдёӢпјҢд№ҹеҮәзҺ°дәҶвҖңдјҠж–Ҝзү№жһ—жӮ–и®әвҖқгҖӮиҝҷ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дёҺжҲ‘еӣҪ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зҡ„收е…ҘжқҘжәҗз»“жһ„жңүе…ігҖӮдјҙйҡҸзқҖе·ҘдёҡеҢ–еҹҺй•ҮеҢ–иҝӣзЁӢпјҢеҶңж°‘еӨ–еҮәеҠЎе·Ҙжҳҫи‘—ж”№еҸҳдәҶеҶңжҲ·е®¶еәӯзҡ„收е…Ҙз»“жһ„гҖӮе…ЁеӣҪеҶңжҲ·е®¶еәӯжқҘиҮӘйқһеҶң收е…Ҙзҡ„еҚ жҜ”е·Із»Ҹз”ұ2006е№ҙзҡ„46.2%еўһеҠ еҲ°2019е№ҙзҡ„76.7%гҖӮеӨ–еҮәеҠЎе·ҘдҪҝеҫ—дәәжҲ·еҲҶзҰ»жҲҗдёәжҷ®йҒҚзҡ„зӨҫдјҡзҺ°иұЎгҖӮ2019е№ҙзҡ„ж•°жҚ®жҳҫзӨәпјҢжҲ‘еӣҪеҶңж°‘е·ҘжҖ»йҮҸиҫҫеҲ°2.91дәҝдәәпјҢе…¶дёӯејӮең°иҝҒеҫҷзҡ„еӨ–еҮәеҶңж°‘е·Ҙдёә1.74дәҝдәәгҖӮжҳҫ然пјҢдёҺеҶңж°‘е·Ҙиө„жҖ§ж”¶е…Ҙеўһй•ҝеҪўжҲҗејәзғҲеҸҚе·®зҡ„жҳҜиҒҢдёҡиә«д»Ҫзҡ„жүӯжӣІгҖҒең°еҹҹзҡ„жӯ§и§ҶгҖҒ家еәӯжҲҗе‘ҳзҡ„еҲҶзҰ»пјҢд»ҘеҸҠдёҺд№Ӣе…іиҒ”зҡ„з”ұз•ҷе®ҲиҖҒдәәгҖҒз•ҷе®Ҳе„ҝз«Ҙеј•еҸ‘зҡ„еҝғзҗҶеҺӢеҠӣдёҺдәІжғ…зјәеӨұгҖҒиә«еӨ„ејӮең°зҡ„еӯӨзӢ¬ж„ҹпјҢиҝҷдәӣе°ҶдёҚеҸҜйҒҝе…ҚеёҰжқҘ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жҚҹдјӨпјҢд»ҺиҖҢеҜјиҮҙеҶңж°‘еңЁе®¶еәӯ收е…ҘеӨ„дәҺиҫғдҪҺж°ҙе№ідёҠеҚіи·Ёи¶ҠдәҶвҖңдјҠж–Ҝзү№жһ—жӮ–и®әвҖқзҡ„жӢҗзӮ№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收е…Ҙж°ҙе№іеҪұе“ҚеҶңж°‘зҡ„з”ҹжҙ»ж»Ўж„ҸеәҰпјҢ收е…ҘжқҘжәҗз»“жһ„д№ҹдјҡж·ұеҲ»еҪұе“ҚзқҖеҶңж°‘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зҹҘ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ҝ…йЎ»жү“з ҙ收е…Ҙеўһй•ҝеҝ…然иғҪеӨҹжҸҗеҚҮ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вҖң收е…ҘзҘһиҜқвҖқгҖӮ
2.收е…Ҙе·®и·қгҖҒ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дёҺ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
жҖ»дҪ“жқҘиҜҙпјҢе№ёзҰҸж„ҹдёҺдәә们зҡ„еҸҜж”Ҝй…Қз©әй—ҙзҙ§еҜҶе…іиҒ”гҖӮ收е…Ҙж°ҙе№ізҡ„й«ҳдҪҺеҪ“然дёҫи¶іиҪ»йҮҚпјҢдҪҶ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пјҢдёҖж—ҰдёӘдҪ“жүҖжӢҘжңүзҡ„иө„жәҗжҳҺжҳҫдҪҺдәҺжүҖеңЁзӨҫдјҡ家еәӯжҲ–дёӘдәәжүҖе№іеқҮж”Ҝй…Қзҡ„иө„жәҗж°ҙе№іпјҢиҝҷзұ»зӣёеҜ№ж”¶е…ҘеҜ№жҜ”зҡ„зӣҙи§ӮжҖ§е°Ҷжӣҙдёәжҳҫи‘—ең°еҪұе“Қдәә们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еңЁ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жқЎд»¶дёӢпјҢз«һдәүжңәеҲ¶еҝ…然引еҸ‘дёӘдҪ“д№Ӣй—ҙжҲ–зҫӨдҪ“д№Ӣй—ҙзҡ„收е…Ҙе·®и·қпјҢиҖҢ收е…Ҙе·®и·қеҝ…然еҜјиҮҙ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„е®ўи§ӮеӯҳеңЁдёҺдё»и§Ӯж„ҹзҹҘгҖӮе°Өе…¶еңЁд№ЎеңҹдёӯеӣҪзҡ„еҶңжқ‘пјҢеҶңж°‘еҸҠ其家еәӯжҳҜж·ұеөҢдәҺжқ‘еә„зҪ‘з»ңд№Ӣдёӯзҡ„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з”ұжқ‘иҗҪе…ұеҗҢдҪ“жүҖиЎЁиҫҫзҡ„йӣҶдҪ“дё»д№үдҝЎеҝөгҖҒең°дҪҚдёҺеЈ°иӘүпјҢжҳҜеҶңж°‘еҝғзҗҶж•Ҳеә”ж„ҹзҹҘ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з”ұдәҺеҶңж°‘зӣёйӮ»иҖҢеұ…еҸҠзӨҫдјҡзҪ‘з»ңдә’еҠЁпјҢзӣёеҜ№ж”¶е…Ҙж°ҙе№ізҡ„й«ҳдҪҺжӣҙжҳ“дәҺеңЁжҜ”иҫғдёӯеҪұе“ҚеҶңж°‘зҡ„еҝғзҗҶж•Ҳз”Ё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з”ұ收е…Ҙе·®и·қжүҖиЎЁиҫҫзҡ„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пјҢдјҡеёҰжқҘдёӨдёӘж–№йқў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зҹҘгҖӮ
дёҖжҳҜе®ўи§Ӯ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дёҺ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иҜҫйўҳз»„и®Ўз®—е…ЁеӣҪ25468дёӘж ·жң¬еҶңжҲ·еңЁе…¶жқ‘еә„дёӯзҡ„家еәӯдәәеқҮ收е…ҘжҺ’еҗҚпјҢ并йҖҡиҝҮеҲӨж–ӯ其收е…ҘжҳҜеҗҰдҪҺдәҺдёӯдҪҚж•°пјҢжқҘиЎЎйҮҸ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ЁӢеәҰгҖӮз»“жһңиЎЁжҳҺпјҡеҶңжҲ·ж”¶е…ҘжҺ’еҗҚи¶ҠдҪҺпјҢеҶңж°‘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и¶ҠдҪҺпјӣеӨ„дәҺ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¶жҖҒ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е…¶е№ёзҰҸж„ҹжҳҺжҳҫеҸ—жҚҹгҖӮиҝҷиЎЁжҳҺпјҢеҸӘиҰҒ收е…ҘжІЎжңүе®һзҺ°з»қеҜ№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еқҮзӯүпјҢеҸӘиҰҒеӯҳеңЁж”¶е…ҘдёҠзҡ„е·®ејӮпјҢе°ұдјҡеҜјиҮҙеҶңж°‘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еҮәзҺ°е·®ејӮгҖӮ
дәҢжҳҜдё»и§Ӯ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дёҺ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иҜҫйўҳз»„иҝӣдёҖжӯҘиҜ·ж ·жң¬еҶңжҲ·д»ҘвҖңдәІжҲҡвҖқвҖңеҗҢеӯҰвҖқвҖңйӮ»еұ…вҖқвҖңжҷ®йҖҡдәәвҖқдёәеҸӮз…§пјҢиҜ„估其家еәӯиҮӘиә«зҡ„зӣёеҜ№з”ҹжҙ»зҠ¶жҖҒпјҢйҖүйЎ№еҢ…жӢ¬вҖңй«ҳеҫҲеӨҡвҖқвҖңй«ҳдёҖдәӣвҖқвҖңе·®дёҚеӨҡвҖқ вҖңдҪҺдёҖдәӣвҖқе’ҢвҖңдҪҺеҫҲеӨҡвҖқпјҢ并жҢүз…§1~5иҝӣиЎҢиөӢеҖјпјҢеҫ—еҲҶи¶Ҡй«ҳиЎЁзӨә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ж„ҹи¶ҠејәгҖӮз»“жһңжҳҫзӨәпјҡеңЁжҺ§еҲ¶дәҶеҶңжҲ·ж”¶е…ҘеҗҺпјҢзӣёеҜ№еүҘеӨәж„ҹи¶Ҡејәзҡ„еҶңжҲ·пјҢе…¶е№ёзҰҸж„ҹи¶ҠдҪҺпјӣеҸӮз…§еҜ№иұЎеҜ№еҶңжҲ·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еҪұе“Қе‘ҲзҺ°еҮәжҷ®йҖҡдәәгҖҒеҗҢеӯҰгҖҒдәІжҲҡгҖҒйӮ»еұ…дҫқж¬ЎејәеҢ–зҡ„и¶ӢеҠҝгҖӮиҝҷиҜҙжҳҺпјҢе№ёзҰҸж„ҹдёҚд»…жқҘжәҗдәҺеҶңжҲ·з»қеҜ№ж”¶е…Ҙж°ҙе№іпјҢжӣҙжҳҜдёҺе…¶е…іиҒ”жҖ§зҫӨдҪ“зҡ„зӣёеҜ№зҠ¶жҖҒ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гҖӮ
дёҖиҲ¬жқҘиҜҙпјҢеңЁз»қеҜ№иҙ«з©·йҳ¶ж®өпјҢж»Ўи¶іеҹәжң¬зҡ„з”ҹзҗҶйңҖжұӮжҲҗдёәиҙ«еӣ°зҫӨдҪ“еҜ№з”ҹжҙ»зҠ¶жҖҒж•ҙдҪ“жҖ§иҜ„д»·зҡ„дё»иҰҒж ҮеҮҶ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йҳ¶ж®өпјҢ收е…Ҙзҡ„еўһеҠ иғҪеӨҹдҝқйҡңе…¶еҹәжң¬з”ҹжҙ»зҡ„ж¶Ҳиҙ№ж”ҜеҮәпјҢдҪҝе…¶з”ҹзҗҶйңҖжұӮеҫ—еҲ°ж»Ўи¶іе№¶иҝ…йҖҹжҸҗй«ҳе…¶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еңЁзӣёеҜ№иҙ«з©·йҳ¶ж®өпјҢдёӘдәәзҡ„з”ҹзҗҶйңҖжұӮеҹәжң¬еҫ—еҲ°ж»Ўи¶іпјҢдәә们ејҖе§ӢжӣҙеӨҡең°иҝҪжұӮеҹәжң¬йңҖжұӮд№ӢеӨ–зҡ„зӣ®ж ҮпјҢеҢ…жӢ¬з»ҸжөҺзӣ®ж Үзҡ„жӣҙеӨҡзү©иҙЁж»Ўи¶іе’Ңйқһз»ҸжөҺзӣ®ж Үзҡ„е№ізӯүе’Ңе°ҠйҮҚзӯүгҖӮз”ұжӯӨпјҢ收е…ҘеҜ№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жӯЈеҗ‘еҪұе“ҚеҸҜиғҪе‘ҲзҺ°еҮәиҫ№йҷ…ж•Ҳеә”йҖ’еҮҸгҖҒејұеҢ–д№ғиҮіжҠ‘еҲ¶ж•Ҳеә”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еңЁжҲ‘еӣҪеҸ–еҫ—и„ұиҙ«ж”»еқҡе…ЁйқўиғңеҲ©зҡ„ж–°йҳ¶ж®өпјҢжңүеҝ…иҰҒжҺўжұӮж–°зҡ„е№ёзҰҸж„ҹж”№иҝӣи·Ҝеҫ„гҖӮ
3.з”ҹжҖҒе®ңеұ…жңүеҠ©дәҺ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
дәәзұ»з»ҸжөҺзі»з»ҹзҡ„еҸ‘еұ•еҝ…йЎ»е»әз«ӢеңЁз”ҹжҖҒзі»з»ҹжүҝиҪҪеҠӣ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жүҚеҸҜиғҪе…·жңүеҸҜжҢҒз»ӯжҖ§гҖӮ然иҖҢпјҢдё»жөҒ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зҗҶи®әеҫҖеҫҖд»Ҙз»ҸжөҺеўһйҮҸжҲ–зү©иҙЁиҙўеҜҢдҪңдёәиҜ„д»·е°әеәҰиҖҢдёҚж–ӯејәеҢ–GDPеҒҸеҘҪпјҢзјәд№ҸеҜ№иҮӘ然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зҡ„е…іжіЁгҖӮеңЁе№ҝжіӣзҡ„еҸ‘еұ•е®һи·өдёӯпјҢиҮӘ然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йҖҡеёёиў«и§Ҷдёә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зҡ„ж—ўе®ҡ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дёҚеҠ иҠӮеҲ¶ең°иҝӣиЎҢж¶ҲиҖ—е’Ңз ҙеқҸгҖӮдәӢе®һиҜҒжҳҺпјҢе·ҘдёҡеҢ–е’ҢеҹҺеёӮеҢ–зҡ„еҝ«йҖҹеҸ‘еұ•йў‘йў‘д»ҘзүәзүІз”ҹжҖҒдёәд»Јд»·пјҢеҠ еү§дәҶеҜ№з©әж°”гҖҒеңҹеЈӨе’Ңж°ҙжәҗзӯүдәәзұ»иө–д»Ҙз”ҹеӯҳиҰҒзҙ зҡ„з ҙеқҸпјҢеҜјиҮҙзҫӨдҪ“жҖ§еҒҘеә·дәӢ件жҖҘеү§еўһеҠ гҖӮзҺҜеўғжөҒиЎҢз—…еӯҰзҡ„з ”з©¶е·Із»ҸиЎЁжҳҺпјҢ1990-2010е№ҙй—ҙпјҢдёӯеӣҪеӣ з©әж°”жұЎжҹ“йҖ жҲҗзҡ„зјәиЎҖжҖ§и„‘иЎҖз®Ўз–ҫз—…гҖҒи®ӨзҹҘеҠҹиғҪжҚҹе®ізӯүдёӯжһўзҘһз»Ҹзі»з»ҹз–ҫз—…еўһй•ҝдәҶ33%гҖӮ
д№ иҝ‘е№іжҖ»д№Ұи®°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иүҜеҘҪ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жҳҜжңҖе…¬е№ізҡ„е…¬е…ұдә§е“ҒпјҢжҳҜжңҖжҷ®жғ зҡ„ж°‘з”ҹзҰҸзҘүвҖқгҖӮиҝҷдёҖйҮҚиҰҒи®әж–ӯж·ұеҲ»жҸӯзӨәдәҶ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дёҺе…ұеҗҢеҜҢиЈ•зҡ„йҮҚеӨ§ж„Ҹи•ҙгҖӮжң¬иҜҫйўҳз»„еҜ№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еҪұе“Қ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е®һиҜҒеҲҶжһҗеҸ‘зҺ°пјҡ第дёҖпјҢжқ‘еә„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зҡ„ж”№е–„иғҪеӨҹжҳҫи‘—жҸҗеҚҮеҶң民家еәӯ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ҢиҖҢдё”е…¶ж”№иҝӣж•Ҳеә”дёҚдјҡйҡҸ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зҡ„жҢҒз»ӯж”№е–„иҖҢеҸ‘з”ҹйҖҶиҪ¬пјӣ第дәҢпјҢжқ‘еә„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дёҺеҶңж°‘е·Ҙиө„жҖ§ж”¶е…Ҙзҡ„дәӨдә’йЎ№иғҪеӨҹжҳҫи‘—жҸҗеҚҮ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ҢиҜҙжҳҺ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еҸҜд»ҘејұеҢ–е·Ҙиө„жҖ§ж”¶е…ҘеҸҠе…¶иҙҹж•Ҳеә”еҜ№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жҚҹдјӨпјӣ第дёүпјҢжқ‘еә„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дёҺеҶңж°‘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и®ӨзҹҘзҡ„дәӨдә’йЎ№жҳҫи‘—еҪұе“Қ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ҢиҜҙжҳҺ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зҡ„ж”№е–„иғҪеӨҹ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јҘиЎҘеҶңж°‘зҡ„иҺ·еҫ—ж„ҹдёҚи¶іпјҢиҝӣиҖҢеўһиҝӣе…¶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
еҝ…йЎ»ејәи°ғпјҢеңЁж”¶е…Ҙеӣ зҙ д№ӢеӨ–пјҢж”№е–„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жҳҜ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иў«дәә们еҝҪи§Ҷзҡ„жңүжңӣ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йҮҚиҰҒй©ұеҠӣгҖӮ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дҝғиҝӣз»ҸжөҺ收е…Ҙе’Ң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зҡ„еҚҸеҗҢеҸ‘еұ•пјҢе°Ҷ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е»¶дјёеҲ°иҮӘ然еӣһеҪ’дёҺз”ҹжҖҒж•Ҳз”Ёд№ӢдёӯпјҢиғҪеӨҹжңүеҠ©дәҺзј“и§Ј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еҸҠе…¶зӣёеҜ№еүҘеӨәж„ҹ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йҖҡиҝҮж”№е–„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пјҢдёҚд»…иғҪеӨҹ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јҘиЎҘ收е…ҘдёҚи¶іеј•еҸ‘зҡ„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й—®йўҳпјҢиҖҢдё”иғҪеӨҹжңүж•Ҳ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зҡ„дё»и§Ӯе№ёзҰҸж„ҹгҖӮеә”иҜҘи®ӨиҜҶеҲ°пјҢжҲ‘еӣҪең°еҹҹиҫҪйҳ”пјҢжҷ®йҒҚйқўдёҙзқҖ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еҸ‘еұ•зҡ„дёҚе№іиЎЎе’ҢдёҚе……еҲҶгҖӮиҷҪ然еҶңжқ‘зҡ„з»қеҜ№иҙ«еӣ°й—®йўҳе·Із»Ҹеҫ—еҲ°е…Ёйқўи§ЈеҶіпјҢдҪҶеҶңж°‘жүҖйқўдёҙзҡ„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й—®йўҳеҸҜиғҪжҳҜй•ҝжңҹеӯҳеңЁзҡ„пј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з”ҹжҙ»зҡ„е®һзҺ°е°Ҷй•ҝжңҹйқўдёҙ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„жҢ‘жҲҳгҖӮеҚ•зәҜзҡ„з»ҸжөҺзӯ–з•Ҙ并дёҚиғҪдёҖеҠіж°ёйҖёзҡ„и§ЈеҶі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й—®йўҳпјҢ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еҝ…йЎ»еҜ»жүҫж–°зҡ„еҠЁеҠӣдёҺи·Ҝеҫ„гҖӮйүҙдәҺ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ж”№иҝӣеҜ№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еӨҡз»ҙжҸҗеҚҮж•Ҳеә”пјҢжүҖд»ҘзҗҶеә”жіЁйҮҚдҝқжҠӨ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пјҢејәеҢ–з”ҹжҖҒе®ңеұ…пјҢе»әз«Ӣиө·жғ еҸҠжңҖе№ҝжіӣдәәзҫӨзҡ„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и§ӮпјҢдҪҝд№ӢжҲҗдёә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йҮҚиҰҒйҖүжӢ©и·Ҝеҫ„гҖӮ
4.д»Һз»ҸжөҺ收е…ҘеҲ°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пјҡеҸ‘еұ•зӯ–з•Ҙзҡ„и°ғж•ҙ
з»ҸжөҺеӯҰе°Өе…¶жҳҜдё»жөҒеҸ‘еұ•з»ҸжөҺеӯҰпјҢдёҖзӣҙжҳҜж»Ўи¶ізү©ж¬ІгҖҒиҝҪжұӮдә§еҮәдёҺ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жңҖеӨ§еҢ–зҡ„з»ҸжөҺеӯҰгҖӮ然иҖҢпјҢз”ұеёӮеңәжңәеҲ¶жүҖй©ұеҠЁ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пјҢеӣ е…¶еӨ©з„¶зҡ„з«һдәүе…ізі»еҸҜиғҪжҒ¶еҢ–дәәж–ҮзӨҫдјҡз”ҹжҖҒпјӣиҖҢеўһй•ҝжңәеҲ¶жүҖеҶ…з”ҹзҡ„зү©иҙЁеҲ©зӣҠиҝҪжұӮпјҢеҲҷеҸҜиғҪжҒ¶еҢ–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„жңүжңәз»ҹдёҖгҖӮиҝӣдёҖжӯҘең°пјҢз»ҸжөҺеўһй•ҝз»©ж•ҲдёҖиҲ¬жқҘжәҗдәҺдә§жқғжҳҺжҷ°жғ…еўғдёӢзҡ„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гҖӮз”ұдә§жқғеҸҠе…¶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жүҖжҝҖеҠұзҡ„иЎҢдёәеҠӘеҠӣгҖҒиҰҒзҙ й…ҚзҪ®дёҺз«һдәүжҖ§дәӨжҳ“пјҢжҳҜж”№е–„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зҡ„ж ёеҝғзәҝзҙўгҖӮй—®йўҳжҳҜпјҢдёҚеҗҢзҡ„иЎҢдёәдё»дҪ“пјҢе…¶иЎҢдёәиғҪеҠӣжҖ»жҳҜеӯҳеңЁе·®ејӮгҖӮеҗҢж ·зҡ„дә§жқғе®үжҺ’并дёҚдҝқйҡңеҸӮдёҺдё»дҪ“зҡ„е№ізӯүдә«зӣҠ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еҶңж°‘еҸҠдҪҺ收е…ҘзҫӨдҪ“еҫҖеҫҖеңЁдә§жқғе®һж–Ҫзҡ„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дёӯеӨ„дәҺејұеҠҝпјҢиҝӣиҖҢеҜјиҮҙе…¶зӣёеҜ№ж”¶е…ҘдёҚи¶іжҲҗдёәеёёжҖҒгҖӮ
дёҺд№ӢдёҚеҗҢпјҢвҖңз»ҝж°ҙйқ’еұұвҖқж—ўжҳҜиҮӘ然иҙўеҜҢпјҢеҸҲжҳҜз»ҸжөҺиҙўеҜҢгҖӮ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дә§жқғзҡ„е…¬е…ұжҖ§еҸҠдә«зӣҠзҡ„йқһжҺ’д»–жҖ§пјҢеҶіе®ҡдәҶ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жҳҜзј“и§ЈзӣёеҜ№ж”¶е…Ҙе·®и·қпјҢиҝӣиҖҢж”№е–„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йҮҚиҰҒжңәеҲ¶гҖӮвҖңз»ҝж°ҙйқ’еұұе°ұжҳҜйҮ‘еұұ银еұұвҖқпјҢзҺҜеўғдҝқжҠӨдёҺз”ҹжҖҒеҸ‘еұ•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дёҖз§Қз”ҹжҙ»ж–№ејҸиөӢжқғгҖҒз”ҹжҙ»иҙЁйҮҸејәиғҪ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з§ҚеҢ…е®№жҖ§еҸ‘еұ•гҖӮиҖҢејәи°ғвҖңд»ҘдәәдёәдёӯеҝғвҖқзҡ„еҢ…е®№жҖ§еҸ‘еұ•пјҢдёҚиғҪд»…д»…ж»Ўи¶ідәҺзү©иҙЁдёҠзҡ„дё°иЈ•пјҢжӣҙиҰҒи°ӢжұӮдәәдёҺдәәгҖҒ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„иһҚеҗҲгҖӮеӣ жӯӨпјҢз ҙйҷӨвҖң收е…ҘзҘһиҜқвҖқпјҢ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Ңеҝ…йЎ»е»әз«Ӣе№ҝд№үзҡ„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и§ӮгҖӮ
е…Ёйқўе®һж–Ҫд№Ўжқ‘жҢҜе…ҙпјҢеҝ…йЎ»вҖңеқҡжҢҒеҶңдёҡеҶңжқ‘дјҳе…ҲеҸ‘еұ•пјҢжҢүз…§дә§дёҡе…ҙж—әгҖҒз”ҹжҖҒе®ңеұ…гҖҒд№ЎйЈҺж–ҮжҳҺгҖҒжІ»зҗҶжңүж•ҲгҖҒз”ҹжҙ»еҜҢиЈ•зҡ„жҖ»иҰҒжұӮпјҢе»әз«ӢеҒҘе…ЁеҹҺд№ЎиһҚеҗҲеҸ‘еұ•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е’Ңж”ҝзӯ–дҪ“зі»пјҢеҠ еҝ«жҺЁиҝӣеҶңдёҡеҶңжқ‘зҺ°д»ЈеҢ–вҖқгҖӮеңЁз”ҹжҖҒзҰҸеҲ©и§Ӯз»ҹйўҶдёӢпјҢж—ЁеңЁжҸҗеҚҮеҶңжқ‘еұ…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зҡ„д№Ўжқ‘жҢҜе…ҙжҲҳз•ҘпјҢеә”иҜҘеҒҡеҮәжҒ°еҪ“зҡ„йҖүжӢ©пјҡ第дёҖпјҢдә§дёҡз”ҹжҖҒеҢ–пјҢеҚіеҶңдёҡдә§дёҡеҸ‘еұ•йҒөеҫӘиҮӘ然з”ҹжҖҒеҫӘзҺҜ规еҫӢпјҢд»Ҙз”ҹжҖҒжүҝиҪҪеҠӣдёәзәўзәҝпјҢйҖҡиҝҮеҜ№з”ҹдә§е’Ңж¶Ҳиҙ№ж–№ејҸзҡ„ж”№иҝӣпјҢжҸҗеҚҮз”ҹжҖҒдҝқиӮІеәҰпјӣ第дәҢпјҢе®ңеұ…з”ҹжҖҒеҢ–пјҢеҚідҝқжҠӨд№Ўжқ‘дј з»ҹиҮӘ然е’Ңдәәж–ҮйЈҺиІҢпјҢйҖҡиҝҮд№Ўжқ‘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ж”№иҝӣдёҺжұЎжҹ“жәҗеӨҙжІ»зҗҶпјҢжҸҗеҚҮдәәеұ…зҺҜеўғиҙЁйҮҸпјӣдёүпјҢд№ЎйЈҺз”ҹжҖҒеҢ–пјҢеҚіиҗҘйҖ иһҚжҙҪе’Ңи°җзҡ„ж–ҮеҢ–ж°ӣеӣҙпјҢйҖҡиҝҮз”ҹеҠЁжҙ»жіјзҡ„ж–ҮеҢ–жҙ»еҠЁеҪўејҸпјҢжҸҗеҚҮд№Ўжқ‘з”ҹжҙ»е“ҒиҙЁж„ҹпјӣ第еӣӣпјҢжІ»зҗҶз”ҹжҖҒеҢ–пјҢеҚіеҒҘе…ЁеҹәеұӮд№Ўжқ‘зҡ„жІ»зҗҶдҪ“зі»пјҢйҖҡиҝҮ规йҒҝејәеҠҝе®—ж—ҸеҜ№еҠЈеҠҝе®—ж—Ҹзҡ„зӣёеҜ№еүҘеүҠпјҢжҸҗеҚҮеұ…ж°‘жңәдјҡе…¬е№іж„ҹпјӣ第дә”пјҢиҙўеҜҢз”ҹжҖҒеҢ–пјҢеҚіжӢ“еұ•еҶңдёҡзҡ„еӨҡе…ғеҠҹиғҪпјҢеҹәдәҺд№Ўжқ‘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еҸ‘еұ•дј‘й—ІеҶңдёҡе’Ңи§Ӯе…үеҶңдёҡпјҢжҸҗеҚҮд№Ўжқ‘з”ҹжҖҒжңҚеҠЎд»·еҖјгҖӮ
д№Ўжқ‘жҢҜе…ҙзҡ„еҮәеҸ‘зӮ№е’ҢиҗҪи„ҡзӮ№пјҢйғҪжҳҜдёәдәҶи®©дәҝдёҮеҶңж°‘з”ҹжҙ»еҸҳеҫ—жӣҙеҠ зҫҺеҘҪпјҢиҖҢзј“и§ЈзӣёеҜ№иҙ«еӣ°зҡ„з»ҲжһҒзӣ®ж Үд№ҹжҳҜдёәдәҶе…ұеҗҢеҜҢ裕并жҸҗй«ҳе№ҝеӨ§еҶңж°‘зҡ„е№ёзҰҸжҢҮж•°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ҝ…йЎ»йҮҚи§ҶеҶңжқ‘з”ҹжҖҒзҺҜеўғе»әи®ҫпјҢд»Ҙз”ҹжҖҒе®ңеұ…еўһиҝӣеҶңж°‘е№ёзҰҸж„ҹпјҢиөӢдәҲеҶңж°‘жӣҙдёәе……еҲҶзҡ„еҸ‘еұ•жқғеҲ©пјҢд»ҺиҖҢеңЁиҮӘз”ұгҖҒе№ізӯүгҖҒе’Ңи°җзҡ„з”ҹжҙ»зҺҜеўғдёӯиҝҪжұӮе№ёзҰҸз”ҹжҙ»гҖӮпјҲжқҘжәҗпјҡйҮҚеҶңиҜ„пј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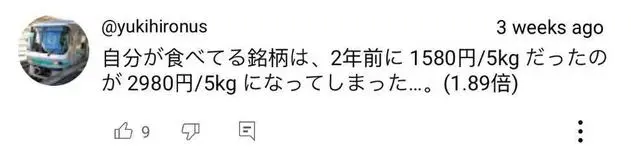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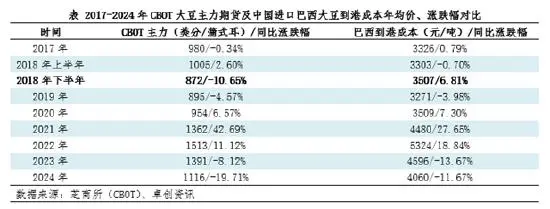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