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иөөзҺ°жө·пјҢз”·пјҢ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еҸӨд»ЈеҸІз ”究жүҖз ”з©¶е‘ҳгҖҒеҸӨд»ЈйҖҡеҸІз ”究е®Өдё»д»»пјҢ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еӨ§еӯҰж•ҷжҺҲгҖҒеҚҡеЈ«з”ҹеҜјеёҲгҖӮ
16иҮі17дё–зәӘпјҢ欧жҙІеҸ‘з”ҹдәҶвҖң科еӯҰйқ©е‘ҪвҖқпјҢдҝғиҝӣдәҶ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ҡ„еҪўжҲҗдёҺеҸ‘еұ•пјҢжҺЁеҠЁж¬§жҙІејҖеҗҜдәҶе…Ёзҗғжү©еј пјҢдҝғдҪҝеӣҪйҷ…ж јеұҖеҸ‘з”ҹдәҶж №жң¬еҸҳеҢ–гҖӮжң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д»ҘиҘҝж–№дёәдё»зҡ„дё–з•ҢиҢғеӣҙеҶ…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йғҪејҖе§Ӣе°қиҜ•жҖқиҖғ科еӯҰзҡ„жң¬иҙЁдёҺ欧жҙІз§‘еӯҰйҒ“и·ҜпјҢжҸӯзӨә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зҡ„科еӯҰеҜ№дәҺ欧жҙІз§‘еӯҰ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з”ҡиҮіе®Ўи§Ҷ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зҡ„科еӯҰйҒ“и·ҜпјҢд»ҺиҖҢжҸҗеҮәдёәд»Җд№Ҳиҝ‘代科еӯҰдә§з”ҹдәҺиҘҝж–№пјҢиҖҢжңӘдә§з”ҹдәҺе…¶д»–ең°ж–№зҡ„йҮҚеӨ§е‘Ҫйўҳ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еҺҶеҸІжҪ®жөҒдёӯпјҢдјҙйҡҸиҘҝж–№иҖ¶зЁЈдјҡеЈ«жқҘеҲ°дёӯеӣҪпјҢиҘҝж–№жҖқжғіз•Ңе·ІејҖе§ӢеҜ№дёӯеӣҪ科еӯҰеұ•ејҖз ”з©¶дёҺеҸҚжҖқгҖӮ20дё–зәӘпјҢиӢұеӣҪ科еӯҰеҸІе®¶жқҺзәҰз‘ҹеҖҹйүҙ科еӯҰеҸІз ”究зҡ„жңҖж–°и·Ҝеҫ„дёҺи§Ҷи§’пјҢйҖҡиҝҮеҜ№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јҖеұ•е…Ёйқўзі»з»ҹ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еҚі15дё–зәӘд»ҘеүҚпјҢдёӯеӣҪ科еӯҰдёәд»Җд№ҲиғҪй•ҝжңҹйўҶе…ҲдәҺ欧жҙІпјҢеҸҲдёәд»Җд№ҲжңӘиғҪдә§з”ҹеҮәиҝ‘代科еӯҰиҝҷдёӨдёӘеҺҶеҸІз–‘й—®гҖӮиҝҷдёҖй—®йўҳжҲҗдёәдё–з•ҢиҢғеӣҙеҶ…е…ідәҺ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ІжңҖеҸ—зһ©зӣ®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дҪҶд»Һ20дё–зәӘеҗҺжңҹејҖе§ӢпјҢиҘҝж–№еӯҰз•Ңз”ҡиҮідёӯеӣҪеӯҰз•ҢпјҢејҖе§Ӣ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жҸҗеҮә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иҙЁз–‘гҖӮиҷҪ然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йқўдёҙдј—еӨҡжҢ‘жҲҳпјҢдҪҶе®ғд»Һдё–з•Ң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е®Ўи§ҶдёӯеӣҪ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дёҺж–ҮжҳҺиғҢжҷҜпјҢд»Қ然еҜ№з§‘еӯҰеҸІз ”究дёӯжүҖеӯҳеңЁзҡ„иӢұйӣ„дё»д№үдёҺеӯӨз«Ӣдё»д№үиҝӣиЎҢдәҶжңҖдёәжңүеҠӣзҡ„жҢ‘жҲҳгҖӮеҪ“еүҚзҡ„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Із ”究пјҢд»Қеә”д»Һдё–з•Ң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зӢ¬зү№йҒ“и·ҜдёҺ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пјҢжҺЁиҝӣдё–з•Ң科еӯҰж•ҙдҪ“еӣҫжҷҜзҡ„ж·ұе…Ҙеұ•зӨәгҖӮиҖҢдҪңдёәж–ҮжҳҺдҪ“зі»дё»еҜјиҖ…гҖҒзӨҫдјҡиө„жәҗжҺ§еҲ¶иҖ…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пјҢж— з–‘жҳҜејҖеұ•иҝҷдёҖз ”з©¶зҡ„е…ій”®зәҝзҙўгҖӮдёҖгҖҒдёңиҘҝж–№жұҮеҗҲиҖҢжҲҗзҡ„иҝ‘代科еӯҰ йүҙдәҺвҖң科еӯҰйқ©е‘ҪвҖқдә§з”ҹдәҺиҘҝ欧пјҢдј—еӨҡиҘҝж–№еӯҰиҖ…д№ғиҮіиҘҝж–№д»ҘеӨ–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д»ҺвҖң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вҖқзҡ„з«ӢеңәеҮәеҸ‘пјҢи®Өдёәиҝ‘代科еӯҰжҳҜ欧жҙІзҡ„зӢ¬зү№еҲӣйҖ гҖӮжқҺзәҰз‘ҹ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иҘҝ欧дәәеҫҲиҮӘ然ең°д»Һиҝ‘д»Јзҡ„科еӯҰе’ҢжҠҖжңҜеӣһжәҜиҝҮеҺ»пјҢи®Өдёә科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еҸ‘еұ•иө·жәҗдәҺеҸӨд»Јең°дёӯжө·ең°еҢә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з»ҸйӘҢе’ҢжҲҗе°ұгҖӮвҖқз”ұдәҺиҝ‘代科еӯҰжүҖиө–д»Ҙдә§з”ҹзҡ„е®һйӘҢзІҫзҘһдёҺеӯҰжңҜе…ұеҗҢдҪ“дә§з”ҹдәҺ欧жҙІпјҢд»ҺиҖҢдҪҝи®ёеӨҡдәәи®Өдёәиҝ‘代科еӯҰеҸӘжңүеңЁж¬§жҙІзҡ„еңҹеЈӨйҮҢжүҚиғҪдә§з”ҹгҖӮдҪҶдәӢе®һ并йқһеҰӮжӯӨпјҢеңЁдёҚеҗҢ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з”ұдәҺе…¶жүҖеұһж–ҮжҳҺзҡ„ж”ҝжІ»еҲ¶еәҰгҖҒз»ҸжөҺеҪўжҖҒгҖҒ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гҖҒ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еӯҳеңЁе·®ејӮпјҢ科еӯҰд»ҘеҸҠж—¶еёёдёҚиў«зәіе…Ҙ科еӯҰзҡ„е®һз”ЁжҠҖжңҜжүҖе‘ҲзҺ°зҡ„еҪўжҖҒгҖҒжүҖиө°иҝҮзҡ„йҒ“и·ҜгҖҒжүҖеҸ‘жҢҘзҡ„дҪңз”ЁйғҪеӯҳеңЁзқҖдёҚе°Ҹзҡ„з”ҡиҮіжҳҜе·ЁеӨ§зҡ„е·®еҲ«пјҢиҖҢжүҖжңүзӨҫдјҡзҡ„дәә们д№ҹйғҪеңЁеҠӘеҠӣеҗ‘еүҚпјҢж”№иҝӣ科жҠҖпјҢеҜ»жұӮжӣҙдёәзҫҺеҘҪ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Ңе»әи®ҫжӣҙдёәй«ҳзә§зҡ„зӨҫдјҡпјҢиҝҷжҳҜ他们е…ұеҗҢзҡ„иҜүжұӮдёҺж„ҝжңӣпјҢиҝҷд№ҹжһ„жҲҗдәҶдёҚеҗҢзӨҫдјҡ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еҶ…еңЁеҠЁеҠӣгҖӮдёҚд»…еҰӮжӯӨпјҢеңЁжј«й•ҝзҡ„еҺҶеҸІй•ҝжІідёӯпјҢдёҚеҗҢзӨҫдјҡд№Ӣй—ҙеӯҳеңЁзқҖжәҗиҝңжөҒй•ҝгҖҒ规模巨еӨ§гҖҒе…ізі»еҜҶеҲҮзҡ„дәӨжөҒдёҺдәӨеҫҖпјҢиҖҢ科еӯҰдёҺжҠҖжңҜжҳҜе…¶дёӯжң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еҶ…е®№д№ӢдёҖпјҢд»ҺиҖҢжһ„жҲҗдәҶдёҚеҗҢзӨҫдјҡ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еӨ–еңЁеҪұе“ҚгҖӮжӯЈжҳҜеҶ…еңЁеҠЁеҠӣдёҺеӨ–еңЁеҪұе“Қзҡ„еҪјжӯӨдә’еҠЁгҖҒе…ұеҗҢдҪңз”ЁпјҢжүҚжһ„жҲҗдәҶдёҚеҗҢзӨҫдјҡ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еӣҫжҷҜпјҢжҸҸз»ҳдәҶдё–з•Ң科еӯҰеҸ‘еұ•йҖҗжёҗеҗҲжөҒгҖҒзў°ж’һгҖҒеҚҮеҚҺзҡ„еҺҶеҸІи„үз»ңдёҺжҪ®жөҒгҖӮ欧жҙІд№ӢжүҖд»Ҙдә§з”ҹ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ж—ўдёҺеҸӨеёҢи…Ҡ科еӯҰи§Ӯеҝөзҡ„еӨҚе…ҙжңүе…і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дёҺжқҘиҮӘдёңж–№зҡ„科жҠҖзҡ„еӮ¬еҠЁ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гҖӮеҚ•зәҜең°е°Ҷ科еӯҰи§ҶдҪң欧жҙІд№ғиҮіиҝ‘代欧жҙІзҡ„зӢ¬зү№дә§зү©зҡ„и§ӮеҝөпјҢиҷҪ然ејәи°ғ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зӣёеҜ№дәҺжүҖжңүзҡ„еҸӨ代科еӯҰзҡ„зӢ¬зү№жҖ§иҙЁдёҺзӨҫдјҡеҪұе“ҚпјҢдҪҶеҚҙеҝҪи§ҶдәҶеңЁжј«й•ҝзҡ„еҺҶеҸІй•ҝжІідёӯпјҢ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зҡ„科еӯҰдј з»ҹеҜ№дәҺиҝҷдёҖжңҖз»Ҳз»“жһңзҡ„жҢҒз»ӯиҖҢе·ЁеӨ§зҡ„иҙЎзҢ®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иҷҪ然еңЁдёҚеҗҢзӨҫдјҡпјҢ科еӯҰзҡ„ең°дҪҚгҖҒеҪўжҖҒгҖҒдҪңз”ЁеӯҳеңЁеҫҲеӨ§е·®ејӮпјҢдҪҶдәәзұ»еҜ№дәҺж”№е–„иҮӘиә«зҡ„ж„ҝжңӣеҚҙжҳҜжҷ®йҒҚиҖҢе…ұеҗҢзҡ„гҖӮ欧жҙІд»ҘеӨ–ең°еҢәеңЁз»ҸеҺҶиҝҮзҺ°д»Јжҙ—зӨјеҗҺпјҢд№ҹеҗҢж ·е‘ҲзҺ°дәҶдёҺ欧жҙІдәәдёҖж ·зҡ„еҜ№дәҺ科еӯҰзҡ„жӢҘжҠӨгҖӮеңЁ20дё–зәӘеҲқжңҹпјҢиӢұеӣҪе“ІеӯҰ家жҖҖзү№жө·гҖҒзҪ—зҙ йғҪеҜ№жӯӨиЎЁиҫҫдәҶеқҡе®ҡзҡ„и®ӨеҗҢгҖӮжҖҖзү№жө·жҳҺзЎ®ең°иҜҙ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зҡ„家жҳҜе…Ёдё–з•ҢгҖӮ1920вҖ”1921е№ҙпјҢзҪ—зҙ жӣҫеҲ°дёӯеӣҪи®ІеӯҰпјҢиў«дёӯеӣҪдәәеҜ№дәҺ科еӯҰзҡ„зғӯжғ…ж·ұж·ұж„ҹжҹ“гҖӮ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дҫқжүҳеҗ„иҮӘзӨҫдјҡпјҢдёҚж–ӯеҸ‘еұ•еҮәеҗ„з§Қ科еӯҰжҠҖжңҜпјҢдә’зӣёдәӨжөҒпјҢеҪјжӯӨеҪұе“ҚпјҢжңҖз»ҲжұҮжҲҗ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еӨ§жҪ®пјҢжҺЁеҠЁ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дә§з”ҹгҖӮеҰӮжһңз«ҷеңЁз§‘еӯҰ家зҡ„и§’еәҰпјҢе°ҡеҸҜд»Ҙж ҮжҰң欧жҙІиҝ‘代科еӯҰеҰӮдҪ•зӢ¬зү№пјҢдҪҶз«ҷеңЁеҺҶеҸІеӯҰ家зҡ„з«ӢеңәпјҢеҰӮжһңд»Қ然еҰӮжӯӨиҖғиҷ‘й—®йўҳ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ж Әе®ҲеҢәеҹҹд№ғиҮіеӣҪ家зҡ„и—©зҜұпјҢиҖҢжңӘзҗҶи§Ј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дә§з”ҹжҳҜж—©жңҹе…ЁзҗғдёҖдҪ“еҢ–жүҖеӮ¬з”ҹдј—еӨҡдё–з•ҢжҖ§еҸҳйқ©зҡ„дёҖдёӘж”ҜжөҒгҖӮиҖғеҜҹ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дёәдҪ•иө°дёҠдёҚеҗҢзҡ„科еӯҰйҒ“и·ҜпјҢз”ұжӯӨиҖҢеЎ‘йҖ дёҚеҗҢзҡ„еҺҶеҸІйҒ“и·ҜпјҢе°ҶжңүеҠ©дәҺжҸӯзӨәиҝ‘д»Ј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зҡ„еҺҶеҸІеҲҶйҖ”дёҺдё–з•ҢеҪұе“ҚгҖӮжӯЈжҳҜд»ҺиҝҷдёҖи§’еәҰеҮәеҸ‘пјҢиҘҝж–№дј—еӨҡжҖқжғіе®¶гҖҒ科еӯҰеҸІе®¶йғҪдё»еј иҝ‘代科еӯҰжҳҜз”ұдё–з•Ң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жүҖе…ұеҗҢжҺЁеҠЁдёҺеЎ‘йҖ зҡ„гҖӮеҹ№ж №гҖҒ马е…ӢжҖқдҫҝдё»еј ж¬§жҙІд№ӢжүҖд»Ҙдә§з”ҹ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ж—ўдёҺеҸӨеёҢи…Ҡ科еӯҰи§Ӯеҝөзҡ„еӨҚе…ҙжңүе…і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дёҺжқҘиҮӘдёңж–№зҡ„科жҠҖзҡ„еӮ¬еҠЁеҜҶеҲҮзӣёе…ігҖӮиҝҷд»Һ他们еҜ№дәҺдёүеӨ§еҸ‘жҳҺдё–з•Ңж„Ҹд№үзҡ„еҙҮй«ҳиҜ„д»·е°ұеҸҜд»ҘзңӢеҫ—еҮәжқҘгҖӮжӯӨеҗҺи®ёеӨҡжҖқжғіе®¶гҖҒ科еӯҰеҸІе®¶еҜ№дәҺ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ҖҖзү№жө·гҖҒиҗЁйЎҝгҖҒе·ҙдјҜзҡ„дёңиҘҝ方科еӯҰдёҚж–ӯжұҮеҗҲпјҢд№ғиҮіе…ұеҗҢдҝғиҝӣ科еӯҰйқ©е‘ҪеҸ‘з”ҹзҡ„и§ӮеҝөпјҢдёҚд»…еҜ№еҪ“时欧жҙІжҷ®йҒҚжөҒиЎҢзҡ„科еӯҰжҳҜ欧жҙІзӢ¬зү№дә§зү©зҡ„и§ӮеҝөеҪўжҲҗдәҶејәзғҲжҢ‘жҲҳпјҢиҖҢдё”еҜ№дәҺжқҺзәҰз‘ҹзҡ„дёӯеӣҪ科еӯҰз ”з©¶еҸҠзӣёе…іи§Ӯеҝөзҡ„еҪўжҲҗпјҢжһ„жҲҗдәҶдёҖз§ҚзҶҸжҹ“е…¶дёӯзҡ„иҲҶи®әж°ӣеӣҙгҖӮиӢұеӣҪе“ІеӯҰ家жҖҖзү№жө·еҜ№з§‘еӯҰзҡ„жёҠжәҗдёҺ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дә§з”ҹ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иҮӘе·ұзҡ„зңӢжі•гҖӮд»–и®Өдёә科еӯҰзҡ„жәҗеӨҙжҳҜдёңиҘҝж–№е…ұеҗҢжһ„жҲҗзҡ„пјҢиҖҢйқһ欧жҙІдёҖж”ҜгҖӮ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д»–еҸҲи®Өдёәиҝ‘代科еӯҰжҳҜ欧жҙІзҡ„зӢ¬зү№дә§зү©пјҢеҢ…жӢ¬дёӯеӣҪеңЁеҶ…зҡ„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пјҢжҳҜжіЁе®ҡдёҚдјҡдә§з”ҹ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гҖӮиҷҪ然д»Ҙ科еӯҰеҸҳиҝҒзҡ„еҺҶеҸІдҪңдёәз ”з©¶еҜ№иұЎзҡ„科еӯҰеҸІеңЁеҸӨеёҢи…Ҡж—¶жңҹе°ұе·Із»ҸиҗҢиҠҪпјҢдҪҶзҺ°еңЁдёҖиҲ¬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科еӯҰеҸІпјҢе§ӢдәҺ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иҜһз”ҹгҖӮиҖҢеҜ№иҝҷдёҖеӯҰ科иҙЎзҢ®жңҖеӨ§зҡ„жҳҜиҗЁйЎҝгҖӮ科еӯҰеҸІеҲӣе§Ӣдәәд№”жІ»В·иҗЁйЎҝеңЁз§‘еӯҰеҸІзҡ„з«ӢеңәдёҠпјҢдёҺжҖҖзү№жө·зӣёе‘јеә”гҖӮиҗЁйЎҝжҖ»з»“дәҶеүҚдәәзҡ„科еӯҰеҸІз ”究жҖқи·ҜпјҢ并иҝӣдёҖжӯҘеӨ§еҠӣйҳҗйҮҠдёҺеҸ‘жү¬пјҢд»ҺиҖҢеҲӣе»әдәҶвҖң科еӯҰеҸІвҖқиҝҷй—ЁеӯҰ科пјҢ并й•ҝжңҹеҪұе“ҚгҖҒеЎ‘йҖ дәҶиҝҷдёҖеӯҰ科зҡ„еҹәжң¬еҸ–еҗ‘гҖӮиҗЁйЎҝи®Өдёә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зҡ„科еӯҰеҸ‘еұ•е№¶дёҚеҗҢжӯҘгҖӮеҹғеҸҠгҖҒзҫҺзҙўдёҚиҫҫзұідәҡгҖҒдјҠжң—гҖҒеҚ°еәҰгҖҒдёӯеӣҪеңЁеҶ…зҡ„дёңж–№ж–ҮжҳҺпјҢжҳҜ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жәҗеӨҙпјҢ科еӯҰдј з»ҹжҜ”欧жҙІжӣҙдёәжӮ д№…пјҢ欧жҙІеҲҷеңЁжҺҘзәідёңж–№ж–ҮжҳҺ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еҠ д»ҘеҸ‘еұ•пјҢиҝҷе…¶дёӯе°ұеҢ…жӢ¬иҝ‘代科еӯҰиҜһз”ҹзҡ„йҮҚеӨ§дәӢ件гҖӮ欧жҙІз»ҸеҺҶдәҶ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й•ҝжңҹй»‘жҡ—дёҺ科еӯҰжӣІжҠҳпјҢжңҖз»Ҳиө°дёҠ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д№Ӣи·ҜпјҢдёҺдёң方科еӯҰе‘ҲзҺ°дәҶеҺҶеҸІеҲҶйҖ”гҖӮиҗЁйЎҝжҳҺзЎ®жҢҮеҮә欧жҙІд№ӢжүҖд»ҘиғҪеӨҹеҸ‘еұ•еҮә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з”ұдәҺеӨҚе…ҙдәҶеёҢи…Ҡзҡ„科еӯҰдј з»ҹпјҢ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№ҹеҗёзәідәҶдёңж–№зҡ„科еӯҰдј з»ҹпјҢе…·дҪ“еҲ°ж¬§жҙІдәәдёҖзӣҙж ҮжҰңзҡ„е®һйӘҢзІҫзҘһд№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®һйӘҢ科еӯҰдёҚжҳҜиҘҝж–№зҡ„зӢ¬зү№еҲӣйҖ пјҢиҖҢжҳҜдёңиҘҝ方科еӯҰзҡ„е…ұеҗҢдә§зү©гҖӮиҖҢжқҘиҮӘдёңж–№зҡ„еҚ°еҲ·жңҜеңЁиҝ‘代科еӯҰеҪўжҲҗдёӯпјҢеҗҢж ·жү®жј”дәҶеҚҒеҲҶе…ій”®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еҰӮжһңд»Һдәәзұ»еҺҶеҸІзҡ„ж•ҙдҪ“и§’еәҰжқҘзңӢпјҢдёҚеҗҢж—¶жңҹ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йҮҚеҝғең°еҢәжҳҜдёҚж–ӯ游移зҡ„гҖӮиҗЁйЎҝе°ҶеҺҶеҸІдёҠзҡ„科еӯҰеҸ‘еұ•пјҢеҲ’еҲҶдёәеӣӣдёӘйҳ¶ж®өпјҢдёңиҘҝж–№еӨ§дҪ“иҖҢиЁҖжҳҜе№іеҲҶз§ӢиүІзҡ„гҖӮж•…иҖҢдёҚеә”е°ҶдёңиҘҝ方科еӯҰд№ғиҮізӨҫдјҡиҝӣиЎҢеүІиЈӮдёҺеҜ№з«ӢпјҢжӣҙдёҚеә”е°ҶеҢ…жӢ¬иҝ‘代科еӯҰеңЁеҶ…зҡ„иҝ‘д»Јж–ҮжҳҺи§ҶдҪң欧жҙІзӢ¬з«ӢеҸ‘еұ•зҡ„зӢ¬зү№дә§зү©гҖӮд»–з”ҡиҮіжү№й©іж¬§жҙІз§‘еӯҰжҳҜиҝӣжӯҘзҡ„пјҢдёӯеӣҪ科еӯҰжҳҜеҒңж»һзҡ„еӣәжңүи§ӮеҝөпјҢжҢҮеҮә欧жҙІ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科еӯҰд№ҹдёҖж ·йҷ·е…ҘдәҶеҒңж»һпјҢе…¶еҺҹеӣ дёҺеёҢи…Ҡ科еӯҰзҡ„ж—©ж…§иҖҢиЎ°жңүе…ігҖӮеңЁиҗЁйЎҝзңӢжқҘпјҢдёңиҘҝж–№з»Ҳе°ҶеҶҚж¬ЎжұҮеҗҲгҖӮиҘҝж–№дәәеә”иҜҘж”ҫејғеҺҹжңүзҡ„еӮІж…ўпјҢд»Һ科еӯҰзІҫзҘһеҮәеҸ‘пјҢз§үжҢҒвҖңж–°дәәж–Үдё»д№үвҖқзҡ„з«ӢеңәпјҢе…ұеҗҢжҲҗй•ҝдёәжӣҙдёәй«ҳе°ҡзҡ„дәәзұ»гҖӮдәҢгҖҒ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дёӯиҘҝдә’и§Ҷ 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пјҢеңЁз”ҹзү©иғҡиғҺеӯҰйўҶеҹҹе·Із»ҸеҚ“жңүжҲҗе°ұзҡ„жқҺзәҰз‘ҹпјҢеңЁеү‘жЎҘеӨ§еӯҰи®ӨиҜҶдәҶжқҘиҮӘдёӯеӣҪ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пјҢдёәд»–жү“ејҖдәҶи®ӨиҜҶдёӯеӣҪ科еӯҰдёҺж–ҮжҳҺзҡ„дёҖжүҮзӘ—жҲ·пјҢд»ҺжӯӨд»–е°Ҷз ”з©¶йўҶеҹҹиҪ¬еҗ‘дәҶ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科еӯҰдёҺж–ҮжҳҺгҖӮеҮәдәҺеҜ№дёӯеӣҪ科еӯҰдёҺж–ҮжҳҺзҡ„зғӯзҲұе’ҢеҜ№дёӯеӣҪжҠ—жҲҳзҡ„з§ҜжһҒж”ҜжҢҒпјҢ1942е№ҙ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ңЁиӢұеӣҪж–ҮеҢ–委е‘ҳдјҡе’ҢиӢұеӣҪз”ҹдә§йғЁзҡ„ж”ҜжҢҒдёӢпјҢжқҘеҲ°дёӯеӣҪпјҢе»әз«Ӣиө·дёӯиӢұ科еӯҰеҗҲдҪңйҰҶпјҢйҖҡиҝҮе№ҝжіӣйҳ…иҜ»дёӯеӣҪ科еӯҰж–ҮзҢ®гҖҒдёҺдёӯеӣҪзІҫиӢұ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жҷ®йҒҚдәӨеҫҖпјҢжһҒеӨ§ең°еҠ ж·ұдәҶеҜ№дёӯеӣҪ科еӯҰдёҺж–ҮжҳҺзҡ„дәҶи§ЈпјҢеӨ§еҠӣжҺЁеҙҮдёӯеӣҪ科еӯҰеңЁдё–з•Ң科еӯҰдёӯзҡ„йҮҚиҰҒең°дҪҚгҖӮжқҺзәҰз‘ҹи®Өдёә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йғҪеҸ‘еұ•еҮәдәҶеҗ„иҮӘзҡ„科еӯҰж”ҜжөҒпјҢйҖҗжёҗжұҮиҒҡ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е…ұеҗҢжҺЁеҠЁ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дә§з”ҹгҖӮиҖҢеңЁиҝҷд№ӢдёӯпјҢдёӯеӣҪ科еӯҰе°ұжү®жј”дәҶ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зҡ„и§’иүІгҖӮж—©еңЁ1964е№ҙ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Ҹ‘иЎЁзҡ„гҖҠдёӯеӣҪ科еӯҰеҜ№дё–з•Ң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е°ұе·Із»Ҹ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жҳ”ж—Ҙзҡ„科жҠҖеӨ§жІіжұҮжөҒе…ҘзҺ°д»ЈиҮӘ然зҹҘиҜҶзҡ„еӨ§жҙӢдёӯвҖқ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1967е№ҙ8жңҲ31ж—Ҙ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ңЁиӢұеӣҪ科еӯҰдҝғиҝӣдјҡеҲ©е…№е№ҙдјҡдёҠеҸ‘иЎЁдәҶд»ҘвҖң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жј”иҝӣвҖ”вҖ”欧жҙІдёҺдёӯеӣҪзҡ„дҪңз”ЁвҖқдёәдё»йўҳзҡ„и®Іжј”пјҢеҶҚж¬ЎеҒҡдәҶжӣҙдёәдё°еҜҢиҖҢз”ҹеҠЁзҡ„жҜ”е–»вҖ”вҖ”вҖңжңқе®—дәҺжө·вҖқгҖӮиҜҘз”Ёд»Җд№ҲжқҘжҜ”е–»иҘҝж–№е’Ңдёңж–№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科еӯҰжұҮе…Ҙ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зҡ„иҝӣзЁӢе‘ўпјҹд»ҺдәӢиҝҷж–№йқўе·ҘдҪңзҡ„дәәдјҡиҮӘ然иҖҢ然ең°жғіеҲ°жұҹжІіе’Ңжө·жҙӢгҖӮдёӯеӣҪжңүеҸҘеҸӨиҜқпјҢвҖңжңқе®—дәҺжө·вҖқгҖӮзҡ„зЎ®пјҢе®Ңе…ЁеҸҜд»Ҙи®ӨдёәпјҢ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зҡ„еҸӨиҖҒзҡ„科еӯҰз»ҶжөҒпјҢжӯЈеғҸжұҹжІідёҖж ·еҘ”еҗ‘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зҡ„жұӘжҙӢеӨ§жө·гҖӮ 1981е№ҙпјҢеңЁдёҖж¬ЎеӯҰжңҜеҜ№и°Ҳдёӯ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иЎЁиҫҫдәҶеҗҢж ·зҡ„ж„ҸжҖқгҖӮжҲ‘и®Өдёәиҝ‘代科еӯҰжҳҜжүҖжңүеҸӨд»Јдәәзұ»дј з»ҹйҒ—дә§зҡ„з»“жҷ¶гҖӮеҪ“然пјҢе®ғжңҖеҲқжҳҜеңЁж¬§жҙІиў«з»ҹеҗҲзҡ„пјҢдҪҶжҳҜе®ғ并дёҚеҸӘеҹәдәҺ欧жҙІдј з»ҹд№ӢдёҠпјҢеңЁжӯӨд№ӢеүҚзҡ„жүҖжңүж–ҮжҳҺйғҪжҳҜжңүиҙЎзҢ®зҡ„гҖӮиҝҷдёҺдёӯеӣҪзҡ„вҖңзҷҫе·қеҪ’жө·вҖқзҡ„жҖқжғіж–№жі•жҳҜеҗҢж ·зҡ„гҖӮ жүҖи°“вҖңзҷҫе·қеҪ’жө·вҖқпјҢе’ҢвҖңжңқе®—дәҺжө·вҖқпјҢж„ҸжҖқжҳҜдёҖж ·зҡ„пјҢеҸӘжҳҜдёҚеҗҢзҡ„зҝ»иҜ‘гҖӮжқҺзәҰз‘ҹеңЁ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 ”з©¶йўҶеҹҹдёӯпјҢеј•еҸ‘е·ЁеӨ§дәүи®®зҡ„дёҖйЎ№з ”з©¶пјҢе°ұжҳҜжҸҗеҮәдәҶ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гҖӮзҺӢеӣҪеҝ и®ӨдёәеңЁ20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·Із»ҸиҗҢз”ҹеҮә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гҖӮ14дё–зәӘеүҚзҡ„дёӯеӣҪпјҢ科еӯҰжҠҖжңҜдёҖзӣҙйўҶе…ҲдәҺиҘҝж–№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дёӯеӣҪеҗҺжқҘжІЎиғҪиҮӘеҸ‘ең°дә§з”ҹиҝ‘代科еӯҰпјҹиҖҢиҝ‘代科еӯҰдёәдҪ•д»…д»…еңЁиҘҝж–№е…ҙиө·пјҹ3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°ұ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еҗ‘и‘—еҗҚз»ҸжөҺеӯҰ家зҺӢдәҡеҚ—иҜ·ж•ҷпјҢзҺӢеҗҺжқҘиҷҪд»Ҙд»–йӮЈеҶҢгҖҠдёӯеӣҪе®ҳеғҡж”ҝжІ»зҡ„з ”з©¶гҖӢдҪңзӯ”пјҢеү–жһҗдәҶдёӯеӣҪе®ҳеғҡж”ҝжІ»иҝҷдёҖдёәе®із”ҡзғҲзҡ„вҖңд№қеӨҙиӣҮвҖқпјҢдҪҶиҝҷд»…жҳҜвҖңйҡҫйўҳвҖқзҡ„дёҖдёӘдҫ§йқўпјҢй—®йўҳиҝңжңӘеҫ—д»Ҙе…Ёйқўи§ЈйҮҠгҖӮ жқҺзәҰз‘ҹеңЁиҝҷйҮҢжҸҗеҮәдёәд»Җд№ҲдёӯеӣҪжІЎжңүеҰӮеҗҢ欧жҙІйӮЈж ·дә§з”ҹ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иҷҪ然关注зҡ„йҮҚеҝғжҳҜ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дҪҶи§Ҷи§’еҚҙжқҘиҮӘдәҺе’Ң欧жҙІзҡ„еҜ№жҜ”пјҢеӣ жӯӨд»Қ然жҳҜдёҖз§ҚеҸҚжҳ вҖң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вҖқзҡ„欧жҙІи§Ҷи§’гҖӮжҚ®жқҺзәҰз‘ҹеңЁгҖҠдёңиҘҝж–№зҡ„科еӯҰдёҺзӨҫдјҡ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зҡ„иҜҙжі•пјҢд»–ж—©еңЁ1938е№ҙж—¶пјҢе°ұе·Із»ҸејҖе§ӢжҖқиҖғ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гҖӮдёҖд№қдёүе…«е№ҙе·ҰеҸіпјҢеҪ“жҲ‘еҠЁеҝөжғіеҶҷдёҖйғЁжңүзі»з»ҹзҡ„гҖҒе®ўи§Ӯзҡ„гҖҒд»ҘеҸҠжқғеЁҒжҖ§зҡ„и®әж–ҮпјҢд»Ҙи®Ёи®әдёӯеӣҪж–ҮеҢ–еҢәзҡ„科еӯҰеҸІгҖҒ科еӯҰжҖқжғіеҸІдёҺжҠҖжңҜеҸІж—¶пјҢжҲ‘е°ұжіЁж„ҸеҲ°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ҡдёәд»Җд№Ҳ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еҸӘиғҪеңЁж¬§жҙІеҸ‘еұ•пјҢиҖҢж— жі•еңЁдёӯеӣҪпјҲжҲ–еҚ°еәҰпјүж–ҮжҳҺдёӯжҲҗй•ҝпјҹ жӯӨеҗҺ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дёҚж–ӯж’°еҶҷж–Үз« гҖҒеҸ‘иЎЁи®Іжј”пјҢжҺЁеҠЁдәҶ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йҖҗжёҗжҳҺзЎ®е’ҢжҲҗзҶҹгҖӮ1954е№ҙиө·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йҷҶз»ӯеҮәзүҲдәҶеӨҡеҚ·жң¬йёҝзҜҮе·ЁеҲ¶гҖҠдёӯеӣҪ科еӯҰжҠҖжңҜеҸІгҖӢпјҢйҖҡиҝҮе…ЁйқўеҜ№з…§дёӯгҖҒиҘҝ科еӯҰжҲҗе°ұ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еқҡе®ҡдәҶд»–зҡ„иҝҷдёҖи§ӮзӮ№пјҢ并йҮҮз”Ёи®ҫй—®зҡ„еҪўејҸпјҢжһ„жҲҗдәҶ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е®Ңж•ҙзүҲжң¬гҖӮдёӯеӣҪзҡ„科еӯҰдёәд»Җд№ҲжҢҒз»ӯеҒңз•ҷеңЁз»ҸйӘҢйҳ¶ж®өпјҢ并且еҸӘжңүеҺҹе§ӢеһӢзҡ„жҲ–дёӯеҸӨеһӢзҡ„зҗҶи®әпјҹеҰӮжһңдәӢжғ…зЎ®е®һжҳҜиҝҷж ·пјҢйӮЈд№ҲеңЁз§‘еӯҰжҠҖжңҜеҸ‘жҳҺзҡ„и®ёеӨҡйҮҚиҰҒж–№йқўпјҢдёӯеӣҪдәәеҸҲжҖҺж ·жҲҗеҠҹең°иө°еңЁйӮЈдәӣеҲӣйҖ еҮәи‘—еҗҚвҖңеёҢи…ҠеҘҮиҝ№вҖқзҡ„дј еҘҮејҸдәәзү©зҡ„еүҚйқўпјҢе’ҢжӢҘжңүеҸӨд»Ј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е…ЁйғЁж–ҮеҢ–иҙўеҜҢзҡ„йҳҝжӢүдјҜдәә并й©ҫйҪҗй©ұпјҢ并еңЁ3еҲ°13дё–зәӘд№Ӣй—ҙдҝқжҢҒдёҖдёӘиҘҝж–№жүҖжңӣе°ҳиҺ«еҸҠзҡ„科еӯҰзҹҘиҜҶж°ҙе№іпјҹдёӯеӣҪеңЁзҗҶи®әе’ҢеҮ дҪ•еӯҰж–№жі•дҪ“зі»ж–№йқўжүҖеӯҳеңЁзҡ„ејұзӮ№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并没жңүеҰЁзўҚеҗ„з§Қ科еӯҰеҸ‘зҺ°е’ҢжҠҖжңҜеҸ‘жҳҺзҡ„ж¶ҢзҺ°пјҹдёӯеӣҪзҡ„иҝҷдәӣеҸ‘жҳҺе’ҢеҸ‘зҺ°еҫҖеҫҖиҝңиҝңи¶…иҝҮеҗҢж—¶д»Јзҡ„欧жҙІ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15дё–зәӘд№ӢеүҚжӣҙжҳҜеҰӮжӯӨпјҲе…ідәҺиҝҷдёҖзӮ№еҸҜд»ҘжҜ«дёҚиҙ№еҠӣең°еҠ д»ҘиҜҒжҳҺпјүгҖӮ欧жҙІеңЁ16дё–зәӘд»ҘеҗҺе°ұиҜһз”ҹдәҶ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иҝҷз§Қ科еӯҰе·Іиў«иҜҒжҳҺжҳҜеҪўжҲҗиҝ‘д»Јдё–з•Ң秩еәҸзҡ„еҹәжң¬еӣ зҙ д№ӢдёҖпјҢиҖҢдёӯеӣҪж–ҮжҳҺеҚҙжңӘиғҪеңЁдәҡжҙІдә§з”ҹдёҺжӯӨзӣёдјјзҡ„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е…¶йҳ»зўҚеӣ зҙ 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ҸҲжҳҜд»Җд№Ҳеӣ зҙ дҪҝеҫ—科еӯҰеңЁдёӯеӣҪж—©жңҹзӨҫдјҡдёӯжҜ”еңЁеёҢи…ҠжҲ–欧жҙІдёӯеҸӨзӨҫдјҡдёӯжӣҙе®№жҳ“еҫ—еҲ°еә”з”ЁпјҹжңҖеҗҺ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дёӯеӣҪеңЁз§‘еӯҰзҗҶи®әж–№йқўиҷҪ然жҜ”иҫғиҗҪеҗҺпјҢдҪҶеҚҙиғҪдә§з”ҹеҮәжңүжңәзҡ„иҮӘ然и§Ӯпјҹиҝҷз§ҚиҮӘ然и§ӮиҷҪ然еңЁдёҚеҗҢзҡ„еӯҰжҙҫйӮЈйҮҢжңүдёҚеҗҢеҪўејҸзҡ„и§ЈйҮҠпјҢдҪҶе®ғе’Ңиҝ‘代科еӯҰз»ҸиҝҮжңәжў°е”Ҝзү©и®әз»ҹжІ»дёүдёӘдё–зәӘд№ӢеҗҺиў«иҝ«йҮҮзәізҡ„иҮӘ然и§ӮйқһеёёзӣёдјјгҖӮ 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пјҢеҲ°гҖҠдёӯеӣҪ科еӯҰжҠҖжңҜеҸІгҖӢеҶҷдҪңзҡ„йҳ¶ж®ө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Ҝ№дәҺ科жҠҖдёҺдёӯеӣҪзҡ„е…ізі»й—®йўҳпјҢжҖқиҖғеҫ—жӣҙдёәжҲҗзҶҹпјҢдёҚд»…еҢ…жӢ¬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‘代科еӯҰдә§з”ҹдәҺ欧жҙІ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дә§з”ҹдәҺдёӯеӣҪвҖқзҡ„欧жҙІи§Ҷи§’пјҢиҝҳеҢ…жӢ¬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еңЁж–ҮиүәеӨҚе…ҙд»ҘеүҚпјҢдёӯеӣҪ科жҠҖжҜ”欧жҙІжӣҙдёәе…ҲиҝӣвҖқзҡ„дёӯеӣҪи§Ҷи§’гҖӮ1976е№ҙпјҢзҫҺеӣҪз»ҸжөҺеӯҰ家иӮҜе°јжҖқВ·еҚҡе°”дёҒ(Kenneth Ewart Boulding)жҠҠжқҺзәҰз‘ҹзҡ„з–‘й—®ејҖе§Ӣз§°дҪң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Ҳthe Needham Question or Needham Grand QuestionпјүгҖӮвҖңдәҢжҲҳвҖқд»ҘеҗҺпјҢеҢ…жӢ¬иҘҝж–№еңЁеҶ…зҡ„ж•ҙдёӘдё–з•ҢпјҢеңЁеҜ№иҘҝж–№ж–ҮжҳҺејҖеұ•ж•ҙдҪ“еҸҚжҖқд№ғиҮіжү№еҲӨзҡ„жҖқжҪ®д№ӢдёӢпјҢеңЁеҗ„дёӘйўҶеҹҹйғҪеңЁеұ•зҺ°еҜ»жұӮ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дё»дҪ“жҖ§зҡ„ж—¶д»ЈиҜүжұӮгҖӮеҙӣиө·зҡ„第дёүдё–з•ҢеҜ№вҖң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вҖқи§Ҷи§’дёӢзҡ„вҖңдёңж–№еӯҰвҖқзҡ„жү№еҲӨжҪ®жөҒпјҢе°ұжҳҜиЎЁеҫҒд№ӢдёҖгҖӮжқҺзәҰз‘ҹеҖҹеҠ©е…¶иҘҝ方科еӯҰ家зҡ„иә«д»ҪпјҢд»ҺдёӯеӣҪ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жҢ–жҺҳ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зҡ„иҫүз…ҢжҲҗе°ұпјҢдёҚдҪҶеҘ‘еҗҲдәҶвҖңдәҢжҲҳвҖқд»ҘеҗҺеҜ»жүҫ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科еӯҰдё»дҪ“жҖ§зҡ„еӣҪйҷ…жҖқжҪ®пјҢжӣҙиҝҺеҗҲдәҶж—Ҙжёҗеҙӣиө·зҡ„дёӯеӣҪиҺ·еҫ—зҺ°д»Јж–ҮжҳҺзҡ„и®ӨеҸҜйҮҚеЎ‘ж°‘ж—ҸиҮӘдҝЎзҡ„ж—¶д»ЈеҝғзҗҶпјҢд»ҺиҖҢеңЁе…Ёдё–з•Ңе°Өе…¶еңЁдёӯеӣҪдә§з”ҹеҮәе·ЁеӨ§зҡ„еӯҰжңҜд№ғиҮізӨҫдјҡж•Ҳеә”гҖӮ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иҝңиҝңи¶…еҮәд№ӢеүҚжүҖжңүжҺўи®Ёзӣёдјјй—®йўҳ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д№ғиҮі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§Қ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жғ…з»“вҖқгҖӮдёүгҖҒ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иҙЁз–‘дёҺеҸҚжҖқ 20дё–зәӘеҗҺжңҹпјҢдёӯеӨ–еӯҰз•Ңе°Өе…¶иҘҝж–№еӯҰз•ҢпјҢејҖе§ӢйҖҗжёҗеҸҚжҖқгҖҒиҙЁз–‘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дјӘ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з”ҡиҮіи®Өдёә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жҳҜвҖң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вҖқпјҢдё»еј и·іеҮәиҝҷдёҖе‘ҪйўҳпјҢеҜ№е…¶з«Ӣж„ҸгҖҒйҖ»иҫ‘дёҺз»“и®әзҡ„еҗҲзҗҶжҖ§пјҢеұ•ејҖж №жң¬жҖ§д№ғиҮійў иҰҶжҖ§зҡ„иҙЁз–‘з”ҡиҮіжү№еҲӨгҖӮ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еҸҚжҖқпјҢд»ҺиҘҝж–№еӯҰз•ҢжңҖе…ҲејҖе§ӢпјҢиҘҝж–№еӯҰиҖ…иӨ’иҙ¬дёҚдёҖпјҢдәүи®әеҫҲеӨ§гҖӮ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жІҷе°”В·йӣ·ж–Ҝи’ӮжІғжҢҮеҮәиҘҝж–№еӯҰиҖ…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дёӯзҡ„第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е…·жңүеӣӣз§ҚдёҚеҗҢзҡ„жҖҒеәҰгҖӮдёҖжҳҜеҰӮеҗҢжң¬-еӨ§еҚ«пјҲJoseph Ben-Davidпјүзҡ„и§ӮзӮ№йӮЈж ·пјҢдёӯеӣҪдә§з”ҹ科еӯҰйқ©е‘ҪпјҢвҖңд»ҺжҷәеҠӣдёҠзңӢжҳҜеҸҜиғҪзҡ„вҖқпјҢд№ҹеҚ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жҳҜжҲҗз«Ӣзҡ„гҖӮдәҢжҳҜеҰӮеҗҢзҫҺеӣҪ科еӯҰеҸІе®¶еёӯж–ҮйӮЈж ·пјҢ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иҷҪ然жҲҗз«ӢпјҢдҪҶеңЁеҲқжӯҘйўҶдјҡдёӯеӣҪ科еӯҰд№ӢеүҚпјҢж— жі•еҜ№е…¶ејҖеұ•е……еҲҶз ”з©¶гҖӮдёүжҳҜеҰӮеҗҢзҫҺеӣҪжұүеӯҰ家иҠ®жІғеҜҝйӮЈж ·пјҢвҖңеҜ№дёӯеӣҪж–ҮеҢ–еҝ…йЎ»жҢүе…¶иҮӘиә«зҡ„дҪ“зі»еҒҡж•ҙдҪ“зҗҶи§ЈпјҢеҜ№е…¶еҸ‘еұ•ж— йЎ»иҜүиҜёе…ЁзҗғжҖ§дё–з•Ң科еӯҰе’ҢеҗҲдҪңзҡ„ж°‘дё»дё–з•Ңзҡ„зӣ®зҡ„и®әи§ӮеҝөвҖқгҖӮеӣӣжҳҜдёҖдәӣиҘҝ方科еӯҰеҸІе®¶и®ӨдёәвҖңзңҹжӯЈзҡ„вҖқ科еӯҰеҸІеҹәжң¬дёҠи°Ҳи®әзҡ„жҳҜиҘҝж–№зҡ„科еӯҰиғҢжҷҜгҖӮеҜ№дәҺ第дәҢ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еёӯж–Үзҡ„жү№й©іжңҖеҠӣ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жқҺзәҰз‘ҹжңӘе°Ҷ科еӯҰдёҺжҠҖжңҜиҝӣиЎҢзі»з»ҹеҢәеҲ«пјҢжүҖжҸҙеј•иҜҒжҚ®зҡ„е……еҲҶжҖ§д№ҹеҖјеҫ—иҙЁз–‘гҖӮдјҙйҡҸи§Јжһ„дё»д№үзҡ„е…ҙиө·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жүҖдё»еј зҡ„дё–з•Ң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зҷҫе·қеҪ’жө·пјҢиў«и§ҶдёәжҳҜдёҖз§ҚзәҝжҖ§дё»д№үеҸ‘еұ•еҸІи§ӮпјҢиў«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йў иҰҶгҖӮ1978е№ҙпјҢиӢұеӣҪжҠҖжңҜеҸІдё“家жҖҖзү№жҢҮеҮәжқҺзәҰз‘ҹжүҖз§үжҢҒзҡ„еҚ•зәҝиҝӣжӯҘзҡ„жҖқз»ҙж–№ејҸе·Із»ҸеғөеҢ–иҝҮж—¶пјҢдј—еӨҡдәӨдә’дҪңз”Ёзҡ„еӣ зҙ жҳҜеҝ…йЎ»иҰҒиҖғиҷ‘зҡ„гҖӮ20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пјҢзҫҺеӣҪ科еӯҰеҸІе®¶еёӯж–Ү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еұ•ејҖдәҶжңҖдёәзі»з»ҹзҡ„иҫ©й©ігҖӮеңЁгҖҠдёәд»Җд№Ҳ科еӯҰйқ©е‘ҪжІЎжңүеңЁдёӯеӣҪеҸ‘з”ҹвҖ”вҖ”жҳҜеҗҰжІЎжңүеҸ‘з”ҹ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пјҢд»–з”ЁдёҖдёӘйҖҡдҝ—жҳ“жҮӮ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иЎЁиҫҫеҮәдәҶ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еҳІи®Ҫ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жҸҗеҮә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еҗҢжҸҗеҮәдёәд»Җд№ҲдҪ зҡ„еҗҚеӯ—жІЎжңүеҮәзҺ°еңЁд»ҠеӨ©жҠҘзәёз¬¬дёүзүҲдёҠиҝҷж ·зҡ„й—®йўҳжҳҜеҫҲзӣёдјјзҡ„гҖӮе®ғеұһдәҺдёҖз»„еҸҜд»Ҙж— дј‘жӯўең°дёҚж–ӯжҸҗдёӢеҺ»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еӣ дёәеҫ—дёҚеҲ°зӣҙжҺҘзҡ„зӯ”жЎҲ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еҺҶеҸІеӯҰ家жҳҜдёҚдјҡжҸҗиҝҷз§Қй—®йўҳзҡ„гҖӮе®ғ们дјҡеҸҳжҲҗе…¶д»–д»Қ然жҳҜй—®йўҳ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 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ёӯж–ҮеҸҲи®Өдёә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»ҷдәә们еёҰжқҘдәҶжҹҗз§ҚеҗҜеҸ‘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дәә们зҡ„жҺўзҙўгҖӮ1994е№ҙпјҢ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жҲҙз»ҙВ·е…°еҫ·ж–ҜпјҲDavid LandesпјүжҢҮеҮә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иө°еҗ‘дәҶвҖңдёҖдёӘиҫүз…Ңзҡ„жӯ»иғЎеҗҢвҖқпјҢ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科еӯҰ并йқһжҳҜжҢҒз»ӯеҸ‘еұ•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й—ҙж–ӯжҖ§зҡ„гҖӮеҗҢе№ҙпјҢиҚ·е…°з§‘еӯҰеҸІе®¶еј—жҙӣйҮҢж–Ҝ·科жҒ©пјҲH. Floris CohenпјүиЎЁжҳҺиҮӘе·ұ并дёҚеҗҢж„ҸжқҺзәҰз‘ҹвҖңзҷҫе·қеҪ’жө·вҖқ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и®ӨдёәжҠҖжңҜеҸҜд»ҘзӣёеҜ№е®№жҳ“ең°дј ж’ӯеҲ°еҗ„дёӘең°ж–№пјҢдҪҶеҸӘжңүеңЁжһҒе°‘ж•°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ёҖз§Қж–ҮжҳҺзҡ„и§Ғи§ЈжүҚиғҪиў«еҸҰдёҖз§Қж–ҮжҳҺжүҖйҮҮзәігҖӮдёӯеӣҪдёҺ欧жҙІеңЁжҖқз»ҙж–№ејҸдёҠиө°еҗ‘дәҶдёҚеҗҢ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пјҢеҸӨеёҢи…Ҡд»ҘжқҘзҡ„欧жҙІиө°дёҠдәҶдёҖжқЎвҖңжңәжў°и®әзҡ„еӣ жһңе…ізі»вҖқд№Ӣи·ҜпјҢдёӯеӣҪеҲҷиө°дёҠдәҶдёҖжқЎдәӢзү©д№Ӣй—ҙвҖңзӣёдә’е…іиҒ”вҖқзҡ„жҖқз»ҙйҒ“и·ҜгҖӮ2010е№ҙпјҢжі•еӣҪеӯҰиҖ…жў…еЎ”жӨ°гҖҠжҺўжһҗдёӯеӣҪдј з»ҹжӨҚзү©еӯҰзҹҘиҜҶ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д№ҹи®Өдёә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жҳҜдёҖдёӘз”ЁиҘҝж–№жҰӮеҝөжқҘеҘ—дёӯеӣҪжҖқжғізҡ„дјӘе‘ҪйўҳгҖӮеңЁеҘ№зңӢ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дёҺиҘҝж–№зҡ„жӨҚзү©еӯҰеҸ‘еұ•пјҢиө°дәҶдёӨжқЎ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зҡ„и·ҜгҖӮдёҺиҝ‘д»ЈжӨҚзү©еӯҰзҡ„и§Јеү–ејҸи§’еәҰдёҚеҗҢпјҢ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жӨҚзү©еӯҰдј з»ҹпјҢжҳҜд»Һе“ІеӯҰе’Ңдәәж–Үзҡ„и§’еәҰпјҢеҜ№жӨҚзү©еұ•ејҖж•ҙдҪ“е’ҢдёӘжҖ§зҡ„иҖғйҮҸпјҢеӣ жӯӨ科еӯҰдёҺдәәж–Үе®Ңе…ЁеҸҜд»ҘйҖҡиҝҮж–ҮеҢ–е’ҢеҺҶеҸІз»ҹдёҖиө·жқҘгҖӮдёҺиҘҝж–№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д»Ҙжү№еҲӨдёәдё»дёҚеҗҢзҡ„жҳҜпјҢдҪңдёә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е…іжіЁеҜ№иұЎзҡ„дёӯеӣҪпјҢеҚҙй•ҝжңҹе‘ҲзҺ°еҮәеҜ№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жү§зқҖиҝҪжұӮпјҢд№ғиҮіеҪўжҲҗдёҖз§Қ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жғ…з»“вҖқгҖӮдҪҶдјҙйҡҸзқҖдё–з•ҢиҢғеӣҙеҶ…еҜ»жұӮ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дё»дҪ“жҖ§жҪ®жөҒ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еҗ„еӣҪйғҪеңЁеҠӘеҠӣ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иҮӘдё»жҖ§зҡ„и®ӨзҹҘдҪ“зі»гҖӮеңЁиҝҷз§ҚеҺҶеҸІжҪ®жөҒдёӢпјҢеҗ„иҮӘж–ҮжҳҺзҡ„еҺҶеҸІдј з»ҹйҮҚж–°еҪ°жҳҫгҖӮеңЁ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Із ”究дёӯпјҢеҜ»жұӮ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Ӣ¬зү№йҒ“и·Ҝзҡ„еЈ°йҹійҖҗжёҗеҮәзҺ°гҖӮ他们з«ҷеңЁиҝ‘代科еӯҰзҡ„з«ӢеңәдёҠпјҢеҸҚи§Ӯ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ејҖе§ӢдәҶ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ҸҚжҖқгҖҒиҙЁз–‘пјҢд№ғиҮіжү№еҲӨгҖӮ1972е№ҙпјҢеј зҹіи§’еҸ‘иЎЁдәҶгҖҠи®ә科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иҜһз”ҹдёҺиЎ°иҖҒ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еҸҚеҜ№жқҺзәҰз‘ҹе°Ҷ科жҠҖзҪ®дәҺз»ҸжөҺгҖҒзӨҫдјҡд№ӢдёӯеҺ»еҜ»жүҫдёҚеҗҢж°‘ж—Ҹ科еӯҰ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дә§з”ҹдёҚеҗҢзҡ„ж №жәҗ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ж ·зҡ„жҖқз»ҙпјҢиӢҘиҝӣдёҖжӯҘиҝҪжәҜпјҢеҸӘиғҪеҪ’з»“дёәжқҺзәҰз‘ҹжң¬дәәжүҖжү№еҲӨзҡ„з§Қж—Ҹдјҳи¶Ҡи®әгҖӮ1991е№ҙпјҢдҪ•дёҷйғҒеҸ‘иЎЁдәҶгҖҠиҜ•д»ҺеҸҰдёҖи§ӮзӮ№жҺўи®ЁдёӯеӣҪдј з»ҹ科жҠҖзҡ„еҸ‘еұ•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е·ІеҜ№жқҺзәҰз‘ҹд»Һ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зҡ„и§ӮзӮ№е®Ўи§ҶдёӯеӣҪ科жҠҖеҸІзҡ„еҒҡжі•еұ•ејҖдәҶеҸҚжҖқпјҢи®Өдёәд»ҘзҺ°д»Јзҡ„иЎЎйҮҸдёәеҮҶеҲҷпјҢиҜ„дј°дёӯеӣҪзҡ„дј з»ҹ科жҠҖе’ҢжҲҗе°ұпјҢиҷҪдёҚиғҪиҜҙи·‘й”ҷи·ҜзәҝпјҢдҪҶеҰӮжһңиғҪд»ҺеҸҰеӨ–зҡ„и§’еәҰиҝӣиЎҢе®Ўи§ҶпјҢе°ҶдјҡеҸ‘зҺ°д»ҺеүҚжІЎжңүжіЁж„Ҹ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1996е№ҙпјҢеёӯжіҪе®—еҸ‘иЎЁдәҶгҖҠе…ідәҺ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ҡҫйўҳвҖқе’Ңиҝ‘代科еӯҰжәҗдәҺеёҢи…Ҡзҡ„еҜ№иҜқ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и®ӨдёәеҺҶеҸІдёҠжІЎжңү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дёҚжҳҜеҺҶеҸІеӯҰе®¶з ”з©¶зҡ„еҜ№иұЎгҖӮ2001е№ҙпјҢжұҹжҷ“еҺҹеҸ‘иЎЁдәҶгҖҠиў«дёӯеӣҪдәәиҜҜиҜ»зҡ„жқҺзәҰз‘ҹгҖӢпјҢи®ӨдёәдёӯгҖҒиҘҝ科еӯҰ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并дёҚзӣёеҗҢпјҢжүҖи°“дёӯеӣҪ科жҠҖй•ҝжңҹйўҶе…Ҳзҡ„з»“и®ә并дёҚеӯҳеңЁпјҢ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жҜ«ж— ж„Ҹд№үгҖӮдёҚиҝ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д»–д№ҹи®ӨдёәеҚідҪҝжҳҜдјӘй—®йўҳпјҢд№ҹжңүеҗҜеҸ‘ж„Ҹд№үгҖӮ2004е№ҙпјҢйӮўе…ҶиүҜеҸ‘иЎЁгҖҠд»ҺзҲұеӣ ж–ҜеқҰи®әж–ӯеҲ°жқҺзәҰз‘ҹйҡҫйўҳвҖ”вҖ”д»Һ科еӯҰеҪўжҖҒзҡ„и§’еәҰиҝӣиЎҢзҡ„зҗҶи®әжҖқиҖғ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еҫ—еҮәдәҶд»ҘдёӢз»“и®әпјҡ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’ҢдҪңдёәиҝ‘代科еӯҰеҪўжҖҒеҹәеӣ зҡ„еҸӨеёҢи…Ҡ科еӯҰжҳҜдёӨз§Қ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зҡ„科еӯҰеҪўжҖҒгҖӮеҸӨеёҢи…Ҡ科еӯҰеҪўжҖҒжҳҜеҸ‘иӮІеҒҘеә·зҡ„ж—©жңҹ科еӯҰеҪўжҖҒпјҢе®ғе…·жңүеҗ‘иҝ‘гҖҒ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еҪўжҖҒеҸ‘иӮІжҲҗй•ҝзҡ„еҒҘеә·еҹәеӣ гҖӮ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ҪўжҖҒжҳҜж—©зҶҹзҡ„科еӯҰеҪўжҖҒ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еҸ‘иӮІгҖҒдә§з”ҹеҮәиҝ‘д»Јж„Ҹд№үзҡ„科еӯҰеҪўжҖҒпјҢд»Һ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еҸҜд»ҘиҜҙпјҢ15дё–зәӘд№ӢеүҚдёӯеӣҪзҡ„科еӯҰжҠҖжңҜй•ҝж—¶жңҹйўҶе…ҲдәҺеҗҢж—¶д»Јзҡ„欧жҙІзҡ„и®әж–ӯжҳҜдёҚжҲҗз«Ӣзҡ„гҖӮ2008е№ҙпјҢдҪҷиӢұж—¶жҢҮеҮәдёӯиҘҝеҜ№иҮӘ然зҺ°иұЎзҡ„жҺўз©¶иҮӘе§Ӣе°ұвҖңйҒ“дёҚеҗҢпјҢдёҚзӣёдёәи°ӢвҖқпјҢеҲҷжүҖи°“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еҸӘиғҪ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еҒҮй—®йўҳвҖқпјҲpseudo-questionпјүпјҢеӨұеҺ»дәҶеӯҳеңЁзҡ„дҫқжҚ®гҖӮжҺҘ收еӯҰз•Ңзҡ„еҸҚйҰҲд№ӢеҗҺ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并жңӘеұҲжңҚдәҺиҝҷдәӣжҢ‘жҲҳгҖӮ科жҒ©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е°ұжҲ‘жүҖзҹҘ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®Ңе…ЁзҹҘйҒ“е№ҙиҪ»дёҖд»Јзҡ„иҝҷдәӣи§ӮзӮ№гҖӮд»–й’ҲеҜ№е…¶дёӯдёҖдәӣдәә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Ҳзү№еҲ«жҳҜеёӯж–Ү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үдёәиҮӘе·ұзҡ„и§ӮзӮ№иҝӣиЎҢдәҶиҫ©жҠӨпјҢеҜ№д»–们зҡ„и§ӮзӮ№е№¶дёҚеңЁж„ҸпјҢ并ж„үеҝ«ең°з»§з»ӯиҝӣиЎҢиҮӘе·ұ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вҖқд»–дёҖзӣҙеқҡжҢҒиҮӘе·ұзҡ„еҹәжң¬еҲӨж–ӯпјҢиҖҢе°Ҷжү№иҜ„ж„Ҹи§Ғи§Ҷдёә欧жҙІз§‘еӯҰдјҳи¶Ҡи®әзҡ„зүҮйқўз»“жһңгҖӮеӣӣгҖҒеӣһеҲ°еҺҶеҸІ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 еңЁжј«й•ҝзҡ„еҺҶеҸІй•ҝжІідёӯпјҢдё–з•Ңеҗ„ж–ҮжҳҺеҫҲж—©е°ұејҖеұ•иө·еҜҶеҲҮзҡ„дәӨеҫҖпјҢжҺЁеҠЁдё–з•ҢеҺҶеҸІзҡ„ж•ҙдҪ“еҸ‘еұ•гҖӮеңЁиҝҷд№ӢдёӯпјҢдәәзұ»дёәдәҶиҝҪжұӮжӣҙеҘҪ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ҢдёҚж–ӯж”№иҝӣжҠҖжңҜпјҢйҳҗеҸ‘жҖқжғіпјҢжҺЁеҠЁдәҶ科еӯҰзҡ„дёҚж–ӯеҸ‘еұ•дёҺзӣёдә’дәӨжөҒпјҢиҷҪ然з”ұдәҺ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гҖҒз»ҸжөҺж–№ејҸгҖҒ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гҖҒжҖқжғіж–ҮеҢ–зҡ„дёҚеҗҢиҖҢеҸ‘еұ•еҮәе…·жңүдёҚеҗҢ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дёҺеҺҶеҸІйҒ“и·Ҝзҡ„科еӯҰжЁЎејҸпјҢдҪҶеҚҙдёҖзӣҙејҖеұ•зқҖжҲ–иҖ…е·Із»ҸеҸ—еҲ°е…іжіЁпјҢжҲ–иҖ…д»Қ然并дёҚеҪ°жҳҫзҡ„еҜҶеҲҮдәӨжөҒпјҢеҪјжӯӨдҝғиҝӣпјҢе…ұеҗҢзј–з»ҮдёҺжһ„е»әиө·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ж•ҙдҪ“еӣҫжҷҜгҖӮеңЁиҝҷд№ӢдёӯпјҢдёӯеӣҪдҪңдёә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й•ҝжңҹйўҶе…Ҳзҡ„йҮҚиҰҒж–ҮжҳҺдҪ“зі»пјҢжүҖд»ҺдәӢзҡ„й•ҝжңҹиҖҢ规模еәһеӨ§зҡ„科еӯҰе®һи·өпјҢж— з–‘жҳҜ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йҮҚиҰҒеҶ…ж¶өпјҢ并еҸӮдёҺеЎ‘йҖ дәҶ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иҪЁиҝ№гҖӮз”ұжӯӨи§’еәҰиҖҢиЁҖпјҢжқҺзәҰз‘ҹеҜ№дәҺиҝ‘代科еӯҰдёәдҪ•жІЎжңүдә§з”ҹдәҺдёӯеӣҪзҡ„еҺҶеҸІз–‘й—®пјҢж— з–‘жӢҘжңүзқҖеқҡе®һзҡ„дҫқжүҳпјҢ并йқһжҳҜдёҖз§Қ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зҡ„ж— ж„Ҹд№үд№Ӣй—®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зҡ„зјәйҷ·пјҢжҳҜеңЁдәҺжқҺзәҰз‘ҹе…¶е®һд»ҚжҳҜз«ҷеңЁж¬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зҡ„з«Ӣеңәд№ӢдёҠпјҢдҫқжүҳиҘҝ方科еӯҰжҰӮеҝөдҪ“зі»пјҢжҢ–жҺҳдёӯеӣҪ科еӯҰйҒ—дә§пјҢе°Ҷд№ӢдёҺ欧жҙІз§‘еӯҰејҖеұ•жҜ”иҫғз”ҡиҮіжҜ”йҷ„пјҢ并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иҝҪй—®зұ»дјјдәҺиҝ‘代科еӯҰйӮЈж ·зҡ„科еӯҰйқ©е‘ҪдёәдҪ•жІЎжңүеңЁдёӯеӣҪдә§з”ҹгҖӮе…¶е®һ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еңЁз§‘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дёҺ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дёҠпјҢеӯҳеңЁзқҖйқһеёёеӨ§зҡ„дёҚеҗҢдёҺе·®ејӮпјҢж•…иҖҢдёҚеә”е°Ҷ欧жҙІзҡ„иҝ‘代科еӯҰжҲҗжһңи§Ҷдёә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жңӘжқҘеҪ’йҖ”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Ҝ№дәҺ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ж—ўдёҚеә”д»Һ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еҮәеҸ‘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й•ҝжңҹдҝқжҢҒдәҶ科еӯҰйўҶе…ҲиҖҢиҮӘиұӘ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еҸҲдёәиҝ‘д»Јж—¶жңҹ科еӯҰзҡ„иҗҪеҗҺе……ж»ЎжғӢжғңпјҢж®ҠдёҚзҹҘиҝҷз§ҚжҖҒеәҰжң¬иә«и•ҙеҗ«зқҖеҶ…еңЁзҡ„зҹӣзӣҫпјҢ并жңӘзңҹжӯЈдәҶи§ЈдёӯеӣҪ科еӯҰзҡ„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пјҢжӣҙдёҚеә”еҶҚж¬ЎеӣһеҲ°ж¬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зҡ„еҺҹе§Ӣи®әзӮ№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зҡ„вҖңдјӘе‘ҪйўҳвҖқпјҢеҸӘжңүиҘҝж–№жүҚжңүзңҹжӯЈзҡ„科еӯҰпјҢд»ҺиҖҢеҜ№дёӯеӣҪ科еӯҰзҡ„иҜ„д»·пјҢеҶҚж¬ЎеӣһеҲ°иҝ‘д»Јд»ҘжқҘиҘҝж–№жҖқжғіз•Ңзҡ„иҙҹйқўж°ӣеӣҙд№ӢдёӯгҖӮзңҹжӯЈеә”иҜҘйҮҮеҸ–зҡ„еҒҡжі•пјҢжҳҜ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дёҺ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пјҢ并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®Ўи§Ҷе…¶еҜ№дәҺ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дё–з•Ң科еӯҰдә§з”ҹзҡ„ж•ҙдҪ“еҪұе“ҚпјҢжҺўи®Ёе…¶жүҖеӯҳеңЁзҡ„ејҠз«ҜдёҺй—®йўҳпјҢдҪ•д»ҘжңӘиғҪе®һзҺ°ж №жң¬зӘҒз ҙгҖӮиҝҷжҳҜзҗҶи§Ј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е…ій”®и§Ҷи§’гҖӮз”ұжӯӨеҮәеҸ‘пјҢеңЁе®Ўи§Ҷ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ж—¶пјҢдёҚеә”д»Һиө·жәҗдәҺиҘҝж–№зҡ„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жҰӮеҝөеҮәеҸ‘пјҢеҜ»жүҫзӣёеә”зҡ„зҺ°иұЎиҝӣиЎҢз®ҖеҚ•зҡ„жҜ”иҫғз”ҡиҮіжҜ”йҷ„пјҢд»ҘжӯӨжқҘи®әиҜҒдёӯеӣҪ科еӯҰзҡ„иҫүз…ҢжҲ–иҖ…иҗҪеҗҺпјҢиҝҷе…¶е®һжҳҜдёҖз§ҚвҖң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вҖқзҡ„еҒҡжі•пјҢжүҖиҺ·еҫ—зҡ„еҸӘиғҪжҳҜеҜ№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зҡ„иӮўи§ЈдёҺй”ҷз»ҳгҖӮзңҹжӯЈеә”иҜҘйҮҮеҸ–зҡ„еҒҡжі•пјҢжҳҜжҠҠдёӯеӣҪ科еӯҰйҮҚж–°ж”ҫеӣһеҲ°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ӯпјҢд»Һ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ж•ҙдҪ“еҺҶеҸІжғ…еўғеҮәеҸ‘пјҢ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зӢ¬зү№зҡ„жҰӮеҝөдҪ“зі»гҖҒеҲ¶еәҰ规иҢғгҖҒе®һи·өж“ҚдҪңдёҺеҺҶеҸІеҪұе“ҚгҖӮеңЁдәәзұ»еҺҶеҸІзҡ„еҶҷдҪңдёҺз ”з©¶дёӯпјҢеҫҲ早并й•ҝжңҹжөҒиЎҢиӢұйӣ„еҸІи§ӮгҖӮиҝҷжҳҜ马е…ӢжҖқдё»д№үз»ҸжөҺеҸІи§Ӯдә§з”ҹд»ҘеүҚпјҢдәә们еҜ№дәҺдё–з•ҢеӯӨз«Ӣи®ӨзҹҘзҡ„зүҮйқўз»“жһңгҖӮйүҙдәҺе·Ҙдёҡйқ©е‘ҪжүҖдә§з”ҹзҡ„е·ЁеӨ§еЁҒеҠӣпјҢ马е…ӢжҖқдё»д№үејҖе§ӢжҸӯзӨәе№ҝеӨ§ж°‘дј—еңЁ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дёӯжүҖжү®жј”зҡ„дё»дҪ“и§’иүІпјҢд»ҺиҖҢжҺЁеҠЁдәҶж•ҙдҪ“еҸІи§Ӯзҡ„еҪўжҲҗгҖӮд»ҺжӯӨд»ҘеҗҺпјҢиӢұйӣ„еҸІи§ӮеңЁеҺҶеҸІз ”究зҡ„дј—еӨҡйўҶеҹҹдёӯпјҢе·Із»ҸжҲҗдёәдәҶ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еҗҚиҜҚгҖӮдҪҶиҖҗдәәеҜ»е‘ізҡ„жҳҜпјҢз”ұдәҺ科еӯҰжң¬иә«зҡ„зү№ж®ҠжҖ§пјҢеңЁз§‘еӯҰеҸІз ”究дёӯпјҢеҚҙд»Қй•ҝжңҹжөҒиЎҢиӢұйӣ„科еӯҰеҸІи§Ӯ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жҠҠ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дёҺжҲҗеҠҹпјҢеҪ’з»“дёәдёҖдёӘдёӘдјҹеӨ§з§‘еӯҰ家дёӘдәәеҝғжҷәзҡ„зӘҒз ҙгҖӮиҝҷз§Қз ”з©¶жЁЎејҸж—ўеҝҪз•ҘдәҶзӨҫдјҡеӣ зҙ еҜ№дәҺ科еӯҰеҸ‘еұ•зҡ„еӨ–еңЁеҪұе“ҚпјҢд№ҹеҝҪи§ҶдәҶ科еӯҰдј ж’ӯдёӯ科еӯҰ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е…ұеҗҢдҪңз”ЁгҖӮиҮӘиҗЁйЎҝеҲӣз«Ӣ科еӯҰеҸІеӯҰ科д»ҘжқҘпјҢеҢ…жӢ¬еә“жҒ©гҖҒеёғйІҒиҜәВ·жӢүеӣҫе°”зӯүеңЁеҶ…зҡ„дј—еӨҡ科еӯҰеҸІе®¶пјҢйғҪдё»еј жҠҠ科еӯҰж”ҫеӣһеҲ°еҺҶеҸІжғ…жҷҜд№ӢдёӯпјҢжҸӯзӨә科еӯҰдёҺж•ҙдҪ“зӨҫдјҡ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еҸӘжңүиҝҷж ·еҒҡпјҢжүҚиғҪж—ўеҪ°жҳҫ科еӯҰдёҺзӨҫдјҡ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’еҠЁпјҢеҸҲжңүеҠ©дәҺжҸӯзӨә科еӯҰзҗҶи®әе¬—еҸҳзҡ„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гҖӮеҜ№дәҺ科еӯҰеҸІз ”究дёӯзҡ„иӢұйӣ„еҸІи§ӮпјҢзҫҺеӣҪ科еӯҰеҸІе®¶еёӯж–Үжү№еҲӨз”ҡеҠӣгҖӮд»–жҢҮеҮәд»ҘеҫҖеҸ—еҲ°з§‘еӯҰиҖҢйқһеҺҶеҸІеӯҰи®ӯз»ғзҡ„科еӯҰеҸІе®¶пјҢз«ҷеңЁз”ұд»ҠжәҜеҸӨзҡ„з«ӢеңәпјҢжӢЈйҖүең°з ”究дёҺзҺ°д»Јз§‘еӯҰзӣёдјјзҡ„жҖқжғігҖӮеҰӮжӯӨеҒҡжі•зҡ„з»“жһңд№ӢдёҖпјҢжҳҜд»…йҖүжӢ©дёҺиҝ‘代科еӯҰзӣёе…ізҡ„дёӘеҲ«з§‘еӯҰ家пјҢиҝӣиЎҢиӢұйӣ„еҸІи§Ӯзҡ„з ”з©¶гҖӮиҝҷз§Қз ”з©¶иҝҮдәҺзӢӯзӘ„пјҢ并дёҚиғҪжңүж•Ҳең°жҸӯзӨә科еӯҰзҡ„ж•ҙдҪ“иғҢжҷҜдёҺеҺҶеҸІеҸҳеҢ–гҖӮиҖҢеңЁе°Ҷ科еӯҰйҮҚж–°ж”ҫеӣһеҺҶеҸІзҡ„з ”з©¶зҗҶи·Ҝд№ӢдёӯпјҢиҷҪ然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гҖҒ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гҖҒжҖқжғіж–ҮеҢ–д№ғиҮідёӘеҲ«дәәзү©пјҢйғҪ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пјҢдҪҶдҪңдёәж–ҮжҳҺдҪ“зі»зҡ„дё»еҜјиҖ…гҖҒзӨҫдјҡиө„жәҗзҡ„жҺ§еҲ¶иҖ…зҡ„еӣҪ家пјҢеҚҙж— з–‘жү®жј”зқҖжңҖдёәзӣҙжҺҘиҖҢйҮҚиҰҒ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еҪ“д»Ҡдё–з•ҢжөҒиЎҢзҡ„ж°‘ж—ҸеӣҪ家пјҢжҳҜеҚҒеҲҶжҷҡиҝ‘зҡ„дә§зү©гҖӮиҘҝ欧еңЁиҝ‘д»ЈеҢ–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ә§з”ҹеҮәиҜёеӨҡд»ҘеҚ•дёҖж°‘ж—ҸгҖҒеҚ•дёҖе®—ж•ҷдёәзү№еҫҒзҡ„зҺ°д»Јж°‘ж—ҸеӣҪ家пјҢеҪјжӯӨд№Ӣй—ҙеӣҙз»•е®—ж•ҷдёҺйўҶеңҹзҲҶеҸ‘жҲҳдәүгҖӮдёәи§ЈеҶіиҝҷдёҖдәүз«ҜпјҢеҗ„еӣҪе…ұеҗҢзӯҫи®ўдәҶгҖҠеЁҒж–Ҝзү№дјҗеҲ©дәҡе’ҢзәҰгҖӢ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еЁҒж–Ҝзү№дјҗеҲ©дәҡдҪ“зі»вҖқпјҢд»ҘеӣҪйҷ…жі•зҡ„еҪўејҸпјҢзЎ®з«ӢдәҶиҝ‘д»Јж°‘ж—ҸеӣҪ家д№Ӣй—ҙдё»жқғзҘһеңЈгҖҒзӢ¬з«Ӣе№ізӯүзҡ„еӣҪйҷ…秩еәҸпјҢдёҖзӣҙеҪұе“ҚиҮід»ҠгҖӮдҪҶеңЁ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пјҢеҚҙеӯҳеңЁдј—еӨҡдёҚеҗҢ规模гҖҒдёҚеҗҢеҶ…ж¶өзҡ„еӣҪ家еҪўжҖҒгҖӮиҖҢеңЁе…¶дёӯжү®жј”дәҶе…ій”®жҖ§и§’иүІгҖҒеҸ‘жҢҘдәҶе…ЁеұҖжҖ§еҪұе“Қзҡ„пјҢжҳҜе…ҲеҗҺж¶ҢзҺ°зҡ„жӢҘжңүе№ҝйҳ”з–ҶеҹҹгҖҒеӨҡз§Қж—ҸзҫӨгҖҒеӨҡе…ғж–ҮеҢ–зҡ„вҖңеәһеӨ§еӣҪ家вҖқгҖӮдёҺиҝ‘д»Јд»ҘжқҘе…ҙиө·зҡ„пјҢз”ұеҚ•дёҖж°‘ж—ҸжҲ–жҹҗдёҖж°‘ж—Ҹдёәдё»дҪ“е»әз«Ӣзҡ„пјҢд»Ҙ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еҮқиҒҡдәәеҝғгҖҒе®һзҺ°зӨҫдјҡж•ҙеҗҲ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еӣҪ家вҖқдёҚеҗҢпјҢвҖңеәһеӨ§еӣҪ家вҖқиө–д»Ҙз»ҙзі»зҡ„еҹәзЎҖжҳҜзҺӢжңқзҡ„ж”ҝжІ»еҗҲжі•жҖ§пјҢиҖҢйқһиҝ‘д»ЈеӣҪ家зҡ„ж°‘ж—ҸзӢ¬зү№жҖ§пјҢз”ұжӯӨи§’еәҰиҖҢиЁҖпјҢеҸҜе°ҶвҖңеәһеӨ§еӣҪ家вҖқз§°дҪң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гҖӮеңЁдәәзұ»ж–ҮжҳҺеҸІдёҠпјҢиҷҪ然йҷӨдәҶе°‘йғЁеҲҶдёҖзӣҙеұҖйҷҗдәҺиҫғдҪҺеҸ‘еұ•йҳ¶ж®өзҡ„ж–ҮжҳҺд№ӢеӨ–пјҢеӨ§йғЁеҲҶж–ҮжҳҺйғҪжӣҫз»ҸеҺҶиҝҮ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еҺҶеҸІеҪўжҖҒпјҢдҪҶз”ұдәҺ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е…·жңүдёҚеҗҢзҡ„ең°зјҳзҺҜеўғгҖҒеҺҶеҸІйҒ“и·ҜдёҺ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пјҢеӣ жӯӨ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е…·дҪ“йқўиІҢд№ҹ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пјҢеҸҚиҝҮжқҘеҪўеЎ‘дәҶ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зҡ„еҺҶеҸІеҸ–еҗ‘пјҢжһ„жҲҗдәҶиҝ‘д»Јдё–з•ҢеҺҶеҸІзҡ„йҮҚиҰҒеҠӣйҮҸпјҢ并еңЁиҝ‘д»Је‘ҲзҺ°еҮәдёҚеҗҢзҡ„еҺҶеҸІе‘ҪиҝҗдёҺеҶ…еңЁе¬—еҸҳгҖӮдәҡ欧еӨ§йҷҶзҡ„дё»дҪ“ж–ҮжҳҺпјҢе°ұжҳҜ欧жҙІж–ҮжҳҺгҖҒйҳҝжӢүдјҜж–ҮжҳҺгҖҒдёӯеҚҺж–ҮжҳҺгҖӮеүҚдёӨиҖ…еӣҙз»•ең°дёӯжө·иҖҢеұ•ејҖпјҢеҗҺиҖ…зӢ¬еӨ„дәҺдёңдәҡеӨ§йҷҶгҖӮеҸӨд»Јзҡ„дәҡ欧世з•ҢпјҢдәҺжҳҜе‘ҲзҺ°еҮәдёҖз§ҚвҖңеӨ©е№із»“жһ„вҖқпјҢдёңгҖҒиҘҝдёӨз«ҜеҲҶеҲ«жҳҜдёңдәҡдё–з•ҢдёҺең°дёӯжө·дё–з•ҢпјҢиҖҢиҝһжҺҘе®ғ们зҡ„жҳҜдәҡ欧иө°е»ҠгҖӮ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е°ұжҳҜеңЁиҝҷз§ҚеӨ©е№із»“жһ„дёӯеҗ„иҮӘеҸ‘еұ•гҖҒеҸҢеҗ‘дәӨжөҒпјҢжңҖз»ҲдёҖдҪ“еҢ–иҖҢиө°еҗ‘иҝ‘д»ЈгҖӮдёңж–№дё–з•ҢгҖҒ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зҡ„еҶ…еңЁе·®ејӮпјҢдёҖзӮ№йғҪдёҚжҜ”е®ғ们д№Ӣй—ҙзҡ„и·қзҰ»жӣҙе°ҸгҖӮдёңгҖҒиҘҝж–№иҷҪ然йғҪжңүи”ҡи“қиүІзҡ„жө·еҹҹпјҢдҪҶеңЁдёңж–№пјҢеҚҙжңүе№ҝйҳ”иҖҢе№іеқҰзҡ„дёңдәҡеӨ§йҷҶпјҢй»„жІігҖҒж·®жІігҖҒй•ҝжұҹгҖҒзҸ жұҹжҸҗдҫӣзҡ„зҒҢжәүзҪ‘з»ңпјҢеӨӘе№іжҙӢжҡ–ж№ҝж°”жөҒеёҰжқҘзҡ„дё°еҜҢйҷҚж°ҙпјҢдҪҝдёӯеҚҺж–ҮжҳҺй•ҝжңҹејҖиҫҹеҮә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жңҖдёәеҸ‘иҫҫзҡ„еҶңдёҡз»ҸжөҺ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з–Ҷеҹҹе№ҝйҳ”гҖҒж—ҸзҫӨдј—еӨҡгҖҒж–ҮеҢ–еӨҡе…ғ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пјҢй•ҝжңҹдҝқжҢҒдәҶдёҖдҪ“еӨҡе…ғзҡ„еҺҶеҸІж јеұҖпјҢж–ҮжҳҺй•ҝжңҹ延з»ӯгҖҒдёҚж–ӯеҸ‘еұ•гҖӮдёҺд№ӢдёҚеҗҢпјҢ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еӣҙз»•зқҖең°дёӯжө·пјҢе…ҲеҗҺе…ҙиө·еӨҡз§Қж–ҮжҳҺпјҢеӨҡзӮ№ејҖиҠұпјҢејӮеҪ©зә·е‘ҲпјҢй•ҝжңҹдҝқжҢҒдәҶеӨҡе…ғеқҮеҠҝзҡ„еұҖйқўгҖӮеұ…дәҺеҢ—йқһзҡ„еҹғеҸҠпјҢиҷҪ然жңүе°јзҪ—жІіе®ҡжңҹжіӣж»ҘеёҰжқҘзҡ„еӨ©з„¶жІғеңҹпјҢдҪҶдёҠеёқеёҰжқҘвҖңе°јзҪ—жІізҡ„иө зӨјвҖқ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жҠҠеҹғеҸҠж–ҮжҳҺе°Ғй—ӯеңЁжІҷжј д№ӢдёӯпјҢдҪҝе®ғйҖҗжёҗеҒңдёӢдәҶеҸ‘еұ•зҡ„и„ҡжӯҘгҖӮиҖҢең°еҪўвҖңз ҙзўҺвҖқзҡ„иҘҝ欧гҖҒйҷҚйӣЁйҮҸе°‘зҡ„дёң欧гҖҒжІҷжј йҒҚеёғзҡ„йҳҝжӢүдјҜеҚҠеІӣпјҢиө„жәҗйғҪзӣёеҜ№еҢ®д№ҸпјҢдҪҝеӨ§еһӢж”ҝжқғзҡ„еӯҳеңЁйқўдёҙзқҖе·ЁеӨ§жҢ‘жҲҳпјҢ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е»әз«ӢдёҺеҸ‘еұ•пјҢйғҪйқўдёҙзқҖе…ҲеӨ©дёҚи¶ізҡ„жғ…еҶөпјҢ欧жҙІеӨ„дәҺй•ҝжңҹзҡ„еҲҶиЈӮпјҢйҳҝжӢүдјҜеҶ…йғЁзә·дәүдёҚж–ӯпјҢ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еҜ№дәҺзӨҫдјҡзҡ„жҺ§еҲ¶йғҪеҸ—еҲ°дәҶеүҠејұгҖӮеҰӮжӯӨдёҚеҗҢзҡ„ең°зјҳж”ҝжІ»е’Ңж–ҮжҳҺзү№еҫҒпјҢд№ҹдҝғдҪҝдёң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зҡ„科еӯҰпјҢе‘ҲзҺ°дәҶеҲҶйҖ”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и„үз»ңгҖӮеҸӨд»ЈдёӯеӣҪ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пјҢж—ўдёҚеҗҢдәҺиҝ‘д»Јж°‘ж—ҸеӣҪ家еңЁ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еҸ‘еұ•иҝҮзЁӢдёӯеҹ№иӮІиҖҢеҮәзҡ„иҝ‘代科еӯҰпјҢд№ҹдёҚеҗҢдәҺеҸӨд»Јең°дёӯжө·ең°еҢәзҡ„科еӯҰпјҢиҖҢжҳҜеҚ•зӢ¬жһ„жҲҗдәҶе…·жңүйІңжҳҺзү№иүІзҡ„еҸ‘еұ•жЁЎејҸгҖӮжң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жңүеҝ…иҰҒз•Ңе®ҡеҮә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Ӣ¬зү№жҰӮеҝөпјҢ并жһ„е»әиө·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җҶи®әжЎҶжһ¶дёҺи§ЈйҮҠдҪ“зі»гҖӮиҝ‘д»Јд»ҘеүҚпјҢжүҖжңүж–ҮжҳҺзҡ„科еӯҰпјҢйғҪ并жңӘеҸ‘еұ•еҮәе®Ңе…ЁзӢ¬з«Ӣзҡ„еӯҰ科йўҶеҹҹпјҢиҖҢжҳҜеҢ…иЈ№дәҺжҖқжғігҖҒе®—ж•ҷгҖҒж–ҮеҢ–гҖҒиүәжңҜд№ӢдёӯгҖӮеҸӘжҳҜеңЁ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д№ӢдёӯпјҢ科еӯҰеҸ—еҲ°ж”ҝжІ»еҪұе“ҚжӣҙдёәжҢҒд№…пјҢд»ҺиҖҢе‘ҲзҺ°жӣҙдёәзўҺзүҮеҢ–зҡ„еёғеұҖгҖӮзӣёеә”ең°пјҢеҜ№дәҺ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科еӯҰеҸ‘еұ•жүҖиҝӣиЎҢ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е°ұдёҚеә”еғҸд»ҘеҫҖз ”з©¶йӮЈж ·пјҢеұҖйҷҗдәҺзі»з»ҹйҳҗеҸ‘科еӯҰжҖқжғід»ҘеҸҠдҫ§йҮҚдәҺеҜ№дё“й—Ёд»ҺдәӢжҠҖжңҜзҫӨдҪ“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йӮЈжҳҜдёҖз§Қи„ұзҰ»еҺҶеҸІжғ…жҷҜпјҢеӯӨз«ӢејҸгҖҒеҸҚеҺҶеҸІзҡ„з ”з©¶ж–№ејҸгҖӮеҜ№дәҺ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еә”еӣһеҲ°ж•ҙдҪ“зҡ„еҺҶеҸІжғ…жҷҜпјҢжҚЎжӢҫеҲҶж•ЈдәҺдј—еӨҡйўҶеҹҹзҡ„科еӯҰзўҺзүҮпјҢжӢјеҗҲиҖҢжҲҗе®Ңж•ҙ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еӣҫжҷҜпјҢ并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Ӣ¬зү№йҒ“и·ҜдёҺ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гҖӮдә”гҖҒ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еҺҶеҸІзү№еҫҒдёҺ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 欧жҙІзҡ„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гҖҒз»ҸжөҺж–№ејҸгҖҒ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гҖҒжҖқжғіж–ҮеҢ–пјҢдёҖзӣҙйғҪдёҺеҸӨд»ЈдёӯеӣҪеӯҳеңЁе·ЁеӨ§зҡ„е·®еҲ«гҖӮиҝ‘д»Јд»ҘжқҘпјҢ欧жҙІйҖҡиҝҮејҖеҗҜе…Ёзҗғжү©еј пјҢе°ҶеҸҚжҳ иҮӘиә«дёҖйҡ…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дёҺеӯҰжңҜдҪ“зі»дј ж’ӯиҮіе…Ёдё–з•ҢпјҢ并еҖҹеҠ©еӣҪеҠӣдјҳеҠҝпјҢе°Ҷе…¶зЎ®з«ӢдёәеӣҪйҷ…иҜқиҜӯдҪ“зі»пјҢд»ҺиҖҢеҺӢеҲ¶д№ғиҮіж¶ҲйҷӨдәҶ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жң¬иә«еӣәжңү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дёҺеӯҰжңҜдҪ“зі»гҖӮиҝ‘д»Јд»ҘжқҘ欧зҫҺеӣҪ家зҡ„ејәеҠҝең°дҪҚпјҢеңЁзӣёеҪ“зЁӢеәҰдёҠдҝғдҪҝе…¶еҺҶеҸІз»ҸйӘҢжҲҗдёәдәҶиЎЎйҮҸ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еҫ—еӨұзҡ„жЁЎжқҝдёҺж ҮжқҶгҖӮж— и®әжҳҜж”ҜжҢҒ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пјҢиҝҳжҳҜжү№иҜ„欧жҙІдёӯеҝғи®әпјҢеҫҖеҫҖйғҪдјҡиҗҪе…ҘжҜ”йҷ„欧жҙІзҡ„зӘ иҮјдёҺйҷ·йҳұгҖӮеҪ“еүҚпјҢжҲ‘们еңЁејҖеұ•еӯҰжңҜз ”з©¶ж—¶пјҢж—ўеә”е……еҲҶ继жүҝгҖҒеҗёж”¶зҺ°д»ЈеӯҰжңҜдҪ“зі»дёӯеҗҲзҗҶ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пјҢд№ҹеә”д»Һжӣҙй•ҝжӣҙе№ҝзҡ„еҺҶеҸІ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е°Ҷ欧зҫҺзҡ„еҙӣиө·е®ҡдҪҚдёә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йҳ¶ж®өпјҢиҖҢйқһеҺҶеҸІз»ҲзӮ№пјҢд»ҺиҖҢй’©жІүдёҺжҸӯзӨә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зҡ„дј з»ҹйҹ§жҖ§дёҺжңӘжқҘеҸҜиғҪ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Ҝ№д»…д»…еҸҚжҳ 欧зҫҺпјҢд№ғиҮіиҘҝ欧ж–ҮжҳҺзү№еҫҒ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пјҢи®Өзңҹең°йүҙеҲ«гҖҒжү¬ејғпјҢе»“жё…з¬јзҪ©еңЁзҹҘиҜҶдҪ“зі»д№ӢдёҠзҡ„иҝ·йӣҫпјҢжҺҘз»ӯдёӯеӣҪдј з»ҹзҡ„еӯҰжңҜдҪ“зі»пјҢжһ„е»әеҸҚжҳ 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зҺ°е®һзҡ„зңҹе®һйқўиІҢпјҢз¬ҰеҗҲ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зҺ°е®һзҡ„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пјҢд»ҺиҖҢе»әз«Ӣиө·дёӯеӣҪжң¬дҪҚзҡ„еӯҰжңҜдҪ“зі»гҖӮе…·дҪ“иҮі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иҖҢиЁҖ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Ё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®ЎзҗҶе№ҝйҳ”з–ҶеҹҹгҖҒдј—еӨҡж—ҸзҫӨгҖҒеӨҡе…ғж–ҮеҢ–зҡ„еҶ…еңЁй©ұеҠЁдёӢпјҢ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жӢҘжңүзқҖжәҗжәҗдёҚж–ӯзҡ„еҸ‘еұ•еҠЁеҠӣгҖӮ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еңЁе№ҝйҳ”зҡ„з–ҶеҹҹеҶ…пјҢйҖҡиҝҮеҸ‘еұ•ж°ҙйҷҶдәӨйҖҡпјҢе»әз«Ӣиө·дәҶй•ҝжңҹзЁіе®ҡгҖҒз©әй—ҙе·ЁеӨ§зҡ„еӣҪеҶ…еёӮеңәпјӣйҖҡиҝҮиһҚеҗҲдј—еӨҡж—ҸзҫӨпјҢиЎҚз”ҹеҮәдәҶжңҖдёәеәһеӨ§зҡ„дәәеҸЈпјӣйҖҡиҝҮдәӨжөҒеӨҡе…ғж–ҮеҢ–пјҢдә§з”ҹеҮәеҶ…ж¶өеӨҚжқӮгҖҒеӨҡе§ҝеӨҡеҪ©зҡ„ж–ҮеҢ–еҪўжҖҒгҖӮдҪңдёәй•ҝжңҹзЁіе®ҡгҖҒдёҚж–ӯеҸ‘еұ•гҖҒ规模еәһеӨ§зҡ„ж–ҮжҳҺдҪ“зі»пјҢдёӯеҚҺж–ҮжҳҺжҺЁеҠЁдј—еӨҡ科еӯҰжҖқжғідёҺе®һи·өжҠҖжңҜж¶ҢзҺ°еҮәжқҘпјҢеҗҺиҖ…дјҙйҡҸз»ҸжөҺгҖҒзӨҫдјҡзҡ„еҸ‘еұ•иҖҢе°Өе…¶еҸ‘иҫҫгҖӮ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Ё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ејәеҠӣз®ЎжҺ§дёӢпјҢ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ж— и®әеңЁжҖқжғіи§ӮеҝөдёҠпјҢиҝҳжҳҜзӨҫдјҡе®һи·өдёҠпјҢиҝҳжҳҜд»Һдёҡдәәе‘ҳдёҠпјҢйғҪе‘ҲзҺ°еҮәдҫқйҷ„жҖ§гҖҒеҲҶж•ЈжҖ§зҡ„еҺҶеҸІзү№еҫҒпјҢж— жі•е®һзҺ°жҖқжғізҡ„зӢ¬з«ӢжҖқиҖғгҖҒжҠҖжңҜзҡ„зі»з»ҹеә”з”ЁгҖҒд»Һдёҡдәәе‘ҳзҡ„дәӨжөҒиһҚеҗҲпјҢд»ҺиҖҢж— жі•жһ„е»әиө·зӢ¬з«Ӣзі»з»ҹзҡ„科еӯҰ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дёҺиЎҢдёҡз»„з»ҮпјҢж— жі•жҺЁеҠЁз§‘еӯҰз ”з©¶е°Өе…¶жҳҜ科еӯҰжҖқжғізҡ„еҜҶеҲҮдәӨжөҒгҖҒзі»з»ҹз§ҜзҙҜгҖҒжңүж•Ҳдј ж’ӯгҖӮеҚідҪҝеӨ–жқҘжҖқжғідёҺ科жҠҖдј е…ҘиҝӣжқҘпјҢд№ҹеҸӘиғҪеҗёж”¶дёҺе…¶ж—ўжңүзҗҶеҝөзӣёеҘ‘еҗҲд№ӢеӨ„пјҢиҖҢж— жі•е®һзҺ°и§Ӯеҝөзҡ„ж №жң¬еҸҳйқ©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дёҖзӣҙйғҪжңӘе®һзҺ°йҮҚеӨ§зӘҒз ҙ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и®ёеӨҡйўҶеҹҹз”ұдәҺзјәд№ҸеӣҪ家зҡ„й•ҝжңҹж”ҜжҢҒиҖҢйҖҗжёҗйҷ·дәҺеҒңж»һпјҢд№ғиҮіеҺҶеҸІеҖ’йҖҖгҖӮиҝҷжҳҜ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ҸҜд»Ҙй•ҝжңҹеҸ‘еұ•пјҢ并еңЁи®ёеӨҡж–№йқўйўҶе…Ҳдё–з•ҢпјҢдҪҶеҚҙж— жі•е®һзҺ°зӘҒз ҙзҡ„еҺҶеҸІж №жәҗгҖӮ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科еӯҰз”ұдәҺдёҖзӣҙеңЁ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жІ»зҗҶд№ӢдёӢиҖҢеҸ—еҲ°еҲ¶зәҰпјҢиҷҪ然众еӨҡеЈ«дәәејҖеұ•дәҶзӣёеҪ“зҡ„科еӯҰзҗҶи®әжҖқиҖғпјҢдҪҶеҚҙж— жі•иҪ»иЈ…дёҠйҳөпјҢжҺЁеҠЁзҗҶи®әзҡ„зІҫзЎ®жҖ§еҸ‘еұ•пјҢж— жі•жҺЁеҠЁз§‘еӯҰ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зҡ„еҪўжҲҗпјҢеҸӘиғҪзӣёеҜ№ең°гҖҒжңүйҖүжӢ©жҖ§ең°дҝқз•ҷйӮЈдәӣеҜ№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жӣҙдёәжңүз”Ёзҡ„е…·дҪ“жҠҖжңҜгҖӮеңЁ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ж— еӨ„дёҚеңЁзҡ„еҪұе“Қд№ӢдёӢ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д»ҺзӨҫдјҡеӨ–еңЁиғҢжҷҜзҡ„и§’еәҰиҖҢиЁҖпјҢиҝҳжҳҜ科еӯҰеҶ…еңЁеҸ‘еұ•зҡ„и§’еәҰиҖҢиЁҖпјҢеҢ…жӢ¬зҡҮеёқгҖҒеЈ«дәәгҖҒе·ҘеҢ зӯүзӨҫдјҡеҗ„йҳ¶еұӮпјҢйғҪжӣҫз»Ҹе№ҝжіӣең°еҸӮдёҺеҲ°з§‘еӯҰжҠҖжңҜзҡ„з®ЎзҗҶгҖҒи®Ёи®әдёҺе®һи·өд№ӢдёӯпјҢе…ұеҗҢжһ„жҲҗдәҶ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еҶ…еӨ–еҠЁеҠӣгҖӮе…¶е®һ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з ”з©¶иҜҒжҳҺпјҢеҚідҪҝ科еӯҰе·Із»Ҹй«ҳеәҰдё“дёҡеҢ–зҡ„д»ҠеӨ©пјҢ科еӯҰз ”з©¶д»Қ然并йқһе®Ңе…ЁеұҖйҷҗдәҺе®һйӘҢе®Өзҡ„е°Ғй—ӯжҖ§е·Ҙ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д»ҺејҖе§ӢеҲ°з»“жқҹпјҢйғҪе…·жңүејәзғҲзҡ„зӨҫдјҡжҢҮеҗ‘дёҺиҜүжұӮпјҢеҸ—еҲ°зӨҫдјҡзҡ„й•ҝжңҹиҖҢе·ЁеӨ§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ж•…иҖҢпјҢеҜ№дәҺеҢ…жӢ¬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еңЁеҶ…зҡ„жүҖжңү科еӯҰ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йғҪеә”з«ҷеңЁвҖңеӨ§з§‘еӯҰвҖқзҡ„и§Ҷи§’пјҢжҸӯзӨә科еӯҰзҡ„ж”ҝжІ»з®ЎзҗҶгҖҒжҖқжғідәӨжөҒдёҺзӨҫдјҡе®һи·өгҖӮиҖҢеңЁиҝҷд№ӢдёӯпјҢдёҺд»ҘеҫҖжҲ‘们е°Ҷз„ҰзӮ№йғҪиҒҡйӣҶдәҺд»ҺдәӢ科еӯҰжҖқжғідёҺжҠҖжңҜе®һи·өзҡ„科еӯҰ家дёҚеҗҢпјҢдёҚеҗҢзӯүзә§зҡ„жқғеҠӣжӢҘжңүиҖ…пјҢеҗҢж ·д№ғиҮіжү®жј”дәҶ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и§’иүІгҖӮдёҚд»…еҰӮжӯӨпјҢдј—еӨҡз ”з©¶е·Із»ҸжҸӯзӨәеҮә科еӯҰз ”з©¶е№¶йқһжҳҜе®Ңе…Ёе®ўи§ӮгҖҒзҗҶжҖ§зҡ„жҙ»еҠЁпјҢиҖҢжҳҜеҸ—еҲ°дәҶеӣҪ家гҖҒзӨҫдјҡпјҢд№ғиҮіз§‘еӯҰ家дёӘдәәи§ӮеҝөгҖҒеҲ©зӣҠ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пјҢж— и®әеңЁеӯҰзҗҶеұӮйқўиҝҳжҳҜе®һи·өеұӮйқўпјҢйғҪй•ҝжңҹиў«з»ҹеұһдәҺ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зҡ„ж”ҝжІ»дҪ“зі»пјҢзӣёеә”еҸ—еҲ°зҺӢжңқж”ҝжІ»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гҖҒж”ҝжІ»дҪ“еҲ¶дёҺж”ҝжІ»е®һи·өиҝҗдҪңзҡ„ж·ұеҲ»еҪұе“ҚгҖӮзӣёеә”ең°пјҢеҜ№дәҺ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еә”е°Ҷд№ӢдёҺ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еҺҶеҸІе……еҲҶз»“еҗҲпјҢж—ўеҠӘеҠӣжҸӯзӨә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жүҖеӨ„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пјҢеҸҲз«ӯеҠӣйҳҗйҮҠеҺҶеҸІеҪұе“ҚдёӢ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пјҢд»ҺиҖҢе…ЁйқўеӢҫеӢ’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гҖӮз”ұжӯӨеҮәеҸ‘пјҢеә”еҜ№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йҳ¶ж®өзү№еҫҒпјҢз»ҷдәҲжӣҙдёәе…ЁйқўиҖҢйІңжҳҺзҡ„жҰӮжӢ¬гҖӮд»ҘеҫҖеҜ№дәҺ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е·Із»ҸеҜ№дёҚеҗҢйўҶеҹҹзҡ„еҸ‘еұ•и„үз»ңдёҺйҳ¶ж®өеҸҳеҢ–иҝӣиЎҢдәҶеӨ§дҪ“зҡ„жўізҗҶпјҢйғЁеҲҶз ”з©¶иҝҳе°қиҜ•з»“еҗҲе…·дҪ“зҡ„зҺӢжңқиғҢжҷҜпјҢиҝӣиЎҢжӣҙдёәе…ЁйқўиҖҢж·ұе…Ҙзҡ„и®Ёи®әгҖӮдҪҶж•ҙ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д»ҘеҫҖзҡ„з ”з©¶д»ҚиҒҡз„ҰдәҺ科еӯҰжң¬иә«пјҢиҖҢеҜ№дәҺзҺӢжңқзҡ„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гҖҒж”ҝжІ»дҪ“еҲ¶гҖҒж”ҝжІ»жҖқжғігҖҒзӨҫдјҡз»ҸжөҺгҖҒеҢәеҹҹзү№еҫҒгҖҒж–ҮеҢ–иғҢжҷҜзӯүж¬ зјәи¶іеӨҹе…ЁйқўиҖҢж·ұе…Ҙзҡ„и®Ёи®әпјҢд»ҺиҖҢдҪҝ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и®Ёи®әдёҖзӣҙеҒңз•ҷеңЁиЎЁеұӮпјҢиҖҢзјәд№Ҹиҫғдёәж·ұе…Ҙзҡ„и®әиҝ°гҖӮзӣёеә”ең°пјҢ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ж•ҙдҪ“еӣҫжҷҜдёҺйҳ¶ж®өзү№еҫҒпјҢдёҖзӣҙйғҪ并дёҚе…ЁйқўдёҺжё…жҷ°гҖӮеҪ“еүҚеә”д»Һдё–з•ҢеҸІзҡ„ж•ҙдҪ“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жҸӯзӨәеңЁ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иғҢжҷҜдёӢ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еҶ…йғЁеҸ‘еұ•дёҺеҜ№еӨ–дәӨжөҒеңЁ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‘еұ•дёӯзҡ„йҳ¶ж®өең°дҪҚдёҺдё–з•Ң科еӯҰеҸ‘еұ•дёӯзҡ„еҺҶеҸІең°дҪҚпјҢиҝҷж ·жүҚиғҪзңҹжӯЈе®һзҺ°з§‘еӯҰдёҺеҺҶеҸІзҡ„е…Ёйқўдә’еҠЁгҖӮз»“ и®ә вҖң科еӯҰйқ©е‘ҪвҖқеҸ‘з”ҹеҗҺпјҢеҜ№дәҺиҝҷдёҖзҺ°иұЎ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ж—ўжңүе°Ҷд№ӢеҚ•зәҜеҪ’з»“дёәеҸӨ代欧жҙІзӢ¬зү№з§‘еӯҰдј з»ҹд№ғиҮідёӘеҲ«з§‘еӯҰ家зҡ„еӯӨз«Ӣдё»д№үгҖҒиӢұйӣ„дё»д№үзҡ„з ”з©¶еҸ–еҗ‘пјӣд№ҹжңүд»Һдё–з•Ң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е°Ҷд№Ӣи§Ҷдёә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科еӯҰдј з»ҹе…ұеҗҢжұҮеҗҲз»“жһңзҡ„з ”з©¶з«ӢеңәгҖӮиӢұеӣҪ科еӯҰеҸІе®¶жқҺзәҰз‘ҹйҖҡиҝҮеҜ№дёӯеӣҪ科еӯҰзҡ„е…Ёйқўзі»з»ҹиҖғеҜҹ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ж—ўеҢ…еҗ«ж¬§жҙІи§Ҷи§’дёӢзҡ„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‘代科еӯҰдә§з”ҹдәҺ欧жҙІ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дә§з”ҹдәҺдёӯеӣҪвҖқзҡ„з–‘й—®пјҢеҸҲеҢ…еҗ«дёӯеӣҪи§Ҷи§’дёӢзҡ„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еңЁж–ҮиүәеӨҚе…ҙд»ҘеүҚпјҢдёӯеӣҪ科жҠҖжҜ”欧жҙІжӣҙдёәе…ҲиҝӣвҖқзҡ„з–‘й—®гҖӮ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й—®йўҳвҖқдёҖж–№йқўеҘ‘еҗҲдәҶвҖңдәҢжҲҳвҖқд»ҘеҗҺдёҚеҗҢж–ҮжҳҺеҜ»жұӮиҮӘиә«дё»дҪ“жҖ§зҡ„ж—¶д»ЈиҜүжұӮпјҢеңЁдё–з•Ң科еӯҰеҸІе°Өе…¶дёӯеӣҪ科еӯҰеҸІдёӯдә§з”ҹдәҶе·ЁеӨ§еҪұе“ҚпјҢд№ғиҮі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§ҚвҖңжқҺзәҰз‘ҹжғ…з»“вҖқпјӣдҪҶ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Қҙд№ҹдјҙйҡҸ科еӯҰеҸІгҖҒ科еӯҰе“ІеӯҰгҖҒ科еӯҰзӨҫдјҡеӯҰз ”з©¶иҢғејҸзҡ„иҪ¬еҸҳпјҢеҸ—еҲ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иҙЁз–‘пјҢз”ҡиҮіиў«и®Өдёә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дјӘй—®йўҳвҖқпјҢд№ғиҮіжҳҜвҖң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вҖқгҖӮдёӯеӣҪдҪңдёәеҸӨд»Јдё–з•Ңй•ҝжңҹйўҶе…Ҳзҡ„йҮҚиҰҒж–ҮжҳҺдҪ“зі»пјҢе…¶еҠіеҠЁдәәж°‘жүҖд»ҺдәӢзҡ„й•ҝжңҹиҖҢ规模еәһеӨ§зҡ„科еӯҰе®һи·өпјҢж— з–‘жһ„жҲҗдәҶ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йҮҚиҰҒеҶ…ж¶өпјҢ并еҸӮдёҺеЎ‘йҖ дәҶдё–з•Ң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иҪЁиҝ№гҖӮжқҺзәҰз‘ҹеҜ№дәҺиҝ‘代科еӯҰдёәдҪ•жІЎжңүдә§з”ҹдәҺдёӯеӣҪзҡ„еҺҶеҸІз–‘й—®пјҢ并йқһжҳҜдёҖз§Қж— дёӯз”ҹжңүзҡ„ж— ж„Ҹд№үд№Ӣй—®гҖӮеҪ“еүҚд»Қеә”д»Һдё–з•Ңи§Ҷи§’еҮәеҸ‘пјҢз«Ӣи¶ідәҺдёӯеӣҪжң¬дҪҚпјҢ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зҡ„еҸ‘еұ•йҒ“и·ҜдёҺеҶ…еңЁйҖ»иҫ‘гҖӮз”ұжӯӨеҮәеҸ‘пјҢ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пјҢдёӯеӣҪеҸӨд»Је»әз«Ӣиө·й•ҝжңҹзЁіе®ҡиҖҢејәеӨ§зҡ„вҖңзҺӢжңқеӣҪ家вҖқ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жҺЁеҠЁдәҶ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жҖқжғідёҺжҠҖжңҜзҡ„дёҚж–ӯж¶ҢзҺ°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е‘ҲзҺ°еҮәеҜ№дәҺ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ејәеҠӣз®ЎжҺ§пјҢеҜјиҮҙ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ж— и®әеңЁжҖқжғіи§ӮеҝөдёҠпјҢиҝҳжҳҜзӨҫдјҡе®һи·өдёҠпјҢиҝҳжҳҜд»Һдёҡдәәе‘ҳдёҠпјҢйғҪе‘ҲзҺ°еҮәдҫқйҷ„жҖ§гҖҒеҲҶж•ЈжҖ§зҡ„еҺҶеҸІзү№еҫҒпјҢиҝҷжҳҜдёӯеӣҪеҸӨ代科еӯҰеҸҜд»Ҙй•ҝжңҹеҸ‘еұ•пјҢ并еңЁи®ёеӨҡж–№йқўйўҶе…Ҳдё–з•ҢпјҢдҪҶеҚҙж— жі•е®һзҺ°зӘҒз ҙзҡ„еҺҶеҸІж №жәҗгҖӮзӣёеә”ең°пјҢеҜ№дәҺ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еә”з«ҷеңЁз§‘еӯҰдёҺеҺҶеҸІе…Ёйқўдә’еҠЁзҡ„з«Ӣеңәд№ӢдёҠпјҢд»ҺзҺӢжңқзҡ„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гҖҒж”ҝжІ»дҪ“еҲ¶гҖҒж”ҝжІ»жҖқжғігҖҒзӨҫдјҡз»ҸжөҺгҖҒеҢәеҹҹзү№еҫҒгҖҒж–ҮеҢ–иғҢжҷҜеҮәеҸ‘пјҢжҸӯзӨә科еӯҰзҡ„ж”ҝжІ»з®ЎзҗҶгҖҒжҖқжғідәӨжөҒгҖҒзӨҫдјҡе®һи·өгҖҒеҶ…йғЁеҸ‘еұ•дёҺеҜ№еӨ–дәӨжөҒпјҢеҲҶжһҗдёҚеҗҢж—¶жңҹвҖңзҺӢжңқ科еӯҰвҖқзҡ„йҳ¶ж®өең°дҪҚгҖҒејҠз«Ҝй—®йўҳпјҢдҪ•д»ҘжңӘиғҪе®һзҺ°ж №жң¬зӘҒз ҙпјҢе®Ўи§Ҷе…¶еҜ№дәҺ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дё–з•Ң科еӯҰдә§з”ҹзҡ„ж•ҙдҪ“еҪұе“ҚпјҢд»ҺиҖҢжҺЁиҝӣдё–з•Ң科еӯҰж•ҙдҪ“еӣҫжҷҜзҡ„е…Ёйқўеұ•зӨәгҖӮзј–иҫ‘пјҡдҪ•еҸӮ ж–Үз« и§ҒгҖҠдёӯе·һеӯҰеҲҠгҖӢ2023е№ҙ第7жңҹвҖңеҺҶеҸІз ”究вҖқж Ҹзӣ®пјҢеӣ зҜҮе№…жүҖйҷҗпјҢжіЁйҮҠгҖҒ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зңҒз•ҘгҖӮ
|  д»ҳжҢҜеҘҮпјҡ家жҲ·е…ізі»и§Ҷи§’
д»ҳжҢҜеҘҮпјҡ家жҲ·е…ізі»и§Ҷи§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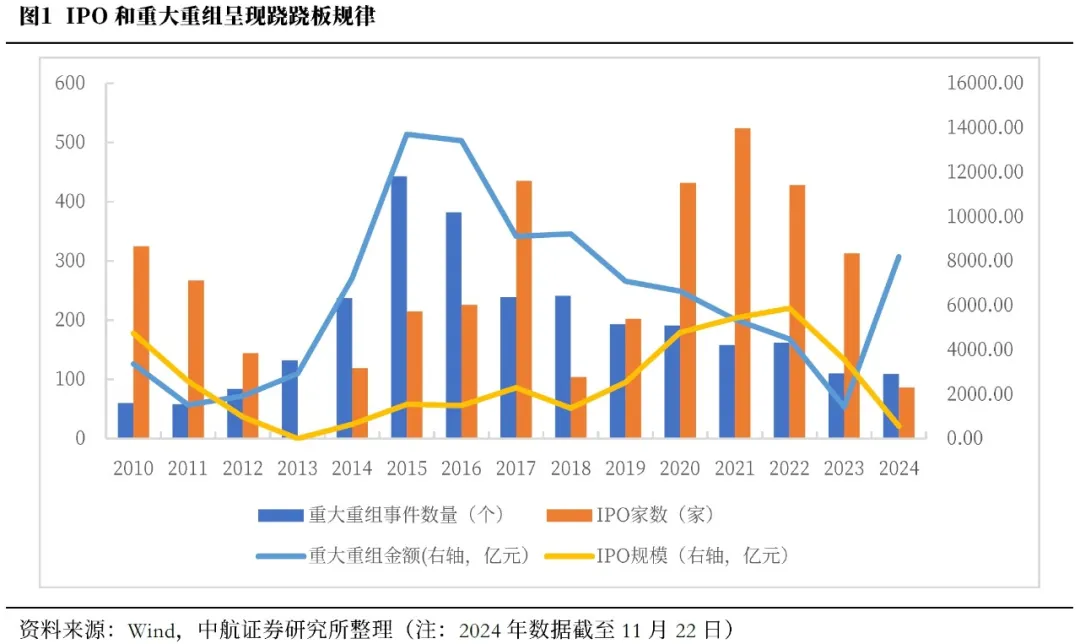 и‘Јеҝ дә‘зӯүпјҡе…іжіЁж–°дёҖиҪ®
и‘Јеҝ дә‘зӯүпјҡе…іжіЁж–°дёҖиҪ® зҪ—еҝ—жҒ’зӯүпјҡеҶ…йҳҒжҲҗе‘ҳжҖқ
зҪ—еҝ—жҒ’зӯүпјҡеҶ…йҳҒжҲҗе‘ҳжҖқ йҖҸи§ҶйғЁеҲҶдё»зІ®иӮІз§ҚвҖңеҗҢ
йҖҸи§ҶйғЁеҲҶдё»зІ®иӮІз§ҚвҖңеҗҢ вҖңдёӯзҫҺеӨ§иұҶиҙёжҳ“йў„жңҹвҖқ
вҖңдёӯзҫҺеӨ§иұҶиҙёжҳ“йў„жңҹвҖқ иұҶзІ•пјҡеҲ©з©әеҮәе°ҪжӢҗзӮ№жңҖ
иұҶзІ•пјҡеҲ©з©әеҮәе°ҪжӢҗзӮ№жңҖ дёӯеӣҪйҮҮиҙӯжҫіжҙІеӨ§йәҰз§ҜжһҒ
дёӯеӣҪйҮҮиҙӯжҫіжҙІеӨ§йәҰз§ҜжһҒ зҺӢж¶ө пјҡж¬ІвҖңзҘёж°ҙеӨ–еј•
зҺӢж¶ө пјҡж¬ІвҖңзҘёж°ҙеӨ–еј•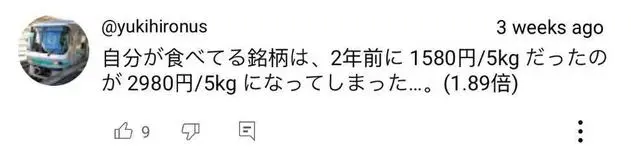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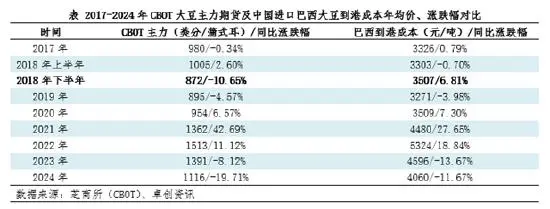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