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дҫҜе»әж–°пјҲеӨ©жҙҘеёҲиҢғеӨ§еӯҰ欧жҙІж–ҮжҳҺз ”з©¶йҷўйҷўй•ҝпјү 16дё–зәӘзҡ„иӢұеӣҪ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пјҢжҳҜеҺҶеҸІдёҠ第дёҖж¬Ўе…·жңүеёӮеңәжҢҮеҗ‘зҡ„еңҹең°зЎ®жқғиҝҗеҠЁпјҢжҳҜжҠҠе…·жңүе…ұеҗҢдҪ“жҖ§иҙЁзҡ„ж··еҗҲеңҹең°жүҖжңүеҲ¶з•Ңе®ҡдёәжҺ’д»–жҖ§зҡ„жҳҺжҷ°дә§жқғпјҢд»ҺиҖҢжҝҖеҠұ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пјҢйў иҰҶ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з»ҸиҝҮж•°дёӘдё–зәӘзҡ„зү©иҙЁз§ҜзҙҜгҖҒжқғеҲ©з§ҜзҙҜе’Ңи§Ӯеҝөз§ҜзҙҜпјҢзӨҫдјҡж·ұеұӮз»“жһ„еҸ‘з”ҹдәҶзӣёеҪ“ж·ұеҲ»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е…¶дёӯ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еҢ–е’ҢеҶңж°‘зҡ„зӨҫдјҡеҢ–жҳҜеҹәзЎҖжҖ§зҡ„еҸҳйҮҸеҸӮж•°пјҢеңҲең°еҚіжҳҜиҝҷз§ҚеҸҳеҢ–зҡ„еҺҶеҸІжҖ§жҖ»з»“гҖӮ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дҪңдёә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иҪҪдҪ“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ҖиғҪеҠЁгҖҒ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ҺЁеҠЁеҠӣйҮҸгҖӮ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йҖҡеёёж–№ејҸжҳҜ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гҖҒ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д»ҘеҸҠ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д»ҘеҗҲжі•еңҲең°дёәдё»гҖӮ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зЎ®е®һеӯҳеңЁпјҢжҳҜиөӨиЈёиЈёзҡ„жҺ еӨәпјҢжҡҙйңІдәҶж—©жңҹиө„жң¬зҡ„еӨұиҢғдёҺиҙӘе©ӘпјӣйўҶдё»жҡҙеҠӣ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еҸ—еҲ°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ҠөжҠ—пјҢдҪғеҶңзҡ„жҠөжҠ—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еҗҲжі•жҖ§е’Ңжңүж•ҲжҖ§пјӣдҪҶиҝҷз§ҚвҖң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еҫҲе°ҸвҖқгҖӮ16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еңҹең°зЎ®жқғд»ҺжқҘжІЎжңүжҠӣејғжі•еҫӢиҖҢжҳҜи¶ҠжқҘи¶Ҡ规иҢғпјҢ18дё–зәӘеҸ‘еұ•дёәвҖң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вҖқеҲҷеұһж°ҙеҲ°жё жҲҗгҖӮд»Һеҹәжң¬еұӮйқўдёҠи®ІпјҢеңҲең°дёҚжҳҜи·өиёҸ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жҒ°жҒ°жҳҜжҳҺжҷ°е’ҢзЎ®е®ҡ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жңүйҷҗпјҢеңҲең°дёӯеҝғең°еҢә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еӨ§жҰӮеңЁ20~25пј…е·ҰеҸі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Ҫұе“ҚиҮідёәж·ұиҝңпјҢжҳҜдёӘиҖҒиҜқйўҳд№ҹжҳҜеҹәзЎҖжҖ§иҜқйўҳпјҢжңүеҝ…иҰҒз»ҷдәҲж–°зҡ„е…іжіЁгҖӮ
16дё–зәӘеүҚеҗҺжҳҜиҘҝ欧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Ў®з«Ӣзҡ„ж—¶д»ЈпјҢдј з»ҹеҸІеӯҰжӣҙе…іжіЁең°зҗҶеӨ§еҸ‘зҺ°гҖҒж–ҮиүәеӨҚе…ҙжҲ–иӢұеӣҪйқ©е‘ҪгҖҒе°јеҫ·е…°йқ©е‘ҪзӯүпјҢ并е°Ҷе…¶и§Ҷдёә欧жҙІд№ғиҮідё–з•Ңиҝ‘д»ЈеҸІзҡ„ејҖзҜҮгҖӮиҝҷж ·зҡ„и§ӮзӮ№ж— еҸҜеҺҡйқһпјҢдҪҶеҗҢж—¶жҲ‘们иҝҳйЎ»зңӢеҲ°еӨ§дәӢ件иғҢеҗҺжӣҙж·ұеҺҡзҡ„иғҢжҷҜгҖӮеңҹең°иҙўдә§жқғ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жҳҜй•ҝж—¶ж®өзҡ„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йқҷжӮ„жӮ„зҡ„пјҢ然иҖҢдёҺжҳҫиө«зҡ„еӨ§йқ©е‘ҪеҚҙжҳҜ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зҡ„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и®ІпјҢдјҙйҡҸ16дё–зәӘиҝҷдёӘеҜҢжңүж„Ҹд№үзҡ„ж—¶й—ҙеҚ•дҪҚзҡ„еҗҜеҠЁпјҢеңЁж¬§жҙІзҡ„ж ёеҝғеҢәеҹҹпјҢжңҖе…·жңүж·ұиҝңеҺҶеҸІеҪұе“Қзҡ„дәӢ件пјҢиҺ«иҝҮдәҺиӢұж је…°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гҖӮ
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ҚжҳҜзҺӢеӣҪж”ҝеәңзҡ„и®ҫи®ЎпјҢзӣёеҸҚпјҢдёҖеәҰз”ҡиҮійҒӯеҲ°ж”ҝеәңзҡ„йҳ»жӯўпјҢ然иҖҢе®ғеҚҙжҳҜ欧жҙІеҺҶеҸІдёҠд№ҹжҳҜдәәзұ»еҺҶеҸІдёҠ第дёҖж¬Ўе…·жңүеёӮеңәжҢҮеҗ‘зҡ„еңҹең°ж”№йқ©иҝҗеҠЁгҖӮ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®һиҙЁдёҠжҳҜжҠҠе…·жңүе…ұеҗҢдҪ“жҖ§иҙЁзҡ„ж··еҗҲеңҹең°жүҖжңүеҲ¶з•Ңе®ҡдёәе…·жңүжҺ’д»–жҖ§зҡ„з§Ғдәәдә§жқғпјҢд»ҺиҖҢжҝҖеҠұ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пјҢжңҖз»Ҳйў иҰҶ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иҜәж–Ҝ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жүҖжңүжқғзҡ„жј”иҝӣпјҢд»ҺеҺҶеҸІдёҠзңӢеҢ…жӢ¬дәҶдёӨдёӘжӯҘйӘӨпјҢе…ҲжҳҜжҠҠеұҖеӨ–дәәжҺ’йҷӨеңЁеҲ©з”Ёиө„жәҗзҡ„ејәеәҰд»ҘеӨ–пјҢиҖҢеҗҺеҸ‘жҳҺи§„з« пјҢйҷҗеҲ¶еұҖеҶ…дәәеҲ©з”Ёиө„жәҗзҡ„ејәеәҰгҖӮвҖқ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…ҲжҳҜеә„еӣӯпјҚ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еҶ…еӨ–жңүеҲ«пјҢеҚіжҺ’ж–Ҙжқ‘зӨҫд»ҘеӨ–зҡ„дәәдҪҝз”Ёиө„жәҗзҡ„ејәеәҰпјӣ继иҖҢжҳҜйҷҗеҲ¶жң¬жқ‘й•ҮеҶ…йғЁдҪҝз”Ёиө„жәҗзҡ„ејәеәҰ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д»ҘдёӘдҪ“дёәеҚ•дҪҚпјҢеңЁеә„еӣӯпјҚ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еҶ…жҳҺзЎ®дёӘдә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зҡ„иҫ№з•ҢгҖӮиҘҝ欧дёӯдё–зәӘд№Ўжқ‘е…ұеҗҢдҪ“жңү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зҡ„иҮӘжІ»дёҺдә’еҠ©еӣ зҙ пјҢеҗҢж—¶ж„Ҹе‘ізқҖжңҚд»ҺгҖҒйҡ”з»қдёҺзӢӯйҡҳ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ӯЈжҳҜжүҖжңүжқғеҺҶеҸІжј”иҝӣзҡ„第дәҢдёӘжӯҘйӘӨпјҢеҚіеңЁеёӮеңәеҢ–е’ҢзӨҫдјҡеҢ–зҡ„жқЎд»¶дёӢпјҢеә„еӣӯе…ұеҗҢдҪ“еҶ…з”ҡиҮіеңЁе®¶еәӯеҶ…жҳҺзЎ®з§Ғдә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гҖӮ
дёҖгҖҒеңҲең°з©¶з«ҹжҳҜжҖҺж ·зҡ„иҝҗеҠЁ
ж¬ІзҹҘеңҲең°жҳҜд»Җд№ҲпјҢе…ҲйЎ»жҳҺдәҶеңҲең°дёҚжҳҜд»Җд№ҲпјҢе®ғзӣёеҜ№дҪ•зү©иҖҢиЁҖгҖӮ
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жҳҜзӣёеҜ№дәҺвҖңж•һз”°вҖқиҖҢиЁҖгҖӮж•һз”°пјҲпҪҸпҪҗпҪ…пҪҺ пҪҶпҪүпҪ…пҪҢпҪ„пҪ“пјүж„ҸжҢҮдј з»ҹеә„еӣӯзҡ„з”°еҲ¶пјҢиҖ•ең°з”ұеҲҶж•Јзҡ„ж•°зҷҫд№ғиҮіжӣҙеӨҡзӢӯй•ҝзҠ¶зҡ„жқЎз”°жүҖжһ„жҲҗпјҢжқЎз”°д№Ӣй—ҙд»…з”ЁиҚүеһ„еҲҶеүІпјҢжІЎжңүж°ёд№…зҡ„еӣҙеһЈпјҢ收еүІеҗҺжӣҙж— жҳҺжҳҫз•ҢйҷҗпјҢдј‘иҖ•ж—¶еҲҷжҲҗдёәжүҖжңүжқ‘ж°‘зҡҶеҸҜдҪҝз”Ёзҡ„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гҖӮе…ідәҺж•һз”°еҲ¶зҡ„еҹәжң¬зү№еҫҒпјҢз‘ҹж–Ҝе…ӢпјҲпјӘпҪҸпҪҒпҪҺ пјҙпҪҲпҪүпҪ’пҪ“пҪӢпјүеҪ’зәідёәеӣӣдёӘдё»иҰҒж–№йқўпјҡдёҖжҳҜдҪғеҶңзҡ„иҖ•ең°дёҚжҳҜйӣҶдёӯеңЁдёҖиө·зҡ„иҖҢжҳҜеҲҶж•ЈдёәдёҚеҗҢең°еқ—дёҠзҡ„жқЎз”°пјҢдәҢжҳҜиҪ®иҖ•еҲ¶пјҢдёүжҳҜе…ұеҗҢж”ҫзү§еҲ¶пјҢеӣӣжҳҜдёҠиҝ°ж•һз”°еҲ¶зҡ„еҹәжң¬и§„еҲҷз”ұ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иҙҹиҙЈе®һж–Ҫ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ж•һз”°е…·жңүжҳҺжҳҫзҡ„жқ‘зӨҫе…ұеҗҢдҪ“иғҢжҷҜпјҢжқ‘ж°‘жңүзӣёеҪ“зЁӢеәҰзҡ„еҚҸдҪңпјҡжҜҸдёӘдәәеҚ жңү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жҳҜеӣәе®ҡзҡ„пјҢдҪҶеңҹең°зҡ„дҪҚзҪ®жҳҜеҸҳеҠЁ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иҖ•ең°е№ҙе№ҙиҪ®жҚўпјҢжүҖд»Ҙдәә们жҢҮзқҖдёҖеқ—ең°иҜҙпјҢд»Ҡе№ҙе®ғжҳҜжҲ‘зҡ„пјҢжҳҺе№ҙе°ұжҳҜеҲ«дәәзҡ„дәҶгҖӮиҖҢзҺ°еңЁжҳҜеҲ«дәәзҡ„йӮЈеқ—жҳҺе№ҙеҲҷжҳҜжҲ‘зҡ„гҖӮзӢӯй•ҝзҡ„жқЎз”°пјҲпҪ“пҪ”пҪ’пҪүпҪҗпјүжҳҜиҪ®иҖ•зҡ„еҹәжң¬еҚ•дҪҚпјҢжҜҸдёӘдҪғжҲ·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еҲҶеёғеңЁеҗ„еӨ„пјҢ并дёҺе…¶д»–дҪғжҲ·зҡ„жқЎз”°зӣёдәӨй”ҷгҖӮ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пјҢдёҖжқЎз”°зӣёеҪ“дәҺпј‘иӢұдә©пјҢеӨ§зәҰ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зүӣйҳҹдёҖеӨ©зҡ„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пјҢжүҖи°“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пјҢеңЁеҪўејҸдёҠе°ұжҳҜе°ҶиҮӘе·ұ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йӣҶдёӯиө·жқҘпјҢе®ЈзӨәеңҲең°иҖ…еҜ№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并жҸҗеҚҮз”ҹдә§ж•ҲзҺҮ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•һз”°иҝҳеҢ…жӢ¬еә„еӣӯе‘ЁеӣҙеӨ§зүҮзҡ„иҚ’ең°гҖҒж°ҙеЎҳгҖҒжІјжіҪе’ҢжЈ®жһ—пјҢжҜҸдёҖдҪҚжқ‘ж°‘йғҪжңүдҪҝз”Ёе®ғ们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жүҖд»Ҙиў«з§°дёәе…ұз”Ёең°пјҢеҸҲз§°е…¬ең°пјҲпҪғпҪҸпҪҚпҪҚпҪҸпҪҺ пҪҶпҪүпҪ…пҪҢпҪ„пҪ“пјүгҖӮжҢүз…§еҸӨиҖҒзҡ„жғҜдҫӢпјҢеҶңж°‘дё–дё–д»Јд»Јең°еҲ©з”Ёе®ғ们пјҢж”ҫжҹҙгҖҒдјҗжңЁгҖҒж”ҫзүІз•ңгҖҒжӢҫж©ЎеӯҗгҖҒйҮҮиҳ‘иҸҮд»ҘеҸҠжё”зҢҺзӯүпјҢжҳҜ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з”ҹжҙ»зҡ„йҮҚиҰҒиө„жәҗгҖӮе…¬ең°зҡ„дҪҝз”ЁдёҚд»…жңүз»ҸжөҺж„Ҹд№үпјҢиҝҳж Үеҝ—зқҖдҪҝз”ЁиҖ…зҡ„е…¬е…ұжқғеҲ©пјҢ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д№ӢеӨ–зҡ„дәәдёҚеҸҜд»ҘдҪҝз”Ёе…¬ең°гҖӮе…ұз”Ёең°еҗҚд№үдёҠйўҶдё»з®Ўиҫ–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иҝңдёҚжҳҜйӮЈд№Ҳз®ҖеҚ•гҖӮеӨ§зәҰ1070е№ҙпјҢиҘҝзҸӯзүҷе·ҙеЎһзҪ—йӮЈжө·е…і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өҒеҠЁзҡ„ж°ҙе’ҢеұұжіүгҖҒиҚүеңәгҖҒзү§еңәгҖҒжЈ®жһ—гҖҒзҒҢжңЁдёӣе’ҢеІ©зҹіпјҢеұһдәҺз”·зҲө们пјҢдҪҶ他们дёҚиғҪд»Ҙе®Ңе…ЁжүҖжңүжқғпјҲпҪ…пҪҺ пҪҒпҪҢпҪҢпҪ…пҪ•пјүзҡ„еҪўејҸжҢҒжңүгҖӮвҖқеҚіпјҢеңЁе…ұз”Ёең°дёҠпјҢз”·зҲө们еҸӘжӢҘжңүеұһдәҺ他们зҡ„йӮЈд»ҪжқғеҲ©пјҢвҖңдҪңдёәйўҶең°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иҝҳиҰҒи®©е…¶жқ‘民们йҡҸж—¶йғҪеҸҜдә«з”Ёиҝҷдәӣиө„жәҗвҖқгҖӮеҰӮжһңе°Ҷе…¬з”Ёең°и§ҶдҪңең°дә§пјҢжҲ‘们еҸ‘зҺ°е…¬ең°дёҠзҡ„дёҚеҗҢжқғеҲ©зҡ„еҸ еҠ е’Ңзә з»“иҫҫеҲ°дәҶжһҒе…¶еӨҚжқӮзҡ„зЁӢеәҰпјҢд»ҘиҮідәҺеёғжҙӣиө«иҜҙпјҡвҖңиҰҒжғіжүҫеҮәи°ҒжҳҜдёӯдё–зәӘе…¬ең°зҡ„зңҹжӯЈдё»дәәжҳҜеҫ’еҠізҡ„гҖӮвҖқе…ұз”Ёең°зҡ„дә§жқғжңҖдёәжЁЎзіҠпјҢжүҖд»ҘеңҲең°дёӯеј•иө·зҡ„дәүз«ҜжңҖеӨҡгҖӮдёҚи®әдҪғеҶңдёӘдәә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иҝҳжҳҜе…ұз”Ёең°пјҢдј з»ҹзҡ„еңҹең°ж··еҗҲжүҖжңүжқғжӯЈеңЁжј”еҢ–дёәжҺ’д»–жҖ§зҡ„з§ҒдәәжүҖжңүжқғгҖӮ
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зӣёеҜ№дәҺжқҹзјҡеңЁж•һз”°дёҠзҡ„дҪғеҶңеҸҠе…¶дҝқжңүең°дә§жқғиҖҢиЁҖгҖӮеңЁдёӯдё–зәӘпјҢеә„еӣӯжі•жҸҸиҝ°дҫқйҷ„дҪғеҶңдёҺеңҹең°е…ізі»зҡ„жі•еҫӢиҜӯиЁҖ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пјҢ称他们жҳҜвҖңжқҹзјҡдәҺеңҹең°дёҠзҡ„дәәвҖқпјҲпҪҮпҪҢпҪ…пҪӮпҪҒпҪ… пҪҒпҪӮпҪ“пҪғпҪ’пҪүпҪҗпҪ”пҪҒпҪ…пјүгҖӮиҝҷж„Ҹе‘ізқҖпјҢд»–дёҚиғҪйҡҸж„Ҹ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ӣд№ҹж„Ҹе‘ізқҖпјҢйҷӨйқһж №жҚ®жҹҗдәӣжқЎд»¶пјҢдёҚиғҪе°ҶдҪғеҶңй©ұйҖҗгҖӮеңЁд№ жғҜжі•зҡ„дҝқжҠӨдёӢпјҢ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еҚ жңүжқғзЁіе®ҡпјҢдё–д»ЈжүҝиўӯпјҢе…¶з§ҜжһҒж„Ҹд№үдёҚеҸҜдҪҺдј°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йЎ»жүҝи®Өе®ғд»Қ然еұҖйҷҗеңЁе°Ғе»әеә„еӣӯеҲ¶зҡ„жЎҶжһ¶дёӢпјҡдәәжҳҜжқҹзјҡдәҺеңҹең°дёҠзҡ„дәәпјҢжңҖз»ҲжҳҜдҫқйҷ„дәҺйўҶдё»зҡ„дәәпјҢиҖҢдҝқжңүең°жҳҺжҳҫжүҝиҪҪзқҖиә«д»Ҫе’ҢжқғеҠӣзҡ„ејәеҲ¶еӣ зҙ гҖӮеҮ дёӘдё–зәӘд»ҘжқҘпјҢйҡҸзқҖдҪғеҶңиҮӘз”ұзЁӢеәҰе’Ң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зҡ„жҷ®йҒҚж”№е–„пјҢ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йҖҗжёҗеҹ№иӮІиө·жқҘпјҢдҪғеҶңеҸҠе…¶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еҶ…ж¶өз»ҸеҺҶдәҶйҮҚж–°е®ҡд№үпјҢ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е°Өе…¶жҳҺжҳҫ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ҪғеҶңдё»дҪ“е·ІжҳҜ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пјҢе…¶еүҚиә«жҳҜдҫқйҷ„жҖ§зҡ„дҪғжҲ·з»ҙе…°пјҲпҪ–пҪүпҪҢпҪҢпҪ…пҪүпҪҺпјүгҖӮе…¬з°ҝеҶңеҸҜиҮӘз”ұиҝҒеҫҷпјҢеҲ°д»–е–ңж¬ўеҺ»зҡ„д»»дҪ•ең°ж–№е°ұдёҡпјӣд»–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ёҚд»…еҸ—еҲ°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иҖҢдё”еҸ—еҲ°зҺӢеӣҪжҷ®йҖҡжі•дҝқжҠӨпјҢеңҹең°еҸҜеҗҲжі•еҮәе”®гҖҒиҪ¬з§ҹе’ҢжҠөжҠј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°Ҫз®Ўе…¬з°ҝеҶңд»Қз»ҹз§°дёә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пјҢдҝқз•ҷзқҖе°Ғе»әе…ізі»зҡ„еӨ–еЈіпјҢе®һиҙЁдёҠдёҺйўҶдё»е·Із»ҸдёҚеҶҚжҳҜдәәиә«дҫқйҷ„е…ізі»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е•ҶдёҡжҖ§зҡ„з§ҹдҪғе…ізі»пјҢеӣ жӯӨе…¶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иҺ·еҫ—дәҶдёҖз§ҚеёӮеңәиҢғз•ҙеҶ…зҡ„жі•еҫӢж—¶ж•ҲжҖ§пјҢдё–иўӯе°Ғе»әдҝқжңүең°д№ҹе°ұиө°еҲ°дәҶе°ҪеӨҙгҖӮжүҖи°“вҖңе…¬з°ҝвҖқе°ұжҳҜдҪғеҶңжҢҒжңү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иҜҒд№ҰпјҢж №жҚ®жі•еәӯзЎ®и®Өзҡ„дёҚеҗҢзҡ„з§ҹзәҰжқЎд»¶пјҢе…¬з°ҝдёҠи®°иҪҪзқҖдёҚеҗ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дёҖ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е…·жңү世代继жүҝжқғпјҲпҪғпҪҸпҪҗпҪҷпҪҲпҪҸпҪҢпҪ„ пҪҸпҪҶ пҪүпҪҺпҪҲпҪ…пҪ’пҪүпҪ”пҪҒпҪҺпҪғпҪ…пјүпјҢеӨ§йғЁеҲҶеҲҷжҳҜжңүжңҹйҷҗ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е…¶дёӯиҫғй•ҝжңҹзҡ„еҸҜиҫҫж•°д»ЈпјҲпҪғпҪҸпҪҗпҪҷпҪҲпҪҸпҪҢпҪ„ пҪҶпҪҸпҪ’ пҪҢпҪүпҪ–пҪ…пҪ“пјүпјҢйҖҡеёёдёүд»ЈжҢҒжңүпјӣзҹӯжңҹиҖ…йҷҗдәҺз»Ҳиә«жҲ–иӢҘе№Іе№ҙжҢҒжңүпјҲпҪҶпҪҸпҪ’ пҪҒ пҪ”пҪ…пҪ’пҪҚ пҪҸпҪҶ пҪҢпҪүпҪҶпҪ… пҪҸпҪ’ пҪҷпҪ…пҪҒпҪ’пҪ“пјүгҖӮжүҝз§ҹиҖ…еңЁз§ҹзәҰжңүж•ҲжңҹеҶ…еҸ—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пјҢдёҖж—Ұз§ҹзәҰжңҹж»ЎйЎ»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жҲ–йҮҚж–°е•Ҷи°ҲжқЎд»¶д»Ҙз»ӯзәҰгҖӮеҪ“然дҪғеҶңд№ҹеҸҜд»Ҙд№°ж–ӯеңҹең°пјҢиҮӘе·ұжҲҗдёәең°дә§дё»гҖӮеҶңж°‘ж‘Ҷи„ұеңҹең°зҡ„жқҹзјҡпјҢиҮӘз”ұең°ж”Ҝй…ҚиҮӘе·ұеҠіеҠЁеҠӣпјҢжҳҜжүҖжңүжқғеҸ‘еұ•еҸІзҡ„йҮҚиҰҒиҠӮзӮ№пјҢиҝҷз§ҚеҜ№иҮӘе·ұеҠіеҠЁеҠӣзҡ„第дёҖдёӘвҖңжүҖжңүвҖқжҳҜзҺ°д»Јиҙўдә§жқғзҡ„зңҹжӯЈйј»зҘ–гҖӮеҸ—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зҡ„дәәиә«иҮӘз”ұи·қзҰ»иҙўдә§иҮӘз”ұд»…дёҖжӯҘд№ӢйҒҘпјҢиӢұеӣҪеҶңж°‘еңЁ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дёӯжҺҖиө·з¬¬дёҖжіўдәәиә«и§Јж”ҫжөӘжҪ®пјҢд№ҹжҳҜ第дёҖдёӘзЎ®з«Ӣз§Ғдәәдә§жқғеҲ¶еәҰзҡ„еӣҪ家пјҢдёҚжҳҜеҒ¶з„¶зҡ„гҖӮеңЁдёӘдҪ“еҶңж°‘жҷ®йҒҚеҸ‘еұ•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иӢұеӣҪйҰ–е…ҲеҮәзҺ°дҫқйқ йӣҮдҪЈеҠіеҠЁзҡ„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пјҢ他们дёҺдёҖйғЁеҲҶд№Ўз»…жҗәжүӢеҪўжҲҗд№Ўжқ‘зӨҫдјҡзҡ„вҖң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вҖқпјҢеҚіеҗҺжқҘвҖң第дёүзӯүзә§вҖқзҡ„дё»дҪ“гҖӮ他们з§ҜжһҒеҸӮдёҺеңҲең°пјҢжҲҗдё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дёҚеҸҜжӣҝд»Јзҡ„еҠӣйҮҸпјҢе…¶дёӯдёҖдәӣдәәжҲҗдёәж–°еһӢең°дә§дё»гҖӮжҳҫ然пјҢ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еҚіеңЁ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еңҹең°зҡ„е‘Ёеӣҙзӯ‘иө·зҜұз¬ҶжҲ–жҢ–дёӢжІҹеЈ‘пјҢиЎЁзӨәиҜҘең°жҳҜз§Ғжңүиҙўдә§гҖӮ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еңЁеҪўејҸдёҠд»Һж•һз”°дёӯеҲҮеүІеҮәжқҘ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еңЁдә§жқғдёҠд№ҹдёҺж•һз”°дёҚеҗҢгҖӮ
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д№ҹзӣёеҜ№дәҺ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иҖҢиЁҖ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е®һдёәе°Ғе»әең°з§ҹ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еңЁд№ жғҜжі•зәҰжқҹдёӢдҪғеҶңжҢүз…§е°Ғе»әжқЎд»¶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гҖҒдәӨзәіең°з§ҹпјҢд№ҹж„Ҹе‘ізқҖең°з§ҹеҹәжң¬дёҚеҸҳгҖӮ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з»Ҳз»“дәҶдё–иўӯ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ң°пјҢеҠҝеҝ…д№ҹдјҡз»Ҳз»“дё–д»ЈдёҚеҸҳзҡ„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пјҢдҪҝд№Ӣзәіе…ҘеёӮеңәд»·ж јдҪ“зі»пјҢжҲҗдёәе•Ҷдёҡең°з§ҹ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зҡ„зЁіе®ҡеҜ№еҶңжқ‘з»ҸжөҺз№ҒиҚЈеҒҡеҮә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дёҖеҗ‘дёәеҸІеӯҰз•Ңе…¬и®Ө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йҒҸеҲ¶дәҶйўҶдё»зҡ„иҙӘж¬І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еңҹең°еўһеҖјйғЁеҲҶжөҒиҝӣеҶңж°‘еҸЈиўӢпјҢдҝғиҝӣе°ҸеҶң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гҖӮжңүиҜҒжҚ®жҳҫзӨәпјҢе°ҸеҶңзҡ„з»ҸжөҺз№ҒиҚЈжҳҜд»Һдёӯ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ејҖе§Ӣзҡ„пјҢ他们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规模е’ҢеҶңдёҡиҖ•дҪңдёӯзҡ„иҮӘдё»жҖ§йғҪжңүжүҖеўһй•ҝпјҢд»ҘиҮідәЁеҲ©дёғдё–еңЁдҪҚзҡ„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иў«и§Ҷдёәе°ҸеҶңзҡ„й»„йҮ‘ж—¶жңҹгҖӮд»ҺеҺҶеҸІй•ҝж—¶ж®өжқҘзңӢпјҢйҖҡиҙ§иҶЁиғҖи¶ӢеҠҝжҖ»жҳҜйҡҫе…ҚпјҢеҒҮеҰӮжІЎжңүдёҖе®ҡеҠӣеәҰзҡ„йҷҗе®ҡпјҢ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дәҢдёүзҷҫе№ҙдҝқжҢҒзЁіе®ҡзҠ¶жҖҒжҳҜйҡҫд»ҘжғіиұЎзҡ„гҖӮиҝҷз§ҚејәеҲ¶зҡ„йҷҗе®ҡдҪңз”ЁеҢ…еҗ«дј з»ҹзҡ„жі•еҫӢеӣ зҙ пјҢд№ҹеҢ…еҗ«еҶңж°‘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йЎҪејәжҠөжҠ—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д№ҹйЎ»жё…йҶ’ең°зңӢеҲ°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зҡ„дёӨйқўжҖ§пјҢеҚіеҜ№йўҶдё»зҡ„иҙӘе©Әе’Ңең°з§ҹеёӮеңәиө°еҗ‘зҡ„еҸҢеҗ‘ејәеҲ¶пјҢеҗҺиҖ…еҲ°16дё–зәӘж„ҲеҠ еҮёжҳҫ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й•ҝжңҹзЁіе®ҡзҡ„ең°з§ҹж— з–‘жңүеҲ©дәҺдҪғжҲ·иҙўдә§зҡ„жҷ®йҒҚз§ҜзҙҜ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еҲҷжҳҜең°з§ҹдёҺеёӮеңәд»·ж јзҡ„иғҢзҰ»пјҢиЎЁзҺ°еңЁ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е’ҢдҪғеҶңзәҜ收зӣҠд№Ӣй—ҙзҡ„е·®и·қи¶ҠжқҘи¶ҠеӨ§пјҢдёҖиҲ¬йғҪиҫҫеҲ°4еҖҚжҲ–5еҖҚпјҢз”ҡиҮі18еҖҚгҖӮең°з§ҹеӣ д№ жғҜжі•йҷҗе®ҡиҖҢдёҚеҸҳпјҢ然иҖҢдҪғеҶңжқҘиҮӘеңҹең°зҡ„收зӣҠеҚҙдёҚж–ӯеўһй•ҝ并йҖҡиҝҮеёӮеңәиҺ·еҫ—гҖӮе…¶ж—¶пјҢдёҺд№ жғҜең°з§ҹ并еӯҳзҡ„иҝҳжңүж—ҘзӣҠеҸ‘еұ•зҡ„е•Ҷдёҡең°з§ҹпјҢз”ұдәҺ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дёҺе•Ҷдёҡең°з§ҹзҡ„е·®и·қеҰӮжӯӨжҳҺжҳҫпјҢдёҖдәӣдҪғжҲ·зҙўжҖ§е°Ҷе…¶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ң°дәҢж¬ЎеҮәз§ҹвҖ”вҖ”вҖ”еҪ“然жҢүз…§еёӮеңәд»·ж јеҮәз§ҹпјҢд»ҺдёӯиҺ·еҸ–дәҢиҖ…д№Ӣй—ҙзҡ„е·®д»·гҖӮ1549е№ҙеҮәзүҲзҡ„гҖҠиӢұж је…°жң¬еңҹе…¬е…ұзҰҸеҲ©еҜ№иҜқйӣҶгҖӢдёҖд№ҰпјҢеҸҚеӨҚжҸҗеҲ°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ж»һеҗҺдәҺеёӮйқўжөҒиЎҢзҡ„д»·ж јпјҢиҮҙдҪҝзӨҫдјҡз»ҸжөҺеҮәзҺ°дёҘйҮҚзҡ„дёҚе№іиЎЎ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жң¬жҳҜдҝқжҠӨ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зҡ„вҖңйҳІжіўе ӨвҖқпјҢи°ҒжғіжӯӨж—¶еҚҙжҲҗдёәйҳ»ж–ӯеңҹең°дёҺ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иҒ”зі»зҡ„жңҖеҗҺдёҖйҒ“йҡңзўҚ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дёҺ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ң°дёҖж ·пјҢжҜ•з«ҹжҳҜдёҖз§Қдёӯдё–зәӘи¶…з»ҸжөҺеӣ зҙ ең°з§ҹпјҢиҝҹж—©иҰҒж·ҳжұ°гҖӮ
еҸ—д№ жғҜжі•дҝқжҠӨзҡ„д№ жғҜеңҹең°е’Ң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пјҢжәҗдәҺ欧жҙІе°Ғе»әеҲ¶зҡ„еҘ‘зәҰеӣ зҙ пјҢ然иҖҢеҚҙжңүеҲ©дәҺдёӯдё–зәӘ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з№ҒиҚЈе’Ң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еҸ‘иӮІпјҢиҖҢеҸ‘еұ•иө·жқҘзҡ„еёӮеңәеҸҚиҝҮжқҘеҜ№д№ жғҜеңҹең°еҸҠең°з§ҹжҸҗеҮәжҢ‘жҲҳпјҢиҝ«дҪҝе…¶йҖҗжёҗзәіе…Ҙ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зҡ„иҠӮеҘҸпјҢйў„зӨәзқҖдёәеә„еӣӯз»ҸжөҺеҲ’дёҠдј‘жӯўз¬Ұ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йҡҸзқҖзӨҫдјҡе’Ңз»ҸжөҺеҗ„ж–№еҠӣйҮҸзҡ„еҚҡејҲпјҢдә§з”ҹдәҶеҲқжӯҘе…·еӨҮзҺ°д»Ји§ӮеҝөгҖҒзҺ°д»ЈиҜүжұӮе’ҢеҠӣйҮҸзҡ„ж–°е…ҙдәәзҫӨд»ҘеҸҠзӣёеә”зҡ„зӨҫдјҡзҺҜеўғпјҢеҪ“ж–°ж—§еҠӣйҮҸж¶Ҳй•ҝиҫҫеҲ°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Ҡҝеҝ…еҮәзҺ°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жҖ§иҪ¬жҚ©зӮ№пјҢиҝҷе°ұ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гҖӮ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иҘҝж–№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§Ғдә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зҡ„еҪўжҲҗжҳҜзӣёеҪ“еӨҚжқӮзҡ„пјҢе®ғи„ұиғҺдәҺе°Ғе»әзӨҫдјҡжҜҚдҪ“жңҖз»ҲеҸҲеҗҰе®ҡдәҶйӮЈдёӘжҜҚдҪ“пјҢе®ғжҳҜз»ҸжөҺе’ҢзӨҫдјҡй•ҝжңҹи•ҙеҢ–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
еҗҢж ·пјҢдәә们еҜ№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и®ӨиҜҶд№ҹз»ҸеҺҶдәҶжӣІжҠҳзҡ„иҝҮзЁӢгҖӮ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иӢұеӣҪйғҪй“Һж—¶д»Јзҡ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иў«жҸҸз»ҳжҲҗвҖңзҫҠеҗғдәәвҖқзҡ„иҝҗеҠЁпјҢиҝҷдёҺжүҳ马ж–ҜВ·иҺ«е°”пјҲпјіпҪүпҪ’пјҺпјҙпҪҲпҪҸпҪҚпҪҒпҪ“ пјӯпҪҸпҪ’пҪ…пјүзӯүдәәеҪ“е№ҙеҜ№еңҲең°зҡ„жҺ§иҜүжңүеҫҲеӨ§е…ізі»гҖӮ他们и®ӨдёәпјҢеңҲеҚ 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дёӯжҷ®йҒҚдҪҝз”ЁжҡҙеҠӣпјҢз”ұдәҺиҖ•ең°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еӨ§йҮҸеҶңж°‘иў«й©ұйҖҗеҮәеңҹең°пјҢвҖңеңЁж¬әиҜҲе’ҢжҡҙеҠӣжүӢж®өд№ӢдёӢиў«еүҘеӨәдәҶиҮӘе·ұзҡ„жүҖжңүвҖҰвҖҰйқһзҰ»ејҖ家еӣӯдёҚеҸҜвҖқгҖӮиҮідәҺи°ҒеңЁеңҲең°пјҢдј з»ҹзҡ„зңӢжі•еҪ“然жҳҜйўҶдё»пјҢ他们й©ұйҖҗдҪғеҶңиҝӣиҖҢеңҲең°гҖӮиҝҷдәӣзңӢжі•дјјд№Һе·Із»Ҹ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дёҚеҲҠд№Ӣи®әпјҢйҖ жҲҗдәҶдёҖз§ҚжҖқз»ҙе®ҡејҸпјҡ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°ұжҳҜйўҶдё»еүҘеӨәеҶңж°‘еңҹең°зҡ„иЎҖи…ҘиҝҗеҠЁгҖӮ
然иҖҢпјҢиҝҷдәӣзңӢдјјеӨ©з»Ҹең°д№ү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йҡҸзқҖжӣҙдёәе®һиҜҒзҡ„еҸІж–ҷиў«йҖҗжёҗеҸ‘зҺ°е’Ңз ”и®ЁпјҢеӣҪйҷ…еӯҰз•ҢзңӢжі•ж—©е·Іж”№еҸҳпјҢеңЁ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Ҹ‘з”ҹдёүзҷҫе№ҙеҗҺеҚі20дё–зәӘеҲқеҸ¶пјҢе°ұжңү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и®ӨдёәпјҢ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дәә们еӨёеӨ§дәҶеңҲең°зҡ„规模е’ҢеңҲең°йҖ жҲҗзҡ„жҚҹе®іпјҢе…¶дёӯзҫҺеӣҪеӯҰиҖ…пј§пјҺзӣ–дјҠпјҲпјҘпҪ„пҪ—пҪүпҪҺ пјҰпјҺ пј§пҪҒпҪҷпјүзҡ„з ”з©¶жңҖе…·жңүеҶІеҮ»еҠӣгҖӮ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ҳҜдёҚй”ҷзҡ„пјҢдёҚиҝҮиҝҷд»…д»…жҳҜж•ҙдёӘз”»йқў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дҪғеҶңд№ҹеңЁеңҲең°пјҢ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жӣҙжҳҜдёҫи¶іиҪ»йҮҚгҖӮе…¶е®һж—©еңЁ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°ұжңүеӯҰиҖ…жіЁж„ҸеҲ°дәҶ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зҡ„еҺҶеҸІеҸІе®һпјҢеҸҜжғңжІЎжңүеј•иө·жӣҙеӨҡзҡ„е…іжіЁпјҢдҫӢеҰӮеҶңдёҡеҸІеӯҰ家иҸІиҢЁиө«дјҜзү№пјҲпјҰпҪүпҪ”пҪҡпҪҲпҪ…пҪ’пҪӮпҪ…пҪ’пҪ”пјүе’Ңжө·е°”ж–ҜпјҲпјЁпҪҒпҪҢпҪ…пҪ“пјүпјҢд»ҘеҸҠ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зҡ„иҜәзҷ»пјҲпј®пҪҸпҪ’пҪ„пҪ…пҪҺпјүе’ҢжқҺпјҲпј¬пҪ…пҪ…пјүйғҪе·Із»ҸжҢҮеҮәпјҡйҷӨдәҶ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иҝҳжңүдҪғеҶңзҡ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гҖӮ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зҡ„зӣ®ж ҮжҳҜжҠҠ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еҸҳдёәзҙ§еҮ‘еһӢзҡ„еңҹең°пјҲпҪғпҪҸпҪҚпҪҗпҪҒпҪғпҪ” пҪҶпҪүпҪ…пҪҢпҪ„пјүпјҢз”ЁзҜұз¬Ҷе°Ҷ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еӣҙеңҲиө·жқҘпјҢ并йҖҗжёҗж¶ҲйҷӨ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е’ҢиҚ’ең°пјҢд»ҺиҖҢеўһеҠ е°ҸйәҰдә§йҮҸпјҢжҸҗй«ҳеңҹең°д»·еҖјгҖӮпј‘пјҷ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еҲ©иҫҫе§ҶпјҲпј¬пјҺпјіпјҺпј¬пҪ…пҪҒпҪ„пҪҒпҪҚпјүеҮәзүҲгҖҠеңҲең°жң«ж—Ҙе®ЎеҲӨгҖӢпјҢ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еҶҷжҲҗпјҢд»–жҳҺзЎ®жҢҮеҮ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ҸҜд»ҘеҲҶдёәдёӨз§Қзұ»еһӢпјҢеҚі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е’Ң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пјҢ并и®ӨдёәдёӨз§Қзұ»еһӢеңҲең°еҗ„еҚ дёҖе®ҡзҡ„жҜ”дҫӢгҖӮ20дё–зәӘеҲқеҸ¶зҡ„зӣ–дјҠпјҢе…¶еҗҺзҡ„жІғеӢ’ж–ҜеқҰе’Ңж‘©е°”зҡҶжҢҒзӣёеҗҢ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е·ҙжһ—йЎҝВ·ж‘©е°”е°Өе…¶йҮҚи§ҶеӨ§еҶңзҡ„ејҖжӢ“дҪңз”Ё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жҺЁеҠЁеҶңдёҡеҸҳйқ©зҡ„вҖңзңҹжӯЈе…Ҳй©ұвҖқжҒ°жҒ°жҳҜиҝҷдәӣеӨ§еңҹең°жүҝз§ҹдәәе’ҢеҜҢиЈ•зҡ„дёӘдәәиө„дә§жӢҘжңүиҖ…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вҖңйӮЈдәӣиў«иҝҪжҚ§зҡ„е°‘ж•°жңүиҝӣеҸ–еҝғзҡ„йўҶдё»вҖқгҖӮе…ідәҺйғҪй“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д»ҺпјІпјҺжүҳе°јеҲ°пјӘпјҺжғ зү№е°”пјҢдёҚж–ӯжңүзІҫе“ҒеҠӣдҪңжҺЁеҮәпјҢдёҚж–ӯж·ұеҢ–иҝҷдёҖжҢҒд№…дёҚиЎ°зҡ„иҜқйўҳгҖӮеҸҜжғңпјҢиҝҷдәӣйўҮжңүи§Ғең°зҡ„еӯҰжңҜж„Ҹи§Ғд»ҘеҸҠйҖҗжёҗжҠ«йңІзҡ„ж—©жңҹжі•еәӯжЎЈжЎҲзӯүпјҢеңЁеӣҪеҶ…еӯҰз•ҢеҚҙжІЎжңүеҫ—еҲ°еә”жңүзҡ„еҲҶдә«е’ҢдәӨжөҒпјҢдәә们еҫҖеҫҖеӣҝдәҺж—©жңҹзҡ„вҖңеңҲең°еҚ°иұЎвҖқпјҢд»ҘиҮіжңүе°ҶжһҒе…¶еӨҚжқӮзҡ„еҺҶеҸІиҝҮзЁӢз®ҖеҚ•еҢ–гҖҒжЁЎејҸеҢ–зҡ„еҖҫеҗ‘гҖӮ
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©¶з«ҹжҳҜжҖҺж ·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иҝӣзЁӢпјҹдёҖдёӘи§ӮзӮ№зҡ„жҸҗеҮәжҳҜйҮҚиҰҒзҡ„пјҢ然иҖҢзі»з»ҹиҖҢе‘ЁиҜҰзҡ„и®әиҜҒжӣҙйҮҚиҰҒпјӣдҪ•еҶөи§ӮзӮ№йЎ»з»ҸеҸ—еҸІж–ҷзҡ„жЈҖйӘҢпјҢжҳҜеҗҰиғҪеӨҹзЎ®з«ӢжңҖз»ҲеҸ–еҶідәҺеҸІж–ҷе’Ңж•°жҚ®зҡ„ж”Ҝж’‘зЁӢеәҰ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з»“и®әдёҚиҜҘжҳҜз ”з©¶зҡ„е…ҲеҜјпјҢиҖҢеә”еҪ“еңЁе……еҲҶзҡ„гҖҒе®һиҜҒжҖ§зҡ„еҸІж–ҷз ”иҜ»д№ӢеҗҺгҖӮ
дёӢйқўзҡ„еә„еӣӯе№ійқўеӣҫпјҢеҸҜд»ҘдҪҝжҲ‘们еҜ№еә„еӣӯж јеұҖе’Ңж•һз”°еҲ¶жңүдёӘзӣҙи§ӮеҚ°иұЎ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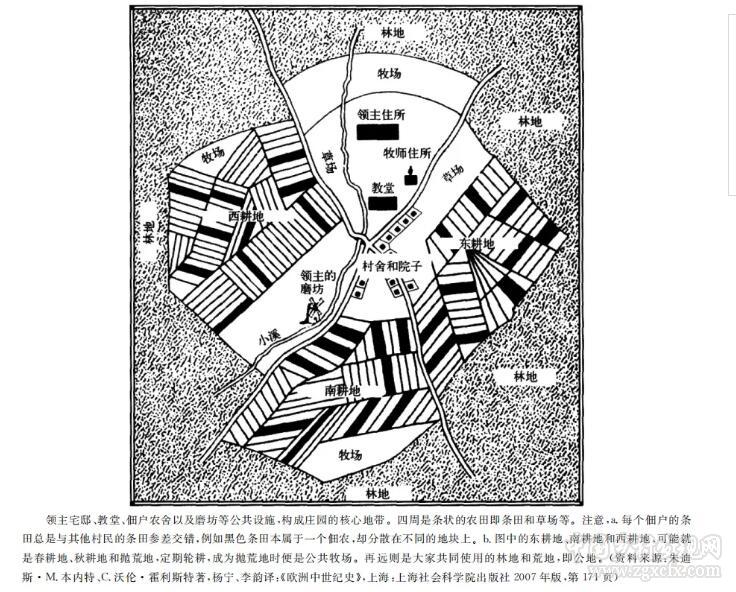
дәҢгҖҒеҶңж°‘ж•ҙеҗҲжқЎз”°пјҡ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
пј‘пјҺеҶңж°‘жҢҒжңүең°зҡ„ж•ҙеҗҲ
еҲ°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пјҢдҪғеҶңжҷ®йҒҚзҡ„ж„ҝжңӣжҳҜпјҢжҠҠж•һз”°дёҠ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еҸҳдёәзҙ§еҮ‘еһӢзҡ„ең°еқ—пјҢеҗҢж—¶еҲҶеүІжқ‘ж°‘е…ұеҗҢдҪҝз”Ёзҡ„иҚүең°гҖҒиҚ’ең°е’Ңжһ—ең°пјҢе°Ҷ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зҪ®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зӣҙжҺҘжҺҢжҺ§дёӢгҖӮеңЁдёӯдё–зәӘеҶңдёҡзүҲеӣҫдёҠпјҢдёӘдәә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ж•ЈиҗҪеңЁж•һз”°дёҠпјҢеҪјжӯӨд№Ӣй—ҙзӣёи·қеҫҲиҝңгҖӮдҪғжҲ·зҡ„жқЎз”°жҖ»жҳҜдёҺе…¶д»–жқ‘ж°‘зҡ„жқЎз”°еҸӮе·®дәӨй”ҷпјҢиҖҢдё”еңЁејәеҲ¶иҪ®иҖ•еҲ¶дёӢпјҢеңҹең°зҡ„з©әй—ҙдҪҚзҪ®д№ҹдёҚеӣәе®ҡгҖӮйҡҸзқҖз»ҸжөҺдёҺзӨҫдјҡзҡ„еҸ‘еұ•пјҢдәә们и¶ҠжқҘи¶ҠдёҚж»Ўж„Ҹиҝҷж ·зҡ„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иҖ•дҪңеҲ¶еәҰгҖӮдёәдәҶж‘Ҷи„ұе…ұеҗҢдҪ“д№ жғҜ规еҲҷзҡ„жқҹзјҡпјҢдёәдәҶеңЁзӢ¬иҮӘеҚ жңү并зӢ¬иҮӘиҖ•дҪңзҡ„еңҹең°дёҠжҠ•е…ҘжӣҙеӨҡеҠіеҠЁпјҢеўһеҠ е°ҸйәҰдә§йҮҸпјҢжҸҗй«ҳеңҹең°зҡ„д»·еҖјпјҢе°Ҷ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йӣҶдёӯеңЁдёҖиө·жҲҗдёәдҪғеҶң们зҡ„жҷ®йҒҚж„ҝжңӣгҖӮжҲ–йҖҡиҝҮеҚҸе•Ҷи°ғжҚўжқЎз”°пјҢжҲ–йҖҡиҝҮеңҹең°д№°еҚ–е’ҢиҪ¬з§ҹпјҢдҪғеҶң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йҖҗжёҗиө°еҗ‘йӣҶдёӯгҖӮжҜ”еҰӮпјҢд»ҘеүҚзӣёйӮ»зҡ„жқЎз”°еҲҶеҲ«еұһдәҺдёҚеҗҢзҡ„дҪғеҶңпјЎгҖҒпјўгҖҒпјЈгҖҒпјӨпјҢзңјдёӢеҸӘеұһдәҺдҪғжҲ·пјЎгҖӮдҪғжҲ·пјЎжҢҒжңүзҡ„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д№ҹ许并没жңүеӨҡе°‘еҸҳеҢ–пјҢдёҚиҝҮеңҹең°з»„еҗҲж–№ејҸдёҚдёҖж ·дәҶпјҢең°зҗҶдҪҚзҪ®еӣәе®ҡпјҢдҪғеҶңеҜ№иҮӘе·ұеңҹең°зҡ„дәІиҝ‘зЁӢеәҰд№ҹдёҚдёҖж ·дәҶгҖӮеҜ№дәҺе…¬ең°зҡ„дҪҝз”Ёд№ҹжҳҜдёҖж ·пјҢдҪғеҶңж”ҫејғдәҶ他们еңЁиҚ’ең°е’Ңе…ұз”Ёзү§еңәжүҖдә«жңү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еҫ—еҲ°дәҶ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иҚүең°е’Ңзү§еңә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жҠҠеӨ§зүҮеңҹең°дёҠзҡ„е…ұеҗҢиЎҢдҪҝзҡ„жқғеҲ©иҪ¬еҸҳдёәе°Ҹ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дёӘдәәиЎҢдҪҝ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ең°еқ—ж•ҙеҗҲзҡ„жөҒиЎҢи¶ӢеҠҝдёҚеҸҜйҒҸжӯўпјҢеІҒжңҲеңЁйқҷж¶Ҳж¶Ҳең°жөҒйҖқпјҢ然иҖҢеҚғзҷҫдёҮеҶңж°‘еҸӮдёҺдёӢзҡ„ж—Ҙз§ҜжңҲзҙҜзҡ„з§Ҝж·ҖпјҢеҚҙз•ҷдёӢдәҶдёҚеҸҜйҖҶиҪ¬зҡ„з—•иҝ№пјҢеҲ°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пјҢдёҺдёӨзҷҫе№ҙеүҚзӣёжҜ”дёҚи®ә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зҡ„дә§жқғзҠ¶еҶөиҝҳжҳҜд№Ўжқ‘з”°й—ҙзҡ„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йғҪеҸ‘з”ҹдәҶж·ұеҲ»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
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зҡ„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жЎҲеҚ·дёӯдҝқз•ҷдәҶеӨ§йҮҸзҡ„дҪғеҶңд№Ӣй—ҙдә’жҚўжқЎз”°зҡ„жЎҲдҫӢ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ңЁиӮҜзү№йғЎзҡ„е“Ҳз‘һж–Ҝжө·е§Ҷеә„еӣӯпјҲпјЁпҪҒпҪ’пҪ’пҪүпҪ…пҪ“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пјҢжҹҗдәәжӢҘжңүпј“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пјҢе…¶дёӯдёҖжқЎз”°еңЁеҸҰ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зҡ„дёӯй—ҙпјҢеҗҺиҖ…иҖ•ең°ж—¶зҠҒиҝҮдәҶең°з•Ң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°Ҷ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еҲ’еҪ’е·ұжңүпјҢдёәжӯӨеҸ‘з”ҹиҜүи®јгҖӮз»“жһңеҸҢж–№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дёәдәҶйҒҝе…Қиҝҷз§ҚдёҚзЎ®е®ҡжғ…еҶөзҡ„еҶҚж¬ЎеҸ‘з”ҹпјҢеҸ—е®ідёҖж–№е°ҶеҲҶж•Јзҡ„пј“иӢұдә©жқЎз”°е…ЁйғЁдәӨз»ҷеҜ№ж–№пјҢеҗҢж—¶жҺҘ收еҜ№ж–№еңЁеҸҰдёҖең°ж®өжҸҗдҫӣзҡ„пј“иӢұдә©зҡ„ж•ҙеқ—еңҹең°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йҖҡиҝҮдәӨжҚўж•ҙеҗҲдәҶеңҹең°гҖӮеҸҲдҫӢеҰ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ҳе№ҙпјҢжІғ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·пҪҲпҪҒпҪ„пҪ„пҪҸпҪҺпјүжі•еәӯжЎЈжЎҲи®°иҪҪпјҡз»ҸеҚҸе•ҶпјҢеҶңеңәдё»дәЁеҲ©В·жң—е’ҢиҜҘеә„еӣӯзҡ„иӢҘе№ІдҪғеҶң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дәЁеҲ©еңҲеҚ дәҶиӢҘе№ІдҪғеҶңжүҖжҢҒжңүзҡ„жқЎз”°пјҢе…ұпј‘пј”иӢұдә©пјҢдҪңдёәдәӨжҚўпјҢдёҠиҝ°иӢҘе№ІдҪғеҶңеңҲеҚ дәҶдәЁеҲ©еҲҶеҲ«дҪҚдәҺдёӨеӨ„е…ұпј‘пј”иӢұдә©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дәҶиҝҷжЎ©еңҹең°дә’жҚўпјҢ并记еҪ•еңЁ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гҖӮдҪғеҶңдә’жҚўжқЎз”°пјҢйҖҡеёёиҰҒиҺ·еҫ—йўҶдё»зҡ„йҰ–иӮҜпјҢ并еұҘиЎҢзӣёеә”зҡ„жі•еәӯжүӢз»ӯгҖӮеҪ“ж—¶дҪғеҶңеҮ д№ҺйғҪжҳҜиҮӘз”ұиә«д»ҪпјҢ然иҖҢ他们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жҖ§иҙЁдҫқ然жңүзӣёеҪ“еӨ§зҡ„е·®ејӮпјҢеҒҮеҰӮдә’жҚўжқЎз”°зҡ„д»·еҖј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пјҢе°ұйңҖиҰҒ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з»ҸжөҺиЎҘеҒҝгҖӮжҜ”еҰӮдёҖж–№жҳҜйҷҗжңҹе…¬з°ҝең°пјҢдёҖж–№жҳҜдё–д»Јжүҝиўӯзҡ„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еүҚиҖ…жҢҒжңүдәәеңЁдә’жҚўжқЎз”°ж—¶иҰҒз»ҷ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дәәиЎҘи¶ідёӨеқ—еңҹең°д№Ӣй—ҙзҡ„еёӮеңәе·®йўқпјҢ并е°ҶиЎҘеҒҝжқЎд»¶и®°еҪ•еңЁжі•еәӯжЎҲеҚ·еӨҮжҹҘгҖӮеҸҜи§ҒеҶңж°‘зҡ„жқЎз”°дәӨжҚўжҳҜиҮӘж„ҝзҡ„пјҢд№ҹжҳҜз»ҸиҝҮжі•еҫӢзЁӢеәҸи®Өе®ҡзҡ„пјҢиҖҢдё”жҖ»жҳҜиҖғиҷ‘еҲ°еңҹең°зҡ„дә§жқғеӣ зҙ е’ҢеёӮеңәд»·ж јеӣ зҙ пјӣеҪ“еңҹең°жҖ§иҙЁзҡ„е·®ејӮеҸҜд»Ҙз”Ёиҙ§еёҒи°ғиҠӮ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ЎЁжҳҺдёӯдё–зә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дёӯзҡ„и¶…з»ҸжөҺеӣ зҙ еҮ иҝ‘ж¶ҲеӨұгҖӮдәӨжҚўжқЎз”°жҳҜеҶңж°‘ж•ҙеҗҲең°еқ—зҡ„йҖҡеёёж–№ејҸпјҢи·Ёи¶Ҡеә„еӣӯе’Ңең°еҢәдәӨжҚўжқЎз”°зҡ„жғ…еҶөд№ҹдёҚе°‘и§ҒгҖӮ
еңҹең°д№°еҚ–жҳҜеҶңж°‘ж•ҙеҗҲжқЎз”°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ё йҒ“гҖӮдёҖйғЁеҲҶдҪғеҶңеҫҲж—©е°ұејҖе§Ӣд№°еҚ–еңҹең°пјҢйҖҡиҝҮ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жү©еӨ§иҮӘе·ұжҢҒжңүең°и§„жЁЎпјҢеҜҢиЈ•зҡ„еӨ§еҶңе°ұжҳҜиҝҷж ·еҪўжҲҗзҡ„пјҢеҗҺжқҘдҪғеҶң们еҸ‘зҺ°еңҹең°д№°еҚ–гҖҒз§ҹиҝӣз§ҹеҮәзӯүпјҢиҝҳеҸҜд»ҘиҫҫеҲ°еңҹең°ж•ҙеҗҲзҡ„зӣ®зҡ„гҖӮдҪғеҶңжҠҠжқЎз”°еҗҲ并жҲҗз”°еқ—зҡ„иҝҮзЁӢж— з–‘жҳҜз»ҸиҝҮж·ұжҖқзҶҹиҷ‘зҡ„гҖӮ他们еҫҖеҫҖж №жҚ®иҮӘе·ұе·І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жқҘе®үжҺ’еңҹең°д№°еҚ–пјҢйҖҗжёҗз”ЁдёҖж•ҙеқ—еңҹең°жқҘд»Јжӣҝ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еңЁиҗЁзҰҸе…ӢйғЎзҡ„ж јеӢ’ж–Ҝ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§пҪҸпҪ’пҪҢ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пјҢдёҖдёӘ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е°ҶиҮӘе·ұжҢҒжңүең°пј‘пј’иӢұдә©зҡ„дёҖеҚҠеҲҶз§ҹз»ҷпјҳдёӘдәәпјҢеҗҢж—¶д»ҺеҸҰеӨ–пјҳеқ—жҢҒжңүең°дёӯиҙӯиҝӣзӣёеә”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еҸҲдҫӢеҰӮпјҢеңЁз§‘йҡҶиҫҫ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’пҪҸпҪҺпҪ„пҪҒпҪҢпјүпјҢзҗҶжҹҘеҫ·йҖҡиҝҮдёҚж–ӯиҡ•йЈҹзҡ„ж–№ејҸжһҒеӨ§ең°жү©е……дәҶиҮӘе·ұзҡ„еҚҠ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з”°еқ—пјҢеҗҢж—¶еҚҙ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пј’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иҪ¬з§ҹз»ҷдәҶеҸҰ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гҖӮдәЁеҲ©жүҝз§ҹдәҶдҪғеҶңзҗҶжҹҘеҫ·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җҢж—¶жҠҠиҮӘе·ұжҢҒжңүең°дёӯзҡ„пјҳиӢұдә©еҚ–з»ҷдәҶеҸҰ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гҖӮжҳҫ然иҝҷдәӣжҙ»еҠЁзҡ„зӣ®зҡ„дёҚе®Ңе…ЁеңЁдәҺжү©еӨ§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пјҢиҖҢжҳҜйҖҡиҝҮеңҹең°дәӨжҳ“и°ғж•ҙиҮӘе·ұжқЎз”°зҡ„ең°зҗҶдҪҚзҪ®гҖӮжӯЈеҰӮжҲ‘们已з»ҸзңӢеҲ°зҡ„пјҢдёҖдҪҚдҪғеҶңеҮәи®©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пјҢеҗҢж—¶еҸ–еҫ—еҜ№ж–№жҲ–д»–ж–№зҡ„еҸҰеӨ–еңҹең°пјҢдәӨжҳ“е®ҢжҲҗеҗҺиҜҘдҪғеҶң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еҸҳеҢ–дёҚеӨ§пјҢеҸӘжҳҜең°еқ—жӣҙзҙ§еҮ‘гҖҒжӣҙжҳ“з®ЎзҗҶпјҢжӣҙзӣҙжҺҘең°еӨ„дәҺиҮӘе·ұжҺҢжҺ§д№ӢдёӢгҖӮдёҖдёӘжҜӢеәёзҪ®з–‘зҡ„дәӢе®һжҳҜ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жҜ”пј‘пј“дё–зәӘжӣҙеҠ зҙ§еҮ‘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еҹәжң¬дәӢе®һдҪҝеҫ—иҫғ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еӣҙеңҲж•һз”°жҲҗдёәеҸҜиғҪгҖӮ
дёӘдәәжҢҒжңүең°ж•ЈиҗҪеңЁж•һз”°дёҠпјҢжҳҜеә„еӣӯеҶңдёҡз»ҸжөҺзҡ„е…ёеһӢз”»йқўгҖӮиҝӣе…Ҙ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пјҢи®ёеӨҡеә„еӣӯиҝҳдҝқз•ҷзқҖжҲ–йғЁеҲҶдҝқз•ҷзқҖиҝҷз§ҚзҠ¶жҖҒпјҢеҗҢж—¶еҮәзҺ°дёҖз§Қж–°и¶ӢеҠҝдёҺд№Ӣ并иЎҢпјҡз»ҸиҝҮеҗҲ并жқЎз”°зҡ„зҙ§еҮ‘еҢ–иҝҗеҠЁпјҢдҪғеҶңдёӘдәәдҝқжңүең°дёҚеҶҚзӣёйҡ”еҫҲиҝңпјҢиҖҢжҳҜеҪјжӯӨзӣёиҝһпјҢеҪўжҲҗдёҖе®ҡ规模зҡ„ең°еқ—жҲ–иӢҘе№Іең°еқ—гҖӮйӮЈдәӣ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ҶҢпјҲ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–пҪ…пҪҷпҪ“пјүз•ҷдёӢжқҘзҡ„ең°еӣҫжҳҫзӨәпјҢеҲ¶еӣҫдәәз”ЁеӨ§жӢ¬еј§е°ҶзӣёйӮ»зҡ„жқЎз”°еҢ…еҗ«еңЁеҶ…пјҢиЎЁзӨәж–°зҡ„еҸҳеҢ–еҚіиҝҷйғЁеҲҶжқЎз”°е·ІеұһжҹҗдёӘдәәжүҖжңүгҖӮ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д№ӢеүҚжҸҸиҝ°дҪғеҶңжҢҒжңүең°зҡ„з”ЁиҜҚжҳҜвҖңдҪҚдәҺеңҹең°пјЎе’Ңеңҹең°пјўд№Ӣй—ҙвҖқпјҢзҺ°еңЁзҡ„ж–°иҜҚжұҮеҲҷжҳҜвҖңе·Із»ҸиҝһеңЁдёҖиө·вҖқпјҲвҖңпҪҢпҪҷпҪүпҪҺпҪҮ пҪ”пҪҸпҪҮпҪ…пҪ”пҪҲпҪ…пҪ’вҖқпјүгҖӮж—¶еёёпјҢең°еӣҫдёҠеӨ§жӢ¬еј§йҮҢзҡ„пј‘пј’дёӘжҲ–пј’пјҗдёӘжқЎз”°еұһдәҺеҗҢдёҖдёӘдәәпјӣжңүж—¶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еҲҷжҢҮеҮәпј‘пј–иӢұдә©жҲ–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дҪҚдәҺдёҖеӨ„гҖӮеҸҲеҰӮиҺ«йЎҝж–ҮзҢ®пјҲпјӯпҪ…пҪ’пҪ”пҪҸпҪҺпҪ„пҪҸпҪғпҪ•пҪҚпҪ…пҪҺпҪ”пҪ“пјү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үҳ马ж–ҜВ·ж–Ҝ科зү№зҡ„пјҷ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е·Із»Ҹиҝһ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дҪҚдәҺвҖҰвҖҰвҖқпјӣвҖңзәҰзҝ°жҢҒжңүпј‘пј–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е·Із»Ҹиҝһ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дҪҚдәҺвҖҰвҖҰвҖқпјӣзӯүзӯүгҖӮжҚ®дј°з®—пјҢпј‘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и§„жЁЎи¶ід»ҘиҙҹжӢ…зӯ‘зҜұе’ҢжҺҳжІҹзҡ„иҙ№з”ЁпјҢдёӢдёҖжӯҘе°ҶиҝһжҲҗдёҖзүҮзҡ„еңҹең°еӣҙеңҲиө·жқҘ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жһҒеӨ§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ңЁеҲҶж•ЈжқЎз”°е’Ңиҫғзҙ§еҮ‘ең°еқ—并иЎҢ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ұҖйғЁеңҲең°дјҡдә§з”ҹдёҚе°‘йә»зғҰпјҢдёӨз§ҚдёҚеҗҢзҡ„иҖ•дҪңеҲ¶еәҰеҗҢж—¶иҝҗиЎҢиӮҜе®ҡдә§з”ҹдёҚеҸҜйҒҝе…Қзҡ„ж··д№ұе’ҢеҶІзӘҒпјҢжҜ”еҰӮжҢүз…§иҪ®иҖ•еҲ¶е’Ң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зҡ„еҺҹеҲҷпјҢж•һз”°дёҠдҪғжҲ·зҡ„зүІз•ңж—¶еёёдјҡиҝӣе…Ҙеә„稼收иҺ·еҗҺзҡ„еңҲең°йҮҢпјҢеҗҺиҖ…еҲҷи®ӨдёәйӮ»еұ…зҡ„зүІз•ңдёҚеҸҜиҝӣе…ҘеңҲең°гҖӮеҸҜжҳҜжғ…еҶөжӯЈеңЁеҸ‘з”ҹеҸҳеҢ–пјҢвҖңдёӘдҪ“дҪғеҶңдёҚеҶҚж„ҹи§үеңҲең°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зҡ„вҖқпјҢд»–еҸҜд»ҘдёҚж–ӯдёҺйӮ»еұ…们еҚҸе•Ҷ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ж•һз”°дёҠдёҚйҡҫеҸ‘зҺ°дёҖеқ—еқ—иў«еӣҙеңҲ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
дёӢйқўзҡ„пј‘пј•пјҷпјҗе№ҙзҡ„зҙўе°”зҰҸеҫ·еә„еӣӯйғЁеҲҶең°еӣҫпјҲпјӯпҪҒпҪҗ пҪҸпҪҶ пј°пҪҒпҪ’пҪ” пҪҸпҪҶ пҪ”пҪҲпҪ… пјӯпҪҒпҪҺпҪҸпҪ’ пҪҸпҪҶ пјіпҪҒпҪҢ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„ пҪүпҪҺ пјўпҪ…пҪ„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„пҪ“пҪҲпҪүпҪ’пҪ… пј‘пј•пјҷпјҗпјүпјҢеҸҜд»ҘеҚ°иҜҒеҶңж°‘ж•ҙеҗҲжқЎз”°зҡ„жғ…жҷҜгҖӮзҺӢе®Ө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и®°иҪҪдәҶиҝҷдёҖиҝҮзЁӢ并з»ҳеҲ¶жҲҗеә„еӣӯең°еӣҫпјҢиҜҘең°еӣҫеҜ№дәҺжҲ‘们зҗҶи§Јжҷ®йҖҡеҶңж°‘еңЁ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ең°дҪҚпјҢйўҮеҜҢд»·еҖј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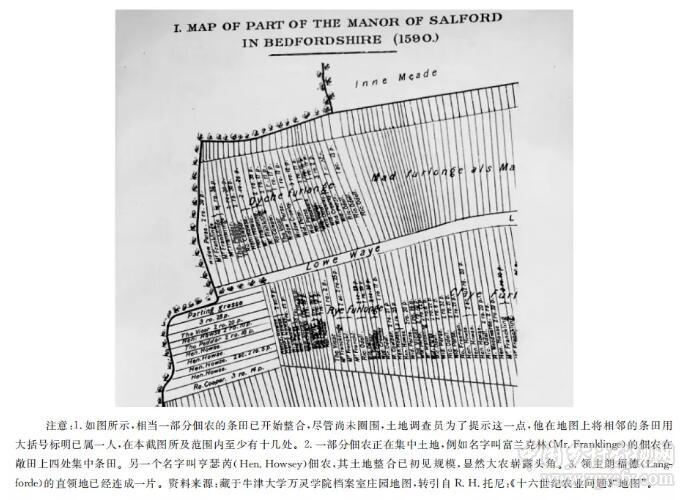
пј’пјҺеҶңж°‘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пјҲпҪҗпҪүпҪ…пҪғпҪ…пҪҚпҪ…пҪҒпҪҢ пҪ…пҪҺпҪғпҪҢпҪҸ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…пјү
з‘ҹж–Ҝе…ӢжҢҮеҮәпјҢеңЁйғҪй“Һж—¶д»Јзҡ„еә„еӣӯйҮҢпјҢдёҖдёӨиӢұдә©иҚ’ең°зҡ„еңҲеӣҙпјҢжҲ–иҖ…ж•һз”°дёӯзҡ„ең°еқ—еңҲеӣҙпјҢйғҪжҳҜж—¶еёёеҸ‘з”ҹзҡ„гҖӮеңЁдәәеҸЈзЁҖз–ҸпјҢеӯҳеңЁеӨ§йҮҸиҚ’ең°иҖҢдё”е®һиЎҢеҲҶж•Ј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зҡ„ең°еҢәпјҢд№ҹиғҪеҸ‘зҺ°еҫҲеӨҡ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зҡ„е®һдҫӢгҖӮдҫӢеҰӮеңЁеҢ—йғЁзҡ„еҘ”е®ҒпјҲпј°пҪ…пҪҺпҪҺпҪүпҪҺпҪ…пјүең°еҢәпјҢвҖңеңҲең°еҫҖеҫҖжҳҜдёӘдҪ“дҪғеҶңиҮӘдё»жҺЁеҠЁзҡ„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йҒҮеҲ°д»Җд№ҲеҸҚеҜ№зҡ„йҳ»еҠӣвҖқгҖӮдҪғжҲ·зҡ„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жҳҜд»ҖзҪ—жҷ®йғЎеңҲең°зҡ„дёҖдёӘзү№зӮ№пјҢж №жҚ®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и®°иҪҪ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җпј”е№ҙпјҢжңүпј—еӨ„еңҲең°жҖ»е…ұпј‘пјҳиӢұдә©пјҢеҸҜи§ҒжҳҜйӣ¶жҳҹеңҲең°гҖӮеңЁеё•ж–ҜжҙӣпјҲпј°пҪ•пҪ’пҪ“пҪҢпҪҸпҪ—пјүзҷҫжҲ·еҢәпјҢ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зЁҚеӨ§дәӣпјҢпј•пј•еӨ„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пј“пј“еӨ„йғҪжҳҜ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е·ҰеҸігҖӮиҜҘйғЎжңҖеӨ§зҡ„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“е№ҙеҮәзҺ°еңЁиӮҜеҲ©еә„еӣӯпјҲпј«пҪ…пҪҺпҪҢпҪ…пҪҷпјүгҖӮиҝҷдәӣеңҲең°жІЎжңүйҖ жҲҗйӘҡд№ұе’Ң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гҖӮеңЁе…Ӣйӣ·ж–Ү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’пҪҒпҪ–пҪ…пҪҺпјүпјҢдёҖдәӣдҪғеҶңе°Ҹ规模ең°еңҲеҚ дәҶйғЁеҲҶиҚ’ең°гҖӮеҘҘж–Ҝз»ҙж–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ҜпҪ“пҪ—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’пҪҷпјүеҲҷдёҚ然пј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’е№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жҳҫзӨәпјҢе…ұжңүпј–пј–пјҷпјҺпј’пј•иӢұдә©иҚ’ең°иў«еңҲеҚ пјҢвҖңе…¶дёӯеӨ§йғЁеҲҶжҳҜз”ұ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е’Ң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йӣ¶жҳҹеңҲеҚ зҡ„вҖқгҖӮеңЁ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пјҢеҶңж°‘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еҗҢж ·жҷ®йҒҚпјҢеңЁеҘҘе…Ӣе§ҶпјҲпјҜпҪҒпҪӢ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зҷҫжҲ·еҢәпјҢдёҖдёӘеҗҚеӯ—еҸ«дәЁеҲ©В·жқ°з»ҙж–Ҝ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жҳҜзҷҪйҮ‘жұүе…¬зҲөзҡ„дҪғжҲ·пјҢд»–еңЁиҝҮеҺ»зҡ„пј”е№ҙйҮҢжҠҠпј‘пј‘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еӣҙеңҲжҲҗзү§еңәпјӣиҝҳжҳҜиҝҷдёӘдҪғжҲ·пјҢеңЁиүҫж јйҮҢйЎҝпјҲпјҘпҪҮпҪҢпҪ…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ж•ҷеҢәеҸҲеңҲеҚ дәҶпј’иӢұдә©жһ—ең°гҖӮеңЁиҙқе°”йЎҝпјҲпјўпҪ…пҪҢ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ж•ҷеҢәпјҢдҪғеҶңзҗҶжҹҘеҫ·В·жі°еӢ’еңҲеҚ дәҶиў«з§°дҪңвҖңйңІжҒ©зү№вҖқ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Ө§зәҰпјҳиӢұдә©пјҢиҝҳеӣҙеңҲдәҶеҸҰеӨ–пј‘пј”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гҖӮеңЁдјҠе®ҫиө«е§ҶпјҲпјҘпҪҚпҪҗпҪүпҪҺпҪҮ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ж•ҷеҢәпјҢд№”жІ»В·йәҰе…ӢжІғжҖқе°Ҷпј–иӢұдә©иҚүең°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зӣ–дјҠВ·еҹғеҫ·и’ҷе…№е°Ҷпј’пј“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иҝҷдәӣеңҲең°иҖ…е…ЁйғЁжҳҜдёҖиҲ¬дҪғеҶңгҖӮ
е…¶е®һпјҢдҪғеҶң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ж—©еңЁеһҰиҚ’иҝҗеҠЁж—¶жңҹеҚіе·ІеҗҜеҠЁпјҢеҸҜи°“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…ҲиЎҢиҖ…гҖӮзұіеӢ’е’Ңе“ҲеҪ»е°”и®ӨдёәпјҢеһҰиҚ’иҝҗеҠЁжҳҜвҖңе°Ҹдәәзү©зҡ„дәӢдёҡвҖқпјҲпҪҒ пҪ“пҪҚпҪҒпҪҢпҪҢ пҪҚпҪҒпҪҺвҖҷпҪ“ пҪ…пҪҺпҪ”пҪ…пҪ’пҪҗпҪ’пҪүпҪ“пҪ…пјүпјҢе……еҲҶиӮҜе®ҡдәҶдёҖиҲ¬дҪғеҶңеңЁж—©жңҹ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ејҖжӢ“дҪңз”ЁгҖӮдҪғеҶңдҫөеҚ иҚ’ең°йҖҡеёёжҳҜиҡ•йЈҹжҖ§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жңүиҝқ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жі•пјҢејҖе§ӢжӮ„жӮ„ең°йҒҝејҖйўҶдё»зҡ„管家гҖӮйҡҸзқҖеңҲеҚ иҚ’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еһҰиҚ’йҖҗжёҗиў«жүҝи®Ө并зәіе…Ҙ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жі•пјҢж–°еһҰиҚ’ең°иў«и§ҶдҪңйўҶдё»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пјҢ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жё…жҷ°ең°жҳҫзӨәеңЁеә„еӣӯз§ҹйҮ‘еҚ·е®—е’Ң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йҮҢйқўгҖӮдҫӢеҰӮпј‘пј”пј’пј’е№ҙпјҢеңЁйҳҝд»ҖйЎҝе®үеҫ·иҺұжҒ©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“пҪҲпҪ”пҪҸпҪҺпјҚпҪ•пҪҺпҪ„пҪ…пҪ’пјҚпј¬пҪҷпҪҺпҪ…пјүпјҢ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е’Ң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еңҲеҚ дәҶеӨ§йҮҸжһ—ең°е’ҢиҚ’ең°пјҢ并дёәе…¶дёӯзҡ„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ж”Ҝд»ҳпј‘пј“е…Ҳд»Өпј”дҫҝеЈ«е’Ңпј‘пјҗе…Ҳд»Өзҡ„иҙ§еёҒз§ҹйҮ‘гҖӮеҸҰж №жҚ®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”е№ҙдёҖд»Ҫзү№и®ёзҠ¶и®°иҪҪпјҢдҪғеҶңдё»еҜјдәҶзҝ°еёғеӢ’йЎҝпјҲпјЁпҪ•пҪҚпҪӮпҪҢпҪ…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е’ҢйңҚе°”еҫ·еҶ…ж–ҜпјҲпјЁпҪҸпҪҢпҪ„пҪ…пҪ’пҪҺпҪ…пҪ“пҪ“пјүдёӨ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йҖҡиҝҮеҚҸи®®еңҲеӣҙдәҶдёҖеӨ„иҚ’ең°гҖӮе°Ҹ规模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дёҖзӣҙеңЁжҢҒз»ӯпјҢеҚідҪҝиҢ…иҲҚеҶңдәҰеҸҜиғҪеңҲеҚ дёҖдёӨиӢұдә©иҚ’ең°пјҢдё”ж—¶еёёеҸҜи§ҒгҖӮпј‘пј–пјҗпјҳе№ҙпјҢе…°ејҖйғЎеҲ©з‘ҹе§Ҷеә„еӣӯзҡ„пј“пј’дёӘдҪғеҶңпјҢз»Ҹ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пјҢжҜҸдёӘдҪғеҶңжҢүз…§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еӨ§е°ҸеңЁе…¬ең°дёҠиҺ·еҫ—дәҶеҗҢзӯүйқўз§Ҝ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җҢж—¶ж”Ҝд»ҳзӣёеә”зҡ„иҙ№з”ЁпјӣиҝҷдәӣдҪғжҲ·иҝҳиҺ·еҫ—并еҲҶеүІдәҶеҸҰеӨ–пј‘пјҗпјҗеӨҡиӢұдә©иҚ’ең°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Қ дәҶеү©дҪҷзҡ„иҚ’ең°пјҢеҗҺжқҘд№ҹжҳҜз§ҹз»ҷдәҶдҪғжҲ·гҖӮд№ҹжңүеә„еӣӯдҪғеҶңдёҺйўҶдё»еҚҸе•ҶеҗҺпјҢжҜҸдәәж— еҒҝеңҲеҚ пј“иӢұдә©е…¬ең°пјҢеҸҜдҫӣзү§е…»пј’еӨҙжҜҚзүӣпјҢж— йЎ»ж”Ҝд»ҳең°з§ҹжҲ–иҙ№з”ЁгҖӮиҝҷеӨ§жҰӮдёҺйӮЈйҮҢзҡ„еңҹең°е®ҪиЈ•жңүе…ігҖӮиҝҷз§Қе…¬ең°дёҠзҡ„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пјҢдёҖиҲ¬йғҪжҜ”иҫғеҲҶж•ЈпјҢеҫҲе°‘еј•иө·иҫғеӨ§зҡ„дәүи®®гҖӮ
然иҖҢпјҢеңЁж•һз”°дёӯеӣҙеңҲжқЎз”°е°ұдёҚйӮЈд№Ҳз®ҖеҚ•дәҶпјҢзүөдёҖеҸ‘иҖҢеҠЁе…Ёиә«гҖӮеңЁж•һз”°еҲ¶дёӢпјҢжқ‘ж°‘з”ҹдә§жҙ»еҠЁжңүзқҖејәзғҲзҡ„ж•ҙдҪ“жҖ§е’ҢеҚҸи°ғжҖ§пјҡеңҹең°жҳҜдёӘдәәдҝқжңүзҡ„пјҢ然иҖҢе…¶еңҹең°зҡ„дҪҚзҪ®жҳҜе®ҡжңҹиҪ®жҚўзҡ„пјҲејәеҲ¶иҪ®иҖ•еҲ¶пјүпјӣдҪғеҶңиҖ•дҪңдёҺж”ҫзү§ж—¶й—ҙд№ҹжҳҜз”ұжқ‘зӨҫз»ҹдёҖе®үжҺ’зҡ„гҖӮдёҖж—Ұжҹҗдәәе°Ҷж•һз”°дёӯдёҖеқ—иҖ•ең°е‘Ёеӣҙз«–иө·зҜұз¬ҶжҲ–жҢ–дёӢжІҹеЈ‘пјҢдёҚи®әеӨ§е°ҸпјҢд»–дјҡз«ӢеҲ»еј•еҸ‘йӘҡд№ұе’ҢдёҚе®үпјҢйҷ·е…ҘдёҺйӮ»еұ…们зҡ„еҶІзӘҒдёӯ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дҫөе®ідәҶдј з»ҹ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д»ҘиҮіеҪұе“Қж•ҙдёӘз”°еҲ¶зҡ„иҝҗиЎҢгҖӮз”ұдәҺ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ж¶үеҸҠдҪғжҲ·зҫӨдҪ“зҡ„е…ұеҗҢеҲ©зӣҠпјҢжқ‘ж°‘еҫҲе®№жҳ“иў«з…ҪеҠЁпјҢз”ҡиҮіеҜ№еңҲең°дҪғеҶңжҡҙеҠӣзӣёеҗ‘гҖӮеңЁиҜәзҰҸе…ӢйғЎзҡ„еёғйӣ·ж–Ҝзү№еҫ·еә„еӣӯпјҢдҪғеҶңзҪ—ж јж–Ҝз”Ёж ‘зҜұжқҘж ҮиҜҶд»–еӣҙеңҲең°зҡ„еҢ—йғЁиҫ№з•ҢпјҢз»“жһңиҜҘ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Ҹ«жқҘдәҶе ӮеҢәж•ҷ士并иҒҡйӣҶдәҢеҚҒеӨҡдёӘдҪғеҶңпјҢеӨңеҚҠж—¶еҲҶ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пјҢз—ӣж®ҙеңҲең°иҖ…зҪ—ж јж–ҜгҖӮзҪ—ж јж–Ҝеҗ“еҫ—дёҚж•ўеӣһ家пјҢжҠұжҖЁйўҶдё»иҰҒй©ұйҖҗ他并еүҘеӨәе…¶еңҹең°з»§жүҝжқғгҖӮдёҺд№Ӣзұ»дјјзҡ„жғ…еҶөеҸ‘з”ҹеңЁеҚЎеёғйІҒе…Ӣеә„еӣӯпјҢеңЁе®һиЎҢиҪ®иҖ•еҲ¶зҡ„ж•һз”°дёҠпјҢдҪғеҶңдҪ©жҒ©зӘҒз„¶з”Ёж ‘зҜұе’ҢжІҹжё еңҲеӣҙпј“иӢұдә©е…¬з°ҝең°пјҢжӯӨдәӢжҲҗдәҶд»–дёҺе…¶д»–жқ‘ж°‘дәүжү§зҡ„з„ҰзӮ№гҖӮеҮәдәҺеҜ№иҮӘиә«е®үе…Ёзҡ„жӢ…еҝғпјҢд»–д»ҺеӣҪзҺӢйӮЈйҮҢеҸ–еҫ—дёҖеј е’Ңе№ід»ӨзҠ¶пјҢ并йҖҡиҝҮжІ»е®үе®ҳиҪ¬дәӨз»ҷйўҶдё»пјҢйўҶдё»зҡ„еӣһзӯ”жҳҜпјҡвҖңдёҠеёқдёәиҜҒвҖҰвҖҰжҲ‘жүҚжҳҜ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зҡ„йўҶдё»пјҒвҖқ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дҪңеҮәдәҶз»ҲжӯўеңҲең°зҡ„еҲӨеҶіпјҢиҜҘдҪғеҶңжӢ’з»қеҮәеәӯпјҢз»“жһңйўҶдё»е‘јжқҘдёғе…«дәәејәиЎҢжӢҶйҷӨдәҶеңҲең°ж …ж ҸгҖӮ
е°Ҫз®ЎеҚ•ж–№йқўеңҲең°еёёеёёеј•иө·зә зә·з”ҡиҮіиҜүи®јпјҢеҸҜжҳҜдҪғеҶңйӣ¶жҳҹеңҲең°иҝҳжҳҜйҖҗжёҗеӨҡдәҶиө·жқҘгҖ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з§ҜзҙҜдәҶ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зҡ„еӨ„зҪҡжЎҲдҫӢпјҢеҸҜд»ҘиҜҒжҳҺдёӘдҪ“дҪғеҶңиҝӣиЎҢзҡ„е°Ҹ规模еңҲең°еӨҡд№Ҳжҷ®йҒҚгҖӮпј‘пј”пјҗпј•е№ҙпјҢзҰҸиөӣзү№пјҲпјҰпҪҸпҪ’пҪҺпҪғпҪ…пҪ”пҪ”пјүеә„еӣӯзҡ„дёҖдәӣ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иў«зҪҡж¬ҫпј’е…Ҳд»Өпј’дҫҝеЈ«пјҢеӣ дёәвҖң他们иҝқеҸҚ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пјҢе°ҶиҮӘе·ұеңЁж•һз”°дёӯзҡ„еңҹең°еңҲеӣҙиө·жқҘпјҢиҮҙдҪҝе…¶д»–дҪғеҶңж— жі•еңЁж”¶еүІеә„зЁјеҗҺиҝӣе…Ҙж”ҫзү§вҖқгҖӮеҸҰ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д№ҹжңүзұ»дјј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他们еӣҙеңҲиҖ•ең°еҗҺйҳ»жӯўе…¶д»–дҪғеҶңиҝӣе…ҘпјҢжң¬еә”ејҖж”ҫдёәзү§еңәпјҢ他们еҚҙж’ӯз§ҚиҖ•дҪңгҖӮпј‘пј”пј‘пјҳе№ҙпјҢеҚЎж–Ҝе°”еә“е§ҶпјҲпјЈпҪҒпҪ“пҪ”пҪҢпҪ… пјЈпҪҸпҪҚпҪӮпҪ…пј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жҢҮжҺ§дёүдёӘдҪғеҶңпјҢжңӘз»ҸйўҶдё»е…Ғи®ёеңЁ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дёҠж’ӯз§ҚпјҢжҢүз…§иҪ®иҖ•еҲ¶и§„е®ҡеә”иҜҘеҗ‘е…ЁдҪ“жқ‘ж°‘ејҖж”ҫдёәзү§еңәзҡ„ж—¶еҖҷ他们еҚҙзӢ¬еҚ дәҶ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гҖӮ
з”ұдәҺеҶңж°‘еӣҙеңҲжқЎз”°жҷ®йҒҚеҢ–пјҢдёҖдәӣ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йҖҗжёҗй»ҳи®ёдәҶеңҲең°пјҢдҪҶжҳҜиҰҒз»ҸиҝҮдёҖе®ҡзЁӢеәҸ并收зјҙдёҖ笔иҙ№з”ЁгҖӮжҚ®и®°иҪҪпјҢпј‘пј”пј”пјҳе№ҙпјҢиҜҘжЎҲдҫӢеҸ‘з”ҹеңЁ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пјҲпјўпҪҢпҪ…пҪ”пҪғпҪҲпҪүпҪҺпҪҮпҪ„пҪҸпҪҺпјүж•ҷеҢәеӨ§дҝ®йҒ“йҷўйўҶең°пјҢ科е…ӢжӢүеӨ«зү№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ҒпҪҢпҪғпҪ’пҪҸпҪҶпҪ”пјүдҪғжҲ·еңҲең°пјҢдёҚиҝҮеңҲең°дҪғжҲ·иҮӘж„ҝж”Ҝд»ҳдёҖ笔иҙ№з”Ёз»ҷж•ҷе Ӯе’ҢйўҶдё»жі•еәӯпјҢйҮ‘йўқж №жҚ®еңҲең°еӨ§е°Ҹж ёи®ЎгҖӮеҪ“ж—¶иҜҘеә„еӣӯжҖ»е…ұжңүпј‘пј’еқ—еңҲең°пјҢжҜҸеқ—еңҲең°ж”Ҝд»ҳзҡ„иҙ№з”Ёд»Һпј‘пј–дҫҝеЈ«еҲ°пј–е…Ҳд»ӨпјҳдҫҝеЈ«дёҚзӯүпјҢжҖ»и®Ўиҫҫпј“пј”е…Ҳд»ӨгҖӮдёҖдёӘдё–зәӘеҗҺпјҢд»ҚжңүеҶңж°‘е°Ҹ规模еңҲең°зҡ„и®°иҪҪпјҡ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ёғйІҒе§ҶйҮ‘ж–Ҝ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’пҪҸпҪҚпҪӢпҪүпҪҺпҪ“пҪ”пҪҲпҪҸпҪ’пҪҗпҪ…пјүпјҢдёӨдёӘзәҰжӣјеҶңпјҢйІҒдёҒе’ҢиҫҫеҶ…зү№дёҖиҮҙиЎҢеҠЁ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‘е№ҙпј—жңҲзҡ„дёҖеӨ©еңҲеҚ дәҶпј’пјҳиӢұдә©ж•һз”°гҖӮеҸҜи§ҒеҶңж°‘зҡ„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жҳҜжҢҒз»ӯиҝӣиЎҢзҡ„пјҢиҝҷзұ»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иҷҪеұһдёҖиҲ¬пјҢеҚҙеҪұе“ҚеҫҲеӨ§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йғЎеҸІдҪңиҖ…жҢҮеҮәпјҡеңҲең°з»ҹи®Ўж•°еӯ—иҜҒжҳҺпјҢиҝҷзұ»йӣ¶зўҺеңҲеҚ зҡ„ж•°йҮҸе’ҢеҗҺжһңдёҚеҸҜе°Ҹ觑гҖӮеә„еӣӯйўҶ主们дәӢе®һдёҠе·Із»Ҹй»ҳи®ёдҪғжҲ·зҡ„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иЎҢдёәпјҢеҸӘжңүйӮЈдәӣжңӘз»ҸйўҶдё»и®ёеҸҜзҡ„еңҲең°иЎҢдёәжүҚдјҡиў«иҜүиҜё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们зңӢеҲ°зҡ„еңҲең°жЎҲдҫӢдёҚи¶ід»ҘеҸҚжҳ 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зҡ„е…ЁиІҢгҖӮжҢү照规е®ҡпјҢ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иҰҒз»ҸйўҶдё»е’Ңе…¶д»–дҪғжҲ·зҡ„еҗҢж„ҸпјҢеҚ•ж–№йқўеңҲең°дјҡеёёеёёйҒӯиҮҙдёҘйҮҚеҗҺжһң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ҷе№ҙпјҢеңЁиҲҚз‘һеј—е“Ҳе°”ж–ҜпјҲпјіпҪҲпҪ…пҪ’пҪүпҪҶпҪҶпҪҲпҪҒпҪҢпҪ…пҪ“пј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пјҢйӮЈдәӣжңӘз»Ҹи®ёеҸҜеңҲең°зҡ„жүҖжңүдҪғжҲ·йғҪиў«иө·иҜүпјҢеҲӨеҶіз»“жһңжҳҜпјҢйҷӨйқһиҺ·еҫ—йўҶдё»зҡ„и®ёеҸҜпјҢеҗҰеҲҷе·Із»ҸеӣҙеңҲзҡ„еңҹең°йЎ»йҮҚж–°ејҖж”ҫгҖӮзүӣжҙҘйғЎйғЎеҸІиҪҪеҸҠзҡ„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пјҢеҜ№дәҺиҝқ规еңҲең°иҖ…дёҚеҸҜи°“дёҚдёҘеҺүпјҡдёҖдёӘеҸ«е·ҙж–Ҝ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иў«жҸҸиҝ°дёәвҖңдҪғжҲ·дёӯзҡ„з ҙеқҸиҖ…вҖқпјҢйҷӨдәҶ科д»ҘзҪҡж¬ҫпјҢиҝҳиў«йҖҗеҮәжҲҝиҲҚдёҺеңҹең°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зҡ„вҖңеңҲең°йҖ жҲҗдәҶеҜ№йӮ»еұ…зҡ„еҚұе®івҖқгҖӮ
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йҖҡеёёжҳҜдёӘдәәиЎҢдёәпјҢеҗҺжқҘеҫҖеҫҖжҳҜиӢҘе№ІдҪғжҲ·зҡ„иҒ”еҗҲиЎҢеҠЁгҖӮеңЁиҙқеҫ·зҰҸеҫ·йғЎзҡ„зҙўе°”зҰҸеҫ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іпҪҒпҪҢ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„пјүпјҢ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д»Қ然еӨ„дәҺжқЎз”°еҲ¶д№ӢдёӢпјҢдёҚиҝҮпјҳдёӘдҪғеҶңиҝҳжҳҜеңҲеӣҙдәҶеӨ§зәҰпј•пј‘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жҜҸдәәеңҲеӣҙпј’иӢұдә©еҲ°пј‘пј—иӢұдә©дёҚзӯүгҖӮеңЁ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зҡ„еЁҒзҷ»йҹҰж–Ҝ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·пҪ…пҪ…пҪ„пҪ…пҪҺпј·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пјҢйҷӨдәҶзӣҙйўҶең°зҡ„жүҝз§ҹиҖ…еӣҙеңҲдәҶеӨ§зүҮеңҹең°д»ҘеӨ–пјҢпј“дёӘиҫғеӨ§зҡ„дҪғеҶңеӣҙеңҲдәҶпј’пјҳиӢұдә©пјҢеҲҶж•ЈеңЁеҮ еӨ„пјҢиў«и®°иҪҪдёәвҖңеңЁеҮ еӨ„ең°еқ—дёҠеңҲеӣҙ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ә„еӣӯдёӯйғЁзҡ„дёҖдәӣеңҹең°пјҢе…¶жҖ§иҙЁдёҚз”ҡжҳҺдәҶпјҢпј‘пј”дёӘдҪғеҶңе°Ҷе…¶еҲҶеүІе№¶еӣҙеңҲпјҢжҜҸеқ—еӣҙеңҲең°е°‘еҲҷдёӨдёүиӢұдә©пјҢеӨҡеҲҷпј‘пј•жҲ–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гҖӮ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еҸ–еҫ—еҫҲеӨ§зҡ„жҲҗеҠҹ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°еӨ„зұіеҫ·е°”еЎһе…Ӣж–ҜйғЎзҡ„еҹғеҘҮйҹҰе°”пјҲпјҘпҪ„пҪҮпҪ…пҪ—пҪҒпҪ’пҪ…пјүе’ҢйҮ‘ж–ҜдјҜйҮҢпјҲпј«пҪүпҪҺпҪҮпҪ“пҪӮпҪ•пҪ’пҪҷпјүдёӨдёӘеә„еӣӯгҖӮд»Һ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з»ҳеҲ¶зҡ„ең°еӣҫдёҠ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иғҪзҢңеҮәйӮЈйҮҢжӣҫз»ҸеӯҳеңЁиҝҮж•һз”°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пјҢжҜҸдёӘдҪғеҶңзҡ„е°Ҹеқ—еңҹең°йғҪжҳҜйӣҶдёӯеңЁдёҖиө·зҡ„пјҢз”ЁзҜұз¬ҶеҪјжӯӨеҲҶйҡ”пјҢдёҚеҶҚжҳҜж—§ејҸзҡ„вҖңиӣӣзҪ‘вҖқеёғеұҖпјҢиҖҢжҳҜдёҚ规еҲҷзҡ„жЈӢзӣҳејҸзҡ„зҺ°д»ЈеҶңдёҡгҖӮиҝҷж ·зҡ„з”°еҲ¶жҷҜи§Ӯз»қйқһжңқеӨ•еҪўжҲҗпјҢе…¶дёӯзӣёеҪ“дёҖйғЁеҲҶеә”иҜҘеҪ’еҠҹдәҺе№ҝеӨ§зҡ„дҪғеҶңгҖӮдёҖзі»еҲ—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еңҲең°йҖҗжёҗиў«дәә们жүҖжҺҘеҸ—пјҢйӣ¶зўҺејҸеңҲең°е·Із»ҸеңЁеҫҲ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зӘҒз ҙдәҶеә„еӣӯе…ұеҗҢдҪ“иҖ•дҪңзҡ„жғҜдҫӢгҖӮ
пј“пјҺеҶңж°‘иҮӘеҸ‘вҖ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вҖқпјҲпҪ…пҪҺпҪғпҪҢпҪҸ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… пҪӮпҪҷ пҪҒпҪҮпҪ’пҪ…пҪ…пҪҚпҪ…пҪҺпҪ”пјү
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иҝҳжңүдёҖз§ҚйҮҚиҰҒеҪўејҸпјҢж—ўдёҚжҳҜдәӨжҚўжқЎз”°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йӣ¶зўҺеӣҙеңҲпјҢиҖҢжҳҜз”ұжқ‘ж°‘е…ұеҗҢдҪ“еҚҸе•ҶеҶіе®ҡпјҢеҸҜз§°дёәвҖ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вҖқ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үҖжңүдҪғеҶңзҡ„еҲ©зӣҠйғҪеҫ—еҲ°дәҶиҖғиҷ‘пјҢ并且жңүжңәдјҡе……еҲҶеҚҸе•ҶпјҢе…¶еҗҲзҗҶжҖ§жҳҺжҳҫй«ҳдәҺдёӘдәә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ҳпјҷе№ҙпјҢзәҰе…ӢйғЎзҡ„еёғжӢүеҫ·зҰҸеҫ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’пҪҒпҪ„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„пјүзҡ„жқ‘ж°‘жӢҹеңҲеӣҙйҷ„иҝ‘зҡ„иҚ’ең°пјҢжқ‘ж°‘еӨ§дјҡеңЁиҚ’йҮҺдёҠдёҫиЎҢпјҢжүҖжңүдҪғеҶңйғҪеҸӮеҠ дәҶпјҢеҹәжң¬иҫҫжҲҗеҲҶеүІе…¬ең°е№¶еӣҙеңҲд№Ӣзҡ„дёҖиҮҙж„Ҹи§ҒгҖӮеңЁ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јҖе§ӢеҗҺпјҢжҜ”иҫғеҝ«ең°з»Ҳз»“дәҶзӣёеҪ“дёҖйғЁеҲҶж•һз”°пј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ҳҜе…¶йҮҚиҰҒж–№ејҸгҖӮиҜҘйғЎзҡ„иҺұж–ҜдјҜйӣ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¬пҪ…пҪ“пҪӮпҪ•пҪ’пҪҷпј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пј‘пј’жңҲпј–ж—ҘпјҢжүҖжңүдҪғеҶңеңЁ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йӣҶеҗҲпјҢз»ҸеҚҸе•ҶеҶіе®ҡпјҡвҖңд»Һд»ҠеӨ©иө·еҲ°зҝҢе№ҙпј“жңҲпј‘ж—Ҙжңҹй—ҙвҖҰвҖҰжҜҸдёӘдҪғеҶңиҰҒ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еӣҙеңҲиө·жқҘгҖӮвҖқ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—е№ҙпјҢиҜҘйғЎзҡ„еЎ”зӣ–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•пҪҮпҪҮпҪҒпҪҢпјүпјҢеёғиҺұзҰҸеҫ·е®¶ж—Ҹзҡ„еңҹең°еҮ д№Һе…ЁйғЁеӣҙеңҲпјҢиҜҘ家ж—ҸжҺҢжҸЎдәҶиҜҘжқ‘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пјҢдёҚеҶҚдёҺе…¶д»–дҪғеҶң继з»ӯжІҝз”ЁеҸӨиҖҒзҡ„е…ұеҗҢ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гҖӮ他们д№ҹжҳҜйҮҮз”ЁдәҶеҚҸи®®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з»Ҹ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пјҢиҜҘжқ‘дҪғеҶңе…ұеҗҢеҚҸе•ҶпјҢеҲҮеүІе…¬ең°е№¶еҲҶеҲ«еӣҙеңҲпјҢиҮіжӯӨиҜҘжқ‘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ж‘Ҷи„ұдәҶ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ж•һз”°еҲ¶гҖӮиӢұеӣҪеӯҰиҖ…ж јйӣ·з§°пјҢиҝҷжҳҜдјҠдёҪиҺҺзҷҪж—¶д»Је…ёеһӢзҡ„еңҲең°ж–№ејҸгҖӮ
еңЁзүӣжҙҘйғЎ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ж•ҷеҢә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ҷпјҚ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–е№ҙй—ҙпјҢйҖҡиҝҮдҪғеҶңй—ҙзҡ„еҗҲдҪңдёҺеҚҸе•ҶпјҢзўҺзүҮеҢ–зҡ„жқЎз”°еңҹең°зҠ¶еҶөиў«зі»з»ҹж”№йҖ пјҢе…¶дёӯеӨ§зәҰжңүпј—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еҫ—еҲ°еӣҙеңҲпјҢеҚ жҚ®иҜҘж•ҷеҢәеҸҜиҖ•ең°зҡ„пј”пјҗпј…д»ҘдёҠгҖӮ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җе№ҙпјҢзүӣжҙҘйғЎзҡ„жқҺеј—йҡҶеә„еӣӯпјҲпј¬пҪ…пҪҒ пјҰпҪ•пҪ’пҪҢпҪҸпҪҺпҪҮпјүпјҢз»ҸдҪғеҶңеҚҸе•ҶеӣҙеңҲдәҶеӨ§зәҰпј“пј–пјҗиӢұдә©зҡ„е…ұз”Ёзү§еңәгҖӮеӣҙеңҲеҗҺзҡ„е…¬ең°еҲҶеұһдәҺдёҚеҗҢ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иҝҷдәӣиҺ·еҫ—дәҶиҚ’ең°зҡ„дҪғеҶңе®Јз§°пјҢд»ҺжӯӨ他们еҸҜвҖңд»Һ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дёҠвҖқиҺ·еҸ–и–ӘжҹҙдәҶгҖӮеҚҸе•Ҷж–№ејҸд№ҹз”ЁдәҺжҜ”йӮ»жқ‘еә„зҡ„е…¬ең°еҲҶеүІ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–пјҚ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”е№ҙй—ҙпјҢе…°ејҖж–Ҝзү№йғЎпјҢжІғеӢ’ж•ҷеҢәпјҲпј·пҪҲпҪҒпҪҢпҪҢпҪ…пҪҷпјүдёҖеқ—е…¬ең°жӣҫиў«дёүдёӘжқ‘еә„жқ‘ж°‘е…ұдә«пјҢзҺ°еңЁз»Ҹз”ұдёүдёӘжқ‘еә„еҚҸи®®еҗҺеҲҶеүІпјҢдёүжқ‘еә„еҲҶеҲ«жҳҜе…ӢиҺұйЎҝпјҚеӢ’пјҚиҺ«е°”ж–ҜгҖҒйҳҝе°”жұүгҖҒйҳҝе…Ӣжһ—йЎҝгҖӮ
жқҘиҮӘ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зҡ„жҠҘе‘ҠжҳҫзӨәпјҢдёҖдәӣең°еҢәеңҲең°зҡ„жҺЁеҠЁиҖ…дёҚжҳҜйўҶдё»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дҪғеҶңдёӘдәәпјҢиҖҢжҳҜ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еҚҸи®®иҝҗдҪңгҖӮеә„еӣӯж–ҮзҢ®еҗ‘жҲ‘们жҸҗдҫӣдәҶ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жҺЁеҠЁе…¬ең°еңҲеҚ зҡ„и®ёеӨҡз»ҶиҠӮпјҢйҖҡеёёзҡ„зЁӢеәҸжҳҜе…Ҳд»Ҙе…ұеҗҢдҪ“еҗҚд№үеҚ жңүзү§еңәе’ҢиҚүең°пјҢ然еҗҺз»ҸеҚҸе•ҶеҗҺеңЁдҪғеҶңд№Ӣй—ҙеҲҶеүІпјҢжҜҸдәәеҲҶеҫ—зҡ„е…¬ең°йқўз§ҜжҳҺжҳҫеҸӮз…§дәҶе…¶жҢҒжңүең°з”°дә©пјҢдёҖеҰӮеҪ“е№ҙдҪғеҶңеңЁе…¬ең°дёҠж”ҫзү§зүІз•ңзҡ„ж•°йҮҸдёҺе…¶жҢҒжңүең°йқўз§ҜжҲҗдёҖе®ҡжҜ”дҫӢдёҖж ·пјҢеҸҜи§Ғд№ жғҜжі•зҡ„еҺҹеҲҷд»Қ然еңЁеҸ‘з”ҹдҪңз”ЁгҖӮе…ұеҗҢдҪ“еҚҸи®®ж–№ејҸд№ҹиҝҗз”ЁдәҺжқЎз”°зҡ„ж•ҙеҗҲе’ҢеӣҙеңҲпјҢеңЁеӨҡеЎһзү№йғЎзҡ„е°Өе°”е°ј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—пҪ…пҪ’пҪҺпҪ…пјүпјҢз»ҸдҪғеҶңеҚҸе•Ҷ并еҫ—еҲ°йўҶдё»зҡ„и®ёеҸҜпјҢдәә们е°Ҷ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еҗҲ并жҲҗзҙ§еҮ‘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гҖӮжһ—иӮҜйғЎзҡ„еҢ—еҮҜе°”иҘҝж•ҷеҢәпјҲпј®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Ҳпј«пҪ…пҪҢпҪ“пҪ…пҪҷпјүдёәдәҶе…ӢжңҚеңҹең°еҲҶж•Јзҡ„зҠ¶еҶөпјҢе°Ҫз®ЎжңүдёҖдәӣең°дә§дё»еҸҚеҜ№пјҢ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дёҺйўҶдё»еҚҸе•ҶеҗҺиҮӘ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‘е№ҙеҗҜеҠЁеңҲең°иҝӣзЁӢпјҢ并且关注еҲ°иҙ«еӣ°е°ҸеҶңзҡ„еҲ©зӣҠпјҢеңЁеңҲең°дёӯеҜ№иҢ…иҲҚеҶңеҒҡеҮә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иЎҘеҒҝгҖӮеңЁдёҖдәӣ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ҪғеҶңдёҺйўҶдё»зҡ„еҸҢж–№ж„Ҹж„ҝдёҖж—¶йҡҫд»ҘиҫҫжҲҗе…ұиҜҶпјҢ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жҖ»жҳҜз»„з»ҮдҪғжҲ·дёҺйўҶдё»и®Ёд»·иҝҳд»·пјҢеҫҖеҫҖз»ҸиҝҮеҸҚеӨҚдәӨж¶үпјҢеҸҢж–№еӨҡж¬ЎеҰҘеҚҸжүҚиғҪ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гҖӮжҚ®еёғиҺұе§ҶеёҢ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’пҪ…пҪҚпҪҲпҪүпҪҢпҪҢпјүжі•еәӯжЎҲеҚ·и®°иҪҪ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ҳе№ҙпјҢйўҶдё»зҲұеҫ·еҚҺВ·иҙқйЎҝеҗҢж„ҸдҪғеҶң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пјҢдҪғеҶңд№Ӣй—ҙд№ҹеҸҜд»Ҙдә’жҚўжқЎз”°пјҢдёҚиҝҮеңҲең°дҪғеҶңжҜҸе№ҙиҰҒеҗ‘йўҶдё»дәӨзәіеӨ§иұҶпјҢжҜҸйӣ…еҫ·еңҹең°дәӨзәідёҖи’ІејҸиҖі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йўҶдё»иҙқйЎҝеҸҠ其继жүҝдәәдёҚеҫ—еңЁеә„еӣӯе…¬ең°дёҠж”ҫзү§гҖӮиҝҷдёҖзұ»еһӢзҡ„еңҲең°еҚҸе•ҶдёӯпјҢеҸҜжҳҺжҳҫзңӢеҮәеҸҢж–№еҰҘеҚҸзҡ„з—•иҝ№пјҢжқ‘зӨҫ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дҪңз”ЁжҳҜжҳҫиҖҢжҳ“и§Ғзҡ„гҖӮ
иҝҳжңүдёҖз§Қжғ…еҶөжҳҜпјҢз»ҸиҝҮй•ҝе№ҙзҙҜжңҲпјҢе…¬ең°е·Із»Ҹиў«дҪғеҶң们йҖҗжёҗиҡ•йЈҹпјҢжңүзҡ„з§Қеә„зЁјпјҢжңүзҡ„иҝҮеәҰж”ҫзү§пјҢиҖҢдё”дёңдёҖеқ—иҘҝдёҖеқ—зҡ„зӣёеҪ“йӣ¶ж•ЈпјҢдёәдәҶжӣҙеҠ еҗҲзҗҶең°дҪҝз”ЁеҺҹжңүе…¬ең°пјҢж»Ўи¶іж”ҫзү§йңҖиҰҒпјҢжқ‘民们еҶіе®ҡйҮҚж–°еҲҶеүІе…¬ең°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ж–Ҝе…ӢжӣІеҲ©еә„еӣӯпјҲпјіпҪӢпҪ…пҪ”пҪғпҪҲпҪҢпҪ…пҪҷпјүеҚіеұһжӯӨзұ»жғ…еҶөгҖӮиҝҷжҳҜдёӘд»…жңүпј–жҲ·дәә家гҖҒпј”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зҡ„е°Ҹжқ‘еә„пјҢ他们жҳҜдёҚеұ…д№Ўзҡ„иӮҜзү№дјҜзҲөзҡ„дҪғжҲ·гҖӮеңЁжІЎжңү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ҸӮдёҺ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ҪғжҲ·д»¬иҫҫжҲҗдёҖиҮҙж„Ҹи§Ғ并жӢҹе®ҡдәҶд№ҰйқўеҚҸи®®д№ҰпјҡдҪғеҶңд№Ӣй—ҙйҖҡиҝҮзӣёдә’дәӨжҚўе·ІеҚ жңү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дҪҝиҮӘе·ұеңЁе…¬ең°дёҠзҡ„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иө·жқҘгҖӮз”ұдәҺдәӨжҚўеҗҺ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еҸҜиғҪеҸҳжҲҗеҲ«дәәзҡ„пјҢдёәдәҶдҝқжҠӨең°еҠӣпјҢдәӨжҚўеүҚйЎ»йҷҗеҲ¶зү§еңәиҝҮеәҰдҪҝз”ЁпјҢжҜҸжҲ·ж”ҫзү§зүІз•ңзҡ„ж•°йҮҸиҮіе°‘еҮҸе°‘дёүеҲҶд№ӢдёҖпјҢдәӢжғ…иҷҪе°ҸеҚҙеҸҚжҳ дәҶеҶңж°‘е…ұеҗҢдҪ“иҖғйҮҸй—®йўҳзҡ„зҗҶжҖ§е’Ңе‘Ёе…ЁгҖӮеҸҜжҳҜе…¶дёӯдёҖдёӘеҸ«жҖҖзү№жӣј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ж— и§Ҷе·ІиҫҫжҲҗзҡ„еҚҸи®®пјҢжӢ’з»қдёҺеҲ«дәәдәӨжҚўеңҹең°пјҢеҰЁзўҚдәҶе®һж–ҪиҝӣзЁӢпјҢжқ‘民们дәҺ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”е№ҙе°Ҷе…¶иө·иҜүеҲ°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пјҲпјЁпҪүпҪҮпҪҲ пјЈ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 пҪҸпҪҶ пјЈпҪҲпҪҒпҪҺпҪғпҪ…пҪ’пҪҷпјүпјҢеҜ»жұӮжі•еҫӢжүӢж®өиҝ«дҪҝе…¶е°ұиҢғгҖӮиҷҪ然法еәӯи®°еҪ•ж®ӢзјәдёҚе…ЁпјҢдҪҶиҝҳжҳҜ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пјҢиө·иҜүжҖҖзү№жӣјд№ӢеүҚе…¬ең°зҡ„еӣҙеңҲе·Із»ҸејҖе§ӢгҖӮж №жҚ®еҚҸи®®жқ‘民们дёҖж–№йқўиҝӣиЎҢеңҹең°дәӨжҚў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и®©з§ҚдёҠеә„зЁјзҡ„еңҹең°йҖҖиҖ•иҝҳзү§пјҢеҰӮжқ°е…ӢйҖҖиҖ•пј’иӢұдә©пјҢжі°еӢ’е’ҢйҮҢеҫ·йҖҖиҖ•пј’иӢұдә©пјҢдёҖдҪҚдёҚе…·еҗҚзҡ„дҪғжҲ·йҖҖиҖ•пј‘пј“иӢұдә©пјҢеҸҰжңүдёӨдҪҚдёҚе…·еҗҚзҡ„дҪғжҲ·йҖҖиҖ•пј”иӢұдә©гҖӮиў«е‘ҠжҖҖзү№жӣјжүҝи®ӨжӣҫеҸӮдёҺи®Ёи®әеңҲең°и®ЎеҲ’пјҢдҪҶеҗҰи®ӨеҗҢж„ҸеңҲең°пјҢд»–д»ҘеқҡжҢҒдј з»ҹзҡ„е…¬ең°жқғеҲ©дёәеҗҚпјҢдёҖжӢ–еҶҚжӢ–гҖӮиҖҢе…¶д»–жқ‘ж°‘жҖҒеәҰдёҖиҮҙпјҢд№ҹеҫҲеқҡеҶіпјҢ他们и®ӨдёәвҖңе…¬ең°еҲ¶еәҰе·Із»ҸеҸҳеҫ—и®©дәәйҡҫд»ҘжҺҘеҸ—вҖқгҖӮжҜ«ж— з–‘д№үпјҢжқ‘ж°‘еңҲең°е®Ңе…ЁжҳҜиҮӘеҸ‘з»„з»Үзҡ„пјҢ并дҫқз…§жі•еҫӢзЁӢеәҸеӨ„зҗҶй—®йўҳпјҢд»Өдәә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жҳҜпјҢжқ‘ж°‘еңҲең°иө·иҜүзҡ„еҜ№иұЎдёҚжҳҜйўҶдё»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еӨ§еҶңпјҢиҖҢжҳҜдёҺ他们дёҖж ·зҡ„жҷ®йҖҡдҪғеҶң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жІЎжңүйҒөе®ҲеӨ§е®¶и®®е®ҡзҡ„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гҖӮж•һз”°еҲ¶жҳҜдёҖз§Қжқ‘ж°‘еҚҸдҪңзҡ„з§Қз”°еҲ¶еәҰпјҢйҖҡиҝҮеҚҸдҪңж–№ејҸдҪҝд№Ӣи§ЈдҪ“жҳҫ然жҳҜжңҖз»ҸжөҺеҗҲзҗҶ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еҸӘжҳҜжҠҠдёҖеӨ§зүҮеңҹең°дёҠе…ұеҗҢиЎҢдҪҝзҡ„жқғеҲ©иҪ¬еҸҳдёәдёҖе°Ҹеқ—еңҹең°дёӘдәәиЎҢдҪҝ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дҪғеҶңж”ҫејғдәҶ他们еңЁе…¬ең°гҖҒиҚүең°е’Ңзү§еңәдёҠжүҖдә«жңүзҡ„д»ҪйўқпјҢеҫ—еҲ°дәҶжӣҙе°Ҹзҡ„дҪҶ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гҖҒиҚүең°е’Ңзү§еңәгҖӮеҗҺиҖ…зҡ„д»·еҖјжҜ”еүҚиҖ…иҰҒй«ҳеҫ—еӨҡгҖӮ
еҶңж°‘е’ҢйўҶдё»пјҢи°Ғдё»еҜјзҡ„еңҲең°зҡ„жҜ”дҫӢжӣҙй«ҳпјҹеҗ„еә„еӣӯжғ…еҶөдёҚдёҖпјҢзүӣжҙҘйғЎзҡ„дёҖеҲҷеҸІж–ҷжҳҺзЎ®жҳҫзӨәдәҶ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зҡ„дҪңз”ЁжӣҙеӨ§гҖӮеңЁзүӣжҙҘйғЎ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ж•ҷеҢә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“пјҚ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”е№ҙй—ҙзҡ„дёҖд»Ҫи°ғжҹҘжҳҫзӨәпјҢйўҶдё»е’ҢдҪғеҶңйғҪжңүеңҹең°еӣҙеңҲпјҢйўҶдё»зҸҖе°”е°ҶзӣҙйўҶең°еӣҙеңҲпјҢиҖҢдҪғеҶңеӣҙеңҲдәҶпј”пј’еӨ„иҖ•ең°е’ҢиҚүең°гҖӮж–ҮзҢ®иө„ж–ҷжІЎжңүжҸҗдҫӣйўҶдё»е’ҢдҪғжҲ·еңҲең°зҡ„йқўз§ҜпјҢдёҚиҝҮеҲ—еҮәдәҶдәҢиҖ…зҡ„з§ҹйҮ‘ж•°йўқпјҢеҪ“ж—¶дәә们жӣҙзңӢйҮҚеңҹең°д»·еҖјиҖҢдёҚжҳҜ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гҖӮвҖңд»Ҙеңҹең°д»·еҖјжқҘзңӢпјҢеӣҙеңҲзҡ„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дёӯзҡ„иҖ•ең°е’ҢиҚүең°пјҢжҜҸе№ҙз§ҹйҮ‘пј”иӢұй•‘пј”е…Ҳд»Өпј‘пјҗдҫҝеЈ«пјӣиҖҢе…¶д»–еҶңж°‘еӣҙеңҲиҚүең°е’ҢиҖ•ең°пјҢжҜҸе№ҙз§ҹйҮ‘й«ҳиҫҫпј“пј”иӢұй•‘пјҷе…Ҳд»ӨгҖӮвҖқжҳҫ然и°ғжҹҘиҖ…ж„ҸеңЁејәи°ғпјҢж•Ји§ҒеңЁеә„еӣӯеҗ„еӨ„зҡ„дҪғжҲ·еңҲең°зҡ„йқўз§ҜжӣҙеӨ§пјҢд»·еҖјжӣҙй«ҳпјҢиҖ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дёҚиҝҮжҳҜ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зҡ„пј‘пјҸпјҷпҪһпј‘пјҸпјҳгҖӮжҲ‘们жңүзҗҶз”ұзӣёдҝЎ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з»қйқһдёӘжЎҲпјҢеҸҜжҳҜйҡҫд»Ҙдј°и®ЎжңүеӨҡеӨ§зҡ„д»ЈиЎЁжҖ§гҖӮ
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зҡ„ж„Ҹд№үдёҚеңЁдәҺж•°йҮҸ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иЎЁжҳҺеҶңж°‘еӨ§дј—зҡ„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иҰҒжұӮдё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–№еҗ‘并иЎҢдёҚжӮ–пјҢе®ғ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ҚеҸҜжҲ–зјә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гҖӮеҶңж°‘е№ҝжіӣеҠ е…ҘдәҶжқЎз”°и°ғж•ҙзҡ„ең°еқ—ж•ҙеҗҲжҙ»еҠЁпјҢжІЎжңүиҝҷж ·жҷ®йҒҚзҡ„еҹәзЎҖжҖ§зҡ„з”°еҲ¶ж”№йҖ 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ҳҜдёҚеҸҜжғіиұЎзҡ„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зј“ж…ўзҡ„зҙҜиҝӣејҸ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дё»иҰҒзӣ®зҡ„жҳҜж”№е–„иҖ•ең°пјҢжҸҗй«ҳж•ҲзҺҮпјҢејҖеҲӣдәҶеңҹең°зҡ„еҚ•зӢ¬иҖ•дҪңеҲ¶пјҲпҪҒпҪ’пҪҒпҪӮпҪҢпҪ… пҪ“пҪ…пҪ–пҪ…пҪ’пҪҒпҪҢпҪ”пҪүпҪ…пҪ“пјүпјҢд»ҺиҖҢеҶІеҮ»е’Ңз ҙеқҸдәҶе…ұеҗҢдҪ“иҖ•дҪңеҲ¶еәҰпјҢеҗҺиҖ…жҳҜ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зӨҫдјҡеҹәзЎҖгҖӮжҷ®йҖҡеҶңж°‘иҝҷж ·зҡ„еңҲең°ж–№ејҸдёҖзӣҙ延з»ӯдёӢжқҘпјҢдёҚи®ә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иҝҳжҳҜ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е°Ҫз®ЎйҒӯйҒҮеҗ„з§Қдәүи®®пјҢеҜ№дә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дҪңз”ЁеҶідёҚеҸҜдҪҺдј°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ӢұеӣҪдәәеҸЈзҡ„з»қеӨ§еӨҡж•°д»Қ然жҳҜеҶңж°‘пјҢдёҖеҚҠд»ҘдёҠзҡ„еңҹең°жҺ§еҲ¶еңЁд»–们жүӢйҮҢпјҢеҖҳиӢҘ他们дёӯзҡ„еӨҡж•°дәәйғҪеҺҢеҖҰдәҶж—§з”°еҲ¶пјҢд№җдәҺжҺҘеҸ—ж–°зҡ„иҖ•зү§ж–№ејҸпјҢе®һйҷ…жіЁе®ҡдәҶжқЎз”°еҲ¶з“Ұи§ЈеҸӘжҳҜдёӘж—¶й—ҙй—®йўҳгҖӮ
дёүгҖҒ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жҳҜеңҲең°дё»еҠӣ
дёҘж јиҜҙжқҘ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иҮӘ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еҚіе·ІеҗҜеҠЁпјҢжҷ®йҖҡеҶңж°‘иҮӘеҸ‘ең°ж•ҙеҗҲеҲҶж•ЈжқЎз”°пјҢеҜ№ж—§з”°еҲ¶е…·жңүеҹәзЎҖжҖ§зҡ„йў иҰҶдҪңз”ЁгҖӮеҶңж°‘зҡ„зӣ®ж ҮжҳҜжҠҠж•һз”°дёҠ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еҸҳдёәзҙ§еҮ‘еһӢзҡ„ең°еқ—пјҢеҗҢж—¶еҲҶеүІ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иҜ•еӣҫзӣҙжҺҘжҺҢжҺ§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йҡҸзқҖ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зҫӨдҪ“зҡ„еҮәзҺ°пјҢ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еҚіеӨ§еҶңеңЁ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дёӯеқҡдҪңз”ЁдёҚеҸҜеҝҪи§Ҷ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еҗҺиҝҷз§ҚдҪңз”Ёж„ҲеҸ‘еҮёжҳҫеҮәжқҘгҖӮ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дҪңиҖ…жҢҮеҮәпјҢеңЁж–°зҡ„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зӨҫдјҡдёҠеұӮе·Із»ҸдёҚиғҪеһ„ж–ӯиҺ·еҫ—еҲ©ж¶Ұзҡ„жңәдјҡпјҢвҖңеҶңж°‘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иҰҒеҸӮдёҺиҖ…вҖқпјҢиҝҷйҮҢзҡ„еҶңж°‘дё»иҰҒжҢҮеӨ§еҶңпјҢеҪ“然иҝҳжңүд№Ўз»…гҖӮжӯЈеҰӮдҪңиҖ…жҺҘдёӢжқҘиҰҒжҢҮеҮәзҡ„пјҢ他们йҖҡиҝҮеңҲең°иҺ·еҫ—еҲ©ж¶ҰпјҢ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гҖӮ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е®¶е°ұжҳҜд»Һиҝҷдәӣдәәдёӯдә§з”ҹгҖӮ他们еҰӮйұјеҫ—ж°ҙпјҢжӯЈеңЁжӢҘжҠұиҮӘе·ұзҡ„ж—¶д»ЈгҖӮ
пј‘пјҺ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жҰӮеҝө
еӨ§еҶң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пјҢиҝҷдёҺ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зҡ„иҮӘиә«жҖ§иҙЁжңүе…ігҖӮдј—жүҖе‘ЁзҹҘпјҢеңЁдёӯдё–зәӘеҶңж°‘иҮӘз”ұе’Ңз»ҸжөҺзҠ¶еҶөжҷ®йҒҚж”№е–„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з»ҸиҝҮиӢҘе№Ідё–зәӘз§ҜзҙҜпјҢеҮәзҺ°дәҶдёҖжү№жңүзқҖиҫғеӨ§еңҹең°йқўз§Ҝе’ҢзҫҠзҫӨзҡ„еӨ§еҶңпјҢ他们зҡ„еңҹең°з»ҸиҗҘдёҚеҶҚд»…д»…ж»Ўи¶іиҮӘ家ж¶Ҳиҙ№пјҢиҖҢдё»иҰҒдёәеёӮеңәжҸҗдҫӣеҶңзү§дә§е“ҒпјҢдёҺеёӮеңәжңүзқҖзӣёеҪ“еҜҶеҲҮ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йҡҸзқҖеңҹең°и§„жЁЎжү©еӨ§пјҢеӨ§еҶңз»ҸжөҺзҡ„еҠіеҠЁеҠӣд№ҹжқҘиҮӘеёӮеңә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е·Із»Ҹе…·еӨҮдәҶ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»ҸжөҺзҡ„еҹәжң¬зү№еҫҒгҖӮеӨ§еҶңеңЁдёҺ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з»ҸжөҺзҡ„еҚҡејҲдёӯеҲқйңІй”ӢиҠ’гҖӮеҠіеҪ№жҠҳз®—пјҢе®һиЎҢиҙ§еёҒең°з§ҹеҗҺйўҶдё»дёҖеәҰд№ҹйӣҮе·Ҙз»ҸиҗҘзӣҙйўҶең°пјҢд№ҹзҰ»дёҚејҖеёӮеңәиҰҒзҙ пјҢеӣ жӯӨдёҺеӨ§еҶңз»ҸжөҺеҪўжҲҗз«һдәүеҜ№жүӢгҖӮеӨ§еҶңдёҚжҳҜйқ иө„йҮ‘е’Ңз»ҸжөҺ规模пјҢжӣҙдёҚжҳҜйқ иә«д»Ҫең°дҪҚпјҢиҖҢжҳҜйқ еӢӨеҘӢзҡ„з»ҸиҗҘпјҢй”ұй“ўеҝ…иҫғзҡ„и®Ўз®—пјҢд»ҘеҸҠеҜ№еёӮеңәиЎҢжғ…зҡ„дәҶеҰӮжҢҮжҺҢгҖӮеҮӯйқ иҮӘе·ұж‘ёзҙўеҮәжқҘзҡ„з”ҹдә§дёҺдәӨжҳ“дёҖдҪ“еҢ–жЁЎејҸпјҢ他们еңЁ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зҡ„жҗҸжқҖдёӯжёёеҲғжңүдҪҷпјҢе……ж»Ўжҙ»еҠӣгҖӮеӨ§еҶңз»ҸжөҺдёҺ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дәүеёӮеңәгҖҒдәүеҠіе·ҘпјҢжңҖз»Ҳз«һдәүз”ҹдә§ж•ҲзҺҮпјҢдҪҝйўҶдё»з»ҸжөҺйҒӯйҒҮеҲ°жһҒеӨ§зҡ„еҺӢеҠӣпјҢжҖ»жҳҜе…ҘдёҚж•·еҮәпјҢеёёе№ҙдәҸжҚҹпјҢеӨ§еӨҡйқўдёҙз ҙдә§зҡ„еЁҒиғҒгҖӮеә„еӣӯжҹҘиҙҰе®ҳе№ҙз»ҲжҠҘиҙҰж—¶жҖ»жҳҜиҜҙпјҡвҖңд»Ҡе№ҙеҸҲдәҸдәҶпјҒвҖқ并е»әи®®йўҶдё»вҖңеә”еҪ“еғҸе…¶д»–еә„еӣӯйӮЈж ·жҠҠзӣҙйўҶең°з§ҹеҮәеҺ»вҖқгҖӮйІҒзү№е…°е…¬зҲөзҡ„еә„еӣӯ管家еңЁиҙҰжң¬йҮҢ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еңҹең°еңЁйўҶдё»жүӢдёӯпјҢж•…ж— еҲ©зӣҠгҖӮвҖқ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з»ҸжөҺзҡ„жңҖеҗҺз»“еұҖпјҢеҮ д№ҺйғҪжҳҜиў«иҝ«еҮәз§ҹпјҢиҖҢдё”еӨ§еӨҡеҮәз§ҹз»ҷеӨ§еҶңгҖӮзӣҙйўҶең°еҮәз§ҹж„Ҹе‘ізқҖ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йҖҖеҮәз”ҹдә§йўҶеҹҹгҖӮ
е°ұ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жөҺиҖҢиЁҖпјҢеңҹең°дёҚеҶҚд»…д»…дёәдәҶзіҠеҸЈпјҢд№ҹдёҚеғҸе°Ғе»әйҮҮйӮ‘йӮЈж ·жҳҜж”ҝжІ»иә«д»Ҫзҡ„еҮӯжҚ®пјҢиҖҢдё»иҰҒжҳҜж”«еҸ–еёӮеңәеҲ©ж¶Ұзҡ„е№іеҸ°гҖӮеңҲең°еҸҜд»ҘжҸҗй«ҳеңҹең°ж•ҲзӣҠпјҢиҝңиҝңй«ҳдәҺ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пјҢеӣ жӯӨеҸҜд»ҘжңүжҠҠжҸЎең°иҜҙ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жҜ”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з»ҸжөҺе®һеҠӣзҡ„еә„зЁјйҮҢжүӢгҖҒеҸҲжңҖе…Ҳд»Һ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жқҖеҮәзҡ„еӨ§еҶңпјҢжӣҙзғӯиЎ·дәҺжү©еј еңҹең°гҖҒеӣҙеңҲеңҹең°пјҢжӣҙжҖҘдәҺж‘Ҷи„ұе…ұеҗҢдҪ“з”°еҲ¶жқҹзјҡгҖӮ他们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зӣҙжҺҘеҠЁеҠӣпјҢжІЎжңү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з»ҸжөҺзҡ„еҪўжҲҗе’ҢеҸ‘еұ•пјҢжҢҒз»ӯеҮ зҷҫе№ҙзҡ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зҡ„гҖӮ
еҲ°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дёҺ乡绅已然зӣёеҪ“жҺҘиҝ‘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ө·зӨҫдјҡйҳ¶еұӮзҡ„жөҒеҠЁжҖ§еўһејәпјҢзәҰжӣјдёҺд№Ўз»…д№Ӣй—ҙзӣёдә’жё—йҖҸе’ҢдәӨеҸүпјҢ他们д№Ӣй—ҙзҡ„з•ҢйҷҗжӣҙеҠ жЁЎзіҠгҖӮи®ёеӨҡжүҖи°“зҡ„д№Ўз»…пјҢдёҚд№…еүҚиҝҳжҳҜзәҰжӣј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‘е№ҙ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дёҖдёӘеҸ«дҪңиө«зҰҸеҫ·зҡ„зәҰжӣјпјҢд»Һд№Ўз»…йҳҝд»ҖжүӢйҮҢд№°дёӢдёҖдёӘпј•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зҡ„еә„еӣ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—е№ҙиҜҘзәҰжӣјеҺ»дё–еҗҺе…¶еӯҷеӯҗ继жүҝ家дә§пјҢ并дәҺ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ејҖе§ӢеңҲең°пјҢеңЁпј‘пјҗе№ҙеҗҺзҡ„дёҖд»Ҫ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дёӯиҜҘзәҰжӣјз»§жүҝдәәзҡ„иә«д»Ҫе·Із»ҸжҳҜд№Ўз»…гҖӮ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并йқһдёӘжЎҲгҖӮзҪ—ж–ҜиҜҙпјҢвҖңзәҰжӣјжңүж—¶жҜ”他们зҡ„д№Ўз»…йӮ»еұ…иҝҳиҰҒеҜҢжңүвҖқгҖӮзәҰжӣје’Ңд№Ўз»…зҡ„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ең°дҪҚеҰӮжӯӨжҺҘиҝ‘пјҢд»ҘиҮҙеҮәзҺ°дәҶвҖңе®ҒдёәзәҰжӣјеӨҙпјҢдёҚеҒҡз»…еЈ«е°ҫвҖқйӮЈж ·зҡ„иӢұж је…°и°ҡиҜӯгҖӮдәҢиҖ…иҝҳжңүзқҖе…ұеҗҢзҡ„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пјҡвҖң他们改йқ©иҖ•дҪңпјҢзәҰжӣјдёҺд№Ўз»…дёҖж ·жҳҜеҶңдёҡж”№йқ©е®¶пјҢд№ҹдёҖеҝғиҝҪйҖҗеңҹең°еҲ©ж¶ҰгҖӮвҖқеҹәдәҺиҝҷз§ҚдәӨиһҚпјҢиӢұеӣҪеңЁиҙөж—ҸдёҺжҷ®йҖҡеҶңеӨ«д№Ӣй—ҙеҮәзҺ°дәҶејәжңүеҠӣзҡ„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пјҢиҝҷдёӘ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жҳҜ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”ҹдә§ж–№ејҸзҡ„жңҖж—©ејҖеҲӣиҖ…пјҢд»ҺиҖҢжңүеҲ«дәҺиӢұж је…°е’Ң欧жҙІе…¶д»–еӣҪ家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иӢұеӣҪзү§еёҲе…јеҺҶеҸІеӯҰ家еҜҢеӢ’пјҲпјҰпҪ•пҪҢпҪҢпҪ…пҪ’пјүжӣҫиҮӘиұӘең°иөһиөҸиҝҷдёҖ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并дёҺжі•е…°иҘҝгҖҒж„ҸеӨ§еҲ©е’Ңеҫ·ж„Ҹеҝ—еҒҡдәҶжҜ”иҫғгҖӮд»–иҜҙпјҢ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пјҢвҖңдёҖдҪҚжқ°еҮәзҡ„зәҰжӣјпјҢе°ұжҳҜдёҖдҪҚж¬ҫжӯҘиҖҢиҮізҡ„д№Ўз»…пјҢиҖҢдё”иҝҷж ·зҡ„зҺ°иұЎи¶ҠжқҘи¶Ҡжҷ®йҒҚгҖӮиҖҢжі•еӣҪе’Ңж„ҸеӨ§еҲ©пјҢеҘҪеғҸ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йӘ°еӯҗпјҢеңЁпј•зӮ№дёҺпј‘зӮ№й—ҙжІЎжңүеҲ«зҡ„зӮ№дҪҚпјҢеҰӮеҗҢ他们йӮЈйҮҢйҷӨдәҶиҙөж—Ҹе°ұжҳҜеҶңж°‘гҖӮеҫ·еӣҪжңүдёҖзұ»еҶңж°‘пјҲпҪӮпҪҸпҪҸпҪ’пҪ“пјүдјјд№ҺдёҺжҲ‘们зҡ„зәҰжӣјзӣёдјјпјҢдҪҶеҸ—еҲ°еҸӨиҖҒзҡ„家ж—Ҹиҙөж—Ҹзҡ„дё“жЁӘдҫөеҗһпјҢдҪҝ他们зҡ„зӨҫдјҡзӯүзә§дёҚеҸҜиғҪжңүд»Җд№ҲеҸҳеҢ–гҖӮвҖң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пјҢиҚЈиӘүзҡ„еңЈж®ҝдёҚеҜ№д»»дҪ•дәәе…ій—ӯпјҢеҸӘиҰҒдҪ иғҪиҝҲиҝҮе®ғзҡ„й—Ёж§ӣгҖӮвҖқеҜҢеӢ’зҡ„жҜ”е–»зӣёеҪ“еҪўиұЎпјҢд»–иҜҙе…¶д»–еӣҪ家зҡ„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еҰӮеҗҢиҝҷж ·зҡ„йӘ°еӯҗпјҢеҸӘжңүпј•зӮ№дёҺпј‘зӮ№пјҢеҚіеҸӘжңүиҙөж—ҸдёҺеҶңж°‘пјӣ然иҖҢиӢұж је…°йқһеҗҢеҮЎе“ҚпјҢеңЁдәҢиҖ…д№Ӣй—ҙдә§з”ҹдәҶ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дјҡиҝҷж ·е‘ўпјҹеӣ зҙ еҫҲеӨҡпјҢ笔иҖ…д»ҘдёәжңҖйҮҚиҰҒд№ҹжҳҜжңҖзӣҙжҺҘзҡ„еҺҹеӣ жҳҜпјҢ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пјҢд»ҘйӣҮдҪЈз»ҸжөҺеӨ§еҶңдёәеҹәзЎҖеҪўжҲҗдәҶ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пјҢиҖҢдё”еҰӮжӯӨејәеӨ§пјҢд»ҘиҮідәҺдёҠеұӮзӨҫдјҡзҡ„еӨ§й—Ёж— жі•е…ій—ӯпјҢеҚізҺӢжқғе’Ңиҙөж—Ҹж— жі•еҪўжҲҗеһ„ж–ӯжҖ§еҠӣйҮҸпјҢеӣ иҖҢж— жі•еһ„ж–ӯж•ҙдёӘзӨҫдјҡгҖӮжҳҫ然пјҢиҝҷд№ҹжҳҜдёәд»Җд№Ҳ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йҰ–е…ҲеҸ‘з”ҹ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зҡ„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
зҺ°д»ЈеҺҶеҸІеӯҰ家жІғеӢ’ж–ҜеқҰд№ҹиӮҜе®ҡдәҶиҜҘж—¶жңҹиӢұж је…°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д»–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пјҢзү№еҲ«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җвҖ”пј‘пј–пј”пјҗе№ҙд№Ӣй—ҙ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йҳ¶зә§пјҢдёҖдёӘ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е®¶йҳ¶зә§е·Із»ҸеҪўжҲҗзҡ„ж—¶жңҹвҖ”вҖ”вҖ”иҝҷдёӘйҳ¶зә§зҡ„дёҠеұӮжҳҜвҖҳд№Ўз»…вҖҷпјҢдёӢеұӮеҲҷжҳҜвҖҳзәҰжӣјвҖҷгҖӮвҖқзәҰжӣјеҚіеӨ§еҶңпјҢ他们е’Ңд№Ўз»…дёҖиө·з»„жҲҗд№Ўжқ‘зӨҫдјҡзҡ„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пјҢд»ҘеҗҺиҝҳжңүжҠ•иө„еңҹең°зҡ„е•ҶдәәзӯүеҠ е…ҘпјҢеҸҜ称他们дёә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пјҢ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е®¶йҳ¶зә§пјҢд№ҹжҳҜ第дёүзӯүзә§зҡ„дё»дҪ“гҖӮ他们жңүзқҖж–°зҗҶеҝөгҖҒж–°е“ҒиҙЁе’Ңж–°иҜүжұӮпјҢжӯЈеңЁжү“йҖ дёҖз§Қж–°зҡ„з”ҹдә§е’Ңз”ҹжҙ»ж–№ејҸгҖӮе…¶дёӯеӨ§еҶңеңЁ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”ҹдә§йўҶеҹҹзҡ„ејҖжӢ“жҖ§е’ҢеҹәзЎҖжҖ§дҪңз”ЁпјҢе°Өе…¶еә”еҪ“з»ҷдәҲе……еҲҶйҮҚи§ҶгҖӮиҜҘйҳ¶еұӮ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үҚ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зҡ„еңҹең°еҚ жңүдјҳеҠҝе·Із»ҸзӣёеҪ“жҳҺжҳҫгҖӮ
пј’пјҺдёәж”«еҸ–еңҹең°з»ҸиҗҘзҡ„еёӮеңәеҲ©ж¶ҰиҖҢеңҲең°
дёәдәҶиҺ·еҫ—еңҹең°еҲ©ж¶ҰпјҢйҰ–е…ҲиҰҒе°Ҷ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иө·жқҘпјҢ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пј‘пј•гҖҒ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Ӣұж је…°зҡ„еңҹең°дёҚжҳҜйӣҶдёӯеңЁ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жүӢйҮҢ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йӣҶдёӯеңЁеңҹең°жҠ•жңәе•ҶжүӢйҮҢпјҢиҖҢжҳҜйӣҶдёӯеңЁдёҖйғЁеҲҶз”ҹдә§иҖ…жүӢйҮҢпјҢеҚізғӯиЎ·дәҺеңҹең°з»ҸиҗҘзҡ„еӨ§еҶңжүӢйҮҢгҖӮпјІпјҺжүҳе°је‘ҠиҜүжҲ‘们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җе№ҙе·ҰеҸіпјҢеҰӮжһңдҪ жңүжңәдјҡдҪңдёәйҷӘе®Ўе‘ҳй—®иҜўд№Ўжқ‘й•ҝиҖ…дёҖдәӣеңҹең°й—®йўҳпјҢдҪ еҫҲе®№жҳ“еҫ—еҲ°дёӢйқўзҡ„еӣһзӯ”пјҡиҝҷйҮҢдёҖзӣҙеӯҳеңЁзқҖеӨ§йҮҸеңҹең°д№°еҚ–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д№ жғҜдҪғжҲ·жүҖдёәпјҢжҖ»зҡ„и¶ӢеҠҝжҳҜжқЎз”°ең°зҡ„еҗҲ并д»ҘеҸҠжҢҒжңүең°зҡ„йӣҶдёӯгҖӮй•ҝиҖ…дјҡиҜҙпјҢвҖңзҘ–зҲ¶ж—¶жңҹзҡ„иӢҘе№І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иҖ•ең°вҖқпјҢвҖңе®ғ们жӣҫеҲҶеҲ«еұһдәҺпјЎгҖҒпјўгҖҒпјЈгҖҒпјӨпјҢзҺ°еңЁеҲҷеҚ•зӢ¬еұһдәҺпјЎгҖӮиҝҮеҺ»жҜҸдәәеҚ жңүдёҖеқ—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зҺ°еңЁеҲҷеҚ жңүдёӨдёүеқ—вҖқгҖӮ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пјҲпҪ–пҪүпҪ’пҪҮпҪҒпҪ”пҪ…пҪ“пјүжҲ–еҚҠ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пјҢеҚіпј“пјҗиӢұдә©жҲ–пј‘пј•иӢұдә©пјҢиҝҮеҺ»жӣҫжҳҜдҪғеҶңзҡ„ж ҮеҮҶд»Ҫең°еҚ•дҪҚпјҢзңјдёӢиҝҷдәӣиҜҚжұҮ已然没жңүд»Җд№Ҳж„Ҹд№үдәҶгҖӮвҖңиҝҮеҺ»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ңүдёҖеқ—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иҖҢдё”жҳҜеҲҶж•Јзҡ„вҖҰвҖҰзҺ°еңЁпјҢе°Ҫз®ЎеҺҹжқҘжҢҒжңүиҖ…еҸӨиҖҒзҡ„еҗҚеӯ—иҝҳеӯҳеңЁпјҢдҪҶжҳҜиҝҷдәӣ家ж—ҸеҗҚеӯ—дёҺеҪ“дёӢе®һйҷ…жӢҘжңүйӮЈд»Ҫиҙўдә§зҡ„家еәӯе·ІжҳҜдёӨеӣһдәӢдәҶгҖӮдҫӢеҰӮеҜҢе…°е…Ӣжһ—иҙӯд№°дәҶиҫҫе…°зү№гҖҒз”ҳзү№е’ҢеёғиҺұе…Ӣ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з»ҙзү№ж–Ҝиҙӯд№°дәҶеё•йҮҢ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еҸҰ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еёғиҺұе…ӢеЁҒе°”еҲҷ收иҙӯдәҶжӣҙеӨҡ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Ң…жӢ¬дҪғеҶңиЈҙиҜәгҖҒжҷ®дјҜе’ҢйңҚйҮ‘ж–Ҝзҡ„иҖ•ең°е’ҢиҚүең°пјҢд»ҘеҸҠеүҚиҝ°еёғиҺұе…Ӣеү©дҪҷзҡ„жҢҒжңүең°гҖӮвҖқзүӣжҙҘдёҮзҒөеӯҰйҷўжЎЈжЎҲе®Өж–ҮзҢ®жүҖдҪңзҡ„дёҠиҝ°жҸҸиҝ°пјҢз”ҹеҠЁжҳҫзҺ°дәҶдёҖиҲ¬дҪғжҲ·зҡ„еңҹең°жӯЈеңЁжөҒеҗ‘еӨ§еҶңгҖӮеҖҹеҠ©з©әеүҚжҙ»и·ғзҡ„еҶңж°‘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пјҢеңҹең°иө„жәҗеңЁиҝҷйғЁеҲҶеҶңж°‘жүӢдёӯдёҚж–ӯең°и°ғж•ҙпјҢжҲҗдёәд№Ўжқ‘еңҹең°ж•ҙеҗҲзҡ„йҮҚиҰҒзҺҜиҠӮгҖӮ
пјЈпјҺжҲҙе°”йҮҮз”ЁжҠҪж ·ж–№ејҸпјҢе°Ҷ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еҶңж°‘дҝқ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дёҺпј‘пј“дё–зәӘжң«еҒҡдәҶжҜ”иҫғпјҢиЎЁжҳҺеҶңж°‘еҚ 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еҸ‘з”ҹдәҶжҳҺжҳҫ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ҡ

жҲ‘们зңӢеҲ°пјҢдёҺпј‘пј“дё–зәӘжң«зӣёжҜ”пјҢ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еӨ§д»Ҫ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жҳҺжҳҫеўһеӨҡпјҢеӨ§д»ҪжҢҒжңүең°еңЁе…ЁйғЁ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дёӯзҡ„жҜ”дҫӢд№ҹеңЁеўһеҠ пјҢеҰӮеңЁе“Ҳзү№дјҜйӣ·еә„еӣӯпјҢеӨ§д»ҪжҢҒжңү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з«ҹ然иҫҫеҲ°пј–пј—пј…пјҢеўһй•ҝпј‘пј—пј…гҖӮд»Өдәә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жҳҜпјҢе°Ҹеңҹең°е№¶жІЎжңүйҡҸд№ӢеўһеҠ пјҢеҸҚиҖҢеҮҸе°‘дәҶпј‘пј‘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пјҢдёӯд»Ҫ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д№ҹйҡҸд№ӢеҮҸе°‘гҖӮе…ӢйҮҢеӨ«еә„еӣӯгҖҒзҝ°дјҜйӣ·еә„еӣӯе’ҢдәЁдјҜйӣ·еә„еӣӯзҡ„еҸ‘еұ•и¶ӢеҠҝдёҺд№Ӣзӣёиҝ‘пјҢеҸӘжҳҜзЁӢеәҰдёҚеҗҢгҖӮ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еӨ§еҶңж–°еўһеңҹең°еҫҲеӨҡжқҘиҮӘеҶңдёҡиҪ¬з§»дәәеҸЈпјҢеҗҺиҖ…з”ұдәҺеңЁе…¶д»–з”ҹдә§йўҶеҹҹжҲ–еҹҺй•ҮжүҫеҲ°жӣҙйҖӮе®ңзҡ„з”ҹи®ЎиҖҢж”ҫејғеңҹең°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ёӮеңәиЎҢдёәзҡ„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жҳҜдёҺз»ҸжөҺзӨҫдјҡзҡ„ж•ҙдҪ“еҸ‘еұ•еҗҢжӯҘзҡ„пјҢеӨ§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дёҚдёҖе®ҡд»ҘжҢӨеҺӢдёҖиҲ¬дҪғеҶңдёәд»Јд»·пјҢжүҖд»Ҙж•°жҚ®жҳҫзӨәе°ҸеҶңдёҚдҪҶжІЎжңүеўһеҠ еҸҚиҖҢеҮҸе°‘гҖӮ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жңӘеҝ…жҖ»жҳҜе“ҖйёҝйҒҚйҮҺгҖӮжҖ»дҪ“жқҘзңӢ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үҚеӨ§д»Ҫ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ж•°йҮҸеўһеҠ дәҶпјҢиҖҢйҡҸзқҖеҠіеҠЁеҠӣиҪ¬з§»дҪғжҲ·жҖ»ж•°еҚҙиҝңе°‘дәҺдәҢзҷҫе№ҙеүҚгҖӮд»ҺеҸҰдёҖдёӘи§’еәҰзңӢпјҢ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зҡ„и„ҡжӯҘеңЁеҠ еҝ«пјҢеҠҝеҝ…дјҙйҡҸзқҖеӨ§еҶңз»ҸжөҺзҡ„з№ҒиҚЈе’ҢеҸ‘еұ•вҖ”вҖ”вҖ”иҜҘж—¶жңҹеӨ§еҶңзҡ„иЎЁзҺ°дёҚеҗҢеҮЎе“ҚгҖӮ
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ж— з–‘жҳҜеңҹең°жөҒйҖҡе’Ңеңҹең°йӣҶдёӯзҡ„йҮҚиҰҒжё йҒ“пјҢиҝӣе…Ҙ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җҺеӨ§еҶңжІЎжңүеҒңдёӢиҒҡйӣҶеңҹең°зҡ„и„ҡжӯҘ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”е№ҙзҡ„дёҖйЎ№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пјҢжҸҗдҫӣдәҶеӨ§еҶңд»Һдҝ®йҒ“йҷўеңҹең°жӢҚеҚ–дёӯиҺ·зӣҠзҡ„дәӢе®һ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дёҖдёӘеҗҚеҸ«жҲҲеҫ·ж–ҜйҖҡ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йҷӨе·Із»ҸеӣҙеңҲзҡ„еңҹең°еӨ–пјҢиҝҳиҙӯзҪ®ең°дә§пј’пј‘пј”иӢұдә©пјӣдёҖдёӘеҶңеӨ«еҗҚеӯ—жҳҜеҘҘж–ҜеҶ…пјҢд№ҹжӢҘжңүеңҲең°пјҢеҗҢж—¶иҙӯзҪ®пј—пј—иӢұдә©пјӣеҸҰжңүдёҖдҪҚдҪғеҶң姓еҗҚдёҚиҜҰпјҢиҝӣиҙҰзәҰпј”пјҳиӢұдә©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зӯүгҖӮзҗҶжҹҘеҫ·жЈ®еҸҜжҲҗдёәеҸҰдёҖдёӘе…ёеһӢжЎҲдҫӢпјҢд»–жҳҜеӨ§еҶңпјҢиҝҳжҳҜдҪ©е°”е§Ҷж–Ҝж•ҷеҢәжү§дәӢпјҢж•°еҚҒе№ҙдёӯдёҚж–ӯиҙӯд№°е’Ңжүҝз§ҹеңҹең°пјҢеӨ§е°ҸдёҚжӢ’пјҢжңүж—¶дёҖдёӨиӢұдә©пјҢжңүж—¶еҲҷдёҖж¬Ўиҙӯиҝӣпј•пјҗиӢұдә©д»ҘдёҠпјҢеҲ°пј‘пј•пј’пјҳе№ҙзҗҶжҹҘеҫ·жЈ®еҺ»дё–ж—¶е·ІеқҗжӢҘпј’пјҷпј—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зӣёеҪ“дәҺпј’пјҗпјҗпјҗеёӮдә©гҖӮдёҚжӯўиҝҷдәӣпјҢд»–иҝҳжүҝз§ҹйўҶдё»жүҳ马ж–ҜВ·жҖҖж–Ҝзү№зӯүдёҖ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пјҢдёәжӯӨж”Ҝд»ҳпј“пјҗе…Ҳд»Өпј•дҫҝеЈ«з§ҹйҮ‘гҖӮжҳҫ然пјҢжӯӨж—¶еӨ§еҶңзҡ„иғғеҸЈжҜ”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ж—¶жӣҙеӨ§гҖӮжңүиҜҒжҚ®жҳҫзӨә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ҹең°еҗҲ并зҡ„и¶ӢеҠҝжҢҒз»ӯеҸ‘еұ•пјҢвҖңеҮәзҺ°дәҶжҢҒжңүеӨ§зүҮеңҹең°зҡ„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йҳ¶еұӮпјҢжңҖеҜҢиЈ•зҡ„е’ҢжңҖдёҚеҜҢиЈ•зҡ„еҶңж°‘д№Ӣй—ҙзҡ„е·®и·қд№ҹи¶ҠжқҘи¶ҠеӨ§вҖқгҖӮи®ёеӨҡд№ жғҜдҪғжҲ·еҚ жңүеңҹең°и§„жЁЎиҫҫеҲ°пјҳпјҗгҖҒпјҷпјҗжҲ–пј‘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пјҢе…¶дёӯдёҚе°‘еңҹең°еҺҹжң¬еұһдәҺдёҚеҗҢзҡ„дҪғжҲ·гҖӮжңүзҡ„д№ жғҜдҪғжҲ·з”ҡиҮіжҲҗдёәе…¶д»–дҪғжҲ·зҡ„йўҶдё»пјҲпҪҢпҪҒпҪҺпҪ„пҪҢпҪҸпҪ’пҪ„пјүгҖӮеңЁдәҡзү№йӣ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№пҪҒпҪ”пҪ…пҪҢпҪ…пҪүпҪҮпҪҲпјүпјҢдёҖдёӘ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жӢҘжңүпј’пјҗдёӘж¬Ўзә§дҪғжҲ·пјҲпҪ“пҪ•пҪӮпјҚпҪ”пҪ…пҪҺпҪҒпҪҺпҪ”пҪ“пјүпјҢеҸҜи§ҒйӣҶдёӯзҡ„еңҹең°д№ӢеӨҡпјҢиҝҷеңЁ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并дёҚе°‘и§ҒгҖӮиҝҳдёҚиҰҒиҜҙжӣҙеӨ§жүӢ笔зҡ„еңҹең°дәӨжҳ“пјҢдәӨжҳ“иҖ…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еҶңж°‘пјҢдҫӢеҰӮдјҠдёҪиҺҺзҷҪдёҖдё–ж—¶пјҢзәҰжӣјеҶңе·ҙеҲ©ж–ҜйЎҝеҮәиө„пј’пјҗпј•пјҗиӢұй•‘д№°дёӢдёҖдёӘз”°еә„пјӣдёҖдёӘеҸ«дҪңеҘҘж–ҜдёҒзҡ„зәҰжӣјеҲҷд»Ҙпј•пјҗпјҗпјҗиӢұй•‘д№°дёӢдёҖдёӘпј”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зҡ„еә„еӣӯгҖӮ
йўҶдё»еңҹең°д№ҹжөҒеҗ‘еӨ§еҶңгҖӮеңЁеёӮеңәжү“жӢјдёӯйҖҗжёҗеҙӯйңІеӨҙи§’зҡ„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пјҢеҫҲд№…д»ҘжқҘе°ұеңЁж•ҙеҗҲе’ҢиҒҡйӣҶе°ҸеҶңең°еқ—пјҢеҗҺжқҘжүҝз§ҹйўҶдё»еӨ§йқўз§Ҝзҡ„зӣҙйўҶең°пјҢ他们жүӢйҮҢзҡ„еңҹең°жҖҘеү§еўһеҠ гҖӮиӢҸеЎһе…Ӣж–ҜйғЎдёҖеҲҷж–ҮзҢ®жҳҫзӨәпјҢеӨ§еҶңеңЁи®ёеӨҡең°еҢәжҲҗдёә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жүҝз§ҹдәәзҡ„дё»дҪ“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җпјҚпј‘пј–пј”пјҷе№ҙй—ҙпјҢпј–пј—дёӘеә„еӣӯзӣҙйўҶең°жүҝз§ҹиҖ…еҰӮдёӢпјҡзәҰжӣјпј“пјҗдәәпјҢе…¶ж¬ЎжҳҜз»…еЈ«пј‘пјҳдәәпјӣеҶҚе…¶ж¬ЎжҳҜе•Ҷдәәпј‘пј’дәәгҖҒеҶңеӨ«пј“дәәгҖӮзәҰжӣје’Ңд№Ўз»…еҚ зӣҙйўҶең°жүҝз§ҹдәәзҡ„пјҷпјҗпј…д»ҘдёҠпјҢе…¶дёӯзәҰжӣјжңҖеӨҡгҖӮеӨ§еҶңжүҝз§ҹзӣҙйўҶең°зҡ„дәӢдҫ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пјҢжӯӨдёҚиөҳиҝ°гҖӮжңүж—¶пјҢеӨ§еҶңиҝҳеҸҜиғҪдёҖж¬ЎжҖ§д№°ж–ӯйўҶдё»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ҳпј–е№ҙпјҢйўҶдё»еҮәе”®зҡ„еңҹең°е’ҢиҚүеңәпјҢдҪҚдәҺдёӨдёӘең°еҢәпјҢз»“жһңе…ЁйғЁиҗҪеңЁдёҖдёӘеӨ§еҶңжүӢйҮҢ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дёҚи®әжқҘиҮӘе°ҸеҶңиҝҳжҳҜжқҘиҮӘйўҶдё»пјҢеңҹең°еңЁ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жүӢйҮҢйҖҗжёҗйӣҶдёӯиө·жқҘгҖӮ他们еҸҜиғҪеҶҚж¬ЎеҮәз§ҹиҝҷдәӣеңҹең°пјҢжӣҙеӨҡзҡ„жғ…еҶөжҳҜпјҢ他们зӣҙжҺҘз»ҸиҗҘиҝҷдәӣеңҹең°гҖӮеҪ“еңҹең°е…ҘиҙҰж—¶пјҢ他们第дёҖдёӘж„ҝжңӣе°ұжҳҜе°Ҷең°еқ—ж•ҙеҗҲиө·жқҘпјҢ继иҖҢеӣҙеңҲиө·жқҘпјҢе®һиЎҢжңүж•Ҳз®ЎзҗҶпјҢжҸҗй«ҳеңҹең°д»·еҖјгҖӮжү©еј еңҹең°гҖҒеӣҙеңҲеңҹең°зҡ„ж„ҝжңӣпјҢеӨ§еҶңжҜ”д»»дҪ•дәәйғҪжӣҙејәзғҲгҖӮ
еӨ§еҶңжүҝз§ҹ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еҗҺе°ұз§ҜжһҒжҺЁеҠЁзӣҙйўҶең°зҡ„еӣҙеңҲпјҢжүҝз§ҹеңҹең°дёәдәҶиөўеҲ©пјҢиҖҢ他们жңҖеҹәжң¬зҡ„иөўеҲ©жүӢж®өе°ұжҳҜж–°еһӢеҶңеңәејҸз»ҸиҗҘпјҢдҪҝеңҹең°жңүеҲ«дәҺж•һз”°пјҢеңҲең°еҠҝеңЁеҝ…иЎҢ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他们жүӢйҮҢжң¬жқҘе°ұиҒҡйӣҶдәҶдёҖе®ҡйқўз§Ҝ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дёә规模жҖ§еңҲең°еҒҡдәҶеҮҶеӨҮ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ЎһдёҒжІғж–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ҲпҪ…пҪ„пҪ„пҪүпҪҺпҪҮпҪ—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ҲпјүпјҢеӨ§еҶң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йҖҡиҝҮеҗ„з§Қж–№ејҸиҒҡйӣҶеңҹең°пјҢжңүзҡ„д»ҺйўҶдё»е’Ңе…¶д»–дҪғжҲ·жүӢйҮҢиҙӯд№°пјҢжңүзҡ„йҖҡиҝҮе©ҡ姻е’Ң继жүҝж–№ејҸиҺ·еҫ—пјҢеҲ°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е…¶жҺ§еҲ¶зҡ„еңҹең°иҫҫпј”пјҗпјҺпј•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пјҢеҚ ж•ҙдёӘжқ‘еә„еңҹең°зҡ„пјҳпјҗпј…д»ҘдёҠ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ҳпј–е№ҙеҗҺпјҢ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еҫҒеҫ—дәҶе…¶д»–иҮӘз”ұеңҹ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зҡ„еҗҢж„ҸпјҢеҹәжң¬е®ҢжҲҗдәҶиҜҘжқ‘еә„е…ЁйғЁеңҹең°зҡ„еӣҙеңҲгҖӮжҚ®зүӣжҙҘйғЎеҸІи®°иҪҪпјҢпј‘пј”пјҷпј–е№ҙпјҢеӨ§еҶңеә“зҸҖжүҝз§ҹдәҶе“Ҳеҫ·з»ҙеҘҮеә„еӣӯпјҲпјЁпҪҒпҪ’пҪ„пҪ—пҪүпҪғпҪӢпјүзҡ„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пјҢйҡҸеҚіејҖе§ӢеңҲең°пјҢе°Ҷе…¶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ж•ҙеҗҲзҡ„еӣҙеңҲиө·жқҘзҡ„еҶңеңәгҖӮд»–еҸҲиҙӯд№°дәҶжқ‘еә„е…¶д»–зҡ„е°Ҹеқ—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дёӨз§Қзұ»еһӢеңҹең°ж··жқӮдёҖиө·пјҢеҪ“д»–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“е№ҙзҰ»дё–ж—¶пјҢе·Іиҙӯ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дёҺжүҝз§ҹең°д№Ӣй—ҙзҡ„з•ҢйҷҗеҸҳеҫ—жЁЎзіҠдёҚжё…гҖӮзүӣжҙҘйғЎзҡ„еҸҰдёҖеҲҷеҸІж–ҷпјҢд№ҹиЎЁжҳҺеӨ§еҶңзҡ„з»ҸжөҺжҙ»еҠЁзӣёеҪ“жҙ»и·ғгҖӮеңЁ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ҒпҪҢпҪ”пҪҲпҪҸпҪ’пҪҗпҪ…пјүпјҢ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—е№ҙпјҢеӣӣдёӘ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еӣҙеңҲдәҶ他们е…ұеҗҢжӢҘжңүзҡ„пј“пј–йӣ…еҫ·иҚүеңәпјҢжҳҫ然еұһйӣ¶ж•ЈеңҲең°гҖӮз”ұдәҺ他们еңЁз»ҙе…Ӣжұүе§Ҷеә„еӣӯпјҲпј·пҪүпҪғпҪӢ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иҝҳ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пјҢж•…жӯӨиҰҒжұӮдә«жңүиҜҘеә„еӣӯ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еј•иө·иҜҘ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дёҚж»ЎпјҢеҸ‘з”ҹиҜүи®јгҖӮж•ҷеҢәжі•еәӯеҶіе®ҡзәҰжқҹ他们дёҖдёӢ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зҰҒжӯўиҝҷдәӣ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дәә继з»ӯеңҲең°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йҷҗеҲ¶д»–们еңЁз»ҙе…Ӣжұүе§Ҷеә„еӣӯ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жҜҸдәәжҜҸйӣ…еҫ·еңҹең°д»…е…Ғи®ёж”ҫзү§пј’пјҗеҸӘзҫҠпјҢдҪҺдәҺдёҖиҲ¬дҪғеҶңж”ҫзү§зүІз•ңзҡ„ж•°йҮҸгҖӮжҳҫ然пјҢеҜҢиЈ•еҶңж°‘еҶңзү§е…јеҒҡпјҢиғғеҸЈи¶ҠжқҘи¶ҠеӨ§пјҢеңЁдёҚеҗҢзҡ„еә„еӣӯжӢҘжңүиҖ•ең°жҲ–зү§еңәпјҢ并且жёҙжңӣжӣҙеӨҡ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ңҲең°йҡҸж—¶еҸҜиғҪеҸ‘з”ҹгҖӮ
еӨ§еҶңд№ӢжүҖд»ҘзғӯиЎ·дәҺеңҲең°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ңҲең°еҗҺеҲ©ж¶ҰжҳҺжҳҫгҖӮ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зҡ„дҪң家иҜәзҷ»жӣҫ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пј‘иӢұдә©еңҲең°д»·еҖјзӯүеҗҢдәҺпј‘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ж•һз”°еңҹең°гҖӮвҖқеҸҰжҚ®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дёҖдҪҚ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жҸҗдҫӣ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әҢиҖ…д№Ӣй—ҙзҡ„д»·еҖјжҜ”жҳҜпј‘пјҡпј’пјҢеҚіжҸҗеҚҮпј‘пјҗпјҗпј…пјҢе…·дҪ“дҫӢиҜҒжҳҜпјҡпј‘пј–пј“пј–е№ҙеңЁ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жңүдёҖеқ—пј“пјҗйӣ…ж ј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…¶дёӯпј’пј’йӣ…ж јиў«еӣҙеңҲпјҢе…¶дҪҷпјҳйӣ…ж јд»ҚеңЁж•һз”°дёӯгҖӮеңҲең°еүҚпјҢдёӨ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зҡ„еҚ•дҪҚд»·ж јзӣёеҗҢпјӣеӣҙеңҲзҡ„еңҹең°жҜҸйӣ…ж јдёҠеҚҮдёәпј’пјҗй•‘пјҢиҖҢж•һз”°дёҠзҡ„еңҹең°д»·ж јд»Қдёәпј‘пјҗиӢұй•‘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дёҖйЎ№и®°иҪҪж”ҜжҢҒдәҶ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пј‘пјҡпј’зҡ„дј°и®Ў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Қ—з«Ҝ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ҸпҪ”пҪ…пҪ“пҪӮпҪҒпҪғпҪҲпјүпјҢеңҹең°зҡ„з»“жһ„еңЁ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зҡ„дёҖзҷҫе№ҙйҮҢжІЎжңүж №жң¬жҖ§еҸҳеҢ–пјҢдҪҶжҳҜ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“е№ҙиҮі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’е№ҙй—ҙеӣ еңҹең°иў«еңҲеӣҙиҖҢдә§еҖјжҳҺжҳҫжҸҗеҚҮпјҢйўҶдё»зҡ„收е…Ҙзҝ»дәҶдёҖеҖҚгҖӮж №жҚ®зҷҪйҮ‘жұүйғЎгҖҒеҢ—е®үжҷ®йЎҝйғЎгҖҒзүӣжҙҘйғЎе’Ң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д№қдёӘж•ҷеҢәзҡ„еңҲең°иө„ж–ҷпјҢеҲ©иҫҫе§Ҷз»ҹи®ЎеҮәеңҲең°еҗҺзҡ„зү§еңәзӣёжҜ”ж•һз”°еҲ¶дёӢзҡ„иҖ•ең°е…¶д»·еҖјжҸҗй«ҳдәҶпј‘пј’пј“пј…гҖӮд№ҹжңүдёҖдәӣдј°и®Ўжӣҙд№җи§Ӯдәӣ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ҖдҪҚеҶңдёҡ专家еӣҫз‘ҹе°”пјҲпјҙпҪ•пҪ“пҪ“пҪ…пҪ’пјүи®ӨдёәпјҢеңҲең°жҳҜжқЎз”°ең°з”ҹдә§иғҪеҠӣзҡ„пј“еҖҚгҖӮдәЁеҲ©В·иҙқзү№жҳҜеҹғе§Ҷж–Ҝз»ҙе°”пјҲпјҘпҪҢпҪҚпҪ“пҪ—пҪ…пҪҢпҪҢпјүзҡ„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д№ҹжҳҜи‘—еҗҚзҡ„пј‘пј–пј”пј’е№ҙеҶңд№Ұзҡ„дҪңиҖ…пјҢд»–еҜ№еңҲең°зҡ„зӣҠеӨ„иҜҙеҫ—жӣҙе…·дҪ“пјҡиҝҷеқ—зү§еңәпјҲеңЁжҲ‘зҲ¶дәІеҲҡиҺ·еҫ—ж—¶пјүеҮәз§ҹз»ҷиҮӘе·ұзҡ„дҪғжҲ·пјҢжҜҸеқ—еңҹең°з§ҹйҮ‘пј’е…Ҳд»ӨпјҢд№ӢеҗҺжҳҜпј’е…Ҳд»Өпј–дҫҝеЈ«пјӣеҶҚд№ӢеҗҺжҳҜпј“е…Ҳд»ӨпјӣдҪҶзҺ°еңЁиў«еңҲеӣҙд№ӢеҗҺпјҢеңҹең°з§ҹйҮ‘зӣёеҪ“дәҺд№ӢеүҚзҡ„пј“еҖҚгҖӮпј‘пјҳдё–зәӘдҪңиҖ…еҜ№еңҲең°еҗҺзҡ„з”ҹдә§ж•ҲзҺҮиҜ„дј°еҲҷжӣҙй«ҳгҖӮ
иҝҷдәӣдј°и®Ўзҡ„еҮҶзЎ®жҖ§йҡҫд»ҘиҜ„еҲӨпјҢдёҚиҝҮеңҲең°еҗҺд»·еҖјеўһй«ҳпјҢз»ҸиҗҘиҖ…иҺ·еҲ©дё°еҺҡжҳҜжІЎжңүејӮи®®зҡ„гҖӮеӨ§еҶңеӣ иҝҪжұӮеҲ©ж¶ҰиҖҢеңҲең°пјҢеҸҲеӣ еңҲең°иҖҢжӣҙеҠ еҸ‘иҫҫиө·жқҘпјҢж јж–Ҝзү№жҙӣжҳҜе…¶дёӯдёҖдҫӢгҖӮзҗҶжҹҘеҫ·В·ж јж–Ҝзү№жҙӣжҳҜеҜҢиЈ•зәҰжӣјзҡ„第дёүдёӘе„ҝеӯҗпјҢеұ…дәҺзүӣжҙҘйғЎзҡ®ж–Ҝеә·зү№еә„еӣӯпјҲпј°пҪ’пҪ…пҪ“пҪғпҪҸпҪ”пҪ…пјү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’е№ҙпјҢд»–д»ҺиҫҫжІғе°”ж–Ҝ家ж—ҸжүӢдёӯиҺ·еҫ—дәҶзӣҙйўҶең°зҡ„第дёҖд»Ҫз§ҹзәҰпјҢйҡҸд№ӢеңҲең°пјҢжҳҺжҳҫжҸҗй«ҳдәҶеңҹең°зҡ„иҙЁйҮҸе’Ңд»·еҖјгҖӮд»ҘеҗҺдёҚж–ӯз»ӯзәҰ并дёҚж–ӯжү©еј еңҹең°пјҢдҫқйқ з»ҸиҗҘеӣҙеңҲ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иҝҷдёӘзәҰжӣјдҪғжҲ·жҲҗдёәзүӣжҙҘйғЎзҡ„дёҖжҲ·ж—әж—ҸпјҢжҢҒз»ӯдәҢзҷҫе№ҙпјҢе…¶еҶңеңәиў«дәә们жҸҸиҝ°дёәвҖңд»ҘеүҚеңҲеӣҙзҡ„гҖҒзҪ•и§Ғзҡ„гҖҒиӮҘжІғ并养жҙ»дәҶзӣёеҪ“еӨҡдәәеҸЈзҡ„еңҹең°вҖқгҖӮзүӣжҙҘйғЎйғЎеҸІдҪңиҖ…и®ӨдёәпјҢвҖңж—©жңҹзҡ„еңҹең°еңҲеӣҙдёәж јж–Ҝзү№жҙӣ家ж—ҸеёҰжқҘ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иҙўеҜҢвҖқгҖӮеҸҲеҰӮпјҢдҪғеҶңеҮәиә«зҡ„ж–Ҝе®ҫеЎһ家ж—ҸеңҲең°е’Ңз»ҸиҗҘеңҹең°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д№ҹжҳҜдёҖйғЁеӨ§еҶңеҸ‘家еҸІпјҢжңҖеҗҺз«ҹжҷӢиә«иҙөж—ҸпјҒж–Ҝе®ҫеЎһеңЁ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иҝҳиә«д»ҪдҪҺеҫ®пјҢ家ж—ҸиҙўеҜҢеҘ еҹәдәәзәҰзҝ°В·ж–Ҝе®ҫеЎһпјҢе…¶еҗҚеӯ—жңҖж—©еҮәзҺ°еңЁпј‘пј”пјҷпј—е№ҙпј‘пј‘жңҲпј’пј–ж—Ҙзҡ„дёҖд»ҪеҘ‘жҚ®дёӯпјҢиә«д»ҪжҳҜзү§еңәдё»гҖӮеӨ§зәҰ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җе№ҙд»–ејҖе§Ӣ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пјҢе°ҶиҙӯиҝӣжҲ–з§ҹиҝӣзҡ„еңҹең°еӣҙеңҲпјҢ并иҪ¬еһӢдёә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зү§еңә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’е№ҙпјҢд»–еӣҙеңҲдәҶ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дёӨдёӘеә„еӣӯпјҢ继иҖҢеӣҙеңҲдәҶ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дёҖеқ—еңҹең°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д»–иҝҳиҺ·еҫ—дәҶ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е’Ң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иӢҘе№ІйұјеЎҳзҡ„иҮӘз”ұйҘІе…»жқғгҖӮеҗҢе№ҙпј’жңҲпј’пјҗж—ҘпјҢд»–е°ҶдёҠиҝ°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дёӨеә„еӣӯзҡ„еҸҰеӨ–пј”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ж’ӮиҚ’пјҢдё»еҠЁжӢҶжҜҒиҮӘе·ұжӢҘжңүзҡ„дёҖеӨ„е®…йҷўпјӣпј‘пј’жңҲпјҢд»–еҸҲеӣҙеңҲдәҶж’ӮиҚ’зҡ„иҝҷпј”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е’ҢеҸҰеӨ–пј”пјҗиӢұдә©жһ—ең°еҸҠе…¶йҷ„еұһзү©пјҢ并дҪҝе…¶дёҺиҮӘе·ұзҡ„еҸҰеӨ–дёҖдёӘзү§еңәзӣёиҝһ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йўҮжңү规模зҡ„зү§еңәгҖӮеҮ е№ҙеҗҺпјҢж–Ҝе®ҫеЎһеҸҲиҙӯд№°дәҶдёҠиҝ°дёӨ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дёҖеқ—еӣҙеңҲең°пјҢеӨ§зәҰеҚҠзҠҒең°пјҢеҺҹеұһдёҖдҪҚе·Іж•…дҫҜзҲөпјҢж–Ҝе®ҫеЎһе°Ҷе…¶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иҮҙдҪҝпј”дәә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гҖӮж–Ҝе®ҫеЎһ家ж—ҸйҖҗжёҗеҸ‘иҫҫиө·жқҘпјҢеҗҺжқҘдёәдәҶиҙӯд№°еӣҪзҺӢзҡ„дёҖеқ—йўҶең°пјҢдёҖжҺ·еҚғйҮ‘пјҢдёҚжғңжҠ•е…Ҙпј’пјҗпјҗпјҗиӢұй•‘гҖӮ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еҲқ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ж–Ҝе®ҫеЎһжҷӢеҚҮдёәиҙөж—ҸгҖӮ
пј“пј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Ҹ‘иө·дәәе’ҢжҺЁеҠЁиҖ…
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Ҫұе“ҚдәҶж•ҙ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з”°еҲ¶ж”№йҖ гҖӮд№Ўз»…е“Ҳж–ҜжұҖж–Ҝ家ж—ҸеңЁдёҖдёӘдё–зәӘеҶ…еӣҙеңҲдәҶж•ҙдёӘеёғеҠіж–Ҝ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’пҪҒпҪ•пҪҺ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Ҫ…пјүпјҢд»–жҳҜеҲҶжӯҘйӘӨзј“ж…ўжҺЁиҝӣзҡ„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еҸІдҫӢдёәж•°дёҚйІңгҖӮдёӢйқўпјҢжҲ‘们дҫқж¬ЎеҲҶжһҗеӣӣдёӘиҫғдёәе…ёеһӢзҡ„жЎҲдҫӢпјҢж—ЁеңЁиҜҙжҳҺ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дёҚд»…жҳҜдҪғеҶңеңҲең°зҡ„йӘЁе№ІпјҢиҝҳ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Ҹ‘иө·дәәе’ҢдёҚжҮҲзҡ„жҺЁеҠЁиҖ…гҖӮ
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ҸпҪ”пҪ…пҪ“пҪӮпҪҒпҪғпҪҲпјүеңҲең°пјҢжҳҜ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дё»еҜјеңҲең°зҡ„жЎҲдҫӢд№ӢдёҖпјҢиҜҘжЎҲдҫӢжҜ”иҫғз»ҶиҮҙең°жҠ«йңІдәҶеҰӮдҪ•е®һж–ҪеңҲең°пјҢдҫқжҚ®д»Җд№ҲеңҲең°гҖӮиҝҷдёӘйҳ¶еұӮ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иҙўеҜҢпјҢеҸҜжҳҜ并没зү№еҲ«зҡ„ж”ҝжІ»жқғеҠӣпјҢжІЎжңүи¶…з»ҸжөҺзҡ„еҠӣйҮҸпјҢжүҖд»Ҙ他们еңҲең°зҡ„жүӢж®өиҝҳжҳҜйўҮд»Өдәә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гҖӮиҜҘеә„еӣӯеқҗиҗҪдәҺ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Қ—з«Ҝ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ҲқеҸ¶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е·Іиў«еӣҙеңҲпјҢзәҰпј’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пјҢзӣёеҪ“дәҺеә„еӣӯеҸҜиҖ•ең°зҡ„пј‘пјҸпј•пјҢе…¶дҪҷеңҹең°дёҖзӣҙиҝҳжҳҜжқЎз”°зҠ¶жҖҒ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–е№ҙиҜҘеә„еӣӯиҗҪеҲ°зәҰзҝ°В·еӨёе°”ж–ҜжүӢйҮҢпјҢд»–жҳҜдёҖдёӘдјҰж•Ұе•ҶдәәпјҢд»ҺеӣҪзҺӢйӮЈйҮҢиҙӯд№°дәҶиҝҷеқ—ең°дә§гҖӮз”ұдәҺиҜҘеңҹең°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§жқғзә и‘ӣпјҢиҙӯд№°еҗҺиҜҘеә„еӣӯеҮ е№ҙйғҪжІЎжңүеҲ°еӨёе°”ж–ҜжүӢйҮҢпјҢзӣҙиҮі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‘е№ҙжүҚеҪ’иҝҳз»ҷд»–гҖӮжӢҝеҲ°еә„еӣӯеҗҺпјҢеӨёе°”ж–ҜдёҖеҝғиҰҒвҖңејҘиЎҘиҝҷд»ҪжҚҹеӨұвҖқпјҢеҰӮдҪ•ејҘиЎҘпјҹд»–еҶіеҝғеңҲең°гҖӮзҗҶз”ұ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жқЎз”°ең°зҡ„д»·еҖјиҝңиҝңиҗҪеҗҺдәҺеёӮеңәиЎҢжғ…пјҢеҸӘжңүеңҲең°е№¶е®һиЎҢеҶңеңәз»ҸиҗҘжүҚиғҪеҲӣйҖ еҲ©ж¶ҰпјҢејҘиЎҘжҚҹеӨұпјҢжӯӨжЎҲдҫӢеҶҚж¬ЎиҜҒжҳҺдәҶиҝҷдёӘйҳ¶еұӮзҡ„еңҲең°еҠЁжңәгҖӮ
еӨёе°”ж–Ҝе·Із»Ҹд№°дёӢжқҘж•ҙдёӘеә„еӣӯпјҢеҸҜжҳҜеҜ№д»–жқҘи®ІвҖңеңҲең°вҖқ并йқһдёҖ件йҡҸеҝғжүҖж¬ІпјҢдәҲеҸ–дәҲжұӮд№ӢдәӢгҖӮз»ҸеҺҶдәҶж•°зҷҫе№ҙ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еӨ§жҪ®зҡ„еҶІеҲ·пјҢ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ң°йҖҗжёҗиң•еҸҳдёәе•Ҷдёҡеңҹең°е’Ңең°з§ҹпјҢеҸҜжҳҜеңЁж–°зҡ„еҺҶеҸІжқЎд»¶дёӢпјҢ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»Қ然дёҚеҸҜе°Ҹ觑гҖӮи®©еӨёе°”ж–Ҝж„ҹеҲ°е№ёиҝҗзҡ„жҳҜпјҢвҖңжӯӨж—¶пјҢдёҖдәӣдҪғжҲ·з§ҹзәҰж—©е·ІиҝҮжңҹвҖқгҖӮиҝҷдәӣдҪғеҶңзҡ„иә«д»ҪеӨ§жҰӮжҳҜжңҹйҷҗ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пјҢз§ҹзәҰеҲ°жңҹжҳҜ收еӣһеңҹең°жҲ–и°ғж•ҙз§ҹйҮ‘зҡ„жңәдјҡпјҢдәҺжҳҜеӨёе°”ж–Ҝе…ҲвҖңеҗ‘иҝҷдәӣдҪғжҲ·жҸҗеҮәжҜҸйӣ…ж јеңҹең°пј•иӢұй•‘зҡ„ж–°з§ҹзәҰвҖқпјҢиӮҜе®ҡеӨ§еӨ§и¶…еҮәеҺҹз§ҹйҮ‘гҖӮдҪғжҲ·д»¬жӢ’з»қдәҶж–°з§ҹзәҰпјҢдёҚиҝҮд№ҹе°ұйқўдёҙдәҶ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Құйҷ©гҖӮеҜ№дәҺ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пјҢеӨёе°”ж–Ҝзҡ„еҜ№зӯ–жҳҜиөҺд№°жҲ–еҚҸе•ҶгҖӮиҜҘеә„еӣӯе…ұжңүпј”дҪҚ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пјҢеӨёе°”ж–ҜеҢәеҲ«еҜ№еҫ…пјҢд№°ж–ӯе…¶дёӯдёҖдәә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дёҺеҸҰеӨ–дёӨдәә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жҲ–еңҹең°зҪ®жҚўжҲ–иҙ§еёҒиЎҘеҒҝгҖӮ第еӣӣдҪҚ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д»…жңүпј’иӢұдә©пјҢеӨёе°”ж–ҜиҝҳжҳҜиЎҘеҒҝдәҶдёҖдәӣеңҹең°гҖӮе…¶дҪҷжҳҜиӢҘе№ІйҖҫжңҹ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пјҢеӨёе°”ж–Ҝд№ҹжҳҜе…Ҳ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пјҢжҸҗй«ҳз§ҹйҮ‘пјҢз»“жһңд№ҹвҖңйҒӯеҲ°дәҶиҝҷдәӣ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зҡ„жӢ’з»қвҖқгҖӮеӨёе°”ж–Ҝзҡ„дёӢдёҖжӯҘдёҫжҺӘе°ұжҳҜиҝ«дҪҝдёҚжҺҘеҸ—ж–°з§ҹзәҰзҡ„дҪғеҶң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ҢеҢ…жӢ¬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е’Ңе…¬з°ҝеҶңгҖӮзңӢжқҘпјҢеңҲеҚ ж•ҙдёӘеә„еӣӯжҳҜд»–зҡ„жңҖз»Ҳзӣ®зҡ„гҖӮ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“е№ҙпјҢеңҲең°еҸ–еҫ—еӣҪзҺӢеҚіиҜҘ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зҡ„еҗҢж„ҸпјҢдҪғжҲ·зҡ„иҜүзҠ¶д№ҹиў«жі•еәӯй©іеӣһпјҢвҖңдҪғжҲ·д»¬йҷӨдәҶжҺҘеҸ—ж–°зҡ„з§ҹзәҰжҲ–иҖ…зҰ»ејҖжқ‘еә„д№ӢеӨ–еҲ«ж— йҖүжӢ©вҖқ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жңүдәӣдәәиҝҳжҳҜйҖүжӢ©з•ҷдёӢпјҢдёҚиҝҮз”ұдәҺз§ҹйҮ‘дёҠж¶ЁпјҢеңҹең°еҮҸе°‘дәҶпјҢ他们дёҖж—¶жІЎжңүиғҪеҠӣжүҝз§ҹеҺҹжқҘзҡ„еңҹең°пјӣдёҖдәӣиҢ…иҲҚе°ҸеҶңж”ҫејғеҺҹжқҘзҡ„дҝқжңүең°пјҢд»…д»…дҝқз•ҷ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еҸҜжҜҸеӨҙзүӣиҝҳйЎ»ж”Ҝд»ҳпј–дҫҝеЈ«гҖӮвҖңе…¶дҪҷжӢ’з»қж–°з§ҹзәҰзҡ„дҪғжҲ·пјҢжңҖз»ҲзҰ»ејҖдәҶжқ‘еә„пјҢжқ‘еә„дҪғжҲ·дәәж•°дёӢйҷҚдәҶдёҖеҚҠвҖқпјҢдёҚж»Ўжғ…з»ӘзӣёеҪ“ејәзғҲгҖӮ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еҜјиҮҙжқ‘еә„дәәеҸЈж•°йҮҸдёӢйҷҚдёҖеҚҠ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жғ…еҶөжҳҜдёҚеӨҡи§Ғзҡ„пјҢжүҖд»ҘеӨёе°”ж–ҜеңҲең°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и‘—еҗҚзҡ„жЎҲдҫӢпјҢж—¶еёёиў«еҗ„з§Қж•ҷ科д№Ұе’Ңи‘—иҝ°еј•з”ЁпјҢеҸӘжҳҜеҜ№дёӘдёӯзјҳз”ұе’ҢйҖ»иҫ‘е…ізі»е°‘жңүдәӨд»ЈгҖӮ
иҝҷзЎ®е®һжҳҜдёҖдёӘеӨ§еҶңзӯү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зҡ„е…ёеһӢжЎҲдҫӢгҖӮеӨёе°”ж–ҜеҸҢз®ЎйҪҗдёӢ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иҙ§еёҒиөҺд№°пјҢдёҺ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зӯүе°Ҹең°дә§дё»жҲҗдәӨпјӣдёҖж–№йқўеҲ©з”Ёз§ҹзәҰйҖҫжңҹпјҢд»Ҙ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гҖҒжҠ¬й«ҳз§ҹйҮ‘зҡ„жүӢж®өпјҢиғҒиҝ«жүҝз§ҹеҲ°жңҹзҡ„дҪғеҶң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Ң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еә„еӣӯе°ұиҝҷж ·еҸҳжҲҗдәҶеӣҙеңҲең°гҖӮ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з»“жһ„еңЁжӯӨеүҚдёҖзҷҫе№ҙйҮҢжІЎжңүж №жң¬жҖ§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然иҖҢ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“е№ҙиҮі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’е№ҙй—ҙпјҢжүҖжңүдёҖеҲҮеӣ еңҲең°иҖҢиў«ж”№еҸҳпјҢеә„еӣӯдё»зҡ„收е…Ҙд№ҹеҸҳжҲҗдәҶд»ҘеүҚзҡ„дёӨеҖҚгҖӮ
жңүзҡ„еӨ§еҶңжҲ–д№Ўз»…е·Із»ҸжҺ§еҲ¶дәҶеә„еӣӯ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пјҢеҖҳиӢҘеҠ д»Ҙиҙ§еёҒиөҺд№°жҲ–еңҹең°зҪ®жҚўзӯүз»ҸжөҺжүӢж®өпјҢйӮЈд№ҲеӣҙеңҲж•ҙдёӘеә„еӣӯеҚідёҖжӯҘд№ӢйҒҘ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ЎһдёҒжІғж–ҜпјҲпјҙпҪҲпҪ…пҪ„пҪ„пҪүпҪҺпҪҮпҪ—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ҲпјүеҚіеұһжӯӨдҫӢгҖӮеЁҒе»үе§ҶВ·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家йҒ“ж®·е®һ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дёҖдҪҚд»ӢдәҺеӨ§еҶңе’Ңд№Ўз»…д№Ӣй—ҙзҡ„дәәзү©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–е№ҙпјҢд»–д»ҺйўҶдё»д»ҘеҸҠе…¶д»–жүҖжңүиҖ…жүӢдёӯиҙӯд№°дәҶпј’пјҳпјҺпј•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ҹең°пјҢиҝҷжҳҜдёҖ笔еҫҲеӨ§зҡ„ең°дә§пјҢд»–еҰ»еӯҗдјҠдёҪиҺҺзҷҪВ·еҫ·е…Ӣж–Ҝзү№е·Іжңүпј–пјҺпј•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ҹең°гҖӮеІіжҜҚзҺӣдёҪВ·еҫ·е…Ӣж–Ҝзү№д№ҹжӢҘжңүпј•пјҺпј•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°дә§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ҳпј–е№ҙеҺ»дё–еүҚд»ҘйҒ—еҳұж–№ејҸиө дёҺиҝҷеҜ№еӨ«еҰҮгҖӮиҝҷж ·пјҢ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е®һйҷ…дёҠжӢҘжңүдәҶпј”пјҗпјҺпј•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ҹең°пјҢеҚ ж•ҙдёӘжқ‘еә„еңҹең°зҡ„пјҳпј“пј…пјҢиҜҘжқ‘еә„жҖ»и®ЎдёҚиҝҮпј”пјҳ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ҹең°пјҲеӨ§зәҰзӣёеҪ“дәҺпј‘пјҗ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пјүгҖӮеү©дҪҷзҡ„еңҹең°еҲҶж•ЈеңЁпј—дҪҚ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жүӢдёӯгҖӮдёәдәҶиҝӣдёҖжӯҘйӣҶдёӯең°дә§пјҢз»ҸеҚҸе•ҶпјҢпј—дҪҚ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и®©жёЎдәҶеңҹең°пјҢиЎЁйқўдёҠжҳҜиҙ§еёҒдёҺвҖңе…·жңүиүҜеҘҪд»·еҖјзҡ„з§ҹзәҰвҖқпјҲпҪҢпҪ…пҪҒпҪ“пҪ…пҪ“ пҪҸпҪҶ пҪҮпҪҸпҪҸпҪ„ пҪ–пҪҒпҪҢпҪ•пҪ…пјүзҡ„дәӨжҚўвҖ”вҖ”вҖ”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们жҺҲдәҲ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зҡ„з§ҹжңҹжҳҜдёҖеҚғе№ҙ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ҮәеҚ–дәҶ他们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вҖң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зҡ„еңҲең°йў„жңҹеҫ—д»ҘжҲҗз«ӢпјҢ并且еҸ–еҫ—дәҶеҗ„зӣёе…іж–№йқўзҡ„еҗҢж„ҸвҖқгҖӮиҜҘеә„еӣӯе’ҢеүҚиҝ°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еә„еӣӯеңҲең°жңүе…ұеҗҢд№ӢеӨ„пјҢд№ҹжҳҜ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зҡ„жҳҫи‘—зү№еҫҒпјҢиҙ§еёҒжҳҜ他们жүӢдёӯзҡ„дёҖеӨ§еҲ©еҷЁгҖӮ
д№Ўжқ‘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дё»еҜјеңҲең°зҡ„еҸҰдёҖз§ҚйҮҚиҰҒжЁЎејҸпјҢжҳҜиӢҘе№ІеӨ§дҪғжҲ·йӣҶдҪ“еҚҸе•ҶпјҢд»ҺиҖҢжҺЁеҠЁж•ҙдёӘжқ‘еә„еңҲең°гҖӮ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зҡ„еҮ дёӘеә„еӣӯйғҪжңүзұ»дјјзҡ„иЎҢдёәпјҢе…¶дёӯиҖғеҪӯ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ҸпҪ—пҪҗпҪ…пҪҺпјүжңҖжңүд»ЈиЎЁжҖ§гҖӮ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ҷе№ҙпјҢиҝҷ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з»ҸеҚҸе•ҶеҗҺпјҢиҜ•еӣҫеҲҶеүІж•һз”°дёҠзҡ„иҖ•ең°гҖҒиҚүең°д»ҘеҸҠйғЁеҲҶе…¬ең°пјҢ他们е…Ҳе°ҶжүҖж¶үдҪғжҲ·зҡ„еңҹең°ж··еҗҲеңЁдёҖиө·пјҲдёҖдәӣеңҹең°е·ІжңүжүҖеӣҙеңҲпјүпјҢ然еҗҺжҢүз…§ж—ўе®ҡеҺҹеҲҷйҮҚж–°еҲҶй…ҚгҖӮиҝҷж¬ЎиЎҢеҠЁз•ҷдёӢжқҘеңҲең°дҪғжҲ·еҚҸи®®д№ҰпјҢеҗҺз»ӯжҙ»еҠЁд№ҹиў«зҝ”е®һең°и®°иҪҪеңЁ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еҸІдёҠгҖӮеҚҸи®®з”ҹж•Ҳж—ҘжңҹжҳҜ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ҷе№ҙпј‘пј‘жңҲпј‘пј•ж—ҘпјҢиҝҷдәӣиҮӘз”ұдҪғеҶңе®Јз§°пјҢвҖңдёәдәҶж”№иҝӣе’Ңжңүж•ҲеҲ©з”Ёеә„еӣӯеңҹең°вҖқпјҢеҶіе®ҡдҪҝиҮӘе·ұжҺ§еҲ¶зҡ„еңҹең°д»Һж—§дҪ“еҲ¶зҡ„зҰҒй”ўдёӯи§Јж”ҫеҮәжқҘгҖӮеҚҸи®®д№ҰејҖеӨҙеӨ„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еңЁжҲ‘们зҡ„и©№е§ҶеЈ«еӣҪзҺӢз»ҹ治第17е№ҙзҡ„пј‘пј‘жңҲпј‘пј•ж—ҘпјҢ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иҖғеҪӯеә„еӣӯеҮ дҪҚеңҹең°зҡ„жүҖжңүиҖ…е’Ңз»ҸиҗҘиҖ…пјҢе°ұжҲ‘们зҡ„иӢҘе№ІеӨ„ең°дә§е’Ңдҝқжңүең°иҪ¬и®©е’ҢеҲҶеүІпјҢеҒҡеҮәзӣёдә’жүҝиҜәпјҢдёҖиҮҙиҫҫжҲҗеҰӮдёӢеҚҸи®®гҖӮвҖқеҸӮдёҺеҚҸи®®зҡ„жҲҗе‘ҳеұһдәҺе…ёеһӢзҡ„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пјҢ他们жҳҜпјҡпј‘дҪҚйӘ‘еЈ«жӢүе°”еӨ«В·еҫ·жӢүз“Ұе°”пјӣпј”дҪҚд№Ўз»…еҢ…жӢ¬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еЁҒдёҒйЎҝгҖҒи·Ҝжҳ“ж–ҜВ·еЁҒдёҒйЎҝгҖҒеҙ”ж–Ҝзү№з‘һе§ҶВ·иҠ¬еЁҒе…Ӣе’Ң马дёҒВ·иҠ¬еЁҒе…Ӣпјӣиҝҳжңүпј•дҪҚеӨ§еҶңпјҢеҢ…жӢ¬е°ҸзәҰзҝ°В·жҷ®еӢ’ж–ҜйЎҝгҖҒиҖҒзәҰзҝ°В·жҷ®еӢ’ж–ҜйЎҝгҖҒеә“ж–ҜдјҜзү№В·жІғжЈ®гҖҒеЁҒе»үВ·ж–ҜжүҳйҮҢд»ҘеҸҠ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еҸІеҜҶж–ҜгҖӮеҚҸи®®дё»иҰҒеҶ…е®№жҳҜпјҡ
е…¶дёҖпјҢиҒҳиҜ·иӢҘе№Іжңүз»ҸйӘҢе’ҢеҸҜйқ зҡ„еңҹең°еӢҳжөӢе‘ҳпјҢеҜ№жүҖж¶үеңҹең°е®һж–ҪеӢҳеҜҹгҖҒжЈҖйӘҢеҸҠдёҲйҮҸпјҢ然еҗҺе°Ҷеңҹең°еҲҶжҲҗдёӨйғЁеҲҶпјҢеҚіеҢ—йғЁе’ҢдёңйғЁең°еқ—гҖӮе…¶дәҢпјҢйҒөеҫӘеҗҲзҗҶе’Ңе…¬е№ізҡ„еҺҹеҲҷе°ҶдёҠиҝ°еңҹең°йҮҚж–°еҲҶй…ҚгҖӮвҖңдёҚеә”еҚ жңүжүҖжңүжңҖеҘҪзҡ„ең°пјҢд№ҹдёҚеә”еҚ жңүжүҖжңүжңҖеқҸзҡ„ең°пјҢ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ӢҘжңүе…¬е№і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е……еҲҶиҖғиҷ‘жүҖеҲҶз”°ең°зҡ„ж•°йҮҸе’ҢиҙЁйҮҸпјҢжқғиЎЎйҖӮеәҰгҖӮвҖқе…¶дёүпјҢж №жҚ®дёҠиҝ°еҺҹеҲҷпјҢдёҠиҝ°жҲҗе‘ҳеҲҶеҫ—дёҚеҗҢең°еқ—зҡ„еңҹең°пјҲиҜҰи§ҒдёӢйқўиЎЁж јпјүгҖӮе…¶еӣӣпјҢжүҖиҒҳеӢҳжөӢе‘ҳзҡ„е·Ҙиө„е’Ңиҙ№з”ЁпјҢиҰҒз”ұдёҠиҝ°жҲҗе‘ҳе…ұеҗҢжүҝжӢ…пјҢеҮәиө„д»ҪйўқдёҺжҜҸдәәеҲҶеҫ—еңҹең°ж•°йҮҸе’ҢиҙЁйҮҸзӣёеҪ“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…·дҪ“жҢҮе®ҡдәҶдёҖдҪҚеҗҚеҸ«й©¬дҝ®зҡ„дёәеңҹең°еӢҳжөӢе‘ҳпјҢд»–жқҘиҮӘзәҪеҚЎж–Ҝе°”пјҲпј®пҪ…пҪ—пҪғпҪҒпҪ“пҪ”пҪҢпҪ…пјүпјӣеҗҢж—¶дёҖиҮҙеҗҢж„Ҹд»ҺеӨ–йқўиҒҳиҜ·жүҳ马ж–ҜВ·з‘һйғҪзӯүдә”дәәз»„жҲҗ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пјҢе…¶й—ҙжңүдёҖеҗҚйӘ‘еЈ«е’ҢдёӨеҗҚд№Ўз»…пјҢиҙҹиҙЈеңҹең°еҲҶеүІпјҢ并иЈҒеҶіжүҖжңүзҡ„еҲҶжӯ§гҖӮ
иҝҷд»ҪиҖғеҪӯеә„еӣӯдҪғжҲ·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д№Ұд»ӨдәәеҚ°иұЎж·ұеҲ»пјҢиҝҷдәӣжқ‘ж°‘жӣҫжңүдёӯдё–зәӘ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еҗҲдҪңз”ҹжҙ»зҡ„й•ҝжңҹи®ӯз»ғпјҢжңүзӣёеҪ“зҡ„иҮӘжІ»иғҪеҠӣгҖӮ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дёӯжңүжҳҺзЎ®зҡ„еңҹең°еҲҶеүІеҺҹеҲҷе’Ңе®һж–ҪжӯҘйӘӨпјҢиҝҳжңүдё“дёҡдәәеЈ«е’Ң第дёүж–№дәәеЈ«зҡ„еҸӮдёҺгҖӮеҲҶеүІзҡ„еҺҹеҲҷејәи°ғе…¬жӯЈдёҺжқғеҲ©пјҢдҫӢеҰӮпјҢе°Ҫз®Ўеңҹең°жү“ж•ЈеҗҺйҮҚж–°еҲҶй…ҚпјҢдҪҶжҳҜеҺҹжқҘеңҹең°зҡ„ж•°йҮҸгҖҒиҙЁйҮҸе’ҢдҪҚзҪ®иҰҒе……еҲҶиҖғиҷ‘гҖӮеҸҲеҰӮеҚҸи®®дәәиҙҹиҙЈж”Ҝд»ҳеңҹең°еӢҳжөӢе‘ҳзҡ„жҠҘй…¬пјҢз”ұдәҺеҲҶеҫ—еңҹең°зҡ„ж•°йҮҸе’ҢиҙЁйҮҸдёҚдёҖж ·пјҢжҜҸдәәеҮәиө„дәҰдёҚеҗҢпјҢеҚідҪҝз»ҶиҠӮдёҠд№ҹеҠӣжұӮеҗҲзҗҶгҖӮиҝҳжңүпјҢеңҹең°еӢҳжөӢе’ҢдёҲйҮҸдәәе‘ҳгҖҒиҙҹиҙЈд»ІиЈҒзҡ„дә”дәә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еқҮжқҘиҮӘ第дёүж–№пјҢдё”з”ұдҪғжҲ·е…ұеҗҢжҺЁдёҫдә§з”ҹпјҢд»Ҙдҝқйҡңе…¬е№іе…¬жӯЈ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зү№еҲ«жҸҗеҲ°дәҶеӣ жң¬ж¬ЎеңҲең°еҸҜиғҪеј•иө·зҡ„жҚҹе®іеҸҠиЎҘеҒҝй—®йўҳгҖӮдёҠиҝ°дҪғеҶң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еЁҒдёҒйЎҝпјҲд№Ўз»…пјүеңЁиҖғеҪӯеә„еӣӯжңүдёӘз…ӨзҹҝпјҢеӣ еңҲең°еҸ—еҲ°еҪұе“ҚпјҢеӣ жӯӨиҰҒеҜ№вҖңз…ӨзҹҝеҺҹжңүзҡ„жқғеҲ©е’ҢеҲ©зӣҠвҖқдҪңеҮәиЎҘеҒҝгҖӮеҗҢж—¶иҝҷдҪҚзҹҝдё»жңүд№үеҠЎз»ҷдёӨеҗҚеҺҹзҹҝе·Ҙе®үжҺ’е·ҘдҪңпјҢвҖңеӣ дёә他们еҸҠе…¶зҘ–иҫҲдёҖзӣҙеңЁжӯӨе·ҘдҪңвҖқ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ёҚиғҪеӣ еңҲең°еҪұе“Қеҗ„ж–№жқ‘ж°‘еҺҹжңүзҡ„е…¬е…ұжқғеҲ©пјҢеҢ…жӢ¬вҖңйҮҮжҺҳжқЎзҹіжҲ–зҹіеқ—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д»ҘеҸҠжқ‘民们дҪҝз”Ёе…ұз”ЁйҒ“и·Ҝзҡ„жқғеҲ©вҖқгҖӮиҝҳжңүпјҢвҖңеңЁжұ еЎҳе’ҢжІіжөҒдёҠжё”зҢҺзӯүжқғеҲ©пјҢ继з»ӯжңүж•ҲпјҢдҝқз•ҷз»ҷеҗ„дҪҚжҲҗе‘ҳеҸҠе…¶еҗҺд»ЈвҖқгҖӮиҜҘеҚҸи®®дәҲд»Ҙе…¬зӨәпјҢеңЁеҚҸи®®зӯҫи®ўдёүдёӘеҚҠжңҲеҗҺпјҢеҚіпј‘пј–пј’пјҗе№ҙпј“жңҲпј‘ж—ҘпјҢе…·дҪ“е®һж–ҪдәҶеңҹең°еҲҶеүІе’ҢеӣҙеңҲгҖӮ
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еҸІи®°дёӢдәҶиҝҷдёӘж—ҘеӯҗпјҢи®°дёӢдәҶдёҠиҝ°дҪғжҲ·еҫ—еҲ°зҡ„еңҹең°зҠ¶еҶөе’Ңе…·дҪ“дҪҚзҪ®пј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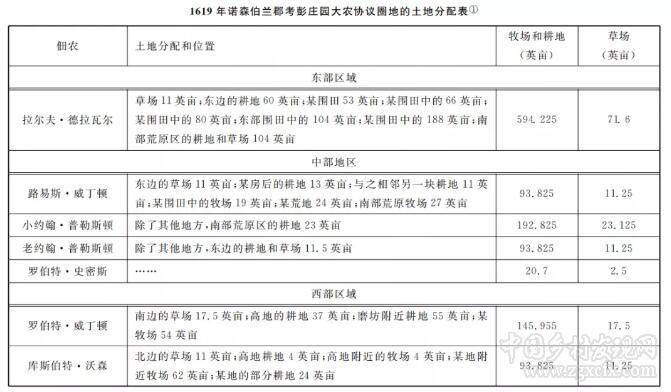
гҖҠ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еҸІгҖӢзј–иҖ…иҜ„д»·иҜҙпјҡвҖңйҖҡиҝҮ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пјҢиҖғеҪӯеә„еӣӯиў«еҲҶеүІжҲҗзӢ¬з«Ӣзҡ„иҖ•дҪңең°еқ—пјҢжҖ»зҡ„зңӢжқҘдёҺд»ҠеӨ©зҡ„еҶңеңәе®Ңе…ЁзӣёеҗҢгҖӮвҖқеңЁдёҖиҲ¬еҶңж°‘дәӨжҚўжқЎз”°гҖҒж•ҙеҗҲең°еқ—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Ө§еҶңдё»еҜјдёӢзҡ„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еӨ§и§„жЁЎең°жӣҙж–°дәҶ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пјҢдҪҝдёӯдё–зәӘж•һз”°еҪ»еә•ж”№еҸҳдәҶйқўиІҢ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Ө§еҶңзҡ„иҝҷзұ»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дёәпј‘пјҳгҖҒпј‘пјҷдё–зәӘжҺЁиЎҢзҡ„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жҸҗдҫӣдәҶе…ҲдҫӢпјҢе®ғ们дёҺеҗҺиҖ…зҡ„зӣёдјјд№ӢеӨ„жҳҜпјҢ延з»ӯе’Ңе°ҠйҮҚд»ҘеҫҖ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’Ңе…¶д»–жқғеҲ©пјҢд»ҘдёҖз§ҚеҘ‘зәҰзҡ„и°Ёж…Һж–№ејҸиҚЎж¶Өж•һз”°еҲ¶еҶңдёҡзҡ„ж—§дҪ“зі»пјӣдёҚеҗҢд№ӢеӨ„жҳҜпјҢвҖңиҝҷз§ҚеңҲең°жҳҜдҪғеҶңиҮӘеҸ‘еҚҸи®®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з«Ӣжі•зҡ„з»“жһңвҖқ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д№ҹдёҚеҸҜе°ҶеӨ§еҶңдё»еҜјдёӢзҡ„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зҗҶжғіеҢ–гҖӮ马дёҒжҢҮеҮәпјҢе°Ҫз®Ў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ҳҜдёӘиҝӣжӯҘпјҢдҪҶеңЁе®һйҷ…иҝҮзЁӢдёӯеҫҖеҫҖдёҚиғҪе®Ңе…Ёе°ҠйҮҚдҪғжҲ·зҡ„еҲ©зӣҠпјҢеҚідҪҝе°ҸдҪғжҲ·дёҚж„ҝеңҲең°д№ҹдёҚеҫ—дёҚеҚ·е…Ҙе…¶дёӯгҖӮжүҖд»Ҙ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д№ҹдёҚиғҪйҒҝе…Қ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并引иө·е°ҸеҶңзҡ„еҸҚжҠ—гҖӮ马дёҒз ”з©¶дә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пј–дёӘеңҲең°жЎҲдҫӢпјҢиҷҪ然йғҪдёә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дҪҶд№ҹеҸ‘з”ҹдәҶеҜ№жҠ—е’Ң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гҖӮ
жңүж—¶пјҢеӨ§еҶңдё»еҜјдёӢзҡ„еңҲең°иҝҳйҒҮеҲ°йўҶдё»зҡ„йҳ»жҢ гҖӮжңҖдёәе…ёеһӢзҡ„жЎҲдҫӢеҸ‘з”ҹеңЁ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пјҲпјЈпҪҒпҪҷпҪ”пҪҲпҪҸпҪ’пҪҗпҪ…пјүпјҢдёҖеҸҚдәә们зҡ„дёҖиҲ¬еҚ°иұЎпјҢ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иҰҒйҳ»еҠӣдёҚжҳҜеҲ«дәәиҖҢжҳҜйўҶдё»гҖӮиҝҷдёӘйўҮе…·з»ҶиҠӮзҡ„еҸІж–ҷпјҢеҮәиҮӘ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дёҖдёӘзӣ®еҮ»иҖ…жүӢзЁҝпјҢзҸҚи—ҸеңЁжһ—иӮҜйғЎеҮҜж–Ҝи’Ӯж–Үж•ҷеҢәпјҲпј«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…пҪ–пҪ…пҪҺпјүжЎЈжЎҲйҰҶпјҢзӣҙеҲ°пј’пјҗдё–зәӘдёӯжңҹжүҚиў«еҸ‘зҺ°гҖӮвҖңиҜҘжүӢзЁҝжҳҜзӢ¬дёҖж— дәҢзҡ„вҖқпјҢи®°еҪ•иҖ…жӢүе°”еӨ«В·ж»•ж–Ҝжүҳе°”ж—¶дёәж•ҷеЈ«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дәІеҺҶиҖ…пјҢз”ҹеҠЁең°еұ•зҺ°дәҶдёүдёӘдё–зәӘеүҚиҜҘж•ҷеҢ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ӣҫжҷҜгҖӮ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жӣҫдёәиҗЁзҰҸе…ӢдјҜзҲөжүҖжңүпјҢдјҜзҲөеӣ йҷ·е…Ҙз»ҸжөҺеӣ°еўғжҖҘдәҺеҮәжүӢеңҹең°пјҢдәҺжҳҜдҪғеҶң们зә·зә·д№°ж–ӯ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еӨ§еҶңжҳҜдё»иҰҒ买家гҖӮеҲ°дәҶпј‘пј–пј•пјҗе№ҙпјҢеә„еӣӯеңҹең°дё»иҰҒз”ұеӨ§е°Ҹ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жүҖж”Ҝй…ҚпјҢдёҖдәӣеӨ§еҶңеҗөзқҖеңҲең°пјҢ他们жҠұжҖЁиҜҙвҖңе®һеңЁеҺҢеҖҰдәҶж— ж•ҲзҺҮзҡ„иҖ•дҪңж–№ејҸпјҢеёҢжңӣж”№иүҜиҮӘе·ұзҡ„еңҹең°вҖқгҖӮиҢ…иҲҚеҶңзӯүе°ҸеҶңжӢ…еҝғе…¬ең°дё§еӨұйҖ жҲҗжҚҹе®іпјҢеҸҜ他们没жңүи¶іеӨҹзҡ„еҠӣйҮҸйҳ»жҢЎпјҢвҖңеҸӘеҫ—жІүй»ҳгҖҒеұҲжңҚвҖқгҖӮеә„еӣӯдё»е°ҸзҲұеҫ·еҚҺеҚҙжҳҺзЎ®ең°еҸҚеҜ№еңҲең°пјҢиЎЁзӨәвҖңеҚідҪҝжүҝеҸ—еҺӢеҠӣд№ҹиҰҒеҸҚеҜ№еңҲең°вҖҰвҖҰдёҺеңҲең°иҖ…зјәе°‘е…ұеҗҢзҡ„жқғзӣҠвҖқгҖӮеӨ§еҶң们дёҚйҖҖи®©пјҢиЈ№жҢҹе°ҸеҶңе’ҢйӣҮе·ҘеҸӮдёҺиҝӣжқҘпјҢеЁҒиғҒйӣҶдҪ“иө·иҜүйўҶдё»пјҢйҖҡиҝҮжі•еҫӢжүӢж®өиҝ«дҪҝйўҶдё»е°ұиҢғгҖӮеӣ дёәвҖң他们预и§ҒеңҲең°иғҪдҪҝеңҲең°иҖ…иҺ·еҫ—иҙўеҜҢе’ҢеЈ°жңӣвҖқпјҢйј“еҠЁж•ҙдёӘжқ‘еә„жүҝжӢ…иҜүи®јиҙ№пјҢе°ҸеҶңе’ҢйӣҮе·Ҙд№ҹиў«иҝ«жҺҸи…°еҢ…пјҢвҖңеӣ дёә他们еҸ—еҲ°еңҲең°иҖ…们иҖізӣ®зҡ„зӣ‘и§ҶпјҢдёҖж—Ұиў«е‘ҠдёҠжі•еәӯпјҢд»Јд»·жӣҙеӨ§гҖӮе°ұиҝҷж ·пјҢжүҖжңүдәәйғҪеҸӮдёҺе…¶дёӯдәҶвҖқгҖӮжҳҫ然еӨ§еҶң们зІҫеҝғзӯ–еҲ’пјҢе№ҝжіӣеҠЁе‘ҳпјҢдҪҝз”ЁдәҶеҗ„з§ҚжүӢж®өгҖӮеңЁејәеӨ§зҡ„ж”»еҠҝдёӢпјҢе№ҙиҪ»зҡ„йўҶдё»еӢүејәеҗҢж„ҸдәҶгҖӮеңЁз»„е»әзҡ„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дёӯпјҢдёҖдәӣд»ЈиЎЁйўҶдё»пјҢдёҖдәӣд»ЈиЎЁжқ‘ж°‘пјҢиҝҳжҢҮе®ҡдәҶеңҹең°и°ғжҹҘе‘ҳпјҢжӢҹеҶҷи§„з« е’ҢжқЎж¬ҫжҢҮеҜјеңҲең°гҖӮеңҹең°иў«дёҲйҮҸеҮәжқҘ并被йҮҚж–°еҲҶеүІпјҢ继иҖҢжҢ–жІҹжё пјҢж ҪзҜұз¬ҶпјҢеңҲең°жңүеәҸең°жҺЁиҝӣгҖӮеҮ е№ҙеҗҺеңҲең°еҹәжң¬е®ҢжҲҗпјҢиҷҪ然жӣҫйҒӯеҲ°йғЁеҲҶдәәзҡ„ејӮи®®иҖҢиў«иө·иҜүпјҢдҪҶжІЎжңүеҪұе“ҚеңҲең°иҝӣзЁӢпјҢеҹәжң¬дёҠжҳҜе№ійқҷ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вҖңеңҲең°е№¶жІЎжңү摧жҜҒеҚЎзҙўжҷ®зҡ„е°Ҹеңҹең°жүҖжңүиҖ…вҖқгҖӮиҝҷжҳҜеӨ§еҶңеңҲең°жІЎжңүеҜјиҮҙ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гҖҒжҲҝеұӢжҜҒеқҸеҸ‘з”ҹзҡ„дёҖдёӘдҫӢиҜҒгҖӮеңЁ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пјҢдёҺеңҲең°еүҚзӣёжҜ”пјҢеңҲең°пјҳе№ҙд№ӢеҗҺпјҢе®…ең°гҖҒжҲҝеұӢе’ҢеҶңиҲҚеҹәжң¬зӣёеҪ“пјҢдҝқз•ҷдёӢжқҘзҡ„пј‘пј–пј–пј•вҖ”пј‘пј–пј–пј–е№ҙзҡ„еЈҒзӮүзЁҺиҜҒе®һдәҶиҝҷдёҖзӮ№гҖӮеңҲең°жІЎжңүеҮҸе°‘жқ‘ж°‘зҡ„ж•°йҮҸпјҢдҪҶиҙ«з©·еұ…ж°‘еӨұеҺ»дәҶеҜ№е…¬ең°е’ҢиҚ’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з”ұдәҺеңҲең°дёӯжқ‘ж°‘д»ҺдјҜзҲөйӮЈйҮҢд№°ж–ӯдәҶд»–зҡ„ең°дә§пјҢе…¶дёӯдёҚе°‘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еӣ жӯӨеҸҳжҲҗдәҶ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пјҢд№°ж–ӯеҗҺзҡ„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еҮ иҝ‘з§Ғдәәең°дә§гҖӮ
д»ҘдёҠпјҢжҲ‘们зңӢеҲ°дәҶ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йҖҡеёёжЁЎејҸгҖӮиҙ§еёҒиөҺд№°гҖҒдә§жқғдәӨжҚўе’ҢеҚҸе•ҶзӯүпјҢжҳҫ然жҳҜ他们з»ҸеёёдҪҝз”Ёзҡ„жүӢж®өпјҢз”ұдәҺ他们зҡ„иҙўеҜҢе®һеҠӣпјҢд№ҹз”ұдәҺдёәиҝҪжұӮжӣҙеӨ§зҡ„еҲ©ж¶ҰпјҢжүҖд»ҘдёәиҫҫеҲ°еңҲеҚ еңҹең°зӣ®зҡ„еҫҖеҫҖдёҚжғңдёҖжҺ·еҚғйҮ‘гҖӮеҖҳиӢҘз§ҹзәҰ规е®ҡзҡ„з§ҹжңҹжңӘеҲ°пјҢ他们еҫҲе°‘ејәиЎҢиҝҗдҪңпјҢеӨ§жҰӮд№ҹжІЎжңүејәеҲ¶иЎҢдёәзҡ„иғҪеҠӣпјҢеӣ дёә他们жң¬иә«д№ҹжҳҜдҪғжҲ·пјҢжҳҜзЁјз©‘з”°й—ҙгҖҒеҘ”иө°еёӮеңәзҡ„ж–°е…ҙ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иҮіе°‘дёҠдёҖдёӨд»ЈдәәиҝҳжҳҜжҷ®йҖҡдҪғеҶңз”ҡиҮіжҳҜдёҖдёӘеҶңеҘҙгҖӮдёҺйўҶдё»зҡ„е…ізі»д№ҹжҳҜиҝҷж ·пјҢеңҲең°е°ҪйҮҸеҸ–еҫ—йўҶдё»зҡ„еҗҢж„ҸпјҢд»Ҙз¬ҰеҗҲжі•еҫӢзЁӢеәҸгҖӮдёҠйқў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жЎҲдҫӢдёӯпјҢеӨ§еҶңе·Із»Ҹе®Ңе…ЁжҺ§еҲ¶дәҶжқ‘еә„еұҖйқўпјҢеҸҜд»ҘйҮҮз”Ёз§Қз§ҚжүӢж®өеҗ‘йўҶдё»ж–ҪеҺӢпјҢ然иҖҢ他们иҝҳжҳҜеңЁ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еҗҺжүҚиЎҢеҠЁпјҢд»ҘеҸ–еҫ—еңҲең°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гҖӮ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пјҢеӨ§еҶңеңҲең°жҳҜжңҖеқҡе®ҡзҡ„гҖӮ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жҳҜеҜҢиЈ•дҪғеҶңеҗҜеҠЁзҡ„пјҢ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жҳҜиҝҷз§Қ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еӣ жӯӨзҗҶеә”жҲҗдёә他们зҡ„з§ҜжһҒйҖүйЎ№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и®ІпјҢеӨ§еҶң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Ҹ‘иө·дәәпјҢж—ўз¬ҰеҗҲеҺҶеҸІйҖ»иҫ‘д№ҹжҳҜеҺҶеҸІдәӢе®һгҖӮеҚЎзҙўжҷ®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Ү з»ҸеҠқеҜјжүҚеҗҢж„ҸеңҲең°пјҢе…¶жҜҚеҜ№дёҖдҪҚең°дә§е§”жүҳдәә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е°Ҫз®Ўиҝҷз§Қж”№е–„жҺӘж–ҪдёҚиғҪеёҰжқҘеӨҡеӨ§еҘҪеӨ„пјҢдҪҶз»Ҳ究жҳҜдёҖз§Қж”№е–„гҖӮвҖқжӯӨиҜқйўҮжңүеҮ еҲҶеӢүејәзҡ„е‘ійҒ“пјҢжҳҫ然пјҢеңҲең°жҺЁиҝӣзҡ„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ж–№ејҸ并дёҚжҳҜдј з»ҹйўҶдё»жүҖзҶҹжӮү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他们жғіиҰҒ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Ң他们已жҳҜй«ҳй«ҳеңЁдёҠзҡ„иҙөж—ҸпјҢе®ҲжҲҗжүҚжҳҜгҖӮеҪ“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еҶңжқ‘жҲҗдёәдёҚеҸҜйҖҶиҪ¬д№ӢеҠҝзҡ„жғ…еҪўдёӢпјҢйўҶдё»дёҚиҝҮжҳҜйҖјдёҠвҖңиҙјиҲ№вҖқпјҢдёҚеҫ—е·ІиҖҢдёәд№ӢпјӣиҖҢеҜҢиЈ•еӨ§еҶңжүҚ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Җеқҡе®ҡзҡ„жҺЁеҠЁиҖ…гҖӮиӢұеӣҪеӯҰиҖ…пјӘВ·жғ зү№е°”д№ҹжҢҒзӣёдјјзңӢжі•гҖӮпј©В·жІғеӢ’ж–ҜеқҰжҢҮеҮәпјҢеңЁ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жңүдёӨз§Қзұ»еһӢ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дёәдәҶжңүж•ҲиҖ•дҪңиҖҢеҗҲ并е°Ҹ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йӮЈз§Қзұ»еһӢзҡ„еңҲең°дёӯпјҢвҖңзәҰжӣјеҶңжү®жј”дәҶдё»и§’вҖқгҖӮе…¶е®һпјҢеӨ§еҶңеІӮжӯўеңЁдёҖз§Қзұ»еһӢзҡ„еңҲең°иҝҮзЁӢдёӯжү®жј”дё»и§’пјҹеңЁдёӨз§Қз»ҸжөҺе’ҢзӨҫдјҡжЁЎејҸи·Ёж—¶д»Јзҡ„дәӨжӣҝдёӯпј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жү®жј”дё»и§’йЎәзҗҶжҲҗз« гҖӮ
пј”пјҺ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жҳҜеңҲең°дё»еҠӣ
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еҮ дҪ•пјҹеӯҰз•ҢиҷҪ然жҷ®йҒҚи®ӨеҗҢеӨ§еҶңеңҲең°пјҢ然иҖҢ他们зҡ„еңҲең°еҚ еӨҡеӨ§жҜ”дҫӢеҚҙйҡҫд»Ҙеҫ—еҲ°зЎ®еҲҮзҡ„ж•°жҚ®гҖӮзҝ»ејҖе…ідәҺ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зҡ„еҺҶеҸІж–ҮзҢ®пјҢ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зҡ„еҸІж–ҷеҸҜдҝЎжүӢжӢҲжқҘпјҢеҸҜжҳҜжІЎжңүеҸ‘зҺ°жңүиҜҙжңҚеҠӣзҡ„жҷ®йҒҚж•°жҚ®гҖӮпј‘пјҷ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й—®дё–зҡ„еҲ©иҫҫе§Ҷзҡ„гҖҠеңҲең°жң«ж—Ҙе®ЎеҲӨгҖӢпјҢж•ҙзҗҶ并еҲҶжһҗдәҶ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е’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зҡ„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пјҢи®Өдёә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жңү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е’ҢеӨ§еҶңзӯүе…¶д»–йҳ¶еұӮ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еҸҜжҳҜе®ғз»ҷеҮәзҡ„ж•°жҚ®иҝҮдәҺйӣ¶зўҺпјҢйҡҫд»Ҙеҫ—еҮәдёҖдёӘж•ҙдҪ“жҰӮеҝөгҖӮжҜ”еҰӮеңЁеү‘жЎҘйғЎгҖҒж јжҙӣж–Ҝзү№йғЎзӯү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иҫғй«ҳпјҢиҖҢеҸҰеӨ–дёҖдәӣең°еҢәдҪғеҶңеңЁеңҲең°дёӯиө·еҲ°зҡ„дҪңз”ЁиҫғеӨ§гҖӮеҰӮеңЁдјҜе…ӢйғЎпјҢ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иҮі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й—ҙеҶңж°‘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дҪ“пјҢеҢ…жӢ¬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гҖҒ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гҖҒ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зӯүпјҢиҖҢ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д»…еҚ иҜҘйғЎеңҲ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пјҷпјҺпј–пј…гҖӮеҲ©иҫҫе§ҶгҖҠеңҲең°жң«ж—Ҙе®ЎеҲӨгҖӢ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жҳҜпјҢе…¶ж•°жҚ®еҲҶжһҗиҢғеӣҙжңүиҫғеӨ§еұҖйҷҗжҖ§пјҢдёҚиғҪиҰҶзӣ–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иҰҒзҡ„ж—¶й—ҙз»ҙеәҰгҖӮ
пј¬пјҺпјЎпјҺеё•е…Ӣе…ідәҺ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пјҚ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й—ҙ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җ„зӨҫдјҡйҳ¶еұӮзҡ„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еҖјеҫ—е…іжіЁгҖӮе…¶дёҖпјҢеңЁ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дёҠпјҢд»–еҸӮиҖғдәҶеҪ“е№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зҡ„жҠҘе‘ҠдҪҶжҳҜжІЎжңүе®Ңе…Ёдҫқиө–е®ғпјҢеё•е…ӢејҖиҫҹдәҶиҮӘе·ұзҡ„еҸІж–ҷжқҘжәҗпјҢиҖҢдё”д»Һж—¶ж®өдёҠеҹәжң¬иҰҶзӣ–дәҶиҝҷж¬ЎеңҲең°зҡ„ж—¶й—ҙз»ҙеәҰпјҢеҚід»Һ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иҮі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гҖӮе…¶дәҢпјҢеё•е…ӢйҮҮеҸ–дәҶе…ёеһӢеҸ–ж ·зҡ„ж–№жі•пјҢжүҖйҖ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дҪҚдәҺзұіеҫ·е…°е№іеҺҹдёӯеҚ—йғЁпјҢжҳҜиҝҷж¬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йҮҚзӮ№еҢәеҹҹпјҢ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д»ЈиЎЁжҖ§гҖӮд»–е°ҶеңҲең°еҲҶдёәдёӨдёӘйҳ¶ж®өпјҢ第дёҖдёӘйҳ¶ж®ө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иҮі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җе№ҙпјҢжҖ»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иҫҫеҲ°пј‘пј“пјҳпј‘пј’иӢұдә©пјҢе…¶дёӯжңүеӣҪзҺӢгҖҒдё–дҝ—иҙөж—Ҹ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пјҢиҝҳжңүж•ҷдјҡйўҶдё»еҚідҝ®йҒ“йҷўеңҲең°пјҢ然иҖҢжІЎжңүдёҖиҲ¬еҶңж°‘зҡ„йӣ¶зўҺеңҲең°зҡ„з»ҹи®ЎпјҢиҝҷжҳҜдёӘз–ҸжјҸпјҢеӨ§жҰӮеҸ—еҲ°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зҡ„еұҖйҷҗгҖӮд№Ўз»…еңҲ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йҮҚжңҖй«ҳпјҢиҫҫпј•пјҳпјҺпј”пј…пјҢиҖғиҷ‘з»ҹи®Ўдёӯиә«д»ҪдёҚжҳҺиҖ…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зҡ„еӣ зҙ пјҢдёӯзӯү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иҫҫеҲ°пј–пјҗпј…е·ҰеҸіеә”иҜҘ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й—®йўҳгҖӮеҸӮи§ҒдёӢиЎЁпјҡ

еңЁз¬¬дәҢдёӘйҳ¶ж®өеҚі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‘иҮі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й—ҙпјҢз»ҹи®Ўдёӯзҡ„зӨҫдјҡиә«д»ҪеўһеҠ дәҶеҶңж°‘пјҲпј°пҪ…пҪҒпҪ“пҪҒпҪҺпҪ”пҪ’пҪҷпјүе’Ңе•ҶдәәпјҢеҺ»жҺүдәҶеӣҪзҺӢе’Ңж•ҷдјҡ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гҖӮиҜҘж—¶ж®өеңҲең°еўһеҠ еҶңж°‘е’Ңе•ҶдәәпјҢиЎЁжҳҺеңҲең°еҠӣйҮҸз»„жҲҗзҡ„ж–°еҸҳеҢ–пјӣеҺ»жҺүж•ҷдјҡйўҶдё»д№ҹжҳҜжңүж №жҚ®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иҝҷдёӘйҳ¶ж®өдҝ®йҒ“йҷўиў«ејәд»Өи§Јж•ЈпјҢең°дә§жӮүж•°жӢҚеҚ–гҖӮжӢҚеҚ–еңҹең°еӨ§йғЁеҲҶжөҒе…ҘдәҶзәҰжӣјгҖҒд№Ўз»…жүӢйҮҢпјҢеҗҺиҖ…жңҖжёҙжңӣеҫ—еҲ°еңҹең°дё”иҙӯд№°еҠӣж—әзӣӣпјҢиҖҢйўҶдё»е°Өе…¶ж•ҷдјҡйўҶдё»иҝӣдёҖжӯҘеҸ—еҲ°йҮҚеҲӣгҖӮеӣ жӯӨеңЁиҝҷдёҖж—¶ж®ө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и¶ҠжқҘи¶Ҡй«ҳжҳҜйў„ж–ҷд№Ӣдёӯзҡ„гҖӮдёҚиҝҮзҺӢе®ӨйўҶең°жІЎжңүеңҲең°зҡ„и®°еҪ•дјјдёҚеә”иҜҘпјҢд№ҹи®ёеҪ’зұ»дәҺиҙөж—ҸжҲ–жҳҜеҸ—еҲ°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зҡ„йҷҗеҲ¶гҖӮдҪңиҖ…жүҝи®Өд»–зҡ„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еҸ—еҲ°дёҖе®ҡйҷҗеҲ¶пјҢдҫӢеҰӮеҜ№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жқ‘иҗҪеңҲең°зҡ„з»ҹи®Ўд»–еҸӘиғҪиҰҶзӣ–зҷҫеҲҶд№Ӣе…ӯеҚҒдёғгҖӮ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пјҢеё•е…ӢеҜ№иҝҷдёҖж—¶ж®өеңҲең°иҖ…зҡ„жҲҗеҲҶиҝҳжҳҜжҸҗдҫӣдәҶзӣёеҜ№е®Ңж•ҙ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ҡд№Ўз»…еңҲең°еҚ пј—пј’пјҺпј•пј…пјҢеҶҚеҠ дёҠе•Ҷдәәзҡ„пјҢд№Ўжқ‘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еңҲең°иҫҫеҲ°пј—пјҷпј…пјҢеҚ жҚ®з»қеҜ№дјҳеҠҝпјҢдёҺеүҚдёҖйҳ¶ж®өжҜ”иҫғеӨ§зәҰеўһеҠ дәҶпј’пјҗ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иҖ…дёӯиӮҜе®ҡеҢ…еҗ«дёҖйғЁеҲҶеӨ§еҶңпјҢиҝҷйҮҢиҝҳжІЎжңүи®Ўз®—еңЁеҶ…пјҢ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пјҢиҝҷдёҖйҳ¶еұӮжҲҗдёәеңҲең°дё»еҠӣж„ҲеҸ‘жҳҺжҳҫпјҢжҳҜжІЎжңүз–‘д№үзҡ„гҖӮ

жҲ‘们иҝҳеҸҜд»Ҙеј•иҜҒдёӯйғЁең°еҢәзҷҪйҮ‘жұүйғЎзҡ„зӣёе…іж•°жҚ®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иҜҙжҳҺдёӯй—ҙйҳ¶еұӮеңЁ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зҷҪйҮ‘жұүйғЎзӣёи·қиҺұж–Ҝзү№дёҚиҝңпјҢжүҖеңҲеңҹең°еӨ§йғЁеҲҶ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дёҖиҲ¬иҜҙжқҘйўҶдё»жҺҢжҺ§зҡ„еңҹең°и§„жЁЎиҫғеӨ§пјҢжӣҙе®№жҳ“иҪ¬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иҝҷйҮҢзҡ„еңҲең°иҖ…жҳҜеҗҰеӨҡдёәйўҶдё»е‘ўпјҹ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жҳҫзӨәпјҢ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иҮі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й—ҙпјҢиҜҘйғЎ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зЎ®еҚ жҚ®дәҶзӣёеҪ“еӨ§зҡ„жҜ”дҫӢпјҢиҫҫеҲ°еңҲ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пј”пј•пјҺпј–пј…пјҢ然иҖҢе…¶дҪҷзҡҶдёәеҶңж°‘еӣҙеңҲпјҢеҗҺиҖ…жүҚ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дҪ“пјҢеҢ…жӢ¬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гҖҒ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пјҲеҗ«з§ҹең°еҶңеңәдё»пјүе’Ң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пјҢе…¶дёӯ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еңҲең°жңҖеӨҡпјҢеҚ иҜҘйғЎеңҲ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пј“пј‘пјҺпјҗпј…гҖӮиҝҷж ·зҡ„еҸІдҫӢиҝҳиғҪеј•иҜҒеҫҲеӨҡпјҢд№ҹдјҡжңүзӣёеҸҚзҡ„дҫӢиҜҒпјҢе…¶зјәйҷ·жҳҜдёҚиғҪиҜҙжҳҺй•ҝж—¶ж®өзҡ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гҖӮиҖҢеё•е…Ӣж•°жҚ®жҳҜй•ҝж—¶ж®өзҡ„пјҲд»Һ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•иҮі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пјүпјҢиҖҢдё”иҺұж–Ҝзү№ең°еӨ„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йҮҚзӮ№ең°еҢәпјҢи¶ід»Ҙз»ҷдәә们жҸҗдҫӣдёҖдёӘжңүд»·еҖјзҡ„еҸӮиҖғж•°жҚ®пјҢеҶҚеҠ еүҚйқўзҡ„йҳ¶ж®өжҖ§ж•°жҚ®е’ҢдёҖзі»еҲ—зҡ„дёӘжЎҲеҲҶжһҗпјҢеҰӮжһңжҲ‘们иҜҙеңЁж•ҙдёӘ延й•ҝзҡ„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пјҲж¶өзӣ–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иҮіпј‘пј—дё–зәӘж—©жңҹпјүпјҢд№Ўз»…е’ҢеӨ§еҶңзӯүеҶңдёҡиө„дә§йҳ¶зә§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пјҢиҝҷдёӘз»“и®әеә”иҜҘжҳҜеҸҜд»ҘжҲҗз«Ӣзҡ„гҖӮ
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җҢж ·жңү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пјҢжҚҹе®ідҪғеҶңзҫӨдҪ“еҲ©зӣҠеӣ иҖҢеҸ—еҲ°и°ҙиҙЈе’ҢжҠөжҠ—гҖӮеңЁеҫ·жҜ”йғЎзҡ„иҙқе…ӢеЁҒ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ҒпҪӢпҪ…пҪ—пҪ…пҪҢпҪҢпјүпјҢд№Ўз»…зәҰзҝ°В·еӨҸжҷ®йҮҮз”Ё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–№ејҸжү©еұ•дҝқжңүең°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’е№ҙзҡ„зұіиҝҰеӢ’иҠӮпјҢиҜҘеә„еӣӯеҲ‘дәӢжі•еәӯпјҲпҪғ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 пҪҢпҪ…пҪ…пҪ”пјүе’Ңе°ҒиҮЈжі•еәӯжҺЁдёҫпј‘пј“еҗҚдҪғжҲ·з»„жҲҗйҷӘе®Ўеӣўе®ЎзҗҶжӯӨжЎҲпјҢйҷӘе®Ўеӣўи®ӨдёәеӨҸжҷ®йқһжі•еңҲеӣҙдәҶдёӨеӨ„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пјҢд»ҘеҸҠиӢҘе№ІдҪғеҶңзҡ„дҝқжңүең°пјҢз”ҡиҮіиҝҳйқһжі•еңҲеҚ дәҶеҸҰдёҖдёӘд№Ўз»…д№”жІ»В·еј—еҶң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гҖӮиҝҳжңүпјҢеӨҸжҷ®иў«жҢҮжҺ§еңҲеӣҙдәҶйғЁеҲҶеӣҪзҺӢеӨ§йҒ“вҖ”вҖ”вҖ”д»Һзҡ®е…ӢеҹҺе ЎеҲ°еҫ·жҜ”йғЎгҖӮиҝҷдәӣиЎҢдёәжҳҫ然вҖңиҝқеҸҚдәҶиҜҘеә„еӣӯзҡ„жі•еҫӢе’Ңд№ дҝ—вҖқгҖ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дёӢиҫҫдәҶжӢҶйҷӨеңҲең°гҖҒжҒўеӨҚ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е’ҢеӣҪзҺӢеӨ§йҒ“зҡ„е‘Ҫд»ӨпјҢеӨҸжҷ®жӢ’з»қжү§иЎҢпјҢз»“жһңйҷӘе®Ўе‘ҳ们ејәиЎҢжҺЁеҖ’еӣҙзҜұ并йҮҚж–°жү“йҖҡеӣҪзҺӢеӨ§йҒ“гҖӮ然иҖҢпјҢеӨҸжҷ®жІЎжңүе°ұжӯӨж”ҫејғдҫөеҚ е…¬ең°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•е№ҙпјҢд»–еҶҚж¬Ўиў«жҺ§вҖңжҡҙеҠӣвҖқеңҲеӣҙпј“пјҗиӢұдә©иҚ’ең°пјҢдҫөе®іиҜҘеә„еӣӯдҪғеҶң们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дҪғеҶң们д№ҹжІЎжңүеҒңжӯўеҜ№еӨҸжҷ®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ҠөжҠ—гҖӮ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пјҲпјіпҪ”пҪҒпҪ’ пјЈпҪҲпҪҒпҪҚпҪӮпҪ…пҪ’пјүзҡ„дёҖжЎ©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дёҖдәӣдҪғеҶңеқҡз§°ж ‘зҜұеҰЁзўҚдәҶ他们дёҖзӣҙжӢҘжңү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жүҖд»ҘжҚЈжҜҒд»–зҡ„еңҲең°е№¶еңЁйӮЈйҮҢ继з»ӯж”ҫзү§зүІз•ңгҖӮеӨ§еҶңеңҲең°иЎҢдёәйҒӯйҒҮжҡҙеҠӣжҠөжҠ—пјҢд№ҹеҸ‘з”ҹеңЁзҷҪйҮ‘жұүйғЎзҡ„еҹҺй•ҮеЁҒ科е§ҶпјҲпј·пҪҷпҪғпҪҸпҪҚпҪӮпҪ…пјүгҖӮзәҰжӣјеӨ§еҶңзәҰзҝ°В·еҠідјҰж–ҜеӣҙеңҲдәҶ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пјҢеӣӣе‘Ёж ‘зҜұжҢ–жІҹпјҢе°Ҷе…¶еҸҳдёәд»–дёҖдәәзҡ„дё“еұһзү§еңәпјҢиҖҢжҢү照规е®ҡпјҢдёҖж—Ұи°·зү©ж”¶еүІд»ҘеҗҺеҹҺй•Үеұ…ж°‘жңүжқғеңЁжӯӨж”ҫзү§пјҢжүҖд»ҘзәҰжӣјеҠідјҰж–Ҝе№ҝеҸ—иҜҹз—…гҖӮйўҶдё»жё©иҺҺзҲөеЈ«гҖҒеҸёзҘӯй•ҝе’Ң管家еҜҹзңӢдәҶзҺ°еңәпјҢе‘Ҫд»ӨеҠідјҰж–ҜжӢҶйҷӨеңҲең°зҡ„еӣҙж ҸгҖӮеҠідјҰж–ҜеҸЈеӨҙзӯ”еә”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继з»ӯйҳ»жҢ еҹҺй•Үеұ…ж°‘ж”ҫзү§пјҢдҫөиўӯе’Ңй©ұйҖҗж”ҫзү§дәәгҖҒжүЈжҠјиҝӣе…ҘеңҲең°зҡ„зүІз•ңзӯүгҖӮз»“жһңпјҢеңЁеёӮж”ҝеҪ“еұҖйј“еҠЁдёӢпјҢеұ…民们ејәиЎҢз Қж–ӯгҖҒзғ§жҜҒеңҲең°зҡ„ж ‘зҜұпјҢ并继з»ӯеңЁеҠідјҰж–Ҝзҡ„еңҹең°дёҠж”ҫзү§гҖӮеҸҜи§ҒеңҲең°зҡ„иҝҮзЁӢжҳҜжӣІжҠҳзҡ„пјҢеӨ§еҶңеҚ•ж–№йқўеңҲең°еҫҖеҫҖеҫҲйҡҫиҫҫеҲ°зӣ®зҡ„гҖӮ
еӨ§еҶңеңҲең°з”ҡиҮідјҡеҜјиҮҙжҝҖзғҲеҶІзӘҒе’Ң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гҖӮ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е’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№ӢдәӨзҡ„дёҖд»Ҫ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е‘ҠиҜүжҲ‘们пјҢеңЁзҷҪйҮ‘жұүйғЎзҡ„еҚҡеҫ—ж–Ҝ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үпҪ’пҪ„пҪ“пҪ”пҪҒпҪҺпҪ…пјүпјҢдёҖдёӘ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еңҲеҚ дәҶпј”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еҜјиҮҙпј”еә§жҲҝеұӢиў«жҺЁеҖ’пјҢпј–пјҗдәәиў«й©ұйҖҗеҮә家еӣӯпјҢд»ҺеүҚйңҖиҰҒпјҳйғЁиҖ•зҠҒ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зҺ°еңЁе®Ңе…ЁеҸҳжҲҗдәҶе…»зҫҠзҡ„зү§еңәгҖӮеүҚйқўжҸҗеҸҠзҡ„дјҰж•Ұе•ҶдәәеӨёе°”ж–ҜеңҲең°пјҢдҪҝжқ‘еә„дәәж•°дёӢйҷҚдәҶдёҖеҚҠпјҢеӣ жӯӨеј•иө·дёҖеңәдёҚе°Ҹзҡ„жҡҙеҠЁгҖӮ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пјҢдёҚж»ЎеҶңж°‘иҒҡйӣҶеңЁеӨёе°”ж–ҜжүҖеңЁзҡ„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еә„еӣӯпјҢиҜҘеә„еӣӯдёҖеәҰжҲҗдёә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иө·д№үеҶңж°‘зҡ„иҒҡйӣҶзӮ№гҖӮеңЁйӮЈйҮҢвҖңжұҮйӣҶзҡ„з”·дәәгҖҒеҘідәәд»ҘеҸҠеӯ©з«Ҙзҡ„дәәж•°иҫҫеҲ°пј•пјҗпјҗпјҗдәәвҖқпјҢ他们жҺЁеҖ’дәҶдёҖйғЁеҲҶеңҲең°зҜұз¬ҶгҖӮиҝҷдәӣиЎҢдёәеј•иө·дә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®ҳе‘ҳзҡ„е…іжіЁпјҢжӢ…еҝғеј•иө·жӣҙе№ҝжіӣзҡ„жІ»е®үй—®йўҳпјҢдәҺжҳҜеңЁпј–жңҲпј–ж—Ҙз«–иө·дәҶдёҖдёӘз»һеҲ‘жһ¶пјҢз”Ёд»ҘиӯҰзӨәйӮЈдәӣдёҫдәӢзҡ„дәә们гҖӮиҝҷдёӘз»һеҲ‘жһ¶еңЁпј–жңҲпјҳж—Ҙиў«ж„ӨжҖ’зҡ„дәәзҫӨжҺЁзҝ»пјҢдёҚиҝҮжІЎеҸ‘з”ҹиҝӣдёҖжӯҘзҡ„йӘҡеҠЁгҖӮиҜҘ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дёҖдәӣд№Ўз»…гҖҒе•Ҷдәәе’ҢеӨ§еҶңпјҢеңҲең°дёӯжҡҙйңІеҮәзҡ„иҙӘе©Әе’ҢеҶ·й…·дёҺ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ж— ејӮпјҢеҗҢж ·йҒӯеҲ°ж„ӨжҖ’е°ҸеҶңзҡ„еҸҚжҠ—гҖӮ
еӣӣгҖҒйўҶдё»еҮӯжҚ®д»Җд№ҲеңҲең°пјҹ
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”ҡиҮі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зҡ„дёҖдёӘе…ёеһӢз”»йқўпјҢд№ҹжҳҜйҮҚиҰҒзҡ„еҸІе®һгҖӮй—®йўҳжҳҜпјҢйўҶдё»еҮӯжҚ®д»Җд№ҲеңҲең°пјҹеңЁ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жңүеӨҡеӨ§жҜ”дҫӢзҡ„дҪғеҶңиў«й©ұйҖҗпјҢеҗҲжі•иҝҳжҳҜйқһжі•пјҢеңҲең°дёӯжҡҙеҠӣжҲҗеҲҶеҮ дҪ•пјҹ
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жҳҜдёӯдё–зәӘйғҪеҫҲе°‘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жӯӨж—¶еҸ‘з”ҹдәҶпјҹдёҖдёӘжһҒе…¶йҮҚиҰҒзҡ„еҺҶеҸІеүҚжҸҗжҳҜпјҢеңҹең°е’Ңең°з§ҹе·Із»Ҹе•ҶдёҡеҢ–жҲ–жӯЈеңЁе•ҶдёҡеҢ–пјҢдҪғжҲ·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и¶ҠжқҘи¶Ҡиў«жё…жҷ°ең°з•Ңе®ҡиҖҢе…·жңүж—¶ж•ҲжҖ§пјҢжүҖд»ҘеҮӯжҚ®еҘ‘зәҰ规е®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—¶й—ҙиҠӮзӮ№пјҢжҲҗдёә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йҖ”еҫ„гҖӮ
пј‘пјҺ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
жүҖи°“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пјҢеҚі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зҡ„ж—¶ж•ҲжҖ§еңҲеҚ еңҹең°гҖӮдҪғеҶңеҜ№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дё–иўӯеҚ жңүпјҢжӣҫжҳҜ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йҮҚиҰҒеҺҹеҲҷпјҢеҸҜеҲ°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пјҢдҪғеҶңдёҺйўҶдё»зҡ„дҫқйҷ„е…ізі»и§ЈдҪ“пјҢе°Ғе»әдҝқжңүең°жҖ§иҙЁд№ҹйҡҸд№ӢеҸ‘з”ҹиң•еҸҳпјҢеңҹең°дёҚеҶҚжҳҜж”ҝжІ»е…ізі»зҡ„зәҪеёҰпјҢиҖҢжҳҜдә§жқғжҳҺзЎ®зҡ„еҸҜиҪ¬з§»зҡ„е•Ҷе“Ғпј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—¶ж•ҲжҖ§жҲҗдёә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зҡ„жҷ®йҒҚ规еҲҷгҖӮдёҖж—Ұз§ҹзәҰжңҹж»ЎпјҢең°дә§дё»еҸҜд»ҘдёҺдҪғжҲ·е•Ҷи®®з»ӯзәҰ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и®©еңҹең°еӣһеҲ°иҮӘе·ұжүӢйҮҢпјҢжҲ–еҮәеҚ–жҲ–иҪ¬з§ҹжҲ–еңҲең°пјҢе…ЁеҮӯиҮӘе·ұеӨ„зҗҶпјҢдёҚиҝқеҸҚ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жі•пјҢд№ҹдёҚиҝқеҸҚжҷ®йҖҡжі•гҖӮ
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иҝҷйҮҢзҡ„еҘ‘зәҰжҳҜе…ідәҺеңҹең°зҡ„规е®ҡ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дәәзҡ„иә«д»Ҫзҡ„规е®ҡпјҢе°ұдҫқйҷ„е…ізі»зҡ„и§Јж”ҫиҖҢиЁҖпјҢжӯӨж—¶з”ҹдә§иҖ…еҹәжң¬йғҪжҳҜиҮӘз”ұдәәгҖӮдёҖ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еҪ’еұһе’ҢеңҲеҚ пјҢдё»иҰҒеҸ–еҶідәҺеңҹең°зҡ„еҘ‘зәҰпјҢиҖҢдёҚеҸ–еҶідәҺд»–жҳҜе“ӘдёҖзұ»зҡ„дҪғеҶң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ж„Ҹд№үдёҠи®ІпјҢдёҖдёӘз»Ҳиә«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дёҺдёҖдёӘпј“пјҗе№ҙз§ҹжңҹ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жІЎжңүеӨҡе°‘еҢәеҲ«гҖӮеңЁе®һйҷ…з”ҹжҙ»дёӯпјҢеҚідҪҝдёҖдёӘ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Ҷңд№ҹеҸҜиғҪеҗҢж—¶жҢҒжңүдёҖеқ—е…¬з°ҝдҝқжңүең°пјҢжҲ–жҢүз…§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жқЎд»¶жүҝз§ҹзӣҙйўҶең°е’ҢиҚ’ең°гҖӮеңЁдёҚеҗҢзұ»еһӢеңҹең°дёҠпјҢд»–зҡ„жі•еҫӢжқғзӣҠжҳҜдёҚдёҖж ·зҡ„пјҡеҰӮжһңд»–жҢҒжңүдёҖеқ—жңү继жүҝжқғзҡ„е…¬з°ҝең°пјҢеңҹең°еә”иҜҘжҳҜе®үе…Ёзҡ„пјҢ然иҖҢиҝҷз§Қжі•еҫӢдҝқйҡңд»…д»…йҷҗдәҺ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дёҠпјҢеҚід»–еңЁе…¬з°ҝең°дёҠдә«жңүзҡ„жқғеҲ©дёҚиғҪйҒҝе…Қд»–еңЁ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ң°дёҠ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Құйҷ©гҖӮ欧жҙІеҺҶеҸІеӯҰ家常常жҠұжҖЁ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дёӯдҪғжҲ·иә«д»ҪжЁЎзіҠдёҚжё…пјҢеҺҹеӣ еҚіеңЁдәҺжӯӨпјҢеңЁ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дёҠжҳҜе®үе…Ёзҡ„пјҢеңЁйӮЈеқ—еңҹең°дёҠдёҚжҳҜе®үе…Ёзҡ„пјҢ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Құйҷ©жқҘиҮӘеңҹең°зҡ„жҖ§иҙЁиҖҢдёҚжҳҜжҢҒжңүдәәзҡ„иә«д»ҪгҖӮеҰӮжһң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д»Һ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ң°дёҠиў«й©ұйҖҗдәҶпјҢе®Ңе…ЁжҳҜеӣ дёә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зҡ„жҖ§иҙЁгҖӮ
жҢүз…§еҘ‘зәҰ规е®ҡпјҢж„Ҹж„ҝең°д»»еҮӯйўҶдё»йҡҸ时收еӣһпјҢйҖҡеёёжҸҗеүҚеҚҠе№ҙзҹҘдјҡпјҢдёҖиҲ¬жғ…еҶөдёӢд№ҹдёҚдјҡеҸ‘з”ҹд»Җд№ҲеҶІзӘҒпјҢжүҳе°ји®Өдёәз”ҡиҮіжІЎжңүеҝ…иҰҒдёҫдҫӢжқҘиҜҒжҳҺ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ҳе№ҙпјҢеңЁеӨҡз©Ҷе°”зҝ°еә„еӣӯпјҲпјӨпҪҸпҪҚпҪ…пҪ’пјҚ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пјҢйўҶдё»е°Ҷеә„еӣӯеңҹең°иҪ¬з§ҹз»ҷдёүдҪҚеӨ§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иҜҘжЎҲдҫӢдёӯзҡ„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ҶңеҸӘеҫ—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ҢвҖң他们仅仅жҳҜи№І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еҰӮд»ҘеҫҖйӮЈж ·й»ҳй»ҳзҡ„жүҝеҸ—зқҖвҖқгҖӮеҸҰ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еҸ‘з”ҹеңЁеҘҲ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«пҪҺпҪҷпҪҮпҪҲ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”е№ҙпјҢиҝҷдёӘеә„еӣӯж•ҙдҪ“еҮәз§ҹз»ҷдёҖдҪҚ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иҪ¬з§ҹдёӯж¶үеҸҠпј–дҪҚ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ҶңеҸҜиғҪиў«й©ұйҖҗгҖӮе…ідәҺжҳҜеҗҰйҒӯйҒҮжҠөжҠ—пјҢйўҶдё»дјјд№ҺиғёжңүжҲҗз«№пјҢд»–иҜҙеҸӘйңҖдёҖеҸҘиҜқдҫҝи¶іеӨҹдәҶпјҢ他们жҳҜвҖңд»–зҡ„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дҪғеҶңвҖқпјҲпҪӮпҪ•пҪ” пҪҲпҪүпҪ“ пҪ”пҪ…пҪҺпҪҒпҪҺпҪ”пҪ’пҪҷ пҪҒпҪ” пҪ—пҪҷпҪҢпҪҢпјү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йўҶдё»йҡҸж—¶иҰҒеӣһеңҹең°дёҚжҲҗй—®йўҳпјҢдёҚиҝқиғҢеҘ‘зәҰд№Ӣ规е®ҡгҖӮеңЁпј‘пј•пјҳпј“иҮі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пјҢ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иҜҰз»Ҷи®°иҪҪдәҶйўҶдё»еңҲеҚ 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еҸ‘з”ҹ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иҘҝйғЁжҖқз»ҙжҷ®ж–ҜйЎҝпјҲпјіпҪ—пҪ…пҪҗ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Ҫ…пјүеә„еӣӯгҖӮйўҶдё»еӣһ收ж„Ҹж„ҝ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ІЎжңүеҸ‘з”ҹд»Җд№Ҳйҳ»зўҚпјҢдёҚиҝҮд№ҹдёҚжҳҜе®Ңе…ЁжІЎжңүиЎҘеҒҝгҖӮ第дёҖжЎ©пјҢйўҶдё»жүҳ马ж–ҜзҲөеЈ«жҺҘз®ЎдәҶдёӨдёӘ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е…ұ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еҲҶеҲ«жҳҜеЁҒе»үе’ҢйҳҝиҜәеҫ·гҖӮдҪңдёәиЎҘеҒҝпјҢеЁҒе»үеңЁеҚ•иә«жңҹй—ҙжҜҸе№ҙеҫ—пјҳиӢұй•‘иЎҘиҙҙпјӣйҳҝиҜәеҫ·иў«е…Ғ许继з»ӯдҝқз•ҷд»–еҰ»еӯҗзҡ„дёҖеқ—еңҹең°гҖӮд»–еҰ»еӯҗжӯ»еҗҺпјҢиҜҘең°иў«йўҶдё»иөҺд№°еҗҺеңҲеҚ пјҢд»–еҫ—еҲ°пј“пјҗиӢұ镑并иҙӯд№°дәҶдёҖеқ—иҮӘз”ұдҝқжңүең°гҖӮ第дәҢжЎ©пјҢйўҶдё»жүҳ马ж–ҜеҲҶеҲ«еңҲеҚ дәҶеҸҰеӨ–дёүдёӘж„Ҹж„ҝ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пјҡпј’пј‘иӢұдә©жқҘиҮӘжө·ж–ҜпјҢйўҶдё»з»ҷдәҲдәҶдёҖдәӣеңҹең°иЎҘеҒҝгҖӮпј’пј–иӢұдә©жқҘиҮӘиҠ¬йЎҝпјҢд»…еҖҹз§ҹз»ҷдёҖеӨ„жҲҝиҲҚпјҢе№ҙз§ҹйҮ‘пј‘пјҗе…Ҳд»ӨгҖӮеҸҰдёҖеӨ„пј’пј–иӢұдә©жқҘиҮӘдёҖдҪҚ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иҘҝиҺұзү№пјҢд»–жңүдјӨж®ӢпјҢжІЎжңүиғҪеҠӣиҖ•з§Қиҝҷеҝ«еңҹең°пјҢйўҶдё»е…Ғ许他继з»ӯз•ҷдҪҸеҺҹжқҘзҡ„жҲҝеӯҗпјҢ并е…Қиҙ№еҚ жңүйўҶдё»зҡ„дёҖеқ—еңҲең°еҒҡеҸЈзІ®з”°гҖӮйўҶдё»еӣҙеңҲдәҶдёҠиҝ°дҪғеҶңе’Ңе…¶д»–дәә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еҗҲ并дёәпј‘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ж–°еҶңеңәпјҢиҪ¬з§ҹз»ҷдәҶдёҖдёӘеҸ«еҘҘйЎҝзҡ„еҶңеңәдё»гҖӮ
жңҖжҺҘиҝ‘зҺ°д»Је•ҶдёҡеҘ‘зәҰе…ізі»зҡ„еңҹең°еҪ“еұһ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пјҲпҪҢпҪ…пҪҒпҪ“пҪ…пҪҲпҪҸпҪҢпҪ„пјүпјҢеҮӯжҚ®жӯӨеҘ‘зәҰйўҶдё»еҸҜйҖӮ时收еӣһ并еӣҙеңҲд№ӢгҖӮжүҝз§ҹиҖ…дёҖиҲ¬жҳҜе°ҸеҶңпјҢд№ҹжңүеӨ§з§ҹең°еҶңеңәдё»пјҢ他们дёҺең°дә§дё»пјҲпҪҢпҪҒпҪҺпҪ„пҪҸпҪ—пҪҺпҪ…пҪ’пҪ“пјү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е·Із»ҸеҸҳжҲҗдәҶе…ёеһӢзҡ„еҘ‘зәҰе…ізі»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ң°еҘ‘зәҰжҳҜд№ жғҜзәҰе®ҡе’Ңе•ҶдёҡеҘ‘зәҰж··еҗҲзү©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ҲҷиҰҒз®ҖеҚ•еҫ—еӨҡгҖӮеңҹең°еҮәз§ҹзҡ„жңҹйҷҗжҳҜжҳҺзЎ®зҡ„пјҢз§ҹдҪғеҸҢж–№еҸҜд»ҘйҖҡиҝҮеҚҸе•ҶзЎ®е®ҡз§ҹжңҹжҲ–иҖ…еҸҳеҠЁз§ҹжңҹпјҢеңЁи§„е®ҡзҡ„з§ҹжңҹеҶ…жүҝз§ҹиҖ…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Ҹ—еҲ°дҝқжҠӨпјҢдёҖж—Ұз§ҹзәҰйҖҫжңҹпјҢйўҶдё»жҲ–ең°дә§дё»еҸҜд»ҘеҗҲ法收еӣһеңҹең°пјҢжҲҗдёә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йҮҚиҰҒеҘ‘жңәгҖӮ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ҪўејҸеңЁпј‘пј‘дё–зәӘдёҺпј‘пј’дё–зәӘд№ӢдәӨеҚіе·ІеҮәзҺ°пјҢдҪңдёә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иЎҘе……еҪўејҸпјҢдёҖиҲ¬з§ҹжңҹиҫғй•ҝгҖӮиҝӣе…Ҙдёӯдё–зәӘжҷҡжңҹеҗҺеӨ§еҶңеңәзҡ„й•ҝжңҹз§ҹзәҰд»Қ然еӯҳеңЁпјҢдёҖиҲ¬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ҲҷеҮәзҺ°з§ҹжңҹи¶ҠжқҘи¶Ҡзҹӯзҡ„и¶ӢеҠҝпјҢдёҖдәӣең°еҢәеҮ д№ҺйғҪжҳҜзҹӯжңҹз§ҹжҲ·пјҢз”ҡиҮіпј‘е№ҙз§ҹжңҹдёәеёёи§ҒгҖӮ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дә§жқғжҜ”иҫғжҳҺзЎ®пјҢеҺҹз§ҹзәҰеӨұж•ҲеҗҺең°дә§дё»еҸҜд»Ҙз»ӯзәҰ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еңҲең°еҗҺеҶҚеҮәз§ҹпјҢдёҺд№ жғҜең°зӣёжҜ”еңҲең°дёӯжӣҙе°‘дә§з”ҹзә зә·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з§ҹзәҰжңҹж»ЎеҗҺдҪғеҶңеҸҜд»ҘиҮӘз”ұең°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ҢдёҚеҶҚиў«ејәеҲ¶еҠіеҠЁпјҢзҰ»ејҖеҗҺд№ҹдёҚдјҡиў«иҝҪжҚ•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еҘ‘зәҰеҶң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ҲҗдёәдёүеӨ§дҪғеҶңзҫӨдҪ“д№ӢдёҖпјҢеҲ°дёӢдёҖдёӘдё–зәӘжҲҗдёәдё»дҪ“дҪғеҶңпјҢиЎЁжҳҺеҘ‘зәҰең°дёҺ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е’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җҢжӯҘеҸ‘еұ•пјҢд»ЈиЎЁдәҶж—¶д»Јзҡ„ж–№еҗ‘гҖӮ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е’Ңе…¬ең°жҳҜ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зҡ„йҮҚиҰҒжқҘжәҗгҖӮд№ жғҜең°д№ҹдёҚж–ӯиҪ¬еҢ–дёәе•ҶдёҡжҖ§еҘ‘зәҰең°пјҢдёҖиҲ¬иҜҙжқҘйўҶдё»жҖ»жҳҜйј“еҠұдё–д»Јжүҝиўӯзҡ„дҝқжңүең°иҪ¬еҸҳжҲҗжңүйҷҗжңҹзҡ„еҘ‘зәҰең°пјҢдёҚж–ӯжқҫејӣзҡ„дҫқйҷ„е…ізі»е’Ң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зҡ„еҸ‘еұ•д№ҹйј“еҠұиҝҷж ·зҡ„иҪ¬еҸҳ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’пј–е№ҙпјҢ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ж•ҷеҢәзҡ„йўҶдё»ж–ҮжЈ®зү№В·зҸҖ尔继жүҝеә„еӣӯеҗҺпјҢжү§ж„ҸеңҲең°пјҢд»–жү©еј 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пјҢеҗҢж—¶еҸҳжӣҙдҪғжҲ·зҡ„еңҹең°дҝқжңүеҲ¶пјҲпҪҒпҪҢпҪ”пҪ…пҪ’ пҪ”пҪҲпҪ… пҪғпҪҸпҪҺпҪ„пҪүпҪ”пҪүпҪҸпҪҺпҪ“ пҪҸпҪҶ пҪ”пҪ…пҪҺпҪҒпҪҺпҪғпҪҷпјүгҖӮдёҖд»Ҫ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жҳҫзӨә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”е№ҙиҜҘйўҶдё»еӣҙеңҲдәҶз§ҹжңҹе·Іж»Ўзҡ„иҢ…иҲҚеҶңдҝқжңүең°пј”пј•иӢұдә©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ҷпјҚ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–е№ҙй—ҙпјҢзәҰжңүпј—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иў«еӣҙеңҲпјҢжӣҙж”№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еҢ…жӢ¬жӣҙж”№е…¬з°ҝеҶңеңҹең°дҝқжңүжқЎд»¶пјҢдҪҝд№ жғҜеңҹең°еҸҳдёәжңүжҳҺзЎ®жңҹйҷҗ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зҡ„йҮҚиҰҒжүӢж®өгҖӮ
йўҶдё»еҮӯжҚ®еҘ‘зәҰеңҲеҚ еңҹең°пјҢеҚҙеҫҲйҡҫеҮҢй©ҫеҘ‘зәҰд№ӢдёҠгҖӮд»–дёҚиғҪйҡҸж„Ҹжӣҙж”№еҘ‘зәҰпјҢз§ҹзәҰжңүж•ҲжңҹеҶ…е°Өе…¶дёҚиғҪжӣҙж”№пјӣ他们дёҚиғҪж— и§ҶеҘ‘зәҰ规е®ҡзҡ„ж—¶й—ҙиЎЁпјҢеҸӘиғҪзӯүеҫ…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•е№ҙпјҢеңЁиҗЁй»ҳеЎһзү№йғЎйҳҝеёғжҙӣеҫ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ӮпҪҢпҪҸпҪ„пҪ…пјүпјҢйўҶдё»е°Ҷеә„еӣӯзӣҙйўҶең°еҮәз§ҹз»ҷдәҶдёҖдёӘ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з§ҹжңҹпјҳпјҗе№ҙгҖӮжҳҫ然иҝҷжҳҜдёҖ笔еӨ§з”ҹж„ҸпјҢйўҶдё»еҪ“然ж„ҝж„Ҹз«ӢеҚіе…‘зҺ°пјҢеҸҜжҳҜжүҖж¶үеңҹең°зҡ„еҺҹз§ҹзәҰе°ҡжңӘз»Ҳз»“пјҢзӣҙйўҶең°иҝҳеңЁеҺҹз§ҹзәҰзҡ„з§ҹжңҹеҶ…пјҢд»Қз”ұдёҖдәӣе°ҸеҶңеҲҶеҲ«жүҝз§ҹгҖӮдәҺжҳҜйўҶдё»е’Ңж–°жүҝз§ҹиҖ…еҸӘиғҪзӯүеҫ…пјҢдёҖзӣҙеҲ°еҺҹз§ҹзәҰеҲ°жңҹпјҢиҝҷдәӣе°ҸеҶңжүҝз§ҹжқғеӨұж•ҲпјҢжүҚиғҪеңҲеҚ иҝҷеқ—зӣҙйўҶең°гҖӮиҝҷдёӘз»ҶиҠӮзү№еҲ«еҶҷиҝӣйўҶдё»е’ҢеҶңеңәдё»зҡ„жңҖз»ҲеҚҸи®®йҮҢпјҢејәи°ғжӯӨд№ғеҶңеңәдё»жүҝз§ҹзӣҙйўҶең°зҡ„жқЎд»¶д№ӢдёҖ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°ҸдҪғеҶң们зҡ„з§ҹжңҹеұҠж»Ўд»ҘеүҚпјҢйўҶдё»е’ҢеҶңеңәдё»йғҪдёҚиғҪй©ұйҖҗ他们пјҢеҸӘиғҪзӯүеҫ…гҖӮжӯӨзұ»дҫӢиҜҒпј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гҖӮе…¬з°ҝеҶңжҳҜ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ҪғеҶңдё»дҪ“пјҢ他们дёӯ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йғҪеҸҜиғҪжҲҗдёәйўҶдё»еҗҲ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еҜ№иұЎгҖӮеҪ“еҶңеҘҙеҲ¶и§ЈдҪ“пјҢеҪ“е№ҙз»ҙе…°жҲҗдёә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пјҢ他们жүӢйҮҢзҡ„е…¬з°ҝеҚі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еүҜжң¬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зЎ®дҝқеҘ‘зәҰ规е®ҡжңҹйҷҗеҶ…еҜ№еңҹең°зҡ„еҚ жңүеҸ—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и§„е®ҡ他们дёҺйўҶдё»зҡ„дё»дҪғе…ізі»дёҚжҳҜж— йҷҗзҡ„пјҢеӣ иҖҢеңҹең°зҡ„з§ҹжңҹд№ҹдёҚжҳҜж— йҷҗзҡ„гҖӮдёҖйғЁеҲҶе…¬з°ҝеҶңд»Қ然дҝқз•ҷдәҶ世代继жүҝжқғпјҢдҪҶеҲ°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Ө§йғЁеҲҶжҳҜжңүжңҹйҷҗ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жңүзҡ„еҸҜдёү代继жүҝпјҢжңүзҡ„з»Ҳиә«пјҲпҪҸпҪҺпҪ… пҪҢпҪүпҪҶпҪ…пјүпјҢжңүзҡ„ж•°еҚҒе№ҙгҖӮдёҖдёӘжңүпј“пјҗе№ҙдҝқжңүжқғзҡ„е…¬з°ҝеҶңдёҺпј“пјҗе№ҙ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еҢәеҲ«пјҢдҪ•еҶөпјҳпјҗе№ҙгҖҒпјҷпјҗе№ҙ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д№ҹдёҚе°‘и§ҒгҖӮ他们д»Қиў«з§°дёә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пјҢ然иҖҢе•ҶдёҡеҺҹеҲҷе·Із»Ҹжё—йҖҸе…¶дёӯ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–°ж—§е…ізі»ж··еҗҲдё”дёҚж–ӯеҲҶеҢ–зҡ„зҫӨдҪ“гҖӮдҪҶеҪ“е…¬з°ҝ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Өұж•Ҳж—¶пјҢйўҶдё»з»ӯзәҰж—¶е…¬з°ҝеҶңеҸҜиғҪеҸҳдёәеҘ‘зәҰеҶңпјҢиҝҷжҳҜе…¬з°ҝеҶңдёҺеҘ‘зәҰеҶңж•°йҮҸе‘ҲжҳҺжҳҫж¶Ҳй•ҝи¶ӢеҠҝзҡ„йҮҚиҰҒеҺҹеӣ пјӣеҪ“е…¬з°ҝ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Өұж•Ҳж—¶пјҢйўҶдё»д№ҹеҸҜиғҪжҺҘ管并еңҲеҚ йӮЈеқ—еңҹең°пјҢе…¬з°ҝеҶңдёҚеҫ—дёҚзҰ»ејҖ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”е№ҙпјҢиҗЁй»ҳеЎһзү№йғЎзҡ„еёғжӢүеҫ·зҰҸеҫ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’пҪҒпҪ„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„пјүдҪғжҲ·иө·иҜүйўҶдё»пјҢе…¶дёӯж¶үеҸҠ他们жӢҘжңү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继жүҝжқғпјҢеҚҙиў«иҝ«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гҖӮйўҶдё»иҫ©з§°пјҢиҝҷдәӣе…¬з°ҝең°е№¶йқһйғҪжңү继жүҝжқғ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д»…еұһз»Ҳиә«дҝқжңүгҖӮзҺӢе®Ө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еҗ‘иҜҘеә„еӣӯжҙҫеҮәдё“е‘ҳжҗңйӣҶиҜҒиҜҚпјҢеҸҜжғңиҜҒиҜҚеӨҡжңүзҹӣзӣҫд№ӢеӨ„пјҢжңҖеҗҺиҝҳжҳҜжұӮеҠ©дәҺ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гҖӮж №жҚ®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пјҢз»“жһңжі•еәӯи®Өдёә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е…¬з°ҝеҶңзЎ®е®һжІЎжңү继жүҝжқғпјҢд»…еұһз»Ҳиә«дҝқжңүгҖӮвҖңж—©е…Ҳзҡ„еҺҹе§Ӣи®°еҪ•ж”ҜжҢҒдәҶйўҶдё»гҖӮвҖқжҳҫ然法еәӯжЎЈжЎҲжҳҜ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зҡ„еҺҹе§Ӣи®°еҪ•пјҢеҶіе®ҡдәҶ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ҳҜеҗҰеҗҲжі•гҖӮ
дәЁе»·йЎҝйғЎзҡ„дёҖжЎ©жЎҲдҫӢж”ҜжҢҒдәҶиҝҷдёҖеҺҹеҲҷ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ҳҜеҗҰжҲҗз«ӢпјҢжңҖз»ҲеҸ–еҶідәҺеҜ№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и®Өе®ҡ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“е№ҙпјҢдёҖдҪҚжқҘиҮӘйӣ·жҷ®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ІпҪүпҪҗ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еңЁзҺӢеӣҪдёҠи®ҝжі•йҷўпјҲпјЈ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 пҪҸпҪҶ пјІпҪ…пҪ‘пҪ•пҪ…пҪ“пҪ”пјүжҢҮжҺ§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пјҢиҜҘеә„еӣӯжӣҫжҳҜжӢүйҪҗе§Ҷдҝ®йҒ“йҷў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дҝ®йҒ“йҷўи§Јж•ЈеҗҺиў«еӣҪзҺӢжҺҲдәҲдәҶзәҰзҝ°зҲөеЈ«гҖӮзәҰзҝ°зҲөеЈ«иў«жҢҮжҺ§ејәиЎҢеҚ жңүдҪғжҲ·еңҹең°пјҲпҪҶпҪҸпҪ’пҪғпҪүпҪӮпҪҢпҪ… пҪ…пҪҺпҪ”пҪ’пҪҷ пҪ•пҪҗпҪҸпҪҺ пҪ”пҪҲпҪ… пҪ”пҪ…пҪҺпҪҒпҪҺпҪғпҪүпҪ…пҪ“пјүгҖӮзәҰзҝ°зҲөеЈ«зӯ”еӨҚйҒ“пјҢд№ӢжүҖд»Ҙй©ұйҖҗ他们жҳҜеӣ дёәе…¶дёҚжӯЈејҸе…·еӨҮе…¬з°ҝеҶңжқғеҲ©пјҢ他们其е®һжҳҜ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пјҢжӯЈиҰҒдҫқжҚ®еӣҪзҺӢзҡ„вҖңдҫөеҚ иҜүи®јжі•д»ӨвҖқиө·иҜү他们гҖӮдёәжӯӨпјҢдёҠи®ҝжі•йҷўжҹҘйҳ…дәҶиҮӘзҗҶжҹҘдәҢдё–ж—¶жңҹпјҲпј‘пј“пј—пј—пјҚпј‘пј“пјҷпјҷе№ҙпјүд»ҘжқҘзҡ„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пјҢзЎ®и®ӨеҺҹе‘ҠзЎ®еұһж„Ҹж„ҝдҪғеҶңпјҢеңҹең°жҳҜ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ң°пјҢжҚ®жӯӨз»ҷеҮәеҲӨеҶіпјҢиў«е‘ҠзәҰзҝ°зҡ„йҷҲиҝ°еұһе®һпјҢеңҲең°жҲҗз«ӢгҖӮ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еңҲең°зҡ„дҫқжҚ®еңЁдәҺеҘ‘зәҰ规е®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
еҸҰдёҖдёӘеҸІдҫӢеҗҢж ·иҜҙжҳҺдәҶйўҶдё»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зҡ„дё»иҰҒеҮӯжҚ®жҳҜд»Җд№Ҳ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ҳе№ҙпјҢжңүдёҖе°ҒйўҶдё»зҲұеҫ·еҚҺдјҜзҲөеӣһеӨҚеӣҪеҠЎеӨ§иҮЈжүҳ马ж–Ҝзҡ„дҝЎд»¶пјҢд»Һдёӯеҫ—зҹҘпјҢзҲұеҫ·еҚҺдјҜзҲөй©ұйҖҗдәҶеҹғе°”ж–Ҝзұі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ҢпҪҢпҪ…пҪ“пҪҚпҪ…пҪ’пҪ…пјүзҡ„пј—дёӘдҪғеҶңпјҢеӣ иҖҢеј•иө·дҪғеҶңзҡ„жҠ•иҜүгҖӮжі•еәӯдёҚеҗ¬дјҜзҲөзҡ„иҫ©и§ЈпјҢеқҡжҢҒжүҫеҲ°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дҪғжҲ·пјҢд»”з»ҶиҜўй—®д»–们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йҒ—жҶҫзҡ„жҳҜпјҢжҜҸдёӘдҪғеҶңзҡ„иҜҒиҜҚйғҪжүҝи®Ө他们зҡ„еңҹең°вҖңжІЎжңүе…¬з°ҝжҲ–иҖ…д№ҰйқўиҜҒжҳҺ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йўҶдё»зҡ„вҖҳж„Ҹж„ҝдёӢвҖҷпјҲпҪҒпҪ” пҪҗпҪҢпҪ…пҪҒ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…пјүеҚ жңүйӮЈеқ—еңҹең°вҖқгҖӮйўҶ主收еӣһ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ң°жң¬еә”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дәүи®®пјҢеҸҜжҳҜеҗҺжқҘзҡ„еҲӨеҶіеҚҙеҜ№йўҶдё»дёҚеҲ©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еҮәдәҺеҜ№ең°ж–№иҙөж—Ҹж”ҝжІ»ж–—дәүзҡ„йңҖиҰҒгҖӮдҪңиҖ…еҲ©иҫҫе§ҶиҜ„и®әиҜҙ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еҲӨеҶіз»“жһңвҖңйҡҫд»ҘзҪ®дҝЎвҖқпјҢжҳҫ然жҳҜдёәдәҶжҹҗз§Қзӣ®зҡ„иҖҢвҖңжӯӘжӣІдәҶжі•еҫӢвҖқгҖӮдҪңиҖ…иЎЁиҫҫзҡ„ж„ҸжҖқжҳҜжҳҺзЎ®зҡ„пјҢжӯЈзЎ®еҲӨе®ҡзҡ„е”ҜдёҖеҮӯжҚ®еә”иҜҘжҳҜеңҹең°еҘ‘зәҰгҖӮжҳҫ然пјҢдәә们еҝғзӣ®дёӯеңҲең°жңүеҗҲжі•е’Ңйқһжі•д№ӢеҢәеҲ«пјҢдҫқжҚ®е°ұжҳҜ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
з”ұдәҺе•ҶдёҡеҺҹеҲҷзҡ„жё—йҖҸ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ҳҫи‘—зү№зӮ№жҳҜ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ӣҙеҠ зЎ®е®ҡ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жқЎд»¶йҷҗе®ҡжӣҙеҠ дёҘеҜҶ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Ҡ е…ҘдәҶж—¶й—ҙжқЎд»¶зҡ„йҷҗе®ҡпјҢеҫҖеҫҖиў«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үҖеҲ©з”ЁгҖӮе…·дҪ“и®ІпјҢ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—¶ж•ҲжҖ§пјҢз»ӯзәҰж—¶еӨ§е№…еәҰжҸҗй«ҳз§ҹйҮ‘пјҢиҝ«дҪҝдҪғжҲ·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гҖӮеә„еӣӯе‘Ёеӣҙзҡ„иҚ’ең°жҳҜ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пјҢиҝҷдәӣиҚ’ең°дёҚж–ӯиў«дҪғеҶңиҡ•йЈҹпјҢеӣ жӯӨиҖҢдәӨз»ҷйўҶдё»зҡ„з§ҹйҮ‘йҖҡеёёжңүеҲ«дәҺ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жҳҜдёҖз§Қе•Ҷдёҡең°з§ҹпјҢеҸҜд»Ҙе®ҡжңҹ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гҖӮ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第д№қд»ЈдјҜзҲөе°ұжҳҜеҲ©з”Ё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зҡ„жңәдјҡпјҢеңҲең°жё”еҲ©гҖӮеңЁиҺұеә·иҸІе°”еҫ·еә„еӣӯпјҲпј¬пҪ…пҪғпҪҸпҪҺпҪҶпҪүпҪ…пҪҢпҪ„пјүпјҢйҰ–е…ҲеҲҶеүІдәҶеү©дҪҷзҡ„е…¬ең°пјҢе…¶й—ҙвҖңйӮЈдәӣиҝҺеҗҲйўҶдё»еҝғж„ҝзҡ„дҪғжҲ·дјҳе…Ҳе®үжҺ’вҖҰвҖҰеҗҰеҲҷе…¶з§ҹзәҰиў«иҪ¬и®©еҲ«дәәвҖқгҖӮдёӢдёҖжӯҘпјҢ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пјҢжҸҗй«ҳең°з§ҹпјҢжҳҜ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ңәдјҡпјҡвҖңйӮЈдәӣжІЎжңүиғҪеҠӣж”Ҝд»ҳй«ҳз§ҹйҮ‘дҪғжҲ·зҡ„иҙўзү©иў«ејәиЎҢжҠөжҠјпјҢ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иғҪеҠӣиөҺеӣһпјҢ他们е°Ҷиў«й©ұйҖҗгҖӮвҖқиҝҷдҪҚдјҜзҲөдёҚжҳҜдёҖе‘ізҡ„иҙӘе©ӘпјҢдёҖд»Ҫд№Ұйқўж–Үеӯ—дёӯжҸҗеҲ°дәҶз©·дәәпјҢвҖң他们еҸҜд»ҘеҰӮе…¶жүҖж„ҝеҲҶеүІдёҖеқ—е…¬ең°вҖқпјҢиҝҷжҳҜеҜ№пј’пј—дҪҚиҢ…иҲҚеҶңзҡ„иЎҘеҒҝгҖӮ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е•Ҷдёҡз§ҹзәҰзҡ„ж—¶ж•ҲжҖ§пјҢжҸҗй«ҳең°з§ҹе’Ң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жҳҜж®ӢеҝҚзҡ„пјҢ然иҖҢеҚҙдёҚжҳҜиҝқжі•зҡ„гҖӮ
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ҳҜ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зҡ„延伸пјҢжі•е®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ҫқ然жҳҜ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дҫқжҚ®пј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еҚійўҶдё»дёҺдҪғжҲ·еҚҸе•ҶеҗҺиҫҫжҲҗеңҲең°зҡ„дёҖиҮҙж„Ҹи§Ғ并еҸ—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пјҢжҳҜ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ё йҒ“гҖӮйғҪй“ҺзҺӢжңқдёӯжҷҡжңҹпјҢеңЁж”ҝеәңе’Ңе…¬е…ұиҲҶи®әеҺӢеҠӣдёӢ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ӣҙеҠ е°Ҹеҝғи°Ёж…ҺпјҢе°ҪеҠӣйҒҝе…ҚжҡҙеҠӣпј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еҸҳеҫ—жӣҙеҠ жҷ®йҒҚ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ҳпј’е№ҙпјҢ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ЎһдёҒжІғж–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ҲпҪ…пҪ„пҪ„пҪүпҪҺпҪҮпҪ—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ҲпјүпјҢйўҶдё»еЁҒе»үВ·еёғзҪ—еҚЎж–ҜдёҺ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们иҫҫжҲҗ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пјҢе…¶дёӯз»ҷдәҲдәҶдҪғеҶңз§Қз§ҚиЎҘеҒҝпјҢиҝҳе…ҒиҜәдјҳжғ ең°з§ҹгҖӮеҸҲдҫӢеҰӮпјҢйІҒжң¬зҝ°еә„еӣӯпјҲпј¬пҪ•пҪӮпҪ…пҪҺ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дҪҚдәҺиҜәжЈ®дјҜе…°йғЎиҫ№з•ҢпјҢдәәеҸЈиҫғеӨҡ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”е№ҙпјҢйўҶдё»еёғйІҒе…ӢзҲөеЈ«дёҺ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зӯҫдёӢ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пјҢжҚ®жӯӨпј‘пј–пјҗпјҗпјҚ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‘е№ҙжқ‘еә„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еҸҳдёәзү§еңә并еӣҙеңҲд№ӢгҖӮ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жҸҗдҫӣзҡ„дҝЎжҒҜиЎЁжҳҺпјҢеңЁеңҲең°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йўҶдё»жҜҒеқҸдәҶдёүеӨ„еҶңеңәпјҢ并е°Ҷпј‘пј’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иҪ¬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ӣеҸҰеӨ–пј‘пјҳдҪҚдҪғеҶңеӣҙеңҲпј•пј‘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е№¶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е…¶дёӯдёҖдҪҚеҸ«жҷ®зү№зҡ„дҪғеҶңжҜҒеқҸдәҶдёҖеӨ„еҶңиҲҚпјҢеҸҰеӨ–дёӨдҪҚжҜҒеқҸдәҶдёӨеӨ„еҶңеңәгҖӮиҝҷж ·пјҢжҖ»и®Ўпј‘пј—пј‘иӢұдә©зҡ„иҖ•ең°иў«еңҲеӣҙжҲҗзү§еңәпјҢзәҰеҚ жқ‘еә„йқўз§Ҝзҡ„пј–пј…гҖӮиҖ•ең°еӣҙеңҲзҡ„еҚҸи®®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пјҢд»ҘдҪғеҶңпј‘пј–иӢұдә©еҜ№зӯүйўҶдё»пј‘пј•иӢұдә©зҡ„жҜ”дҫӢдәӨжҚўиҖ•ең°пјҢе…¶дёӯж¶үеҸҠйғЁеҲҶйўҶдё»зӣҙйўҶең°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з”ұдәҺж¶ҲеҮҸдәҶе…¬ең°пјҢдёҖдәӣиҢ…иҲҚе°ҸеҶңиў«иЎҘеҒҝдәҶеӨ§зәҰпј–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жүҖд»ҘеңҲең°еҗҺвҖң他们зҡ„з”ҹжҙ»иҝҳиғҪиҝҮдёӢеҺ»вҖқгҖӮеҜ№иҢ…иҲҚе°ҸеҶңзҡ„иЎҘеҒҝпјҢиЎЁжҳҺеҜ№иҢ…иҲҚеҶңж—ўжңү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үҝи®ӨгҖӮеңҲең°д№ӢеүҚпјҢеҚҸи®®иҰҒеңЁ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йқўеүҚе®ЈеёғгҖӮеңҲең°иҝҮзЁӢжҳҜе’Ңе№ізҡ„пјҢиҜҘжқ‘еҺҹжңүпј–пјҗжҲ·дәә家пјҢеңҲең°жІЎжңүеҮҸе°‘дәәеҸЈпј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“е№ҙйўҶеҸ–еңЈйӨҗдәәж•°и®°еҪ•иЎЁжҳҺдәҶиҝҷдёҖзӮ№гҖӮ
еңЁеңҲең°йҮҚзӮ№ең°еҢәзұіеҫ·е…°пјҢйғҪй“Һж—¶д»ЈжҷҡжңҹйўҶдё»дёҺдҪғжҲ·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зӣёеҪ“жҷ®йҒҚ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ҸІжҳҫзӨәпјҢзҪ—йҮ‘йЎҝпјҲпј¬пҪҸпҪғпҪӢпҪүпҪҺпҪҮ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еә„еӣӯзҡ„еҚҸи®®иЎЁжҳҺпјҢйўҶдё»дёҖ并еӣҙеңҲжүҖжңүжқЎз”°пјҢеҶҚеҲҶй…Қз»ҷдҪғеҶңдёӘдәәзӢ¬иҮӘиҖ•дҪңгҖӮеҸҲжҚ®иҜҘйғЎйғЎеҸІи®°иҪҪпјҢдәҡеҺҶеұұеӨ§В·з§‘еӨ«зҲөеЈ«жҳҜдёӨдёӘ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•пҪғпҪӢпҪҚпҪүпҪҺпҪ“пҪ”пҪ…пҪ’гҖҒпјіпҪ…пҪ—пҪ“пҪ”пҪ…пҪ’пҪҺпјүзҡ„йўҶдё»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пјҢд»–дёҺпј“пј‘дёӘдҪғеҶң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е…ұеҗҢеңҲең°гҖӮеҸҲеҰӮпјҢи’Ӯе°”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үпҪҢ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йўҶдё»и’ӮжҲҲжҜ”зҲөеЈ«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–дёӘдҪғеҶңзҡ„еҗҢж„ҸдёӢеңҲең°пјҢ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иҫҫпј‘пј“пј“пј•иӢұдә©гҖӮ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җпјҚпј‘пј–пј”пјҗе№ҙй—ҙиҮіе°‘е®ҢжҲҗдәҶпј‘пј•ж¬Ў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иҖҢдәҢеҚҒе№ҙеҗҺ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Ҳҗдёәжҷ®йҒҚж–№ејҸгҖӮеҚҸи®®зҡ„иҝҮзЁӢд№ҹжҳҜдҪғжҲ·дёҺйўҶдё»и®Ёд»·иҝҳд»·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дёҖдәӣ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дҪғеҶңеҢ…жӢ¬дёҖдәӣе°ҸеҶңеңЁеҶ…иғҪеӨҹжҲҗеҠҹең°з»ҙжҠӨиҮӘе·ұ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еңЁе…¶д»–ең°еҢәд№ҹжҳҜиҝҷж ·пјҢеҰӮзүӣжҙҘйғЎзҡ„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ж•ҷеҢәеңҲең°пјҢеңЁпј‘пј–пј’пј“е№ҙзӯҫи®ўеҚҸи®®пјҢеңҲең°жңүиҖ•ең°д№ҹжңүиҚ’ең°пјҢе…¶дёӯе°‘ең°ж— ең°зҡ„е°ҸеҶңеҲ©зӣҠжҳҜиҖғиҷ‘зҡ„иҰҒзӮ№д№ӢдёҖгҖӮеҚҸи®®з”ұдёүж–№зӯҫи®ўпјҢжңүйўҶдё»зәҰзҝ°В·дјҰз‘ҹе°”зҲөеЈ«пјҢжңү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•ҷеЈ«е’Ңпј‘пј•еҗҚдҪғеҶңгҖӮеңҲ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пј—пјҳпј•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пјҢеӣҙеңҲеҗҺеҲҶй…ҚеҰӮдёӢпјҡпј”пј—пјҳиӢұдә©еҪ’йўҶдё»пјҢпј‘пјҷпј’иӢұдә©еҪ’ж•ҷеҢәзҡ„ж•ҷеЈ«пјҢдёӨеҗҚдҪғеҶңеҲҶеҲ«иҺ·еҫ—пј–пјҗиӢұдә©е’Ңпј•пј–иӢұдә©пјҢеү©дёӢзҡ„еңҹең°з”ұпј‘пј“еҗҚдҪғжҲ·еҲҶеүІпјҢе…¶дёӯжңүпј•дәәжүҖиҺ·еңҹең°дёҚи¶іпј‘пјҗиӢұдә©гҖӮ
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зҡ„дә”еҚҒе№ҙйҮҢпј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–№ејҸдјјд№Һжӣҙ规иҢғдәҶдёҖдәӣгҖӮ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зӯҫи®ўиҰҒеңЁдёҖдёӘе°Ҹз»„зҡ„зӣ‘зқЈдёӢпјҢиҜҘе°Ҹз»„йҖҡеёёз”ұпј•дёӘд»ІиЈҒе‘ҳе’Ңпј’дёӘеӢҳжөӢе‘ҳз»„жҲҗпјҢ他们жңүд№үеҠЎж №жҚ®вҖңеңҹең°зҡ„ж•°йҮҸгҖҒиҙЁйҮҸе’ҢжҜҸдёӘдәә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вҖқзӯүеӣ зҙ пјҢйҮҚж–°еҲҶй…Қеңҹең°гҖӮдҪңдёәиЎҘеҒҝпјҢжңү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зҡ„иҢ…иҲҚеҶңе’Ңз©·дәәпјҢйғҪиў«иЎҘеҒҝзӣёеә”зҡ„иҖ•ең°гҖӮеңЁз»ҸиҝҮдёҖдёӘиҷҡжһ„зҡ„и®јжЎҲжөӢиҜ•еҗҺпјҢеҚҸи®®жңҖз»Ҳз”ұеҸҢж–№е…¬ејҖзӯҫзҪІпјҢ并еңЁ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пјҲпјЈпҪҲпҪҒпҪҺпҪғпҪ…пҪ’пҪҷпјүзҷ»и®°гҖӮеӣ жӯӨеңЁ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’ҢиҙўеҠЎзҪІжі•еәӯпјҲпјҘпҪҳпҪғпҪҲпҪ…пҪ‘пҪ•пҪ…пҪ’пјүдёҚйҡҫеҸ‘зҺ°еҪ“е№ҙзӯҫзҪІзҡ„еңҲең°еҚҸи®®д№ҰгҖӮеҚҸи®®ж–№ејҸ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ҮҸиҪ»дәҶдҪғеҶңзҡ„з—ӣиӢҰпјҢ并且дёәпј‘пјҳдё–зәӘзҡ„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еҒҡеҮәе°қиҜ•гҖӮеҪ“然пјҢдёҚи®әиҝҷйҮҢзҡ„вҖңеҘ‘зәҰвҖқиҝҳжҳҜвҖңеҚҸи®®вҖқ并йқһжҖ»жҳҜе…¬е№і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зҺ°д»Ј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еҘ‘зәҰе’ҢеҚҸи®®гҖӮдҪғжҲ·жҜ•з«ҹеӨ„дәҺејұеҠҝдёҖж–№пјҢ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еҚҸи®®еҪўејҸж¬әиҙҹдҪғеҶңзҡ„жғ…еҶөж—¶жңүеҸ‘з”ҹпјҢдёҠиҝ°иҺұеә·иҸІе°”еҫ·еә„еӣӯдјҜзҲөйўҶдё»еңЁе…¬ең°еҲҶеүІж—¶йўҗжҢҮж°”дҪҝгҖӮжӣҙжңүиҙӘеҫ—ж— еҺҢзҡ„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еҶңж°‘зҡ„иҝҹй’қпјҢз”Ёж¬әйӘ—зҡ„жүӢж®өзӯҫдёӢеҒҮеҚҸи®®пјҢ然еҗҺеҸҲеҖҹе·ІзӯҫеҚҸи®®зҡ„жі•еҫӢж•ҲеҠӣпјҢиҫҫеҲ°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зҡ„зӣ®зҡ„пјҢзүӣжҙҘйғЎ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ж•ҷеҢәеңҲең°е°ұжҳҜдёҖжЎ©е…ёеһӢжЎҲдҫӢгҖӮ
пј’пјҺ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пјҲпјҘпҪҺпҪғпҪҢпҪҸ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… пҪӮпҪҷ пҪғ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пјү
йўҶдё»еҮӯжҚ®жі•еәӯзҡ„и®Өе®ҡиҖҢеңҲең°еҚі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гҖӮеңҹең°еҸҳйқ©ж—¶жңҹзҡ„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й”ҷз»јеӨҚжқӮпјҢйўҶдё»е’ҢдҪғжҲ·еёёеёёеӣ еңҲең°еҸ‘з”ҹеҶІзӘҒпјҢеҜ№з°ҝе…¬е ӮпјҢйҖҡиҝҮжі•еәӯеҺҳжё…еҸҢж–№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并еҲӨе®ҡ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жҳҜеҗҰжҲҗз«ӢгҖӮжҜ”з…§еүҚиҝ°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д№ҹжҳҜд»ҺеҸҰдёҖдёӘж–№йқўеҸҚиҜҒ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еҺҹеҲҷгҖӮжі•еәӯеҘҪжҜ”дёҖжҠҠеҸҢеҲғеү‘пјҢйўҶдё»йҖҡиҝҮжі•еәӯи®Өе®ҡеҸ–еҫ—еңҲең°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пјҢд»ҺиҖҢжҲҗдёә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йҮҚиҰҒжё йҒ“пјӣеҗҢж—¶пјҢд»Ҙжі•е®ҡзҡ„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ёәеҹәзЎҖпјҢжі•еәӯд№ҹжҳҜжҠ‘еҲ¶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дёҖйҒ“еұҸйҡңгҖӮ
иҜҘж—¶жңҹеә„еӣӯз»„з»Үи¶Ӣеҗ‘и§ЈдҪ“пјҢ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и¶ҠжқҘи¶Ҡж— еҠӣи§ЈеҶіиҝҷзұ»зә зә·пјҢж„Ҹж¬ІеҺӢжҠ‘ең°ж–№иҙөж—ҸеҠҝеҠӣзҡ„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и¶Ғжңәд»Ӣе…ҘпјҢиҜёеҰӮжҷ®йҖҡжі•жі•еәӯгҖҒ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е’Ң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зӯүпјҢйҖҗжёҗжӣҝд»Јж—ҘзӣҠиЎ°иҗҪзҡ„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гҖӮпјҘпјҺпјўпјҺеј—йҮҢеҫ·жҢҮеҮәпјҢйқўеҜ№иў«йўҶдё»й©ұйҖҗзҡ„еҚұйҷ©пјҢеҪ“ж—¶зҡ„дҪғеҶңдё»еҠЁз”іиҜ·е’ҢжҠ•иҜүдәҺ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пјҢжҳҜеӣ дёә他们и®ӨдёәйҖҡиҝҮ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еҜ№жҠ—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иЎҢдёәжҳҜжңүж„Ҹд№үзҡ„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зү№е®ҡзҡ„ж—¶жңҹеҶ…пјҢ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дҝқжҠӨдәҶ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зҺӢжқғйҖҗжёҗд»Ӣе…Ҙең°ж–№дәӢеҠЎ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з®ҖеҚ•ең°еҗ‘ең°ж–№жҺЁиЎҢжҷ®йҖҡжі•пјҢиҖҢжҳҜе°Ҷеҗ„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дҝқз•ҷдёӢжқҘпјҢ并еӨ§йҮҸзәіе…Ҙжҷ®йҖҡжі•еҪ“дёӯгҖӮз”ұдәҺеҗ„ең°д№ жғҜе·®ејӮйўҮеӨ§пјҢжҷ®йҖҡжі•жҺҘзәід№ жғҜжі•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дёҚж–ӯеҗҰи®Өеҗ„ең°дёҚеҗҲзҗҶзҡ„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гҖӮдҫӢеҰӮжҷ®йҖҡжі•зә жӯЈдәҶи®ёеӨҡеә„еӣӯеҸҚеҜ№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иҪ¬з§ҹеңҹең°зҡ„д№ жғҜпјҢе®ЈеёғиҪ¬з§ҹеңҹең°еңЁиӢұж је…°жүҖжңүеә„еӣӯйғҪжҳҜеҗҲжі•зҡ„гҖӮеҪ“然пјҢ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дё»жҢҒд»ІиЈҒйўҶдё»е’Ң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дәүз«Ҝж—¶пјҢеҲӨжЎҲдҫқжҚ®еҹәжң¬иҝҳжҳҜ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и®°еҪ•еҚі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жі•гҖ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еҜ№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и®Өе®ҡиҮіе…ійҮҚиҰҒгҖӮ
д№ жғҜжі•еңЁйҖҗжёҗи°ғж•ҙпјҢдҪҶеңЁ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д»Қ然具жңүз”ҹе‘ҪеҠӣгҖӮиҝҷжҳҜеҸ‘з”ҹеңЁ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еүҚзҡ„дёҖжЎ©жЎҲдҫӢпјҡеҺҹе‘ҠжҳҜжқӮиҙ§е•Ҷзҡ„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пјҢеҘ№д»¬зҡ„еңҹең°з»§жүҝжқғеҸ—еҲ°дәҶдёҖдҪҚеҗҚеҸ«зәҰзҝ°В·жҹҜе°”е…Ӣзҡ„дҪғеҶңзҡ„жҢ‘жҲҳвҖ”вҖ”вҖ”йўҶдё»зҡ„管家и¶ҒеҺҹдҪғжҲ·пјҲжқӮиҙ§е•ҶеӨ«еҰ»пјүеҺ»дё–д№Ӣжңә收еӣһеңҹең°пјҢ并з»Ҹ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е°Ҷеңҹең°иҪ¬з»ҷдәҶжҹҜе°”е…ӢгҖӮеҺҹе‘ҠиҜ·ж„ҝиҮі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пјҢиҜ·жұӮжүҝи®ӨеҘ№д»¬еҜ№дәҺзҲ¶жҜҚзҡ„е®…ең°е’Ңдҝқжңү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ејәи°ғиҝҷдәӣдёҚеҠЁдә§жҳҜвҖңжҢү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д»Ҙе…¬з°ҝеҪўејҸдҝқжңүзҡ„вҖқпјҲпҪҲпҪ…пҪҢпҪ„вҖҳпҪӮпҪҷ пҪғпҪҸпҪҗпҪүпҪ… пҪҒпҪҶпҪ”пҪ…пҪ’ пҪғпҪ•пҪ“пҪ”пҪ•пҪҚпҪ… пҪҸпҪҶ пҪҚпҪҒпҪҺпҪҸпҪүпҪ’вҖҷпјүпјҢвҖңеёҢжңӣ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дј е”ӨзәҰзҝ°В·жҹҜе°”е…ӢеҸҠйўҶдё»зҡ„管家пјҢ并иҰҒжұӮеҗҺиҖ…еёҰдёҠ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вҖқгҖӮеҸҜи§ҒдҪңдёәеҲӨжЎҲдҫқжҚ®пјҢеә„еӣӯд№ жғҜжі•иҮіе…ійҮҚиҰҒгҖӮжқҘиҮӘеЎһе°”зҷ»еҚҸдјҡжі•еәӯжЎЈжЎҲ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пјҢд№ҹиҜҒжҳҺдәҶиҝҷдёӘдәӢе®һпјҢж—¶й—ҙжҳҜ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пјҢж¶үжЎҲең°еңЁеңЈеҘҘе°”жң¬ж–Ҝдҝ®йҒ“йҷўгҖӮжӯЈеҰӮжі•еҫӢеҸІеӯҰ家AпјҺиҗЁж–ҮжүҖ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жі•еәӯзҡ„зӣ®зҡ„дёҚжҳҜдҝ®ж”№жғҜдҫӢпјҢиҖҢжҳҜиҝҳеҺҹжғҜдҫӢгҖӮжі•еәӯеҜ»жұӮзҡ„дҫқжҚ®вҖҰвҖҰеңЁдәҺеә„еӣӯи®°еҪ•зҡ„ж•…зәёе ҶдёӯвҖқгҖӮ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еҠһжЎҲеҚҙиҝҪиёӘеҲ°еә„еӣӯпјҢеӣ дёәеҸӘжңү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дҝқз•ҷзқҖ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еҺҹе§Ӣи®°еҪ•пјҢеҸҜи§Ғ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ҳҜжі•еәӯеҲӨж–ӯеңҲең°еҗҲжі•жҖ§зҡ„еҹәжң¬дҫқжҚ®гҖӮ
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еңЁдҫқжі•з”„еҲ«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ҒжҠөеҲ¶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дёӯ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пјӯпјҺиүҫдҪӣйҮҢи®ӨдёәпјҢе·ІзҹҘзҡ„иө„ж–ҷиЎЁжҳҺпјҢеңЁдәЁеҲ©дёғдё–еңЁдҪҚж—¶жңҹпјҲпј‘пј”пј•пј—пјҚ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ҷе№ҙпјүпјҢ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·Із»ҸејҖе§Ӣд»Ҙе№ізӯүжҖҒеәҰеҜ№еҫ…дҪғжҲ·иә«д»Ҫзҡ„еҺҹе‘Ҡе’ҢйўҶдё»иә«д»Ҫзҡ„иў«е‘ҠдәҶгҖӮ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жңүжқғеҠӣејәеҲ¶иҰҒжұӮеҪ“дәӢдәәеҮәеәӯгҖӮиҝҷз§Қж–№ејҸжҜ”жҷ®йҖҡжі•жі•еәӯпјҲпјЈ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пҪ“ пҪҸпҪҶ пјЈпҪҸпҪҚпҪҚпҪҸпҪҺ пј¬пҪҒпҪ—пјүжӣҙдёәй«ҳж•ҲгҖӮ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йўҶ主们дёҚеҫ—дёҚи®ӨзңҹеҜ№еҫ…пјҢзІҫеҝғеҮҶеӨҮзӯ”иҫ©пјҢ并表зӨәиҮӘе·ұжңҚд»Һ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зҡ„еҲӨеҶіпјҢе°Ҫ管他们еҸҜиғҪдјҡд»ҘеҫӢеёҲд»ЈжӣҝиҮӘе·ұ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йҮҚиҰҒзҡ„иҝӣжӯҘгҖӮиҝҷз§ҚеӨ–жҳҫзҡ„еҺӢеҠӣдёҖе®ҡдјҡеҪұе“ҚеҲ°йўҶ主们пјҢеҪұе“ҚеҲ°жӯӨеҗҺйўҶдё»дёҺиҮӘе·ұдҪғжҲ·жү“дәӨйҒ“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иҜҘж—¶жңҹдҝқз•ҷдёӢжқҘзҡ„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зҡ„жЎҲдҫӢжңүйҷҗпјҢе…¶дёӯ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еҸ‘з”ҹеңЁпј‘пј”пј”пјҗе№ҙпј‘пј‘жңҲпјҢиӢҸеЎһе…Ӣж–ҜйғЎжҹҗе…¬з°ҝеҶңеӨ«еҰҮжҺ§иҜү他们йўҶдё»зҡ„жҒ¶иЎҢгҖӮиҝҷеҜ№дҪғеҶңеӨ«еҰҮеЈ°з§°пјҢ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и®°еҪ•еҸҜиҜҒпјҢ他们дҝқжңүдёҖй—ҙжқ‘иҲҚе’Ңпј‘з»ҙе°”зӣ–зү№еңҹең°гҖӮдҪҶйўҶдё»д»Ҙж— жі•и§ЈйҮҠзҡ„зҗҶз”ұжӢ’з»қ他们иҝӣе…Ҙиҝҷд»Ҫдҝқжңүең°гҖӮиҝҷеҜ№еӨ«еҰ»и®Өдёә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ҸҜд»ҘејәеҲ¶дј е”ӨйўҶдё»пјҢеҪ“еңәиҙЁиҜўд»–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қиғҢиҮӘе·ұеҪ“е№ҙзҡ„еңҹең°и®Өе®ҡ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қиғҢ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зҡ„и®°иҪҪвҖқпјҢдјјд№ҺеҜ№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жҚ®жі•еҜ№жҠ—йўҶдё»дёҚж— дҝЎеҝғгҖӮжі•еҫӢеҸІеӯҰиҖ…ж јйӣ·пјҲпјЈпјҺпјӯпјҺпј§пҪ’пҪҒпҪҷпјүи®ӨдёәиҜҘжЎҲдҫӢжҳҜжңҖжңүеҠӣзҡ„иҜҒжҚ®д№ӢдёҖпјҢиЎЁжҳҺ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жүҝи®Ө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пјҢжүҝи®ӨдҪғжҲ·жі•е®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д»ҘжӯӨеә”еҜ№йӮЈдәӣйўҶ主们гҖӮ
дәә们еҸҜд»ҘеҸ‘зҺ°дҪғжҲ·иғңиҜүзҡ„жЎҲдҫӢ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иүҫе°”ж–ҜеЁҒе…Ӣ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ҢпҪ“пҪ—пҪүпҪғпҪӢпјүе…¬з°ҝеҶңдёҺ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Ҝ№з°ҝе…¬е ӮпјҢдәүз«Ҝзҡ„ж ёеҝғй—®йўҳжҳҜд»–зҡ„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ң°жҳҜеҗҰжңү继жүҝжқғпјҢжңҖеҗҺд№ҹжҳҜжҹҘйҳ…дәҶ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жЎҲеҚ·гҖӮеҘҪеңЁ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и®°еҪ•жҳҺзЎ®пјҢжҚ®жӯӨжі•еәӯзЎ®и®ӨиҜҘдҪғжҲ·зҡ„е„ҝеӯҗеҸҜд»Ҙ继жүҝиҝҷеқ—еңҹең°пјҢйўҶдё»дёҚиғҪ收еӣһеңҹең°еӣҙеңҲ?гҖӮдёҖдәӣ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еҚідҪҝеңҹең°е·Іиў«еӣҙеңҲпјҢжі•еәӯд№ҹеҸҜиғҪеҒҡеҮәдёҺйўҶдё»еҲ©зӣҠдёҚдёҖиҮҙзҡ„иЈҒеҶіпјҢж”№еҸҳеңҲең°зҡ„ж—ўжҲҗдәӢе®һ?з‘Ҹз‘ЎгҖӮеҸҰдёҖдёӘзұ»дјјзҡ„жЎҲдҫӢеҸ‘з”ҹ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пјҢеӨ§зәҰеңЁ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пјҢйўҶдё»еЁҒе»үеңҲең°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ҜҒеқҸдәҶдёҖдәӣжҲҝеұӢпјҢеј•иө·дҪғжҲ·дёҚж»ЎпјҢжҢҮжҺ§йўҶдё»гҖӮжі•еәӯеҲӨеҶійўҶдё»еҝ…йЎ»йҮҚе»әжҜҒжҺүзҡ„жҲҝеұӢпјҢ并е°Ҫеҝ«д»ҳиҜёе®һж–ҪгҖӮеҲӨеҶіе®һж–ҪеҗҺпјҢжі•еәӯжҙҫдё“дәәжҹҘзңӢзҺ°еңәпјҢ并иҜҰз»ҶиҜўй—®еҪ“дәӢдҪғжҲ·жҲҝеұӢйҮҚе»ә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
зҺӢе®Өжі•еәӯж¶үи¶ідҝқжҠӨ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еӨ§зәҰе§ӢдәҺ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пјҢеҸ‘з”ҹдәҺзұіеҫ·е°”иөӣе…Ӣж–ҜйғЎпј‘пј”пј–пј•пјҚпј‘пј”пј—пј‘е№ҙй—ҙзҡ„дёҖжЎ©жЎҲдҫӢпјҢи®°иҪҪдәҶж—©жңҹзҡ„жі•еҫӢе®һи·өгҖӮеҺҹе‘ҠжҳҜдҪғеҶңйҮ‘ж–ҜйЎҝпјҢжқҘиҮӘжүҳиҸІе°”еҫ·В·йңҚе°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ҸпҪҷпҪҶпҪүпҪ…пҪҢпҪ„ пјЁпҪҒпҪҢпҪҢпјүпјҢд»–жҺ§е‘ҠйўҶдё»еҗүжң¬гҖӮж¶үжЎҲеңҹең°дёәдёҖеқ—е®…ең°гҖҒдёҖдёӘиҠұеӣӯе’Ңпј•пјҺпј•иӢұдә©иҚүең°пјҢжүҖиҜүеңҹең°жқҘиҮӘд»–е·Із»ҸиҝҮдё–зҡ„зҲ¶дәІпјҢд»–зҗҶеә”еҫ—еҲ°з»§жүҝжқғгҖӮеҺҹе‘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ё»еј еҫ—еҲ°дәҶеә„еӣӯдҪғжҲ·йҷӘе®Ўеӣўзҡ„ж”ҜжҢҒпјҢиҖҢйўҶдё»еҗүжң¬еңЁжі•еәӯдёҠеҸҚеӨҚж— еёёпјҢеүҚеҗҺзҹӣзӣҫпјҢеј•иө·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зҡ„дёҚж»ЎпјҢвҖңйўҶдё»еңЁдёҺеҺҹе‘Ҡзҡ„еҜ№жҠ—дёӯеӨ„еўғдёҚдҪівҖқгҖӮеҺҹжЎЈжЎҲжІЎжңүз•ҷдёӢе®Ңж•ҙзҡ„иҝҮзЁӢе’Ңз»“жһңпјҢдҪҶж јйӣ·еҜ№иҜҘжЎҲдҫӢзҡ„дёҖж®өеҲҶжһҗйўҮеҖјеҫ—жҖқиҖғпјҡвҖңжң¬жЎҲдёӯеҺҹе‘ҠдёҺиў«е‘ҠжҸҗдәӨзҡ„дёҖзі»еҲ—зҡ„иҜүд№ҰиЎЁжҳҺпјҢ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Ҝ№еҫ…йўҶдё»е’ҢдҪғжҲ·зҡ„жҖҒеәҰиҫғдёәе…¬е…ҒгҖӮ然иҖҢпјҢеҰӮжһңйўҶдё»жғій’»з©әеӯҗпјҢ他们дјҡжңүеҫҲеӨҡеҠһжі•еҸҜд»ҘйҖғйҒҝжҢҮжҺ§пјҢеңЁ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дёӢдҪғжҲ·йҖҡиҝҮеә„еӣӯжғҜдҫӢзЎ®и®ӨзңҹзӣёгҖҒи°ӢжұӮе…¬жӯЈзҡ„иҜүжұӮпјҢе°ұдјҡеҸҳеҫ—еӣ°йҡҫйҮҚйҮҚгҖӮвҖқ
е®һйҷ…дёҠд№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дёҖиҲ¬иҜҙжқҘпјҢеңЁжі•еәӯдёҠдҪғжҲ·жҖ»жҳҜеұһдәҺејұеҠҝдёҖж–№гҖӮеҮәиҮӘ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пјҲпјҙпҪҲпҪ…пјЈ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 пҪҸпҪҶ пјІпҪ…пҪ‘пҪ•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“пјүзҡ„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еңЁе…ідәҺе…¬з°ҝ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дәүи®®дёӯпјҢйўҶдё»жҗәе°Ғе»әеҲ¶д№ӢдҪҷеЁҒпјҢжҖ»жҳҜеҠӣеӣҫжү©еӨ§е…¶еңЁж··еҗҲ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дёӯзҡ„д»ҪйўқпјҢдҫөе®ідҪғеҶңжқғзӣҠиҝӣиҖҢдёәеңҲең°еҲӣйҖ жқЎд»¶пјӣдҪғжҲ·дёҖж–№еҲҷжҳҜеҖҫеҠӣжҠөжҠ—пјҢдёҚиӮҜйҖҖи®©гҖӮеҲ©иҫҫе§Ҷжӣҫзј–иҫ‘еҮәзүҲдәҶпј‘пј’еҚ·еЎһе°”зҷ»еҚҸдјҡпјҲпјіпҪ…пҪҢпҪ„пҪ…пҪҺ пјіпҪҸпҪғпҪүпҪ…пҪ”пҪҷпјүзҡ„жі•еәӯж–Үжң¬пјҢе…¶дёӯдёӨ件公з°ҝжҢҒжңүжЎҲдҫӢйўҮдёәе…ёеһӢгҖӮе…¶дёӯ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жқҘиҮӘдәҺдәЁе»·йЎҝйғЎзҡ„йҳҝдјҜзү№еҲ©жҷ®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ӮпҪӮпҪҸпҪ” пјІпҪүпҪҗпҪ”пҪҸпјү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“е№ҙпјҢдҪғеҶңжҢҮжҺ§йўҶдё»д»Ҙж®ӢеҝҚзҡ„жүӢж®өеӨәиө°дәҶйғЁеҲҶдҪғжҲ·зҡ„е…¬з°ҝпјҢе°Ҷ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пјҲпҪғпҪ•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ҚпҪҒпҪ’пҪҷ пҪ”пҪ…пҪҺпҪ•пҪ’пҪ…пҪ“пјүжҚўжҲҗдәҶпј”пјҗе№ҙеҘ‘зәҰжүҝз§ҹпјҲпҪҶ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ҷпјҚпҪҷпҪ…пҪҒпҪ’ пҪҢпҪ…пҪҒпҪ“пҪ…пҪ“пјүгҖӮйўҶдё»иҫ©з§°пјҢиҝҷдәӣжқ‘ж°‘жҢҒжңүе…¬з°ҝеҸӘжңүпј’пјҗе№ҙеҺҶеҸІпјҢ他们其е®һжҳҜж„Ҹж„ҝдҝқжңүеҶңгҖӮ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»Қ然жҳҜдәүи®®зҡ„ж ёеҝғпјҢдёәжӯӨпјҢ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жҙҫеҮәдёӨдҪҚдё“е‘ҳиҝӣе…Ҙеә„еӣӯжҹҘиҜўгҖӮеҸҜжҳҜе‘ҲзҺ°еңЁзҫҠзҡ®зәёдёҠзҡ„иҜҒиҜҚзӣёдә’зҹӣзӣҫпјҢдёҚи¶ід»Ҙи§ЈејҖи°ңеӣўгҖӮ继иҖҢдёӨдҪҚдё“е‘ҳжҹҘиҜў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ж–ҮзҢ®иҜҒжҚ®пјҢеҸ‘зҺ°зҗҶжҹҘдәҢдё–ж—¶д»ЈпјҲпј‘пј“пј—пј—пјҚпј‘пј“пјҷпјҷе№ҙеңЁдҪҚпјүзҡ„ж—§еҚ·е®—жҲҗдёәи§ЈеҶіжЎҲ件зҡ„е…ій”®гҖ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жҠ«йңІпјҢеҪ“ең°зҡ„е…¬з°ҝеҲ¶еҮәзҺ°еңЁзҲұеҫ·еҚҺеӣӣ世第21е№ҙпјҲ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‘е№ҙпјүд»ҘеҗҺпјҢеӨ§еӨҡж•°еҲҷеҮәзҺ°еңЁдәЁеҲ©е…«дё–第26е№ҙпјҲ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”е№ҙпјүпјҢжҚ®жӯӨжі•еәӯж–ӯе®ҡеҺҹе‘Ҡзҡ„е…¬з°ҝиө„ж јжҺҲдәҲж—¶й—ҙз”ҡзҹӯпјҢдёҚи¶ід»ҘеҸ—еҲ°жҷ®йҖҡжі•дҝқжҠӨпјҢеӣ жӯӨд»Қ然и®Өе®ҡдёәж„Ҹж„ҝеҶңгҖӮжі•еәӯзҡ„ж„Ҹеҗ‘жҳҫ然жҜ”иҫғиӢӣеҲ»пјҢйўҶдё»иҰҒжұӮд»Ҙпј”пјҗе№ҙеҘ‘зәҰе•ҶдёҡеҮәз§ҹеҸ–д»Ј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пјҢжі•еәӯеҚҙиҰҒжҢүз…§ж„Ҹж„ҝең°жқЎд»¶ж”¶еӣһеңҹең°гҖӮеҜ№жӯӨпјҢиӢұеӣҪеҸІеӯҰ家AпјҺиҗЁж–ҮиҜ„и®әиҜҙпјҡвҖңзңӢдёҠеҺ»пјҢеҸҚиҖҢжҳҜйўҶдё»еңЁдәӢеҗҺжҢҪж•‘дәҶиҝҷдәӣдҪғжҲ·зҡ„зҒӯйЎ¶д№ӢзҒҫгҖӮвҖқдё»дҪғеҸҢж–№еҰҘеҚҸеҗҺпјҢйӮЈдәӣдҪғеҶңдёҚеҫ—дёҚеҗ‘йўҶдё»дҪҺеӨҙпјҢжҺҘеҸ—жңүе№ҙйҷҗзҡ„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пјҢйўҶдё»иғңиҜүгҖӮиҝҷж„Ҹе‘ізқҖпј”пјҗе№ҙеҗҺйўҶдё»еҸҜд»ҘеҗҲжі•ең°ж”¶еӣһеңҹең°пјҢжҲ–еңҲеҚ жҲ–иҪ¬з§ҹе…ЁеҮӯе…¶еҶіе®ҡгҖӮиҗЁж–ҮеңЁеј•еҮәдёҠиҝ°жЎҲдҫӢеҗҺжҢҮеҮәпјҢ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еЈ°з§°е®ғд»Ғж…Ҳең°дҝқжҠӨдҪғеҶңзҡ„еҲ©зӣҠ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вҖңжі•еәӯеҜ№дәҺйўҶдё»еҲ©зӣҠзҡ„жҖҒеәҰжҳҜеҫ®еҰҷзҡ„вҖқгҖӮжҳҫ然дҪңиҖ…еңЁе©үиҪ¬ең°жү№иҜ„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зҡ„е…¬жӯЈжҖ§гҖӮ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зҡ„зЎ®еӯҳеңЁеҺӢеҲ¶иҙөж—ҸеҠҝеҠӣзҡ„еҖҫеҗ‘пјҢдёҚиҝҮпјҢеӨ§еҚғдё–з•ҢпјҢдә”еҪ©зјӨзә·пјҢд»ҺжқҘдёҚиғҪдёҖжҰӮиҖҢи®әгҖӮ
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і•еҫӢ规е®ҡжҳҜеңҹең°е®үе…Ёзҡ„еҹәзЎҖпјҢдёәжӯӨйўҶдё»еҸҜи®ҫжі•ж”№еҸҳдҪғеҶңдҝқжңүең°жқЎд»¶пјҢд»ҺиҖҢеҲ©з”Ёжі•еҫӢиҫҫеҲ°еңҲеҚ еңҹең°зҡ„зӣ®зҡ„гҖӮеҖҳиӢҘе°Ҷжңү继жүҝжқғзҡ„е…¬з°ҝең°ж”№дёәз»Ҳиә«жҲ–пј’пјҗе№ҙгҖҒпј‘пјҗе№ҙдҝқжңү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ж— ејӮдәҺ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гҖӮ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жүҖи®°еҪ•зҡ„еңҹең°жҳ“дё»иҙ№пјҢи®°еҪ•дәҶеҶңж°‘зҡ„дҝқжңүжңҹйҷҗпјҢд№ҹжҳҜ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ңүж•ҲжңҹпјҢвҖңиҝҷдёҖжғ…еҶөдёәеҶңж°‘зҡ„дҝқжңүең°пјҲпҪ”пҪ…пҪҺпҪ…пҪҚпҪ…пҪҺпҪ”пҪ“пјүеўһж·»дәҶдёҖд»Ҫж–°зҡ„гҖҒйҮҚиҰҒзҡ„жі•еҫӢж„Ҹд№үвҖқгҖӮиҫҫжӢүи°ҹзҡ„ж•ҷдјҡең°дә§еҚіеұһжӯӨдҫӢгҖӮиҜҘең°дә§дҪҚдәҺиӢұж је…°дёҺиӢҸж је…°дәӨз•ҢпјҢз”ұдәҺжүҝжӢ…еҶӣдәӢеҪ№еҠЎпјҢй•ҝжңҹдә«еҸ—дҪҺйўқд№ жғҜең°з§ҹе’Ңеңҹең°з»§жүҝжқғзӯүжғҜдҫӢгҖӮзҺ°еңЁж•ҷдјҡйўҶдё»жү§ж„ҸжҠҠжңү继жүҝжқғзҡ„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еҲ¶иҪ¬еҢ–дёәеҘ‘зәҰз§ҹдҪғеҲ¶пјҢдёәжӯӨ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ҳе№ҙж•ҷдјҡеЁҒиғҒе°Ҷеңҹең°еҸҰз§ҹд»–дәәпјҢеҺҹдҪғеҶңеҝ…йЎ»ж”Ҝд»ҳзӣёеҪ“дәҺеңҹең°е№ҙ收е…ҘпјҷпјҚпј‘пјҗеҖҚзҡ„йҮ‘йўқжүҚиғҪиөҺеӣһгҖӮдҪғеҶңжӢ’з»қпјҢдёӨж¬Ўй—№еҲ°дәҶжһўеҜҶйҷў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—пј—е№ҙжһўеҜҶйҷўжі•еәӯж‘ҶеҮәдёӨеҘ—ж–№жЎҲпјҢеҹәжң¬иҰҒжұӮе·®дёҚеӨҡ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еӨ§е№…еәҰжҸҗеҚҮеңҹең°жҳ“дё»иҙ№пјҢеңҹең°з»§жүҝд№ҹйҷ„еҠ дәҶжқЎд»¶пјҢеҗҰеҲҷйўҶ主收еӣһеңҹең°гҖӮең°з§ҹйҡҸеёӮеңәеҢ–иҖҢдёҠж¶ЁпјҢ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ўһж·»дәҶеӨұж•ҲжңҹпјҢеӯҳеңЁ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Құйҷ©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°ұжңүпј“жҲ·дҪғеҶңеӨұеҺ»еңҹең°гҖӮиҝҳжңүзҡ„йўҶдё»еңЁжі•еәӯдёҠе·§иЁҖд»ӨиүІпјҢж”№еҸҳдәҶдј з»ҹзҡ„жҳ“дё»иҙ№гҖӮеҪ“然пјҢд№ҹжңүеҶңж°‘еңЁжі•еәӯдёҠдёҚе®Ҳ规зҹ©зҡ„жғ…еҶөпјҢжңҖеҗҺеҫ—дёҚеҒҝеӨұпјҡеҹғе…ӢеЎһзү№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ҳпҪ…пҪ”пҪ…пҪ’пјүзҡ„дҪғжҲ·еҸ‘дјӘиӘ“иҮӘз§°жҳҜзҙўе…ӢжӣјпјҢиҮӘз”ұеңҹ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пјҢеҫҲеҝ«и°ҺиЁҖиў«жҸӯйңІпјҢиў«еӨ„д»Ҙпј“пјҗе…Ҳд»Өзҡ„зҪҡйҮ‘гҖӮ
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ҹй—ҙж”ҝеәңеҸёжі•жңәжһ„иӮҜе®ҡеҸ‘жҢҘдәҶдҪңз”ЁпјҢдёҚиҝҮе®ғзҡ„жңүж•ҲжҖ§д»ӨдәәжҖҖз–‘гҖӮдёҚе°‘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и®®иҖҢдёҚеҶіпјҢеҶіиҖҢдёҚиЎҢпјҢдҫӢеҰӮпјҢ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жі•жҒ©зҷ»еә„еӣӯпјҲпјҰпҪүпҪҺпҪ…пҪ„пҪҸпҪҺпјүжқ‘ж°‘дёҺдёӨд»ЈйўҶдё»д№Ӣй—ҙдәүи®јпјҢжҢҒз»ӯдәҶпј“пјҗе№ҙпјҢд»Қ然дёҚдәҶдәҶд№ӢгҖӮиҮӘ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ҷе№ҙйўҶдё»й»ҳе°”зҙўеңҲеҚ дёҖйғЁеҲҶе…¬ең°е’ҢдёҖжқЎдҫӣжқ‘民们йҖҡиЎҢзҡ„з”°еҹӮпјҢ并йҘІе…»еӨ§йҮҸе…”еӯҗжҜҒеқҸжқ‘ж°‘и°·зү©пјҢжқ‘ж°‘жҸҗеҮәжҢҮжҺ§еҗҺпјҢзҺӢе®Ө委е‘ҳдјҡпјҲпјІпҪҸпҪҷпҪҒпҪҢ пјЈпҪҸпҪ•пҪҺпҪғпҪүпҪҢпјүе‘Ҫд»Ө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пјҢеҸҜйўҶдё»й»ҳе°”зҙўжӢ’з»қжү§иЎҢпјҢзӣёеҸҚиҝҳ继з»ӯжү©еӨ§еңҲең°гҖӮеҸҲпјҢдёҖд»ҪзҺӢе®ӨдҝЎеҮҪдёҘзҰҒжҠ¬й«ҳеңҹең°жҳ“дё»иҙ№пјҢеҸҜй»ҳе°”зҙўзҪ®иӢҘзҪ”й—»пјҢиҝҳжҳҜе°Ҷжҳ“дё»иҙ№жҸҗй«ҳдәҶдёҖеҖҚгҖӮйўҶдё»й»ҳе°”зҙўиҝҳиў«жҢҮжҺ§иҝҮеәҰз Қдјҗ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е…¬е…ұжһ—ең°зӯүпјҢдёәжӯӨ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з»„жҲҗдёҖдёӘең°ж–№е§”е‘ҳдјҡејәиҝ«еҸҢж–№е’Ңи§ЈпјҢз»“жһңдёҚдҪҶжІЎжңүи§ЈеҶій—®йўҳиҝҳеј•еҸ‘дәҶжӣҙеӨҡзҡ„еҶІзӘҒгҖӮеҸҜи§ҒеӣҪзҺӢжі•еәӯжқғеЁҒжҖ§дёҚи¶ігҖҒзјәд№Ҹжү§иЎҢеҠӣеәҰгҖӮжі•еҫӢжё йҒ“дёҚз•…йҖҡпјҢд№ҹжҳҜеј•еҸ‘жҡҙеҠӣиЎҢдёә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
пј“пјҺејәеҲ¶жҖ§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пјҲпјҘпҪҺпҪғпҪҢпҪҸпҪ“пҪ•пҪ’пҪ… пҪӮпҪҷ пјЈпҪҸпҪҚпҪҗпҪ•пҪҢпҪ“пҪҸпҪ’пҪҷпјү
ејәеҲ¶жҖ§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еҚіж— и§Ҷе’Ңи·өиёҸ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еҮӯеҖҹејәжқғе’Ң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пјҢе…¶е…ій”®иҜҚжҳҜвҖңйқһжі•вҖқдәҢеӯ—пјҢе®Ңе…ЁжҳҜиҙҹйқўж„Ҹд№үзҡ„иЎҢдёә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ұЎзӮ№гҖӮвҖң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вҖқвҖң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вҖқе’ҢвҖ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вҖқдёҖиҲ¬жҳҜе’Ңе№ізҡ„пјҢдёҚжҺ’йҷӨеңЁжҹҗдәӣжғ…еҶөдёӢдјҡеҮәзҺ°ејәеҲ¶зҺ°иұЎпјҢдёҚиҝҮжҖ»зҡ„зңӢжҳҜдёҖз§Қз»ҸжөҺиЎҢдёәгҖҒеҘ‘зәҰиЎҢдёәпјҢйҖҡеёёеңЁеҗҲжі•иҢғеӣҙеҶ…гҖӮйўҶдё»ејәеҲ¶жҖ§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жҳҜи¶…з»ҸжөҺзҡ„ејәеҲ¶пјҢжҳҜйҮҺиӣ®зҡ„е’Ңз ҙеқҸжҖ§зҡ„пјҢжҝҖиө·жқ‘ж°‘зҡ„жҖЁжҒЁпјҢеј•иө·зӨҫдјҡзҡ„е№ҝжіӣи°ҙиҙЈпјҢ并дёәзҺ°д»Јж–ҮжҳҺзӨҫдјҡжүҖдёҚйҪҝгҖӮиҷҪ然йқһжі•й©ұйҖҗдҪғеҶңзҺ°иұЎдёҚ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еёёжҖҒпјҢдҪҶжҜ•з«ҹ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йҮҚиҰҒдёҖ幕пјҢеҶҚзҺ°дәҶдёӯдё–зәӘйўҶдё»еҶ·й…·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д№ҹжҡҙйңІдәҶж—©жңҹиө„жң¬зҡ„еӨұиҢғдёҺиҙӘе©ӘгҖӮ
иҝҷзұ»еңҲең°еӨҡжҳҜеҜ№еә„еӣӯе…¬ең°зҡ„еңҲеҚ 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ҷе№ҙпјҢ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жі•жҒ©зҷ»еә„еӣӯпјҲпјҰпҪүпҪҺпҪ…пҪ„пҪҸпҪҺпјүйўҶдё»еңҲеҚ йғЁеҲҶе…¬ең°е’ҢйңёеҚ дёҖжқЎйҖҡйҒ“зҡ„иЎҢдёәпјҢиӮҜе®ҡжҳҜйқһжі•зҡ„пјҢжүҖд»Ҙжқ‘ж°‘жҺ§е‘ҠеҗҺзҺӢе®Ө委е‘ҳдјҡдёӢиҫҫдәҶ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зҡ„е‘Ҫд»ӨгҖӮиҜҘйўҶдё»иҝҳжҡҙеҠӣдҫөеҚ дёҖеқ—еҺҹеұһдҪғеҶңдәЁеҲ©В·еЎһе°”жҜ”зҡ„жһ—ең°пјҢеёҰйўҶпјҳеҗҚжӯҰиЈ…дәәе‘ҳиҝӣе…ҘпјҢеӣ жӯӨйҒӯеҲ°иҜҘдҪғжҲ·зҡ„жҢҮжҺ§гҖӮжҚ®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гҖӢи®°иҪҪпјҢдёҖдә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еҮ д№Һе°ұжҳҜиөӨиЈёиЈёең°жҺ еӨәгҖӮеңЁ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пјҢж јйӣ·иҫӣеҺ„е§Ҷеә„еӣӯпјҲпј§пҪ’пҪ…пҪ“пҪ“пҪүпҪҺпҪҮ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е’Ңжүҳе»·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ҸпҪ”пҪ”пҪүпҪҺпҪҮ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еҗҢеұһдёҖдёӘйўҶдё»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“пјҚпј‘пј•пј•пј”е№ҙпјҢиҜҘ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еңҲеҚ жқ‘еә„зҡ„иҚ’ең°пјҢвҖңж®ӢеҝҚең°еүҘеӨәдәҶдҪғеҶң们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вҖқгҖӮз”ұдәҺдёҚж–ӯ收еҲ°дҪғеҶңзҡ„жҠұжҖЁпјҢ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зҡ„еүҜйғЎй•ҝд»»е‘ҪдәҶдёҖдёӘ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пјҢдё“дәӢи°ғжҹҘдҫөеҚ иҚ’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д»…д»Ҙ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дёәдҫӢпјҢиҪҪе…ҘеҸІеҶҢзҡ„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дәӢ件пјҢиҝҳеҸ‘з”ҹеңЁйңҚйӣ·жҙӣеә„еӣӯпјҲпјЁпҪҸпҪ’пҪ…пҪҢпҪҸпҪ—пҪ…пјүгҖҒиҫҫе°”ж–Үеә„еӣӯпјҲпјӨпҪҒпҪ’пҪ—пҪ…пҪҺпјүд»ҘеҸҠдјҠдёҪиҺҺзҷҪж—¶жңҹзҡ„з‘һеҫ·пјҲпјІпҪ…пҪҒпҪ„пјүгҖҒжІғж–ҜйЎҝпјҲпј·пҪҸпҪ’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гҖҒеҪ“е“Ҳе§ҶпјҲпјӨпҪҸпҪ—пҪҺпҪҲпҪҒпҪҚпјүе’ҢиҺ«еҲ©пјҲпјӯпҪ…пҪҒпҪ’пҪҢпҪ…пҪҷпјүеә„еӣӯ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јҚе°”ж–ҜйЎҝпјҲпј·пҪҸпҪҸпҪҢпҪ“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гҖҒеҚҡе°”йЎҝпјҲпј°пҪҸпҪ•пҪҢ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гҖҒзҡ®е…Ӣж–Ҝж•ҰпјҲпјІпҪүпҪҳ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дёү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дәӨз•ҢеӨ„пјҢжңүеӨ§зәҰпј•пјҗпјҗиӢұдә©зҡ„иҚ’ең°е’ҢжІјжіҪең°иў«йўҶдё»дҫөеҚ пјҢеӣ жӯӨ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”е№ҙдҪғеҶң们иҰҒжұӮжҒўеӨҚиҝҷзүҮ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гҖӮзЁҚжҷҡдёҖдәӣпј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‘е№ҙпјҢжө·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ЁпҪ…пҪҷ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жІјжіҪең°д№ҹиў«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еңҲеҚ пјҢжӯӨеүҚжӣҫжңүдҪғеҶңеӣҙеңҲдәҶйғЁеҲҶжІјжіҪең°пјҢзҺ°иў«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жӢҶйҷӨзҜұз¬Ҷ并й©ұйҖҗдәҶдҪғеҶңжң¬дәәгҖӮ
дёҖзӣҙеҲ°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ң«пјҢдёҚж–ӯжңү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еҸ‘з”ҹгҖӮ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иҙқе°”йЎҝж•ҷеҢәпјҲпјўпҪ…пҪҢ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е№¶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еј•еҸ‘жқ‘ж°‘ејәзғҲдёҚж»Ў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ҷпјҷе№ҙйўҶдё»з«ҹ然ејәиЎҢеңҲеҚ иҖ•ең°пјҢеҶҚж¬Ўиў«жқ‘ж°‘жҺ§е‘ҠпјҡйўҶдё»д»ҺдҪғеҶңж•һз”°дёӯејәиЎҢеӣҙеңҲдәҶпј‘пј“пјҚпј‘пј”йӣ…еҫ·еңҹең°пјҢдҪҝдҪғеҶңд»¬ж— жі•еғҸиҝҮеҺ»йӮЈж ·жңүеәҸзҡ„иҖ•дҪңгҖӮиҝҷдәӣиў«ејәиЎҢеӨәиө°зҡ„еңҹең°еҸҳжҲҗйўҶдё»зӢ¬еҚ зҡ„иҚүеңәпјҢд»–дәәдёҚиғҪиҝӣе…ҘгҖӮиҜҘйўҶдё»иҝҳйј“еҠЁе…¶д»–дҪғеҶңе’ҢеҶңеңәдё»еӣҙеңҲеңҹең°пјҢеҸҳиҖ•ең°дёәзү§еңәгҖӮеӨ§йқўз§Ҝ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еҫҖеҫҖеҜјиҮҙ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иҝҷжҳҜ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дёҖдәӣеҶңж°‘еҸӮеҠ дәҶеҮҜзү№иө·д№үзҡ„еҺҹеӣ д№ӢдёҖгҖӮдәӢеҸ‘еүҚиҗЁй»ҳиөӣзү№е…¬зҲөжӣҫиҜ•еӣҫзј“и§ЈеҶңж°‘зҡ„дёҚж»Ўжғ…з»ӘпјҢйўҒеёғдәҶдёҖйЎ№еҸҚеңҲең°е®ЈиЁҖпјҢе‘Ҫд»Өе…¬ең°еҝ…йЎ»йҮҚж–°ејҖж”ҫпјҢеҸҜеҫҲе°‘з”ҹж•ҲпјҢжүҖд»ҘеҶңж°‘иө·д№үиҝҳжҳҜзҲҶеҸ‘дәҶгҖӮеҜ№дәҺжӯӨең°зҹӣзӣҫжҝҖеҢ–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еҸІжҳҜиҝҷж ·и§ЈйҮҠзҡ„пјҡвҖң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зҡ„е…¬ең°еңҲеҚ з»ҷдёҖдәӣе°ҸеҶңеёҰжқҘз—ӣиӢҰпјҢеӣ дёәжӢүзү№е…°жҳҜдёҖдёӘзәҜзІ№зҡ„еҶңдёҡең°еҢәпјҢжІЎжңүе·ҘдёҡеҹҺй•ҮпјҢеӨұдёҡзҡ„еҶңж°‘ж— еӨ„е®үзҪ®гҖӮвҖқжӢүзү№е…°е’ҢеүҚиҝ°е…°ејҖеӨҸпјҢдҪҚдәҺиӢұж је…°дёӯйғЁпјҢзҡҶеұ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йҮҚзӮ№ең°еҢәпјҢ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гҖӢиҜҒжҳҺпјҢеңЁиҝҷдәӣең°еҢәйўҶдё»ејәиЎҢдҫөеҚ е…¬ең°зҡ„жғ…еҶө并дёҚе°‘и§ҒгҖӮ
еҸ‘з”ҹеңЁе·ҙж јжӢүеӨ«еә„еӣӯпјҲпјўпҪҒпҪҮпҪҮпҪ’пҪҒпҪ–пҪ…пјү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иӮҜе®ҡжҳҜдёҖжЎ©жҡҙеҠӣ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пјҢиҖҢдё”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规模пјҢеҗҺз»ҸдҪғжҲ·иө·иҜүиҖҢз»ҲжӯўгҖӮзҺӢе®Ө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зҡ„жҲҗе‘ҳ们жҢҮеҮә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җе№ҙпј‘пј‘жңҲпј–ж—ҘпјҢдҝ®йҒ“йҷўй•ҝзәҰзҝ°В·еҪӯе°јеңЁе·ҙж јжӢүеӨ«еә„еӣӯеңҲеӣҙпј’пј‘пј–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пјҢе°Ҷд№ӢеҸҳжҲҗзү§еңәпјҢ摧жҜҒпј•жҲ·дҪҸе®…е’Ңпј’й—ҙеҶңиҲҚпјҢеҗҢж—¶е°Ҷпј“пјҗдәәиө¶еҮә家еӣӯгҖӮ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жҳҜж•ҙдёӘеә„еӣӯзҡ„еӣӣеҲҶд№ӢдёҖпјҢжҺҘдёӢжқҘеҸҲеңҲеӣҙдәҶеә„еӣӯзҡ„еү©дҪҷйғЁеҲҶ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җпј‘е№ҙпј‘пјҗжңҲйўҶдё»еҪӯе°јеҸҲеӣҙеңҲдәҶдҝ®йҒ“йҷўжүҖиҫ–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еә„еӣӯжҹҜе…ӢжҜ”马жҙӣйҮҢпјҲпј«пҪүпҪ’пҪӢпҪӮпҪҷ пјӯпҪҒпҪҢпҪҢпҪҸпҪ’пҪҷпјүпјҢжҜҒжҺүпј“жҲ·еҶңе®…пјҢеңҲеӣҙдәҶпј‘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е№¶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пјҢпј‘пјҳдәәиў«й©ұйҖҗпјҢпј•еј зҠҒиў«ејғзҪ®гҖӮпј’пј“е№ҙеҗҺпјҢдҝ®йҒ“йҷўй•ҝ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иЎҢеҫ„йҒӯеҲ°дҪғжҲ·д»¬иө·иҜүпјҢжңҖеҗҺдҝ®йҒ“йҷўй•ҝиў«иҝ«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пјҢеӨҚиҖ•пј‘пјҳпјҗиӢұдә©еңҹең°пјҢ并дҝ®еӨҚжҜҒеқҸзҡ„пј“жҲ·дҪҸе®…гҖӮжі•еәӯжЎЈжЎҲжІЎжңүе…·дҪ“иҜҙжҳҺйўҶдё»дҫөзҠҜдҪғеҶңеҗҲжі•жқғзӣҠзҡ„е…·дҪ“иҝҮзЁӢпјҢ然иҖҢйўҶдё»иҙҘиҜү并被иҝ«жӢҶйҷӨеңҲең°еӣҙзҜұзҡ„еҲӨеҶіи¶ід»ҘиҜҒжҳҺйўҶдё»еұ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пјҢиҖҢдё”жңүжҳҺжҳҫзҡ„жҡҙеҠӣиЎҢдёәгҖ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дёӯеёёеёёжңүйўҶдё»иҙҘиҜүеӣ иҖҢдёӯжӯўеңҲең°зҡ„и®°еҪ•пјҢиЎЁжҳҺ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е№¶йқһжҖ»иғҪеҫ—йҖһгҖӮ
дёҖдәӣжЎҲдҫӢиЎЁжҳҺпјҢ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ж—¶йӣҮз”ЁдёҖдәӣдёҚиүҜеҲҶеӯҗжҡҙеҠӣеЁҒиғҒпјҢиҝҳдҪҝз”ЁдёҖдәӣж¬әйӘ—жүӢж®ө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пјҢиӢҸеЎһе…Ӣж–ҜйғЎпјҢйўҶдё»пјӘпјҺеё•й»ҳд»ҺеӣҪзҺӢйӮЈйҮҢиҙӯеҫ—еҹғе…ӢиҺұж–Ҝзҷ»еә„еӣӯпјҲпјҘпҪғпҪғпҪҢпҪ…пҪ“пҪ„пҪ…пҪҺпјүпјҢиҝӣе…ҘеҗҺе°ұејәеҚ дәҶжқ‘ж°‘зҡ„дёҖдёӘ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гҖӮ继иҖҢжҠҠеә„еӣӯдёҖеқ—е…¬ең°еҸҳдёәз§Ғ家йұјеЎҳгҖӮдёӢдёҖжӯҘеҲҷеӣҙеңҲдҪғжҲ·иҖ•ең°пјҢйўҶдё»её•й»ҳд»Ҙеңҹең°зҪ®жҚўдёәеҗҚзӯҫдёӢеҗҲеҗҢпјҢе®һдёәжҺ еӨәиүҜз”°гҖӮд»–й©ұиө¶дёҖйғЁеҲҶе…¬з°ҝеҶңзҰ»ејҖеҺҹжҢҒжңүең°пјҢејәиҝ«д»–们жҺҘеҸ—иҙ«зҳ еңҹең°пјҢдёҚд»…йқўз§Ҝе°ҸдәҶпјҢиҖҢдё”жІЎд»Җд№Ҳд»·еҖјпјҢдҪғеҶңзҡ„жҲҝеұӢд№ҹиў«ејәеҚ гҖӮеӨұеҺ»еңҹең°зҡ„еҶңж°‘жІЎжңүиҺ·еҫ—д»»дҪ•иЎҘеҒҝпјҢжІҰдёәиөӨиҙ«пјҢдёҚеҫ—дёҚзҰ»ејҖгҖӮдёҖдәӣеӨ§иғҶдәӣзҡ„дҪғеҶңжӢ’з»қжңҚд»ҺпјҢйўҶдё»е°ұйӣҮдҪЈдәҶдёҖдәӣжҒ¶дәәжүӢжҢҒжЈҚжЈ’пјҢй—Ҝе…ҘдҪғжҲ·е®¶йҮҢиғҒиҝ«д»–们зҰ»ејҖпјҢеё•й»ҳж— иҖ»ең°е–ҠйҒ“пјҡвҖңдҪ 们зҹҘйҒ“еӣҪзҺӢе·Із»ҸжӢҶжҜҒдәҶдҝ®йҒ“йҷўеҗ—пјҹж—¶еҖҷеҲ°дәҶпјҢзҺ°еңЁиҜҘжҳҜжҲ‘们иҝҷдәӣз»…еЈ«жӢҶжҜҒдҪ 们иҝҷдәӣеҮәиә«дҪҺиҙұзҡ„дәәзҡ„жҲҝеұӢдәҶпјҒвҖқ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йўҶдё»д»—еҠҝж¬әдәәпјҢйқһжі•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гҖӮж— иҖ»зҡ„жҳҜпјҢйўҶдё»еҲ©з”ЁйӮЈдёӘж¬әйӘ—жҖ§зҡ„иҝҒеҫҷеҚҸи®®пјҢиҮҙдҪҝдҪғжҲ·д»¬зҡ„жҺ§е‘ҠдёҚиғҪжҲҗз«Ӣ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•е№ҙпјҢдҪғжҲ·д»¬иө·иҜүеҲ°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пјҢйўҶдё»дёҚеҗҰи®Ө他们жҳҜе…¬з°ҝеҶңпјҢ并дә«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е®үе…ЁпјҢд№ӢжүҖд»Ҙй©ұйҖҗ他们жҳҜеӣ е…¶ж’•жҜҒеҗҲеҗҢзҡ„иҝқзәҰиЎҢдёәгҖӮжүҖи°“вҖңеҗҲеҗҢвҖқе°ұжҳҜеүҚиҝ°ж¬әйӘ—жҖ§зҡ„еңҹең°зҪ®жҚўеҚҸи®®пјҢеҸҜйўҶдё»е°ұжҳҜеҮӯиҝҷдёӘеҒҮеҗҲеҗҢдҪҝдҪғжҲ·иҙҘиҜүгҖӮеҘҪеңЁеҺҹе‘ҠеҸҜд»ҘеңЁдёҚеҗҢжі•еәӯиө·иҜүпјҢеҗҺжқҘдёҖдёӘдҪғжҲ·е°ұиҜҘдәӢ件еҸҲеңЁдёҠи®ҝжі•еәӯиө·иҜүйўҶдё»пјҢз«ҹеҫ—иғңиҜүгҖӮжңҖз»ҲеӨ„зҗҶз»“жһңдёҚеҫ—иҖҢзҹҘпјҢ然иҖҢ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дәӢе®һд»ҘеҸҠдҪғеҶңжҠөжҠ—жҳҜжІЎжңүз–‘д№үзҡ„гҖӮж— зӢ¬жңүеҒ¶пјҢ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пјҢиҜәе…Ӣж–ҜиҫӣйЎҝеә„еӣӯпјҲпј«пҪҺпҪҸпҪ“пҪ“пҪүпҪҺпҪҮпҪ”пҪҸпҪҺпјүпјҢпј‘пј–пј‘пј‘е№ҙдёҖдёӘдҪғеҶңжҺ§е‘ҠйўҶдё»еңҲеҚ д»–зҡ„иҖ•ең°пјҢд№ҹжҳҜдҪҝз”ЁзҪ®жҚўеңҹең°зҡ„ж¬әйӘ—жүӢж®өпјҢеҫ…д»–еҸ‘зҺ°еҸ—йӘ—ж—¶пјҢиҜҘйўҶдё»е°ұйӣҮжқҘдёҖдәӣе“ҒиЎҢдёҚз«ҜиҖ…йҳ»жӯўд»–йҮҚиҝ”еҺҹжқҘ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жҳҫ然еҸ—еҲ°жі•еҫӢеҲ¶зәҰпјҢйўҶдё»е°ұйҮҮз”Ёж¬әйӘ—жүӢж®өеҲ¶йҖ еҒҮеҗҲеҗҢпјҢеӨ–еҠ жҡҙеҠӣеЁҒиғҒпјҢжҚҹдәәиҮӘиӮҘгҖӮ
е…¶е®һ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ж—©е·Іжңүд№ӢпјҢж—©еңЁ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°ұжңүиҝҷж ·зҡ„жЎҲдҫӢи®°еҪ•гҖӮжЎҲдҫӢд№ӢдёҖеҸ‘з”ҹеңЁпј‘пј”пјҳпј–пјҚпј‘пј”пјҷпј“е№ҙй—ҙпјҢеҺҹе‘ҠжҳҜдёҖдҪҚе…¬з°ҝеҶңпјҢе…¶еңҹең°дҝқжңүжқғеҸ—еҲ°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зҡ„дҫөе®івҖ”вҖ”вҖ”д»–йҒӯеҲ°дәҶйўҶдё»зҡ„й©ұйҖҗгҖӮеҺҹе‘Ҡдёәз»Ҳиә«е…¬з°ҝеҶңгҖӮд»–зјҙзәідәҶеңҹең°жҳ“дё»иҙ№пјҢ并еңЁжӯӨеҗҺжҢүж—¶зјҙзәіең°з§ҹпјӣд»–иҝҳжҠ•е…ҘдәҶдёҖдәӣиҙ№з”Ёж”№е–„еңҹең°пјҢз»“жһңиҝҳжҳҜиў«й©ұйҖҗгҖӮ第дәҢдёӘжЎҲдҫӢз”іиҜүиҮі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пјҢжҳҜеңЁпј‘пј•пјҗпјҗпјҚпј‘пј•пјҗпј‘е№ҙй—ҙпјҢеҺҹе‘ҠжҳҜдёҖдҪҚеҜЎеҰҮпјҢйҒӯеҲ°дәҶйўҶдё»зҡ„йқһжі•й©ұйҖҗгҖӮеҘ№е’ҢдёҲеӨ«жӣҫз»ҸиҒ”еҗҲдҝқжңүпјҲпҪҠпҪҸпҪүпҪҺпҪ” пҪ”пҪ…пҪҺпҪ•пҪ’пҪ…пјүдёҖеқ—еңҹең°пјҢдҝқжңүжңҹйҷҗдёәеӨ«еҰ»дәҢдәәз»Ҳиә«пјҲпҪҶпҪҸпҪ’ пҪ”пҪҲпҪ…пҪүпҪ’ пҪҢпҪүпҪ–пҪ…пҪ“пјүпјҢд№ҹжӣҫеҗ‘йўҶдё»ж”Ҝд»ҳдәҶжҳ“дё»иҙ№пј‘пјҗиӢұй•‘гҖӮдёҲеӨ«иҝҮдё–еҗҺпјҢиҝҷдҪҚеҜЎеҰҮеҚҙйҒӯеҲ°йўҶдё»й©ұйҖҗпјҢеҘ№ејәи°ғиҝҷжҳҜвҖңиҝқиғҢйўҶдё»жҺҲең°и§„еҲҷпјҲвҖҳпҪғпҪҸпҪҺпҪ”пҪ’пҪҒпҪ’пҪҷ пҪ”пҪҸ пҪҲпҪүпҪ“ пҪҸпҪ—пҪҺ пҪҮпҪ’пҪҒпҪҺпҪ”вҖҷпјүвҖқпјҢеӣ дёәжҢүз…§иҒ”еҗҲдҝқжңүзҡ„еҺҹеҲҷпјҢеҰ»еӯҗиҮӘеҠЁз»§жүҝдәЎеӨ«еңҹең°гҖӮ第дёүдёӘжЎҲдҫӢзҡ„жғ…еҶөдёҺ第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зұ»дјјгҖӮеҺҹе‘Ҡд№ҹжҳҜдёҖдҪҚ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з»Ҳиә«е…¬з°ҝеҶңпјҢд№ҹдҫқ规ж”Ҝд»ҳдәҶпј•иӢұй•‘еңҹең°жҳ“дё»иҙ№гҖӮеҺҹе‘ҠеңЁиҜүи®јд№Ұдёӯејәи°ғд»–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иў«дҫөе®іпјҢжӣҫеӨҡж¬Ўеҗ‘йўҶдё»з”іиҜ·иҮіе°‘йҖҖиҝҳдёҖйғЁеҲҶжҳ“дё»иҙ№е’Ңж”№е–„еңҹең°зҡ„жҠ•е…Ҙиҙ№пјҢ然иҖҢдёҖзӮ№иЎҘеҒҝд№ҹжІЎжңүеҫ—еҲ°е°ұиў«й©ұйҖҗдәҶгҖӮ
жң¬йғЁеҲҶд»ҘдёҠжЎҲдҫӢйғҪеұһдәҺ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йўҶдё»иҝқеҸҚз”ҡиҮіи·өиёҸдҪғжҲ·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йқһжі•й©ұйҖҗдҪғжҲ·гҖӮејәеҲ¶иЎҢдёәжңӘеҝ…йқһжі•пјҢ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гҖҒ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д»ҘиҮі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йғҪеҸҜиғҪдјҙйҡҸеҜ№иҝқзәҰж–№зҡ„ејәеҲ¶иЎҢдёәпјҢдҪҶжҳҜдёҺйқһжі•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ңүжң¬иҙЁжҖ§еҢәеҲ«пјҢдёҚе®№ж··ж·ҶгҖӮд»ӨдәәйҒ—жҶҫзҡ„жҳҜпјҢдёҚе°‘дёӯеӨ–еӯҰиҖ…еј•иҜҒзҡ„еңҲең°еҸІж–ҷд»…ж‘ҶеҮәеңҲең°йҖ жҲҗзҡ„з ҙеқҸжғ…еҶө并еҠ д»Ҙз—ӣж–ҘпјҢжІЎжңүеҒҡеҸҢж–№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қЎд»¶еҲҶжһҗ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еҒҡеҗҲжі•жҲ–йқһжі•зҡ„еҲӨж–ӯ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и®әдҪ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гҖӮдёҖдәӣеҺҹе§Ӣж–ҮзҢ®жң¬иә«д№ҹжҳҜж®Ӣзјәзҡ„пјҢеңЁеҪ“е№ҙеҸҚеҜ№еңҲең°зҡ„ж…·ж…ЁжҝҖжҳӮзҡ„е°ҸеҶҢеӯҗйҮҢпјҢеңЁ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дёӯпјҢд»ҘеҸҠдҝқз•ҷдёӢжқҘзҡ„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е’ҢйғЎеҸІдёӯ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й©ұйҖҗдҪғеҶңгҖҒз ҙеқҸеҶңиҲҚзҡ„ж•°еӯ—пјҢ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з ҙеқҸжҖ§зҡ„еңҲең°жЎҲдҫӢ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зӣёе…і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ҲҶжһҗе’Ңзјҳз”ұд»Ӣз»ҚпјҢжҮөжҮӮжҮӮд»Өдәәж— д»ҺзҪ®е–ҷгҖӮиө„ж–ҷж®ӢзјәеҸҜиғҪйҷҗеҲ¶дәҶдҪңиҖ…иҝӣдёҖжӯҘзҡ„еҲҶжһҗпјҢ然иҖҢе®ғдәӢе…і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д»·еҖјеҲӨж–ӯпјҢеӣ жӯӨд»Ҙ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й—®йўҳжҳҜдёҚеҸҜеӣһйҒҝзҡ„гҖӮ
д»ҘдёҠпјҢд»…е°ұжҲ‘们жҺҢжҸЎзҡ„иө„ж–ҷзңӢ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д»ҘеҗҲжі•еңҲең°дёәдё»пјҢ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гҖҒ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д»ҘеҸҠ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жҳҜйҖҡеёё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зЎ®е®һеӯҳеңЁпјҢдёҚиҝҮдёҚжҳҜе…¶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иҰҒж–№ејҸгҖӮ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ұЎзӮ№пјҢеҚҙдёҚ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 ҮиҜҶ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иҝҷз§ҚжҡҙеҠӣиЎҢдёәдёҖзӣҙеҸ—еҲ°жҠөеҲ¶е’Ңжү№иҜ„пјҢ并жңҖз»Ҳиў«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¬иә«жүҖжҠӣејғпјҢдёӢдёҖйҳ¶ж®өзҡ„еңҲең°е®Ңе…Ёиө°дёҠ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зҡ„жі•жІ»еҢ–иҪЁйҒ“гҖӮдё»жөҒиӢұеӣҪеҺҶеҸІеӯҰ家еҚЎзү№еӢ’пјҲпј·пјҺпјЁпјҺпјІпјҺпјЈпҪ•пҪ’пҪ”пҪҢпҪ…пҪ’пјүи®Өдёә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вҖңд»ҘеңҲең°дёәзӣ®зҡ„зҡ„йқһжі•й©ұйҖҗеҫҲе°‘и§ҒвҖқ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жҳҜеңҲең°йҮҚзӮ№ең°еҢәд№ӢдёҖпјҢиҜҘйғЎйғЎеҸІ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еҫҲе°ҸвҖқпјҢжӣҙеӨҡзҡ„жҳҜ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иҖҢдё”еҗҺиҖ…жҳҜеҸ‘еұ•и¶ӢеҠҝ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пјҢвҖңйўҶдё»дёҺдҪғжҲ·д№Ӣй—ҙзҡ„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жҷ®йҒҚвҖқпјҢд»ҘеҗҺзҡ„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зҡ„жЁЎејҸдёҚжҳҜеҒ¶з„¶зҡ„гҖӮ
жңҖеҗҺеҜ№еңҲең°йўҶдё»зҡ„жҰӮеҝөеҒҡдёҖз®ҖеҚ•иҜҙжҳҺгҖӮеңҲең°зҡ„йўҶдё»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йқҷжӯў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他们дёӯзӣёеҪ“дёҖйғЁеҲҶдәәе·Із»ҸдёҚжҳҜеҺҹжқҘж„Ҹд№үдёҠзҡ„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гҖӮеҰӮеё•е…ӢжҢҮеҮәзҡ„йӮЈж ·пјҡвҖңеӨ§еӨҡж•°еңҲең°зҡ„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пјҢе…¶е®һжҳҜвҖҰвҖҰж–°е…ҙиө·зҡ„зәҰжӣје’Ңе•ҶдәәпјҢ他们д»Һ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иҙӯзҪ®еңҹең°еҗҺжҲҗдёәд№Ўз»…пјҢиҝӣиҖҢжҲҗдёә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гҖӮвҖқжүҖд»ҘеҪ“жІ»е®үжі•е®ҳжҸҗдәӨеңҲең°иҖ…еҗҚеҚ•з»ҷ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ж—¶пјҢжүҖи°“зҡ„д№Ўз»…жҲ–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еҗҚеҚ•дёӯпјҢвҖңйҡҗи—ҸдәҶиҝҷж ·дёҖдёӘдәӢе®һпјҡдёҚд№…д№ӢеүҚ他们иҝҳиә«еӨ„дёҖдёӘдёҚжҳҫи‘—зҡ„йҳ¶еұӮвҖқгҖӮдёҖдәӣеҮәзҺ°еңЁ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дёӯзҡ„еңҲең°иҖ…е…¶е®һеҮәиә«дҪҺеҫ®пјҢз”ҡиҮіеӨ§еӨҡеҰӮжӯӨпјҢдҫӢеҰ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жҸҗеҲ°зҡ„пј”пј•дёӘ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пјҢеҸӘжңүпј‘пј‘дәәжқҘиҮӘдёҖзӣҙжӢҘжңүеә„еӣӯзҡ„家ж—ҸпјҢе…¶дҪҷзҡ„йғҪжҳҜ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еүҚпј—пјҗе№ҙй—ҙиҺ·еҫ—еә„еӣӯзҡ„ж–°йўҶдё»гҖӮеңЁе®һйҷ…з”ҹжҙ»дёӯпјҢд№Ўз»…е’ҢйўҶдё»зЎ®жңүдәӨеҸүгҖӮиҝҷйҮҢеҶҚж¬ЎеҚ°иҜҒдәҶ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еңЁ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зҡ„иғҪеҠЁдҪңз”ЁгҖӮиҝҷдёӘж–°е…ҙйҳ¶еұӮжңүжһҒеӨ§зҡ„еј еҠӣпјҢе®ғжҳҜдёҖж”ҜзӣёеҜ№зӢ¬з«Ӣзҡ„еҠӣйҮҸпјҢ第дёүзӯүзә§е°ұжҳҜ他们еңЁи®®дјҡзҡ„д»ЈиЎЁпјӣеңЁе®һйҷ…з”ҹжҙ»дёӯеҸҲдёҺ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дәӨеҸүе’ҢдәӨиһҚгҖӮ
дә”гҖҒдҪғеҶңеҜ№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ҠөжҠ—
пј‘пјҺ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ҳҜйҡҫд»ҘйҖҫи¶Ҡзҡ„еұҸйҡң
еҜ№жҠ—йўҶдё»зӯү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еҠӣйҮҸпјҢжҳҜеҶңж°‘ж—ўжңү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иҪҪдәҺеә„еӣӯжі•еәӯеҚ·е®—йҮҢзҡ„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жҳҜеҸ—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并被еҗ„зұ»жі•еәӯжүҖжүҝи®Өзҡ„пјҢжҳҜе®ЎзҗҶеңҲең°зә зә·жЎҲ件дёӯзҡ„еҲӨжЎҲдҫқжҚ®гҖӮиҜҙеҲ°еә•пјҢеңҹең°зҡ„еҪ’еұһпјҢеңҲең°жҳҜеҗҰжҲҗз«ӢпјҢдёҚжҳҜйўҶдё»зҡ„ејәжқғе’Ңж„ҝжңӣжүҖиғҪе·ҰеҸі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ж”ҝеәңзҡ„规е®ҡпјҢиҖҢжҳҜеҚғдёҮеҶңж°‘е®һйҷ…жӢҘжңү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ж·ұж·ұж №жӨҚдәҺзӨҫдјҡз”ҹжҙ»дёӯпјҢжңүзқҖжһҒе…¶е№ҝжіӣзҡ„зӨҫдјҡе…ұиҜҶпјҢеӣ жӯӨеҗ„зұ»дҪғеҶң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ҳҜжҠ‘еҲ¶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йҡҫд»ҘйҖҫи¶Ҡзҡ„еұҸйҡңгҖӮ
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дёҚдёҖж ·пјҢеңҲең°дёӯзҡ„йҷ…йҒҮд№ҹе°ұдёҚеҗҢ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Ӣұж је…°еҶңж°‘дё»иҰҒеҲҶдёә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гҖҒ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е’Ң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еҶңгҖӮ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жңҖдёәе®үе…ЁпјҢз”°дё»еҺ»дё–еҗҺеңҹең°з”ұе…¶еҗҺдәә继жүҝпјҢ继жүҝдәәеҸҜд»Ҙж°ёиҝңжҢҒжңүеңҹең°гҖӮ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еҶңзҡ„жқғеҲ©еҮ д№Һж— жҮҲеҸҜеҮ»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дёҺе°Ҹең°дә§дё»пјҲпҪҢпҪҒпҪҺпҪ„пҪҸпҪ—пҪҺпҪ…пҪ’пјүжІЎжңүеӨҡе°‘еҢәеҲ«пјҢйўҶдё»еҘҲдҪ•дёҚдәҶ他们гҖӮ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ӯпјҢж—¶жңү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ҶңжҠұжҖЁеүҘеӨәдәҶ他们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д№ҹжңүдёҖдәӣе…ідәҺ他们е’ҢеңҲең°йўҶдё»д№Ӣй—ҙзҡ„иҜүи®јпјҢдҪҶжҖ»зҡ„жқҘзңӢ他们没жңүйҒӯеҸ—еӨҡе°‘з—ӣиӢҰпјҢдәәж•°д№ҹжІЎжңүжҳҺжҳҫ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Ғ°жҳҜиҮӘз”ұ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еҸ‘еұ•зҡ„ж—¶жңҹгҖӮе…¶ж¬Ўиҫғе°‘еҸ‘з”ҹ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дәүз«Ҝзҡ„жҳҜ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пјҢе®ғ们жң¬иә«е°ұжҳҜжёёзҰ»дәҺдј з»ҹеә„еӣӯз»ҸжөҺд№ӢеӨ–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дё»дҪғе…ізі»еҲҶжҳҺпјҢз§ҹжңҹжҳҺзЎ®пјҢе•ҶдёҡжҖ§зү№еҫҒи¶ҠжқҘи¶ҠйІңжҳҺгҖӮжүҝз§ҹиҖ…зҡ„жқғеҲ©еҸ—еҲ°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пјҢжүҖд»Ҙеңҹең°еҮәз§ҹжңҹеҶ…дёҚеҫ—еңҲең°пјҢдёҚи®әең°дә§дё»иҝҳжҳҜйўҶдё»йғҪдёҚиғҪпјҢеҸӘиғҪзӯүеҫ…еҮәз§ҹжңҹйҷҗеұҠж»ЎпјҢеңҹең°жҒўеӨҚеҺҹзҠ¶еҗҺжүҚиғҪйҮҚж–°еӨ„зҪ®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пј“пјҗе№ҙд»ЈеӣҪзҺӢжі•йҷўеҶҚж¬ЎдёӢиҫҫвҖңз§ҹжңҹеҶ…дёҚеҸҜй©ұйҖҗжүҝз§ҹдәәд»ӨзҠ¶вҖқпјҲпҪ‘пҪ•пҪҒпҪ’пҪ… пҪ…пҪҠпҪ…пҪғпҪүпҪ” пҪүпҪҺпҪҶпҪ’пҪҒпҪ”пҪ…пҪ’пҪҚпҪүпҪҺпҪ•пҪҚпјүпјҢд»Ҙдҝқйҡңжүҝз§ҹдәә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еүҚиҝ°и®ёеӨҡдҫӢиҜҒе·ІиҜҒжҳҺеңЁз§ҹжңҹеҶ…йўҶдё»дёҚиғҪ收еӣһз§ҹең°пјҢд№ҹдёҚиғҪеӣҙеңҲпјҢеҸӘиғҪзӯүеҫ…пјҢеҗҰеҲҷеҚідёә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гҖӮиҝҷ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ҝҳиў«зәіе…Ҙжҷ®йҖҡжі•е•ҶдёҡеҘ‘зәҰзҡ„дҝқжҠӨиҢғз•ҙгҖӮдёҖдәӣз§ҹең°еҶңжҳҜеӨ§з§ҹең°еҶңеңәдё»пјҢй•ҝжңҹжүҝз§ҹ并еҜ№еңҹең°жңүиҫғеӨ§зҡ„жҠ•е…Ҙ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жҳҜжңүдёҖе®ҡзӨҫдјҡең°дҪҚзҡ„еҶңдёҡиө„жң¬е®¶гҖӮеҪ“然пјҢз§ҹзәҰеҲ°жңҹеҗҺ他们еҗҢж ·йЎ»жҢүеҘ‘зәҰдәӨиҝҳеңҹең°пјҢйҷӨйқһ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з»ӯзәҰпјҢжҲ–з»ҸйўҶдё»еҗҢж„ҸеҗҺд№°ж–ӯеңҹең°гҖӮеҘ‘зәҰз§ҹең°зҡ„жқғеҲ©ж—¶ж•ҲжҖ§жңҖдёәе…ёеһӢпјҢйҖӮйҖў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ж—¶жңҹпјҢиҜҘзұ»еһӢеңҹең°жү©еј жңҖеҝ«пјҢз»Ҹиҝ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зҡ„зҷҫе№ҙеҸ‘еұ•з«ҹз”ұе°‘ж•°еҸҳжҲҗеӨҡж•°гҖӮ
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жҳҜ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ҪғеҶңзҡ„дё»дҪ“пјҢ他们зҡ„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жңҖдёәеӨҚжқӮпјҢеҸ‘з”ҹдәүз«Ҝ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жңҖеӨ§пјҢзҝ»ејҖ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зҡ„еҗ„зұ»жі•еәӯжЎҲеҚ·пјҢеӨ§йғЁеҲҶж¶үи®јеңҹең°жЎҲ件жҳҜе…¬з°ҝеҶңзҡ„гҖӮжңү继жүҝжқғзҡ„е…¬з°ҝең°дёҺиҮӘз”ұжҢҒжңүең°е®һйҷ…дёҠзӣёеҪ“жҺҘиҝ‘пјҢдёҖж—ҰйҷӘе®Ўеӣўзҡ„иҜҒиҜҚиҜҒжҳҺдәҶиҝҷж ·зҡ„еңҹең°жҖ§иҙЁ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ҷж ·зҡ„еңҹең°жҖ§иҙЁи®°иҪҪдәҺеә„еӣӯжЎЈжЎҲпјҢ他们еңЁжі•еәӯиҜүи®јдёӯдјјд№Һжӣҙе®үе…ЁпјҢдёҖиҲ¬иҜҙжқҘйўҶдё»иҙҘиҜүж— з–‘гҖӮдёҚиҝҮиҜҘж—¶жңҹеӨҡж•°е…¬з°ҝең°жҢҒжңүжқғжҳҜжңүж—¶ж•Ҳзҡ„пјҢиҷҪ然他们д»Қиў«з§°дёәд№ жғҜдҪғеҶңпјҢ然иҖҢе•ҶдёҡеҺҹеҲҷе·Із»Ҹжё—йҖҸе…¶дёӯ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—©жңҹпјҢеҶңеңәз§ҹжңҹдёҖиҲ¬иҫғй•ҝпјҢйҖҡеёёжҳҜпј‘пјҗе№ҙпјҢжңүж—¶й•ҝиҫҫпј–пјҗе№ҙ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пјҷпјҷе№ҙгҖӮдҪҶ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пј”пјҗе№ҙд»Јд»ҘеҗҺпјҢз§ҹжңҹеҸҳзҹӯгҖӮеңЁдёңйғЁпјҢз§ҹжңҹдё»иҰҒдёәпј—е№ҙгҖҒпј‘пј”е№ҙе’Ңпј’пј‘е№ҙпјҢжҜҸдёғе№ҙжӣҙж–°дёҖж¬Ўз§ҹзәҰгҖӮеңЁиҘҝйғЁпјҢз§ҹзәҰд»ҘдёҖд»ЈгҖҒдёӨд»ЈжҲ–иҖ…дёүд»ЈдёәжңҹйҷҗпјҢйҖҡеёёдёәдёүд»ЈпјҢ并且еңЁжҜҸдёҖдҪҚдҪғеҶңеҺ»дё–д»ҘеҗҺжӣҙж–°з§ҹзәҰгҖӮеңЁ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е’ҢеҢ—йғЁпјҢз§ҹзәҰеҮӯеҖҹеҗҲеҗҢпјҲпҪүпҪҺпҪ„пҪ…пҪҺпҪ”пҪ•пҪ’пҪ…пјүпјҢеӨҡдёәпј’пј‘е№ҙжҲ–дёүд»ЈгҖӮеҰӮжһңеңҹең°еҲ°жңҹеҗҺдёҚиғҪиҫҫжҲҗж–°зҡ„еҚҸи®®пјҢеңҹең°жҢҒжңүжқғеҸҜиғҪеҸ‘з”ҹеҸҳеҢ–гҖӮдёҚиҝҮеңЁз§ҹзәҰ规е®ҡзҡ„ж—¶й—ҙйҮҢдёҚеҸҜй©ұйҖҗпјҢиҖҢдё”е…¬з°ҝеҶңиҮӘд»Һпј‘пј•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е°ұејҖе§ӢеҸ—еҲ°жҷ®йҖҡжі•дҝқжҠӨгҖӮзҺӢе®Өеҗ„зұ»жі•еәӯйғҪеҸ—зҗҶе…¬з°ҝжҢҒжңүеҶңзҡ„з”іиҜүпјҢдёҚе°‘е…¬з°ҝеҶңеҮӯжҚ®ж—ўжңү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ңүеҠӣжҠөеҲ¶дәҶйўҶдё»зҡ„йқһжі•дҫөжқғгҖӮдёҠиҝ°еңҲең°жЎҲ件зҡ„йҳҗиҝ°дёӯеӨҡжңүж¶үеҸҠпјҢжӯӨдёҚиөҳиҝ°гҖӮжҳҫ然пј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ҳҜдҪғеҶңжҠөжҠ—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жүӢж®өпјҢеҸҚиҝҮжқҘпј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и–„ејұзҺҜиҠӮжҲ–иҖ…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Өұж•ҲжңҹеҶ…пјҢе°ұдјҡдә§з”ҹиҙҘиҜүжҲ–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еҸҜиғҪгҖӮд»Һеҹәжң¬еұӮйқўдёҠи®ІпјҢеңҲең°дёҚжҳҜи·өиёҸ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жҒ°жҒ°жҳҜжҳҺжҷ°е’ҢзЎ®е®ҡ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жүҖд»Ҙз»ҸжөҺеҸІеӯҰ家иүҫдјҰжҢҮеҮә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еңҹең°д№ жғҜдҝқжңүжқғдёҚе®үе…Ё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жүҚдјҡеҮәзҺ°й©ұйҖҗејҸзҡ„еңҲең°гҖӮ
е…¬ең°еҚіиҚ’ең°гҖҒжһ—ең°е’ҢжІјжіҪзӯүпјҢиҷҪ然еҗҚд№үдёҠеұһдәҺйўҶдё»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жҜҸдёӘжқ‘ж°‘йғҪжңүж”ҫзү§е’ҢдҪҝз”Ёзҡ„жқғеҲ©пјҢиҖҢдё”дё–дё–д»Јд»ЈйғҪеңЁдҪҝз”ЁгҖӮе®ғзҡ„е…ұз”ЁжҖ§жңҖејәпјҢ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жңҖдёәжЁЎзіҠпјҢд№ҹжҳҜжңҖе®№жҳ“еҸ—еҲ°йўҶдё»дҫөжқғзҡ„еңҹең°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’пјҳиҮі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җе№ҙй—ҙпјҢе…°ејҖеӨҸйғЎзҡ„и®ёеӨҡеңҹең°зә зә·пјҢзҡҶеӣ йўҶдё»дҫөе®іе…¬ең°иҖҢиў«еҶңж°‘е‘ҠдёҠжі•еәӯгҖӮжҚҚеҚ«д№ жғҜжқғеҲ©жҳҜдҪғеҶңеҸҚжҠ—ж–—дәүзҡ„дёҖйқўж——еёңпјҢ他们еҸҚеӨҚз”іжҳҺеҮ дёӘдё–зәӘд»ҘжқҘ他们еңЁе…¬ең°дёҠдёҖзӣҙе…·жңүж”ҫзү§жқғе’ҢеҲ©з”Ёе…¬ең°е…¶д»–иө„жәҗзҡ„жқғеҲ©гҖӮдёҖдәӣжЎҲдҫӢзҡ„еҲӨеҶідёҚз”ҡжҳҺдәҶпјҢдёҖдәӣжЎҲдҫӢжҳҫзӨәдҪғеҶңзҡ„жҠ—дәүжҳҜжңүж•Ҳзҡ„гҖӮеЁҒж–Ҝж•Ҹж–Ҝзү№жі•еәӯеҪ“е№ҙе®ЎзҗҶзҡ„еңҲең°жЎҲдҫӢпјҢжҸҸиҝ°дәҶдёҚеҶҚжё©йЎәзҡ„еҶңж°‘пјҢеҚідҪҝиў«иҝ«зҰ»ејҖжқ‘еә„пјҢ他们д№ҹвҖң并дёҚеұҲжңҚпјҢдёҚд»…еёҰзқҖзңјжіӘе’ҢжӮІж„ӨпјҢиҖҢдё”дёҫиө·вҖҳеҸӨиҖҒд№ жғҜвҖҷдәҲд»ҘжҠөжҠ—вҖқгҖӮжңү时他们зҡ„дёҖдәӣжҠөжҠ—е…·жңүжҡҙеҠӣеҖҫеҗ‘пјҢ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дҪңиҖ…иҜ„и®әиҜҙ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ҷе№ҙеҸҚеңҲең°еҶңж°‘йӘҡд№ұдёҚжҳҜеҒ¶з„¶зҡ„гҖӮдёӢйқўжЎҲдҫӢи®°иҪҪдәҶжқ‘ж°‘дёҺдёӨд»ЈйўҶдё»зҡ„ж–—дәүпјҢжңүжі•еәӯжҠ—дәүпјҢд№ҹжңүжҡҙеҠӣеҜ№жҠ—пјҢж—¶й—ҙй•ҝиҫҫдёүеҚҒеӨҡе№ҙгҖӮ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ҲқпјҢ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жі•жҒ©зҷ»еә„еӣӯпјҲпјҰпҪүпҪҺпҪ…пҪ„пҪҸпҪҺпјүжқ‘ж°‘иө·иҜүйўҶдё»й»ҳе°”зҙўйқһжі•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гҖӮеҸҜжҳҜйўҶдё»дёӨж¬ЎжҠ—жӢ’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зҡ„жі•еәӯе‘Ҫд»Ө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’пјҷе№ҙпјҢдҪғеҶң们дёҚе ӘеҝҚеҸ—пјҢиҒҡйӣҶиө·жқҘпјҢжҡҙеҠӣеҠҲзўҺдәҶеӣҙеңҲең°еӨ§й—Ёе’Ңй—ЁжҹұгҖӮжҺҘзқҖеҸҲиҒҡйӣҶдәҶпј–пјҗдҪҚжқ‘ж°‘пјҢе°Ҷж ‘зҜұиҝһж №еҲЁйҷӨгҖӮиҝҷж¬ЎйӘҡд№ұжҢҒз»ӯпјҳеӨ©пјҢвҖңйёЈй’ҹгҖҒеҡҺеҸ«гҖҒе–§й—№е’ҢжҡҙеҠӣвҖқгҖӮйўҶ主并дёҚзҪўдј‘пјҢз«ҹ然жүЈжҠјжқ‘ж°‘зҡ„зүІз•ңпјӣжқ‘ж°‘еҲҷй—Ҝе…Ҙе…¬ең°ж°ҙеЎҳпјҢеӨәеӣһзүІз•ңпјҢ并е°Ҷе…¶иө¶е…ҘйўҶдё»зҡ„зү§еңәпјҢе•ғе…үйӮЈйҮҢзҡ„йқ’иҚүгҖӮеҪ“йўҶдё»ж¬Ій©ұиө¶зүІз•ңеҲ°пј‘пј“иӢұйҮҢиҝң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з•ңж Ҹж—¶пјҢжқ‘民们иҺ·зҺӢе®Өд»ӨзҠ¶пјҢеҶҚж¬Ўи§Јж•‘дәҶзүІз•ңгҖӮдёәжҢҮжҺ§йўҶдё»пјҢжқ‘民们зӯ№йӣҶпј’пјҗиӢұй•‘иҜүи®јиҙ№пјҢеҸҜи§ҒеҸӮдёҺиҖ…дёҚйғҪжҳҜз©·дәәгҖӮиҜүи®јеҮ з»ҸеҸҚеӨҚпјҢжҳҹе®Өжі•еәӯгҖҒ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пјҲпҪ”пҪҲпҪ… пјЈпҪҸпҪ•пҪ’пҪ” пҪҸпҪҶ пјЈпҪҲпҪҒпҪҺпҪғпҪ…пҪ’пҪҷпјүзӯүе…ҲеҗҺе№Ійў„пјҢйғҪдёҚиғҪз»“жқҹиҝҷеңәж—ўжңүжі•еәӯд№ҹжңүжҡҙеҠӣзҡ„дәүз«ҜгҖӮиҖҢеҸ‘з”ҹеңЁеӣӯиө«ж–Ҝжң¬е…№В·еҚҡж–ҜжІғж–ҜпјҲпјЁпҪ•пҪ“пҪӮпҪҒпҪҺпҪ„пҪ“ пјўпҪҸпҪ“пҪ—пҪҸпҪ’пҪ”пҪҲпјүеә„еӣӯзҡ„жЎҲдҫӢпјҢжқ‘ж°‘еҲҷиөўеҫ—иғңиҜүпјҢиҷҪ然йўҶдё»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иҫҫж•°еҚҒе№ҙд№Ӣд№…пјҢдҪҶжқ‘ж°‘еӣўз»“дёҖиҮҙпјҢдёҚеұҲдёҚжҢ пјҢз»ҲдәҺиҝ«дҪҝйўҶдё»жӢҶйҷӨеӣҙзҜұпјҢжҒўеӨҚдәҶжқ‘ж°‘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гҖӮдҪғеҶңзҫӨдҪ“еқҡжҢҒ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жҠөжҠ—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–—дәүж—ўжҳҜйЎҪејәзҡ„пјҢд№ҹжҳҜжңүж•Ҳзҡ„гҖӮйғҪй“ҺзҺӢжңқеңҲең°жҷҡжңҹпјҢ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зү№еҲ«жҳҜе…¬ең°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зӣёе…іжқ‘ж°‘йғҪд»Һе…¬ең°ж¶ҲеӨұдёӯеҫ—еҲ°иЎҘеҒҝпјҢд»ҺдёҖе®ҡж„Ҹд№үдёҠи®ІжҳҜдҪғеҶңзҫӨдҪ“жҠ—дәүзҡ„з»“жһңгҖӮ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жҳҜеҜ№жҠ—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ңүеҠӣеұҸйҡңпјҢдёҚд»…еҸ—еҲ°жі•еҫӢдҝқжҠӨпјҢд№ҹеҸ—еҲ°ж•ҙдёӘзӨҫдјҡиҲҶи®әзҡ„ж”ҜжҢҒпјҢеӣ дёә他们зҡ„жі•еҫӢж №жӨҚдәҺзӨҫдјҡгҖӮ
пј’пјҺиҙ«еӣ°е°ҸеҶңзҡ„жҡҙеҠӣеҸҚжҠ—
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ҳҜдёҖең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еҸҳйқ©пјҢд№ҹжҳҜдёҖеңә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зҡ„еҶҚеҲҶй…Қ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ҖеӨ§зҡ„иҺ·зӣҠиҖ…пјҢйӮЈд№ҲдёҖйғЁеҲҶиҙ«з©·зҡ„е°‘ең°е°ҸеҶңеҲҷжҳҜжңҖеӨ§зҡ„еҸ—е®іиҖ…гҖӮжқЎз”°зҡ„еңҲеҚ дә§з”ҹдёҖйғЁеҲҶж— ең°гҖҒе°‘ең°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他们е’ҢеҺҹжқҘзҡ„иҢ…иҲҚеҶңдёҖиө·пјҢеҜ№е…¬ең°зҡ„дҫқиө–зЁӢеәҰжӣҙж·ұдәҶпјҢжүҖд»ҘеҪ“е…¬ең°д№ҹиў«еңҲеҚ 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°Ҹеңҹең°жҢҒжңүиҖ…е’ҢиҢ…иҲҚеҶңеҸҚеҜ№зҡ„жҖҒеәҰжңҖеқҡеҶіпјҢжңүзҡ„жҠөжҠ—зӣҙжҺҘиҜүиҜёжҡҙеҠӣ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“е№ҙйўҶдё»пјІпјҺеёғйҮҢе°”йЎҝзҲөеЈ«жҺ’е№ІдәҶеӨҡе“ҘиҺ«е°”пјҲпјӨпҪҸпҪҮпҪҚпҪҸпҪҸпҪ’пјүжІјжіҪең°е№¶еңҲеҚ пјҢеј•еҸ‘дәҶеҪ“ең°е°ҸеҶңжҡҙеҠӣжҠөжҠ—пјҢй•ҝжңҹдёҚиғҪе№іжҒҜгҖӮеңЁеҘҘж–Ҝз»ҙж–ҜпјҲпјҜпҪ“пҪ—пҪ…пҪ“пҪ”пҪ’пҪҷпјүеә„еӣӯпјҢеӨ§и§„жЁЎеӣҙеңҲиҚ’ең°еҗҢж ·йҒӯеҲ°дёҖдәӣе°ҸеҶңйЎҪеӣәйҳ»жҢ 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“пј•е№ҙпј–жңҲпјҢеқҺдјҜе…°дјҜзҲөеӣҙеңҲдәҶжҙҘж је°”ж–ҜеЁҒе…ӢпјҲпј§пҪүпҪҮпҪҮпҪҢпҪ…пҪ“пҪ—пҪүпҪғпҪӢпјүеә„еӣӯзҡ„е…¬ең°пјҢеӨ§зәҰпј”пјҗпјҗдәәйӣҶз»“иө·жқҘжӢҶжҜҒеңҲең°зҡ„еӣҙзҜұпјҢпј—жңҲеҲқжҡҙеҠӣжіўеҸҠзӣёйӮ»зҡ„е…Ӣйӣ·ж–ҮпјҲпјЈпҪ’пҪҒпҪ–пҪ…пҪҺпјүең°еҢә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пјҳпј’дәәиў«иө·иҜүпјҢе…¶дёӯпј”пјҗдәәжҳҜдјҜзҲөзҡ„дҪғеҶңпјҢпј‘пјҳдәәиў«зӣ‘зҰҒгҖӮ
иҙ«з©·е°ҸеҶңжҳҜеҸҚеңҲең°жҡҙеҠӣзҡ„еҹәжң¬дәәзҫӨпјҢжңүж—¶йўҶеӨҙдәәеҚҙдёҚжҳҜ他们гҖӮдёҖжЎ©е…ёеһӢзҡ„еҸҚеңҲең°жҡҙеҠӣдәӢ件иө·дәҺзүӣжҙҘзҡ„жұүжҷ®йЎҝзӣ–дјҠеә„еӣӯпјҲпјЁпҪҒпҪҚпҪҗпҪ”пҪҸпҪҺ пј§пҪҒпҪҷпјүпјҢиҜҘеә„еӣӯпј—дәәдәӨзәіеҚҸеҠ©йҮ‘пјҢеҸҜи§ҒжҳҜдёӘиҙ«з©·зҡ„жқ‘еә„гҖӮйўҶдё»е·ҙйҮҢзҲ¶иҫҲеҒҡзҫҠжҜӣз”ҹж„ҸиҮҙеҜҢпјҢд»–жң¬дәә继жүҝеә„еӣӯеҗҺе°ұжҺЁеҠЁдәҶеңҲең°пјҢеҚҙеј•иө·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–е№ҙзҡ„дёҖеңәйӘҡд№ұгҖӮйӘҡд№ұеҸ‘иө·дәәжҳҜйӮ»иҝ‘еә„еӣӯзҡ„е·ҙеЎһжҙӣзјӘВ·ж–Ҝи’Ӯе°”пјҢиҖҢзЈЁеқҠдё»зҗҶжҹҘеҫ·В·еёғжӢүеҫ·иӮ–жёёиө°дәҺе‘Ёеӣҙжқ‘еә„пјҢж•ЈеёғеҜ№еңҲең°зҡ„дёҚж»ЎгҖӮе“Қеә”иҖ…еӨ§зәҰжңүеҮ еҚҒдәәпјҢ他们жӢҝзқҖй•ҝзҹӣе’Ңеү‘пјҢиҒҡйӣҶеңЁеёғиҺұе»·йЎҝзҡ„еӣ жҖқиҗҪеұұең°пјҲпјҘпҪҺпҪ“пҪҢпҪҸпҪ—пјЁпҪүпҪҢпҪҢпјүпјҢжҡҙеҠӣзҡ„зӣ®ж ҮжҳҜжҜҒеқҸеңҲең°зҡ„еӣҙж Ҹ并攻еҮ»еңҲең°иҖ…пјҢиҝҳи®ЎеҲ’еҺ»дјҰж•ҰпјҢдәүеҸ–йӮЈйҮҢеӯҰеҫ’е·Ҙдәәзҡ„ж”ҜжҢҒгҖӮйӘҡд№ұдёӯпјҢдёҠиҝ°йўҶдё»ж–ҮжЈ®зү№В·е·ҙйҮҢеҸҠе…¶еҘіе„ҝдёҖ并被жқҖе®ігҖӮе®ҳж–№йҮҮеҸ–иЎҢеҠЁеҜ№жҠ—йӘҡд№ұиҖ…гҖӮең°ж–№е®ҳж–ҜиҠ’еҫ·ж–ҜдәӢе…ҲжӣҫжҸҗйҶ’иҝҮйўҶдё»е·ҙйҮҢгҖӮеңЁиў«жӢҳз•ҷиҖ…дёӯпјҢдә”дёӘжұүжҷ®йЎҝзӣ–дјҠеә„еӣӯдәәиў«йҒЈйҖҒдјҰж•ҰпјҢдёҖдәәиў«еӨ„д»Ҙз»һеҲ‘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еҪ“жңүдәәй—®иҜўж”ҝеәңеҰӮдҪ•зңӢеҫ…жӯӨдәӢж—¶пјҢиҜҘең°ж–№е®ҳдёҚжҳҜдёҖе‘іең°ж–ҘиҙЈйӘҡд№ұеҶңж°‘пјҢиҖҢжҳҜиҖғиҷ‘ж”ҝеәңеә”иҜҘеҒҡд»Җд№Ҳ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ж”ҝеәңеә”еҪ“жҺ§еҲ¶еңҲең°вҖҰвҖҰи®©з©·дәәиғҪеӨҹз”ҹеӯҳдёӢжқҘгҖӮвҖқжҜ«ж— з–‘й—®пјҢиҝҷеңәйӘҡд№ұеҪұе“ҚеҲ°дәҶи®®дјҡ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жҺЁеҠЁ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—е№ҙиҖ•дҪңжі•д»ӨйҖҡиҝҮпјҢе…¶дёӯеҢ…жӢ¬дёҖдәӣеӣҙеңҲзү§еңәеӨҚиҖ•зҡ„жқЎдҫӢгҖӮ
жңҖ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еҪ“еұһ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ҷе№ҙ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еҮҜзү№йўҶеҜјзҡ„еҸҚ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пјҢиҝҷжҳҜ继з“Ұзү№В·жі°еӢ’иө·д№үеҗҺиӢұеӣҪеўғеҶ…жңҖ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дёҖж¬ЎеҶңж°‘иө·д№үпјҢжӣҫиҒҡйӣҶиө·еҗ‘еӣҪзҺӢиҜ·ж„ҝзҡ„дёҠдёҮеҗҚеҹҺд№Ўеұ…ж°‘пјҢдёӨеәҰж”»еҚ дәҶиҜәзҰҸе…ӢйҰ–еәңиҜәйҮҢеҘҮеёӮпјҢжҢҒз»ӯпј”дёӘжңҲд№Ӣд№…гҖӮ他们дёүж¬ЎжӢ’з»қж”ҝеәңзҡ„еӨ§иөҰпјҢжңҖеҗҺиў«ж”ҝеәңзҡ„еҶӣйҳҹй•ҮеҺӢпјҢдёҠеҚғдәәеңЁжҝҖжҲҳдёӯиў«жқҖгҖӮеҮҜзү№еңЁдјҰж•ҰеҸ—е®ЎпјҢз»һжӯ»еңЁиҜәйҮҢеҘҮеҹҺе ЎгҖӮиҝҷж¬Ўиө·д№үзҡ„иҢғеӣҙжңүйҷҗпјҢ然иҖҢе…¶еҪұе“ҚеҚҙиҝңиҝңи¶…еҮәиҜәзҰҸе…ӢпјҢдёҚж–ӯжңүзӣёе…із ”究жҲҗжһңй—®дё–гҖӮжҚ®з ”究пјҢеҮҜзү№жҳҜдёӘеҜҢиЈ•зҡ„зәҰжӣјпјҢжӢҘжңүеңҹең°пјҢе…јеҒҡзҡ®еҢ пјҢдёҖдёӘеҒ¶з„¶дәӢ件дҪҝд»–еҸӮеҠ дәҶеҪ“ең°йҖ еҸҚеҶңж°‘зҡ„йҳҹдјҚпјҢ并жҲҗдёәйўҶиў–гҖӮеҮҜзү№дёҺеҗҢжқ‘д№Ўз»…еј—еҠіе°”иҝӘжңүжҖЁпјҢеҗҺиҖ…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зҡ„зҜұз¬Ҷиў«жҚЈжҜҒпјҢд»ҘдёәеҮҜзү№е…„ејҹдәҢдәәжүҖдёәпјҢдәҺжҳҜиҠұпј”пјҗдҫҝеЈ«жү“еҸ‘йӣҮе·ҘжҺЁеҖ’еҮҜзү№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зҡ„ж ‘зҜұгҖӮз»“жһңпјҢиҝҷдәӣдәәйқһдҪҶжІЎжңүеҺ»жҺЁеҲ°ж ‘зҜұпјҢеҸҚиҖҢеңЁеҮҜзү№зҡ„еҠқеҜјдёӢеҖ’еҗ‘дәҶеҮҜзү№дёҖиҫ№гҖӮеҮҜзү№йҒ“й«ҳдёҖзӯ№пјҢеңЁжҠҘеӨҚйӮЈдёӘд№Ўз»…еүҚпјҢе…ҲжӢҶжҜҒдәҶиҮӘ家зҡ„еңҲең°ж ‘зҜұпјҢиЎЁзӨәеҗҢжғ…з©·дәәпјҢеҸҚеҜ№йқһжі•дҫөеҚ 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пјҢд»ҺиҖҢиөўеҫ—дәҶеӨ§е®¶зҡ„ж¬ўиҝҺе’ҢдҝЎд»»пјҢзә·зә·еҠ е…Ҙд№үеҶӣгҖӮеҮҜзү№йј“еҠұеӨ§е®¶з”Ёз”ҹе‘ҪдҝқеҚ«жқ‘еә„е…¬ең°пјҢи®ёиҜәиө·д№үиҖ…иҝҮдёҠеҘҪж—ҘеӯҗгҖӮдёҚеҸҜеҗҰи®ӨпјҢеҺҶеҸІдәӢ件зҡ„еҸ‘з”ҹжңүзқҖдёҖе®ҡзҡ„еҒ¶з„¶еӣ зҙ пјҢдҪҶд»Һеҹәжң¬еұӮйқўи®ІпјҢеҮҜзү№иө·д№үеҸҚжҳ дәҶеҪ“ж—¶зӨҫдјҡеҶІзӘҒзҡ„зЁӢеәҰпјҢеҗҰеҲҷжҖҺд№ҲдјҡжҢҜиҮӮдёҖе‘јпјҢд»ҺиҖ…дёҠдёҮпјҒ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пјҢиӢұж је…°еңҹең°ж”№йқ©жӯЈеӨ„дәҺз—ӣиӢҰзҡ„иғ¶зқҖзҠ¶жҖҒпјҢеҮҜзү№иө·д№үз»қдёҚжҳҜеӯӨз«Ӣзҡ„пјҢжҚ®зҲұеҫ·еҚҺе…ӯдё–ж—¶жңҹзҡ„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пјҢиҜҘиө·д№үжү©ж•ЈеҲ°пј‘пј‘дёӘйғЎпјҢеҢ…жӢ¬дёҺд№ӢзӣёйӮ»зҡ„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пјҢд»ҺдәЁе»·йЎҝдјҜзҲө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ҷе№ҙпјҷжңҲпј‘пј’ж—Ҙзҡ„дҝЎд»¶дёӯеҸҜд»Ҙж„ҹзҹҘеҪ“ж—¶еҸҚжҠ—зҡ„ж°”ж°ӣпјҢжҠ—и®®дәәзҫӨвҖңйҒҚеёғжӢүзү№е…°еҗ„ең°вҖқгҖӮеҮҜзү№йўҶеҜјзҡ„йҖ еҸҚжҳҜеҠЁиҚЎзӨҫдјҡиЎЁиұЎ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еҒ¶еҸ‘дәӢ件дёҚиҝҮеҜјзҒ«зҙўиҖҢе·ІгҖӮ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ҳвҖ”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ҷе№ҙеҸ‘з”ҹиҝҮзҡ„е°ҸйҖ еҸҚгҖҒе°ҸйӘҡд№ұпјҢе…ЁеӣҪеӨ§зәҰжңүеҮ еҚҒиө·д№ӢеӨҡпјҢз”ҡиҮідёҖдәӣеҹҺеёӮд№ҹеҸ‘з”ҹдәҶеҸҚеҜ№е…¬ең°еӣҙеңҲзҡ„йӘҡд№ұгҖӮ
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жң«зүӣжҙҘйғЎеҶҚж¬ЎзҲҶеҸ‘еҸҚеңҲең°иө·д№ү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е°ҸеҶңзҡ„иҙ«еӣ°жҳҜ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пј‘пј•пјҷпј–е№ҙеҶ¬еӨ©пјҢзүӣжҙҘйғЎжӯҰиЈ…иө·д№үиҖ…и®ЎеҲ’ж”»еҮ»йўҶдё»пјҢжҠўеҠ«зІ®йЈҹпјҢжӢҶжҜҒеңҲең°еӣҙж ҸпјҢжңӘж–ҷж¶ҲжҒҜжі„йңІиҮҙдҪҝиө·д№үжөҒдә§пјҢйҰ–йўҶиў«жҚ•гҖӮз»Ҹе®Ўй—®пјҢиө·д№үиҖ…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жӢҶйҷӨеңҲең°еӣҙж ҸжқҘйҷҚдҪҺзІ®д»·гҖӮдёҖдәӣеҶңж°‘з”ҹи®Ўйҷ·дәҺеӣ°еўғпјҢеј•иө·зӨҫдјҡдёҠеұӮдәәеЈ«зҡ„еҝ§иҷ‘пјҢе°Ҫз®ЎйўҶдё»иҜәйҮҢж–ҜжӯҰеҷЁе’Ң马еҢ№зҡҶиў«еҠ«жҺ пјҢеҸҜжҳҜд»–иҝҳжҳҜиҜ·жұӮи®®дјҡеҜ№зүӣжҙҘйғЎиҘҝйғЁзҡ„еңҲең°еҠ д»ҘеҲ¶жӯўгҖӮжҚ®гҖҠзүӣжҙҘйғЎйғЎеҸІгҖӢи®°иҪҪпјҢдёҚе°‘еҹҺй•Үе……ж»Ўз©·дәәе’ҢжҠұжҖЁжғ…з»ӘпјҢдёҖдәӣдәәжӣҫи®ЎеҲ’еҲ°дјҰж•ҰжёёиҜҙпјҢеҜ»жұӮжӣҙеӨҡзҡ„ж”ҜжҢҒиҖ…пјҢйўҶеӨҙдәәжҳҜдёҖдёӘеҗҚеӯ—еҸ«ж–Ҝи’Ӯе°”зҡ„жңЁеҢ гҖӮ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иө·дәӢпјҢиҝҷжҳҜжңҖеҗҺдёҖж¬Ўе°ҸеҶңеҸҚеңҲең°жҡҙеҠЁгҖӮз”·еҘіиҖҒе°‘дә”еҚғдәәиҒҡйӣҶ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зҡ„иҖғзү№ж–Ҝе·ҙиө«ж•ҷеҢәпјҢеӣҙеңҲзҡ„е…¬ең°иў«жҡҙеҠӣжҚЈжҜҒ并йҮҚж–°ејҖж”ҫгҖӮиҝҷж¬Ўиө·д№үзҡ„дёҖдёӘз»“жһңжҳҜпјҢж”ҝеәңжҲҗз«ӢдәҶ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пјҢеҠ ејәдәҶеҜ№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зӣ‘жҺ§гҖӮжҳҫ然пјҢе°ҸеҶңзҡ„жҡҙеҠӣжҠөжҠ—зӣҙжҺҘжҠ‘еҲ¶жҲ–еЁҒж…‘дәҶ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гҖӮ
жҖ»зҡ„зңӢпјҢеҸҚеҜ№йқһжі•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зҡ„йҮҚиҰҒеҠӣйҮҸжқҘиҮӘиҙ«з©·е°ҸеҶңпјҢе°‘ең°з”ҡиҮіж— ең°зҡ„е°ҸеҶңеҜ№е…¬е…ұзү§еңәзҡ„дҫқиө–зЁӢеәҰжңҖж·ұпјҢеҸҲеҫ—дёҚеҲ°еҗҲзҗҶзҡ„иЎҘеҒҝпјҢжҲҗдёәиҝҷеңәеҶңдёҡеҸҳйқ©иў«зүәзүІзҡ„зҫӨдҪ“гҖӮиҝҷйғЁеҲҶе°ҸеҶңжҲҗдёәжҡҙеҠЁе’Ңеҗ„з§ҚйӘҡд№ұдәӢ件зҡ„дё»иҰҒеҸӮдёҺиҖ…гҖӮеҸҚеңҲең°жҡҙеҠЁдёҖиҲ¬е…·жңү规模е°ҸгҖҒең°еҢәжҖ§ејәзӯүзү№зӮ№пјҢеҮҜзү№иө·д№үз•ҷдёӢпј’пјҷжқЎиҜ·ж„ҝдё»еј пјҢд»ҺдёӯеҸҜзӘҘи§ҶиҝҷйғЁеҲҶеҶңж°‘зҡ„еҹәжң¬иҜүжұӮгҖӮ他们зҘӯеҮәдҝқеҚ«е…¬ең°е’Ңд№ жғҜжқғеҲ©зҡ„ж——еёңпјҢйўҮдёәжӮІжғ…гҖӮеҗҢж—¶жҢҘеҮәвҖңе№ізӯүвҖқд№Ӣеү‘пјҢжҢҮеҗ‘йўҶдё»д№Ўз»…пјҢзү№еҲ«жҢҮеҗ‘дёҖдёӢеӯҗеҶ’еҮәжқҘзҡ„еҜҢдәәпјҢдҫӢеҰӮдё»еј е№ҙ收е…Ҙпј”пјҗиӢұй•‘иҖ…пјҢдёҖеҫӢдёҚеҫ—еңЁе…¬ең°ж”ҫзү§пјӣвҖңе№ізӯүвҖқд№Ӣеү‘д№ҹзӣҙжҺҘжҢҮеҗ‘еёӮеңәпјҢдҫӢеҰӮеҸҚеҜ№еңҹең°е’Ңең°з§ҹд»·ж јйҡҸиЎҢе°ұеёӮпјҢеҸҚеҜ№иҮӘз”ұиҙӯд№°е’ҢеҮәз§ҹеңҹең°гҖӮд»ҺйҒ“д№үдёҠи®ІпјҢдҪңдёә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зҡ„дёҖе‘ҳпјҢ他们зҺ°еңЁдёҖдёӢеӯҗеӨұеҺ»дәҶдё–дё–д»Јд»Јдә«жңүзҡ„е…¬е…ұж”ҫзү§жқғпјҢжІЎжңүеҫ—еҲ°иЎҘеҒҝжҲ–жІЎжңүи¶іеӨҹзҡ„иЎҘеҒҝпјҢеҸҚжҠ—жҳҜеҗҲзҗҶеҗҲжі•зҡ„пјҢжҳҜжӯЈд№үзҡ„пјҢжүҖд»ҘиҺ·еҫ—дәә们зҡ„е№ҝжіӣеҗҢжғ…пјӣдҪҶе…¶з»ҸжөҺдё»еј жҳҫ然жҳҜиҰҒйҖҖеӣһдёӯдё–зәӘеә„еӣӯз»ҸжөҺпјҢжҳҜд№ҢжүҳйӮҰзҗҶжғіпјҢеҖҳиӢҘиҝҷж ·зҡ„дё»еј жҲҗз«ӢпјҢж— з–‘дјҡеүӘж–ӯж–°е…ҙ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иө·йЈһзҡ„зҝ…иҶҖгҖӮ
е…ӯгҖҒ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гҖҒ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зӯүй—®йўҳиҜ„дј°
жңҖеҗҺпјҢжҲ‘们з®ҖиҰҒеӣһзӯ”дёҖдёӢ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и§„жЁЎгҖҒеңҲең°йҖ жҲҗзҡ„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д»ҘеҸҠ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зҡ„жҜ”дҫӢзӯүй—®йўҳгҖӮ
пј‘пјҺеӨҡеӨ§жҜ”дҫӢзҡ„еҸҜиҖ•ең°иў«еңҲеҚ пјҹ
е…ідәҺ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иӢұж је…°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йўҮжңүдәүи®®зҡ„иҜқйўҳгҖӮйҡҸзқҖж—©жңҹ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дҪңе“Ғзҡ„еЈ°еҗҚиҝңж’ӯ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ж №ж·ұи’Ӯеӣәзҡ„вҖңеңҲең°еҚ°иұЎвҖқпјҢеҚідҪҝдёҚжҳҜвҖңжҠҠжҜҸеҜёеңҹең°йғҪеӣҙиө·жқҘеҒҡзү§еңәвҖқпјҢеӣҙеңҲдәҶеӨ§йғЁеҲҶеңҹең°еә”иҜҘ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з–‘д№үгҖӮеҸҜжҳҜ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зҡ„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пјҢд»ҘеҸҠпј‘пјҷ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д»ҘжқҘзҡ„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ж ·зҡ„з»“и®әжңүжӮ–дәҺеҺҶеҸІдәӢе®һпјҢд»ҘеҫҖзҡ„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иў«еӨёеӨ§дәҶгҖӮ
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й—®йўҳз ”з©¶зҡ„дё»иҰҒиө„ж–ҷпјҢжқҘжәҗдәҺ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зҡ„еҮ ж¬Ў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пјҢеҚі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гҖҒ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ҳе№ҙгҖҒ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–е№ҙд»ҘеҸҠ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е®һж–Ҫ并еҸ‘еёғ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пјҢе…¶дёӯ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гҖҒ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зӣёеҜ№е®Ңж•ҙпјҢиў«дәә们жҷ®йҒҚдҪҝз”Ё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”пјҳе№ҙе’Ңпј‘пј•пј–пј–е№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еҸӘз•ҷдёӢдёҖдәӣйӣ¶жҳҹзҡ„и®°еҪ•пјҢиҖҢдё”д»…ж¶үи¶ідёӨдёүдёӘйғЎпјҢеҲ©з”Ёд»·еҖјжңүйҷҗпјҢеҗҺжқҘдәә们еҫҲе°‘жҸҗиө·гҖӮ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е°ҡеҘҪпј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зҡ„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иҷҪ然д№ҹжңүдёҚе°‘зјәйЎ№пјҢеҘҪеңЁиғҪеӨҹеҹәжң¬еҸҚжҳ дёӯйғЁең°еҢәеҚіеңҲең°йҮҚзӮ№еҢәеҹҹзҡ„жғ…еҶөпјҢиҝҷжҳҜпј‘пј•пј‘пј—е№ҙе’Ң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иў«дәә们еҸҚеӨҚеј•иҜҒзҡ„еҺҹеӣ гҖӮ
жӯЈжҳҜд»ҘиҝҷдёӨдёӘ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дёәдҫқжҚ®пјҢпј‘пјҷ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иӢұеӣҪеҺҶеҸІеӯҰ家еҲ©иҫҫе§ҶеҮәзүҲдәҶгҖҠеңҲең°жң«ж—Ҙе®ЎеҲӨгҖӢдёҖд№ҰпјҢејҖеҗҜдәҶ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ё“дёҡжҖ§з ”究зҡ„е…ҲжІі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зҫҺеӣҪеҺҶеҸІеӯҰ家зӣ–дјҠпјҲпјҘпҪ„пҪ—пҪүпҪҺпјҰпјҺпј§пҪҒпҪҷпјү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иҝһз»ӯеҸ‘иЎЁ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зҡ„й•ҝзҜҮи®әж–ҮпјҢжҺЁз®—еҮәж•ҙдёӘ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зҡ„жҜ”йҮҚпјҢд»ҺиҖҢеҲ·ж–°дәҶдәә们зҡ„вҖңеңҲең°еҚ°иұЎвҖқгҖӮеҸҜжғңиҝҷдёҖ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пј’пјҗдё–зәӘпјҳпјҗе№ҙд»ЈжүҚд»Ӣз»ҚеҲ°дёӯеӣҪеӯҰз•ҢпјҢж—¶йҡ”пј—пјҗе№ҙд№Ӣд№…гҖӮзӣ–дјҠзҡ„з»“и®әжҳҜпјҡд»Һпј‘пј”пј•пј•еҲ°пј‘пј–пјҗпј—е№ҙй—ҙпјҢе°ұжүҖи°ғжҹҘзҡ„пј’пј”дёӘйғЎиҖҢиЁҖпјҢе…ұеңҲең°пј•пј‘пј–пј–пј—пј“иӢұдә©пјҢеҚ пј’пј”дёӘ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пј’пјҺпј—пј–пј…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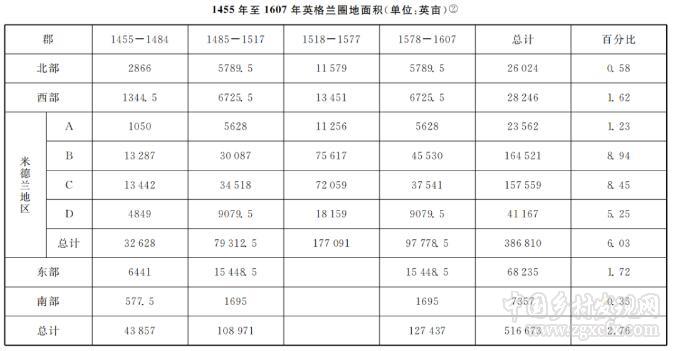
зӣ–дјҠжҸҗдҫӣзҡ„ж•°жҚ®иЎЁжҳҺпјҢеңҲең°зҡ„规模дёҚеӨ§пјҢжҳҫ然еӨ§еӨ§еҮәд№Һдәә们еҜ№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дёҖиҲ¬еҚ°иұЎпјҢдёәжӯӨзӣ–дјҠи§ЈйҮҠиҜҙпјҡвҖ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ҳҜжёҗиҝӣзҡ„пјҢжҳҜж–ӯж–ӯз»ӯз»ӯзҡ„гҖӮе®ғз»қжІЎжңүйӮЈд№Ҳжҷ®йҒҚ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йҖҡеёёжүҖжҸҸиҝ°зҡ„йӮЈд№Ҳе…·жңүз ҙеқҸжҖ§гҖӮвҖқд»–и®ӨдёәпјҢеңҲеҚ е…¬ең°еҲәжҝҖдәҶдёҖдәӣең°еҢәзҡ„йӘҡд№ұпјҢдёҚиҝҮе…¶еҪұе“Қд№ҹдёҚжҳҜйӮЈд№ҲжҝҖзғҲиҖҢе№ҝжіӣгҖӮеңҲең°йҖҗжёҗжҺЁиЎҢпјҢе®ғеј•иө·зҡ„иҙ«еӣ°е’ҢжҠұжҖЁд№ҹжҳҜйҖҗжёҗиҒҡйӣҶиө·жқҘзҡ„пјҢдё»иҰҒеңЁеңҲең°ж ёеҝғеҢәеҚіиӢұж је…°дёӯйғЁиҜёйғЎгҖӮд»–жҖ»з»“иҜҙпјҡвҖңжҲ‘们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е°Ҫз®ЎеӯҳеңЁдёҚи¶іпјҢдҪҶе®ғжҸҗйҶ’дәә们дёҚиғҪеӨёеӨ§еңҲең°зҡ„е®һйҷ…иҢғеӣҙгҖӮвҖқеә”иҜҘиҜҙпјҢзӣ–дјҠзҡ„з»“и®әд»ЈиЎЁдәҶдёҖдәӣеӯҰиҖ…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и§„жЁЎе’Ңе®һйҷ…зҠ¶еҶөзҡ„еҸҚжҖқгҖӮз”ұдәҺж¶үеҸҠж—¶ж®өиҝҮй•ҝпјҢеҺҹе§Ӣж•°жҚ®дёҚе®ҢеӨҮпјҢеӯҳеңЁдёҖе®ҡзҡ„йЈҺйҷ©пјҢдҪҶжҜ•з«ҹжҳҜд»ҘеҪ“ж—¶ж”ҝеәңзҡ„з»ҹи®ЎжҠҘе‘ҠдёәеҹәзЎҖжҺЁеҮәзҡ„пјҢ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жҜ”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е°ҸеҶҢеӯҗзҡ„жғ…з»ӘжҖ§зҡ„жҸҸиҝ°еҸҜйқ 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зӣ–дјҠејәи°ғеҗ„ең°еҢәзҡ„еңҲең°зЁӢеәҰе·®ејӮжҳҺжҳҫпјҢ继еҲ©иҫҫе§Ҷд№ӢеҗҺпјҢзӣ–дјҠеҶҚж¬Ўз”Ёж•°жҚ®иЎЁжҳҺеңҲең°дё»иҰҒйӣҶдёӯеңЁ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гҖӮдёӯйғЁең°еҢә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жңҖй«ҳжҳҜпјўз»„пјҲеҗ«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ҒеҢ—е®үжҷ®йЎҝйғЎгҖҒжӢүзү№е…°йғЎе’Ң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пјүпјҢеңҲең°жҜ”йҮҚиҫҫпјҳпјҺпјҷпј”пј…пјӣпјЈз»„д№ҹй«ҳиҫҫпјҳпјҺпј”пј•пј…гҖӮдёӯйғЁең°еҢәд»ҘеӨ–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йғҪжІЎжңүи¶…иҝҮпј’пј…пјҢ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жңҖе°Ҹзҡ„еҢ—йғЁе’ҢеҚ—йғЁең°еҢәдёҚиҝҮпјҗпјҺпј•пј…е·ҰеҸігҖӮйңҖиҰҒиҜҙжҳҺзҡ„жҳҜпјҢзӣ–дјҠдј°и®Ў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пјҢдёҚжҳҜеҚ еҸҜиҖ•ең°зҡ„зҷҫеҲҶжҜ”пјҢиҖҢжҳҜеҚ еңҲең°жүҖеңЁ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зҷҫеҲҶжҜ”пјҲпҪ”пҪҸпҪ”пҪҒпҪҢ пҪҢпҪҒпҪҺпҪ„ пҪҒпҪ’пҪ…пҪҒ пҪҸпҪҶ пҪғпҪҸпҪ•пҪҺпҪ”пҪҷпјүгҖӮ
пј’пјҗдё–зәӘеҲқпјҢ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еҶІеҮ»дәҶеӯҰз•Ңзҡ„дј з»ҹи®ӨзҹҘпјҢеҫ—еҲ°дәҶ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еӯҰиҖ…зҡ„е‘јеә”пјҢд№ҹеҸ—еҲ°дәҶдәә们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Ңе°Өе…¶еҜ№зӣ–дјҠ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йҮҚпјҢеҚівҖң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вҖқдёҺвҖңеңҲең°зҡ„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вҖқд№ӢжҜ”зҡ„ж–№жі•пјҢдәә们жҷ®йҒҚдёҚдәҲи®ӨеҗҢгҖӮвҖңеңҲең°жүҖеңЁзҡ„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жҠҪиұЎзҡ„з©әй—ҙжҰӮеҝөпјҢйҷӨеҜ№ең°зҗҶеӯҰ家д»ҘеӨ–йғҪж„Ҹд№үз”ҡеҫ®вҖқпјҢзңҹжӯЈ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еҚ еҸҜ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зҡ„жҜ”йҮҚ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еҸҜиҖ•ең°еҢ…жӢ¬еә„зЁјең°жқЎз”°пјҢд№ҹеҢ…жӢ¬иҚүең°зү§еңәе’Ңжңүеҫ…ејҖеҸ‘зҡ„иҚ’ең°е’Ңжһ—ең°пјҢеҚідј з»ҹзҡ„ж•һз”°гҖӮ马дёҒпјҲпјӘпҪҸпҪҲпҪҺ пјҘпјҺпјӯпҪҒпҪ’пҪ”пҪүпҪҺпјүд№ҹжҢҮеҮә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Ҫұе“Қзҡ„зңҹе®һиЎЁиҫҫжҳҜ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дёҺеҸҜ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д№ӢжҜ”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дёҺеңҲең°жүҖеңЁйғЎзҡ„жҖ»йқўз§ҜжҲ–иӢұж је…°жҖ»йқўз§Ҝд№ӢжҜ”гҖӮжҢүз…§дҝ®жӯЈеҗҺзҡ„жҰӮеҝөеҚі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дёҺеҸҜ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д№ӢжҜ”пјҢ并дҫқжҚ®й©¬дёҒе…ідәҺеҸҜ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дёәйғЎйқўз§Ҝзҡ„пј–пјҗпј…зҡ„дј°и®ЎпјҢзӣ–дјҠдј°з®—зҡ„пј’пјҺпј—пј–пј…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йҮҚе®һйҷ…дёҠжҳҜпј”пјҺпј–пј…гҖӮдёҚиҝҮдәә们зҡ„жү№иҜ„дёҚжӯўдәҺжӯӨпјҢдёҖдәӣеӯҰиҖ…и®ӨдёәпјҢеҚідҪҝдҝ®жӯЈд»ҘеҗҺпјҢзӣ–дјҠ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йҮҚд»Қ然иҝҮдҪҺгҖӮиҫғж—©зҡ„жү№иҜ„иҖ…жҳҜжүҳе°ј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зӣ–дјҠ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зҡ„иҜ„дј°жңүзјәйҷ·пјҢд»–жІЎжңүе°ҶеҪ“ж—¶ең°ж–№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жјҸжҠҘгҖҒзһ’жҠҘзҡ„еӣ зҙ иҖғиҷ‘еңЁеҶ…пјҢеӣ дёәйӮЈдәӣ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жңүж—¶д»ҺеҪ“ең°еңҹең°жүҖжңүиҖ…дёӯжҢ‘йҖүпјҢиҖҢ且委е‘ҳдјҡзҡ„и°ғжҹҘжҙ»еҠЁеҫҖеҫҖеӨ„дәҺйўҶдё»зҡ„зӣ‘и§Ҷд№ӢдёӢгҖӮжүҳе°јжҸҗеҮәиҙЁз–‘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жӢҝеҮәиҮӘе·ұзҡ„зі»з»ҹж•°жҚ®гҖӮ
еӣҙз»•зӣ–дјҠзҡ„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пјҢдёҚж–ӯжңүж–°и§Ғи§Је’Ңж–°жҲҗжһңеҸ‘иЎЁгҖӮеҗҢж—¶д»Јзҡ„еӯҰиҖ…йҳҝз‘ҹВ·пјЁВ·зәҰзҝ°йҖҠпјҲпјЎпҪ’пҪ”пҪҲпҪ•пҪ’ пјЁпјҺпјӘпҪҸпҪҲпҪҺпҪ“пҪҸпҪҺпјүеҹәжң¬иөһеҗҢзӣ–дјҠзҡ„з»“и®әпјҢеҗҢж—¶з»ҷдәҲдәҶдёҖдәӣдҝ®жӯЈ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еҺҶж¬Ў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зҡ„ж•°жҚ®еҸҜиғҪйғҪдҪҺдәҺ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пјҢжүҖд»Ҙ1455пјҚ1607е№ҙеңҲең°дёҚжӯўзӣ–дјҠз»ҹи®Ўзҡ„ж•°жҚ®гҖӮ1517е№ҙ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еҝҪз•ҘдәҶеҫҲеӨҡеңҲең°пјҢдҫӢеҰӮе°ҶдёҖдәӣеңҲең°еҪ“дҪңвҖңжңүзӣҠвҖқеңҲең°вҖ”вҖ”вҖ”з»Ҹжқ‘еә„е…ұеҗҢдҪ“еҚҸе•ҶдёҚдә§з”ҹз ҙеқҸжҖ§зҡ„еңҲең°вҖ”вҖ”вҖ”жүҖд»ҘдёҚи®Ўз®—еңЁеҶ…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ңҲең°еҸҜиғҪиў«зһ’жҠҘгҖӮжө·е°”ж–ҜжҳҜ1607е№ҙ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жҲҗе‘ҳд№ӢдёҖпјҢд»–еҫҲи®Өзңҹең°и®°иҪҪдәҶ他们еңЁи°ғжҹҘеңҲең°ж—¶йҒҮеҲ°йЎҪејәжҠөжҠ—гҖҒиҺ·еҫ—иө„ж–ҷзӣёеҪ“еӣ°йҡҫ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дёҖдәӣеңҲең°иҖ…иҝ«дҪҝе…¶дҪғжҲ·еңЁжі•еәӯеүҚеҸ‘иӘ“пјҢеҗҰе®ҡеңҲең°зҡ„дәӢе®һпјӣдёҖдәӣз©·дәәеҮәеәӯеҸ—еҲ°еЁҒиғҒгҖӮи°ғжҹҘ委е‘ҳ们д№ҹз»Ҹеёёиў«ж¬әйӘ—гҖӮзәҰзҝ°йҖҠдј°и®Ўе®һйҷ…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дёҚжӯўзӣ–дјҠз»ҹи®Ўзҡ„516673иӢұдә©пјҢиҖҢжҳҜ744000иӢұдә©пјҢеҚ еңҲең°зҡ„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3.6пј…пјҢжҢү照马дёҒдҝ®жӯЈеҗҺ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зӣёеҪ“дәҺпј–пј…пјҢжҜ”зӣ–дјҠжҸҗй«ҳдәҶиҝ‘1.5дёӘзҷҫеҲҶзӮ№гҖӮ20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иӢұеӣҪеӯҰиҖ…жІғиҝӘпјҲJпјҺWordieпјүеҸ‘иЎЁгҖҠиӢұж је…°еңҲең°иҝӣзЁӢ1500пјҚ1914е№ҙгҖӢдёҖж–ҮпјҢдҪңиҖ…еҫ—еҮә16дё–зәӘе…ұеңҲең°643469иӢұдә©пјҢиҝҷдёӘж•°жҚ®д»ӢдәҺзӣ–дјҠе’ҢзәҰзҝ°йҖҠд№Ӣй—ҙпјҢдёҺ他们иҝҷдёӘж—¶жңҹзҡ„еңҲең°дј°з®—жҜ”иҫғжҺҘиҝ‘пјҢд№ҹжҳҜжҜ”иҫғдҪҺзҡ„гҖӮдёҚиҝҮд»–е°Ҷпј‘пј–дё–зәӘд»ҘеүҚ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дј°з®—зҡ„иҫғй«ҳвҖ”вҖ”вҖ”1500е№ҙж—¶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е·Із»ҸиҫҫеҲ°45пј…пјҢеҲ°1600е№ҙеңҲең°е·ІжҺҘиҝ‘е…ЁеӣҪеҸҜиҖ•ең°зҡ„дёҖеҚҠпјҢд»–иҜҙвҖңиҝҷжҳҜдёӘзІ—з•Ҙзҡ„дј°и®ЎвҖқпјҢдҪҶиҜҒе®һдәҶеҪ“ж—¶еҺҶеҸІиҜҫжң¬дёӯ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ҚіиӢұж је…°еӨ§йғЁеҲҶеҸҜиҖ•ең°д»ҚеӨ„дәҺжқЎз”°зҠ¶жҖҒпјҢд»–иҝҳеҲ—еҮәж•°зҷҫе№ҙеңҲең°е№ҙиЎЁгҖӮжҳҫ然жІғиҝӘ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дј°з®—ж–№ејҸжҜ”иҫғз–Ҹйҳ”пјҢи·іи·ғжҖ§д№ҹеӨ§пјҢжқғдҪңеҸӮиҖғгҖӮеҰӮжӯӨзңӢжқҘпјҢе…ідәҺйғҪй“Һж—¶д»Ј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зҡ„еҲҶжһҗиҝҳеӯҳеңЁиҫғжҳҺжҳҫзҡ„еҲҶжӯ§пјҢжҲ‘们жңҹеҫ…зқҖеҸІж–ҷзҡ„ж·ұеәҰжҢ–жҺҳпјҢд№ҹжңҹеҫ…зқҖжӣҙ科еӯҰзҡ„з»ҹи®Ўж–№жі•пјҢдҪҝеңҲең°зҡ„жҖ»дҪ“ж•°жҚ®иҜ„дј°жңүиҝӣдёҖжӯҘзҡ„ж”№е–„гҖӮ
еңЁзҺ°жңүиө„ж–ҷ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дәә们жҳҜеҗҰеҸҜд»Ҙе…ҲеңЁеҢәеҹҹжҖ§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з ”з©¶дёҠжңүжүҖзӘҒз ҙпјҢд»ҺиҖҢж”№е–„жҖ»дҪ“иҜ„дј°пјҹеңЁеңҲең°ж ёеҝғеҢәеҹҹзұіеҫ·е…°з ”究方йқўе·ІжңүеӯҰиҖ…еҒҡеҮәе°қиҜ•пјҢж–°иҘҝе…°еҺҶеҸІеӯҰ家JпјҺ马дёҒжҳҜе…¶дёӯдёҖдҪҚгҖӮд»–йҰ–е…ҲжҢүз…§дёҖиҲ¬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еҚ йғЎ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60пј…пјҢжҺЁз®—еҮәеҸҜиҖ•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пјҢ然еҗҺеҲҶдёӨжӯҘи°ғж•ҙзӣ–дјҠзҡ„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пјҢе…ҲиЎҘе……дәҶзӣ–дјҠз»ҹи®ЎдёӯйҒ—жјҸзҡ„1518пјҚ1577е№ҙй—ҙзҡ„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пјӣиҖҢеҗҺиЎҘи¶ідәҶ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еҝҪз•Ҙзҡ„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гҖӮжңҖеҗҺеҫ—еҮәз»“и®әпјҡеҲ°17дё–зәӘеҲқеҸ¶пјҢ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еҚ еҸҜиҖ•ең°йқўз§Ҝзҡ„21.1пј…пјҢеҚідә”еҲҶд№ӢдёҖзҡ„еңҹең°и„ұзҰ»дәҶж•һз”°еҲ¶гҖӮ

马дёҒзҡ„зұіеҫ·е…°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ж•°жҚ®еҖјеҫ—еҸӮиҖғгҖӮ马дёҒзҡ„з ”з©¶иЎҘе……е’Ңи°ғж•ҙдәҶ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ёҚиҝҮжІЎжңүе®Ңе…Ёж‘Ҷи„ұ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»–зҡ„з ”з©¶иҝҳжҳҜеңЁзӣ–дјҠз ”з©¶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жҺЁиҝӣзҡ„гҖӮд»–ж”№е–„дәҶ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然иҖҢеҫҲйҡҫиҜҙе®Ңе…ЁйҒҝе…ҚдәҶзӣ–дјҠз ”з©¶зҡ„еҶ’йҷ©жҲҗеҲҶгҖӮеҖҳиӢҘд»Қ然иҒҡз„ҰеңҲең°ж ёеҝғеҢәеҹҹзұіеҫ·е…°пјҢиғҪеҗҰйҮҮз”Ёжӣҙе®һиҜҒзҡ„з ”з©¶ж–№жі•пјҢеҫ—еҲ°йғҪй“Һж—¶жңҹеҢәеҹҹжҖ§еңҲең°зҡ„зҷҫеҲҶжҜ”е‘ў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жҳҜд»ҺеҸҰдёҖдёӘжё йҒ“жқҘйӘҢиҜҒ马дёҒеҢәеҹҹжҖ§зҡ„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е‘ўпјҹ
иҝҳеҘҪпјҢзүӣжҙҘеӨ§еӯҰеё•е…Ӣзҡ„еңҲең°з ”究жҲҗжһңдёәжҲ‘们е®һзҺ°дёҠиҝ°и®ҫжғі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еҸҜиғҪгҖӮеё•е…ӢпјҲLпјҺAпјҺParkerпјүдё“й—Ёд»Һдә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з ”究пјҢеҗҺиҖ…жҳҜеңҲең°ж ёеҝғеҢәеҹҹзұіеҫ·е…°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её•е…Ӣзҡ„з ”з©¶дёҚжҳҜйҮҚж–°и§ЈйҮҠ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зҡ„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пјҢиҖҢжҳҜе®Ңе…ЁдҫқжҚ®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ҸІж–ҷпјҢзӢ¬з«ӢдәҺ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№ҹзӢ¬з«ӢдәҺ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зҡ„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еҫ—еҮәиҮӘе·ұ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еӣ жӯӨжӣҙе…·ең°еҢәжҖ§д№ҹжӣҙе…·е®һиҜҒжҖ§гҖӮиҲҚеҺ»её•е…Ӣз№ҒеӨҚгҖҒзҝ”е®һзҡ„еҸІе®һиҖғиҜҒе’ҢжҺЁи®әпјҢе…¶жңҖеҗҺжҸҗдҫӣзҡ„з»ҹи®Ўж•°жҚ®жҳҜпјҡ1485пјҚ1607е№ҙжңҹй—ҙпјҢеңЁж•ҙдёӘ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370дёӘжқ‘еә„дёӯпјҢеӨ§зәҰдёүеҲҶд№ӢдёҖзҡ„еңҹең°еҚі118дёӘжқ‘еә„еҸ—еҲ°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Ҫұе“ҚжҳҺжҳҫпјҢиҖҢ118дёӘжқ‘еә„дёӯеңҲең°зЁӢеәҰд№ҹдёҚдёҖж ·пјҢе…¶дёӯеӨ§зәҰдёүеҲҶд№ӢдёҖжқ‘еә„зҡ„еңҹең°иў«е®Ңе…ЁеңҲеӣҙгҖӮеё•е…Ӣзҡ„ж•°жҚ®е’Ңи§ЈйҮҠйғҪзӣёеҪ“жңүеҲҶйҮҸпјҢеҸҜжғңд»–жӯўжӯҘдәҺжӯӨпјҢжІЎжңүеҜ№жүҖж¶үзҢҺзҡ„118жқ‘еә„дҪңеҮәж•ҙдҪ“еҲӨж–ӯпјҢеӨ§жҰӮеҝ—дёҚеңЁжӯӨгҖӮ笔иҖ…и®ӨдёәпјҢеҸҜд»ҘжІҝзқҖеё•е…Ӣз»ҷе®ҡзҡ„ж•°жҚ®еҗ‘еүҚжҺЁеҚҠжӯҘпјҢе°ұеҸҜд»ҘеҜ№118дёӘжқ‘еә„еңҲең°еҫ—еҮәеҹәжң¬жҰӮеҝөпјҢеә”иҜҘжІЎжңүд»»дҪ•йЈҺйҷ©пјҡе·ІзҹҘ118дёӘжқ‘еә„дёӯжңү1/3жқ‘еә„иў«е®Ңе…ЁеңҲеӣҙзҡ„дәӢе®һпјҢеҒҮи®ҫдҪҷдёӢзҡ„жқ‘еә„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дёәйӣ¶пјҢйӮЈд№ҲеҸҜд»ҘиҜҙ118жқ‘еә„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дёҚдҪҺдәҺ33пј…гҖӮеҶөдё”пјҢдҪҷдёӢжқ‘еә„зҡ„еңҲең°дёҚжҳҜйӣ¶пјҢжӯЈеҰӮеё•е…Ӣе‘ҠиҜүжҲ‘们зҡ„пјҢжңүж–ҮзҢ®иҜҒжҳҺдҪҷдёӢжқ‘еә„д№ҹжңүдёҚеҗҢ规模зҡ„еңҲең°пјҢвҖңдёҖдәӣжқ‘еә„еңЁ16дё–зәӘеҶ…з»ҸеҺҶдәҶ2жҲ–3ж¬ЎеұҖйғЁеңҲең°вҖқпјҢеӣ жӯӨпјҢжҢүз…§жһҒдёәдҝқе®Ҳзҡ„жҖҒеәҰжҲ‘们д№ҹе®Ңе…ЁжңүжҠҠжҸЎең°жҺЁе®ҡпјҢиҝҷ118дёӘжқ‘еә„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иӮҜе®ҡй«ҳдәҺ33пј…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1/3жқ‘еә„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й«ҳдәҺ33пј…пјҢйӮЈд№ҲпјҢеҸҰеӨ–2/3жқ‘еә„еңҹең°зҡ„еңҲең°жғ…еҶөе‘ўпјҹ
еҖјеҫ—еәҶе№ёзҡ„жҳҜпјҢе…ідәҺ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ж•ҙдёӘ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пјҢжҲ‘们еңЁ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еҸ‘зҺ°дәҶдёҖдёӘйўҮжңүж №жҚ®зҡ„жҖ»дҪ“дј°и®ЎпјҢеҸҜдёҺеё•е…Ӣзҡ„з ”з©¶дә’дёәиЎҘе……е’ҢеҚ°иҜҒгҖӮйӮЈж—¶иҝҳжІЎжңүе…ідәҺеңҲең°зҡ„и®®дјҡжі•д»Өи®°еҪ•пјҢжүҖд»ҘжҖ»дҪ“иҜ„дј°зҡ„дҫқжҚ®жҳҜжүҖиғҪжҗңйӣҶеҲ°зҡ„жі•еәӯжЎЈжЎҲгҖҒжүӢзЁҝзӯүеҺҹе§Ӣж–ҮзҢ®гҖҒз»ҹи®ЎжҠҘе‘Ҡе’Ңе…¬и®Өзҡ„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гҖӮжҚ®жӯӨпјҢ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йҖҗжқЎи®°дёӢдәҶжҜҸдёӘжқ‘еӯҗеңҲең°еҗҜеҠЁе’Ңе®ҢжҲҗзҡ„ж—¶й—ҙпјҢ并注жҳҺ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пјҢе…ұ246дёӘжқ‘еә„пјҢеҚіиҰҶзӣ–дәҶиҜҘйғЎжқ‘еә„зҡ„иҝ‘70пј…пјҢжҳҜеё•е…Ӣж•°жҚ®жқҘжәҗзҡ„дёӨеҖҚд»ҘдёҠгҖӮжҲ‘们еңЁ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йҷ„еҪ•дёҠеҸ‘зҺ°пјҢд»ҘвҖ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пјҲйқһи®®дјҡжі•д»Өи®°еҪ•пјүвҖқдёәйўҳпјҢеҲ—еҮәдәҶй•ҝиҫҫж•ҙж•ҙ6йЎөзҡ„з»ҹи®Ўж•°жҚ®еҸҠе…¶ж–ҮзҢ®жқҘжәҗгҖӮдҪңиҖ…жңҖеҗҺзҡ„з»“и®әжҳҜпјҡ
еҹәдәҺзҺ°жңүзҡ„иҜҒжҚ®пјҢиҮі1607е№ҙпјҢдј°и®ЎиҮіе°‘жңү25пј…жң¬йғЎеҶ…зҡ„еҸҜиҖ•ең°иў«еңҲеҚ гҖӮиҝҷжҳҜзӣёеҪ“еҸҜи§Ӯзҡ„йқўз§ҜвҖҰвҖҰиҮі1640е№ҙпјҢжҜҸ3дёӘжқ‘еә„дёӯе·®дёҚеӨҡжңү1дёӘе®Ңе…Ёиў«еңҲеҚ гҖӮ
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д»Һ15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иҮі1607е№ҙ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иҮіе°‘жңү25пј…зҡ„еңҹең°иў«еӣҙеңҲпјӣиҮі1640е№ҙеӨ§зәҰжңү33пј…зҡ„еңҹең°иў«еӣҙеңҲгҖӮиҖғиҷ‘еҲ°её•е…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1/3жқ‘еә„еҚі118дёӘжқ‘еә„33пј…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зҡ„е®һиҜҒз ”з©¶пјҢз»“еҗҲ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ҸІжңүж №жңүжҚ®зҡ„жҖ»дҪ“иҜ„дј°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еҚ еҸҜиҖ•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25пј…е·ҰеҸіеә”иҜҘжҳҜеҸҜдҝЎзҡ„гҖӮ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зҡ„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ж•°жҚ®пјҢеҜ№16дё–зәӘиӢұж је…°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жҖ»дҪ“иҜ„дј°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еҸӮиҖғд»·еҖјгҖӮеңЁ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 ёеҝғзҡ„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пјҢеҪ“еңҲең°йЈҺжҡҙеёӯеҚ·20~25пј…ж•һз”°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Ҫ“ең°еҶңж°‘дёҚж–ӯеҸ‘з”ҹеӨ§е°Ҹ规模зҡ„жҡҙеҠӣжҠөжҠ—еҸҜд»Ҙеҫ—еҲ°и§ЈйҮҠпјҢж•ҙдёӘиӢұж је…°еҸ—еҲ°еҸІж— еүҚдҫӢзҡ„йңҮиҚЎе№¶еј•иө·ж”ҝеәңе’ҢзӨҫдјҡиҲҶи®әе…іжіЁд№ҹ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дәҶгҖӮеҪ“然е°ұе…ЁеӣҪжғ…еҶөиҖҢиЁҖпјҢз”ұдәҺеңҲең°зҡ„иҮӘеҸ‘жҖ§пјҢе№ҝйҳ”зҡ„йқһж ёеҝғең°еҢәдёҺж ёеҝғең°еҢәе·®ејӮжҳҺжҳҫпјҢеңҲең°дё»иҰҒйӣҶдёӯеңЁ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пјҢе…¶д»–ең°еҢәзӣёеҪ“еӨ§иҢғеӣҙзҡ„еңҹең°д»Қ然еӨ„дәҺж•һз”°зҠ¶жҖҒгҖӮ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ең°иҜҙпјҢе№іеқҮ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дёҺж ёеҝғең°еҢәзӣёжҜ”дҪҺеҫ—еӨҡпјҢзӣ–дјҠе’ҢзәҰзҝ°йҖҠзӯүдәәе…ідәҺе…ЁеӣҪ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зҡ„估算并йқһдёҚз»Ҹд№ӢиҜҙгҖӮзӣ–дјҠиҜҙзҡ„дёҚй”ҷпјҢйғҪй“Һж—¶жңҹеңҲең°зЎ®е®һдёҚжҳҜйӮЈж ·е№ҝжіӣиҖҢжҝҖзғҲ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еҗҰеғҸд»–дј°з®—зҡ„йӮЈж ·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д»…еҚ еҸҜиҖ•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ҷҫеҲҶд№ӢеҮ пјҢжҳҫ然иҝҳжңүжҺўи®Ёзҡ„з©әй—ҙгҖӮ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Ҝ•з«ҹеҪұе“ҚдәҶж•ҙдёӘиӢұж је…°пјҢејҖеҲӣдәҶеҶңдёҡгҖҒеҶңжқ‘е’ҢеҶңж°‘еҺҶеҸІзҡ„ж–°ж—¶д»ЈгҖӮжңҹеҫ…зқҖеӣҪеҶ…еӨ–еҸІеӯҰз•Ңдә§з”ҹжӣҙжңүиҜҙжңҚеҠӣзҡ„ж•°жҚ®гҖӮе°ұйҮҚзӮ№еҢәеҹҹз ”з©¶иҖҢиЁҖпјҢжҲ‘们зҡ„иҺұж–Ҝзү№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дёҺ马дёҒзҡ„еҗҢдёәж ёеҝғеҢәеҚіж•ҙдёӘзұіеҫ·е…°еңҲең°ж•°жҚ®пјҲ21.1пј…пјүпјҢзӣёеҪ“жҺҘиҝ‘пјҢиҷҪ然дёӨз§Қж•°жҚ®йҖҡиҝҮ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жё йҒ“иҺ·еҫ—пјҢ然иҖҢж®ҠйҖ”еҗҢеҪ’пјҢжҲ‘们зӣёдҝЎжҳҜд»ҺдёҚеҗҢи§’еәҰйҖҗжёҗйқ иҝ‘еҺҶеҸІеҺҹиІҢдҪҝ然пјҒ
пј’пјҺеӨҡе°‘дҪғеҶңиў«й©ұйҖҗпјҹ
дёҺ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е’ҢжҝҖзғҲзЁӢеәҰзҙ§еҜҶзӣёиҝһ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жҳҜпјҢеңҲең°жңҹй—ҙжңүеӨҡе°‘еҶңж°‘д»Һеңҹең°дёҠиў«й©ұйҖҗгҖӮ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еңҲең°и°ғжҹҘжҠҘе‘ҠпјҢзӣ–дјҠиҝҳжҸҗдҫӣдәҶ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з ҙеқҸж•°жҚ®пјҡдҫӢеҰӮ1485пјҚ1517е№ҙй—ҙиў«жҜҒжҲҝеұӢж•°йҮҸ1745еӨ„пјӣеҶңж°‘жөҒдәЎж•°йҮҸ6931дәәгҖӮ1578пјҚ1607е№ҙй—ҙиў«жҜҒеқҸжҲҝеұӢ966еӨ„пјӣеҶңж°‘жөҒдәЎж•°йҮҸ2232дәәпјҢиҝҷдәӣзІҫзЎ®еҲ°дёӘдҪҚзҡ„ж•°жҚ®з»ҷдәәеҚ°иұЎж·ұеҲ»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й•ҝж—¶ж®өзҡ„з»ҹи®ЎжңӘеҝ…жңүиҝҷж ·зІҫзЎ®дәҶгҖӮзӣ–дјҠжӣҫе®Ҹи§Ӯдј°з®—дәҶж•ҙдёӘеңҲең°еүҚеүҚеҗҺеҗҺеј•иө·зҡ„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д»–и®Ўз®—еҮә1455е№ҙиҮі1637е№ҙй—ҙеӨ§зәҰжңү34000дәәеӨұдёҡпјҢжҢүз…§йҖҡеёёзҡ„жҜ”дҫӢпјҢжҜҸдёӘжҲҗе№ҙз”·жҖ§еҜ№еә”5дёӘдәәпјҢиҝҷе°ұж„Ҹе‘ізқҖжңү17дёҮдәәеҸ—еҲ°дәҶеҪұе“ҚпјҢеҪ“ж—¶иӢұж је…°жҖ»дәәеҸЈеӨ§зәҰжҳҜ300дёҮгҖӮWпјҺжҹҜзү№еӢ’жҢҮеҮәпјҢеҰӮжһңиҝҷдәӣж•°жҚ®жҳҜжӯЈзЎ®зҡ„пјҢе°ұдёҚиғҪиҜҙ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йқһеёёдёҘйҮҚ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иҝҷж ·ж•°йҮҸзҡ„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еҸ‘з”ҹеңЁе°Ҷиҝ‘дёӨдёӘдё–зәӘйҮҢгҖӮ
пјЎпјҺзәҰзҝ°йҖҠ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пјҢе№¶ж №жҚ®1зҠҒең°пјҲpIoughпјүе…»жҙ»5еҸЈд№Ӣ家гҖҒжҺЁжҜҒдёҖеӨ„е®…йҷўзӣёеҪ“дәҺ5дәәиў«иҝ«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зҡ„еҒҮи®ҫпјҢйҮҚж–°и®Ўз®—дәҶ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зҡ„дәәеҸЈж•°йҮҸпјҢд»ҺиҖҢи°ғж•ҙе’ҢиЎҘе……дәҶзӣ–дјҠ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ҫӢеҰӮд»–е°Ҷ1578пјҚ1607е№ҙ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зҡ„дәәеҸЈдј°з®—дёә5002дәәпјҢиҖҢзӣ–дјҠеҺҹжқҘзҡ„дј°з®—жҳҜ2232дәәгҖӮ1607пјҚ1637е№ҙзҡ„ж•°жҚ®е®Ңе…ЁжҳҜзәҰзҝ°йҖҠж·»еҠ дёҠеҺ»зҡ„пјҢдҪҝж•°жҚ®й“ҫжӣҙеҠ е®Ңж•ҙпјҢиҜ·зңӢдёӢйқўеҲ—иЎЁпј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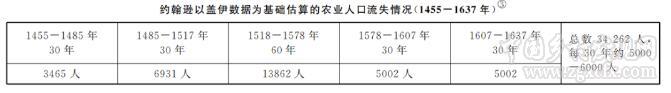
иҝҷйЎ№з»ҹи®Ўе‘ҠиҜүжҲ‘们пјҢеңЁз»ҹи®ЎжүҖеҸҠзҡ„180е№ҙзҡ„еңҲең°жңҹй—ҙпјҢ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е…ұеҮҸе°‘34262дәәпјӣеҰӮжһңд»ҘйғҪй“ҺзҺӢжңқдёәи®Ўз®—е‘ЁжңҹпјҢйғҪй“Һиҝ‘зҷҫе№ҙзҡ„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ҹй—ҙпјҢе…ұеҮҸе°‘25795дәә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иҝҳйңҖ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зәҰзҝ°йҖҠе…ідәҺ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зҡ„иЎЁиҝ°жҳҜдәәеҸЈвҖңжөҒеӨұвҖқпјҲdispIacedпјүиҖҢдёҚжҳҜвҖңй©ұйҖҗвҖқпјҲevictionпјүпјҢ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дёҚд»…еҢ…жӢ¬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дәәеҸЈпјҢиҝҳеҢ…жӢ¬иҮӘ然еҮҸе‘ҳе’ҢеҠіеҠӣиҪ¬з§»дәәеҸЈ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ҚідҪҝеҒҮе®ҡ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йғҪеӣ й©ұйҖҗеј•иө·пјҢйӮЈд№ҲжҜҸ30е№ҙд№ҹдёҚиҝҮе№іеқҮ5000пјҚ6000дҪғеҶңиў«иҝ«зҰ»ејҖеңҹең°пјҢиЎЁжҳҺдҪғеҶң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жғ…еҶөдёҺжҲ‘们зҡ„дј з»ҹеҚ°иұЎдјјйўҮжңүи·қзҰ»гҖӮеҜ№16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й©ұйҖҗдәәеҸЈиҝӣиЎҢйҮҸеҢ–дј°з®—пјҢж— з–‘жҳҜе®ўи§ӮиҜ„дј°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еҪұе“Қзҡ„йҮҚиҰҒж•°жҚ®пјҢ然иҖҢеҸҜйқ зҡ„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зЁҖе°‘пјҢдј°з®—зҡ„йҡҫеәҰжһҒеӨ§пјҢжүҖд»ҘеҸӘжңүе°‘ж•°дҪңиҖ…еңЁиҝҷж–№йқўеҒҡеҮәиҝҮдёҖдәӣе°қиҜ•гҖӮ
20дё–зәӘ50е№ҙд»ЈпјҢеҸӨе°”еҫ·пјҲJпјҺDпјҺGouIdпјүзҡ„з ”з©¶иЎҘе……дәҶжһ—иӮҜйғЎиў«й©ұйҖҗдәәеҸЈзҡ„ж•°жҚ®гҖӮ1607е№ҙ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еңҲең°е§”е‘ҳдјҡе®һйҷ…дёҠи°ғжҹҘдәҶ7дёӘйғЎ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е’ҢеңҲең°зҠ¶еҶөпјҢдҪҶиЎЎе№іжі•еәӯеҸӘдҝқз•ҷдәҶ6дёӘйғЎзҡ„и°ғжҹҘж–ҮзҢ®пјҢжһ—иӮҜйғЎзҡ„иө„ж–ҷдёўеӨұпјҢжүҖд»Ҙзӣ–дјҠжүҖз”Ёзҡ„1607е№ҙзҡ„и°ғжҹҘж•°жҚ®дёӯдёҚеҢ…жӢ¬жһ—иӮҜйғЎ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жһ—иӮҜйғЎи°ғжҹҘж•°жҚ®зҡ„ж‘ҳиҰҒдҝқеӯҳдәҶдёӢжқҘпјҢиҜҘж–ҮзҢ®зј–еҶҷдәҺ1608е№ҙ9жңҲеә•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дҪңеҸӮиҖғжүӢеҶҢд№Ӣз”ЁпјҢж ҮйўҳдёәвҖңжһ—иӮҜйғЎеңҲең°и°ғжҹҘ委е‘ҳдјҡ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и°ғжҹҘз®ҖжҠҘвҖқпјҢи—ҸеӯҳеңЁеӨ§иӢұеҚҡзү©йҰҶзҡ„CaesarpapersжЎЈжЎҲдёӯпјҢеҸӨе°”еҫ·жӯЈжҳҜж №жҚ®иҝҷйғЁеҲҶиө„ж–ҷжҺЁз®—еҮәжһ—иӮҜйғЎ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дәәеҸЈж•°йҮҸгҖӮиҜҘж‘ҳиҰҒеҲҶдёүдёӘйғЁеҲҶпјҢеҲҶеҲ«жҳҜеҮҜж–Ҝи’Ӯж–ҮпјҲKestevenпјүгҖҒжһ—еҫ·иөӣпјҲLindseyпјүе’ҢйңҚе…°еҫ·пјҲHoIIandпјүдёүдёӘең°еҢәзҡ„иө„ж–ҷгҖӮйҒ—жҶҫзҡ„жҳҜжҲҝеұӢжҜҒеқҸе’Ң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зҡ„е…·дҪ“ж•°жҚ®йғҪйҒ—еӨұдәҶпјҢдҪҶеҸӨе°”еҫ·йҖҡиҝҮйҒ—еӯҳзҡ„жқҗж–ҷиҝҳжҳҜжҺЁжөӢеҮәеҶңжҲ·жҲҝеұӢжҚҹе®і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ҡ1578пјҚ1607е№ҙиҜҘйғЎеҶңжҲ·жҲҝеұӢжҜҒеқҸгҖҒз©әзҪ®жҲ–иҖ…еҸҳдёәиҢ…иҲҚзҡ„ж•°йҮҸжҖ»и®Ў1292жҲ·пјҲеҢ…жӢ¬еҮҜж–Ҝи’Ӯж–Үең°еҢә260жҲ·пјҢжһ—еҫ·иөӣең°еҢә966жҲ·пјҢйңҚе…°еҫ·ең°еҢә66жҲ·пјүгҖӮеҸӨе°”еҫ·зҡ„ж•°жҚ®жҳҫ然жңүзӣёеҪ“зҡ„еҒҮи®ҫжҲҗеҲҶпјҢжқғдҪңеҸӮиҖғгҖӮ
20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пјҢ马дёҒжҸҗдҫӣдәҶйҮҚзӮ№ең°еҢәйғЁеҲҶж—¶ж®өзҡ„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жғ…еҶөгҖӮ马дёҒжҢҮеҮәпјҢеңЁж•ҙдёӘйғҪй“Һж—¶жңҹпјҢиӢұж је…°и¶…иҝҮ80пј…зҡ„еңҲең°е’Ң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и®°еҪ•еҸ‘з”ҹеңЁзұіеҫ·е…°ең°еҢәпјҢеңЁ16дё–зәӘеҗҺеҚҠжңҹпјҢеңҲең°иЎҢдёәжӣҙеҠ йӣҶдёӯдәҺзұіеҫ·е…°и…№ең°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гҖҒ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’Ң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гҖӮеңЁ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пјҢ1578пјҚ1607е№ҙжңүеңҲең°и®°иҪҪзҡ„67дёӘж•ҷеҢәдёӯпјҢ51дёӘж•ҷеҢә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иҮіе°‘195жҲ·дҪҸе®…жҚҹжҜҒпјӣеңЁ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пјҢйғЎеҶ…400дёӘж•ҷеҢәдёӯжңү34дёӘж•ҷеҢә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иҮіе°‘113жҲ·жҲҝеұӢжҚҹжҜҒпјӣеңЁ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пјҢ118дёӘж•ҷеҢәдёӯжңү358жҲ·дҪҸе®…жҜҒеқҸгҖӮжҳҫ然пјҢеҚідҪҝеҗҢеңЁеңҲең°зҡ„ж ёеҝғең°еҢәпјҢеҗ„йғЎзҡ„жғ…еҶөд№ҹдёҚдёҖж ·пјҢеңЁиҝ‘пј“пјҗе№ҙзҡ„ж—¶й—ҙйҮҢпјҢ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Өҡж•°ж•ҷеҢәйғҪеҸ‘з”ҹдҪғжҲ·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иҖҢ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еҚҙеӨ§зӣёеҫ„еәӯпјҢеҸӘжңү8пј…зҡ„ж•ҷеҢәеҸ‘з”ҹеҶңжҲ·жөҒеӨұгҖӮжҖ»зҡ„зңӢпјҢ马дёҒе…ідәҺ16дё–зәӘеҗҺжңҹиҜҘең°еҢә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жөҒеӨұзҡ„ж•°жҚ®дёҚй«ҳпјҢиҝ‘30е№ҙеҶ…жҜҸдёӘж•ҷеҢәеҚіжқ‘еә„дёҚиҝҮеҮҸе°‘иӢҘе№ІжҲ·пјҢеӨ§жҰӮдёҺиҜҘж—¶жңҹ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йҖҗжёҗжөҒиЎҢжңүе…ігҖӮ
йғҪй“ҺзҺӢжңқж—¶д»Јз•ҷдёӢзҡ„дёҖдәӣи®әиҫ©жҖ§зҡ„иө„ж–ҷеҗҢж ·е…·жңүд»·еҖјпјҢдёҚиҝҮеҝ…йЎ»еҠ д»ҘеҲҶжһҗгҖӮиЁҖеҸҠйғҪй“Һж—¶д»ЈдҪғеҶңзҡ„дёҖж®өж–Үеӯ—еҶҷйҒ“пјҢ他们ж”ҫејғдәҶиҖ•дҪңпјҢзҰ»ејғдәҶ他们зҡ„иҖ•зҠҒпјҢвҖңзҹӯзҹӯеҮ е№ҙеҶ…пјҢ500дёӘй“ҒзҠҒе°ұиҝҷд№Ҳз”ҹй”ҲдәҶвҖқпјҢд»ҘеҸҠвҖңеңЁ8000иӢұдә©иҖ•ең°дёӯпјҢиҝ‘е№ҙд»Қ然иҝҳз§Қеә„зЁјеңҹең°дёҚиҝҮдёҖдёӨзҷҫиӢұдә©вҖқ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еңЁ20дё–зәӘ欧жҙІеӯҰз•Ңдә«жңүзӣӣиӘү并被称дёәеҹәзқЈж•ҷ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иҖ…зҡ„жүҳе°ји®ӨдёәпјҢиҝҷдәӣжҸҸиҝ°вҖңжҳҫ然д»ӨдәәжҖҖз–‘пјҢжүҖдёҫдәӢдҫӢд№ҹеӨҡжҳҜеӯӨдҫӢпјҢиҖҢйқһе…ёеһӢвҖқгҖӮд»–иҜҙжӣҙжңүз”ҡиҖ…пјҢе°Ҷ1485пјҚ1550е№ҙд№Ӣй—ҙиў«й©ұйҖҗзҡ„дәәеҸЈеҸ еҠ иө·жқҘпјҲеҢ…жӢ¬дёҚеҗҢе№ҙйҫ„ж®өзҡ„дәәпјүпјҢеҫ—еҲ°30дёҮиҝҷдёӘж•°еӯ—пјҢвҖңж— з–‘жҳҜжӯҰж–ӯзҡ„пјҢз”ҡиҮіиҝһеӢүејәзҡ„зҢңжөӢйғҪз®—дёҚдёҠвҖқгҖӮжүҳе°јжҢҮеҮәпјҢ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дё»жөҒи§ӮзӮ№еӯҳеңЁиҜҜеҢәпјҢдёҚи®әжүҳ马ж–ҜВ·иҺ«е°”пјҲSir Thoma s Moreпјүиҝҷж ·ж—©жңҹзҡ„зҗҶжғідё»д№үиҖ…пјҢиҝҳжҳҜзЁҚеҗҺзҡ„еӯҰиҖ…еј—жң—иҘҝж–ҜВ·еҹ№ж №пјҲFrancis BaconпјүпјҢи®ӨдёәеҶңдёҡйқ©е‘ҪиҝӣзЁӢдёӯеӨ§йҮҸдәәеҸЈиў«й©ұйҖҗпјҢжңүиҝқдәӢе®һгҖӮжүҳе°јзӣёеҪ“йҮҚи§Ҷ并系з»ҹеј•иҜҒдәҶзӣ–дјҠе…ідәҺй©ұйҖҗдәәеҸЈ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дёҚиҝҮеҜ№е…¶зІҫзЎ®еәҰд№ҹжҸҗеҮәдәҶз–‘й—®гҖӮд»–и®ӨдёәжҲ‘д»¬ж— жі•еҲӨж–ӯеҪ“ж—¶еҲ°еә•еҚ еӨҡеӨ§жҜ”дҫӢзҡ„дәәеҸЈиў«й©ұйҖҗгҖӮ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пјҢиў«й©ұйҖҗдәәеҸЈзҡ„йҮҸеҢ–еҲҶжһҗд»Қ然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еҸҜжӣҝд»Јзҡ„з»ҙеәҰ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们жңҹеҫ…зқҖеҸ‘зҺ°жӣҙеӨҡзҡ„ж•°жҚ®жқҘжәҗпјҢд№ҹжңҹеҫ…зқҖжӣҙжңүиҙЁйҮҸзҡ„еҲҶжһҗгҖӮ
пј“пјҺеңҲең°дё»иҰҒз”ЁдәҺзү§зҫҠпјҲshipпјҚfarmingпјүпјҹ
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пјҢ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жҖ»жҳҜдёҺвҖңе…»зҫҠвҖқиҝһ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еңҲең°зңҹзҡ„дё»иҰҒз”ЁдәҺзү§зҫҠпјҲshipпјҚfarmingпјүеҗ—пјҹйқһд№ҹгҖӮ19дё–зәӘжң«еҸ¶еҲ©иҫҫе§Ҷзҡ„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е·ІжҳҺзЎ®еҗҰи®ӨдәҶиҝҷдёҖзӮ№пјҢд»–д»ҘеҸІе®һе’Ңзӣёе…іж•°жҚ®дёәжҚ®жҢҮеҮәпјҢе…¶ж—¶еҫҲеӨҡеңҲең°еҠЁжңәжҳҜдёәдәҶжӣҙжңүж•ҲзҺҮең°иҖ•дҪңпјҢиҖҢйӮЈдёҖж—¶жңҹзҡ„дҪңиҖ…жҳҫ然еӨёеӨ§дәҶ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й”ҷиҜҜең°е°Ҷе…¶и®ӨдҪ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Җ»ж–№еҗ‘гҖӮдёҚиғҪеҗҰи®ӨпјҢеӣҪйҷ…еёӮеңәеҜ№зҫҠжҜӣзҡ„йңҖжұӮпјҢжҺЁеҠЁдәҶе…»зҫҠдёҡпјҢ并еҜјиҮҙеӨ§зүҮ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пјҢ然иҖҢ并йқһжүҖжңүеңҲең°йғҪеҸҳжҲҗзү§еңәгҖӮж·ұе…Ҙи§ӮеҜҹдёҖдёӢе°ұдјҡеҸ‘зҺ°пјҢ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жҳҜдёҺе…»зҫҠдёҡд»ҺиҖҢдёҺ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еҜҶеҲҮзӣёиҝһзҡ„гҖӮ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еңҲең°жҲҗдёәзү§еңәзҡ„йқўз§ҜеҚ иҜҘйғЎеңҲең°жҖ»йқўз§Ҝзҡ„86пј…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жғ…еҶөйўҮдёәе°‘и§ҒпјҢеӣ дёәйӮЈйҮҢзҡ„ең°зҗҶзҺҜеўғжӣҙйҖӮеҗҲж”ҫзү§иҖҢдёҚйҖӮеҗҲиҖ•дҪңгҖӮ16дё–зәӘж—…иЎҢ家йҮҢе…°еҫ·пјҲLeIandпјүеңЁ1532пјҚ1536е№ҙзҡ„ж—…иЎҢж—Ҙи®°дёӯиҝҷж ·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жІғйҮҢе…ӢйғЎиў«еҹғж–ҮжІіпјҲAvonRiverпјүеҲҶдёәеҚ—еҢ—дёӨйғЁеҲҶпјҢеҢ—йғЁжҳҜйҳҝзҷ»пјҲArdenпјүжЈ®жһ—еҢәпјҢеңҹең°еӨ§еӨҡжҳҜиҚүең°пјҢдёҚйҖӮе®ңеҶңиҖ•пјӣеҚ—йғЁжҳҜж•һз”°ең°еҢәпјҢиҖ•ең°иӮҘжІғгҖӮвҖқеҢ—е®үжҷ®ж•ҰйғЎиҘҝеҚ—йғЁжҳҜдёҳйҷөең°еёҰпјҢеҢ—йғЁжҳҜй«ҳең°пјҢеңЁжӯӨиҫғеӨ§и§„жЁЎеңҲең°е№¶еҸҳдёәзү§еңәзӣёеҪ“зҡ„жөҒиЎҢпјҢдёҖдәӣеҶңеңә主规模жҖ§ең°йҘІе…»зҫҠзҫӨгҖӮ16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еј—ж–ҜеҲ©зҷҫжҲ·еҢәпјҲFawsIeyпјүпјҢеҪ“ең°жңҖеӨ§зҡ„зҫҠзҫӨ2500еҸӘпјҢе…¶д»–зҫҠзҫӨ规模дёә500еҸӘгҖҒ600еҸӘгҖҒ2000еҸӘгҖӮ1547е№ҙе…»зҫҠж•°йҮҸз»ҹи®ЎдёӯпјҢиҜҘйғЎе…ұе…»зҫҠ66700еҸӘпјҢд»…17е№ҙеҗҺпјҢиҮі1564е№ҙпјҢи®°еҪ•еңЁжЎҲзҡ„зҫҠзҫӨж•°йҮҸеўһеҠ еҲ°173зҫӨпјҲеўһй•ҝдәҶ54пјҺ5пј…пјүпјҢе…»зҫҠж•°йҮҸд№ҹеўһеҠ еҲ°69980еҸӘпјҲеўһеҠ дәҶ4пјҺ9пј…пјүгҖӮиҝҷдәӣең°еҢәеңҲең°еҫҖеҫҖдјҙйҡҸзқҖжҲҝеұӢжҜҒеқҸгҖҒеҶңдёҡдәәеҸЈеҮҸе°‘пјҢдёҖдәӣеӨ§зү§еңәжүҖеңЁең°жӯЈжҳҜйӮЈдәӣиў«иҚ’еәҹзҡ„жқ‘еә„жүҖеңЁең°еҢәгҖӮиҝҷжҳҜзңҹе®һ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дёҚиҝҮеҸӘжҳҜеҸ‘з”ҹеңЁдёҖйғЁеҲҶең°еҢәпјҢеҮҶзЎ®иҜҙеҸӘжҳҜеҸ‘з”ҹеңЁе°‘йғЁеҲҶең°еҢәгҖӮ
иҝҳжңүдёҖз§Қи§ӮзӮ№и®ӨдёәпјҢиҫғеӨ§еһӢеңҲең°еҶңеңәжӣҙе®№жҳ“иҪ¬еҸҳдёәд»ҺдәӢе…»зҫҠдёҡзҡ„зү§еңәпјҢеӣ дёәеҶізӯ–дәәж•°е°‘пјҢжӣҙе®№жҳ“иҪ¬еҸҳз»ҸиҗҘж–№еҗ‘пјҢиҖҢдё”дёҖеҝғж”«еҸ–еҲ©ж¶ҰгҖӮеҗ¬иө·жқҘжңүдёҖе®ҡйҒ“зҗҶпјҢдәӢе®һдёҠд№ҹжңӘеҝ…然гҖӮдёӢйқўдёӨз»„ж•°жҚ®пјҢеҸҜд»Ҙеӣһзӯ”дёҠиҝ°й—®йўҳгҖӮдёҖз»„еҶңеңәзҡ„ж•°жҚ®пјҢиЎЁжҳҺ65дёӘеҶңеңәзҡ„еҶңзү§дёҡз»“жһ„пјҢжқҘиҮӘдёҚеҗҢең°еҢә50дёӘеә„еӣӯпјҢе…¶дёӯ60пј…д»ҘдёҠзҡ„еҶңеңә规模иҫҫеҲ°200иӢұдә©д»ҘдёҠ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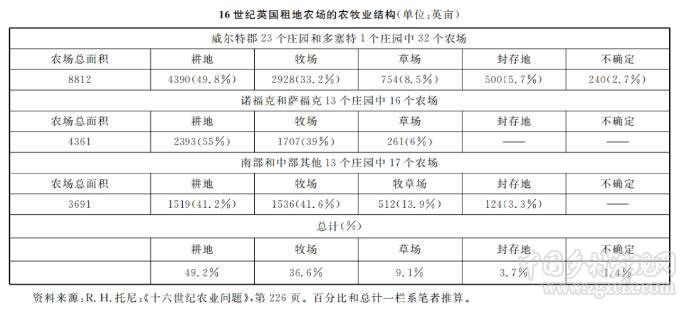
дёҠиҝ°ж•°жҚ®иЎЁжҳҺпјҢиҫғеӨ§еһӢеңҲең°еҶңеңәд№ҹжңӘеҝ…е…»зҫҠпјҢ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жҳҜи°·зү©з§ҚжӨҚзҡ„еңҹең°е’Ңж”ҫзү§зҡ„еңҹең°еӨ§зәҰеҗ„еҚ дёҖеҚҠпјҢз•ңзү§дёҡ并没жңүеҚ жҚ®дјҳеҠҝ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еҶңеңә主并йқһжҖ»жҳҜзү§зҫҠиҖ…пјҢйӮЈдёӘж—¶жңҹзҡ„дҪңиҖ…жҳҫ然жҠҠиҖ•ең°еҸҳзү§еңәзҡ„жҜ”дҫӢеӨёеӨ§дәҶгҖӮиҖҢдёҖиҲ¬еҶңжҲ·жүӢйҮҢзҡ„еңҹең°жӣҙдёҚдјҡдё»иҰҒз”ЁдәҺзү§зҫҠпјҢдёҚи®әеӣҙеңҲең°иҝҳжҳҜйқһеӣҙеңҲең°гҖӮжүҳе°јеҗҢж—¶жҸҗдҫӣдәҶ16дёӘеә„еӣӯдҪғеҶңжҢҒжңүең°зҡ„еҶңзү§дёҡз”Ёең°жҜ”дҫӢпјҢжҜӢеәёзҪ®з–‘пјҢз§ҚжӨҚи°·зү©зҡ„иҖ•ең°еҚ жҚ®з»қеҜ№дјҳеҠҝпјҢй«ҳиҫҫ87пјҺ7пј…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зӣ®зҡ„жҳҜдёәдәҶжҳҺзЎ®еңҹең°дә§жқғпјҢжҸҗй«ҳеңҹең°зҡ„дҪҝз”Ёж•ҲзҺҮпјҢжүҖд»ҘеңҲең°еҗҺд»Қ然用дәҺи°·зү©з§ҚжӨҚпјҢеҸҳжҲҗзү§еңәзҡ„еҸӘеҚ е°‘йғЁеҲҶгҖӮ
дёғгҖҒз»“иҜӯ
зҺ°еңЁпјҢжҲ‘们еҜ№е…Ёж–ҮеҪ’зәіеҰӮдёӢгҖӮ
е…¶дёҖпјҢвҖңеңҲең°вҖқжҳҜдё–з•ҢеҺҶеҸІдёҠзҡ„第дёҖж¬Ўе…·жңүеёӮеңәжҢҮеҗ‘зҡ„еңҹең°зЎ®жқғиҝҗеҠЁпјҢжҳҜжҠҠе…·жңүе…ұеҗҢдҪ“жҖ§иҙЁзҡ„ж··еҗҲеңҹең°жүҖжңүеҲ¶з•Ңе®ҡдёәжҺ’д»–жҖ§зҡ„з§Ғдәәдә§жқғпјҢд»ҺиҖҢжҝҖеҠұ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пјҢйў иҰҶ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з»ҸиҝҮж•°дёӘдё–зәӘзҡ„зү©иҙЁз§ҜзҙҜгҖҒжқғеҲ©з§ҜзҙҜе’Ңи§Ӯеҝөз§ҜзҙҜпјҢзӨҫдјҡж·ұеұӮз»“жһ„еҸ‘з”ҹдәҶжһҒдёәж·ұеҲ»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е…¶дёӯеңҹең°еёӮеңәеҢ–е’ҢеҶңж°‘зҡ„зӨҫдјҡеҢ–жҳҜеҹәзЎҖжҖ§зҡ„еҸҳйҮҸеҸӮж•°пјҢеңҲең°жҳҜиҝҷз§ҚеҸҳеҢ–зҡ„еҺҶеҸІжҖ§жҖ»з»“гҖӮйүҙдәҺжӯӨпјҢ笔иҖ…ејәи°ғжҢҮеҮәпјҢеӣҪеҶ…еӯҰз•ҢйІңжңүжҸҗеҸҠзҡ„еҶңж°‘еңҲең°пјҡдёҚд»…йўҶдё»д№Ўз»…еңҲең°пјҢе…¶е®һеҶңж°‘д№ҹеңЁеңҲең°пјҢ他们иҮӘеҸ‘ең°ж•ҙеҗҲеҲҶж•Јзҡ„жқЎз”°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йҮҚиҰҒз»„жҲҗйғЁеҲҶгҖӮеҸҚиҝҮжқҘпјҢ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дҪҝеҶңж°‘жңҖз»ҲеүҘзҰ»дәҶеә„еӣӯе…ұеҗҢдҪ“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жү«жё…дәәиә«дҫқйҷ„еҲ¶зҡ„ж®ӢдҪҷгҖӮ
е…¶дәҢпјҢ笔иҖ…жҸҗеҮәвҖң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вҖқжҰӮеҝөпјҢи®Өдёә他们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ҖиғҪеҠЁгҖҒ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ҺЁеҠЁеҠӣйҮҸгҖӮе®һйҷ…дёҠжІЎжңүдәәжҜ”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з»ҸжөҺе®һеҠӣгҖҒжңҖе…ҲејҖжӢ“еҶңжқ‘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йӣҮдҪЈз»ҸжөҺзҡ„еӨ§еҶңпјҢжӣҙзғӯиЎ·дәҺжү©еј еңҹең°гҖҒеӣҙеңҲеңҹең°пјҢжӣҙжҖҘдәҺж‘Ҷи„ұе…ұеҗҢдҪ“з”°еҲ¶жқҹзјҡгҖӮеӨ§еҶңпјҚд№Ўз»…йҳ¶еұӮеңЁеңҲең°йҮҚзӮ№еҢәеҹҹзҡ„еңҲең°йқўз§ҜеҚ еҪ“ең°е…ЁйғЁеңҲең°зҡ„дёҖеҚҠд»ҘдёҠпјҢиЎЁжҳҺиҜҘйҳ¶еұӮеңЁдёӨз§Қз»ҸжөҺе’ҢзӨҫдјҡжЁЎејҸзҡ„дәӨжӣҝдёӯжү®жј”дё»и§’гҖӮ他们д№ҹжңү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ж®ӢеҝҚиЎҢдёәпјҢжүҖд»ҘеҗҢж ·йҒӯеҲ°ж„ӨжҖ’е°ҸеҶңзҡ„еҸҚжҠ—гҖӮ
е…¶дёүпјҢ笔иҖ…жҳҺзЎ®жҸҗеҮәеңҲең°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й—®йўҳгҖӮдҫқжҚ®жі•еҫӢ规е®ҡзҡ„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еңҲең°дёәеҗҲжі•пјҢеҸҚд№Ӣдёәйқһжі•гҖӮе°ұжҲ‘们жҺҢжҸЎзҡ„иө„ж–ҷзңӢпјҢйўҶдё»еңҲең°зҡ„йҖҡеёёж–№ејҸжҳҜеҘ‘зәҰеңҲең°гҖҒжі•еәӯеңҲең°д»ҘеҸҠ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пјҢд»ҘеҗҲжі•еңҲең°дёәдё»гҖӮ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зЎ®е®һеӯҳеңЁпјҢжҳҜиөӨиЈёиЈёзҡ„жҺ еӨәпјҢжҡҙйңІдәҶж—©жңҹиө„жң¬зҡ„еӨұиҢғдёҺиҙӘе©ӘпјҢ他们еҜ№еӨұең°е°ҸеҶңйҖ жҲҗзҡ„з—ӣиӢҰеә”еҸ—еҲ°йҒ“д№үдёҠзҡ„и°ҙиҙЈгҖӮдёҚиҝҮвҖң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үҖеҚ жҜ”дҫӢеҫҲе°ҸвҖқгҖӮйқһжі•жҡҙеҠӣеңҲең°жҳҜ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зҡ„жұЎзӮ№пјҢжңҖз»Ҳиў«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¬иә«жүҖжҠӣејғ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ң¬ж–Үз•Ңе®ҡдәҶвҖңеңҲең°йўҶдё»вҖқ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他们дёӯзӣёеҪ“дёҖйғЁеҲҶдәәе·Із»ҸдёҚжҳҜдј з»ҹзҡ„е°Ғе»әйўҶдё»пјҢиҖҢжҳҜеҮәиә«дәҺеӨ§еҶңгҖҒе•Ҷдәәе’Ңд№Ўз»…зҡ„ж–°е…ҙйҳ¶еұӮпјҢиҜҘйҳ¶еұӮж—ўжҳҜдёҖж”ҜзӣёеҜ№зӢ¬з«Ӣзҡ„еҠӣйҮҸпјҢеҸҲдёҺеә„еӣӯйўҶдё»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дәӨеҸүе’ҢдәӨиһҚгҖӮ
е…¶еӣӣпјҢйўҶдё»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еҸ—еҲ°дҪғеҶң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зҡ„жҠөжҠ—пјҢдҪғеҶңзҡ„жҠөжҠ—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еҗҲжі•жҖ§е’Ңжңүж•ҲжҖ§пјҢеҢ…жӢ¬иҙ«з©·е°ҸеҶңзҡ„жҡҙеҠӣеҸҚжҠ—пјҢиҷҪ然жңү规模е°Ҹең°еҢәжҖ§ејәзӯүзү№зӮ№пјҢдҪҶжҳҜеҜ№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е…·жңүйңҮж…‘дҪңз”ЁгҖӮеңҲең°жҳҜиҮӘеҸ‘зҡ„пјҢдҪҶ并йқһеҸҜд»ҘиғЎдҪңйқһдёәпјҢзӣёеҸҚпјҢжқ‘еә„д№ жғҜжі•д»Қ然еҜҢжңүз”ҹе‘ҪеҠӣпјҢжҳҜеңҲең°гҖҒд№ҹжҳҜеҸҚжҠ—йқһжі•еңҲең°зҡ„еҹәжң¬дҫқжҚ®гҖӮ16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еҚҸи®®еңҲең°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пјҢеңҹең°зЎ®жқғд»ҺжқҘжІЎжңүжҠӣејғжі•еҫӢиҖҢжҳҜи¶ҠжқҘи¶Ҡ规иҢғпјҢпј‘пјҳдё–зәӘеҸ‘еұ•дёәвҖңи®®дјҡеңҲең°вҖқеҲҷеұһж°ҙеҲ°жё жҲҗгҖӮд»Һеҹәжң¬еұӮйқўдёҠи®ІпјҢеңҲең°дёҚжҳҜи·өиёҸ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пјҢжҒ°жҒ°жҳҜжҳҺжҷ°е’ҢзЎ®е®ҡеңҹең°жқғеҲ©гҖӮ
е…¶дә”пјҢжң¬ж–ҮжўізҗҶдәҶ16дё–зәӘеңҲең°и§„жЁЎе’ҢеңҲең°з ҙеқҸзӯүиҜ„дј°з ”з©¶пјҢ并жҸҗеҮәдәҶ笔иҖ…еҖҫеҗ‘жҖ§зҡ„ж„Ҹи§ҒгҖӮ20дё–зәӘеҲқпјҢзӣ–дјҠж №жҚ®йғҪй“Һж”ҝеәңеңҲең°жҠҘе‘ҠжҺЁз®—еҮәзҷҫеҲҶд№ӢеҮ зҡ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пјҢд»ҘеҫҖе№ҝжіӣиҖҢжҝҖзғҲзҡ„вҖңеңҲең°еҚ°иұЎвҖқеҸ—еҲ°жһҒеӨ§зҡ„еҶІеҮ»пјҢеҫ—еҲ°дәҶ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еӯҰиҖ…зҡ„е‘јеә”пјҢд№ҹеҸ—еҲ°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жү№иҜ„пјҢиҝҳжңӘиҫҫжҲҗе№ҝжіӣзҡ„е…ұиҜҶгҖӮеңЁеё•е…ӢзӯүиӢұеӣҪеӯҰиҖ…еҢәеҹҹжҖ§з ”究жҲҗжһң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笔иҖ…з»“еҗҲгҖҠз»ҙеӨҡеҲ©дәҡйғЎеҸІВ·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гҖӢзӣёе…іж•°жҚ®пјҢеҫ—еҮәеңҲең°дёӯеҝғең°еҢәзҡ„иҺұж–Ҝзү№йғЎеңҲең°жҜ”дҫӢиҫҫ20пҪһ25пј…зҡ„з»“и®әгҖӮзӣёдҝЎиҜҘең°еҢәжҖ§ж•°жҚ®еҜ№иӢұж је…°еңҲең°жҖ»дҪ“规模иҜ„дј°жңүдёҖе®ҡеҸӮиҖғд»·еҖјгҖӮеҸҰпјҢжң¬ж–ҮеҜ№еңҲең°иҝҗеҠЁжңҹй—ҙй©ұйҖҗдҪғеҶңзҡ„дәәж•°пјҢеңҲең°зҡ„дё»иҰҒз”ЁйҖ”д»ҘеҸҠд»ҘеҫҖзҡ„зӣёе…із ”究еҒҡдәҶеӯҰжңҜжўізҗҶе’Ңз”„еҲ«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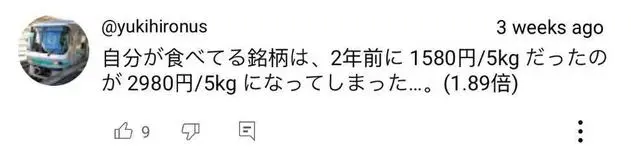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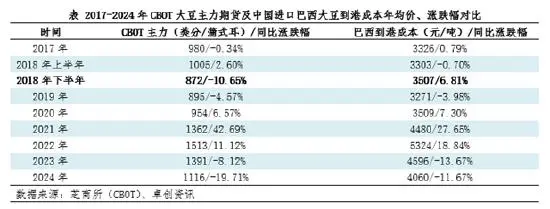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