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дёҠжіЁеҶҢе…ҘдјҡпјҢз»“дәӨ专家еҗҚжөҒпјҢдә«еҸ—иҙөе®ҫеҫ…йҒҮпјҢи®©дәӢдёҡз”ҹжҙ»еҸҢиөўгҖӮ
жӮЁйңҖиҰҒ зҷ»еҪ• жүҚеҸҜд»ҘдёӢиҪҪжҲ–жҹҘ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еёҗеҸ·пјҹз«ӢеҚіжіЁеҶҢ


x
жҪҳ家еҚҺпјҲ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еӯҰйғЁе§”е‘ҳгҖҒеҹҺеёӮеҸ‘еұ•дёҺзҺҜеўғз ”з©¶жүҖжүҖй•ҝпјү

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еј•еҸ‘зҡ„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пјҢеҸ‘з”ҹеңЁз§‘жҠҖеҸ‘иҫҫгҖҒзӨҫдјҡе®үе®ҡгҖҒзү©иҙЁиҙўеҜҢдё°еҜҢзҡ„21дё–зәӘ20е№ҙд»Јзҡ„еҗҜе§Ӣд№Ӣе№ҙпјҢе…¶зҒҫйҡҫжҖ§еҪұе“Қд№Ӣе·ЁеӨ§пјҢеңЁж–°дёӯеӣҪжҲҗз«Ӣд»ҘжқҘ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д»ҘжқҘпјҢжҳҜеҲӣзәӘеҪ•зҡ„гҖӮз–«жғ…зҲҶеҸ‘еүҚжңҹеӨұжҺ§пјҢжңүдҪ“еҲ¶гҖҒжІ»зҗҶе’Ңе®ҳе‘ҳзҙ иҙЁзӯүж–№йқў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е…·жңүдё»и§ӮдёҚдҪңдёәжҲ–иғЎдҪңдёәзү№еҫҒпјҢиҝҷжҳҜдё»иҰҒзҡ„пјӣдҪҶд»Һз–«жғ…жү©ж•ЈжңәзҗҶзңӢпјҢеҹҺеёӮзҡ„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гҖҒ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ж јеұҖзҡ„жһҒеҢ–гҖҒ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зҡ„дёӯеҝғеҢ–зҗҶеҝөпјҢжҳҜз–«жғ…дј ж’ӯгҖҒзҒҫе®іеҪұе“Қж”ҫеӨ§гҖҒеҠ еү§зҡ„е®ўи§ӮжқЎд»¶гҖӮ
жҲ‘еӣҪеҹҺеёӮеҢ–е·Іиҝӣе…ҘдёӯеҗҺжңҹйҳ¶ж®өпјҢдәҹйңҖд»Һ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зҡ„и§Ҷи§’пјҢжЈҖи§Ҷ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зҡ„и„ҶејұжҖ§пјҢеҸҚжҖқжҲ‘еӣҪеҹҺеёӮ规еҲ’зҡ„дёӯеҝғеҢ–зҗҶеҝөдёҺе®һи·өпјҢ规йҒҝйЈҺйҷ©пјҢеўһиҝӣйҹ§жҖ§пјҢжҸҗеҚҮ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ж°ҙе№ігҖӮжң¬ж–ҮеҲҶжһҗжүҖиҒҡз„Ұзҡ„пјҢдёҚеңЁдәҺ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зҡ„дё»и§Ӯеӣ зҙ 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еҪўжҖҒж–№йқўзҡ„еӨ–еңЁжҲ–е®ўи§ӮжқЎд»¶гҖӮ

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蔓延
д»Һ2019е№ҙ12жңҲ8ж—ҘеҸ‘зҺ°з–«жғ…пјҢеҲ°12жңҲеә•зЎ®и®Өз–«жғ…е…ғеҮ¶вҖ”вҖ”2019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пјҢеҲ°2020е№ҙе…ғжңҲ23ж—ҘжӯҰжұүе°ҒеҹҺпјҢйҡҸеҗҺеӣӣе·қгҖҒжөҷжұҹгҖҒе№ҝдёңгҖҒж№–еҢ—зӯүең°иҝ…еҚіеҗҜеҠЁдёҖзә§е“Қеә”жңәеҲ¶пјҢе…¶еҪұе“Қе·Із»Ҹи¶…и¶ҠдәҶ2003е№ҙйӣҶдёӯзҲҶеҸ‘дәҺе№ҝдёңе’ҢеҢ—дә¬зҡ„йқһе…ёз–«жғ…пјҢдҪҝе…ЁзӨҫдјҡе°Өе…¶жҳҜжӯҰжұүеҸҠж№–еҢ—е…¶д»–еҹҺеёӮд»ҳеҮәдәҶжғЁз—ӣзҡ„з”ҹе‘ҪеҒҘеә·д»Јд»·пјҢе…ЁеӣҪе…ЁйғЁзңҒзә§иЎҢж”ҝеҢәеҹҹзҡҶжңүз–«жғ…жҠҘйҒ“пјҢжңүзҡ„зңҒеёӮзЎ®иҜҠз—…дҫӢз”ҡиҮіи¶…иҝҮеҚғдәәпјӣдёҚд»…жҳҜж№–еҢ—пјҢеңЁе…ЁеӣҪиҢғеӣҙеҶ…еј•иҮҙзӨҫдјҡз”ҹжҙ»жӯЈеёёиҠӮеҘҸеҮ д№ҺеҒңж‘ҶпјҢдј—еӨҡжӯЈеёёз”ҹдә§з»ҸиҗҘжҙ»еҠЁеҮ иҝ‘еҒңж»һпјӣе…¶еӣҪйҷ…еҪұе“ҚеҸҜиғҪдјҡдёҘйҮҚйҳ»зўҚдәәзұ»е‘Ҫиҝҗе…ұеҗҢдҪ“е»әи®ҫ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№Іжү°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еӨҚе…ҙзҡ„дјҹеӨ§иҝӣзЁӢгҖӮиҝҷдёҖ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жүҖйҖ жҲҗзҡ„зҒҫе®іпјҢдёҚд»…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дё–з•ҢдёҠпјҢйғҪе Әз§°21дё–зәӘзҡ„вҖңж–°еҶ вҖқпјҢжҳҜеҲӣзәӘеҪ•зҡ„гҖӮ
ж–°еҶ з—…жҜ’жүҖйҖ жҲҗзҡ„з”ҹе‘Ҫе’ҢеҒҘеә·д»Јд»·пјҢжҳҜе·ЁеӨ§зҡ„гҖҒжғЁз—ӣзҡ„гҖӮз”ҹе‘Ҫж— д»·пјҢеҒҘеә·дёәиҰҒгҖӮж–°еҶ з—…жҜ’ж„ҹжҹ“жӯ»дәЎдәәж•°пјҢе·Із»Ҹиҝңиҝңи¶…иҝҮдәҶ2003е№ҙзҡ„йқһе…ёгҖҒдёӯдёңе‘јеҗёз»јеҗҲз—ҮгҖҒеҹғеҚҡжӢүзӯүйҮҚеӨ§дј жҹ“жҖ§з–«жғ…гҖӮж•°д»ҘеҚғи®Ўзҡ„еҚұйҮҚгҖҒйҮҚз—Үз—…дәәпјҢжңүеҸҜиғҪйҖғиҝҮжӯ»зҘһпјҢдҪҶжІ»з–—иҝҮзЁӢдёӯеҸҜиғҪз•ҷдёӢзҡ„еҗҺйҒ—з—Үд№ҹеҸҜиғҪдјҙйҡҸз»Ҳиә«гҖӮж•°д»ҘдёҮи®ЎзЎ®иҜҠгҖҒз–‘дјјжӮЈиҖ…пјҢеңЁз—…з—ӣд№ӢеӨ–иҝҳиҰҒйқўеҜ№еҜ№дәҺз–«жғ…зҡ„еҝғзҗҶжҒҗжғ§пјҢд»ҘеҸҠеҸҜиғҪдј жҹ“иҮідәІзҡ„еҝғзҗҶжҒҗж…ҢпјҢйҒӯеҸ—з—…йӯ”е’ҢеҝғзҗҶзҡ„еҸҢйҮҚжҠҳзЈЁгҖӮйӮЈдәӣз…§йЎҫз—…дәәзҡ„дәІдәәгҖҒеҢ»жІ»з—…дәәзҡ„еҢ»жҠӨе·ҘдҪңиҖ…пјҢеңЁйҳІжҠӨеҸҜиғҪдёҚеҲ°дҪҚгҖҒзү©иҙЁиҫғдёәеҢ®д№Ҹ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иҙҹйҮҚеүҚиЎҢгҖӮе°Ҫз®ЎеҢ»з–—иҙ№з”ЁеҸҜд»Ҙи®Ўд»·пјҢдҪҶз”ҹе‘ҪеҒҘеә·зҡ„д»Јд»·пјҢеҜ№дәҺйҒӯеҸ—з—…йӯ”зҡ„жӮЈиҖ…пјҢжҳҜйҡҫд»ҘжүҝеҸ—д№ӢйҮҚгҖҒдёҚеҸҜи®Ўд»·зҡ„гҖӮ
з–«жғ…е°ҒеҹҺиҖҢдҪҝжӯЈеёёзҡ„з”ҹжҙ»иҠӮеҘҸеҮ д№ҺеӨ„дәҺеҒңж‘ҶзҠ¶жҖҒпјҢзӨҫдјҡд»Јд»·еҸҠе…¶жІүйҮҚ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пјҢ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иӮҶиҷҗеңЁдёӯеӣҪдј з»ҹдҪіиҠӮвҖ”вҖ”жҳҘиҠӮжңҹй—ҙпјҢдҪҝеҫ—дәІдәәдёҚиғҪеӣўиҒҡгҖҒдәІеҸӢдёҚиғҪзӣёиҒҡпјҢзҫӨдҪ“жҖ§еЁұд№җж–ҮеҢ–жҙ»еҠЁе…ЁйқўеҸ«еҒңпјҢеұ…家йҡ”зҰ»з”ҹжҙ»зү©иө„зҹӯзјәпјҢеҝ…иҰҒзҡ„еҮәиЎҢйҡҫд»ҘеҮәжҲ·гҖӮе°ҒеҹҺгҖҒе°Ғжқ‘гҖҒе°Ғе°ҸеҢәгҖҒе°ҒжҘјгҖҒй—ӯжҲ·пјҢ дёҚжҳҜдёҖж—¶дёҖең°пјҢиҖҢжҳҜйҒҚеҸҠж№–еҢ—еҹҺд№ЎпјҢжіўеҸҠе…ЁеӣҪеӨ§йғЁгҖӮиҝҷж ·и§„жЁЎзҡ„зӨҫдјҡеҪұе“ҚпјҢе·Із»Ҹи¶…еҮәдәҶдәә们зҡ„жғіиұЎе’ҢжүҝеҸ—иҢғеӣҙгҖӮ
з”ҹдә§з»ҸиҗҘзӯүз»ҸжөҺжҙ»еҠЁзҡ„дё»дҪ“пјҢйҷӨз–«жғ…йҳІжҺ§йңҖиҰҒиҖҢе…Ғи®ёиҝҗиҗҘзҡ„йғЁй—ЁеӨ–пјҢеңЁз–«еҢәе’ҢеҪұе“ҚдёҘйҮҚзҡ„ең°еҢәйғҪиў«е°Ғй—ӯпјҢе°Ҫз®Ўе°‘йғЁеҲҶеҸҜиғҪеұ…家е·ҘдҪңгҖҒиҝңзЁӢеҠһе…¬пјҢдҪҶеҜ№дәҺеҲ¶йҖ дёҡжқҘи®ІпјҢеӨҡж•°еҸӘиғҪеӨ„дәҺвҖңеҶ»з»“вҖқзҠ¶жҖҒгҖӮж—…жёёдёҡгҖҒйӨҗйҘ®е®ҫйҰҶдёҡгҖҒдәӨйҖҡиҝҗиҫ“дёҡпјҢд№ғиҮідәҺйҮ‘иһҚжңҚеҠЎгҖҒжҲҝең°дә§дёҡпјҢжү“еҮ»йҰ–еҪ“е…¶еҶІпјӣе·ҘеҺӮиҪҰй—ҙзҡ„дёҖзәҝе·ҘдәәпјҢеҒҮжңҹиҝ”д№ЎпјҢеӣһзЁӢе°Ғе өпјҢеӨҚе·Ҙиү°йҡҫгҖӮдёҖе№ҙд№Ӣи®ЎеңЁдәҺжҳҘпјҢеҶңж°‘жҳҘиҖ•зӣёеҜ№дәҺйӣҶдёӯйҡ”зҰ»зҡ„еҹҺеёӮпјҢеҸҜиғҪжӯЈеёёиҝҗиЎҢпјҢдҪҶеҶңдёҡз”ҹдә§иө„ж–ҷзҡ„жҸҗдҫӣе’ҢдҝқйҡңпјҢж— з–‘д№ҹдјҡеҸ—еҲ°еҪұе“ҚгҖӮ
иҙёжҳ“иҮӘз”ұеҢ–пјҢз»ҸжөҺе…ЁзҗғеҢ–пјҢдёӯеӣҪеҖЎеҜје№¶и·өиЎҢзҡ„дәәзұ»е‘Ҫиҝҗе…ұеҗҢдҪ“е»әи®ҫпјҢеңЁ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зҡ„еҶІеҮ»дёӢпјҢе°Ҫз®ЎдёҚдјҡдёӯжӯўпјҢдҪҶеҝ…然иҰҒжҺҘеҸ—иҖғйӘҢпјҢз»ҸеҸ—жҢ«жҠҳгҖӮ2020е№ҙ1жңҲ30ж—ҘпјҢдё–з•ҢеҚ«з”ҹз»„з»Үе®ЈеёғпјҢе°Ҷ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еҲ—дёәеӣҪйҷ…е…іжіЁзҡ„зӘҒеҸ‘е…¬е…ұеҚ«з”ҹдәӢ件гҖӮе°Ҫз®ЎWHOжҖ»е№ІдәӢи°ӯеҫ·иөӣи®ӨдёәжІЎжңүеҝ…иҰҒйҮҮеҸ–йҷҗеҲ¶еӣҪйҷ…дәәе‘ҳжөҒеҠЁзҡ„жҺӘж–ҪпјҢдҪҶ欧гҖҒзҫҺгҖҒж—ҘгҖҒдёңеҚ—дәҡпјҢд№ғиҮідәҺйқһжҙІгҖҒжӢүзҫҺзҡ„и®ёеӨҡеӣҪ家еҜ№дёӯеӣҪжёёе®ўе®һж–Ҫе…Ҙеўғз®ЎеҲ¶пјҢеӨҡеӣҪиҲӘз©әеҒңйЈһгҖӮеңЁдёҖдәӣеҸ‘иҫҫеӣҪ家з”ҡиҮіеҮәзҺ°еӣ з–«жғ…еҜ№дёӯеӣҪе…¬ж°‘иҝӣиЎҢдәәиә«ж”»еҮ»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дёӯеӣҪжІ»еӣҪзҗҶж”ҝзҡ„з»ҸйӘҢпјҢд№ҹеҸҜиғҪеӣ жӯӨиҖҢеҸ—еҲ°еӣҪйҷ…зӨҫдјҡ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•ҢеҜ№еҠҝеҠӣзҡ„иҙЁз–‘гҖӮ
2020е№ҙ1жңҲ27ж—ҘпјҢжңқйІңе®ЈеёғжҡӮж—¶зҰҒжӯўдёӯеӣҪе…¬ж°‘е…ҘеўғгҖӮйҡҸеҗҺпјҢйҷҶз»ӯжңүдёҖдәӣеӣҪ家дёәйҳІ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еҜ№дёӯеӣҪе…¬ж°‘ж—…иЎҢйҮҮеҸ–е…Ҙеўғз®ЎеҲ¶жҺӘж–ҪгҖӮеӣҪ家移民管зҗҶеұҖжўізҗҶе…¬еёғзҡ„дҝЎжҒҜиЎЁжҳҺпјҢ1жңҲ29ж—Ҙжңү18дёӘеӣҪ家пјӣ2жңҲ11ж—ҘиҫҫеҲ°128дёӘеӣҪ家гҖӮ
2020е№ҙпјҢжҳҜвҖңеҚҒдёүдә”вҖқзҡ„收е®ҳд№Ӣе№ҙпјҢжҳҜе…Ёйқўе»әжҲҗе°Ҹеә·зӨҫдјҡзҡ„зӣ®ж Үе№ҙпјҢеңЁ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дјҹеӨ§еӨҚе…ҙзҡ„еҺҶеҸІиҝӣзЁӢдёӯпјҢ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зҡ„ең°дҪҚгҖӮжҢҒз»ӯж•°е№ҙзҡ„дёӯзҫҺиҙёжҳ“ж‘©ж“ҰпјҢ并дёҚдјҡеӣ дёә2019е№ҙеә•дёӯзҫҺиҙёжҳ“еҚҸе®ҡзҡ„зӯҫзҪІиҖҢз»Ҳз»“пјҢд»ҘзҫҺеӣҪдёәйҰ–зҡ„иҘҝж–№еӣҪ家еҜ№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йҒ“и·Ҝзҡ„еӣҙе өе°ҒжқҖпјҢд№ҹдёҚеҸҜиғҪеҒғж——жҒҜйј“гҖӮ2019е№ҙпјҢдёӯеӣҪGDPжҠөиҝ‘зҷҫдёҮдәҝдәәж°‘еёҒпјҢдәәеқҮиҝҲдёҠдёҖдёҮзҫҺе…ғзҡ„еҸ°йҳ¶пјҢдҪҶзҰ»й«ҳ收е…ҘеӣҪ家дәәеқҮж°ҙе№ізҡ„иө·зӮ№зәҝпјҢд»Қзӣёи·қ30%гҖӮ2019е№ҙз»ҸжөҺеўһйҖҹ6.1%пјҢ第дёүгҖҒеӣӣеӯЈеәҰе·Із»ҸдҪҺиҮі6%гҖӮ2020е№ҙ第дёҖеӯЈеәҰйӣҶдёӯеә”еҜ№з–«жғ…пјҢеҸҜиғҪиҰҒеҲ°з¬¬дәҢеӯЈеәҰдёӯеҗҺжңҹжүҚдјҡжӯҘе…ҘжӯЈиҪЁгҖӮ

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зҡ„з–«жғ…жү©ж•ЈжңәзҗҶ
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蔓延жҲҗзҒҫпјҢжҳҫ然жңү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гҖҒеҚ«з”ҹйҳІз–«гҖҒе®ҳе‘ҳзҙ е…»зӯүж–№йқўзҡ„еҶ…еңЁеӣ зҙ пјҢдҪҶеҰӮеҗҢйқһе…ёдёҖж ·пјҢе…¶еҸ‘з«Ҝ并еҪўжҲҗзҒҫеҸҳдәҺе·ЁеһӢ规模зҡ„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пјҢиЎЁжҳҺеҹҺеёӮеҪўжҖҒдёҠзҡ„иҝҮеәҰ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пјҢжһҒжңүеҸҜиғҪжҳҜеӨ–еңЁзҡ„е®ўи§ӮеҠ©жҺЁеӣ зҙ гҖӮеҰӮжһңеү–жһҗиҝҷдәӣеӨ–йғЁжқЎд»¶еҠ©жҺЁзҡ„жү©ж•ЈжңәзҗҶпјҢдё»иҰҒеҢ…жӢ¬пјҡ
йҰ–е…ҲжҳҜй«ҳеҜҶеәҰгҖҒи¶…й«ҳеұӮеұ…ж°‘дҪҸе®…еҢәзҡ„зӮ№зҠ¶жү©ж•ЈгҖӮжӯҰжұүдҪңдёәвҖңд№қзңҒйҖҡиЎўвҖқзҡ„еӣҪ家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пјҢеңҹең°иө„жәҗзҙ§еј пјҢдәәеҸЈй«ҳеәҰйӣҶиҒҡпјҢеӣ иҖҢжүҝжӢ…еұ…дҪҸеҠҹиғҪзҡ„дҪҸе®…е°ҸеҢәпјҢеӨҡдёәйӣҶдёӯиҝһзүҮејҖеҸ‘зҡ„еӨ§еһӢй«ҳеҜҶеәҰгҖҒи¶…й«ҳеұӮеҚ•е…ғжҘјжҲҝ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дҪҚдәҺжӯҰжұүеёӮжұҹеІёеҢәзҡ„зҷҫжӯҘдәӯзӨҫеҢәпјҢеҚ ең°5.5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пјҢеұ…дҪҸе’Ңз”ҹжҙ»дәәеҸЈи¶…иҝҮ18дёҮпјҢ规еҲ’е»әжҲҗеҚ ең°йқўз§Ҝ7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е…ҘдҪҸ30дёҮдәәзҡ„зҷҫжӯҘдәӯж–°еҹҺгҖӮ
иҜҘзӨҫеҢәзҺ°жңүдәәеҸЈеҜҶеәҰжҜҸ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3.3дёҮдәәпјҢжҢү规еҲ’е»әжҲҗеҗҺдәәеҸЈеҜҶеәҰжҜҸ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4.3дёҮдәәгҖӮеұ…ж°‘дҪҸе®…жҘјй—ҙи·қиҝ‘гҖҒз©әй—ҙзӢӯгҖҒи¶…й«ҳеұӮгҖҒеҚ•е…ғжҲҝйқўз§ҜеӨҡеңЁ100е№ізұіе·ҰеҸігҖӮеҰӮжӯӨе»әзӯ‘й«ҳеҜҶеәҰгҖҒ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еҹҺеёӮзӨҫеҢәпјҢй«ҳеәҰеҜҶйӣҶзҡ„дәәеҸЈеұ…дҪҸз”ҹжҙ»еңЁзӣёеҜ№зӢӯе°Ҹзҡ„з©әй—ҙпјҢиҝӣе…ҘиҮӘ家еҝ…йЎ»иҰҒдҪҝз”Ёе°Ғй—ӯзҺҜеўғзҡ„з”өжўҜгҖӮдёҖж—ҰеҮәзҺ°з–«жғ…пјҢеҰӮжһңи®ӨзҹҘдёҚеҸҠж—¶гҖҒз®ЎжҺ§дёҚеҲ°дҪҚпјҢеҝ«йҖҹжү©ж•ЈжҳҜеҝ…然зҡ„гҖӮжҚ®зӣёе…іеӘ’дҪ“жҠҘйҒ“пјҢжҲӘжӯўеҲ°2020е№ҙ2жңҲ4ж—ҘпјҢзӨҫеҢәеҶ…зҡ„е®үж°‘иӢ‘55 ж ӢжҘјйҮҢпјҢжңү33ж ӢеҮәзҺ°еҸ‘зғӯз—…зҠ¶гҖӮ
жңүйҷҗе°Ғй—ӯз©әй—ҙеӨ§иҢғеӣҙж„ҹжҹ“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е…ёеһӢдҫӢиҜҒжҳҜж—Ҙжң¬жёёиҪ®вҖңй’»зҹіе…¬дё»еҸ·вҖқпјҢ2020е№ҙ1жңҲ20ж—Ҙд»ҺжЁӘж»Ёиө·иҲӘпјҢ5ж—ҘеҗҺз»ҸеҒңйҰҷжёҜеҸ‘зҺ°ж„ҹжҹ“з—…дҫӢзҙ§жҖҘиҝ”иҲӘпјҢиҮі2жңҲ12ж—ҘпјҢзЎ®иҜҠз—…дҫӢе·Із»ҸеҲ°иҫҫ218дәәпјҢж„ҹжҹ“зҺҮй«ҳиҫҫ5.9%гҖӮеҰӮжһңдҪҺжҘјеұӮгҖҒдҪҺеҜҶеәҰпјҢзӮ№зҠ¶жү©ж•Јзҡ„规模гҖҒйҖҹеәҰгҖҒиҢғеӣҙеҝ…然иҰҒе°Ҹеҫ—еӨҡпјҢз®ЎжҺ§йҡҫеәҰд№ҹдјҡе°ҸеҫҲеӨҡгҖӮ
е…¶ж¬ЎжҳҜеӨ§е®№йҮҸгҖҒй«ҳйў‘ж¬Ўе…¬е…ұдәӨйҖҡзҡ„зәҝзҠ¶еӨ–延гҖӮз”ұдәҺиҒҢдҪҸеҲҶзҰ»гҖҒеҹҺеёӮж‘ҠеӨ§йҘјпјҢең°й“ҒгҖҒз”өиҪҰгҖҒе…¬жұҪзӯүе…¬е…ұдәӨйҖҡ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дёҠдёӢзҸӯй«ҳеі°ж—¶й—ҙпјҢ ж‘©иӮ©жҺҘиёөдәәжҢӨдәәпјҢеҚідҪҝдёҘеҠ йҳІжҠӨпјҢд№ҹжңүй«ҳйЈҺйҷ©гҖӮ1000еӨҡдёҮдәәеҸЈзҡ„еӨ§жӯҰжұүпјҢеҲҶжӯҰжҳҢгҖҒжұүеҸЈгҖҒжұүйҳідёүй•ҮпјҢдёәй•ҝжұҹгҖҒжұүж°ҙжүҖеҲҶеүІпјҢе…¬дәӨзәҝи·ҜеӨҡгҖҒи·қзҰ»й•ҝгҖҒд№ҳе®ўеӨҡпјҢз–«жғ…еңЁеёӮеҶ…зәҝжҖ§еӨ–延пјҢиҰҶзӣ–еӨ§е®№йҮҸе…¬дәӨзәҝи·ҜйҖҡеҗ‘зҡ„жҜҸдёҖдёӘи§’иҗҪгҖӮ
е»әдәҺ1999е№ҙзҡ„еҢ—дә¬еӨ©йҖҡиӢ‘е°ҸеҢәпјҢеҚ ең°8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пјҢжңүдә”еӨ§еӣӯеҢә16дёӘеҲҶеҢәз»„жҲҗпјҢжҖ»е…ұ645ж ӢжҘјгҖӮжҚ®дёҚе®Ңе…Ёз»ҹи®ЎпјҢеӨ©йҖҡиӢ‘е°ҸеҢәйҮҢиҒҡйӣҶзқҖ40дёҮдәәе·ҰеҸігҖӮе°ҸеҢәеҶ…жңүдёӨдёӘең°й“Ғз«ҷгҖҒ40еӨҡдёӘе…¬дәӨз«ҷгҖӮеҸҜд»ҘжғіиұЎй«ҳеі°ж—¶й—ҙе…¬дәӨе°Өе…¶жҳҜең°й“Ғзҡ„дәәеҸЈжӢҘжҢӨзЁӢеәҰгҖӮ
еҶҚж¬ЎжҳҜжӯҰжұүдҪңдёә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иө„жәҗиҷ№еҗёиҢғеӣҙеҶ…зҡ„е‘Ёиҫ№иҫҗе°„гҖӮж№–еҢ—зҡ„еҹҺеёӮе’Ңз»ҸжөҺж јеұҖжҳҜдёҖдё»пјҲжӯҰжұүпјүдёӨеүҜпјҲе®ңжҳҢгҖҒиҘ„йҳіпјүпјҢжӯҰжұүеҹҺеёӮеңҲпјҲ1+8пјҢ жӯҰжұүгҖҒй»„зҹігҖҒй„Ӯе·һгҖҒй»„еҶҲгҖҒеӯқж„ҹгҖҒд»ҷжЎғгҖҒеӨ©й—ЁгҖҒжҪңжұҹгҖҒе’ёе®ҒпјүдёҖеҹҺзӢ¬еӨ§гҖӮжӯҰжұүеҜ№иҝҷеҮ дёӘе‘Ёиҫ№еҹҺеёӮпјҢиҷ№еҗёдҪңз”ЁејәпјҢиҫҗе°„ж•ҲжһңеӨ§гҖӮд»Һз–«жғ…еҸ‘з”ҹжғ…еҶөзңӢпјҢиҝҷ8дёӘеёӮзҡ„зЎ®иҜҠдәәж•°е’Ңжӯ»дәЎдәәж•°пјҢеҮ д№ҺеҚ ж№–еҢ—зңҒжӯҰжұүд»ҘеӨ–зҡ„жҖ»ж•°зҡ„дёҖеҚҠгҖӮжӯҰжұүеҹҺеёӮеңҲзЎ®иҜҠе’Ңжӯ»дәЎдәәж•°пјҢеҚ е…ЁзңҒжҖ»ж•°зҡ„90%е·ҰеҸігҖӮжӯҰжұүиҫҗе°„еҠӣиҫғејәзҡ„йӮ»иҝ‘зңҒд»ҪжІіеҚ—гҖҒж№–еҚ—е’ҢжұҹиҘҝпјҢдёүзңҒзЎ®иҜҠз—…дҫӢеҚ ж№–еҢ—д»ҘеӨ–е…ЁеӣҪе…¶д»–зңҒпјҲеҢәгҖҒеёӮпјүжҖ»ж•°зҡ„1пјҸ4гҖӮ
жңҖеҗҺжҳҜеӣҪ家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д№Ӣй—ҙеҢәеҹҹдә’иҒ”зҡ„иҝңзЁӢдј ж’ӯгҖӮеңЁе…ЁеӣҪиҢғеӣҙпјҢжӯҰжұүдёҺй•ҝдёүи§’еҹҺеёӮзҫӨең°еҢәпјҲжұҹгҖҒжөҷгҖҒжІӘгҖҒзҡ–пјүгҖҒзҸ дёүи§’еҹҺеёӮзҫӨпјҲе№ҝдёңпјүгҖҒжҲҗжёқеҹҺеёӮзҫӨпјҲе·қгҖҒжёқпјүе’Ңдә¬жҙҘеҶҖеҹҺеёӮзҫӨе…іиҒ”еҜҶеҲҮпјҢиҝҷеӣӣдёӘеҹҺеёӮзҫӨжүҖеңЁзңҒеёӮзЎ®иҜҠз—…дҫӢпјҢеҚ ж№–еҢ—д»ҘеӨ–е…ЁеӣҪжҖ»ж•°зҡ„дёҖеҚҠд»ҘдёҠпјҢе…¶дёӯжӯҰжұүдҪңдёәй•ҝжұҹз»ҸжөҺеёҰзҡ„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пјҢдёҺй•ҝдёүи§’е’ҢжҲҗжёқең°еҢәзҡ„е…іиҒ”жӣҙдёәеҜҶеҲҮпјҢй•ҝдёүи§’е’ҢжҲҗжёқең°еҢәзҡ„зЎ®иҜҠдәәж•°еҚ ж№–еҢ—д»ҘеӨ–е…ЁеӣҪжҖ»ж•°зҡ„1пјҸ3д»ҘдёҠгҖӮзҸ дёүи§’ең°еҢәе№ҝе·һгҖҒж·ұеңізҡ„зЎ®иҜҠз—…дҫӢжҳҜеҢ—дә¬гҖҒеӨ©жҙҘзҡ„1.5еҖҚе·ҰеҸігҖӮ
дёҠиҝ°еӣӣз§Қдј ж’ӯжңәзҗҶжҲ–йҖ”еҫ„пјҢжҳҫ然дёҺеҹҺеёӮеҪўжҖҒгҖҒеҹҺеёӮ规模гҖҒеҹҺеёӮдҪ“зі»зӯү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зҠ¶еҶөеҜҶеҲҮе…іиҒ”гҖӮ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зҡ„еҜҶеәҰи¶Ҡй«ҳгҖҒзЁӢеәҰи¶ҠејәпјҢеҲҷз–«жғ…дј ж’ӯзҡ„зҒҫжғ…и¶ҠйҮҚгҖӮд»Һ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дј ж’ӯзҡ„зҒҫжғ…еҪұе“ҚзЁӢеәҰдёҠзңӢпјҢеҸҜд»ҘеңЁиҫғеӨ§зЁӢеәҰдёҠеҲҶжһҗжӯҰжұүдҪңдёә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дёҺзңҒеҶ…гҖҒзңҒеӨ–дәәеҸЈе’Ңз»ҸжөҺиҒ”зі»зҡ„зҙ§еҜҶзЁӢеәҰгҖӮе°ҒеҹҺгҖҒе°ҒзӨҫеҢәгҖҒе°Ғжқ‘гҖҒе°ҒжҘјпјҢе°ұжҳҜйҖҡиҝҮејәиЎҢзү©зҗҶйҡ”зҰ»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йҳ»жӯўз–«жғ…жү©ж•ЈгҖӮ

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й«ҳеәҰиҒҡйӣҶзҡ„йЈҺйҷ©ж•Ҳеә”
д»Һ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ж јеұҖдёҠзңӢпјҢиҒҡйӣҶзЁӢеәҰи¶Ҡй«ҳпјҢеҜ№еҗ„з§ҚеӨ–жқҘеҶІеҮ»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зӘҒеҸ‘еҶІеҮ»иЎЁзҺ°еҫ—е°ұи¶Ҡи„ҶејұпјҢ 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е°ұи¶Ҡй«ҳгҖӮйЈҺйҷ©ж•Ҳеә”дё»иҰҒиЎЁзҺ°еңЁи§„жЁЎгҖҒи·Ҝеҫ„й”Ғе®ҡгҖҒеӨ–жәўеҠ йҖҹе’Ңеә”еҜ№ж—¶ж»һзӯүж–№йқўгҖӮ
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规模ж•Ҳеә”пјҢдё»иҰҒиЎЁзҺ°еңЁдәәеҸЈиҒҡйӣҶж•°йҮҸдёҠгҖӮжҲ‘еӣҪеӨ§еҹҺеёӮзҡ„дәәеҸЈи§„жЁЎпјҢеҠЁиҫ„еңЁ300дёҮгҖҒ500дёҮд»ҘдёҠпјҢдёҖдәӣе…·жңүдјҳиҙЁе…¬е…ұиө„жәҗеһ„ж–ӯиҒҡйӣҶжқғйҷҗзҡ„еүҜзңҒзә§еҢәеҹҹжҖ§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пјҢеӨҡе°ҶдәәеҸЈи§„жЁЎиҝҮеҚғдёҮдҪңдёәзӣ®ж ҮгҖӮдёҖдәӣеҢәеҹҹжҖ§дёӯеҝғеҹҺеёӮдҫӢеҰӮеӨ©жҙҘгҖҒжӯҰжұүгҖҒиҘҝе®үзӯүеҹҺеёӮпјҢе°ұжӣҫеңЁ2017гҖҒ2018 е№ҙж”ҫе®ҪиҗҪжҲ·жқЎд»¶вҖңжҠўдәәвҖқжү©е®№гҖӮ
2014е№ҙпјҢеӣҪеҠЎйҷўеҚ°еҸ‘гҖҠе…ідәҺи°ғж•ҙеҹҺеёӮ规模еҲ’еҲҶж ҮеҮҶзҡ„йҖҡзҹҘгҖӢпјҢж–°ж ҮеҮҶд»ҘеҹҺеҢәеёёдҪҸдәәеҸЈдёәз»ҹи®ЎеҸЈеҫ„пјҢе°ҶеҹҺеёӮеҲ’еҲҶдёәдә”зұ»дёғжЎЈгҖӮе°ҸеҹҺеёӮдәәеҸЈдёҠйҷҗз”ұ20дёҮжҸҗй«ҳеҲ°50дёҮпјҲдёҚеҢ…жӢ¬жң¬ж•°пјҢдёӢеҗҢпјүдёӯзӯүеҹҺеёӮзҡ„дёҠдёӢйҷҗеҲҶеҲ«з”ұ20дёҮгҖҒ50дёҮжҸҗй«ҳеҲ°50дёҮгҖҒ100дёҮпјҢеӨ§еҹҺеёӮзҡ„дёҠдёӢйҷҗеҲҶеҲ«з”ұ50дёҮгҖҒ100дёҮжҸҗй«ҳеҲ°100дёҮгҖҒ500дёҮпјҢ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дёӢйҷҗз”ұ100дёҮжҸҗй«ҳеҲ°500дёҮгҖӮ
дәәеҸЈжҳҜ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зҡ„ж ёеҝғиҰҒд№үпјҢ规模и¶ҠеӨ§пјҢиҒҡйӣҶеәҰи¶Ҡй«ҳпјҢйЈҺйҷ©еҝ…然и¶ҠеӨ§гҖӮеҜ№дәҺдј жҹ“жҖ§з–«жғ…пјҢдәәеҸЈи¶ҠеӨҡпјҢеҜ№еӨ–з•Ңзҡ„иҒ”зі»еҝ…然д№ҹеӨҡпјҢдј ж’ӯзҡ„иҰҶзӣ–йқўд№ҹе°ұи¶Ҡе№ҝгҖӮиҝҷз§ҚйЈҺйҷ©зҡ„规模ж•Ҳеә”пјҢдёҚд»…иЎЁзҺ°еңЁе…¬е…ұеҚ«з”ҹзӘҒеҸ‘дәӢ件дёҠпјҢе…¶д»–зҒҫе®ідҫӢеҰӮең°йңҮгҖҒжҙӘж¶қгҖҒжҲҳдәүпјҢйЈҺйҷ©д№ҹйҡҸдәәеҸЈи§„жЁЎиҖҢйқһзәҝжҖ§еўһеҠ гҖӮ
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й”Ғе®ҡж•Ҳеә”пјҢдё»иҰҒиЎЁзҺ°еңЁеҹҺеёӮж јеұҖгҖҒеҠҹиғҪе’Ң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зҡ„зү©зҗҶеӣәеҢ–иҖҢдә§з”ҹзҡ„й”Ғе®ҡгҖӮеҹҺеёӮеҠҹиғҪеҲҶеҢәгҖҒиҒҢдҪҸеҲҶзҰ»иҖҢеј•иҮҙзҡ„жҠҖжңҜй”Ғе®ҡ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еҹҺеёӮеұ…дҪҸзӨҫеҢә规模еҝ…然еӨ§пјҢдә§дёҡеӣӯеҢәеҝ…然йӣҶиҒҡпјҢеҚ•дёҖдёӯеҝғзҡ„еҗ‘еҝғеҠӣпјҢеҸҲеҝ…然дә§з”ҹеҗ‘дёӯеҝғйӣҶиҒҡиҖҢеҗ‘еӣӣе‘Ёжү©ж•Јзҡ„зү©зҗҶйҖҡйҒ“пјҢеҚідәӨйҖҡзәҝи·ҜеӨҡгҖҒи·қзҰ»иҝңгҖҒе®№йҮҸеӨ§гҖҒйў‘ж¬Ўй«ҳгҖӮеҰӮжһңиҒҢдҪҸдёҖдҪ“пјҢйҖҡеёёзҡ„е·ҘдҪңе’Ңз”ҹжҙ»еҚҠеҫ„еңЁ2е…¬йҮҢе·ҰеҸіпјҢжҳҫ然йЈҺйҷ©з®ЎжҺ§е°ұз®ҖеҚ•еҫ—еӨҡдәҶгҖӮеҹҺеёӮеұ…ж°‘дҪҸе®…зҡ„й«ҳеҜҶеәҰи¶…й«ҳеЎ”жҘјпјҢйҒҮеҲ°зҒ«зҒҫпјҢж¶ҲйҳІйҖҡйҒ“зҡ„з•…йҖҡе’Ңж¶ҲйҳІж°ҙжһӘзҡ„дҪңдёҡйҡҫеәҰжӣҙеӨ§гҖӮй«ҳеұӮеұ…ж°‘й«ҳз©әжҠӣзү©дјӨдәәгҖҒе„ҝз«Ҙй«ҳжҘјеқ иҗҪйЈҺйҷ©пјҢд№ҹеӣ жҘјй«ҳиҖҢеўһеҠ гҖӮ
еҹҺеёӮеҠҹиғҪеҲҶеҢәпјҢеҹҺеёӮйҒ“и·Ҝе’ҢдәӨйҖҡеҹәзЎҖи®ҫж–ҪгҖҒжҘјжҲҝпјҢдёҖж—Ұе»әжҲҗпјҢ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пјҢе°ұеӯҳеңЁжҠҖжңҜеұӮйқўдёҠзҡ„зү©зҗҶй”Ғе®ҡж•Ҳеә”гҖӮ
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ж”ҫеӨ§жҲ–еҠ йҖҹж•Ҳеә”пјҢеңЁдәҺзҺ°д»ЈжҠҖжңҜжүҖдә§з”ҹзҡ„дәҢйҮҚжҖ§ж•ҲжһңгҖӮзҺ°д»ЈеҹҺеёӮжҚ·иҝҗзі»з»ҹпјҢ еҹҺйҷ…еҝ«йҖҹдәӨйҖҡгҖҒзү©жөҒгҖҒз»Ҹиҙёжҙ»еҠЁзҡ„йў‘з№ҒеҫҖжқҘпјҢжҳҜзҺ°д»ЈеҢ–зҡ„ж Үеҝ—пјҢдҪҶеҚҙеҠ йҖҹ并ж”ҫеӨ§дәҶз–«жғ…зҡ„дј ж’ӯпјӣдә’иҒ”зҪ‘дҝЎжҒҜзҡ„ејҖж”ҫжҖ§е’ҢеҚіж—¶дј ж’ӯпјҢз”ұдәҺдёҚиғҪз«ӢеҚіз”„еҲ«иҷҡеҒҮе’Ңй”ҷиҜҜдҝЎжҒҜпјҢжһҒжҳ“йҖ жҲҗзӨҫдјҡжҒҗжғ§еҝғзҗҶпјҢдҪҝеҫ—жң¬жқҘеҸҜжҺ§зҡ„зҒҫйҡҫеҸҳеҫ—дёҚеҸҜжҺ§пјҢиҜҜеҜјзӨҫдјҡеӨ§дј—еј•иҮҙеә”еҜ№еӨұзӯ–гҖӮеҪ“然иҝҷе…¶дёӯд№ҹжңүж”ҝеәңеңЁ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дёӯзҡ„дёҚдҪңдёәе’ҢиғЎдҪңдёәпјҢиҙ»иҜҜжҲҳжңәпјҢдҪҝйЈҺйҷ©еӨұжҺ§гҖӮ
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ж—¶ж»һж•Ҳеә”пјҢжҢүеёёзҗҶи®ІпјҢеә”иҜҘдёҚеӯҳеңЁпјҢеӣ дёәеңЁи§„жЁЎиҒҡйӣҶ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Ө§еҹҺеёӮе°Өе…¶жҳҜ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жұҮйӣҶеӨ§йҮҸзҡ„гҖҒдјҳиҙЁзҡ„еә”жҖҘиө„жәҗпјҢжңүзқҖе°–з«ҜгҖҒејәеӨ§зҡ„з§‘з ”йҳҹдјҚе’ҢиғҪеҠӣпјҢе®Ңе…ЁеҸҜд»Ҙеҝ«йҖҹеҸҚеә”пјҢйҳІиҢғйЈҺйҷ©гҖӮеҚідҪҝеҰӮжӯӨпјҢеңЁиЎҢж”ҝеұӮзә§жқғйҷҗдёҚи¶іиҖҢеҸҲеҮәзҺ°еҶізӯ–зҠ№з–‘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ҝЎжҒҜж»һеҗҺгҖҒиЎҢеҠЁе»¶иҜҜпјҢд»ҘиҮідәҺдәӢжҖҒжү©еӨ§пјҢеҺҹжң¬и¶іеӨҹзҡ„еә”жҖҘиө„жәҗпјҢеңЁйЈҺйҷ©жҖҘеү§жү©еӨ§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йңҖиҰҒжү©е»әжҲ–ж–°е»әпјҢиҖҢдҪҝжңүж•Ҳеә”еҜ№ж—¶й—ҙдёҚи¶ігҖӮ
иҝҷдёҖж•Ҳеә”пјҢж—ўжңү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зҡ„дё»и§ӮеұһжҖ§пјҢдҫӢеҰӮең°ж–№ж”ҝеәңеә”еҜ№з–«жғ…зҡ„жҺҲжқғжҲ–жӢ…еҪ“дёҚеҲ°дҪҚпјҢд№ҹжңү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иҝҮеәҰиҒҡйӣҶиҖҢдә§з”ҹзҡ„еҜ№з§ҜжһҒиЎҢеҠЁзҡ„еҗҺжһңзҡ„жӢ…еҝ§гҖӮдёҠеҚғдёҮдәәзҡ„еҹҺеёӮпјҢеҒҡеҮәе°ҒеҹҺзҡ„еҶізӯ–пјҢеҝ…йЎ»иҰҒи°Ёж…ҺпјҢдёүжҖқиҖҢеҗҺиЎҢгҖӮеҰӮжһңеҹҺеёӮиҒҡйӣҶзЁӢеәҰиҫғдҪҺпјҢе°ҒеҹҺзҡ„еҶізӯ–пјҢе°ұеғҸеҶңжқ‘еңЁз–«жғ…еҸ‘з”ҹеҗҺз«ӢеҚіе°Ғжқ‘зҡ„еҶіе®ҡпјҢ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д»»дҪ•йҡңзўҚгҖӮ

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зҡ„зҗҶжҖ§йҖүжӢ©
жҲ‘еӣҪеҹҺеёӮзҡ„з©әй—ҙ规еҲ’пјҢд»Һи®ЎеҲ’з»ҸжөҺжқЎд»¶дёӢзҡ„еӨ§дёӯе°Ҹ并дёҫпјҢд»Ҙдёӯе°ҸеҹҺеёӮдёәдё»пјҢеҲ°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жқЎд»¶дёӢзҡ„ж•ҲзҺҮдјҳе…ҲиҖҢйј“еҠұеӨ§еҹҺеёӮе°Өе…¶жҳҜ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еҸ‘еұ•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ж—ҘеүҚзӨҫдјҡдјҳиҙЁиө„жәҗйҡҸеҹҺеёӮзӯүзә§е’Ң规模иҖҢдёҚж–ӯжҸҗеҚҮеһ„ж–ӯең°дҪҚзҡ„иҒҡйӣҶжғ…еҶөгҖӮдёҚи®әжҳҜи®ЎеҲ’жҖқи·ҜиҝҳжҳҜеёӮеңәеҜјеҗ‘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еҹҺеёӮеҢ–зҡ„жәҗеҠЁеҠӣжҳҜе·ҘдёҡеҢ–пјҢеҹҺеёӮ规еҲ’зҡ„зҗҶжҖ§дёҚеӨ–д№Һ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гҖҒ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’Ң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пјҢе°Ҫз®ЎеңЁеӨҡж•°жғ…еҶөдёӢйңҖиҰҒдёүз§ҚзҗҶжҖ§зҡ„еҚҸеҗҢжҲ–жҠҳиЎ·пјҢдҪҶд№ҹеҝ…然жңүдёҖз§ҚзҗҶжҖ§еҚ жҚ®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зҡ„дё»еҜјең°дҪҚгҖӮ
дҪңиҖ…и®ӨдёәдёӯеӣҪ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40е№ҙзҡ„жҲҗеҠҹпјҢ 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еӣ зҙ жҳҜе°ҶдәҢе…ғз»“жһ„дёӯз”ҹдә§еҠӣзӣёеҜ№дҪҺдёӢе’ҢиҗҪеҗҺзҡ„еҶңж°‘е’ҢеҶңең°йҮҠж”ҫеҮәжқҘпјҢиҝӣе…Ҙе·Ҙдёҡе’ҢеҹҺеёӮйғЁй—ЁгҖӮеҸӮи§ҒжҪҳ家еҚҺпјҡгҖҠд»Һз”ҹжҖҒеӨұиЎЎиҝҲеҗ‘з”ҹжҖҒж–ҮжҳҺпјҡ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40е№ҙдёӯеӣҪз»ҝиүІиҪ¬еһӢеҸ‘еұ•зҡ„иҝӣзЁӢдёҺеұ•жңӣгҖӢпјҢгҖҠеҹҺеёӮдёҺзҺҜеўғз ”з©¶гҖӢпјҢ2018е№ҙ第4жңҹ
д»ҺеҹҺеёӮ规еҲ’зҡ„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дёҠзңӢпјҢеҹҺеёӮдјҳиҙЁиө„жәҗи¶ҠйӣҶдёӯпјҢ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зЁӢеәҰи¶Ҡй«ҳпјҢеҲҷ规模ж•Ҳеә”и¶ҠеӨ§пјҢ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и¶ҠдјҳгҖӮж–°з»ҸжөҺең°зҗҶеӯҰзҡ„зҗҶи®әеҲҶжһҗиЎЁжҳҺпјҢиө„жәҗи¶ҠиҒҡйӣҶпјҢ规模и¶ҠеӨ§пјҢеҲҷдҝЎжҒҜжҲҗжң¬и¶ҠдҪҺпјҢеҠіеҠЁеҠӣгҖҒзү©жөҒгҖҒжңҚеҠЎжҲҗжң¬и¶Ҡжңүз«һдәүеҠӣгҖӮ
еҖӘй№ҸйЈһзӯүдё»зј–зҡ„гҖҠеҹҺеёӮз«һдәүеҠӣи“қзҡ®д№ҰгҖӢпјҢгҖҠ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з«һдәүеҠӣжҠҘе‘ҠпјҲNo. 13пјүвҖ”вҖ”е·ЁжүӢпјҡжүҳиө·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ж–°зүҲеӣҫгҖӢ2015е№ҙзүҲдёӯж•°жҚ®жҳҫзӨәз«һдәүеҠӣжңҖејәзҡ„еүҚ25дёӘеҹҺеёӮпјҢдәәеҸЈи§„жЁЎе°ҸдәҺ500дёҮзҡ„еҸӘжңүеҸ°еҢ—еёӮпјҲ270дёҮпјҢжҺ’еҗҚ第3пјүе’Ңжҫій—ЁпјҲ63 дёҮпјҢжҺ’еҗҚ第9пјүгҖӮдҪҷиҖ…зҡҶдёәдәәеҸЈеҚғдёҮе·ҰеҸізҡ„зӣҙиҫ–еёӮгҖҒеүҜзңҒзә§еҹҺеёӮпјҲе”ҜеҺҰй—ЁдёҚи¶і400дёҮпјүе’Ң500дёҮ规模еҸҠд»ҘдёҠзҡ„дёңйғЁжІҝжө·ең°зә§еёӮгҖӮ
жҠҠйҰ–й’ўе’ҢзҮ•еұұзҹіеҢ–е»әеңЁеҢ—дә¬пјҢжҠҠе®қеұұй’ўй“Ғеҹәең°е»әеңЁдёҠжө·пјҢжҳҫ然жҳҜеӣ дёәеҢ—дә¬гҖҒдёҠжө·жңүдәәжүҚдјҳеҠҝгҖҒ科жҠҖдјҳеҠҝпјҢе°Ҫз®ЎиҝҷдәӣеҹҺеёӮ规模已з»ҸеҫҲеӨ§пјҢиҮӘ然з”ҹжҖҒе’ҢеҺҹжқҗж–ҷдҫӣеә”并дёҚе…·еӨҮжҳҫи‘—дјҳеҠҝпјҢдҪҶз¬ҰеҗҲ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е№¶дёҚеҝ…然з¬ҰеҗҲ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е’Ң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гҖӮйҰ–й’ўжҗ¬иҝҒпјҢжҳҫ然жҳҜеҢ—дә¬зҡ„зҺҜеўғе®№йҮҸдёҚиғҪж”Ҝж’‘йҰ–й’ўзҡ„йңҖиҰҒгҖӮиҝҷдёҖ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зҡ„еҶізӯ–дёә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жүҖеҗҰе®ҡпјҢдҪҝеҫ—еҺҹжң¬зҡ„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йҡҫд»Ҙз«Ӣи¶ігҖӮ
2015е№ҙ8жңҲ12ж—ҘпјҢеӨ©жҙҘж»Ёжө·ж–°еҢәеҚұйҷ©е“Ғд»“еә“еҸ‘з”ҹзҲҶзӮёпјҢдәӢж•…йҒҮйҡҫдәәж•°иҫҫ165дәәпјҢеұ…ж°‘дҪҸе®…еҸ—жҚҹй«ҳиҫҫдёҖдёҮжҲ·пјҢжҳҫ然йғЁеҲҶжҳҜеӣ дёәжіЁйҮҚж•ҲзҺҮдјҳе…Ҳзҡ„з©әй—ҙиө„жәҗиҒҡйӣҶиҖҢеҝҪз•ҘдәҶ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гҖӮйқһе…ёе’Ң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иӮҶиҷҗпјҢдәҰдёҺйҮҚи§ҶеҹҺеёӮ规模ж•Ҳеә”иҖҢеҜ№е…¬е…ұеҚ«з”ҹе®үе…Ёзҡ„иҖғиҷ‘дёҚи¶іжңүе…ігҖӮ
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дёӢзҡ„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ж јеұҖпјҢеҝ…然иҰҒжұӮжҺ§еҲ¶еҹҺеёӮ规模е’ҢеҢәеҹҹзҡ„еқҮиЎЎеҚҸеҗҢеёғеұҖгҖӮ195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пјҢиӢҸиҒ”жҸҙе»әдёӯеӣҪзҡ„156дёӘеӨ§жҠ•иө„йЎ№зӣ®пјҢ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еёғеұҖеҲ°е…·жңүжҳҫи‘—дәәжүҚе’Ңиө„йҮ‘дјҳеҠҝзҡ„дёңеҚ—жІҝжө·ең°еҢәпјҢ1960е№ҙд»ЈеҗҜеҠЁзҡ„вҖңдёүзәҝе»әи®ҫвҖқзҡ„еҶ…еңЁзҗҶжҖ§жҳҫ然дёҚжҳҜ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пјҢиҖҢжҳҜеӣҪ家з»ҸжөҺе’ҢжҲҳз•Ҙе®үе…ЁгҖӮ
вҖңдёүзәҝе»әи®ҫвҖқжҳҜдёӯеӣҪз»ҸжөҺеҸІдёҠдёҖж¬ЎжһҒ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е·ҘдёҡиҝҒ移иҝҮзЁӢпјҢеҸ‘з”ҹиғҢжҷҜжҳҜдёӯиӢҸдәӨжҒ¶д»ҘеҸҠзҫҺеӣҪеңЁдёӯеӣҪдёңеҚ—жІҝжө·зҡ„ж”»еҠҝгҖӮдёәеҠ ејәжҲҳеӨҮпјҢ 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’ҢжҜӣжіҪдёңдё»еёӯдәҺ20дё–зәӘ6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дҪңеҮәйҮҚеӨ§жҲҳз•ҘеҶізӯ–пјҢз”ұдёңеҗ‘иҘҝж”№еҸҳжҲ‘еӣҪз”ҹдә§еҠӣеёғеұҖзҡ„дёҖж¬ЎжҲҳз•ҘеӨ§и°ғж•ҙпјҢе»әи®ҫзҡ„йҮҚзӮ№еңЁиҘҝеҚ—гҖҒиҘҝеҢ—гҖӮ
еңЁ1964е№ҙиҮі1980е№ҙпјҢиҙҜз©ҝдёүдёӘдә”е№ҙи®ЎеҲ’зҡ„16е№ҙдёӯпјҢеӣҪ家еңЁеұһдәҺдёүзәҝең°еҢәзҡ„13дёӘзңҒе’ҢиҮӘжІ»еҢәзҡ„дёӯиҘҝйғЁжҠ•е…ҘдәҶеҚ еҗҢжңҹе…ЁеӣҪеҹәжң¬е»әи®ҫжҖ»жҠ•иө„зҡ„40%еӨҡзҡ„2052.68дәҝе…ғе·Ёиө„пјӣ400дёҮе·ҘдәәгҖҒе№ІйғЁгҖҒ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гҖҒи§Јж”ҫеҶӣе®ҳе…өе’ҢжҲҗеҚғдёҮдәәж¬Ўзҡ„ж°‘е·ҘпјҢеңЁвҖңеӨҮжҲҳеӨҮиҚ’дёәдәәж°‘вҖқгҖҒвҖңеҘҪдәәеҘҪ马дёҠдёүзәҝвҖқзҡ„ж—¶д»ЈеҸ·еҸ¬дёӢпјҢе»әиө·дәҶ1100еӨҡдёӘеӨ§дёӯеһӢе·ҘзҹҝдјҒдёҡгҖҒз§‘з ”еҚ•дҪҚе’ҢеӨ§дё“йҷўж ЎгҖӮ
еҪ“然пјҢ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җҺпјҢз»ҸжөҺж•ҲзҺҮдјҳе…ҲпјҢвҖңдёүзәҝе»әи®ҫвҖқз”ұдәҺ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еҠӣдёҚи¶іпјҢеӣҪ家иҙўж”ҝжҠ•е…ҘеҮҸе°‘вҖңеӯ”йӣҖдёңеҚ—йЈһвҖқпјҢдёүзәҝең°еҢәзҡ„дјҳиҙЁдәәжүҚгҖҒиө„жң¬е’ҢжҠҖжңҜиө„жәҗеӨ§йҮҸжөҒе…ҘдёңйғЁең°еҢәпјҢдҪҝеҫ—дёңйғЁең°еҢәеҹҺеёӮиҒҡйӣҶеәҰдёҚж–ӯж”ҖеҚҮгҖӮд»Һе…¬е…ұеҚ«з”ҹзӘҒеҸ‘дәӢ件зңӢпјҢдёҚи®әжҳҜйқһе…ёиҝҳжҳҜ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пјҢиҘҝйғЁеҹҺеёӮзҡ„з®ЎжҺ§пјҢжҳҜзӣёеҜ№жңүж•Ҳзҡ„гҖӮз¬ҰеҗҲ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зҡ„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ж јеұҖпјҢдёҺ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…·жңүдёҖе®ҡзҡ„е…је®№жҖ§пјҢеӣ иҖҢиҮӘ然з”ҹжҖҒгҖҒзҺҜеўғе®№йҮҸд№ҹе…·жңүз©әй—ҙеұһжҖ§гҖӮ
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ңЁ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дёҠиЎЁзҺ°еңЁдёӨдёӘж–№йқўгҖӮдёҖжҳҜз”ҹжҖҒзҗҶеҝөпјҢејәи°ғеӨҡж ·жҖ§гҖҒзЁіе®ҡжҖ§гҖҒеҚҸеҗҢжҖ§пјҢдәҢжҳҜе®№йҮҸеҲҡжҖ§гҖӮеҸҜи§Ғ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№¶дёҚеҝ…然ж”Ҝж’‘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пјҢдёҺеҹҺеёӮиө„жәҗзҡ„йҖӮеәҰиҒҡйӣҶдёҺ规模пјҢжҳҜзӣёе®№зҡ„пјҢдёҺи¶…еӨ§еһӢзҡ„规模е’ҢиҒҡйӣҶпјҢеҲҷжҳҜзӣёеҶІзӘҒзҡ„гҖӮ
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з»қеҜ№дёҚж”ҜжҢҒ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зҡ„дё“дёҡеҢ–з”ҹдә§е’Ң规模дҫӣз»ҷпјҢдҫӢеҰӮпјҢ2000еӨҡдёҮдәәеҸЈзҡ„е·ЁеһӢеҹҺеёӮеҢ—дә¬пјҢеёӮеҶ…еҹәжң¬дёҚз”ҹдә§еҶңеүҜдә§е“ҒпјҢ蔬иҸңгҖҒиӮүзҰҪдә§е“Ғе…ЁйғЁд»ҺеӨ–ең°иҝңи·қзҰ»и°ғе…ҘгҖӮеҹҺеёӮе°Өе…¶жҳҜеӨ§еҹҺеёӮзҡ„еҶңеүҜдә§е“Ғ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д№ҹжІЎеҝ…иҰҒиҮӘз»ҷиҮӘи¶іпјҢдҪҶд»Һ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зңӢпјҢеӨ§и§„жЁЎиҝңи·қзҰ»иҝҗиҫ“гҖҒиҙ®еӯҳгҖҒдҝқйІңпјҢйңҖиҰҒж¶ҲиҖ—еӨ§йҮҸиғҪжәҗпјҢдә§з”ҹеӨ§йҮҸжҺ’ж”ҫпјҢиҖҢдё”дә§е“ҒиҙЁйҮҸ并дёҚдёҖе®ҡжҜ”жң¬ең°еҘҪгҖӮеҢ—дә¬гҖҒдёҠжө·гҖҒе№ҝе·һгҖҒж·ұеңізӯүдёҖзәҝ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жҺ§еҲ¶и§„жЁЎзҡ„иҝӣдёҖжӯҘжү©еј 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зҡ„иҰҒжұӮпјҢд№ҹжҳҜ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зҡ„йңҖиҰҒгҖӮ
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дёӯзҡ„иө„жәҗиҒҡйӣҶпјҢеҰӮжһңеҹәдәҺ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зҡ„еҶізӯ–еҝҪз•Ҙ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’Ң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пјҢеҸҜиғҪжңҖеҗҺ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д№ҹдёҚиғҪжҲҗз«ӢгҖӮ2003е№ҙйқһе…ёе’Ң2020е№ҙ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еј•иҮҙзҡ„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пјҢе°ұеңЁзӣёеҪ“зЁӢеәҰдёҠжҳҜеҜ№еҹҺеёӮ规模иҝҮеӨ§иғҢеҗҺзҡ„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зҡ„иҙЁз–‘гҖҒејұеҢ–з”ҡиҮіеҗҰе®ҡгҖӮ
дёүзәҝеҹҺеёӮе»әи®ҫзҡ„еҹәзЎҖжҳҜ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пјҢеҪ“ж—¶еҜ№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еҸҜиғҪжҳҜеҝҪз•Ҙзҡ„пјҢдҪҶзҺ°еңЁеҸҚиҝҮжқҘзңӢпјҢд»ҺжҲҳз•Ҙе’Ңе®Ҹи§Ӯз»ҸжөҺдёҠзңӢпјҢе…¶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дёҚж–ӯеҮёжҳҫгҖӮ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жң¬иә«е°ұе…·жңү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е’Ң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зҡ„еҶ…ж¶өпјҢеҢ—дә¬йқһйҰ–йғҪеҠҹиғҪиө„жәҗзҡ„з–Ҹи§ЈпјҢй•ҝжұҹз»ҸжөҺеёҰе№Іж”ҜжөҒдёӨеІёеҹҺеёӮеҸ‘еұ•дёҚжҗһеӨ§ејҖеҸ‘пјҢе…ұжҠ“еӨ§дҝқжҠӨпјҢе°ұжҳҜ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Җ’йҖјзҡ„йҒөеҫӘ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е’Ң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зҡ„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зҡ„дҪ“зҺ°гҖӮ

йҳІиҢғ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еҹҺеёӮ规模иҒҡйӣҶдёҺз©әй—ҙж јеұҖ
2003е№ҙйқһе…ёжүҖеј•еҸ‘зҡ„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е…¬е…ұеҚ«з”ҹ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зҡ„еҪұе“ҚдёҚеҸҜи°“дёҚеӨ§пјҢдҪҶ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е№¶жІЎжңүеј•иө·и¶іеӨҹйҮҚи§ҶпјҢж•ҷи®ӯ并没жңүе……еҲҶжұІеҸ–гҖӮ2020е№ҙжҳҘиҠӮжңҹй—ҙзҲҶеҸ‘зҡ„ж–°еһӢеҶ зҠ¶з—…жҜ’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пјҢ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еҶҚеәҰеӨұжҺ§пјҢзҒҫжғ…д№ӢдёҘйҮҚпјҢиҝңиҝңи¶…еҮәдәҶжҲ‘们зҡ„жғіиұЎгҖӮ
еӣә然пјҢжҲ‘们йңҖиҰҒд»Һ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дҪ“зі»зҡ„и§Ҷи§’дёҘеҠ е®Ўи§ҶпјҢеңЁдҪ“еҲ¶жңәеҲ¶дёҠж”№иҝӣе®Ңе–„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д»ҺеҹҺеёӮ规模еҰӮ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ж јеұҖдёҠеҲҶжһҗз–«жғ…蔓延зҡ„еӨ–йғЁжҲ–硬件жқЎд»¶пјҢеңЁеҹҺеёӮз©әй—ҙ规еҲ’дёҠиҝӣиЎҢи°ғж•ҙпјҢйҷҚдҪҺе’ҢйҳІиҢғ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йЈҺйҷ©гҖӮеҹҺеёӮе®үе…ЁжҳҜеҹҺеёӮй«ҳиҙЁйҮҸеҸ‘еұ•зҡ„ж ёеҝғиҰҒд№үпјҢе°Өе…¶йңҖиҰҒйҒҝе…ҚеҹҺеёӮдҪ“зі»е’ҢеҹҺеёӮеҪўжҖҒдёҠзҡ„йЈҺйҷ©жәҗгҖӮ
йҰ–е…ҲпјҢеҹҺеёӮ规模е’Ңз©әй—ҙиҒҡйӣҶпјҢйңҖиҰҒеҚҸеҗҢиҖғиҷ‘з»ҸжөҺзҗҶжҖ§гҖҒз”ҹжҖҒзҗҶжҖ§е’Ң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пјҢе°ҶеҢ…жӢ¬з”ҹжҖҒе®үе…ЁеңЁеҶ…зҡ„е®үе…ЁзҗҶжҖ§ж”ҫеңЁжӣҙеҠ зӘҒеҮәжҲ–дјҳе…ҲиҖғиҷ‘зҡ„дҪҚзҪ®пјҢеўһејәеҹҺеёӮзҡ„е®үе…ЁжҖ§гҖӮ
е…¶ж¬ЎпјҢеҹәдәҺ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蔓延зҡ„жү©ж•ЈжңәзҗҶе’ҢйЈҺйҷ©ж•Ҳеә”пјҢеҹҺеёӮ规模е’Ңз©әй—ҙиө„жәҗзҡ„иҒҡйӣҶжҳҜйҮҚиҰҒзҡ„еӨ–йғЁжқЎд»¶зҡ„з»“и®әпјҢжҲ‘们йңҖиҰҒеңЁеҹҺеёӮзҫӨзҡ„з©әй—ҙж јеұҖдёҠпјҢжіЁйҮҚжҺ§еҲ¶еӨ§еҹҺеёӮ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зү№еӨ§еҹҺеёӮзҡ„规模пјҢйҖӮеәҰиҒҡйӣҶпјҢеқҮиЎЎз©әй—ҙеҸ‘еұ•гҖӮ
жңҖеҗҺпјҢеҹҺеёӮеҸ‘еұ•зҡ„дјҳиҙЁиө„жәҗ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•ҷиӮІгҖҒеҢ»з–—гҖҒ科жҠҖз ”еҸ‘пјҢйңҖиҰҒеңЁжӣҙеӨ§еҢәеҹҹеҶ…еқҮиЎЎй…ҚзҪ®пјҢйҒҝе…Қеӣ еҹҺеёӮзӯүзә§дёҚеҗҢиҖҢжқғеҠӣеҜ»з§ҹйҖ жҲҗеҜ№дјҳиҙЁиө„жәҗзҡ„еһ„ж–ӯгҖӮең°зә§еёӮд№ғиҮіеҺҝзә§еёӮ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иҖҢдё”еә”иҜҘ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дё–з•ҢдёҖжөҒеӨ§еӯҰпјҢй«ҳж–°жҠҖжңҜеӣӯеҢәд№ҹеҸҜд»ҘиҖҢдё”еә”иҜҘеёғеұҖеңЁдёӯиҘҝйғЁзҡ„дёӯе°ҸеҹҺеёӮпјҢд»ҘйҷҚдҪҺеҹҺеёӮйЈҺйҷ©пјҢжҸҗеҚҮе®үе…ЁжҖ§гҖӮ
еҹҺеёӮжІ»зҗҶзҡ„жүҒе№іеҢ–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дёӯе°ҸеҹҺеёӮе’ҢеҶңжқ‘д№Ўй•ҮеңЁз©әй—ҙ规еҲ’дёҠжҸҗеҚҮеҹҺеёӮзӨҫеҢәзҡ„йҹ§жҖ§пјҢе…·еӨҮзӣёеә”зҡ„еә”жҖҘ硬件и®ҫж–ҪпјҢйҒҝе…Қж–°еҶ иӮәзӮҺз–«жғ…еңЁж№–еҢ—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зӣёеҜ№ж»һеҗҺең°еҢәдёҘйҮҚзјәд№ҸеҢ»з–—и®ҫж–Ҫе’ҢеҹәзЎҖзү©иө„иҖҢж— еҠӣеә”жҖҘзҡ„еұҖйқўгҖӮ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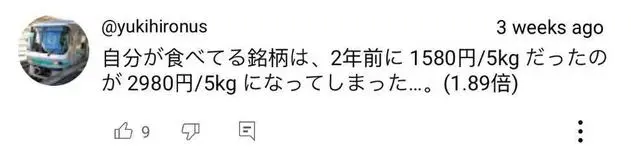 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
д»·ж јжҡҙж¶Ё ж—Ҙжң¬еӨҡең°зҺ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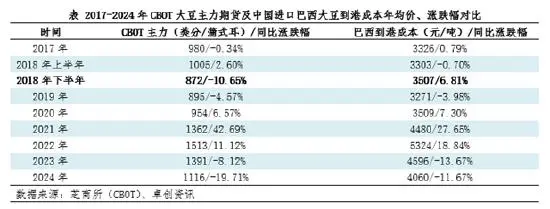 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
зү№жң—жҷ®д»»жңҹдёӢзҡ„е…ЁзҗғеӨ§ 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
ж–°еһӢеҶңдёҡз»ҸиҗҘдҪ“зі»е»әи®ҫ 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
еј жҳҺпјҡдёӯзј…иҫ№иҙёеҫҖжқҘдёӯ 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
й«ҳз‘һдёңзӯүпјҡ2025е№ҙиө„дә§ 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
еҲҳдҝҠжқ°зӯүпјҡжһ„е»әйҖӮеә”еҶң 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
11жңҲе…Ёзҗғи°·зү©еёӮеңәдёҺиҙё 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
з®Ўж¶ӣзӯүпјҡпјҡдәәж°‘еёҒжұҮзҺҮ 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
й’ҹжӯЈз”ҹпјҡеҗ‘е®ҢжҲҗйў„з®—зӣ® 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
жқҺиҝ…йӣ·пјҡжҳҺе№ҙиҙўж”ҝиөӨеӯ— 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еј зәўе®Үпјҡжһ„е»әе…·жңүдёӯеӣҪ




